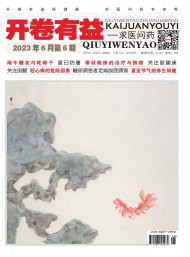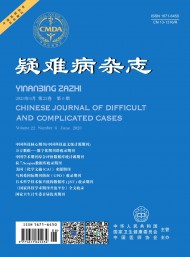疑人竊履范文
時間:2023-04-11 14:03:2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疑人竊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篇2
一、感受:即我對“人大代表應怎樣在依法履職中加強與群眾密切聯系”的這個專題的理解和認知。對此,我想用兩句話來概括
一句話就是:省級人大常委會的高度重視,為省域范疇內各級人大代表在依法履職中加強與群眾的密切聯系提供了切實指導。如回顧近幾月來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已連續三次召開的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座談會,我們就會明白,這是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在為全省各級人大代表依法履職、加強與群眾密切聯系所展開的一系列相關的先期行動,其目的就是為了進一步在全省全面推行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活動提供切實指導。如早在2012年12月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就專門召開了“依法履職,充分發揮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作用”的座談會。這次會議特別提出,全省各級人大代表要密切聯系群眾,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依法履職,始終保持與黨同心、與民貼心,始終踐行“人民選我當代表,我當代表為人民”的莊嚴承諾,以密切聯系群眾的實際行動,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正是由于四川省人大常委會連續三次召開的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的座談會,以及下發的相關文件和制定的代表聯系群眾工作辦法的推動,所以才指導和保障了四川全省各級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這一活動的順利開展,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二句話就是: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必須依法而為。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真心為民辦實事辦好事的表現形式及其先進事跡各有所不同,但他們身體力行、不辱使命、爭做人民滿意的人大代表的履職成效是共同的,是帶有共性的。即不少人大代表在實際工作中所取得的依法履職、密切聯系群眾、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突出成效,確實又是依法而行的。因為憲法和法律就是這樣規定和要求的。如我們國家的母法、也就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法就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代表法在規范各級人大代表應當履行的義務時更是進一步明確規定,各級人大代表應“與原選區選民或者原選舉單位和人民群眾保持密切聯系,聽取和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努力為人民服務”。同時,代表法也對代表履職的途徑和方式同樣做了明確的規定。可見,人大代表密切聯系群眾的所作所為,與憲法和法律的原則規定完全一致,是依法而為的。而這一點,也正是與勞動模范、先進工作者的主要區別所在。也就是說,雖然不少人大代表在依法履職、密切聯系群眾、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的過程中事跡典型、先進而感人,但由于他們是依法履行代表職務所取得的成效,所以他們并非是勞動模范或先進工作者。
二、探索:即結合自身體會對“人大代表在依法履職中應怎樣加強與群眾密切聯系”的這個專題作些必要的理性思考
筆者認為,人大代表之所以要在依法履職中加強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就是因為這樣的聯系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職的天職所在,也就是人大代表依法履職加強與群眾的密切聯系,就是在踐行天職之責。雖然,我們都知道“天職”在現代漢語中是個由天和職兩個字組合而成的很普通很常用的偏正結構的合成詞。然而,天與職組合而成的這個天職,確具有不斷演變的多重含義。如這個詞被廣泛運用于社會倫理領域,即成為規范和引導人們的行為及其促使人們所要履行的應盡之職。比如,我們常說的“服從命令、保家衛國是軍人的天職”、“關愛學生是老師的天職”、“救死扶傷是醫生的天職”等等。那么,人大代表的天職是什么?我認為就是為民履職的強烈社會責任感!而人大代表要為民履職,首先就必須通過法律規定的履職方式去了解民眾、熟悉民眾,就必須真正做到“會學習、會調查、會溝通”,然后才能真正做到“會思考、會提案、會建言”,最后才能取得“會代表”的依法履職的好成效。而這一點筆者是怎樣概括出來的呢?其實就是從相關法律規定中概括出來的。例如,現行代表法的第三條、第四條就分別對代表應當履行的權利和義務作了明確規定。所以,我認為人大代表“會學習、會調研、會溝通”,以及“會思考、會提案、會建言”,最后達到“會代表”的最高層次,確實是符合法律的有關明確規定的。
篇3
因此,有必要重申一個觀點:平視孔子。
平視是孔子自己的主張
事實上,平視是孔子自己的主張。
他一生對己對人,都采取平視姿態。他平視自己,從來沒有“老子天下第一”的心態,更不認為自己是“圣人”,甚至坦承自己不如對方,說過“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之類的話。他也敢于承認自己有缺點有過失,所謂“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認為諱言過失毫無意義。
他平視別人。盡管有“上智下愚”的成見,卻并不拒收差生,實行“有教無類”,即便引來許多批評,也沒有為此修改“招生大綱”。他甚至以學生為“友”,“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
對強者,孔子也沒有一點仰視或奴顏婢膝。他一再批評君子“好色”、“好利無厭”、“荒怠慢游”。對于貴族,他敢于直言,評季氏的“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甚至對堯舜這樣自己心中的“圣人”也取平視態度,認為“圣人”并不神秘,修養到某個境界,人皆可以為舜堯。
坦然接受別人的平視
事實上,在孔子生活的那個時代,周圍的人對孔子也采取平視態度,并不奉若神明,孔子也坦然接受這種平視。
先看學生怎樣平視他。他的學生可以公開對他說“不”。有一次,學生子游直接對孔子的前后言論不一提出質疑,孔子趕緊嚴肅地認錯。
學生家長對孔子也是平視。有的學生家長竟可以對他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論語?先進》記載,顏淵死后,其父顏路要求孔子賣掉乘坐的車子,給顏淵買外槨。如果家長覺得孔子不可冒犯,怎敢啟齒?今天有沒有家長敢于讓老師賣掉小轎車來給自己的孩子交學費?
社會上的人對孔子提出各種批評更是家常便飯。晨門批評他“知其不可而為之”,荷丈人批評他“四體不勤,五谷不分”。鄭人說他外貌“累累若喪家之狗”,孔子聽后卻欣然笑著說:“然哉!然哉!”(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
不能平視是對孔子的最大扭曲
事實上,對孔子不能平視是后來的事。
不錯,子貢說過“仲尼,日月也”,那是因為有人詆毀孔子。再者,子貢的評價,并不能代表孔子對本人的意愿。
篇4
一、“班婕妤”本身成為“被棄宮女”的代名詞
班婕妤賢而見棄的悲涼命運引得無數后世文人的同情與共鳴,他們根據班婕妤創作了大量詩歌,借以抒發人生際遇中的感慨與不平。唐前以班婕妤為主題的詩歌被收入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在《樂府詩集》一個獨立的門類下有直接以“班婕妤”、“(班)婕妤怨”為題的詩歌。
最早有關班婕妤的詩歌是傅玄的《朝時篇》:“自傷命不遇,良辰永乖別。已而可奈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流星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紈素裂”指的是班婕妤所作的《怨歌行》中的“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甘心要同穴”指班婕妤死后要葬于漢成帝墓旁的遺愿①。傅玄此詩并沒有特殊的寓意,而是單純地就班婕妤的本事進行闡發,高度評價班婕妤對丈夫至死不渝的忠誠。而以宮體詩風描述班婕妤的陸機則撇開班婕妤身上的道德光環,僅僅將班婕妤視為一個美麗憂傷、孤獨無助的宮女——“婕妤去辭寵,淹留終不見。寄情在玉階,托意惟團扇。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陸機《班婕妤》)。陸詩中的“玉階”、“春苔”、“秋草”等意象,都是套用自班婕妤的《自悼賦》。如“玉階”出自班賦:“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棲兮綠草生”一句,為班婕妤感懷春去秋來,蕭瑟的秋季偏又逢幕落時分,讓人難免產生一種韶華易逝、寵難再的傷感。而陸詩中的“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則直接化用了班賦的“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兮云屋,雙涕兮橫流”,道盡了相思無極的哀傷與凄苦。陸機的《班婕妤》側重感情的渲染,極力刻畫班婕妤作為一個被棄宮女的無助與絕望,讓人憐愛之心頓生。
南北朝時期,關于班婕妤的唱和之作風行一時,最典型的代表是梁元帝蕭繹與其臣子之間的《班婕妤》詩歌酬唱。梁元帝蕭繹曾作《班婕妤》一詩感嘆:“婕妤初選入,含媚向羅幃。何言飛燕寵,青苔生玉墀。誰知同輦愛,遂作裂紈詩。以茲自傷苦,終無長信悲。”在班婕妤哀傷的宮女形象之外,梁元帝看到了她以詩排遣悲苦的詩人性情。唱和之作中孔翁歸的“長門與長信,日暮九重空。雷聲聽隱隱,車響絕瓏瓏”,以及何思澄的“寂寂長信晚,雀聲喧洞房。蜘蛛網高閣,薄蘚被長廊”,都是從宮殿等外部環境的寂靜烘托班婕妤成為被棄宮女后的寂寞與幽怨。劉孝綽與其妹劉令嫻亦有唱和之作,尤其是劉令嫻的《和婕妤怨詩》中的“只言爭分理,非妒舞腰輕”,不落將婕妤塑造成柔弱無助的棄婦形象這一窠臼,大膽寫出班婕妤內心的控訴與反抗,展現婕妤高潔的品格與尊嚴。
自唐一代,班婕妤的被棄宮女形象被進一步刻畫,例如,詩仙李白的《怨歌行》:“寧知趙飛燕,奪寵恨無窮。沉憂能傷人,綠鬢成霜蓬”,以及“寒苦不忍言,為君奏絲桐。腸斷弦亦絕,悲心夜忡忡”,將班婕妤內心的“恨”、“憂”、“苦”、“悲”等情感抒發得淋漓盡致,一個被棄宮女的凄楚形象被刻畫得入木三分。王維有《班婕妤三首》,其一:“玉窗螢影度,金殿人聲絕。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其二:“宮殿生秋草,君王恩幸疏。那堪聞鳳吹,門外度金輿”。其三:“怪來妝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里,花間笑語聲”,都是從失寵宮人、寂寞難挨的角度描寫班婕妤的。
唐朝之后,班婕妤的被棄宮女形象逐漸被定格化,詩人大多承襲班婕妤被棄宮女這一哀怨形象進行描寫,如宋末元初的張玉孃的《班婕妤》“一自煌捐棄,香足玉階疏。聞道西宮路,近亦絕鶯與”,以及清代詞人納蘭性德的《班婕妤怨歌》:“扇棄何足道,感妾傷懷抱。對月淚如絲,君恩異舊時”,等等,都是描寫班婕妤被棄后的哀怨與惆悵。
二、由《自悼賦》產生的詩歌意象
1.長信宮
如果說司馬相如的《長門賦》是后世宮怨文學的發端的話,那么《自悼賦》就是宮怨體的濫觴。《自悼賦》中的詩詞意象——“長信宮”,逐漸被等同于被棄宮女居住的冷宮,成為宮怨的發源地。因此,后世出現以“長信宮”、“長信宮怨”命名的宮怨詩。如孟遲《長信宮》:“自恨身輕不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王昌齡《長信秋詞五首·其三》:“奉帚平明金殿開,且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班婕妤移居長信宮,從后宮的脂粉場上悄然隱退。伴著清晨的曙光,打開長信宮的大門,她開始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打掃,風中飄來遠處昭陽宮里歡樂的喧嘩聲,而她依舊拖著孤寂的背影單調地灑掃著。
2.玉階
晉代陸機《班婕妤》有“寄情在玉階,托意唯團扇”,其中“玉階”即從賦中“華殿塵兮玉階菭,中庭棲兮綠草生”一句而來。從此,“玉階”成為宮怨詩最具代表的詩歌意象。如謝朓的《玉階怨》:“夕殿下珠簾,流螢飛復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的題名即受此句啟發而來。初唐詩人沈佺期的《長門怨》說:“玉階 聞墜葉,羅幌見飛螢。”亦借此詩歌意象描寫冷宮的清幽。李白膾炙人口的名篇《玉階怨》:“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卻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更深刻地描繪出“玉階”的清冷寒涼。
此外,賦中的“春苔秋草”、“羅幃”、“玉墀”、“履綦”等都成為宮怨題材的經典詩歌意象。如前邊提到的陸機《班婕妤》中的“春苔暗階除,秋草蕪高殿。黃昏履綦絕,愁來空雨面”。陳代詩人陰鏗的《班婕妤》中的“花月分窗進,迨草共階生”,以及何楫《班婕妤》中的“履跡隨恩故,階苔逐恨新”。王昌齡《長信秋詞五首·其一》“秋夜守羅帷,孤燈耿不滅”等都沿用這類詩歌意象。
三、《怨歌行》中的“團扇”意象
班婕妤的《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成為后來諸多宮怨詩尊奉的經典,被鐘嶸的《詩品》列為上品。雖然《怨歌行》為班婕妤所作這一問題仍然存疑,但顯然后人并不執著于作者的真實歸屬,人們只是認同婕妤的古德、才情,同情她“團扇見捐”的悲劇命運,進而借物嘆人罷了。正是基于這一情感因素,以“團扇”為主題的詩作才會大量問世。
江淹的《班婕妤》:“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采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劉孝綽的《班婕妤》:“妾身似秋扇,君恩絕履綦,詎憶游輕輦,從今賤妾辭。”這兩首詩有些像《怨歌行》的續篇,都是就班婕妤的本事進行闡發的,將班婕妤被棄的悲慘命運借助“團扇”這一意象進行傾訴。謝玄暉的《和王主簿怨情一首》:“相逢詠蘼蕪,辭寵悲班扇。”雖同樣以班扇代指被棄女子,但在這里,謝玄暉還有更深層的喻指:以“團扇見捐”嘆“淑女遭棄”,不過是為了以“淑女被棄”喻“士人不遇”。謝詩脫離了班婕妤本事的狹小創作思路,拓寬了“團扇”的意象涵指。
其后的朝代中,“團扇”的意蘊得到進一步發展。東晉王獻之的愛妾桃葉曾作《答王團扇歌三首》,其一“七寶畫團扇,燦燦明月光。與郎卻喧暑,相憶莫相忘”。其二“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桃葉以團扇為情感的載體,表達出對丈夫的濃濃深情,團扇寓意永不相離相忘的團圓美好,更豐富了“團扇”的內涵。
到了唐代,“團扇”的意象被更廣泛地運用,成為一時之盛。杜審言的《妾薄命》:“自憐春色罷,團扇復迎秋。”與李白的《長信宮》:“誰憐團扇妾,獨坐怨秋風。”都是描寫一位獨坐自憐的女子哀嘆命運的悲苦,由此團扇成為閨怨的載體。唐天寶年間,有位宮女曾作詩《題洛苑梧葉上》:“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這位宮女以物度己,深宮幽寂又壓抑難耐,無人可訴滿腔悲情,只能將與班婕妤一樣的深宮幽怨揮灑于一葉梧桐,讓它隨著涓涓溪水飄流出這東都洛苑。張祜《相和歌辭·團扇郎》:“白團扇,今來此去捐。愿得入郎手,團圓郎眼前。”承襲桃葉的夫妻繾綣羨愛之愿,取團扇團圓和美之意。至此,“秋扇”已成為班婕妤的化身,千百年來訴說著幽幽的哀傷。但并非所有詩中的團扇之怨都是哀婉纏綿的,不乏慷慨激昂之音。韋應物之《悲紈扇》:“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顏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暗使銷光彩。”一語道出團扇被棄的原因并非來自于外部,而是由于人心變了,將矛頭直指變心的人,一針見血,將團扇之怨裹挾上一層剛烈不屈之氣。由上可知,唐人對團扇意象的運用變得更嫻熟,并在運用中不斷融入新的意蘊,借團扇表達不同的蘊指。
直到清代,亦有納蘭性德的名篇《木蘭辭·擬古決絕詞柬友》:“人生若只如初見,何事秋風悲畫扇,等閑變卻故人心,卻道故人心易變。”“秋風畫扇”已經自然而然地代替班婕妤這一人物形象,成為特指班婕妤的詩歌意象,它承載著女子對自身的嘆惋和文人“哀士不遇”的感傷。
四、《搗素賦》中的“搗素”、“搗衣”意象
搗衣詩是閨怨詩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月下搗衣凄涼、哀怨的砧杵之聲,是古代詩歌作品中反復出現的意象。搗衣詩的原型意象始于漢代班婕妤的《搗素賦》,作者以搗素女自比,委婉地表達自己的凄怨思念之情。自此之后,“搗衣”常常被用來表現婦女的懷遠之思,成為閨怨詩的異名。這篇工于體物的言情小賦直接開創了“搗衣”一類題材的詩歌創作。
南朝劉宋文學家謝惠連有一首著名的《搗衣詩》:“楹長杵聲哀,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紈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將“搗衣”提煉為思婦的象征,后世開始廣泛運用搗衣意象描繪游子婦、征婦的凄苦與哀怨。如唐代王勃的《秋夜長》:“調砧亂杵思自傷。思自傷,征夫萬里戍他鄉。”李白的名篇《子夜吳歌·秋歌》:“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秋風吹不盡,總是玉關情。”描寫的都是秋風漸起,風寒露重,征婦杵杵的搗衣聲道不盡她們的遙遙期盼與刻骨相思。描寫游子思婦的還有唐代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玉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楊凝的《秋夜聽搗衣》:“砧杵聞秋夜,裁縫寄遠方。”宋代賀鑄的《夜搗衣》:“收錦字,下鴛機。凈拂床砧夜搗衣。馬上少年今健否,過瓜時見雁南歸。”寒砧聲作為思婦情感的形式或象征,被逐漸抽象化、符號化,已經凝固到文學意象的傳承中。
迄今為止,《怨歌行》和《搗素賦》是否為班婕妤所作,學者們各執一詞。即使如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團扇”、“搗衣”等詩 歌意象正是借助婕妤的故事,才得以存在發展。人們欣賞的是婕妤的才情與品德,作者的存疑并不足以影響千百年來班婕妤在人們心中的崇高地位。正因有了班婕妤,這些詩歌意象才具有了更豐富的寓意,才成了中國古典詩歌史上不可或缺的經典意象。
注釋:
①漢書·外戚傳第六十七下.“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參考文獻:
[1]班固撰.漢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徐陵編,吳兆宜注,程琰刪補,穆克宏點校.玉臺新詠箋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3]郭茂倩編.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篇5
關鍵詞:《列子》;敦煌;選本;體例;楊思范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04(2012)06?0216?04
敦煌《列子》是迄今為止所發現的存世最早的手寫本,雖然所存多為殘卷,但與今本相較,也可略知《列子》一書的流傳狀況。對于殘卷文字的整理,更加有助于我們了解《列子》一書的流傳情況。通過對于殘卷的分析,可知在盧重玄注出現之前,只有張湛注一種,并無新注出現。本文在殘卷整理的基礎上,對殘卷《列子》的體例作一簡略分析。
一、殘卷文字整理
敦煌殘卷《列子》碎片較多,其中以編號S6134、S777、S10799[1]、P2495[2]四種內容較多,現以宋本《列子》[3]為底本,整理如下:
1. 編號S6134(《列子·黃帝》篇)
(上闕)弇之西、古州之北。乘空如履實,寢虛(闕)床。云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闕)飲露不食五谷。姑射山在河州中,上有(闕)醉者墜車,雖疾不死死生驚罹,不入其胸(闕)無人射,引弓盈貫,厝杯水于肘(闕)高山,履危石,猶能射乎?困履登高(闕)潛黃泉揮斥(闕)能使存者亡、亡者存(闕)之,有寵于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名勢(闕)貧有丘先生,假糧荷畚往諸子華之門,見(闕)無所不為。子華遂與丘開乘高臺,于眾中(闕)丘開遂頭刑若飛鳥。復渭,丘開曰:彼阿曲之隈(闕)得珠鳥。俄而子華之庫遇火,謂丘開曰:火(闕)入火了無難色。子華曰:自今乞兒馬醫不(闕)吾養野禽獸于園庭,虎狼鵰。
2. 編號S777(《列子·楊朱》篇)
(前闕)陽性稟五行也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御,趨走]不足以從利逃害。無毛羽以御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則身非我有,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既有,不得去之。身因生之主,物[為]養之主。雖全生,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之物者,其唯至人矣。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唯圣人邪?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天下之物同之我物。非至人如何既覺私之為非,又知公之為是?故曰至至也。
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不放恣其嗜欲者也,二為名不敢恣其所行也,三為[位曲意]求通,四為貨專利惜費。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形,此謂遁民違其自然。可殺可活,制命(后闕)。
此卷為《列子》張湛注本,文中[]內文字為據宋本所補。此片所引文字與宋本略有差異,王重民曾有校記[4],仍有遺漏,現重校于下。
①“不足以從利逃害”,宋本作“逃利害”。
②“必將資物以為養”,宋本“養”下有“性”字。
③“然則身非我有”,宋本作“然身非我有也”。
④“物非我有”,宋本作“物非我有也”。
⑤“既有不得去之”,宋本作“既有不得不去之”,王校缺。
⑥“物[為]養之主”,宋本作“物亦養之主”。敦煌殘卷此字不清,似“為”字。
⑦“雖全生不可有其身”,宋本作“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
⑧“不橫私天下之身,不橫私天下之物者”宋本無此句。
⑨“其唯至人矣”,宋本作“其唯圣人乎”。王重民校記曰“作圣人是也”,敦煌本張湛注亦作“圣人”,王說是。
⑩“故曰至至至也”,宋本作“故曰至至也”。敦煌本第二個“至”字為省略寫法,同正文“此之謂至至者也”句中第二個“至”同。王校缺。
“違其自然”,宋本后有“者也”二字。
3. 編號S10799(《列子·楊朱》)
(闕)古猶今也。變易(闕)之矣,既見之矣,既(闕)多以生之苦乎?(闕)或好或惡,或安或危(闕)耶?則重來之物無所復(闕)急不可(闕)者矣孟孫陽曰:若(闕)入湯火淂(闕)任之(闕)。
4. 編號P2495(《列子·說符》)
(闕)丁壯者皆(闕)①五刃常在空中有人(闕)刃常在空中宋元君見大喜(按:后一行字跡漫漶,無法辨認)(闕)與爾同者,可得從(闕)若沒若亡,若夫絕塵弭(闕)不可以天下馬也。臣有共擔薪(闕)使方罩求,三月而反得驪穆公恠之伯樂曰:方舉之所見天機(闕)不知所從(闕)。
楚人鬼,越人(闕)大王必封汝,汝慎勿受利地。楚(闕)也死子請寢丘故(闕)氏財貨登高樓(闕)其上樓下有矣。若相見而行(闕)政中俠(闕)盡云博一名也(闕)狐父之見而饗之三餔(闕)地而歐之不出遂爵而死(闕)有三子知之乎?爵高者人妬之(闕)之叔敖曰:吾爵益高志益下,吾(闕)益也。
夏食菱芰,冬食橡栗莒敖公居海上,食菱芰橡栗有難得往死之世人之知臣者也。
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既反,楊子問其故,答曰:失羊矣,歧路之中復有歧矣。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
楊布,楊子之弟。衣素衣出行,遇雨,著絹衣而反,狗不識,迎而吠之。楊布將撲之,楊朱曰:向(闕)狗白而往、黑而歸汝犬正旦放鳩邯鄲民以正月旦獻趙簡子鳩,簡子曰:放之。正旦放鳩,示有恩也。厚賞獻客。于是民爭鳩,死者眾矣。欲生之,不若禁勿捕之也。齊有貧者常乞于城,城市患之,不與,遂適田氏庭,從馬醫作役,不復知辱。
拾得遺契宋人有于道得人遺契藏之,密數其齒。注云: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人有種枯梧樹者,鄰父言曰:枯梧不祥。其家遽伐之,鄰父即請為薪其家疑不與也。
人有亡鈇者,意鄰子盜之,視其行步顏色皆竊鈇也。俄而其谷得鈇,見鄰子無復竊鈇之容。
倒杖缽杖頤不知痛也白公勝欲為也。罷朝,倒杖貫頤,血流至地,知。鄭人聞之,不知,將何不者。
奪市人金齊人有欲得金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而去。吏捕得問,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耳。
二、體例分析
敦煌文獻殘存多片《列子》,主要為英國國家圖書館及法國國家圖書館所收藏。英國國家圖書館收藏碎片較多,其中以編號為S777、S6134及S10799三個殘片內容最多,S777為《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本,正文大字,注文小字雙行,起自注文“陽性稟五行也”,迄自正文“可殺可活制命”,與今《四部叢刊》影宋本體例相同,文注分明。S6134為《列子·黃帝》篇文,起自小字“弇之西古州之北”,迄自大字“虎狼鵰”,體例與今本《列子》不符。S10799亦為《列子·楊朱》篇張湛注本,起自正文大字“古猶今也”,迄自正文大字“任之”,與今本《列子》相符。S777與10799文注分明,基本上與今本《列子》相差無幾,惟S6134與今本出入很大。今本正文與注文分界清晰,敦煌殘片以大字為正文,有刪節。以雙行小字的形式出現的文字,綴于大字之下,且從文義上看,顯系解釋大字正文。如,“飲露不食五谷”以大字出現,而小字“姑射山在河州中上有”,顯然是對大字文義的進一步解說。解說文字是從原文中節選出來的,其中并無新的內容。
法藏編號為P2495的《列子》殘片,屬《說符》篇內容,與《莊子》合卷,嚴靈峰《老列莊三子補編》收錄此卷,并有整理文字,稱其為《列子莊子抄》。只是嚴靈峰稱《列子》殘卷起自“揚子鄰人亡一羊”,標明上缺,今法藏敦煌文獻殘片實起自“丁壯者皆”,結處則意見相同。由體例來看,此殘卷與S6134相同,也為節抄本,注文也是節取原文,并無新的文字出現②。
編號S6134與編號P2495敦煌殘片《列子》,內容上為節抄,注釋既非張湛原注,也非新的注解,而是用《列子》原文來對其所節取的文字作進一步說明。首先我們可以確定這是《列子》的一個節選本。他的選取內容是在對原文的高度概括下而總結出來的多個主題,對于說理性強的文字則多選,甚至與原文相差無幾。而對于故事性強的文字則總結出一個主題來,再用原文中的故事來對這個主題作進一步說明。如其所選《說符》篇中“正旦放鳩”與“楊子之鄰人亡羊”兩個故事即可說明這個問題。“正旦放鳩”《列子》原文為: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于趙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這樣一件事被作者用四個字“正旦放鳩”來概括,注文即對原文略加刪削而以小字雙行形式綴于其下:“邯鄲民以正月旦獻趙簡子鳩,簡子曰:放之。正旦放鳩,示有恩也。厚賞獻客。于是民爭鳩,死者眾矣。欲生之,不若禁勿捕之也。”③相較于原文,此處注文雖是節選,但也經過了作者的加工概括,是以《列》來解《列》,是基于文本而對原文所載故事的深入理解。類似的典型事例還有“奪市人 金”。《列子》原文為:“其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 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敦煌殘卷雙行小字文為:“齊人有欲得金者,旦,衣冠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而去。吏捕得而問,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耳。”④以小字形式出現的文字,也是對原文的因襲,且略有刪節,類似于后世的選本。由這兩個事例可知,對于故事性強的文字,作者都高度概括,并用《列子》原文來解說概括后的文字,類似于后世根據某一故事而總結出來的成語。
“楊子之鄰人亡羊”一節,敦煌殘片原文為: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既反,楊子問其故,答曰:失羊矣,歧路之中復有歧矣。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此處也是對原文的刪略,省去了楊子因此事而不言不笑,孟孫陽答心都子問的細節,直接以說理而結。在作者看來,亡羊失路,恰如多方喪生一樣,所以專門節取這一處來說明“本一末異”的道理。這段文字后面沒有解說性文字。再如,人有種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曰:枯梧不祥。其家遽伐之,鄰父即請以為薪。雙行小字為:其家不與也。這段文字也有刪節,只保留了敘述的部分。由此看來,對于說理性較強的文字,作者都予以保留。而對那些可有可無的細節對話,則不予保留。這樣的處理方式,與后世的選本體例相近。
距敦煌寫卷最近的選本是唐人魏征的《群書治 要》[5]及馬總的《意林》[6]。魏征的《群書治要》選取《列子》中有關治國的文字,間有注解,與敦煌《列子》略有差異。馬總的《意林》與《群書治要》不同,他是志在“防守教之失”、“補比事之闕”、“佐屬文之緒”,選文皆以理合。從選文內容上來看,有的與敦煌《列子》選文相近。如“楊子鄰人亡一羊,相率追之,歧路之中復有歧矣。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本一末異也。”與前者所引敦煌文字相較,此處節選文字只略去了“之”及“既反,楊子問其故,答曰:失羊矣”一句話,后多加一個“曰”字。再如,“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往市,適見貨金者,因攫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耳。”與敦煌文字相較,也是相差無幾。由此可暫且做出這樣的推斷:編號S6134與編號P2495的敦煌《列子》殘卷,極有可能即是與此相關的《列子》選本。南北朝時梁庾仲容有《子書抄》三十卷,其為諸子的選本,選錄標準是“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馬總的《意林》即是在這個基礎上“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而成。從時間上看,敦煌本《列子》中“民”字缺筆,可知其抄寫年代為太宗之時或之后。那么,可以確定在敦煌寫本之前及之后,均有關于《列子》的節選文字流傳于世。而敦煌文字與《意林》所選如此相近,這樣似可進一步推斷:敦煌《列子》與庾仲容《子書抄》⑤也存在某種聯系。由此可知,敦煌殘卷《列子》為選本,并不是全本。而且選錄的標準是有助于世風教化的說理性文字,對于敘述性文字則在不影響文意的情況下適當刪略。
對于殘卷中以小字雙行形式出現的說明性文字,楊思范[7]認為是在張湛注基礎上的另一種新注,似過于武斷。古人注書的體例往往是在原文的基礎上盡情發揮,其間夾雜著作者個人及時代的影響。而敦煌殘卷《列子》的說明性文字也是原文的節選,并無之外的文字對其作引申說明,這點似不合注書常規。編號為S777的《列子》張湛注殘卷,亦為《楊朱》篇,其體例則與此不同,與宋本相較,則相差無幾,可知其為張湛注本無疑,并非節抄本。而與S6134和P2495兩張殘卷體例不同,可知這兩張殘片所代表的《列子》抄本決非張湛注本,亦不是新的注本。那文中的小字作何解釋呢?這一點從《永樂大典》殘卷所遺留的信息似可說明一些問題。如《永樂大典》卷二三三七“教吾伐梧”條下引《列子》原文:《列子·說符》篇:人有枯梧樹,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為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其可也?這樣的處理方式與敦煌《列子》的處理方式極為相似。“教吾伐梧”是以大字形式出現的一個條目,后面的《列子》引文則是以小字雙行形式出現,是對上面條目所作的解釋說明。
敦煌殘卷中還有一處值得特別注意的地方,就是引用了張湛的注文。編號P2495殘片“合得遺契”下小字雙行文為:宋人有于道得人遺契藏之,密數其齒。注云:刻處似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這里出現了一處“注云”,其為張湛原注。楊思范認為這是敦煌殘卷作者新注中所殘留的張湛注文,此說不甚恰當。若是新注,則注文作者一般都注明作者,如張湛注中就多處引用郭象、向秀的文字,均注明“郭象曰”、“向秀曰”,此處若是新注,則應標明“張湛曰”,但卻直接用“注云”,并未出現任何的新注跡象。
由此可知,編號S6134與編號P2495所代表的敦煌本《列子》,以張湛注本為基礎,在原文的文字基礎上進行重新整理,根據一定的標準對原書文字進行刪略。所選文字也盡量保留原意,而以說理為主。以小字形式出現的文字,既是對選文的進一步說明,又是根據張湛注本《列子》進行的又一次刪節,且為說明問題,其中還采用了張湛的注文來作進一步說明。而且,重要的是其中僅僅是選取《列子》原文而對其所節選的文字作進一步說明,并未加入作者的任何發揮性話語。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看,編號S6134與編號P2495所代表的敦煌本《列子》不能算作是《列子》的一個注本,稱其為選本似更恰當一些。
注釋:
① 由于寫卷多有殘缺及字跡漫漶而無法辨認字句之處,為保持文
獻原貌,凡是無法辨認字句的地方,本文一律以“”符號代替。
② 楊思范認為這兩張殘片出于同一張寫卷,筆者認為這種判斷過于武斷。對于敦煌文本的鑒定,方廣锠先生已明確指出,不應僅從文字的相若來斷定其是否相同,對于紙張的鑒定、書寫的款式等各方面都應綜合考慮。由于我們無法見到實物,只憑文字不能貿然決定。
③ 嚴靈峰整理文字為:邯鄲民以正月旦獻趙簡子鳩簡子曰放之正旦放之示有恩也厚賞獻容于是民爭鳩死者眾矣欲之不若禁勿捕之。未斷句。楊思范在整理文字為:邯鄲民,以正月旦,獻鳩趙簡子,鳩簡子曰:放之正旦方,示有恩也。厚賞獻客,于是民事之,死者眾矣,生之,不若禁民勿捕之也。兩相比較,楊文不若嚴文符合實際,且斷句多處不通。此處系筆者參校兩者文字,再仔細比對殘片整理而成。
④ 嚴靈峰整理文字為:人有得金者而去吏捕得問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耳。楊思范整理文字為:齊人有欲得金者,旦衣冠往市,適貨金者,因攫而去。吏捕得,問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但見金。嚴文省略甚多,楊文斷句不恰當。
⑤《南史·庾仲容傳》載“仲容抄子書三十卷,諸集三十卷,眾家地理書二十卷”,《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均著錄。今佚。
參考文獻:
[1] 英藏敦煌文獻(漢文佛經以外部分)[Z].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0: 96?97, 148.
[2] 法藏敦煌西域文獻. 第十四輯[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309?310.
[3] 王重民. 敦煌古籍敘錄[M]. 北京: 商務印書館, 1958: 257?258.
[4] 張湛. 列子注[M]. 民國間《四部叢刊》影宋本.
[5] 馬總. 意林[M]. 民國間涵芬樓影印明正統《道藏》本.
[6] 魏徵. 群書治要[M]. 民國間涵芬樓影印明正統《道藏》本.
[7] 楊思范. 敦煌本《列子注》考[J]. 文獻, 2002, (3): 16?20.
Sorting out The Incomplete Liezi from Dunhuang——
and discussing it with Mr Yang Sifan
LIU Peid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Liezi from differences the earliest edition in extant text, and it is obviously of great value. There are between the incomplete Liezi from Dunhuang with the Liezi of today in style. From the document, it seems to be another book by someone comment. When we inspected the interrelated abridged edition, we knew it is just an abridged edition of Liezi.
Key Words: Liezi; Dunhuang; abridged edition; style
篇6
【關鍵詞】樹立;警察戰術理念;技能培養
一、樹立現代警察戰術理念
人民警察是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的守護神,警察是世界黑白間的一堵墻。和平年代,沒有哪一種職業會像警察那樣時刻面對生與死的考驗,沒有哪一種職業會像警察那樣隨時要準備付出血的代價。當你在萬家燈火平安之夜盡情歡樂時,當你舉家團聚安然入夢時,你可曾想到這一切融進了我們警察的生命、鮮血和護衛?
從頭頂國徽、穿上警服的那天起,為人民的利益勇于獻身就成為他們無悔的選擇。但是,警察也是凡人,他們也有母親,也有戀人,也有妻兒。
他們也懂得生命的珍貴,也留戀美好的生活。可是為了社會的安寧,他們用熱血寫就了輝煌,用生命鑄造了警魂。他們的人生雖然短暫,卻光彩奪目,令世人仰止。
畢竟,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面對我國每年幾百名警察因公犧牲、幾千名警察因公負傷的沉重數字,特別是面對執法戰斗中的警察被暴力犯罪分子攻擊而流血犧牲的沉痛現實,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一個沉重的問題,即在取得最大的治安成效的同時,如何最低限度地減少警察的傷亡,這是我們必須探討的嚴峻問題。
這些年來,我國警察在執法戰斗中壯烈犧牲的案例很多。有些案例一直縈繞在我們的心頭,而且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如2002年2月15日,湖北省某市公安局一名派出所指導員帶領一民警巡邏時,接到“110”指揮中心要求處置一起持刀殺人搶劫案的指令,二人迅速趕赴現場。在抓捕犯罪嫌疑人過程中,只攜帶警棍的二人敵不過手持殺豬刀的犯罪嫌疑人,指導員被刺犧牲,另一民警被刺成重傷。2005年3月23日下午,河南省某市公安局反扒支隊接到舉報,有4名竊賊在某公交車站伺機行竊。竊賊在公交車進站時,趁機將一名女乘客褲兜內的手機偷走,并擠出人群準備逃竄。赤手空拳的5名反扒民警從四個方向同時上前抓捕,竊賊掏出匕首猛刺竹警官的左胸,鮮血頓時染紅了公交站牌的立柱。這名竊賊趁機逃走,4名竊賊中的另一名也趁機逃走。下午6時許,竹警官因失血過多壯烈犧牲。這就是我們要說的戰術理念。人們普遍認為,我國警察高傷亡的主要原因是警察反制抗暴的技能低、裝備差等。其實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于,我們的警察還缺乏戰術理念。
具體來說在執法戰斗中,我們的警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我國警察的傷亡自然與警察缺乏嚴格的戰術訓練、抗暴技能差,由于立法和有關規章制度內容的不確定性,導致民警有槍不敢用,同時缺乏相應的警用武器裝備。因此,加強警察的戰術技能訓練,配備先進的警用武器裝備,完善有關立法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我們如果從更深層次進行分析,就應看到我們的警察缺乏自我保護意識,這是我國警察高傷亡的一個根本原因。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治安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特別是暴力犯罪多發,暴力手段殘忍,包括警察在內,都成了犯罪分子暴力侵害的對象。但是我們很多警察的防衛意識還沒有適應這樣的治安形勢,仍然憑著“平安無事”或“我是警察誰敢動我”的盲目感覺執法。即使進入戰斗狀態,也“如入無人之境”。因此,一旦遇到暴力襲警時,無法迅速作出反應,往往不知所措,陷入被動。
上述原因有直接關系,由于警察缺乏對戰斗的反應能力,也就是當危險的緊急狀態突然發生時,不能夠迅速作出心理與行為反應來化解危險,從而造成無謂傷亡。樹立現代警察戰術理念,能從容應對執法戰斗,保護自己,克敵制勝。警察戰術理念的核心,就是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保護自己才能完成執法戰斗任務。警察上崗執法,特別是一線警察執法,就是處在一種臨戰狀態之中,頭腦中必須要樹立起戰術理念。
現有的對警察戰術的研究成果不少,但實際上主要是對警察戰術技能的研究,這對警察的執法戰斗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本人認為,對警察戰術還應該從另一層面去研究,即研究適用于當今執法戰斗的戰術理念。警察戰術應該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警察戰術技能;二是警察戰術理念。“理念”實際上就是我們對某種事物的觀點或看法。警察戰術理念就是我們對警察戰術活動內在規律的認識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對警察戰術活動的看法和觀念。
警察戰術理念與戰術技能不同。首先,戰術理念主要表現為心智;戰術技能主要表現為動作。其次,戰術理念活動的對象是頭腦的映象,具有主觀性;戰術技能活動的對象是具體的犯罪嫌疑人、武器及其動作操作。再次,戰術理念是借助內在語言思維來實現;戰術技能是一系列動作的連續。最后,戰術理念著重掌握正確的思維方法;戰術技能著重要求掌握一套行為反應聯結。
警察戰術理念與戰術技能又是相互聯系的:首先,兩者相互依存,戰術理念在戰術技能基礎上形成;戰術技能必須依靠戰術理念指導。其次,兩者相互提高,戰術理念建立在戰術技能基礎上,并不斷地總結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不斷改進;戰術技能又是依靠先進的戰術理念指導不斷得以提高。
我們研究警察戰術理念,具有很強的實戰指導意義。首先,警察戰術理念是警察與犯罪嫌疑人進行戰斗的指導思想和行動指南。
可以這樣說,有什么樣的戰術理念就會產生什么樣的戰術行為,戰術行為受戰術理念的支配。我們以案例說明:
黑接江省某客運站附近發生一起持刀傷人案件。已經下班的鎮派出所民警劉警官路經客運站時得知這一情況;他立即安排在場群眾將受傷人員送往醫院,同時與其他民警去抓刺傷人逃跑回家的犯罪嫌疑人張某。這時已是晚⒏時左右,天特別黑,劉警官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從后窗逃跑,便一人趕到后院進行堵截。這時被驚動的張某狗急跳墻,手持尖刀,從后窗跳出。劉警官不顧個人安危,沖上前去拽住張某說: “我是警察,請你跟我們到派出所去一趟。窮兇極惡的張某不容分說,掏刀就佝劉警官胳膊連刺兩刀,劉警官仍不松手。犯罪嫌疑人張某又朝著劉警官的腹部連刺數刀。在腹部、胸部、腋部、胳膊、背部連中7刀的情況下,劉警官依然抓住張某就是不放,與犯罪嫌疑人進行殊死搏斗,直至失血過多,體力不支,被張某掙脫逃跑。距窗戶十幾米距離的范圍內灑盡了英雄的鮮血,當同去執行任務的民警聞聲趕過來時,劉警官已倒地休克。劉警官肝臟、腹部、肺部均為貫通傷,腋下動脈血管破裂,因失血過多,經搶救無效犧牲。當地政府發出通知,學習他英勇無畏、不怕犧牲的崇高精神。劉警官赤手空拳被刺傷時,就應該放開犯罪嫌疑人,以避免受到進一步的傷害。“民警不畏身中數刀,勇擒歹徒決不松手”的宣傳,客觀上鼓勵其他民警不顧受傷情況,寧死也要斗到底。
其次,警察戰術理念分為兩個層次:宏觀戰術理念及操作層面的戰術理念。宏觀戰術理念從理論上說是對警察戰術總的、一般的看法;操作層面的戰術理念,是在具體的戰術情景中運用某些心理學、戰術學理論,使之實踐化,并具有可操作性。本文盡量避免空洞的理念闡述,而是運用大量的案例進行分析,以案例表明觀點,從形象化的角度,清晰簡明地分析戰術理念,使民警處于緊急戰斗情境時能運用自如。本人經常到深圳等一些公安基層單位進行警察戰術理念調研。
我們傳統的執法戰術觀念,首要想的就是如何戰勝犯罪分子,而對自己的人身安全則毫不考慮,因此,人家說“中國的警察不怕犧牲,敢于犧牲”。其實“不怕犧牲,敢于犧牲”,在精神上可以提倡,但從戰術理念角度是不能提倡的。現代警察戰術理念的核心就是首先要保護好自己,然后戰勝犯罪分子,即要求執法中始終要保持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如何保護好自己,關鍵是我們的警察要在頭腦中牢固地樹立現代戰術理念,才能在執法戰斗中,特別是在突發的戰斗中,迅速反應,靈活機動地實施戰術技能。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警察在執法戰斗中既要保護好自己,又能戰勝犯罪分子,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因此,研究現代警察戰術理念,是嚴峻的執法戰斗的需求,也是愛護警察的一種責任。
二、警察技能培養的方法
由上可以看出,隨著暴力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警察在執行職務中傷亡人數不斷增加,為減少或避免警察的傷亡,必須加強警務技能訓練,主要做好以下幾點:
(一)體能訓練。無論是制服犯罪嫌疑人還是執行不分晝夜的追逃任務,都要求警察有強健的體魄和充沛的精力作保證,因此,體能訓練是其他警務技能訓練的基礎,是確保司法警察履職效果的保障。強化體能訓練作為經常性訓練的內容,其重要性是勿庸置疑的,關鍵是如何確定訓練項目,保證訓練效果。通常,體能訓練的要求包括力量、速度、耐力、柔韌性和抗擊打能力五個方面,因此在訓練中就應綜合這五項內容,制定科學的訓練項目。當然,訓練的內容多種多樣,重要的是能持之以恒,警察也可根據當地實際作適當地調整,只要能達到訓練目的就行,有條件的地方還可以因地制宜地增加如拳擊、游泳等訓練項目。
(二)隊列及擒拿格斗訓練。隊列訓練、擒敵(捕)拳訓練、摔擒技術訓練是此項訓練的主要內容,本人之所以將它們合而為一,主要是考慮到三者之間在實際操練時往往依次進行,合并訓練效果會更好。此外,隊列及擒拿格斗訓練與體能訓練的結合也很緊密,只有通過一定量的體能訓練,提高身體素質才能更好地完成各種摔擒動作練習。
隊列訓練是警察系統訓練的基礎,也是警察精神面貌的一種表現,通過嚴格地訓練不但能加強團結、嚴整警容風紀,還能提高隊伍的組織紀律性、增強戰斗力。因此,不能因為隊列訓練的內容單調、枯燥就不認真,走過場,要隨時保持協調一致的動作和嚴肅緊張的工作作風。訓練時應從單個隊列動作開始,動作規范后再進行分隊的隊列動作練習,最后達到整齊劃一、步調一致的效果。
擒敵(捕)拳和摔擒技術的訓練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擒敵(捕)拳是擒敵技術主要動作的單人綜合練習,為保證訓練效果應對參訓人員逐個進行動作指導直至熟練,而后可以集體練習,要求動作協調、一致。而摔擒技術訓練則從實戰出發,要求操、配手配合默契,掌握動作要領,通過訓練達到迅速制服對手的目的。擒敵(捕)拳訓練一般以現行16組動作為主,摔擒技術訓練可在倒功(前倒、后倒、側倒)、絆腿跪襠、掀腿壓頸、涮腿踹腹、擰踝跪膝、挾頸別肘、抱腿撞襠、抱臂踹肋、抱腿跪襠、卷腕奪刀、挾臂奪匕首、頂摔鎖喉、擊腹別臂、抱腰解脫、鎖喉解脫等組合練習中全部或部分選擇進行有針對性的訓練。由于摔擒技術難度大,危險性高,稍不注意就會造成損傷,因此在保證動作完成質量的同時也要確保訓練人員的安全,嚴禁擅自進行高難度和無保護動作的練習,以及在訓練時追逐、打鬧。
(三)警用裝備使用訓練。警用裝備一般包括警用械具、警用車輛、警用通訊工具及監控設備等,熟練地掌握它們的使用方法是保證履職任務順利完成的基本要求。
警用械具通常包括警棍、手銬、警繩等攻擊性器械和盾牌、警笛等防衛性器械,其中手銬、警棍是使用頻率最高的,手銬的前銬、后銬、一銬兩人、兩銬兩人等使用方法要經常練習,既要保證辦案安全,又要防止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肢體造成損害。警棍的使用可配合警棍術進行練習,同時考慮到大多數警察支隊、隊都配備了電警棍,對其使用方法也應該加強了解,安全使用,掌握使用電警棍迅速制服試圖行兇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方法。此外,像警繩、腳鐐等舊式警械的使用方法也應加強訓練,有條件的地方還應及時更新警用裝備并熟練掌握其使用方法。同時,警用械具在不斷更新,操作要求和科技含量都在提高,我們的訓練內容也要與時俱進,不能還是“小米加步槍”了。同時要強調人性化執法,如及時給貼身的警械具消毒,使用一次性面罩等。
(四)射擊訓練。射擊訓練一般就是特指手槍射擊訓練。熟練掌握射擊技術和槍支的佩戴、保管、使用等方法是該項訓練的重要內容。首先,認真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讓每名警察都牢記在什么情況下才能使用武器,同時結合心理訓練,克服因緊張、害怕等心理因素造成的武器使用不當、射擊精度不高等問題;其次,熟悉槍支的結構并能熟練地進行分解、結合,同時掌握槍支保管、擦拭、檢查及故障排除的方法;最后,在進行實彈射擊訓練時要嚴格執行射擊場的組織和安全規則,掌握要領,循序漸進,提高成績。
近年來,槍支管理越來越嚴格,出現緊急情況倉促使用易出問題、甚至是大問題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因此,我們只有通過刻苦地訓練做到“平時多流汗,戰時少流血”。
(五)其他訓練。除了前面提到的四種警務技能訓練外,本人認為下面幾項訓練內容也十分重要:
1、綜合戰術訓練。警察在參與執行追逃、警戒、保護犯罪現場及搜查等任務時,周密部署、相互配合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相應的綜合戰術訓練就顯得尤為重要。
2、心理素質訓練。良好的心理素質是司法警察必備的素質之一,其考核在幾年前就已經納入了公安機關錄用警察的考試范圍,與體能和業務知識并重。由于心理上的問題或一時沖動造成的悲劇是有慘痛的教訓的。因此,警察在加強組織紀律學習的同時也要加強心理素質訓練,遇事保持冷靜,學會釋放壓力,并建議在錄用警察時增加心理素質測試。
3、野外生存訓練及創傷急救訓練。無論是辦案出差還是執行追逃任務,出現意外時野外生存和創傷急救本領都是重要的技能。實際訓練時可以通過組織拉練,到醫院實習,聽專家講解等形式進行。
【參考文獻】
[1]何貴初.現代警察戰術理念――如何避免致命錯誤[M].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
[2]陳曉明.警務實戰基礎與安全[M].國防科技大學出版社,2006.
篇7
[關鍵詞]袁黃勸善功過格
在晚明思想界,勸善是一種很流行的思潮,“各種‘功過格’‘感應篇’‘陰騭文’等宗教倫理之色彩非常濃厚的道德實踐手冊或通俗倫理教科書竟然一下子大量涌現,稱其為一場思想運動毫不為過。在這一思想運動中,袁黃無疑是最突出的一位。袁黃(1533-1606年),字坤儀,號了凡,浙江嘉善人,萬歷十四年(1586年)進士,明代著名學者。他的勸善思想尤其是其功過格思想,在十六七世紀影響很大,清初思想家張履祥在《與何商隱》的信中說:“袁黃功過格,竟為近世士人之圣書。”當然,張履祥站在程朱正統的角度上,尤其是站在其師劉宗周所為《人譜》的角度上,對袁黃持批評態度。《告先師文》中,張履祥說:“本朝至隆、萬以后,陽明之學滋敝,而人心陷溺極矣。卑者冥冥于富貴利達,既惟流俗之歸,而其高者率蠱于李贄、袁黃猖狂無忌之說,學術于是乎大裂。”雖然被攻擊為“猖狂無忌”,卻也客觀地表明袁黃勸善思想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的現實。袁黃的功過格思想也一直影響到18世紀,其《了凡四訓》更是屢經刊刻。因此,在十六七世紀的勸善運動中,袁黃的功過格思想有重大意義。酒井忠夫稱袁黃功過格在善書思想的發展史上“產生了劃時代的意義”,不為過譽。那么,袁黃的勸善思想根源是什么,為什么對社會上一般民眾具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在勸善思想發展史上,袁黃的貢獻是什么?
一、袁黃勸善思想中的儒學因素
袁黃的父親與王畿、王艮等人都有交往,而袁黃本人是王畿的門人,與王畿的其他門人丁賓、周汝登等人都有交往。因此,從學術淵源上看,袁黃屬于陽明后學。沈大奎在《訓兒俗說序》中說:“司馬坤儀袁公幼即志圣賢之學,從事于龍溪諸先生之門。”袁黃亦自言:“我在學問中,初受龍溪先生之教,始知端倪,后參求七歲,僅有所省。”因此袁黃對于心體的論述始終是陽明后學的論調,強調即凡即圣。陽明后學式的思想表達在袁黃作品中隨處可見。其論“明明德”云:“明德不是別物,只是虛靈不昧之心體。此心體在圣不增,在凡不減……汝今為童子,自謂與圣人相遠。汝心中有知是知非處,便是汝之明行,但不昧了此心,便是明明德。針眼之空,與太虛之空,原無二樣。吾人一念之明,與圣人全體之明,亦無二體。”陽明曾對朱子所言“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一語曾加一“心外無理,心外無事”的轉語,意指心體為虛靈不昧。“一念之明與圣人全體之明,亦無二體”的思想也與王陽明所說不同分量精金只論足色不論分量的思想很相近。袁黃論“至善”,亦以“虛空”為喻,說:“何以見至善?此德明朗,猶如虛空,舉心動念,即乖本體。”這與陽明、王畿以來以“無善無惡”釋“至善”一脈相傳。袁黃論“親民”,也是謹守陽明學遵行古本《大學》的路徑。當然,袁黃曾以同為嘉善籍的云谷禪師為師,習靜坐之法,又交妙峰法師,深信天臺之教,受到佛學的影響。他說:“吾師云谷大師靜坐二十余載,妙得天臺遺旨,為余談之甚備。余又交妙峰法師,深信天臺之教,謂禪為凈土要門。”從《祈嗣真詮》看,袁黃自述還曾經在南京棲霞寺得異人傳授祈嗣之訣,謂“天不能限,數不能拘,陰陽不能阻,風水不能囿”。雖然沒有說這異人的身份,但屬于宗教人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袁黃的勸善思想毫無疑問糅合了三教的思想。在儒、佛、道三種思想中,盡管有些學者認為對袁黃“心性”修養影響最大的乃佛門中人,但在袁黃勸善思想的表達中,儒學及陽明心學的痕跡是非常清晰的。
袁黃的勸善觀念有其哲學根源,而這種哲學主要是儒學。袁黃對于勸善的熱衷與投入,源于他對儒學中“親民”與“萬物一體”等思想的理解。在討論“親民”時,袁黃對兒子說:“親民以萬物為一體則親……汝今未做官,無百姓可管,但見有人相接,便要視他如骨肉則親,敬他如父母,則親。倘有不善,須生惻然憐憫之心,可訓導則多方訓導,不可訓導則負罪引慝以感動之。”在陽明的思想中,親民不只是修身,不只是自了,袁黃同樣是這么認為的。那么,對于為官之人來說。親民就是安百姓,但是沒有官位的人既然不能只圖自了,那又該如何親民呢?袁黃提出的親民之法便是與人相接使其感到親近,使不善之人負罪引慝以感動。見不善,可訓導則多方訓導,這是每個人都可以做到的。因此,勸善思想在袁黃那里的來源之一就是作為儒學士人“親民”的社會責任感。由“親民”觀念可以發展到為官愛民的政治理念,也可以發展到勸人行善的教化觀念。袁黃自己說:“親民原是吾儒實學,故一切眾人,皆當愛敬。”因此,袁黃對于勸善的熱情,有其根源于儒家思想的部分。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改過”是王學重要的議題之一。晚明大儒劉宗周也說,致良知必須落在“改過”上講。重視“改過”在明代中后期的表現是,思想層面上對自省、內訟的強調和實踐層面上大量省過簿的出現。功過格雖然借用了宗教的形式,但其思想的根源卻是明代中后期以來儒學尤其是陽明學的“改過”思想。
進而言之,在對“善”的闡釋上,袁黃的勸善思想還清晰地表露了他作為陽明后學的特點。正如儒學士人經常強調義利之辨一樣,袁黃強調“善有真有假”。他曾經借中峰和尚之口說:“有益于人是善,有益于已是惡。”由此出發,對于善的評判不在于事物或行為的表面,而在于動機或本心。袁黃說:“是故人之行善,利人者公,公則為真。利己者私,私則為假。又根心者真,襲跡者假。又無為而為者真,有為而為者假。”在這里,利人與利己、公與私、心與跡、無為與有為,成了“善”與“惡”的分界,成為判斷行善與否的標準。只有根源于本心,而不流于外在形跡,那樣的善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善。因此,行善不是要邀譽,不是要獲得回報,而只需要遵從自己的本心。因此,袁黃又說:“凡欲積善,決不可狗世人之耳目。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默默檢點。純是濟世之心則為端,茍有一毫媚世之心即為曲,純是愛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憤世之心則為曲,純是敬人之心則為端,有一毫玩世之心則為曲,皆當細辨。”所謂濟世、愛人、敬人的勸善之心。必須是純粹的,不夾雜一絲一毫的媚世、憤世和玩世的心。唯有秉持這樣的心,行善、勸善才是真正之善。因此,人們行善應不著于善,“心不著于善,則隨所成就,皆得圓滿;心著于善,則終身勤勵,止于半善而已”。
二、袁黃勸善思想表達之策略
袁黃的勸善思想為什么影響大,為什么能吸引社會大眾?除了袁黃的勸善思想契合了普通人的心理之外,其表達策略也值得研究。其一,袁黃在其勸善思想的表述中,抓住了當時社會人群最關心的兩個議題――科舉與子嗣,而這兩件事情在明清社會無疑是人們最重要的關注。正如袁黃門人韓初命在《刻祈嗣真詮引》中所說:“子嗣于人生系至重矣,曷論王公韋布、貧賤富貴之殊?”袁黃向人們積極宣揚,一個人積善就可以得子。他說:“愛者生之本,忍則自絕其本矣。君子寧過于愛,毋過于忍。”另外,在明代社會,科舉可以說是整個社會的耦合劑之一。一位研究者主張,在看待明清社會的科舉時,要由錄取者擴展到整個應試群體,再擴展及家庭,以此視角看待明清時代科舉制影響的真正范圍及其深入社會的路徑。因為即便通過科舉改變身份的概率不大,但“在實際社會生活中,人們仍然對科舉制抱以極大的熱情,科舉考試在日常生活中處于中心地位”,形成“社會結構以士紳為中心、社會價值以功名為中心”,而“這兩個中心耦合成傳統社會整合的重心”。正因為人們的高度關注,晚明各類與科舉相關的傳說、夢境都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袁黃勸善以科舉、子嗣為話題,容易獲得人們的認同感。
其二,從表達策略上來看,袁黃在宣講其勸善思想時,常以近人為例,甚至以自己為例。例如,他講鎮江靳翁拒納鄰家女為妾而終生子,而子最終取科第,為大學士;又如舒芬的父親因捐金十三兩代人償官銀而救人一命,生子舒芬.為正德十二年(1517年)進士第一;屠勛疏請恤刑而生三子,“子孫科第,至今未絕”;邯鄲張翁積錢十年而代鄰人完贖銀,得子弘軒先生,子孫相繼登科第。這些都是求子、子孫獲科第結合的典型案例,“一念之善,遂成世家”,足以動人。袁黃甚至還常以自己為喻,以傳記、訓子書的形式來傳遞這種思想觀念。例如,袁黃勸人重視祭祀自己的祖宗,就強調這是自己的經驗,說:“我在寶坻,每祭必盡誠,禱無不驗。天人相與之際亦微矣哉!”在一個故事的流傳中,在一種道德信念的宣講中,事情的真偽往往在其次,有沒有具體的活生生的人來“認領”無疑是最重要的。袁黃本人是這種善惡報應事例的最生動的認領者。這并不意味著袁黃在講述這些故事的時候有偽造和虛構的成分,而是說他愿意坦然地以自己作為故事的主角講述出來,本身就是勇于勸善的表現。
其三,袁黃的勸善思想雖然融合三教,但根本不離儒學,而且始終抓住緊貼普通人的倫常綱紀來做文章。孔子奠定了中國儒學“親親”的原則,即一切社會行為的出發點要從自己做起,從身邊的人與事做起。這也確立了儒學與佛道之學的差異。同樣,家庭倫理是袁黃勸善的首要著眼點。他的勸善思想的表達常以家訓或訓兒語的形式呈現,而重視家庭倫常、以倫常為先是中國傳統家訓最基本的原則。在袁黃的《訓兒俗說》中,“立志第一”之后緊接著便是“敦倫第二”。袁黃認為,只有從恪守夫婦、父子之倫做起,方有推而廣之的可能,“以此事君則為忠臣,以此事長則為悌弟,無時無處而不愛敬,則隨在感格”。袁黃本人也著力實踐這種家庭倫理,有睦族之舉。袁黃訓子云:“吾家族屬不多,自吾罷宦歸田,卜居于此。族人皆依而環止。今擬歲中各節,袒嶙迦耍正月初一外,十五為燈節,三月清明、五月端午、六月六日、七月七日、八月中秋、九月重陽、十月初一、十一月冬至,遠者亦遣人呼之,來不來唯命。此會非飲酒食肉,一則恐彼此間隔,情意疏而不通,二則有善相告,有過相規,即平日有問言,亦可從容勸諭,使相忘于杯酒間。睦族與勸善融為一體,勸善才可以深入人心。
其四,行善之法簡便易行,因而更吸引人。欲導人向善,當教人如何行善。然而,設置的目標越虛玄越高遠,則對普通人的吸引力就越遠。但袁黃卻不同,他的勸善從強調家庭倫常開始,因此容易實施,不易受到傳統家庭倫理的抵制。而且,袁黃提倡隨緣濟眾,不著意地給每個向善之人增加額外的經濟壓力,從而使行善簡單易行。袁黃說:“隨緣濟眾,其類至繁。約言其綱,大略有十。竊謂種德之事,第一與人為善,第二愛敬存心,第三成人之美,第四教人為善,第五救人危急,第六興建大利,第七舍財作福,第八護持正法,第九敬重尊長,第十愛惜物命。”在這十類行為之中,盡管有施財的內容,但大部分還是要求人們精神上向善。而且,袁黃也強調說,人們勸善不是要去直接地出言教人,而是要“收斂才智,若無若虛,見人過失,且涵容而掩覆之,一則令其可改,二則令其有所顧忌而不敢眾。見人有微長可取,小善可錄,翻然舍己而從之,且為艷稱而廣述之”。這大概也是前述第三條的“成人之美”、掩人之惡的具體解釋。這樣的行為雖不難,但往往是之前勸善思想所忽略的。至于如何“隨緣濟眾”,袁黃在《凈行別品》中談得甚多。袁黃認為,《華嚴凈行品》中“觸事遇物,輒求有益于眾生,萬類在懷,一膜可撤”實儒家“親民之上軌也”,因此仿其意而將“儒者所宜行”者隨類演輯,廣列若干事,作《凈行別品》,所載均系生活中常見的細碎之事,但卻是行善之路徑。
三、袁黃對勸善思想之發展
勸善思想在儒學歷史上起源頗早。儒家倫理說教中對“德福之道”的闡述,最早可追溯到《尚書》《國語》等先秦著作。從《尚書?洪范》“五福”之一的“攸好德”、《春秋》“懲惡而勸善”之義法、魏晉時代善惡報應和因果輪回的表述,直至明代陽明心學的勸善思想、明末清初的勸善運動,源遠流長。朝廷在勸善的推動上也常起到重要作用。在明代,《為善陰騭》《孝順事實》之類的御制勸善書流傳甚廣。從16世紀起,勸善與鄉約等基層教化相結合,由官方或士紳號召向下層擴展。晚明以同善會為代表的勸善運動也在南北多地展開。袁黃的功過格思想正是這種大背景之下的產物。然而,無論從縱向的源流看,還是從同期的勸善運動背景來看,袁黃的功過格都有特別的意義。
晚明勸善成為風潮,不僅陽明后學勵行勸善,以程朱為宗的東林學者也積極響應勸善思潮。像周汝登、袁黃等人,均是王門后學,王畿的門人,勸善尤篤。東林學派的高攀龍、錢一本等人,也倡行同善會以勸善。這一思潮的出現,更多地似乎有應對社會現實的無奈。高攀龍說:“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如樹之必枝葉必花必實,自然而不容已也。彼豈以善之可以有功獲福而為之乎?然而人之為不善者,動于欲而不能自克,語之以禍福,猶有所慕而勉、畏而不敢,語之以理則以為迂而無當……姑以禍福告人,引不知者入于善也。入而安焉,而后知人之不為善乃樹之不枝葉不花不實者也,伐無日矣。”在高攀龍看來,人之為善雖然像“樹之必枝葉必花必實”一樣乃是自然不容已的,然而對于那些陷入欲望之中而不能自拔的人來說,以禍福勸諭使其向善,乃是一種權宜之法,可以逐漸讓他們在行為上向善,最后知“理”。對于袁黃來說,勸善不只是改變社會道德狀況的權宜之策,而且是根本之學。
袁黃的貢獻,是把勸善的形式由公共的、說教的、例證的轉化為個人的、私密的、可以量化的。他繼承了儒學重視道德與倫理的傳統,同時結合了道教功過格的形式,從而使勸人為善與自修緊密地結合起來。儒家對于個人道德修養的要求,不只是在公共場合如何說如何做,而且對私密環境中如何思考、如何為善去惡也提出了要求,即所謂君子不欺暗室。然而,在袁黃推廣功過格之前,勸善與自修之間存在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勸善更多體現在言語上、行事上,而它究竟能讓自己內心得到多少凈化是不清楚的。而功過格不一樣,功過格既可以用以勸人為善,也可以用以自修,作為自己改過向善的工具。因此,功過格就不會像一般的善書、鄉約俗講那樣流于言語之間,流于外在形式之上,而更強調個人的自覺性。完全做到不欺暗室,大概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到。然而,既然勸善要針對每一個平凡的個人,那么能否做到暗室中稍有警醒自律,或者過后而能反思,也是一種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善惡報應,只是督促人們信還是不信,是外在的、附加的,而功過格本身所具有的私密性、個人性,充分表明了這種修習方式更強調人的自覺。實際上,如果追溯淵源,功過格在形式上雖然取材于道教的功過格,但其思想根源卻更多地源于明代中后期士人克己改過的思想,而且更像是通俗易行、底層民眾可以操作的修身日記。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功過格的出現,不但不會使勸善流于形式,反而是個人修行可以鞭辟入里的工具。因此,勸善在同時代許多思想家那里也許是權宜之計,而在袁黃那里卻是根源深處的修行之法。這一點應該說同時代的思想家周汝登看得很清楚。周汝登在萬歷二十九年(1601年)《立命文序》一文中,以對答的方式表達了他對袁黃功過格思想的評價:“客曰:‘子談無善無惡,宗旨奚取?茲言果盡上乘語耶?’余日:‘無善者,無執善之心。善則非虛。未嘗嚼著一顆米,而饔飧之養廢乎?未嘗掛著一縷絲,而衣裳之用缺乎?且中所述云谷老人語,明禍福由已,約造化在心,非大徹者不能道。謂非上乘法,不可也。’”周汝登認為,袁黃的勸善不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是上乘之法。而且,受袁黃的影響,周汝登也作《日記錄》。周汝登《日記錄序》云:“余覽了凡公立命之言,因以勸二三子共發積善之愿,而予以身先焉,為綠以記,月系以日,日系以事,雖纖小弗遺,雖冗沓弗廢也。客有問日:‘子為是,弗勞矣乎?’日:‘樂此,則不為疲矣。不有博奕者乎,予差以是勝之。’客日:‘善可紀,不有限矣乎?’日:‘余旦旦而起,則竊自念日:其無忘是綠乎?一喚醒問,而吾之善念已盎然溢矣。”那么,當人們質疑說,善可以用數量來統計嗎?周汝登說,當我們在統計善或者說記錄善的時候,我們的善念就會盎然溢于全身。而且,內省、自訟此類的傳統士人修身之法,經過功過格的“量化”的轉變,成為普通大眾都可以接受和實施的修行之法。
因此,在善書思想演變史中,袁黃功過格帶來兩個轉變:一是由例證式的、說教式的轉變為可操作的、可實踐的;二是把過于理想化的修行方式向現實作了一定的妥協,從而保證善書的實際效用。后來劉宗周及其門人對功過格的不滿主要在于功過格所秉持的功過抵消的思想。因為在正統的思想家看來,人在道德境界上,應該是要不斷地、單箭頭式地向上攀登,而功過相抵便有可能導致人在這一向上路徑上偶爾墮落而且輕易地原諒自己。這是正統的儒學思想家所不能接受的。然而,既然功與過都是這個現實世界中存在的,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烏托邦式理想的道德直線主張又有什么意義呢?
篇8
一、生態農業――江南農業的一種新經營方式
二、江南生態農業的特點
三、江南生態農業的生產率
四、生態農業在江南的普及歷史意義
五、質疑與回應
近年來國際經濟史研究中的一個熱點,是如何用新的眼光來看工業化以前(pre-industrial)的經濟 [1] 。其中的焦點問題之一,又是如何對所謂的傳統農業作出評價 [2] 。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那種我稱之為“近(現)代人對過去的傲慢與偏見”的盛行,傳統農業一向被當作陳舊、過時和落伍的代名詞。然而近年來,隨著社會科學的發展,學界對西歐中心論和由此派生出來的“近(現)代至上”論的批判也日益深入。在此背景下,人們也越來越多地發現了近(現)代農業的弊病和傳統農業中的積極因素 [3] 。在這方面,生態農業就是一個重要的例子。
“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是二十世紀中后期發達國家中出現的一種針對現代農業的弊端而提出的新農業理念。所謂“現代農業”,也稱“石油農業”、“化學農業”或“石化農業”,其主要特點是通過資源、技術的大量投入和生產的集約化,獲取更多產量和經濟收入 [4] 。由于現代農業片面強調農業生產效率而輕視生態環境保護,因此在實現大幅度增長的同時,也使得環境污染加劇,土壤侵蝕、退化,農產品質量下降,而大量的投入也使農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種人口與環境、資源與生態、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不平衡,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農業與人口、環境、資源之間的關系,使得農業生產與生態環境彼此協調,以求農業的可持續性發展,并且保證人類生存環境的改善。
基于這種考慮,自1960年代末以來,許多國家先后提出了有機農業、無公害農業、生物農業、自然農業、持續農業等概念,并將其作為新的農業發展模式付諸實施。由于這些模式都以生態、自然資源保護與農業協調發展為主要內容,所以也統稱為生態農業 [5] 。但是這里所說的生態農業,還只是廣義的生態農業[6] 。狹義的生態農業的概念,是美國土壤學家阿爾布雷奇(W. Albreche)于1970年首先提出的。英國農學家沃星頓(M. Worthington)于1981年對生態農業作出明確的定義,即“生態上能自我維持,低輸入,經濟上有生命力,在環境、倫理和審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農業”[7] 。此后,學界對生態農業的認識繼續不斷改進和發展。到了今天,按照比較普遍的理解,生態農業指的是以生態經濟系統原理為指導建立起來的資源、環境、效率、效益兼顧的綜合性農業生產體系。在這種生產體系中,運用生態學、生態經濟學原理和系統科學方法,把現代科學技術的成就與傳統農業技術的精華有機結合,把農業生產、農村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治理與保護、資源的培育與高效利用融為一體,具有生態合理性,能夠功能良性循環,實現高產、優質、高效與持續發展目標,達到經濟、生態、社會三大效益統一[8] 。由于生態農業的這種優越性,因此被視為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9] 。
生態農業雖是現代科技發展的最新產物,但與目前盛行的現代農業在若干方面卻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主要在于生態農業與被現代農業所取代的傳統農業有密切的聯系。因此,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生態農業是一種“返樸歸真”。這種聯系表現在:
首先,生態農業雖然是一種新科學,但是其基礎不僅包括現代科學的因素,而且包括傳統農業知識的因素。生態農業思想的精髓是“順應自然”,而這種“順應自然”正是許多地方的傳統農業的基本原則 [10] 。
其次,生態農業通常被視為一種自我循環的小型農業,或者一種生態工程。因為強調“系統”,偏重于自然的或半人工的“流”和“循環”,因此生態農業往往被限定在一個較小的界限范圍內[11] 。
就中國而言,這兩個特點都早就存在。首先,“順應自然”的原則,與中國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或者“三才”理論頗為一致。在此意義上來說,生態農業理念的核心成份,在中國可以追溯到兩三千年以前。其次,小型農業是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征。因此生態農業與中國傳統的小農經營之間并非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由于中國傳統農業在若干方面體現了生態農業理念并與生態農業所需的經營形式不悖,因此某種形式的生態農業很早就出現于中國,是很可能的,盡管這種生態農業與今天的生態農業具有很大的差別。然而,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到了十六、十七世紀,這種生態農業才在江南地區發展到一個較高的水平 [12] ,取得了良好的生態和經濟效益,并且逐漸普及了開來。我在過去的研究中,強調江南農業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中期的三個世紀中有頗大的發展 [13] 。生態農業經營方式的出現和普及是這個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但是我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涉及。有鑒于此,本文就以十六、十七世紀的情況為例,對近代以前江南的生態農業問題作一探討。
一、生態農業――江南農業的一種新經營方式
至少是從十六世紀起,江南農業中出現了一種新的經營方式,即經營者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來經營 [14] 。其最出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常熟的譚曉(即談參)[15] 。這種經營方式與我們所要討論的生態農業具有非常密切的關系。
譚曉,嘉靖時常熟人,因“倭亂時曉獻萬金城其邑城”,后縣令王叔杲“撰譚曉祠議以旌其功”。關于譚曉的記載,主要見于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談參”條和《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軼聞。二者關于譚氏的經營活動的記載大體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別。茲將二者俱臚列于下,然后進行分析。
《戒庵老人漫筆》卷四“談參”條:“談參者,吳人也,家故起農。參生有心算。居湖鄉,田多洼蕪。鄉之民逃農而漁,田之棄弗辟者以萬計,參薄其直收之。傭饑者,給之粟。鑿其最洼者,池焉。周為高塍,可備坊泄,辟而耕之。歲之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魚。池之上,為梁,為舍,皆畜豕,謂豕涼處,而魚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污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入,某匭果入,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復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軼聞:“譚曉,邑東里人也,與兄照俱精心計。居鄉湖田多洼蕪,鄉之民皆逃而漁,于是田之棄弗治者以萬計。曉與照薄其值,買傭鄉民百余人,給之食,鑿其最洼者為池,余則圍以高塍,辟而耕,歲入視平壤三倍。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之上架以梁,為茇舍,畜雞、豕其中,魚食其糞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諸果屬,其澤種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藝四時諸蔬,皆以千計。……室中置數十匭,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匭魚,某匭果,入盈乃發之。月發者數焉,視田之入又三倍”。
從上述記載可見,譚氏農場的規模很大,實行多種經營,即把種植業、飼養業等不同生產部門都包括了在內,不僅生產糧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產品,而且也生產豬、雞、魚等動物性產品。更重要的是,這些生產彼此結合,從而產生了更高的經濟效益。
在自此以后的一個世紀中,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到了明清之際,以譚氏農場為代表的大經營在江南已罕見,農業中盛行的經營形態是以個體農戶為單位的小經營。但是上述這種新經營方式卻并未隨著大經營的消失而不復存在。相反,我們可以從一些小經營中發現這種新經營方式的發展。這種情況可以張履祥在《策鄔氏生業》一文中所作的描述為代表。鄔行素是張氏友人,在海寧甪里堰附近(距離張履祥所居住的桐鄉不遠),種田為生,有田十畝,池一方。鄔氏歿后,母老子幼,無以為生,張氏為之作策劃。茲將其所述引錄于下:
“今即其遺業,為經畫之如左:瘠田十畝,……莫若止種桑三畝(原注:桑下冬可種菜, 四旁可種豆、芋,此項行素已種一畝有余,今宜廣之,已種者勿令荒蕪)。種豆三畝(原注:豆起則種麥;若能種麻更善……)。種竹二畝(原注:竹有大小,筍有遲早,雜植之,俱可易米)。種果二畝(原注:如梅、李、棗、桔之屬,皆可易米;成有遲速,量植之。惟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樹下仍可種瓜蔬。亦有宜燥宜濕,宜濕者于卑處植之)。池畜魚(原注: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魚,歲終可以易米)。畜羊五六頭,以為樹桑之本(原注:稚羊亦可易米。喂豬須資本,畜羊飼以草而已)。……竹果之類雖非本務,一勞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原注:計桑之成,育蠶可二十筐。蠶茍熟,絲綿可得三十斤。雖有不足,補以二蠶,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豆麥登,計可足二人之食。若麻則更贏矣,然資力亦倍費,乏力,不如種麥。竹成,每畝可養一二人;果成,每畝可養二三人;然尚有未盡之利。若魚登,每畝可養二三人,若雜魚則半之)”。
需要指出的是,張氏為鄔氏制定的這個方案并非紙上談兵,而是一個精通當地農事的農學家,經過深思熟慮,為其摯友的遺屬的生存而提出的切實可行的計劃。事實上,鄔行素生前已經在這個方向努力了,不僅已經在經營理念上已有類似的考慮 [16] ,而且也采取了一些實際行動[17] 。因此張履祥的策劃,不過是將類似情況進行優化后作出的一個總結而已。
對比譚氏經營和張氏方案中的經營,可以看到二者之間盡管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其中最著者有三:
首先,二者的經營規模懸殊。譚氏的經營規模很大,“池以百汁”,種植梅桃諸果、菇茈菱芡、四時諸蔬“皆以千計”。其所雇傭的人手也達百余人之多。張氏方案是為友人鄔行素的遺屬制定的,而鄔氏家庭是一個貧苦農戶 [18] ,家里勞動力有行素夫婦、長子和侄子(此外還有老母、幼子,都不能勞動),而其全部田產不過是“瘠田十畝”和一方池塘而已。鄔行素死后,這個家庭失去了主要勞動力,情況變得更差。因此張氏方案是一個符合貧弱農戶經營的實際情況的方案。
其次,二者在對資源的利用程度方面也存在明顯的差別。譚氏農場的土地復種或間種率,李翊等人都未提到,看來還不高。但是在張氏方案中,卻達到了很高的水平。據此方案,在鄔氏農場的各種田地上,都采取復種或間種。例如在桑地上,“桑下冬種菜,四周種豆芋”;在豆地上,“豆起則種麥;若能種麻更善”;在果地上,“(土)肥者樹下仍可種瓜蔬”。而張氏在另外一文中講到:“(桐鄉)不得已則于桑下種菜,謂菜不害桑也。其實種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盡,亦見人工偷惰,無足取也”[19] 。換言之,他為鄔氏遺屬作的規劃中,土地利用率已達到極高的程度。
再次,二者在江南實行的程度也頗為不同。譚氏大經營成功的主要背景,是明代中期江南因稅重而出現大批農民棄田不耕,從而導致土地和勞動力價格非常低廉。因此這種大經營可能只是一種在特定時期出現的特殊的現象。與此相反,張氏方案反映的是明末清初的江南嘉、湖一帶的情況。此時這一地區,如張履祥所述,已是“人稠密地,不易得田”,“人工既貴”[20] 。由于田地和人工都必明代中葉昂貴,因此譚氏的大經營已經失去了賴以成功的基礎。而以張氏方案為代表的小經營由于能夠充分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況,因此有可能被眾多小農接受,成為普遍的模式 [21] 。
然而,如果從經濟的層面上來看這兩種經營,卻會發現二者也有很大的共同性。
首先,在這兩種經營中,經營者都根據自然資源的特點,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進行不同的生產活動。譚氏的做法是在池中養魚,池上架設豬圈雞舍養豬和雞。塍上種植各種水果。田地種植水稻。稻田之外的零星地塊,特別低洼的(即“污澤”之處)種植菇茈菱芡,稍高一些的則種植各種蔬菜。張氏方案則是在改造所得的旱地上,因地制宜種植種桑、菜、芋、豆、麥、麻、竹、果等不同作物,并且在池塘中則養魚,以及利用桑業生產的副產品枯桑葉養羊。因此兩種經營都包含了多種農業生產活動,可以說是一種因地制宜的綜合性農業。
其次,這兩種經營都十分商業化。譚氏農場的產品主要為了出售,因此每日都有收入,每月會計數次。而據張氏方案,鄔氏農場雖然規模很小,但其經營活動卻也十分商業化。不僅如此,譚氏農場生產出來的稻米,有相當一部分要留作譚氏家族和雇工的口糧;而張氏方案中的鄔氏農場不生產稻米,該戶所需要的食米全部依靠出售蠶桑、魚、羊、果、竹等生產的產品所得的收入來購入。就此意義上而言,鄔氏農場的商業化的水平,可能比起譚氏農場還更高。
不斷提高自然資源合理利用的水平和農業的商業化程度,是明代中期以來江南農業發展的兩條主要途徑 [22] ,因此并非本文所要討論的新經營方式獨具的特色。本文所討論的新經營方式的主要特色,在于它與生態農業具有密切的關系。換言之,它體現了今日我們所說的生態農業的主要特點。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我們將運用這種新經營方式的農業稱為江南的生態農業。
轉貼于 二、江南生態農業的特點
從譚氏經營和張氏方案中,我們可以看到以下明顯的共同特點:
第一,改造田地。譚氏和張氏方案都把原有自然資源的改造作為首要任務。譚氏的農場原為無人愿耕種的“洼蕪”之地,而鄔氏農場也是“瘠田”。這些土地的生產能力都不高,因此都必須加以人工改造,使之成為具有更高生產能力的農業資源。譚氏將其購買的田地中最低下的部分挖深為池塘,挖起的泥土則筑成高塍,圍繞田地。結果是把原來相對平整的低洼土地改造為高低有別的池、塍、田,從而形成三種不同種類的農業資源。鄔氏農場的耕地“形勢俱高,種稻每艱于水”,但如種旱地作物則又嫌高度不夠。張氏建議浚池取得淤泥,用來培高原有耕地,從而將這些水田改造為適合桑、豆、麥、果、竹等作物生長的旱地。
第二,利用廢物。在上述經營中,農場上的不同生產活動被結合了起來。由于這種結合,一種生產活動所產生的廢物(如豬、雞、羊、魚的糞便,或者枯桑葉),便可作為另外一種生產活動所需要的資源,得到再利用。相對而言,在譚氏農場上,各種經營活動之間的聯系還不十分密切,而在張氏規劃的經營中,各種經營活動之間的關系卻已十分緊密。因此在資源再利用的范圍和水平方面,后者處于更高的階段。
下面,我們就從生態學的角度出發,對這兩個特點進行分析。
(一)資源改造:營造生態農業小環境
每一種農業生產活動都要求特定的自然生態環境,即一定氣候和水土條件。即使在一個較小的地區內,盡管氣候條件大體相同,水土條件也會有相當的差異。正如張履祥所指出的那樣:“天只一氣,地氣百里之內即有不同,所謂陽一而陰二也。正如一父之子,所受母氣不同,則子之形貌性情亦從而異”[23] 。只有承認這種差異,把不同的生產活動配置在水土條件最有利的地方,才能取得較好的效果。因此包世臣說:“省偏枯之失宜,酌高下之定勢,精其所習,興其所缺,因地制利,以力待歲”[24] 。這就是農業中“因地制宜”的原則。但是,天然的水土條件往往不能很好適合特定的農業生產活動,因此必須加以人工改造,造成一個有利于人們所選定的農業生產活動的微觀生態環境。營造這樣的環境,就是發展生態農業的基礎。
在江南的杭嘉湖一帶,地勢低洼多水。這不僅頗不利于桑、果、豆、麥、麻等旱地作物的生長,而且對稻田用水的排灌也有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不利于水稻生產。要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對原有的自然條件加以人工改造,即如張履祥所說:“陰陽運數,有齊與不齊。齊者,數也;不齊者,人事使然”[25] 。具體而言,張履祥提出了“提行農事大綱”三條,其二為“溝渠宜浚”,其三為“塍岸宜修筑”。由于“一方有一方之蓄泄,一區有一區之蓄泄,一畝亦有一畝之蓄泄”,因此這種水利活動“其事系一家者,固宜相度開浚。即事非一家,利病均受者,亦當集眾修治”[26] 。亦即農民必須根據具體的情況,進行各種規模的浚渠修塍。
在江南,浚渠和修塍(以及與此相類的浚池等)不僅是一般的水利工程,而且也是改造原有水土資源的重要手段。在生產能力較差的稻田上改種桑等經濟作物,是當時增加收益的重要手段[27] 。然而“桑性惡濕而好干,惡瘠而好肥,惡陽蔽而好軒敞”[28] 。因此“桑地宜高平而不宜低濕。低濕之地,積潦傷根,萬無活理”,“高平處亦必土肉深厚乃可”[29] 。水田必須經改造才能種桑,而主要方法就是用河塘泥來培高地基(包括筑為圩岸等形式)。張履祥在談到浚河時說:“浙西之利,繭絲為大。近河之田,積土可以成地,不三四年,而條桑可食矣;桑之未成,菽麥之利未嘗無也”[30] 。“桑利圩泥,歲增高厚,瘠產化為膏壤”[31] 。“勤農貪取河土以益桑田,雖不奉開河之令,每遇水干,爭先挑掘,故上農所佃之田必稔,其所車戽之水必深。蓋下以擴河渠,即上以美土疆,田得新土,不糞而肥,生植加倍,故雖勞而不恤”[32] 。
這些工作不僅可以單獨地改良某一種資源(如田地),而且還可以使得相關資源(如田地及其鄰近的水池等)的綜合品質也得到明顯改善。例如浚池,張履祥說:“鑿池之土,可以培基。基不必高,池必宜深。其余土可以培周池之地。池之西或池之南,種田之畝數,略如其池之畝數,則取池之水,足以灌禾矣。……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33] 。錢泳則說:“(浚池)為利無窮。旱年蓄水以資灌溉,水年藏水以備不虞,深者養魚為利,淺者種荷為利;其地瘠者,每年以濁泥取污,既為肥田之利”[34] 。換言之,浚池擴大了池塘的容量,因此也提高了農田排灌能力并增加了水資源的儲備力,從而使得農業用水更有保障。同時,池塘深浚之后,水容量擴大,可以養更多的魚,從而獲得更高的魚產量。不僅如此,浚池挖起的淤泥(即塘泥)具有一定肥力,用來培高耕地,不僅可以改變這里土地過于卑濕的狀況,而且可以改良土壤,增加土地的肥力。這種培高了的土地,尤其適合于種植桑樹。而在當時的杭嘉湖一帶,種桑養蠶是最有利可圖的農業生產活動 [35] 。
原先生產能力不高的洼地,經過這樣的改造,就形成了旱地、水田和池塘三種不同形態的資源,這三種資源又組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微觀生態環境。在這個微觀生態環境中,不同的作物都有合適的生長條件。因此在這個很小的生態環境內,農民可以因地制宜地從事多種經營活動。這不僅降低了天災和市場風險可能給農業帶來的危害的程度,而且也減少了農業生產在特定時間對某一資源(例如農業用水、肥料乃至特定時間和種類的勞動力等)的需求。這種微觀生態環境的典型,就是張氏為鄔氏設計的方案中的那種小農場。陳恒力、王達指出:在杭嘉湖地區,“以一家一戶為單位來進行基本建設,一家的水田十畝或二十畝與鄰家的十畝或二十畝隔絕了。許多家都如此,形成田段分散,塍岸隔離,彼此不相連屬。在一個家庭的十畝或二十畝田中,各有溝、池、桑地的錯綜,各家都如此,又形成地面凸凹不平,桑地高,水田在地平面上,池與溝低于水田面的景觀”。這就是土地經人工改造所形成的微觀生態環境的一般形式。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對原有資源進行人工改造,目的是營造一個生產者所希望的生態環境。在這個人工營造出來的生態環境中,農民不僅能夠選擇最有利的生產活動,而且能夠把不同生物種群組合起來,利用空間,形成多物種共存、多層次配置、多級物質能量循環利用的立體種植與立體養殖相結合的農業經營模式 [36] 。阿爾鐵里在談到生態農業時強調:生態農業的首要原則,是農業活動“永遠要多樣性,決不要單一種植”[37] 。而對水土資源進行人工改造,正是農業活動多樣性的一個基礎。
(二)廢物的再利用
如果說營造一個理想的生態環境是建立生態農業的基礎,那么廢物的再利用就可以說是生態農業的核心內容之一。我們知道,各種生產活動都會產生廢物,而生態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對這些廢物進行再利用,從而減少對自然資源的索取,并且也減少廢物對環境的污染。
對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廢物進行利用,在我國已有悠久的歷史。在江南,農民很早就把廢物作為肥料加以利用,并且發明出了不少有效的利用方法。但直到明代中葉,這種利用方式基本上還比較簡單,亦即將一種農業生產活動產生的廢物,直接作為肥料而用于另一種農業生產活動。到了明代中期,精明的譚曉發明了一種利用廢物的新方式——把豬和雞的糞便作為魚的飼料。按照當時蘇州一帶的習慣,有魚糞便的淤泥,通常被罱取來作為稻、桑的肥料。因此譚氏的方法,體現出他的農場對某種廢物(豬和雞的糞便)進行了兩次利用。但是由于沒有明確的記載,詳情難以確知,因此我們只能說當時的廢物利用可能出現了新的方法,但是還不普及,而且也還比較單一。到了明末清初,從張氏方案來看,廢物再利用已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張氏已明確地說把含有魚糞的池塘中淤泥,用來作竹、桑的肥料 [38] 。張氏在其他著述中,又講到用枯桑葉(種桑活動產生的廢物)作羊的飼料,用羊糞(養羊活動產生的廢物品)作為作種桑的肥料,而蠶沙(養蠶活動產生的廢物)又成為種麥和種豆的肥料。由于各種經營活動之間建立了一種連鎖關系,所以廢物得到多次利用。然而,大概是由于上述許多活動在當時已是人人皆知,因此張氏在其方案中未對有關的具體情況進行詳細說明。為了更深入地分析廢物再利用的問題,我們特把這些情況作一更全面的討論。
當時杭嘉湖一帶農業所產生的廢物,主要有四類,即:(1)人、畜(包括蠶、魚)的糞便,(2)農作物殘留物(如作物秸稭、枯桑葉等),(3)池塘和溝渠的淤泥,(4)田間雜草與池中水草。其中,有一些(第一、三類)可以直接作為肥料使用;另一些(第二、四類)則可作為飼料利用,轉化為糞便后又作為肥料使用。前一種利用是一次性的,而后一種利用則是多次性的。在明代中期以前,農戶養羊、養魚似乎還不普遍,所以對廢物的利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多次性利用開始流行起來。而到了明末清初,多次性利用技術已經比較成熟了。下面我們就從養魚講起。
當時江南農民在水資源利用方面,主要方法是養魚。由于養魚利大,當時人把養魚列為畜牧養殖業之首 [39] 。養魚的方法,王士性說是“吳越養魚,……入池當夾草魚養之。草魚食草,鰱魚則食草魚之矢。鰱食矢而近其尾,則草魚畏癢而游。草魚游,鰱又覓隨之。……故鰱、草兩相逐而易肥”[40] 。而鰱魚的糞便最后又會和塘底淤泥一同罱起作為農田肥料,因此對于利用已經不止一次。但是如果把養魚與養羊結合起來,則利用次數還更多。這一點,明末徐光啟已作了明確的說明:“(羊)或圈于魚塘之岸,草糞則每早掃于塘中以飼草魚,而羊之糞又可以飼鰱魚,一舉三得矣”;“作羊圈于塘岸上,安羊每早掃其糞于塘中以飼草魚,而草魚之糞又可以飼鰱魚。如是可以損人打草”[41] 。
在張氏方案中,養魚和養羊均占有重要地位。張履祥說養魚應仿效湖州人,以草為飼料 [42] ,可知所養之魚主要是草魚。張氏在又說到“若魚登,每畝可養二三人,若雜魚則半之”[43] ,可知養的不止一種魚。由于是多種魚混養,可知使用的方法應即王士性所說的那種在江南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時,由于張氏方案把養魚和養羊并重,因此在養魚和養羊時采用徐光啟所說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能的。關于羊的飼料,張氏說“畜羊飼以草”[44] ,而據《沈氏農書》,當時羊的飼料除了草外,還有枯桑葉(作為過冬飼料),二者在飼料總量中所占的比重大體相同,各占一半 [45] 。因此在張氏規劃的鄔氏經營中,枯桑葉先被用為羊的飼料,而后產生的羊糞被用作草魚的飼料,草魚的糞便又成為鰱魚的飼料,而最后鰱魚的糞便連同淤泥一同又成為桑地使用的肥料。這樣就形成了對枯桑葉的多次利用。
由此可見,在這個過程中,原為廢物的枯桑葉經過了五次利用,最后變成肥料,然后又開始新的一輪多次利用,從而形成了枯桑葉這種廢物的多次利用和循環利用。
此外,桑地生產出來的桑葉是蠶的飼料,而蠶產生的糞便(蠶沙),又是一種優質肥料。嘉湖農民通常把蠶沙與蠶吃剩桑葉梗、垃圾加入畜糞,一同下窖漚熟 [46] ,制成混合肥料,施用到田地中。這又形成了另外一個再利用的過程。
上述兩種對廢物的利用方式,比起以前將這些枯葉焚燒后作為草木灰肥來使用的一次性利用方式,都更加復雜,也更加科學,形成了一種對廢物的循環利用,從而大大提高了對廢物的利用程度。
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對廢物的循環利用的基本機理是生物的食物鏈原理。游修齡說:“生物在自然界的長期演化過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約的食物鏈聯系,形成了分級利用自然資源的高效率的系統。現代把這種自然生態中高經濟效能的結構原理應用于農業生產,稱之為生態工程。生態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種就是物質能量的分級使用”。他還從“食物鏈的綜合利用”的角度,對明清江南太湖地區的“農田生態平衡模式”進行了分析,指出在這種模式中,“動植物生產和有機廢物的循環從田地擴大到了水域,組成了水陸資源的綜合循環利用。糧食生產方面實行稻麥一年兩熟,并在冬季插入紫云英綠肥、蠶豆等,其他肥料來自豬糞、河泥等,蠶桑方面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墩種桑,用稻稈泥、河泥、羊糞壅桑;桑葉飼蠶,蠶矢喂魚,水面種菱,水下養魚蝦,菱莖葉腐爛及魚糞等沉積河塘底,成為富含有機質的河泥。羊吃草,過冬食桑葉,可得優質羊羔皮,等等。就這樣,把糧食、蠶桑、魚菱、豬羊等的生產組成一個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網,使各個環節的殘廢部分都參加有機質的再循環,人們從中取得糧食、蠶絲、豬羊肉、魚蝦、菱角、羔皮等動植物產品,而沒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這是中國傳統農業中充分利用太陽能的高度成就”[47] 。而明清江南的生態農業就最好地體現了這個成就。
從現代生態學的原理出發來看,生態農業的基本原則包括 [48] :
(1)以“食物鏈”原理為依據發展起來的良性循環多級利用原則。生物之間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約,一個生態系統中往往同時并存著多種生物,它通過一條條食物鏈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如按照食物鏈的構成和維系規律,合理組織生產,就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資源潛力,節省資源且減少環境污染 [49] 。
(2)根據生物群落演替原理發展起來的時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則。根據生物群落生長的時空特點和演替規律,合理配置農業資源,組織農業生產,是生態農業重要內容之一。采用這種模式,可充分利用農業資源,使產業結構趨向合理,并保護好農業生態環境 [50] 。
(3)在生態經濟學原理指導下的系統調節控制原則。在一個生態系統中,生物為了繁衍生息,必須隨時隨地從環境中攝取物質和能量,同時環境在生物生命活動過程中也得到某些補給,以恢復元氣和活力。環境影響生物,生物也影響環境,受到生物影響而改變了的環境又對生物產生出新的影響。所以必須通過合理耕作、種養結合來調節控制生態系統,實現良性循環和可持續發展 [51] 。
把這些原則運用到實際生產中,就形成了今天生態農業工程的模式設計。這種模式設計常采用三種類型,即:[52]
(1)時空結構型:采用平面設計、垂直設計和時間設計,在實際應用中多為時空三維結構型,包括種群的平面配置、立體配置及時間的疊加嵌合等。這種時空結構型包含山體生態梯度開發型、林果立體間套型、農田立體間套型、水域立體種養型和庭院立體種養型等。
(2)食物鏈結構型:模擬生態系統中的食物鏈結構,在農業生態系統中實行物質和能量的良性循環與多級利用。食物鏈模式設計通常采用“依源設模,以模定環,以環促流,以流增效”方法,通過鏈環的銜接,使系統內的能流、物流、價值流和信息流暢通。
(3)時空-食物鏈結構型:是時空結構型和食物鏈結構型的有機結合,即將生態系統中生物物質的高效生產和有效利用有機結合,把“開源與節流”高度統一,以求適投入、高產出、少廢物、少污染、高效益。
從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譚氏的經營主要是利用以食物鏈原理為依據發展起來的良性循環多級利用原則,因此可以說是食物鏈結構型的生態農業;而張氏為鄔氏設計的經營,所依據的則不僅是食物鏈原則,而且也是時空演替合理配置原則和系統調節控制原則,因此應當說屬于時空-食物鏈結構型的生態農業。這一變化意味著江南的生態農業出現后不斷發展,逐漸演化出不同的模式,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由此而言,就近代以前技術水平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態農業可以說已經相當成熟了。
注釋
[1] 在此方面,最新也是最具概況性的著作為Jack Goldstone的《Effloresce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World History: Rethinking the “Rise of the West”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Fall 2002.
[2] 在2002年于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第13屆國際經濟史學會(International Economic History Association)大會上,由李伯重主持、有10個國家經濟史學家參考的“18世紀與19世紀初期歐亞的農業勞動生產率”(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in 18th and 19th century Eurasia)的專題討論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3] 這種情況,集中地反映在克萊夫·龐廷的新著《綠色世界史――環境與偉大文明的衰落》(中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
[4] 路明為現代農業下的定義是:“用現代工業、現代科學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裝備起來的農業稱為現代農業。其基本特征是:各種機器成為主要工具;石油電力成為主要能源;具備優良的農業基礎設施;電子、激光、遙感、信息等新技術廣泛采用;建立在現代科技上的科研、推廣體系完備;農工商一體化的服務體系完備;現代科學管理方法運用廣泛”。他為生態農業下的定義則是:“在現代化裝備的基礎上,運用生態學原理和生態經濟原理為指導,節約使用資源,減少能量輸入,適當減少化肥、農藥施用量,加環增鏈,多層次利用生物有機質,做到廢棄物資源化,物質循環再生,使農業不對環境產生污染,在為人民生產出健康、安全的農產品的同時,還能安排更多的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使農業成為可持續發展的產業”。見路明:《21世紀現代生態農業展望》,刊于《中國農業科學》(北京)第34卷(2001年)。
[5] 孫敬水:《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選擇》,轉載于《中國經濟信息網》2002年11月28日。
[6] 曹東風與戈峰把1960年代以來出現的世界農業的各種新觀念、新模式,分為四種類型:一是完全不使用人為因素,而只是靠自然界中的自然因素進行病蟲草調節的回歸型農業(Regressive Agriculture),如現代自然農業(Modern & Natural Agriculture)、有機農業(Modern & Organic Agriculture)、無為農業(No-doing Agriculture)、生物動力農業(Biodynamic Agriculture)、素食農業(Veganic Agriculture)等;二是不使用化學農藥,但可使用生物防治制劑進行病蟲草防治的替代型農業(Alternative Agriculture),如生物農業(Biological Agriculture)、生態農業(Ecological Agriculture)、立體農業(Three dimensional Agriculture)等;三是以發揮自然控制為主,但可適量使用化學農藥的持續型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如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低投入農業(Low-Input Agriculture)、低熵農業(Low-Entropy Agriculture)、生態經濟農業(Ecological Economical Agriculture)、綜合農業(Integrated Agriculture)、精久農業(Intensive & Sustainable Agriculture);四是強調高投入、高產出,可大量使用化學農藥以取得顯著經濟效益的集約型農業(Intensive Agriculture)(見曹東風與戈峰:《面向21世紀可持續農業的植物生態保護芻議》(轉載于ipmchina.net/meeting98/)。
在上述這些農業形態中,與生態農業關系最為緊密的是有機農業,因此在一些文獻中,生態農業也稱有機農業。但是如阿爾鐵里所強調的那樣,有機農業并不是生態農業,因為有機農業仍舊是單一種植和原材料替代,用一些原材料取代另外一些原材料,與常規農業遵循著同一標準;而生態農業依靠的是農作物與動物相協作的結合關系,或者說是一種對原材料沒有依賴性的體系。此外,有機農業供應的是上層社會市場(實際上,美國的大多數有機農業只是一種商標,一種說明沒有使用有毒物質來生產這些產品的商標)。相反,生態農業以科學為基礎,實行一種關注社會公正、糧食安全和消除貧困的替展模式。見《生態農業的推動者》――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授阿爾鐵里答墨西哥《標志》周刊記者問(轉引自《參考消息》2001年12月21日)。
[7] 侯向陽:《生態農業--前景廣闊的現代農業》,刊于《中國特產報》2003年4月7日。
[8] 《農業名詞》“生態農業”條(轉載于chinapoultrysci.com/nymc/);孫敬水:《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選擇》。
[9] 路明:《生態農業是我國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刊于《人民日報》1999年11月25日。
[10] 阿爾鐵里把這種傳統農業知識成為“人種科學”,即“關于農業生產者的知識”。他指出:“所有土生土長的老農民都有一種宇宙運動觀。他們發展了一種體系,即大自然的分類并適應自然。人種科學就是研究這些農民的智慧。”阿爾鐵里強調:生態農業“不是具體技術”,而是原則,因為“是原則產生技術”。他所說的原則亦即前注中所引的“土生土長的老農民”都有的“大自然的分類并適應自然”的知識體系。見前引《生態農業的推動者》。
[11] 侯向陽:《生態農業--前景廣闊的現代農業》。
[12] 即長江三角洲地區。在本文中,主要指杭嘉湖一帶。
[13]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Houndmills, England) & St. Martin’s Press, Inc. (New York, USA), 1998.
[14] 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業師傅衣凌先生,他說:明代中期江南農村經濟中出現的新經營方式,即一些地主“企圖把農業變成企業性的東西,并使用大量的雇傭勞動者”。見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57年,第63-64頁
[15] 李翊《戒庵老人漫筆》,中華書局(北京)1982年排印本,卷四“談參”條說:他所談的,其實是“淡參,實譚曉,常熟湖南人(原注:行三,參者三也)”。由于李氏所言本來自“邵北虞圭潔所撰”,而“北虞系同邑,不欲顯論之耳”。故作談參。
[16] 因此張履祥說“竊觀行素生前規劃,或者已有此意,恨不及與之論定也”。
[17] 陳確到鄔氏家,見到其家“周按桑田,閑閑十畝”。見《陳確集》,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文集卷九《暮投鄔行素山居記》。張履祥也說:“行素今年已種豆二三畝,善策也”。見《策鄔氏生業》,收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增補本),農業出版社(北京)1983年,第177-178頁。
[18] 據鄔氏的師友陳確(同時也是張履祥的友人)所見,鄔行素生前與其子力耕養母,生活十分貧困(見前引陳確:《暮投鄔行素山居記》)。因此其境況只能屬于下等農戶。
[19]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26頁。
[20]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14、148頁。
[21] 事實上,如后所述,這種方案后來確實得到了廣泛的采納,成為江南許多地方小農經濟的特色。
[22] 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刊于《中國農史》(南京)1985年第3期;《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刊于《農業考古》(南昌)1985年第2期; Bozhong Li: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ch.3,4,5.
[23]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16頁。
[24] 包世臣:《安吳四種》,光緒十四年刻本,卷二《齊民四術》第一農一上。
[25] 張履祥:《禱雨疏》,收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72頁。
[26] 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45頁。
[27] 李伯重:《“桑爭稻田”與明清江南農業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明清江南農業資源的合理利用》。
[28] 高時杰:《桑譜》,收于汪日禎:《湖雅》,光緒六年刻本。
[29] 沈練:《廣蠶桑說》,仲昴庭輯補本,農業出版社(北京)1960年。
[30] 《楊園先生全集》卷六《辛丑與曹射侯》,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64頁。
[31] 《荒政議上甘中丞》,收于咸豐《南潯鎮志》卷十九災祥一。
[32] 《陳確集》文集卷十五《投當事揭》。
[33] 張履祥:《策溇上生業》,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79頁。
[34] 錢詠:《履園叢話》,中華書局(北京)1979年排印本,卷四水學圍田、浚池條。
[35] 李伯重:《明清江南蠶桑畝產考》,刊于《農業考古》(南昌)1995年第3期與第4期。
[36] 這種模式也被稱為“充分利用資源和空間的立體農業生態模式”。見前引路明:《21世紀現代生態農業展望》。
[37] 見前引《生態農業的推動者》。
[38] 張氏在此文中明確指出:“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他在《策溇上生業》中也說:“池中淤泥,每歲起之以培桑、竹,則桑、竹茂,而池益深矣”。
[39] 明代《致富奇書》(木村蒹堂本)“牧養致富”說:“養五牸之法:一曰養魚,二曰養羊,三曰養豬,四曰養雞,五曰養鵝鴨。五牸之中,惟水畜之利最大”。
[40] 王士性:《廣志繹》,中華書局(北京)1981年排印本,卷四“江南諸省”。
[41] 徐光啟:《農政全書》,石聲漢校釋本(即《農政全書校釋》),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79年,卷四十一牧養。
[42] 《補農書》總論說:“若以湖州畜魚之法,而盡力于吾地之池,取草既便,魚價復高,又無潰溢之患,損脊之憂,為利不亦多乎!……嘗見其鄉一叟戒諸孫曰:‘豬買餅以喂,必須資本;魚取草于河,不須資本。然魚、肉價常等,肥壅上地矣等。奈何畜魚不力乎!’”。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32頁。
[43] 《策鄔氏生業》。
[44] 這里說的草,主要當指水草。詳前注。
[45] 《沈氏農書》蠶務(六畜附)。見于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86頁。
[46] 參閱陳恒力:《補農書校釋》,第12、15、16、17頁。
[47] 游修齡:《中國古代對食物鏈的認識及其在農業上應用的評述》。
[48] 以下三條,均見《農業詞典》“生態農業的三種模式”條(轉載于 suhome.8u8.com/paper/paper.htm)。
[49] 例如利用作物秸稈作飼料養豬,豬糞養蛆,蛆喂雞,雞糞施于作物,在這種循環中,廢棄物被合理利用,可減少環境污染。利用食物鏈組織生產的還有作物-畜牧-沼氣循環;作物-食用菌循環等。
[50] 例如為了讓農副業生產向空間或地下多層次發展,可在田間實行高稈、矮稈作物搭配種植,同時在田間的溝、渠、過道的空間搭設棚架,栽種葡萄、云豆等爬蔓作物;還可將種植植物和動物養殖搭配起來等。在時間演替上,可采用間作方式,在同一土地上種植成熟期不同的作物,以充分利用資源。
[51] 如果不顧這個規律,只顧索取,不給回報,便會使環境質量下降,資源枯竭。
篇9
關鍵詞:徐渭;本色;曲學思想;求真尚情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596(2013)04-0115-04
徐渭在繼承古代文論本色觀念的基礎上,結合自身進步的曲學理念,面對明代中期曲壇的發展現狀,創作性地提出了以本色為主的曲學思想。王驥德曾經說過:“先生好談詞曲,每右本色。”[1]“本色”一詞在明代戲曲領域的應用極為廣泛,后來得益于徐渭的倡導,逐漸成為戲曲領域的一個重要審美標準。徐渭關于戲曲本色思想的闡釋雖不多,但卻十分精確,涉及到戲曲藝術的各個方面,準確地抓住了戲曲藝術的特征和創作規律。
徐渭融合各家之說,在《西廂序》中說道:“世事莫不有本色,有相色。本色猶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替身者,即書評中婢作夫人終覺羞澀之謂也。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帶,反掩其素之謂也。故余于此本中賤相色,貴本色,眾人嘖嘖者我獨也。其惟劇者,凡作者莫不如此。嗟哉,吾誰與語!眾人所忽,余獨詳,眾人所旨,余獨唾。嗟哉,吾誰與語!”[2]
徐渭在本色思想上強調自然,崇尚真性,認為戲曲創作要表現事物的本來面目。通過對徐渭的曲學理論和戲曲創作加以認真審視,我們就會發現在“求真尚情”自然觀的指導下,徐渭以本色為主的戲曲思想極為深刻,內涵也極為豐富。它已不僅僅停留于戲曲的審美標準層面上,而是深入到對戲曲藝術特征和創作規律等方面的探求,涉及到戲曲創作中內容、形式、聲律等各個方面。
一、“求真尚情”為核心的曲學思想
求真尚情是晚明文學思潮的鮮明特征之一,也是徐渭曲學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徐渭率先在戲曲領域倡導求真尚情的曲學思想,從而成為其曲學思想的核心部分。
戲曲本身是一種以敘述為主的綜合性藝術,要求真實地再現社會現實生活,展現真摯動人的情感。徐渭曾在一個戲臺的楹聯中說:“隨緣設法,自有大地眾生。作戲逢場,原屬人生本色。”[3]他明確認識到戲曲源于人民群眾,又必須走進人民群眾的藝術創作規律。所以,他重視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最終實現“歌之使奴、童、婦、女皆喻,乃為得體”的藝術效果,展現“人生本色”。徐渭真正意識到戲曲藝術的生命力在于人民群眾這一藝術真理。從這點出發,他在戲曲題材的選擇上要求反映真實的生活,追求與現實人生結合的淳樸、自然的戲曲審美境界。為了使自己的戲曲作品通俗易懂,徐渭把自己的藝術視角轉向民間,從民間文學中汲取了豐富的養料。徐渭的《四聲猿》,題材都來自民間,《狂鼓史》取材于演義故事,《玉禪師》取材于西湖傳說,《雌木蘭》取材于樂府詩詞,《女狀元》則是取材于民間傳奇。徐渭憑借自己對民間生活的了解,融合了民間俗語,把這4個民間故事連綴在一起,創造了新的戲曲表現形式,完成了對民間戲曲藝術的改造,使戲曲真正成為人民群眾的鮮活藝術。
然而,徐渭對戲曲藝術的追求并不僅僅停留在一般意義上的淺俗本色上,而是追求一種融入自己藝術追求和主體精神的俗中見雅、雅中見俗、大俗大雅的本色思想。
所以要探討徐渭本色思想的深層內涵,就必然要對徐渭的主體精神和藝術審美的獨特追求進行探討。
高明曾在《琵琶記》中說:“論傳奇,樂人易,動人難。”[4]表達了他在戲曲創作實踐中的無限感慨。徐渭在《選古今南北劇序》中進一步闡述道:“人生墜地,便為情使。聚沙作戲,拈葉止啼,情此已。迨終身涉境觸事,夷拂悲愉,發為詩文騷賦,璀璨偉麗,令人讀之喜而頤解,憤而毗裂,哀而鼻酸,恍若與其人即席揮塵,嬉笑悼唁于數千百載之上者,無他,摹情彌真則動人彌易,傳世亦彌遠,而南北劇為甚……”[5]在明代曲壇首先提出了“摹情彌真則動人彌易,傳世亦彌遠”的摹情劇論。
“摹情論”是徐渭求真尚情曲學思想的具體主張。從戲曲創作的角度而言,就是要求作家必須要有對現實生活的真切感受和真摯的情感,通過抒發真實的思想感情和描寫真實的社會現實,達到“動人”、“傳世”的最終目的。
徐渭認為人的情感是與生俱來的,是為“人生墜地,便為情使”。“聚沙作戲,拈葉止啼”等都是人們情感活動的外化。人與人的經歷不同,感情也是不一樣,只有“終身涉境觸事”,有深刻的社會現實生活的體驗和感受,才會產生“夷拂悲愉”之情。只有這樣,人們的感情才會郁積于胸,噴薄而發。徐渭在《曲序》中對感情的郁積、抒發做了精彩的總結:“語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郁,郁而有所宣,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6]戲曲作為一種表演藝術,也應該借助于各種藝術表現手法,抒發作者的真實感情,展現個性精神,才能達到“令人讀之喜而頤解,憤而毗裂,哀而鼻酸,恍若與其人即席揮塵,嬉笑悼唁于數千百載之上者”的藝術效果,才能“動人”、“傳世”。正是基于此,徐渭認為戲曲必須抒寫真情,以展現“人生本色”。
徐渭認為戲曲創作必須要以真性情作為基礎的。徐渭生活的時代,是個人性真正覺醒的時代,人的價值日益得到肯定。所以,對自我個性精神和主體意識的張揚,對日常世俗生活的追求,對男女平等觀念的肯定都鮮明的體現在徐渭的曲學思想和戲曲創作中。
二、聲律上的本色思想
徐渭非常注重曲律的研究和運用。
在《南詞敘錄》中徐渭對南戲進行了研究,認為南戲源于民間,以“村坊小曲而為之”,特點是“本無宮調,亦罕節奏”、“順口可歌”。南戲起源于民間的村坊小曲,宋元南戲很好地保存了南戲的民間特色。后來在發展中,不斷融合了唐宋大曲、古曲、詞調、諸宮調音樂,形成較為嚴謹的南戲音樂體系,但在曲律的運用方面還是極為靈活自由的。所以徐渭堅決反對以《南九宮譜》來限制南戲的創作,提出“必欲窮其宮調,則當自唐、宋詞中別出十二律,二十一調,方合古意。是九宮者,亦烏足以盡之?多見其無知妄作也”,“彼既不能,盍亦姑安于淺近。大家胡說可也,奚必南九宮為?”的偏激之見。并且也對于周德清《中原音韻》也提出了疑義。正因為這個原因,一些研究者認為徐渭在戲曲創作上是不主張曲律的。這是不盡符合徐渭曲學思想實際的說法。
徐渭從本色思想出發,在當時提出這樣的戲曲聲律觀還是比較客觀、合理的。徐渭在當時采取了這樣的戲曲聲律主張是有著極為樸素的文化背景和濃厚的時代背景的。南戲本來就興起于民間,本當保存淳樸的民間特色。徐渭清晰地看到,如果在南戲創作中過于強化戲曲音律,必然會失去戲曲的民間本色。徐渭采取這樣的戲曲音律觀點只是不希望以簡單的曲譜形式來限制、束縛戲曲的創作,這在當時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徐渭在戲曲創作上并不是不要求聲律,他只是從南戲曲律靈活自由的角度著眼,試圖保持戲曲的本色。所以他說:“或以則誠‘也不尋宮數調’之句為不知律,非也,此正見高公之識”,正是他認識到南戲曲律靈活自由的緣故。南戲本身就有自身的音樂特點,“南之不如北有宮調,固也;然南有高處,四聲是也。北雖合律,而止于三聲,非復中原先代之正”。在體制上“詞調兩半篇乃合一闕,今南曲健便,多用前半篇,故曰一支,猶物之雙者,止其一半,不全舉也”。徐渭認為:“《南九宮》全不解此意,兩支不同處,便下‘過篇’二字,或妄加一‘么’字,可鄙。”在音韻上,南曲也相對較為靈活,可以從權相押。“曲有本平韻者亦可作入韻,[高陽臺]、[黃鶯兒]、[畫眉序]、[蝦序]之類是也”。徐渭認識到了南戲自由靈活的音樂美,所以才在戲曲領域提出了較為偏頗的聲律觀點。
當然,徐渭不是完全反對音調宮律。他在《南詞敘錄》中說:“南曲固無宮調,然曲之次第,須用聲相鄰以為一套,其間亦自有類輩,不可亂也。如[黃鶯兒]則繼之以[簇御林],[畫眉序]則繼之以[滴溜子]之類,自有一定之序,作者觀于舊曲而遵之可也”,又說:“凡曲引子,皆自有腔,今世失其傳授,往往作一腔直唱,非也。若[晝錦堂]與[好事近],引子同,何以為清、濁、高、下?然不復可考,惜哉!”徐渭認為,南戲雖然沒有嚴格的聲律限制,但在發展的過程中還是積累了一些創作規律和經驗。在音樂的曲牌連套上也有一定的規律,“曲之次第,須用聲相鄰以為一套,其間亦自有類輩,不可亂也。”同時,徐渭也講究音腔調的“清、濁、高、下”。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徐渭還是通曉曲律的,也認識了到了南戲創作中“語多鄙下”的落后現實,對于南戲融合唐宋大曲、古曲、詞調、諸宮調音樂從而形成結構龐大、較為嚴謹的南戲音樂體系的現實也是認可的,所以他在評價高明的《琵琶記》時說:“用清麗之詞,一洗作者之陋,村坊小伎,進與古法部相參,卓乎不可及已。”
很顯然,徐渭在戲曲聲律上的主張,是想既保持民間戲曲樸素、清新的特色,同時也注意戲曲聲律的規律性,而不是單純追求聲律而束縛戲曲情感的真正抒發。這也是符合其本色戲曲思想的。《四聲猿》的創作就是其戲曲聲律理論的真正履踐。
三、語言上的本色思想
明代戲曲家在論述“本色”觀念的時候,多是從語言的角度去探索戲曲的藝術規律。徐渭也是如此,其本色思想也包含語言本色的基本要求,主要表現在追求通俗、自然、易曉、淡薄的語言風格,反對戲曲語言的文采、脂粉、濃郁。
所以,徐渭說:“語入要緊處,不可著一毫脂粉,越俗越家常,越警醒。此才是好水碓,不雜一毫糠衣,真本色。若于此一恧縮打扮,便涉分該婆婆,猶作新婦少年共趨,所在正不入老眼也。至散白與整白不同,尤宜俗宜真,不可著一文字,與扭捏一典故事,及截多補少,促作整句。錦糊燈籠,玉鑲刀口,非不好看,討一毫明快,不知落在何處矣!此皆本色不足,仗此小做作以媚人,而不知誤入野孤,作妖冶也。”[7]
徐渭在戲曲的語言上要求通俗自然。他認為戲曲語言要“不可著一毫脂粉”、“俗”、“家常”,只有這樣才能符合戲曲語言的發展規律,才能“警醒”世人,實現戲曲的審美愉悅功能,“不雜一毫糠衣”,才是“真本色”。
徐渭把俗語、家常語引入戲曲,也是有針對性的。南戲興起于民間,較好地保存了樸實、質樸的風格特色。徐渭極為推崇宋元南戲,認為“句句是本色語,無今人時文氣”,并且認為“以時文為南曲”,“其弊起于《香囊記》”。在徐渭看來,《香囊記》就藝術成就而言,“未至瀾倒”,“至于效顰《香囊》而作者,無一不孜孜汲汲,無一句非前場語,無一處無故事,無毛發宋、元之舊”。徐渭在《葉子肅詩序》中也強烈批評了以抄錄典故、堆砌古人文辭的不良現象,他說:“不出于己之所自得,而徒竊于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于鳥之為人言矣。”[8]因此,他說:“《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從本色的思想出發,徐渭提出戲曲創作要不避俚俗,認為“點鐵成金者,越俗越雅,越淡薄越滋味,越不扭捏動人越自動人”,并進一步提出尤其是“語到要緊處,略著文采,自謂動人,不知減卻多少悲歡,此皆是本色不足者”[9]。
在徐渭看來,戲曲的創作,要恰當的使用俗語、家常語,以增強戲曲的藝術感染力。如果一味追求曲詞的典雅華麗,就會失去戲曲的原生態生命力,使戲曲創作走向偏頗,偏離了“大眾人生”的審美需求。基于此,徐渭積極倡導方言入戲曲。在《四聲猿》劇本中,更是方言、隱語、俚語比比皆是。同時,徐渭在評點《西廂記》時,也是極力贊賞方言的使用。
篇10
[關鍵詞]書院;人文教育;學規;科舉
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大學將進入社會的中心,直接參與經濟活動的運作,這使得大學的功利趨向愈來愈明顯,直接影響到大學人文教育的實施,甚至因過分強調科學教育,使得大學淪為職業培訓機構,這既不利于大學生的全面發展,也不符合大學自身的發展邏輯。人文教育是中國古代書院教育的主要特點,并形成了實施人文教育的較為完備的制度,挖掘古代書院人文教育的理論是構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的重要基礎。本文主要從探討儒家人文精神出發,對書院人文教育進行分析,力圖管窺書院人文教育的一斑,以為當代大學人文教育理論建設提供些許借鑒。
一
北宋以降,書院逐漸發展成為傳承、創新和普及儒家學說的重要機構,在中國傳統社會的文化發展中擔當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可以說,書院是儒家文化傳播、創新和普及最有力的推動者,也是儒家精神的有力踐履者。
儒學是以人為本位的學說,主要表現為在對人的價值和人格肯定的同時,也強調人應該具備社會責任心,并認為這二者之間存在前后依存的關系,即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內圣外王之道”,通過“正心”、“誠意”、“修身”、“格物”、“致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達到“內圣”的境界。在此基礎上,儒家學者通過自身的努力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社會責任,即所謂的“外王”。這種由內圣走向外王的思想,即是儒家人文精神的主要內涵。換言之,儒家人文精神包含著兩個相互關聯的層面:其一,士人通過忠實踐履儒家的道德規范,并將其內化為自身人格、價值的追求方面,使個體道德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理想在于將儒家的道德要求付諸實踐,最終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儒家將這種人文精神滲透到教育的各個環節,使中國古代教育呈現出典型的人文特色。書院教育不僅將以道德養成為核心的人文教育擺在首要位置,而且按照儒家的理想來設計人才培養模式,使其人文精神得到貫徹落實。
作為宋代儒學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創建、修復并講學于多所書院,在長期的書院教學生涯中,朱熹將培養書院生徒的道德品質作為首要任務,他在《白鹿書院揭示》中指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在朱熹的設想中,道德養成被視為人才模式的核心,他說:“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修諸身,行于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務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他的這一人才模式的基本內涵與儒家道德所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是完全吻合的,道德培養被提高到首要地位。
不惟朱熹如此,幾乎所有的書院大師都強調儒家人文精神在教育活動中的絕對地位。長期主講南宋長沙岳麓、城南二書院的著名學者張拭則認為書院應該“傳道而濟斯民”,將以儒家道德為核心的“道”作為教學的主要內容。明代心學的代表人物王陽明的為學之路雖然與朱、張二人明顯不同,但在書院人才培養模式的選擇上,卻是與二人一致的,對書院人才培養的首要標準也是“明人倫”。在(增修萬松書院記)中他指出:“今書院之設……士之來集于此者……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于人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于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圣賢之學也。”而“古圣賢之學明倫而已。”所謂“明倫”就是要精通儒家的倫理道德,并將其內化為信念,進而外化為行為準則。此外,王陽明還將書院的道德教育與自己的學術主張結合起來,認為書院教育應啟發良知、培養圣人,即所謂的“致良知”。
盡管明清代大多數書院是以培養科舉人才為主要任務,但書院仍然重視人文精神的灌輸,強調良好的道德素養和扎實的儒學功底是科舉應試的前提條件。道光中葉,主講廬州涇川書院的著名漢學家胡培暈認為:“國家設立書院造就人才,原欲其講明修己治人之道,備他日任使,非徒以膏火月廩周其空乏,亦并非望其博取科第為一身之榮已也。”許完寅認為當時書院教學的主要弊端是“聚諸生課文詞,為科舉而已”。盡管他也承認“當今之世,士之起于鄉也以科舉,勢不得不專于文詞”,但他還是認為片面追求科舉文詞會妨礙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說:“然而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所至,其有道德而能文詞者如彼也,其文詞當于理而進于道者又如此也。夫何有今昔之異哉?”因此,他要求桐鄉書院的生徒通過潛心學習儒家經典,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他說:“吾愿吾鄉之士,講習于其中,無誘乎功名名利而存茍簡之心,相與究孔孟之遺,為修己治人之大,勇于自立,而以積久持之,待其學之成履之為德性,發之為文章,舉而用之為豐功偉業,斯所謂人材于此出,斯所謂造士于此始矣。”嵩陽書院的執掌者耿介也認為從事舉業的生徒要重視“有本之學”的學習,他說:“今日論學,不必煩為之辭,即于舉業加一行字,使修其辭為有德之言見諸用,為有本之學。”
雖然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書院對人文教育的重視程度不盡相同,甚至淪為科舉附庸的書院對人文教育相當不重視,但人文教育貫穿于書院千余年的發展始終,成為其區別于中國古代其他教育機構的顯著特征。
二
由于人文教育在要求生徒掌握儒家經典知識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將儒家人文精神內化為道德品格,因此不但要求書院重視教學環節的人文精神培養,而且將人文教育滲透到其活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既體現在學規之類的制度化文件中,也從書院內部環境的創設、祭祀等方面鮮明地體現出來。
學規是規定書院的辦學宗旨、辦學目的、教學內容及其學習方法等方面內容的制度性文件,書院的人文教育也在學規中得到充分的表現。在中國書院發展史上,朱熹所制定的《白鹿書院揭示》是最有代表性、影響最大的書院學規,不僅為歷代書院所采用,而且還成為南宋中后期以來官辦教育機構的規范性文件之一。《白鹿書院揭示》將儒家的道德規范作為書院辦學指導方針,首先就提出:“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為獲得這些道德規范,《揭示》認為掌握儒家經書是關鍵,朱熹說:“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而問辨之。”為此,他提出了“為學之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從這個“為學之序”來看,朱熹要求生徒學習儒家經典的最終落腳點就在于篤行上,即將道德規范轉化為行為實踐。在朱熹看來,行為實踐更多地會表現在日常行為中,他說:“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以至于處事接物,亦各有要。”為此,《白鹿書院揭示》對生徒的日常行為規范也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在修身方面,要求生徒“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在處事方面,要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在接物方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為達到學規中的各項要求,朱熹強調自我主觀努力的作用,他說:“則夫規矩禁防,豈待他人設之后有持循哉?”與此同時,他認為學規還有警示作用,對于生徒的道德教育必須具有一定的強制性,指示生徒嚴格遵守這一學規,“諸君其相于講明遵守而責之于身焉……其有不然,而或出于禁防之外,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白鹿書院揭示》不但規定了人文教育在書院教育中的地位,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實施辦法。
與《白鹿書院揭示》強調主觀自覺性不同,在同為南宋著名學者的呂祖謙為麗澤書院制定的《規約》中,則強調外部力量的強制性在人文教育實施過程中的作用。在道德教育方面,《規約》主張建立書院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將社會輿論作為人文教育的重要手段。他認為生徒違反道德準則之后,要先對其進行勸勉。如果勸勉無效,則要對其進行嚴厲的譴責。如果譴責仍然無效,則需要公之于眾,借助社會輿論的力量來促使其悔過。對于那些屢教不改的生徒,書院應當開除其學籍。為使人文教育落到實處,《規約》要求生徒使用日記簿,將每天所學的內容和疑問記錄下來,“肄業當常有,日紀所習于簿,多寡隨意。如遇有干輟業,亦書于簿”。等到生徒聚會探討學術時,各自提出自己有關于經書的疑問,互相商榷。對懶惰不愿意寫日記的生徒,應當“共擯之”。我們認為朱熹和呂祖謙的學規在開展人文教育方面,各有特點,朱熹重視生徒的道德自覺性的培養,而呂祖謙則重視輿論的監督與強制作用。
盡管實施人文教育的方式不盡相同,但書院利用學規開展以儒家道德倫理為核心的人文教育的傳統為后世所繼承,只是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使書院的人文教育在強調道德自覺和輿論強制方面走了調和的路線。
清代岳麓書院山長王文清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制定的《岳麓書院學規》,現仍刊在岳麓書院講堂東墻之上。這一學規延續了書院重視人文教育的傳統,從孝、忠、莊、儉、和、悌、義等方面對生徒作出了嚴格的要求,學規的前半部分為:“時常省問父母,朔望恭(謁)圣賢;氣習各矯偏處,舉止整齊嚴肅;服食宜從儉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齒序,痛戒訐短毀長;損友必須拒絕,不可閑談廢時。”不但保持了歷代學規對儒家倫理道德進行嚴格要求的傳統,它還將儒家道德倫理規范貫穿于日常行為中,力圖使生徒養成良好的素養和人格形象。因此,這一學規使書院的人文教育更加易于落實,也使得書院人文教育效果更易于考核。
除學規之外,書院人文教育實施的方式還有很多,如書院內部環節的創設與祭祀是最為典型的。書院建筑的總體布局是遵循儒家綱常倫理的,內部環境的布置也時刻彰顯出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采取類似潛在課程的方式實施人文教育。如岳麓書院講堂的布置就十分具有代表性,講堂東、西兩墻上嵌有朱熹手書的“忠、孝、廉、節”和清代山長歐陽正煥手書的“整、齊、嚴、肅”八個大字,集中體現了岳麓書院的院風和人文教育傳統。這種布置使書院生徒置身于濃厚的儒家倫理道德氛圍之中,時刻警醒他們保持對儒家倫理道德的體悟和追求。
書院祭祀也是實施人文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書院祭祀是中國古代廟學體制的延伸,并結合書院的需要形成了自身的特點。除與官學同樣將孔子等先圣、先師、先賢作為祭祀對象之外,書院還供奉本院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以及與本院息息相關的人物,其目的在于一方面彰顯本院的學派學風和旨趣,另一方面意在將這些人樹立為本院生徒,甚至成為書院所在地的道德和學術的榜樣。通過開展祭祀禮儀,向生徒與地方民眾傳達書院的道德與學術追求,使生徒與地方民眾受到儒家人文精神的浸染。
這些實施人文教化的方式多是重在對于人文教育的第一個層面——完善自我道德修養的要求,而對于第二個層面——治國、平天下的方面則顯得相對忽略。這與儒家認為道德修養是承擔社會責任的基礎的思想是一致的,加之書院作為教育機構,強調個體道德教育亦在情理之中。
三
盡管如此,書院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對生徒參與社會政治的實際運作也是相當重視的,這使得書院人文教育的內涵進一步拓展。書院不是修道院,不以培養清心寡欲的儒學教徒為目標;書院亦不是純粹的文官訓練營,不以培養追名逐利為終生目標的勢利之徒為任務。書院教育應該通過完善生徒道德,進而實現全社會道德的完善,以此充分體現出儒家所要求的人文精神。
為此,書院學者們往往將這種人文追求與社會政治、日常人倫結合在一起。而在傳統中國的政治體制下,科舉是幾乎將儒家經典知識權力化的唯一制度,也是士人將文化話語權轉化為政治話語權的必經之途,書院與社會政治的結合往往表現為對科舉仕進的追求。因而,為實現個體道德完善與“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大多數書院都將道德教育與應試教育統一起來,目的在于培養“德業”與“舉業”并重的人才。書院大師們認為士人必須在研習儒家經典的基礎上,將儒家思想內化為良好的道德修養和崇高的品格,而不是片面追求科舉之學,即所謂立志。朱熹說:“若高見遠識之士,讀圣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明代王陽明的高足王畿亦持基本相同的觀點,認為“舉業”與“德業”并不是對立的雙方,二者是相互促進的,他說:“是非舉業能累人,人自累于舉業耳。舉業、德業原非兩事……其于舉業不惟無妨,且位有助;不惟有助,即舉業為德業,不離日用證圣功,合一之道也。”
此外,不少書院的創建者或修復者則進一步認為生徒努力學習“有本之學”,不僅能提高自身素質,而且還能提高科舉及第的機率。廣西洛江書院要求生徒全面研習《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將學習心得付諸實踐。這樣不但自然會形成觀察社會的獨特視角,而且還能在場屋競爭中穩操勝券。饒拱辰創建巴東信陵書院以后,反對書院生徒“惟是習文藝、取科第為富貴資”,注重在講明義理和提高自身修養上下工夫,使自己成為學問淹通、修身慎行的君子,這樣能使“其文藝必能卓然自樹立于流俗之外”,在科場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機率自然也更大,即使“不得科第,亦能為鄉黨所倚賴而矜式”。
書院教育的這種轉變,使得科舉應試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在一起,成為實施人文教育的主要資源了。乾隆五年(1740年)制定的臺灣(海東書院學規)云:“‘六經’為學問根源。士不通經,則不明理。而史以記事。歷代興衰治亂之跡柢,亦胥在焉。舍經史而不務,雖誦時文千百篇,不足濟事。”以科舉考試所必須掌握的基本知識與人文教育結合起來,將人文教育寓于科舉應試教育之中,應該說這是書院科舉化背景下,書院人文教育的一種自我調適,以適應生徒普遍讀書應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