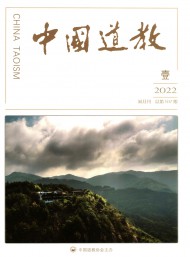道教范文10篇
時間:2024-01-17 14:42:04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道教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道教音樂研究綜述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道教音樂研究綜述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談論道教音樂研究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宋代道教文學概況
兩宋道教處于轉折、復興階段,又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堅實的信仰基礎,道教文化取得長足進展。此期道教文學,隨著內丹道的興起、新道派的迭出,張伯端、白玉蟾等眾多高道大德創作大量道教文學作品,成就了一代宗教文學的特殊風貌和鮮明特征。
一、宋代文學史與宋代道教文學史
兩宋三百多年的歷史文化,在整個古代社會中光輝燦爛。朱熹有言,“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1],王國維、陳寅恪、鄧廣銘等更有宋代文化“造極”與“空前絕后”之語,這樣的評價雖有絕對或夸大之嫌,但幾位真正“大師級”學者的直覺感悟和深層把握,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近年又有論者提出宋代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也不是簡單的“積貧積弱”可以概括的,兩宋的歷史地位和文化成就有待重新審視。文學作為宋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特征、地位和發展脈絡,自近代學術展開以來就不乏系統關注。柯敦伯1934年出版了《宋文學史》[2],這是第一部宋代文學專史,宋散文、詩、詞、四六、小說、戲曲都在論述之列,基本奠定了后世宋文學史撰寫的框架和范圍。建國后,宋代文學專史著作有程千帆、吳新雷撰寫的《兩宋文學史》,孫望、常國武主編的《宋代文學史》,張毅著《宋代文學思想史》,王水照、熊海英著《南宋文學史》,曾棗莊、吳洪澤編的四巨冊《宋代文學編年史》等,再加上數十種的中國文學通史、體裁史對宋代文學的描述,一代文學的風貌已經從藝術思想、創作水平、存世文獻、歷史編年等多個維度日益豐滿而靈動。比如新近出版的《南宋文學史》對南宋文學特征及其在整個文學史上的承啟作用所作的描述,都相當精準恰切。但是,完整的文學發展史離不開宗教文學史的撰寫。一個時代的文學史應該是三維立體的,除了“世俗文學”,還應該包括僧人、道士等教內信徒創作的大量具有文學性的作品———“宗教文學”。如從信仰角度劃分,完整的文學樣態應由世俗文學和宗教文學共同組成,而宗教文學,尤其道教文學研究的力度尚有不逮。近年道教文學研究雖取得一些成績,但總體來看,水平參差不一,廣度和深度尚未達到成熟意義上的學術范型的標準。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概始于《道教文學史》[3]。詹石窗先生習慣從宗教學立場把握道教文學個性,揭示其獨特的表達空間、觀照方式和演變歷程,體現了宗教史與文學史結合的研究路數。該書從道教雛形時期的漢起,直至北宋的道教碑志與道教傳奇,南宋以后均未涉及,可謂“半部”道教文學史。2001年詹石窗先生出版了《南宋金元道教文學研究》,此書雖未以“史”名之,卻進一步拓展了道教文學縱深發展的歷史脈絡[4],兩部書合二為一,一部完整的宋代道教文學史也基本成型,但詹先生似有意區別北宋與南宋道教文學史的特征與內在理路。兩宋道教文學有一己自足的內在聯系和宗教藝術特征。詹先生在一次訪談中曾提及“隋唐五代北宋”是道教文學的“豐富期”,南宋為“完善期”,南宋因新道派迭出,道教理論更為倫理化,在道教文學創作上也有深刻體現[5]。文學如何體現“豐富”與“完善”,二者有何區別?都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兩宋分開來寫,南宋與遼金元一并探討,照顧了歷史時、空的同一而忽視了內在的文化區別。南宋避居一隅,與金元對峙,但賡續北宋,仍以中原文化為主線。道教是典型的中原漢文化,南宋內丹派、符箓派、凈明道的興起與北宋道教一脈相承,道教文學自然也密切相連。另外,《唐宋道家道教文學研究》一書中的宋代部分從文學出發,注重分析涉道文人及其作品的深刻蘊涵[6],但這畢竟不是“文學史”,對宋代道教文學獨特的發展脈絡缺乏深入的思考和論述。《道教文學史論稿》也涉及兩宋部分,以詩、詞、傳記、宮觀名山志為類別,分別論述總結教內道徒和教外文人的道教文學成就[7]。最近出版的《唐宋道教文學思想史》則從文學思想角度對宋代內丹理論與文學養性的通融,道教隱語系統與文學隱喻的關系及內丹南宗的文學觀念等重要理論問題作了深入開掘[8],值得關注。回顧兩宋道教文學研究,還有兩篇文章不得不提,即《宋代文學與宗教》[9]和《宋代道教文學芻論》[10]。兩文發表于20世紀八九十年代,距今已一二十年,但翔實而富有識見,對兩宋道教文學的存世文獻與藝術特征,都有相當深切的把握。綜括以上宋代文學史及道教文學史研究,我們可以形成這樣的印象:前人做過很大努力,有開拓之功,搭建了基本框架,提供了大量線索,但也存在一些毋庸置疑的問題。就宋代道教文學來說,有些著作限于全書體例,論述相對簡略,面對浩瀚的宋代道教文學資料和復雜的宗教文學現象,未作系統關照。如兩宋青詞、步虛詞的創作數量相當龐大,但少有論著對這部分內容作過系統分析。另外,有些論著雖名之曰“文學史”,但更像一部道教文學資料集,缺乏針對道教文學自身發展和演變形態的深入分析。道教文學史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專史。克羅齊反對社會學式的文學史和借由文學藝術了解風俗習慣、哲學思想、道德風尚、思維方式等,強調藝術和藝術家的獨特精神與天才創造[11]。這一觀點值得思考,文學藝術史的書寫不必勉強尋找藝術之間的某種聯系。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會著重作家作品的深入解讀,盡量避免“非美學研究”,努力呈現宗教文學的固有特征和自足性的一面。但這樣的文學史,也絕不是作家作品的資料編年。道教文學作者的創造與想象,離不開他們所處的時代、從屬的道派和所反映的教義思想,他們與道教史、社會史、世俗文學史的發展演變存在更為密切的聯系。所以,兩宋道教文學史的撰寫,在紛繁的頭緒面前,還需作縱深的理論探索。
二、宋代道教文學文獻的體量與規模
宋代道教不及佛教興盛,道士、女冠人數比不上僧尼人數,宮觀規模與數量也遠不如寺廟,但官方對道教的重視程度卻不遜于佛教,帶有若干官方色彩[12]。從道教史上看,道教在兩宋仍處于上升階段,上自皇族宗室,下至庶民百姓,崇信道教、利用道教,有宋三百多年雖有消長,但基本處在一種復興與滋衍的繁榮狀態。道教文學兼具宗教與文學的雙重特質。考察兩宋道教文學,除了對此期道教發展的總體趨勢要有準確的把握,還需要對此期文學形態特征、創作水平等有深入的了解。兩宋文學作為“宋型”文化的體現之一,在唐代文學盛極而變的趨勢下重建了文學輝煌。宋代各體文學,尤其宋詞的數量和質量成就了堪稱“一代所勝”的文學代表。宋代詩、文也不遜色,兩宋詩、詞、文俱善的大家,歐陽修、蘇軾、陸游等不勝枚舉。而此期話本、志怪、傳奇、筆記類創作,也頗有可觀者。據統計現存宋人筆記約500余種。兩宋道教與文學在各自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作為綜括二者的道教文學,其特征與地位,并非簡單的“加法”可以推論。“道教文學”在兩宋道教與文學繁榮發展過程中,如何參與其中,又如何成就一己自足的文學史意義?這需要從兩宋道教文學寫作主體的確認、作品的區分、數量的統計等角度加以明晰。“中國宗教文學史”對“宗教文學”如此界定:“宗教文學史就是宗教徒創作的文學的歷史,就是宗教實踐活動中產生的文學的歷史……從宗教實踐這個角度出發,一些雖非宗教徒創作或無法判定作品著作權但卻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也應當包括在內。這部分作品可以分成兩大類別:一類是宗教神話宗教圣傳宗教靈驗記,一類是宗教儀式作品。”[13]以此,道教徒的作品容易區隔劃分,但非宗教徒創作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則需要在大量別集、總集、類書等文獻中檢尋和鑒別。《道藏》中大量具有文學性的作品都可以算作“宗教徒創作的文學”。朱越利《道藏分類解題》第七部“文學類”統計詩文集有11部,詩詞集36部,文集8部,戲劇表演類153種,神話類49種;第九部“歷史類”中的歷史資料、仙傳部分,多為古代小說文獻,也屬于文學類作品;第十部地理類中的道教宮觀、仙山志中也蘊藏著大量文學資料[14]。《道藏》中的文學性文獻,兩宋編撰者概有70余人,作品上百部,大致具有以下兩個特征:1.兩宋道教文學的作品形式涵蓋了詩歌、詞、小說、文賦、戲曲等傳統文學題材與文獻類別,并以仙歌、仙傳為主,有非常鮮明的宗教文學色彩。2.《道藏》中的70余位兩宋時期的道教文學作者,縱向比較并不算少。如張伯端、白玉蟾等部分作者在道教文學創作上卓然有成,引領一代宗教文學風尚,在道教文學史上彪炳千秋。《道藏》失收的道教文學文獻不在少數,有待進一步發掘探索,如《宋人總集敘錄》卷十考錄的《洞霄詩集》,明《道藏》未收。該書十四卷,編撰者孟宗寶,宋末元初道士,所編《洞霄詩集》據宋紹定刊本刪補而成,一般歸入宋人文集。是集所收詩歌,卷二至卷五為宋人題詠,卷六為“宋高道”,卷七為“宋本山高道”作品,收了陳堯佐、王欽若、葉紹翁等人的詩作。“非宗教徒創作或無法判定作品著作權但卻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實踐場合的作品”大多見于教外文獻,如《全宋文》、《全宋詩》、《全宋詞》、《全宋筆記》。《全宋文》中的道教文學作品,主要由道教齋醮章表、祝文、青詞、宮觀碑銘等文體組成。其中青詞占了相當大的比重,但青詞作者,大多為文人,道士反而很少。《全宋詩》是今人編輯的大型斷代詩歌總集,全編72冊,3785卷,再加上近年各種補苴文章和《全宋詩訂補》[15],詩人和篇什數量還有增加。其中道教詩歌數量很大,但真正為道士創作者并不算多,而且兩宋編纂的科儀類文獻中的經咒作品,《全宋詩》所收甚少。陳尚君教授的《全唐詩補編》曾收大量齋醮經咒,這類作品自有其存在的文化價值,如南宋金允中《上清靈寶大法》、呂元素《道門定制》、呂太古《道門通教必用集》等科儀文獻中的經咒、贊頌、步虛詞等,《全宋詩》訂補者均應予以注意。《全宋詞》中的道士詞作主要有張伯端等人的作品。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即多個始于兩宋的詞牌與道教關系密切,如《聒龍謠》始自朱敦儒游仙詞《聒龍謠》,《明月斜》始于呂洞賓《題于景德寺》詞,《鵲橋仙》始自歐陽修詠牛郎織女,《法駕導引》始于宋代神仙故事,《步虛子令》始于宋賜高麗樂曲[16],等等。道教小說是一個成熟的文體類別,《道教小說略論》對此有過較系統的論述,指出《新唐書•藝文志》等各種書目子部大多列“道家”、“神仙類”,宋代羅燁《醉翁談錄》將小說分為八目,其中就有“神仙”目。兩宋道教小說文獻,主要見于各種道經、類書、叢書及筆記、話本類作品。張君房《云笈七籤》是《大宋天宮寶藏》縮編,時雜北宋道教故事;李昉《太平廣記》卷一至卷八十多為神仙、方士故事;《太平御覽•道部》仙傳、筆記類作品也有部分載錄。曾慥曾纂《道樞》、《集仙傳》等,所纂《類說》一書中的道教小說文獻亦夥。另有類書《窮神記》、《分門古今類事》、《紺珠集》,內中道教小說也相當豐富。宋代佛道信仰與小說出現世俗化傾向,說話藝術漸趨發達。林辰參考《寶文堂書目》及胡士瑩先生的考證,指出兩宋話本體神怪小說有19種,其中神仙類有《種瓜張老》、《藍橋記》、《水月仙》、《郭瀚遇仙》、《孫真人》、《劉阮仙記》等六種[17]。另外,緣起于仙歌道曲的道情,在宋代也開始出現。《道教與戲劇》第八章《道情彈詞與傳奇戲曲》指出,宋代不僅道情流傳于民間,而且受到宮廷的歡迎[18],惜存留的宋代道情文本很少。道情與話本體道教小說,數量雖然有限,但作為宋代新出現的文體,豐富了兩宋道教小說的體式與內容,有特殊的宗教文學史意義。兩宋時期的齋醮科儀文獻非常豐富,如孫夷中輯錄的《三洞修道儀》、賈善翔編輯的《太上出家傳道儀》、張商英重撰的《金籙齋三洞贊詠儀》、金允中的《上清靈寶大法》等。這些科儀文獻蘊涵著多個文學品類,有著豐富的文學因素。如齋醮儀節強調儀式與服飾的象征意義,把文學藝術象征與宗教象征統一起來[19],對文學創作本身有極大啟示意義;齋醮科儀各個儀節之間變換、角色的擔當,又有豐富的戲劇表演元素。另外,隨著時代演進,道教新神不斷出現,新神話的建構就是在道教儀式中最直接、最有效地完成;音樂文學在道教科儀中也有體現,宋徽宗在修齋設醮時,就創作了大量“樂歌”類作品,這類典型的道教文學文獻對于認識宗教文學本身的特質具有重要價值。總之,兩宋道教文學文獻是一個體量龐大、內容駁雜的特殊的文獻類別。撰寫兩宋道教文學史,全面考察這類文獻的數量、種類、形式與內容,是必備的基礎工作,但絕非一兩篇文章可以解決。以上所論,僅為這類文獻的基本框架和大致范圍,尚有不斷充實和完善的空間。
三、兩宋道教文學作者的教派歸屬與空間分布
道教對古代科技的影響思索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道輕器,把科學技術當作“奇淫巧技”,向來不為社會重視,但中國卻出現了“四大發明”等對世界發展影響深遠的科技。這里面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教的影響,本文從道教對中國古代科技的影響看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
魯迅先生在《致許壽裳》一文中提到“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迎刃而解”。在《小雜感》里說到:“人們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國大半。”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也說:“道家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包括各種對傳統習俗的反抗,個人從社會上退隱,愛好并研究自然,拒絕出任官職……中國人性格中的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自于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的大樹。”從這些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無法替代的地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對古代化學研究的推動。
在一般人看來,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學的。但事實上,道教與古代尚未與冶煉術分家的化學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道士們從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長生的觀念與方法。道士們認為,人可以長生,但要長生,必須服食不死之藥。那么,這種不死之藥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藥之類,因為草木藥本身易腐爛,在火中會化為灰燼。由于草木藥自身沒有堅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體中,自然不能使人長生不死。因此,必須發現一種堅固不朽、無變化的藥物,通過服用這種藥物,使其不朽性傳入人體中,服用者便可以長生不死。這種不朽的藥物,就是金丹。“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蓋假求于外物以自堅固……”道家煉丹學說把服食還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視對礦物質藥材的燒煉。晉代道士葛洪在《抱樸子?金丹篇》里講到“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學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狀呈紅色,經過燒煉(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離出來。這樣就得到了煉丹術里重要的藥物——水銀(道教外丹術中稱“玄明龍膏”)。
道教煉丹理論認為經常服用“玄明龍膏”可以成仙,在《陰真君金石五相類》一書中提到“玄明龍膏……服食一道,有不可思量之功。”“積變又還成丹砂”就是把汞(Hg)與硫磺(S)化合(Hg+S→HgS)變成硫化汞(HgS),性狀呈黑色,經過升華成硫化汞的結晶,性狀呈紅色,即又變成丹砂。黃金不易與其他元素化合,難于溶解。
二、道教與古代醫學、藥物學也有著密切的關系。
淺談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
摘要:丘處機作為金庸武俠小說中的人物為現代人熟知,同時也是我國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道教史上著名的宗教領袖。作為金元時期道教重要支派全真道的掌教人之一,丘處機仁慈反戰的和平思想、無為即有為的入世思想、性命雙修的內丹思想,極大地推動了全真教的進一步發展,且對道教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關鍵詞:丘處機;道教思想;全真道
一、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形成的背景
(一)成長背景。丘處機(1148-1227)自幼失怙,嘗遍人間辛苦,童年伊始就向往修道成“仙”。后全真道祖師王重陽收其為徒,為其取名處機,號長春子。1169年,重陽真人攜弟子四人西游,途中得道飛升于汴梁城,囑咐馬鈺授其功課,也因此,丘處機的知識和道業迅速長進。其在王重陽羽化后入磻溪穴居六年,行攜蓑笠,故稱“蓑笠先生”。后又赴饒州龍門山(今寶雞)隱居潛修七年。在這苦修的十三年,因深知自幼文化素養欠缺,故發奮圖強,其所學領域融攝儒佛和老莊思想。在遷往終南祖庭,開始掌教生涯之時,聞得成吉思汗的鐵蹄使得生民涂炭,在其春秋七十有余之際,以天下蒼生為己任,毅然西覲,迎來一生不朽的篇章。(二)社會背景。歷史的發展往往具有驚人的相似。距離北宋王朝滅亡不到八十年,金廷就已經開始重蹈覆轍。在此之前,金章宗當政雖有“明昌之治”的美稱,然而卻似“回光返照”。而在此時,另一隅的南宋窺視金廷內憂外患,決定北伐。但卻因金人早有準備,且宋軍進軍輕率、用人不當而導致北伐失敗。所謂“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成吉思汗在宋金酣戰之際崛起。已經一統蒙古草原的成吉思汗在多次入侵西夏之后,便有了滅金之志。成吉思汗的鐵蹄所到之處,灰飛煙滅。這樣,雪山論道、止殺寡欲的使命,歷史地落在了丘處機的肩上。
二、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和平思想:仁慈反戰,保衛和平。深受儒家仁愛思想影響的丘處機,基于當時戰火連綿的時代背景,指出仁慈是獲得和平的基本途徑,因為眾生皆有道性,眾生本應平等。面對戰亂硝煙,他強烈呼吁統治者憐愛黎民蒼生免于性命之憂。其詩曰:“造物通神化,流形滿大千。群迷長受苦,萬圣不能悛。”[1]697明昌四年(1193年),黃河泛濫,饑民流離,瘟疫頻發,他悲憤蒼天置眾生千瘡百孔,呼吁每一個世人,尤其是每一個道徒要積德行善,常懷悲天憫人之心。他認為以仁慈為本,行善救難,方可成仙。他對民眾的苦難充滿同情,并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使其苦難解除。因此,丘處機率徒弟祈雨,且疾呼:“安得人心似我心,免遭痛徹臨頭厄。”[1]686除提倡仁慈之外,丘處機還渴望和平。磻溪隱居時,在金世宗的統治下,社會有了短暫的安寧,丘處機十分喜悅。然而好景不長,風云突變。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成吉思汗辟地千里,勢如破竹,殺人如麻,黎民蒼生恐將不得保全。見聞此狀,他不顧高齡之軀,毅然決然率領弟子西行大漠,希望以自己西覲之勸誡止殺,拯救百姓于苦海。歷時三年,終于到達成吉思汗行營,開始講道。其講道內容收錄于耶律楚材所整理的《玄慶風會錄》,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道家所倡導的“清心寡欲”和“固精守神”的理念;二是儒家“恤民保眾”“以孝治國”“布法推恩”的治國方略。正是因為丘處機有條不紊地論道,成吉思汗觸動頗多,于是以丘處機論道言論為準繩,將仁愛和平的詔諭散布各地。據此可以看出丘處機作為宗教領袖仁慈的一面,如《老子》所言:“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2]40(二)入世思想:無為即有為。《老子》三十七章如是:“道常無為而無不為。”[2]42道是萬物的本體,它的產生不受任何外力的作用,所以“道”是無為的。而萬物皆由道而生,因之,“道”又是“無不為”的。老子試圖要求人們效法“道”,以“無為”為綱要,順其自然,清靜寡欲,與世無爭,慎行遠禍,不可妄自作為。王重陽完全繼承了這一教義,力主棄世離俗,拋家專修,要求弟子不問世事,煉氣養生,將自己置于虛空之地。而丘處機卻與以上觀點截然相反。他從道的高度對“有為”和“無為”之間的關系進行理論上的論證。丘處機認為,所謂“有為”和“無為”,不過是道在動靜之時互為體用的表現,動則以“無為”為體,靜則以“有為”為體。就本質而言,他們是一樣的,都是道,不過是道的特性的不同表現形式。“無為”和“有為”不再是一對矛盾的哲學范疇,而是道的一體兩用。人們循道行事,就要根據道的要求,正確理解“有為”與“無為”的含義,發揮好道之“用”。他得出結論,無為即有為,無為即無所不為。其詩曰:“有動緣無動,無為即有為。三光不照處,萬象顯明時。”[1]699在政治層面,丘處機在存無為而行有為的入世思想的指導下,一改往日全真教不睬世事的純樸形象,開始結交權貴。當然,在與權貴交往的過程中,也積極為封建政權效力。我們也應該看到,丘處機依附朝廷的真實目的在于謀求全真道的發展,希望以封建士大夫為后盾,為全真道的發展尋求政治支持和經濟保障。在宗教問題上,丘處機的入世思想表現為把“打塵勞”納入道徒必行的外日用之內。所謂打塵勞即是服勤苦,就是折其強梗驕吝之氣。而在具體實踐上,服勤苦,即為盡心建立宮觀,發展教徒,壯大隊伍。打塵勞一旦被納入外日用,就和道徒所追求的成仙目標聯系起來。即外功全在自身,自己用力則可得功。功是得道成仙的階梯,功的大小深淺取決于自身的努力程度。所以,打塵勞積功是得道的重要途徑。丘處機告誡弟子,重作塵勞,不容少息。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數年間,全真教道觀的增加速度如雨后春筍,一躍成為北方道教大宗。(三)內丹思想:性命雙修。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對王重陽內丹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在內丹心性學說方面,對正念和邪念、真心和常心、性和命等作了較為仔細的區分,對其相互之間的關系和作用做了深入探討;在內丹理論的核心問題,即修煉步驟上,從三教合一思想出發,以王重陽心性理論作為指導,對修性過后怎樣達到修命目標的過程及途徑作了系統的闡釋。一直以來有這樣一種說法:道家有南北二宗,南宗不信性,北宗則是性命雙修。北宗先學心性,叫作性宗,繼而以坐功得丹得藥,稱作命宗。因之,曰性命雙修。丘處機認為,道生萬物,萬物生而有性,元神即性,任何形體中都有性。人因有七情六欲從而使性迷惑,而不得返樸,所以需煉性,讓其歸本。與此同時,丘處機更重視命功。據《長春真人語錄》記載:“吾宗唯貴見性,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凝神為處機,以明心見性為實地,以忘識化障為作用,回視龍虎鉛汞,皆法相而不可拘執。反次便為外道,非吾徒也。”[3]153由此可見,丘處機關于性命問題,主張以性為主,命為輔,先性后命,性命雙修,非輕視命功。他認為,性與命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為了論證修行,丘處機著《青天歌》。而為了論證修命,又著《西江月》十六首和《大丹直指》。凡此種種,都表明丘處機內丹思想是以雙修為主旨,在重視性的同時又重視命,二者不可偏廢其一。三、丘處機道教哲學思想的影響丘處機以獨特的身份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時間雖然不長,卻對中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丘處機仁慈反戰、捍衛和平的言論和行為,造就了一批在干戈不息形勢下濟世救民的門徒。如祁志誠,本是蒙古俘虜,同行百人皆遭殺戮,獨他幸免,于是投身全真,于云州筑樂全庵居住,用醫符來給百姓治病。《洞明真人祁公道行碑》記載其“往往為人傳誦”,“一方多賴以全濟”[4]699。王志謹《棲云王真人開澇記》載:“見終南山之地雨澤不恒,多害耕作,遂集道眾千余人……了無干旱之患。”[4]620凡此弟子,不勝枚舉,眾弟子皆以丘處機為楷模,身體力行濟世救民之道,保護在災亂中痛苦不堪的百姓。同時也為全真教樹立了良好的社會形象,擴大了社會影響。我們也應該看到,丘處機及其門徒對和平思想的實踐活動,起到了封建政府無法達到的宗教教化作用,具有穩固社會秩序的良好效應。第二,丘處機無為而行有為的入世思想,實際是對傳統道教中“無不為”思想的發展。丘處機深處動蕩變革的年代,國內民族矛盾十分尖銳,長期受民族文化熏陶的漢人,對少數民族的統治有一種敵視或不合作的態度,面對這一尖銳而復雜的社會矛盾,僅靠武力解決是不夠的,金世宗以及其他統治者都無能為力。基于此,統治者便拉攏道教,求助其解決自身的矛盾,以鞏固統治。與此同時,道教也需要強有力的政權及經濟基礎來謀求自身的發展,這就為丘處機履行傳統道教“無不為”的思想提供了社會需要。此外,全真教倡導三教融合,以返淳還樸為口號,把儒家倫理宗教化后作為教徒的行為規范,以齋蘸祈禱等方術作為聯系社會的橋梁,從而擴大了群眾基礎。所以,丘處機的入世觀是傳統道教無不為思想同時代結合的產物,較典型地反映了他的宗教改革和創新意識。第三,丘處機的內丹思想是對王重陽思想的繼承,并將三教圓融貫穿其中,在他的內丹心性理論中,融入大量的禪宗“正念”“邪念”“不動心”“真心”等概念,煉心最終也是達到一念無空的境界。而他的命功原理則以中國哲學中的陰陽元氣論和五行生克說為理論基礎。同時,丘處機的心性之正念中,也包含了仁、善、慈等儒家觀念;丘處機的內丹方法,簡明扼要,易學易記,便于宗教實踐,給修煉者帶來極大的方便,這也是全真教在丘處機掌教時期發展鼎盛的原因之一。我們可以看出,丘處機的內丹思想體系完整,且創見頗多,既是對前人經驗的總結和繼承,也是自己長期宗教實踐的積累和探索的結果。當然,他的心性理論受王重陽的影響極為深刻,是對王重陽的內丹心性理論的進一步發展,而其修煉方法也是對王重陽修煉方法的具體闡發。
道教對古代科技的影響綜述
[摘要]道教根植于中國文化土壤,在長期發展熔融過程中,對我國古代的思想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產生過巨大而復雜的輻射作用,留下它的深刻影響。本文談一下道教對中國古代科技的影響。
[關鍵詞]道教中國古代科技。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重道輕器,把科學技術當作“奇淫巧技”,向來不為社會重視,但中國卻出現了“四大發明”等對世界發展影響深遠的科技。這里面包含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教的影響,本文從道教對中國古代科技的影響看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
魯迅先生在《致許壽裳》一文中提到“中國文化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讀史,有許多問題可迎刃而解”。在《小雜感》里說到:“人們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基督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者,懂得中國大半。”英國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也說:“道家思想和行為的模式包括各種對傳統習俗的反抗,個人從社會上退隱,愛好并研究自然,拒絕出任官職……中國人性格中的許多最吸引人的因素都來自于道家思想。中國如果沒有道家思想,就會像是一棵某些深根已經爛掉的大樹。”從這些論斷中,我們可以看出道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具有無法替代的地位,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對古代化學研究的推動。
在一般人看來,宗教是迷信,是反科學的。但事實上,道教與古代尚未與冶煉術分家的化學有密切的關系。中國古代道士們從神仙方士那里接受了追求長生的觀念與方法。道士們認為,人可以長生,但要長生,必須服食不死之藥。那么,這種不死之藥是什么呢?其不可能是草木藥之類,因為草木藥本身易腐爛,在火中會化為灰燼。由于草木藥自身沒有堅固性、永恒性,移入人的身體中,自然不能使人長生不死。因此,必須發現一種堅固不朽、無變化的藥物,通過服用這種藥物,使其不朽性傳入人體中,服用者便可以長生不死。這種不朽的藥物,就是金丹。“金丹之為物,燒之愈久,變化愈妙。黃金入火,百煉不消,埋之,畢天不朽。服此二物,煉人身體,故能令人出生不死。此蓋假求于外物以自堅固……”道家煉丹學說把服食還丹金液看作修行的最上乘的方法,故此十分重視對礦物質藥材的燒煉。晉代道士葛洪在《抱樸子?金丹篇》里講到“丹砂燒之成水銀,積變又還成丹砂。”丹砂即朱砂,化學成分是硫化汞(HgS),性狀呈紅色,經過燒煉(HgS+O2→Hg+SO2),硫被氧化成了二氧化硫(SO2),把汞(Hg)分離出來。這樣就得到了煉丹術里重要的藥物——水銀(道教外丹術中稱“玄明龍膏”)。
道教醫學辟谷養生方法
在現代養生大潮中,各種養生方術蜂擁而至。道教醫學辟谷養生術因其實踐操作性較強,日益受到現代養生者的關注。但受歷史局限性影響,其又具有精華與糟粕同在、科學與神秘并存的雙重性質。研究者應以科學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分析,揚棄糟粕,對某些不合理的認識給予批判,以澄清誤區還原真相。同時,挖掘其科學內涵與現代應用價值,為現代養生學、治療學提供借鑒指導。
辟谷是歷代高道大醫經常采用的一種修煉養生之術,又稱“斷谷”、“絕粒”、“休糧”、“卻谷”等,即不食五谷雜糧。意指避免或減少谷類、肉類等食物的攝取,實際上是改善飲食結構的一種方法。葛洪在《抱樸子內篇•雜應》問辟谷“凡有幾法,何者最善與?”、“其服術及餌黃精,又禹余糧丸其服諸石藥,一服守中十年五年者及吞氣服符飲神水輩,但為不饑耳”[1]226。據此分析,早期辟谷術可分為4大類,即服餌辟谷、服氣辟谷、服石辟谷、服水辟谷。孫思邈在《千金方》中有類似記載,歷代文獻中常出現的辟谷術亦可照此類分。服餌辟谷,即服藥辟谷,是一種服食有益于身體的藥物以代替五谷雜糧的養生之法。服餌辟谷方種類繁多,使用到的藥物一般營養價值較高,消化時間長,能夠起到“不饑”的效果,并且經常服用亦有健身益氣之功效。馬王堆3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卻谷食氣》,最早提到了服餌辟谷的藥物為石韋。常出現在服餌辟谷方中的藥物有:豆、麻、茯苓、松脂、黃精、禹余糧、白術、白芷、天門冬、人參、柏葉、松子等。常配制成膏、丸、散、丹等便于儲存、攜帶的劑型,以代替日常的飲食,效果頗佳。如葛洪云:“令人多氣力,堪負擔遠行,身輕不極”[1]228。孫思邈論述服餌辟谷時,強調其醫療作用,如服天門冬辟谷方:“久服令人長生,氣力百倍。治虛勞絕傷,年老衰損羸瘦,偏枯不隨,風濕不仁。冷痹心腹積聚。惡瘡癰疽腫癩疾。重者周身膿壞,鼻柱敗爛”[2]。并進一步指出,堅持服用此方,無病不治,心腹固疾皆去。服氣辟谷,即以服氣之法與辟谷術相配合,通過呼吸吐納鍛煉達到辟谷養生之目的。服氣辟谷歷來被視為辟谷方術中最難修煉者,通常情況下服藥、辟谷、服氣三者相配合而用,并非提倡只憑借呼吸而不食用任何藥物和食物,在諸多辟谷術中服氣作為辟谷的一種輔助手段而起到養生保健的作用。服石辟谷,即服用一些礦物質藥物,達到辟谷養生的目的。據葛洪記載,辟谷術:“近有一百許法,或服中石藥數十丸,便辟四五十日不饑,練松柏之術,亦可守中,但不及大藥,久不過十年以還乃吞石子大如雀卵十二枚,足辟百日,輒更服散,氣力顏色如故也。欲還食谷者,當服葵子湯下石子,乃可食耳”[1]226。葛洪在此描述的就是服石辟谷。孫思邈《千金翼方》詳細記載了服石辟谷的藥方。以服食云母為例,其具體服法為:“云母擘薄,淘凈去水余濕,沙盆中研萬萬遍。以水淘澄取淀”[3]。
服石辟谷兼有治療“金瘡一切惡瘡”、“風癩”、“痔”、“淋”等疾患的作用。此辟谷之法并不宜使用。服水辟谷。孫思邈的《千金翼方》專辟“服水”篇,認為:“夫天生五行,水德最靈,浮天以載地,高下無不至。故水之為用,其利博哉。可以滌蕩滓穢,可以浸潤焦枯”[3]。詳細闡述了服水的禁忌、時間、服法等。葛洪《抱樸子內篇•雜應》亦稱:“又符水斷谷,雖先令人羸,然宜兼知者,倘卒遇荒年,不及合作藥物,則符水為上矣”[1]227。此“水”常指酒類。辟谷效應古人對辟谷的效應的記載主要有兩個方面,即養生保健與祛病療疾。如葛洪記載:“余數見斷谷人三年二年者多,皆身輕色好,堪風寒暑濕,大都無肥耳”[1]227。長期堅持辟谷的人,多身體健康,狀態較好。《抱樸子內篇•對俗》記載了潁川人張廣定的幼女墜落古墓穴中,因仿效龜息,辟谷三年存活下來的故事。《梁書》、《魏書》則分別有陶弘景、寇謙之善用辟谷導引之術而終獲強身健體之效的記述。《宋史》則記述了陳摶等長壽之人善于辟谷之事實。孫思邈則認為辟谷服水能“滌蕩滓穢,浸潤焦枯”,即辟谷能浸潤六腑,蕩滌五臟行氣活血,排除病氣,加強自身的抗病能力。文獻中記載的辟谷效應多為身輕體健,年壽高歲,預防疾病等,與辟谷者常服用的藥物有著直接的關系。《神農本草經》中記載了18種用于辟谷服食的藥餌。葛洪的煉丹專著《抱樸子》則辟“仙藥”專篇,論述了仙藥125種,多為“養性”“除病”之屬。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記載辟谷方54首,涉及到的藥物有25種。這些常被辟谷者青睞的藥物多為性溫熱,味甘苦,如黃精、茯苓、松脂、白術、枸杞等,這些藥物含有人體所需的營養,并兼有療疾之功效。
1.“三尸”說道門中人認為,人食五谷雜糧,在腸中會積聚糞便,產生穢氣。另,道教理論中有“三尸”之說,“三尸”為“人之生也,皆寄形于父母胞胎,飽味于五谷精氣。是以人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并進一步指出其“種類群多,蛔蟲長四寸、五寸或八寸,此蟲貫心人死;白蟲長一寸,相生甚多,長者五寸,躁人五臟”[4]。“三尸”靠體內的谷氣生存,是人體生病的根由。某些學者認為,道教理論中的“三尸”接近于現代醫學中的蛔蟲、寄生蟲,若實施辟谷,斷絕其賴以生存的谷氣,那么“三尸”在體內亦無法生存。葛洪據“三尸”之說,提倡實施辟谷術,強身健體。孫思邈在《千金翼方•辟谷》卷中記載了練松脂方,即為除“三尸”的辟谷方。
2.節制飲食節制飲食是道教醫學養生思想的一大特點,其核心內涵是過量的飲食會損害身體健康。《黃帝內經》提倡節制飲食,認為飲食失節是致病因素。《素問•上古天真論》篇提倡“飲食有節”,《素問•痹論》篇則認為“飲食自倍,腸胃乃傷”,飲食過量,就要損傷腸胃,這是脾胃病的常見病因,堪稱經典之言。葛洪指出:“欲得長生,腸中當清;欲得不死,腸中無滓”[1]226。陶弘景關于飲食的認識是:“所食欲少,心愈開,年愈益。所食愈多,心愈塞,年愈損焉”[5]。并且進一步指出:“百病橫夭,多由飲食。飲食之患,過于聲色。聲色可絕之逾年,飲食不可廢之一日。為益亦多,為患亦切”[5]。飲食與我們關系密切,“不可廢之一日”,而人體生病亦多與飲食有關,對此孫思邈則進一步指出“安身之本、必資于食”,合理的飲食才安身之本,健康之源。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反復強調節制飲食的重要性:“凡常飲食,每令節儉,若貪味多餐,臨盤大飽,食訖,覺腹中脹氣,短氣,或致暴疾”[6]。并且特別指出老人節制飲食的養生意義,因為人的臟腑功能會隨年齡的老化而衰退,無節制的飲食往往是致病之因。過量的飲食會損害身體健康。現代科學證明,科學合理的飲食是人類健康長壽的一條重要途徑。制定合理的膳食結構,嚴格控制食量已成為現代人保健身體的一種共識。蓋建民指出:“從理論上來講,降低攝食量可以減緩生命的成長和老化過程,吃的越少,體內產生的自由基的量也少,而自由基是導致人體日益朽壞老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控制飲食是人類的一條長壽之道”[7]。
現代醫學證明很多疾病的發生都和糞便在體內的滯留有關,長期的排便不暢會引起慢性中毒,以致發生疾病,加速衰老和死亡。通過短時間的辟谷,清除腸內的腐敗物質,加強腸胃的消化吸收能力,從而消除了很多潛藏的疾病危險。科學指導進行下的短期辟谷確有保健療疾之功用。但我們不提倡沒有任何輔助手段的單純的絕食之舉,長時間的忍饑挨餓有損身體健康,不但起不到辟谷養生的效果,反而會引發疾病。現代養生有提倡辟谷者,常見連續多天不吃任何東西,這是對辟谷術的一種誤解。辟谷不等同于絕食,并非某些人所認為的絕對不吃任何東西,并且宣揚其效應為長生不死。葛洪早已明確指出辟谷的效用:“敢問斷谷人可以長生乎?斷谷人止可息肴糧之費,不能獨令人長生也。問諸曾斷谷積久者云,差少病痛,勝于食谷時”[1]226。對某些夸大其詞之說,不可盲信、盲從,更不可無限擴大其萬能的作用。針對社會上流傳的一些錯誤認識有必要澄清,辟谷并非絕對地不吃任何東西,其具體操作更要在科學的指導下進行,并且要伴有服氣、服餌等輔助辟谷的養生手段,以達到科學健身、延年益壽的目的。
道教音樂研究分析論文
一直以來,道教音樂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漢族地區。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近現代道教音樂研究,即是始于漢族地區的,這從50年代中后期進行的幾項對道教音樂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來,例如:50年代以中國音樂史學家楊蔭瀏等學者組成的湖南音樂普查小組,對湖南地區的民間音樂進行了普查,其中對湖南衡陽地區的道教音樂等作了調查,并與以文字、記譜方式和佛教音樂等的調查結果一起登載于《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中;其后,相繼有《蘇州道教藝術集》、《揚州道教音樂介紹》等漢族不同地區道教音樂資料問世(注:《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之一宗教音樂》民族音樂研究所編,該所1958年油印,音樂出版社1960年出版《蘇州道教藝術集》中國舞蹈藝術研究會1957年油印《揚州道教音樂介紹》揚州市文聯編,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斷了20余年的道教音樂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復蘇和興起(仍主要集中于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上海音樂學院研究者陳大燦等開展對上海及其臨近地區道教音樂的錄音錄像工作;武漢音樂學院部分師生對武當山道教音樂的收集整理;中國音樂學院等音樂院校的一些學者,分別對北京白云觀、沈陽太清宮、四川青城山等宮觀的道教音樂進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學中國音樂資料館先后與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香港圓玄學院和《人民音樂》編輯部等聯合,分別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開了“國際道教科儀及音樂研討會”和“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1990年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道教協會等單位在北京白云觀召開了中國道教音樂學術研討會;1991年香港圓玄學院、人民音樂出版社、《音樂研究》編輯部和沈陽音樂學院在香港聯合召開了“第二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為基礎的對道教音樂進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參見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現狀與展望》載《音樂研究》1991(4),頁65~66)。
從整體來看,近年來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所加強,研究地區和范圍有所擴大,研究成果也不斷推出。這些成果主要來源于伍一鳴的《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甘紹成的《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陳天國的《潮州道教音樂》、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和《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吳學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潘忠祿的《巨鹿道教音樂》、張鴻懿的《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史新民的《論武當道樂之特征》、劉紅的《“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張鳳林的《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蒲亨強的《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王忠人和劉紅的《龍虎山天師道音樂》、曹本冶和蒲亨強的《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王純五和甘紹成的《中國道教音樂》、呂錘寬的《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周振錫和史新民的《道教音樂》(注:伍一鳴《江南道教音樂的由來和發展》載《中國道教》1989(1),頁40~44甘紹成《川西道教音樂的類型及其特征》載《音樂探索》1989(3),頁37~47陳天國《潮州道教音樂》載《星海音樂學院學報》1989(4),頁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儀式音樂初述》載《人民音樂》1989(8),頁26~29吳學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儀音樂探析》發表于第一屆道教科儀音樂研討會潘忠祿《巨鹿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2),頁17~20,10張鴻懿《北京白云觀的道教音樂》載《中國音樂》1990(4),頁31~34呂錘寬《臺灣天師派道教儀式音樂的功能》載《中國音樂學》1991(3),頁21~33曹本冶《道樂研究與香港道樂》載《黃鐘》1991(4),頁4~7史新民《論武當道樂之特征》載《黃鐘》1991(4),頁8~14;劉紅《“武當韻”與楚文化的淵源關系》載《黃鐘》1991(4),頁15~24張鳳林《蘇州道教音樂特點要述》載《黃鐘》1991(4),頁110~114蒲亨強《武當道樂曲目分類考源》載《黃鐘》1991(4),頁36~43王忠人、劉紅《龍虎山天師道音樂》載《黃鐘》1993(1~2)合刊,頁65~74曹本冶、蒲亨強《武當山道教音樂研究》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純五、甘紹成《中國道教音樂》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呂錘寬《臺灣的道教儀式與音樂》臺灣學藝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錫、史新民《道教音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究計劃”,將道教音樂的研究推向了中國境內更廣闊的區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圍包括北京、上海、蘇州、無錫、杭州、溫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計劃地對包括北京白云觀、蘇州玄廟觀、江西龍虎山、湖北武當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內的全國主要道教宮觀和道教勝地的道教音樂進行地域性與跨地域性的系統研究。全國近20名專家學者參加了該計劃第一階段有關道教音樂的20余個子項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進入尾聲之際,他們聚集于香港,參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學召開的“中國傳統儀式音樂研討會”。研討會上學者們結合各自的研究項目作了總結,并對道教儀式音樂研究的概念和方法進行了討論。該計劃第一階段的研究,共有20余項成果問世,目前已由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的論著有《中國道教音樂史略》、《龍虎山天師道教科儀音樂研究》、《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和《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研究》等(注:《中國道教音樂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紹成、劉紅、周耘編寫,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龍虎山天師道音樂研究》曹本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觀施食科儀音樂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樂研究》袁靜芳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蘇州道教科儀音樂研究》劉紅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當韻——中國武當山道教科儀音樂》王光德、王忠人、劉紅、周耘、袁冬艷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項研究成果反映出當今學術界對漢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道教不獨為漢族所有,除漢族外,分布于中國東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區的22個民族均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據覃光廣等編著的《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概覽》(北京中央民族學院,1982年版)提供的資料反映出,在滿、朝鮮、蒙古、達斡爾、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壯、瑤、仫老、納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個民族中,都存在著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對云南的彝、白、瑤、納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樂文化的影響尤為廣泛。
少數民族地區的道教音樂與漢族地區的道教音樂不盡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與漢族傳統文化交融發展的產物,既蘊涵著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質,也不乏漢族傳統文化風貌,內涵甚為豐富,頗具學術研究價值。
但與漢族地區的情況相比,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研究卻顯得比較薄弱,開始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區特有的具道教性質和色彩的洞經音樂。就筆者目前所知,有關少數民族洞經音樂的調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對昆明、下關、大理、麗江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調查的起因是:當時傳聞麗江保存有宋詞樂調。于是,在云南省委有關部門領導下,由曹汝群、周詠先、黃林、和鴻春、倪立跟等五人組成云南省宋詞樂調調查組,于1962年9月中旬赴麗江進行調查,經反復搜尋查找,初步證明此傳說實屬訛傳。轉而他們確定以麗江四個古老樂種之一的洞經音樂作為進一步探尋宋詞樂調的主要對象,并相繼對麗江、下關、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經音樂作了較深入的調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們分別撰寫了《關于宋詞樂調的調查報告》和《麗江、下關、大理、昆明洞經音樂調查記》(注:參見周詠先、黃林《洞經音樂調查記》載《民族音樂》1983(2),頁78)。作為該次調查地之一的麗江是納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則是白族的主要聚居縣(現已與下關一起合為大理市)之一,因此,該調查組對麗江和大理等地洞經音樂的調查,可視為有關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早調查。從起因看,這實為學術界一次“無心插柳”的對少數民族地區道教音樂的最初調查。
詮釋關于道教的孝道思想的探究
論文關鍵詞:道教孝道思想人道忠孝儒家教理為道神仙追求仙道
“忠孝”是儒家提倡的一種普遍道德,“神仙”是道教追求的一種終極理想,在許多人看來,二者似乎風馬牛不相干。然而,在道教發源地青城天師洞,一塊“忠孝神仙”的金字巨匾,堂而皇之地懸掛門庭。在道教眾多的教派,尚有以忠孝為本的凈明忠孝宗。于是,當我們認真審視道教的教理教義時,便發現儒家的倫理道德早已深浸入道教的思想學說之中。正因為如此,要學仙道,先修人道,人道不具,焉論神仙,這已成為道教界的一個共識。這里,就道教的孝道思想做一探索。
考察道教孝道思想的來源,無疑來自儒家。儒家繼承西周以來的傳統禮制,十分重視倫理道德的建設,其中即包括對孝道的肯定與發揚。“孝”的思想,其產生約當于西周時期。從金文及《周書》和《詩經》等文獻中,可以看到已有大量關于“孝”的內容,表明“孝”的倫理觀念已經形成。《說文解字》日:“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說明“孝”乃是一種家庭倫理,并在當時社會生活中,有著相當重要的規范作用,被視為高尚的道德情操而為人們自覺力行。
中國古代文化屬倫理型文化,在中國這樣的宗法制社會中,其倫理的核心就是忠孝人倫,這一點特別表現在以忠孝為本的思想上面。孔子在《論語》中曾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儒家主張積極入世,認為治國必先齊家,因此將忠孝說成“為仁之本”是合乎邏輯的。
從歷史角度上看,孝道是在個體家庭出現以后,作為家庭內部的行為規范而產生的。其思想內涵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在世的上輩的敬愛、服從和贍養,二是對于已故上輩和先祖的敬仰和追念。應當說,這個倫理概念主要是針對現實的世俗生活。但是,在其發展意義上,卻遠不止于此。其中的第二個方面,即對于已死之先輩的“追孝”態度和方式,導致了中國傳統的祖先崇拜進一步發展。顯然,也正是這點首先溝通了儒家與道教的內在交流,這對于道教神學與倫理學的建設是很重要的。因為“宗教”一詞本身,就同祖先崇拜有著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而祖先崇拜的目的,就是以先輩為倫理范型,昭示于人,要求人們循蹈其跡。
然而,兩家追求的終極理想畢竟有較大的差異。在解決“仙道”與“人道”內在的矛盾時,就必須以某種價值觀為基礎。對此,道教所提出的調和方法,就是要求慕道修仙之人,首先必須履行社會共同的“人道”價值。《無上秘要》卷l5說:“父母之命,不可不從,宜先從之。人道既備,余可投身。違父之教、仙無由成。”先當“仁愛慈孝,恭奉尊長,敬承二親”。《洞玄安志經》亦說:“夫學道之為人也,先孝于所親,忠于所君,憫于所使,善于所友,信而可復,諫惡揚善,無彼無此,吾我之私,不違外教,能事人道也;次絕酒肉、聲色、嫉妒、殺害、奢貪、驕恣也;次斷五辛傷生滋味之肴也;次令想念兼心睹清虛也;次服食休糧,奉持大戒,堅質勤志;導引胎息,吐納和液,修建功德。”如此則仙道可成。這樣一來,就將儒家忠孝仁信的思想與道教養生修仙之間的關系有機地融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