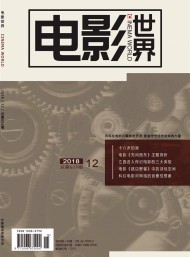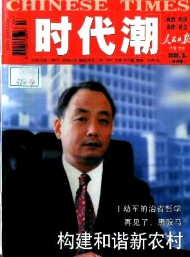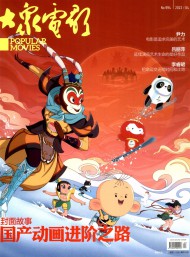大片時代范文10篇
時間:2024-01-17 19:59:30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大片時代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大片時代底層敘事管理論文
從2002年《英雄》以來,中國電影可以說進(jìn)入了一個“大片”時代,以《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等為代表,中國式的大片呈現(xiàn)出愈演愈烈之勢,在根本上來說,這些大片是反市場、反藝術(shù)的,因為它以壟斷性的宣傳和檔期取代了市場的自由競爭,以華麗的外表和大而無當(dāng)?shù)闹黝}、支離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對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切與藝術(shù)上的探索,以海外資金與跨國運(yùn)作取代了對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但這些“大片”卻憑借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dǎo)演”在1980年代以來積累的象征資本,占領(lǐng)了“中國電影”在國內(nèi)、國際的市場資源,形成了一種壟斷,在國內(nèi)電影觀眾中,也形成了一種“越罵越看,越看越罵”的奇怪觀影心理。
但同時,伴隨著“新紀(jì)錄運(yùn)動”的展開以及第六代導(dǎo)演的轉(zhuǎn)型,中國電影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鐵西區(qū)》、杜海濱《鐵路沿線》等紀(jì)錄片,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李楊的《盲井》、張揚(yáng)的《落葉歸根》等故事片。這些影片在對“底層”的關(guān)注中,發(fā)展出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代表著中國電影突破“大片”的壟斷,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并進(jìn)行藝術(shù)探索的新希望。
在今天,“底層”越來越成為文藝界關(guān)注的一個中心,這是在新世紀(jì)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藝思潮,它與中國現(xiàn)實(shí)的變化,與思想界、文藝界的變化緊密相關(guān),是中國文藝在新形勢下的發(fā)展。在文學(xué)界,以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為代表,涌現(xiàn)出了一批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說,如陳應(yīng)松的《馬嘶嶺血案》、劉繼明的《我們夫婦之間》、胡學(xué)文的《命案高懸》、羅偉章的《大嫂謠》等,此外還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打工詩歌”等現(xiàn)象。在戲劇領(lǐng)域,黃紀(jì)蘇的《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突破了小劇場的局限,在文藝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與反響。在電視劇領(lǐng)域,《星火》甚至創(chuàng)造了中央電視臺近十年來最高的收視率,達(dá)到了12.9℅;而在流行音樂界,也出現(xiàn)了“打工青年藝術(shù)團(tuán)”的音樂實(shí)踐。伴隨著以上文藝實(shí)踐,《文學(xué)評論》、《文藝?yán)碚撆c批評》、《天涯》等刊物紛紛推出理論與批評文章,從各個角度對“底層敘事”、文藝的“人民性”等問題進(jìn)行辯論與研討。
我們可以說,電影中的“底層敘事”是這一思潮的一部分,但在這些影片對“底層”的具體表現(xiàn)中,仍存在著不同的視角與價值觀,值得我們做進(jìn)一步的分析,在這里,我們將分析的范圍限定于故事片。
1、精英視角下的“底層”
2006年,賈樟柯的《三峽好人》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國內(nèi)同期上映,但票房大敗,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僅意味著第六代與第五代的對決,也是“中國式大片”與“底層敘事”的對決,兩種電影觀念、兩種電影發(fā)展方向的對決。
大片時代底層敘事管理論文
從2002年《英雄》以來,中國電影可以說進(jìn)入了一個“大片”時代,以《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等為代表,中國式的大片呈現(xiàn)出愈演愈烈之勢,在根本上來說,這些大片是反市場、反藝術(shù)的,因為它以壟斷性的宣傳和檔期取代了市場的自由競爭,以華麗的外表和大而無當(dāng)?shù)闹黝}、支離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對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切與藝術(shù)上的探索,以海外資金與跨國運(yùn)作取代了對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但這些“大片”卻憑借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dǎo)演”在1980年代以來積累的象征資本,占領(lǐng)了“中國電影”在國內(nèi)、國際的市場資源,形成了一種壟斷,在國內(nèi)電影觀眾中,也形成了一種“越罵越看,越看越罵”的奇怪觀影心理。
但同時,伴隨著“新紀(jì)錄運(yùn)動”的展開以及第六代導(dǎo)演的轉(zhuǎn)型,中國電影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鐵西區(qū)》、杜海濱《鐵路沿線》等紀(jì)錄片,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李楊的《盲井》、張揚(yáng)的《落葉歸根》等故事片。這些影片在對“底層”的關(guān)注中,發(fā)展出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代表著中國電影突破“大片”的壟斷,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并進(jìn)行藝術(shù)探索的新希望。
在今天,“底層”越來越成為文藝界關(guān)注的一個中心,這是在新世紀(jì)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藝思潮,它與中國現(xiàn)實(shí)的變化,與思想界、文藝界的變化緊密相關(guān),是中國文藝在新形勢下的發(fā)展。在文學(xué)界,以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為代表,涌現(xiàn)出了一批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說,如陳應(yīng)松的《馬嘶嶺血案》、劉繼明的《我們夫婦之間》、胡學(xué)文的《命案高懸》、羅偉章的《大嫂謠》等,此外還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打工詩歌”等現(xiàn)象。在戲劇領(lǐng)域,黃紀(jì)蘇的《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突破了小劇場的局限,在文藝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與反響。在電視劇領(lǐng)域,《星火》甚至創(chuàng)造了中央電視臺近十年來最高的收視率,達(dá)到了12.9℅;而在流行音樂界,也出現(xiàn)了“打工青年藝術(shù)團(tuán)”的音樂實(shí)踐。伴隨著以上文藝實(shí)踐,《文學(xué)評論》、《文藝?yán)碚撆c批評》、《天涯》等刊物紛紛推出理論與批評文章,從各個角度對“底層敘事”、文藝的“人民性”等問題進(jìn)行辯論與研討。
我們可以說,電影中的“底層敘事”是這一思潮的一部分,但在這些影片對“底層”的具體表現(xiàn)中,仍存在著不同的視角與價值觀,值得我們做進(jìn)一步的分析,在這里,我們將分析的范圍限定于故事片。
1、精英視角下的“底層”
2006年,賈樟柯的《三峽好人》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國內(nèi)同期上映,但票房大敗,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僅意味著第六代與第五代的對決,也是“中國式大片”與“底層敘事”的對決,兩種電影觀念、兩種電影發(fā)展方向的對決。
大片時代底層敘事管理論文
從2002年《英雄》以來,中國電影可以說進(jìn)入了一個“大片”時代,以《英雄》、《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無極》等為代表,中國式的大片呈現(xiàn)出愈演愈烈之勢,在根本上來說,這些大片是反市場、反藝術(shù)的,因為它以壟斷性的宣傳和檔期取代了市場的自由競爭,以華麗的外表和大而無當(dāng)?shù)闹黝}、支離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對現(xiàn)實(shí)的關(guān)切與藝術(shù)上的探索,以海外資金與跨國運(yùn)作取代了對民族國家的認(rèn)同,但這些“大片”卻憑借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dǎo)演”在1980年代以來積累的象征資本,占領(lǐng)了“中國電影”在國內(nèi)、國際的市場資源,形成了一種壟斷,在國內(nèi)電影觀眾中,也形成了一種“越罵越看,越看越罵”的奇怪觀影心理。
但同時,伴隨著“新紀(jì)錄運(yùn)動”的展開以及第六代導(dǎo)演的轉(zhuǎn)型,中國電影中也出現(xiàn)了一些反映現(xiàn)實(shí)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如王兵的《鐵西區(qū)》、杜海濱《鐵路沿線》等紀(jì)錄片,賈樟柯的《三峽好人》、李楊的《盲井》、張揚(yáng)的《落葉歸根》等故事片。這些影片在對“底層”的關(guān)注中,發(fā)展出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代表著中國電影突破“大片”的壟斷,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并進(jìn)行藝術(shù)探索的新希望。
在今天,“底層”越來越成為文藝界關(guān)注的一個中心,這是在新世紀(jì)出現(xiàn)的一種新的文藝思潮,它與中國現(xiàn)實(shí)的變化,與思想界、文藝界的變化緊密相關(guān),是中國文藝在新形勢下的發(fā)展。在文學(xué)界,以曹征路的小說《那兒》為代表,涌現(xiàn)出了一批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小說,如陳應(yīng)松的《馬嘶嶺血案》、劉繼明的《我們夫婦之間》、胡學(xué)文的《命案高懸》、羅偉章的《大嫂謠》等,此外還出現(xiàn)了“打工文學(xué)”、“打工詩歌”等現(xiàn)象。在戲劇領(lǐng)域,黃紀(jì)蘇的《切?格瓦拉》和《我們走在大路上》突破了小劇場的局限,在文藝界和思想界引起了巨大的爭論與反響。在電視劇領(lǐng)域,《星火》甚至創(chuàng)造了中央電視臺近十年來最高的收視率,達(dá)到了12.9℅;而在流行音樂界,也出現(xiàn)了“打工青年藝術(shù)團(tuán)”的音樂實(shí)踐。伴隨著以上文藝實(shí)踐,《文學(xué)評論》、《文藝?yán)碚撆c批評》、《天涯》等刊物紛紛推出理論與批評文章,從各個角度對“底層敘事”、文藝的“人民性”等問題進(jìn)行辯論與研討。
我們可以說,電影中的“底層敘事”是這一思潮的一部分,但在這些影片對“底層”的具體表現(xiàn)中,仍存在著不同的視角與價值觀,值得我們做進(jìn)一步的分析,在這里,我們將分析的范圍限定于故事片。
1、精英視角下的“底層”
2006年,賈樟柯的《三峽好人》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在國內(nèi)同期上映,但票房大敗,這是一個具有象征性的事件,不僅意味著第六代與第五代的對決,也是“中國式大片”與“底層敘事”的對決,兩種電影觀念、兩種電影發(fā)展方向的對決。
中國電影領(lǐng)軍人物韓三平制片藝術(shù)及成就論文
摘要:近年,我國的電影事業(yè)有著突飛猛進(jìn)的發(fā)展,無論是在電影的質(zhì)量還是票房的收入上,都比以前有巨大的改觀,尤其是08年國產(chǎn)電影票房的井噴,都與一個人有著密切的關(guān)系,他就是中國電影集團(tuán)公司董事長韓三平,由他率領(lǐng)的中影團(tuán)隊退出一系列高成本,高回收的商業(yè)電影的運(yùn)作,使中國電影開始走向成熟的大片時代.他對電影具有獨(dú)特的把握性,能讀懂電影,能把握劇本,在他的手下,制片是門藝術(shù),他將中國制片帶入全新的時代,他隊中國電影的推動作用是功不可沒的.
關(guān)鍵詞:中國商業(yè)電影;韓三平;制片藝術(shù);
緒論
在2000年,張藝謀《英雄》掀起中國大片序幕后,由韓三平所領(lǐng)導(dǎo)的中國電影集團(tuán)相繼推出《無極》、《投名狀》、《長江七號》、《梅蘭芳》、《赤壁》等一系列高成本高回收的商業(yè)電影,使得中國電影開始進(jìn)入成熟的大片時代,并使得中國電影票房實(shí)現(xiàn)井噴。這一系列事件使得中國電影有重大改變。
本文將就韓三平的推出的影片進(jìn)行制片分析,深入研究韓三平在《建國大業(yè)》中的突出作用及強(qiáng)大的號召力,并且對其他作品回顧,簡要分析,提取突出制片藝術(shù)。
通過韓三平在任中影集團(tuán)老總后,推出的一系列措施,提煉他對中國電影事業(yè)的貢獻(xiàn),及對商業(yè)電影方面做出的成就。
淺談中國電影“類型化”發(fā)展與突破
【摘要】全球化語境下,中國電影全面推行市場化轉(zhuǎn)型,類型電影的話題成為社會熱點(diǎn)。類型電影是影視商品化的一種創(chuàng)作方式,模式相對固定。中國的類型電影與好萊塢的類型電影生產(chǎn)系統(tǒng)有著很深的歷史淵源。類型電影的概念也不是永恒不變的,它會受到時代和市場環(huán)境的影響。商業(yè)化是未來電影市場的基本規(guī)律,類型電影是電影商業(yè)化的重要方式。
【關(guān)鍵詞】類型電影;意識形態(tài);電影美學(xué);新類型電影;創(chuàng)新突破
一、中國電影呈現(xiàn)多樣化發(fā)展
新中國成立70年以來,幾代中國電影人勇于承擔(dān)使命,創(chuàng)作出了大量電影。這些影片以不斷開拓的題材內(nèi)容和多樣復(fù)雜的類型,展現(xiàn)中國的社會變遷,反映時代精神。在積累與交流中,中國電影的題材類型不斷發(fā)展、豐富、融合,逐漸形成了獨(dú)特的中國電影文化景觀。建國早期,中國電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獨(dú)特的類型與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大量電影表現(xiàn)工農(nóng)兵形象,革命歷史題材、軍事驚險題材等題材占比較大,很多英雄形象至今記憶猶新;少數(shù)民族影片與中國歷史相結(jié)合,有益地探尋了電影的語言和情感設(shè)計,維護(hù)了民族團(tuán)結(jié);戲曲片、兒童片、諷刺喜劇片、名著改編片、紀(jì)錄片等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深得觀眾喜愛;還包括人物傳記片等,都為中國類型電影的未來發(fā)展打下了基礎(chǔ)[1]。改革開放階段,中國電影發(fā)展潮起潮落。電影導(dǎo)演在實(shí)踐創(chuàng)作中探尋自我命運(yùn),展現(xiàn)鮮明個性,反思民族文化,不斷解放思想和創(chuàng)新影像風(fēng)格。第四代導(dǎo)演追求質(zhì)樸自然的風(fēng)格,探求時代中的個人命運(yùn)。第五代導(dǎo)演有著獨(dú)特的民族化訴求,巧妙地打破傳統(tǒng),追尋中國電影的審美特質(zhì),推崇電影創(chuàng)新與意境,通過本土化的敘事方式、現(xiàn)代化的視聽語言,營造具有民族特色的電影意境。第六代導(dǎo)演“自我命名”,放棄重大的歷史民族題材,將紀(jì)實(shí)美學(xué)融入作品。世紀(jì)之交階段,電影的類型化發(fā)展加速。“馮氏賀歲商業(yè)喜劇電影”反映平民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變遷,可以看作是早期具有“類型”味道的中國電影。在此期間,有不少現(xiàn)實(shí)主義題材的影片展示出了青春情感和文化特色。導(dǎo)演關(guān)注和思考“人”在世紀(jì)變遷和時代變革中的個性表達(dá)。新世紀(jì)之后,電影題材更加多樣。很多新生代導(dǎo)演加入電影創(chuàng)作中,港臺合拍片增加,電影文化出現(xiàn)繁榮局面。張藝謀電影《英雄》采用市場化和工業(yè)化的運(yùn)作,使電影的產(chǎn)業(yè)觀和營銷觀等進(jìn)入人們的視野。中國逐漸進(jìn)入大制作大投資的“中國式商業(yè)大片時代”,其他小成本電影、喜劇電影也不斷出現(xiàn),多種類型影片共存。新世紀(jì)之后,電影的產(chǎn)業(yè)化和類型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式大片大量出現(xiàn),越來越多的觀眾走進(jìn)影院,但電影大片激增的同時,卻缺乏全球性的敘事經(jīng)驗,不少影片形式大于內(nèi)容,觀眾逐漸審美疲勞,中國式大片亟待轉(zhuǎn)型。后來,東方魔幻電影將國產(chǎn)大片的工業(yè)水平提升到了新高度,電影后期特效技術(shù)不斷升級。隨著電影市場的改革,更多青年導(dǎo)演開始參與到主旋律電影的創(chuàng)作中,促進(jìn)了主旋律電影與商業(yè)類型電影的融合。小成本、小人物、多線并行敘事的喜劇片也逐漸受到觀眾關(guān)注,中國電影“大片”帶動了小成本電影。公路喜劇類型電影不斷擴(kuò)展著喜劇新美學(xué);青春電影拓展了愛情電影的范疇;玄幻魔幻類型電影糅合多種風(fēng)格技術(shù);警匪犯罪偵破電影小眾化;藝術(shù)電影風(fēng)格獨(dú)特,自成一體;港臺電影導(dǎo)演北上合拍電影,促進(jìn)了國產(chǎn)電影市場的多元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社會現(xiàn)實(shí)題材的電影和社會主旋律電影在電影影像語言和拍攝手法方面實(shí)現(xiàn)了全方位的升級,同時科幻奇幻電影和動畫電影實(shí)現(xiàn)了票房突破。新導(dǎo)演關(guān)注社會現(xiàn)實(shí),與觀眾形成情感共鳴,講述新時代社會現(xiàn)象。主旋律電影在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形象上也取得巨大突破。中國電影正向著類型不斷健全、產(chǎn)業(yè)全面發(fā)展、技術(shù)不斷與國際接軌的方向穩(wěn)步前進(jìn)。截至目前,動作類型電影《戰(zhàn)狼2》、動畫電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和科幻類型電影《流浪地球》,位居國內(nèi)電影票房前三甲,電影題材不同,類型不同,風(fēng)格多樣,呈現(xiàn)繁榮態(tài)勢。
二、從意識形態(tài)看中國電影體制的變遷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電影嘗試類型化的探索時,中國的市場還大部分處于封閉狀態(tài),尚未融入世界市場。影片題材以革命歷史為主,表現(xiàn)特殊年代的革命思想觀念。改革開放之后,思想逐漸變得開放。軍事、戰(zhàn)爭、歷史等題材的影片敘事宏大,現(xiàn)實(shí)題材影片的觀念意識也不斷調(diào)整。此時,謝晉的《天云山傳奇》(1981)、《牧馬人》(1982)、《芙蓉鎮(zhèn)》(1987)等影片成為反思社會的特殊代表。人們逐漸開始關(guān)注現(xiàn)實(shí)主義審美視角和個人情感表達(dá),張暖忻的《沙鷗》、吳天明的《老井》等影片,或記錄生活,或挖掘人性。張藝謀等執(zhí)導(dǎo)的現(xiàn)實(shí)主義風(fēng)格鮮明的作品,創(chuàng)造了經(jīng)典的藝術(shù)形象。《少林寺》創(chuàng)造的高票房高觀影記錄,體現(xiàn)了電影創(chuàng)作者對電影題材、表現(xiàn)和傳播機(jī)制的不斷探索。2000年以后,中國電影逐漸嘗試構(gòu)建明確的本土意識形態(tài),社會環(huán)境的新變化提升了電影創(chuàng)作的自信。在大片興起的時代,創(chuàng)作主體的主觀構(gòu)造成為踐行電影題材探索與藝術(shù)創(chuàng)新活動的重要意識載體[2]。概括地說,中國電影高速發(fā)展的過程中,形成了以主流意識形態(tài)文化為主導(dǎo),多元文化兼容共存的模式。
商業(yè)電影大片管理論文
[摘要]中國商業(yè)大片轟轟烈烈地拓展和打進(jìn)海外市場,從外國觀眾手里賺得大把的鈔票,國人對此并沒有表現(xiàn)出太多的激動和興奮,更沒有油然而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情不自禁的喝彩聲,反而非理性的質(zhì)疑和責(zé)罵聲鋪天蓋地,這種悖論現(xiàn)象值得人們深思。
[關(guān)鍵詞]中國商業(yè)大片大投資大規(guī)模
2002年張藝謀執(zhí)導(dǎo)的影片《英雄》開啟了中國大陸商業(yè)大片的序幕,并被評論界譽(yù)為大陸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yè)大片。隨后,《十面埋伏》、《無極》、《夜宴》、《神話》《功夫》、《滿城盡帶黃金甲》、《墨攻》、《投名狀》、《赤壁》等影片的閃亮登場,無疑讓國人領(lǐng)略了中國導(dǎo)演呈現(xiàn)給觀眾的大片視角,商業(yè)大片逐漸在國內(nèi)形成了氣候,并在海外的電影市場占據(jù)了一席之地。
一、“牽手”——中國商業(yè)電影大片
所謂商業(yè)大片,引用一位資深電影學(xué)者的觀點(diǎn):一是制作規(guī)模,包括大投資、高科技、強(qiáng)大的明星陣容:二是制作目標(biāo),跨國族、跨文化而進(jìn)入全球性的主流市場:三是看它在全球性主流市場上的效益和業(yè)績,三者不可或缺。
事實(shí)證明,這種概括是非常準(zhǔn)確、權(quán)威和到位的。中國幾乎所有的商業(yè)大片確實(shí)都是巨額投資,《英雄》投資3100萬美元;《無極》投資3.5億元人民幣《滿城盡帶黃金甲》投資3.6億元人民幣;《赤壁》投資則高達(dá)六億,可謂空前,卻不敢說后無來者。而且,這種巨額投資使商業(yè)大片同樣獲得了更為令人驚嘆的高回報的票房業(yè)績。如《英雄》僅在北美上映的一個月內(nèi),票房收入就高達(dá)5000萬美金,并連續(xù)幾周蟬聯(lián)全美票房排行榜的冠軍。這在當(dāng)時是亞洲電影在北美票房的最高紀(jì)錄,不僅寫就了張藝謀國際級導(dǎo)演的個人神話,也唱響了中國電影的贊歌,讓世人不得不為之矚目和驚嘆。《華爾街日報》認(rèn)為“《英雄》真正拉開了中國大片時代的幃幕。”《紐約時報》甚至以兩個版面的篇幅報道了《英雄》在美國上映的盛況,并做了贊譽(yù)有加又不失客觀的評論:“《英雄》這部中國電影,經(jīng)典得就像中國的《紅樓夢》,也是我們美國奧斯卡的無冕之王。”
新世紀(jì)電影文化主體性
自上世紀(jì)8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市場化轉(zhuǎn)型,歷經(jīng)三十余年,創(chuàng)造了世界經(jīng)濟(jì)史上的奇跡。持續(xù)的經(jīng)濟(jì)增長帶來民族國家的文化自信,由此引發(fā)了一系列中國崛起的敘事,央視政論片《大國崛起》、《復(fù)興之路》是其中的標(biāo)志性作品。與此同時,中國電影在長期低迷之后,從新世紀(jì)伊始,持續(xù)在產(chǎn)量、票房等主要經(jīng)濟(jì)指標(biāo)上快速增長,成為世界上發(fā)展最快的電影國家。與大國崛起敘事相得益彰,新世紀(jì)中國電影亦進(jìn)入一個大片時代,《英雄》的成功刺激了一系列大制作電影的出現(xiàn),《集結(jié)號》、《建國大業(yè)》、《建黨大業(yè)》、《金陵十三釵》等,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商業(yè)大片的繁榮,主旋律大片的跟進(jìn),并與前者最終合二為一,被認(rèn)為是中國電影第三次轉(zhuǎn)型的標(biāo)志:走向國家主流商業(yè)電影。[1]然而,新世紀(jì)中國電影一方面通過主流商業(yè)電影的繁榮,建構(gòu)了“復(fù)興崛起”的想象,另一方面則以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影像,如賈樟柯電影、李玉電影、張猛電影等,反映了社會轉(zhuǎn)型過程中的階層斷裂與文化危機(jī)。也許,《集結(jié)號》、《建國大業(yè)》等主流商業(yè)大片的票房成功,的確讓中國電影獲得了新的想象空間,但中國電影目前存在的諸多傾向:分裂的價值結(jié)構(gòu)、去政治化的商業(yè)追求、好萊塢化的大片風(fēng)格等,使其并不能真正完成一種基于自我文化肯定的主體認(rèn)同。作為一種文化產(chǎn)品,電影在其商品、文化價值之外,亦由聲像組合體現(xiàn)政治訴求,從而與社會主流價值、國族共同體想象形成對話與協(xié)商。然而,中國式大片卻是一個極端強(qiáng)調(diào)電影的商品屬性,以消費(fèi)主義與市場需求作為價值基礎(chǔ),極力“去政治化”的“類型”。實(shí)際上,中國大片的實(shí)質(zhì)就是資本及其流動,其虛無的內(nèi)涵導(dǎo)致了主體———作者與觀眾的死亡。也許,主體死亡的狀態(tài)恰好契合于現(xiàn)代人的異化身份,就像賈樟柯電影《世界》里的那些游蕩于“世界擬像”中的人們。
一、資本化、景觀社會與中國式大片
《世界》是一部寓言電影,濃縮了當(dāng)代中國的現(xiàn)實(shí)圖景:在全球化想象中沉淪的廢墟。在電影里,京郊大興的微縮景觀———“世界公園”構(gòu)成了當(dāng)代中國的世界想象,來自山西的土著群聚其中。一方面,個人因置身“世界”而重構(gòu)了自己的鄉(xiāng)土身份,仿佛已經(jīng)是全球化語境中的成員;另一方面,“世界”其實(shí)是個荒蕪孤寂的角落,個人生命無以托付。賈樟柯因此憤怒地說:“不存在世界,只存在角落。”[2]《世界》表征了豐盛與匱乏并存的當(dāng)代中國:簇?fù)碇鵁o數(shù)全球化的擬像,呈現(xiàn)出無比豐盛的景象,但在這些極度繁華的現(xiàn)代性景觀之下,卻是一個內(nèi)在價值匱乏的主體形象。自《英雄》之后,中國式大片亦在結(jié)構(gòu)“世界”性的電影景觀,其強(qiáng)烈的視聽震撼、聳動的營銷手段,都與以好萊塢為代表的全球文化工業(yè)模式接軌。然而,視聽盛宴中是顧此失彼的價值立場,華麗形式下是意義匱乏的文化黑洞。
目前的中國電影,無論是商業(yè)大片,還是地下電影,都與全球資本息息相關(guān),已經(jīng)進(jìn)入資本時代。中國電影生產(chǎn)全然依據(jù)資本邏輯:觀眾被大片消費(fèi)的沖動綁架,電影生產(chǎn)則被資本牟利的沖動綁架,資本流動又再生產(chǎn)出新的消費(fèi)欲望,中國式大片最終成為“資本的附庸”。《英雄》票房成功之后,古裝武俠加宮廷政治的電影形式受到資本追捧,《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夜宴》等電影相時而生,直到其作為一個商品模式被榨干所有利潤,資本才會棄之而去。在大片盛宴中,電影在盛極一時后往往迅速歸于沉寂,寂寞之余唯有利潤、票房等令人瞠目的數(shù)目字產(chǎn)生,而這些數(shù)目字就是資本符號化的終極體現(xiàn)。中國大片的票房拜物教在2010年又達(dá)新高,《趙氏孤兒》、《讓子彈飛》與《非誠勿擾2》三部大片爭雄賀歲檔的火暴景觀,確實(shí)顯示了資本、消費(fèi)與傳媒的強(qiáng)大力量。不過,中國式大片在資本的迅速流動中被加速度消費(fèi)、然后遺忘,因此表征出一種即生即死的趨向———它由片段化的、超現(xiàn)實(shí)的畫格構(gòu)成,消除了意義構(gòu)成所需要的敘事性。對觀眾來說,中國大片呈現(xiàn)出視覺中心主義的暴力性,頻繁發(fā)生的震驚性圖景讓前一個景觀未曾進(jìn)入意識領(lǐng)域,便已經(jīng)被下一個覆蓋,一切震驚都無曾沉淀,便在引發(fā)了無意識領(lǐng)域的一片混亂之后,迅即煙消云散。
作為中國大片肇始之作的《英雄》便具有景觀化的典型癥候,明信片般的影片令人目不暇接,“影像的流動勢如破竹,這一流動的影像類似于隨意控制這個可感覺的世界的單一化內(nèi)涵的他人;他決定影像流動的地點(diǎn)和它應(yīng)該如何顯示的節(jié)奏,像不斷的而又任意的奇襲一樣,他不留時間給反思,并完全獨(dú)立于觀眾可能對他的理解或者思考。”[3],而《讓子彈飛》則是中國大片“景觀化”趨向的新例證,一切言語和鏡頭都在迫不及待地奔向高潮,而高潮之后卻是空虛一片。大片的景觀化追求使之不得不極端依賴暴力和色情,《滿城盡帶黃金甲》將大片的暴力話語和色情話語推向極致,《集結(jié)號》、《投名狀》等皆以集團(tuán)性的血腥暴力景觀作為電影噱頭,而《讓子彈飛》則是硬暴力與軟色情的二位一體。至于2011年歲末的《金陵十三釵》,則以女性肉身的堆疊,置換民族主義意識形態(tài),構(gòu)成了一個近乎癲狂的商業(yè)電影奇觀。景觀化是社會物化、資本化的體現(xiàn),在其生成的邏輯中,“資本變成為一個影像,當(dāng)積累達(dá)到如此程度時,景觀也就是資本。”[3]世界的景觀化和人類生存的日益表象化互為表里,世界的景觀化是對社會存在的遮蔽,而電影的景觀化則是對電影本質(zhì)的遮蔽。在大片時代,作為“物質(zhì)世界還原”的電影仿佛是史前傳說,電影誕生不過百余年,其本體便從映像變成了擬像———像之幻象。今天,世界電影總體上已經(jīng)好萊塢化了,好萊塢已經(jīng)構(gòu)成了其世界性的文化霸權(quán),世界已經(jīng)是一個好萊塢星球。中國式大片則是好萊塢星球上的“東方奇觀”。在市場化過程中,中國電影的融資、制作、營銷等環(huán)節(jié)與好萊塢亦步亦趨,完成了與“好萊塢星球”的產(chǎn)業(yè)接軌。本土的電影制作———特別是商業(yè)大片,已經(jīng)有好萊塢娛樂巨頭的資本投入,像諸多大片都有西方跨國娛樂公司的參與。各大民營影視公司像華誼兄弟、保利博納等復(fù)雜的資本結(jié)構(gòu)中,也都隱藏著跨國娛樂資本的身影。新世紀(jì)以來,表面上看國產(chǎn)電影的市場份額似乎總是高于進(jìn)口影片,但如果從電影的資本結(jié)構(gòu)進(jìn)行分析,以資本比例占據(jù)的市場份額來說,卻未必樂觀。
中國電影的生態(tài)結(jié)構(gòu)在大片的擠壓下也日趨惡化,中國式大片占據(jù)了國內(nèi)電影市場,小公司、小制作的電影雖然數(shù)量眾多,卻難得有立足之地。而在藝術(shù)上,中國式大片極力模仿好萊塢電影,具有好萊塢電影的主要特點(diǎn):“制造夢幻和商品文化,逃避主義式幻想以及對自身生產(chǎn)過程的約束”。[4]從市場機(jī)制的好萊塢化,到文化風(fēng)格、價值內(nèi)涵的好萊塢化,中國大片徹底獲得了好萊塢星球的身份特征,并以此“成就”作為中國電影產(chǎn)業(yè)成功躋身世界的證據(jù)。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好萊塢身份是中國電影的追求,那么直接做好萊塢跨國娛樂帝國的一員,生產(chǎn)好萊塢電影就是了,《功夫熊貓》、《臥虎藏龍》、《花木蘭》、《黑客帝國》等好萊塢電影并非沒有中國元素。顯然,好萊塢化并不是中國電影的本體性追求,它毋寧說是一種面對全球化挑戰(zhàn)時的綏靖策略,結(jié)果卻帶來了實(shí)質(zhì)性的困惑:中國電影的未來就是好萊塢化?中國電影在過去三十年間的市場化追求,明顯表現(xiàn)出為適應(yīng)美國主導(dǎo)的全球文化工業(yè)體系而進(jìn)行調(diào)整的努力。跨國媒體集團(tuán)徑直進(jìn)入國內(nèi)娛樂市場,培育中產(chǎn)階級的電影消費(fèi)群體,而中國電影也成為全球消費(fèi)文化和消費(fèi)符號的載體。中國電影的景觀化便是資本神話的映像:資本通過國產(chǎn)大片的形式構(gòu)成的好萊塢景觀,為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kuò)張在中國的視覺空間里建立了一座光影交織的虛擬紀(jì)念碑,而國人通過觀影活動完成了資本/商品拜物教的無意識塑造。中國電影的產(chǎn)業(yè)救贖與文化失落、商業(yè)成功與身份危機(jī)仿佛一體兩面,時刻糾纏在一起,民族電影的市場化和全球化過程充滿了爭議和不確定性,并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文化危機(jī)。
大中華下香港電影新布局
香港電影一直是華語電影乃至世界電影版圖上一支奇妙的力量,香港以其獨(dú)特的地理環(huán)境和歷史際遇,中西交融的文化特征,高效專業(yè)的商業(yè)化社會形態(tài),吃苦耐勞、開拓應(yīng)變的香港精神,讓其電影產(chǎn)業(yè)在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隨著經(jīng)濟(jì)的高速發(fā)展達(dá)到鼎盛,那些獨(dú)具風(fēng)格不可復(fù)制的“香港制造”,成為一代人的經(jīng)典記憶。1997年香港回歸,之后幾年經(jīng)歷了亞洲金融危機(jī)、經(jīng)濟(jì)滑坡、SARS、禽流感等打擊,香港電影業(yè)一度低迷,香港經(jīng)濟(jì)在中國內(nèi)地的扶持下逐漸走出低谷。2003年,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qū)政府簽署CEPA協(xié)定,為香港電影在內(nèi)地的發(fā)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港產(chǎn)片只需通過審查就可以不受進(jìn)口配額限定在內(nèi)地發(fā)行,這讓香港電影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內(nèi)地市場空間。與此同時,中國內(nèi)地經(jīng)濟(jì)的騰飛和市場的整合,讓“大中華”文化圈進(jìn)一步整合和開拓,華語文化聯(lián)系更為緊密。香港電影格局在各種形勢的推動下發(fā)生顯著變化,香港著名影評人列孚將CEPA之后的香港電影稱為“后港產(chǎn)片”①。港片與中華文化母體匯合的趨勢日益顯著,而對內(nèi)地市場的依賴也日趨加強(qiáng),香港電影人在新的歷史語境下開始調(diào)整創(chuàng)作策略,或意氣風(fēng)發(fā)北上開拓,或執(zhí)著留守香港制造,無論何種創(chuàng)作方向,港片的思路和模式都在發(fā)生變化。
一、北上:變通與平衡之道
香港電影人進(jìn)軍內(nèi)地,已經(jīng)成為潮流,內(nèi)地廣闊的電影市場對熟諳電影商業(yè)運(yùn)作的香港導(dǎo)演充滿誘惑,而內(nèi)地經(jīng)濟(jì)高速發(fā)展帶來的對大投資、高成本的“大電影”的雄厚支撐,也讓中國內(nèi)地超越了單純“賣片地”的位置,而是擁有資金、資源、市場全面保障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對于大多數(shù)電影人來說,制作巨額資金氣勢磅礴的“大電影”始終是一種情結(jié),而這種電影單純依靠香港本土的資金和市場很難實(shí)現(xiàn),于是香港導(dǎo)演紛紛“北上”拍片,尋求與內(nèi)地的合作,更有大量香港電影人已將中國內(nèi)地作為主要創(chuàng)作基地。“北上”之路勢必碰到文化審美、創(chuàng)作思路、精神氣質(zhì)上的“水土不服”,香港導(dǎo)演為適應(yīng)內(nèi)地市場調(diào)整原有的創(chuàng)作策略和影片風(fēng)格是必然的,但如果只是一味“迎合”,就會誤入雷區(qū),完全喪失香港精神氣質(zhì)和文化特色,生硬地拼湊并不駕輕就熟的“內(nèi)地模式”,只會兩頭不討好。因此“如何剪裁出一個合乎中國想象的電影場景,但同時又不會掉失了寄語香港故事的基調(diào)”②,是香港“北上”電影人的平衡之道。
徐克導(dǎo)演是香港電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影片曾一路領(lǐng)跑“香港制造”如火如荼的20世紀(jì)八九十年代,無論是飄逸乖張的亂世江湖,還是神秘絕美的鬼怪奇情,都成為港片黃金時代的典范。2005年,徐克以他一貫擅長的武俠片《七劍》正式征戰(zhàn)內(nèi)地,開始了艱辛的北上之路。徐克希望讓《七劍》成為他武俠動作片的“分水嶺”,一改往日的天馬行空輕盈飄逸,代之以莊重渾厚的寫實(shí)風(fēng)格,并輔以“華語大片”必要的明星云集、聲勢浩大、震撼視聽等要素,雖然做足了功夫,但《七劍》當(dāng)年的票房并不理想,也被觀眾批評過于刻板凝重,喪失了徐克電影灑脫雋逸的風(fēng)骨,“北上”第一炮并未打響。此后,不斷求新求變的徐克又嘗試靈異題材和都市題材,2008年推出兩部《深海尋人》和《女人不壞》,都徹底顛覆了徐克以往的風(fēng)格,并完全沒有香港痕跡,無論是發(fā)生在神秘海洋的玄異傳說包裝下的愛情故事,或是發(fā)生在北京都市的時尚女人的先鋒戀愛,雖都附庸市場潮流刻意求新,但結(jié)果卻并不討好,遺世獨(dú)立的徐克電影幾乎就要被定格在曾經(jīng)的香港電影的記憶里。直至2010年《狄仁杰之通天帝國》的出爐,古靈精怪的玄幻想象,撲朔迷離的大唐奇案,流光飛舞的魔幻武俠,“徐克風(fēng)格”再度回歸,伴隨精美制作和浩大場面,3億票房讓“北上”以來一度“水土不服”的徐克終于翻身。
陳可辛導(dǎo)演是“北上”派中較為成功的案例,2005年首度進(jìn)軍內(nèi)地的《如果•愛》,歌舞片的瑰麗絢爛,虛實(shí)時空縱橫交錯,曠世之戀扣人心弦,影片雖未大紅大紫卻也開始在內(nèi)地漸入佳境。2007年《投名狀》成為合拍片成功典范,跌宕的劇情起伏,動人的情義取舍,震撼的場面制作,香港金像獎八個大獎和內(nèi)地2億票房讓影片榮利雙收。2010年監(jiān)制《十月圍城》,九大影帝齊聚繪成一副義士群像,舍生取義的正劇回歸,再破票房新高。陳可辛的北上之路充分體現(xiàn)了香港電影人的變通之道。陳可辛在“北上”之前,在香港就是一個“善于把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市場判斷糅合在一起”③的電影人,無論是愛情文藝片《甜蜜蜜》,喜劇片《金枝玉葉》,驚悚片《三更》系列,“陳可辛制造”往往能得到口碑和票房的雙重肯定。2003年陳可辛監(jiān)制《金雞》,通過一個妓女的人生,笑中帶淚的喜劇方式敘說香港歷史20年的變遷,獨(dú)特的港式幽默和港人記憶,是標(biāo)志性的“香港制造”,影片在香港大受垂青,但因題材問題無法進(jìn)軍內(nèi)地,僅靠香港市場1000萬元的票房無法收回1500萬的投資。陳可辛意識到香港電影市場的局限,也預(yù)見到中國內(nèi)地不斷增長的市場潛力和疾速擴(kuò)大的觀眾群,知道下一步必須放眼合拍片。
2005年,陳可辛北上“試水”的首部影片是他所擅長的愛情文藝題材《如果•愛》,其實(shí)除卻歌舞片的華麗包裝,影片的故事內(nèi)核與十年前的《甜蜜蜜》如出一轍,連導(dǎo)演自己都說:“《如果•愛》其實(shí)只是《甜蜜蜜》一個殘酷版而已,故事根本就是同一個。”④但從《如果•愛》中可以看到諸多適應(yīng)內(nèi)地市場的策略性處理,最明顯的就是“時空”和“地域”的模糊,不再有《甜蜜蜜》中來“香港”打工的“內(nèi)地人”這種顯著的身份差別,甚至模糊了具體年代和地理概念,代之以光怪陸離的現(xiàn)實(shí)與虛擬時空的交錯。《如果•愛》試水之后,陳可辛逐漸摸索制作大華語電影的整合途徑,終于在2007年以《投名狀》驚艷內(nèi)地,被譽(yù)為“香港電影北上最成功的一次生產(chǎn)活動”,列孚更贊其是“20年來古裝類型片中最成功的作品”⑤。影片的運(yùn)作方式,是當(dāng)代華語商業(yè)大片的運(yùn)作模式,巨資鋪陳的壯麗場面,頂級明星的豪華陣容,永難釋懷的人性沖突,中國式的情義與背叛,劇情推進(jìn)中尚依稀可見香港黑幫片的底子,但黃沙狼煙的宏大廝殺和千軍萬馬的浩然聲勢,早已不是傳統(tǒng)港產(chǎn)片的格局。《投名狀》的成功讓陳可辛認(rèn)識到“中國電影已不只是小陽春了”⑥,中國內(nèi)地的大片時代已經(jīng)成熟。2009年,陳可辛監(jiān)制香港導(dǎo)演陳德森早在十年前就想實(shí)現(xiàn)卻無法如愿的電影《十月圍城》,實(shí)景還原了清末香港中環(huán)城,九大影帝的全明星陣容,華人世界廣泛認(rèn)同的忠誠義士,堅定無悔的舍身成仁,甚至包括獨(dú)具中國特色的“名導(dǎo)效應(yīng)”,這時的陳可辛在內(nèi)地進(jìn)行電影運(yùn)作幾乎已是駕輕就熟,影片對革命大業(yè)不容置疑的犧牲,20世紀(jì)末港片中常見的流離失所的情緒不見蹤影,代之以堅定的“投入懷抱”的姿態(tài),尋找殖民城市的根脈和與中國歷史的淵源。這是陳可辛“北上”之路的第三部影片,還是12月賀歲檔,第一部《如果•愛》與陳凱歌的《無極》對壘票房不濟(jì),第二部《投名狀》大獲全勝但票房仍不敵同時上映的馮小剛的《集結(jié)號》,而此時與《十月圍城》競爭的是張藝謀的《三槍拍案驚奇》,《十月圍城》終于一路領(lǐng)跑。陳可辛的北上“三級跳”可謂步步為營。
電影資本奴隸論文
在剛剛落幕的第十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國產(chǎn)電影的集中亮相以及關(guān)于中國電影生存與發(fā)展的討論,格外引人注目。
近年來,中國電影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數(shù)位元組節(jié)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憂慮的現(xiàn)象。
以研究電影理論、中國電影史為專業(yè)特長的北京大學(xué)教授戴錦華認(rèn)為,以國產(chǎn)大片為代表的中國電影,其體征已經(jīng)暴露出一些亟須予以診治的病癥。
正視問題,才能及時解決問題,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請教您一個問題:有人說,從2002年的《英雄》開始,中國電影進(jìn)入了“大巨片時代”、“復(fù)興的時代”,對此您怎么看?
戴錦華:這種“大巨片時代”、“復(fù)興的時代”的提法,根據(jù)是什么?
電影資本奴隸管理論文
在剛剛落幕的第十一屆上海國際電影節(jié)上,國產(chǎn)電影的集中亮相以及關(guān)于中國電影生存與發(fā)展的討論,格外引人注目。
近年來,中國電影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但在票房數(shù)位元組節(jié)走高的背后,也不乏令人憂慮的現(xiàn)象。
以研究電影理論、中國電影史為專業(yè)特長的北京大學(xué)教授戴錦華認(rèn)為,以國產(chǎn)大片為代表的中國電影,其體征已經(jīng)暴露出一些亟須予以診治的病癥。
正視問題,才能及時解決問題,才能更好地前行。
解放周末:戴教授,我想先請教您一個問題:有人說,從2002年的《英雄》開始,中國電影進(jìn)入了“大巨片時代”、“復(fù)興的時代”,對此您怎么看?
戴錦華:這種“大巨片時代”、“復(fù)興的時代”的提法,根據(jù)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