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哲學范文10篇
時間:2024-03-09 14:14:48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儒家哲學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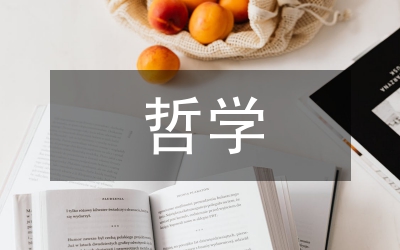
儒家哲學多重含義分析
摘要:在儒家哲學中,“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而從先秦儒家三大代表“孔、孟、荀”對于“天”內涵的理解看,可以說是一個非完全哲學不斷向著完全哲學轉變的全過程。文章主要以先秦三大代表對“天”的理解,來詮釋儒家哲學中“天”的多重含義。
關鍵詞:儒家;哲學;“天”;多重含義
在中國古代哲學中,“天”是最早出現的哲學概念,尤其在儒家哲學中更為顯著。可以說,先秦時期中國人對于“天”的理解,是一個非完全哲學向完全哲學轉變的過程。這一點,從先秦儒家三大代表對于“天”的不同理解,就可以詮釋。
一、中國儒家哲學中“天”的哲學解釋
對于中國儒家哲學中的“天”,一般有幾種解釋,包括物質之天、意志之天(也稱為主宰之天)、命運之天、義理之天(道德之天)、自然之天等。唯心主義所理解的“天”通常為意志之天或是義理之天,而唯物主義所理解的“天”一般為自然之天,這些觀點是人們對于客觀世界以及人類社會生活的不同解釋。自然之天也就是古人眼中的星辰、日月、四季、風雨等自然現象,屬于天之運行范疇,當屬物質之天;命運之天指的是某個團體或個人的運氣,通常被認為是天命,也就是天的命令所導致,歸為主宰之天。唯物主義者一般認為社會上的道德法則,是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產生的,并非來自蒼天;而唯心主義者則會把道德法理解為天意,認為是受到上天的指使而為之,被歸入主宰之天的范疇。古人對于主宰之天猶如宗教信仰般的崇拜,所以主宰之天又可以稱之為宗教之天,它與自然之天完全對立。被認為是儒家哲學中“天”的兩重內涵。馮友蘭先生曾在研究中將孔孟思想歸入了唯心主義,將荀子思想歸入唯物主義,并認為孔孟思想中的“天”為宗教之天,而荀子思想中的“天”為自然之天。[1]1.自然之天的哲學詮釋在《論語?易》中,孔子對子貢提出的“夫子何以老而好”的疑惑進行了解釋,并闡述了天道與地道、人道與四季的變化規律,提出天、地與人是相對的,天即為物質之天。同時,孔子還說“天言何哉,四行時焉,百物生焉”也就是說,自然界中的“天”是亙古不變,并且有一定的運行秩序與運動規律。而孟子在《離婁下》中,也對自然之天的內涵進行了詮釋,并說道“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茍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簡言之,天之高,星辰之遠,若要尋求他們運行的本原,千年的日至都能坐而得知。《荀子?天論》中關于“天”的詮釋則較繁復,在自然之天中,其認為“天”的內涵為布列于天空的恒星,以及太陽月亮的交替照耀,四季輪流控制著節氣,陰陽二氣催生的萬物生長等。(“列星隨旋,日月遞照,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人和天相對,人職和天職相對。天地間的變化,有內在的自然規律,與人的意志無關。儒家三大代表人物孔孟荀在自然之天的哲學范疇中都認為“天”為自然界,雖然自然界中的萬事萬物都變幻莫測,但依舊遵循一定的運行規律,且這種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不會被人們的認識、意志所轉移。[2]且在人類社會在生產實踐中,需要遵循這種客觀的規律,才能在遇到問題時有效的趨利避害,否則將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2.主宰之天的哲學詮釋主宰之天這種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天”,一般認為源于殷周之際,是殷人“上帝”觀念的形成,以及周人對殷人宗教思想進行改造的產物。而孔子主宰之天,在某一程度而言,是對前者的繼承。《論語?子罕》中提到,在孔子被匡人圍困時說:周文死后,周國的禮樂文化豈不是都體現在我身上了?上天要是想要消除這種文化,那我就無法再掌握這種文化了,如果上天不消除這種文化,那匡人又能夠拿我怎么樣呢?這里,“主宰之天”的意義已經十分明顯了。孟子的主宰之天,則更側重于站在民眾的立場上,認為宇宙萬物皆為天生。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講道“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也就是說,上天降生了民眾,再幫他們降生了君王和師表,而君王與師表的職責,就是幫助上天來愛護民眾百姓的。這種關于“天”的思想,是以政治文化為基礎,對上天神圣性的論證。在《孟子?離委下》中他闡述了“天”是社會制度的設計者,也是君王更替的決定者。并認為“天視”的本質其實是“民視”,而“天聽”的本意則是“民聽”。荀子與孔孟思想也有很多互通之處,其“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認為天會懲治惡者,也會給善者福報。在《天論》中荀子提到,人類社會的亂象與治理,與主宰之天有關,與自然之天無關。在《宕坐》中,荀子認為上天并不會偏袒“曾參、閔子騫、孝己”這類人而拋棄眾人,他們遵循了孝道且成就了孝子的名聲,并且竭力奉行禮儀,所以才受袒護。正是由于上天的公正性,所以才有了主宰之義。3.義理之天的哲學詮釋義理之天是儒家哲學中一貫的觀點,無論是孔孟荀,還是后面的董仲舒都對義理之天有極高的認同。唐君毅曾對孔子評價道:孔子用仁道重新建構了“天道”,所以才讓“天道”呈現出生命力。這里,孔子立人道來承天道,讓很多人道觀點的存在有了合理性,并受到世人的認可。在《論語?述而》中孔子說“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他認為自己懷仁行德,有上天護佑,壞人是對自己無可奈何的。“仁者無畏”是孔子要表達的觀點,同時也是義理之天所在。而孟子則在孔子的基礎上提出“天爵”的觀點,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有講“這世上有上天賜予的爵位,有俗世認可的爵位。仁義忠信,好善不疲,這是上天賜予的爵位;公卿大夫,這是俗世認可的爵位”(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這里的“天爵”是講人之所以會成為人,是因為人的心源自天心,而人性則源于天性,因為義理的存在,才讓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根本,也就是“盡心-知性-知天”這一思維模式。而與孔子不同的是,孟子對儒家思想所存在的合理性有一定的自覺論證。[3]并認為天道彰顯在人心的時候,又體現在人上,成為人性,并且“天”是具有道德屬性的一個精神實體,是天賦有至。在《離妻章句上》中,孟子還將“誠”視為至高無上的倫理道德,并將其說成是“天”的化身,認為“誠”是上天的準則;而追求誠,是為人的準則。荀子在義理之天中很多觀點與孟子不謀而合,并且都在德化之天中,有邏輯性的延展。
二、儒家三大代表對“天”的含義的理解
儒家哲學研究論文
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中外學者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國是一個缺少邏輯思維的民族,他們在這里所說的“邏輯思維”主要指的是形式邏輯。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的統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邏輯而沒有辯證邏輯的思維,也不可能只存在著辯證邏輯而沒有形式邏輯的思維。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形式邏輯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國缺少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的演繹法則。三段論的演繹法是一種最樸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無論在《易經》還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種方法的應用。如《易經》根據觀物取象原則認為凡是陽剛的事物都可用一長橫“一”符號表示。凡是陰柔事物都用兩短橫“--”符號表示,太陽是陽剛的事物,所以用符號“一”表示,月亮是陰柔的事物,所以用兩短橫符號“--”表示,此處便用歸納結論作演繹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經》的判卦方式雖然充滿著矛盾法則,但都不離演繹和歸納的思維法則。
章太炎認為《墨經》充滿著“三段論”,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適舉《墨子》一書中“狗也,犬也,殺狗非殺犬也”、“盜,人也,愛盜,非愛人,……殺盜非殺人也”等判斷句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說法①但是,胡適不懂得《墨經》中包含著矛盾的邏輯已超越了形式主義的不包含矛盾的邏輯,是一種比形式邏輯更高級的邏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墨子》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不包含矛盾的邏輯。不少學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邏輯的應用上,比亞里士多德毫不遜色,如張靜虛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組判斷為例指出《墨子》一書中確鑿無誤地運用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邏輯。②
近代以來,人們總是把形式邏輯看得十分深奧,當然,形式邏輯的系統化是始自希臘哲學中經阿拉伯學者傳下來的一項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比較之下,中國哲學中的形式邏輯理論體系不完備。但是,每個人的思維都自覺地不自覺地使用著形式邏輯,恩格斯說過,形式邏輯的思維甚至在動物那里都有:普通邏輯(形式邏輯)所承認的一切研究手段對人和高等動物是完全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辯證法思維——正因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對于較高發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晚得多,在現代哲學中才達到。”③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形式邏輯是思維的低級階段,辯證法是思維的高級階段,創造了這種高級思維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臘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卻首先把它歸功于“佛教徒”的發明,——這是發人尋味的。
眾所周知,印度佛學傳到中國來的邏輯學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學”,而“因明學”所闡明的實為一種形式邏輯。應該說,佛教邏輯中已經包含著一些辯證思維的因素,但佛學辯證法主要生長和發育在中國,宋明新儒學的辯證法內在地包容了儒釋道三家辯證學說的精髓,其中有華嚴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辯證法、道家關于矛盾及其轉化的辯證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當英國對印度實行殖民統治時,佛教在印度早已絕滅幾個世紀了。恩格斯的時代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家,當時歐洲人所接觸的佛教資料有許多來自中國,如德國詩人海涅在法國大革命的感召下寫道:“當革命的波濤在巴黎,在這個人類的大洋中洶涌沸騰的時候,那時萊因河那邊底德國人的心臟也吼動著了。……他們站在中國制造的佛像之下,這佛像對著全無感覺的瓷器、茶器、咖啡壺和任何的東西,都像無所不知似地點著頭。”④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壺都是從中國傳來的,恩格斯所說的那些發明了辯證邏輯的“佛教徒”是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的泛稱,實際上就是指的中國人。這無疑在說:中國是辯證邏輯(辯證法)的發源地。
馬克思的辯證法來自黑格爾哲學的“合理內核”,但是,它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有著本質差異,即把黑格爾“頭足倒置”的體系又顛倒了過來,從而把辯證法與唯物論相結合,所以列寧指出,辯證法也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邏輯學。⑤有趣的是:黑格爾正是否定了中國哲學中具有唯物主義趨向的“實在”論,而悄悄吸取了東方哲學的辯證法。這種被黑格爾顛倒了的哲學在馬克思主義那里被再顛倒,那就是在唯物的實在論基礎上辯證的思維和辯證的認識論。這至少在表面上完全是對儒學辯證法的“復歸”。
儒家哲學的辯證法有如下特點:
儒家哲學的重建綜述
一、前言
儒家哲學的重建,是每一個時代儒學發展的基本課題。當代儒者遭逢西方現代文化(尤其在科學、民主、經濟方面)的強力沖擊,已經就這個課題努力了許久。其中,由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張君勱等人所開辟,①再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予以轉化、升進,先在港臺地區流布開展,然后逐漸受到全球漢語學圈和西方學界的注意,向來被稱作“當代新儒家”的一派,可說是一個特別集中而凸顯的例子。“當代新儒家”,這稱號隨順“(宋明)新儒家”一詞而來。當代新儒家以先秦孔孟思想為第一期儒學,以宋明理學為真正繼承先秦孔孟思想而來的第二期儒學,然后又以它自身為真正繼承孔孟思想、宋明理學而來的第三期儒學。它對荀子思想的看法,借用牟宗三[1]204,215的話來說便是“荀子之學不可不予以疏導而貫之于孔孟”、“荀子之廣度必轉而系屬于孔孟之深度,斯可矣。”也就是說,荀子思想在本原上有所不足,因此不具有獨立的價值,必須安置在孔孟思想的框架里才有價值可言。總之,向來所謂的“當代新儒家”學派走的是孟學——宋明理學的一路,可以看作一個旗幟鮮明的“當代新孟學”;從熊、馬、梁等人開始至今,它師生相傳,逐漸開展;除了出版論著,還創辦刊物、舉辦學術會議;是當代儒學圈最活躍最有創造力的一個學術社群。雖然它對社會的實質影響有限,但它向來是外界對當代儒學所認知的一個標桿與代表。相較之下,當代儒學圈里荀學一路的發展就顯得低迷、沉寂了。多年來,在港臺地區,表面上關于荀子思想的研究論著不少,但它們多半是基于孟學立場所作的詮釋與批評,只能看作廣義的孟學研究的一環。此外,雖然也有許多學者從現代學術與科技的眼光來推崇荀子《正名》、《天論》中的思想,但這種推崇跟儒學核心價值關系不大,對荀子思想地位的提升沒有根本的作用。前輩學者中,陳大齊[2-3]似乎是比較肯定、看重荀學的人。但他在《荀子學說》中也只是平實地從正面詮論荀子思想,遠不如他在《孔子學說》中對孔子思想的贊嘆有加和推崇備至。不過,或許因為當代新儒家的發展逐漸出現困境與瓶頸,也或許因為現實人生、現實社會無形的召喚,晚近臺灣地區一個跳出當代新儒家理路、重新詮釋荀學傳統的新動向已經悄悄開始了。2003年12月,《“國立”政治大學哲學學報》推出一期“國際荀子研究專號”。2006年2月,云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舉辦一個“荀子研究的回顧與開創”國際學術會議。①以上兩件事可說是這個新動向稍稍明顯的代表。除此之外,有關荀學的論著、課程、學位論文、學術活動也都有逐漸增加的跡象。②從我的感受來說,一個“當代新荀學”的運動似乎正在試探、發展中。③大陸的儒學發展在1949年以后中斷了30多年。不過等80年代政治束縛放寬后,港臺當代新儒家的思想便陸續傳入。1986年起,由方克立所主持的“現代新儒學思潮研究”大型計劃集合了數十位中青年學者,大規模編印了《現代新儒家學案》、《現代新儒學輯要》、《現代新儒學研究叢書》等書。逐漸地,當代新儒家思想也在大陸流傳開來;一些學者甚至欣賞、認同、歸宗港臺新儒家,自稱“大陸新儒家”了。[4]148-149,245然而,或許同樣因著現實人生、現實社會(包括社會主義思維背景)的召喚,大陸的儒學復興也逐漸出現了不同的聲音。方克立[4]253-255曾撰文論及“有異于港臺新儒家的‘另一派’大陸新儒家會崛起嗎?”;宋志明[5]403則說,一個“發端于現代新儒家,但不限于現代新儒家”的“現代新儒學思潮”已經來到;而干春松[6]235更具體指出,“大陸新儒學”關注儒學與制度更甚于道德理想主義,具有明顯的實踐性傾向。就我接觸所及來說,所謂有別于港臺新儒家的“大陸新儒家(學)”,在幾種不同的可能性(馬列主義新儒學、社會主義新儒學等)中,便有屬于或接近荀學的一路。例如旅居美國的李澤厚[7]131,140,他批評當代新儒家的“儒學三期說”片面地以心性——道德理論來概括儒學,又用偏見抹殺了荀學和漢代儒學;他主張儒學應分四期:孔、孟、荀為第一期,漢儒為第二期,宋明理學為第三期,現在或未來為第四期。他解釋道[7]154-155﹐第四期儒學的主題是“情欲論”﹐它是“人類學歷史本體論”的全面展開;以工具本體和心理本體為根本基礎,重視個體生存的獨特性,闡釋自由直觀、自由意志和自由享受,重新建構“內圣外王之道”;以充滿情感的“天地國親師”的宗教性道德,范導自由主義理性原則的社會性道德,來承續中國“實用理性”、“樂感文化”、“一個世界”、“度的藝術”的悠久傳統。顯然,這樣的四期說遠于孟學,而頗接近荀學的路線。④又如目前擔任《中國儒學》主編的王中江[8]72,91,107,他肯定地指出,荀子除了有功于儒家學統外,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醇正的儒家以及儒家道統堅定不二的傳承者和復興者。這樣的觀點也表現了一定的荀學立場。必須澄清的是,曾在1989年發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的蔣慶,他在晚近也表彰荀學——公羊學,大力提倡“政治儒學”。不過他[9]30-33,550是以孟子一系的心性學作為荀學一系公羊學、政治禮法制度等之根本,因此,嚴格地說,他的“政治儒學”基本上屬于牟宗三“荀子之廣度必轉而系屬于孔孟之深度”的立場,而不是荀學一路。總之,從兩岸當代新儒家(學)發展的最新趨勢來看,向來低迷、沉寂的荀學一路已經逐漸覺醒,一個屬于荀學立場或者說“當代新荀學進路”的“當代新儒家”似乎即將出現了。
二、本文所謂“當代新荀學進路”
如上所述,一個“當代新荀學”或者說一個“當代新荀學進路的當代新儒家哲學”正在兩岸儒學圈里嘗試、發展中;本文便是基于這樣的背景與契機而作。這一節先說明本文所謂“當代新荀學進路”的具體內涵。
(一)重新詮釋荀子哲學,彰明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與正當性
一般根據荀子的意謂認定荀子哲學無非是“天人相分”、“性惡”、“禮義外于人性”,從而論斷荀子哲學中“禮義”之價值無有根源,因而所謂“強學禮義”與“化性起偽”都得不到保障。其實上述理解并未觸及荀子哲學的全面和整體。今天我們若采取傅偉勛所謂“創造的詮釋學”的視野,兼顧荀子的意謂、蘊謂兩層,并松解、開放他對某些重要概念(如天、人、心、性等)界定、使用的脈絡、范圍,便可以重新建構一個具有普遍意義、合乎華人文化心理傾向的荀子哲學。它跟荀子自己表述的理路在理論上等值,但更適合于后代人們的辨識、認取、比較,可以稱作“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簡單地說:
儒家哲學邏輯研究論文
黑格爾說,陰陽觀念是人智慧的“全部”,這里指的正是中國中的陰陽辯證法。若對中國二、三千來的辯證法史作一次總觀,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一門思維發達、條理清晰和博大精深的學說體系,相比之下,我們把黑格爾說成是一名“站在巨人肩上的小孩”并不為過。我們今天所說的唯物辯證法或“科學的辯證法”實際上直接改造于黑格爾,其與儒學辯證法的關系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意味著“科學的辯證法”在更高的基點上改造了黑格爾,因而也就內在地包含和超越了儒學的陰陽辯證法。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利用辯證法才揭示了隱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從而發現了剩余價值及其,并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辯證法》中指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客觀辯證法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而已。很簡單的例子莫過于一塊磁鐵,截然對立的兩極就存在于同一個物體之中,無論你怎么將它分解,原來的兩極仍然不變。然而,事實上正是中國人在全人類首先認識到了磁鐵的這種特性才發明了指南針,中國人對大自然中“到處盛行的”客觀的陰陽關系具有最敏銳的經驗觀察能力,客觀辯證法最早反映到中國人的頭腦中來的,從而形成了中國哲學中的邏輯——這就是中國人超越形式邏輯的根深蒂固的辯證思維邏輯。
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中外學者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國是一個缺少邏輯思維的民族,他們在這里所說的“邏輯思維”主要指的是形式邏輯。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的統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邏輯而沒有辯證邏輯的思維,也不可能只存在著辯證邏輯而沒有形式邏輯的思維。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形式邏輯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國缺少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的演繹法則。三段論的演繹法是一種最樸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無論在《易經》還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種的。如《易經》根據觀物取象原則認為凡是陽剛的事物都可用一長橫“一”符號表示。凡是陰柔事物都用兩短橫“--”符號表示,太陽是陽剛的事物,所以用符號“一”表示,月亮是陰柔的事物,所以用兩短橫符號“--”表示,此處便用歸納結論作演繹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經》的判卦方式雖然充滿著矛盾法則,但都不離演繹和歸納的思維法則。
章太炎認為《墨經》充滿著“三段論”,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適舉《墨子》一書中“狗也,犬也,殺狗非殺犬也”、“盜,人也,愛盜,非愛人,……殺盜非殺人也”等判斷句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說法①但是,胡適不懂得《墨經》中包含著矛盾的邏輯已超越了形式主義的不包含矛盾的邏輯,是一種比形式邏輯更高級的邏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墨子》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不包含矛盾的邏輯。不少學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邏輯的應用上,比亞里士多德毫不遜色,如張靜虛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組判斷為例指出《墨子》一書中確鑿無誤地運用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邏輯。②
近代以來,人們總是把形式邏輯看得十分深奧,當然,形式邏輯的系統化是始自希臘哲學中經阿拉伯學者傳下來的一項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比較之下,中國哲學中的形式邏輯體系不完備。但是,每個人的思維都自覺地不自覺地使用著形式邏輯,恩格斯說過,形式邏輯的思維甚至在動物那里都有:普通邏輯(形式邏輯)所承認的一切手段對人和高等動物是完全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辯證法思維——正因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對于較高發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晚得多,在哲學中才達到。”③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形式邏輯是思維的低級階段,辯證法是思維的高級階段,創造了這種高級思維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臘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卻首先把它歸功于“佛教徒”的發明,——這是發人尋味的。
眾所周知,印度佛學傳到中國來的邏輯學的代表性成果是“因明學”,而“因明學”所闡明的實為一種形式邏輯。應該說,佛教邏輯中已經包含著一些辯證思維的因素,但佛學辯證法主要生長和發育在中國,宋明新儒學的辯證法內在地包容了儒釋道三家辯證學說的精髓,其中有華嚴宗的“共相和殊相”的辯證法、道家關于矛盾及其轉化的辯證法以及儒家的“正反合”的思想等等。在西方人的眼里,“佛教徒”并非特指印度人,當英國對印度實行殖民統治時,佛教在印度早已絕滅幾個世紀了。恩格斯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佛教國家,當時歐洲人所接觸的佛教資料有許多來自中國,如德國詩人海涅在法國大革命的感召下寫道:“當革命的波濤在巴黎,在這個人類的大洋中洶涌沸騰的時候,那時萊因河那邊底德國人的心臟也吼動著了。……他們站在中國制造的佛像之下,這佛像對著全無感覺的瓷器、茶器、咖啡壺和任何的東西,都像無所不知似地點著頭。”④這里的佛像和瓷器、茶器、咖啡壺都是從中國傳來的,恩格斯所說的那些發明了辯證邏輯的“佛教徒”是對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東方人的泛稱,實際上就是指的中國人。這無疑在說:中國是辯證邏輯(辯證法)的發源地。
深究儒家人生哲學之孔子人生哲學
人生哲學是個人對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有關人生目的、人生態度以及人生價值等方面的看法。它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人生安身立命的問題,涉及到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以及人面對自己的處境應當采取的態度,簡言之凡是探討一個人生存在天地之間根本做人之道的學問,都屬于人生哲學的范疇。孔子創立的人生哲學要求的是入世,倡導建功立業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最大限度地實現自我價值,其思想不僅在社會生活中是強大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政治、教育和社會風氣上也處于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中國社會的國民精神。
一、孔子之名:修養及發展的起點
孔子生在春秋末期大國爭霸的亂世,當時社會諸侯不安于位爭權奪利。他雖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但因其思想與現實不合而不被重用。一生生活貧賤顛沛流離,生在亂世又雪上加霜,中國常言的人生三大悲哀:幼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孔子都遇上了。他經歷了幼年喪父,青年喪母,中年喪妻,晚年喪子,一生的坎坷不幸他沒怨天尤人而把命運變成使命,沒有強調自己所遭受的苦難卻時時關心社會。孔子在其人生道路上戰勝了自己使自己不為苦痛所系,致力于謀求社會大眾的福利。他的經歷教誨了后世,其思想和智慧更是影響著一代又一代人,開啟了儒家文化的先河。
孔子在論及名分時指出:“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亂世的禮樂不興淵源于名不正,導致言不順事不成。孔子生逢的亂世始于人際關系的迷失,人際關系的失常則由于名不正,因此孔子提出了正名,以此作為化解人際關系危機的前提。所謂正名就是用周禮匡正已經發生變化的社會現實,使君臣父子各安其位遵守各自的名分不越位不辱禮。孔子重視禮視其為維護制度的手段并認為維護禮需要從正名入手。在那種名分已失天下大亂之時,“孔子懼,作春秋”,他所害怕的正是人際關系的沉淪社會的混亂及人心的敗壞。他雖然重視禮樂教化卻認為禮樂的根本在于仁德的修養,要正名得從個人的修養開始,于是提出了其道德哲學的核心概念——仁。
二、孔子之仁:人生哲學思想的核心
孔子將仁作為人格的核心視其為完全人格,只有達到這種境界的人才被稱為仁人。仁是個體的道德內在性是個體成圣的內在依據,所謂成圣是個體修養所達到的最高境界。仁的意義首先是獨善其身的君子;其次是兼濟天下的圣人,兩者的綜合就是仁人即內圣外王,此為儒家的理想人格。仁的內涵有以下解釋:其一仁者愛人。“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泛愛眾”愛一切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其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此為仁者愛人的道德規范。其三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們通過加強自我修養做到以禮為行事準則。其四“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家的五倫即“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孔子仁學思想的精妙在于將外在的傳統轉化為內在的道德倫理意識的自覺要求,從最基本的家庭入手講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使仁學植根于家庭倫理深入最基本的血親觀念之中。他們之間關系準則更突出的體現在孝悌、友仁和守信三個方面即人際關系中涉及的孝、仁、信。
儒家哲學邏輯辯證法特征透析論文
黑格爾說,陰陽觀念是中國人智慧的“全部科學”,這里指的正是中國哲學中的陰陽辯證法。若對中國二、三千來的辯證法發展史作一次總觀,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一門思維發達、條理清晰和博大精深的學說體系,相比之下,我們把黑格爾說成是一名“站在歷史巨人肩上的小孩”并不為過。我們今天所說的唯物辯證法或“科學的辯證法”實際上直接改造于黑格爾,其與儒學辯證法的關系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意味著“科學的辯證法”在更高的基點上改造了黑格爾,因而也就內在地包含和超越了儒學的陰陽辯證法。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利用辯證法才揭示了隱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從而發現了剩余價值及其規律,并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客觀辯證法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而已。
很簡單的例子莫過于一塊磁鐵,截然對立的兩極就存在于同一個物體之中,無論你怎么將它分解,原來的兩極仍然不變。然而,事實上正是中國人在全人類首先認識到了磁鐵的這種特性才發明了指南針,中國人對大自然中“到處盛行的”客觀的陰陽關系具有最敏銳的經驗觀察能力,客觀辯證法最早反映到中國人的頭腦中來的,從而形成了中國哲學中的邏輯——這就是中國人超越形式邏輯的根深蒂固的辯證思維邏輯。
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中外學者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國是一個缺少邏輯思維的民族,他們在這里所說的“邏輯思維”主要指的是形式邏輯。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的統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邏輯而沒有辯證邏輯的思維,也不可能只存在著辯證邏輯而沒有形式邏輯的思維。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形式邏輯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國缺少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的演繹法則。三段論的演繹法是一種最樸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無論在《易經》還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種方法的應用。如《易經》根據觀物取象原則認為凡是陽剛的事物都可用一長橫“一”符號表示。凡是陰柔事物都用兩短橫“--”符號表示,太陽是陽剛的事物,所以用符號“一”表示,月亮是陰柔的事物,所以用兩短橫符號“--”表示,此處便用歸納結論作演繹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經》的判卦方式雖然充滿著矛盾法則,但都不離演繹和歸納的思維法則。
章太炎認為《墨經》充滿著“三段論”,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適舉《墨子》一書中“狗也,犬也,殺狗非殺犬也”、“盜,人也,愛盜,非愛人,殺盜非殺人也”等判斷句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說法。但是,胡適不懂得《墨經》中包含著矛盾的邏輯已超越了形式主義的不包含矛盾的邏輯,是一種比形式邏輯更高級的邏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墨子》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不包含矛盾的邏輯。不少學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邏輯的應用上,比亞里士多德毫不遜色,如張靜虛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組判斷為例指出《墨子》一書中確鑿無誤地運用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邏輯。
近代以來,人們總是把形式邏輯看得十分深奧,當然,形式邏輯的系統化是始自希臘哲學中經阿拉伯學者傳下來的一項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比較之下,中國哲學中的形式邏輯理論體系不完備。但是,每個人的思維都自覺地不自覺地使用著形式邏輯,恩格斯說過,形式邏輯的思維甚至在動物那里都有:普通邏輯(形式邏輯)所承認的一切研究手段對人和高等動物是完全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辯證法思維——正因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對于較高發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晚得多,在現代哲學中才達到。”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形式邏輯是思維的低級階段,辯證法是思維的高級階段,創造了這種高級思維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臘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卻首先把它歸功于“佛教徒”的發明,——這是發人尋味的。
儒家哲學邏輯辯證法特征研究論文
摘要:黑格爾說,陰陽觀念是中國人智慧的“全部科學”,這里指的正是中國哲學中的陰陽辯證法。若對中國二、三千來的辯證法發展史作一次總觀,就不難發現中國的辯證法思想也是一門思維發達、條理清晰和博大精深的學說體系,相比之下,我們把黑格爾說成是一名“站在歷史巨人肩上的小孩”并不為過。我們今天所說的唯物辯證法或“科學的辯證法”實際上直接改造于黑格爾,其與儒學辯證法的關系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這意味著“科學的辯證法”在更高的基點上改造了黑格爾,因而也就內在地包含和超越了儒學的陰陽辯證法。
眾所周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正是利用辯證法才揭示了隱藏在商品中的矛盾,從而發現了剩余價值及其規律,并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矛盾。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指出,所謂主觀辯證法即辯證的思維,不過是客觀辯證法在人們思維中的反映而已。
很簡單的例子莫過于一塊磁鐵,截然對立的兩極就存在于同一個物體之中,無論你怎么將它分解,原來的兩極仍然不變。然而,事實上正是中國人在全人類首先認識到了磁鐵的這種特性才發明了指南針,中國人對大自然中“到處盛行的”客觀的陰陽關系具有最敏銳的經驗觀察能力,客觀辯證法最早反映到中國人的頭腦中來的,從而形成了中國哲學中的邏輯——這就是中國人超越形式邏輯的根深蒂固的辯證思維邏輯。
包括愛因斯坦在內的一些中外學者不厭其煩地指出,中國是一個缺少邏輯思維的民族,他們在這里所說的“邏輯思維”主要指的是形式邏輯。然而,正像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形式邏輯和辯證法本來就是一對矛盾的兩個方面,是對立的統一,不可能只存在形式邏輯而沒有辯證邏輯的思維,也不可能只存在著辯證邏輯而沒有形式邏輯的思維。那種認為中國沒有形式邏輯的主要理由在于中國缺少亞里士多德的“三段論”的演繹法則。三段論的演繹法是一種最樸素、最基本的推理形式,無論在《易經》還是在墨家的著作中我們都不難找到這種方法的應用。如《易經》根據觀物取象原則認為凡是陽剛的事物都可用一長橫“一”符號表示。凡是陰柔事物都用兩短橫“--”符號表示,太陽是陽剛的事物,所以用符號“一”表示,月亮是陰柔的事物,所以用兩短橫符號“--”表示,此處便用歸納結論作演繹推理的前提。整部《易經》的判卦方式雖然充滿著矛盾法則,但都不離演繹和歸納的思維法則。
章太炎認為《墨經》充滿著“三段論”,大故就是大前提,小故就是小前提,胡適舉《墨子》一書中“狗也,犬也,殺狗非殺犬也”、“盜,人也,愛盜,非愛人,殺盜非殺人也”等判斷句為例否定了章太炎的說法。但是,胡適不懂得《墨經》中包含著矛盾的邏輯已超越了形式主義的不包含矛盾的邏輯,是一種比形式邏輯更高級的邏輯。盡管如此,我們不能就此否定《墨子》無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種不包含矛盾的邏輯。不少學者指出,先秦墨家在形式邏輯的應用上,比亞里士多德毫不遜色,如張靜虛就以墨子《耕柱》篇中的一組判斷為例指出《墨子》一書中確鑿無誤地運用了三段論的演繹推理邏輯。
近代以來,人們總是把形式邏輯看得十分深奧,當然,形式邏輯的系統化是始自希臘哲學中經阿拉伯學者傳下來的一項寶貴的人類文化遺產,比較之下,中國哲學中的形式邏輯理論體系不完備。但是,每個人的思維都自覺地不自覺地使用著形式邏輯,恩格斯說過,形式邏輯的思維甚至在動物那里都有:普通邏輯(形式邏輯)所承認的一切研究手段對人和高等動物是完全一樣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己。“相反地,辯證法思維——正因為它是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于人才是可能的,并且只對于較高發展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晚得多,在現代哲學中才達到。”恩格斯在這里明確指出形式邏輯是思維的低級階段,辯證法是思維的高級階段,創造了這種高級思維形式的巨大成就有希臘人的一份,但恩格斯卻首先把它歸功于“佛教徒”的發明,——這是發人尋味的。
儒家哲學人性論思考論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孟子的“性善說”;荀子的“性惡說”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古今中外的哲學史上,在人的本質屬性這一問題上的爭論、“人性論”是舊哲學探索人的共同本質屬性的一種學說、在戰國時期,孟子第一個提出了系統的人性善的理論、人要不斷地膨脹自己的心,才能認識自己的本性、人性之所以是善的,是因為人生來就具有天賦的“善端”、孟子的性善論是其仁政學說的思想基礎、荀子是中國古代哲學史上,第一個明確提出了“性惡論”的人性論思想的哲學家、人生而好利,有疾惡,好生色、人之行善,師法教化而成、禮義不在人性之中,不出自人性、荀子批評了孟子的先天道德論、荀子把人的本性說成是先天就是惡的,也是錯誤的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在我國古代哲學家中,就有性善說、性惡說、性有善有惡說、性無善無惡說等等理論。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最具代表性,這兩種學說均對后期儒家哲學的人性論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對此做一個粗淺的探討。
關鍵詞:人性論;孟子;性善說;荀子;性惡說
古今中外的哲學史上,在人的本質屬性這一問題上的爭論,充分顯示出人類對自身本質的高度關注。“人性論”是舊哲學探索人的共同本質屬性的一種學說。在我國古代哲學家中,就有性善說、性惡說、性有善有惡說、性無善無惡說等。其中以孟子的“性善說”和荀子的“性惡說”最具代表性,這兩種學說均對后期儒家哲學的人性論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下采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兩種中國古代的哲學思想做一個評述。
1孟子的“性善說”
在戰國時期,孟子第一個提出了系統的人性善的理論,性善論是孟子整個學說的理論基礎。在孟子看來,人和禽獸是有本質區別的,這種區別的主要表現是人性和禽獸之性不同,人的生活高于禽獸的生活,因為人有自覺的道德觀念。他指出,人的本性和禽獸本來是不同的,但由于有的人不知道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而把本心放了,人性丟了,結果變得和禽獸差不多了。因此,孟子十分強調“立心”、“養心”、“養性”、只有這樣,才能成為善人。
儒家人本哲學醫學價值論文
1儒家人本哲學的產生和形成
儒家人本哲學的發展和確立與我國古代人本思想的發展是密切相關的。商朝以前,統治者為了加強對人們思想的控制,強化王權統治,在意識形態領域對鬼神大加尊崇[1]。《禮記•表記》中也有說:“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禮。”到了西周時期,人們對鬼神是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并把人們的行為和意愿看做是天、神意志的代表,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2],“民之所欲,天必從之”[3]。進入春秋以后,“重人輕神”的思想逐步形成。春秋中期已出現“以人為本”的思想,由當時輔佐齊桓公稱霸的宰相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4]”,道出了人民在國家穩固、安危中的根本地位。之后到了春秋末期,儒學創始人孔子在前人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和重視人在宇宙的中心地位和在社會的主體地位,并結合自己的學說,創立了人本主義哲學。儒家人本哲學重視對人性的認識,認為人不僅具有生物屬性,還具有社會屬性和道德屬性。儒家人本哲學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愛人。要做到“仁”,就要做到以下5點:恭、寬、信、敏、惠。具體來說,就是推己及人,也就是遵循“忠恕之道”。“修齊治平”在儒家人本哲學中體現了“修己安人”的待人之道。
2儒家人本哲學的現代意義和價值
2.1儒家人本哲學的人性觀與現代人類醫學
人具有運動性語言中樞和知覺性語言中樞的特殊結構,人是以語言擁有世界的動物,人們通過語言的交流,可以引發情感、開放內心世界;同時,人也是唯一可以被語言符號傷害以及患語言疾病的動物,而且,人還是唯一可以通過語言符號醫治的動物[8]。人的疾病與健康,不僅僅涉及到生理、心理或社會某一個單一層面,而是他們的整合,且三者密切聯系,相互影響。根據現代衛生組織對健康的定義,只有當三者是一種和諧統一的良好狀態時才是現代意義上的健康。而某一方面的疾患都會牽涉和影響到其他方面,如心理或生理疾病所致社會功能損害和缺失,還有社會關系引發的心理和生理問題等。所以,與動物醫學不同,人類醫學除了自然科學性外,還具有人文性質。醫生在給患者看病時,不僅要看到患者的生理層面,而且要看到其社會層面和心理層面。隨著現代社會和醫學的發展,人們已逐漸認識到這一點,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的提出就是很好的例證。
2.2“仁”的人本哲學與現代醫學人文關懷
解讀人性與儒家政治哲學
從儒家倫理政治理論建構的必然需要著眼,在人性假設上,善應當是一個共同認可的思維焦點。不承認善作為人性的預設,勢必不能進一步陳述倫理政治的德治之術。但以孔孟荀董四人的言述來看,盡管一方面可以以善通約、從而保證了倫理政治有可靠的人性基石:另一方面,四人撐開人性之善的格架之方式,卻有明顯不同,有直陳的(孟)、有曲表的(荀),也有不言而喻,而將關注力轉向一般秉賦之人向善可能性的(董)。但其一致之處是,善為其共同嘉許。因此,人性問題落到政治治理上面,倫理政治便在天佑價值之外,又獲得了人間保障。
一、以善通約:倫理政治的觀實起點是對人治的高度信賴
倫理政治理論建構中,早期階段的四位政治哲學家,對人性都表示關注。尤其是孟荀對人性的論述,更凸顯了人性論在其理論構造中的重要地位。但是,至少從理論表象看,他們的人性預設,有極大的差異。孔子較少言性,以致學生“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孫丑》),孟子道性善,荀子說性惡,董仲舒則對性的層次劃分表現出更大的興趣。僅就四人言性的特點而言,似乎其人性主張相差過大,實在難以說他們的人性論還有相當一致之處,還有為倫理政治提供可以相互打通關節的理論功用。表象之蒙蔽人,常誤導人下出表象化的判斷。其實,深入追究一下四人的人性論說就不難發現,善,構成為一個最大公倍數。向善的集結,以善的通約,在四人的言述中,可謂一個表面分歧之下的共同歸結、一致特性。
孔子對人性問題的關注程度較低。一部《論語》,僅有一句直接談性。而且也只是簡單地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論語·陽貨》)為此,有兩點需做確認,其一,孔子對人性問題的忽略,是一個合理的忽略。原因在于,他的關注焦點是怎樣用一個互補的架構,同時收拾人心秩序,整頓社會秩序。其二,孔子少言性,但并不等于對“仁者愛人”的人性依據懸擱不顧。從“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八字上推展開去,以孔于的基本主張進行進一步的解釋,是可以確定孔子的人性論趨善的思想傾向的。一方面,性與習對舉,證明性是先天獲得的,而不是后天習得的。而孔子所倡導的仁,恰可被視為對人之天賦秉性的一個抽象歸納。因為,仁者,“從人從仁,古文仁從千心”。(許慎:《說文解字》)可知仁是對共同的人的特點的一種概括,而這種共同特點,又因為具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性質,可知是一種人本有的特性,否則人無論怎么想具有,也不可能。其二,仁的解釋中間包含的先天性質,發子外,表現為“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可見,它是善的,而不包含惡的雜質。而對習得之不仁,人亦能根據仁而惡之。孔子的這一思想傾向,自然是他倫理政治的祈求所注定的。
孔子的人性言述,畢竟要經過一番推導,才能凸顯其底蘊。而孟子以“私淑孔子”領會得孔子精神,因而,以良心說性善,最直接而又最貼切地揭示了倫理政治的人性要求。在孟子思想中,性善既是言人性的起點,同時又是論政治的根據,并且還是向人的尊嚴回歸的據點。就前者而言,他以“不忍人之心”的普遍性為一個基本的設準,以善性四端內置于人心為倫理規范的原始型態,以對物之性與人之性的特質分辨為性善論提供有力的方法支持,從而,以救孺子的生命內在敬畏與同情,證得人性之善。就居中一點而論,“非由外爍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的良心善性,本是一種良知之智、良能之具,為人擴而充之,可成大丈夫:為君擴而充之,可成就仁政。而這種擴充,由于是救治人“放失”之心的必然選擇,也由于是人與禽獸之別的根本標志,更由于是“保四海”的充要條件,變成為一種勢不可擋的人性發展趨勢。也正是在孟子那里,對倫理政治內蘊效用的信心,達到了最頂點(“仁政無敵”)。由此明顯可見,人性善與倫理政治具有內在的親合關系,甚至是內在的一致關系。前存后在,前去后失。性善與不善,對倫理政治行與不行,至關緊要。
荀子從性惡處解人性,拒斥孟子的性善論。直接看上去,他對人性的理解與孟子迥然相異,而且,他對孟子的批評,更強化了這一印象。但是,荀子論政的起點、主要支持根據、最后的歸結點,卻仍然是一個善字。在他論政的起點上,圣人以化性起偽為目標,而“為”什么呢?為善。善畢竟還是社會政治生活、公共活動秩序的目的所在,為善畢竟還是太極在握者、德性先覺者追尋建構的唯一對象。而之所以“化性起偽”構成圣人圣君的天賦性職責,也是因為荀子對人的為善抱有充分的信心。最典型的論據,一是抽象人性論的,所謂“涂之人可以為禹”;(《荀子·性惡》)一是歷史哲學總結性的,所謂“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粱紂存則天下從而亂,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荀子·榮辱》)前者,一般性地提供了人向善而圣的可能性;后者,具體地分辨了人向善的條件性。但整體而言,荀子對善的期許,是溢于言表的。因而,落在做人治世的最后期望與最高祈求的為圣上面,荀子講的,還是一個“積善成德”的問題。這說明,倫理政治在理論上要能夠成立,一方面,離不開善;另一方面,善也在最大范圍內圈定了這類論說的倫理苑地。因為,缺乏善的支撐,其一,化政治人倫理不可能。這是由于人以惡相向,人有各以權力要求和利益分享為人生追求的惡性膨脹可能,崇高變成為一種受虐,從而從根本上消除掉人們的向善心。同時,化倫理人政治也不可能。這是由干人以惡相向,人在權力和利益的強烈驅使之下.會走向同類相殘、規范崩解、“群”性消夫的嚴重地步,再周密的強控也會失去約束能力,政治秩序隨人心秩序的紊亂而紊亂。其二,既無法解釋中國古史治亂原因,又無法構想消除混亂走向有序的政治圖景。這是由于倫理政治理論建構者都有一個“前見”,都毫不猶豫地確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