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任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4-14 17:53:15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政府信任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公眾視野下的政府信任研究論文
摘要:信任是社會(huì)秩序的基礎(chǔ)之一。隨著公共管理理論的發(fā)展,政府信任逐漸成為重要議題。政府信任是整個(gè)社會(huì)最大的信任,整個(gè)社會(huì)信任基于政府信任來推動(dòng)和發(fā)展政府的權(quán)力,必須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監(jiān)督與制約,以確保行政責(zé)任的忠實(shí)履行。如何認(rèn)識(shí)和化解中國(guó)政府信任問題,是當(dāng)前研究的重點(diǎn)。
關(guān)鍵詞:公共危機(jī);政府信任;誠(chéng)信
西方哲學(xué)家史里斯?博克曾指出,“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hù)的東西,因?yàn)樗拖窨諝夂退匆粯樱坏┦軗p,我們所居住的社會(huì)就會(huì)土崩瓦解”[1]。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強(qiáng)社會(huì)成員的凝聚力,降低社會(huì)運(yùn)行的成本,提高社會(huì)運(yùn)行的效率。
一、政府信任的理論闡釋
1.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基礎(chǔ)。民眾對(duì)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是任何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重要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是任何政體順利運(yùn)作的重要保障。當(dāng)政治權(quán)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眾相當(dāng)程度的信任時(shí),民眾就會(huì)相信權(quán)威當(dāng)局會(huì)了解其需要,能夠?yàn)槠渲\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無貪污腐敗之事。
2.促進(jì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良性運(yùn)轉(zhu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德基礎(chǔ)最重要的就是信譽(yù)或信任(張維迎,2001)。目前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還是政府主導(dǎo)型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公眾對(duì)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就有著較大的影響。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潤(rùn)滑劑,其運(yùn)作效果如何,與政府的誠(chéng)信直接相關(guān)。
政府信任問題分析論文
一、政府信任的理論闡釋
1.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基礎(chǔ)。民眾對(duì)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是任何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重要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是任何政體順利運(yùn)作的重要保障。當(dāng)政治權(quán)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眾相當(dāng)程度的信任時(shí),民眾就會(huì)相信權(quán)威當(dāng)局會(huì)了解其需要,能夠?yàn)槠渲\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無貪污腐敗之事。
2.促進(jì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良性運(yùn)轉(zhu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德基礎(chǔ)最重要的就是信譽(yù)或信任(張維迎,2001)。目前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還是政府主導(dǎo)型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公眾對(duì)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就有著較大的影響。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潤(rùn)滑劑,其運(yùn)作效果如何,與政府的誠(chéng)信直接相關(guān)。
3.降低行政過程的交易成本。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來看,信任的經(jīng)濟(jì)意義在于它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合作的雙方必須相互信任,否則達(dá)成合作協(xié)議及監(jiān)督合作協(xié)議實(shí)施的交易成本太高,合作行動(dòng)就難以發(fā)生。合作者之間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關(guān)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
二、中國(guó)政府信任問題的現(xiàn)狀
1.社會(huì)政策缺乏穩(wěn)定性與連續(xù)性。當(dāng)前中國(guó)個(gè)別地區(qū)的政策制定卻缺乏嚴(yán)肅性和連續(xù)性,導(dǎo)致現(xiàn)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陷入混亂的狀態(tài),減損既得利益者現(xiàn)有的合法利益,也對(duì)政策的目標(biāo)群體心理產(chǎn)生許多不良影響。
提升政府民眾信任支持論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府公信力的內(nèi)涵和變動(dòng)機(jī)制;當(dāng)前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在現(xiàn)有環(huán)境和條件下,如何提高我國(guó)政府的公信力進(jìn)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已是黨和政府及社會(huì)各界的廣泛共識(shí)、政府公信力,即政府獲得公眾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同政府能力、滿意度、動(dòng)員力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現(xiàn)代政府的公信力源于三個(gè)方面、我國(guó)各級(jí)政府的公信力整體上處于下降態(tài)勢(shì)、各級(jí)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樣的、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觀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政府公信力受眾多因素的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歷來受到中外政府的重視、嚴(yán)懲權(quán)力腐敗和克服官僚主義,加強(qiáng)廉政建設(shè)、建設(shè)服務(wù)性政府,努力提供足夠和優(yōu)質(zhì)的公共產(chǎn)品、加大力度推進(jìn)陽(yáng)光行政和依法行政等。具體請(qǐng)?jiān)斠姟?/p>
[摘要]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不能缺少民眾對(duì)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本文闡述了現(xiàn)代政府公信力的主要來源及其變動(dòng)機(jī)制,分析了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現(xiàn)狀和影響因素,并依據(jù)公信力的變動(dòng)機(jī)制。試圖指出在現(xiàn)有條件下快速、有效、可持續(xù)地提高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方式方法。
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已是黨和政府及社會(huì)各界的廣泛共識(shí)。建設(shè)的主體是廣大民眾。建設(shè)的主導(dǎo)力量應(yīng)該是各級(jí)政府,建設(shè)和諧社會(huì)是主導(dǎo)力量和主體力量相互信任、互為支持和共同配合的長(zhǎng)期過程。擁有一個(gè)得到廣大民眾信任與支持,擁有高度公信力的現(xiàn)代政府是建設(shè)和諧社會(huì)的關(guān)鍵。
一、政府公信力的內(nèi)涵和變動(dòng)機(jī)制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獲得公眾的信任度,是政府能力在公眾心中的綜合評(píng)價(jià)和公眾對(du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wù)的滿意度,也是政府對(duì)公眾的凝聚力和動(dòng)員力的重要決定因素。
政府公信力同政府能力、滿意度、動(dòng)員力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1)公信力不同于政府能力,公信力的評(píng)價(jià)主體是公眾,政府能力只有轉(zhuǎn)化為行為和行為結(jié)果才能獲得公眾的評(píng)判。一般而言,政府能力和公信力是正比關(guān)系。如果政府能力越強(qiáng),社會(huì)發(fā)展越快,人民物質(zhì)生活水平越高,那么政府公信力就越強(qiáng),但前提是政府能力必須主要去滿足廣大公眾的利益需要。(2)公信力與滿意度基本相同。正常社會(huì)狀況下,公信力來源于公眾對(duì)政府的滿意程度。滿意度越高對(duì)政府也就越信任:兩者稍有差別,滿意度更多是公眾對(duì)政府在物質(zhì)利益提供方面的感受,而公信力是對(duì)多種方面和長(zhǎng)遠(yuǎn)利益的綜合感知,特別是在強(qiáng)意識(shí)形態(tài)下的社會(huì),公信力可能更多地源于對(duì)敵人的仇恨和未來美好的夢(mèng)幻。(3)公信力與動(dòng)員力有區(qū)別,動(dòng)員力依賴于政府公信力,但政府公信力并不能完全轉(zhuǎn)化為動(dòng)員力,其中要受到多種中介因素的影響,比如社會(huì)組織程度、公民的政治心理等。公民社會(huì)發(fā)達(dá)、社會(huì)組織程度高及民眾參與意識(shí)強(qiáng),公信力在轉(zhuǎn)化為動(dòng)員力的過程中就流失得較少。
政府信任問題研究論文
摘要:信任是社會(huì)秩序的基礎(chǔ)之一。隨著公共管理理論的發(fā)展,政府信任逐漸成為重要議題。政府信任是整個(gè)社會(huì)最大的信任,整個(gè)社會(huì)信任基于政府信任來推動(dòng)和發(fā)展政府的權(quán)力,必須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監(jiān)督與制約,以確保行政責(zé)任的忠實(shí)履行。如何認(rèn)識(shí)和化解中國(guó)政府信任問題,是當(dāng)前研究的重點(diǎn)。
關(guān)鍵詞:公共危機(jī);政府信任;誠(chéng)信
西方哲學(xué)家史里斯·博克曾指出,“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hù)的東西,因?yàn)樗拖窨諝夂退匆粯樱坏┦軗p,我們所居住的社會(huì)就會(huì)土崩瓦解”[1]。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強(qiáng)社會(huì)成員的凝聚力,降低社會(huì)運(yùn)行的成本,提高社會(huì)運(yùn)行的效率。
一、政府信任的理論闡釋
1.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基礎(chǔ)。民眾對(duì)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是任何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重要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是任何政體順利運(yùn)作的重要保障。當(dāng)政治權(quán)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眾相當(dāng)程度的信任時(shí),民眾就會(huì)相信權(quán)威當(dāng)局會(huì)了解其需要,能夠?yàn)槠渲\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無貪污腐敗之事。
2.促進(jì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良性運(yùn)轉(zhu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德基礎(chǔ)最重要的就是信譽(yù)或信任(張維迎,2001)。目前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還是政府主導(dǎo)型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公眾對(duì)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就有著較大的影響。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潤(rùn)滑劑,其運(yùn)作效果如何,與政府的誠(chéng)信直接相關(guān)。
現(xiàn)有條件提高民眾對(duì)政府信任力論文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政府公信力的內(nèi)涵和變動(dòng)機(jī)制;當(dāng)前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狀況及影響因素;在現(xiàn)有環(huán)境和條件下,如何提高我國(guó)政府的公信力進(jìn)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已是黨和政府及社會(huì)各界的廣泛共識(shí)、政府公信力,即政府獲得公眾的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同政府能力、滿意度、動(dòng)員力既有聯(lián)系又有區(qū)別、公信力三個(gè)方面之間的關(guān)系是相依存互促進(jìn)的、國(guó)各級(jí)政府的公信力整體上處于下降態(tài)勢(shì)、各級(jí)政府的公信力水平是不一樣的、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下降有其宏觀的社會(huì)大環(huán)境、政府公信力受眾多因素的影響、政府的公信力歷來受到中外政府的重視、嚴(yán)懲權(quán)力腐敗和克服官僚主義,加強(qiáng)廉政建設(shè)、建設(shè)服務(wù)性政府,努力提供足夠和優(yōu)質(zhì)的公共產(chǎn)品,滿足人民生活和發(fā)展需要,提高政府行政績(jī)效公信力、加大力度推進(jìn)陽(yáng)光行政和依法行政、穩(wěn)步推進(jìn)人大制度的規(guī)范和完善等,具體請(qǐng)?jiān)斠姟?/p>
摘要: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不能缺少民眾對(duì)政府的信任和支持。本文闡述了現(xiàn)代政府公信力的主要來源及其變動(dòng)機(jī)制,分析了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現(xiàn)狀和影響因素,并依據(jù)公信力的變動(dòng)機(jī)制。試圖指出在現(xiàn)有條件下快速、有效、可持續(xù)地提高我國(guó)政府公信力的方式方法。
關(guān)鍵詞:政府公信力;公信力現(xiàn)狀;提高
構(gòu)建和諧社會(huì)已是黨和政府及社會(huì)各界的廣泛共識(shí)。建設(shè)的主體是廣大民眾。建設(shè)的主導(dǎo)力量應(yīng)該是各級(jí)政府,建設(shè)和諧社會(huì)是主導(dǎo)力量和主體力量相互信任、互為支持和共同配合的長(zhǎng)期過程。擁有一個(gè)得到廣大民眾信任與支持,擁有高度公信力的現(xiàn)代政府是建設(shè)和諧社會(huì)的關(guān)鍵。
一、政府公信力的內(nèi)涵和變動(dòng)機(jī)制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獲得公眾的信任度,是政府能力在公眾心中的綜合評(píng)價(jià)和公眾對(du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wù)的滿意度,也是政府對(duì)公眾的凝聚力和動(dòng)員力的重要決定因素。
探索公共管理下的政府誠(chéng)信度
摘要:信任是社會(huì)秩序的基礎(chǔ)之一。隨著公共管理理論的發(fā)展,政府信任逐漸成為重要議題。政府信任是整個(gè)社會(huì)最大的信任,整個(gè)社會(huì)信任基于政府信任來推動(dòng)和發(fā)展政府的權(quán)力,必須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監(jiān)督與制約,以確保行政責(zé)任的忠實(shí)履行。如何認(rèn)識(shí)和化解中國(guó)政府信任問題,是當(dāng)前研究的重點(diǎn)。
關(guān)鍵詞:公共危機(jī);政府信任;誠(chéng)信
西方哲學(xué)家史里斯·博克曾指出,“信任是我們必須保護(hù)的東西,因?yàn)樗拖窨諝夂退匆粯樱坏┦軗p,我們所居住的社會(huì)就會(huì)土崩瓦解”[1]。信任的存在有助于增強(qiáng)社會(huì)成員的凝聚力,降低社會(huì)運(yùn)行的成本,提高社會(huì)運(yùn)行的效率。
一、政府信任的理論闡釋
1.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基礎(chǔ)。民眾對(duì)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是任何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重要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是任何政體順利運(yùn)作的重要保障。當(dāng)政治權(quán)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眾相當(dāng)程度的信任時(shí),民眾就會(huì)相信權(quán)威當(dāng)局會(huì)了解其需要,能夠?yàn)槠渲\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無貪污腐敗之事。
2.促進(jì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良性運(yùn)轉(zhu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德基礎(chǔ)最重要的就是信譽(yù)或信任(張維迎,2001)。目前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還是政府主導(dǎo)型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公眾對(duì)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就有著較大的影響。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潤(rùn)滑劑,其運(yùn)作效果如何,與政府的誠(chéng)信直接相關(guān)。
解析公共信任及信任問題
公共信任的凸顯及其界定
毫無疑問,在人類社會(huì)發(fā)展的過程中,社會(huì)逐步組織化的過程與信任形態(tài)的變化相伴隨。如盧曼所言,“從歷史上看,而且從實(shí)質(zhì)上看,信任采取了許多不同的形式。在古代社會(huì)系統(tǒng)所具有的特征不同于在文明社會(huì)系統(tǒng)它具有的特征。”[2](p.125)這一觀點(diǎn)提醒我們這樣一個(gè)事實(shí):即不能忽視信任類型轉(zhuǎn)化中的一個(gè)基本的趨勢(shì),那就是,在社會(huì)發(fā)展及其信任形態(tài)變化的過程中,有一種信任類型,即公共信任,總是與人類社會(huì)的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相伴隨。從共同生活或者公共生活的層面而言,不管是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還是在工業(yè)社會(huì),被統(tǒng)治者對(duì)統(tǒng)治者應(yīng)該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的期待、公民對(duì)執(zhí)政黨社會(huì)責(zé)任的期待、社會(huì)公眾對(duì)社會(huì)組織基本功能的期待都是存在的,這種以期待為基礎(chǔ)的信任類型是一種客觀的力量,是維持統(tǒng)治秩序和社會(huì)生活秩序的一個(gè)重要因素,是王朝或者現(xiàn)代國(guó)家合法性的基礎(chǔ),也是促進(jìn)社會(huì)有效整合與和諧運(yùn)行的基礎(chǔ)。毫無疑問,缺乏公共信任的任何統(tǒng)治者或者管理者都缺乏社會(huì)基礎(chǔ),即使在服務(wù)型政府的建設(shè)中,這種信任也起著關(guān)鍵作用。在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統(tǒng)治行政體系及統(tǒng)治關(guān)系中,臣民對(duì)統(tǒng)治體系和統(tǒng)治者地位的合法性認(rèn)可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最原始的基礎(chǔ),這種認(rèn)可來源于臣民對(duì)擬神化的統(tǒng)治者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優(yōu)良教化社會(huì)、穩(wěn)定社會(huì)秩序和統(tǒng)治秩序等社會(huì)責(zé)任的期待。被統(tǒng)治者對(duì)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身份的認(rèn)可以及實(shí)現(xiàn)這些社會(huì)責(zé)任的盡心期待是這種信任形成和產(chǎn)生的社會(huì)基礎(chǔ)。盡管,在統(tǒng)治者看來,統(tǒng)治的邏輯不一定如此,而是“君權(quán)神授”的應(yīng)該如此。但是,從社會(huì)科學(xué)的角度來理解,前者才是其合法統(tǒng)治的基礎(chǔ)。唐太宗李世民的治理名言:“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中的“水”,一般意義上都理解為被統(tǒng)治者,即老百姓,但從信任的角度來看,更合適的理解是被統(tǒng)治者對(duì)統(tǒng)治者的統(tǒng)治功能和責(zé)任的一種信任,無論是“載”或者是“覆”,都與這種信任有關(guān)。進(jìn)一步分析,從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統(tǒng)治行政體系中信任建構(gòu)的角度來理解,統(tǒng)治者一般通過祭祀神的方式去自然地獲得一種基于神的人格的“共同信任”,并因此獲得統(tǒng)治的合法性。這是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統(tǒng)治者獲得“共同信任”或者“公共信任”最為快捷的最基本的途徑,也是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統(tǒng)治技巧和方法。因此,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無論是在戰(zhàn)爭(zhēng)或和平時(shí)期,王朝總是要祭祀神和統(tǒng)治者的先祖,這既可以理解為對(duì)“君權(quán)神授”的一種社會(huì)闡釋和呈現(xiàn),更是統(tǒng)治者因此獲得被統(tǒng)治者信任的基本途徑。這種信任是鏈接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合法性關(guān)系的紐帶。當(dāng)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信任還不完全是統(tǒng)治行政體系形成的基礎(chǔ)。因?yàn)椋r(nóng)業(yè)社會(huì)的統(tǒng)治行政體系主要是通過血緣關(guān)系和擬血緣關(guān)系來建立信任的,從而,在體系內(nèi)部,維護(hù)其行政體系基礎(chǔ)的信任形態(tài)主要是人際信任而不是我們所說的“公共信任”或者“共同信任”。但是,從構(gòu)成統(tǒng)治者和被統(tǒng)治者的關(guān)系基礎(chǔ)來看,其統(tǒng)治的合法性和“公共信任”密切相關(guān),被統(tǒng)治者對(duì)統(tǒng)治者的合法性的不認(rèn)可乃至暴力的反抗,主要還是因?yàn)樗麄儧]有履行好發(fā)展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優(yōu)良教化社會(huì)和穩(wěn)定秩序等社會(huì)責(zé)任,這些責(zé)任的喪失所導(dǎo)致的“公共信任”的喪失,是統(tǒng)治者失去統(tǒng)治合法性的根本原因。到了工業(yè)社會(huì),啟蒙思想家使人們逐漸脫離了對(duì)神的精神依賴以及對(duì)倫理生活的依賴;特別是隨著社會(huì)分工的細(xì)化,隨著個(gè)體生活的社會(huì)化和社會(huì)生活的組織化,建立在個(gè)體知識(shí)能力基礎(chǔ)上的職業(yè)專業(yè)化與個(gè)體對(duì)組織的依賴密不可分,失業(yè)問題就是個(gè)體對(duì)組織依賴的典型說明。在工業(yè)社會(huì),社會(huì)組織不僅成為了社會(huì)運(yùn)行和社會(huì)管理的載體,而且不同類型的社會(huì)組織共同構(gòu)成了個(gè)體生活無可脫離的環(huán)境,并形成了一股主導(dǎo)公共生活的力量。特別是在專業(yè)分工細(xì)密的城市中,人們的生活深陷于無法回避的社會(huì)組織的包圍和牽制之中,因此,很多社會(huì)學(xué)學(xué)者把組織類型作為社會(huì)結(jié)構(gòu)劃分的基礎(chǔ)。從行政學(xué)的視角來看,在工業(yè)社會(huì)的公共生活中,公民和社會(huì)組織中存在的一個(gè)不可忽視的關(guān)系是公民對(duì)政府的依賴關(guān)系。特別是在民族國(guó)家成長(zhǎng)為行政國(guó)家后,盡管個(gè)體的生活空間日益擴(kuò)大到了各種不同的社會(huì)組織,但在公共服務(wù)層面,公民“從搖籃到墳?zāi)埂倍继幱谡墓苤浦校鐣?huì)生活對(duì)組織的依賴完全體現(xiàn)為公民對(duì)政府的依賴,政府在國(guó)家行政化的過程中成為了公共生活的中心,公共領(lǐng)域或者公共生活中的責(zé)任就是政府的責(zé)任。從公共信任關(guān)系來看,相應(yīng)地,政府信任也就處于信任體系的核心。政府在公共領(lǐng)域中的中心地位成為政府信任凸現(xiàn)的重要原因之一。與此同時(shí),公民對(duì)政府的集中依賴淡化了其他組織在公共生活中的地位。從公共信任形成的角度來看,很明顯,在工業(yè)社會(huì)的信任體系中,政府在公共領(lǐng)域中的中心化及其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dǎo)地位是一種治理現(xiàn)實(shí)。當(dāng)前,人類社會(huì)正處于從工業(yè)社會(huì)向后工業(yè)社會(huì)過渡的過程中。在此過程中,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新的信任類型將逐漸凸顯出來。在《道德的市場(chǎng)》中,鮑曼指出,“影響行為人的因素主要在于他人的行為。而此類社會(huì)依存的情形下存在著參與人的一種‘社會(huì)行為’,其以他人過去的、現(xiàn)在的或預(yù)計(jì)未來采取的行為為取向。”[3](p.46)根據(jù)這一社會(huì)依存理論來理解,我們認(rèn)為,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后工業(yè)化過程中各種社會(huì)類型的公共責(zé)任結(jié)構(gòu)的變化密切相關(guān)。第一,公共信任的凸顯與群體間的依存度增加有關(guān)。如果說工業(yè)化過程是個(gè)體對(duì)政府組織依賴的過程,那么,后工業(yè)化過程則是不同社會(huì)組織之間互依性增加的過程。在后工業(yè)化的過程中,由于個(gè)體進(jìn)一步群體化,群體進(jìn)一步組織化,在社會(huì)互依性增加的過程中,社會(huì)構(gòu)成的群體性和社會(huì)生活方式的組織性,一方面使群體的生活形式演變?yōu)槿后w間組織的依賴;另一方面,在公共生活中,除了政府對(duì)社會(huì)責(zé)任的承擔(dān)以外,組織規(guī)模日益擴(kuò)大而且社會(huì)管理技能日益增加的其他社會(huì)組織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也相應(yīng)地得以增加。無論我們把后工業(yè)社會(huì)稱為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開放社會(huì)、多元社會(huì)、流動(dòng)社會(huì)還是虛擬社會(huì),其實(shí)這個(gè)社會(huì)還是群體組織的社會(huì)。群體的形成、群體對(duì)組織的依賴和群體間的互依是這個(gè)社會(huì)的普遍特征。這種組織間的互依性關(guān)系是當(dāng)今社會(huì)合作潮流形成的原因,也是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第二,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各類社會(huì)組織公共性的重疊相關(guān)。有研究者指出,“在今日的社會(huì)條件下,公共性是一個(gè)‘重疊式’結(jié)構(gòu):經(jīng)濟(jì)形態(tài)—資本(商品與貨幣是資本的兩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政治形態(tài)—行政權(quán)力與制度;文化—精神形態(tài):公共理性與公共精神。”[4](p.115)在后工業(yè)化過程的公共生活中,公共性的重疊或日趨整體化表明了這樣一種趨勢(shì),那就是,公共責(zé)任不只是政府等擁有公共權(quán)力的組織的“特權(quán)”,而是參與和形成公共生活的所有社會(huì)組織的基本責(zé)任。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yíng)利性組織對(duì)公共生活中的公共責(zé)任的共同擔(dān)負(fù),成為公共信任凸顯的重要原因。相應(yīng)地,公共信任也成為了公共生活有序運(yùn)行的基礎(chǔ),是各種社會(huì)組織是否能夠得到社會(huì)認(rèn)可并承認(rèn)其參與公共生活的合法性基礎(chǔ)。第三,公共信任的凸顯與多元社會(huì)治理主體間合作性互動(dòng)關(guān)系的形成有關(guān)。在各種類型的社會(huì)組織被賦予或者主動(dòng)承擔(dān)了增加社會(huì)福利、維護(hù)社會(huì)安全和促進(jìn)社會(huì)公平等社會(huì)責(zé)任的功能與使命后,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提供的主體結(jié)構(gòu)不再是以政府為中心的一種管制性結(jié)構(gòu),而轉(zhuǎn)變?yōu)橹卫磉^程中的一種合作性互動(dòng)結(jié)構(gòu)。盡管這種合作性互動(dòng)結(jié)構(gòu)目前還比較薄弱,而且,很多社會(huì)組織對(duì)社會(huì)責(zé)任的承擔(dān)是在政府的引導(dǎo)下進(jìn)行的。比如,企業(yè)的社會(huì)責(zé)任的承擔(dān)就是政府對(duì)其促進(jìn)的結(jié)果,但不可否認(rèn),這種促進(jìn)及其有效互動(dòng)的基礎(chǔ)是信任而不只是支配性的權(quán)力。由于互動(dòng)基礎(chǔ)的改變,這種因?yàn)楹献餍躁P(guān)系而形成的信任不是人際信任,也不是組織信任,而是公共生活中一種以社會(huì)責(zé)任為基礎(chǔ)的信任,即公共信任。它是社會(huì)公共生活中的支撐力量。這樣一來,工業(yè)社會(huì)以政府信任為中心的信任體系結(jié)構(gòu)不可避免地轉(zhuǎn)化為一種以多元合作治理主體共同建構(gòu)的公共信任體系結(jié)構(gòu)。對(duì)于理論研究而言,無可回避的問題是,當(dāng)公共信任作為一種成熟的信任類型凸顯并逐漸成為影響公共生活和社會(huì)秩序最為關(guān)鍵的因素之一后,我們必須對(duì)這一概念進(jìn)行界定,并指出其內(nèi)在特征。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相對(duì)于私人信任而言的,是與公共生活及公共交往相聯(lián)系的信任,是現(xiàn)代社會(huì)尤其是民主制度下的新型信任。作為一個(gè)寬泛的概念,主要包括四個(gè)層次的內(nèi)容:對(duì)社會(huì)成員的一般信任、對(duì)社會(huì)角色的信任、對(duì)社會(huì)制度及運(yùn)行機(jī)制的信任、對(duì)民主社會(huì)的一般價(jià)值觀的信任。[5](p.56)我們認(rèn)為,如果把信任一分為二地類型化為公共信任和私人信任過于簡(jiǎn)單,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公共信任確實(shí)與公共生活有關(guān),與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性重疊和公共責(zé)任在社會(huì)組織結(jié)構(gòu)中的逐漸分散有關(guān)。思考公共信任不但要思考它產(chǎn)生的基礎(chǔ),而且只有結(jié)合公共性來思考,只有立足于公共生活和公共性來思考,才能歸納、揭示公共信任這一概念。在綜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我們認(rèn)為,公共信任是社會(huì)公眾對(duì)于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yíng)利性組織共同維護(hù)公共生活有序運(yùn)行的社會(huì)責(zé)任的系統(tǒng)化的有限期待,是維持公共生活良性運(yùn)行的一種客觀整合力量。在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huì),社會(huì)公眾與各種社會(huì)組織之間存在一種和諧的社會(huì)交往關(guān)系,社會(huì)組織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社會(huì)公眾的合理期待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反之,存在公共信任問題的社會(huì)則意味著失去了一種最有力的社會(huì)整合力量,這一社會(huì)整合力量的消失是致使社會(huì)整體失信的重要原因,也是導(dǎo)致社會(huì)整體誠(chéng)信危機(jī)的重要原因。作為公共生活中的一種信任形式,公共信任有如下特點(diǎn):第一,公共信任的系統(tǒng)性。公共信任的系統(tǒng)性表現(xiàn)為非營(yíng)利性組織中的公益信任、私人領(lǐng)域中的企業(yè)信任和公共領(lǐng)域中的政府信任之間是相關(guān)的,因此體現(xiàn)了公共信任系統(tǒng)化的特征,公共信任體系中的各要素是互動(dòng)的。因此,有時(shí)候政府不被信任,不是因?yàn)檎旧硇湃味炔桓撸钦疀]有管理好其他組織的公共信任。現(xiàn)階段,由于政府在公共生活中的主導(dǎo)性地位,政府對(duì)其他類型組織的公共信任有管理的權(quán)力和義務(wù)。因此,在規(guī)劃中國(guó)公共誠(chéng)信體系建構(gòu)的過程中,從學(xué)者到民眾都認(rèn)為首先要從政府誠(chéng)信抓起。這是符合公共信任及其管理的特點(diǎn)的。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社會(huì)管理過程中如果只重視政府信任,而忽視對(duì)其他承擔(dān)公共責(zé)任的組織的信任度的管理,照樣會(huì)產(chǎn)生公共信任危機(jī)。第二,公共信任體系的層次性。盡管不同社會(huì)組織公共責(zé)任的性質(zhì)是相同的,但它們公共責(zé)任的大小是有層次性的。在一般意義上,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信任度與它們對(duì)公共生活的影響程度及其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的大小密切相關(guān)。例如,盡管社會(huì)責(zé)任的性質(zhì)一樣,但一個(gè)跨國(guó)公司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與一個(gè)個(gè)體企業(yè)所承擔(dān)的社會(huì)責(zé)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同樣,一個(gè)大公司的社會(huì)責(zé)任缺失所引發(fā)的信任問題及其導(dǎo)致的社會(huì)影響也是巨大的。在社會(huì)組織的合作性治理結(jié)構(gòu)的形成和成熟過程中,不同組織社會(huì)責(zé)任的大小與政府的責(zé)任相比依然相差很大。因此,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剑湃芜€是公共信任體系結(jié)構(gòu)中的主要要素。當(dāng)然,我們不能因?yàn)楣残湃误w系中這一主要要素的存在,就去否認(rèn)其他組織對(duì)公共生活所負(fù)有的責(zé)任,去否認(rèn)它們?cè)诠残湃瓮癸@過程中的作用。第三,公共信任關(guān)系的模糊性。在公共信任體系所呈現(xiàn)的信任主體關(guān)系中,一方是與社會(huì)責(zé)任相聯(lián)系的社會(huì)組織,另一方是社會(huì)公眾,這就形成了公共信任關(guān)系中一對(duì)多的關(guān)系,盡管這種一對(duì)多的關(guān)系不是嚴(yán)格數(shù)學(xué)意義上的,但正是這種關(guān)系導(dǎo)致了公共信任關(guān)系的模糊性。例如日益嚴(yán)重的食品安全問題,表面看起來是食品生產(chǎn)企業(yè)的問題,但實(shí)質(zhì)上,因?yàn)槭称钒踩珜?duì)公共生活的重大影響,這一問題本質(zhì)上是社會(huì)的公共信任問題。也正是由于公共信任的體系性和政府在社會(huì)中的主體性角色,社會(huì)公眾很容易把系統(tǒng)化的公共信任等同于碎片化的政府信任,也很容易忽視其他社會(huì)組織在公共信任中的作用。不可否認(rèn),公共信任的這一特征也是很多學(xué)者視之若有若無,不給予足夠重視的關(guān)鍵原因。第四,公共信任關(guān)系的壓力性。公共信任關(guān)系是社會(huì)組織和社會(huì)公眾之間所形成的一種關(guān)系,由于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和社會(huì)公眾對(duì)公共生活的依賴,從而,在公共信任度低的環(huán)境中,公共信任主體和社會(huì)公眾之間形成了一種壓力性關(guān)系。這種壓力性關(guān)系的存在意味著信任者與被信任者之間的空間關(guān)系是狹小的。如同一個(gè)孩子無法選擇其父母一樣,一個(gè)國(guó)家的公民也無法隨意選擇其所在的國(guó)家;社會(huì)公眾在公共生活過程中不得不接受不同社會(huì)組織的產(chǎn)品、服務(wù)和管理。這恰恰是公共信任起作用的基礎(chǔ),但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huì),社會(huì)組織和社會(huì)公眾之間便形成了一種不可回避的壓力性關(guān)系。例如我們要購(gòu)買食品、藥品等生活用品,盡管它們可能存在安全風(fēng)險(xiǎn),但是誰也無法完全知道更無法完全回避這些風(fēng)險(xiǎn),因?yàn)槲覀円蕾囁鼈兩?同樣,公民要接受行政、司法和立法機(jī)構(gòu)根據(jù)權(quán)力和規(guī)則的管理或服務(wù)。在一個(gè)政府的階段性統(tǒng)治時(shí)期內(nèi),社會(huì)公眾必須給予這些組織以信任支持,這是難以回避的客觀事實(shí)。因此,有研究者指出,“公共信任是個(gè)人無從選擇的。其表現(xiàn)為選擇空間的狹小和高成本的退出機(jī)制。”“表現(xiàn)為信息、影響力與承受力的非均衡性,不可避免地造成信任的非相互性,從而使作為信任方的公民處于不利的地位”。[6](p.8)但從另一個(gè)角度來理解,公共信任卻因此成為了一種客觀事實(shí)和客觀力量。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公共信任的破裂則對(duì)公共機(jī)構(gòu)和公民的影響是破壞性的,甚至是災(zāi)難性的”。[6](p.8)第五,公共信任關(guān)系的脆弱性。“正如我們看到的,信任和不信任是符號(hào)傳播的泛化的態(tài)度,它們并不隨明確的具體客觀原因而變化,而是主觀過程控制的,經(jīng)驗(yàn)借此過程得到處理并且簡(jiǎn)單化。”[2](p.99)因此,與真理或法律相比,“信任機(jī)制的相對(duì)下級(jí)的,相對(duì)低的‘技術(shù)水平’,除了別的以外,在于比較難于轉(zhuǎn)化為對(duì)立面:信任轉(zhuǎn)化為不信任比不信任轉(zhuǎn)化為信任容易”。[2](pp.118~119)這表明了公共信任的脆弱性。盡管公共信任關(guān)系是一種壓力性關(guān)系,但這種關(guān)系是脆弱的。如果一個(gè)社會(huì)不對(duì)公共信任進(jìn)行有效的管理,這種信任關(guān)系會(huì)變得更加脆弱。在一個(gè)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社會(huì),一個(gè)負(fù)面的謠言就可以將整個(gè)政府或者社會(huì)的誠(chéng)信系統(tǒng)框架擊垮。如果我們正確認(rèn)識(shí)了公共信任在當(dāng)代社會(huì)的凸顯,我們就能夠?qū)残湃芜M(jìn)行有效的管理,其客觀事實(shí)的一面就會(huì)呈現(xiàn)出來,并可以發(fā)展成為一種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有序的客觀力量,從而減少社會(huì)交往成本,穩(wěn)定社會(huì)心態(tài)。
公共信任問題及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
在界定了公共信任的形成階段、概念和特征后,公共信任管理成為必須關(guān)注的重要問題。要提出公共信任的管理思路,首先要考察公共信任問題產(chǎn)生的邏輯及其社會(huì)影響。第一,公共信任問題起因于“公共質(zhì)疑”。“公共質(zhì)疑”是社會(huì)公眾對(duì)負(fù)有公共責(zé)任的某一類社會(huì)組織的負(fù)面性事實(shí)的失望與反對(duì),是對(duì)這一類組織的社會(huì)功能及其社會(huì)責(zé)任的不認(rèn)同。例如,如果社會(huì)公眾共同質(zhì)疑企業(yè)產(chǎn)品的安全性、共同質(zhì)疑食品和藥品的安全性;或者公民共同質(zhì)疑行政、司法等公共權(quán)力機(jī)構(gòu)行為的公平和正義……對(duì)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質(zhì)疑就形成了。公共質(zhì)疑會(huì)導(dǎo)致對(duì)某一類型的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公共不信任”的發(fā)展可以逐步累積成公共信任問題。當(dāng)“公共不信任”累積到一定程度后,社會(huì)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chǎn)生了,我們所說的社會(huì)誠(chéng)信危機(jī)就產(chǎn)生了,因?yàn)樯鐣?huì)公眾對(duì)多種類型的社會(huì)組織的社會(huì)功能都給予了“公共不信任”。如果一個(gè)社會(huì)產(chǎn)生了誠(chéng)信危機(jī),這就意味著“公共不信任”在公共生活中起了質(zhì)的變化。第二,公共信任問題導(dǎo)致公眾對(duì)負(fù)有公共責(zé)任的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生活功能整體性的負(fù)期待。在目前的社會(huì),公共組織、私人組織和非營(yíng)利性組織對(duì)社會(huì)的有效運(yùn)行都有一份責(zé)任,公眾對(duì)這些組織的功能和責(zé)任也有一種期待。比如,任何人都期待企業(yè)的產(chǎn)品是安全的,它們的服務(wù)是公平、公正的;任何人都期待社會(huì)公益組織是增加社會(huì)福利的,是幫助弱勢(shì)群體的;任何人都期待政府是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的,是維護(hù)社會(huì)公平和正義的。如果說公共質(zhì)疑起因于某一事件的結(jié)果與公眾對(duì)這一類型組織功能的原有期待整體不符(比如,三鹿集團(tuán)的三聚氰胺事件引起了公眾對(duì)三鹿奶粉甚至整個(gè)奶粉行業(yè)產(chǎn)品安全的質(zhì)疑),那么,這種公共質(zhì)疑若任其發(fā)展,某一類型的組織的公共信任問題就產(chǎn)生了。如果這種公共信任問題不再局限于某類型組織,而是社會(huì)整體層面的各個(gè)組織,就會(huì)動(dòng)搖整個(gè)社會(huì)公共信任體系的基礎(chǔ)。第三,公共信任問題可以導(dǎo)致公共生活的混亂和社會(huì)的誠(chéng)信危機(jī)。“沒有信任,只有非常簡(jiǎn)單的當(dāng)場(chǎng)互動(dòng)的人類合作形式是可能的;沒有信任,超過當(dāng)下確保的環(huán)節(jié),即便個(gè)人行動(dòng)也對(duì)破裂極為敏感以致無法做出計(jì)劃。”[2](p.117)由于公共信任是社會(huì)良性運(yùn)行的基石,一旦私人組織或者非營(yíng)利性組織的公共質(zhì)疑沒有被政府或者引起這一問題的組織有效化解;社會(huì)公眾對(duì)這一類型的組織就會(huì)產(chǎn)生整體性失望,形成對(duì)某一類型組織的“公共不信任”。再任其發(fā)展,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具有“上訴性”,最終將連帶質(zhì)疑政府的合法性。公共信任問題不可避免地要對(duì)有序的社會(huì)交往、運(yùn)行及其秩序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四點(diǎn):其一,社會(huì)尊重缺乏,社會(huì)依附性產(chǎn)生。由于社會(huì)公眾失去了對(duì)社會(huì)組織的信任,公共生活就碎片化了,社會(huì)公眾對(duì)社會(huì)組織的尊重也逐漸淡化,并有可能會(huì)發(fā)展成為仇視;這樣一來,私人信任慢慢成為支持社會(huì)運(yùn)行的主因,這樣運(yùn)行的社會(huì)也就成為了一個(gè)“關(guān)系型”的社會(huì)。由于缺乏公共信任,公共權(quán)力組織的許多功能就會(huì)在很大程度上喪失,社會(huì)公眾不得不依附于非公共權(quán)力或者非公共性權(quán)力的庇護(hù),形成社會(huì)的依附性。其二,社會(huì)合作缺失,社會(huì)惡性競(jìng)爭(zhēng)產(chǎn)生。由于社會(huì)公眾公共信任的缺乏,特別是公民對(duì)公共權(quán)力組織的信任缺乏,公眾和社會(huì)組織之間應(yīng)有的合作便慢慢消失。如果任其發(fā)展,公眾、政府及其它社會(huì)組織之間就會(huì)慢慢形成一種惡性的競(jìng)爭(zhēng)和對(duì)抗關(guān)系,并最終造成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不可調(diào)和。其三,社會(huì)資本流失,與信任有關(guān)的經(jīng)濟(jì)資本流失。顯然,公共信任是一種有效的社會(huì)資本,公共信任缺乏意味著最容易整合社會(huì)秩序的公共信任資本的流失;與此同時(shí),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經(jīng)濟(jì)資本,比如民眾基于對(duì)公司信任而購(gòu)買的股票,會(huì)因?yàn)楣镜囊粋€(gè)失信事件而大量拋棄,公司的經(jīng)濟(jì)資本會(huì)因此而承受巨大的損失。其四,社會(huì)整體失信,社會(huì)整體的道德危機(jī)產(chǎn)生。由于公共信任是體系性的,因此,公共信任的缺失將導(dǎo)致社會(huì)的整體失信,從而導(dǎo)致社會(huì)整體的道德危機(jī)。由于公共信任問題是引起社會(huì)信任危機(jī)的關(guān)鍵因素,對(duì)公共信任進(jìn)行有效管理便成為社會(huì)管理的基本內(nèi)容。其實(shí),學(xué)者們對(duì)信任管理的思考由來已久。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認(rèn)為,在一個(gè)簡(jiǎn)單封閉的社會(huì),對(duì)信任的管理是可行的,但在一個(gè)開放分化的社會(huì),信任管理是很困難的。盧曼就指出,“信任和法律只是在非常簡(jiǎn)單的社會(huì)系統(tǒng)中彼此相等,那些社會(huì)系統(tǒng)幾乎沒有任何結(jié)構(gòu)問題,小到足以使所有系統(tǒng)成員彼此熟識(shí)。在這種系統(tǒng)中,信任受到期待,不信任成為公開侮辱,成為一種對(duì)集體生活的規(guī)則從而對(duì)該系統(tǒng)法律的冒犯……”[2](p.44)“相反,在所有比較分化了的,比較復(fù)雜的社會(huì)體系中,法律和信任不可避免的以此方式相分離。”由于“信任又是太普遍、太分散的一種社會(huì)要求”,“法律和信任在他們的動(dòng)機(jī)形態(tài)的基礎(chǔ)上也彼此分離。”[2](p.45)也就是說,在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看來,在復(fù)雜社會(huì)體系中,由于信任的普遍化、情景性、分散化與法律的剛性不一致,信任管理是很難的事情。很顯然,公共信任的管理也是很困難的,但在目前的社會(huì)階段,公共信任的凸顯以及它對(duì)當(dāng)前社會(huì)秩序和公共生活的重要性,對(duì)其進(jìn)行有效的管理已成為社會(huì)管理不可回避的問題。針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舊道德觀念的維持和新道德的生長(zhǎng)面臨前所未有的復(fù)雜的社會(huì)生態(tài),很多學(xué)者提出信任管理問題。一些社會(huì)學(xué)學(xué)者建議“執(zhí)政者可以引入社會(huì)‘誠(chéng)信工程’來推進(jìn)社會(huì)道德建設(shè)”[8]。我們認(rèn)為,無論是西方社會(huì)還是東方社會(huì)整體性的社會(huì)危機(jī),最終都體現(xiàn)為公共信任的危機(jī)。很多學(xué)者認(rèn)為后工業(yè)社會(huì)是一個(gè)風(fēng)險(xiǎn)社會(huì),其實(shí)后工業(yè)化過程中最大的風(fēng)險(xiǎn)是公共信任問題所產(chǎn)生的風(fēng)險(xiǎn),因此,更需要對(duì)公共信任進(jìn)行有效的管理。在社會(huì)轉(zhuǎn)型的過程中,不但每一個(gè)社會(huì)個(gè)體和組織要對(duì)自身的信任進(jìn)行管理,而且,如果我們要提高社會(huì)的整體信任度,就必須明確公共信任的特征,充分理解公共信任問題產(chǎn)生的原因,并制定有效管理公共信任的措施。這既是一個(gè)可操作的方法又是一個(gè)解決社會(huì)整體失信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對(duì)于社會(huì)管理而言,公共信任管理是一個(gè)復(fù)雜的充滿挑戰(zhàn)性的新問題,本文只對(duì)這一問題與社會(huì)管理的關(guān)系提出一個(gè)宏觀的思路。首先,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理念,對(duì)隱性的公共信任進(jìn)行顯性管理。有效的社會(huì)管理不只是要對(duì)社會(huì)行為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等顯性要素進(jìn)行管理,更為關(guān)鍵的是,還要對(duì)公共信任等隱性要素進(jìn)行管理。由于“公共不信任”導(dǎo)致的公共信任問題是社會(huì)整體失信的關(guān)鍵,因此,在社會(huì)管理過程中,要解決社會(huì)整體的信任危機(jī),就不能只使公共信任成為一種期待、信賴關(guān)系或是一種社會(huì)信心,而要通過社會(huì)管理使其演變?yōu)轶w系化的、治理社會(huì)的系統(tǒng)性力量;特別是要通過公開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即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huì)組織的一個(gè)顯性指標(biāo),以此來督促社會(huì)組織,同時(shí)提示社會(huì)公眾對(duì)這些組織的公共信任度進(jìn)行監(jiān)督。這樣一來,公共信任就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社會(huì)管理力量。其次,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內(nèi)容,將公共信任作為社會(huì)管理的重要任務(wù)。這主要包括兩個(gè)方面的任務(wù):一方面,公共信任本身應(yīng)該成為一個(gè)重要的社會(huì)管理要素,把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個(gè)重要的管理任務(wù)。要對(duì)一般意義上的、負(fù)有公共責(zé)任的各種組織的公共信任進(jìn)行管理,特別重要的是,要及時(shí)評(píng)測(cè)政府體系中各個(gè)部門和機(jī)構(gòu)的公共信任度,及時(shí)提醒各級(jí)機(jī)構(gòu)根據(jù)公共信任度來糾正自己的行為,這也是提高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在后工業(yè)化及其后工業(yè)社會(huì),在社會(huì)管理主體多元化以后,合作治理將成為社會(huì)治理的主流,以公共信任度來衡量合作主體的合法性將是政府引導(dǎo)合作治理良性運(yùn)行的重要基礎(chǔ)。因此,社會(huì)管理還需要對(duì)合作治理主體間的公共信任度進(jìn)行管理。也就是說,要促進(jìn)政府、企業(yè)和其他組織之間的合作,要使合作治理有效的運(yùn)行,社會(huì)公眾和政府就有必要以公共信任度作為一個(gè)指標(biāo)來衡量社會(huì)組織參與社會(huì)管理的合法性。在合作治理的過程中,對(duì)于公共信任度不高的組織,不能給予它們參與管理社會(huì),提供公共產(chǎn)品和公共服務(wù)的權(quán),而對(duì)于公共信任度高的社會(huì)組織,要給予他們更多的提供公共產(chǎn)品和服務(wù)的機(jī)會(huì),以此作為一種社會(huì)激勵(lì)措施。再次,創(chuàng)新社會(huì)管理的方式,對(duì)公共信任管理進(jìn)行硬法和軟法方面的設(shè)計(jì)。羅豪才指出,“公共領(lǐng)域的現(xiàn)實(shí)、我們所追求的治理目標(biāo)和軟硬法各自的特點(diǎn),決定了公共領(lǐng)域應(yīng)當(dāng)采取一種軟硬結(jié)合的混合法治理模式”。[9](p.5)對(duì)于公共信任的管理而言,與法律作為一種造就強(qiáng)制性秩序的規(guī)范不同,公共信任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造就非強(qiáng)制性秩序的管理方式。因此,公共信任管理不可能是一種完全的強(qiáng)制性硬法式的管理,而必須用一種硬法強(qiáng)制與軟法治理相結(jié)合的混合模式。對(duì)于政府而言,在社會(huì)管理過程中,要把加強(qiáng)對(duì)自身和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信任管理作為一項(xiàng)主要內(nèi)容,并采取對(duì)公共信任管理進(jìn)行立法的方式,使公共信任管理制度化,有法可依,實(shí)現(xiàn)對(duì)公共信任的“硬法”管理。此外,由于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信任需要通過兌現(xiàn)其公共承諾來實(shí)現(xiàn),因此,公共承諾是公共信任管理的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如果有了有效的公共承諾,社會(huì)公眾就可以通過觀察社會(huì)組織公共承諾的實(shí)現(xiàn)程度來考察社會(huì)組織履行社會(huì)責(zé)任的情況,從而觀測(cè)、了解和評(píng)價(jià)社會(huì)組織的公共信任度。因此,在社會(huì)管理層面,需要以公共承諾為核心環(huán)節(jié),對(duì)公共信任管理進(jìn)行全面和系統(tǒng)的設(shè)計(jì),實(shí)現(xiàn)在“軟法”方面的管理。
本文作者:謝新水工作單位:南京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
政府公共危機(jī)管理論文
一、政府信任的理論闡釋
1.作為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基礎(chǔ)。民眾對(duì)政府的支持與信任,是任何政權(quán)合法性來源的重要基礎(chǔ),當(dāng)然也是任何政體順利運(yùn)作的重要保障。當(dāng)政治權(quán)威的能力以及操守得到民眾相當(dāng)程度的信任時(shí),民眾就會(huì)相信權(quán)威當(dāng)局會(huì)了解其需要,能夠?yàn)槠渲\福利并且依法行政而無貪污腐敗之事。
2.促進(jì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良性運(yùn)轉(zhuǎn)。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道德基礎(chǔ)最重要的就是信譽(yù)或信任(張維迎,2001)。目前中國(guó)的經(jīng)濟(jì)還是政府主導(dǎo)型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公眾對(duì)政府信任度的高低對(duì)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也就有著較大的影響。信任作為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的潤(rùn)滑劑,其運(yùn)作效果如何,與政府的誠(chéng)信直接相關(guān)。
3.降低行政過程的交易成本。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來看,信任的經(jīng)濟(jì)意義在于它能夠降低交易成本。合作的雙方必須相互信任,否則達(dá)成合作協(xié)議及監(jiān)督合作協(xié)議實(shí)施的交易成本太高,合作行動(dòng)就難以發(fā)生。合作者之間是否相互信任以及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關(guān)系到合作效率的高低。
二、中國(guó)政府信任問題的現(xiàn)狀
1.社會(huì)政策缺乏穩(wěn)定性與連續(xù)性。當(dāng)前中國(guó)個(gè)別地區(qū)的政策制定卻缺乏嚴(yán)肅性和連續(xù)性,導(dǎo)致現(xiàn)有的利益分配格局陷入混亂的狀態(tài),減損既得利益者現(xiàn)有的合法利益,也對(duì)政策的目標(biāo)群體心理產(chǎn)生許多不良影響。
公眾良性預(yù)期的監(jiān)管條件綜述
論文關(guān)鍵詞:監(jiān)管失靈,適應(yīng)性預(yù)期,低信任陷阱,消費(fèi)者信任
論文摘要:近年來在多個(gè)領(lǐng)域政府監(jiān)管屢屢失靈。本文對(duì)乳品行業(yè)質(zhì)量監(jiān)管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為:初次發(fā)生食品安全事件時(shí),公眾對(duì)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預(yù)期,消費(fèi)者對(duì)違規(guī)企業(yè)的信任能迅速恢復(fù);但財(cái)稅分權(quán)的制度設(shè)計(jì)決定了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yè)利益的高度契合,質(zhì)檢機(jī)構(gòu)縱容、偏袒、保護(hù)違規(guī)企業(yè)是經(jīng)濟(jì)生活的常態(tài),只有爆發(fā)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會(huì)公共安全時(shí),政府才會(huì)對(duì)違規(guī)企業(yè)進(jìn)行運(yùn)動(dòng)式打擊;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繁爆發(fā)導(dǎo)致消費(fèi)者不斷修正對(duì)政府治理的預(yù)期,最終導(dǎo)致消費(fèi)者對(duì)政府和企業(yè)都喪失信任。政府監(jiān)管頻頻失控比市場(chǎng)自發(fā)調(diào)整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的損害更為嚴(yán)重。
一、引言
近年來在衣食住行領(lǐng)域,“房?jī)r(jià)居高不下”,“假藥”、“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輪番爆出。治理機(jī)制有多種,但由于中央集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軌路徑依賴,公眾對(duì)政府依然具有強(qiáng)的依戀情結(jié),所以每當(dāng)爆發(fā)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時(shí),公眾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會(huì)應(yīng)運(yùn)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顯著。以近幾年頻繁發(fā)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臺(tái)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頒布了新的乳品標(biāo)準(zhǔn)、下發(fā)了《奶業(yè)整頓和振興規(guī)劃綱要》,出臺(tái)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國(guó)務(wù)院副總理領(lǐng)導(dǎo)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huì)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陰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來。
本文關(guān)注的主要問題是:對(duì)于頻繁爆發(fā)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徹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這將會(huì)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修復(fù)起什么作用?本文通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業(yè)“毒奶粉”的治理為例,探尋政府在不同階段所出臺(tái)的政策措施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修復(fù)、乳品行業(yè)發(fā)展的階段性影響、最終影響,并提出相應(yīng)對(duì)策。
二、適應(yīng)性預(yù)期與政府調(diào)控效果的關(guān)聯(lián)性分析
公眾良性的監(jiān)管條件的構(gòu)建透析
論文關(guān)鍵詞:監(jiān)管失靈,適應(yīng)性預(yù)期,低信任陷阱,消費(fèi)者信任
論文摘要:近年來在多個(gè)領(lǐng)域政府監(jiān)管屢屢失靈。本文對(duì)乳品行業(yè)質(zhì)量監(jiān)管進(jìn)行了實(shí)證分析,結(jié)果為:初次發(fā)生食品安全事件時(shí),公眾對(duì)政府治理效果具有良好預(yù)期,消費(fèi)者對(duì)違規(guī)企業(yè)的信任能迅速恢復(fù);但財(cái)稅分權(quán)的制度設(shè)計(jì)決定了地方政府與地方企業(yè)利益的高度契合,質(zhì)檢機(jī)構(gòu)縱容、偏袒、保護(hù)違規(guī)企業(yè)是經(jīng)濟(jì)生活的常態(tài),只有爆發(fā)大的食品安全事件危及社會(huì)公共安全時(shí),政府才會(huì)對(duì)違規(guī)企業(yè)進(jìn)行運(yùn)動(dòng)式打擊;食品安全事件的頻繁爆發(fā)導(dǎo)致消費(fèi)者不斷修正對(duì)政府治理的預(yù)期,最終導(dǎo)致消費(fèi)者對(duì)政府和企業(yè)都喪失信任。政府監(jiān)管頻頻失控比市場(chǎng)自發(fā)調(diào)整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的損害更為嚴(yán)重。
一、引言
近年來在衣食住行領(lǐng)域,“房?jī)r(jià)居高不下”,“假藥”、“假疫苗”、“毒奶粉”事件輪番爆出。治理機(jī)制有多種,但由于中央集權(quán)的經(jīng)濟(jì)體制轉(zhuǎn)軌路徑依賴,公眾對(duì)政府依然具有強(qiáng)的依戀情結(jié),所以每當(dāng)爆發(fā)大的公共安全事件時(shí),公眾都把有效治理的重望寄托于政府,一系列的行政性治理手段也會(huì)應(yīng)運(yùn)而生,但政府治理效果并不顯著。以近幾年頻繁發(fā)生的“三聚氰胺”事件為例,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密集出臺(tái)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頒布了新的乳品標(biāo)準(zhǔn)、下發(fā)了《奶業(yè)整頓和振興規(guī)劃綱要》,出臺(tái)了《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食品安全法》,成立了以國(guó)務(wù)院副總理領(lǐng)導(dǎo)下的食品安全委員會(huì)等措施,但是2008年的“三聚氰胺”的陰霾尚未褪去,2009年底、2010年“三聚氰胺”事件再次卷土重來。
本文關(guān)注的主要問題是:對(duì)于頻繁爆發(fā)的食品安全事件,政府能否真正徹底治理?如政府不能有效治理,這將會(huì)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修復(fù)起什么作用?本文通過主成分分析的方法,以乳品行業(yè)“毒奶粉”的治理為例,探尋政府在不同階段所出臺(tái)的政策措施對(duì)消費(fèi)者信任修復(fù)、乳品行業(yè)發(fā)展的階段性影響、最終影響,并提出相應(yīng)對(duì)策。
二、適應(yīng)性預(yù)期與政府調(diào)控效果的關(guān)聯(lián)性分析
熱門標(biāo)簽
政府通知格式 政府調(diào)研報(bào)告 政府匯報(bào)材料 政府工作方案 政府政務(wù) 政府工作報(bào)告 政府工作匯報(bào) 政府整改措施 政府工作意見 政府支出
相關(guān)文章
1政府投資項(xiàng)目工程造價(jià)審計(jì)探討
3鄉(xiāng)鎮(zhèn)政府人力資源管理存在問題及對(duì)策
相關(guān)期刊
-

政府法制
主管:山西出版集團(tuán)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影響因子:--
-

政府管制評(píng)論
主管:浙江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中國(guó)政府管制研究院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影響因子:--
-

政府管理評(píng)論
主管:中國(guó)管理現(xiàn)代化研究會(huì)政府戰(zhàn)略與公共政策研究專業(yè)委員會(huì);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政府管理學(xué)院;中央財(cái)經(jīng)大學(xué)戰(zhàn)略管理研究中心
級(jí)別:部級(jí)期刊
影響因子:--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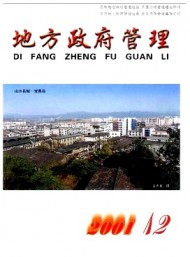
地方政府管理
主管:江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
級(jí)別:省級(jí)期刊
影響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