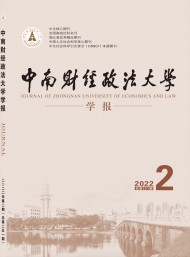周敦頤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4-19 02:09:06
導(dǎo)語(yǔ):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周敦頤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周敦頤性別意識(shí)探究論文
摘要:用敦頤開(kāi)顯宋明道學(xué)之源頭活水,世人對(duì)其研究甚多,卻鮮有就其性別思想進(jìn)行研究者。本文通過(guò)對(duì)《太極圖說(shuō)》和《通書(shū)》兩書(shū)的分析概括其性別思想為:陰陽(yáng)交感,化生萬(wàn)物;陽(yáng)健陰順,陽(yáng)尊陰年;陰陽(yáng)理而后和。顯然,孔子以來(lái)的前儒家性別意識(shí)是周敦頤性別思想的重要思想資源,同時(shí)這些思想也對(duì)后世宋儒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
關(guān)鍵詞:周敦頤;《太極圖說(shuō)》;《通書(shū)》;性別意識(shí)
被尊為“道學(xué)宗主”的周敦頤開(kāi)顯宋明道學(xué)之活水源頭,其重要的理論貢獻(xiàn)在于構(gòu)建儒學(xué)之形上本體,并以陰陽(yáng)五行之理貫之天人,首發(fā)宋儒心性義理學(xué)之端。世人對(duì)其研究甚多,但極少有人涉及到他的性別思想。而實(shí)際上,他的兩本主要著作《太極圖說(shuō)》和《通書(shū)》中蘊(yùn)含著豐富的性別意識(shí)。本文旨在通過(guò)分析其兩本著作來(lái)探討其性別思想如何上承前儒,并具有自己的理論特征以及周敦頤的性別思想對(duì)后世宋儒所產(chǎn)生的深遠(yuǎn)影響。
一、陰陽(yáng)交感,化生萬(wàn)物
《宋史·周敦頤傳》中言周敦頤的《太極圖說(shuō)》是“明天理之根源,究萬(wàn)物之終始”。顯然,《太極圖說(shuō)》探究的是宇宙的本源及萬(wàn)物與人的生成過(guò)程。其宇宙生成圖式可用“太極——陰陽(yáng)——五行——萬(wàn)物”來(lái)表示。從中可看出他所推測(cè)的宇宙生成是由最原始的“無(wú)極而太極”開(kāi)始的,“無(wú)極而太極”是混沌而無(wú)形無(wú)限的原始物質(zhì),也是萬(wàn)物存有的最終根源。天地的本源是太極,而太極乃是無(wú)極,太極動(dòng)而生陽(yáng),動(dòng)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fù)動(dòng)。一動(dòng)一靜,互為根本,分化出陰陽(yáng)二氣。二氣的交互作用就生出五行,五行相互配合而形成四時(shí)與天地萬(wàn)物。由此可看出,在這一圖說(shuō)中,上溯宇宙本源,下極天地萬(wàn)物,生生不息,變化無(wú)窮的整個(gè)宇宙變化過(guò)程被包含在其中。同時(shí),在此過(guò)程中,離不開(kāi)陰陽(yáng)的交互感通作用,“有陰陽(yáng),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wàn)物。”在這里乾與坤,陰與陽(yáng)是作為對(duì)等的詞而提出,孤陰,孤陽(yáng)或陽(yáng)與陽(yáng),陰與陰都是不能化生萬(wàn)物。即從宇宙生成論的高度和意義上談陰陽(yáng)因相互差異而相互需要,相互補(bǔ)充,即陰陽(yáng)的相交相生,相生相濟(jì)。
同時(shí)在《通書(shū)》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周敦頤不少這方面的思想。如在《訓(xùn)化第十一》中有“天以陽(yáng)生萬(wàn)物,以陰成萬(wàn)物。生,仁;成,義也。”《家人睽復(fù)無(wú)妄第三十二》中引用《易經(jīng)》中的“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
小議周敦頤的教育倫理思想
論文關(guān)鍵詞:周軟頤;教育思想;倫理思想
論文摘要:我國(guó)古代教育家大多數(shù)人是以倫理為基礎(chǔ)來(lái)論述其他們的教育思想的.理學(xué)莫基人周孰頤,雖然沒(méi)有直接從事過(guò)教育工作,但他的教育倫理思想?yún)s十分豐富.因此.很有必要從教師職業(yè)倫理、教育目的倫理、道德教育倫理,教學(xué)倫理等方面對(duì)周孰頤的教育倫理思想進(jìn)行概括和總結(jié).這些思想中盡管夾雜著一些封建糟粕,但總體上是瑕不掩玉.,此外,關(guān)于周教頤的教育倫理思想的研究對(duì)于我們當(dāng)今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jìn)素質(zhì)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周教頤(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實(shí),避英宗諱,改名敦頤。他于宋真宗天喜元年生于道州(今湖南道縣)的營(yíng)樂(lè)里波溪保,又名波溪。
周敦頤長(zhǎng)期仕事主簿、縣令、參軍,州通判、提點(diǎn)刑獄等工作,每到一地都力主建學(xué)校,“個(gè)人亦收授生徒,講論學(xué)術(shù),培養(yǎng)人才,是一個(gè)官吏兼教育家。”周敦頤一生著述頗豐,留存至今的有《太極圖》、《太極圖說(shuō)》、《通書(shū)》以及少量的文、詩(shī)、賦、書(shū)集、題名等,皆收入《周敦頤集》中。
周敦頤改道教《無(wú)極圖》為論證宇宙本體及其發(fā)展的《太極圖》,建立了一個(gè)以孔孟正統(tǒng)思想為主的哲學(xué)理論體系,開(kāi)創(chuàng)了理學(xué)的先聲。周敦頤的教育倫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哲學(xué)理論體系中。筆者認(rèn)為,周敦頤的教育倫理思想主要包括教師職業(yè)倫理、教育目的倫理、德育倫理和教學(xué)倫理等方面。
一、教師職業(yè)倫理思想
愛(ài)蓮說(shuō)讀后感
周敦頤的《愛(ài)蓮說(shuō)》從“水陸草木之花,可愛(ài)者甚眾”。開(kāi)篇深沉大氣,既點(diǎn)明了《愛(ài)蓮說(shuō)》之蓮也屬水陸草木之花,也點(diǎn)明了蓮的可愛(ài),只是“甚蕃”者里的之一罷了。這為他下文的“予獨(dú)愛(ài)蓮”埋下了順理成章的伏筆。如此開(kāi)篇,出筆皆成不凡,吸人眼球也。接下去周敦頤并沒(méi)在甚蕃里糾纏,只是直接縮景,一句“晉陶淵明獨(dú)愛(ài)菊”,更加明確了題意,陶淵明可以愛(ài)菊抒懷,我怎不可獨(dú)愛(ài)蓮呢?
接下句“自李唐來(lái),世人甚愛(ài)牡丹”,像是重復(fù),但實(shí)為加深語(yǔ)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讓對(duì)比感更為強(qiáng)烈,為其求蓮之高潔鋪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頤本人獨(dú)愛(ài)蓮與晉陶淵明的愛(ài)菊避世不同,為保持一份高潔,寧愿終老南山。他要在塵世中當(dāng)個(gè)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這種在污世保持清白與獨(dú)自避世求真的心態(tài),與眾人皆羨富貴(牡丹)的從眾心態(tài)是有著思想境界上本質(zhì)的區(qū)別的。這為愛(ài)蓮說(shuō)所要表達(dá)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鋪墊。
下句周敦頤就直接進(jìn)入了正題“予獨(dú)愛(ài)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蓮而不妖,中通外直,可遠(yuǎn)觀而不可褻玩焉”,寫(xiě)蓮之語(yǔ),愛(ài)蓮之心,喻蓮之志,可謂一氣呵成,看似是對(duì)蓮的直觀描寫(xiě),其實(shí)字字句句皆是借蓮之表像傾訴心衷也。此運(yùn)筆之老到,實(shí)讓人嘆為觀止。可說(shuō)通篇讀者都無(wú)一絲喘息之機(jī)。語(yǔ)言超凡脫俗,而回味卻是雋永綿長(zhǎng),越品越有滋味。
收篇,周敦頤先用花進(jìn)行比喻,讓花的特性喻人,雖平淡,但比喻帖切,讓人讀來(lái)也別有一番滋味。“予謂菊,花之隱者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節(jié)“晉陶淵明獨(dú)愛(ài)菊;自李唐來(lái),世人甚愛(ài)牡丹;予獨(dú)愛(ài)蓮……”可謂渾然一體,不著絲毫痕跡。而更重要的是,借花喻人,將陶淵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榮華富貴的心態(tài)描寫(xiě)的淋漓盡致,而無(wú)一言直接指責(zé)。
周敦頤通過(guò)這樣的對(duì)比,將自已比喻為君子。君子難為,猶勝于避世也。從這一點(diǎn)來(lái)看,周敦頤有些孤芳自賞的意思。不過(guò)周敦頤也有些自知之明,接下去他發(fā)出了深沉的感嘆“菊之愛(ài),陶之后鮮有聞;蓮之愛(ài),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ài),宜乎眾矣”。是的,滾滾紅塵,又有多少人能避世以求一份真呢?晉有陶淵明,可現(xiàn)在卻聽(tīng)都沒(méi)聽(tīng)到還有人會(huì)這樣做的。或是像我一樣的,在塵世中能相守一份純凈的,有著我這樣追求君子風(fēng)范的,又有幾人?大多數(shù)的人,皆在紅塵世事中從眾罷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周敦頤是高傲的,他那種不從眾只求純凈的心態(tài),在碌碌塵世中是難能可貴的。他感嘆,是因?yàn)槭里L(fēng)日下,大多數(shù)人皆被世事玷染也。
此文高風(fēng)亮節(jié),清雅脫俗,精短,鋃鋃上口,實(shí)為古文中難得的精品短篇。而且一文雙解,內(nèi)容厚實(shí)而意境深遠(yuǎn)。加上其文近似白話,易讀易解,所以成了流傳后世膾炙人口的傳世佳品。在賞析此文的時(shí)候,如果能感動(dòng)于文中的志節(jié),這也就是讀此文的最佳所得吧。
品讀愛(ài)蓮說(shuō)個(gè)人體會(huì)
周敦頤的《愛(ài)蓮說(shuō)》從“水陸草木之花,可愛(ài)者甚眾”。開(kāi)篇深沉大氣,既點(diǎn)明了《愛(ài)蓮說(shuō)》之蓮也屬水陸草木之花,也點(diǎn)明了蓮的可愛(ài),只是“甚蕃”者里的之一罷了。這為他下文的“予獨(dú)愛(ài)蓮”埋下了順理成章的伏筆。如此開(kāi)篇,出筆皆成不凡,吸人眼球也。接下去周敦頤并沒(méi)在甚蕃里糾纏,只是直接縮景,一句“晉陶淵明獨(dú)愛(ài)菊”,更加明確了題意,陶淵明可以愛(ài)菊抒懷,我怎不可獨(dú)愛(ài)蓮呢?
接下句“自李唐來(lái),世人甚愛(ài)牡丹”,像是重復(fù),但實(shí)為加深語(yǔ)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讓對(duì)比感更為強(qiáng)烈,為其求蓮之高潔鋪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頤本人獨(dú)愛(ài)蓮與晉陶淵明的愛(ài)菊避世不同,為保持一份高潔,寧愿終老南山。他要在塵世中當(dāng)個(gè)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這種在污世保持清白與獨(dú)自避世求真的心態(tài),與眾人皆羨富貴(牡丹)的從眾心態(tài)是有著思想境界上本質(zhì)的區(qū)別的。這為愛(ài)蓮說(shuō)所要表達(dá)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鋪墊。
下句周敦頤就直接進(jìn)入了正題“予獨(dú)愛(ài)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蓮而不妖,中通外直,可遠(yuǎn)觀而不可褻玩焉”,寫(xiě)蓮之語(yǔ),愛(ài)蓮之心,喻蓮之志,可謂一氣呵成,看似是對(duì)蓮的直觀描寫(xiě),其實(shí)字字句句皆是借蓮之表像傾訴心衷也。此運(yùn)筆之老到,實(shí)讓人嘆為觀止。可說(shuō)通篇讀者都無(wú)一絲喘息之機(jī)。語(yǔ)言超凡脫俗,而回味卻是雋永綿長(zhǎng),越品越有滋味。
收篇,周敦頤先用花進(jìn)行比喻,讓花的特性喻人,雖平淡,但比喻帖切,讓人讀來(lái)也別有一番滋味。“予謂菊,花之隱者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節(jié)“晉陶淵明獨(dú)愛(ài)菊;自李唐來(lái),世人甚愛(ài)牡丹;予獨(dú)愛(ài)蓮……”可謂渾然一體,不著絲毫痕跡。而更重要的是,借花喻人,將陶淵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榮華富貴的心態(tài)描寫(xiě)的淋漓盡致,而無(wú)一言直接指責(zé)。
周敦頤通過(guò)這樣的對(duì)比,將自已比喻為君子。君子難為,猶勝于避世也。從這一點(diǎn)來(lái)看,周敦頤有些孤芳自賞的意思。不過(guò)周敦頤也有些自知之明,接下去他發(fā)出了深沉的感嘆“菊之愛(ài),陶之后鮮有聞;蓮之愛(ài),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ài),宜乎眾矣”。是的,滾滾紅塵,又有多少人能避世以求一份真呢?晉有陶淵明,可現(xiàn)在卻聽(tīng)都沒(méi)聽(tīng)到還有人會(huì)這樣做的。或是像我一樣的,在塵世中能相守一份純凈的,有著我這樣追求君子風(fēng)范的,又有幾人?大多數(shù)的人,皆在紅塵世事中從眾罷了。從這里可以看出,周敦頤是高傲的,他那種不從眾只求純凈的心態(tài),在碌碌塵世中是難能可貴的。他感嘆,是因?yàn)槭里L(fēng)日下,大多數(shù)人皆被世事玷染也。
此文高風(fēng)亮節(jié),清雅脫俗,精短,鋃鋃上口,實(shí)為古文中難得的精品短篇。而且一文雙解,內(nèi)容厚實(shí)而意境深遠(yuǎn)。加上其文近似白話,易讀易解,所以成了流傳后世膾炙人口的傳世佳品。在賞析此文的時(shí)候,如果能感動(dòng)于文中的志節(jié),這也就是讀此文的最佳所得吧。
文化思想對(duì)現(xiàn)代教育發(fā)展的影響
【摘要】湖湘文化形成的過(guò)程中,涌現(xiàn)了一大批注重教育,投身教育的先驅(qū)者,他們的教育理念歷時(shí)千年,形成了自己獨(dú)特的傳統(tǒng):重視學(xué)思并重與知行統(tǒng)一,重視獨(dú)立思考與理性批判。這對(duì)湖湘文化乃至整個(gè)中華文化都產(chǎn)生了影響。
【關(guān)鍵詞】湖湘文化;核心精神;本土教育
湖湘文化形成的過(guò)程中,涌現(xiàn)了一大批注重教育,投身教育的先驅(qū)者,他們的教育理念對(duì)湖湘文化甚至整個(gè)中華文化都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重視學(xué)思并重與知行統(tǒng)一,重視獨(dú)立思考與理性批判。其中周敦頤、王船山、魏源、曾國(guó)藩等人都是湖湘本土教育的開(kāi)拓者與踐行者,而岳麓書(shū)院更是此傳統(tǒng)的見(jiàn)證與代表。下面就幾位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對(duì)本土教育的影響進(jìn)行研究探討:
一、周敦頤純心修身,自學(xué)為主的教育思想對(duì)湖湘教育的影響
周敦頤(1017年-1073年,湖南省道縣人)的教育思想明確而突出,他認(rèn)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人向善,同時(shí)教育又是一種己立立人的事業(yè),要求施教者先要有所立、有所達(dá),才能夠去立人、達(dá)人。因此教學(xué)過(guò)程應(yīng)該是一個(gè)人格感化、以德服人的過(guò)程。所以優(yōu)秀的教育者不僅是向?qū)W生傳授知識(shí),還要以身作則,注重個(gè)人品德才能讓學(xué)生崇敬,從而達(dá)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育效果。周敦頤的教育內(nèi)容概括起來(lái)就是“純其心以修身”。他認(rèn)為要以仁義禮智為根本才能做到純心。周敦頤一直提倡“自學(xué)為主,重在啟發(fā)”的教學(xué)方法,教導(dǎo)學(xué)生以自學(xué)為主,鼓勵(lì)多進(jìn)行思考,采用啟發(fā)式教學(xué),并邀請(qǐng)當(dāng)時(shí)的學(xué)界名流來(lái)進(jìn)行講學(xué),始終堅(jiān)持開(kāi)明的教育方法。周敦頤這種講究人格氣節(jié)與操守的教育理念,對(duì)湖湘文化的發(fā)展和學(xué)子的成長(zhǎng)都產(chǎn)生了極大的影響。周敦頤重視教育和人才的培養(yǎng),建立了“景濂書(shū)院”,收徒眾多,其中包括程顥程頤兄弟倆,這是他在人才培養(yǎng)上最為突出的貢獻(xiàn)。周敦頤的一代代弟子們紛紛在湖南講學(xué)授徒,開(kāi)創(chuàng)了湖湘地區(qū)教育鼎盛的局面。兩宋時(shí)期湖南書(shū)院達(dá)到了近70所,其中岳麓書(shū)院和石鼓書(shū)院是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四大書(shū)院之二。周敦頤的三傳弟子胡安國(guó)父子在衡山創(chuàng)建的碧泉書(shū)院成了湖湘學(xué)派的教育基地,開(kāi)啟了湖湘學(xué)派的源流。周敦頤所開(kāi)創(chuàng)的教育事業(yè)繁榮局面為湖湘文化的鼎盛和湖南人才的鵲起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作為湖湘地區(qū)第一個(gè)本土大思想家,在他之前湖南人才“罕見(jiàn)史傳”數(shù)量上并無(wú)任何優(yōu)勢(shì),由于他對(duì)教育的推動(dòng),在他之后湖南逐漸成為一個(gè)引人注目的人才大省。周敦頤仿若湖南人才發(fā)展史上的一盞明燈,照耀著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學(xué)子不斷前行。在他的教育思想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下,湖湘地區(qū)在南宋、明后期和清朝中期涌現(xiàn)了三個(gè)人才高峰期,并且出現(xiàn)了湖南近現(xiàn)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體。
二、王船山“經(jīng)世致用”教育思想對(duì)湖湘教育的影響
理性情感分析論文
摘要:情感是孔子仁學(xué)的第一原則。理性和情感的關(guān)系是孔子仁學(xué)的主要課題。孔子以“仁是理性的普遍情感”這一論斷解決了理性和情感的統(tǒng)一。宋明新儒學(xué)以“生生”為核心,重新肯定了被佛學(xué)消解的理性和情感,在自然目的論中理性和情感完成了統(tǒng)一。
關(guān)鍵詞:理性;情感;仁;生
成德踐履,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這是儒家的不易信條。“親親、尊尊”的德性倫理,是儒家義理的核心內(nèi)容。在先秦,孔子首次為儒家的德性倫理提出了一個(gè)合理可靠的論證,其核心在于情感原則。在孔子之前,“人為什么要過(guò)道德生活”這個(gè)命題是和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天、帝關(guān)聯(lián)在一起的。孔子的仁學(xué),以情感為第一原則,以理性和情感的統(tǒng)一為主線,開(kāi)創(chuàng)了以“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須”為根本課題的儒家哲學(xué)。孔子的仁學(xué)中,天的人格神意味淡化,而道德實(shí)踐的主體-人的作用凸顯,以親情為起點(diǎn)的情感原則和有別于認(rèn)知理性的實(shí)踐理性原則雙翼并舉,最終指向一條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圣之路。道德何以可能?何以必須?要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個(gè)普遍性的原則。孔子從孝、悌這種真真切切的可感可驗(yàn)的家庭親情為出發(fā)點(diǎn),為他的仁學(xué)體系建立了一個(gè)普遍性原則-情感。孔子認(rèn)為,人是有情感的生靈,每個(gè)人從一出生,就有“三年之愛(ài)于其父母”[1],從出生到老死,時(shí)時(shí)刻刻都處于父母、兄弟、朋友等五倫的情感互動(dòng)之中。情感生活是每個(gè)人都無(wú)法逃避的;人又是有理性的生靈,每個(gè)人都能從“有限”的愛(ài)親推廣到“無(wú)限”的愛(ài)人。既然情感是必須的,而且又可以是普遍的,因此,德性倫理就完全可以也完全應(yīng)該有共同的,不因人、因時(shí)、因地而變的標(biāo)準(zhǔn)。這樣,孔子的仁學(xué)就為“人要過(guò)有德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個(gè)合理的論證。還應(yīng)該強(qiáng)調(diào)的是,情感原則,是內(nèi)在的。因此儒家哲學(xué)注重體驗(yàn)、體證。孔子為儒家哲學(xué)建立的主體性原則,以情感為核心的情感和理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對(duì)后世儒學(xué)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孟子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實(shí)際上就是指惻隱之情人皆有之。孟子的“義在內(nèi)”,“仁義內(nèi)在”的論述,是對(duì)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則的內(nèi)在性和普遍性的進(jìn)一步論證,而且有了新的內(nèi)容。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則,是從孝、悌的親情而來(lái)的,其主要特點(diǎn)是真實(shí)無(wú)偽,孔子是用“人之生也直”[1]這一說(shuō)法來(lái)說(shuō)明此點(diǎn)的。真實(shí)的情感在理性的提撕下成為“愛(ài)人”的普遍情感,并在實(shí)踐過(guò)程中,無(wú)過(guò)無(wú)不及地表達(dá)為禮儀,也就是外王層面。在孟子的時(shí)代,對(duì)“情”的討論進(jìn)一步深入了。(郭店竹簡(jiǎn)有很多這方面的資料)孟子承繼了孔子的義理規(guī)模,認(rèn)證了情感原則的內(nèi)在性和普遍性,但他比孔子更進(jìn)一步,他在源頭上,把情感認(rèn)定為是“善”的,以“惻隱之情”來(lái)講“情”,就是說(shuō),情之本是善的,這體現(xiàn)在他的性本善的說(shuō)法中。“性本善”就是“情本善”。愛(ài)是情,但是,愛(ài)也有個(gè)是非對(duì)錯(cuò),“今人乍見(jiàn)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nèi)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yù)于鄉(xiāng)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2]這樣的惻隱之情,已經(jīng)是知是知非的理性的情感了。也就是說(shuō),孟子把在孔子處必須交付給理性的,要在實(shí)踐過(guò)程中予以調(diào)節(jié)才得以無(wú)過(guò)無(wú)不及的情感簡(jiǎn)潔地濃縮到他的本善之情中。因此,在孟子的理論中,他很少言及“中庸”,很少言及在孔子處時(shí)時(shí)要言及的以理性調(diào)節(jié)情感。因?yàn)椋献拥谋旧浦橐呀?jīng)具有理性的品格,即無(wú)過(guò)無(wú)不及的中庸品格。這樣,在孟子處,重心就著落在如何把這個(gè)本善之情“擴(kuò)而充之”了。當(dāng)然,擴(kuò)而充之,這也涉及到了人的理性的作用。儒家義理的核心是情感和理性,即便象孟子,已經(jīng)把理性品格內(nèi)化在本善之情中,他也同樣強(qiáng)調(diào)在道德實(shí)踐過(guò)程中,理性是不可或缺的。《中庸》說(shuō),“喜、怒、哀、樂(lè)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喜怒哀樂(lè)當(dāng)然是情感。這是強(qiáng)調(diào)了情感的內(nèi)在性和普遍性。用“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的表述把孔子仁學(xué)的核心原則-情感原則完全肯定下來(lái),并做為成人之“道”的出發(fā)點(diǎn),同時(shí),強(qiáng)調(diào)“發(fā)而中節(jié)謂之和”,也就是說(shuō),在成德踐履的過(guò)程中,理性的調(diào)適功能同樣不可忽視,所以才要“修道之謂教”。《中庸》的思想和孟子的“性本善”的學(xué)說(shuō),都是在孔子開(kāi)出的義理框架內(nèi)的,核心在于情感原則,理性和情感的關(guān)系是其中的主線。通常把“天人合一”做為先秦儒學(xué)的指歸,似乎并不確切。先秦儒學(xué)是基于內(nèi)在情感的主體性道德哲學(xué)。先秦道家,基于批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形而上的負(fù)的方法”實(shí)現(xiàn)人對(duì)自身理性的否定性的超越,才是一種天人合一的理路。而先秦儒學(xué),從孔子開(kāi)始,把情感作為道德實(shí)踐的出發(fā)點(diǎn)后,天就基本上只是個(gè)虛位,而同時(shí),對(duì)人的理性是作正面的評(píng)述的,不然,何以言“克己復(fù)禮”?何以言“修身”?如果說(shuō)在孔子處,還有“天何言哉,四時(shí)行焉,百物生焉”[1]的感嘆,到了孟子和《中庸》,就只講知天、事天,講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是天下之達(dá)道,進(jìn)一步把情感原則作為道德踐履的出發(fā)點(diǎn)和核心,并把這一內(nèi)在而普遍性的原則完全肯定下來(lái)。正因?yàn)榍楦性瓌t,儒學(xué)才要講體驗(yàn)、體證,它有別于思辨的道家智慧,不需要形而上的體系的完美構(gòu)造;正因?yàn)閷?shí)踐理性原則,儒學(xué)才需要修身,才需要道德踐履,由此成圣之道是個(gè)死而后已的永無(wú)止境的過(guò)程,需要慎思,明辨和篤行,需要不斷學(xué)習(xí)和反省。而先秦道家則是種境界形態(tài)的思辨哲學(xué)。
漢代董仲舒以天人感應(yīng)說(shuō)來(lái)重建儒家的綱常倫理,是有其深刻的社會(huì)和政治原因的。在董仲舒的理論中,天是賞善罰惡的絕對(duì)至善的人格神。這是一種神學(xué)目的論思想。從儒學(xué)內(nèi)部的發(fā)展來(lái)看,他的這一理論是和孔孟儒學(xué)異質(zhì)的,關(guān)鍵之處就在于他不象孔孟那樣把情感作為綱常倫理的出發(fā)點(diǎn)和核心原則。因此,他就必須張揚(yáng)人的理性。在神學(xué)目的論的大框架下,他同時(shí)極力張揚(yáng)了作為道德實(shí)踐主體的理性,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他并沒(méi)有背離儒家,而且,還作出了他的獨(dú)特貢獻(xiàn)。同時(shí),他的目的論思想,在一定意義上,為宋明理學(xué)的自然目的論提供了思路。
魏晉間玄學(xué)思潮起。有無(wú)之辨和名教與自然的關(guān)系成為這一時(shí)代的主要課題。在政治和社會(huì)層面上,儒家的綱常倫理并沒(méi)有受到大的挑戰(zhàn)。而如果純粹從思想史的層面看,玄學(xué)反倒為儒家的道德倫理作了形而上的論證。這是一種時(shí)代背景下的儒道合流。玄學(xué)為儒家道德哲學(xué)提供了一種思辨的方法論,到了宋明理學(xué)時(shí)期,就發(fā)展為儒學(xué)的體用論了。郭象的理論,認(rèn)為名教和自然不是對(duì)立的,而是統(tǒng)一的,裴頠的崇有論則認(rèn)為名教不可越,而王弼的貴無(wú)論是最具有形而上的理論色彩的,認(rèn)為必須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是,王弼仍然聲稱(chēng)孔子是圣人。圣人有情無(wú)情論,也是當(dāng)時(shí)論爭(zhēng)的一個(gè)大問(wèn)題。我們可以看到,孔孟儒學(xué)的兩個(gè)基本要素理性和情感,在玄學(xué)思潮中都得到了相當(dāng)充分的討論。貴無(wú)論和貴有論,實(shí)際上都對(duì)人的理性能力進(jìn)行了深入探討,再加上情感問(wèn)題的重新提出,自然這一概念的重新闡釋?zhuān)@些都開(kāi)啟了有宋一代新儒學(xué)的先驅(qū)者們的思路。
真正對(duì)儒學(xué)義理構(gòu)成挑戰(zhàn)的是佛學(xué)。佛教于東漢時(shí)期傳入中國(guó),魏晉期間有個(gè)大發(fā)展,而到了隋唐,是其鼎盛時(shí)期。華嚴(yán)宗、唯識(shí)宗、天臺(tái)宗,尤其是禪宗的盛行,使得儒家道德哲學(xu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在現(xiàn)實(shí)的社會(huì)政治層面,儒家的綱常倫理依然是占統(tǒng)治地位,但是,有識(shí)之儒者清醒地看到,如果儒家仁義的內(nèi)圣之學(xué)已然動(dòng)搖,那綱常倫理的外王層面的大廈就岌岌可危了。韓愈、李翱等人作了重建人文價(jià)值體系的嘗試。韓愈的《原道》辟頭就說(shuō),“博愛(ài)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他在《原性》中進(jìn)一步提出性三品說(shuō),認(rèn)為性是與生俱來(lái)的,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性的內(nèi)容是仁義禮智信,情則包括喜怒哀懼愛(ài)惡欲。李翱在《復(fù)性書(shū)》中,則明確提出,要為儒家義理立性命之源,他說(shuō),“人之所以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他們?cè)噲D找到一個(gè)內(nèi)在的普遍性的原則,重新來(lái)論證儒家德性倫理。他們?cè)谌寮医?jīng)典中以《大學(xué)》和《中庸》為據(jù),這也是一個(gè)貢獻(xiàn)。從這個(gè)意義上來(lái)說(shuō),他們是上承先秦儒學(xué),而下啟宋明理學(xué)的。然而,他們對(duì)孔孟儒學(xué)的義理核心并沒(méi)有把握住,對(duì)佛學(xué)之于儒學(xué)義理的真正挑戰(zhàn)之處看得不清,因此,他們沒(méi)能建立一個(gè)符合時(shí)代要求的新儒學(xué)。這個(gè)歷史性任務(wù)有待于來(lái)者。
傳統(tǒng)之“樂(lè)”的特征論文
摘要:傳統(tǒng)之“樂(lè)”認(rèn)為,“樂(lè)”是“安而不憂”、“善美愉悅”與“自然順適”心理體驗(yàn);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風(fēng)輕”、“率性而為”人生狀態(tài);還是過(guò)程的、信仰的、指向未來(lái)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與信仰。在傳統(tǒng)之“樂(lè)”這種理想與信仰包括兩個(gè)方面:“天人合一”與“各得其所”。通過(guò)分析,傳統(tǒng)之“樂(lè)”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個(gè)方面即“靜底”、“善底”、“天底”、“和底”。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之“樂(lè)”;人生幸福
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樂(lè)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樂(lè)也。
暫且不論此“樂(lè)”因何而來(lái),先看此“樂(lè)”以什么樣的形式,或在什么樣的形象進(jìn)入到我們心中。這“樂(lè)”既不是突然到來(lái),也不是猛然闖進(jìn),而是“天然自有”的,可謂“真樂(lè)天成”。似飄然而至,但又不夠確切,因?yàn)榇恕皹?lè)”乃我自有之,非從外來(lái)。同時(shí),也說(shuō)明并非由人在心中生一個(gè)“樂(lè)”來(lái),而是本來(lái)就以某種形式潛在著,只是沒(méi)到一定時(shí)候不會(huì)顯現(xiàn)。
依曹端所說(shuō):已經(jīng)有一個(gè)“樂(lè)”存在于心中了,想要幸福就只要想法子把心中那個(gè)“樂(lè)”找出來(lái)就行了。曹端所說(shuō)的這種“樂(lè)”真得存在嗎?
實(shí)際,這正是儒家之“樂(lè)”的一個(gè)重要特點(diǎn):幸福往往不在于外在客觀物事,而在于內(nèi)心,只要養(yǎng)性就可以獲得真樂(lè)。這正是一種“樂(lè)”的一種即境界之樂(lè),一種非物質(zhì)欲望之滿足式的幸福,也正是我們要談?wù)摰摹皹?lè)”或幸福。
宋學(xué)文化特點(diǎn)論文
宋代是春秋戰(zhàn)國(guó)以后中國(guó)哲學(xué)思想另一個(gè)繁榮的時(shí)代。理學(xué)是宋代哲學(xué)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晉以來(lái),傳統(tǒng)儒學(xué)不斷受到來(lái)自玄學(xué)、佛教的挑戰(zhàn);隋唐時(shí)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為當(dāng)時(shí)主導(dǎo)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學(xué)家便在吸收佛、道兩家的思想的基礎(chǔ)上,對(duì)古典儒學(xué)作了新的詮釋、發(fā)展和重建,創(chuàng)立了理學(xué)。理學(xué)在宋代也稱(chēng)“道學(xué)”,近代以來(lái)則稱(chēng)為“新儒學(xué)”。理學(xué)的基本特點(diǎn)是把儒家的價(jià)值理念本體化,并貫穿至心性理論和為學(xué)功夫。理學(xué)作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對(duì)民眾生活有其引導(dǎo)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禮》對(duì)宋代社會(huì)觀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當(dāng)?shù)挠绊憽D纤瓮砥冢韺W(xué)成為中國(guó)的正統(tǒng)思想,自此支配中國(guó)文化數(shù)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國(guó)歷史上士大夫階層的黃金時(shí)代,宋太祖立國(guó)后,為了避免北宋成為五代之后第六個(gè)短命王朝,積極推行“重文輕武”政策,防止軍人奪權(quán)或割據(jù)。而讀書(shū)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過(guò)科舉考試,也就進(jìn)身士大夫階層,獲得較高的社會(huì)及政治地位,于是棄武習(xí)文成為社會(huì)風(fēng)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興辦各級(jí)官學(xué),帶動(dòng)了重視教育的社會(huì)風(fēng)氣。但人口的增長(zhǎng)和官府財(cái)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會(huì)需求遠(yuǎn)不能滿足,于是私人興辦的講學(xué)書(shū)院應(yīng)運(yùn)而發(fā)展起來(lái)。同時(shí),書(shū)院作為與官學(xué)不同的社會(huì)文化力量,與理學(xué)發(fā)展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理學(xué)家批評(píng)科舉與官學(xué)教育只引導(dǎo)學(xué)子追求功名利祿,他們大興書(shū)院講學(xué)之風(fēng),以書(shū)院為宣傳理學(xué)的基地,從而擴(kuò)大了書(shū)院的影響,導(dǎo)致了南宋書(shū)院的鼎盛。南宋的書(shū)院幾乎取代了官學(xué),成為當(dāng)時(shí)的主要教育機(jī)構(gòu)。書(shū)院,最早見(jiàn)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辦的書(shū)院只是藏書(shū)與修書(shū)的場(chǎng)所。宋初有六大書(shū)院,江西廬山的白鹿洞書(shū)院、潭州的岳麓書(shū)院、河南應(yīng)天府的睢陽(yáng)書(shū)院、河南登豐的嵩陽(yáng)書(shū)院、湖南衡陽(yáng)的石鼓書(shū)院以及江寧茅山書(shū)院。白鹿洞書(shū)院、岳麓書(shū)院創(chuàng)建于宋開(kāi)寶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復(fù)白鹿洞書(shū)院,興學(xué)講授;紹熙五年(1194),朱熹又復(fù)興岳麓書(shū)院,積極講學(xué),對(duì)當(dāng)時(shí)書(shū)院的發(fā)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為白鹿洞書(shū)院擬定的學(xué)規(guī),成為各書(shū)院的標(biāo)準(zhǔn)規(guī)范,為書(shū)院的制度化建設(shè)作出了重要貢獻(xiàn)。朱熹知南康軍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書(shū)院講學(xué)。朱熹任湖南安撫使時(shí),在岳麓書(shū)院講學(xué)授徒,雖為時(shí)僅兩月,但影響極大。由此可見(jiàn)理學(xué)家對(duì)書(shū)院建設(shè)的重要推動(dòng)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縣官學(xué)興起,書(shū)院的發(fā)展一度消沉,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jì),北宋時(shí)期建立的書(shū)院,約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學(xué)大師書(shū)院講學(xué)的影響下,僅江西的書(shū)院便達(dá)160余所。有人根據(jù)各省方志統(tǒng)計(jì),兩宋書(shū)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華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來(lái)的思想文化的發(fā)展也見(jiàn)證了中國(guó)歷史和文化變遷的新階段。北宋文學(xué)的古文運(yùn)動(dòng)和儒家思想的新開(kāi)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發(fā)展是理學(xué),它特別重視古典儒家的《論語(yǔ)》《孟子》《大學(xué)》《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釋和發(fā)展,并最后由朱熹把這四種著作合編為《四書(shū)》的新經(jīng)典體系。理學(xué)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彌補(bǔ)和發(fā)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環(huán)節(jié),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應(yīng)對(duì)佛道的挑戰(zhàn),故理學(xué)的興起標(biāo)志著唐代以來(lái)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結(jié)構(gòu)進(jìn)入了一個(gè)新的階段。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是北宋著名的理學(xué)家,也是理學(xué)的創(chuàng)立者。南宋時(shí)期,朱熹繼承了程顥、程頤“洛學(xué)”,又吸收周敦頤的“濂學(xué)”、張載的“關(guān)學(xué)”等理學(xué)學(xué)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學(xué)之大成,形成了“理學(xué)”的主流;陸九淵則建立了“心學(xué)”的體系,也有很大影響。宋代所開(kāi)創(chuàng)的理學(xué),后來(lái)成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導(dǎo)地位的學(xué)術(shù)體系,構(gòu)成了11世紀(jì)以來(lái)中國(guó)思想史的主流發(fā)展。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shuō)》是《太極圖》的解說(shuō),這是一個(gè)寫(xiě)意圖,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無(wú)極而為太極”的最原始的本體狀態(tài);第二個(gè)圈是坎離二卦的交合圖式,表示陽(yáng)動(dòng)陰?kù)o,也就是陰陽(yáng)二氣的分化;第三個(gè)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個(gè)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類(lèi)的產(chǎn)生;第五個(gè)圈表示萬(wàn)物化生。此圖從總體上顯示了“太極”產(chǎn)生世界的整個(gè)過(guò)程。
書(shū)院文化與環(huán)境藝術(shù)關(guān)系論文
處于我國(guó)中原地帶的河南古代書(shū)院,都很講究選址,刻意營(yíng)造一種恬靜宜人的意境,如陽(yáng)明書(shū)院建在大山、紫云書(shū)院建在紫云山、百泉書(shū)院建在百泉;至少也要符合鬧中取靜的要求。再如靈芝書(shū)院建于新安城北芝泉之畔、弋陽(yáng)書(shū)院建于潢川城南原清真大寺廢墟、寡過(guò)書(shū)院建于長(zhǎng)垣縣城東南隅。
白鹿洞書(shū)院的山水環(huán)境是古代文人仕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著名理學(xué)家、教育家朱熹,(字考亭,號(hào)紫陽(yáng))。第一次來(lái)到白鹿洞書(shū)院時(shí),對(duì)它所處的環(huán)境贊美有加,感嘆“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環(huán)合,無(wú)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xué)遁跡之所”,并自任洞主,廣招門(mén)徒,制定學(xué)規(guī),致力于白鹿洞書(shū)院的振興。
當(dāng)時(shí)間的跨度進(jìn)入九十年代,聯(lián)合國(guó)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huì)專(zhuān)家評(píng)估廬山申報(bào)世界遺產(chǎn),首先考察的就是白鹿洞書(shū)院。他們對(duì)書(shū)院古建筑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贊不絕口,認(rèn)為它最能代表廬山“以其獨(dú)特的方式,融會(huì)在具有突出價(jià)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極高美學(xué)價(jià)值、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相聯(lián)的世界文化景觀”的特征。
儒學(xué)崇尚天人合一、自然比德、人與自然的親和。儒學(xué)之祖孔子在《論語(yǔ).雍也》中曰:“智者樂(lè)水,仁者樂(lè)山。智者動(dòng),仁者靜。智者樂(lè),仁者壽”,以自然山水來(lái)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德。山水本無(wú)情,而從儒家道統(tǒng)上來(lái)說(shuō),山水映照人之智和仁,山水即文章,充滿了哲理和寓意。
北宋歐陽(yáng)修《醉翁亭記》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一句,把歐陽(yáng)修這一文人仕子寄情山水,安民樂(lè)豐的內(nèi)心世界描寫(xiě)得淋漓盡致。醉翁亭因歐陽(yáng)修及其《醉翁亭記》而聞名遐邇,數(shù)百年來(lái)雖然歷遭變劫,但終不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對(duì)聯(lián)所言:“翁去八百載,醉鄉(xiāng)猶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明代文震享的《長(zhǎng)物志》稱(chēng)“居山水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白鹿洞書(shū)院“傍山帶水,盡幽居之美”,其間充滿詩(shī)情畫(huà)意,是隱逸清淡之士詠?lái)灥慕^佳境地。
詮釋書(shū)院文化與環(huán)境藝術(shù)論文
處于我國(guó)中原地帶的河南古代書(shū)院,都很講究選址,刻意營(yíng)造一種恬靜宜人的意境,如陽(yáng)明書(shū)院建在大山、紫云書(shū)院建在紫云山、百泉書(shū)院建在百泉;至少也要符合鬧中取靜的要求。再如靈芝書(shū)院建于新安城北芝泉之畔、弋陽(yáng)書(shū)院建于潢川城南原清真大寺廢墟、寡過(guò)書(shū)院建于長(zhǎng)垣縣城東南隅。
白鹿洞書(shū)院的山水環(huán)境是古代文人仕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著名理學(xué)家、教育家朱熹,(字考亭,號(hào)紫陽(yáng))。第一次來(lái)到白鹿洞書(shū)院時(shí),對(duì)它所處的環(huán)境贊美有加,感嘆“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環(huán)合,無(wú)市井之喧,有泉石之勝,真群居講學(xué)遁跡之所”,并自任洞主,廣招門(mén)徒,制定學(xué)規(guī),致力于白鹿洞書(shū)院的振興。
當(dāng)時(shí)間的跨度進(jìn)入九十年代,聯(lián)合國(guó)世界遺產(chǎn)委員會(huì)專(zhuān)家評(píng)估廬山申報(bào)世界遺產(chǎn),首先考察的就是白鹿洞書(shū)院。他們對(duì)書(shū)院古建筑優(yōu)美的自然環(huán)境贊不絕口,認(rèn)為它最能代表廬山“以其獨(dú)特的方式,融會(huì)在具有突出價(jià)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極高美學(xué)價(jià)值、與中華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相聯(lián)的世界文化景觀”的特征。
儒學(xué)崇尚天人合一、自然比德、人與自然的親和。儒學(xué)之祖孔子在《論語(yǔ).雍也》中曰:“智者樂(lè)水,仁者樂(lè)山。智者動(dòng),仁者靜。智者樂(lè),仁者壽”,以自然山水來(lái)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德。山水本無(wú)情,而從儒家道統(tǒng)上來(lái)說(shuō),山水映照人之智和仁,山水即文章,充滿了哲理和寓意。
北宋歐陽(yáng)修《醉翁亭記》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一句,把歐陽(yáng)修這一文人仕子寄情山水,安民樂(lè)豐的內(nèi)心世界描寫(xiě)得淋漓盡致。醉翁亭因歐陽(yáng)修及其《醉翁亭記》而聞名遐邇,數(shù)百年來(lái)雖然歷遭變劫,但終不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對(duì)聯(lián)所言:“翁去八百載,醉鄉(xiāng)猶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明代文震享的《長(zhǎng)物志》稱(chēng)“居山水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白鹿洞書(shū)院“傍山帶水,盡幽居之美”,其間充滿詩(shī)情畫(huà)意,是隱逸清淡之士詠?lái)灥慕^佳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