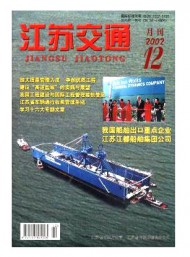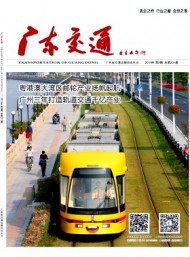交通事故賠償起訴書范文
時間:2023-05-06 18:21:3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交通事故賠償起訴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據《南方日報》報道 曠日持久的深圳居民蔡壯欽狀告奔馳公司產品質量糾紛案終于有了結果。東莞市中級人民法院日前作出一審判決:由于轎車安全帶斷裂加之氣囊不能適時彈出,導致駕駛員在交通事故中死亡,奔馳公司應對其涉案車輛產品質量缺陷承擔責任,賠償受害人由此造成的物質和精神損失28萬多元。這是中國大陸首例消費者狀告奔馳公司勝訴的案例。
1999年1月31日下午,深圳居民蔡壯欽的長子蔡衍鵬開著奔馳S320轎車在廣深高速公路虎門路段發生交通事故,車子撞斷護欄后墜入路下水溝,安全帶斷裂,氣囊未彈出,蔡衍鵬當場死亡,同車兩人受傷。事后,蔡壯欽認為,奔馳車安全氣囊未彈出是造成孩子死亡的重要原因。在交涉一年無果的情況下,2000年1月,蔡先生將奔馳的生產商戴姆勒?克萊斯勒股份公司告上法庭(見2000年1月12日本報報道)。由于奔馳方面堅持要求以外交方式將起訴書送達德國總部,所以東莞中院立案后遲遲不能開庭,僅起訴書就送了7次。該案成為東莞中院碰到的最棘手的馬拉松式跨國糾紛
篇2
內容摘要:刑事審判權范圍尚未有明確與統一的定位,文章僅僅是擇取現實糾結的角度,分三個層面對此問題進行了總結與梳理。糾結之一,附帶民事訴訟被告準入規則不一致。糾結之二,贓款贓物的處理與民事訴訟的“不和”。糾結之三,在罪名變更與累犯兩個問題上暴露定罪量刑權與公訴權的相互僭越。本文針對不同情況主要從程序的合理設置入手,以求法律上的衡平。其一,附帶民事訴訟被告的準入規則統一為“有責主體”;附帶民事訴訟被告的追加要遵循一事不再理原則并配套相關的程序。其二,贓款贓物可以一并判決退賠的,一并在刑事文書中予以判決;不能判決的,待刑事判決生效后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訴訟而不需等待追贓完畢。其三,罪名變更要經歷一定的辯論程序;累犯要分情況在起訴書中予以認定。
一、刑事審判權范圍的內涵
(一)審判權的性質與范圍
法學理論中有一種社會契約論,即社會成員認識到了集體力量的強大,他們就集合起來,通過彼此之間的默契,把自己的權利交給國家。國家就擔負起了保護社會成員的義務,國家通過審判的方式來保護社會成員,這就是審判權。因此,審判權在性質上是國家權力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另一方面,為了防止國家權力、審判權力的濫用,以“依法治國、法治社會”為理念基礎的社會制度應世而生。審判權必然要受法律的規范,法律也必然影響著審判權的范圍命運。在實證法中,審判權限主要集中于憲法和程序法的規則中。間接地,實體法權利也決定著審判權的范圍。因此,現行實體法律規范和程序法律規范,正是本文研究審判權的范圍所在。
(二)刑事審判權的范圍
刑事審判權的范圍,從審判權的外延而言,是指區別于訴權、行政權、檢察權,以定罪與量刑為核心的案件審判權;從審判權的內涵而言,是指區別于民事審判權、行政審判權,以刑事案件的處理為核心的案件審判權。因此,刑事審判權的范圍,是圍繞被告人,以定罪量刑為核心的審理權。
審判權,顧名思義,是行使對于案件的審查權與裁判權,查明案件的法律事實并對案件依據法律作出裁判。刑事案件審判權的范圍,一方面涉及刑事案件的審查權,如對刑事案件立案的審查、對證據的審查以及對程序的審查。另一方面,也是最核心的方面,刑事審判權需要根據查明的事實對案件作出裁判,具體又可分為對實體事項的裁判權和對部分實體事項、程序事項的裁定權、對純粹程序事項的決定權。前者主要以定罪、量刑為核心,對被告人的罪名、刑期、贓物的處理以及追繳或者賠償(涉及附帶民事)等問題作出判決;后者如裁定維持原判或發回重審、裁定減刑、假釋以及決定轉為普通程序等。可見,刑事審判權的范圍在廣義上是一個非常寬泛的內容。此處,筆者僅僅是從狹義的實體事項判決權角度,對刑事審判權的范圍問題做進一步的分析與思考。具體而言,主要是涉及刑事審判權范圍中的附帶民事訴訟被告、贓物贓款的處理以及定罪量刑的兩個問題在實踐中遭遇的糾結。
二、糾結1——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個人管轄權”囧境
刑事審判權的一項特殊之處就是還享有對附帶民事案件的審判權,即不僅僅涉及對犯罪案件的處理,還涉及到對一些民事侵權案件的處理。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也有其“管轄權”,當然這里的管轄權不是指各級人民法院之間或同級人民法院之間受理一審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權限,而是筆者特指附帶民事案件與普通民事案件的分工和權限。法院要對案件具有管轄權,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即法院對所涉案件具有“主題管轄權”(subject matter jurisdiction),即法院具有審理該類型的案件的權力,同時,法院還需對案件當事人具有“個人管轄權”(personal jurisdiction),即法院具有對訴訟中涉及的當事人作出影響其權利義務的裁決的權力。那么,法院對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的哪些當事人具有“個人管轄權”,特別是哪些被告人可以區別民事訴訟而進入刑事訴訟程序,實踐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困惑。
(一)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范圍問題
附帶民事訴訟,是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而提起的賠償訴訟。雖然是以犯罪行為為核心,但是具體起訴的被告人又不限于作出犯罪行為的刑事被告人。根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十六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的人包括:刑事被告人(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及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其他共同致害人;未成年刑事被告人的監護人;已被執行死刑的罪犯的遺產繼承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案件審結前已死亡的被告人的遺產繼承人;其他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可見,對附帶民事訴訟的的被告范圍認定不是以“行為主體”為標準(即誰犯罪,誰賠償),而是以“責任主體”為標準(即誰有責,誰賠償)。然而,實踐中對被告范圍問題,特別是作為共同被告問題,何去何從,真有種讓人霧里看花的感覺。
以下,筆者以經常處理的交通肇事罪案件為例,來說說關于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那些事兒。
1.肇事司機與車主不是同一人,車主是否可以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共同被告?從“責任主體”標準入手,車主承擔責任的法律依據決定了其是否應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共同被告。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一條規定了“承擔賠償責任的機動車駕駛員暫時無力賠償的,由駕駛員所在單位或者機動車的所有人負責墊付”,即車主的墊付責任。但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取消了這一規定,因此對于車主是否應當承擔責任人,承擔怎樣的責任,都不一而足。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解釋,對以下三種情況下車主的賠償責任做出了具體的規定:由于車輛被盜而導致司機與車主不是同一人的,車主不承擔賠償責任;由于連環購車未辦理過戶手續而導致司機與車主不是同一人的,車主不承擔賠償責任;由于使用分期付款購買的車而導致司機與車主不是同一人的,車主不承擔賠償責任。另外,車輛發生借用、租賃、承包、掛靠等情況的,省高院以會議紀要、批復等文件形式,根據各種情況分散地規定了車主的連帶責任作為實踐操作的依據,但具體在判決書的制作過程中并不能予以引用。可見,關于車主責任的問題在2008年之后,雖然有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解釋,但都規定的是不賠的責任;而省高院的文件雖規定了賠償的責任,但效力范圍僅限于一省之內。當然,這些問題將隨著2010年7月1日侵權責任法的施行而畫上句號。
2.雇主雇傭雇員的的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雇主是否可以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共同被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九條規定,雇員在從事雇傭活動中致人損害的,雇主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雇員因故意或者重大過失致人損害的,應當與雇主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因此,從法律規定角度而言,雇員(即駕駛員)交通肇事的,雇主亦是附帶民事訴訟中依法負有賠償責任的人,應該作為共同被告。但是司法實踐中,一般卻傾向于不將雇主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共同被告。
3.交通肇事中,保險公司可否作為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要求其承擔相應的保險責任。
筆者認為,在交通肇事罪中,駕駛員也即被告人往往負事故的主要責任或者全部責任,其投保的保險公司應在有效保險合同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但是,此處保險公司的賠償責任是基于保險合同的相對性,由保險公司向投保人承擔,而不是向其他人承擔。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有責賠償主體,應是指應向被害人承擔賠償責任的主體。因此,保險公司是賠償責任的主體,但不是向刑事被害人賠償的主體。也即,這里其實存在兩個不同的訴訟——被害人與肇事人的侵權之訴和肇事人與保險公司的合同之訴。故,從理論上來講,保險公司不宜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實踐中,對該問題的操作也經歷了一番“變革”,即由起先的不允許將保險公司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到現在慢慢地允許將交強險中的保險公司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但不允許將商業險中的保險公司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
以上是筆者舉例的三種情況,結論似乎是對被害人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主體未必是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而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又未必是對被害人應承擔賠償責任的主體。
(二)對另案處理的同案犯可否追訴
實踐中,偶爾會出現這樣的情況(case1):a(已判決)、b(在逃另案處理)共同犯罪給c造成了經濟損失。c在對a的刑事訴訟中已經提起過附帶民事訴訟并形成了生效的法律文書(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書或調解書),但未能得到全額賠償,其在b歸案后是否可以對b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即,被害人是否可以追訴另案處理的同案犯,要求其承擔共同賠償責任。答案只能是可以或者不可以。
如果可以追訴,那么追訴的程序怎么走?如果仍然是按照附帶民事訴訟進行,那么在前案已經就附帶民事訴訟問題判決或者調解結案的,后案又該如何處理?比如,前案已經判決的,后案的附帶民事訴訟既不合適判決也不調解。因為,如果再次判決或者調解,則將出現因同一訴訟請求形成前后兩份不同的法律文書,嚴重損害了先前生效法律文書的既判力。如果前案已經調解的,后案同樣也不適合判決或者調解。如果不可以追訴,駁回其起訴的理由是什么?不能追訴做是否違背了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則,損害了被害人的合法利益?這些問題都將是看似無法解決的死結。
以上是我們從事后的角度來看待和思考問題。那么,我們能否從事前角度來預防此類尷尬情境的出現呢?比如,再遇到這類情形時,我們已經預料到了將來可能出現被害人追訴b的情況,那么在對a的附帶民事訴訟過程中,能否通知c追加b為共同被告?從民事訴訟程序設計的角度而言,a、b作為共同侵權人,c僅對a提起民事侵權之訴,人民法院應當通知其追加被告b。即,作為一個共同侵權之訴,其訴的標的具有不可分性,是必要共同訴訟,人民法院必須合一審理和判決,以避免同一方多數人各自為訴訟行為的結果所形成的裁判抵觸。可見,民事訴訟的程序設計已經考慮到了類似本案的情況。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法院通知c追加b作為共同被告,c可能同意追加,也可能不同意追加。
情景一:c同意追加。然而b因為在逃而無法參加訴訟。所幸,民事訴訟還設計了缺席判決制度,對b缺席的情況經法定傳喚之后仍可以繼續開庭審理。但是,最主要的問題還是在開庭之后,法院就處在既不能判決也無法調解的嚴重問題。因為b同時還是刑事被告人,其是為了躲避刑事責任才在逃的,法院處理此類刑民共存的案件時,有一個先刑后民的原則,即要先對其刑事部分作出判決,再對其民事部分作出判決。因此,對于在逃的b,由于其刑事部分尚未判決,民事部分自然也不能作出判決。先刑后民的理念強調的是刑事未判,民事也不能判,但可以調解,問題是b人都無法找到,自然也就不可能調解。
情景二:c不同意追加。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則,則法院應通知b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b在逃,因此存在通知不能的情形。
綜上,無論從事前還是事后的角度,我們似乎都難以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三、糾結2——贓款贓物的刑事審判權與民事侵權之訴的糾纏
根據法律的相關規定,贓款贓物可以是指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刑法第64條),可以是指公、檢、法扣押、凍結的被告人的財物(刑訴法第198條),也可以是指追繳的財物(《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76、277條)。因筆者要討論是贓款贓物的刑事審判權與民事侵權之訴的關系,故此處所謂的贓款贓物也主要限于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但實為被害人所有的合法財物。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第一條規定,因人身權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質損失或者財物被犯罪分子毀壞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同時,該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被追繳、退賠的情況,人民法院可以作為量刑情節予以考慮。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這些規定給我們的一個直接信號就是,對于被犯罪分子非法侵占和處置的被害人的財物,只有先經過追贓程序且追贓不能的情況下,才可以另行提起民事侵權之訴。這一方面可能是基于對先刑后民的規則顧慮,但另一方面也無疑給被害人維權設置了一道無形的門檻。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法院認為屬于追臟范圍而不予受理,而偵查機關認為屬于可以提起民事訴訟的范圍而追繳已基本無望的尷尬局面。難怪有同仁質疑其是“刑事優先處理的原則似乎早已習慣性的忽悠了我們民事權利的獨立性”。贓款贓物的刑事審判權與民事侵權之訴何去何從,我們還在反思的路上。
四、糾結3——定罪量刑權與公訴權的“灰色”地帶
定罪量刑權是一個很豐富的研究課題。這里,筆者主要觸及的是與公訴權相聯系的兩個方面,及法院的直接變更罪名權與檢察院的累犯認定問題。
(一)刑訴法162條——審判權對公訴權的僭越之嫌
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2條第(一)項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76條第一款第(二)項的規定,法院在刑事公訴案件審理完畢后,認為檢察機關起訴指控的罪名與法院審理查明的犯罪事實不符,法院直接根據審理查明的事實、證據重新認定罪名,對被告人作出有罪判決。該條規定,向來為司法界所詬病。
上述條款規定了法院直接變更罪名的權力,其本意可能是提高訴訟效率、節約司法資源,但卻背負了審判權僭越公訴權的巨大嫌疑。實際上,上述條款的規范不僅僅是偷襲了公訴權,還一定程度地剝奪了辯護人和被告人的正當辯護權。缺乏必要的辯論程序,無疑是法院直接變更罪名權的阿基里斯之踵。
(二)累犯問題——公訴權對審判權的逾越之疑
累犯(一般累犯),是指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犯罪分子,刑罰執行完畢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內再犯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的犯罪分子。對于累犯這個概念基本沒有異議,但對于實踐認定累犯這個問題還是存有一定的疑問。
例如(case2),甲2004年曾因犯非法拘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又因盜竊2000元財物被提起公訴。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的起訴書上除了寫明甲構成盜竊罪,提請法院依法判處外,一般還會另寫上這么一句“……甲系累犯……”。這里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甲因一個犯罪行為而被兩次加重刑罰,是否有重復評價的嫌疑;二是后罪“應當判處有期徒刑”的認定主體是誰。如上述案例中甲盜竊2000元財物(盜竊罪的起點數額)的量刑一般是拘役四個月,由于要認定累犯,因此其基礎刑起碼要提升至有期徒刑六個月(第一次加重),之后由于是在五年內再犯應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之罪,系累犯,應當從重處罰并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第二次加重)。這樣對于甲來說是明顯不公平的。再者,從行使公訴權的角度而言,公訴權是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等部門偵查終結后移送起訴的案件,進行審查,并依法作出提起公訴、不起訴的決定的權力。公訴權其本質仍是一種請求權,只能提請法院依法判決。因此,筆者認為對于累犯中的后罪是否“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認定主體仍在法院。除非該罪適用的法定刑幅度已經毫無爭議的規定只是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罰,否則檢察院在起訴書上不宜直接認為是累犯。
五、刑事審判權范圍的法律衡平追求
(一)附帶民事問題的抉擇
1.統一附帶民事訴訟被告人的“入門”標準。既然規定傾向于“責任主體”的標準,那么就統一以此為標準。責任主體——“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行為依法(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家屬)應當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單位和個人”,賠償的對象要件是該條的一個隱含條件。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得出,上述的車主和雇主都可以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而保險公司則不宜作為附帶民事訴訟的被告人,不管其投保的是交強險還是商業險。
2.根據一事不再理的原則,拒絕對另案處理的案件再次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并嚴格遵循必要的程序。一事不再理原則是指同一糾紛經人民法院終審裁判后,當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實和同一理由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也不得重復立案和審理。一事不再理原則中的“一事”指的是“一訴”。判斷前訴與后訴是否同一訴,原則上可從當事人和訴訟標的兩個方面進行判斷。一般而言,當事人不同,訴也不同。但在必要共同訴訟中,必要共同訴訟人在前后訴中即使人數不同,也不構成不同的訴。
再以case1為例,在對a附帶民事的判決或調解生效后,再對b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則不應允許。依據就是一事不再理的原則。但是,這里還是有個程序的遵循問題需要探討。一是法院追加被告人的職權問題。如a、b作為共同的侵權人是必要共同訴訟人,c在起訴a的時候,依照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一十九條的規定,通知b參加訴訟;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的規定,法院應當追加b為共同被告。二是起訴權作為一項私權,當事人有自由選擇被告的權利。根據民法理論,共同侵權行為是債的發生原因之一,也就是說,受害人為債權人,共同侵權人是債務人,其法律效果就是全體侵權人負連帶責任。我國《民法通則》第87條對連帶之債規定為:“債權人或者債務人一方人數為二人以上的,依照法律的規定或者當事人的約定,享有連帶權利的每個債權人,都有權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負有連帶義務的每個債務人,都負有清償全部債務的義務,履行了義務的人,有權要求其他負有連帶義務的人償付他應當承擔的份額。”因此,c在起訴是有權只選擇a作為被告,法律應當尊重當事人的選擇。基于這種局面,筆者認為,法院在追加b為被告時,應詢問c是否同意。如果c同意追加b,基于b的刑事責任先于其民事責任處理原則,中止附帶民事訴訟的處理。如果不同意追加b,c必須作出如下選擇:(1)放棄對b的全部訴訟,只要求a承擔全部賠償責任,并在之后要受一事不再審原則的限制,不能對b追訴;(2)暫時放棄對b的應承擔責任部分訴訟,但是只能要求a承擔其應當承擔的部分,允許在判決生效后對b應承擔賠償的部分予以追訴。
綜上,筆者認為針對case1的類似情況,可以這樣處理:對于已經受理尚未處理完畢的,以程序瑕疵為由(未經過通知及追加被告人)撤銷原判決或者調解,將b追加為共同被告重新立案審理;對于尚未受理的,在以后的訴訟中法院通知并追加b作為共同被告,c同意追加的,中止審理并待b抓獲后再恢復審理,c不同意追加的,由c選擇放棄對b全部訴訟或者其應承擔賠償部分的訴訟。
(二)追贓與訴訟的協調
對于財物被被告人非法占有或者處置的,雖然法律規定了追贓和訴訟雙重保護模式(即先進行追贓,在追贓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經濟損失的,可以提起民事訴訟),但是權利人實際上并不能及時維護其權利。一是,追贓時間過于漫長,被害人需要等待追贓處理完畢才能提起民事訴訟;二是即使能夠及時提起民事訴訟,可能還要受到先刑后民原則的限制而被中止審理。實際上,被害人的財物被毀壞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而財物被非法占有或處置不能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對后者已經是一次不公平待遇;在后者被排除出附帶民事訴訟范疇的同時,對其另行提起民事訴訟又設置了另外一道追贓的屏障,則是再次的不公平待遇。因此,看似追贓與訴訟的雙重保護模式,實則為對其的兩次“貶謫”。
那么,如何在現有的法律框架下,協調追贓與訴訟的關系?筆者的意見如下:案件尚處于偵查或者公訴階段的,走追贓程序,依法由公安機關、檢察機關進行追贓;案件到了審理階段,則分情況處理。(1)符合附帶民事訴訟規定的,可以在刑事案件處理的同時一并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不用走追贓程序;(2)不符合附帶民事訴訟,但贓款贓物的數額、去向等證據到位的,可以在刑事審理的過程中一并判決對贓物贓款予以追繳后者退賠;不符合附帶民事訴訟的,有關贓款贓物的數額、去向等證據也不到位的,在刑事審理的過程中不宜對贓款贓物一并作出判決,但可以在刑事判決生效后提起民事訴訟,不必無限期地等待法院追贓。
(三)定罪量刑的兩個方面
1.設置變更罪名的辯論程序
變更罪名的規定業內批評已久,其問題的癥結仍在于缺乏一個正當的程序。目前,司法界有關將量刑納入庭審程序的司法改革及試點工作正在如火如荼的展開。罪名的變更往往涉及到量刑變更,因此,有必要將罪名變更納入庭審程序并進行充分的辯論。下面,筆者分兩種情況對此進行討論。
第一種情況,法院認為需要變更罪名的(大多數情況如此),以二次開庭為原則。第一次開庭先查明起訴書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實,以此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并進而判斷是否需要變更罪名。第一次開庭是為了確保“未經人民法院判決任何人不得被認定為有罪”。第一次開庭是確定被告人有罪無罪的前提,也是變更罪名的基礎。第二次開庭則是針對案件查明的事實,人民法院認為需要變更罪名的再次開庭。為了保障控辯雙方充分地行使控訴權與辯護權,在第二次開庭前,法院應將擬定變更的罪名告知控辯雙方并給予一定的準備時間(比如十天)。在第二次開庭的時候,主要就變更的罪名進行罪名的辯論及相應的量刑的辯論。
第二種情況,被告人或辯護人認為需要變更罪名的,可以在第一次開庭的辯論階段提出。如果案件是適用簡易程序的,由于公訴人通常不出席庭審,則宜轉為普通程序再進行審理。如果案件是適用普通程序的,被告人或者辯護人當庭在法庭辯論階段提出變更罪名的,審判長則應先詢問公訴人是否需要一定的準備時間再就變更后的罪名參加法庭辯論。如果公訴人認為不需要準備的,則法庭繼續進行辯論;如果公訴人認為需要時間準備的,則審判長應宣布休庭并擇日再次開庭就變更后的罪名主持辯論。
2.累犯與起訴書認定問題
累犯(一般累犯)與起訴書的認定問題,歸根究底是對法條規定的后罪“應當判處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的不同理解和操作問題。針對類似case2的情況,筆者的建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