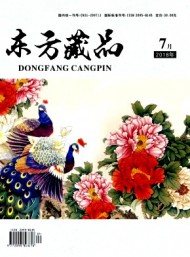關于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考范文
時間:2023-10-20 17:33:3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關于人工智能的哲學思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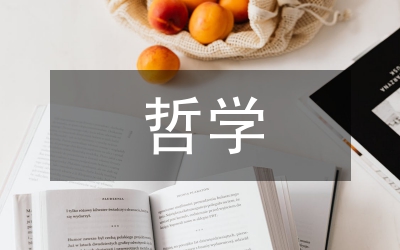
篇1
“人工智能”從人工智能概念的提出就已經有關于這方面爭論。而筆者通過對麥克盧漢的媒介理論和其背后的現象學哲學基礎的研究,認為一些科學家之所以在對待人工智能和人類的關系上各執一端,主要是因為他們所秉承主客二元思維方式,即把人工智能看成一種具有獨立思維的客觀實體,進而取代人類的主體地位,將人類變成其發展的客體。而對于主客二元思維方式的批判一直麥克盧漢的媒介學和現象學的重要任務之一。
1 現象學及其反主客二元思維方式
主客二元思維方式是起源于笛卡爾的西方近代哲學觀念,這種觀點主張嚴格區分主體和客體進而來高揚人的主體意識和理性審視能力。應該說這種主客二元思維方式對于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但是科學高歌猛進的背后掩蓋不了這種思維方式背后的根本性矛盾。
從哲學根基上講,這種主客二元思維方式在本體論上表現為二元論,在真理觀上表現為符合論,這本身就帶來了一個問題,即如何證明主體對于客體認知的合法性。正如胡塞爾所說,這種二元論和符合論的思維無論如何解決不了所謂的客觀感覺材料和主觀意識的溝通問題。那么這個問題又是如何產生的,胡塞爾的現象學認為,其實是它混淆了意識活動的對象。在胡塞爾看來,意識活動的對象并不是那個超越與意識之外的所謂“客觀實在對象”,而是內在于意識的,被實項和質料充盈著并且時刻被意向性意指的一種意向的對象,而兩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那個意向對象并非超越于意識的,而是一種意向性活動之中,由意向性描述所建構出的意向性本質結構的屬性的集合。在這個認知模型中,我們發現,雖然有意向主體和意向對象,但是他們共處于一個意向性活動的行為框架之中,這實際上是跳出了主客二元思維方式的第一步,即在認識過程中承認了一種“共在域”的存在。
而對于這種“共在域”,海德格爾的論述就更加有說服力。首先,對于人和事物的打交道,海德格爾有一種“上手狀態”理論,即用具所具有的一種為人所操作的良性互動狀態,而這種“上手狀態”對于人和用具之間的關系協調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1)它意味著用具一定是作為一個整體出現。“嚴格地說,從沒有一件用具這樣的東西‘存在’。屬于用具的存在意向總是一個用具的整體。[1]80
2)用具在和人進入操作場域的時候用具本身是不被意識到的。“切近之‘物’特有的自明的‘自在’是在那種使用著它們卻不曾明確注意它們的操勞中來照面的。”[1]87
而海德格爾用一種“煩”的理論為這種用具在行為場中的一種不被注意做出了解釋:即人要最大程度上減少對于自身行為在時間進程中的缺乏,窘迫和不適應的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減少一種“操心”的狀態和生存的一種壓力感。
綜上,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現象學的反主客二元思維主要體現在其對于人和外在世界的交互行為的考察上,其關注于具體的意識,目的,和操作行為在一個具體行為場域中的發生結構,在這個結構中所謂原有觀念中的主體意識和客觀實在的東西都參與了這個結構的發生和延展,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近代哲學主客二元思維方式的限制。
2 麥克盧漢“媒介延伸論”背后的現象學思維
麥克盧漢的媒介學和現象學不謀而合的地方則是它們對于傳統西方的線性的,邏輯的理性思維方式的批判。正如麥克盧漢所說“西方人頭腦接受的訓練是從A到Z,而不是從Z到A。這個頭腦正在逐漸退化,越來越迷糊,它完全靠視覺原理(即邏輯)工作;……到了電氣時代……視覺和理性統治的時代從此終結”[2]這句話其實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說麥克盧漢的研究方法不是一種由原理來推出方法的西方應用科學思維,而是恰恰相反,要回過頭看來考察一切技術和藝術發生的本源性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要排除所有先入為主的意見,徹頭徹尾地對于眼前的現象進行考察。這實際上就和現象學的一種“先驗還原”的思維不謀而合,它要求我們要僅僅從當下的絕對被給予出發,來解決事物的依據和基礎問題。而另一方面麥克盧漢在此排除的是兩種媒介研究傾向:即追求精確的經驗主義和追求社會批判功能的歐陸哲學,比如法蘭克福學派等。而之所以要懸置他們的原因實際上就是這句話的第二層意思:對于媒介本質的把握不能像傳統的理性主義那樣或者通過精確的測量,或者通過嚴密的邏輯,而是通過直觀。這其實就和現象學的另一種方法“本質直觀”不謀而合,它要求在無前提性的意識里面確切地把握事物的本質。
所以我們發現,麥克盧漢的媒介學有著深深的現象學烙印,而最能體現出麥克盧漢的反主客二元思維的便是他的“媒介延伸論”。麥克盧漢的“媒介延伸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1)媒介互動論。媒介作為人的器官的延伸,其本身和人處于一種統合的狀態。人們通過延伸自己的感官能力,來使得人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同時媒介的樣態反過來會對人自身的行為和人類的社會組織產生一定變化。麥克盧漢以電力技術的發展為例:“在機械化時代,我們實現了自身的空間延伸。如今,在經歷了一個多世紀的電子技術的發展之后,我們已在全球范圍內使中樞神經系統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圍內消除了時空差別。”[3]
2)自我截除理論。自我截除在麥克盧漢眼里是人的任何延伸都必然造成的結果。“人體在無法探查或避免刺激的根源時,就訴諸于自我截除的力量或策略。”[4]58按照麥克盧漢的說法,自我截除實際上是一種自我因適應外在系統所產生的強烈的身體壓力的手段。而人們對于截除的一部分是感到麻木的,無意識的,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正是刺激的壓力所造成的自我截除或延伸。作為一種抗自己的機制,他的形象產生泛化,難以覺察的麻木或震撼。自我截除不容許自我認識。”[4]59
聯系我們上節講到的海德格爾的“上手狀態”我們發現,自我截除的目的就是為了進入“上手狀態”而使得人自身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自我截除后的整個社會就會變成一個由人和用具組成的大主體。所以我們可以發現,麥克盧漢的“媒介延伸論”深受現象學思維方式的影響,而他們的基本的觀點都是反主客二元的思維方式。
3 “人工智能”主客二元思維傾向
現階段,科學界會按照人工智能的智能程度問題,將人工智能劃分為弱人工智能和強人工智能,所謂弱人工智能,即是“發展研究人類和動物智能的理論,并能通過建立工作模型來測試這些理論,……他們并不認為機器本身能夠思考、具有感情和意識。因此,對于弱人工智能來說,模型只是幫助理解思維的工具。”[5]所以很多人并不認為弱人工智能會對人類造成多大的威脅。
但是問題出在強人工智能身上,持強人工智能觀點的科學家認為強人工智能應該和人類一樣擁有獨立的思考和判斷能力,并且具有創造力,自我意識和自我進化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在強人工智能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它會取代人類的主體地位,進而將人類變成其自我發展和進化的工具。一些科學家甚至還認為,人類根本無法遏制這種人工智能的發展,而且它將是現階段所有弱人工智能的發展目標和人工智能最終的不可避免的發展方向。
但是,我們在看待這些觀點是應該意識到:無論是弱人工智能還是強人工智能根本的目標都是建立一種獨立于人的意識和行為的客觀實在體,都是實現“機器也可以像人一樣思考”,只是弱人工智能者認為機器能夠部分做到這一點,強人工智能則認為機器能夠完全做到這一點,甚至很多行為主義科學家還不滿足于機器僅僅是思考,而是和人一樣擁有社交,協作甚至是共生等更加廣泛意義上的
獨立。
所以,基于這種思維,所以很多科學家才會產生“人和人工智能”的關系問題的爭論,即所謂誰才是主體的問題,進而才會產生“人工智能”這樣的將人工智能和人極端對立的命題。
4 對于人工智能概念理解與發展的新思路
那么我們就必須要做一個論證,即這種像科學家所想的完全由人的技術打造,獨立于人而存在的人工智能存在的可能性問題,筆者基于麥克盧漢的媒介學及其現象學基礎的理論基礎認為:人類試圖通過純粹技術打造一種獨立于人的意識和行為而存在,并具有自身獨立自主的思考和判斷能力的行為體在根本上是不可行的。
1)現象學證明:基于海德格爾的“上手狀態”理論,人類之所以將技術和人自身打造成一種整體,其根本的目的就是在于避免一種由于和完全獨立和陌生的“他者”而產生的“煩心”和“操勞”,即一種缺乏,窘迫和不適應的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減少一種“操心”的狀態和生存的一種壓力感。而如果一種完全獨立于人的,具有自主的思考和判斷能力的人工智能行為體的出現,不但沒有減少這種壓力感,反而增加了人的這種打交道的壓力感,所以人和這種人工智能行為體的打交道必然會有不適感,所以這種技術的市場化一定會遭到抵制。
2)麥克盧漢媒介學證明:根據自我截除理論,人和工具的最佳關系就是人不會意識到工具的存在,進而避免一種因強刺激所引起的壓力,但是一種獨立于人的人工智能的出現,雖然會導致人們在應對自然和機械問題的壓力會減少,但是同時,人和人工智能,任何人的社交信息的壓力會增加,所以此消彼長,人的根本壓力綜合并不會發生根本的變化。其次,根據自我截除理論,人的進化不同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的進化不是依靠對自己身體的加強,而是通過延伸身體,避免強制身體而使得身體受到壓力進而獲得一種大腦的輕松的環境,進而使得信息在腦中進行復合,產生創造。而根據這種推論,人工智能目前首要的任務,還是要替人類做很多機械的工作,比如大量重復和復雜的計算。在這種情況下,人工智能史不可能自己通過自我解除來減少壓力,激發自身內部的創造性的。
所以,基于以上論證,那種試圖通過純粹技術打造一種獨立于人的意識和行為而存在,并具有自身獨立自主的思考和判斷能力的行為體的做法,無論是在和人的關系的角度還是其自身的發展創造力的角度都是不可行的。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筆者認為,人工智能是一個整體,它的終極發展不是一種獨立于人的客觀實體,而是一種集合人腦智能,工具和技術智能,社會智能等多種交互因素綜合而成的一種行為和操作狀態。它的本質是在于通過對于人身體的延伸,連接和雜糅,使得個人的能力能夠在龐大的延伸和連接交互網絡中能夠:
1)最有效的進行任何的操作。
2)最大化提升人的操作體驗感。
3)最大化減輕人們通過外感官應對強刺激的壓力,讓人們更加專注于創造。
篇2
關鍵詞:人工智能;選修課;專題討論
中圖分類號:G642.0?搖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2)12-0053-02
一、引言
《人工智能》是一門跨學科的課程,它的內涵十分豐富,包含了符號學、數理邏輯、神經網絡、遺傳算法、知識表示和推理、模式識別、機器學習等方面的知識,并且內容抽象,使得一般本科生望而生畏。目前在大多數院校里尤其是二本院校,《人工智能》只是作為一門選修課程。既然是作為選修課程,我們可以不拘泥于傳統的教學方式,采取靈活多樣的教學形式,培養學生研究這個領域的興趣,使得學生既能掌握人工智能領域的基礎理論,又能了解目前人工智能的前沿課題,擴大知識面,并為今后的研究打好基礎。
二、改革教學方法
在傳統的教學模式里,教師往往就一本教材從頭到尾講授給學生,教師講什么,學生就聽什么。但是人工智能涉及太多的數理邏輯推理知識,內容抽象,講解起來不免有點枯燥無味,學生的興趣就會隨著講課的進程逐漸變得淡薄。另一個問題是在傳統的教學模式下,學生接觸不到該研究領域的前沿問題。事實上,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工智能技術也在不斷發展,再加上人工智能本身的特點,即它是一門交叉學科,涉及計算機科學、信息科學、控制科學、認知學、生物學、哲學等等領域。因此當學生了解了當前國內外學者所研究的前沿課題,這樣不僅能克服“枯燥無味”的問題,而且會拓寬他們的知識面,從而他們可以將自己所學專業作為人工智能的潛在應用或研究領域。基于以上分析,考慮到人工智能是適合任何專業學生學習的一門選修課,我們設立分專題講授模式,這些專題包括:人工智能與類人思維,人工智能與機器進化,人工智能與知識表示,人工智能與決策規劃等等。下面分別敘述之。
1.人工智能與類人思維。什么是人工智能?Nilsson指出:“人工智能是關于人造物的智能行為,而智能行為包括知覺、推理、學習、交流和在復雜環境中行為。人工智能的一個長期目標是發明出可以像人類一樣或更好地完成以上行為的機器……”那么為了這個長遠目標,我們應該深入地探討人類大腦是如何思維的,或者說是如何思考問題的,人類是如何感知、理解以及應付外界龐雜的世界。只有深刻理解了人腦功能原理以后,人工智能才能“貢獻出”相應的類人思維模型。這相當于空氣動力學,人類飛行器只是根據空氣動力學的原理構造的,它并不要求人類制造像鳥兒一般的飛行工具。因此在這部分教學過程中,可以先提出“大腦是如何思維的”問題,讓學生自己動腦思考,相互探討:人腦的結構是什么?人類思考問題分層次嗎?什么是智力?智力的本質是什么?……課后,學生可以帶著這些問題查閱資料文獻,分組討論,甚至可以寫一些文章來闡述自己對思維的理解。這樣既充分調動了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又培養他們的興趣。然后,我們在課堂上進行具體講解,講解內容自然而然地引入了人工智能的定義,人工智能歷史知識,圖靈測試方法以及認知模型方法,接著再介紹目前國內外類人思維模型的研究現狀。這樣的教授過程,一開始就使得學生不排斥這門課,在了解人工智能基礎知識外也接觸到認識論方面的知識,培養了學生查閱文獻和撰寫科技論文的能力。
2.人工智能與機器進化。這部分專題主要給學生講解遺傳算法方面的知識,比如遺傳算法的產生與發展,遺傳算法的基本操作,遺傳算法的應用情況。并且在教學過程中結合實例來講述。實例可以從最基本的簡單函數優化到復雜的旅行商問題。學生可以自己設計函數優化的解決方案,指出初始種群大小、進化代數、交叉率等因素對求解結果的影響,并要求學生自己編寫程序來分析和理解這些問題。這些實驗和設計極大地提高了學生的動手能力。
3.人工智能與知識表示。知識表示可看成是一組描述事物的約定,在人工智能里,它研究怎樣把“人類知識”表示成機器能處理的數據結構。經典人工智能的主要表示方法有:一階謂詞邏輯表示方法,這是最基本的表示方法,具有嚴謹的公理體系;產生式規則表示方法,這是使用最廣泛的表示方法;語義網絡、框架、腳本表示方法,這是結構化的表示方法,等等。但是學生在學習這部分的知識時,對于邏輯推理覺得非常枯燥無味。我們的想法是在介紹這部分的知識時,不僅透徹闡述各種表示方法的精神實質,而且建議學生閱讀Sowa所編著的《知識表示》一書,該書提供了知識表示方面廣泛的知識,是這一領域的公認權威著作。Sowa在介紹新思想的同時捕捉到這一領域的最新成就,并且將邏輯學、哲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結合到知識表示,并將其轉換為可計算形式。該書中還包含了大量的哲學和語言學的知識,閱讀該書可以使得學生知識面得以拓寬,加上該書目前沒有翻譯版本,鼓勵學生閱讀英文原著,對學生各方面能力的提高都有所幫助。
4.人工智能與決策規劃。在決策規劃中,著重介紹增強學習、偏好理論等基礎知識,由于我們在這個方面上做了許多工作,因此在講解時聯系自己的研究進行一些專題探討,例如雙馬爾科夫過程決策模型,協同算法,超濾偏好模型,樸素描述邏輯在中醫理論上的應用等等,并歡迎學生和我們共同研究這些專題,這樣做無疑會增加師生之間的學術交流,促進學生的研究興趣,形成良好學術氛圍。
5.豐富多樣的教學形式。除了以上的專題外,還可以開設其他的人工智能專題。事實上可以針對不同專業的學生確定專題的內容和形式。例如對于工程類的學生,可以著重講述神經網絡,進化計算等方面的內容,并且借助于Matlab提供的相關工具箱進行實驗設計。因為大多數工程類的本科生都學習過Matlab語言,該語言在科學研究和工程實踐中應用廣泛,在教學過程中也要充分發揮這些優點。如是文科類的學生,教學方面可以著重講述人工智能的符號學,哲學等方面的知識,這讓文科學生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人工智能。課堂上,充分利用多媒體教學,采取多樣的教學手段,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好奇心。還可以播放國際機器人大賽等錄像片段,增強課堂的教學效果。
三、結束語
總之,將人工智能分專題來講授,讓學生立刻能接觸到當前人工智能的前沿研究問題,并且領會其中的實質。再加以多元化的教學手段,使得學生好學,樂學,更好地實現教學目標,提高教學水平。
參考文獻:
[1]Nils J. Nilsson,著.人工智能[M].鄭扣根,莊越挺,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4,6.
[2]John F. Sowa.Knowledge Representation:Logical,Philosophical,and computational Foundations[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3,6.
[3]韓麗娟,孫玉紅,李圣君.《人工智能》教程改革初探[J].電腦知識與技術,2007,(13):222-223.
[4]馮愛祥,羅雄麟.本科“人工智能”課程的教學改革探索[J].中國電力教育,2011,(10):111-112.
[5]李春貴,王萌,何春華.基于案例教學的“人工智能”教學的實踐與探索[J].計算機教育,2008,(9):53-54.
[6]曾安,余永權,曾碧.人工智能課程教學模式的探討[J].江西教育學院學報(綜合),2006,27(6):40-43.
[7]王蓁蓁,邢漢承.擬人類思維的形式結構數學模型[J].智能系統學報,2008,3(6):529-535.
篇3
[關鍵詞]人工智能 自我意識 情感
[中圖分類號]TP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5349(2012)04-0108-02
智能機器如何更像人?這是人工智能56年來亟待解決的問題。人類智慧被譽為地球上“最美麗的花朵”,是造物主的“恩賜”,人類夢想著在自己的身上再現這一奇跡。但大腦是一個巨大的復雜系統,想要破解人類思維的奧秘需要各個學科的共同努力,人工智能實現類人模擬也必須建立在能夠清晰掌握人類思維機制的基礎上。人對自身的了解程度將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關鍵。
一、智能機器能否具有“自我意識”
人的記憶分為情節記憶和語意記憶,其中語意記憶是間接的知識,語意記憶的真實性靠的是社會的一致決定;情節記憶的直接信息來源是感覺。在情節記憶系統中,信息的典型單位是事件或情節,這些事件總是包括記憶者在內的,回憶者可以是參與者或者是觀察者,總是與自身的感覺相聯系。李伯聰認為:“所謂‘我’或者說‘自我’,其重要的含義之一,就是指‘我’有‘我的記憶’。”因此,情節記憶是屬于“我”而非任何“他人”的。
情節記憶總是同“我”經歷的“過去”相聯系,其內容一定是“我”的直接經驗。如果把情節記憶看做是一個“抽象空間”,那么“我”就是這個“空間”中的坐標原點。不同的人擁有相同的外部時間,但是卻不可能具有相同的記憶情節。即使有兩個人經歷了完全相同的一個事件,事后在兩個人的記憶系統中留下的情節記憶卻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從哲學上看,世界上沒有兩個相同的人,相應地,世界上也不可能有兩個人有完全相同的情節記憶。
假設三個人在畫廊同時欣賞一幅畫,因為每個人的世界結構、價值觀不同,所以他們的“注意力”總是會集中在他們在意的地方,這些被“注意力”篩選的情節進入記憶系統,就形成了三個人獨特的情節記憶,而這三個人對事件的回憶也總會帶有個人色彩。所以,在一個特定的含義上,可以說所謂“我”就是“我”的情節記憶。
與情節記憶相對,語意記憶不是與“我”不可分割的個體性,而是揚棄了“我”的個體性的共同的社會性。我們可以設想對同一事件的參與者具有不同的情節記憶,而對某一歷史事件卻有著相同的語意記憶。語意記憶不像情節記憶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語意記憶涉及的是外部世界。在許多情況下,個人所具有的知識可能只與外部世界有間接的聯系,從這個方面看,語意記憶是反映客觀世界、依賴外部世界的。
計算機的存儲記憶更像是語意記憶的形式,它的獲取形式是間接的外界知識和信息,不具有任何的主觀性,而且具有通用性,即在一臺計算機上是如此,換作另一臺計算機也是如此。在人工智能機器所需要鏈接的數據庫中,各種知識和經驗按照統一的格式被儲存,并且被打上時間標記。各個智能終端的作用只是在提取和分享數據庫中的已有內容,并把搜集到的新知識上傳回數據庫,這其中不包含任何的個人情感,也沒有個人體驗的參與,一切都是冷靜的理性內容。每一個智能個體都是一模一樣的復制體,在它們的處理模塊中找不到任何與“個體”相關的成分。即使計算機具有了智能,單純地對間接知識進行加工,而沒有情節記憶的內容,“我”的意義被去除了,因此也不可能具有獨立的意識。
二、智能機器是否能模擬人類“情感”
情感問題是千百年來人們一直在談論的話題,但是機器是否也能具有情感? 這是目前人工智能哲學中最為熱門的研究問題之一。至今為止,我們對微觀的粒子和宏觀的恒星知之甚多,而對大腦結構知之甚少。“也許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大部分心理學家都是在模仿物理學家,通過找尋同樣簡潔的途徑來解決關于精神過程的問題。”人腦是一個龐大而且復雜的開放系統,用這樣的方法從來都沒有找到一點關于人類思維規律的定律。
有人說:機器只能做那些被制定好了的事情,而且在執行的過程中沒有任何的思考或感覺。機器是不會勞累的,不會厭煩,或根本就不會有任何的情感。當出現問題的時候,機器即使做對了,也不會為自己的成就感到高興、自豪或者愉悅。生機論者說:那是因為機器沒有精神或靈魂,沒有愿望、抱負、欲望或目標。那也是為什么機器遇到問題的時候只會停下來,而人卻可以努力做一些事情的原因。當然,這肯定與人是由不同的原料構成的相關。人是活的,而機器卻是死的。機器不能理解“意義”或者說行為、事件的結果對自身的反饋作用,它只會按照命令去執行任務,結果只有完成或者失敗,對其本身來說,這兩種結局沒有本質上的不同,都是任務的一個結束狀態,無所謂“成就、利益、價值”。
為什么嬰兒在出生之后就會因為饑餓而哭泣,因為快樂而笑?在沒有任何外界因素干擾的情況下,每一個嬰兒都是如此,是什么讓初生的孩子具備了先天的“情緒”表達?顯然,生命的形式起著關鍵的作用。心理學研究表明,人的行為都含有“動機”的參與,這也是事物發展的內因,只有具有“動機”的行為才具有目的性,而行為的結果與預測目的差異是導致產生情感的基礎。但是只有這些就足夠產生我們所體驗到的情緒變化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個人后期的經歷與價值觀對情感的表達方式起著很重要的作用。
哭泣是表達不滿的一種方式,在人類進化的歷史上,這種方式被寫在遺傳密碼中傳承下來,而在人們得到價值觀的改造之后,哭泣所表達的含義也發生了改變。“喜極而泣”所表達出來的含義早已不是祖先遺留下來的、對某種不滿的宣泄,而是對喜悅的流露。機器雖然也會獲取價值觀的內容,卻無法解釋其意義,因為機器缺少“目的性”,這種目的不是指要完成的任務是什么,而是任務對其自身的價值。
機器不具有內在的動因,沒有發展的動力,也沒有對“生命”“價值”“死亡”的理解。智能機器沒有生命構成的物質基礎,沒有內部的需求和欲望,失去能量而導致的系統關閉不能帶來對“生命”和“死亡”的敬畏。沒有痛覺的反饋機制存在,機器對自身的保護無從談起,而動物特有的自我保護很大程度都來自于感受器接收的信息是否讓自己感到不舒服和威脅,這是機器所難以達到的。
“當人開始把自己同其他動物加以比較時,就意味著人已經萌芽了關于自己存在的自我意識。”人工智能現在還無法自主地對比自身和外界其他事物的差別,還沒有從混沌的世界中脫離出來,不能明白自身和外界的關系。在智能機器沒有產生真正的自主性動機之前,“情感”還是個不可模擬的狀態。
三、結論
現階段人工智能的模擬只能是對人的行為和部分邏輯思維的模擬,由于人與機器的物質形式不同,智能機器無法產生和人一樣的需求機制,也無法產生人所特有的個體性差異。“自我”“情感”是人在數百萬年的進化中不斷地與外界自然相互作用的結果,實踐對認識的反作用促使人脫離了原始的混沌狀態,從而與外界客體區別開來。
人工智能研究是一個交叉性研究領域,其自身的發展要依靠計算機科學、腦科學、心理學、哲學等學科的共同努力。在人對自身知之甚少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的發展將遇到很大的阻礙,現在乃至未來數十年的智能機器始終只能作為“聰明的工具”參與人的生活,而無法真正做到與自然人的等同。人類實現“造物主”夢想的路途還很遙遠。
【參考文獻】
[1]李伯聰.選擇與建構[M].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篇4
Abstract: Since 1956, when Dartmouth institute put forward the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the past 50 years has achieved great developmen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three factions-symbol school, behaviorism school, connectionism school-led by the situation, each school has its own unique opinion. Based on the unique angle of view,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opin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關鍵詞: 人工智能;研究現狀;發展趨勢;社會力量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search status;development tendency;social force
中圖分類號:TP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3)28-0005-03
0 引言
人工智能是自1956 Dartmouth學會后發展起來的新型學科,其有著涉及學科廣、需要技術高端、使用范圍廣等特點。在過去的50多年時間中人工智能經歷了學科發展中都會遇到的發展——否定——否定的否定階段,現在人工智能大致分成了符號主義學派、行為主義學派、聯結主義學派三大學派。其各有優勢,獨樹一幟。一直以來重大前沿科學研究都是以國家牽頭,等到時機成熟了再轉為民用。這樣無形中浪費了很多社會中的人才,比如android智能機的問世,當開發商源代碼公布后android智能機獲得了飛速的發展。這是社會資源集體作用的結果,人工智能能否通過這種方式獲得飛速的發展呢,文中給出了問題的答案。
1 人工智能的現狀
1.1 人工智能的發展過程 人工智能是由“人工”與“智能”組成。“人工”十分容易理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人類開發研究出來的事物。“智能”則是十分復雜的一個詞匯,是指如由意識(Consciousness)、自我(Self)、思維(Mind)(包括無意識的思維(Unconscious_mind))等等組成的有機集合。通常我們所說的人工智能是指人本身的智能。總體來說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是研究、開發用于模擬、延伸和擴展人的智能的理論、方法、技術及應用系統的一門新的技術科學。關于人工智能的傳說一直可以追述到埃及,直到電子計算機的問世才使人們真正具備了發展人工智能的基本技術,而直到1956年的Dartmouth學會之后“人工智能”才逐漸地被大家所熟知接受。人工智能作為一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技術科學交叉的邊沿學科,涉及哲學和數學,認知科學,心理學,神經生理學,計算機科學,控制論,不定性論,信息論,社會結構學,仿生學與科學發展觀等眾多前沿學科。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被稱為世界三大尖端技術之一(空間技術、能源技術、人工智能),也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基因工程、納米科學、人工智能)三大尖端技術之一[1]。
人工智能在其過去的50多年時間里,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并不是十分順利。目前人們大致將人工智能的發展劃分成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萌芽期(1956年之前)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在尋找能夠提高工作效率、減輕工作強度的工具。只是受限于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人們只能制作一些簡單的物品來滿足自身的需求。而人類的歷史上卻因此留下了很多膾炙人口的傳說。傳說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時期,人們制造出了可以自己轉動的大門,自動涌出的圣泉。我國最早的記載是在公元前900多年,出現了能歌能舞的機器人。這一時期出現了各種大家:法國十七世紀的物理學家、數學家B.Pascal、德國十八世紀數學家、哲學家Leibnitz以及二十世紀的圖靈、馮·諾伊曼等。他們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貢獻。
第二階段:第一次期(1956年-1966年)
1956年夏季,以麥卡賽、明斯基、羅切斯特和申農等為首的一批有遠見卓識的年輕科學家在Dartmouth學會上引發一場歷史性事件——人工智能學科的誕生。Dartmouth會議結束后,人工智能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代。會議上誕生了幾個著名的項目組:Carnegie-RAND協作組、IBM公司工程課題研究組和MIT研究組。在眾多科學家的努力下,人工智能取得了喜人的成果:1956年,Newell和Simon等人在定理證明工作中首先取得突破,開啟了以計算機程序來模擬人類思維的道路;1960年,McCarthy建立了人工智能程序設計語言LISP。此時出現的大量專家系統直到現在仍然被人使用,人工智能學科在這樣的氛圍下正在茁壯的成長。
第三階段:低谷發展期(1967年-八十年代初期)
1967年之后,人工智能在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發展的時候遇到了很大的阻礙。這一時期沒有比上一時期更重要的理論誕生,人們被之前取得的成果沖昏了頭腦,低估了人工智能學科的發展難度。一時之間人工智能受到了各種責難,人工智能的發展進入到了瓶頸期。盡管如此,眾多的人工智能科學家并沒有灰心,在為下一個時期的到來積極的準備著。
第四階段:第二次期(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初期)
隨著其他學科的發展,第五代計算機的研制成功,人工智能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人工智能開始進入市場,人工智能在市場中的優秀表現使得人們意識到了人工智能的廣闊前景。由此人工智能進入到了第二次期,并且進入發展的黃金期。
第五階段:平穩發展期(九十年代之后)
國際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使得人工智能的開發研究由之前的個體人工智能轉換為網絡環境下的分布式人工智能,之前出現的問題在這一時期得到了極大的解決。Hopfield多層神經網絡模型的提出,使人工神經網絡研究與應用再度出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人工智能已經滲入到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1.2 人工智能的主要學派 人工智能發展的50多年時間里,經歷了符號主義學派、行為主義學派和聯結主義學派,三大學派各有特點,各自從不同的角度研究人工智能,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1.2.1 符號主義學派 符號主義學派,又稱為邏輯主義、計算機學派或心理學派。符號主義學派理論基礎是物理符號系統假設和有限合理性原理,他們認為人類的認知基元是符號,認知的過程是對符號的計算與推理的過程。人與計算機均可以看做物理符號系統,因此人們可以使用計算機來模擬人的行為。符號主義學派認為人的認知基元可以通過計算機上的數學邏輯方法表示,然后通過計算機自身的邏輯運算方法模擬人類所具備的認知系統的機能和功能,進而實現人工智能[2]。
符號主義學派無視了認知基元的本質,對于所有的認知基元均使用數學邏輯方法表示。符號主義學派重點研究認知基元的邏輯表示以及計算機的推理技術,早期的眾多人工智能的研究都是在這一思想的推動下進行的。符號主義學派在歸結推理、翻譯、數學問題證明以及專家系統和知識工程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貢獻,為后期的人工智能研究打下了基礎。專家系統的出現更是將人工智能的研究推上了一個頂峰,其在礦業探究、醫療診查、教育推廣、工業設計的應用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效益。
1.2.2 行為主義學派 行為主義又被稱作進化主義或控制論學派。行為主義學派認為智能取決于感知和行動,不需要像符號主義學派的邏輯知識以及推理。行為主義學派認為人的本質能力是行為能力、感知能力和維持生命及自我繁殖的能力,智能行為是人與現實世界環境的交互作用體現出來的。人工智能應像人類智能一樣通過逐步進化而實現,而與知識的表示和知識的推理無關[3]。行為主義學派的與傳統人工智能截然不同的觀點吸引了眾多的科學家,雖然到現在還沒有獨立完善的知識理論系統,但其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獨樹一幟還是奠定了其霸主地位。該學派重點研究人類的控制行為,目前已有的機器昆蟲已經證明了行為主義學派的理論正確性。雖然大部分人認為機器昆蟲不能導致高級行為,但是行為主義學派的崛起標志著控制論在人工智能領域有著獨樹一幟的作用。
1.2.3 聯結主義學派 聯結主義學派是近年來最熱門的一個學派,又被成為仿生學派或心理學派,建立于網絡聯結基礎之上模仿人類大腦的結構和工作模式。聯結主義學派主要研究能夠進行非程序的,可適應環境變化的,類似人類大腦風格的信息處理方法的本質和能力,是基于神經網絡及網絡間的連接機制和學習算法的人工智能學派。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認知的基本元素不是符號是神經細胞(神經元),認知過程是大量神經元的聯接,而大腦是一切智能活動的基礎,因而從大腦神經元及其連接機制出發進行研究,搞清楚大腦的結構以及它進行信息處理的過程和機理,就有望揭示人類智能的奧秘,從而真正實現人類智能在機器上的模擬。[4]
聯結主義學派通過模擬人類神經網絡模仿人類的認知行為,由此進行人工智能的學習記憶、模式識別。聯結主義學派構建了大量的神經網絡模型,方便在不同的情景模式下選擇相應的模型,進而快速的得出答案。聯結主義學派采用分布式存儲數據,對數據進行并行處理,這樣使得人工智能在處理問題的時候的速度有了明顯的提升,由此聯結主義學派在人工智能領域中受到大家的一致熱捧。
三大學派在人工智能的發展史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每一個學派的興起都代表人工智能的一個新高峰。三大學派各有優缺點,在人工智能領域三者相輔相成,人工智能學科在三大學派的帶領下正在茁壯成長。
2 對人工智能主要理論學派的評述
在過去的50多年時間中,人工智能獲得了巨大的發展,基本實現了從無到有的過程,構建了基本完善的理論知識體系,構建了各種模型,形成各種技術方法,但是人工智能的發展依然任重道遠,前景依然不容樂觀。三大主義學派有著自身獨到的優點,同時也有著各自的缺點,符號主義學派將人的認知基元符號用數學邏輯表示,通過計算機邏輯處理系統分析得出結果,但是在面對沒有明確結果的非確定問題時經常不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答案,它對信息要求十分精確完整,現實生活中的很多問題都不能滿足條件,因此符號主義學派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行為主義學派認為智能取決于感知與行動,但是缺乏足夠的理論知識支撐學派觀點,而且缺乏足夠的成果表明理論的正確性。學派認為人工智能與知識的表達和知識推理無關,與人類認知的發展是不相符的。聯結主義學派采用仿生學的方法,模擬人腦的神經網絡,通過類似人腦的結構和運行機制模仿人類智能。這一觀點十分有吸引力,在提出之后馬上就有大量的支持者,但是人腦神經系統的復雜性遠遠超出人們的預知,現階段人們對人腦的構造以及運行機制還沒有深入的理解,在此基礎上想模擬出人腦的神經系統顯然是有些不不切實際。聯結主義學派的發展更多的受制于對人腦結構和運行機制的研究,因此其發展相對緩慢。綜上,三大學派固然有著自身的優勢,各自的成果,但是其同樣有著明顯的局限性,人工智能要想進一步發展必須要對現有的發展方式進行創新。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經歷了兩次期后再次回落到了平穩發展時期,社會公眾對人工智能的熱度有了明顯的降溫。人工智能的研究再次變成了國家以及一些超級公司的工作,擁有的資源有了大幅度的縮水,研究的進度也受到干擾。在此狀態下沒有重大的技術創新,人工智能恐怕很難再有重大的突破。
3 對人工智能發展的評述
3.1 對人工智能涵義的認識 同樣的詞匯在不同時期的有著不同的解釋,人工智能也不例外,大家都認可的人工智能是指在人類制造的機器工具上實現人類智能,即實現人類的認知能力、行為能力以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人類智能有著一個明確的特點,在面對未知問題時,人類智能能夠得出自身想要的答案,也就是消除答案的不確定性。符號主義學派的邏輯解決方式、行為主義學派模擬人的行為能力、聯結主義學派的神經網絡,三大主義學派各自以自身的方式實現了對問題消除或減弱不確定性。可見減弱甚至消除問題的不確定性也將是人工智能的一個研究方向。
3.2 人工智能研究模式的發展 目前人工智能領域中,符號主義學派通過數學邏輯表示人類的認知基元,對數學邏輯經過解讀分析,得到答案,進而實現智能。該學派重點運用還原思想,將人類的認知基元全部使用數學邏輯表示。行為主義學派認為人工智能取決于感知和行動,不需要學習知識與知識推理,是一步步,由低級到高級慢慢進化的。聯結主義學派是通過人工神經網絡的形式模仿人類智能,理論上講該方法是最符合人類智能的運行方式的。而在一系統中,最重要的是系統的運行機制,如何將接受到的信息轉化為我們的知識并通過表述、行為展示出來,在了解了人類智能的運行機制之后,人工智能將會更加符合人們的需求。
3.3 人工智能研究方法的發展 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消除答案的不確定性,然后做出相應的反應。在消除答案不確定性的時候便有了各種方法,其中有一種便是突出解決問題的目標,在有明確目標的前提下會削弱干擾問題解決的條件,提高人工智能解決問題的效率。明確問題的目標便需要引入目標函數,在動態目標函數的引導下會減弱答案的不確定性。而在已有的人工智能基礎上設立人工智能模型,通過人工智能自身的計算結果結合目前的研究成果去優化目前的人工智能系統,則會提升人工智能的發展速度。
3.4 人工智能時期的發展 人工智能自發展到現在已經經歷了五個時期,在兩次期中人工智能均獲得了迅速的發展。然而現在人工智能的發展步入到了緩慢發展時期,如何將人工智能的發展緩慢時期加速度過同樣是十分嚴肅的問題,傳統說來需要重大的科學進步。我們往往認為人工智能屬于頂端科技只能由國家和超級公司研究,卻忽略了社會所擁有的重大的力量。小小的android智能手機在問世的短短時間內變改變了之前的市場格局,其中固然有著android智能手機的特點,但是我想他的市場策略同樣給與了莫大的助力。人工智能應該向android一樣,適當的開放出來一部分根基,放開其研究門檻,甚至鼓勵民間研究。量變引發質變,當有足夠專家在研究人工智能時,人工智能的研究會加快的。而且民間的研究成果也會作為經驗反作用于人工智能的進一步研究,實現科學與社會的雙贏。
4 結論
人工智能是人們長久以來的夢想,同時也是一門很有挑戰性的學科。像所有的學科一樣,人工智能會經歷各種各樣的挫折,但是,只要我們有信心、有毅力,我們相信人工智能終將會成為現實,融入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為我們的生活帶來極大的改變。
參考文獻:
[1]朱祝武.人工智能發展綜述[J].中國西部科技,2011,10(17):8-10.
[2]陳慶霞.人工智能研究綱領的發展歷程和前景[J].科技信息,2008,20(33):49,234.
篇5
[關鍵詞]人工智能,常識推理,歸納邏輯,廣義內涵邏輯,認知邏輯,自然語言邏輯
現代邏輯創始于19世紀末葉和20世紀早期,其發展動力主要來自于數學中的公理化運動。當時的數學家們試圖即從少數公理根據明確給出的演繹規則推導出其他的數學定理,從而把整個數學構造成為一個嚴格的演繹大廈,然后用某種程序和方法一勞永逸地證明數學體系的可靠性。為此需要發明和鍛造嚴格、精確、適用的邏輯工具。這是現代邏輯誕生的主要動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紀邏輯研究的嚴重數學化,其表現在于:一是邏輯專注于在數學的形式化過程中提出的問題;二是邏輯采納了數學的方法論,從事邏輯研究就意味著象數學那樣用嚴格的形式證明去解決問題。由此發展出來的邏輯被恰當地稱為“數理邏輯”,它增強了邏輯研究的深度,使邏輯學的發展繼古希臘邏輯、歐洲中世紀邏輯之后進入第三個高峰期,并且對整個現代科學特別是數學、哲學、語言學和計算機科學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是:21世紀邏輯發展的主要動力將來自何處?大致說來將如何發展?我個人的看法是: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將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泉,并將由此決定21世紀邏輯學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擬人的智能,它的難點不在于人腦所進行的各種必然性推理(這一點在20世紀基本上已經做到了,如用計算機去進行高難度和高強度的數學證明,“深藍”通過高速、大量的計算去與世界冠軍下棋),而是最能體現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動性、創造性思維,這種思維活動中包括學習、抉擇、嘗試、修正、推理諸因素,例如選擇性地搜集相關的經驗證據,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礎上作出嘗試性的判斷或抉擇,不斷根據環境反饋調整、修正自己的行為,……由此達到實踐的成功。于是,邏輯學將不得不比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維活動,并著重研究人的思維中最能體現其能動性特征的各種不確定性推理,由此發展出的邏輯理論也將具有更強的可應用性。
實際上,在20世紀中后期,就已經開始了現代邏輯與人工智能(記為AI)之間的相互融合和滲透。例如,哲學邏輯所研究的許多課題在理論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AI從認知心理學、社會科學以及決策科學中獲得了許多資源,但邏輯(包括哲學邏輯)在AI中發揮了特別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學邏輯家去發展關于非數學推理
的理論;基于幾乎同樣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進行類似的探索,這兩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鑒,甚至在逐漸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別關心下述課題:
·效率和資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計劃和計劃再認;
·關于他人的知識和信念的推理;
·各認知主體之間相互的知識;
·自然語言理解;
·知識表示;
·常識的精確處理;
·對不確定性的處理,容錯推理;
·關于時間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釋或說明;
·對歸納概括以及概念的學習。[①]
21世紀的邏輯學也應該關注這些問題,并對之進行研究。為了做到這一點,邏輯學家們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關進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應用性。
我認為,至少是21世紀早期,邏輯學將會重點關注下述幾個領域,并且有可能在這些領域出現具有重大意義的成果:(1)如何在邏輯中處理常識推理中的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2)如何使機器人具有人的創造性智能,如從經驗證據中建立用于指導以后行動的歸納判斷?(3)如何進行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特別是基于已有的知識庫以及各認知主體相互之間的知識而進行的推理?(4)如何結合各種語境因素進行自然語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機器人能夠用人的自然語言與人進行成功的交際?等等。
1.常識推理中的某些弗協調、非單調和容錯性因素
AI研究的一個目標就是用機器智能模擬人的智能,它選擇各種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問題進行實踐,希望能做出各種具有智能特征的軟件系統。AI研究基于計算途徑,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號模型。一般而言,AI關于智能系統的符號模型可描述為:由一個知識載體(稱為知識庫KB)和一組加載在KB上的足以產生智能行為的過程(稱為問題求解器PS)構成。經過20世紀70年代包括專家系統的發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識,認識到知識在智能系統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統事實上是一種基于知識的系統,而知識包括專門性知識和常識性知識,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領域內專家的常識。于是,常識問題就成為AI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它包括兩個方面: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類的常識,并運用這些常識去進行符合人類行為的推理。顯然,如此建立的常識知識庫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協調的,但這種矛盾或不協調應不至于影響到進行合理的推理行為;常識推理還是一種非單調推理,即人們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結論,當人們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變甚至收回原來的結論;常識推理也是一種可能出錯的不精確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許有錯誤知識的情況下進行的推理,簡稱容錯推理。而經典邏輯拒斥任何矛盾,容許從矛盾推出一切命題;并且它是單調的,即承認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則pùq?r;或者說,任一理論的定理屬于該理論之任一擴張的定理集。因此,在處理常識表示和常識推理時,經典邏輯應該受到限制和修正,并發展出某些非經典的邏輯,如次協調邏輯、非單調邏輯、容錯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識推理的邏輯是次協調邏輯和非單調邏輯的某種結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對容錯推理的簡單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種形式化。[②]
“次協調邏輯”(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達·科斯塔等人在對悖論的研究中發展出來的,其基本想法是:當在一個理論中發現難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論時,與其徒勞地想盡各種辦法去排除或防范它們,不如干脆讓它們留在理論體系內,但把它們“圈禁”起來,不讓它們任意擴散,以免使我們所創立或研究的理論成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協調邏輯中,能夠容納有意義、有價值的“真矛盾”,但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統推出一切,導致自毀。因此,這一新邏輯具有一種次于經典邏輯但又遠遠高于完全不協調系統的協調性。次協調邏輯家們認為,如果在一理論T中,一語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則T是不協調的;否則,稱T是協調的。如果T所使用的邏輯含有從互相否定的兩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規則或推理,則不協調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經典邏輯為基礎的理論,如果它是不協調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這一現象表明,經典邏輯雖可用于研究協調的理論,但不適用于研究不協調但又足道的理論。達·科斯塔在20世紀60年代構造了一系列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以用作不協調而又足道的理論的邏輯工具。對次協調邏輯系統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題:(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從兩個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說,矛盾不會在系統中任意擴散,矛盾不等于災難。(iii)應當容納與(i)和(ii)相容的大多數經典邏輯的推理模式和規則。這里,(i)和(ii)表明了對矛盾的一種相對寬容的態度,(iii)則表明次協調邏輯對于經典邏輯仍有一定的繼承性。
在任一次協調邏輯系統Cn(1≤n≤w)中,下述經典邏輯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為經典邏輯,則系列C0,C1,C2,…Cn,…Cw使得對任正整數i有Ci弱于Ci-1,Cw是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經為Cn設計出了合適的語義學,并已經證明Cn相對于此種語義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協調命題邏輯系統Cn還是可判定的。現在,已經有人把次協調邏輯擴展到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多值邏輯、集合論等領域的研究中,發展了這些領域內的次協調理論。顯然,次協調邏輯將會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③]
非單調邏輯是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它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1980年,D·麥克多莫特和J·多伊爾初步嘗試著系統發展一種關于非單調推理的邏輯。他們在經典謂詞演算中引入一個算子M,表示某種“一致性”斷言,并將其看做是模態概念,通過一定程序把模態邏輯系統T、S4和S5翻譯成非單調邏輯。B·摩爾的論文《非單調邏輯的語義思考》(1983)據認為在非單調邏輯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貢獻。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動認知推理”之間做了區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沒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證據的條件下進行推理的過程,這種推理的特征是試探性的:根據新信息,它們很可能會被撤消。自動認知推理則不是這種類型,它是與人們自身的信念或知識相關的推理,可用它模擬一個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對于在計算機和人工智能中獲得成功的應用而言,非單調邏輯尚需進一步發展。
2.歸納以及其他不確定性推理
人類智能的本質特征和最高表現是創造。在人類創造的過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繹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為重要的是具有某種不確定性的歸納、類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計算機要成功地模擬人的智能,真正體現出人的智能品質,就必須對各種具有不確定性的推理模式進行研究。
首先是對歸納推理和歸納邏輯的研究。這里所說的“歸納推理”是廣義的,指一切擴展性推理,它們的結論所斷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斷定的范圍,因而前提的真無法保證結論的真,整個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體說來,這種意義的“歸納”包括下述內容:簡單枚舉法;排除歸納法,指這樣一些操作:預先通過觀察或實驗列出被研究現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選擇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實驗,根據某些標準排除不相干假設,最后得到比較可靠的結論;統計概括:從關于有窮數目樣本的構成的知識到關于未知總體分布構成的結論的推理;類比論證和假說演繹法,等等。盡管休謨提出著名的“歸納問題”,對歸納推理的合理性和歸納邏輯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質疑,但我認為,(1)歸納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類必須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認知策略,對于人類來說具有實踐的必然性。(2)人類有理由從經驗的重復中建立某種確實性和規律性,其依據就是確信宇宙中存在某種類似于自然齊一律和客觀因果律之類的東西。這一確信是合理的,而用純邏輯的理由去懷疑一個關于世界的事實性斷言則是不合理的,除非這個斷言是邏輯矛盾。(3)人類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并且,歸納邏輯的這種可能性正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動下慢慢地演變成現實。恩格斯早就指出,“社會一旦有技術上的需要,則這種需要比十所大學更能把科學推向前進。”[④]有人通過指責現有的歸納邏輯不成熟,得出“歸納邏輯不可能”的結論,他們的推理本身與歸納推理一樣,不具有演繹的必然性。(4)人類實踐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相應的經驗知識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了歸納邏輯和歸納方法論的力量。毋庸否認,歸納邏輯目前還很不成熟。有的學者指出,為了在機器的智能模擬中克服對歸納模擬的困難而有所突破,應該將歸納邏輯等有關的基礎理論研究與機器學習、不確定推理和神經網絡學習模型與歸納學習中已有的成果結合起來。只有這樣,才能在已有的歸納學習成果上,在機器歸納和機器發現上取得新的突破和進展。[⑤]這是一個極有價值且極富挑戰性的課題,無疑在21世紀將得到重視并取得進展。
再談模糊邏輯。現實世界中充滿了模糊現象,這些現象反映到人的思維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題,如“矮個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輕”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題和模糊推理的邏輯理論叫做“模糊邏輯”。對它的研究始于20世紀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馬林諾斯。模糊邏輯為精確邏輯(二值邏輯)解決不了的問題提供了解決的可能,它目前在醫療診斷、故障檢測、氣象預報、自動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獲得重要應用。顯然,它在21世紀將繼續得到更大的發展。
3.廣義內涵邏輯
經典邏輯只是對命題聯結詞、個體詞、謂詞、量詞和等詞進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語言中,除了這些語言成分之外,顯然還存在許多其他的語言成分,如各種各樣的副詞,包括模態詞“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時態詞“過去”、“現在”和“未來”、道義詞“應該”、“允許”、“禁止”等等,以及各種認知動詞,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斷”、“猜測”、“考慮”、“懷疑”,這些認知動詞在邏輯和哲學文獻中被叫做“命題態度詞”。對這些副詞以及命題態度詞的邏輯研究可以歸類為“廣義內涵邏輯”。
大多數副詞以及幾乎所有命題態度詞都是內涵性的,造成內涵語境,后者與外延語境構成對照。外延語境又叫透明語境,是經典邏輯的組合性原則、等值置換規則、同一性替換規則在其中適用的語境;內涵語境又稱晦暗語境,是上述規則在其中不適用的語境。相應于外延語境和內涵語境的區別,一切語言表達式(包括自然語言的名詞、動詞、形容詞直至語句)都可以區分為外延性的和內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語境的表達式,后者是提供內涵性語境的表達式。例如,殺死、見到、擁抱、吻、砍、踢、打、與…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達式,而知道、相信、認識、必然、可能、允許、禁止、過去、現在、未來等都是內涵性表達式。
在內涵語境中會出現一些復雜的情況。首先,對于個體詞項來說,關鍵性的東西是我們不僅必須考慮它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慮它們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內涵性表達式,它提供內涵語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這是因為:這個推理只考慮到“晨星”和“暮星”在現實世界中的外延,并沒有考慮到它們在每一個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一個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們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換規則,由該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結論:“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內涵語境中,語言表達式不再以通常是它們的外延的東西作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們的內涵的東西作為外延。以“達爾文相信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這個語句為例。這里,達爾文所相信的是“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稱的真值,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的”所表達的思想(命題)就構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內涵語境中,雖然適用于外延的函項性原則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拋棄不可,可以把它改述為新的形式:一復合表達式的外延是它出現于外延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外延加上出現于內涵語境中的部分表達式的內涵的函項。這個新的組合性或函項性原則在內涵邏輯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個好的內涵邏輯至少應滿足兩個條件:(i)它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能處理的問題;(ii)它還必須能夠處理外延邏輯所不能處理的難題。這就是說,它既不能與外延邏輯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邏輯的局限。這樣的內涵邏輯目前正在發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輪廓。從術語上說,內涵邏輯除需要真、假、語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類、謂詞的同范圍或不同范圍等外延邏輯的術語之外,還需要同義、內涵的同一和差異、命題、屬性或概念這樣一些術語。廣而言之,可以把內涵邏輯看作是關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許”、“禁止”等提供內涵語境的語句算子的一般邏輯。在這種廣義之下,模態邏輯、時態邏輯、道義邏輯、認知邏輯、問題邏輯等都是內涵邏輯。不過,還有一種狹義的內涵邏輯,它可以粗略定義如下:一個內涵邏輯是一個形式語言,其中包括(1)謂詞邏輯的算子、量詞和變元,這里的謂詞邏輯不必局限于一階謂詞邏輯,也可以是高階謂詞邏輯;(2)合式的λ—表達式,例如(λx)A,這里A是任一類型的表達式,x是任一類型的變元,(λx)A本身是一函項,它把變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種類型的對象映射到A所屬的那種類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態的或內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個內涵邏輯的解釋,則由下列要素組成:(1)一個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個可能個體的非空集D;(3)一個賦值,它給系統內的表達式指派它們在每w∈W中的外延。對于任一的解釋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內涵邏輯系統中的任一表達式X相對于解釋Q在w∈W中的外延總是可能的。這樣的內涵邏輯系統有丘奇的LSD系統,R·蒙塔古的IL系統,以及E·N·扎爾塔的FIL系統等。[⑥]
在各種內涵邏輯中,認識論邏輯(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義。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認識論邏輯研究與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斷定、理解、懷疑、問題和回答等相關的邏輯問題,包括問題邏輯、知道邏輯、相信邏輯、斷定邏輯等;狹義的認識論邏輯僅指知道和相信的邏輯,簡稱“認知邏輯”。馮·賴特在1951年提出了對“認知模態”的邏輯分析,這對建立認知邏輯具有極大的啟發作用。J·麥金西首先給出了一個關于“知道”的模態邏輯。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個基于6條規則的相信邏輯系統。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識和信念》一書是認知邏輯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認知邏輯的系統,并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語義學,后者是可能世界語義學的先導之一。當今的認知邏輯紛繁復雜,既不成熟也面臨許多難題。由于認知邏輯涉及認識論、心理學、語言學、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等諸多領域,并且認知邏輯的應用技術,又稱關于知識的推理技術,正在成為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認知邏輯在20世紀中后期成為國際邏輯學界的一個熱門研究方向。這一狀況在21世紀將得到繼續并進一步強化,在這方面有可能出現突破性的重要結果。
4.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
對自然語言的邏輯研究有來自幾個不同領域的推動力。首先是計算機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機對話和通訊、計算機的自然語言理解、知識表示和知識推理等課題,都需要對自然語言進行精細的邏輯分析,并且這種分析不能僅停留在句法層面,而且要深入到語義層面。其次是哲學特別是語言哲學,在20世紀哲學家們對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問題傾注了異乎尋常的精力,發展了各種各樣的意義理論,如觀念論、指稱論、使用論、言語行為理論、真值條件論等等,以致有人說,關注意義成了20世紀哲學家的職業病。再次是語言學自身發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語言的意義問題時,不能僅僅停留在脫離語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結合使用語言的特定環境去研究,這導致了語義學、語用學、新修辭學等等發展。各個方面發展的成果可以總稱為“自然語言邏輯”,它力圖綜合后期維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論,J·L·奧斯汀、J·L·塞爾等人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以及P·格賴斯所創立的會話含義學說等成果,透過自然語言的指謂性和交際性去研究自然語言中的推理。
自然語言具有表達和交際兩種職能,其中交際職能是自然語言最重要的職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語交際總是在一定的語言環境(簡稱語境)中進行的,語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語境僅指一個語詞、一個句子出現的上下文。廣義的語境除了上下文之外,還包括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整個社會歷史條件,如該語詞或語句出現的時間、地點、條件、講話的人(作者)、聽話的人(讀者)以及交際雙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識,這里的背景知識包括交際雙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習慣,以及共同的知識和假定等等。這些語境因素對于自然語言的表達式(語詞、語句)的意義有著極其重要的影響,這具體表現在:(i)語境具有消除自然語言語詞的多義性、歧義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嚴格規定語言表達式意義的能力。(ii)自然語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詞、人稱代詞、時間副詞等,要弄清楚這些句子的意義和內容,就要弄清楚這句話是誰說的、對誰說的、什么時候說的、什么地點說的、針對什么說的,等等,這只有在一定的語境中才能進行。依賴語境的其他類型的語句還有:包含著象“有些”和“每一個”這類量化表達式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論域,包含著象“大的”、“冷的”這類形容詞的句子的意義取決于依語境而定的相比較的對象類;模態語句和條件語句的意義取決于因語境而變化的語義決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語言表達式的意義在語境中會出現一些重要的變化,以至偏離它通常所具有的意義(抽象意義),而產生一種新的意義即語用涵義。有人認為,一個語言表達式在它的具體語境中的意義,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義,一旦脫離開語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義。語言的抽象意義和它的具體意義的關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體與活人肢體的關系一樣。邏輯應該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當然不是去研究某一個(或一組)特定的語句在某個特定語境中唯一無二的意義,而是專門研究確定自然語言具體意義的普遍原則。[⑦]
美國語言學家保羅·格賴斯把語言表達式在一定的交際語境中產生的一種不同于字面意義的特殊涵義,叫做“語用涵義”、“會話涵義”或“隱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組“交際合作原則”,包括一個總則和四組準則。總則的內容是:在你參與會話時,你要依據你所參與的談話交流的公認目的或方向,使你的會話貢獻符合這種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疇區分為量、質、關系和方式四類,格賴斯提出了如下四組準則:
(1)數量準則:在交際過程中給出的信息量要適中。
a.給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給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質量準則:力求講真話。
a.不說你認為假的東西,。
b.不說你缺少適當證據的東西。
(3)關聯準則:說話要與已定的交際目的相關聯。
(4)方式準則:說話要意思明確,表達清晰。
a.避免晦澀生僻的表達方式;
b.避免有歧義的表達方式;
c.說話要簡潔;
d.說話要有順序性。[⑧]
后來對這些原則提出了不和補充,例如有人還提出了交際過程中所要遵守的“禮貌原則”。只要把交際雙方遵守交際合作原則之類的語用規則作為基本前提,這些原則就可以用來確定和把握自然語言的具體意義(語用涵義)。實際上,一個語句p的語用涵義,就是聽話人在具體語境中根據語用規則由p得到的那個或那些語句。更具體地說,從說話人S說的話語p推出語用涵義q的一般過程是:
(i)S說了p;
(ii)沒有理由認為S不遵守準則,或至少S會遵守總的合作原則;
(iii)S說了p而又要遵守準則或總的合作原則,S必定想表達q;
(iv)S必然知道,談話雙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須假設q;
(v)S無法阻止聽話人H考慮q;
(vi)因此,S意圖讓H考慮q,并在說p時意味著q。
試舉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車旁,b向a走來。a說:“我沒有汽油了。”b說:“前面拐角處有一個修車鋪。”這里a與b談話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據關系準則,b說這句話是與a想得到汽油相關的,由此可知:b說這句話時隱涵著:“前面的修車鋪還在營業并且賣汽油。”
篇6
【關 鍵 詞】語言哲學/心智哲學/認知科學/腦與心智
20世紀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的發展,有一條明顯的線索,那就是從語言研究到心智研究,再從心智研究進入到認知科學發展的新領域。
語言哲學的兩位代表性人物喬姆斯基(n.chomsky)和塞爾(john r.searle)都經歷了同樣的發展道路。喬姆斯基從句法研究(1957),到語言和心智研究(1968,1972),再到心智和認知研究(1990,2000,2002);塞爾則從言語行為理論研究(1969),到人工智能新標準cra的提出(1984),再到意向性和心智哲學(1983,1997,2002)。兩人為何殊途而同歸,從不同的出發點而達到共同的終點?在這其中有何規律值得思考?這是本文所要探究的問題。
關于對喬姆斯基發展道路的探索,筆者已有專論闡述,請參閱《沒有喬姆斯基,世界將會怎樣》一文[1]。本文主要討論另一位世界著名語言哲學家塞爾從語言到心智和認知的發展路徑,以及這一發展路徑給我們的啟迪。
約翰·塞爾系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哲學系心智和語言哲學威里斯和邁琳·斯盧瑟講座教授,世界著名心智和語言哲學家,在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等方面成就卓著。自1977年至今任美國國家人文科學院院士,2004年獲得美國國家人文科學總統獎章。塞爾還獲得過美國、英國和歐洲多所大學榮譽學位,以及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瑞典、西班牙、韓國等多個國家的獎勵或獎章。2007年,塞爾受聘為中國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一、20世紀60—70年代: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
綜觀塞爾半個世紀的學術生涯,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期的主要工作集中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研究,代表作有《言語行為:語言哲學論集》(1969)、《表述與意義:言語行為理論研究》(1979)。
在言語行為的研究方面,塞爾是少數原創性哲學家之一。20世紀50年代,他在牛津大學求學時,師從著名的牛津分析哲學家奧斯汀(j.l. austin)等人,而奧斯汀是公認的言語行為理論的創始人[2]。
塞爾這樣評價自己在言語行為和語言哲學方面的工作:
當我首次進入心智哲學領域的時候,大多數人都沒有關于言語行為的概念,他們認為,心智哲學、語言哲學和一般語言學研究語句,而語句是存在的對象。有時,他們把語句看作在實際上與陳述相同的東西,并且用研究語句的方法來研究陳述。由于奧斯汀、維特根斯坦和其他所有哲學家的工作,我們開始認識到,語言學習中所涉及的東西并不僅僅是抽象的語句形式,而是使用這些語句來實施一種言語行為,這種言語行為正是通過說出這些語句來完成的。因此,這種認識業已為我們研究語言哲學指明了一個新的方向,因為它將語言研究變為人類意向行為的一種形式,我們具有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理論,也就是人類活動的理論,這樣我們就有一種語言理論,如果我們將這些東西都一起加以吸收的話,這就是言語行為理論。我曾經致力于言語行為理論的研究,我認為在語言哲學中,整個言語行為理論是對傳統的語言研究的狹隘性的一個非常了不起的突破。當然,言語行為理論也開啟了心智哲學的研究,因為心智哲學和語言哲學是同一學科的分支。而在語言哲學中,從我們研究的所有東西都是抽象的語句這樣一種靜態的假設中突圍出來,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言語行為理論指出,我們研究的是人類行為的實際操作[3]。
塞爾對言語行為理論的發展和貢獻是多方面的:
第一,塞爾將奧斯汀的理論普遍化和規范化,并建立了言語行為理論和它的邏輯分析系統。
奧斯汀建立言語行為理論時,將通過說話來做事(doing something in saying something)看作是語言的一種特殊功能。塞爾則認為,“說事”也是“做事”,因此,通過說話來做事是語言的普遍性質和一般功能。奧斯汀區分了三種基本的言語行為,這就是語謂行為(locutionary acts)、語用行為(illocutionary acts)和語效行為(perlocutionary acts)。其中,語用行為是最重要的言語行為。奧斯汀還將語用行為分為判定式(verdictives)、執行式(exercitives)、承諾式(commissives)、表態式(behabitives)和闡述式(expositives)等五類。塞爾繼承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三分法,但卻不同意奧斯汀對語用行為的分類。為了提出自己的分類,塞爾首先分析了語用行為的形式結構,他用f(p)的形式來表達基本的語用行為,并對其中的語用力量f做了認真的分析。塞爾把自然語言中任何能夠按照字義用來說明話語的語用力量,或說明語用力量范圍的成分,稱為語用力量指示成分(illocutionary force indicating device,簡稱ifid)。塞爾認為,語用力量包括七種要素:(1)語用要點;(2)語用要點的力度;(3)完成模式;(4)命題內容條件;(5)前提條件;(6)誠實性條件;(7)誠實性條件的力度。
語用力量的七種要素可以被歸結為成功而無缺陷地作出一個基本語用行為的四種不同充要條件。假定聽話者理解一個話語的所有條件都被滿足,那么,在一個話語語境中成功而無缺陷地作出形如f(p)的語用行為,當且僅當下列四個充要條件被滿足:(1)說話者在該語境中以所要求的特征完成模式和語用要點力度成功完成命題p上的語用力量f的要點;(2)說話者表達了命題p,而且該命題滿足語用力量f限定的命題內容條件;(3)在該話語世界中,語用的前提條件和命題預設是得到公認的,并且說話者也假設它們得到公認;(4)說話者以語用力量f的誠實性條件的特征力度表達并具有該力量確定的心理狀態。
塞爾認為,語用行為在十二個方面能夠相互區分開來:(1)在行為類型的要點或目的方面的區別;(2)在詞和世界之間適應方向上的區別;(3)在表現出來的心理狀態方面的區別;(4)提出語用要點時,在力量或強度方面區別;(5)說話人和聽話人的身份和地位在對話語的語用力量影響方面的區別;(6)在與說話人或聽話人的興趣相關的說話方式上的區別;(7)在與談話的其他有關方面的不同;(8)在由語用力量指示成分決定的命題內容方面的區別;(9)在下述兩種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必定始終是言語行為,另一種行為可以是言語行為,但不必作出言語行為;(10)在下述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的完成需要語言之外的約定,另一種行為則不需要;(11)在下述行為之間的區別:一種行為的相應的語用動詞具有行為式的用法,另一種行為的相應的語用動詞則不具有行為式的用法;(12)在作出語用行為的風格方面的區別。
在上述工作的基礎上,塞爾提出了自己對語用行為的分類。他也將語用行為分為五類:
(1)斷定式(assertives),符號化表述為: b(p)
(2)指令式(directives),符號化表述為:! w(h does a)
(3)承諾式(commissives),符號化表述為:ci(s does a)
(4)表情式(expressives),符號化表述為:e(p)(s/h+property)
(5)宣告式(declaratives),符號化表述為:dβ(p)
可以看出,塞爾的分類及其依據與奧斯汀有很大的不同。塞爾的這個分類和它所依據的理論是對語言哲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的貢獻,并且已經成為關于言語行為的權威理論。
1985年,塞爾和他的合作者建立的語用邏輯(illocutionary logic),將言語行為理論的研究推進到邏輯分析的階段[4]。
半個世紀以來,奧斯汀和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在自然科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眾多領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除了對語言學、語言哲學、邏輯學和計算機科學特別是人工智能產生的影響外,對心理學、社會學、腦神經科學乃至整個認知科學,也都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史密斯(barry smith)評價說:“20世紀上半葉,英美哲學最重要的方面是被弗雷格的邏輯思想所塑造的。這種新邏輯所取得的成就帶來的副作用就是,它一直主導著那種亞里士多德式的觀念,即從本質上把語言看作不過是由或真或假的陳述或命題所組成的。因此,奧斯汀和塞爾的工作代表了對這種觀念的突破,這是非同尋常的。”[5](p49)
第二,塞爾提出言語行為的建構規則,在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建立了建構性關系,不僅豐富和發展了言語行為理論,也為他的社會哲學奠定了理論基礎。
塞爾強調,他的哲學由三個部分構成,即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他不僅把語言哲學與社會哲學聯系在一起,而且把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聯系在一起。在第一種聯系當中,塞爾為奧斯汀的一般言語行為理論充實了具體的內容。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除了言語行為理論的分類之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他提供了這樣一種理論框架:使得言語行為所涉及的話語(utterance)、意義(meaning)和行為(action)這三個向度被統一到了一起。因此,在塞爾的理論中,規則、意義和事實這三個要素在其后的思想發展中充當了重要的角色。
塞爾首先區分的是“調節的規則”(regulative rule)和“建構的規則”(constitutive rule)。前者是指用來調節已經存在的行為方式的規則,如用來調節“吃飯”禮儀的規則,而“吃飯”這種行為是獨立于該規則的。另一類規則是用來創建或規定新的行為方式,如下棋的規則,使人們有可能從事下棋的這類行為,而這種行為正是從給定的規則產生出來的。
塞爾指出,建構的規則具有“在語境c中,x被當作y”的基本形式。例如,在一輛行駛的汽車內發出“向左轉”的信號,在確定的方式下和確定的環境中就被當作向左轉的行為;在拍賣會上,舉起手指就會被當作投標的行為;說出“我答應給草地除草”,就將說話人置于一種責任之中。在建構的規則中,y代表某種結果,它或者是一種獎勵,或者是一種懲罰,或者是某人在將來有責任作出的行為。
塞爾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假設是,言語行為是一種根據相應的建構規則說出的話語表達式來完成的行為。因此,塞爾要區分僅僅是發出一些聲音,還是作出言語行為。這就意味著,他必須按照“x被當作y”的公式來分析通過一個話語所作出的行為。塞爾的分析與胡塞爾(e.husserl)或亞里士多德和弗雷格完全不同,他的分析的出發點,不是沉默的獨角戲中的語言,而是涉及說話者和聽話者的言語行為。
在塞爾看來,說話者說出一個語句t,這就意味著下面三個條件要得到滿足[6](p49):
(1)說話者具有意向i,即他的話語使聽話者意識到相應于t的事態是確實的。
(2)說話者通過確認意向i,想要使聽話者產生這種意識。
(3)說話者利用支配語句t的規則,想要聽話者確認意向i。
因此,當你作出一個言語行為時,也就創造了一個建構的事實。按照里德(t.reid)的說法是,你創造了一個微型的“市民社會”。建構事實的存在,僅僅是由于我們是在確定的(即認知的)方式下,并在確定的(即建構的)語境之中來對待這些世界。后來,塞爾又區分了與觀察者獨立的世界的特征和與觀察者相關的世界的特征。前者有力量、物質和地球引力等,后者有貨幣、財產、婚姻和政府等。在塞爾看來,后面的這些建構事實都是建構規則的系統。
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比奧斯汀要豐富得多,因為他不僅提供了言語行為理論的一般框架,還提供了關于言語行為自身詳細結構的豐富的說明。這樣,他就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切當性(felicity)條件:作出一個言語行為的條件和它的滿足性條件。在《語用行為的分類》[7]一文中,塞爾提出“適應方向”(direction of fit)這個重要的條件來判斷是否可以成功作出一個語用行為。按照他的說法,斷定式具有從語詞到世界的適應方向,用“”表示;指令式具有從世界到語詞的適應方向,用“”表示;承諾式也具有從世界到語詞的適應方向;表情式的適應方向為空,用“”表示;宣告式具有從語詞到世界和從世界到語詞兩個適應方向,用“β”表示。由此可以看出,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通過說出一個話語作出的言語行為與現實世界之間是具有密切關聯的。換句話說,塞爾的言語行為是先定的和必然的具有社會實在性的。
第三,塞爾通過對意向性和人工智能標準等重大理論問題的研究,完成了從言語哲學到心智和認知研究的轉向。
更為重要的是,塞爾不僅是一位語言學家,還是一位語言哲學家。他不僅要研究語詞和語詞的使用等有關語言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研究語言所涉及的哲學問題,如義務的性質、力量的性質和責任的性質等。在塞爾近期的著作中,還提出了自由行為、自愿行為和理性行為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他逐漸認識到,我們不僅要研究語言,還要研究大腦、心智、物理學的定律和社會組織形式。
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已經含有心智和認知的因素。例如,在他的基本的語用行為表達式f(p)中,包括語用力量f和命題內容p這兩個基本的成分(變元)。我們可以分別考察這兩個要素的變化,從而考察和表達一個語用行為所反映出來的說話者的意愿。事實上,在前面所給出的語用力量的七種要素中,對每一種要素的考察,如語用要點、完成模式、命題內容條件、前提條件、誠實性條件,都涉及對心智的分析。在《意向性》(1983)一書中,塞爾將言語行為研究延伸和擴展到認知行為(cognitive act)的領域。他所區分的命題模式(propositional modes)和意向內容(intentional contents),這類似于胡塞爾在《邏輯研究》一書中對性質(quality)和物質(matter)的區分。
在完成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創新性研究(20世紀60—70年代)以后,塞爾并沒有停止前進。他不會像一般的學者那樣,終身固守于一個屬于自己的領域,即便是業已取得巨大成就的領域。他以探索的精神去挑戰新的問題,開拓新的疆域。20世紀70年代后期,塞爾轉向心智哲學研究,其研究領域包括意向性、心智和意識、人工智能標準(中文房間論證)等。此后,他逐步成為一位公認的、卓有成效的心智哲學家。
二、20世紀80年代以后:意向性和心智哲學
塞爾的哲學由語言哲學、心智哲學和社會哲學構成。20世紀70年代末以前,塞爾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1975年以后,由于斯隆基金的投入和認知科學的建立,作為基隆基金主要受益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著名學者、認知科學的創始人之一,塞爾的研究方向發生了改變,他的興趣從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研究逐步轉向心智哲學和認知科學的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的兩項代表性學術成果是《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1983)和《心智、大腦和科學》(1984)。其中,他提出的“中文房間論證”成為反駁強人工智能的論據和人工智能的新標準。90年代以后,他在心智哲學方面的著作包括《重新心智的發現》(1992)、《意識之謎》(1997)、《意識和語言》(2002)以及《心智:簡短的導論》(2004)等。
塞爾的社會哲學貫穿在他的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之中,這與他的語言和心智觀有關。塞爾認為,語言不僅僅是一種能力,更重要的是一種社會行為。語言一經使用,言語一經說出,就建構了一種社會現實。因此,塞爾的社會哲學與他的言語行為理論、語言哲學和心智哲學是緊密相關的。(對塞爾社會哲學的討論不在本文范圍之內。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塞爾的《校園戰爭》(1972)、《建構社會現實》(1995)、《心智、語言和社會》(1998)、《行為中的理性》(2001)等。)
本節集中討論塞爾心智哲學的兩本重要著作《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和《心智》。
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適應方向”也體現了對心智的分析,而在《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中,塞爾將這種分析普遍化了。例如,信念具有從心智到世界的適應方向,愿望則具有從世界到心智的適應方向。每一個不同的心智行為都是如此,它們都反映了心智與世界的某種關系。信念、愿望、意向的滿足條件也被普遍化了。塞爾說:
在具有適應方向的情況下,滿足條件的概念非常普遍地應用于言語行為和意向狀態。例如,我們說陳述是或真或假的,命令是或者被服從或者被違背的,承諾是或者被遵守或者被破壞的。在每一種情形下,我們都把語用行為的成功和失敗歸結為該行為與現實的適應關系,而這種適應關系是由語用要點所規定的特殊的適應方向所確定的。我們可以對所有的條件貼上“滿足條件”或“成功條件”的標簽,從而得到一個表達式。這樣,我們說一個陳述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真的;一個命令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被服從的;一個承諾是被滿足的,當且僅當它是被遵守的,如此等等。現在,這種滿足概念也可以被清晰地應用于意向狀態。我的信念將被滿足,當且僅當事情就是我所相信的那樣;我的愿望將被滿足,當且僅當它們會被實現;我的意向將被滿足,當且僅當它們會被實行。因此,不論對言語行為還是意向狀態,滿足概念在直觀上看起來都是相當自然的,并可以相當普遍地應用于所有具有適應方向的地方[8](p10)。
可以看出,《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仍然留有言語行為理論和語言哲學的痕跡。但兩者又是截然不同的。在該書中,作者首先分析了心理狀態的意向(第一章);他發現不得不研究感知意向性(第二章)和行為(第三章);但如果不理解意向因果性則不可能理解感知和行為(第四章);這些研究導致對非表現的心理能力的基礎研究(第五章);作者的最初目標——揭示語言意向性與心理意向性之間的關系,體現在第六章的討論之中;第七章討論兩種特殊意向的語言表現形式;第八、九兩章使用前面的理論批評了當時有影響的指稱和意義理論,提出了對索引表達式和專名的意向性思考;最后,第十章提出關于“心身問題”(mind-body problem)和“心腦問題”(mind-brain problem)的一些結論。
塞爾認為,視覺經驗或其他類型的知覺經驗是具有意向性的,這一點在關于知覺的研究中被忽視了。在塞爾的言語行為理論中,他曾經為相信、害怕、希望等這些言語行為確定過“適應方向”的滿足條件。塞爾論證說,視覺經驗也具有滿足條件,就如同想念和希望具有滿足條件一樣。例如,我們不能將一輛車的視覺經驗與這輛車是黃色的旅行轎車這樣的經驗事實分離開來,正如我們不能把相信天正在下雨這個信念與天正在下雨這個事實分離開來一樣。兩者的類似之處在于:
第一,視覺經驗的內容總是由一個完整的命題來表達的,兩者是完全相同的。信念的內容也是如此。從意向性的觀點看,所有看見的視覺感知都是看見了如此這般的東西。因此,描述一個視覺感知的語句不能使用第一人稱的直接陳述句,而應該使用第三人稱的間接引語:
1a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of a yellow station wagon(我有一個關于一輛黃色旅行轎車的視覺感知)。
1b i have a visual experience that there i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there(我有這樣一個視覺感知,這是一輛黃色旅行轎車)[9](p41)。
1a不能清楚地表達一個視覺感知,1b才是視覺感知的正確表達形式。一般地說,在語言形式上說,x看見y只能用一個第三人稱的間接引語來表示。因此,一個完整的命題內容是視知覺的內容,即視知覺的意向內容。例如:
2a jones saw a yellow station wagon,but did not know it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瓊斯看到一輛黃色旅行車,但他不知道那是一輛黃色旅行車)。
2b jones sa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 but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a yellow station wagon in front of him(瓊斯看到,在他面前有一輛黃色旅行車,但他不知道在他前面有一輛黃色旅行車)[9](p42)。
2a沒有任何問題,是完全一致的。2b卻有問題,是古怪而難以理解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原因是前者不帶意向性,“看見y”的形式并不要求說話人報告y對主體的意味;而“看見+從句”的形式卻帶有意向性,從句表達了一個事實,它顯示了該事實對主體的意味,即對意向內容的限定。
第二,視知覺總是具有從心智到世界的適應方向,它的適應方向與信念一樣,但與愿望不同,后者的適應方向是從世界到心智。如果視知覺的滿足條件在事實上不能實現,如幻覺、錯覺、幻想等等,這是視知覺的過錯,而不是世界的過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說,“我們的感覺欺騙了我們”,而不是說我們的視知覺對或錯。視知覺不僅僅是表達的問題,它的對錯涉及適應方向。哲學家們用一些專門的術語來描述視知覺適應方向的錯誤,如“欺騙”、“誤導”、“歪曲”、“幻覺”、“錯覺”等,而用“如實”來描述視知覺適應的成功。
第三,視覺經驗與信念和希望一樣,是由其意向內容來表明其特征的。如果不用一個that從句來說明相信的內容,是不可能完全表述一個信念的;類似地,如果不用一個of短語來說明經驗的內容,也是不可能描述一個視覺經驗的。分析哲學家們所犯的典型錯誤就是認為對視覺經驗滿足條件的限定這樣一種謂詞可以從字面兒上來判定其對經驗自身的真假。這種假設是完全錯誤的。事實上,是由“黃色”和“旅行車”這種表示顏色及形狀的意向內容限定成分直接影響視覺經驗,而不是表示原因的謂詞影響視覺經驗。
在不使用概念和語言的情況下,視覺經驗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響呢?我們來看下面的例子。
例一,維特根斯坦的鴨—兔兩可圖。
在我們面前只有一幅畫,卻可以形成兩種不同的視覺內容,一種是鴨,另一種是兔。維特根斯坦對此的解釋是,這是對動詞“看”的不同使用所引起的結果。這種解釋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塞爾的方案是,我們可以按照類似于前面的“字面兒上的”解釋,在一種情況下觀察者看到的是這幅圖畫的一種樣式,在另一種情況下看到的是它的另一種樣式。那么,是什么因素使我們看到的是這種樣式而不是另一種樣式呢?塞爾認為,這是由心理因素決定的。正如約翰愛薩莉,他看到的是薩莉可愛的一面,而看不到薩莉不好的一面。事實上,對各種各樣的兩可圖的解釋,現在更多地采用心理學的方法。兩可圖是認知心理學的重要研究領域。
例二,繆勒—萊爾線(müller-lyer lines)。
上面兩個圖形中心部分線段的長度是完全一樣的,但a看起來比b長。在這里,我們視覺經驗的意向內容與我們信念的意向內容是矛盾的,前者破壞了后者。我們對月亮的視知覺也是類似的。月亮當空時顯得比在地平線上時要小,雖然我們相信月亮的實際大小并沒有改變。所以,如果沒有關于月亮大小不會改變的信念,我們的視覺就會提醒我們月亮當空時比它在地平線上時要小,但我們知道那只是一種錯覺。
在《心智》一書中,塞爾對意向性問題有了更深刻的表述。在該書中,塞爾是從心智哲學的立場來看待意向性問題的。塞爾認為,意向性問題是心智哲學中僅次于意識問題的另一個困難而又重要的問題。塞爾認為,意向性問題是意識問題的一個鏡像。這樣,塞爾就把意向性問題與心智哲學緊密結合起來了。
在《心智》一書中,塞爾從三個方面來研究意向性問題:第一,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第二,既然假設意向性狀態是可能的,那么,它的內容又是如何確定的;第三,意向性作為一個完整的系統又是如何工作的。
意向性是如何可能的?塞爾對二元論的解決方案、功能主義的解決方案、消解論的解決方案一一作了駁斥,認為它們都不能提供正確的途徑來解決這一問題。塞爾認為,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應該是腳踏實地的,我們無須考慮人的思想為何會到達太陽、月亮、凱撒和盧比肯河,因為這些問題太復雜;如果我們考慮動物為什么會感到饑餓和口渴,問題就要簡單得多。塞爾認為,這時我們所說的是關于心智的生理學能力問題,它是基本的,是我們考慮饑餓、口渴、性沖動、感知和其他意向行為的基礎。現在,“意向性如何可能”這個問題可以歸結為大腦何以會產生口渴的感覺這個問題。塞爾認為,這是因為,口渴是一種意向現象,而大腦具有處理這些意向性形式的功能。感覺口渴是有一種喝水的愿望。當2號血管收縮素到達大腦視丘下部的時候,它就會激發神經元的活動,神經元的活動最終會引起口渴的感覺,即引起一種意向的感覺。意識和意向性的基本形式是由神經行為引起的,也是由腦系統來實現的。由大腦和神經系統的機制來解釋口渴的意向,同樣適用于對饑餓、害怕、知覺、愿望和其他各種意向的解釋。塞爾認為,一旦我們將意向性問題從抽象的精神層面放回到真實的動物生理學的具體層面,意向性問題的神秘性就被破除了。這樣一來,動物何以具有意向狀態這個問題就再也沒有任何難解之謎。
意向性的結構和內容又是如何確定的呢?塞爾將意向性結構分為:(1)命題內容和心理模式;(2)適應方向;(3)滿足條件;(4)因果自我指稱性;(5)意向性網絡和前意向能力背景。顯然,塞爾繼承與發展了他在言語行為理論和意向性研究方面的思想。前三種意向性結構是對言語行為理論和《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相關內容的繼承和發展,后兩種意向性結構是塞爾的新創造。在因果自我指稱性方面,塞爾認為,大多數生物學上基本的意向現象都具有其滿足條件的邏輯特征。例如,關于我昨天去野餐的記憶,一定是由我去野餐這件事引起的。因此,記憶的滿足條件不僅包括已經發生的事件,也包括該事件的發生所引起的關于該事件發生的記憶。我們可以說,記憶、意向和感覺經驗統統都是因果自我指稱的。但另一些意向狀態卻不具有因果自指性,如相信、愿望等等,塞爾將它們與具有因果自指性的意向狀態區別開來。塞爾認為,每一個具有適應方向的因果自指的意向狀態同時也具有因果方向。塞爾將認知和意愿兩個族的因果自指性、適應方向和因果方向列表對照如下[10](p171—172):
由此出發,塞爾發展了一種關于意向因果性的全新的理論。他揭示了這樣一個事實,一個意向被滿足,當且僅當意向自身成為其滿足條件的其他各個方面被滿足的原因。因此,如果我要舉起我的手臂,這個意向被滿足并不是我要舉起我的手臂,而是這個意向引起我要舉起我的手臂這個行為。
與過去在《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中所作的分析不同,在《心智》一書中,塞爾不僅對意向性繼續做語言學和語言哲學的分析,而且將意向性研究與神經科學結合起來。下面是塞爾在《心智》一書中給出的關于意向分析的一個新的模型[10](p210—211):
其中,頂層的結構顯示行為意向引起身體運動;底層結構顯示神經活動引起生理變化;兩邊顯示神經活動與行為意向、生理變化與身體運動的關系,總之就是底層的活動引起頂層的活動。顯然,這是一個由神經活動(neuron firings)、行為意向(intention-in-action)、生理變化(physiological changes)、身體運動(bodily movement)構成的綜合模型,其關系是因果鏈關系,用符號表示,讀為“引起”。我們可以把這個模型表示為:
塞爾認為,這個模型在教育法上是有用的,但它容易讓人產生誤解,似乎意向在神經之上,宛如糖霜在蛋糕之上一樣。塞爾認為下面的圖示也許更恰當[11](p211)。其中,小圓圈代表神經元,陰影代表分布在神經元系統中的意識狀態。意向是整個系統的功能而不僅僅是在系統的上部。
三、幾點重要結論
我們以著名語言和心智哲學家塞爾為例,分析了從語言哲學到心智哲學的發展,從中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1.20世紀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體現了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再到心智哲學的發展路徑,塞爾是這一發展路徑的典型代表。
過去的一個世紀,西方哲學特別是英、美哲學有一條明顯的發展路線,這就是從分析哲學到語言哲學,再到心智哲學的發展路線。這條發展路線在塞爾哲學中得到了印證。在20世紀80年代以前,塞爾的主要工作是言語行為理論。70年代末,認知科學在美國建立,作為斯隆基金的主要資助對象和認知科學最早的發起單位,塞爾所在的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于1984年成立了認知科學研究的oru,塞爾是其中的重要成員。1983年,《意向性:心智哲學論集》一書問世,是他從語言哲學過渡到心智哲學的橋梁和標志。此后,他的工作重點轉向意向性和心智研究,并發表和出版了大量的論著,包括《心智、大腦和科學》(1984)、《心智的重新發現》(1992)、《意識之謎》(1997)、《心智、語言和社會:現實世界的哲學》(1998)、《行為中的理性》(2001)、《意識和語言》(2002)、《心智:簡明的導論》(2004)等。在塞爾看來,語言哲學是心智哲學的一部分,語言哲學最終一定會導向心智哲學。塞爾說:
我認為我們已經從以語言哲學為研究中心轉移到以心智哲學為研究中心。發生這種轉向的原因有很多。原因之一是,在語言哲學中正在發生許多激動人心的事情,而當我們對大腦如何工作有更多的發現,以及當我們對語言和意識的諸多問題做了透徹的研究時,在心智哲學中也有大量激動人心的事情正在發生,心智哲學已經轉移到了前臺。我認為,我們業已從語言轉到心智最簡明的原因就是,語言的最重要的性質是基于心智的,因此,意義和意向性是先于語言的心理能力,在我們能夠闡明語言的性質之前,我們必須將先于語言的心理能力搞清楚。語言依賴于心智,甚于心智依賴于語言[3]。
2.心智哲學與過去的哲學理論包括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既是一脈相承的,又有本質區別。心智哲學是認知科學的哲學,也就是在認知科學發展的背景下,特別是在腦和神經科學發展的背景下重新建構的哲學理論。
古代哲學是本體論哲學,它所關注的是世界的本原問題;近代哲學是認知論哲學,它所關注的是主體的認知能力問題;20世紀以英、美為主流的現代哲學是分析哲學,它將哲學的關注點轉向主客體之間的中介——語言。這種“語言轉向”又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前一時期是以前期維特根斯坦為代表的早期分析哲學,它以形式語言為哲學分析的基礎,以形式語言為基礎建立起來的數學邏輯為哲學分析的工具;后一時期是以后期維特根斯坦、奧斯汀、喬姆斯基、塞爾等一大批語言哲學家為代表的語言哲學,它將哲學的基礎重新轉向自然語言,以在經典邏輯的擴充和變異的基礎上建立的哲學邏輯、語言邏輯、人工智能的邏輯為哲學分析的工具。語言哲學是分析哲學的高級發展階段。
心智哲學繼承了古代哲學、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全部發展的積極成果,特別是與20世紀以來的分析哲學和語言哲學一脈相承。例如,心智哲學同樣認為哲學分析是與語言密切相關的,心智哲學不僅注重對形式語言的分析,而且更加注重對自然語言的分析。在語言哲學的三分框架中,心智哲學不僅注重句法分析和語義分析,而且更加注重語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關系的分析,即語用學的分析。在喬姆斯基的語言學理論中,單純的自然語言的句法結構分析屬于語言哲學的范疇,而先天語言能力、內在語言、普遍語法、唯理主義和心理主義這些理論由于將語言分析與心智相結合,它們已經屬于心智哲學的范疇。在塞爾的語義學理論中,意向性是理解語言意義的重要因素,而意向性是意識的反映,是與個人的心智相關的。意義的客觀性不復存在,任何意義都是主觀的建構,都是主客觀相結合的產物。在語用學方面,奧斯汀、塞爾建立和發展的言語行為理論是語用學的基礎理論及核心,根據言語行為理論,語言的意義是與說話者、聽話者、時間、地點和語境這五大要素密切相關的,人的因素第一次進入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的范疇,從而也就進入哲學分析的范疇。從以上發展可以看出,心智哲學最初是孕育于語言哲學母體中的一個嬰兒,兩者是血脈相連、不可分割的。但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以來,隨著認知科學的建立和發展,心智哲學已經逐漸脫離語言哲學的母體而誕生為一個獨立的生命,并發展壯大,逐步轉移到了以英、美為主流的西方哲學的前臺。
心智哲學與過去各種哲學理論的本質區別是:不論是在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基礎和邏輯方法上,心智哲學處處都將哲學問題與人的身體、心智聯系起來,哲學不再是一種脫離人的抽象的概念體系,而是與人的身體構造、生理結構、心理結構、心智狀況密切相關的理論,是“體驗哲學”[12]。萊考夫(g.lakoff)和約翰遜(mark johnson)在《體驗哲學——涉身的心智及其對西方思想的挑戰》一書中,一開始就提出三個重要的命題:心智與生俱來是被體驗的;思維通常是無意識的;抽象概念大多數是隱喻的。萊考夫說:“這是認知科學的三個重大發現。兩千多年以來,哲學家關于理智的性質的思考已經完結。由于這些發現,哲學決不可能再與過去一樣了。”[13](p3)萊考夫說:
理智不可能如傳統哲學所廣泛接受的那樣是與身體無關的,而是來源于大腦、身體和涉身的經驗。……
理智是進化的,抽象的理智基于“低等”動物所具有的感知的和原始的推理形式。……
理智不是超驗意義上“普遍的”,即它不是一種普遍結構。如果說它是普遍的,僅僅是指它是所有人類共同具有的普遍能力。……
理智不是完全理智性的,它大多數是無意識的。
理智不是純粹字面兒上的,它大部分是隱喻的和想象的。
理智不是與情感無關的,而是涉及情感的[13](p4)。
根據萊考夫和約翰遜,靈與肉完全分離的笛卡兒哲學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按照普遍理性的律令而具備道德行為的康德哲學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僅僅依靠內省而具備完全了解自身心智的現象主義意義上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功利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喬姆斯基語言學意義上的人、后結構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計算主義哲學意義上的人以及分析哲學意義上的人統統都不存在。在認知科學的背景下,哲學已經進入一個與人相關、與人的身體、大腦和心智緊密相關的全新的發展階段,這就是心智哲學的發展階段。
3.基于經驗和重視個體差異性的認知科學決定了心智哲學的本質。認知科學與過去的科學理論的區別是,在學科特征上,過去的科學強調的是科學原理的一般性,數學和邏輯的定理、物理學的公式、化學結構等,它們都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認知科學卻強調特殊性與個體差異性,曹雪芹之所以成為曹雪芹,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為愛因斯坦,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在基因表達上完全相同的同卵雙胞胎為什么會是不同的個體?這些都是認知科學所要關注的問題。
在學科目標上,20世紀的科學要上天入地,人類不僅要遨游太空,還要潛入深海;人類不僅要釋放核能,還要創造生命——這些都是20世紀科學所要解決并且已經解決的問題。21世紀的認知科學所要關心的卻是人自身。人類要搞清楚自己的大腦是如何工作的,腦如何產生心智,這就是腦科學特別是認知神經科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要了解人類所特有的符號語言與腦和認知的關系,這是認知語言學所要解決的問題;我們還想知道心理與認知的關系,如感知和注意、模式識別、學習、記憶、知識表征、推理與問題解決、情感與認知等,這是認知心理學所關注的問題;認知人類學要解決由人類文化發展和人類進化過程所決定的與人類種群特征有關的認知問題,如符號的起源、語言的地方性和民族性、人的文化存在方式、文化的進化、文化的適應性和不適應性、文化與基因的雙重進化等;認知計算機科學即人工智能要解決機器智能的問題,如人工智能的標準、人工智能與人類智能、機器的感覺和知覺、機器人和智能體等。心智哲學要解決困擾人類數千年的心身(mind and body)問題、人類的意識之謎、意向性問題、心理因果性問題、自由意志問題、無意識行為的問題、感知問題、自我問題等。因此,心智哲學是一種“以人為本”的哲學。
在科學與人的關系上,過去的科學理論標榜自己的客觀性,排斥一切與人相關的因素,試圖創建一種絕對的知識體系和以真假來判定的真理標準。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和數個世紀,甚至在人類歷史的漫長歲月中,人類尋求的科學原理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普適的知識。科學來源于實踐,它的理論又超越于實踐而凌駕于實踐之上。在現代社會中,科學技術甚至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宗教。與此不同,認知科學不假設過去的科學理論所肯定的這些前提,而把科學理論看作是人的創造與建構。
4.由于對心智和腦的研究,由于認知科學的發展,許多學科的面貌就煥然一新了。認知科學對21世紀科學研究和學科建設有以下三個層面的推進作用:
首先,形成nbic聚合技術,促進人類的生存和發展。2000年,人類進入新世紀之初,由美國近八十名科學家所作的一份研究報告將新世紀的帶頭學科確定為納米技術(nanotechnology)、生物技術(biotechnology)、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y)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合稱為nbic,亦稱為聚合技術(converging technology)。該研究報告指出:“在下個世紀,或者在大約五代人的時期之內,一些突破會出現在納米技術(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統之間的界限)、信息科學(導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機器)、生物科學和生命科學(通過基因學和蛋白質學來延長人類生命)、認知和神經科學(創造出人工神經網絡并破譯人類認知)與社會科學(理解文化信息,駕馭集體智商)領域,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術進步的步伐,并可能會再一次改變我們的物種,其深遠的意義可以媲美數十萬代人以前人類首次學會口頭語言知識。nbics(納米—生物—信息—認知—社會)的技術綜合可能成為人類偉大變革的推進器。”[14](p102)
這份重要的研究報告還指出,在nbic四大科學技術中,認知科學是先導:
我們看到,聚合技術的協調綜合以認知科學為先導。因為一旦我們能夠以如何(how)、為何(why)、何處(where)、何時(when)這四個層次上理解思維,我們就可以用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來建造它,用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來實現它,最后,我們就能夠用信息技術來操縱和控制它,使它工作[14](p281)。
其次,在認知科學的學科框架內,促進六個相關學科的發展。認知科學由哲學、心理學、語言學、人類學、計算機科學和神經科學等六大學科所支撐,在這個框架內,已經形成心智哲學、認知心理學、語言與認知、認知人類學、人工智能、認知神經科學等六個新興學科,它們被稱為認知科學的核心學科。(1)心智哲學研究與人類心智相關的哲學問題。哲學與心智相關的三個經典的問題是:精神與物質的關系;心智的結構和知識;第一人稱視角和第三人稱視角。與認知科學相關的其他哲學問題和領域還有: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和二元論;分析哲學、日常語言哲學和自然轉向;科學哲學;認知科學中的心智;民族心理學問題;意向性和心理內容;邏輯與心智科學;哲學與生理學,等等。(2)認知心理學是與信息處理相關的心理學,它涉及感覺的輸入和生理運動的輸出。鳥類和哺乳動物,特別是靈長類動物(尤其是大猩猩和人)都具有最復雜的智能形式,需要建立理論來處理它們的思維機制和內在經驗。認知心理學所關注的問題有情感、感知、注意、記憶、決策和問題解決、語言和交際、認知發展和認知結構、學習、智力等。(3)認知神經科學也是關于信息處理的科學,它涉及的問題有如何獲得信息(感覺);如何建立解釋、確定意義(感知和認識);信息的存儲和修改(學習和記憶);沉思(思維和意識)、預測未來的環境狀態和行為結果(決策)、指導行為(神經動力控制)以及語言交際,等等。(4)人工智能有兩種含義:一種是關于智能機器創造的工程學科;另一種是關于人類智能的計算機建模的經驗學科。在早期,這兩種含義常常不加區分,現在已逐漸將它們區分開來,前者(人工智能)是現代計算機科學的一個分支,后者(計算機智能)是現代認知科學的一個分支。計算機智能所關注的領域和問題有機器和認知;人工智能;認知建構;知識基礎系統;邏輯表達式和推理;邏輯決策;不確定信息的表達和推理;不確定性下的決策;學習;語言;視覺;機器人技術;復雜性、合理性和智能,等等。(5)認知科學的語言學重視自然語言的研究,尤其重視言語(口語)的研究。語言與認知所關注的問題有語詞和意義;語言結構(語詞和聲音,短語結構和生成語法,詞庫,語言界面和語義學,意義);語言使用(語境中的語言,變動中的語言,心智中的語言)。其他被關注的問題還有人機交互;機器的言語識別;言語合成;腦與雙語學習,等等。(6)認知人類學或稱文化、進化與認知不僅要研究認知的個體差異性,而且要研究認知的群體性、民族性和社會性。個體是屬于群體的,個人的機體是種群的成員并享有同一基因組;生物體在本質上具有種群特征的認知能力,同時帶有表面的個體差異性。人類的社會生活是富有文化特征的。由于人類的認知能力,社會性和文化才成為可能。認知人類學研究這些認知能力發展的個體發生學和系統發生學,并對認知過程提供社會的和文化的信息。認知人類學關注人口層次的認知現象,它從三大視角來研究文化、進化與認知的關系——從比較和進化的視角來看認知;從進化和認知的視角來看文化;從生態的、社會的和文化的視角來看認知。
最后,通過多級交叉、綜合與輻射,認知科學將會推動更多學科的發展。例如,通過認知科學六大基礎學科和六大核心學科之間的交叉,已經形成更多的新興學科,如控制論、神經語言學、神經心理學、認知過程仿真、計算語言學、心理語言學、心理哲學、語言哲學、人類學語言學、認知人類學、腦進化等。
實際上,認知科學對學科發展的影響遠非如此,即便是傳統學科,如邏輯學、數學、物理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法學、管理科學、教育學的發展也離不開認知科學,因為所有這些學科的研究都與人相關,與人的心智相關,因而與認知科學相關。可以說,在21世紀,如果不做認知科學研究,或者不與認知研究相結合,很多學科都無法深入發展。
這就是本文通過對過去的一個世紀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思想和學術發展的主線“語言心智認知”的分析,所試圖昭示和預測的未來發展藍圖。
【參考文獻】
[1]蔡曙山.沒有喬姆斯基,世界將會怎樣[j].社會科學論壇,2006(6).
[2]austin, j. l.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蔡曙山.關于哲學、心理學和認知科學12個問題與塞爾教授的對話[j].學術界,2007(3).
[4]searle, john r. and vanderveken, d. (1985) foundations of illocutionary logic. cambrid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蔡曙山.言語行為和語用邏輯[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5]smith, barry (2003) john sear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searle, john r.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searle, john r. (1975) a taxonomy of illocutionary acts. in keith gunderson (ed.), language, mind and knowledge: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vol. 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8]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9]searle, john r. (1983) intentionality: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mi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0]searle, john r. 2004.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searle, john r. 2004. mind: a brief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lakoff, g. and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篇7
一、 意識與生命的探索
《超驗駭客》與《超體》兩部影片,分別借助人工智能體與“進化人”的構想,傳達人類對于意識與生命無盡探索的深刻主題。通常意義上,“人類意識不僅能反映外部客體,形成三維空間的立體物象,而且能覺知實物在空間和時間中的變化,把握事物的運動規律;不僅能駕馭主觀狀態,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精神世界,而且能發展高度的監控和調節能力,超前地反映和評價自己的行為后果,選擇最佳的行為方式,實現預定目標”。[1]古今中外,基于對意識不同的闡釋形成了諸多理論體系,人類從來沒有停止研究意識問題的腳步,篤定終有一天揭開其神秘的面紗。
影片《超驗駭客》中,致力于研究超級人工智能計算機開發的科學家威爾夫婦,在威爾將死的時候突然決定將威爾的意識傳入超級電腦,這種冒險行為卻為驗證意識力量的強大奠定基礎,不久,威爾以計算機的形態“復活”于世,并將他的意識通過電磁波傳達出來。之后,在大量太陽能的供應下,威爾通過互聯網生成了納米微粒技術,這種納米微粒無處不在,其功能在于專門修復受損細胞,使其再生重建。凡是經受過納米微粒醫治的傷者或是殘疾人,手術后都會自動“聯網”,由此,這些人隨時都有可能成為威爾指令、表達情感的客體,世界進入一個由超級智能計算機“控制”的時代。另一部影片《超體》則主要借助主人公Lucy呈現了人類意識的開發由低到高直至100%的奇妙過程。女主角Lucy原本只是個在中國臺北工作的美國公民,遭人欺騙后不慎卷入國際某販毒組織的黑暗陰謀――利用人體的方式運送新研制出的CPH4到指定地點。一次意外的攻擊讓藏在其腹部的CPH4擴散出來,Lucy的身體逐漸產生異樣,隨即開始了爭分奪秒超人類的生活。隨著意識的開發程度提高,Lucy先是掌握控制自己身體的技能――在零麻醉的狀態下,徒手掏出右側胸部的子彈,而后Lucy的學習能力飛速增強――短時間內就可以熟識外語與開車,到最后Lucy可以隨意穿梭時空――來到相隔萬里的城市,來到遙遠的侏羅紀時代。兩部影片關于意識力量的夸大想象,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整個人類社會對于意識探索領域的美好期待。
關于生命的探索,同樣是兩部影片共同傾向表達的主題。影片《超驗駭客》中,“復活”后的威爾仍舊信奉并踐行“智慧科技可以治愈疾病,掃除貧苦與饑餓,甚至治愈地球”的價值觀,他生成的納米微粒技術可以醫治將死之人,可以讓普通人達到人類前所未有的速度與力量的限度,這種科技化“仙丹”的構想無疑襯托出現代人對生命無限延續的希冀與渴望。
二、 人性多元化的展現
提及科幻片,眾多好萊塢影片的主旨建構,大都集中于正義戰勝邪惡,或是人類戰勝異類,而《超驗駭客》與《超體》兩部影片卻將這一慣性主旨加以深化拓展,在探索意識與生命無限奧秘的同時,同樣注重對于人性多元化的展露。關于人的本性問題的研究,在中國,自古有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以及莊子的性自然論等等;在西方,有宗教神學的原罪性惡論,也有人文主義提出的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觀點等等。面對日夜憧憬的高科技時代的到來,兩部影片《超驗駭客》與《超體》分別采用逃離與直面的方式,于相似的結局中深刻詮釋人性的多元化。
影片《超驗駭客》中,逼迫威爾選擇的逃離的異端力量是反科學,他們很早就暴露其令人畏懼的殺傷力――將涂有鐠同位素的子彈射進威爾體內,使其中毒身亡。之后,他們拉攏威爾的好友麥克斯與約瑟夫博士,鼓吹超級人工智能計算機的稱霸野心,最終成為毀滅智能“威爾”的主謀。弗洛伊德早期的研究曾經指出人類除了性(欲)本能,還有避險求安的本能。影片中約瑟夫博士等人驚異于納米微粒技術的同時,更懷疑人工智能“威爾”在建造自己的軍隊,他讓納米微粒隨著氣流散播到世界各地,使原有的有機生命終結,最終使得所有的一切都為服務于一臺機器而活。“保守勢力”的妄然猜測源于對太過異樣現象的無知與恐慌,同樣也是避險求安人性本能的恰當體現。此外,作為科幻片,《超驗駭客》并沒有以正義與邪惡兩勢力的對抗草草收尾,而是選擇一條溫情路線――在毀滅智能“威爾”的過程中,伊芙琳意識到“威爾”的意圖并不在于毀滅世界,而是要超驗人類,他所堅持的一切都是在幫助自己完成最初的夢想。愛情的忠貞不渝雖然沒能躲過外界的擊打與對方的背叛,但是威爾那份真摯的感情充分展現出善與美的人性。
與智能“威爾”不同,影片《超體》中的超人類Lucy則選擇了直面的應對方式,在得知大量CHP4的攝入使自己具備“超能力”后,Lucy一改之前誤入虎穴的恐慌,從容地接受著體內細胞的進化。當預感到這種超能力隨時會終結自己,Lucy更是果斷地找到人腦研究專家諾曼教授,試圖將自己所掌握宇宙萬物的知識――量子物理、應用數學以及細胞核無限潛能的相關理論全部傳輸給教授,用以研究,造福人類。在藥物的控制下,“進化”后的Lucy雖然喪失疼痛與欲望的能力,但她仍舊清醒地認識到強大的過程意味著人性的逐漸喪失,當幫手戴爾里奧警官想要離開時,Lucy動情地挽留他:他會提醒自己人性的存在。令人深感欣慰的還有諾曼教授,面對Lucy的求助,他沒有不屑與嘲笑,而是第一時間表現出信任與關懷,這種尊重科學,尊重生命的態度引人深思。當然,單純依靠諾曼教授的支持,并不能保證Lucy獻身科學之路的一帆風順,CHP4的研制組織在利益的驅動下誓死要鏟除Lucy,拿到剩余的藥物劑量。黑幫大佬和毒梟韓國人張先生最初耗費天價研制CHP4,不過是將其視為,并沒有料想催生出一個“女超人”,在追殺Lucy的過程中,黑幫勢力不惜運用大量殺傷性武器,濫殺無辜,這種利己主義,拜金主義的舉動無疑印證了Lucy關于“人類只想著權力與利益”的說法,當Lucy聲稱是人性扭曲了人對世界的感知能力的時候,影片的精神內涵不言而喻。
三、 超人類技能的呈現
比起令人炫目的未來之戰的科幻片,《超驗駭客》與《超體》兩部影片看似以深奧博大的觀念或是假說吸引觀眾,但其炫技的功力同樣值得稱贊。影片《超驗駭客》中,伊芙琳將威爾的意識與互聯網相連,從最初的與金融體系和教育機構的數據庫聯結,到后來納米微粒技術的開發,智能“威爾”展現了超人類智能的威力與潛力。網絡與電子設備保證“威爾”時刻忠誠地守護在伊芙琳身旁,他引導伊芙琳來到光明樹的小鎮,試圖在這里建造純凈的原生環境;伊芙琳孤獨的時候,他會點燃蠟燭讓客廳溫馨起來;為了能夠讓伊芙琳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威爾”先是將自己的聲音與思想通過與自己聯網的技術員傳達出來,之后更是制造出真實存在的自己,讓伊芙琳既驚喜又驚慌。此外,隨著智能“威爾”對網絡利用率的日漸提高,“威爾”可以借助任何與網絡相連的電子設備了解所需的一切,他可以獲悉反科學的任務計劃,甚至還可以肆意窺測每個人的被數據化的身體狀況與情感狀況。影片《超體》中,藥物CHP4通過血液在Lucy腹部擴散至全身的特寫鏡頭,拉開了影片超人類技能的呈現帷幕。“進化”后的Lucy,其腦力的運用可以逐步達到100%,細胞的異常迅速增長賦予其超強的學習能力,她可以極速掌握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知識,也可以兩個手同時操作電腦,對獲取的資料過目不忘。CPH4賦予Lucy更強大的則是控制能力,她可以控制自身的新陳代謝;可以控制常見的電磁波,通過電視機、電腦、手機等通訊設備隨意接收并傳遞信息;還可以控制他人的身體,通過肢體接觸獲取對象的記憶,通過意識操控他人的思想與行為等等,展現了一個“女超人”所具有的各種技能。
兩部影片關于超人類技能的展現,一方面滿足觀眾對于人類超常技能的幻想欲望,另一方面也試圖借用夸張的想象驚醒人們關注科技的兩面性。影片《超驗駭客》中的納米微粒技術使人獲得永生的同時,一定程度上泯滅了個體的原生情感,這種反殘缺反銷毀的理念,實際同樣破壞著長久以來萬物竭力遵循與維護的生態平衡。影片《超體》中的CHP4是一種花費巨資研制成功的藥物,少量攝入使人產生幻想,令人精神萎靡,大量的吸收則造就了超人類。與一樣,CHP4同樣使人表現出藥物依賴的癥狀,個體需要不斷攝入才能保證機體的維持,才能保證最終“進化”的完成。科技帶給人們便利生活的同時,也會伴有潛在的威脅,恰如影片《超驗駭客》的結尾處留給我們思考:“科技帶給人類什么?”
結語
人類的科技水映著現代文明的進步程度,然而現代文明并不意味著原始生態環境的消亡,科技的發達應當兼顧對污染的治理與對自然環境的修復。《超驗駭客》與《超體》兩部影片在闡述意識與生命的無限深奧之余,同樣表達著對人類遵循自然規律及回歸原始自然環境的暗示與勸誡。當Lucy與原始人互動的鏡頭出現,當露水從威爾夫婦的向日葵上滴落下來,人們不禁感嘆:唯有自然賦予生命色彩。
篇8
關鍵詞:意義;話語;社會
[中圖分類號]H31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2831(2013)02-0192-4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1.045
劍橋大學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了著名語料庫語言學家、《國際語料庫語言學》雜志原主編、英國伯明翰大學英語系教授Wolfgang Teubert的新作《意義、話語與社會》(Teubert, 2011)。話語是復雜的,能夠傳遞的意義亦并非單一理論能完全解釋,語言哲學與社會學研究對話語意義的討論亦從未終止,而該書的出版無疑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話語意義本質的認識。
1. 主要內容
本書290頁,共16章,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意義,心智及大腦”(1~7章)詳述認知范式意義研究存在的問題,第二部分“話語與社會”(8~16章)深入論述作者在意義、話語與社會三者關系上所持的觀點。
第一章,認知范式的語言研究。喬姆斯基語言學與認知語言學在過去五六十年里各自建立了一套反映該機制如何運作的語言認知模型。然而,這些模型在作者看來根本無法真實反映個體令人難以捉摸的心智以及其內在的語言機制,原因是這些認知模型本質上是由一系列話語建構而來的話語客體,而非真實經驗的客觀存在,即所謂的內在機制。而且由于忽視了語言的社會性,此類建構語言認知模型的嘗試,充其量亦只能體現某一交際個體的經驗。
第二章,認知語言哲學的歷史回顧。作者指出,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基本主張,即話語的意義需要訴諸于人的心智中某個特定機制的思想并非是新創的。相反,它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Aristotle的《論詮釋學》:自然語言中的口語或書面語均依賴于相同的心靈體驗而產生意義;阿拉伯哲學家Averroes贊同Aristotle的觀點,認為口語或書面語的意義是規約的,而心理概念則是普遍的。中世紀英國哲學家Anselm of Canterbury主張心理意象即為口語或書面語的意義;另一位中世紀哲學家William of Ockham則進一步發展了心理意象理論。無論是Aristotle的心靈體驗,Averroes的心理概念,或是Anselm of Canterbury的心理意象,指的均是認知語言學的術語中的“概念表征”。
第三章,心理概念。作者回顧了20世紀后50年里認知語言學家對心理概念的討論,其中亦是仁者見仁。Chomsky主張心理概念是天賦的,Hilary Putnam則反對這種看法,他認為“意義不只存在于大腦中”(Putnam, 1981);Jerry Fodor在其1975年出版的《思維的語言》(The Language of Thought)中指出,自然語言的所有詞都有與之相對應的心理概念,而Anna Wierzbicka則認為,不同的語言擁有不同的心理概念,人的心智只包含數量有限的基本心理概念或語義啟動,復雜的心理概念的配置是依靠這些語義啟動來完成的。另外,基本心理概念是相互獨立的項還是彼此之間存在一套心靈語言句法,不同學者亦是智者見智。
第四章,理論義素與客觀現實。作者探討了歐洲結構語義學與認知語義學在詞匯意義的概念化方面的不同看法。Bernard Pottier最初使用義素一詞,是用它來指代詞匯意義的最小語義構成成分的。而當時深受喬姆斯基語言學影響的德國語言學家Manfred Bierwisch則將義素視為基于人的認知的實體,認為義素同心理概念一樣是天賦的。這種對義素的知識本體的堅持,一方面使認知語義學有別于結構語義學,另一方面反倒使義素概念亦變得難以捉摸。
第五章,從概念表征到概念知識本體。隨著計算科學的發展,概念、概念表征等認知概念得到廣泛應用,計算語言學家試圖依靠概念與概念知識本體(相關概念的集合)實現復雜的機器翻譯與人工智能。但作者認為,由機器翻譯或人工智能得到的語言充其量只能稱為受控語言,不是自然語言。
第六章,何為意義。作者詳細列舉了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問題。其一,術語繁雜,缺乏統一認識。其二,對心理概念與詞匯意義的關系也存在不同的看法。Jerry Fodor與Ray Jackendoff認為心理概念與現實詞匯是一一對應的,Stephen Levinson認為心理概念應是更加具體化的,即心理概念多于現實詞匯,而Dan Sperber與Deirdre Wilson則主張心理概念是抽象的,即心理概念少于現實詞匯。其三,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根本問題,是完全忽視了語言的社會性,而過分聚焦于為心理概念建立結構性的分析與描寫。
第七章,意義何處尋。作為對該書第一部分“意義,心智及大腦”的總結,作者指出,認知語言學沒能說服我們心智即意義之所在。心智與心理概念是不可捉摸的,認知范式或神經語言學的意義研究無益于對意義的本質的認識。意義并非相互獨立的個體意向性,亦非個體概念知識本體,更不存在于個體的大腦中。
第八章,作為話語的語言。本章是該書第二部分“話語與社會”的開始。作者提出一般話語是人類話語客體的總和,而具體話語則指代的是具體的自然真實語料(即具體的話語客體)。Wolfgang Teubert主張意義是源于自然真實語言的,因此本章特別強調了自然真實語料在分析語言意義時的唯一可靠性。
第九章,語言與社會。符號化是交際產生意義的前提。話語的意義是話語社團的集體意向性,也是話語社團的成員對話語客體的解讀。
第十章,口述社會。作者指明外在現實與話語共享現實的區別,并指出在口述社會中話語客體語料源于話語共享現實。
第十一章,口述社會與文字社會。作者駁斥了關于寫作的起源的錯誤認識。之后,舉例說明了文字的產生在話語社團的集體意向性即話語意義的產生中的作用。文本同口傳社會交際一樣,其意義依語境而變而非一成不變。
第十二章,實證性語言研究離不開語言數據。作者反對認為只有口語才是語言學研究對象的觀點。另外,在作者看來,通過綜合語言分析、探究說話人意圖等途徑推導出意義的嘗試是沒有必要的。
第十三章,意義,知識及話語現實的建構。作者指出意義與知識只是從不同角度對同一話語客體的不同描述。意義在話語社團成員的協作際行為過程中不斷被加以修改。協作際行為建構話語共享現實。
第十四章,科學實驗報告。作者不同意科學實驗報告是描述客觀實驗現實的文本的觀點。他認為科學實驗報告描述的是各種已存在于話語共享現實中的相關話語客體,如方法論、實驗設備、實驗數據等,其所傳遞的知識或意義亦是一種話語知識,而非真理。
第十五章,歷時性、互文性及闡釋學。作者指出,闡釋學與后結構主義均認為我們所說的現實是話語建構的現實,是話語構念而不是客觀存在。在話語共享現實的社會建構中,對某一話語客體的闡釋,依賴于它與其所在話語共享現實內部的其他話語客體的相對關系而不依賴于客觀現實。因此所產生的話語意義不是一成不變的。
第十六章,俳句的意義。作者通過實例詳述了互文性與闡釋學在解讀俳句,分析話語客體的意義中的作用。
最后是該書的結論。作者回顧了全書的主要內容,并再次指明,文本(經轉寫的口語或文本)的意義是話語社團成員對相關文本的互動性闡釋與再闡釋。因此,考察文本的意義無需關注個體意向性、作者的心理意圖或所謂的心理概念,而只需關注文本本身以及它與其他文本的互文性。
2. 評述
何為話語意義?話語意義從何而來又如何去尋它?這是自從古希臘哲學家就開始思考的問題。不同哲學家與語言學家對這些問題亦是各持己見。尤其是如今方興未艾的認知語言學,其理論對話語意義研究的影響日益深刻,但作者Wolfgang Teubert在該書中所闡釋的話語意義觀與認知語言學對話語的認識大相徑庭,他作為語料庫語言學家的背景在這本探討話語意義的書中亦展露無遺。該書的亮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該書對于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反駁是全面的、根本的。作者并未在本書一開篇便開始闡釋他本人的話語意義觀。相反,作者用該書第一部分,即“意義,心智及大腦”整整六章的內容系統地分析了古希臘與中世紀哲學、歐洲結構主義語義學、喬姆斯基語言學及認知語義學等話語意義研究的歷史發展。這種歷時性的分析無疑使作者更為準確地發現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缺陷。作者從追問心智語言學研究的歷史開始,到深入批評認知范式所指的意義即“心理概念”的不可捉摸,再到最后指出計算科學(機器翻譯與人工智能)采納“概念知識本體”作為自動生成語義的計算單位的不切實際,作者對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基本主張提出根本性的質疑,即這類研究存在以下問題:其一,研究對象心理概念完全不可及;其二,研究內部對其基本術語都缺乏共識;其三,研究過分注重認知而完全忽視了語言的社會屬性。
第二,該書關于意義、話語與社會三者的動態關聯的闡釋是建設性的。作者認同批評話語分析關于社會意識形態影響話語建構的論述,但他不同意后者所持的社會在話語與社會的二元關系中起主導作用的主張,他認為情況恰好相反。原因是“權力”、“意識形態”等所謂的影響話語建構的社會因素首先必須是話語共享現實中的話語客體。因此,作者不認為話語是一種社會實踐,相反,首先是話語建構了社會。Wolfgang Teubert所說的話語建構社會的過程是指話語建構起社會中的人即話語社團成員所共享的話語現實的過程。作者看來,人類唯一可及的現實是話語建構的現實,是話語共享現實中的各種話語客體即包括批評話語分析側重的“權力”、“意識形態”等,而非外在現實中的客觀存在。話語的意義,或者Wolfgang Teubert所指的話語客體的意義,正是在話語社團成員對這種共享現實進行協作性闡釋與再闡釋的過程中產生并不斷變化的。對某一話語客體的闡釋與再闡釋依賴于話語共享現實中的其他相關話語客體,即話語客體的意義之源在話語建構社會的過程中,而非心智中的某個內在機制。它是話語社團的集體意向性而非話語社團成員的個體意向性。由于不斷被闡釋與再闡釋,話語客體的意義因此是暫時的、可協商的。
第三,該書強調了自然真實語料在話語意義研究中的作用。Wolfgang Teubert指出,正是由于話語(客體)的意義是在話語建構社會的過程中產生與變化的,因此話語意義要在話語社團成員在協作性的社會交際中說了些什么中找尋,所以自然真實語料在話語意義研究中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無法獲知大腦是怎樣工作的,所以不得不依靠所掌握的事實,也就是真實的語言數據(張瑞華,2009)。Wolfgang Teubert還同時指出,經轉寫的口語語料或文本均可作為實證性語言研究的研究對象,因為二者均為構成人類一般話語的一部分,是具體的話語客體的集合。作者不遺余力地強調自然真實語料在話語意義研究中的作用,因為語料庫語言學不僅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而且提供了一種新的看待語言的方式(張瑞華,2009)。
最后,該書亦有不足之處。其一,Wolfgang Teubert給予認知范式意義研究的部分批評有失偏頗,難脫一概而論之嫌。例如,作者聲稱認知范式意義研究完全忽略了語言的社會性與語境對話語意義的影響。然而,例如認知語用學中的關聯理論所講的言語交際的明示——推理模式中語境顯然是推導話語意義必不可少的因素。其二,作者對如何借助自然真實語料找尋話語意義的具體方法討論顯少,似乎是乏于為其正名所致。其三,該書在內容版排上存在瑕疵,時而以某個語詞作章節題目,時而又以成句代之。不過,這些缺陷不足以影響Wolfgang Teubert所著此書為話語意義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論與方法論參考。
參考文獻
Putnam, Hilary. Reason, Truth and Histor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篇9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科技異化;科技人化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4-0008-02
經濟全球化是指,由于科技的發展,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了更高的水平,社會生產超越國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等的過程。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高科技變得越來越不神秘。撲面而來的高科技浪潮沖擊著、改變著人類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也沖擊著、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高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發展,為社會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財富,為經濟全球化奠定了物質技術基礎,同時,經濟全球化也反過來促進了科技在全球性的蔓延和擴張。科技與經濟的迅速發展在給人類帶來巨大財富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加劇了業已存在的全球問題,環境問題、能源問題、人口問題等變得異常尖銳,并隨之產生了科技異化問題,威脅人類的生存。面對這樣的境況,能夠提供給我們什么樣的解決思路呢?首先,我們需要先明確,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科技異化并不代表著對科技文明的徹底懷疑和全盤否定。在的指導下,全文通過分析科技異化的產生的背景、表現及其危害,尋找出消解科技異化的途徑即科技人化,以使科技更好地服務于我們的生活。
一、科技異化產生的背景及原因
(一)理論背景
異化是指主體所產生的對象物、客體,不僅同主體本身相脫離、相對立,而且反過來束縛支配乃至壓抑主體。人是異化的核心,在現實中從事社會實踐活動的并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的人是異化的最終落腳點。
勞動異化是指在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創造的財富被資本家占有并用來支配和奴役工人。勞動所生產的勞動產品作為異己的存在物同勞動主體相對立。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勞動是一種異化勞動。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異化的四個方面:其一,勞動產品同勞動者相異化。實質上揭示的是資本主義社會里勞動者與對象世界的關系處于一種異化狀態。其二,勞動活動同勞動者相異化。其三,人同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是類的存在物,人具有能動性,能全面自由地把握任何事物的本質屬性和可能性。而把這種可能性轉變成現實性是由勞動來完成的。其四,人從人中的異化。“人從人中的異化”指的是異化出與勞動者相對立的資本家。資本家不勞動卻統治了勞動對象和勞動產品,勞動產品不歸勞動者所有而是為資本家追求利潤服務的。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現代科技的突飛猛進,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類的文明開辟了更為廣闊的空間,也為人類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經典作家早就看到了科學的這一歷史作用。但是,科學的作用也表現出另外一面。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體系內部,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使工人崎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機器的附屬品,……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
所謂科技異化,就是科技作為人類的創造物和本質力量的體現,本應由人駕馭、為人服務、造福于人,卻反過來控制、威脅甚至危害人類。具體表現為:科技的發展漸漸超出人類控制,甚至成為支配、統治人類的外在異己力量;科技已不再是給人類帶來自由和解放的偉大工具,它導致了人的物化和自由的喪失,造成了精神的空虛和人格的分裂;人由掌控科技發展的主人發展成為被不能控制的科技推動的社會的發展的工具。
(二)實踐背景
工具理性是一種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在當前這個高速發展,重物質輕精神的時代,全人類都以現代化為社會目標,追求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現代化雖帶來了巨大的物質進步,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也造成了社會病態。現代化的基調就是理性化,而理性主義獲得最有力的表現是科學和技術。根源于科學的技術實際上塑造了現代世界的性格。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稱這種現性為“工具理性”,因為它無視生命的價值問題,只涉及了達到目標的手段和工具的合理性。隨著工具理性的極大膨脹,物極必反,過度地追求效率致使理性由解放的工具退化為統治自然和人的工具,進一步導致了人的異化和物化。
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進而極大地推動了工業文明的發展。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進行了多次科技革命。一方面,將科技革命的成果應用于具體的生產過程,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同時,生產力的發展改變了生產關系,推動了社會的轉型與進化。另一方面,科學技術為人類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和益處,使科學主義深入人心,人們把科技視為神明,認為科技無所不能,可以解決人類存在的所有問題,這種極端性造成了科技的異化。
(三)原因
通過上文對科技異化問題的理論背景和實踐背景的分析,我們就可以總結出科技異化的原因。科技異化產生的直接原因是工具理性主義——以工具崇拜和技術主義為生存目標的價值觀;具體原因——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資本主義國家利用科技以實現利潤最大化;深層次原因是資本主義的本質——最大限度地攫取剩余價值。
二、科技異化的表現及其危害
(一)科技異化造成生態危機
科學技術的發展縱使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和進步,但是同時人們不斷地消耗自然資源,同時,把大量的廢棄物排放到環境中去,破壞了我們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危機。這不得不說是科技異化帶來的問題。空調本來是為了使人們能夠享受到清涼,但是最終確由于排放的大量氣體導致人類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熱。日本福島突發的核泄漏、核輻射不僅給民眾造成極大的恐慌,也給人類賴以生存的環境造成極大的壓力。這些都是科技異化的結果。
(二)科技異化使人的精神和行為發生異化
現在的科學技術發展使人類生存于一個充滿了信息的時代。我們生活于一個充滿了電話、傳真、手機、電子郵件、電腦、網絡等現代化通信工具的環境。這些現代的通信工具極大地方便了人類的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人類過多的依賴于這些電子產品,漸漸地成為了信息的奴隸。人跟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和交流越來越少,人和人的關系越來越冷漠,也最終導致了社會上很多不可思議的現象,讓人覺得異常可悲。
除了人類日常生活中體現出來的異化,人類在利用科學技術進行機器大生產時也失去了人類的主體性。自動化的生產技術雖然減輕了工人的體力勞動,卻剝奪了工人的主體意識,也喪失了人類的主觀能動性,由工人操作支配機器變成了機器操作支配工人。隨著技術的發展,作為客體性的異己力量的技術逐漸吞沒著人的主體性,致使人的行為失去主動性和目的性。
(三)科學異化的不確定性
轉基因技術是21世紀的尖端技術之一,目前利用該技術培育的農作物很多,但是這項技術產生的長遠后果卻不是人類現在所能估量的。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工被機器所取代,甚至產生了智能機器。如果機器有了人類的智慧,人的存在就越來越微不足道了。一些人工智能機器人可能會模擬人類的特征進行犯罪行為。如無人駕駛汽車的失控,家居機器人和秘書機器人的惡意失靈,這些離我們的生活也越來越近了,人工智能是否會發動機器革命引發熱議。
三、科技異化的消解途徑——科技人化
科技人化的關鍵在人。正如愛因斯坦所說:“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手段,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于人自己而不是取決于工具。”同時,科技人化就是要以人為本。我們所說的人的發展,不是指少數人或少數國家中的一部分人的發展,而是指所有各國人民都應得到公平的發展;也不僅僅是指當代人的發展,還應包括后代人的可持續發展;不僅僅是指滿足人的物質生活需求,還包括滿足人們在社會生活、精神生活、政治生活、生態生活等方面的各種價值需求,使人的體力和智力上的各種潛能得到充分的展現。
科技人化需要進行主體建設。社會上大致有三種主體構成,科技主體、政府主體和公眾主體。這些主體構成有不同的利益需要,有時一致,有時沖突。科技要發展,就要處理好這三者的關系。具體地說,就科技主體而言,主要是提高其道德素質,增強社會責任感,這是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徑。除此之外,政府主體應從政策、經費、人力等方面對科技的研究和應用加強引導、監督和管理,公眾主體應該積極關注并對科技增強辨別是非的能力。
要解決當前的科技異化問題,使科技更好地為人類服務,除了要不斷提高和發展主體的素質和能力,最為根本的是必須對社會制度進行變革。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來說,我們要通過完善我們的制度結構建立一種新的人類文化價值觀。這種文化價值觀既要能體現科技自身的發展規律與特性,同時又能符合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價值準則,從而使科技真正為人類服務。同時,在實踐當中,我們要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意識,在追求高科技、追求自身滿足的同時也應注重科技與自然的和諧,不要以破壞自然為代價。要使科學技術的發展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生存構成威脅,建立無毒、無副作用的綠色可持續發展科技。
參考文獻:
[1] 李桂花.“科技異化”釋義[J].吉林師范大學學報,2007,(1):13-18.
[2] 李桂花.科技異化與科技人化[J].哲學研究,2004,(1):83-87.
[3] 邱海燕.解讀“勞動異化”及其揚棄[J].湖北大學學報,2007,34(6):34-37.
篇10
正如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在20世紀60年代預言的一般,如今我們已經開始步入“知識社會”,知識成為重要的經濟資源,知識工作者成為社會的主角,創新成為社會發展的第一驅動力。企業也認識到了知識的重要性,逐步開展知識管理的工作。隨著信息技術的蓬勃發展,現有信息和知識的搜索和瀏覽變得更加便利,但是如何創造新的知識、如何實現技術創新,仍然是困擾企業管理者的難題。
知識管理領域的拓荒者野中郁次郎所提出的組織知識創造理論,系統地闡明了組織是如何創造知識,以及組織是怎樣對知識創造的過程進行管理的。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中國企業面臨創新的難題,這套知識創造理論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管理者提供借鑒,幫助企業更好地進行創新。
被忽視的“隱性知識”
作為一位受過西方教育的東方學者,野中郁次郎將西方哲學影響下的管理思想與日本知識傳統進行對照和結合,分析日本企業對知識認識的獨到之處。
野中郁次郎首先在哲學層面上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對于知識的認識,西方哲學中關于“知識是什么”,以及“知識是如何產生出來的”的探究被稱為“認識論”。而日本缺少這方面的論述,沒有專門關于知識的哲學理論,日本人的知識傳統特征主要有:主客一體,即“人類與自然的一體化”;身心如一,“知識意味著根據全人格的觀念獲得的智慧”,而不是像西方身體與精神分離的觀點;自他統一,“重視自身與他人之間的互動關系”,“自己與他人產生共感中達成一體化”。日本的知識傳統與西方笛卡爾式主體與客體、精神與身體的二元論截然不同,野中郁次郎認為要遵循日本的知識傳統,身行合一,身體和精神彼此相互補充。
同時,他認為西方學者在努力克服“笛卡爾兩分法”在理論上的局限性,但是還“沒有哪位思想家曾經明確地闡述過,人類為了改變世界可以積極地創造知識方面的動態理論”。笛卡爾學派認為組織是“處理信息”的機器,并不能對創新過程進行真正的解釋。野中郁次郎發現,與西方的經濟與管理理論不同,日本企業在管理過程中對知識有獨特的理解。他使用邁克爾?波蘭尼(M.Michael Polanyi)的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概念對日本企業的理念進行解釋:日本企業認為創造新的知識,并不僅僅是在處理顯性知識,而是發掘每個員工的高度個人化、難以進行形式化和交流的隱性知識,為整個企業所用。
野中郁次郎認為,隱性知識可以分為兩個層面。“技術”層面包括“非正式和難以明確的技能或手藝”,稱之為“秘訣”(know-how),這些知識可能源自親身體驗、高度主觀和個人的洞察力、直覺、預感及靈感。專業工匠的技能就屬于這個范疇,雖然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但是很難將自己知道的技能表達出來。“認知”層面包括信念、領悟、理想、價值觀、情感及心智模式。這些認知因素同樣很難表述,但是會在人的行動中有所體現。
對隱性知識價值的發掘,是野中郁次郎提出知識創造理論的基礎。
創造知識的“場”
雖然西方的知識理論和日本企業的知識傳統大相徑庭,但是野中郁次郎秉持辯證的觀點,認為東西方的理論是互補的。他提出知識創造理論,力求實現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這一對立事物的轉換和統一,在組織內以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創造知識。在他的觀念里,“知識創造的本質,深深地扎根在建立對知識的綜合,以及對綜合知識的管理過程之中”。組織可以通過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之間的轉換來創造和利用知識。據此,野中郁次郎提出SECI模型,包括四類知識創造過程:從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社會化(Socialization),從隱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外顯化(Externalization),從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組合化(Combination),從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內隱化(Internalization)。
SECI模型可以在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相互轉換上提供理論上的指導,不過創造知識還需要“場”的推動。野中郁次郎將“場”定義為分享、創造及運用知識的動態的共有情境。“場”為“進行個別知識轉換過程及知識螺旋運動提供能量、質量及場所”。這里的“場”既包括會議室、辦公室、工作車間這樣的實體空間,也包括工作小組、項目團隊、非正式團體、臨時會議、虛擬空間、客戶交流活動這樣在特定時空發生的相互作用。知識不僅存在于人的認知層面,也依存于特定的情境,“場”就是參與者共享情境,通過互動創造新知識的存在場所。
企業中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場”,領導者可以對企業內的“場”進行有機配置,推動知識螺旋的進行。通過提供諸如實際空間(比如會議室)、網絡空間(比如算機網絡)或精神空間(比如共同目標)的“場”,可以使企業內的員工分享、創造、運用知識的過程更加方便順暢,促進知識創造。
野中郁次郎認為,知識創造可以分為五個子過程:共享隱性知識;創造概念;驗證概念;建造原型;知識轉移。因此,想要營造知識創造的“場”,首先需要鼓勵員工進行隱性知識的共享,實現知識創造的第一步。不同的企業,知識共享方式有很大不同,具體為以下五種。
隱性知識傳承型企業
這類企業依靠的是知識口頭或手把手的傳授,是一種“師傅帶徒弟”的模式。人類出現以來,主要靠這種方式繼承和傳播知識。存在問題是:知識傳遞的效率不高,范圍有限,“場”不夠大,遠不能滿足當今復雜產品創新的需求。
基于命令的知識貢獻型企業
這類企業的知識共享依靠的是強制命令,例如,規定企業員工必須每年多少條知識,提多少條建議。或者規定員工在工作完成后,必須總結自己的經驗,將知識保留下來。這對于企業知識的積累有一定的作用。特別是當員工意識到這些知識的共享,對于企業發展有重要價值的時候,他們會認真對待這些工作。典型的案例是美國軍隊的“事后總結”制度,軍人認識到自己所總結的經驗對于戰友的生命安全至關重要,所以他們會去認真執行這一制度。存在的問題是:員工往往更多考慮自己的利益,不愿上傳有價值的知識。因為這是他們的吃飯本領,擔心“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上傳的知識多數是些無價值的垃圾知識。所以在基于命令的知識貢獻型企業中,如果員工只是被動地去共享知識,難以形成有效的創造知識的“場”。
基于知識共享數目的激勵型企業
這類企業對員工的知識共享數目進行統計,然后將知識數目折算成點數,給予相應的經濟和精神激勵。員工對此的反應是:或者一些價值不大的知識,或者少或者不知識。因為員工會覺得,這么點激勵不能反映自己知識的價值。而過多沒有價值的知識來拿獎金,又不好意思。例如,中國某研究所曾經規定,發一條知識獎勵400元獎金,但大家知識共享的積極性還是不高。這類的激勵因為標準不科學準確,對形成創造知識的“場”作用不大。
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業
利用信息技術,對知識生命周期,即知識螺旋進化過程進行跟蹤統計和分析,最終可以獲取知識對企業發展的貢獻情況,然后據此給予員工公平的激勵。這樣可以解決員工對于貢獻有價值的知識得不到合理回報的擔憂,使員工愿意貢獻自己的知識。這也是一種內部知識市場型的企業。其難點是,知識生命周期和知識的效益不易評價,激勵很難做到充分準確。但互聯網和大數據為建立基于知識生命周期的透明公平型企業提供了機遇,有助于使企業中的知識生命周期變得越來越透明,激勵越來越公平。這對形成創造知識的“場”有積極的作用。IBM的創新夢工廠、西門子的ShareNet都是這類創造知識的“場”。
幸福型企業
員工在企業中感到很幸福,以企業為家,將知識無私貢獻給企業。幸福型企業依靠文化和價值觀激勵員工貢獻知識,這是最理想的企業。日本的稻盛和夫曾致力于此類企業的建設,并已經在影響一些中國的民營企業,如寧波中興精密和方太集團。深圳華為也在打造這類企業。這類企業的主要問題是,在目前的市場環境和企業制度環境中要實現幸福型企業,難度很大。因為這種企業文化的建立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特別重要的是首先要求企業領導做到無私忘我,要求領導有很好的人格魅力。
合伙人制、稻盛和夫的“阿米巴經營”理念及管理方式等,再加上互聯網和大數據帶來的企業透明化,可以促進幸福型企業的成長,讓員工與企業成為“精神共同體、命運共同體、目標共同體、利益共同體”,釋放員工潛能。這是比較理想的創造知識的“場”,因為它能使員工真正以企業為家,全心全意為企業發展出謀劃策,貢獻自己的知識,無私地開展協同創新。日本的精益生產模式也代表了這種“場”。
成為知識創造型企業
知識以及創造、利用知識的能力,被認為是企業可持續競爭力的最重要來源,很多企業都開始重視這項工作,但是這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知識創造的過程中,存在一些壁壘:在個人層面,員工在接受新情況、新信息及新情境時,在新方式短期內不能產生效果的時候,可能會對新方式持消極態度,而采用舊的、穩妥的做法;使新的方式短期內不能產生效果;在組織層面,企業范式(company paradigm),即企業的戰略意圖、愿景或使命宣言及核心價值觀,根植于每個組織,并且影響員工的思考和工作方式,當出現的新知識與企業范式有沖突時,在推廣上會遇到阻礙。在這些壁壘的阻擋之下,知識創造過程在企業可能難以維持。因此,野中郁次郎認為需要在知識創造過程中進行知識促進,并且歸納總結了以下五個知識促進要素。
灌輸知識愿景
灌輸知識愿景,是指組織制定企業戰略時,將企業的愿景概念化,指導員工應該開發哪些知識,同時在管理過程中對知識創造過程進行促進。例如,本田汽車在開發新概念轎車時,提出口號“讓我們一起去冒險”。管理者認為,需要一款與傳統的思域(Civic)和雅閣(Accord)車型設計理念不同的汽車。于是,一群由年輕工程師和設計人員組成的新產品開發團隊根據管理團隊的思路指導,設計了既“短”(長度上)又“高”的城市型轎車――本田城市(Honda City)。這種“球形”的汽車形狀可以為乘客提供最大的內部空間,同時占用路面空間最小,特別適合日本空間有限的國情。
管理交談
管理交談是指協助組織成員之間的交流,以及與組織外部的人員之間的交流,比如與供應商、利益相關者及顧客等之間的交流。管理交流的方式包括:使用共同語言,澄清和避免任何誤解及誤讀,鼓勵組織成員之間的積極溝通,即創造交流的“場”。野中郁次郎認為,相比購買昂貴的信息系統來管理和處理數據,交談才是分享和創造知識的最佳手段,應該受到重視。互聯網技術的發展,使得員工之間的交流變得更加方便。例如,西門子公司的ShareNet將數據庫、聊天室、搜索引擎結合在一起,在ShareNet中,員工可以存儲任何有可能對同事有用的信息,而且不必拘泥于形式,因此在ShareNet上有很多個人或部門的陳述、評論;ShareNet上的“緊急求助”論壇是很多人愿意光顧的地方,在這里員工可以緊急詢問在世界各個角落、對這個問題有了解的同事;ShareNet中的每一個知識貢獻都能被大家評論。從使用結果來看,ShareNet是很好的工作助手,在使用的最初4年為西門子帶來了1.22億美元的額外銷售額,而創造這套系統的成本只有780萬美元 。
調動知識行動者的積極性
知識行動者是企業內將知識信息傳播給每個人的“傳教士”,他們幫助建立適當的促進情境,使隱性知識得以分享出來。他們為知識創造的過程進行準備工作,比如建立各種微型知識社群、聯系不同部門的員工等。雖然他們一般不會參與到具體的知識創造過程中來,但是他們的工作減少了知識創造需要的時間和成本,改善了知識創造活動的條件。當今基于互聯網的各種知識社區、微信群、博客等,使得知識行動者的人群范圍已經大大擴展,企業需要對于知識行動者的行為給予肯定和鼓勵,提高他們的積極性,間接地推動知識創造過程。
創造正確的情境
創造正確的情境包括:培育扎實的關系及建立有效合作的組織結構,促進跨職能及跨業務單元活動。在當今的互聯網環境中,企業組織在發生著變化,分布化企I將是企業組織的未來模式。一方面大企業將權力下放,形成各種具有較大自的小團隊或“阿米巴”,甚至是海爾的平臺型企業中的創客,另一方面大量小企業紛紛涌現,如淘寶上的千萬網商。他們是企業的主人,目標明確,創新非常積極。同時,互聯網和大數據幫助專業化分工協同,并進行監管,防止投機取巧現象。
將本地的知識全球化
本地知識的全球化,指的是考慮在全球范圍內復雜的知識傳播問題。在跨國公司中,將局部知識全球化,利用各國員工的智慧,就有可能縮短創造知識所需的時間,降低創造知識的成本。野中郁次郎知識創造理論的提出過程,就是知識全球化的一種體現。他分析日本企業的成功秘訣,把總結出的管理理念與西方的管理思想對照結合,向全世界的研究者發表知識創造的學說,由此東西方的企業管理者可以互相借鑒經驗,更好地進行知識管理工作。
國內的一些企業先驅如華為,已經在進行著知識促進的工作,在公司層面上提出知識管理的目標和戰略,開辟線上線下的知識交流平臺,任命知識管理專員負責知識行動,同時也組建跨職能及跨業務單元的團隊來解決問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