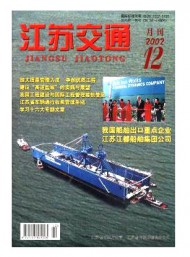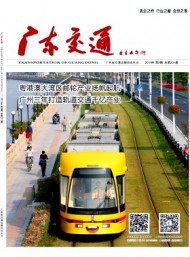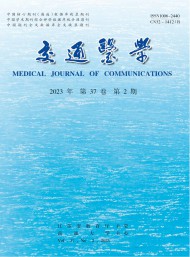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條例范文
時間:2023-11-06 17:22:0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條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酒后駕駛在我國刑法的量刑上,一般是通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樣兩款罪名來定罪和量刑的。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存在窘境,也即“交通肇事罪”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定罪量刑是建立在刑法理論中的結果犯的基礎上的,具有危害結果才會被定性為犯罪,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針對情節較為輕微的行為又顯得處罰過重。那么,由此便產生了交通肇事案件行為人逃逸后的保險理賠困境。如果采取行政處罰措施來規制,會遇到的問題是法律應有的震懾和規制效果不足,亦會由于行政執法本身自由裁量空間中的不同,事實上很難做到統一。可就交通肇事逃逸后的保險理賠實例來分析和認識。具體理賠實例:2012年4月25日,北京的小于駕駛小轎車與一輛三輪車相撞,造成三輪車駕駛者死亡,小于棄車逃逸,第二天才到交警部門說明情況,一次性對死者家屬賠償16萬7千多元,之后被以交通肇事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服刑期間,小于將保險公司告上法庭,因為他投保了交強險,而保險公司以他逃逸為由拒絕理賠。對于這樣的理由小于不服,于是便到法院。
二、分析:從不同保險所屬范疇進行區分
對于交通肇事案件行為人逃逸后的理賠問題,反映了不同的解釋立場,在當前法制轉型期和保險合同法律體系下,用類型思維解釋法律更具合理性,且應堅持法律解釋形式解釋的優先性,不輕易突破文意解釋的本來含義。對于上述問題筆者是這樣認為的:第一,《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與《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中保險公司免責條款不沖突。根據《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機動車肇事后逃逸的,保險公司不予賠付。這一法條的正確解讀是,機動車肇事逃逸之后,投保人不能申請賠償。但是被害人可以將交通肇事者、保險公司列為共同被告申請賠償。第二,交強險屬于財產險的一種,但不同與一般的財產險。根據民法及其他保險法規及司法解釋,交強險也即交納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是由保險公司來理賠的,使得事故中的受害者,有錢治病,有人賠償,體現的正是法的正義價值。保險合同的雙方當事人是保險人與保險事故中的第三人,即保險公司和保險事故中的受害人。第三,責任險與財產險是不同概念,第三者責任保險屬于責任險。與第三者責任保險不同的是,對于一般的財產保險而言,保險事故發生時,保險人對投保人履行了賠償義務,則保險人以賠償的金額為限,保險人對于第三人享有代位求償權。若發生在交通肇事案件中,投保人若是被害人,則保險人對投保人履行賠償義務后,保險人享有對肇事者的代位追償權。
三、焦點:法律解釋的不同立場
第一,三者責任險的本意為,對第三者負意外責任的保險。從法理學的角度來分析,責任險的實質為:被保險人或駕駛人在使用保險車輛過程中發生意外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傷亡或第三者責任險財產直接損毀,依法應當由被保險人承擔的經濟賠償責任,保險人依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和保險合同的規定負責賠償。但因事故產生的善后工作,保險人不負責處理。這里所強調的意外事故,排除了被保險人或其允許的駕駛人故意犯罪。上述案例中,小于的交通肇事逃逸行為非故意犯罪,但就交通事故本身(不含死亡結果),案例符合第三者責任險的承保范圍,故《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條例》第二十四條之設立有待商榷。第二,交通肇事逃逸且已獲刑,是否應當使得投保人喪失保險合同權利。里格斯訴帕爾馬遺產繼承案“任何人不得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獲得利”。案件是如此經典以至于一百多年來,許多西方人對此案津津樂道。“任何人不能因為自己的過錯而獲得利益”已成為世界立法通行的一條重要法律原則。其背后的假設為,如果允許人從自己的錯誤行為中獲取利益,那么維持這個社會的秩序便會蕩然無存,法律便失去了它賴以生存的基礎。逃逸加劇了被害人的傷害,卻帶了保險人的脫離法律關系,無疑加重了第三人獲得賠償的難度。
四、結論:論行為人逃逸后的保險理賠問題的法律出路
篇2
內容提要:工傷賠償請求權競合問題涉及私法上請求權和社會法上請求權的關系。工傷事故損害中的私法上契約責任和侵權責任的競合,應當允許當事人自由選擇;私法上請求權與社會法上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的競合,應當以替代主義為原則,兼采補充主義為例外;第三人責任與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競合時,則構成特殊情形下的不真正連帶責任。在整合私法和社會法的基礎上,我國應當實現工傷賠償模式的統一建構。
現代社會,工傷事故頻發,如達摩克里斯之劍高懸于勞動者頭頂,因而勞工權利保護日益矚目,誠如王澤鑒先生所言,“如何解決勞動災害救濟問題,乃成為現代法律之重要課題”。[1]就此問題,傳統民法和現代的勞動與社會保障法之間,不無緊張關系。調整勞動關系的法律歷經私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之演變,法律適用冗雜紛亂,且基于工傷所發生的請求權關系涉及勞動者、雇主、加害之第三人、工傷保險機構,其間關系錯綜復雜。雖早在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即有所規定:“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告知其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但侵權損害賠償和工傷賠償是否允許雙重求償,如何處理則語焉不詳。工傷賠償請求權競合問題,涉及工業事故嚴格責任、勞動契約保護義務、請求權競合、不真正連帶責任等諸多理論,本文擬就民法及社會保障法逐層梳理,以求澄清該問題。
一、違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請求權
遵循從簡單到復雜的認識規律,首先剝離出其它因素,僅就工傷關系之基本當事人———雇主與勞動者之間的關系,從純粹私法視角予以考察。該情形適用于沒有參與工傷保險的條件下,即無社會保障法介入時的勞務提供關系。發生工傷事故之后,受害的勞動者對雇主享有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但該請求權之基礎不無爭議,需要根據請求權基礎理論,對請求權體系次第檢討,以確定其規范依據。
(一)基于違約的請求權是否適用于工傷?
傳統合同理論一般認為,合同法是調整交易關系的法律,合同義務以當事人約定為準,合同標的以給付為主,其保護范圍以履行利益為限。因此,基于勞動合同提起工傷賠償請求權的障礙在于:(1)工傷之賠償范圍為勞動者人身利益之損害,其性質為絕對權,應屬侵權行為法保護的客體,故應適用侵權行為法保護而非合同法保護;(2)勞動合同當事人約定給付義務,而未約定人身保護義務,對絕對權負有不侵害的義務應由侵權法規定,而非合同約定;(3)利益衡量上,合同請求權對勞動者未必有利,因為雇主可通過約定預先免除其責任,也可通過與有過失、可預見規則等限制其賠償范圍。
但現代合同法發展趨勢,其義務來源日趨多元化,其保護利益的類型日益擴大,表現為附隨義務納入合同關系,其中保護義務至為顯著。附隨義務的機能之一在于維護他方當事人人身或財產上利益,例如雇主應盡注意其所提供工具的安全性,避免受雇人因此而受損害。其與給付義務的關系較遠,但債之關系作為一種法律上的特別結合關系,依誠實信用原則,一方當事人自當善盡必要注意,以保護相對人的權益,不受侵害。[2]此種利益,德國學者埃瑟爾(Esser)稱“保持利益”或“完全利益”,指對此加以保護、使之免遭不完全給付或其他的義務違反行為產生之侵害的利益。[3]2002年德國債法修改,新增第241條第2款規定,“債務關系可以根據其內容,使任何一方承擔照顧對方權利、法益和利益的義務”。[4]該條款以立法的形式規定了合同給付義務之外的保護義務,將履行利益之外的人身、財產等利益涵攝入合同義務的保護范圍。況且,勞動合同作為一種特殊的合同,對受雇勞動者的保護義務為題中應有之義。德國民法典第618條規定了雇主應當采取保護措施的義務,違反該義務將導致損害賠償責任。依史尚寬先生見解,“雇用人對于受雇人負有保護之義務,此義務與受雇人之忠實義務相對立,由勞動契約之身份的關系所生之特別義務,即雇用人對于受雇人之生命、健康、風紀、信教等應加以庇護”。[5]且該義務作為附隨義務,依其性質不得由當事人約定排除。
我國勞動法第92條規定了用人單位的勞動安全設施和勞動衛生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或未向勞動者提供必要的勞動防護用品和勞動保護設施的行為所應負的公法上的責任,對民事責任并未規定,但此種違反勞動安全保護義務的行為構成責任聚合,行政責任及刑事責任的適用并不意味著民事責任的排除。新勞動合同法第5條也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依法建立和完善勞動安全衛生、勞動紀律、職工培訓、休息休假以及勞動定額管理等方面的規章制度,保障勞動者享有勞動權利、履行勞動義務。”且根據勞動法第89條,“用人單位制定的勞動規章制度違反法律、法規規定的,由勞動行政部門給予警告,責令改正;對勞動者造成損害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該條款作為違反勞動合同的一般規定,自可以解釋為違反勞動合同保護義務的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基礎。因此,基于勞動合同的保護義務,工傷受害人當有權向用人單位請求損害賠償。
(二)基于侵權行為的請求權是否適用于工傷?
工傷作為對勞動者人身權益造成的損害,其性質為絕對權之侵害,適用侵權行為責任固無疑問。問題在于,究竟適用一般侵權抑或特殊侵權?我國司法實踐中已有判例采用過錯歸責的一般侵權責任處理。[6]王澤鑒先生亦認為,基于勞動災害的雇主侵權責任為過失責任,須證明雇主或其他加害人具有過失,始得賠償,“過失責任之基本原則,始終維持未變”。[7]有學者對此采批評態度,認為“受雇人在執行職務中遭受傷害,稱為工業事故,依現代民法屬于特殊侵權行為,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8]從而將民法通則第123條的高度危險責任作為請求權基礎。但由此產生的問題是,民法通則第123條所規定的高度危險作業僅包括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而不能涵蓋所有的工傷事故,例如無危險設備或其他危險物條件下的日常人力勞動所發生的工傷事故,顯然無法適用高度危險作業責任。因而有學者針對此缺陷,主張確定工傷事故損害賠償責任,應首先適用民法通則第106條第3款,“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屬于高度危險作業致人傷害的,同時適用第123條高度危險責任。[9]
考察現代法治之變遷,雇主責任有嚴格化的趨勢。現代社會,傳統過失主義一元化的歸責原則日漸動搖,特殊的侵權責任日趨擴張。德國學者埃瑟爾在《危險責任之基本問題及其發展》一文中力倡“過失、危險”歸責并立的“侵權行為法二元化”理論,獲學界一致響應,并于立法上產生一般條款規定危險責任的趨勢。[10]如意大利民法第2050條明文規定:“在進行危險活動時,對他人造成的任何損害,根據危險的性質或運用手段的特征,行為人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已采取所有避免損害發生的適當措施者不在此限。”我國臺灣地區債法修改亦新增第191條之3規定一般危險責任,立法理由為“近代企業發達,科技進步,人類工作或活動之方式及其使用之工具與方法日新月異,伴隨繁榮而產生危險性之機會大增。……為使被害人獲得周密之保護,凡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它工作或活動之人,對于因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適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他人之危險,對于他人之損害,應負損害賠償責任”。[11]因此,問題癥結在于民法通則第123條現行立法之缺陷,如采一般危險責任條款自可涵蓋工傷事故大部,而我國高度危險責任系采個別列舉的方法,若囿于文義,不免掛一漏萬,有失公允。根本解決之道應修改現行法,在民法典中規定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
(三)違約請求權與侵權行為請求權的競合
關于工傷損害賠償請求權競合問題,史尚寬先生認為:“(雇傭合同之保護義務)并無須雇用人有債務不履行或侵權行為之存在,如同時具備此等要件時,則發生請求權之并存。因一方請求權之行使受損害之填補時,他方面請求權應于其范圍消滅。惟與未能受滿足之部分,不妨基于他方面之請求權,更為請求。”[12]現代民法由于合同義務的拓展以及侵權法中危險責任的擴張,法律義務重疊交織,使得基于工傷的民事賠償請求權不可避免發生競合問題。請求權競合理論主要學說有三,即法條競合說、請求權競合說、請求權規范競合說。其中,請求權競合說為傳統民法主流學說,我國合同法第122條規定:“因當事人一方的違約行為,侵害對方人身、財產權益的,受損害方有權選擇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承擔侵權責任。”因此,因工傷受害的勞動者可以選擇對其有利的請求權提訟,以期最大限度保護勞動者權益,但對競合的實體請求權的分別讓與和重復訴訟則應采限制態度。有學者認為,工傷事故侵權的無過錯責任更有利于保護受害者,此時應優先適用侵權責任,排除合同責任,限制請求權自由競合。筆者認為,原則上雖然如此,但不排除合同特別約定的違約金責任和加重責任條款使合同責任更有利于受害者,當事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斷者和維護者,允許自由選擇請求權主張權利對當事人有利而無弊。
二、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與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
在民事領域發生工傷請求權競合,工傷受害人得擇一向用人單位主張。但近代以降,保護勞工理念高漲,社會保障法興起,以強制保險、雇主繳費、程序便捷、無條件給付、統一支付標準等為特征的工傷保險制度漸次代替私法解決勞動安全問題。19世紀末期,工業國家開始建立社會職業傷害保險法律制度,逐漸完成了由雇主責任制向職業傷害社會保險制度的轉變。[13]由此也出現了對工傷保險機構的保險賠償請求權與對雇主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關系問題。
兩種請求權在適用程序、請求權基礎、構成要件、賠償標準、舉證責任諸方面均有不同,[14]總體而言,工傷保險更為便捷、確定、安全。關于兩者之關系,比較各國法制之異同,有代替、兼得、選擇、補充幾種模式:
其一,代替主義。以德國為典型,貫徹“以保險保護取代侵權責任”理念,雇員參加工傷保險的全部費用由雇主承擔,對于受害者或其未亡人根據契約或侵權行為的一般原則而可能提出的任何事故索賠主張,法律都相應地免除了雇主及其雇員的責任。[15]除雇主繳費之外,該模式適用前提必須工傷賠償不低于損害賠償數額,否則勞動者權益得不到充分保障。一般來說,工傷保險金無條件支付,賠償標準確定,程序簡易,比民事賠償更為優越。
其二,兼得主義。弊端在于雙重給付,甚為不妥,對于雇主不公,企業負擔過重,對于雇工雖為有利,但易誘發道德風險。我國臺灣地區雖采“雙份補償”制度,其實際原因在于工傷給付及民事損害賠償給付標準均顯偏低,不足填補受害人損失。英國采兼得模式,由于保費并非雇主完全承擔,雇員須負擔近半數。[16]
其三,選擇主義。允許勞動者任意選擇一種請求權主張。其不妥之處在于勞動者為了及時獲得救濟,可能選擇較低的工傷賠償,對其并非有利;如選擇雇主主張損害賠償,給付數額預先極不確定,由于過失相抵、訴訟耗費,可能最終取得較少的補償。
其四,補充主義。受害人對于工傷保險及民事損害賠償均得主張,但須以實際損失為限,禁止不當的雙重獲益。但在實踐中,兩者賠償數額孰高孰低,無法確定計算,因為工傷賠償有的終身享有,取決于實際壽命。且雇主繳納保費而不能免除工傷事故風險,也有失公平。
就法理邏輯考察,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在傳統民法理論上應當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的關系。所謂不真正連帶債務,系指多數債務人就同一內容之給付,本于個別之發生原因,對于債權人各負全部履行之義務,因一債務人之履行,則全體債務人即同免其責任之債務也。[17]不真正連帶債務屬于廣義的請求權競合的一種,狹義的請求競合是在特定的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就單一法益發生數個請求權,而不真正連帶債務,則就單一法益而發生對于數個不同債務人的請求權。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究其性質,并非基于同一法律事實而產生,雇主與雇員之間的請求權關系單純基于工傷事故的違約或侵權事實而發生,工傷保險請求權并非基于單純工傷事故事實,而是基于事先投保而發生的工傷保險關系,因此這兩種請求權是“本于個別之發生原因”,但具有同一給付目的,所以構成廣義的請求權競合,即不真正連帶債務關系。史尚寬先生即認為:“人身保險于事故發生前,既已發生被保險人之債權,僅其期限為不確定,故保險金之取得,不得謂為基于事故發生之利益。……此時加害人之賠償義務與保險人之支付義務,為損害賠償義務之競合,依一方之實行而受損失之填補,他方即歸消滅。”[18]
但是問題在于,如果按照不真正連帶債務的邏輯,對于工傷保險與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受害的勞動者應當擇一請求,其目的滿足后,全體債務人共同免除責任。這意味著選擇主義的模式當最具法理依據,我國近年來也有呼聲主張工傷賠償可由當事人自由選擇法院訴訟或工傷申請。然而事實上,采選擇模式立法的國家極少,曾采此制的英聯邦國家“業已廢止”,理論界亦認為“選擇主義誠非良制”。[19]筆者也認為,以社會法救濟取代私法救濟是大勢所趨,代替主義相比較而言更為合理,其理由在于:
第一,兩者雖然在邏輯上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但此種不真正連帶債務為特殊的不真正連帶債務。與一般的民事權利競合不同,兩種權利并不同質,損害賠償請求權為私法上的請求權,工傷保險請求權為社會保障法上的請求權,不具有純粹私法的性質,不能像私權一樣允許當事人任意選擇、處分、拋棄。國家在雇主責任之外另行設置工傷社會保險制度,不同于私法側重消極自由之保障,其理念基于生存權、勞動權、社會權等思想,其目的在于保障人的尊嚴和價值,維護社會正義。因而工傷保險請求權就其價值位階而言具有優于私法權利的優先性。社會保障法的立法目的以及其社會救濟權在價值上的優先性排除了在邏輯上的當事人自由選擇的可能性。
第二,就利益衡量而言,工傷保險的及時性、確定性、安全性、終身性,較民事損害賠償對勞動者保護更為充分。賠償范圍,民事賠償以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計算,工傷以《工傷保險條例》計算,其給付數額大體相同,僅在傷殘補助金、死亡賠償金、護理費計算上可能有所出入,[20]但通過修改工傷待遇標準則不難解決。
第三,工傷保險為強制保險,雇主事先已負擔保費,工傷保險不但旨在保護勞動者,對用人單位也具有分散經營風險的機能。工傷保險賠償具有替代給付的性質,工傷保險機構不得向用人單位代位求償。如果繳納保費依然不能免責,用人單位可能承受雙重負擔,有失公平。
因此,兩種請求權雖然在邏輯上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的競合關系,但基于工傷保險請求權價值上的優先性和利益上的優越性,應當優先適用工傷保險制度,從而排除民事賠償請求權,受害人受領保險金后,給付目的完成,兩種請求權歸于消滅。值得注意的是,依照不真正連帶債務理論,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是因為共同的給付目的滿足而消滅,并不由于工傷保險存在而自始、當然地消滅,此時只是被工傷保險請求權所遮蔽、排除而位階次序居后。但當工傷保險請求權存在障礙時,例如因為勞動合同無效而導致工傷保險請求權有瑕疵、工傷保險請求權罹于時效等情形,無法有效獲得工傷保險賠償,受害人向雇主主張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權,也應當允許。
三、涉及第三人責任的請求權與工傷保險賠償
工傷事故因第三人侵害造成,此時發生第三人侵權損害賠償與工傷保險請求權競合,如何處理?典型情況如,雇員執行業務途中遇交通事故,因交通肇事的第三人的過錯而遭受損害。此時,受害人對加害的第三人請求損害賠償,還是對工傷保險機構行使工傷賠償請求權?我國實踐中曾有的處理模式是:民事損害賠償優先,再由工傷保險隨后補充,未獲民事賠償前可由工傷預先墊付。例如,根據勞動部《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第28條規定,由交通事故引起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處理。交通事故賠償已補償職工損失,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不再支付相應待遇;如果賠償不足保險的,則由其補足差額部分;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幫助職工向肇事者索賠,職工獲得賠償前可墊付其有關醫療、津貼等費用,等職工獲得交通事故賠償后應當予以償還。這種模式的不妥之處在于:先民事后社保,與工傷社會保險救濟的目的相背;墊付具有任意性,不利于勞動者及時、充分獲得補償;墊付后受害人可能喪失了向第三人的積極性,而工傷保險賠償機構缺乏相應的針對第三人的訴權;返還墊付費用容易誘發新的債務糾紛。
分析該種請求權競合的結構,第三人過錯導致的侵權行為責任與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也應構成不真正連帶債務。如前所述,基于工傷社會保險制度的優先性,受害人應當首先請求工傷保險救濟,這和雇主責任與工傷保險賠償的競合同理。但不同之處在于:雇主是保費承擔者,工傷賠償機構收繳保費即承擔最終的賠償責任;而為加害行為的第三人是工傷事故的發生原因,對工傷損害具有終局的賠償責任。因此,欲理順受害人與保險賠償機構的利益關系,應當先由保險機構對受害的勞動者予以保險賠償,再由保險機構向加害的第三人代位求償,即工傷保險賠償在涉及第三人責任時將發生代位求償關系。
不真正連帶債務雖然原則上無各自分擔部分,各債務因給付目的滿足而消滅,邏輯上一般不存在各債務人間的代位求償。但依學者見解,例外時也可發生內部代位求償之關系,如因債務人各自負擔全部義務之性質有差異,或其中一人可認為應最終負責者,亦得發生與求償同樣之結果。例如,保險公司代為賠償時,就債權人對于侵權行為人之權利有讓與請求權或代位權。[21]此類關系,曾世雄先生亦稱之為“非終局之賠償權義人”,認為一對一之復數賠償關系中,成放射狀結構,賠償權利人基于同一損害賠償事故取得復數之賠償請求權,行使一個賠償請求權,損害如已獲得賠償,依法律之規定,其它賠償請求權或當然移轉或依請求讓與賠償義務人。一般言之,應以損害事故之肇事行為人為最終賠償義務人,以此理念為中心而定其彼此間位階關系。[22]因此,在工傷保險機構先行賠償之后,應當允許其享有對第三人的代位求償權。保險代位求償權實質上是一種債權移轉,是被保險人對第三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轉移。當保險標的因保險事故而發生的損失,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權或違約行為所致,被保險人即有權向其提出賠償請求。[23]代位求償作為一種法定的債權移轉,理論上有債權主義與物權主義之別,[24]筆者認為,我國采代位求償權概念,理應采物權主義理論,此時無須當事人讓與行為,依法律規定自動發生損害賠償請求權向保險人移轉。
四、結語:工傷賠償模式的統一建構
現代社會為解決工傷問題,無不綜合多種救濟手段,實行跨法域調整。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工傷事故中受害的勞動者對雇主、第三人、工傷保險賠償機構產生多個請求權,引發責任競合問題。欲解決競合問題,消除法律混亂,切實保護勞動者權益,最終需要工傷救濟模式的統一建構與相關法律的體系化整合。但我國目前出臺法規零散,大多采條例、規章形式,各制度不相銜接,對勞動者保障甚為不利,亟待制定統一的工傷保險法。在立法中應當規定強制保險、代替主義、代位求償等制度,適當調整工傷待遇標準與民事損害賠償相一致。惟此才能將具體的案件事實涵攝于法律規范的構成要件之下,以使諸多規范之各種價值決定得藉此法律思想得以正當化、一體化,并因此避免其彼此間的矛盾,[25]籍此默默耕耘的廣大勞動者們也得以公平地分享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法治發展的現代文明成果。
注釋:
[1]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75.
[2]王澤鑒.債法原理(第一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41-42.
[3]韓世遠.違約損害賠償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5.
[4]德國債法現代化法[M].邵建東,孟翰,牛文怡,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25.
[5]史尚寬.勞動法原論[M].臺北:正大印書館,1978:45.
[6]張連起、張國莉訴張學珍損害賠償糾紛案[J].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89,(1).
[7]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77.
[8]梁慧星.民法學說判例與立法研究[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71.
[9]楊立新.論工傷事故與損害賠償[J].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1994,(5).
[10]邱聰智.民法研究(一)[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95.
[11]黃立.民法債編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327.
[12]史尚寬.債法各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305.
[13]楊燕綏.社會保險法[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82.
[14]林嘉.社會保障法的理念、實踐與創新[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243.
[15][德]羅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漢斯.萊塞.德國民商法導論[M].楚建,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357.
[16]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95.
[17]劉春堂.論不真正連帶債務[J].輔仁法學,1986,(5).
[18]史尚寬.債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315.
[19]王澤鑒.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第三冊)[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295.
[20]相比較而言,民事損害賠償的賠償范圍相對較寬泛、賠償標準較高。這是該問題產生爭議的根本原因。具體數額比較參見張新寶《工傷保險賠償請求權與普通人身損害賠償請求權的關系》,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2期。
[21]史尚寬.債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676.
[22]曾世雄.損害賠償法原理[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36-37.
[23]李玉泉.保險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84.
篇3
內容提要: 醫療過失的本質在于對醫療注意義務的違反。注意義務阻卻事由主要包括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鑒于醫療行為較之其他業務行為具有更高的風險性,因而更有必要在醫療過失犯的認定中適用注意義務阻卻事由。在對醫療危險進行合理分配的基礎上,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通過對行為人注意義務的否定,阻卻了行為人的過失責任。從價值理念來說,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從適用效果來看,就是醫療過失犯的限縮。
醫療過失犯罪是指從事醫療業務的人員在具備注意能力的前提下,因違反醫療注意義務而導致構成要件的結果發生的行為。由于過失犯的違法性根據在于違反注意義務和發生構成要件規定的結果這兩個要素,而結果的有效性又是以注意義務的存在為前提,所以注意義務是過失犯的核心。通常認為,只要存在預見義務和避免義務,就產生了注意義務。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具有一定危害風險的業務活動大量增加,“如果絕對地堅持行為人回避危害結果的義務,從事風險業務的人員負刑事責任的可能性就會隨著過失機會的增多而相應擴大。事實上,法律并非、也不可能禁止一切危險行為,不一定要求行為人認識到危害便要回避危害。”① 例如,醫學的發展已經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益處,但是伴隨這些益處的是相當大的風險。如果我們讓醫院和醫生對所發生的任何不幸事都承擔責任的話,這將會導致醫生更多考慮自身安全而不是患者的利益。因此,鑒于醫療業務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必要性,可以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違反回避危害的義務不是違反注意義務,不具有成立過失的條件。由此便涉及到下文擬探討的注意義務阻卻事由與醫療過失犯的限縮問題。
一、注意義務阻卻事由與醫療過失
(一)醫療過失的判斷
醫療過失是指醫療行為人在實施醫療行為時,沒有履行自己應盡的注意義務,從而造成危害結果發生的主觀心理態度。醫療過失的判斷實際上就是對醫方是否違背醫療注意義務的考量。而醫療注意義務是醫方技術性注意義務、倫理性注意義務和組織性注意義務組成的諸多注意義務集群。② 由于刑法條文并不規定各種業務的注意義務,在司法實踐中,主要依據業務人員遵守的相關法律、法規、規章制度的具體規定。具體來講,在判斷醫療過失能否成立時,主要看行為人是否違背了以下醫療注意義務:
1.依醫療衛生管理領域的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和規章制度所產生的注意義務
醫療行為需要相當的醫學專業知識,且具有高度的復雜性,為了保護病人的合法權益,國家法律、法令和規章制度對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作了比較詳細的規定。例如《執業醫師法》、《醫療事故處理條例》、《消毒管理辦法》等詳細規定了各類醫務人員應盡的職責以及對違反這些職責的處罰,這為認定醫務人員的注意義務提供了較為明確的依據。
2.依習慣及常規所產生的注意義務
社會生活領域中的各種注意規則,特別是各種業務行為的注意事項,一般都由有關的法律和規章制度加以明確規定。但是,將導致犯罪事實發生的過失態度在法律上完全類型化是不可能的,是否具有注意義務和注意義務的范圍,最終還是根據一般的道義習慣等社會規范來認定。③ 醫療領域存在大量的不成文習慣及常規,醫務人員在實施醫療行為時,也要受它們的約束,否則,即為違反注意義務。
3.依據醫學文獻產生的注意義務
醫學文獻是指符合醫學水準的醫學、藥學書籍、藥典等,其中有關各種治療方法的記載、醫療儀器的消毒要求、藥品使用的說明等,是醫務人員在實施醫療行為時必須遵守的。醫學文獻的記載作為一種科學的表現,既不同于衛生法律的規定,也不同于診療護理常規的規定,因而是醫務人員注意義務的一種獨立的根據。在有些情況下,醫學文獻的記載也會上升為衛生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文件的規定和診療護理常規的規定。例如,藥典中明確規定了使用青霉素類藥物之前要進行皮試,過敏者禁用。醫生在給病人開注射青霉素的處方時,并不向護士下達必須先做皮試的醫囑,但如果護士不做皮試就給病人注射,因而造成病人死亡等嚴重后果的,則該護士主觀上具有過失。
概括而言,在判定醫療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從而構成過失方面,法律所適用的是一個“合理醫務人員”的標準,即以診療當時臨床醫學實踐中通常醫療人員的正當技術水準為判斷標準。但是,對醫療人員是否盡到“合理注意”從而達到“合理醫務人員”標準的考察不是一個純粹的理論演繹過程,它需要具體到醫療人員所在的具體情境和具體醫療行為,要根據醫務人員的分工、職責、工作條件、緊急性等情況進行判斷。也就是說,實踐臨床上的醫療水準并非固定不變的,而是具有動態性。
(二)注意義務阻卻事由的界定
當前,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高風險的醫療行為日益增多。在考察醫療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時,不應以行為人對醫療風險的一般認識為過失的認識內容,而應當考慮行為人、受害人、社會各自負擔多少注意義務,也就是將醫療行為人的注意義務的一部分分配給社會或者他人。“分配給社會的那部分義務對行為人而言就構成被允許的危險,而分配給他人的那部分注意義務對行為人而言就成為信賴原則的基礎。”④ 這種通過分擔或者減輕行為人的注意義務,而使行為人的某些注意義務免除的法定規則就是注意義務的阻卻事由。⑤
通常認為,被允許的危險是在目的行為論的基礎上,為了彌補舊過失論的缺陷,在人的違法觀以及社會相當性理論的基礎上提出的。它強調既然某些危險勢在難免,那么就只應當要求危險業務者集中精力注意最可能發生危險結果的事項,縮小或限定其注意義務的范圍,不強求他對該危險業務可能導致的一切危險都有所注意,而將某些注意義務配置給社會或從危險業務中得益的人。因此,被允許的危險理論又被人們稱為“解放的理論”,擔負著縮小風險業務人員注意義務范圍、緩和或減輕風險業務人員過重刑事責任的任務。
而信賴原則從理論上講是被允許的危險在過失犯罪中的具體運用,當行為人實施某種行為時,如果可以信賴被害人或者第三人能夠采取相應的適當行為,由于被害人或者第三人不適當的行為而導致結果發生的,行為人對此不承擔過失責任。它強調,既然人們共同生活于一個社會空間,那么為了維持社會生活的和諧和有序,每個人都應當承擔一些注意義務,而不能把注意義務只加于某一些人,而且人們還應當彼此信任。⑥ “在某種條件下,行為人雖然具有預見危害結果的可能性,但不一定就有預見的義務。信賴原則免除了行為人預見他人可能實施不正常的非法行為的義務。”⑦ 也就是說,信賴原則與被允許的危險一樣,也具有縮小過失責任的功能。
二、被允許的危險與醫療過失
(一)醫療過失中被允許的危險之適用緣由
1.醫療業務活動是具有危險性的行為,這是在醫療過失認定中適用被允許的危險的首要原因。醫療行為是一種高風險的活動,如檢查、手術、藥物的應用等,都可能危害人體的健康或生命。另外因患者體質各異,病情千變萬化,各種疑難病癥不斷出現,而醫務人員對新開展的手術、新藥的應用,都有一個認識過程,這就使其在認識、分析和診治病情時可能發生判斷上的錯誤。若因醫療行為具有危險性便停止業務活動或者不采取危險性較高的治療方法,則不僅無法促成醫療技術的進步,而且對病人有害。因此,在醫療過失的認定中適用被允許的危險理論,可以將醫療行為人的注意義務轉移一部分由社會來承擔,從而使行為人不再負有預見以及避免這種危險發生的義務。
2.醫療業務活動是對社會有益且必要的行為。被允許的危險之所以被容許,是因為它們對社會生活起了正面效用,如果沒有它們,現實生活將難以維續。換言之,人們為了追求一個更大的利益必須得接受危險行為的附帶風險,這實際上是一種兩利相權取其重而兩害相權取其輕的道理。德國學者雅科布斯對此道理作了說明:刑法規范的存在,并不是為規范而規范,而是為了使社會生活成為可能而規范。其間,透過規范可以使人們有期待的可靠性。……為了維持各種社會接觸的可能性,我們必須接受某些對于期待的挫折。⑧ 醫療行為附帶的風險即為很好的例證。
3.在醫療過失認定中適用被允許的危險有助于醫療行為人進行創新活動。被允許的危險的實質在于主張理性冒險。“在現代多元的風險社會中,人類必須放膽行事,不能老是在事前依照既定的規范或固定的自然概念,來確知他的行為是否正確,亦即,人類必須冒險行事。”⑨ 實際上,被允許的危險理論既是人們在科技發展背景下作出的一種價值選擇(即使作出部分犧牲也要優先保護科學技術的進步、保護社會的整體利益),同時也體現了鼓勵人類對于未知領域進行探索的思想。
由于人類理性的有限性,致使人們對于醫療行為的發展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預知和掌控,但只要是屬于理性冒險的醫療行為,即使不幸造成了利益侵害,此行為也不違法。也就是說,對于被允許的醫療行為而言,不是由于行為不具有法益侵害的性質而阻卻違法,而是因為此醫療行為在一定社會范圍內具有容許的性質才對引起的具體危險不予追究。我們現在強調違法性的判斷重在行為無價值,而不是結果無價值,這實際上是對醫療行為的實施采取了一種較以前更為寬容的態度。⑩ 畢竟寬容是多元風險社會的首要原則,“寬容必定能夠使有責任感的人類勇于行事,而無須對行動失敗的法律后果有所疑懼。”(11)
(二)醫療過失中被允許的危險之適用要件
被允許的危險在刑法領域里主要體現為利益保護的相對性,即刑法對于生命利益、身體健康利益、財產利益等的保護不是絕對的,否則醫生給病人動手術的行為就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可以說,生活利益隨時隨地在接受或多或少的侵害。但關鍵問題是,應該接受侵害的程度有多大。(12) 通常我們認為,這個應該接受侵害的程度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侵害行為的必要性和相對利益的大小而浮動。具體來講,醫療行為必須滿足相應條件才認為是被允許的危險,筆者將其歸納為以下四個要件:
1.主體條件:醫療行為必須是由醫師、護士或者其他醫療關系者所實施。
2.客觀條件:實施的醫療行為必須適當。對被允許的危險理論作出重大貢獻的Exner認為,行為是否可以認為是被允許的危險,應以該行為是否適當或無錯誤為準。(13) 容許危險的行為要求行為人必須已遵守各項危險業務所定的規則及實施危險行為時所應有的注意,另外還得斟酌當時的實際情形,看行為是否符合一般社會生活觀念的相當性。實施醫療行為須遵守當時醫學所承認的學理及技術。若行為人不具備其所從事的醫療行為所要求的醫學知識和技能,則不能適用被允許的危險。
3.主觀條件:醫療行為的實施者須盡醫學上必要的注意義務,“在風險的程度和注意義務,特別是注意標準之間存在一種清晰的關系。任何擬行的治療措施所涉及的風險越大,醫療執業人員在決定訴諸此種擬行治療方案之前就應越加謹慎和勤勉地去權衡和考慮其它可能的替代方案。”(14) 因此,如果一位麻醉師處置的是一種高度易燃的物質,而他知道手術室中靜電火花產生的危險,則他必須相應地負很高的注意義務,采取特殊的預防措施以避免對患者造成傷害。
4.目的/益處條件:具體的判斷標準主要包括四個方面:(1)被害法益的重要性;(2)急迫危險的重大性;(3)侵害法益的蓋然性;(4)行為目的的正當性。(15) 醫療行為的實施要以治療或預防人的傷病為目的。醫療行為對患者所帶來的益處越大,法律對風險漠視行為的容忍度就越高,哪怕是較大的風險。例如,在Battersby v. Tottman一案(16) 中,醫生給一位精神疾病患者開了非常高劑量的藥物,此種藥物會導致嚴重的和永久性的眼部損害。但醫生認為如果不這樣治療,該患者會有自殺的危險,顯然藥物對患者的益處超過了它所帶來的風險。最終法院認同了醫生的看法,認定醫生明顯超過正常建議劑量開藥的行為并不存在過失。
上述條件體現了被允許的危險理論的核心不僅在于“容許”,更在于“容許多少”,在于法規范必須為“容許”確定限度,(17) 即寬容中更需謹慎。概括而言,某種風險業務對社會越有益、越重要,目的越正當,被免除注意義務的可能性就越大。(18) 由其所產生的危險,才能成為被允許的危險,也才能阻卻行為人的過失責任。
(三)醫療過失中被允許的危險之適用結果
現在,被允許的危險理論已廣泛應用于醫療行為中,成為醫務人員免責的重要事由之一。一些醫療行為雖然造成了不良后果,但依據被允許的危險理論,行為人的結果避免義務被免除,因而不承擔過失責任,這在探索性、試驗性等高風險的醫療行為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例如,為了挽救人的生命,允許采用危險的醫療方法救治病人。(19) 如果醫務人員在醫療行為中嚴格遵循醫療規章制度和診療護理常規,由于無法抗拒的原因而致患者傷亡,未能履行結果避免義務,醫務人員不承擔過失責任,按意外事件處理。還有器官移植手術,因其本身具有相當的危險性,只要是為挽救病人生命所必需,且不違反操作規程,縱然手術失敗,醫生也不存在過失的問題。
但是,適用被允許的危險的醫療行為,必須在合理的范圍內行使,如果超出了一定范圍,那么該醫療行為很可能受到刑法的否定評價。例如行為人若以殺人或傷害的故意實施了危險的醫療行為,導致患者死傷的,毫無疑問構成故意殺人罪或故意傷害罪。然而,理論上對醫療過失行為能否用刑法進行規制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假若以刑法作為醫療過失行為的制裁手段,則免不了遭受醫療人員的抗議,將會造成防御性醫療,最終會阻礙醫學的進步與發展,并且嚴重損害病人的應有權益。(20) 筆者認為,肯定刑法對于醫療工作的調整,并不意味著只要發生醫療事故就一味地追究醫務人員的刑事責任。刑法調整的目的在于合理地劃分正當醫療行為與醫療過失的界限,同時通過對過失行為的懲治促進醫療事業的良性健康發展。我們要做的是,一方面通過制度建設來鼓勵醫療創新,另一方面通過改善醫療條件、提高醫療水平等方式以減少或避免醫療事故的發生。另外,對于某些高風險醫療事業,我們可以通過設定特殊的法律制度如意外事故保險等來保障創新醫務人員的合理權益。因此,刑法的干預不是為了鼓勵防御性醫療行為,而是鼓勵醫務人員在自身業務活動中正確地履行自己的注意義務,謹慎地從事醫療工作。
具體來講,醫務人員實施具有危險性的醫療行為,是否具有過失,應從以下方面進行判斷:第一,從現有醫療水平來看,該醫療行為是否確實具有危險;第二,實施該醫療行為是否確實必要,并具有目的的正當性;第三,是否具有科學根據,存在著成功的可能性;第四,行為人在醫療行為中有無違反規章制度。只要醫務人員有違反規章制度的行為,且這一行為本身就足以造成危害結果的,縱然所實施的醫療行為具有危險性且目的正當,也不能免除行為人的過失責任。
三、信賴原則與醫療過失
(一)醫療過失中信賴原則之適用范圍
肇始于交通運輸業的信賴原則能否適用于醫療過失,在理論上存在否定說與肯定說之爭。否定說認為,信賴原則是針對交通事故的特點并經過長期理論與判例的發展逐漸形成的,醫療事故在性質上與交通事故未必相同,考量的重點也不一致,并沒有適用信賴原則的余地,可以考慮醫療行為的特點,經過理論與實踐的充實以形成其它的一些原則。(21) 持肯定說的學者認為,醫療行為與交通行為同屬于為改善民眾生活、提高生活質量所必需的行為,既然在交通事故中可以發展并適用信賴原則,就沒有理由在醫療行為中排除信賴原則的適用。(22) “從容許信賴的基本原理來看,所適用的范圍應該不僅及于交通事件的范疇。基本上,社會生活的參與者有權信賴其他的參與者會遵守社會生活的規范。”(23) “如果僅因信賴原則產生于交通運輸領域而排斥其他領域的適用,未免顯得教條。信賴原則完全可以適用于其他領域。”(24) 德國有學者認為,原則上,人們承認信賴原則可以擴展到由參與工作人共同作用的案件之中,尤其是在醫生行為的領域內(例如在一個手術隊伍之中)。聯邦最高法院也已經承認,在一種手術活動中,“參加這個手術的專業醫生,在原則上能夠信賴來自其他專業方向的同事的共同工作是沒有錯誤的”。(25)
另外,有學者認為,醫療過失中能否適用信賴原則不能一概而論,筆者將其稱為限定說。如日本刑法理論界大多贊同在醫療事故中適用信賴原則,(26) 但他們同時認為,醫療過失常因個案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條件或后果,如果一概適用信賴原則,未必符合社會的需要。“醫師具有專業知識、掌控醫療之必要人員、器具、設備;而患者方面大多缺乏醫學知識,且處于身心衰弱狀態,期待其遵守注意義務以回避危險之可能性低,故醫師對患者不宜適用信賴原則。”(27) 臺灣有學者認為,信賴原則除了團隊醫療此特殊情形外并不能適用。(28)
筆者原則上贊成肯定說,但在適用上要符合相應的條件(適用條件將在下一個問題討論)。醫療行為與交通運輸行為同屬具有高度危險性而又對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業務活動,二者都具有組織型的特點,都有適用信賴原則的余地。信賴關系的存在不僅是醫療工作的起點,也是醫療行為得以順利開展的關鍵性因素。在現代高度分工的醫療體制下,醫師分工越來越細,每一個醫師僅在自己所從事的醫療工作領域內具有相應的醫療能力,對于自己專業領域之外的事項不得不求助于其他醫療人員的判斷與治療。特別是在組織性醫療行為中,醫務人員只有密切配合才能保證該醫療工作的順利完成。每一個醫療行為人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對其他醫療行為人的具體醫療行為進行詳細的復查,所以醫療行為人之間的信賴是必需的。如主治醫師對其他參與輔醫療工作的醫務人員的信賴;醫師、護士對麻醉師、藥劑師的信賴;醫師對檢驗人員的信賴等。
同時,筆者認為“醫師對患者不宜適用信賴原則”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因為不管我們是否愿意承認,醫療人員之間以及醫療人員與患者之間存在信賴關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醫療行為的成功實施除有賴于醫療行為的參與者共同協力外,還有賴于就診人的配合診療。對于這種信賴關系,蔡墩銘教授稱其為實質的信賴關系。(29) 在現代社會中,只有強調作為社會活動參與者的相關人員之間的責任心以及社會連帶責任感,“只有在只對自己的缺欠行動承擔責任而不對可以預料的他人的缺欠行動承擔責任這種信賴受到保護”(30) 時,才能做到實質的公平,保證社會生活平穩有序地發展。醫療行為作為一項危險事業,必須基于危險分配的原理,在醫生與患者間進行合理的危險分配,這樣才能促進醫療行為的健康發展。當然,由于醫師具有專門知識,并經過專門訓練,其相對患者而言擁有較多的醫學知識,因此,在危險義務的分配上應適當考慮患者的弱勢地位,在義務的承擔上應給予患者適當的減輕,但是這并不能成為否定醫師和患者間適用信賴原則的理由。
(二)醫療過失中信賴原則之適用條件
信賴原則作為認定行為人是否具有過失的一個基準,對于合理地緩和過失犯的成立范圍,限制刑罰權的發動具有積極意義。但其適用必須具有一定的界限,概括來講,醫療過失中適用信賴原則必須符合主客觀條件。
1.客觀條件
在醫療事業領域,適用信賴原則的客觀要件具體表現為以下三點:第一,醫務人員具有相關醫療知識,患者也知曉配合醫生工作的重要性。只有醫務人員接受了正規的醫學教育和訓練,并取得主管機構頒發的資格證書,同時患者知道自己有義務協助醫療行為時,才可能期待其參與醫療行為時采取合適的行為,也才有適用信賴原則的可能。因此,在無資格和無能力人員參與醫療行為時,由于他們作出合適醫療行為的可能性低,故不能適用信賴原則。第二,醫療設備必須完備。(31) 醫療設備不完備,如醫療器材、消毒設備、安全設備等欠佳,就沒有信賴原則的適用或信賴原則的適用程度就低。第三,行為人遵守了醫療行為的一般規則,或即使違反了醫學規則,但其違反醫學規則的行為并不是該醫療事故發生的原因。(32) 該行為人就不因此而承擔過失責任。
2.主觀條件
主觀條件是行為人對于他人實施合法行為能產生信賴、并具有信賴的相當性。主觀條件的適用以客觀條件的滿足為要件。第一,信賴的存在。指行為人有信賴其他醫療參與者能實施適當行為的事實。如醫生信賴患者能如實提供自己的既往病史,也能信賴制藥公司在說明書上所說的藥物功能,而不必親自進行有無副作用的調查。第二,信賴的相當性。這是適用信賴原則的主要依據。為了確認信賴是否具有相當性,需要以一定社會的倫理秩序為根本判斷標準,只有在一定社會中具有社會相當性的行為,才能肯定信賴相當性的確立。在具體案件中,主要看行為人是否履行了相應的業務規則,如醫療規則等。對于那些不具備相應醫學資格的醫療參與人或不能充分理解相應義務的年老年幼患者,原則上就沒有信賴的相當性。
3.限制條件
關于醫療行為中信賴原則適用的例外情形,主要有:第一,容易預見參與醫療行為的醫療人員采取不適當行動的;第二,其他參與醫療行為的醫療人員不具備合法資格的;第三,該醫療行為產生醫療過失頻率較高的;第四,行為人本身違反醫學規則,或違反診療當時所謂臨床醫學實踐的醫療水準;第五,其他情形,例如設有急診處的醫院或施行急治的醫師因負有特別注意義務,不得主張信賴救護車與警察或消防人員的急救措施而免責。(33)
筆者認為,信賴原則的限制條件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醫療行為人自身違反注意義務,應當采取特別措施避免結果發生的,不能適用信賴原則。如醫師未履行診察、檢查、告知等義務的。二是對方由于特定原因容易采取異常行動的,或醫療行為人有充足的時間采取措施回避結果發生的,也不能適用信賴原則。
(三)醫療過失中信賴原則之適用效果
1.醫療人員與患者間適用信賴原則的法律效果
(1)醫師已盡其適當的問診、檢查義務,但由于患者沒有如實提供信息而導致診斷錯誤造成傷亡結果的,醫師不承擔過失責任。問診是醫療行為的邏輯前提,也是后續醫療行為的基礎,患者對于醫師所提問題有義務給予充分回答,例如是否具有特異體質或過敏性體質、在接受治療前是否自行服藥等。但要注意的是,問診過程中適用信賴原則的前提是醫師別無他法知悉患者的有關信息,如果醫師能通過檢查或其他手段得知患者有關信息時,即使患者違反了診斷協助義務,若醫師怠于知悉該信息時,則其不能主張對患者的信賴原則而免除自己的責任。
(2)醫師已盡其指導義務,因患者不遵守醫囑導致傷亡的,醫師可以主張信賴原則免除自己的過失責任。如日本富山地方法院昭和36年12月13日就一起患者因大腿骨折,在接受骨移植手術的愈合期內多次外出、飲酒等引起右下肢短縮后遺癥,作出如下判決:在醫療行為中,醫師的治療方法及過程,技術上并不存在問題,醫師已盡一般醫師所應有的注意義務,該牽引不足并非由于醫師處理不當所致,而是由于患者在接受骨移植手術后的愈合期間(約需3個月)內,不遵守醫囑,經常外出、飲酒的行為妨礙了牽引效果,致右下肢短縮,對此,醫師不需承擔過失責任。(34)
2.組織性醫療人員適用信賴原則的法律效果
在組織性醫療行為中,各主體的地位與作用不同,因此,信賴原則對他們的適用條件也存在差異。下面僅以主刀醫師為例說明在組織性醫療行為中信賴原則適用的效果。
(1)免除監督義務,在組織性醫療過程中,主持醫療的行為人對于其他參與輔助醫療工作的護士、檢驗人員等行為人的監督義務可因合理的信賴而被免除;
(2)免除指示義務,在合理的信賴的場合,行為人對參與輔助醫療工作的行為人的工作可以不必詳細加以指示說明,由他們自行處理;
(3)免除檢查義務,對于參與輔助工作的行為人的醫療工作的結果,行為人沒有必要檢查其是否正確。(35)
但是,假若在濫用信賴原則的情況下,主刀醫師對于參與輔助工作的醫務人員的過失應承擔監督過失的責任。(36) 也就是說,在參與人(例如指導手術的醫生)具有特別的監管義務(例如面對還沒有經驗的助理醫生)或者其他監督任務時,信賴原則必須退居次要地位。(37)
結語
隨著醫療科技的發展,醫療危險隨之增多,較之其他業務行為具有更高的風險性,但人類對醫療行為的依賴也越來越廣泛。因此,注意義務阻卻事由在醫療過失的認定中顯得尤為重要。在對醫療危險進行合理分配的基礎上,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減輕或否定了特定行為人對于該風險實現的義務承擔,從而阻卻了行為人的過失責任。從價值理念來說,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從適用效果來看,就是醫療過失犯的限縮。同時應當看到,在我國目前的刑法理論中,注意義務阻卻事由的地位還沒有得到形式上的肯定,但事實上,它們在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正發揮著作用。(38) 由于我國不存在德、日等國的多層次犯罪論體系,也沒有獨立的違法性和有責性判斷階層,我們可以將被允許的危險和信賴原則作為過失構成中的消極要件看待,與注意義務的肯定即過失構成的積極要件相對應。筆者相信,注意義務阻卻事由不僅會在學理上被廣泛地探討,更會在司法實務中越來越多地被引用,其在醫療過失犯的認定中將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注釋:
① 姜偉著:《罪過形式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97頁。
② 技術性義務要求醫方負有謹慎診斷、謹慎治療、嚴格遵循操作規程等診療護理義務和對患者及其家屬盡告知、說明義務,勸告患者轉診的義務和保密義務等;倫理性義務有不得拒診的義務、危機情形的救護義務、創新治療的義務等;組織性義務包括圍繞診療活動而完成的組織結構問協調一致、高效服務患者的義務。參見郭升選、李菊萍:“論醫療注意義務與醫療過失的認定”,載《法律科學》2008年第3期。
③ 參見[日]西原春夫主編:《日本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李海東等譯,法律出版社、日本成文堂1997年聯合版,第257頁。
④ 劉守芬、林嵐:“注意義務履行之探討”,載《甘肅政法學院學報》2008年第3期。
⑤ 參見張小虎著:《犯罪論的比較與建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345頁。
⑥ 參見周光權著:《注意義務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頁。
⑦ 姜偉著:《罪過形式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2頁。
⑧ 參見Jakobs, AT7/35,轉引自黃榮堅著:《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臺灣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第235頁。
⑨ [德]考夫曼著:《法律哲學》,劉幸義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6頁。
⑩ 舊過失論注重結果無價值,新過失論強調行為無價值,認為違法性的實質并不在于具體危害事實,而在于違反避免結果義務的行為,如果已采取避免結果發生的行為,即使發生了危害結果也不負過失責任。被允許的危險使行為無價值的觀念更加具體化。
(11) [德]考夫曼著:《法律哲學》,劉幸義等譯,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427頁。筆者認為,此處所說的“寬容”與被允許的危險在本質上是一致的。
(12) 參見黃榮堅著:《刑法問題與利益思考》,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241-242頁。
(13) 參見周治平:“可以容許的危險概說”,載臺灣《刑事法雜志》第9卷第2期。
(14) 趙西巨:“醫療訴訟中的醫療專家意見和法官自由裁量:誰主沉浮?”,載《法律與醫學雜志》2007年第3期。
(15) 參見蔡振修著:《醫事過失犯罪專論》(增訂一版),作者2005年版,第149頁。
(16) Battersby v. Tottman(1985)37 SASR 524.
(17) 參見方泉著:《犯罪論體系的演變》,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14頁。
(18) 參見姜偉著:《罪過形式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頁。
(19) 1997年7月17日,華西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接診了一位罕見的急性中毒患者,年近60歲的徐某因服用大劑量精神類藥物“氯氮平”中毒而導致深度昏迷。對該患者無法按照對一般中毒病人的常規搶救方法進行治療,醫院決定用血漿交換的方法除去患者身上的毒素,但這種利用進口血漿交換儀所進行的“換血療法”是一種危險性極大的治療方法,國內外醫學界極少采用,西南地區更無人嘗試。醫院經過經心組織實施了此種解毒療法,經過幾個小時搶救病人終于蘇醒。本例中,醫務人員對該醫療方法的高度危險性已經清楚地予以預見,但在法律上卻可以因該療法的高度危險性而免除醫務人員的結果避免義務。詳細報道見《成都商報》1997年8月14日第5版。
(20) 參見邱清華:“醫療過失能免除刑責嗎?”,載《醫學法學》第3卷第3期。
(21) 參見曾淑瑜著:《醫療過失與因果關系》(下冊),臺灣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65頁。
(22) 參見曾淑瑜:“信賴原則在醫療過失中之適用”,載臺灣《月旦法學》1997年第9期。
(23) 黃榮堅著:《刑罰的極限》,臺灣元照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60頁。
(24) 游偉、謝錫美:“信賴原則及其在過失犯罪中的運用”,載《法律科學》2001年第5期。
(25) [德]羅克辛著:《德國刑法學總論》(第1卷),王世洲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718頁。
(26) 參見臧冬斌著:《醫療犯罪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1頁。
(27) 許世賢:“信賴原則于醫療過失之適用”,臺北中興大學法律學研究所1997年碩士論文,第175頁。
(28) 參見鄭淑屏:“醫療過失之刑事責任”,載《現代刑事法與刑事責任》,刑事法雜志社1997年版,第412頁。
(29) 參見蔡墩銘:“醫療與信賴原則”,載臺灣《刑事法雜志》第39卷第3期。
(30) [德]格呂思特·雅科布斯著:《行為·責任·刑法——機能性描述》,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頁。
(31) 參見趙慧著:《刑法上的信賴原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頁。
(32) 日本神戶地方法院姬路分院昭和43年9月30日就一起有關護士為患者靜脈注射鞍基比林鎮疼解熱劑后,因患者本身為過敏性特異體質而引起休克死亡的案件中,作出了如下判決:在該案例中,雖然醫師違反了法規而任由護士為靜脈注射,沒有特別就注射要注意注射速度等向護士作出指示,但由于該護士為具有約14年經驗的老練護士,對于靜脈注射的知識、技巧應該比較熟悉,并且事實上醫師不可能對日常醫療活動中的所有靜脈注射都逐一加以注意,況且在該案件中,該護士的注射方法并沒有錯誤,不論由醫師親自注射或又護士為之,都無法避免患者因藥物過敏而死亡的結果,因此不能認定醫師具有過失。
(33) 參見曾淑瑜著:《醫療過失與因果關系》(下冊),臺灣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569頁。
(34) 參見趙慧著:《刑法上的信賴原則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175頁。
(35) 臧冬斌著:《醫療犯罪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頁。
(36) 參見蔡墩銘著:《醫事刑法要論》,景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30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