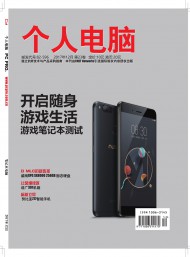個人執行力心得體會范文
時間:2023-04-10 04:01:01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個人執行力心得體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從本課程中學到了什么
持續兩天的“團隊執行力”學習中,我主要學到如何打造核心團隊,如何選出團隊執行者與及常見的團隊執行不利的原因分析。首先領導者需要修己安人修自我的品德,修自我的格局,修自我的本事,同時修自我的形象。再一個明確公司的愿景及戰略規劃,身先士卒做到歡樂奮斗。
二、感受最深的幾點是
1、企業咒語:是,保證完成任務!
2、執行步驟中:明確目標期限、明確檢查流程、獎罰分明與及承諾。
3、制度建設中:領導與制度、朝夕制度。
4、管理模式中:團隊溝通、團隊激勵。
三、這幾點對我的總體啟發和目前工作的幫忙
與其說是咒語不如說是激發活力的口號,是,保證完成任務!它充分體現團隊勇于理解工作任務,只對實現目標增加措施,不能降低目標草草了事的管理工作作風。總結下來,目前我們團隊的執行力一方面仍需要加強部門員工技術本事,另一方面增加員工間的溝通,同時更應當提高部門領導對下屬的關心,增加他們的歸宿感。
感激公司給我這次培訓學習的機會,經過參加XXX先生主講的《團隊執行力》的課程,讓我受益匪淺,感觸良多。異常是讓我明白了做一個負職責且敢于承擔職責的人和有執行力的人對一個公司的發展和員工個人職業化的成長的重要性。
如今,在企業發展孰優孰劣的問題上,人們談論得越來越多的是執行力。阿里巴巴的馬云與日本軟銀集團總裁孫正義曾探討過一個問題:一流的點子加上三流的執行水平,與三流的點子加上一流的執行水平,哪一個更重要結果兩人得出一致答案:三流的點子加一流的執行水平。再好的決策必需要得到嚴格執行和組織實施。一個好的執行人能夠彌補決策方案的不足,而一個再完美的決策方案,也會死在差勁的執行過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處于現今市場經濟中的現代企業,沒有執行力,就沒有競爭力。
而對于個人,一個沒有執行力的人,在現今社會是根本無法立足的。一個團隊的執行水平是由其中的每一分子的執行力所匯集而成的,公司要發展,要規范,需要的就是務實的人而不是務虛,需要的是真正發揮每個崗位的作用,每個員工都做到這點,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能使得公司業績蒸蒸日上,從而實現共贏。
中國傳統文化提倡“知行合一”,最終一個字就落實在“行”上。阿里巴巴馬云還有一句話:阿里巴巴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是“此刻、立刻、立刻”干出來的。如果我們每個員工嚴格按照制度的要求,按照流程要求去工作,不互相推諉、不拖拉懈怠、盡心盡職,團結協作,將每一個環節的工作都落實到實處,將每一件任務都不折不扣地完成,這樣的公司何愁不能壯大發展呢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每個人的職業素養同樣得到了相當的提升,作為公司的一分子,我們要樹立良好的工作態度和工作作風,愛崗敬業,掌握工作技能,提高工作效率,強化執行力,實實在在地為公司的發展付出最大的努力。
個人學習執行力的最新心得體會
執行力,顧名思義就是執行的效力,也就是把目標和想法變成結果的本事。對于企業而言,執行力是企業競爭力的核心,是把企業戰略、規劃轉化成為效益、成果的關鍵。眾所周知,執行力與企業各個層級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也有著很多相互制約的因素。究竟該如何提高執行力,在眾多因素中,下頭3點最為重要:
1、簡潔高效的制度是提高執行力的保障
制度的作用就是讓員工按照規定的要求和流程高效地處理各自的工作。任何一項任務、流程,都應當把“誰做、怎樣做,做到什么程度”等相關問題在制度上加以明確,分清職責,理順程序,能簡則簡,務求實效,這樣才能提高辦事效率,提高執行力。否則,冗繁的制度流程只會阻礙高效的執行力度。
2、營造企業文化是提高執行力的基礎
企業文化是一種氛圍、是一種環境、更是一種準則。導向正確的企業文化是提高執行力的基礎。企業是由職責不一樣的眾多部門組成,各個部門又是由分工不一樣的員工構成。只要有了導向正確的企業文化,每個員工的目標才可能都是一致的,也才可能做到講求速度、崇尚行動、團隊協作、有職責心、拒絕無作為、相互尊重、相互鼓勵、樂于分享、共同成長。
3、科學的激勵措施是提高執行力的源泉
企業在在提高執行力的同時,要異常注重對員工的激勵。激勵就是動力,有了好的激勵措施,員工才會自發的提高執行力。如果沒有激勵,則員工后勁不足、有始無終。建立公正、科學的激勵措施至少應當做到:獎要立刻獎,不拖欠、不克扣;罰要立刻罰,不心慈、不手軟,獎罰分明才是真正的執行力。一項激勵措施,一旦制定,就要一以貫之地執行下去,不要開始時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到之后避而不談、不了了之了,這本身就不貼合執行力的思想要求。
篇2
【關鍵詞】 個體韌性;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抑郁;軀體化;遇難者家屬;橫斷面研究
中圖分類號:B845.67,R749.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6729(2010)004-0309-05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0.04.017
Individual resilience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social support and mental health of
survivors with family members lost in Wenchuan earthquake
WU Sheng-Tao1,2,LI Juan1,ZHU Zhuo-Hong3
1Center on Aging Psychology,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2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3Crisis Intervention Center(Chengdu),Institute of Psycholog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LI Juan,E-mail:lijuan@psych.省略;ZHU Zhuo-Hong,E-mail:zhuzh@psych.省略
【Abstract】 Objective:To explore the individual resilience in survivors with family members lost in Wenchuan earthquake,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social support,life satisfaction,depression,and somatization.Methods:Totally 166 survivors with family members lost and 180 survivors without family member lost from earthquake sites were screened out through individual interview.They were assessed with the Individual Resilience Scale(IRS),Social Support Scale,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and 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At the same time,133 participants from normal area were assessed with the Individual Resilience Scale.Results:(1)The scores of IRS in survivors with family members lost were lower than that in survivors without family member lost and participants from normal area[(2.41±0.74)vs.(2.74±0.71),(2.76±0.72);P
【Key words】 individual resilience;social support;life satisfaction;depression;somatization;survivor with family members lost;cross-sectional study
韌性是人類面對逆境時的一種良好適應[1-3],是諸多環境因素及個人、環境交互作用的動態過程[4],因此廣義的韌性既包含內部的個體因素(如積極、樂觀等品質,即個體韌性),又包含外部的環境因素(如社會支持)[5]。由于過程的系統復雜性,片面強調某一方的韌性必然會造成簡單化的傾向[2],但以往的實證研究誤以為韌性是一種個人品質,甚至在逆境給人帶來心理壓力時指責個體未能按環境要求行事,應該為他們自己的心理問題負責[6];尤其韌性一詞被引入中國以來,由于被認為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不謀而合,而被看作是一種重要的個人技能或品質[7],是中國青少年面對逆境時最顯著的特點[8]和中國工人最重要的心理資本之一[9]。
然而,一些研究證實僅有個體的韌性對于整個逆境復原過程而言是非常有限的。如,關于9.11災難的研究表明個體身上的韌性品質并非普遍流行,在高暴露環境下,韌性會相對較少[10];對地震災區老人的研究發現,個體韌性只能幫助脆弱的老人在認知層面上對生活滿意度進行調節,但是還不足以強大到緩解他們的抑郁和軀體癥狀,因此在極端條件下個體韌性的逆境復原作用是有限的[11]。
災難是一種逆境,家人遇難更是極端創傷條件下的逆境。以往的研究者主要關注青少年的復原機制與心理健康 [12],很少有人針對遇難者家屬的創傷復原做專門的研究。本研究以廣義韌性為基礎,同時從個體韌性與社會支持兩個維度考察遇難者家屬的逆境復原機制,并以生活滿意度、抑郁、軀體化作為心理健康的指標,來驗證個體韌性的有限性[11]。
1 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5.12地震后8個月,研究者在重災區(綿竹、什邡、北川)的居民安置點開展了為期1周的春節前慰問活動。民眾在領取禮品后參加一個個體訪談,期間談及家人在地震中的傷亡情況,并自愿參加后續的研究。
災區遇難者家屬:共有272人報告其在地震中有親友遇難,研究者排除遇難者為受試者的親戚、朋友等家屬關系不明確的情況,最終獲取確有家人(即父母、愛人、兒女)遇難的有效受試166名,其中女性97名;年齡21~70歲,平均(42±10)歲。
災區家庭完好無損者:共有401人報告其在地震中無任何親友傷亡,但樣本量是遇難者家屬的近2.5倍。為減少隨機誤差,研究者對401個樣本進行隨機分半,最終獲取180名家庭完好無損的受試作為災區遇難者家屬的對照組,其中女性77名;年齡18~80歲,平均(40±12)歲。
非災區受試:研究者在非災區(北京、四川射洪)的社區開展了類似的節前調研,共有150名當地居民同意參加本研究。排除戶籍信息不清和中途退出的情況,最終獲取有效受試133名,其中女性70名;年齡18~64歲,平均(38±10)歲。
1.2 工具
1.2.1 個體韌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13]
共10個條目,每個條目采用0(從不)~4(總是)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個體韌性越強。
1.2.2 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SSS)[14]
共10個條目,采用1~4點或0~8點計分,得分越高表明社會支持越高。
1.2.3心理健康指標
生活滿意度量表(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SWLS)[15],共5個條目,已在包括中國在內的150 多個國家應用過 。原量表采用Likert式1~7點計分[16],為避免東方人在量表選項上的中間作答偏差,本研究在施測時將計分方式由奇數點改為偶數點(1=非常不贊同,6=非常贊同),其內部一致性α系數為0.86。
癥狀自評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 )[17],共90個項目,采用1~5點(1=從無,5=嚴重)計分。本研究選用抑郁(13個條目)和軀體化(12個條目)2個分量表,其內部一致性α系數分別為 0.94和0.91。
地震8個月后,經過培訓的志愿者采用入戶訪談的形式對災區受試進行問卷調查。同時,另一項調研也在非災區進行,但實測工具只包含上述調研的個體韌性量表和基本的人口學信息。
1.3 統計方法
數據采用SPSS11.5和Lisrel8.72進行統計分析,方法包括t檢驗、方差分析、相關分析和路徑分析。
2 結 果
2.1個體韌性、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組間差異
3組受試間的個體韌性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事后檢驗表明,遇難者家屬的個體韌性低于家庭完好無損者和非災區受試。獨立t檢驗表明,遇難者家屬的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得分低于家庭完好無損者,而其抑郁、軀體化得分高于家庭完好無損者(表1)。
2.2個體韌性、社會支持與心理健康的路徑分析
對災區受試各量表得分的相關分析表明,個體韌性與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呈正相關(r=0.24,0.33;均P
按照差異檢驗及相關分析的結果,以受災程度為自變量(0=家庭完好無損,1=家人遇難),以個體韌性、社會支持以及生活滿意度、抑郁、軀體化為因變量,并將軀體化與生活滿意度之間的路徑系數設定為0,其余變量間路徑系數設定為自由估計,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所得模型的擬合指標(χ2=10.12,P= 0.001,df = 1, RMSEA = 0.16,NFI = 0.98,NNFI = 0.72,CFI = 0.98,IFI = 0.98,AGFI = 0.80)未達到可接受的標準[18],個體韌性與抑郁(β= -0.04,P>0.05)、個體韌性與軀體化(β= -0.09,P>0.05)之間的路徑系數未達到統計顯著性,于是刪除上述路徑,新的模型擬合良好(χ2=12.85,P = 0.005,df = 3,RMSEA = 0.098,NFI = 0.97,NNFI = 0.90,CFI = 0.98,IFI = 0.98,AGFI = 0.91)。個體韌性較高者,其社會支持也較高(β=0.23,P
為進一步驗證個體韌性的有限性模型的特異性,恢復個體韌性到抑郁、軀體化的路徑,刪除社會支持到抑郁、軀體化的路徑,得到的社會支持有限性模型未達到可接受的標準(χ2=32.64,P< 0.001,df = 3,RMSEA = 0.17,NFI = 0.93,NNFI = 0.69,CFI = 0.94,IFI = 0.94,AGFI = 0.79)。
3 討 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家庭完好無損的災區受試與非災區受試的個體韌性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表明在一般災難環境下人們自身的良好個人品質依然能夠保留完好。但是,遇難者家屬的個體韌性低于災區家庭完好無損者與非災區受試,并且其社會支持、生活滿意度低于家庭完好無損者,抑郁、軀體化得分高于家庭完好無損者,表明遇難者家屬的復原狀況較差,驗證了高暴露環境下韌性不足這一結論[10]。
在相關分析中,個體韌性和社會支持均與生活滿意度正相關,與抑郁、軀體化負相關,與以往研究結果一致[13,19]。這提示,在韌性研究的初始階段,研究者一般都能得出韌性與積極心理狀態的簡單相關,但忽視社會支持及個體、環境交互作用的逆境復原機制顯然是不科學的[6]。同時考慮個體韌性與社會支持的路徑分析發現,雖然個體韌性較高者的生活滿意度較高,但個體韌性與抑郁、軀體化之間的直接關系卻并不顯著,再次驗證了個體韌性的有限性[11];同時,社會支持與個體韌性這兩個維度的相關,以及社會支持與生活滿意度的正向關聯、與抑郁、軀體化的負向關聯,支持了廣義的韌性模型,即韌性、復原不僅意味著自身具有較高的個體韌性,更意味著擁有較多的社會支持[9]。也就是說,一些學者所謂的普遍存在的個體韌性,并不同于創傷后的復原,因而對于那些在極端創傷條件下表現出嚴重心理癥狀的個體(如遇難者家屬)未必適用[1]。
本研究中的路徑分析發現了社會支持和生活滿意度、抑郁、軀體化的穩定關聯,而刪除社會支持與抑郁、軀體化之間路徑的社會支持有限性模型未達到可接受的標準。這表明,相對于個體韌性,社會支持在災后復原機制中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再次驗證了從外部保護性因素的角度來探討韌性復原機制的重要性[4-5]。這提示,災區的創傷心理輔導工作尤其要重視受災群眾社會支持系統的重建,而不應片面強調個體自身的內部調節。然而,鑒于個體韌性對于中國文化的重要價值[7-9],以及中國文化強烈的個體指責的傾向[20],本研究對災難條件下個體韌性有限性的探討,對于反思中國傳統文化面對現代社會的復雜系統時如何尊重個體的脆弱,以及面對創傷(或災難)時如何更有效的復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2,6]。
致謝:中科學院心理所危機干預中心、四川團省委12355心靈驛站、什邡市大學生志愿者協會的工作人員對本研究的取樣給予了大力支持;余云紅、郭卿、陳柳、楊曉婷、聶潤秋、周嬋、陳曦、王寧等同學,為本研究的受試取樣、數據分析給予了幫助;中科院心理所吳振云研究員給予了指導!
參考文獻
[1]Bonanno G.Loss,trauma,and human resilience[J].Am Psychol,2004,59(1):20-28.
[2]Fiksel J.Sustainability and resilience:toward a systems approach[J].Sustainabil Sci Pract Policy,2006,2(2):14-21.
[3]Hamel G,Valikangas L.The quest for resilience[J].Harvard Business Rev,2003,81(9):52-65.
[4]Agaibi C,Wilson J.Trauma,PTSD,and resilience: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Trauma Violence Abuse,2005,6(3):195.
[5]Mandleco B,Peery J.An organizational framework for conceptualiz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J].J Child Adolesc Psychiatr Nurs,2000,13(3):99-112.
[6]Luthar S,Cicchetti D.The construct of resilience: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social policies[J].Dev Psychopathol,2000,12(4):857-885.
[7]于肖楠,張建新.韌性(resilience)――在壓力下復原和成長的心理機制[J].心理科學進展,2005,13(5):658-665.
[8]Shek D.Chinese cultural beliefs about adversity:its relationship to psychological well-being,school adjustment and problem behaviour in Hong Kong adolescents with and without economic disadvantage[J].Childhood,2004,11(1):63.
[9]Luthans F,Avey J,Clapp-Smith R,et al.More evidence on the value of Chinese workers'psychological capital:A potentially unlimited competitive resource?[J]Int J Human Resource Manage,2008,19(5):818-827.
[10]Bonanno G,Galea S,Bucciarelli A,et al.Psychological resilience after disaster.New York City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September 11th terrorist attack[J].Psychol Sci,2006,17(3):181-186.
[11]Hamamura T,Heine S,Paulhus D.Cultural differences in response styles:The role of dialectical thinking[J].Pers Individ Differ,2008.44(4):932-942.
[12]張姝,王芳,許燕,等.受災情況和復原力對地震災區中小學生創傷后應激反應的影響[J].心理科學進展,2009,17(3):556-561.
[13]Yu Xiaonan,Zhang Jianxin.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with Chinese people[J].Soc behave Pers,2007,35(1):19-30.
[14]肖水源.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應用[J].臨床精神醫學雜志,1994,4(2):98-100.
[15]Pavot W,Diener E.Review of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Scale[J].Psychol Assess,1993,5(2):164-164.
[16]Chen C,Lee S,Stevenson H.Response style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of rating scales among East Asian and North American students[J].Psychol Sci,1995:6(3):170-175.
[17]吳文源,王征宇.癥狀自評量表(SCL-90)[J].上海精神醫學,1990,2(1):68-69.
[18]溫忠麟,侯杰泰.結構方程模型檢驗:擬合指數與卡方準則[J].心理學報,2004,36(2):186-194.
[19]Campbell-Sills L,Stein M.Psychometric analysis and refinement of the 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Validation of a 10-item measure of resilience[J].J Traumat Stress,2007,20(6):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