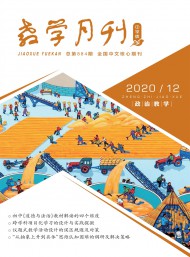直播間的盈利模式范文
時(shí)間:2024-01-04 17:46:35
導(dǎo)語(yǔ):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直播間的盈利模式,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guān)鍵詞 集束化護(hù)理 內(nèi)鏡黏
>> 內(nèi)鏡下胃息肉切除術(shù)圍手術(shù)期應(yīng)用集束化護(hù)理的效果分析 內(nèi)鏡下胃黏膜剝離治療胃間質(zhì)瘤的手術(shù)配合體會(huì)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在胃異位胰腺治療中的應(yīng)用 健康教育在內(nèi)鏡粘膜剝離術(shù)患者圍手術(shù)術(shù)期的實(shí)施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胃食管連接部癌前病變的臨床效果觀察 內(nèi)鏡粘膜下剝離術(shù)(ESD)圍手術(shù)期的護(hù)理體會(huì) 護(hù)理告知在內(nèi)鏡黏膜剝離術(shù)中的應(yīng)用觀察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早期上消化道腫瘤的圍術(shù)期護(hù)理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早期結(jié)直腸癌的圍術(shù)期護(hù)理 分層級(jí)管理在內(nèi)鏡下黏膜剝離術(shù)患者中的應(yīng)用及分析 淺談胃間質(zhì)瘤的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護(hù)理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在消化道隆起性病變治療中的應(yīng)用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在治療早期胃癌及癌前病變中的應(yīng)用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消化道病變的臨床研究 腹腔鏡下胃轉(zhuǎn)流術(shù)的圍手術(shù)期護(hù)理 內(nèi)鏡下黏膜剝離術(shù)的護(hù)理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的護(hù)理配合探討 二氧化碳?xì)怏w灌注在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中的應(yīng)用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上消化道黏膜病變及黏膜下腫物臨床研究 內(nèi)鏡黏膜下剝離術(shù)治療早期胃癌的護(hù)理 常見(jiàn)問(wèn)題解答 當(dāng)前所在位置:.
3 Resar R,Pronovost P,Haraden C,et al.Using a bundle approach to improve ventilator care processes and reduce 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J].J Qual Patient Saf,2005,31:243-248.
4 郝晉雍,黃曉俊.ESD在治療早期胃癌及癌前病變中的應(yīng)用[J].胃腸病學(xué)和肝病學(xué)雜志,2011,20(6):58.
5 單君,朱建華,顧艷葒.集束化護(hù)理理念及其臨床應(yīng)用的研究進(jìn)展[J].護(hù)士進(jìn)修雜志,2010,25(10):890.
6 Masaki Tanaka,Hiroyuki Ono,Noriaki Hasuike.Endoscopic submucosal dissection Of early gastriccancer.Digestion,2008,77(1):23-28.
篇2
廣播欄目創(chuàng)意與創(chuàng)新的趨勢(shì)有哪些呢?
一、互聯(lián)網(wǎng)新技術(shù)對(duì)廣播創(chuàng)新的影響日益深化
近十年的廣播創(chuàng)新一直與互聯(lián)網(wǎng)新技術(shù)發(fā)展密切相關(guān)。從網(wǎng)絡(luò)誕生之初,廣播節(jié)目創(chuàng)新便一直伴隨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不斷升級(jí)而“水漲船高”。無(wú)論是在節(jié)目?jī)?nèi)容的提供,還是與受眾之間的互動(dòng),互聯(lián)網(wǎng)都從一個(gè)互動(dòng)平臺(tái)、內(nèi)容平臺(tái),慢慢升級(jí)成為了介質(zhì)平臺(tái)、“創(chuàng)意T臺(tái)”。甚至,有的廣播節(jié)目,沒(méi)有互聯(lián)網(wǎng)就難以持續(xù)。1999年開(kāi)始,騰訊公司的QQ聊天軟件開(kāi)始流行,到了2000年,注冊(cè)用戶突破1000萬(wàn)。廣播節(jié)目中開(kāi)始有了“QQ聊天秀”等優(yōu)秀廣播節(jié)目。2008年第一屆“贏在創(chuàng)意”大賽中的獲獎(jiǎng)作品《博客斗秀堂》也是與當(dāng)時(shí)火爆網(wǎng)絡(luò)的博客相結(jié)合的廣播節(jié)目。2011年第4屆“贏在創(chuàng)意”大賽中涌現(xiàn)出一批微博類作品。例如:獲得原創(chuàng)金獎(jiǎng)的《愛(ài)微博》欄目。它將微博作為重要的內(nèi)容渠道,將微博客出現(xiàn)的熱門話題擴(kuò)大為自身的新聞源以豐富自身新聞線索。獲得原創(chuàng)優(yōu)秀獎(jiǎng)的《我們的微電臺(tái)》則是將微博作為與受眾互動(dòng)的主要渠道,通過(guò)微博求助信息,分享有用知識(shí),以微博互動(dòng)話題搭建節(jié)目與受眾互動(dòng)的橋梁。除了微博,移動(dòng)網(wǎng)絡(luò)新技術(shù)也在廣播欄目創(chuàng)新中得到了體現(xiàn)。例如:奪得創(chuàng)新鼓勵(lì)獎(jiǎng)的作品《今天吃什么》,這個(gè)欄目是根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的LBS移動(dòng)定位服務(wù)概念創(chuàng)意的欄目。它讓聽(tīng)眾發(fā)送手機(jī)短信告知所處區(qū)域和用餐性質(zhì),主持人通過(guò)網(wǎng)站搜索后發(fā)送短信告訴合適的飯館,并進(jìn)行優(yōu)惠券推送等。從以上的例子我們不難看出,互聯(lián)網(wǎng)對(duì)廣播的影響正在日益加深。廣播媒介與新媒體的聯(lián)合使得媒介聯(lián)合成為傳媒間合作共贏的新范本。
二、深度互動(dòng)和多重互動(dòng)成為廣播節(jié)目創(chuàng)新的媒介特性
開(kāi)放性是廣播強(qiáng)于其他媒介的比較優(yōu)勢(shì),從聽(tīng)眾來(lái)信到熱線電話、從短信平臺(tái)到網(wǎng)絡(luò)聽(tīng)眾論壇、從節(jié)目博客到主持人的微博,縱觀廣播互動(dòng)的每次飛躍,其背后蘊(yùn)含的真正變革是受眾本位的實(shí)現(xiàn),是受眾更為深入地參與、更為多重地參與。尤其有了主持人的微博、節(jié)目的微博之后,聽(tīng)眾之間的互動(dòng)更加便捷了,這更加拉近了受眾與媒介的距離。在近些年的廣播創(chuàng)新節(jié)目中,對(duì)聽(tīng)眾互動(dòng)能力的開(kāi)發(fā)越來(lái)越完善。從前由聽(tīng)眾貢獻(xiàn)內(nèi)容,現(xiàn)在使互動(dòng)既是一種形式,也是一種內(nèi)容。聽(tīng)眾本身參加互動(dòng)也能提供節(jié)目的內(nèi)容。吉林人民廣播電臺(tái)教育廣播的創(chuàng)新節(jié)目《提問(wèn)?回答》就是由聽(tīng)眾提出問(wèn)題,天南海北無(wú)所不含,答案也是由聽(tīng)眾來(lái)回答。主持人只是承上啟下的作用,節(jié)目開(kāi)設(shè)多種互動(dòng)方式,節(jié)目的內(nèi)容基本由聽(tīng)眾本身全部填滿。
三、廣播節(jié)目盈利模式的創(chuàng)新
目前,我國(guó)的廣播節(jié)目仍依靠較為單一的廣告盈利模式。發(fā)現(xiàn)并運(yùn)用全新的盈利模式也是廣播節(jié)目可持續(xù)發(fā)展的一劑良藥。例如:《我的團(tuán)長(zhǎng)我的團(tuán)》,將團(tuán)購(gòu)、秒殺等流行的電子商務(wù)模式融入廣播節(jié)目,并對(duì)節(jié)目的線下運(yùn)作提出了明確的品牌與產(chǎn)業(yè)運(yùn)作規(guī)劃。這類欄目創(chuàng)新了廣告和購(gòu)物類節(jié)目的內(nèi)容與形式。他們?cè)跒橛脩籼崞泛头?wù)的同時(shí),打造自己的團(tuán)購(gòu)平臺(tái),實(shí)現(xiàn)電臺(tái)、聽(tīng)眾、廣告三方的共贏。
四、“戲說(shuō)新聞”成為廣播新聞?lì)惞?jié)目創(chuàng)新的新趨勢(shì)
新聞?lì)悪谀砍尸F(xiàn)出向軟新聞、接近性、實(shí)用性靠攏的特點(diǎn)。在內(nèi)容選擇上,竭力從嚴(yán)肅新聞中挖掘其娛樂(lè)元素;在表現(xiàn)技巧上,強(qiáng)調(diào)故事性、情節(jié)性,按照快樂(lè)原則處理新聞。例如:吉林人民廣播電臺(tái)教育廣播《新聞表情》,以說(shuō)新聞的形式,對(duì)新聞加以“喜怒哀樂(lè)”式的解讀,在一定程度上使新聞放下了嚴(yán)肅面孔,讓聽(tīng)眾在接受信息的過(guò)程中獲得愉悅體驗(yàn),傳播效果也大大提升。
五、“平臺(tái)意識(shí)”和“收聽(tīng)體驗(yàn)”助力廣播節(jié)目創(chuàng)意和創(chuàng)新
截至目前,省級(jí)廣播媒體基本都有了自己的專業(yè)網(wǎng)站和在線收聽(tīng)的電臺(tái)。加強(qiáng)廣播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建設(shè)、短信平臺(tái)建設(shè)、媒資系統(tǒng)建設(shè)、人力資源平臺(tái)等“平臺(tái)建設(shè)”已經(jīng)成為業(yè)界共識(shí)。這其中,尤其以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建設(shè)為主。越來(lái)越多的廣播節(jié)目、互動(dòng)方式依仗于本臺(tái)自身的專業(yè)性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這個(gè)平臺(tái)為節(jié)目帶來(lái)諸多便利與服務(wù)的同時(shí),在一定程度上,也為節(jié)目本身帶來(lái)了創(chuàng)意的源泉和創(chuàng)新的可能。
越來(lái)越多的廣播節(jié)目期望能像Iphone手機(jī)一樣,給受眾帶來(lái)不同凡響的“收聽(tīng)體驗(yàn)”。這種“收聽(tīng)體驗(yàn)”應(yīng)用在創(chuàng)新節(jié)目中,不僅僅是收聽(tīng)內(nèi)容的標(biāo)新立異,同時(shí)在收聽(tīng)方式、互動(dòng)方式上同樣帶來(lái)全新的聽(tīng)覺(jué)享受。例如:廣播節(jié)目《愛(ài)上微電臺(tái)》,這就是一檔在傳統(tǒng)收音機(jī)和網(wǎng)絡(luò)廣播同時(shí)直播的音樂(lè)脫口秀節(jié)目。受眾可以在微電臺(tái)中一邊聽(tīng)節(jié)目一邊互動(dòng),甚至可以通過(guò)節(jié)目自身的平臺(tái),與其他聽(tīng)眾對(duì)話、聊天、視頻,并可以看見(jiàn)主持人在直播間的狀態(tài)等等。視頻直播、廣播和網(wǎng)絡(luò)等媒體之間融合聯(lián)動(dòng)、受眾之間深度互動(dòng),這些看似與傳統(tǒng)廣播媒介大相徑庭的收聽(tīng)體驗(yàn)也許將馬上改變我們對(duì)廣播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
篇3
6月11日,蘋果公司在其開(kāi)發(fā)者網(wǎng)站上更新《安全審核指南》。其中明確,應(yīng)用內(nèi)向原創(chuàng)作者的打賞屬于“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英文In-App Purchase,下稱IAP機(jī)制)。
由于該支付通道下的所有付款均需向蘋果公司分成30%,就何為打賞、硬件廠商能否對(duì)打賞分成等,引發(fā)了爭(zhēng)議。不論是2016年的網(wǎng)絡(luò)直播“風(fēng)口”,還是近年來(lái)屢被提起的“知識(shí)變現(xiàn)”潮流,網(wǎng)絡(luò)打賞都作為重要商業(yè)模式被頻繁提起。
在被稱為中國(guó)互聯(lián)網(wǎng)獨(dú)有的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的同時(shí),互聯(lián)網(wǎng)語(yǔ)境下,打賞也面臨著性質(zhì)上的種種不確定性。 中國(guó)式商業(yè)模式:“打賞”
在一個(gè)網(wǎng)絡(luò)直播間里,觀看約10分鐘后,用戶ltfy123按下屏幕下方的“贈(zèng)送禮物”按鈕,系統(tǒng)提示需充值。充值成功后,ltfy123選擇向主播贈(zèng)送一枚折合人民幣約7元的“鉆戒”。系統(tǒng)以虛擬動(dòng)畫的形式在屏幕上顯示了這一贈(zèng)送。
2016年移動(dòng)直播風(fēng)口中,作為直播平臺(tái)的主要盈利模式,“網(wǎng)絡(luò)打賞”的金額紀(jì)錄屢被刷新。頭部網(wǎng)對(duì)四家主流直播平臺(tái)前1萬(wàn)名主播的統(tǒng)計(jì)顯示,2016年,2名主播收入過(guò)千萬(wàn)元,45%的主播收入在5萬(wàn)-10萬(wàn)元之間。
“打賞是沒(méi)法舍棄的,這是最成熟的商業(yè)模式。”2016年8月的“ふ抑泄創(chuàng)客”會(huì)議上,歡聚時(shí)代執(zhí)行副總裁、YY直播平合創(chuàng)始人董榮杰表示。
早在2013年,縱橫中文網(wǎng)上,就有一名書迷向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者的新書打賞折合約100萬(wàn)元人民幣的紀(jì)錄。
“知識(shí)變現(xiàn)”是近年來(lái)打賞模式被廣泛應(yīng)用的另一場(chǎng)景。除了先充值再向主播或作者贈(zèng)送虛擬禮物的形式外,許多內(nèi)容平臺(tái)推出的功能是,讀者可向作者直接打賞等值現(xiàn)金。
知乎、微博、微信等社交和內(nèi)容平臺(tái)都開(kāi)通了對(duì)文章的相應(yīng)功能。
新浪微博于2014年對(duì)長(zhǎng)微博“文章”開(kāi)通了打賞功能。其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6年1月-9月,微博打賞交易額連續(xù)保持增長(zhǎng)態(tài)勢(shì),三季度打賞訂單量超過(guò)200萬(wàn)筆。
內(nèi)容問(wèn)答網(wǎng)站知乎的漫畫話題優(yōu)秀回答者lian告訴《財(cái)經(jīng)》記者,他開(kāi)設(shè)的線上講座(知乎Live)需付費(fèi)15元參與,但在互動(dòng)過(guò)程中,仍有許多參與者會(huì)打賞幾元到幾十元不等的現(xiàn)金。盡管主講話題較為冷門,一場(chǎng)線上講座仍能獲得3000多元的現(xiàn)金,據(jù)他介紹,這一收入在該平臺(tái)十分普遍。
是否付費(fèi)、付費(fèi)多少均由打賞者決定,介于“高境界的免費(fèi)”和“內(nèi)容付費(fèi)”之間,網(wǎng)絡(luò)打賞被稱為中國(guó)式互聯(lián)網(wǎng)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
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rèn)為,打賞模式下,用戶可表達(dá)對(duì)個(gè)別主播和作品的贊賞,被打賞者可以獲得著作權(quán)的補(bǔ)償,平臺(tái)則可通過(guò)打賞分成等方式有價(jià)值地經(jīng)營(yíng)下去,是良性的商業(yè)和內(nèi)容傳播模式。
4月19日,由于長(zhǎng)久未能與蘋果公司達(dá)成協(xié)議,iOS版微信關(guān)閉公眾號(hào)內(nèi)文章下的贊賞功能后,影響大批自媒體作者。艾媒咨詢的調(diào)查數(shù)據(jù)顯示,71.5%網(wǎng)民認(rèn)為蘋果公司對(duì)打賞收費(fèi)30%不合理。艾媒咨詢告訴《財(cái)經(jīng)》記者,該數(shù)據(jù)樣本統(tǒng)計(jì)量約為6000人。 介于“高境界的免費(fèi)”和“內(nèi)容付費(fèi)”之間,網(wǎng)絡(luò)打賞被稱為中國(guó)式互聯(lián)網(wǎng)商業(yè)模式創(chuàng)新。
而隨著網(wǎng)絡(luò)打賞數(shù)量和金額的不斷提高,也引發(fā)一些問(wèn)題。
2015年天津港爆炸事故后,楊某先通過(guò)手機(jī)搜索了“微博打賞功能怎么設(shè)置”后,虛假微博文章稱其父親在爆炸中喪生,一夜之間獲得大量網(wǎng)民關(guān)注,收到近4000筆總金額為96576.44元人民幣的打賞,并在此后搜索了“新浪微博打賞如何提現(xiàn)”。因構(gòu)成詐騙罪,楊某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三年。
2016年11月25日,作家羅爾于個(gè)人微信公眾號(hào)的《羅某笑,你給我站住》(下稱《站住》)一文中,描述了其女兒患白血病的經(jīng)歷,引發(fā)轟動(dòng),獲得約11萬(wàn)人總計(jì)200萬(wàn)余元贊賞金。此后羅爾經(jīng)濟(jì)實(shí)力和其用于治療女兒白血病的實(shí)際花銷遭到多次質(zhì)疑,幾經(jīng)反轉(zhuǎn)后,贊賞金被全部退還。
“朋友們后來(lái)分析,退還《站住》一文贊賞金,是我最愚蠢的沖動(dòng)。《站住》一文本來(lái)是正常的公眾號(hào)文章,我一退,坐實(shí)了我的錯(cuò)誤。”羅爾撰文表示。
“一般情況下,主播或者作者獲得的打賞收益可理解為版權(quán)費(fèi)用或者對(duì)著作權(quán)的補(bǔ)償”。朱巍說(shuō),不過(guò)羅爾獲得贊賞金遠(yuǎn)超其文章價(jià)值,不屬于版權(quán)費(fèi)用,其行為屬于個(gè)人求助。
多起關(guān)于網(wǎng)絡(luò)打賞的糾紛背后,法律界對(duì)打賞的性質(zhì)看法不一。 何為打賞?
在蘋果公司對(duì)打賞要求抽成的事件中,打賞屬于贈(zèng)與行為還是銷售行為,說(shuō)法不一。
最為廣泛的觀點(diǎn)是,打賞屬于用戶間的贈(zèng)與行為,因而蘋果公司將其列入“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項(xiàng)目沒(méi)有依據(jù)。
北京志霖律師事務(wù)所副主任、中國(guó)政法大學(xué)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趙占領(lǐng)分析,從情形看,打賞主要分為兩種,即用戶閱讀文章后基于對(duì)內(nèi)容的肯定而給出的贈(zèng)與;另一種則為作者通過(guò)內(nèi)容傳達(dá)出需要幫助的困難狀態(tài),用戶基于此表達(dá)一種捐贈(zèng)型的打賞。
趙占領(lǐng)認(rèn)為,以上打賞情形下,支付發(fā)生時(shí)間點(diǎn)均為閱讀完之后,也沒(méi)有購(gòu)買行為所需要的對(duì)價(jià);而且,銷售行為需要有銷售者并表達(dá)銷售意愿,但在打賞中,作者沒(méi)有表達(dá)銷售明確種類和價(jià)格的商品的意愿。因此,蘋果公司將贊賞列為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與實(shí)際不符。蘋果公司不屬于贈(zèng)與合同的任何一方,也沒(méi)有提供任何服務(wù),所以沒(méi)有資格收取費(fèi)用。
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法學(xué)院助理教授熊丙萬(wàn)則認(rèn)為,通過(guò)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的打賞行為,無(wú)論是直播打賞和文章打賞,通常情況下并不是一種單向的施惠行為。相反,打賞者之所以打賞,通常是因?yàn)閺谋淮蛸p者的表演活動(dòng)或者文章思想上獲得了精神上的滿足感,獲得了現(xiàn)實(shí)的利益。
《合同法》第185條規(guī)定,“贈(zèng)與合同是贈(zèng)與人將自己的財(cái)產(chǎn)無(wú)償給予受贈(zèng)人,受贈(zèng)人表示接受贈(zèng)與的合同。”
熊丙萬(wàn)表示,贈(zèng)與合同的一個(gè)核心特征是“無(wú)償性”,即贈(zèng)與人將自己的財(cái)產(chǎn)無(wú)償?shù)剞D(zhuǎn)讓給受贈(zèng)人,是一種單向的施惠行為,而不是一種雙向的互利互惠行為。而網(wǎng)絡(luò)平臺(tái)打賞是一種雙向的互利互惠行為,在性質(zhì)上可以歸入“服務(wù)合同”。即被打賞者提供了表演服務(wù)或者思想啟發(fā)服務(wù),打賞者向被打賞者支付服務(wù)價(jià)金。
作為對(duì)比,熊丙萬(wàn)指出,很多針對(duì)重大疾病患者的捐贈(zèng)眾籌平臺(tái)上的資金轉(zhuǎn)讓一般是贈(zèng)與合同,因而適用《合同法》關(guān)于贈(zèng)與的規(guī)則。
中南財(cái)經(jīng)政法大學(xué)法學(xué)院副院長(zhǎng)、教授黎江虹也認(rèn)為,在微信公號(hào)打賞中,贊賞人提供有價(jià)值的文章作為對(duì)價(jià),贊賞人與被贊賞人之間并非構(gòu)成單務(wù)法律關(guān)系,因此不符合贈(zèng)與行為的構(gòu)成要件。
對(duì)于打賞的性質(zhì)之爭(zhēng),導(dǎo)致的直接影響還包括,被打賞者獲得的收益是否需要納稅。
在羅爾事件中,盡管200萬(wàn)余元贊賞金被悉數(shù)退還,但網(wǎng)絡(luò)語(yǔ)境下打賞迅速集聚的金額屢創(chuàng)紀(jì)錄,巨額贊賞金是否需要納稅的話題也再被提起。
現(xiàn)行《個(gè)人所得稅法》所列明的11種應(yīng)納個(gè)人所得稅的情形中,“贈(zèng)與所得”并未明確被納入其中。因此,許多觀點(diǎn)認(rèn)為,一個(gè)自然人從另一自然人處取得的打賞收入,受贈(zèng)人暫無(wú)納稅依據(jù),不需要繳納個(gè)人所得稅。
但黎江虹認(rèn)為微信打賞不能被認(rèn)定為贈(zèng)與關(guān)系,理由如上。不過(guò),黎也表示對(duì)于微信打賞收入規(guī)模如何,是否具有現(xiàn)實(shí)可稅性,有待進(jìn)一步的權(quán)威數(shù)據(jù)支撐。互聯(lián)網(wǎng)經(jīng)濟(jì)作為新生事物,稅收也應(yīng)保持一定的謙抑性,給予新生事物較大的寬容。因此,在當(dāng)前階段對(duì)打賞收入所得不予征稅有正當(dāng)性和必要性。
而就直播打賞而言,“打賞”這一商業(yè)模式下所產(chǎn)生的巨大利潤(rùn),和被打賞者所獲得的巨額收益,平臺(tái)被認(rèn)為需為主播代繳個(gè)人所得稅。
3月10日,北京市朝陽(yáng)區(qū)地稅局曾披露,某直播平臺(tái)2016年支付給直播人員的收入高達(dá)3.9億元,但未按規(guī)定代扣代繳個(gè)人所得稅,今年最終補(bǔ)繳稅款6000多萬(wàn)元。“這家企業(yè)自成立以來(lái)確認(rèn)的所有收入,均未包括支付給網(wǎng)絡(luò)主播的個(gè)人分成收入,也未給主播代扣代繳個(gè)人所得稅。”
某平臺(tái)主播“kry-jing”告訴《財(cái)經(jīng)》記者,其與直播平臺(tái)的分成約為7.5∶2.5,從未聽(tīng)說(shuō)過(guò)需要納稅,也未跟平臺(tái)就此溝通過(guò)。
除了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打賞所得是否應(yīng)納稅,應(yīng)屬于哪一種個(gè)人所得稅的爭(zhēng)議外,對(duì)于網(wǎng)絡(luò)打賞征稅的另一問(wèn)題在于,平臺(tái)是否應(yīng)承擔(dān)代繳個(gè)人所得稅的義務(wù)。
一些說(shuō)法認(rèn)為,平臺(tái)是否在打賞收入中獲得分成,可以成為其是否需要替被打賞者代繳個(gè)人所得稅的依據(jù)。
在黎江虹看來(lái),若認(rèn)可打賞具有可稅性,則有必要將開(kāi)通“打賞”功能的平臺(tái)作為代繳義務(wù)人。即使平臺(tái)稱僅為信息服務(wù)的提供者,不對(duì)打賞所得分成。一方面,《個(gè)人所得稅法》規(guī)定,扣繳義務(wù)人的確定并不以其從納稅義務(wù)人的收入中獲利為前提;另一方面,從民間披露數(shù)據(jù)來(lái)看打賞收入普遍不高,在目前稅收征管條件下稅收機(jī)關(guān)難以監(jiān)管該部分收入,若不實(shí)行代扣代繳,可能造成稅款流失。
騰訊公司的《微信公眾平臺(tái)贊賞功能使用協(xié)議》中曾聲明:“騰訊僅作為提供信息功能的中立平臺(tái)方,贊賞用戶應(yīng)依法繳納的各種稅費(fèi),由贊賞用戶自行繳納。”
目前,協(xié)議相關(guān)規(guī)定已增補(bǔ)“依照法律規(guī)定須由騰訊代扣代繳的,騰訊將予以代扣代繳。”
“如果平臺(tái)不代繳,個(gè)人根本不可能有主動(dòng)納稅的自主性。”朱巍說(shuō)。 打賞“抽成”的競(jìng)爭(zhēng)法爭(zhēng)議
蘋果公司要求對(duì)iOS端下所有應(yīng)用“打賞”金額收取30%費(fèi)用,有人擔(dān)憂,或?qū)?duì)以打賞為主要商業(yè)模式的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tái)等帶來(lái)負(fù)面影響。而蘋果公司對(duì)打賞抽成的行為是否違法的問(wèn)題,也屢被提起。
依據(jù)蘋果公司規(guī)則,如果開(kāi)發(fā)者想提供用戶訂閱、游戲內(nèi)虛擬貨幣、會(huì)員內(nèi)容、完整版本等付費(fèi)功能,均需通過(guò)IAP機(jī)制。同時(shí),相關(guān)軟件不得以外部鏈接、按鈕等其他方式,引導(dǎo)消費(fèi)者使用該通道以外的支付方式。
蘋果公司官網(wǎng)介紹,“理解Apple Pay(蘋果支付)和‘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之間的區(qū)別是非常重要的。Apple Pay用于銷售物理商品”,而“‘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只用于銷售虛擬物品”。
用戶在應(yīng)用內(nèi)購(gòu)買虛擬物品時(shí),只需通過(guò)輸入蘋果賬號(hào)驗(yàn)證的方式,即可完成付款,無(wú)需跳轉(zhuǎn)至其他頁(yè)面。通過(guò)這種方式支付,蘋果公司會(huì)向APP開(kāi)發(fā)者抽取30%的平臺(tái)傭金。而對(duì)于“APP以外的實(shí)物商品和服務(wù)”,則不得通過(guò)該機(jī)制,也即與30%費(fèi)用無(wú)關(guān)。
許多直播平臺(tái)早已將打賞充值規(guī)則修改并納入IAP機(jī)制。映客直播回應(yīng)《財(cái)經(jīng)》記者稱,一開(kāi)始就遵守蘋果公司規(guī)則,因此這一規(guī)則對(duì)其并無(wú)影響。
艾媒咨詢分析師劉杰豪稱,iOS端在直播畫面流暢度等用戶體驗(yàn)方面,具有一定優(yōu)勢(shì),所以相對(duì)于微信公眾號(hào)、知乎等文字類內(nèi)容收費(fèi)平臺(tái)來(lái)講,直播平臺(tái)對(duì)iOS系統(tǒng)的依賴度更為明顯,這一點(diǎn)也是YY、映客等直播平臺(tái)服從蘋果收費(fèi)條款的主要考慮因素。
不^,許多業(yè)內(nèi)人士認(rèn)為,蘋果公司針對(duì)應(yīng)用開(kāi)發(fā)者的這一強(qiáng)制條款涉嫌“濫用市場(chǎng)支配地位”的壟斷,并呼吁相關(guān)執(zhí)法機(jī)構(gòu)啟動(dòng)對(duì)該行為的反壟斷調(diào)查。
要認(rèn)定蘋果公司濫用市場(chǎng)支配地位,首先須界定其相關(guān)市場(chǎng),證明蘋果公司在相關(guān)市場(chǎng)上具有支配地位,并以明顯不合理高價(jià)等方式濫用這一地位。
一些觀點(diǎn)認(rèn)為,“相關(guān)市場(chǎng)”應(yīng)界定為“基于iOS應(yīng)用程序的分發(fā)市場(chǎng)”,而在這一市場(chǎng),蘋果公司毋庸置疑占有絕對(duì)支配地位。
中國(guó)青年政治學(xué)院互聯(lián)網(wǎng)法治研究中心執(zhí)行主任劉曉春并不同意該觀點(diǎn)。界定相關(guān)市場(chǎng),需考慮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份額、可替代性、消費(fèi)者的選擇可能性等。“如果將一個(gè)產(chǎn)品界定為一個(gè)市場(chǎng),那么所有企業(yè)都將不可避免地成為壟斷者。”她說(shuō)。
趙占領(lǐng)認(rèn)為,若進(jìn)行反壟斷法意義上的相關(guān)市場(chǎng)界定,應(yīng)以移動(dòng)智能終端市場(chǎng)為宜。
IDC中國(guó)季度手機(jī)跟蹤報(bào)告顯示,2016年蘋果手機(jī)在中國(guó)出貨量約為4490萬(wàn)臺(tái),市場(chǎng)份額為9.6%,排名第四。這一數(shù)據(jù)下,關(guān)于蘋果公司這一行為涉嫌壟斷的指責(zé),或難以成立。
劉曉春表示,只有在有足夠的證據(jù)證明,其行為已延伸至可以通過(guò)市場(chǎng)支配地位控制支付行為,使得其他支付工具競(jìng)爭(zhēng)者受到限制的情況下,方可討論其壟斷問(wèn)題,否則需謹(jǐn)慎認(rèn)定。
關(guān)于蘋果與微信打賞“抽成”之爭(zhēng)的另一個(gè)法律指責(zé)是,蘋果公司強(qiáng)制將打賞行為列入IAP機(jī)制,對(duì)于應(yīng)用開(kāi)發(fā)者來(lái)說(shuō)屬于“附帶不合理的交易條件”或者“搭售”,涉嫌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
《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第12條規(guī)定,經(jīng)營(yíng)者銷售商品,不得違背購(gòu)買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的條件。
對(duì)此,趙占領(lǐng)分析,若蘋果公司通過(guò)將打賞功能納入IAP機(jī)制,來(lái)強(qiáng)化蘋果支付的核心地位,這種借助平臺(tái)強(qiáng)行搭售的行為,對(duì)于其他支付工具廠商來(lái)說(shuō),可能構(gòu)成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
劉曉春的看法是,蘋果公司這一將打賞行為列入IAP的條款,屬于格式條款,可以以合同法上的格式條款是否合理進(jìn)行判定。格式合同不合理至一定程度,可能有搭售的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嫌疑。因此,如果蘋果公司規(guī)定,所有虛擬物品的支付通道,均必須通過(guò)Apple Pay(蘋果支付)進(jìn)行,則可能構(gòu)成搭售。
目前,購(gòu)買虛擬物品的IAP機(jī)制,在中國(guó)支持支付寶、銀聯(lián)等方式,不包括微信支付,并未強(qiáng)制僅能通過(guò)蘋果支付進(jìn)行。
就打賞列入IAP的壟斷和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指責(zé)而言,劉曉春提醒說(shuō),競(jìng)爭(zhēng)法僅保護(hù)競(jìng)爭(zhēng)秩序,而非競(jìng)爭(zhēng)者。特別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在各種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層出不窮的前提下,競(jìng)爭(zhēng)法層面的規(guī)制更需審慎。是否違背購(gòu)買者的意愿,以及購(gòu)買者是否有選擇權(quán),是評(píng)價(jià)其行為的關(guān)鍵。
北京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副院長(zhǎng)薛軍亦認(rèn)為,蘋果公司與微信之間的行為,難言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律的目的不是干預(yù)所有問(wèn)題,自由競(jìng)爭(zhēng)和技術(shù)迭代自會(huì)解決大部分問(wèn)題。”
薛軍撰文指出,特別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領(lǐng)域,對(duì)于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的司法認(rèn)定,法院應(yīng)遵守謙抑的原則,不應(yīng)在并不了解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shù)發(fā)展趨勢(shì)和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態(tài)勢(shì)的情況下,被迫頻繁地就某種行為是否構(gòu)成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進(jìn)行定性。
熱門標(biāo)簽
直播 直播培訓(xùn)總結(jié) 直播油菜 直播栽培 直播衛(wèi)星 心理培訓(xùn) 人文科學(xué)概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