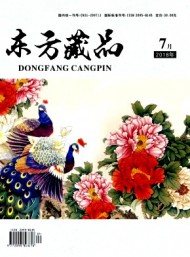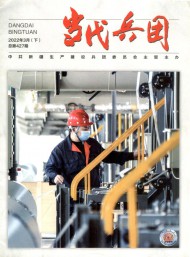關于民法典的相關知識范文
時間:2024-04-01 11:31:2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關于民法典的相關知識,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內容提要: 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要求我國知識產權法學界樹立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要求對知識性權利和知識性利益進行區分,主張民法才是知識產權權益的兜底保護法,并且要求民法建立與利益保護相適應的不法行為責任制度,只授予利益享有者債權性質的請求權。我國當下的知識產權法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司法實踐都存在諸多問題,因此,必須以民法為核心,重塑整體性知識產權法。
一、問題點
我國知識產權法理論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已有20多個年頭了。其中的研究成果自然不可否認。但和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知識產權法理論研究成果相比,我國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水平就顯得有些相形見絀了。 [1]考察我國知識產權法理論研究的現狀,至少存在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基本上從立法論的角度去研究問題,批判多于建構,理論重于實用,觀念超于現實。也就是說只注重應然問題的研究,而忽視實然問題的研究。從制定、修改和完善知識產權法的角度看,立法論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從實際解決問題的角度看,立法論就顯得有些過于超前。吹毛求疵是知識產權法學界學者的一個特點,但也是一個致命的錯誤。學者們經常抱怨法官們缺少理論知識或者批判法官們在任意甚至胡亂適用法律,但是法官們又何嘗不在抱怨學者們提出的一大堆空洞無物、對他們適用法律解決糾紛幾乎起不到任何作用甚至是廢話的理論呢?不管誰是誰非,知識產權法理論界和司法界缺乏真正的交流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樣的局面應該促使知識產權法學者從根本上反思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
二是即使注重實然問題的研究,但也是一般性論述多于特殊性論述、整體性論述多于細節性論述,研究視野狹窄,研究結論浮于表面。這種研究方法幾乎貫穿在知識產權法的所有領域。舉一個例子即可說明這個問題。如在論述注冊商標權和在先權利的關系時,大家一般都很簡單地認為在先權利能夠阻止他人商標注冊和成為注冊商標撤銷的理由。但是在先權利的范圍到底有多大?是否任何在先權利都可以成為阻止他人申請商標注冊和撤銷他人已經注冊商標的理由?注冊商標權是否能夠剝奪他人現有的在先權利?在先權利者能否擴大自己的營業范圍以至形成和注冊商標權人競爭的局面等問題都還無人問及。結果必然是:雖然相關論述多如牛毛,但是對于法官適用法律能夠起到學理上的借鑒和指導作用的,則少之又少。
為什么我國知識產權法的理論研究會呈現出這種狀況?這里面除了我國知識產權立法起步較西方發達國家要晚、整個理論研究的環境十分浮躁、學術評價體系存在嚴重問題、研究者個人的理論厚度不夠和研究視野狹窄等非常復雜的原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我國知識產權法立法界、司法界和學界忽視或者根本缺失民法基本觀念。 [2]本來,民法是知識產權法的母法是一個基本常識,但就是這樣一個基本常識卻被我國整個知識產權法學界甚至包括立法界和司法界有意或者無意地忘記了。如在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關系問題上,幾乎整個知識產權法學界都想當然地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法。 [3]這種觀點雖然看到了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的補充保護作用,但是卻完全忽視了民法位于知識產權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母法地位的基本事實。
民法觀念的缺失導致的惡果不僅僅是研究方法上的問題化,更為重要的是使知識產權立法和理論研究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立法和研究都顯得非常孤立、零碎,不能在民法的統一指導下形成一個完整而協調的體系。這種狀況嚴重遲滯了我國知識產權立法的進步和研究水準的提升。
上述狀況說明,重塑以民法為母法和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在我國已經刻不容緩。在此,筆者試圖對重塑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表明自己的觀點,以求教于大家。
二、理論基礎: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
重塑以民法作為核心的知識產權法首先碰到的一個問題是應當堅持何種知識產權觀念的問題。知識產權的觀念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知識產權自然權利觀念,一種是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在我國,知識產權自然權利觀念是梁慧星教授首先提出并經易繼明教授發展的觀念。 [4]該種觀念的核心主張是,洛克的勞動理論是知識產權合法性的基礎,勞動是知識產權的直接權源。由于現有知識產權法存在類型化不足的問題,因此應當由法官通過自由裁量,在利益考量的基礎上,為原告創設某種知識產權特別法沒有規定的權利。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則是鄭勝利教授首先提出并經朱理博士和筆者所發展的一種觀念。 [5]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的核心是,知識產權是一種由制定法(知識產權特別法——專利法、商標法、著作權法、植物新品種保護法、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法,以下提到制定法時,含義相同)賦予的權利,除了制定法之外,任何人都不能為知識生產者創設特定的權利。知識產權制定法沒有明確授予知識生產者的權利,也就是知識產品生產者不能享有的權利。在知識產權領域中,必須對授予知識生產者的權利和利益進行區分,并且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必須貫徹到整個知識產權立法和司法領域中。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可以說是知識產權自然權利觀念和知識產權工具主義觀念的統一體, [6]它既堅持勞動在知識產權配置中的抽象基礎作用,但是又認為不能將勞動作為唯一的、直接的考量因素,知識產權的配置還必須考量社會整體效率和社會正義的因素。
由于知識產權自然權利觀念存在無限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蠶食公共領域的危險,因此,為保護公共利益,知識產權必須堅持法定主義觀念。理由在于:
1.考察知識產權制度的立法歷史,可以發現,盡管英美法系國家和大陸法系國家由于自身的法律傳統、法律理念、立法技術等方面的原因導致其法典化的差別,但在知識產權的問題上則沒有什么分歧,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采取單行制定法的形式保護知識產權,并且使知識產權發展成為一個獨立于有形財產權的獨特法律體系。這說明,知識產權從誕生之日起就表現出法定主義的特征。比如,英國最早于1623年制定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專利法即《壟斷法規》,1709年制定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著作權法即《安娜女王法令》,其后又于1875年制定了商標法。美國則分別于1790年、1790年、1870年先后制定了著作權法、專利法和商標法。法國分別于1791年、1793年、1857年制定了專利法、著作權法和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商標法。德國分別于1837年、1874年和1877年制定了著作權法、商標法和專利法。日本分別于1884年、1885年、1899年制定了商標法、專利法和著作權法。
專利在英國一開始就表現為君授特權或者是議會法案授予的特權,并沒有像版權那樣發生過是否存在永久專利權的爭論。 [7]即使在深受自然權利影響的美國和法國,自然權利對專利權的影響也非常有限。“在這兩個國家,專利權從一開始就被看做是實在法可以任意設計、限制并最終可以廢棄的權利。” [8]
與專利制度不同的是,版權在英國最終由特權轉化為法定權利則經歷了一個長期爭論的過程。爭論的焦點倒不是作為特權的版權能不能轉化為法定性質的私權,而是作為法定權利的版權在保護期限過后,普通法上的版權是否存在、如果存在能不能作為一種自然權利繼續享有永久性保護的問題。最后爭論的結果是普通法上的永久版權被安娜女王法規定的法定權利所取代。 [9]
上述情況說明,盡管專利權和版權合理性的論證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自然法的理論,但是它們并沒有完全沿著自然權利的軌跡發展,而是由制定法進行了多方面的修正,最終由自然權利轉化為法定權利。
2.洛克勞動理論本身存在的缺陷說明,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客觀上需要制定法進行明確限定。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認為,由于上帝將世界給了全人類所共有,每個人對他的人身擁有所有權,每個人的勞動只屬于他自己,因此當某人將自己的勞動與處于共有狀態的某物結合在一起的時候,也就取得了該物的所有權。但是某人在取得財產權的時候,還必須留有足夠多的同樣好的共有物給其他共有者(充足限制要件),而且任何人不得超過自己所需要的限度取得共有物(浪費限制條件)。 [10]
盡管洛克的勞動理論為包括知識產權在內的財產權提供了一個抽象的權源, [11]但是并不能將洛克勞動理論中所說的勞動作為知識產權直接的、唯一的權源和決定性的因素。康德和盧梭認為,勞動所導致的占有只是事實問題,這種占有事實要變成法律上的權利,還必須有社會公意的承認。 [12]除了將勞動與財產之間的關系過分簡單化之外,洛克財產權勞動理論在作為財產權來源的理論根據時,還存在著一個勞動難以劃分財產權的邊界的問題。格勞秀斯指出,通過占有而產生私人所有權應當具備一個事實上的前提,即占有物必須具備一定的邊界,私人能夠通過自己的物理力量占有它。 [13]格勞秀斯的這個觀點雖然不是針對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的,但無疑揭示出了勞動產生財產權的基本前提條件。一個有形物體本身的邊界無限擴大時,私人要想通過勞動來確定其對這個物體的財產權將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如果說財產權勞動理論在論證有形財產權權源時就存在劃界難題的話,那么對于在沒有實物形態的知識產品上設定的知識產權而言,這種困難就顯得有些空前絕后。知識產品所具有的經濟上的消費和使用上的非排他性、非競爭性以及歷史繼承性,使得某種知識產品被生產出來后,一公開就會脫離生產者個人的控制,勞動再也難以確定其邊界。而且從價值實現的途徑看,知識產品必須依賴于市場,并因此形成具有獨立意義的知識產品市場價值。
從知識產品經濟特征和價值形成途徑出發,德拉霍斯從另一個角度指出,嚴格堅持勞動作為界定知識產權的標準,結果不但不是維護了私人財產權的合法性,反而會使知識產權變成一種集體所有的財產權。原因是“在一個互相依賴的多元社會中,任何個人的勞動都是因他人的勞動而成為可能”。 [14]結果由于知識產品的歷史繼承性,任何一種知識產品都將因為存在無限多的勞動而變成許多人共同所有的財產。當然,洛克勞動理論中含混不清的勞動概念也可能成為知識產權侵權者的合法性理由,從而使知識產權倒退到“過去財產權的黑暗時代”,倒退到“暴徒的神圣權利時代”。 [15]
洛克含混不清的勞動概念不但可能成為“知識海盜”手中的法寶,更有可能成為知識產品生產者手中的利器。既然勞動可以不受任何爭議地產生財產權,知識產品的生產者就可以合理地主張擁有自己知識勞動的所有成果,因為這是一種自然權利。這樣做的后果,按照曲三強教授的話說就是:“如果一種制度是在勞動理論之下運作,可以預期,它的知識產權主要集中在對知識共有物的財產化和占有上”。 [16]
總之,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雖然可以為知識產權的權源提供抽象哲學基礎,但是無論從正反哪個方面看,都必須通過工具主義的制定法對其加以修正。法定主義至少可以對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作出三個方面的修正:一是可以通過確定知識產品的主體能夠控制的行為范圍來確定其權利的范圍,從而滿足知識創造者的財產權利需求;二是可以恰當地處理勞動和資金、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在知識財產分配方面的關系;三是可以利用洛克的兩個條件(充足限制條件和浪費限制條件),比較合理地克服財產權勞動理論本身蘊含的無限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和強度的危險,確保公共利益不受侵害。這深刻說明,僅僅從自然權利的角度出發,僅僅通過勞動來解釋整個財產權制度是片面的、行不通的。 [17]
3.知識產品的經濟特性客觀上需要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知識產品雖然具有私人物品屬性,但更具有公共物品屬性。 [18]知識產品在使用和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和非消耗性。知識產品同時具有擴散性和歷史繼承性。知識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決定了知識產權的主體、客體和權利范圍等重要事項的劃定客觀上都需要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制定法在確定知識產權主體、客體和權利范圍時,既是一個確權和創權的過程,也是一個限權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看,知識產權制度是一種比較標準的制度產品,知識產權也是一種法定壟斷性權利。
知識產品的生產過程則呈現出首效性、風險性和個人性特征。 [19]這三個特征具有重要意義。知識產品生產的首效性意味著一項新的知識產品被生產出來以后,其他所有人的勞動都將成為無效勞動,因為最先的成功者將被作為發現者或首創者永久性地贏得和擁有這項知識的首創權和首創利益,同時也就排斥或剝奪了其他人對這項知識的首創權利。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任何一項新的知識都可能同時有許許多多的人在進行研究和開發,因此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重復研究、開發和無效勞動的現象。那么如何協調這樣一些創造者之間的關系呢?勞動在此是說明不了問題的。因為按照財產權勞動理論,時間上在后成功的創造者同樣應當享有權利。這樣勢必出現在同一個知識產品上存在許多個不同主體的產權不明晰現象。這是經濟學家最忌諱的,也是法律學家所不贊成的。知識產品生產的首效性從實質上看,就是首創者的自由和權利妨礙了后來者的自由,剝奪了后來者的權利。洛克財產權勞動理論雖然存在兩個條件的限制,但是很難適用于知識產品的這種首效性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從工具主義的制定法出發,協調不同創造者之間的自由、權利關系。作為法定主義的制定法首先應當承認首創者的權利,因為這樣既體現了對首創者勞動的尊重,有利于刺激新知識產品的生產,也有利于信息公開,盡量避免重復研究和開發以及資源的浪費。當然,這本身就是對創造者自由的尊重。但是,由于首創者權利的享有排除了他人再享有相同權利的可能性,加上知識產品本身的公共物品特征,因此,制定法也不能將首創者的利益絕對化,否則對后來者同樣的勞動就有失公允。當然由于知識產品具有的使用和消費上的非排他性和傳播上的擴散性,事實上使得制定法也不可能將首創者的利益絕對化。因此制定法在肯定首創者利益的基礎上,也必須對其權利加以保護范圍、合理使用、保護期限等方面的限制,或者通過一些特殊制度的設計,來適當協調首創者和后來者的利益分享關系,比如專利制度中的先用權制度、強制許可制度等。
知識產品生產的風險性、個人性意味著個人的知識生產活動具有巨大的風險性,而知識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則告訴我們,知識產品一旦生產出來并公開以后,全社會都存在免費進行使用和消費的可能性。顯然,知識產品的公共物品屬性和其生產的風險性以及個人性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任何試圖解決這個矛盾的機制都必須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給擔負巨大風險的知識生產者提供足夠的激勵,以保證有足夠多的知識產品被生產出來?二是如何維持知識產品固有的公共物品屬性,以保證整個社會公共利益不受侵害?洛克財產權勞動理論由于存在無限擴大知識產品生產者權利、縮小公有領域知識財富的危險傾向,因此無法用來解決這個矛盾。而如果純粹依靠市場機制,盡管經濟理性人的假設和市場利益的驅動可以保證足夠多的知識產品被生產出來,但是由于沒有相應的保護機制,知識生產者只得借助自力的保密手段來保護自己,這樣將無法保證知識產品的公共屬性,非常不利于知識的擴散和傳播,對整個社會是弊大于利。在此,只有充分發揮知識產權法定主義作為立法原則所具有的創設權利的功能來解決這個矛盾。因為知識產權制定法一方面可以利用經濟學的成果將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權進行配置,以解決創造性激勵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可以根據知識產品的生產特征對它作出嚴格的限制,以解決知識產品作為公共物品供應不足的問題。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知識產品非物質性特征導致的公共物品屬性和生產的首效性、風險性和個人性之間的矛盾,知識產權法盡管堅持了勞動在知識產權保護中的抽象作用,但是并沒有將勞動作為劃定知識產權的直接標準,知識產權的保護并不等同于勞動本身直接的保護,也不簡單等同于經濟效率的保護。知識產權的創設雖然不應當排除勞動和經濟效率的因素,但是平等的創造性的自由等道德價值應當被更多地予以考慮。
4.社會正義問題與知識產權法定主義。知識產品具有的非物質性的特征導致它在使用和消費上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在生產上具有歷史繼承性、首效性,并且這些特征決定了勞動無法作為界分知識產權的具體標準。然而盡管如此,立法者在制定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時,由于創造即自由的前提,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社會整體性效率的假設,又不得不承認勞動在配置知識產權時的抽象作用和基礎作用。這樣一種悖論導致的結果是知識產權的配置和享有盡管從形式上看是正義的,但實質上具有不正義的色彩。其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因為凝結在知識產品中的抽象勞動本身到底有多少,不太容易說清楚;二是知識產品的價值必須通過交換才能體現出來,沒有了市場,沒有了市場交換,幾乎可以說所有的知識產品都一錢不值,而通過勞動創造的價值和通過市場增加的價值之間的確切邊界究竟在哪里很難進行劃定。三是因為知識產品的生產無不利用了現存的公有領域中積累的大量知識財富或者他人依然享有權利的知識財富。在這三個前提下,即使再精明的數學家也很難嚴格區分一個新的知識產品中到底哪些知識是屬于公有領域的或者是他人的,哪些才是屬于個人的勞動創造。在這種兩難境地下,立法者顯然只能主要采取抽象而含混的勞動標準進行權利的配置。因為其他標準的選擇,比如絕對平均主義,結果可能會更壞。在這種明知不可為卻不得不為之的情況下,知識產權的配置和享有自然難以保證其公正性了。就是在這種難以界分的情況下,法律卻將權利賦予了私人,這無論如何難以排除其掠奪公有領域中知識財富或者他人知識財富的嫌疑。又由于知識產品生產的首效性,最先將知識產品生產出來的人享有了該知識帶來的所有利益,從而剝奪了時間上在后的生產者享有權利和利益的可能性,就使得知識產權的持有更加顯得不正義。如果說人類社會存在所有人不得不忍受的不正義制度的話,那就是知識產權制度了。
正是由于知識產權的持有本身帶有很大的不正義色彩,所以必須根據羅爾斯的分配正義原則對知識產權的享有進行再分配。具體的做法是在賦予知識產品生產者權利的同時,也對其權利范圍和內容進行嚴格的限定,以確保公有領域中的知識財富不受過度的侵害。這樣的一種正義我們可以將它稱之為“持有不正義的正義”。它既表明知識產權的持有是一種不得不接受的不正義制度,也說明必須對這種不正義進行改造,使之符合正義。這與目前知識產權立法者以及所有知識產權學者所思考問題的角度正好相反。目前的立法者和學者是這樣看待和思考知識產權問題的:知識產權制度本身是正義的,這種正義的制度存在弊端,所以應該對它加以一定限制,追求所謂的利益平衡。而持有不正義的正義觀恰好相反。它認為,知識產權的持有本身就是不正義的,因而在進行制度設計的時候,就要嚴格控制其權利范圍和內容,以避免這種不正義的制度發揮更大不正義的作用。前者是擴權主義的,而后者可以說是限權主義的。這不僅僅是兩者看問題的角度的不同,而是有著原則和本質區別的。這種區別如果貫徹到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去,將會產生重大不同。比如,在立法活動中,面對任何一種新的知識產權權利訴求,前者首先考慮的是配置這種權利會給社會帶來多少好處,然后考慮的才是其弊端,因此往往輕率地配置權利。而后者堅持經濟效率不能取代人們某些基本的自由和權利,因此首先考慮的是配置這種權利會給社會帶來多少壞處,然后考慮的才是其可能帶來的好處,因而對權利的配置會持更加慎重的態度,對其限制也就會更加嚴格。在司法實踐中,前者導致的一個現象是,法官在遇到模棱兩可的問題時,總是從權利主義的角度出發,傾向于作出有權解釋,并導致嚴重的法官造法現象。而后者在遇到類似問題時,要求法官嚴格從法定主義原則出發對案件作出有利于公共利益的解釋,反對法官造法。也可以說,持有不正義的正義觀是站在人性惡的角度看待問題的。
總之,洛克勞動理論的缺陷、知識產品的經濟特性和社會正義問題要求堅持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并進而堅持整體性知識產權法的觀念。
三、應然選擇:以民法為核心
如前所述,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點并不否認勞動在配置知識產權中的抽象的基礎性作用,它強調的是知識勞動的結果應不應當成為、是否能夠成為知識產權制定法上的權利,必須經過制定法綜合考量所有相關因素后加以必要的選擇。只有經過制定法選擇并且明文規定下來的權利才是知識勞動生產者所能夠享有的權利,制定法沒有選擇并且沒有明文規定的,則是知識勞動者不能享有的權利。正是因為這樣,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主張知識產權立法必須堅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對知識勞動者的成果在法律上的形態應當作出權利和利益的區分,知識產權司法必須堅持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
(一)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的立法選擇
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主張,面對實踐中新出現的某種知識產品的保護問題,首先必須充分利用現有知識產權制定法資源來加以解決,反對動不動就通過立法來為該知識產品(如域名、數據庫)創設某種新的知識產權的現象。知識產權的創設涉及復雜的利益關系,特別是關系到公共利益,因此必須堅持十分慎重的態度。在沒有充分把握確認創設某種新的知識產權種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可能出現的后果時,最好不要輕易地加以創設,而毋寧將它作為一種利益,留給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來保護,或者干脆留給公共領域。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認為,在創設某種新的知識產權種類時,必須綜合加以考量的因素包括:
平等的創造自由問題。即創設某種知識產權能否保證每個人能夠享有平等的創造自由?如果不能保證,那么,應當通過什么機制來保障平等的創造自由受到侵害的人的利益?
有或者沒有這種知識產權會給社會帶來多少壞處?這里面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如成本與個人效率和整個社會效益的關系問題、公有知識財富的維持和保養問題,等等。
市場上是否存在相關替代品?這里包括兩個因素:一個是市場本身的作用,另一個是是否存在其他替代性保護機制? [20]
在綜合考量了這些因素后,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認為,創設一種新的知識產權的必要性包括如下幾點:(1)某種新知識產權的設置不侵害他人平等的創造自由或者在侵害了他人平等的創造自由后具有相應的恢復或者補償機制;(2)缺少這種知識產權對自由的創造和社會公共利益都會產生重大傷害;(3)有了這種權利既不會對公共利益造成危害同時又有利于社會整體效益;(4)市場上不存在替代性機制同時權利的運行成本大大小于權利的保護收益。總體上來說,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認為立法者應當按照平等地創造自由—社會整體利益—社會正義這樣一個前后相依的基礎模式來創設知識產權。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社會大眾廣泛地參與和聽證程序必不可少,因此必須堅決杜絕現在普遍存在的那種所謂專家躲在書齋里盲目造法的現象。
(二)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對權利和利益的界分
權利和利益本身的界定是法理學領域中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課題,這里不去涉及。就本文的旨趣而言,權利是指知識產權制定法亦即知識產權特別法明文規定的權利,包括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植物新品種權、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權等。利益則是指知識產權特別法以外的其他法律規定的某些沒有確定內容的知識性利益,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明文規定加以保護的某些市場先行利益,如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商業秘密、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知名的企業名稱和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所保護的商品表示、商品形態、域名、數據庫、商業秘密,等等。二是反不正當競爭法沒有明文規定,但是由于知識勞動者付出了足夠的勞動或者投資,其產品符合社會需要,因而應當禁止“搭便車”的行為,應當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基本原則或者民法關于不法行為的規定加以保護的某些利益。
權利和利益的界分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權利是知識產權特別法的制定者以勞動作為抽象的基礎,在綜合考量了自由、社會整體效率和社會正義之后進行選擇的結果。利益同樣是立法者在綜合考量了自由、社會整體效率和社會正義之后,認為沒有必要通過知識產權特別法加以保護但有必要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加以保護的結果。由此有必要糾正一些知識產權領域中流行而錯誤的觀念,如域名權的法律保護、數據庫特殊權利的法律保護,等等。盡管從立法論的角度即從應然的角度可以認為應當為域名的擁有者、數據庫的制作者創設某種權利,但是在沒有創設權利之前,就不能將之稱為域名權、數據庫特殊權利,而只能稱為域名、數據庫,或者域名擁有者的利益、數據庫制作者的利益。從司法的角度看,如果具體案件中的原告以自己所謂的域名權、數據庫特殊權利等知識產權特別法根本就沒有明確規定的權利受到侵害為由,并且根據知識產權特別法提起訴訟,法官理所當然應當判決原告敗訴。從實務上看,電視節目時間預告表、 [21]電話號碼簿等數據庫侵害案件,原告往往以著作權受到侵害為由來起訴被告。由于電視節目時間預告表、電話號碼簿等數據庫絕大多數沒有著作物性,因此不能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在這種情況下,審理案件的法官就不能行使所謂的自由裁量權,在著作權法之外主動為原告創設某種知識產權。當然,如果原告主動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或者民法的有關規定提起訴訟,并且要求保護的是某種財產性利益而不是權利,則法官應當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 [22]
界分權利和利益的意義不僅僅在于為具體案件中的原告提供訴訟策略、為法官審理案件提供思維方法上的指導,更為重要的是對民法提出了這樣的一個任務,即在為法利益的享有者創設請求權時,必須區分物權請求權和債權請求權,賦予利益享有者的應當是一種債權請求權而非物權請求權。
(三)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和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
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對知識產權立法提出的要求、對權利和利益進行界分的主張,進一步對知識產權司法提出了應當堅持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觀念的要求。
所謂整體性知識產權法,是指從司法的角度看,知識產權法是一個整體,既包括人們通常所說的知識產權特別法——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植物新品種法、集成電路布圖設計法,也包括反不正當競爭法,還包括民法。知識產權特別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民法三者之間的關系應當是特別法—普通法(特別法)—普通法的關系。其中知識產權特別法與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之間是特別法和普通法的關系,反不正當競爭法相對于民法來說又是特別法和普通法的關系。根據特別法和普通法適用關系的原理,凡是專利法等特別法有規定的,應當優先適用專利法等特別法的規定。只有專利法等特別法沒有規定的,才能適用作為普通法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而在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時,反不正當競爭法有規定的,則應當優先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規定。只有當知識產權特別法、反不正當競爭法都無法適用時,才能適用民法的規定。 [23]可見,反不正當競爭法并不是知識產權(包括知識利益)的兜底保護法,民法,只有民法才是知識產權(包括知識利益)的兜底保護法。
我國知識產權法學界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是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法,這完全是一種無視民法存在的觀點。其實,不但知識產權特別法來源于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也來源于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最初誕生于19世紀的歐洲,當時法國法官為了保護誠實的商人,創造性地將1804年的《拿破侖民法典》第1382條和第1383條中關于侵權法的一般規定用于制止經濟生活中的不正當行為,后來才逐漸發展而成為一項獨立的法律制度,即反不正當競爭法律制度。 [24]為了讓司法者能夠正確適用法律處理案件,現在是徹底糾正對知識產權特別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民法關系錯誤認識的時候了。
整體性的知識產權法觀念不但要求將民法作為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法,而且要求在適用知識產權特別法時,應當特別注意各個特別法調整功能的不同,充分發揮各個特別法獨特的作用,而不能混淆它們之間的界限。但是,為了避免知識產權演變成一種和物權沒有任何區別的私權利而與知識產權創設的宗旨背道而馳、混淆知識產權作為無形財產權和有形財產權的區別,民法只能作為最后的適用手段。而且觀念上應當明確,即使適用民法,也并不意味著原告享有知識產權特別法上的某種權利,此時民法保護的只是某種市場先行利益。更為重要的是,此時的利益享有者所享有的只是一種債權請求權而非物權請求權。 [25]
從整體上看,知識產權特別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民法的適用關系中還必須注意的一點是,知識產權特別法明確禁止保護的或者已經過了保護期限的,也就不再存在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的可能性。 [26]也就是說,只有知識產權特別法不禁止的,也就是在知識產權特別法上地位模糊但是知識勞動者又付出了足夠的知識性勞動或者投資的知識產品才有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加以保護的可能性。
區分知識性權利和知識性利益,理順民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知識產權特別法之間的關系,是我國知識產權法學界目前面臨的一個重大任務。
四、對民法的制度訴求:針對侵犯知識財產利益的不法行為創設債權請求權
怎樣將民法的母法地位和兜底保護貫徹到知識產權保護制度中,真正建立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需要民法學者和知識產權法學者攜手進行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目前的困境在于我國現有知識產權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根本缺失民法觀念或者忽視民法在知識產權制度中的基礎地位,沒有認真去研究知識產權法和民法的關系,沒有自覺利用或者沒有很好地利用民法中的契約、侵權行為、不當得利等基本制度,并且形成了既有的封閉而自足的立法格局和觀念。這種封閉和自足現象的一個突出反映是有的學者鼓吹現代知識產權制度已經進入了所謂的法典化時代,因此我國應當制定知識產權法典。 [27]在根本沒有厘清知識產權法和民法的基本關系、在知識產權基礎理論研究還十分薄弱、在連制定民法典的條件都沒有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宣稱知識產權已經進入法典化時代、我國應當制定知識產權法典,只會成為一個微風一吹就立即破滅的美麗的泡影。
就本文的主旨而言,樹立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觀念、建立以民法為核心的整體性知識產權法制度、對知識勞動者財產利益的保護區分權利和利益的不同形式,從立法論的角度看,對民法提出的迫切訴求是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以下簡稱《民法通則》)第5條相配套的不法行為責任制度。
《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顯然,《民法通則》將保護的對象進行了權利和利益的區分,知識產權特別法沒有創設為權利的知識性利益也應當在《民法通則》的保護范圍內。問題在于,對這些知識性利益的保護,是否也能夠像知識產權特別法規定的權利一樣,既授予被侵害者請求損害賠償的債權請求權,也授予被侵害者請求停止侵權行為的物權請求權?這個問題如果不加以區分,就會使知識性利益的保護演變為知識性權利的保護。從邏輯上分析,從《民法通則》第5條的規定中當然得不出請求權不加區分的結論,否則《民法通則》第5條就沒有必要對權利和利益進行區分。從知識產權法的角度看,如果不對權利被侵害者和利益被侵害者的請求權加以區分的話,知識產權立法者根本就沒有必要對保護的對象進行立法選擇,而直接根據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將一切知識性勞動的成果都規定為權利進行保護就可以了。這種無限擴大知識產權保護范圍的做法當然是行不通的。因此,知識產權法制度中對權利和利益進行區分保護是非常必要的。具體來說,對于權利的保護,法律既應當賦予享有者請求停止侵權行為的物權性質的請求權,又應當授予享有者請求損害賠償的債權性質的請求權。而對于利益的保護,只要授予享有者請求損害賠償的債權性質的請求權就可以達到保護的目的,沒有必要授予享有者物權性質的請求權。由于知識產權特別法從其立法宗旨來說,保護的只能是權利,因此,知識性利益的保護只能交給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進行。這就要求作為母法的民法應當建立與權利和利益保護相匹配的不法行為責任制度。
我國民法究竟如何建立與權利和利益的保護相匹配的不法行為責任制度(從權利或者利益享有者的角度看,就是請求權制度),筆者認為可以借鑒《日本民法典》的有益經驗。《日本民法典》第5章所使用的“不法行為”的概念,其含義要廣于《民法通則》第6章第3節“侵權的民事責任”中的“侵權”概念,包括不法的侵害權利的行為和不法的侵害他人利益的行為。相比之下,《日本民法典》中所使用的“不法行為”的概念顯然要比《民法通則》中所使用的“侵權”概念科學、準確和全面。從《民法通則》第6章第1節的“一般規定”和第3節的“侵權的民事責任”的規定看,《民法通則》所使用的“侵權”概念明顯沒有包括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為。從立法論的角度看,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在規定不法行為的民事責任時,應當借鑒《日本民法典》第5章所使用的“不法行為”的概念,與《民法通則》第5條的規定相適應,將利益也涵蓋到不法行為侵害的對象中去。
從具體的立法技術上看,《日本民法典》第5章第709條只是規定了行為人因為故意或者過失侵害他人權利或者合法利益的行為應當承擔損害賠償責任,而沒有規定行為人應當停止侵權的責任,但這絲毫不說明在日本侵害權利的行為不應當承擔停止侵權行為的責任。理由在于:《日本民法典》只是作出一個最基本的規定,侵害某種具體權利的不法行為的責任,包括停止侵權行為的責任都規定在了各個特別法當中。根據特別法和普通法適用關系的一般原理,一旦發生某種侵害權利的不法行為,應當優先適用特別法的規定,不法行為人必須根據各個特別法的規定承擔停止侵權行為的責任。《日本民法典》這樣規定的好處是,一旦發生了各個特別法沒有規定的針對某種利益的不法侵害行為,被侵害者就可以直接利用其第709條的規定請求損害賠償。這樣就將利益的保護和權利的保護無形當中進行了區別對待,利益的享有者所能夠享有的,也就只能是債權請求權性質的損害賠償請求權。從日本知識產權的裁判實務上看,裁判所總是力求在知識產權特別法和不正當競爭防止法的范圍內解決有關爭端,因此很少利用《日本民法典》第709條的規定來處理相關案件。但是也發生過這樣的案例。如在一個關于簡短的新聞標題的侵害案件中,被告沒有經過原告同意,直接大量復制原告的新聞標題在網絡上進行。由于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沒有基本原則的規定,原告只能依據著作權法和《日本民法典》第709條的規定起訴被告。裁判所在否定了這些新聞標題的著作物性之后認為,原告對自己的勞動和投資行為享有民法上的合法權益,被告未經原告同意的復制和使用行為侵害了原告的合法利益,構成《日本民法典》第709條規定的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不法行為,因此判決被告賠償原告的經濟損失。 [28]
如上所述,《民法通則》第5條雖然規定了受民法保護的對象包括權利和利益,但是在其第6章規定民事責任時,卻明確使用“侵權”的概念,沒有能夠將侵害他人合法利益的行為包括進去。同時,從責任形式上看,由于忽略了侵害他人利益的不法行為,因此第6章也只規定了侵權行為承擔責任的方式,而沒有規定侵害利益的行為應當承擔責任的方式,這樣就使得合法利益的保護落了空。當然,也許會有人認為,既然《民法通則》第5條規定了合法利益應當受到保護,那么在發生侵害知識產權特別法沒有規定或者不能適用知識產權特別法規定的利益時,就可以直接通過選擇適用《民法通則》第134條的規定,追究行為人的損害賠償責任。但是,由于民事責任方式的選擇權在原告而不是法院,既然《民法通則》規定了停止侵害、賠償損失等責任方式,而且這些責任方式可以合并使用,原告自然會既選擇要求賠償損失又選擇要求停止侵害。這樣的話,利益的享有者事實上就會享有和權利的享有者一樣的請求人的地位,從而使知識性利益轉化為知識性權利。由此從立法技術上看,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在規定不法行為的責任時,應當借鑒《日本民法典》第5章第709條的規定,創設一個既保護權利又保護利益的明確條款。
總之,知識產權法定主義的觀念和整體性知識產權法的觀念要求我國未來的民法典制訂者轉變思路,在不法行為的內涵和責任方面借鑒《日本民法典》的有益經驗,只授予利益的享有者債權性質的請求權,以區別知識性權利和知識性利益的不同法律后果,使知識產權法真正形成以民法為核心的一個完整的保護體系。
注釋:
[1]筆者受聘在日本北海道大學COE擔任研究員期間,比較系統地研究了日本的知識產權法,并且參加了各種有美國、德國學者參加的知識產權法國際學術會議。在研究和參加會議的過程中,筆者發現,日本、美國、德國學者根本就沒有提及過中國知識產權法學者的觀點,并且很少提及中國知識產權法律。就研究問題的深度和廣度看,我國知識產權法學界總體上落后很多。這里面的原因除了美國、德國、日本學者幾乎沒有人懂中文、我國知識產權制度建立和理論研究起步都比較晚之外,主要原因還在于我國知識產權法學者大多缺少深厚的民法功底和法理學功底。
[2]比如,在我國關于知識產權法的教科書和專著不下幾百種,但是幾乎沒有看到過哪本教材或者專著中提及過民法和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問題。而在日本的同類知識產權法著作中,在總論部分絕大多數都會談到民法和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參見[日]中山信弘:《工業所有權法(上)》第2版增補版,弘文堂2000年版;高林龍:《標準特許法》第2版,有斐閣2005年版;《半田正夫紀念文集民法和著作權的諸問題》,法學書院1993年版,等等。
[3]代表性的觀點,參見鄭成思:《完善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制度》,《工商行政管理》1998年第23期;鄭成思:《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頁;韋之:《論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薛虹:《網絡時代的知識產權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頁;楊明:《試論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知識產權的兜底保護》,《法商研究》2003年第3期。
[4]參見梁慧星:《電視節目預告表的法律保護和利益衡量》,《法學研究》1995年第2期;易繼明:《知識產權的觀念:類型化及法律適用》,《法學研究》2005年第3期。
[5]參見鄭勝利:《論知識產權法定主義》,載鄭勝利主編:《北大知識產權評論》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朱理:《知識產權法定主義——一種新的認知模式》,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李揚:《知識產權法定主義及其適用——兼與梁慧星、易繼明教授商榷》,《法學研究》2006年第2期。
[6]知識產權工具主義觀念是澳大利亞學者德拉霍斯提出的。該種觀念的核心是反對洛克財產權勞動理論和知識產權財產權主義的主張,認為知識產權不過是政策考量的產物。知識產權工具主義以偏愛公共利益為特色。但是,由于該種理論完全拋棄了洛克勞動理論的合理因素,使知識產權完全變成了一個政策考量的工具,存在一種否定知識產權的傾向,因此也不可取。See Peter.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
[7] See Peter.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29.
[8] See Peter.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29.
[9] See Ronan Deazley,On the Origin of the Right to Copy,Part7,Hart Publishing,2004.
[10]參見 [英]洛克:《政府論》(下篇),葉啟芳、瞿菊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9-20頁。
[11] See C.B.Macpherson,The Political Theory of Possessive Inpidualism,Oxford,1979,pp.209-220.
[12]參見[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淑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55頁;[法]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紅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頁。
[13] See H.Grotius,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1625;F.W.Kelsey Tr.,New York,Lodon,1964),II,2,3.
[14] Peter.Drahos,A Philosophy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Dartmouth,1996,p.52.
[15] See Ejan Mackaay,The Economics of Emergent Property Rights on the Internet,P.Bernt Hugenhoitz(ed.),Kluuer Law International,1996,p.13.
[16]參見曲三強:《傳統財產權理論與知識產權觀念》,載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編:《中國高校知識產權研究會第10屆年會論文集(2002)》,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33頁。
[17]為什么洛克的財產權勞動理論在解釋知識產權制度時會出現問題呢?除了上述已論證的原因外,還和時代背景的限制有關。洛克所處的時代,還是一個有形財產居絕對地位的時代,知識產權現象雖早已產生,但從立法上看,世界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著作權法——《安娜女王法令》——出現于1709年,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專利法——英國的《壟斷法規》——出現于1623年,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商標法——《法國商標法》——出現于1857年,而洛克出生于1632年,卒于1704年,這種狀況說明在洛克的有生之年,知識產權尚未在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據主導地位,知識產權問題還沒有成為引起人們足夠重視的問題。因此,洛克只可能以有形的物質世界作為他財產權勞動理論的邏輯起點,對知識產權問題還不能主動進行系統思考,所以他的財產權勞動理論不能充分解釋復雜多變的以無形的知識產品為客體的知識產權現象是在所難免的。
[18]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的劃分,參見[美]羅伯特考特、托馬斯尤倫:《法和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46-147頁。
[19]參見杜月升:《論知識生產及其經濟特征》,《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2期。
[20]朱理博士在分析知識產權創設的時候,提出了立法者應當考量的四個因素,即:“該權利的設定和行使的成本是否小于該權利所帶來的社會收益?沒有這種新權利是否會阻礙智力成果的創造?市場上是否存在該權利的替代品以至于該權利的設定變得沒有必要?新權利的設定是否侵害了社會公眾的傳統公有領域?”顯然,朱理博士在這里沒有進行排序,也沒有區分自由和效率的關系。也正因此,筆者拋棄了他的這幾個因素。參見李揚等:《知識產權基礎理論和前沿問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
[21]比如,發生在我國廣西的“《廣西廣播電視報》訴《廣西煤礦工人報》”一案。詳細案情參見WWW.zhinazhen.net/bbs/dispbbs.asp?boardid=8did=3993.
[22]從這個角度看,梁慧星教授在評論“《廣西廣播電視報》訴《廣西煤礦工人報》”一案時所得出的一個方面的結論,即《廣西廣播電視報》的合法利益應當受到保護的觀點還是非常正確的。參見梁慧星:《電視節目預告表的法律保護和利益衡量》,《法學研究》1995年第2期。
[23]需要指出的是,法律適用是從司法的角度來進行說明的。就具體案件中的當事人來說,他當然可以自由選擇,但是一旦選擇,就必須承擔這種選擇在訴訟上的后果。
[24]參見韋之:《論不正當競爭法與知識產權法的關系》,《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6期。
[25]在日本的知識產權理論界和司法實務界,一般不會利用《日本民法典》第709條規定的不法行為來分析和處理相關知識產權案件。因此,學者和法官總是尋求在知識產權特別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的范圍內分析和解決問題。即使到了萬不得已適用《日本民法典》第709條關于不法行為的規定時,按照這條規定,原告也不得享有物權請求權,而只享有損害賠償請求權即債權請求權。但是在我國,即使法官最后選擇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5條和第118條的規定,也沒有將這兩種請求權分開,即關于知識產權權益的侵害,不管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權益人都擁有物權請求權。這樣的一種處理方式過于簡單,沒有考慮到在知識產品上設置的權益和有形財產權的區別,從立法論的角度看有待于修正。
[26]但是注冊商標權保護期滿后,如果原商標權人繼續將該商標作為未注冊商標使用,則存在利用先用權保護以及反不正當競爭法和民法保護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