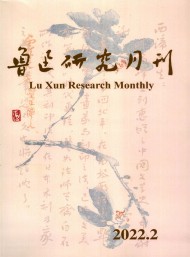魯迅的小說范文
時間:2023-03-28 09:13:3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魯迅的小說,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引言
語言是不斷發展的,語言的內部因素使語言的發展呈現漸進性,而外部因素作用于語言的內部因素會使語言產生突變性的變革。近代中國的落后挨打使先進的知識分子不再固步自封,他們開始開眼看世界。五四時期,面對文言文幾千年來積累下的陳腐、僵化,舊白話文的少而不精,他們不再抱殘守缺,轉而學習、吸收西方語言中精確的語法表達來完善新白話文。魯迅作為的主將、“漢語歐化以自救”的提倡者和踐行者之一,他的作品中的歐化語法現象很是典型。本文選取魯迅小說中的歐化句法加以分析以求為魯迅研究提供新的視角。
首先我們需要確定“歐化”的概念所指,“歐化”概念的界定并不明確,大致說來有寬窄兩種理解。狹窄的理解是把語法上的歐化限定在對印歐語語法結構的移植,即限定在漢語原本沒有、且完全出自于對印歐語語法格式的仿造而產生的語法結構形式上。寬泛的理解則把主要是在印歐語影響下產生的語法現象都歸入歐化,既包括漢語原本沒有,完全是由于對印歐語語法結構的模仿而出現的新興語法形式,即狹義的歐化語法,也包括漢語原本雖有,但只是在印歐語的影響下才得以充分發展的語法形式。本文采用的是寬泛的定義。
根據前人在歐化句法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文將歐化句法的表現總結為以下四類:
1.插入語使用的變化
所謂插入語,通常指的是句子中插入一些與整個句子語義關聯不大但可以增強這個句子感彩的話語。漢語本來的插入語往往是插入一兩句不相干的話,且插入語省略后不影響這個句子的語義。
2.語序的變化
蕭立明說過,曲折性越弱的語言,語序在句子中的作用就越重要。漢語作為孤立語強調的是意合,通常依據語義和語句間的邏輯關系來實現上下文的連貫,因此語序在漢語語義的實現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覷。在漢語傳統中通常定語位于中心語的前面,賓語位于謂詞的后面;在復句中,尤其是條件復句和讓步復句中,通常從屬分句在前,主要分句在后。而歐化語言多屬于曲折性語言,注重語言形式上的銜接,語序卻相對靈活。受歐化影響現代漢語定語和中心語、賓語和謂語、主句和從句的位置變得較為靈活。
3.句子長度的變化
漢語屬于意合性語言,較少使用連接詞形成的長句而往往采用簡潔的短句,句子之間跳躍性很大,句子成分能省則省。古漢語的特點是簡練但不精確。而通過連接詞形成長句是英語的一大特點。像現代漢語文章里的句子越來越長、長句越來越多,長定語、長賓語、長謂語的出現顯然是歐化的結果。
4.標志詞使用的變化
漢語屬于意合性語言,“意合”是指句子中的語法關系和語法意義不用外部標識顯明,而需要通過語義和邏輯關系以及語境來體會。所以在漢語傳統中標志詞使用并不頻繁,而印歐語言是曲折性語言,通常通過介詞、連詞等形式標志來連接。漢語受歐化影響,標志詞使用的頻率有了顯著增加,使用范圍也得到擴展。比較明顯的是,被字句“被”和判斷句“是”在現代漢語中的使用。
歐化句法的表現大體上可以分為以上四類,但在具體作家作品中的表現卻不盡相同。所以本文將分析歐化句法現象在魯迅小說中的具體體現以及對作品語言風格的影響。首先,本文將對魯迅小說的歐化句法的表現進行類型分析。
二、魯迅小說的歐化句法的類型
根據以上歐化句法的四種表現,魯迅小說的歐化句式大致可分為以下六種類型:
(一)插入語的使用的變化
插入語在某種意義上起的是限制范圍、精確表達和補充說明的作用。漢語中本有插入語,如《紅樓夢》“倒是這個和尚道人,阿彌陀佛,才是救寶玉的命的”。但舊白話文往往插入一兩句不相干的話。魯迅小說中的插入語卻不是這樣。如:
(1)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么可怕,也沒有這么兇。(《狂人日記》)
(2)于是我自己解釋說:故鄉本就如此——雖然沒有進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涼,這只是我自己的心情改變罷了,因為我這次回鄉,本沒有什么好心緒。(《故鄉》)
句(1)對“他們”進行精確的范圍的限定,“他們”指的是一群弱肉強食社會中的被人欺凌的弱勢群體,他們的恨該指向的是知縣、紳士、衙役、債主。這與后面的對“我”更兇的臉色形成反差,體現的是匡時救世的知識分子的情感的失落。所以,句(1)的插入語起到很好的注釋補充說明的作用。
句(2)插入語對“故鄉”進行注釋說明,它沒有什么進步,但也沒作者所感知的悲涼,作者把悲涼歸因于自己的情緒。這只是作者自我慰藉之語罷了,字句之間透出的是深深的失望。作者對故鄉的復雜情感則是通過這個插入語表現出來的。
所以,魯迅作品中的插入語多起補充說明的作用,使句子的意義表達得更加具體明白,而這一用法在舊白話文中很少見。
(二)定語、賓語易位現象
漢語與印歐語言一個很大的句法區別就是漢語的語序除了極少數情況,大多語序是固定的,如:定語位于中心語的前面,賓語位于謂詞的后面。但印歐語言中的賓語、定語的位置較為靈活,可在前也可在后。五四時期受歐化句法的影響開始出現定語、賓語易位的現象。在魯迅小說中這種句法現象就很普遍,如:
(3)他們似乎別有心思,我全猜不出。(《狂人日記》)
(4)現在我聽見的故事清楚起來了,美麗,優雅,有趣,而且分明。(《好的故事》)
句(3)是賓語前置的歐化現象。“猜”的賓語是“他們的心思”,正常語序應該是“我全猜不出他們的心思”。而在句中賓語卻前置于句首,起到了突出強調的效果,強調的是“他們”的心機。
句(4)是定語后置的歐化現象。“故事”的定語“美麗、優雅、有趣,而且分明”后置于句尾。這種用法可以平衡句子結構,同樣有突出的作用。
所以,魯迅小說的定語、賓語易位的歐化句法現象,起到的是突出強調的作用。
(三)長定語、長賓語、長謂語的出現
漢語是意合語言,往往采用簡練、短小的句子。受歐化句法的影響,句子延長,由連接詞連接形成長句。所以出現了長定語、長賓語、長謂語的歐化句法現象。首先,本文先介紹長定語現象:
王力先生曾指出:“歐化句法的顯著特點之一是定語越來越長”。長定語的歐化句法現象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如下:
(5)我這回在魯鎮所見的人們中,改變之大,可以說無過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頭發,即今已經全白,全不像四十上下的人;臉上瘦削不堪,黃中帶黑,而且消盡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是木刻似的;只有一個眼珠間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祝福》)
句(5)描述祥林嫂頭發、臉、眼睛的三個從句,構成修飾“她”的三重定語。這種長定語是漢語句法受歐化影響的典型實例。
接著,本文將介紹長謂語現象,長謂語一般有兩種情況:
第一,動詞前面連用兩個以上助動詞。在印歐語言中,能愿動詞可以充當助動詞,也就形成了兩個以上助動詞共同支配一個動詞的長謂語現象。這一歐化句法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如下:
(6)倘使插了草本到廟市去出賣,也許能得幾文錢罷,然而我們都不能,也不愿這樣做。(《傷逝》)
句(6)中“不能”和“不愿”兩個助動詞一同修飾“做”這個動詞,形成長謂語結構。
第二,兩個以上的動詞共同支配一個賓語。這一現象先秦就已經出現了,如“宋女至而好,魯公奪而自妻之”,但在舊白話文中只是偶有出現,一直到五四時期受印歐文學直譯作品的影響這一用法才興盛起來。這一歐化句法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如下:
(7)普國有個算數家,說要觀察研究實地,對月球開一條通路。(《月界旅行》)
例(7)中“觀察”和“研究”兩個動詞支配同一賓語“實地”。這種歐化的句法在現代漢語中使用已很廣泛。
王力先生在《漢語語法史》中闡述了這一句法格式,他把這種結構叫做“共動和共賓”,即平行的能愿動詞共同支配一個動語(共動)和兩個以上的動詞共同支配一個賓語(共賓)。所以,根據王力先生的理論,長謂語現象又可以分為,共動和共賓兩種現象。而在魯迅小說中的實例(6)呈現便是共動的歐化句法現象,實例(7)便是共賓的歐化句法現象。
最后,本文將介紹長賓語現象。長賓語現象是指句子具有多個賓語的語法現象。漢語傳統講究簡練,所以,長賓語現象并不常見,但受五四時期歐化的影響,長賓語的句法現象開始出現得頻繁起來。這一句法現象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如下:
(8)屋子和讀者漸漸消失了,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士兵,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豐中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杰,講臺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子君——不在近旁。(《傷逝》)
例(8)中的賓語有“漁夫”“士兵”“貴人”“投機家”“豪杰”“教授”“偷兒”七個并列賓語,這是長賓語很典型的實例。這一長賓語的使用是為和后文形成對比,突出的是后文中子君的離開。
(四)主從復合句的語序變化
復合句包括主從復合句和并列復合句兩種。因為并列復句無主次之分,也就沒有語序問題。所以,復句的語序問題也就是主從復合句的語序問題。在文言文和舊白話文中除非是特殊用法,主從復合句一般都是從句在前主句在后。但五四后,從句的位置變得靈活了,可前可后。而且從句后置的句法現象也增多了。在魯迅小說中我們可以發現很多從句后置的句法現象,這明顯是受印歐句法的影響形成的歐化句法。如:
(9)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驅除的,因為這于我太痛苦。(《自序》)
例(9)是一個因果復句,按照漢語的傳統,原因從句在前,結果主句在后。而在這一實例中主句的結果主句提前,原因從句后置。這是漢語歐化句法語序靈活的表現。同時,這一用法起到突出強調的效果。
(五)“被”字句的發展
被動句分為有標志的被動句(有被動詞)和無標志的被動句(無被動詞)。“被”字句屬于有標志的被動句。“被”字句古已有之,受五四時期歐化句法的影響,這一用法得到了發展。具體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其一,“被”字句語義色彩的變化;
在文言文和舊白話文中“被”字句多用于消極義,這表明漢語傳統是一般都表達消極義。但五四之后,這一限制得到了消解,用于積極義和中性義的比重得到了增加。受印歐語法被動句也可表示期望或如意的事的影響,漸漸地不受傳統句法的約束,靈活地運用被動句于積極或中性的語義中。在魯迅小說中的表現如下:
(10)老頭子和大哥,都失了色,被我這勇氣正氣鎮壓住了。(《狂人日記》)
“老頭子和大哥”是“吃人的人”被“我”這個覺醒的人鎮住,這是好的有意義的事物壓住不好的事物具有積極義,這種語義環境下使用“被”是“被”語義色彩的發展,這是歐化句法的典型表現。
其二,“被”字句使用頻率的增加。
漢語傳統中,被動句的使用由于受語體的限制,有標志的被動句的使用頻率并不高。但在印歐語言中,由于被動句不受語體限制而且印歐語言重形式,所以,有標志的被動句使用率很高。由于受印歐語言的影響,五四以后“被”字句使用的頻率明顯增加。
在漢語中可意會的被動可以使用無標識的被動句,但五四以后往往要再加上一個標志詞“被”字如:在“NP1+是+NP2+VP+的”的結構中,如果NP2所表示的事物是有生命的或有行為能力的,NP1是受事主語,句中的被動關系是可以意會的。像“自行車是他修的”,但魯迅的小說中卻喜歡多加一個標志詞“被”,如:
(11)妹子是被大哥吃了,母親知道沒有。(《狂人日記》)
句(11)表明受歐化的影響,漢語由重意會向重形式轉變。“被”字使用頻率的增加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六)判斷句中“是”的使用頻率的增加
判斷句,是根據謂語的性質給句子分類得出的一種句型,一般是用名詞或名詞性詞組作謂語,對事物的屬性作出判斷,即說明某事物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在文言文中,判斷句不使用判斷詞,直接判斷,或者用“者”“也”表判斷。否定判斷用“非”,漢語句子的謂語既可以是動詞性成分,也可以是形容詞或名詞性成分;而印歐語法中的謂詞必須由動詞或動詞短語擔任。英漢翻譯中的系動詞往往翻譯成“是”,于是,“是”從表示判斷或是強調作用的標志變成英語be一樣的必需的普遍形式。魯迅小說中大量使用了判斷詞“是”。
(12)我曉得他們的方法,直接殺了,是不肯的,而且也不敢,怕有禍祟。(《狂人日記》)
(13)她的體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為了忘卻的紀念》)
句(12)的用法現代漢語已屬少見,而(13)“是”顯得多余,已被現代漢語淘汰。
以上是魯迅小說的歐化句法的六種類型。不同的句法會促成不同語言風格的形成。下面本文將探討歐化句法對魯迅小說語言風格的影響。
三、魯迅小說的歐化句法和語言風格
作品的風格是指作家所創的眾多文學作品中,內容及形式上所表現出的穩定的獨特性。一個作家語言風格的形成離不開兩種因素:外部因素和內部因素,其中外部因素包括時代、環境、歷史等因素,而內部因素作家的氣質、思想、藝術修養等方面,而外部因素通過內部因素起作用。五四時期是一個激烈的變革的時期,而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承擔著兩個任務,即:廢除文言文,改革白話文。由于五四時期是改革的初始時期,所以,五四時期的作品呈現的是文白交雜、中西交會的過渡性特點。魯迅先生支持歐化句法以實現白話文的改革,所以,魯迅“雖然主張歐化,卻又使歐化得合語言的自然”,形成了自己獨到的成熟的語言風格。
(一)精確性
魯迅先生支持歐化的原因是想借印歐語言嚴密的語法補漢語表達含混的不足。魯迅先生的小說大量采用了歐化句法,比如:起補充說明作用的插入語完善了整個句子的意義表達;長定語、長賓語、長謂語使整個句子的信息量更為充足;形式標志詞的大量使用使句子意義更加一目了然……總之,魯迅先生的小說較之于中國傳統的小說信息量更為充足,句子跳躍性更小,小說的主題得到更為明確和精確的表述。
(二)新穎性
魯迅先生的小說采用不同于傳統小說的文白交雜、夾雜歐化語法的獨特語言風格,對于當時的讀者這是新鮮的。對于改造國民性的主題的表達,這種語言形式是具獨創精神的、是成功的。但由于不符合傳統漢語的表達習慣以及與現代漢語的表達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導致魯迅先生的小說晦澀難懂。
四、結語
從歐化句法的角度研究魯迅小說有利于從語法角度解讀分析魯迅小說的文學語言的使用規則。追根溯源,參照歐化句法能更好的理解魯迅作品獨特的語言風格,為魯迅研究打開一個全新的角度。
參考文獻:
[1]劉復.中國文法通論[M].北京:中華書局,1939.
[2]魯迅.魯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3]魯迅.魯迅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4]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5]黎運漢.邁入21世紀的修辭學研究[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1.
[6]賀陽.現代漢語歐化語法現象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
[7]王力.現代漢語語法[J].北京:商務印書館,1943,(1).
[8]朱自清.文學的標準與尺度[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9]朱自清.王力《中國現代語法》序[J].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
[10]錢鐘書.錢鐘書散文[M].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7.
[11]呂叔湘.劉堅《近代漢語讀本》序[J].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
篇2
魯迅先生的小說突出地體現了這種悲劇意味。他在《狂人日記》中寫到: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幾千年的中國演繹著吃人的悲劇史。“我吃了妹子的幾片肉,現在也輪到我了”,“狂人”的恐懼引起我們的恐懼,引起我們對歷史的反思。祥林嫂死在祝福的大年夜,革命者夏瑜的鮮血成為華小栓治病的藥,魏連殳從窮愁潦倒到墮落,再至死亡,阿Q不明不白地被當作“革命者”槍殺,單四嫂子的小寶病死… …這些悲劇主人公不一定具有十分的美德,不一定十分的公正,但他們卻遭受著不幸失敗和死亡。魯迅特別地突出了“死”這一主題,加深了小說的悲劇性,在對他們命運的憐憫中引起我們的不安和恐懼。
魯迅小說中人物的悲劇并不相同。夏瑜是為人類正義事業而犧牲的革命者,他的死使人走向精神的崇高與悲壯,一如普羅米修斯、哈姆雷特、梁山好漢,“能在我們心中里引起熱烈的同情,極大的敬意,同時又能激發新的銳氣”(盧那察爾斯基《論文學》)。而祥林嫂、孔乙己、陳士成、涓生與子君、單四嫂子是“小人物”的悲劇。他們是我們社會普通民眾的極平凡的一員,他們的毀滅提醒了我們對自身地位和命運的深切擔憂。孔乙己、陳士成是迂腐沒落的封建科舉文人,他們的悲劇是舊事物、舊制度的消亡。“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馬克思《導言》)
我特別要提到魏連殳、涓生與子君和阿Q的悲劇。他們有致命的人性的弱點,如魏連殳的消沉,涓生的意志薄弱,阿Q的精神勝利,但同時也表現出人性光輝的一面,魏連殳的“沒有顧忌的議論”,涓生與子君追求個性的解放,阿Q迫切要求改變自身地位和對革命的神往。他們的悲劇是“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魯迅)。正如阿Q,他既令人厭惡,又令人同情,我們“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涓生、子君、魏連殳,他們有奮斗抗爭的實際經歷,有走向勝利的可能性,有成為革命者的可能性,但他們恰恰失敗了,“精神價值越高,沖突與毀損的悲劇性也越大”。
恩格斯在《致斐拉薩爾》的信中指出,悲劇的本質正是由“歷史的必然性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之間的悲劇性的沖突”。阿Q、祥林嫂連“奴隸也做不穩”,孔乙己、陳士成的命運是舊事物與新時代相沖突的結果。夏瑜、涓生、魏連殳要求變革現實,表現出歷史的新動向,但這個要求遇到舊勢力的壓制而無法實現,他們的悲劇是必然的。
篇3
⑴我們坐火車去嗎?(《故鄉》)
⑵你們的茶不冷了么?(《長明燈》)
⑶他們忘卻了紀念,紀念也忘卻了他們。(《頭發的故事》)
⑷直到她說到嗚咽,她們也就一齊流下那停在眼角的眼淚……(《祝福》)
⑸可是其實都很瘦,因為它們早已每日只能得到幾粒高粱了。(《傷逝》)
⑹咱們大王的龍準是很高的。(《鑄劍》)
例⑴―⑹是第一、二、三人稱代詞加“們”的例子,這類例子在魯迅的小說中數量較多。本文擬就“們”在魯迅小說中的用法與現代漢語中“們”的用法的對比考察的基礎上,探究魯迅小說中“們”的特殊用法及其成因。
由于魯迅先生所處的語法史上的特殊時期,他的小說中“們”的用法有其獨特之處。本文就一些具體問題提出一些個人看法。
一.第一人稱復數“咱們”
第一人稱復數“咱們”, 在魯迅所有小說中只出現了6例,全部用作定語。
(1)咱們大王的龍準是很高的。(《鑄劍》)
(2)不過您要想想咱們的太上皇。(《理水》)
(3)咱們大王只有一個頭,那一個是咱們大王的呢?(《鑄劍》)
(4)啊呀,咱們大王的頭還在里面哪,……(《鑄劍》)
(5)咱們大王就帶了諸侯,進了商國。(《采薇》)
(6)咱們的局長這幾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起死》)
這幾個“咱們”全部出現在《故事新編》中。為什么《吶喊》《彷徨》中未出現一例“咱們”呢?
究其原因,我認為應該有兩方面的原因。其一,魯迅先生祖籍紹興,又長期生活在吳語區,吳語中第一人稱代詞沒有“咱們”、“我們”之分。吳語區的人不稱“咱們”是可想而知的。但魯迅先生從1918年1月至1926年9月在北京生活,接觸到了北方方言,一定也知道“咱們”、“我們”的區別。其二,《吶喊》《彷徨》中描寫的大都是江南的風情、人物,這些人物的口語里不會有“咱們”一說。《故事新編》是歷史小說集,所寫人物并不拘于一定方言區,這些人物的口語中出現的“咱們”,不會和人物形象的塑造相抵牾。
二.指物名詞+們
在魯迅小說中有“指物名詞+們”的形式,表示物的多數。呂叔湘先生在《近代漢語指代詞》中認為這種“指物名詞+們”的用法,似乎多少有點受西方童話的影響。這種推測一時難以考證。而從魯迅作品中出現的幾個例子來看,都可以分析出“指物名詞+們”是修辭中擬人手法的運用。例如:
(1)這些眼睛們似乎連成一氣,已經在那里咬他的靈魂。(《阿Q正傳》)
(2)……恭請福神們來享用……(《祝福》)
(3)于是吃我殘飯的便只有油雞們……自覺了我在這里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傷逝》)
(4)狼們站定了,聳著肩,伸出舌頭,咻咻地喘著,放著綠光的眼睛看著他揚長的走。(《鑄劍》)
(5)巨鰲們似乎點一點頭,成群結隊地駝遠了。(《補天》)
例(1)中“眼睛們”和“咬”的搭配,例(2)中“福神們”和“享用”的搭配,例(3)中“狼們”的“看”,例(4)中“巨鰲們”的“點頭”,或是把本來無生命的事物寫得有了生命,或賦予了本來不具備人的思想意識的生物以思想意識。這都是擬人這種修辭手法的運用。例(3)中“油雞們”和“叭兒狗”與“我”放在了一起,體現了“我”為生活所迫的那種無奈。“油雞們”和“叭兒狗”都擬人化了。
不管這種用法是否是受了西方童話的影響,至少我們可以從實際的用例中分析出這是一種修辭手法的運用,并不代表一般的規范。而且魯迅先生同時期的小說中另有一些符合現代漢語習慣的指物名詞的復數形式。例如:
(1)許多狗都拖出舌頭來……(《示眾》)
(2)后來仲密家里果然有了許多小雞,滿院飛跑……(《鴨的喜劇》)
(3)剛進房門,卻看見滿眼明亮,連一群雞也正在笑他。……(《白光》)
(4)待到四處蛙鳴的時候,小鴨也已經長成。(《鴨的喜劇》)
例(4)中的“小鴨”本身就有復數意義,所以不需要再加“們”。這是漢語有別于印歐系語言的特點之一。
三.專用表人名詞+們
近代漢語中,“指人名詞+們”的用例中,指人名詞可以是“校長”、“學生”之類的可以代表某一類人的詞,也可以是“馬都頭”、“楊大個兒”、“李四”這樣的專用表人名詞。而現代漢語中可以使用的符合人們表達習慣的一般用例只有第一種,沒有“專用表人名詞+們”這種用法。魯迅小說則存在兩種用法交替錯雜使用的情況。從使用頻率來說,魯迅小說中較普遍的是“闊人們”、“百姓們”、“學者們”等形式,屬現代漢語中的規范用法。特殊的是“專用表人名詞+們”的用法。例如:
(1)夏天夜短,老拱們嗚嗚的唱完了不多時,東方已經發白……(《明天》)
(2)七斤們連忙招呼……(《風波》)
(3)闊亭們立刻面面相覷……(《長明燈》)
(4)門外是大良們笑嚷的聲音。(《孤獨者》)
(5)幾個孩子聚在屋外,就是大良二良們。(《孤獨者》)
例(1)中“老拱們”指的是與老拱一起在酒店喝酒的人,例(2)中“七斤們”指七斤全家,例(3)中“闊亭們”指和闊亭在一起的人,均屬“專用表人名詞+們”的用法。這種用法可以說是承近代漢語的用法而來的。而在現代漢語中,如果需要表達上述例句中的特定的語言環境中的某一些人時,一般用“七斤他們”、“闊亭他們”這樣的“專用表人名詞+他們”的形式來表達,不再用“專用表人名詞+們”的用法。這種形式在魯迅小說中也出現了兩例:
(6)木蘭他們被船家的聲音警覺時,前面已經是魁星閣了。(《離婚》)
(7)秀兒她們也不必進什么學堂了。(《肥皂》)
這似乎是作者當時已經開始嘗試的一種新的用法。但因例證太少,不足以說明問題,只能作為一種現象提出來。
例(4)、例(5)“大良們”“大良二良們”都指大良、二良等兄弟姊妹四人。特殊的是這個“大良二良們”,表義和“大良們”相同。呂叔湘先生曾在《近代漢語指代詞》中提到過這種“甲+乙+們”的用法。這里的甲、乙都是專用表人名詞。甲、乙為表示單數的專用表人名詞加“們”時,在近代漢語的用例中一般指“甲和乙”兩個人,較少有“甲、乙和別人”的意思,規范的現代漢語中已不再這樣用了;甲、乙若為也可表示復數的專用表人名詞相連,加“們”使用,如“老師同學們”等,現在仍使用。“大良二良們”這類用法,在魯迅小說中僅此一例。如果按我們現在的觀點來看,算是一個不規范的特殊用例罷了。
四.對比下面A、B兩組例句
A組:
(1)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吶喊?自序》)
(2)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們便很厭惡我。(1920年?《頭發的故事》)
(3)只有一班閑人們卻還要尋根究底的去探阿Q的底細。(1921年?《阿Q正傳》)
(4)他們小孩們知道些什么。(1924年?《肥皂》)
(5)許多人們的耳朵里、心里,都有了一個可怕的聲音“放火”。(1925年?《長明燈》)
(6)還有幾位少爺們……(1925年?《離婚》)
B組:
(7)店里坐著許多人,老栓也忙著……(1919年?《藥》)
(8)幾個酒肉朋友圍著柜臺,吃喝著正高興……(1920年?《明天》)
(9)那孩子后面還跟著一群相識和不相識的人。(1925年?《弟兄》)
(10)“站住!”幾個人大叫道。(1935年?《出關》)
(11)只有許多巡警和探子,在呆聽他們的閑談。(1935年?《出關》)
(12)店里又有三個學生來買東西。(1924年?《肥皂》)
在A、B兩組例句的對比中,我們可以考慮下面兩個問題:
(一)“幾位(個)+指人名詞+們”與“幾個(位)+指人名詞”
我們知道,“位”是用于人而含敬意的量詞,“個”則是可以用于任何沒有專用量詞的名詞,也可以用于人。“位”和“個”在用于人時從語法意義上講是大同小異的。
“幾位(個)”和“們”并用,這種用法在《水滸傳》《紅樓夢》中有,魯迅小說中也有這種“幾位(個)”和“們”并用的例句。如A組中例(2)中的“幾位”“同學們”,例(6)中的“幾位”“少爺們”。魯迅小說中也有“幾個”只加指人名詞不加“們”的例句,如B組中例(8)“幾個酒肉朋友”,例(10)中“幾個人”。
“幾位(個)”、“許多”、“一”加上指人名詞之后,加或不加“們”只是語法形式上不同,從表義角度上看是沒有區別的。現代漢語發展至今基本淘汰了“幾位(個)” 和“們”并用的形式,原因應該是“幾位(個)”本身就有表復數的意義,再加“們”就重復多余了。
(二)“許多人們”與“許多人”
在A、B兩組的例句中我們可以看到,魯迅小說中有“許多人們”和“許多人”交錯使用的情況,在時間上無法分出這兩種用法誰先誰后,從使用頻率上也無法分清誰主誰次。如例(1)中的“許多熟睡的人們”,例(7)中的“許多人”;例(3)中的“一班閑人們”,例(9)中的“一群相識和不相識的人”。
現在規范的現代漢語中,如果指人名詞前已經有了表示不計量多數的“許多”、“一群”等,后面一般不帶“們”。如人們習慣說“一群學生”、“許多人”,一般不說“一群學生們”、“許多人們”。這是不是就能證明“許多人們”之類的不能正確表義呢?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我們知道,“們”表示的是不計量的多數,“許多”、“一群”等表示的是不確定的多數。這樣“許多人們”就與“三個學生們”不同。例(12)中之所以用“三個學生”而不用“三個學生們”,原因是“三個”為確定數,“們”為不確定多數,同時使用前后矛盾。從這個角度看,“許多人們”不存在前后矛盾的問題。但“許多”“們”和指人名詞連用,存在的是前后重復的問題。這應該是人們淘汰“許多人們”之類的說法的原因。
書面作品中出現兩種甚至多種表義相同而形式不同的語法格式,這在語言運用是常見的。處于近、現代漢語的交界時期,現代漢語發展初期的魯迅小說中出現這種情況更是正常現象。在語言的發展中,是兩種或多種同義表達形式并存使用,還是最終選擇其中一種淘汰另一種,就要看語言自身的發展情況和使用語言的人們的選擇和約定俗成了。這也充分證明了語言是不斷變化發展的。
參考資料:
[1]魯迅:《魯迅小說集》,1979
[2]呂淑湘著、江藍生補:《近代漢語指代詞》,1985(7)
[3]王力:《漢語語法綱要》,1982(2)
[4]黎錦熙:《國語運動史綱》,2011(5)
[5]陳望道: 《陳望道文集》,1979(7)
[6]陳望道:《陳望道語言學論文集》,2009(8)
篇4
《社戲》中,作者首先向我們展示了一種文化心靈,一種純潔心靈的生長環境。小說中,我和母親為了消夏,住在平橋村的外祖母家。平橋村離海邊不遠,是個臨河的小村莊。村民們種田打魚,村子里只有一個很小的雜貨店。
當我來到了平橋村,便受到了優待。許多小朋友,因為有了遠客,可以從父母那里減少工作,來伴我游玩。
平橋村有著和平、民主、友好的交際氛圍。在平橋村,一家的遠客是公共的客人。“我”在平橋村,受到了從沒有過的尊重。在村里,大家不因為輩分的高低而有所講究封建禮教,即便是偶爾吵鬧,打了所謂的太公,大家也不用“犯上”這兩個字來評判。
平橋村的小朋友,有一種良好的生長環境。“我”和平橋村的小朋友一起做什么呢?一個是掘蚯蚓來釣蝦,小伙伴們釣了一大碗蝦,最后照例送到“我”的嘴里去。其次是跟平橋村的小朋友一同放牛,但是因為黃牛水牛都欺生,敢于欺負“我”,所以“我”不敢靠近水牛,只能遠遠地跟著、站著,所以“我”又成了小朋友、小伙伴嘲笑的對象。在這里,作者通過釣蝦和放牛,向我們展示了和諧、文明、友好的鄉村文化,即便是小朋友們對我的嘲笑,也是善意的、理解的。平橋村的小朋友們就是在這樣的文化心理、文化氛圍中生長著。因此他們身上多的是樸素可愛,多的是聰明機智。課文中,平橋村的小朋友心懷坦蕩、為人寬厚。可以說,社戲的故事還沒有發生,作者就向我們展示了純潔心靈所需要的生長環境,即寬松、自由、和諧。
“我”在平橋村消夏,第一盼望的是到趙莊去看社戲,但因為平橋村只有一只早出晚歸的航船,“我”沒有能夠及時地到趙莊去看社戲。于是外祖母很氣惱,怪家里的人不早定,而“我”又急得要哭。到了下午,小朋友們都去了。作者寫“我”的情緒變化:聽到了鑼鼓的聲音,知道他們在戲臺下買豆漿喝。在家的“我”,不釣蝦也不吃東西,外祖母很不高興,認為他們待客禮數太怠慢。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吃過飯以后,吃過晚飯后,看過社戲的少年們都聚攏來了,他們高高興興地講社戲,而“我”不開口。這時,小伙伴們是既嘆息又表同情。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最聰明的雙喜提議——八叔的航船不是回來了嗎?于是,十幾個少年恍然大悟,立刻攛掇起來說,可以坐著航船和“我”一同去。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平橋村少年純潔的心靈,他們都到趙莊看過戲,然而還愿意陪“我”一同去趙莊看社戲。在祖母和母親擔憂會出意外時,雙喜則大聲地說:“我寫包票!船又大,迅哥兒向來不亂跑……”當外祖母和母親不再駁回時,我們立刻一哄地出了門。從這個情節看,以雙喜為代表的平橋村的這一群小朋友非常寬厚,非常理解人。在和朋友相處時,他們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所以,作者在這個情節里所展示的,就是鄉村文化中對他人理解的情懷。作者通過描寫一群少年的熱情好客,就把鄉村自然、淳厚、熱情的文化心理寫出來了。
在去看社戲的途中,“雙喜拔前篙,阿發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艙中,較大的聚在船尾”。他們“架起兩支櫓,一支兩人,一里一換,有說笑的,有嚷的,夾著潺潺的船頭激水的聲音,在左右都是碧綠的豆麥田地的河流中,飛一般徑向趙莊前進了”。平橋村的這群少年,勤勞樸實,熱情好客,從不斤斤計較。他們來到趙莊,近臺沒有什么空時,便擠在船頭看社戲。當“我”有些疲倦時,便托桂生買豆漿去。但賣豆漿的回去了,桂生甚至寧愿舀一瓢水來給“我”喝。這里寫的是桂生純潔的心靈,桂生甘愿為我服務,為我著想,這是多么美好的一種心靈啊!當大家終于熬不住時,便“回轉船頭,駕起櫓,罵著老旦,又向那松柏林前進了”。
在回來的路上,大家因為太用力,許久沒有吃東西,于是桂生提議,“羅漢豆正旺相,柴火又現成,我們可以偷一點來煮吃”。于是,大家都贊成,立刻近岸停了船,上岸摘那“烏油油的都是結實的羅漢豆”。在看羅漢豆時,發生了這樣一幕——
“阿阿,阿發,這邊是你家的,這邊是老六一家的,我們偷哪一邊的呢?”雙喜先跳下去了,在岸上說。
我們也都跳上岸。阿發一面跳,一面說道,“且慢,讓我來看一看罷,”他于是往來的摸了一回,直起身來說道,“偷我們的罷,我們的大得多呢。”一聲答應,大家便散開在阿發家的豆田里,各摘了一大捧,拋入船艙中。雙喜以為再多偷,倘給阿發的娘知道是要哭罵的,于是各人便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又各偷了一大捧。
這里我們可以看到,偷哪一家不偷哪一家的羅漢豆,不是出自自私自利,而是由羅漢豆的大小決定。當偷了阿發家的羅漢豆以后,這群孩子擔心被阿發的娘知道,于是又到六一公公的田里各摘了一大捧。從這里可以看出,這群孩子,他們平實公正、胸懷坦蕩、純潔明朗,心里從來沒有裝著一個“私”字。這一段話把平橋村的這一群少年純潔善良、友好坦蕩的心理描寫得淋漓盡致。
魯迅的小說多描寫主人物的冷漠自私、麻木愚昧、保守封建、自私自利、自高自大,無論是受封建科舉毒害的孔乙己,還是自高自大而精神上不斷勝利的阿Q,亦或是麻木愚昧且備受折磨、仍然逃脫不了死亡的祥林嫂,他們身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著所謂的國民的劣根性,然而唯獨在《社戲》中,魯迅給我們描寫了一群善良可愛、天真活潑、勇敢樸實的少年。可見魯迅一方面展示著中國農民身上存在的問題,另一方面,也在展示著中國農村下一代身上的善良、可愛、誠實。
魯迅的心中一邊是冰天雪地,一邊是春花嬌媚。他在小說中批判著、審丑著,他也在小說中期待著、渴望著。在《狂人日記》中,他在小說的結尾奮力地喊出“救救孩子”。在《故鄉》的結尾,他希望宏兒和水生有自己的新生活,期望宏兒和水生有自己的新征途。魯迅對中國少年,中國兒童,是抱以希望和期盼的。在《社戲》中,他描寫了一群天真善良,勤勞樸實的農村少年,給我們展示了這群農村少年的美好純潔的心靈。這群農村少年,恰恰是魯迅心中最美好的農村少年形象。他們沒有封建禮教的束縛,他們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冷酷、麻木、自私,他們敢說敢做、勇于擔當,他們才是中國農村發展的新一代。
要生成這樣的新一代,就需要有一個自由、理解、寬容的鄉村環境。小說中,我們偷了六一公公家的羅漢豆、用了八公公的鹽柴,大人們并沒有難為我們。小說在最后給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個場面——
“雙喜,你們這班小鬼,昨天偷了我的豆了罷?又不肯好好的摘,蹋壞了不少。”我抬頭看時,是六一公公棹著小船,賣了豆回來了,船肚里還有剩下的一堆豆。
“是的。我們請客。我們當初還不要你的呢。你看,你把我的蝦嚇跑了!”雙喜說。
篇5
作為初中語文教師,我們有責任把魯迅先生的這份豐厚的文學遺產傳承給學生,讓他們較多地接觸魯迅,學習魯迅,讓魯迅在課堂上大放異彩。筆者擬從魯迅先生小說塑造人物形象的技巧中汲取營養,指導學生寫作,例談一二。
一、肖像描寫
魯迅先生說:“要極省儉地畫出一個人的特點最好是畫他的眼睛。我以為這話是極對的。倘若畫了全副的頭發,即使細得逼真也毫無意思。”魯迅給人物畫像擅長畫眼睛,《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在河邊遇見“我”,“我”便從“她瞪著的眼睛的視線,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來的”。說明眼神能傳達自己內心的需求,而對方也能從她的眼神中看出她有什么需求。這是無聲的語言。接著作者用簡潔的語言把祥林嫂“木刻似的”外貌刻畫出來,全然一副僵尸,然而祥林嫂本是一個活人,只是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如何把這個活人表現出來呢?作者這樣寫道:“只有那眼珠或一輪,還可以表示她是一個活物”。這真是神來之筆,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這一筆就把祥林嫂在死神來臨前的形象展現在讀者面前,也為下文寫祥林嫂在祝福聲中凄涼地死去作了鋪墊。
在初中生作文中也有寫人物眼睛的,但他們筆下的眼睛常常是“炯炯有神”的。炯炯有神形容人很有精神,充滿朝氣和活力,而生活中的人不全是這樣,即使是小孩子的眼睛也不都是“炯炯有神”的,有的小孩的眼睛就沒神,有的小孩子眼睛還近視,甚至眼皮拉下像要打盹一樣,所以不能寫成千人一面。如果是小說,刻畫人的外貌,還要同人物的性格、氣質、命運相結合,成為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能推動情節的發展,像魯迅先生筆下的許多人物形象就具有個性特征。
魯迅先生筆下的人物不僅眼睛畫得好,而且對人物臉色、衣服也寫得很出色。
如對孔乙己這個人物的外貌,就運用了概括描寫和具體描寫相結合的寫法。可謂精雕細琢,不厭其煩。但每一點都有著豐富的內涵,哪一點都不能少,而且為下文情節的展開作鋪墊。“外形是理解人物的鑰匙”(果戈里語)我們讀魯迅關于孔乙己的肖像描寫,就可以看出他的身世,預示他的悲慘結局。
通過以上分析,學生能體會到刻畫人物肖像既可以用概括描寫,又可以作具體描繪,濃墨重彩。但究竟如何寫,寫什么,則要根據文章需要而定,?詳則詳,該略則略。要寫好人物的肖像就要認真的觀察,就“要練習我們的眼睛善于觀察人的動作、態度和表情”(艾蕪語)。
二、動作描寫
“一個人物的性格不僅表現在他做什么,更表現在怎樣做”(恩格斯語)小說中人物的動作要與人物的文化程度、性格、氣質相協調,也就是個性化。魯迅小說中人物動作的個性化特征更為鮮明。如:孔乙己兩次來到咸亨酒店柜臺前掏錢買酒的動作,第一次是“排出九文大錢”,“第二次是摸出四文大錢”。“排”說明孔乙己既把錢展示在掌柜的面前,又是把錢展示在旁邊酒客的面前,表示自己一文不少,動作顯得很自然文雅,以顯示自己與短衣幫的不同。“摸”是在他被打折腿之后,盤著兩腿來到酒店,錢是藏在身上的。這一字之差,說明了孔乙己的命運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化。
由此可見魯迅小說中的人物動作簡捷而富有個性,在學生作文中人物的動作單個的缺乏個性,多個動作又沒有連續性,更無法表現人物的性格特征,學習魯迅先生的小說后,使他們的作文扭轉這種狀況。
三、環境烘托
人物的活動,事件的展開,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自然環境中進行的。“人創造環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因此,寫人詞常常需要對環境進行描寫。茅盾在《關于藝術的技巧》中指出:“人物不得不在一定的環境中活動,因此,作品中就必須寫到環境。作品中的環境描寫,不論是社會環境或自然環境,都不是可有可無的裝飾品,而是密切地聯系著人物的思想行動。”
小說要塑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環境描寫能為塑造人物形象服務。《孔乙己》中酒客分兩大類:穿長衫的和短衣幫。掌柜對穿長衫的竭盡巴結、奉承之能事,讓他們在包間里坐著喝酒。而對短衣幫不僅讓他們站著喝酒,而且要向酒里摻水。伙計要能侍候長衫主顧,否則就在外面應付短衣幫。接待短衣幫要有背著顧客摻水的本領,以獲得盡量多的利潤。如果這兩件事都做不了,那就只能做溫酒這樣一種無聊的事了。掌柜對人是一副兇臉孔,這主要是對短衣幫、小伙計、和孔乙己這三類人。作者設置這樣一個金錢至上的環境為孔乙己的出場渲染了悲劇氣氛。
篇6
摘要:每個民族都有自己引為自豪的文學遺產,我們以有《紅樓夢》而自豪。一部“紅樓”,傾倒了多少中外讀者!曹雪芹的偉大不僅在于他從那一派紅紅火火的“虛熱鬧”中,感受到了“呼啦啦似大廈傾”的封建社會的頹倒之勢;還在于他在小說中所表現出的那種萌芽的民主意識。這種意識又集中地表現為作家的“女性意識”――為女性張目,為女性吶喊。《紅樓夢》為我們塑造了一個迷人的“女性世界”!而魯迅的小說中女性的形象更為我們讀者所關注。
關鍵詞:魯迅;形象;小說;女性
在人類進化史上,女性同男性一同出現并創造著這個世界,但是有史以來,女性所受到的待遇,一直是不公平的。在人類生活的辭典里,恐怕再沒有比“女人”更難以解釋、評說的了。長時間以來,婦女在現實生活中的狀況及其價值,像植物中的葛藤,沒有自己的枝干,靠攀緣其他植物而生活――女性需要依附;像天空中的流云,沒有自己的根基,風可以隨便把它吹走――女性缺乏自身的價值。從中國兩千多年前孔夫子的“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到西歐中世紀“女人是男人身上一根筋骨所做”,歷史的傳統偏見在男女之間掘出一道難以逾越的鴻溝。
有史以來,中國婦女承受了巨大的苦難和痛苦,魯迅先生為此而深深地悲哀、憂憤。他說,中國人向來沒有掙到過“人”的價值,至多不過是奴隸。魯迅小說中也塑造了一個不容忽視的“女性世界“。“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并非魯迅先生“偏愛”女性,只是因為女性有著太多的苦難和憂傷,因此,對于女性命運的關注,成為魯迅先生的一個創作傾向。魯迅先生以其理性批判的精神,審視著二十世紀的中國現狀,關注著中國勞動婦女的歷史命運,并從此出發思考著有關社會、歷史的諸多問題。
全面地揭示中國婦女靈與肉、尤其是靈的苦痛是魯迅小說的主題。魯迅在他的小說中寫出了中國農村婦女無限的人生悲劇,顯示出他對中國農村社會深深地理解與同情。《藥》中,夏瑜的母親本來就窮得“榨不出一點油水”,如今又死了兒子,孤苦老人何人贍養,其未來的命運是可想而知的。《明天》中喪夫的單四嫂子,“須專靠著自己的一雙手紡出棉紗來養活自己和她三歲的兒子”,貧困,使一家幾代農婦幾乎到了相互仇視的地步:“九斤老太”嫌曾孫女吃得多“吃窮了一家人”;“六斤”以極不恭敬的這“老不死的!”回敬曾祖母。“六斤”僅僅因為弄爛一個破碗,便遭父親重重一拳,打倒在地(《風波》)。貧窮,使二十年前人稱“豆腐西施”的楊二嫂變得潑辣、放肆。為了從“我”家撈點東西,交替著虛偽的吹捧、尖刻的嘲諷,還中傷閏土偷碗碟,活得頗為悲哀(《故鄉》),但這些,并不構成魯迅小說探索婦女命運的主要之點,魯迅先生把他探索的筆觸伸向因封建專制壓迫所造成的婦女心靈的深深的苦痛中。
華大媽和夏瑜之母(《藥》)在精神愚昧困頓中度日。前者篤信人血饅頭可以醫病,送了兒子的性命,后者對兒子并不理解,去給兒子上墳,看到別人瞧她甚至還感到“膽怯”、“躊躇”,面帶羞愧的顏色,“硬著頭皮”走到兒子墳旁。兩位境遇不同的婦女,在封建統治下,以其迷信麻木達到精神上的同歸。
阿Q向吳媽(《阿Q正傳》)下跪,要與她“困覺”的戀愛方式是荒唐的,但吳媽為此大哭大鬧、尋死覓活,求告趙太爺的舉動更是悲哀的。吳媽之所以感到羞辱,甚至不惜準備以死洗得“清白”,其鑒事的原則是封建的“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信條。封建道德已使她失去一個“女人”的正常思維、要求,因此才將最普通的男女求愛之事視為“非禮”的、洪水猛獸一樣的事情。
《風波》中的七斤嫂頗有幾分“強悍”,但這是外在的、虛弱的,她的靈魂已被封建道德所吞噬。面對著封建復辟勢力趙七爺的威逼,她顯得那么驚恐、絕望。她乞求“皇恩大赦”,無望之后,“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七斤嫂感到驚慌的是趙七爺的“學問”,是“書上寫的”東西――封建階級的“圣經賢傳”給農村婦女鑄下了難以卸脫的精神桎梏,使她們活得那樣艱難、沉重!《離婚》中的愛姑表面上看起來比七斤嫂更“強悍”、“潑野”,她敢于公開辱罵欺侮她的公公、丈夫為老小“畜生”。但這種抗爭中隱伏著“危機”,因為她認定自己是“三茶六禮定來的,花轎抬來的”,而且她盡了婦道:“自從我嫁過去,真是低頭進,低頭出,一禮不缺”。“小畜生”不應背棄她這個“正”的去外面胡亂。她根本不是從維護自我尊嚴、人格、地位方面去論定是非。婦女是沒有這種權力的。不是“節”、“烈”,便是被“休”,如此而已。愛姑實質上仍是重復了封建社會千百萬婦女的命運。
篇7
關鍵詞:魯迅 女性形象 國民劣根性
魯迅先生認為,國民劣根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存在于國人內心深處的奴性。他認為長期的非人的生存境遇造成國人對暴力和強權產生了與生俱來的敬畏和盲從心理。人們俯首貼耳,唯唯諾諾,安于命運,不敢逆天犯上,陷于奴隸的深淵而不能自拔。人們為保住奴才的地位,在自覺或不自覺地隨之而形成了馴服、乖巧的特性,以及“驕和諂”相糾結的畸形性格,他們“對于羊顯兇獸相,而對于兇獸顯羊相,所以即使顯著兇獸相,也還是卑怯的國民”。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仆,仆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魯迅在《燈下漫筆》里辛酸的一語,道盡了中國女性千百年來深受壓迫的卑微屈辱的命運,對她們的命運給予深切的同情。但是,正是由于女性比男性遭遇了更多的壓迫,她們靈魂里的奴隸意識,比男性更加深厚。魯迅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更能反映國民劣根性。
一
《祝福》中的祥林嫂是飽受封建禮教約束的中國底層女性的典型形象。魯迅深深感悟到幾千年作為封建社會最底層的女性經受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創傷。這些最底層的中國女性,靈魂中積淀著沉重的奴隸意識,因為她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她們是可以爭取做“人”的權利的。祥林嫂即是這樣,她最大滿足和幸福竟是“坐穩奴隸”。在旁人看來,“安分耐勞”是祥林嫂最大的特點。“安分”證明她只想做個好寡婦,沒有任何“非分之想”,決心按照封建禮教對寡婦的要求辛苦地過日子。但是,封建社會中的寡婦所遭受的待遇是“非人”的。魯迅曾在雜文中說到:“節烈苦么?很苦。”在那個男權時代,“男主外、女主內”,女人很難依靠自己的力量養活自己。除了經濟條件艱難,寡婦還常常遭受人們的白眼,被視為“不潔之物”。人們很難把做人的權力跟寡婦聯系起來,在他們的眼里,寡婦無疑于“活死人”罷了。 “耐勞”則是她的堅忍不拔吃苦和簡直抵的過一個男子的勞動能力,是她做個好女人,好寡婦的資本。但是,當魯迅在表現祥林嫂的耐勞、儉樸、善良的時候,魯迅分明感覺到沉重、苦澀甚至激憤,因為魯迅發現,而且她在《祝福》中表現了:祥林嫂的耐勞也好,儉樸也好,善良也好,都帶著奴隸的麻木,她的耐勞、儉樸、善良僅僅使祥林嫂充其量只能是個好奴隸。
其實祥林嫂并非沒有反抗精神,當她被賣給賀老六做老婆時,她是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拼死反抗,因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祥林嫂反抗的目的,只是為了做一個從一而終的好寡婦!這種反抗,難道不是越真誠、越激烈,反抗精神越強,也就越是可悲,越是證明著奴隸意識越沉重,越深刻嗎?
魯迅通過祥林嫂形象,畫出了現代的我們國人的女性的靈魂,提示了祥林嫂靈魂里沉重的奴隸意識,寄希望于中國女性從這個形象中認識自己,覺醒過來,自己改變自己的處境和命運,爭取到做人的權利和價值。
二
表面看來,《風波》中的七斤嫂并不是一個逆來順受之人。她敢跟九斤老太頂嘴——將飯籃在桌上一摔,憤憤的說,“你老人家又這么說了。六斤生下來的時候,不是六斤五兩么?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稱,十八兩秤;用了準十六,我們的六斤該有七斤多哩。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見得正是九斤八斤 十足,用的秤也許是十四兩……”。敢跟丈夫發威——“你這死尸怎么這時候才回來,死到那里去了!不管人家等著你開飯!”可見,她在這個家里的地位并不低。她也不是一個平庸的女流之輩,雖然是地處偏僻的鄉村婦女,卻并沒有一般人想象中的愚妄無知。她精明能干,與天天進城的丈夫相比,她更是多了一份洞察事物的敏銳。在七斤告訴她皇帝要辮子時,她便感覺出事情不妙;當看到趙七爺以光滑的頭皮烏黑的發辮以及那件寶藍色竹布長衫的形象出現在土場時,她便“心坎里禁不住突突跳起來,當然這種感覺并不是出于對趙七爺的政治權威的膜拜,也不是經濟實力的壓迫,而是她通過多年的生活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感到七斤有危險了。果然,趙七爺終于借要辮子之名向七斤報仇了。更為難得可貴的是,七斤嫂不僅敏銳地洞察危險,還能準確地判斷時局的 變化。這么一個潑辣精明的女人,仍然帶有深深的奴性。當趙七爺向七斤要辮子時,她“竭力賠笑”。當趙太爺嘴里振振有詞:“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時,覺得有學問的七爺這么說,事情自然非常重大,無可挽回,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耳朵里嗡的一聲,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她對“兇獸”趙七爺等顯“羊”像;對著比她弱的六斤,卻立刻顯出“兇獸”像——當六斤剛吃完一大碗飯,拿了空碗,伸手去嚷著要添。七斤嫂正沒好氣,便用筷子在伊的雙丫角中間,直扎下去,大喝道,“誰要你來多嘴!你這偷漢的小寡婦!”女兒也成了她的泄憤對象。七斤嫂這類女人精明能干,潑辣有為。但仍然帶著深深的奴性,對強勢者諂媚,對弱小者欺凌。冷漠愚昧使得她們渾渾噩噩度日,雖然陷入奴隸的隊伍里也不知反抗。
魯迅小說中的女性是冷漠、麻木、愚昧、沉默的,她們渾渾噩噩地度日,對社會的變動、改革茫然無知;她們面對欺凌與煎熬,不是逆來順受就是泄憤于他人;她們的身上有著明顯的弱點,卻認識不到自己悲劇的根源,她們更能體現國民的劣根性。她們的反抗又無一例外地表現出深層思想的保守傾向,具有反傳統性質的反抗是局部的、外在的、現象的、暫時的,而骨子里的封建傳統卻是內在的、本質的和難以改變的,最終暴露出因襲重負下精神根底里的奴性。
參考文獻:
[1] 舒蕪,《母親的頌歌——魯迅婦女觀略說》,《魯迅思想研究》1990版
篇8
在對魯迅作品的研究中,《吶喊》和《彷徨》仍然是被關注的熱點。這些小說曾被廣泛、深入地研究了幾十年,現在一般地解讀其藝術內涵也許并不困難,重要的在于有所發現。胡尹強的《破毀鐵屋子的希望——〈吶喊〉、〈彷徨〉新論》發現,《吶喊》、《彷徨》的二十來篇作品其實是有內在聯系的系列小說,它們相互補充、相互闡釋,從不同側面表現了鐵屋子意象所隱喻的豐富底蘊——魯迅對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宏觀把握和感悟。作者以鐵屋子意象統攝全書,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魯迅對現代中國人的存在命運與狀態的深刻的人道主義關懷。李靖國的《〈狂人日記〉重探》發現,狂人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備徹底性與不妥協性,但這絲毫不降低作品的思想價值。恰恰相反,魯迅的憂憤深廣,正是通過一個清醒深刻的思想者被封建宗法制度強行剝奪自由思想獨立人格而致“狂”,進而刻畫了傳統勢力和禮教連“迫害妄想”癥患者病發時的種種表現都不容許存在。最后,封建宗法制度與傳統文化系統居然將“狂人”治“愈”,將反封建者馴服為其忠實的維護者與奴才,以此揭示封建主義“吃人”的兇殘、虛偽與“高明”,從而警示改革者必須直面慘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鮮血,具備堅強的心理素質。
日本學者丸尾常喜的《“人”與“鬼”的糾葛——魯迅小說論析》發現,魯迅小說中有一個“鬼”的形象系列:傳統文化“鬼”、民間民俗“鬼”、國民性弊端“鬼”、自身意識到的“鬼”,在這些“鬼”的意象中,《吶喊》和《彷徨》顯示出獨特的文化批判價值。王冰的《魯迅作品中生命群像的存在主義哲學色彩》以存在主義哲學觀點,發現魯迅作品中有一個“佯狂”、“向死而生”的生命群像。曹書文的《論魯迅小說創作的家族意蘊》發現,魯迅也是中國現代家族小說的創始人,《吶喊》和《彷徨》對女性命運與精神悲劇的關注,對封建家庭叛逆知識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為我國現代家族小說不斷走向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繆軍榮的《永遠的地獄——論祥林嫂之死》發現,祥林嫂之死的原因其一是舊禮教各條律之間的內在矛盾,是族權與夫權之間的相悖;其二是愚昧大眾“看客”的兇眼,通過“心理暗示”的作用使祥林嫂產生犯罪之感、自我心靈折磨以致跨入地獄之門。解志熙的《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新小說中的舊文化情緒片論》認為,《吶喊》誠然是一部悲憤控訴舊文化、舊禮教,熱情鼓吹新文化、新道德的“吶喊”之作,但某些篇章如《故鄉》、《社戲》等其實也自覺不自覺地流露出對舊文化和傳統生活方式的眷戀與反顧。江業國的《魯迅筆下阿Q之死的“儀式感”》認為,魯迅描述阿Q之死的“儀式感”,既是為了在藝術上終結這個“問題人物”,更是為了使“阿Q”徹底成為關于人的存在問題的哲學思辨的藝術符號。
不少研究魯迅小說藝術形式的成果也頗具新意。嚴加炎的《復調小說:魯迅的突出貢獻》利用巴赫金的復調理論,發現魯迅小說是有著多種聲音的復調形式,正是這種形式賦予了作品以豐富、多義的美學意蘊。張直心的《神思會通:魯迅小說的現代主義審美取向》認為,魯迅小說創作的成功實踐印證了魯迅化的現實主義理論與西方現代主義藝術方法并非勢不兩立,恰恰相反,它蘊涵著集合諸種方法沖突作用力的開闊性。李春林的《魯迅與世界現代主義文學》也持同樣的觀點,他特別一反那種認為魯迅只是受西方現代主義影響的觀點,提出了“平行”說:“他并未完全拋棄傳統現實主義,而又融入了新的‘文學趨勢’——現代主義”。
張箭飛的《魯迅小說的音樂式分析》認為,魯迅小說中的許多章節和段落都契合了變奏、復格段、回旋曲、復調等音樂的旋律結構,具有獨特的音樂美。趙卓的《魯迅心理小說藝術綜論》認為,魯迅的小說大都屬于心理小說,它以豐富多彩的心理結構形態和圓熟深刻的心理表現技巧,率先打開了一個全新的審美視野,是帶動中國小說現代化轉型的先鋒創作。鄒賢堯的《魯迅小說的先鋒性》把魯迅小說放到今天的后現代文學的語境中,仍然發現了其形式的先鋒和前衛:“我們在先鋒作家作品中看到的‘敘事實驗’、‘語言狂歡’等等,在魯迅那里就有。魯迅在現代文學奠基時期發出的聲音,抵達遙遠的今天,依然清晰而鮮活”。朱壽桐的《〈吶喊〉:敘事的變焦》認為,《吶喊》的敘事方式可分為“宏觀敘事”、“中觀敘事”和“微觀敘事”三種。
對下層社會不幸者精神狀態的批判和鞭撻,基本上建立在魯迅改良社會、民族進步的宏觀視野上,屬于“宏觀敘事”,體現出的是作者對改造國民性的吶喊:“中觀敘事”則指作品將敘述的背景移到比較封閉的、日常的人生場景,將主人公移向一些準“不幸”者,即被拋離了上流社會軌道而直接墮入下流社會的讀書人,體現出的是作者對人性善的呼喚;而另外一些作品如《社戲》、《兔和貓》等,則主要是魯迅自我情感的微波細流的寄托與抒發,屬于“微觀敘事”。這三種敘事方式共同構成了《吶喊》的“表現的深切”。
篇9
文本互涉是研究魯迅鄉土小說思想意蘊和藝術形式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之一。在魯迅鄉土小說中存在著很多文本互涉現象,使文本內部和文本之間獨具連續性和整體感,從而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對話關系,加深了魯迅鄉土小說的思想性和藝術性。
【關鍵詞】 鄉土小說 文本互涉 對話關系
文本互涉,主要是指“不同文本之間結構、故事等相互模仿(包括具有反諷意味的滑稽模仿或正面的藝術模仿)、主題的相互關聯或暗合等情況。當然也包括一個文本對另一文本的直接引用”①。這種現象,不但在同一文本之間體現,而且也在同一作家的不同文本之間體現。因為作家筆下描述的對象,總是處于三維共時狀態下的立體化對象,由于語言表述的一維性,使得作者不可能在有限的段落或篇幅,塑造他心目中完美的藝術形象,有些作者甚至在所有的作品中也未必能完整地表現他全部的思想觀念,所以作者必然會在潛意識里多次修補他的作品,從而導致文本之間的對話。魯迅的鄉土小說更是如此。
一
文本內部的互涉現象,通俗一點說,就是文本內部的一種對話關系。即文本內部的上下文關系,文本顯義與隱義的承接關系,文本題與主題間的照應等。這種關系必須落實到文本的物化形式上才能較好地說明。
《祝福》的開頭渲染了舊歷年底大年三十的盛大景象,天空中“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間時時發出閃光”,到處都能聽到“鈍響”的“送灶的爆竹”聲,“空氣里已經散滿了幽微的火藥香”。在這樣的氣氛烘托下,“家中卻一律忙,都在準備著‘祝福’”。這景象雖隆重但也壓抑,和結尾的“只覺得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即互相以對方為依托,又都反過來呈現出對方的微妙的對話效果。這一對話,不是以一方來說另一方,而是雙方互相加以言說,并也對相互的言說予以反應。進言之,這種對話與其說是作為作家的魯迅頭腦中擬構的,毋寧說是語言規則本身的規定,也毋寧說是人們的接受心理上具有的“格式塔”的慣性,人們在感知外物時往往是將它們看成一個聯系著的整體。
在《藥》中,華老栓一家與夏瑜一家的悲劇故事,由兩家姓氏的組合可以概括為“華夏悲劇”,即由具體的人物和故事寫出了中國社會的悲劇,而用小說末尾的墳上“分明有一圈紅白的花”,暗示出悲劇之后可能有的新的希望。在這里,小說的具體生動性與整體象征性,語義與象征義之間就有了一種對話關系,象征意蘊要由具體描寫襯托才有血肉,具體描寫又得靠象征意蘊才有深度。《狂人日記》《長明燈》莫不如此。
魯迅以非凡的洞察力和廣博的知識,在狂人與瘋子作為“精神界之戰士”之間,“在形象與語意義之間發見到某些類似點”。籠罩社會的傳統勢力從來就把“精神界之戰士”及覺醒的叛逆者和改革者,當做是狂人與瘋子的胡思亂想;而叛逆者和改革者在對待壓迫的敏感和抗爭上,在對待舊生活常規的驚人的懷疑和破壞上,在執著地追求自己的目標上,或許與狂人與瘋子有著某些表面上的相似。狂人和瘋子的隨意聯想和雜亂無章的語言也便于寄托作者的真實意圖,這正是利用和發揮了形象和意義之間的“一種內在聯系”,它在完全不違背生活邏輯和人物真實性和統一性的情況下,巧妙地將象征意義融于具體的描寫之中,通過狂人的許多瘋話和瘋子的一些超常舉動,來寄托作者對幾千年來封建制度和封建傳統的深廣憂憤與哲理思考。
對此,我們當然也還可以說這是魯迅在構思、寫作該小說時就有的思想,因為他一直反對在藝術表現上的淺、直、露,認為“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魯迅的所謂“詩美”,也即是詩的情景交融的境界,詩的含蓄和韻味。魯迅不僅在他的散文詩里顯示“詩美”,而且在他的鄉土小說中同樣追求“詩美”。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考慮到這種追溯作者“原意”的思路在有些場合下是行不通的,譬如《紅樓夢》的主題探討,就可以從政治到宣,從影響國家大事的“反清復明”思想到作者的個人情感遭際等方面做很大跨度的躍動,我們最好還是將“原意”這一幾乎無法稽考的問題擱置起來,將其看做是文本內部的一種意義上的對話關系,它可以有一經寫出就獨立于作者控制的能力,這樣才能給各種對文本的釋讀敞開一道大門,使對文本的閱讀有更多意趣。
二
文本之間的互涉現象,是指文本作為一種話語來顯示它的存在時,各個文本之間也就有了對話關系,其中一個文本的狀況對另一個文本的狀況就會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相互都以對方作為文本,自己則成為描述的話語。
魯迅的鄉土小說,雖然大多屬于短篇,最長的《阿Q正傳》也只能勉強稱為中篇。但是從文本結構上看,我們可以把魯迅創作的全部小說視為一個互涉的整體,也就是說,把小說中的主要人物、場景和話語都看做是互相關聯、互相補充的,就像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那樣。雖然魯迅并沒有運用“人物再現法”和“分類整理法”把他的全部小說組織起來,但只要稍加留意就會發現,魯迅時不時地通過小說人物之口或敘述人物語言,或明或暗地提醒著讀者,他的小說中的人物和環境是具有內在一致性和結構互補性的。
談到環境,這就不得不談到“魯鎮”。李歐梵通過分析概括為:“從一種現實基礎開始,在他二十五篇小說的十四篇中,我們仿佛進入了一個以S城(顯然是紹興)和魯鎮(她母親的故鄉)為中心的城鎮世界。”②張定璜說得更為明白:“魯鎮只是中國鄉間,隨便我們走到哪里都遇到的一個鎮,鎮上的生活也是我們從鄉間來的人兒時所習見的生活。”③王瑤、劉綬松、張畢來等老一輩學者他們也認為,魯鎮就是指中國的農村,魯鎮和未莊上的人主要就是地主和農民,人物的沖突或主人公的悲劇就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壓迫關系的表現④。20世紀80年代以來,嚴家炎、錢理群、溫儒敏、楊義等學者也都注意到了魯鎮和其他鄉土小說作家作品中的其他市鎮。因此,他們在概括這一場域時,都在把這一場域界定為農村的同時,加上括號注明:“或小城鎮。”⑤魯迅雖然無意去描畫魯鎮,鋪敘開“鄉土小說”作者筆下那樣的“風俗畫”“風情畫”“風景畫”的鄉土色彩⑥,但是,魯鎮卻是魯迅建構鄉土小說的一個重要形式,主題、思想、人物行動的邏輯和方式、人物關系結構等這些營造作品“基調”和氛圍的要素都統一在這個場所中。
我們仔細咀嚼魯迅的鄉土小說就會發現:在魯鎮這個環境中,人物和環境是相互勾連的。《 孔乙己 》中咸亨酒店的隔壁就是《 明天 》中單四嫂子的家;《 風波 》中發生的事就在未莊附近的一個村子里;當七斤上城被剪掉辮子的時候,阿Q正在做著他的造反發財夢……順此思路,我們似乎可以做出進一步的推斷:《 阿Q正傳 》中的趙太爺,《 風波 》中的趙七爺,《 祝福 》中的魯四老爺等,說中間經常往來甚至還密謀過什么事情。還有未莊的男女和城里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吉光屯那些怕自己變成泥鰍的老小,魯鎮上又冷又尖的人們,《 示眾 》中愛看熱鬧的小市民等這些看客簡直是一個面孔。
按照巴赫金的看法,“小說不是建筑在抽象的思想分歧上,也不是建筑在純粹的情節糾葛上,而是在具體的社會雜語上。”⑦他進一步指出:“長篇小說是用藝術方法組織起來的社會性的雜語現象,偶爾還是多語種現象,又是個人獨特的多聲現象。”⑧在這里,巴赫金所強調的是長篇小說的“雜語”現象和特質,而魯迅的兩個短篇小說集是否也具有同樣的“雜語”現象和特質呢?
魯鎮是《 吶喊 》《 彷徨 》中的主要人物、場景和話語的連接中心,各個不同層次的話語社團就在魯鎮這個背景中存在、展開,并相互抗衡著,形成一個豐富龐雜的話語系統。下面我們就借用巴赫金的話語系統,試著把魯迅小說中的各個不同層次的人物化分為六個層次。
第一個層次,是代表封建勢力的紳士老爺們,如《 阿Q正傳 》中的趙太爺,《 離婚 》中的七大人,《 祝福 》中的魯四老爺,《 高老夫子 》中的高老夫子等,他們擁有土地,具有絕對的權威,是封建統治的維護者,而且是話語權力的擁有者;第二個層次,是代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 阿Q正傳 》中的阿Q,《 明天 》中的單四嫂子,《 祝福 》中的祥林嫂等,他們受壓迫、受損傷、受歧視,常常受制于第一層次的人物,他們喪失了自己的話語,只能以他人的話語來作為自己的話語;第三個層次,是代表魯鎮和未莊的看客,《 阿Q正傳 》中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 長明燈 》中吉光屯那些怕自己變成泥鰍的老小,《 祝福 》中魯鎮上又冷又尖的人們,《 示眾 》中愛看熱鬧的小市民等,他們多數沒有名姓,麻木不仁,得過且過,稀里糊涂地混日子,他們往往又取笑、調侃甚至欺侮第二個層次的人物。他們是以傳播他人的話語,擴散他人的話語為己任的話語集團。第四個層次,是代表知識分子階層的,《 孔乙己 》中的孔乙己,《 祝福 》中的“我”等,他們雖然擁有知識,擁有自己的話語,但常常授人以柄,出于無奈和尷尬的境地;第五個層次,《 狂人日記 》中的假洋鬼子、長衫黨人等,他們代表新舊混雜的話語集團。由于時代的變遷,他們從第一層次中分離出來,有機會接受“新學”,掌握了一種新的話語權,但他們還擺脫不了傳統話語對他們的影響;第六個層次,是代表已覺醒的人,《 狂人日記 》中的狂人,《 長明燈 》中的瘋子,《 孤獨者 》中的魏連殳等,他們是新生的力量,屬于啟蒙者階層但往往為社會所不容,被視為真的“狂人”或“瘋子”,他們是新生的話語力量,將在中國社會的變革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這樣看來,《 吶喊 》《 彷徨 》中的人物是能夠分類的,并且是成系統的。如果把這些小說聯結起來,將這六個層次的人物像巴爾扎克的《 人間喜劇 》那樣,運用“人物再現法”和“分類整理法”,讓人物依次上下場,不斷地交換場景,那么魯迅小說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更加清晰的思路和線索。那些趙太爺一類的“爺字輩”,祥林嫂一類的“嫂字輩”等,完全可以作為一個人或一類人在小說中出現。縱觀《 吶喊 》《 彷徨 》,“它們無論在其思想性還是在其藝術性上,都更多地具有內在的統一性。”⑨因此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把魯迅的《 吶喊 》《 彷徨 》視為一個統一而完整的長篇小說。
魯迅在《 中國小說史略 》里評析《 儒林外史 》的結構特征時,說其“雖云長篇,頗同短制”,而魯迅先生的小說集《 吶喊 》和《 彷徨 》,在筆者看來,卻系“雖云短篇,頗同長制”。我們的確可以把他的中短篇小說應該視為一個完整的長篇小說,當做一個共同的文本世界。魯迅先生正是以一種“散點透視”的筆法讓各種人物登場、下場,表現其思想觀念。而這些人物,卻又往往在文本對話中“互涉”,可以在互照互證的對讀中領悟到更為深刻的理解。
三
魯迅小說文本對話還存在于獨特的觀念和意象之中,這是有別于其他作家的小說很獨到的地方,它體現了魯迅小說文本之間的內在氣韻,是形成魯迅小說文本互涉不可或缺的一個方面。
錢理群說過:“第一個有獨創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總是有自己慣用的、幾乎已經成為不自覺的心理習慣的、反復出現的觀念(包括范疇)、意象;正是在這些觀念、意象里,凝聚著作家獨特的精神世界和藝術世界。”⑩錢理群的《 心靈的探尋 》就是從《 野草 》中捕捉觀念和意象進行深入開掘和探尋的。魯迅小說中出現的觀念和意象雖然沒有《 野草 》中那么集中,那么飽含著詩意,然而我們在對魯迅小說細細的咀嚼中,同樣也能感受到魯迅所慣用的熔鑄著魯迅深刻思考和濃烈情感的觀念和意象,這些觀念和意象與小說中所描述的故事和情節融為一體,形成了小說中內在的對話關系。
魯迅小說中出現最多的人物是看客。魯迅在《 復仇 》中把看客比作“爬在墻壁上的槐蠶”,并說他們“拼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槐蠶”散出溫熱,使人討厭,“偎倚,接吻,擁抱”令人想起擁擠、煩躁、不安。魯迅正是看到了看客的郁悶和麻木,才會幾乎篇篇都讓看客出現,使看客之間形成了較為廣泛的對話關系。《 阿Q正傳 》中圍觀阿Q殺頭的“許多張著嘴的看客”,像“螞蟻似的”左右跟著,并且還伴隨著“豺狼”似的喝彩聲,這和《 祝福 》中那些無聊的魯鎮人為了在祥林嫂身上尋找“新的趣味”,許多人“都又來逗她說話了”,這又和《 孔乙己 》中,“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著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臉上又添上新傷疤了!’引得眾人都哄笑起來:店內外充滿了快活的空氣。”這些看客真是如出一轍,他們不是魯鎮的,就是未莊的,好像商量過似的,一樣的在取笑他人,揭他人的“傷疤”。魯迅還專為這些看客寫了《 示眾 》這篇小說,似乎在做總結發言。這篇小說沒有情節,沒有名姓,只是為了“看”。錢理群在分析這篇小說時說:“小說中所有只有一個動作:‘看’;他們之間只有一個關系:一面‘看別人’,一面‘被別人看’,由此而形成一個‘看被看’的模式。”進而說這是“中國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也是“人與人的基本關系”{11}。
魯迅在《 狂人日記 》中首先提到了黑屋子。這個黑屋子魯迅在《 吶喊·自序 》中有較為詳細的闡述,這是一個“絕無窗戶”的鐵屋子,并且“里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而且“不久要悶死了”,這是一個后國民麻木而昏睡的生命狀態,是對當時黑暗現實的真實寫照,同時也反映了為民族的苦難和未來而憂患的一位現代啟蒙者對歷史和現實的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可以說這個黑屋子和《 狂人日記 》中的黑屋子給人的感覺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狂人已被月光驚醒,受著“臨終的苦楚”,想“掙脫出來”,但“出了一身汗”,雖如此,但“你不能說沒有摧毀這鐵屋子的希望”。《長明燈》中也描繪了一個覺醒的瘋子,他一心想吹熄吉光屯中從梁武帝時傳下來的長明燈,但他的舉動遭到了傳統勢力的強烈不滿,因此也被關進廟里一間有粗木直柵的只有一小方窗的黑屋子里。這種黑屋子與狂人的黑屋子是何等的相似。1925年,魯迅在《聰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中,也描繪了一個“晦氣沖著鼻子,四面又沒有一個窗”的黑屋子。從狂人在黑屋子里發出“救救孩子”的吶喊,到瘋子的“吹熄它”、“我放火”的舉動,到傻子的義憤填膺的破屋開窗,體現了層遞式的對話關系,顯示了魯迅思想的發展和變化。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還談到了橫跨在人們中間的一堵“高墻”:“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柜臺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柜臺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柜臺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12}少年魯迅在質鋪和藥房所面對的高高的柜臺,顯然是魯迅鄉土小說中反復出現的高墻的原版。魯迅少年時代在高高的柜臺前所感受到的社會不公、世態炎涼都深深地烙入他的心底,因此,他鄉土小說中的“高墻”意象,應該是過去生活的感受和經驗。
《故鄉》中閏土和“老爺”之間,《孔乙己》中穿著長衫坐著喝酒和穿著短衣站著喝酒的人們,《藥》中的革命者夏瑜和華老栓之間,《祝福》中祥林嫂和魯鎮那些幸災樂禍的人們,都可以看到有一堵高墻森然可怖地矗立著。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中再次談到這堵高墻:“別人我不得而知,在我自己,總仿佛覺得我們人人之間各有一道高墻,將各各分離,使大家的心無從相印。”{13}魯迅將其視為是“古訓所筑成的高墻”。深切地期望拆毀這堵高墻,因此在《故鄉》的尾聲中,“我”真誠地期望下一代的宏兒和水生“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
另外,魯迅鄉土小說中還存在著許多觀念和意象。如民俗、黑夜、月光、荒原、吶喊等,這些觀念和意象在小說中都形成了相互照應和補充的對話關系,這些關系大大加深魯迅小說創作的獨特與深刻的思想內涵。
在文學史上,任何新的巨著的問世都可能追溯到一個古老的源頭,從而影響到整個文學史的局部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寫,這也都是文本間“互涉”關系的體現。羅蘭·巴特曾說:“所有寫作都表現出一種與口語不同的封閉的特性。寫作根本不是一種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條僅僅為語言意向的通行而敞開的大路……它根植于語言的永恒的土壤之中,如同胚芽的生長,而不是橫線條的延伸。它從隱秘處顯現出一種本質和威懾的力量,它是一種反向交流,顯示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勢態。”{14}小說文本一方面確實可以用于交流,另一方面又如巴特所說是“反向交流”,即文本不斷地接納詮釋者,并圍繞詮釋者再作詮釋,這就形成了循環式的對話關系。西方結構主義批評理論也強調事物之間關系的研究,認為任何一個系統的個體單位只有靠它們彼此間的聯系才有意義,這被他們也稱之為“文本互涉關系”。現代意象批評家也常常吸收結構主義的批評的“文本互涉”的觀點和方法,認為“文本中的某一意象的隱喻——象征涵義只是在它與構成整個龐大文學、乃至文化傳統的諸文本的相互關系上才有意義”{15}。文本的這種在顯示自己對話意義的同時又不斷形成新的對話意義的這一特性,從文本互涉以外的角度是無法窺見的,魯迅小說就是最好的見證。
① 王耀輝.文學文本解讀[M].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167.
② 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128-129.
③ 張定璜.魯迅先生[J].現代評論. 1925,(7)、(8).
④ 范伯群.論都市鄉土小說[J].文學評論.2002 (1).
⑤ (英)湯因比.藝術的未來[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2,92.
⑥ 李歐梵.鐵屋中的吶喊[M].岳麓書社,1999,66.
⑦⑧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白春仁等譯,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3,40-41.
⑨ 丁帆.朱曉進.中國現當代文學[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10.
⑩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M].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19-20.
{11} 錢理群.魯迅作品十講[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39.
{12}{13} 魯迅.魯迅全集 (第三卷) [M].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52.
篇10
重評的發生與新時期文學的規劃
80年代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譯介與接受
前夕激進文人詩文中的新型婚戀意識書寫
論后期創造社的實踐觀及其實踐之維的淪陷
工具革命:“活”與“死”的實用辯證法——論白話文理論的命意基點及內在理路
日本的現代批判與魯迅
紫發女孩·暮年老翁·壯年過客——試析魯迅《過客》中的三位“過客”
魯迅與蘇童
“當代文學史”的理論建構與實踐——評陳曉明《中國當代文學主潮》
論舊體詩詞的文學史書寫問題——從李遇春《中國當代舊體詩詞論稿》說開去
八十年代北京詩歌發展概況
永世為農的文學表達——重讀李銳《厚土》系列小說
論《芙蓉鎮》的傳統
由“殊途”走向“同歸”——柳青《創業史》中“民間話語”和“政治話語”的融合
道德理想主義的困境與小說的折斷性敘述——評許春樵長篇小說《酒樓》
論阿來小說中的反諷精神
文學的另一種“現代啟蒙”:畢淑敏寫作意義略論
走進新時代——從劉震云寫作風格的變化看新世紀城市生活轉變
文學與性別研究領域的新收獲——讀畢新偉《暗夜行路:晚清至民國的女性解放與文學精神》
論梁啟超戲劇
試論20世紀初小說中“英雌”構型的基本要素
沈從文“湘西世界”中的“動物世界”
中國當代女性主義文學的藝術價值
肉身之痛與靈魂之美——論新時期農村小說的悲劇風格
論戴厚英的小說創作
在波詭云譎的歷史中叩問人性——評艾偉長篇小說《風和日麗》
從“底層寫作”到“打工詩歌”的批評綜述
魯迅與庫切小說的批判精神之比較
試論莎士比亞對早期戲劇創作的影響
敘述的魅力——張愛玲與張恨水言情小說敘述者形象之比較
與唐對話——從匡燮文化散文專著《唐詩里的長安風情》談起
晚清旅美華人文學的美國形象和中國形象
世俗的死滅與神性的顯明——陳映真短篇小說《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意義闡釋
羅門蓉子六十年詩歌創作研討會綜述
篳路藍縷的學科研究史——評黃修己、劉衛國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
作為方法的“對話”——讀張麗軍的《對話與爭鳴:新世紀文學文化熱點問題研究》
評古遠清《香港當代新詩史》
現代性幻象——基于聽覺維度的理性主義文化批判
文史見道——章學誠“六經皆史”論
南理工詩學研究中心舉辦長篇散文體小說《平民之城》研討會
五四新文學理性與非理性的思考
批判與重構——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文學史寫作視野下命運及文學革命
試論“家庭苦情”系列對“傷痕文學”的藝術超越——重讀張平1980年代的“家庭苦情”系列
祥林嫂的人生困境與魯迅的現代性焦慮——以《祝福》為中心
異中求同:魯迅與創造社、太陽社的論爭——魯迅與中國左翼文學的發生之二
順逆之間的文化接力——關于“魯迅與莊子”關系的研究
21世紀初魯迅與中國文化關系研究新趨勢
“村委直選”與鄉土中國——李洱長篇小說《花腔》到《石榴樹上結櫻桃》閱讀隨筆
精神還鄉與宏大夢魘——評阿來《空山》
回憶不止于撫摸——評楊劍龍長篇小說《金牛河》
三城記——都市景觀與作家心態
后學語境中的女性主義日常生活理論及其啟示
越界狂歡:肉體獻祭之譫妄及消解——對木子美等網絡現象性別政治的文化解讀
戴著鐐銬起舞——解讀《紅日》的情愛敘事
朱曉平知青小說創作的藝術風格
精神的難度與韌性——讀譚湘散文
將筆當槳以詩證史——評《舟行紀——同濟百年詩傳(上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