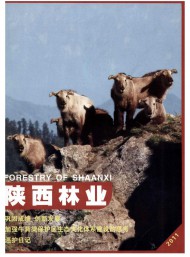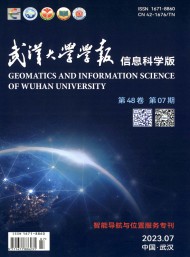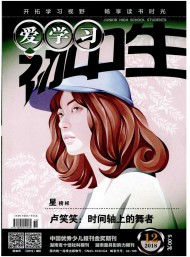本杰明巴頓臺詞范文
時間:2023-04-11 10:20:1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本杰明巴頓臺詞,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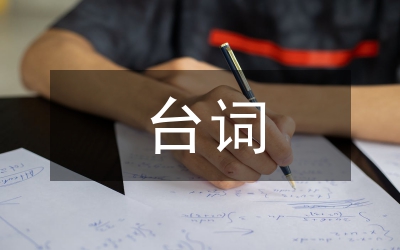
篇1
[關鍵詞] 《返老還童》;大衛•芬奇;本杰明•巴頓;敘事策略;主題
電影《返老還童》講述了主人公本杰明富有奇幻色彩的“返老還童”的生命經歷。編劇在保持原著傳奇性的風貌下,對其進行了精彩改編,融入了真摯的情感與深刻的哲理。與此同時,強大的演員陣容和逼真的視覺效果,也為影片大大增色,一舉囊括了第81屆奧斯卡最佳化妝、視覺效果和藝術指導三個獎項。本文試圖從別具匠心的敘事模式、獨特的意象以及富有哲理意味的臺詞三方面,來分析影片的敘事策略及其呈現出來的主題,即導演對時間與生命的獨特思考。
一、別具匠心的敘事模式
影片為了呈現出主人公本杰明富有奇幻色彩的“返老還童”的生命經歷,采用了他者敘述與自我追憶相結合的敘事模式來講述主人公“倒帶般”的人生。不僅制造出一種“陌生化”效果,還傳達了主人公對回流的生命狀態的獨特思考。
首先,影響影片敘事模式的兩條敘事線索:一條發生在2003年新奧爾良的颶風來臨之際,年老的黛西躺在醫院病床上病重垂危,女兒卡洛琳守護在她身旁,拿出塵封已久的日記本念給她聽――黛西臨終時的追憶;另一條則是這本日記的主人本杰明從1918年開始的傳奇經歷――本杰明對其人生軌跡的自述。兩條線索各自展開,又彼此交錯著向觀眾娓娓道來本杰明的傳奇人生,讓觀影者產生了一種時空交錯的感覺。
其次,我們需要了解導演對此所采用的敘事手段。影片中,在沒念日記之前,卡洛琳與母親黛西在鏡頭前的對話屬于第三人稱敘事;開始念日記時,卡洛琳的朗讀則屬于第一人稱敘事;緊接著本杰明的自述通過他的第一人稱敘事進行過渡,主要是以畫外音的形式來展開。我們以影片開頭那一段為例:“這是我最后的遺言,也是遺囑。我沒留下什么,沒財產,沒錢,真的。我孤獨地來,孤獨地去,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的名字叫本杰明,本杰明•巴頓。我的出生很不尋常,那時一戰剛結束,后來我聽說,我出生的那個夜晚特別好……”電影里對于兩個場景的變換常常采用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即在卡洛琳的朗讀聲中畫面逐漸從病房內轉換到本杰明的故事場景,同時卡羅琳的朗讀與本杰明的自述之間重疊了部分聲音和畫面,兩者的聲音互為畫外音。除此之外,影片還利用了大量的閃回鏡頭去輔助呈現這一敘事模式。對比畫外音的主觀情感表達,閃回鏡頭更具客觀寫實性,它是該片使用最多的剪輯方式。這樣的敘事手段不僅讓影片具有更加厚重的時間感,而且極具張力。如影片中本杰明不同尋常的出生就是通過閃回形式,用雙重倒敘的方式表現出來。片頭黛西的敘述將畫面切回到一戰結束之際,她講到新奧爾良的火車站里安裝了一個新的掛鐘,掛鐘的制造者是蓋圖先生,他的兒子不幸死在了戰場上。蓋圖為了寄托喪子之痛,將掛鐘設計成按照逆時針運行的樣子,影片中隨之出現一系列時間倒流的鏡頭――在戰場上死去的人們重新站了起來,又回到出發去征戰的火車站。
影片別具匠心的敘事模式,不僅讓觀眾看到了生命狀態極其豐富的人物和真實奇幻的情節,還看到了影片是如何將21世紀的技術和19世紀的文學敘事技巧相融,把主人公逆行的生命歷程與回環往復的時空流轉互滲相交,用以表現20世紀的這部史詩傳奇。
二、獨特的意象
從某種角度而言,《返老還童》是一則關于時間的寓言,影片在精彩的故事背后,常常會有時鐘的滴答聲響起,時間與人之間的關系成為理解本片的一個關鍵點。導演在影片中設置了一些意象來巧妙地隱喻時間,最主要的無疑是時鐘意象,特別是片中倒行的時鐘。影片一開始就不惜用了5分多鐘從黛西的視角來講述一段鐘表匠的故事:雙目失明的鐘表匠蓋圖先生制造出一口舉世矚目的倒行大鐘,希望時間可以倒流,讓在一戰中犧牲的兒子可以活過來。在這個荒誕但卻美好的期盼中,本杰明出生了,如同蓋圖先生的愿望被實現了。影片將本杰明逆行的人生軌跡與大鐘的倒走聯系起來,意味著時光能夠倒流。實際上,時鐘作為一種寓言式的隱喻在影片中隨處可見,充滿象征意味。如影片最后,給了那座倒行的時鐘一個特寫鏡頭,颶風席卷了整個新奧爾良,棄置在倉庫里的大鐘依然在靜靜地倒走。顯然,這里的時鐘隱喻了時間和生命。
另外,蜂鳥也是影片中較為獨特的一個意象,它一共出現過三次:一次是在小酒館里邁克船長向人們介紹它;一次是本杰明在告別拖船時;第三次則出現在颶風來襲前黛西的病房窗外。影片告訴我們,“蜂鳥不是一般的鳥類。它的心率達到每分鐘1 200下,它的翅膀每秒扇動80次。要是讓它無法扇動翅膀,不到10秒就會死掉。這不是一般的鳥,簡直就是奇跡。有人用攝影的方法觀察了它的慢動作,它們的翅膀是這樣的。”船長用手比劃出一個在數學上代表“無限”的符號。對于蜂鳥有限的生命而言,它的心跳和飛翔就是無限和永恒。在這里,蜂鳥不僅僅是一種惟一可以向后飛行的鳥,它與本杰明一樣,都是宇宙中奇特的生命。它讓我們明白:“不論生命是向前還是向后,也許所有的一切都不意味著什么,只要我們好好對待我們的生活,生命沒有什么不同。”[1]
養老院是影片中又一個別具意味的意象,它基本貫穿了整部影片。對于常人而言,養老院是走向生命終點的地方。但對本杰明而言,它卻是生命開啟的所在,是思考生命意義的場域。在這里,老人們溫和、淡定、豁達、幽默的性情讓本杰明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沒有留下任何心理陰影。他不斷目睹死亡,但從未抱怨,淡定地面對死亡,思考生與死這一關于生命狀態的人生主題。正如影片中本杰明的旁白所說的一樣,“死亡也是這里的常客,人們來到這里,又安靜地離去。你可以感覺到有人離開了。那時房子里總是寂靜無聲。這是個值得成長的美好地方。在這個地方,人們過往生命中的矛盾。每天只關心天氣,洗澡水溫度,一天行將結束的陽光。總會有人來重新填補死者的房間。”養老院與世無爭的那種氛圍,為他的性格打上了善良、平和、從容的底色,讓本杰明比其他人更早看透了生命的無常。
縱觀全片,其中的“每一個意象都值得慢慢咀嚼、細細品味,而且這些意象出現時的片段也都意味深長、發人深省。一個個象征和隱喻穿插在影片中,揭示了一個個深邃的人生主題”[2]。
三、富有哲理性的臺詞
梅普爾夫人是讓本杰明最記不清楚名字但卻印象最深的一個人――養老院里那位戴著鉆石、穿得很漂亮但卻孤獨的老婦人。她在影片中話雖不多,但句句充滿哲理。在教本杰明彈鋼琴時對他說:“無所謂你彈奏得怎樣,重要的是你彈琴時的感受,情不自禁沉浸于音樂中。”這就像是每個人離去的時候,對于自己走過的一生,他收獲的不是名利和財富,而是他的經歷一樣。也即是說,生命的狀態比生命本身更重要。當梅普爾夫人幫本杰明理發時,她又說道:“本杰明,我們命中注定要失去所愛之人。不然我們怎么知道,他們在我們生命中有多么重要。”這句話,讓本杰明陷入了深思。爾后,面對自己身邊的親人一一離去時,我們都看到了他的從容淡定與平和。
同樣,奎尼作為收養本杰明的一位黑人女性,她的臺詞也深深地啟發著影片內外的人。她說:“這個孩子,他是個奇跡。”她將每個生命都看做是上帝的兒女,他們生而平等。爾后奎尼對韋瑟斯說“你永遠不清楚接下會發生什么”,一句簡淡的話,卻飽含著深意;當本杰明的童年充滿了別人對他的嘲弄時,奎尼卻告訴他:“每個人對于自己的感受都不一樣,但是我們的終點是一樣的,只是走的路不同罷了。你有你自己的道路,本杰明!”這讓格外孤獨的本杰明備受鼓舞,更加勇敢地面對只屬于他的孤獨,就像本杰明的黑人朋友歐緹。歐緹經歷坎坷,曾經被關進動物園,每天有3 000人來動物園把他當做動物參觀。然而,他卻開朗自信。他曾對本杰明說:“很多時候人們是孤獨的。但我告訴你一個秘密――無論什么膚色,什么體型,人們都是孤獨的。但可怕的不是孤獨,而是懼怕孤獨。”話語之中,我們都能感受到奎尼的博愛和歐緹的樂觀開朗。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一生被閃電擊中七次但還好好活著的多斯先生,戲份不多但卻十分出彩。無論是在修屋頂、過馬路取信,還是遛狗、開車想著自己的心事,他都會遭到意外的閃電之災。即便如此,他卻認為,“雖然眼瞎了一只,耳也聾了,但老天爺總是不斷地提醒我,讓我知道自己還活著,有多幸運。”面對生命中的諸多無常,我們從多斯先生身上看到的不是抱怨,而是一份平靜。確切地說,應該是平和,這一點讓本杰明也感觸良多。與多斯先生的平淡中顯見真意的話相比,邁克船長臨終時的遺言則更加觸動了本杰明:“不順心的時候,你可以像瘋狗一樣發狂,可以破口大罵,詛咒命運,但到頭來,還是得放手!”這一段臺詞,不僅讓本杰明面對命運的無常時,懂得了灑脫和釋然。
正如導演通過本杰明在影片中的獨白一樣,揭示了他奇特但又真實的生命感受。他逆行的人生軌跡,“使其在他人身上毫無經驗可循,只能靠自己積極的嘗試與感受。從而也就對生命、生活、情感、世界獲得了更加深刻的認知、思考與理解。”[3]這也是影片最為打動人心的地方。發人深省的是影片最后通過兩組蒙太奇鏡頭,以畫外音的形式去表現兩段富有深意的臺詞:“一件事情,無論是太早,或者對于我們來說太晚,都不會阻攔你想成為的那個人。這個過程沒有時間的期限,只要你想,隨時都可以開始……我希望最終你能成為你想成為的那個人,如果和你想象的生活不一樣,我希望你能有勇氣――重新啟程。”[4]這是電影里本杰明在日記本里寫給女兒卡洛琳的一段話。另一段則是片尾:“有些人,生來就注定可以悠閑地坐在河邊;有些人,會被閃電擊中;有些人,會音樂;有些人,是藝術家;有些人,是游泳健將;有些人,懂紐扣;有些人,懂莎士比亞;有些人,是媽媽;有些人,是舞者。”這兩段深刻而不晦澀、感人而不煽情的臺詞,讓人感受到寓意深遠的人生主題――勇于開啟生命的征程,勇于面對一切全新的可能。
四、結 語
他者敘述與自我追憶相結合的敘事模式,講述主人公“倒帶般”的人生,讓我們對影片中的奇幻色彩多了一份真實感;別具意味的獨特意象,適時出現,讓我們從物的層面體會到了導演所要指向的富有深意、引人深思的主題表達;充滿哲理性的臺詞,敘議結合,則讓我們從人的層面對時間與生命的獨特思考有了更加深入細微的感受:假如生命可以重來,我們應該珍惜匆匆時光,用行動去實現生命的無限可能,體味人生、笑對挫折、順應無常,勇于開啟生命的征程,勇于面對一切全新的可能!
[參考文獻]
[1] 李斌.傳奇具備真實,魔幻飽含情理――《返老還童》評析兼與原作比較[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09(03).
[2] 李超.解讀電影《本杰明•巴頓奇事》反映出的人生主題――從時鐘隱喻談起[J].電影文學,2009(22).
[3] 林瑜.時間不止 生命不息――評《本杰明•巴頓奇事》[J].電影文學,2009(16).
篇2
——觀《返老還童》有感
工商1502高依晨
其實在大學之前真的沒有太多自己的時間,加上最近剛好在經歷一段不曾體驗但又不得不說很難熬的失戀時間,也不只是因為在別人提起經典而自己不曾聽聞而慚愧,也不覺當別人都在影院追著最新院線時自己還抱著電腦,看著上個世紀的懷舊情懷,總之各種原因,最近在惡補老片子。
其實內心也一直有經典情懷,總覺得即便會有人噴,會有那么多不解,但或許他被稱為經典總有一種不可企及的高度,或許正是"經得起多大的詆毀,才受得起多大的贊美".
《返老還童》是印象最深的,且不說女王凱特和男神皮特的演技,或者其中我窺探到最多的是班杰明與黛西不同尋常的愛情,這世間的陰差陽錯總有一種讓你遺憾入骨。第三次遇見,無論生理還是心理,他們都剛剛好相會交融,度過一生之中最寶貴但在常人看來在尋常不過的戀人時光,如若將凡人比作同向的涉嫌,那么他們就剛好是方向相反的射線,一旦相交,就再也沒有回頭。"當我皮肉松垮時,你還會愛我嗎?"從凱特口中吐出的臺詞溫和沉穩但斂著一種讓人難以抗拒的神傷;"當我長青春痘時,你還會愛我嗎?"他說。當他的女兒慢慢長大,他知道自己該離開,他收拾好要為母女倆留下的財產,將支票傾情放在屋內的書桌上,在黑暗的房間里,他想最后回望,卻正好迎上黛西的目光,四目相對時,我開始哭,一直哭,從流淚到哀嚎,哭到最后我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為什么哭,是他們明知相遇即分別的一生的愛情,是這世間所有的陰差陽錯造化弄人的人生,還是我自己。
這或許更是一場關于性命的領悟 ,一場一個人一個時代的史詩,影片以凱克先生為新奧爾良火車站制造的大鐘開始,一口倒走的大鐘,他想讓時光倒流,試圖戰死沙場的兒子重生,試圖減少一場戰爭的進行,還有麥克船長的藝術家夢,多次出現的雷聲是何用意呢?性命中的意外會有很多次,但即便這樣,這位老人仍坐在養老院中并沒有因雷擊而離世,在我看來,這是在告訴班也是告訴觀眾,人總是要完成生命帶來的使命,尋求安身立命之平和,安心和歸屬感。
"你可以像瘋狗一樣去對周圍的一切憤憤不平,你可以詛咒命運,但等到最后一刻,你還是得平靜的放手讓一切過去。"這句話在影片中出現過三次,一次是船長臨終前對班所說,一次是在父親離世前告訴他,最后一次是在他游歷世界知識告訴自己的。人生如白駒過隙,短到歡樂之時不過數年,這生死之間的一瞬,竟也是說來就來,凡物質必不永恒,但當死亡真的來臨,不管你以怎樣的姿態,也不論你是否做好準備,都請坦然放手,沒有什么可以長留時間太陽每一天都會照常升起,正如無法阻擋的降臨的出生與死亡一樣。
或者也窺探出了生命的意義,可能電影想給我們傳達的太多,又或者一千個人的一千種解讀過于深刻,這場奇遇,因為愛而顯得濃墨重彩。
蜂鳥
——觀《返老還童》有感
孫天辰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本杰明的成長與大部分普通人似乎是千差萬別。從一個八十多歲的老翁變成一個襁褓中的嬰兒,這是他奇異的人生旅途,而正是因為這樣的逆生長,注定了他的不平凡。
母親因為誕下一個八十歲的"男嬰"難產而死,父親因為恐懼將自己拋棄在養老院,這是本杰明人生的開始。之后的一段時間里,他蜷縮在輪椅上,過著一個"新生兒"不該有的老年生活,身體的衰老使他無法行走,直到他遇見了一個神父。
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上帝真的聽見了信徒呼喊"哈利路亞"時的篤信與真誠,總之,神父用他自己的方式,讓本杰明邁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跌了人生的第一跤,又第一次一個人爬起。就在本杰明站起后,神父卻倒下了,生死不知,但我能夠肯定的是,本杰明之后的路上,再也沒有遇過這個讓他邁出第一步的神父。
第一次帶本杰明走出那個滿是肥皂味的養老院的人,是一個勇敢的黑人,在本杰明的眼里,他有著講不完的冒險故事,和一個身材高大的女朋友。他讓本杰明第一次知道世界的奇妙,但他最終又踏上了冒險的道路,與本杰明草草作別,再也沒有出現。
本杰明還遇見了一個憶不起名字的老奶奶,他在日記中寫到:"有時候我們最不記得的人,我們對他的印象最深。"——而這個老奶奶,教會了本杰明彈琴。
音符的世界是最神奇的,鋼琴就像是魔術師的匣子,每按下一個琴鍵,就會有一個聲音從匣子里溜出來,雖然曲會終人會散,但就像老奶奶所說,"我們注定要失去我們愛的人,否則怎么知道他們對我們有多重要呢?".終于,在一個午后,老奶奶安詳的去世了,什么也沒有留下,只有溫煦的陽光照在身體上僅存的余溫,以及墻邊的那臺鋼琴……
有一天,本杰明拄著拐棍一搖一晃的出門時,結識了一個叫黛西的小女孩,黛西有著漂亮的眼睛。她用她藍色的眼眸,洞穿了本杰明與外表截然不同的內心世界,她發現本杰明與她之前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一樣,所以她愿意觸碰他布滿皺褶的臉,愿意與他靠在一起聽袋鼠的故事,直到他們分開。
后來,本杰明漸漸健壯起來,離開了養老院,上了一條名為切爾西號的拖船,認識了一個叫邁克的酒鬼、船長、懶蟲兼藝術家。邁克是一個痞子,也是一個瘋子,他帶著本杰明去妓院逍遙,讓本杰明第一次體驗了;他在身上紋出各種各樣的圖案,美其名曰藝術;他習慣喝的爛醉如泥,然后在周末的時候睡一上午;在遭遇敵軍的時候,他在駕駛室里憤怒的吼叫,嫻熟的操控著切爾西號。
他所做這一切,只是將對生活的無奈發泄出來罷了,只是將對無法完成藝術家這個理想的不滿發泄出來罷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在邁克被機槍打的肚破腸流,癱倒在陪伴他一生的切爾西號的駕駛艙之際,他對自己的一生做了一個總結:"不順的時候,你可以像瘋狗一樣對周圍一切憤憤不平,你也可以詛咒命運,但到頭來,你還是得放手。".邁克,就是這樣一條"瘋狗",最終,他平靜的放手了。
離開切爾西號,本杰明又結識了一個名為伊麗莎白的女人,兩人發生了婚外情,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美妙的夜晚,她也是第一個讓本杰明全心全意愛上的女人。但伊麗莎白選擇了離開,悄無聲息地結束這一段沒有結果的感情,只留下了一張字條:"Nice to meet you.".
本以為兩人的故事到此結束,可是造化弄人,多年以后,當本杰明在電視上再一次看見伊麗莎白時,她已經成為第一個成功游過英吉利海峽的女性,在接受采訪的時候,伊麗莎白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沒有什么不可能".那一刻我愣住了,就像影片中的本杰明一樣。即使已經分開多年,當年的感情依舊互相影響著,雖然僅有屈指可數的幾個日夜。伊麗莎白選擇了離開,但她還是盡力留下了對本杰明的一切感情。
在影片的最后,颶風襲擊了美國本土,大雨所積成的洪水涌進了各個角落,淹沒了屋里的那口巨大的鐘,黛西也在同時悄然離世。
其實不論你是冒險家、藝術家、舞蹈家、神職人員、鋼琴家、船長、游泳者、紐扣生產者、甚至被雷電劈了七次……時間就像流水一樣,會將一切都帶走,將你推向死亡,你明白,卻阻止不了,所以你恐慌,害怕淹死在這時間長河中。
但仔細想想,一個人的人生沉沒是必然的,但是一個人的人生沉默則是可悲的。重要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就好像本杰明的那個比喻——蜂鳥。
篇3
何謂“奇幻逆緣”?如果肥羅在科林蒂安還是腆著個大肚子在場上夢游,如果阿德回到弗拉門戈只是為了里約熱內盧夜店里豐乳翹臀的舞娘,如果貝隆、里克爾梅那種慢吞吞的足球早已被世人所遺忘,那么這段逆緣就無任何奇幻成分可言。事實明擺在我們眼前,近五年來這一伙“南美返鄉團”絕對不是歷史上那些“養老團”,他們回來了,他們的職業生涯因此煥發出“第二春”,或者說“第×春”。
在大學生隊這種級別球隊踢球的貝隆尚能被南美各國足球記者推選為2008年南美足球先生,此時,你也許才會發現,這群人不是越變越老了,而是越變越小了,就像電影里的本杰明?巴頓一樣。
“明天,當我滿臉長滿青春痘時,你還會愛我嗎?”這句經典臺詞也是這群南美回鄉老兵留給你我最浪漫的一個問題。
早去早回 畸形掠奪的回扣
職業生涯參賽440場,進球134個,創造這個數字的不是一名前鋒,而是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隊的偉大隊長帕薩雷拉。1982年,帕薩雷拉加盟佛羅倫薩,后來又轉投國米兩年,1988年他返回河床,并于1989正式掛靴。帕薩雷拉的履歷體現了他那個時代眾多識時務的南美球員希望“善始善終”的心愿,值得注意的是,帕薩雷拉出國時已年近30歲,返回阿根廷時已年滿35歲。
無獨有偶,薩莫拉諾返回智利科洛科洛隊、鄧加回到巴西國家隊時都已是36歲的高齡,馬拉多納回博卡時也35歲了,那個時代的南美球員返鄉更像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退役儀式”,形式主義遠遠大于實際意義。
據法國《隊報》2008年11月的統計,最近十年,南美洲僅巴西每年向全世界輸送的球員就穩定在800―1000人,被豪門哄搶,或者被萬人矚目的只是極少數,絕大多數球員都被分配到歐洲各大聯賽的俱樂部進行“加工培養”,這其中,素質好的、運氣好的也許會逐漸揚名,一步一步實現自己的歐洲夢,不適應的、運氣差的就會長期“滯留”在歐洲低級別聯賽的小球會,或者直接被“退貨”回國。但正如《隊報》資深記者伊斯特指出:“這些巴西小孩,有很多都沒有被歐洲真正的認識或接納,他們來歐洲的時候太小,一切都還沒有成型就被退還,這是命運的殘酷,也是歐洲足球人才鏈的巨大損失。”
以羅納爾多為例,他1994年這一年就完成了三件在他的前輩身上很可能要跨度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大事:3月首次進國家隊,5月打進國家隊第一球,8月就以470萬美元的身價轉會埃因霍溫。那時,肥羅尚未滿18歲!諸如此類的“資源掠奪” 在今日足壇的歐美貿易鏈中已經司空見慣,甚至變態到很多南美球員一場本國職業聯賽都沒踢過就被販賣到歐洲的地步,正因如此,現在不少南美球員到了27、8歲左右就已有被歐洲“榨干”的跡象,而他們的生理年齡絕對沒到職業暮年,比如里克爾梅回博卡時才28歲,這種“去得早回得也早”的現象發生很像是歐洲對南美人才畸形掠奪的一種“回扣”,這個現象也從根本上決定了新一波返鄉團的素質與性質都與二十多年前的養老團截然不同,年齡首先就確保了他們不是歐洲淘汰下來的“廢品”。
曲高和寡 風格才是生態美
穆里尼奧說:“不是切爾西不適合貝隆,是整個英超都不適合貝隆。”弗格森不是不喜歡貝隆,而是屢次給他機會之后還是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貝隆的風格與曼聯不配,英超的節奏更容不下這樣的中場球員。
在世界足球風格流派的界限日趨模糊,尤其是南美洲球員越來越“歐化”的大背景下,還會出現諸如貝隆和里克爾梅這種“水土不服”的現象,真不愧為世界足壇最后的“原生態話題”,風格論在很多時候都是一個偽命題,但在南美球員身上這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
“對我而言,足球就是游戲,我需要在球場上盡情享受自己的比賽。”里克爾梅說。這位即便在阿根廷國內都充滿巨大爭議的“極慢大師”天生不是屬于歐洲聯賽的球員,他享受足球的那種過程并不為大多數歐洲球隊所接受,巴塞羅那和比利亞雷亞爾是全歐洲最講究地面配合、球路最細膩的俱樂部,即便如此,里克爾梅的“木吉他”風格還是顯得太古典、太不食人間煙火了,所以最終他還是只有回到糖果盒里,品嘗那種“自產自銷”的甘甜。
因“水土不服”而返回南美足壇的球員本來不屬于“偽劣產品”范疇,這其中反而暗藏有曲高和寡的曠世天才,他們所需要的僅僅是一雙伯樂的慧眼。最喜歡里克爾梅的佩克爾曼就說過:“羅曼(里克爾梅)應該回阿根廷踢球,這里每家俱樂部都有他的位置,他也不需要去適應誰,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步調踢球。”事實證明佩克爾曼的話沒錯,里克爾梅回博卡的近兩年時間,不僅成為球隊的戰術核心,在馬拉多納的國家隊慘敗于拉巴斯高原之后,球迷首先呼吁的人也是里克爾梅,雖然羅曼已經單方面表示退出國家隊。在6月初與哥倫比亞的高壓之戰中,馬哥不得不起用貝隆為組織核心――一個曾被英超所拒絕的南美足球先生。
從南美球員出口歐洲的傳統來看,阿根廷和烏拉圭球員的適應能力最強,而哥倫比亞最弱,巴西因出口數量大、位置覆蓋面廣而不易整體定論,但幾乎所有的南美球迷都知道,哥倫比亞的國內聯賽觀賞價值極高,藝術感很強,巴西聯賽同樣如此,在這些聯賽中,個性球員數不勝數,他們為表演而踢球,他們更提供給我們一種評估的角度,那就是因風格而在歐洲“早謝”的球星回歸故土多半是要發光的!
水漲船高 心態全靠球迷給
比爾?貝斯威克是英格蘭著名運動心理學家,先后在米德爾斯堡、伯明翰、狼隊等多家球會擔任過“心理輔導師”,在他看來,南美球員的心理素質要比歐洲球員弱很多,他一般一周會為歐洲球員做一到兩次心理輔導,以減輕他們的壓力,但如果是南美球員,尤其是進攻型球員,他每周都會做不少于三次心理輔導,他說:“關心球員的心理健康與關心他們的生理健康一樣重要,尤其是心理起伏很大的南美球員,他們在沒有跑道間隔的眾多英國專用球場內就像是一個三歲的孩子。”
南美球員普遍天性熱情,情感表達非常直接和外露,正因如此他們的心理更加脆弱。對絕大多數南美球員而言,他們去歐洲踢球的前一兩年都要面對極其苛刻的審判,無論是教練席上還是看臺上的眼光,都是冷冰冰、純功利計算的。這種氛圍會大大影響南美球員的心理,導致他們在球場上過于緊張、對失誤感到沮喪和不安,原本具備的表演天賦更是瞬間全毀。肥羅、梅西和卡卡這種一帆風順的早熟天才畢竟是極少數案例。
南美足壇的“看臺文化”則與歐洲全然不同,巴西球迷對球星的癡迷程度更是舉世無雙。據統計,科林蒂安隊只要有肥羅出場的比賽票房就狂好,在總共600多萬雷亞爾收入中,有510萬都來自羅納爾多出場的比賽,占了全年收入的81.3%,在羅納爾多簽約后對圣卡埃塔諾隊的首次亮相中,比賽收入居然高達近55萬雷亞爾!5月31日巴西聯賽第四輪,有7.1萬球迷到馬拉卡納現場觀看了阿德里亞諾回歸弗拉門戈的首秀,當阿德下半場進球時,馬拉卡納球場大屏幕上打出“皇帝歸來”的字樣,里約球迷齊聲高唱:“貧民窟!貧民窟的節日!”
眼下一個潛在的心理暗流是,南美足壇長期處于歐洲足壇的“原材料基地”,一直是貿易鏈中的“賣”方,巴西和阿根廷這些大國的聯賽已經被掠奪性“淘寶”搞得破敗不堪,在此背景下,肥羅、里克爾梅和阿德這些巨星居然會回來,并保持上佳的狀態,這好比一個乞丐突然撿到了一個鉆戒,對于這樣的“奢侈品”能為自己所享用,南美球迷的心理從一開始就是感恩、陶醉和包容的。正因球迷如此,回來的球星更加輕松自如,他們可以享受最純粹的快樂足球,在這一享受過程中,他們的最佳狀態自然而然的回來了,畢竟當考生和當偶像的心理是有天壤之別的。
與生俱來 在家的感覺真好
阿德里亞諾今春在穆里尼奧眼皮底下上演的足球版《越獄》現在看來都讓人感覺不可思議:3月底,他利用回國參加預選賽的機會,滯留巴西不歸,并失蹤了3天,然后當他現身的時候,他宣布了無限期休戰;4月,他與國米正式解除勞動合同,5月,他就與弗拉門戈隊簽約,巴西記者打趣說:“阿德這三大步,在NBA都看不到!”
聽聽阿德這個浪子怎么說吧――“我回家了,我回到巴西是為了重新找回幸福感。在意大利,踢球壓力很大,生活沒有樂趣,我太累了……!”南美與非洲一樣光怪陸離,在這片豐饒的土地上,人情風俗極其濃厚,其實不要整體拿南美與歐洲比較,就是南美洲各國與國之間,風俗差異性也極大,絕不類歐洲那樣“一元化”。
多元化的社會必然造就出五彩斑斕的人性。阿德的回歸演說曾讓現場球迷和記者集體落淚,他說:“我不想再做國王,也許在歐洲踢球會賺更多的錢,但是錢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我要找到做人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