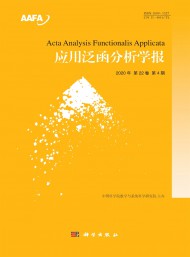對偶詩句范文
時(shí)間:2023-03-14 13:41:19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對偶詩句,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1、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2、苦凋凄金石,清音入杳冥。
3、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4、投我以木桃,報(bào)之以瓊瑤。
5、幾處早鶯爭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6、鄉(xiāng)淚客中盡,歸帆天際看。
7、遲遲白日晚,裊裊秋風(fēng)生。
8、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
9、日斜江上孤帆影,草綠湖南萬里情。
10、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多登臺。
11、樹深時(shí)見鹿,溪午不聞鐘。
12、窗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13、泛樓船兮濟(jì)汾河,橫中流兮揚(yáng)素波。
14、高江急峽雷霆斗,古木蒼藤日月昏。
15、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
16、日晚愛行深竹里,月明多上小橋頭。
17、城闕輔三秦,風(fēng)煙望五津。
18、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
19、風(fēng)鳴兩岸葉,月照一孤舟。
20、百丈游絲爭繞樹,一群嬌鳥共啼花。
21、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
22、七八個(gè)星天外,兩三點(diǎn)雨山前。
23、聽猿實(shí)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
24、一水護(hù)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
25、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26、游子魂銷青塞月,美人腸斷翠樓煙。
27、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
28、兩個(gè)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29、海日升殘夜,江春入舊年。
30、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31、三杯竹葉穿心過,兩朵桃花上臉來。
32、三分割據(jù)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
33、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34、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冢臥麒麟。
35、淑氣催黃鳥,晴光轉(zhuǎn)綠蘋。
36、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
37、估客晝眠知浪靜,舟人夜語覺潮生。
38、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
39、處處春光好,村村氣象新。
40、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41、堅(jiān)冰已經(jīng)打破,航道已經(jīng)開通。
42、室有惠崇山水,人懷與可風(fēng)流。
43、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
44、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45、玉璽不緣歸日角,錦帆應(yīng)是到天涯。
46、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
47、漫步半月溪畔,徘徊六角井傍。
48、塵世難逢開口笑,須插滿頭歸。
篇2
關(guān)鍵詞:簡約;環(huán)保;實(shí)用主義;技術(shù)精湛
中圖分類號:J524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3)06-0063-01
一、北歐家具設(shè)計(jì)特點(diǎn)
(一)材質(zhì)
上等的楓木、云杉、橡樹、松樹、白樺是主要生產(chǎn)家具的材料,木質(zhì)自身的柔軟度、顏色、精致的紋理非常完美的融合在家具設(shè)計(jì)中,顯現(xiàn)出一個(gè)簡單的、新鮮的、原始的美,代表著獨(dú)特的北歐風(fēng)格。
(二)功能
多功能,可拆卸折疊,可以自由組合是北歐家具的主要功能。一般情況下在家具店選擇好樣品之后,只需購買一套附有裝配圖和零件的成型板材,就可由家庭成員根據(jù)個(gè)人需求和喜好來裝配。這種生產(chǎn)程序使得北歐家具的制作工藝更先進(jìn),表面木材的處理更復(fù)雜,家具質(zhì)量和光潔度同時(shí)需要達(dá)到一個(gè)相當(dāng)高的水平。
(三)技術(shù)
在技術(shù)過程中,藝術(shù)和工藝在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huì)被認(rèn)為是一種活體樣本的技術(shù),至今仍然被廣泛使用在北歐國家的設(shè)計(jì)之中。這種人本主義的態(tài)度也已經(jīng)被世界廣泛的認(rèn)可,創(chuàng)造一個(gè)天人合一的自然天堂,北歐人似乎有不可替代的天賦。 “宜家家居”在中國的流行即解釋了一切。從宜家的家具中我們可以看到,瑞典家具追求一種簡單的風(fēng)格,優(yōu)雅的顏色,沒有一點(diǎn)點(diǎn)的鋪張浪費(fèi)在設(shè)計(jì)之中。
北歐家具擁有一個(gè)非常強(qiáng)大的后現(xiàn)代特征,注重平滑線條設(shè)計(jì),這代表了一種時(shí)尚的、回歸自然的、崇尚原木的魅力,同時(shí)現(xiàn)代、實(shí)用、美觀的藝術(shù)設(shè)計(jì)風(fēng)格,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城市人們在新時(shí)代中的某種取向和旋律。
二、現(xiàn)代北歐家具的表現(xiàn)
(一)溫暖的感覺
北歐人注重“家”,所以設(shè)計(jì)的住宅,從陳設(shè)、家具和家居用品都是飽含人情味的,這樣用戶就可以得到一個(gè)身心平衡、舒適、安全、方便的家居環(huán)境。因此,北歐家具的顏色或曲線無論是在白天的日光下還是夜晚的燈光下,全都非常強(qiáng)調(diào)一種溫暖的感覺,展現(xiàn)了自然安靜的北歐生活。
(二)實(shí)用主義
北歐家具設(shè)計(jì)師更加注重人體工程學(xué)的研究,并將其應(yīng)用到家具的設(shè)計(jì)中。設(shè)計(jì)師們達(dá)成共識:人體工學(xué)設(shè)計(jì)是最符合人類使用標(biāo)準(zhǔn)的。家具的主要功能是舒適,其次是滿足人體健康的標(biāo)準(zhǔn)。
(三)環(huán)保自然
北歐家具的原材料除了偏好木頭之外,藤棉織品和其他天然材料全都已經(jīng)被賦予了新的生命。除了原材料,北歐家具追求自然也反映在工藝制作這一過程中,由于北歐現(xiàn)代家具在機(jī)械加工的同時(shí),一些家具的部分工藝還使用手工藝加工,這種結(jié)合傳統(tǒng)工藝和現(xiàn)代技術(shù)的搭配,是北歐家具精湛的加工技能至今不能被別人復(fù)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北歐家具的代表
(一)丹麥設(shè)計(jì)
在世界木制家具設(shè)計(jì)行業(yè)中,最經(jīng)典的是丹麥設(shè)計(jì)。“丹麥設(shè)計(jì)”似乎已經(jīng)成為一個(gè)特殊的專有名詞。丹麥設(shè)計(jì)追尋以人為本的本質(zhì)。例如設(shè)計(jì)一把椅子,一個(gè)沙發(fā),丹麥設(shè)計(jì)不僅追求其外形美觀,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人體的構(gòu)造,分析它的曲線如何與人體達(dá)到完美的結(jié)合。它突破了工藝、技術(shù)呆板的概念,融入主體意識,從而成為一個(gè)理性的作品。
(二)瑞典現(xiàn)代家具
北歐各個(gè)國家的家具生產(chǎn)都有其自身的特點(diǎn)和風(fēng)格,優(yōu)雅和時(shí)尚在瑞典風(fēng)格中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與丹麥家具不同,瑞典風(fēng)格不是很強(qiáng)調(diào)個(gè)性,更加注重藝術(shù)和市場中高流行的大眾化家具的研究開發(fā)。傳統(tǒng)上,瑞典人更加偏向于使用本土的松樹、樺樹作為材料制作白木家具。
瑞典家具設(shè)計(jì)強(qiáng)調(diào)具有功能性的現(xiàn)代主義原則,同時(shí)也強(qiáng)調(diào)圖案的裝飾性,傳統(tǒng)和自然形式的重要性。
(三)芬蘭人的造型天賦
篇3
原告:劉華清,男,60歲,漢族,原瀘州市電信分公司調(diào)研員,現(xiàn)已退休,住本單位職工宿舍。
被告:四川省瀘州市公安局江陽區(qū)分局。
法定代表人:趙權(quán),局長。
第三人:孔豫蓉,女,38歲,漢族,瀘州市公安局干警,倥瀘州市江陽區(qū)官井坎2號樓。
第三人孔豫蓉之父原系瀘州市電信局局長,與原告劉華清是止下級關(guān)系,劉曾因工作問題對其不滿。2001年3月15日上午,第三人孔豫蓉受單位指派到原告劉華清所在單位瀘州市電信分公司(劉當(dāng)時(shí)任該公司調(diào)研員)與該公司部門經(jīng)理黃良(劉與黃在同一辦公室)聯(lián)系業(yè)務(wù),其間在與該公司職工趙昌庭言談中,原告劉華清因插話并出言不遜,致雙方發(fā)生口角,隨即原告:劉華清抓起自己辦公桌上盛滿水的茶杯欲向第三人潑去,被他人制止,隨后原告劉華清又走到第三人孔豫蓉面前出手將孔豫蓉往門外推,雙方發(fā)生推拉、抓扯,致孔豫蓉受傷,經(jīng)醫(yī)院診斷:孔豫蓉“腦外傷”、“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經(jīng)法醫(yī)鑒定孔豫蓉的損傷程度屬于輕微傷。對此,瀘州市公安局江陽區(qū)分局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第二十二條(一)項(xiàng)之規(guī)定,于2001年5月24日以“毆打他人”為由,對劉華清作出治安拘留7日的處罰。劉華清不服該處罰,向?yàn)o州市公安局申請行政復(fù)議,瀘州市公安局經(jīng)復(fù)議維持了原處罰決定。劉華清不服,向?yàn)o州市江陽區(qū)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審判
瀘州市江陽區(qū)人民法院經(jīng)審理認(rèn)為:被告認(rèn)定第三人孔豫蓉在與原告劉華清發(fā)生糾紛的過程中受到輕微傷害的基本事實(shí)清楚,處罰裁決在程序方面并無違法之處。故依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一)項(xiàng)之規(guī)定,于2001年11月7日作出判決:
維持被告瀘州市公安局江陽區(qū)分局的處罰裁決。
劉華清不服一審判決,向?yàn)o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稱:被上訴人提供的證據(jù)不能證明上訴人具有毆打第三人的行為,原判是以損害結(jié)果推定毆打行為;證人證言以及第三人的陳述有相互矛盾、前后矛盾之處;糾紛的發(fā)生雙方均有責(zé)任,僅處理上訴人是不公正的;處罰裁決書未告訴申請復(fù)議或提起訴訟的途徑、期限,程序違法。請求二審法院撤銷一審判決,撤銷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作出的處罰決定。
被上訴人辯稱:被上訴人對第三人實(shí)施毆打的基本事實(shí)清楚,證據(jù)充分,上訴人應(yīng)當(dāng)對其行為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被上訴人對上訴人的處罰是在查清事實(shí)的基礎(chǔ)上并結(jié)合法醫(yī)鑒定結(jié)論而作出的;處罰裁決書告訴了上訴人申訴的時(shí)間和途徑。請求維持原判
第三人孔豫蓉認(rèn)為自己是受單位指派如約到上訴人單位聯(lián)系工作的,上訴人因個(gè)人恩怨挑起事端對我實(shí)施毆打并造成輕微傷,應(yīng)當(dāng)受到處罰。一審判決正確,請求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認(rèn)為:上訴人劉華清在與第三人孔豫蓉發(fā)生糾紛的過程中,第三人并無過錯(cuò),且其受到輕微傷害的基本事實(shí)存在,上訴人劉華清的行為違法,應(yīng)當(dāng)受到處罰。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以毆打他人決定給予治安拘留7日的處罰在認(rèn)定事實(shí)、證據(jù)和適用法律方面并無不當(dāng),程序亦不違法,一審判決予以維持正確。據(jù)此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一)項(xiàng)之規(guī)定,于2001年11月7日作出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評析
本案是一起比較普通的治安處罰行政案件。有幾個(gè)問題值得探討。
一、本案有一定的社會(huì)影響
本案的原告是一單位領(lǐng)導(dǎo),第三人是市公安局干警,而其父又是原告的老領(lǐng)導(dǎo),但因原告對其父有積怨而欲對第三人發(fā)泄,由此導(dǎo)致原告在第三人到其單位聯(lián)系業(yè)務(wù)時(shí)挑起事端先與第三人發(fā)生口角后又發(fā)展為抓扯,造成第三人的輕微傷害。此事在雙方單位都產(chǎn)生了較大的影響,當(dāng)一名公安干警的人身權(quán)利受到侵害的時(shí)候,對當(dāng)事人的處理過輕,公安干警的權(quán)利得不到充分保護(hù),而處理過重,又會(huì)引起不良影響。因此法院在審理中也要把握好這樣的原則。
二、關(guān)于對劉華清行為的如何定性
本案原告與第三人的糾紛發(fā)生突然,盡管從公安機(jī)關(guān)調(diào)查收集的證據(jù)來看,有的證人證言前后敘述不盡一致,還有的證人證言相互矛盾,但綜合所有的證人證言可以反映出糾紛起因、發(fā)展、持續(xù)的全部過程,即是原告首先無故挑起事端,在口角中原告欲將茶杯向第三人潑去被制止,后原告又先出手推搡第三人致雙方發(fā)生推拉、抓扯。結(jié)合第三人事發(fā)后到醫(yī)院就診的傷情記載和法醫(yī)鑒定結(jié)論以及第三人受傷與原告行為的因果關(guān)系,認(rèn)定原告對第三人實(shí)施了毆打并以“毆打他人”對原告予以處罰是正確的。而并非原告所認(rèn)為的是以結(jié)果推斷事實(shí)。
篇4
煙鎖對云封是一個(gè)對子,字面意思就是煙鎖住和云封住了。對子一般指對聯(lián),對聯(lián)是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之一,又稱楹聯(lián)或?qū)ψ樱菍懺诩垺⒉忌匣蚩淘谥褡印⒛绢^、柱子上的對偶語句。
對聯(lián)對仗工整,平仄協(xié)調(diào),是一字一音的中華語言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對聯(lián)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瑰寶。對聯(lián)在自身發(fā)展過程中,又吸收了古體詩、散文、詞曲等的特點(diǎn)。因而對聯(lián)所用句式,除了律詩句式、駢文句式外,還有古體詩句式、散文句式、仿詞曲句式。不同句式適用格律不同、寬嚴(yán)不同。其中律詩句式平仄要求最嚴(yán),古體詩句式則除了對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篇5
探究用典化句的妙用,古詩詞常引用典故,化用詩句,以豐富的內(nèi)涵,引人聯(lián)想。鑒賞古詩詞,一定要了解典故及化用詩句的來源和含義,發(fā)掘典故及詩句在古詩詞中的妙用。
2、修辭手法
體會(huì)修辭手法的表達(dá)效果,古詩詞中,因形象性與抒情性的需要,常借助各種藝術(shù)手法來表現(xiàn),其中最主要的是比喻、起興、擬人、夸張、對偶、反復(fù),襯托等,把握了這些手法的表達(dá)效果,就能更好地體會(huì)詩詞的形象,領(lǐng)悟作者的感情。
3、深化理解
篇6
主題:《游山西村》詩人在語調(diào)極其自然親切的詩句中向人們展示了農(nóng)村自然風(fēng)景之美、農(nóng)民淳樸善良之美,并把自己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熱愛生活、熱愛自然的高尚情操美融于其中。
寫作手法:全詩層次清晰,語言生動(dòng),對偶自然工整,寓景于情。
原文:莫笑農(nóng)家臘酒渾,豐年留客足雞豚。山重水復(fù)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簫鼓追隨春社近,衣冠簡樸古風(fēng)存。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shí)夜叩門。
(來源:文章屋網(wǎng) )
篇7
關(guān)鍵詞:唐五代詩格 形式 中西對話
詩格是中國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學(xué)批評形式之一。詩格批評既源遠(yuǎn)流長,又豐富多彩,是非常寶貴的文學(xué)理論遺產(chǎn)。詩格作為審美范疇在唐五代加以確立。張伯偉先生強(qiáng)調(diào):“在古代文學(xué)批評著作中,作為專有名詞的‘詩格’是到唐代才有的。”①唐五代詩格批評,在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史上,是一筆豐厚的值得研究的詩學(xué)資源。
一、唐五代詩格的歷史流變
(一)初唐詩格
初唐統(tǒng)治者們反對齊梁以來的文風(fēng),重文學(xué)的功利作用。但他們并不否定文學(xué)的藝術(shù)特質(zhì),講求抒情與文采。這種思想為文學(xué)形式的探討留下了廣闊的余地。律詩在這一時(shí)期得以定型化,齊梁時(shí)期的“永明體”講四聲與病犯,初唐發(fā)展到講求平仄律。這一時(shí)期的主要詩格批評文本有上官儀的《筆札華梁》、無名氏的《文筆式》、元兢的《詩髓腦》、崔融的《唐朝新定詩格》、李嶠的《評詩格》等等。初唐人集中探討聲律與對偶問題。聲律的研究始于南朝齊沈約等人的“四聲八病”理論。
沈約《宋書謝靈運(yùn)傳論》說:“夫五色相宣,八音協(xié)暢,由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jié),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nèi),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dá)此旨,始于言文。”②沈約認(rèn)為五言詩每一句的用字應(yīng)該四聲各不相同,而且一聯(lián)上下句間同一位置上的字也須在聲調(diào)上互有區(qū)別。“八病”則是為了貫徹這一原則而規(guī)定的一些禁格,即“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 沈約等人雖以“四聲八病”為原則來規(guī)范詩文創(chuàng)作,但如何把這一原則具體化,使之有可操作性,則是由唐代詩格類著作來解決完成的。唐人將四聲作了平仄二元化的處理,使平仄相間,構(gòu)造出切實(shí)可行的聲律定式。
初唐時(shí)期主要以沈約“八病”為中心來展開探討,并逐漸提出了調(diào)聲之術(shù)。《詩髓腦》云:“調(diào)聲之術(shù),其例有三:一曰換頭,二曰護(hù)腰,三曰相承”③通過調(diào)聲之術(shù),初唐人已經(jīng)將平聲與上、去、入三聲對舉,實(shí)際已是把聲律二元化,放寬了聲律規(guī)則。在此之前,人們多著眼于一聯(lián)之內(nèi)兩句的聲律協(xié)調(diào),到元兢的“換頭”之術(shù)中,已擴(kuò)展為解決一首五言詩內(nèi)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的平仄粘對關(guān)系,真正使得齊梁聲律理論具有了可操作性,促進(jìn)了律詩的定型與繁榮。
(二)盛唐詩格
盛唐時(shí)期追求風(fēng)骨,要求詩歌表現(xiàn)高昂明朗的感情和雄渾壯大的氣勢。同時(shí),盛唐人又提出了“興象”概念,要求寫出情景交融的完整的意境,使得這一時(shí)期詩格探討也從聲律、對偶深入到對句勢、詩意等的研究。釋皎然的《詩式》、《詩議》涉及到聲律、對偶及詩歌體式,并深入研究了“意”與境的關(guān)系。他們的批評不僅深化了對聲律對偶的認(rèn)識,提出了切實(shí)可行的句法,而且涉及到“景”與“情”,詩歌的語言運(yùn)用與詩的整體印象等更深的層面。這一時(shí)期的著作開始注重詩的句法、篇法,研究句與句之間的關(guān)系,深入探討了句勢問題。早在崔融《唐朝新定詩格》中就列有十體,一形似體、二質(zhì)氣體、三情理體、四直置體、五雕藻體、六映帶體、七飛動(dòng)體、八婉轉(zhuǎn)體、九清切體、十菁華體。王昌齡《詩格》中有“十七勢”之說,承續(xù)了崔融論體的基本精神,并且由對詩歌風(fēng)貌的關(guān)注深入到創(chuàng)作的藝術(shù)手法和修辭手法的具體運(yùn)用。每一種名目除釋義外,并附有詩句說明。皎然《詩式》中也說到體式。“評曰:夫詩人之思初發(fā),取境偏高,則一首舉體便高;取境偏逸,則一首舉體便逸。才性等字亦然。體有所長,故各功歸一字。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詩體、篇目、風(fēng)貌不妨。一字之下,風(fēng)律外彰,體德內(nèi)蘊(yùn),如車之有轂,眾輻歸焉。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體,風(fēng)味盡矣,如《易》之有《篆辭》焉。”④五代王玄《詩中旨格》的“擬皎然十九字體”一節(jié)于每體后列有詩句說明,延續(xù)了皎然論體的特色。
(三)晚唐五代詩格
晚唐時(shí)期,唐王朝徹底崩潰,政局不可收拾,處在這種環(huán)境中的作家和批評家,普遍具有消沉心態(tài)與悲觀心理。這個(gè)時(shí)期有一部分作家主張“詩教說” 與抒寫民生疾苦,也有一部分人崇尚清麗綺艷的詩風(fēng),但總體的傾向是追求淡泊的情思與境界。司空圖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理論。人們更加著力于對聲律、對屬、字句等方作面的琢磨與錘煉。另外,科舉取士對詩律的要求在這一時(shí)期也更趨細(xì)密,故而大量的詩格著作也應(yīng)運(yùn)而生。這些著作所討論的范圍更加寬廣,論述更加深入,增添了宗教神秘主義的色彩,主要有僧齊己等人對句勢的繼續(xù)探討和王叡的“拗律”說。
齊己《旨格》,也有十體之說,即一曰高古,二曰清奇,三曰遠(yuǎn)近,四曰雙分,五曰背非,六曰無虛,七曰是非,八曰清潔,九曰覆妝,十曰闔門。這十體都有詩句附后,但并無解釋,還是就詩歌整體風(fēng)貌而言的。五代的《詩格》中列有十勢,其中龍潛巨浸勢、獅子返擲勢見于《旨格》,孤鴻出塞勢即孤雁失群勢,其他七勢為新增,即芙蓉映水勢,龍行虎步勢,寒松病枝勢,風(fēng)動(dòng)勢,驚鴻背飛勢,離合勢,虎縱出群勢。芙蓉映水勢。由上觀之,晚唐五代詩格,承續(xù)了初盛唐人對體式的研究,而且名目更加繁多。齊己等人多以動(dòng)物姿態(tài)動(dòng)作來為句勢命名,其意義往往難以索解,不似王昌齡十七勢簡單明了。但這些名目不僅探討了句與句之間的關(guān)系,而且深入到全篇的意義布局問題,如《詩格》“論詩勢”節(jié)云:“先須明其體勢,然后用思取句。”⑤
二、 唐五代詩格的邏輯構(gòu)成
中國古典詩學(xué)關(guān)于“言、象、意”的探討由來已久。早在先秦,道家學(xué)派創(chuàng)始人老子就提出“大象無形”的命題。老子從“無”和“有”、虛和實(shí)的辯證關(guān)系出發(fā),認(rèn)為“有無相生”,以“無”為本,這種“無”又必須依靠“有”才能體現(xiàn)出來。所以,最美的形象就是沒有形象,但又要有某種具體的“形”來暗示與象征,方能使人體會(huì)到。魏晉玄學(xué)將無有體用思想運(yùn)用于認(rèn)識論,把“言、象、意”關(guān)系表述為“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言”和“象”都是有形的、有限的,而“意”則是無形的、無限的,“言”和“象”是得“意”之工具,沒有“言”和“象”就無以得“意”。因此,從形式視野來觀照,唐五代詩格的“格”概念具有豐富的內(nèi)涵,從邏輯上也包括了言、象、意三個(gè)層次。唐五代詩格中往往以“格”論詩,所出現(xiàn)的有關(guān)稱名主要有:“格”、“風(fēng)格”、“體格”“高格”、“格力”、“氣格”等。這些對“格”的運(yùn)用,其含義可歸為兩個(gè)方面:一是體式、詩法之意,指向詩歌的總體風(fēng)貌與外在形式,一是格調(diào)、品格之意,指向詩歌的審美特質(zhì)與審美內(nèi)蘊(yùn)。可以說,唐人有關(guān)聲律、對偶的探討,屬于詩格的語言層,對物象、作用、句勢的探討,屬于詩格的意象層,對意與境、用事的探討,屬于詩格的意蘊(yùn)層。
(一)詩格的語言層
文學(xué)作品的語言是一種獨(dú)特性的存在,特別是詩歌語言。俄國形式主義頗為看重這一點(diǎn)。“形式主義的研究工作是從研究詩句中的聲音開始的。”“詩句中的聲音問題特別受到人們的重視。”⑥可以說在這方面唐五代詩格對聲律的論述表現(xiàn)出對聲音的特別重視。朱光潛先生說:“律詩有兩大特色,一是意義的排偶,一是聲音的對仗。”⑦他還指出音與義的關(guān)系在詩歌進(jìn)化史中可分為四個(gè)時(shí)期:一、有音無義時(shí)期二、音重于義時(shí)期三、音義分化時(shí)期四、音義合一時(shí)期,但聲音的對仗稍后于意義的對仗。“永明體”講究句內(nèi)各字的聲律,不過是一種理論,到隋唐才作為律詩的通例。關(guān)鍵是詩樂分開后,詩人如何在文字本身上見出音樂,唐人作了最大的貢獻(xiàn),唐五代詩格予以了很好的總結(jié)。
(二)詩格的意象層
意象層主要指藝術(shù)作品的章法與結(jié)構(gòu),唐五代詩格中的物象、作用與“勢”的研究正是對這幾方面的關(guān)注。唐人詩格中講物象,也就是用一定的物象來暗示某種意義。舊題賈島《二南密旨》、虛中撰《流類手鑒》、徐寅《雅道機(jī)要》中都說到物象。《二南密旨論物象是詩家之作用》說:“造化之中,一物一象,皆察而用之,比君臣之化。君臣之化,天地同機(jī),比而用之,得不宜乎。”⑧這些物象已不是純粹的外在客觀景物,而是主客觀的有機(jī)交融,包括了意與象兩個(gè)方面。自然界中的一物一象,都是被用來寄托某種意義的。
唐五代詩格中,比較集中地論述到“勢”問題的著作,主要有王昌齡的《詩格》、釋皎然的《詩議 》和《詩式》等。“勢”作為一種力,它相關(guān)于主體的情感與構(gòu)思,是作者的生命力與內(nèi)在精神力量之驚濤中所形成的動(dòng)態(tài)表現(xiàn),是詩作意脈流貫與渾整一體的氣力之美。
(三)詩格的意蘊(yùn)層
唐五代詩格中的意境的探討,用事問題的提出,都是指向作品的意蘊(yùn)層。舊題王昌齡撰《詩中密旨》“詩有二格”云:“詩意高謂之格高,意下謂之格下。”⑨把“意”作為詩之品位高低之標(biāo)準(zhǔn)。皎然《詩式》中“重意詩例”云:“兩重意已上,皆文外之旨。”⑩皎然已經(jīng)認(rèn)識到詩意的多重性與豐富性,文外之重旨,并把“但見情性,不睹文字” 之詩作視為極品。總之,唐五代詩格中,對“意”這一范疇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并深入探討了“意”與境,情與景的關(guān)系,發(fā)展了古典詩學(xué)的意境理論。
三、唐五代詩格的現(xiàn)實(shí)意義
以西方形式批評為參照,來透視唐五代詩格,二者既存在著共相,又存在著歧異,通過互照互補(bǔ),從而在一定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對話。中國古代詩論追求渾然天成的美學(xué)境界,所以往往把詩歌的整體意蘊(yùn)置于具體的語言操作之上。“立象盡意”、“得意忘言”、“言不盡意”這樣的命題都是輕言重意,以為意是目的,言是手段。因此古代詩格雖然也關(guān)注藝術(shù)技巧和形式的問題,但只是視其為一種手段。而西方形式論則賦予文學(xué)作品本體的地位,研究純粹的藝術(shù)形式,不重視形式與內(nèi)容的關(guān)系。
詩格研究從具體可感的作品形式入手,對詩歌進(jìn)行“細(xì)讀”,而不是空談韻、格、氣等讓人摸不著邊際的范疇概念,這是一種“自下而上”的詩論理路。然而,唐五代詩格遠(yuǎn)未達(dá)到西方形式批評的體系性與理論水平,只是靠直覺與天才認(rèn)識到某些重要問題,是對當(dāng)時(shí)豐富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如何吸取西方文論之長,促進(jìn)中國詩論的發(fā)展,將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注釋:
①張伯偉.中國古代文學(xué)批評方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47頁.
②羅根澤.中國文學(xué)批評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頁.
③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頁.
④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242頁.
⑤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493頁.
⑥汪正龍.西方形式美學(xué)問題研究.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
⑦朱光潛.詩論.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98年版.第241頁.
⑧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匯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頁.
篇8
一、讀出駢文之美
讓學(xué)生自由大聲朗讀課文,發(fā)現(xiàn)行文的突出特點(diǎn)――基本上由對偶句連綴成文,告訴學(xué)生這樣的文章古代叫做駢文,并作適當(dāng)介紹。然后,進(jìn)一步引導(dǎo)學(xué)生發(fā)現(xiàn)駢文的特點(diǎn),讀出駢文的味道。第一,多為對偶句,要讀出節(jié)奏美。對偶句兩句之間意思相近或相對,停頓稍短,要讀得音斷氣連,重音突出。第二,講究押韻,要讀出音樂美。文章一韻到底,瑯瑯上口。全文押韻的字為“名、靈、馨、青、經(jīng)、形、亭”,每句讀完,有一種旋律的回環(huán)之美;偶句之間平仄相對,起伏變化,要讀得抑揚(yáng)頓挫,韻味十足。第三,用詞凝練,讀出畫面美。駢文講究煉字,辭藻華麗,言簡意豐,讀時(shí)要想象其畫面,才能讀出身臨其境的感受。例如朗讀“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時(shí),想象碧綠的青苔長滿臺階、青蔥的草色映入窗簾之景,朗讀就會(huì)有一種喜悅之情;讀“可以調(diào)素琴,閱金經(jīng)”時(shí),想象作者彈琴讀書時(shí)自在的生活場景,朗讀就會(huì)有一種怡然自得之情。在這一環(huán)節(jié)中,根據(jù)學(xué)生的朗讀,教師注重幫助學(xué)生糾正讀音、理清詞義。
二、讀出作者之情
通過第一步的美讀,學(xué)生對文章內(nèi)容應(yīng)該比較熟悉,教師可層層深入,拋出“三問”。一問:題為“陋室銘”,可結(jié)尾卻說“何陋之有”,到底是“陋”還是“不陋”呢?引導(dǎo)學(xué)生分析,作者評價(jià)房子陋與不陋的關(guān)鍵不是看房子本身,而是看房子里面所住的人,文章的關(guān)鍵句子“惟吾德馨”點(diǎn)明了房子不陋的原因。二問:何以見得房子主人“德馨”?主人身居幽雅的自然環(huán)境之中,且能夠感受到自然之美,一見“德馨”;與主人交往的都是儒雅之人,沒有俗人,二見“德馨”;主人在室內(nèi)彈琴、讀經(jīng)書,都是優(yōu)雅之事,三見“德馨”。三問:主人寫“陋室銘”就是為了告訴我們“陋室不陋”嗎?向?qū)W生介紹“銘”這種文體一般是用來警戒自己或稱述功德,幫助學(xué)生理解文章主旨。通過“談笑有鴻儒”、“無絲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等句子,可見作者不慕榮利、安貧樂道的生活情趣,從文章開頭以“仙”和“龍”的自喻以及結(jié)尾處“南陽諸葛廬,西蜀子云亭”的類比,可見作者有諸葛、子云之志趣和抱負(fù),作者實(shí)際上是采用托物言志的寫法,借陋室不陋來表明自己的傲岸高潔的情操和安貧樂道的生活態(tài)度。要求學(xué)生帶著這樣的理解,搖頭晃腦地讀,讀出作者心中之情。
三、讀出個(gè)人之悟
篇9
古典詩歌是文學(xué)作品中最簡練、內(nèi)涵最豐富的藝術(shù)形式。古詩的表達(dá)技巧很多,從修辭角度來看,常見的有比喻、夸張、擬人、對偶、對比、雙關(guān)、反問等;從表達(dá)方式來看,有敘述、議論、描寫、抒情等;從表現(xiàn)手法來看,有借景抒情、托物言志、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直抒胸臆、虛實(shí)結(jié)合、想象、襯托、用典、象征等。
對表達(dá)技巧的鑒賞,就是辨識詩歌中所使用的修辭手法、表達(dá)方式和表現(xiàn)手法,分析其本身的藝術(shù)效果,評價(jià)其對表現(xiàn)詩人的思想感情所起到的作用。
二、古詩中常見藝術(shù)手法
1.古典詩詞中常用的修辭手法有:比喻、夸張、擬人、對偶、對比、反問、設(shè)問、通感、借代、雙關(guān)等。
對修辭手法的鑒賞,就是要明確辨識和判斷修辭手法是什么,掌握和了解各種修辭手法的特點(diǎn),分析和評價(jià)它們對于塑造形象、表現(xiàn)情感和體現(xiàn)主旨的作用。
①比喻 比喻能將抽象化為具體,能將無形化為有形。例如寫“愁”:李后主云“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江水寫愁,則使人想到愁意之漫長。
②夸張 夸張就是為了突出和強(qiáng)調(diào)某種事物或事物的某種特征,借助于想象,對它進(jìn)行夸大或縮小,以引人注目,烘托氣氛,增強(qiáng)聯(lián)想,給人啟示。如陸游《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詩中的“三萬里”“五千仞”“上摩天”“淚盡”都是夸張,正是這些夸張描寫,把詩人對祖國的熱愛,對茍且偷安、不去收復(fù)失地的求和派的憤懣,以及對遺民遭受的苦難的深切同情,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
③擬人 把物人格化,可以使描繪生動(dòng)形象,表意更加豐富。如劉頒《新晴》詩中將“南風(fēng)”人格化,通過一系列動(dòng)作描寫,表現(xiàn)了久雨初晴后作者寧靜恬適的心情,以及對南風(fēng)“惡作劇”的親切喜愛之情。
2.古典詩詞中常用的表達(dá)方式有:敘述、議論、描寫、抒情。考查的重點(diǎn)是描寫和抒情。其中,描寫主要分為正面描寫和側(cè)面描寫,工筆(使用大量生動(dòng)、貼切的比喻,絢麗的文字,斑斕的色彩,進(jìn)行濃筆涂沫)和白描(以質(zhì)樸的文字,抓住人物或事物的特征,寥寥幾筆就勾勒出人物或事物形象的寫法),細(xì)節(jié)描寫等。抒情可分直抒胸臆(直接抒情)、間接抒情(手法常是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托物言志等)。
3.詩歌中常用的表現(xiàn)手法有:對照、襯托、渲染、烘托、用典、鋪墊、象征、動(dòng)靜結(jié)合、虛實(shí)相生、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借古抒懷、借古諷今、托物言志、以樂景寫哀情、以哀景寫樂情等。
①托物言志 詩人借自然界中的某物自身具有的特征,來表達(dá)某種志向或情感,詩中的物帶有了人格化的色彩。如王冕的《墨梅》詩以梅自喻,運(yùn)用了托物言志的手法,表現(xiàn)了作者要像梅花那樣的高潔、淡雅,不向世俗獻(xiàn)媚的堅(jiān)貞、純潔的操守。
②渲染 渲染是指對環(huán)境、景物作多方面的描寫形容,以突出形象,加強(qiáng)藝術(shù)效果。“風(fēng)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杜甫《登高》)首聯(lián)俯仰所見所聞,一連出現(xiàn)六個(gè)特寫鏡頭,渲染秋江景物的特點(diǎn)。
③烘托 襯托或烘托指的是以乙托甲,使甲的特點(diǎn)或特質(zhì)更加突出。有正襯和反襯兩種。這本是國畫的一種技法,用水墨或色彩在物象的輪廓外面渲染襯托,使物象明顯突出。用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指從側(cè)面著意描寫,作為陪襯。
④移情 移情就是將人的情感轉(zhuǎn)移到事物身上,使外物與人同喜同悲。比如杜牧的“蠟燭有心還惜別,替人垂淚到天明”,詩人沒有說怎樣惜別,卻把這種感情轉(zhuǎn)移到蠟燭身上,蠟燭無情,尚且替人垂淚,何況人乎?《揚(yáng)州慢》也有“廢池喬木,猶厭言兵”之句,喬木尚且厭惡戰(zhàn)爭,何況揚(yáng)州百姓呢?
⑤虛實(shí)結(jié)合 虛實(shí)結(jié)合是指現(xiàn)實(shí)的景、事與想象的景、事互相映襯,交織在一起表達(dá)同一樣的情感。如柳永《雨霖鈴》上片多是實(shí)寫;下片對別后生活的設(shè)想,是虛寫,著意描繪詞人孤獨(dú)寂寞的心情。虛實(shí)結(jié)合,淋漓盡致地寫出了離別的依依不舍。
⑥借景抒情 即詩人把自身所要抒發(fā)的情感、表達(dá)的思想寄寓在景物之中,通過描寫景物予以抒發(fā)。如杜甫的《絕句》:“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全詩抒發(fā)了羈旅異鄉(xiāng)的感慨,詩人借對清新美好的春光景色的描寫,透露出了思?xì)w的感傷,以樂景寫哀情,別具韻致。
篇10
關(guān)鍵詞:楚辭;音樂藝術(shù);節(jié)奏;音樂結(jié)構(gòu);動(dòng)態(tài)意象;時(shí)間;旋律
中圖分類號:J01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無論《楚辭》當(dāng)初是否合樂,音樂無疑在《楚辭》中占據(jù)重要位置,孫群星先生在《音樂美學(xué)的始祖》一書中,指出戰(zhàn)國詩人屈原在《楚辭·遠(yuǎn)游》篇中首次提出“音樂”這一詞:“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①《楚辭》文本中,對于音樂也有過多次細(xì)致的描繪。可以說,音樂性以各種形態(tài)反映于《楚辭》語音和語義的各個(gè)層面。文本的音樂性有兩個(gè)層次:首先是語音層面,通過聲音層面反映出來;其次是語義的音樂性,即吟唱主體將世界作為一個(gè)時(shí)間對象來感知和把握,進(jìn)而呈現(xiàn)為一系列相互聯(lián)系的特定的時(shí)間意象。杜夫海納指出:“在旋律被打斷的地方,打斷它的還是旋律,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構(gòu)思。”②而對于詩歌來說,情況似乎更為復(fù)雜。聲音旋律被打斷的地方,打斷聲音旋律的可能是意義旋律。詩歌和音樂原為共生,且語言和聲音若能恰如其分地配合,往往能使其各自的表現(xiàn)力得到淋漓盡致的發(fā)揮,在意義的表達(dá)過程中互相推波助瀾。但一首完整的詩歌,歷來具有擺脫外在音樂的沖動(dòng),一方面趨向擁有更完美的語音曲線和節(jié)奏,同時(shí)也不斷在其內(nèi)部開拓出意義層面的音樂時(shí)空,以呈現(xiàn)出那個(gè)寂靜又流動(dòng)的音樂結(jié)構(gòu)本身。音樂性由外自內(nèi)的滲透過程,是漢語詩歌發(fā)展史的全部動(dòng)力。《楚辭》的音樂性首先來自于它的語音構(gòu)成,更來自于其語義所指的動(dòng)態(tài)意象及其所呈現(xiàn)的節(jié)奏和內(nèi)在旋律。其次,語義所揭示的動(dòng)態(tài)意象是《楚辭》音樂性的重要方面,它和語音之節(jié)奏和旋律相互伴隨,構(gòu)建出一種語義層面的音樂節(jié)奏和旋律。而敘述主體之往來飛升形成作品之主要?jiǎng)訖C(jī),作者采取了一種回環(huán)往復(fù)的結(jié)構(gòu)方式,多視角、多聲部的變奏方式,在相當(dāng)長的時(shí)間和空間中,對主題進(jìn)行深化;作品以宏大、唯美、飄逸、悲愴充滿旋律意味的聲音展現(xiàn)一個(gè)具有強(qiáng)烈質(zhì)感的虛擬時(shí)空,它雖然不直接體現(xiàn)為樂音,而人們正是在這一意義上來談?wù)摵徒?gòu)音樂的。本文將通過《楚辭》之語音、語義和敘述視角體現(xiàn)出來的音樂性,對其音樂結(jié)構(gòu)和展現(xiàn)方式進(jìn)行深入分析。
一、語音層面的節(jié)奏和旋律
首先,作品構(gòu)成形式異常豐富,有可唱的《九歌》,有散文化傾向嚴(yán)重的《楚辭》和《九章》。《楚辭》不僅僅在語音模式上求助于一種較為復(fù)雜多變的音樂模式,而在聲音消失的地方,我們發(fā)現(xiàn)了來自語言深處的聲音。語言內(nèi)在音樂性和語言外部的音樂形式發(fā)生沖突,結(jié)果之一就是《楚辭》句法的散文化傾向嚴(yán)重。有人因此認(rèn)為《楚辭》中的很多篇目不可歌唱。詩歌文本的是否具有音樂性和它是否可歌唱宜分而論之,音樂性的并不等于可歌唱的如帕格尼尼的大部分曲子不宜歌唱,但依然是難以超越的音樂經(jīng)典。就聲音層面而言,《楚辭》最為突出的語音現(xiàn)象便是對于疊詞和韻律的運(yùn)用,如“邈蔓蔓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楚辭·悲回風(fēng)》)。由疊詞所帶來的音樂效果也存在于《楚辭》中,這毋庸贅言。當(dāng)然,和《詩經(jīng)》相比押韻和疊詞的使用遠(yuǎn)非其主要語言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