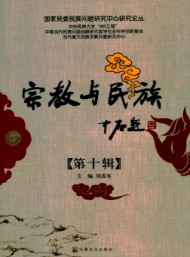薩滿(mǎn)祭祀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3-09 18:06:38
導(dǎo)語(yǔ):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薩滿(mǎn)祭祀范文,還可以咨詢(xún)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清代薩滿(mǎn)祭祀分析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jì)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guó)薩滿(mǎn)信仰習(xí)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xué)者對(duì)阿爾泰語(yǔ)系廣袤世界同類(lèi)民俗事象的關(guān)注,并在此后的三個(gè)世紀(jì)中,學(xué)者們對(duì)薩滿(mǎn)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發(fā)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guó)際上許多學(xué)者對(duì)薩滿(mǎn)習(xí)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duì)“薩滿(mǎn)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通常也使用“薩滿(mǎn)教”一詞,但誰(shuí)都知道,薩滿(mǎn)在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lái)已久,它從形成的時(shí)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chǎn)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fā)的狀態(tài)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shù)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mǎn)”絕非一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shù)行為,也可以稱(chēng)之為薩滿(mǎn)巫術(shù)。這樣看來(lái),薩滿(mǎn)信仰屬于中國(guó)巫文化系統(tǒng),或者說(shuō)它是中國(guó)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
中國(guó)的巫文化是一個(gè)歷史悠久,內(nèi)容十分龐雜的系統(tǒng),根據(jù)歷史文獻(xiàn)記載和現(xiàn)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guó)的巫文化作學(xué)術(shù)上的分類(lèi),筆者認(rèn)為它包括了兩個(gè)有機(jī)的組成部分:即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mǎn)文化和中國(guó)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lái)中國(guó)民俗學(xué)對(duì)中國(guó)巫文化的宏觀關(guān)照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新的走向。過(guò)去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mén),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lái)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mǎn)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guān)照,一定會(huì)使中國(guó)巫文化的研究出現(xiàn)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shí)也稱(chēng)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zhǎng)期以來(lái),“宗教”一詞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經(jīng)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qū)別于“現(xiàn)代宗教”,學(xué)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lái)方便。中國(guó)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guó)文化的源頭,中國(guó)古老的科學(xué)和文化發(fā)展均與巫文化有關(guān),如文字、天文、醫(yī)療、數(shù)學(xué)、文學(xué)、音樂(lè)、舞蹈、繪畫(huà)、歷史學(xué)的產(chǎn)生、發(fā)展,都和巫術(shù)活動(dòng)有關(guān),甚至連知識(shí)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fā)展而來(lái)。可見(jiàn)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jī)r(jià)值。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huì)尚未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時(shí),尤其如此。在那時(shí)由巫文化所構(gòu)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dāng)社會(huì)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特別是國(guó)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shí),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xù)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tǒng)治階級(jí)吸收,并將其系統(tǒng)化,儀禮化,用來(lái)為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服務(wù)。作為中國(guó)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mǎn)文化,都沒(méi)有逃脫這種命運(yùn)。本文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民間薩滿(mǎn)信仰和宮廷薩滿(mǎn)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mǎn)信仰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也是為歷來(lái)的薩滿(mǎn)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wèn)題。現(xiàn)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yàn)榍宕墨I(xiàn)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huì)典》(雍正、嘉慶時(shí)代)、《禮部則例》、《大清會(huì)典事例》、《紐祜祿氏滿(mǎn)洲祭天、祭神典禮》、《國(guó)朝宮史》等,詳細(xì)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mǎn)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yǎng)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guān)薩滿(mǎn)祭祀的實(shí)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mǎn)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mǎn)族薩滿(mǎn)習(xí)俗和清代宮廷薩滿(mǎn)儀典,提供了翔實(shí)可靠的資料。
薩滿(mǎn)及其信仰,本是中國(guó)北方阿爾泰語(yǔ)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xí)俗,流傳地區(qū)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mǎn)族、達(dá)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mǎn)習(xí)俗流傳。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的薩滿(mǎn)信仰在長(zhǎng)期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形成了一個(gè)獨(dú)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mǎn)文化傳承最穩(wěn)固的地區(qū)。這種傳承無(wú)論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chēng)為森林薩滿(mǎn)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qū),是中國(guó)薩滿(mǎn)傳承的又一個(gè)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chēng)為草原薩滿(mǎn)文化圈。蒙古族薩滿(mǎn),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傳播和逐漸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一部分薩滿(mǎn)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mǎn)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mǎn)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dāng)時(shí)一些大薩滿(mǎn)(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hù)偶像,并諳星術(shù),預(yù)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xún)。“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jīng)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yùn)。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shù)。托其欲構(gòu)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xún)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yǔ)以答之。”[3]當(dāng)時(shí),薩滿(mǎn)幾乎主宰部落或國(guó)家大事。據(jù)《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yīng)有適合其新勢(shì)權(quán)之尊號(hào)。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zhǎng)開(kāi)大會(huì)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fā)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hào)之?dāng)?shù)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hào)。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qiáng)者之汗。’諸部長(zhǎng)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hào)成吉思汗。時(shí)年44歲。”[4]此類(lèi)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xiàn)中經(jīng)常見(jiàn)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huì),喇嘛與薩滿(mǎn)之間的斗爭(zhēng)從未間斷過(guò),特別是對(duì)薩滿(mǎn)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mǎn)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wèi)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guī)定取締翁袞。對(duì)邀請(qǐng)男女薩滿(mǎn)來(lái)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duì)請(qǐng)來(lái)男女妖術(shù)師耍魔術(shù)者的乘馬和妖術(shù)師的馬,歸告發(fā)者所有,知而不報(bào)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duì)薩滿(mǎn)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mǎn)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mǎn)信仰[6]。
薩滿(mǎn)祭祀探究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jì)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guó)薩滿(mǎn)信仰習(xí)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xué)者對(duì)阿爾泰語(yǔ)系廣袤世界同類(lèi)民俗事象的關(guān)注,并在此后的三個(gè)世紀(jì)中,學(xué)者們對(duì)薩滿(mǎn)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發(fā)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guó)際上許多學(xué)者對(duì)薩滿(mǎn)習(xí)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duì)“薩滿(mǎn)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通常也使用“薩滿(mǎn)教”一詞,但誰(shuí)都知道,薩滿(mǎn)在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lái)已久,它從形成的時(shí)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chǎn)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fā)的狀態(tài)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shù)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mǎn)”絕非一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shù)行為,也可以稱(chēng)之為薩滿(mǎn)巫術(shù)。這樣看來(lái),薩滿(mǎn)信仰屬于中國(guó)巫文化系統(tǒng),或者說(shuō)它是中國(guó)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
中國(guó)的巫文化是一個(gè)歷史悠久,內(nèi)容十分龐雜的系統(tǒng),根據(jù)歷史文獻(xiàn)記載和現(xiàn)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guó)的巫文化作學(xué)術(shù)上的分類(lèi),筆者認(rèn)為它包括了兩個(gè)有機(jī)的組成部分:即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mǎn)文化和中國(guó)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lái)中國(guó)民俗學(xué)對(duì)中國(guó)巫文化的宏觀關(guān)照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新的走向。過(guò)去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mén),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lái)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mǎn)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guān)照,一定會(huì)使中國(guó)巫文化的研究出現(xiàn)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shí)也稱(chēng)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zhǎng)期以來(lái),“宗教”一詞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經(jīng)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qū)別于“現(xiàn)代宗教”,學(xué)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lái)方便。中國(guó)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guó)文化的源頭,中國(guó)古老的科學(xué)和文化發(fā)展均與巫文化有關(guān),如文字、天文、醫(yī)療、數(shù)學(xué)、文學(xué)、音樂(lè)、舞蹈、繪畫(huà)、歷史學(xué)的產(chǎn)生、發(fā)展,都和巫術(shù)活動(dòng)有關(guān),甚至連知識(shí)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fā)展而來(lái)。可見(jiàn)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jī)r(jià)值。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huì)尚未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時(shí),尤其如此。在那時(shí)由巫文化所構(gòu)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dāng)社會(huì)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特別是國(guó)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shí),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xù)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tǒng)治階級(jí)吸收,并將其系統(tǒng)化,儀禮化,用來(lái)為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服務(wù)。作為中國(guó)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mǎn)文化,都沒(méi)有逃脫這種命運(yùn)。本文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民間薩滿(mǎn)信仰和宮廷薩滿(mǎn)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mǎn)信仰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也是為歷來(lái)的薩滿(mǎn)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wèn)題。現(xiàn)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yàn)榍宕墨I(xiàn)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huì)典》(雍正、嘉慶時(shí)代)、《禮部則例》、《大清會(huì)典事例》、《紐祜祿氏滿(mǎn)洲祭天、祭神典禮》、《國(guó)朝宮史》等,詳細(xì)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mǎn)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yǎng)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guān)薩滿(mǎn)祭祀的實(shí)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mǎn)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mǎn)族薩滿(mǎn)習(xí)俗和清代宮廷薩滿(mǎn)儀典,提供了翔實(shí)可靠的資料。
薩滿(mǎn)及其信仰,本是中國(guó)北方阿爾泰語(yǔ)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xí)俗,流傳地區(qū)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mǎn)族、達(dá)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mǎn)習(xí)俗流傳。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的薩滿(mǎn)信仰在長(zhǎng)期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形成了一個(gè)獨(dú)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mǎn)文化傳承最穩(wěn)固的地區(qū)。這種傳承無(wú)論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chēng)為森林薩滿(mǎn)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qū),是中國(guó)薩滿(mǎn)傳承的又一個(gè)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chēng)為草原薩滿(mǎn)文化圈。蒙古族薩滿(mǎn),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傳播和逐漸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一部分薩滿(mǎn)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mǎn)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mǎn)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dāng)時(shí)一些大薩滿(mǎn)(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hù)偶像,并諳星術(shù),預(yù)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xún)。“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jīng)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yùn)。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shù)。托其欲構(gòu)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xún)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yǔ)以答之。”[3]當(dāng)時(shí),薩滿(mǎn)幾乎主宰部落或國(guó)家大事。據(jù)《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yīng)有適合其新勢(shì)權(quán)之尊號(hào)。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zhǎng)開(kāi)大會(huì)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fā)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hào)之?dāng)?shù)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hào)。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qiáng)者之汗。’諸部長(zhǎng)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hào)成吉思汗。時(shí)年44歲。”[4]此類(lèi)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xiàn)中經(jīng)常見(jiàn)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huì),喇嘛與薩滿(mǎn)之間的斗爭(zhēng)從未間斷過(guò),特別是對(duì)薩滿(mǎn)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mǎn)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wèi)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guī)定取締翁袞。對(duì)邀請(qǐng)男女薩滿(mǎn)來(lái)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duì)請(qǐng)來(lái)男女妖術(shù)師耍魔術(shù)者的乘馬和妖術(shù)師的馬,歸告發(fā)者所有,知而不報(bào)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duì)薩滿(mǎn)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mǎn)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mǎn)信仰[6]。
古代薩滿(mǎn)祭祀研究論文
自從十七世紀(jì)末葉和清代初年,隨著中國(guó)薩滿(mǎn)信仰習(xí)俗被介紹到西方[1],引起西方學(xué)者對(duì)阿爾泰語(yǔ)系廣袤世界同類(lèi)民俗事象的關(guān)注,并在此后的三個(gè)世紀(jì)中,學(xué)者們對(duì)薩滿(mǎn)世界的考察和研究就從未停止,而且使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發(fā)展成為世界性的課題。
國(guó)際上許多學(xué)者對(duì)薩滿(mǎn)習(xí)俗的考察和研究,一般歸于對(duì)“薩滿(mǎn)教”(Shamanism)的研究,中國(guó)學(xué)術(shù)界通常也使用“薩滿(mǎn)教”一詞,但誰(shuí)都知道,薩滿(mǎn)在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中的傳承由來(lái)已久,它從形成的時(shí)候起就是一種原始的民間崇拜和信仰的產(chǎn)物,其傳承和傳播完全處于一種自發(fā)的狀態(tài)之中,屬于信仰文化或巫術(shù)文化的范疇。直到今天,“薩滿(mǎn)”絕非一種現(xiàn)代意義上的“宗教”,它的傳承和傳播方式,仍然是一種巫術(shù)行為,也可以稱(chēng)之為薩滿(mǎn)巫術(shù)。這樣看來(lái),薩滿(mǎn)信仰屬于中國(guó)巫文化系統(tǒng),或者說(shuō)它是中國(guó)巫文化的一種特殊表現(xiàn)形式。
中國(guó)的巫文化是一個(gè)歷史悠久,內(nèi)容十分龐雜的系統(tǒng),根據(jù)歷史文獻(xiàn)記載和現(xiàn)代的民俗傳承,如果將中國(guó)的巫文化作學(xué)術(shù)上的分類(lèi),筆者認(rèn)為它包括了兩個(gè)有機(jī)的組成部分:即中國(guó)北方諸民族傳承的薩滿(mǎn)文化和中國(guó)南方諸民族中傳承的儺文化(即面具文化)。這也是近幾年來(lái)中國(guó)民俗學(xué)對(duì)中國(guó)巫文化的宏觀關(guān)照和學(xué)術(shù)研究的新的走向。過(guò)去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薩滿(mǎn)文化的研究一直是熱門(mén),考察所得資料異常豐富。最近幾年,儺文化的考察和研究后來(lái)居上,造成一種十分熱烈的空氣。薩滿(mǎn)文化與儺文化的相互關(guān)照,一定會(huì)使中國(guó)巫文化的研究出現(xiàn)嶄新局面。
巫文化,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往往將其歸入原始信仰,有時(shí)也稱(chēng)為“民俗宗教”[2],在這種情況下,“宗教”一詞使用了廣義的概念。長(zhǎng)期以來(lái),“宗教”一詞在民俗學(xué)研究中經(jīng)常給研究者造成困惑,以致使我們很難描述某些民俗事象。為了區(qū)別于“現(xiàn)代宗教”,學(xué)者們于是提出了“民俗宗教”的概念,也是完全適用的。“民俗宗教”將巫文化包含其中,為敘述和研究帶來(lái)方便。中國(guó)文化發(fā)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巫文化曾是中國(guó)文化的源頭,中國(guó)古老的科學(xué)和文化發(fā)展均與巫文化有關(guān),如文字、天文、醫(yī)療、數(shù)學(xué)、文學(xué)、音樂(lè)、舞蹈、繪畫(huà)、歷史學(xué)的產(chǎn)生、發(fā)展,都和巫術(shù)活動(dòng)有關(guān),甚至連知識(shí)分子階層都是由巫發(fā)展而來(lái)。可見(jiàn)巫文化作為各種文化的母體,具有重要的研究?jī)r(jià)值。嚴(yán)格說(shuō)來(lái),巫文化是一種民間傳承,它在原始社會(huì)尚未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時(shí),尤其如此。在那時(shí)由巫文化所構(gòu)成的精神世界,正是原始民的宇宙觀。當(dāng)社會(huì)出現(xiàn)階級(jí)分化,特別是國(guó)家形成之后,巫文化的傳播情景則完全不同。這時(shí),巫文化除在民間繼續(xù)傳承外,其中許多成分被統(tǒng)治階級(jí)吸收,并將其系統(tǒng)化,儀禮化,用來(lái)為鞏固其統(tǒng)治地位服務(wù)。作為中國(guó)巫文化組成部分的儺文化和薩滿(mǎn)文化,都沒(méi)有逃脫這種命運(yùn)。本文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探討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并在此基礎(chǔ)上將民間薩滿(mǎn)信仰和宮廷薩滿(mǎn)典禮作些比較。
清代宮廷的薩滿(mǎn)祭祀是民俗宗教——薩滿(mǎn)信仰研究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也是為歷來(lái)的薩滿(mǎn)文化研究所忽視了的問(wèn)題。現(xiàn)在將他提上研究日程,是因?yàn)榍宕墨I(xiàn)史料中,如《八旗通志》、《大清通典》、《大清會(huì)典》(雍正、嘉慶時(shí)代)、《禮部則例》、《大清會(huì)典事例》、《紐祜祿氏滿(mǎn)洲祭天、祭神典禮》、《國(guó)朝宮史》等,詳細(xì)記載了清代宮廷薩滿(mǎn)祭祀的典章制度。曼殊、震鈞的《天咫偶聞》、昭梿的《嘯亭雜錄》、吳振城的《養(yǎng)吉齋叢錄》、姚元之的《竹葉亭雜錄》、麟慶的《鴻雪因緣圖記》等著作中也涉及到清代宮廷、王室有關(guān)薩滿(mǎn)祭祀的實(shí)錄。特別是清代乾隆12年(1747年)奉旨編纂的《欽定滿(mǎn)洲祭神祭天典禮》,為我們研究滿(mǎn)族薩滿(mǎn)習(xí)俗和清代宮廷薩滿(mǎn)儀典,提供了翔實(shí)可靠的資料。
薩滿(mǎn)及其信仰,本是中國(guó)北方阿爾泰語(yǔ)系諸民族普遍傳承的一種習(xí)俗,流傳地區(qū)十分廣闊。居住在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白山黑水和大小興安嶺一帶的滿(mǎn)族、達(dá)斡爾族、赫哲族、鄂倫春族、鄂溫克族、錫伯族及部分入旗的漢族(漢軍旗人)中,直到今天,仍有薩滿(mǎn)習(xí)俗流傳。中國(guó)東北地區(qū)的薩滿(mǎn)信仰在長(zhǎng)期的歷史發(fā)展過(guò)程中,形成了一個(gè)獨(dú)特的文化圈,也是薩滿(mǎn)文化傳承最穩(wěn)固的地區(qū)。這種傳承無(wú)論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帶有森林、狩獵和漁獵色彩,可稱(chēng)為森林薩滿(mǎn)文化圈。華北蒙古族地區(qū),是中國(guó)薩滿(mǎn)傳承的又一個(gè)文化圈,這一文化圈帶有濃郁的草原游牧特色,可稱(chēng)為草原薩滿(mǎn)文化圈。蒙古族薩滿(mǎn),傳承十分古老,但變異也較大。在元代(1279-1368)隨著藏傳佛教(喇嘛教)在蒙古地區(qū)的傳播和逐漸占據(jù)統(tǒng)治地位,一部分薩滿(mǎn)信仰融入喇嘛教,一部分漸次消失,人為的因素曾一度割斷了蒙古族薩滿(mǎn)信仰的傳承。蒙古族在信奉喇嘛教之前,薩滿(mǎn)信仰在部落上層和民眾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dāng)時(shí)一些大薩滿(mǎn)(巫師)都被收羅在蒙古宮廷中,他們守護(hù)偶像,并諳星術(shù),預(yù)言日月之蝕,擇定吉日兇日,人們有事必去咨詢(xún)。“凡宮廷所用之物,以及貢品,必經(jīng)此輩以火凈之,此輩得留取若干。兒童之誕生,則召其至,以卜命運(yùn)。有病者亦延其至而求助于其咒術(shù)。托其欲構(gòu)諂某人,只須言某人之疾,蓋因某人厭禳所致。人有咨詢(xún)者,此輩則狂舞其鼓而召魂魔,已而昏迷,偽作神語(yǔ)以答之。”[3]當(dāng)時(shí),薩滿(mǎn)幾乎主宰部落或國(guó)家大事。據(jù)《多桑蒙古史》載:“塔塔爾諸游牧部落既平,鐵木真應(yīng)有適合其新勢(shì)權(quán)之尊號(hào)。1206年春,遂集諸部長(zhǎng)開(kāi)大會(huì)于斡難河流附近之地,建九旅白旄纛。珊蠻或卜者闊闊出者,常代神發(fā)言,素為蒙古人所信奉,茲莊然告鐵木真曰:‘具有古兒汗和大汗尊號(hào)之?dāng)?shù)主既已敗亡,不宜采用此有污跡之同一尊號(hào)。今奉天命,命其為成吉思汗或強(qiáng)者之汗。’諸部長(zhǎng)群贊其議,乃上鐵木真尊號(hào)成吉思汗。時(shí)年44歲。”[4]此類(lèi)記載,在蒙古族古代文獻(xiàn)中經(jīng)常見(jiàn)到。有元一代,在蒙古族上層社會(huì),喇嘛與薩滿(mǎn)之間的斗爭(zhēng)從未間斷過(guò),特別是對(duì)薩滿(mǎn)供奉的偶像“翁袞”,歷加取締。元代滅亡之后,蒙古民族退居漠北,喇嘛教信仰日漸深入民間,薩滿(mǎn)更處于不利地位。1640年制定的《蒙古衛(wèi)拉特法典》,其中明文規(guī)定取締翁袞。對(duì)邀請(qǐng)男女薩滿(mǎn)來(lái)家者,給予不等馬匹的處罰。對(duì)請(qǐng)來(lái)男女妖術(shù)師耍魔術(shù)者的乘馬和妖術(shù)師的馬,歸告發(fā)者所有,知而不報(bào)者受罰,甚至使高貴者受到詛咒,也要罰馬五匹等等[5]。這些條律,對(duì)薩滿(mǎn)信仰是很大的打擊。但盡管如此,在廣袤的蒙古草原,薩滿(mǎn)信仰并未絕跡,甚至在近代,科爾沁草原仍流行薩滿(mǎn)信仰[6]。
民歌發(fā)展論文:滿(mǎn)族民歌繼承與發(fā)展
本文作者:李鑫李世綱單位:大慶師范學(xué)院藝術(shù)學(xué)院音樂(lè)系
小調(diào)滿(mǎn)族民歌中以小調(diào)體裁數(shù)量為最多,這個(gè)題材不僅觸及到歷史題材,而且也反應(yīng)當(dāng)代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滿(mǎn)族人民英勇好戰(zhàn),這種崇尚武功的精神滲透于滿(mǎn)族人的生活之中,同時(shí)也反映在滿(mǎn)族民歌之中,小調(diào)《軍歌》就及其具有代表性。滿(mǎn)族自古就有尊老敬上、禮貌待客的傳統(tǒng)美德。在一些群體性的大型活動(dòng)之中,大都離不開(kāi)民歌。在祭祀活動(dòng)中演唱“祭祀歌”,在祝壽或結(jié)婚儀式上演唱“空齊歌”,在喪葬儀式中唱的“哭喪調(diào)”等等。滿(mǎn)族的小調(diào)曲調(diào)活潑,情節(jié)生動(dòng),風(fēng)趣幽默的詼諧歌曲也頗具特點(diǎn)。例如《拜年調(diào)》、《打花名》等,在人物神態(tài)的刻畫(huà)和語(yǔ)言的表達(dá)上都較為準(zhǔn)確細(xì)致。此外流傳的現(xiàn)代民歌,也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滿(mǎn)族的生活。如《六月探妹》、《四季抗戰(zhàn)歌》、《新五勸》、《黑龍江好地方》等等歌曲,都傾吐了滿(mǎn)族人的理想和愛(ài)憎。兒歌與其他民歌一樣,滿(mǎn)族兒歌的內(nèi)容除了反映社會(huì)生活外,大多與游戲及傳播知識(shí)有關(guān)。至今流傳的兒歌有《搖籃曲》、《對(duì)花》、《壓板歌》、《莊稼十花名》等,其中人們最熟悉的是《搖籃曲》。由于《搖籃曲》流傳的地域極為廣泛,并且千百年來(lái)一直在滿(mǎn)族婦女中流傳,因此唱調(diào)是多種多樣的。《搖籃曲》的唱詞一般都比較簡(jiǎn)練,而且大同小異,最初都是用滿(mǎn)語(yǔ)演唱的,但隨著滿(mǎn)族人逐漸放棄民族語(yǔ),現(xiàn)在流傳下來(lái)的《搖籃曲》大都是用漢語(yǔ)演唱的,能夠用滿(mǎn)語(yǔ)演唱的人已經(jīng)不多了。但不管語(yǔ)言如何變換,《搖籃曲》的曲調(diào)形式基本上沒(méi)有改變,滿(mǎn)族的《搖籃曲》,是最富滿(mǎn)族民族特色的傳統(tǒng)民歌之一。也是千百年來(lái),一代一代人口耳相傳的結(jié)果,不僅為我們保留下了極好的滿(mǎn)族音樂(lè),也保留了極好的滿(mǎn)族古歌,同時(shí)也構(gòu)成了滿(mǎn)族獨(dú)特的育兒風(fēng)俗。薩滿(mǎn)神歌“薩滿(mǎn)神歌”是滿(mǎn)族薩滿(mǎn)祭祀時(shí)所演唱的歌。由于神歌與薩滿(mǎn)教同時(shí)產(chǎn)生,因此有了薩滿(mǎn)教,就有了神歌。所以薩滿(mǎn)神歌更能代表滿(mǎn)族早期音樂(lè)形式。每逢豐收吉慶之日,滿(mǎn)族人民都要舉行隆重的祭祀儀式,演唱祭祀調(diào),祭祀儀式的主司者便是薩滿(mǎn)。祭祀活動(dòng)多則三天至五天,少則也得兩天,祭祖時(shí)主人家請(qǐng)“薩滿(mǎn)”和“扎力”來(lái)家里舉行各種祭祀儀式。“薩滿(mǎn)”頭戴神帽,身穿神裙,腰系神鈴,手擊神鼓。隨著《祭祀調(diào)》的節(jié)奏且歌且舞。各地區(qū)和各姓氏的“薩滿(mǎn)”在祭祀儀式和演唱程序上各有不同,因此也多種多樣。與其他類(lèi)型的滿(mǎn)足民歌不同的是,滿(mǎn)族薩滿(mǎn)音樂(lè)有比較固定的曲調(diào)形式,神歌大多是用滿(mǎn)語(yǔ)保存下來(lái)的。
滿(mǎn)族民歌的音樂(lè)特征
滿(mǎn)族民歌中的調(diào)式、音階構(gòu)成的特色以五聲音階和五聲性調(diào)式構(gòu)成的歌曲最為常見(jiàn)。隨著歷史的發(fā)展,滿(mǎn)族民歌在清朝時(shí)期雖然很繁榮興盛,但到了清末,由于受到漢文化的影響,相當(dāng)一部分民歌都發(fā)展成了說(shuō)唱和戲曲,只保留下來(lái)很少一部分。除了薩滿(mǎn)神歌以外的勞動(dòng)號(hào)子、小唱以外,民歌還采用規(guī)整的五聲音階,音程的構(gòu)成形式大多數(shù)都以大、小三度音程為主,音域多數(shù)在八度以?xún)?nèi),所以說(shuō)并不是所有的民歌都使用五聲音列,很少出現(xiàn)七聲音節(jié)。在薩滿(mǎn)神歌中多數(shù)是多采用三、四聲的調(diào)式音階,有時(shí)也有二聲調(diào)式音節(jié)的出現(xiàn)。滿(mǎn)族民歌歌詞內(nèi)容豐富多彩,其內(nèi)容與人們現(xiàn)實(shí)生活情況緊密相連。既有反映滿(mǎn)族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生活環(huán)境的內(nèi)容,也有表現(xiàn)獨(dú)特民風(fēng)民俗和民族性格的歌詞。歌詞有純滿(mǎn)語(yǔ)的,也有滿(mǎn)漢兼用和純漢語(yǔ)三種。滿(mǎn)族民歌經(jīng)常采用以三音組為基礎(chǔ)的各種基本調(diào)式,如以宮調(diào)式、商調(diào)式較多,其中強(qiáng)調(diào)以三音向上級(jí)進(jìn)組成的旋律較多。由于調(diào)式功能性不強(qiáng),在調(diào)性的轉(zhuǎn)移上簡(jiǎn)潔明了,不需要具備許多條件。因此宮商角三音小組是滿(mǎn)族民歌曲調(diào)產(chǎn)生的一個(gè)重要基礎(chǔ)。在演唱方面,滿(mǎn)族民歌的唱法各具特色,根據(jù)不同的曲調(diào)不同的演唱形式大致可分:真聲唱法、輕聲唱法、真假聲結(jié)合唱法等。以真假聲結(jié)合唱法為例,在演唱時(shí)根據(jù)風(fēng)格的不同,隨時(shí)調(diào)整唱歌狀態(tài),大大提高了歌唱能力,豐富了音樂(lè)的表現(xiàn)手法,拓寬了演唱音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這種唱法一般運(yùn)用在號(hào)子、山歌和小唱中。正是由于這些特殊演唱效果的運(yùn)用,才使得我國(guó)各地的民歌具有獨(dú)特的魅力和風(fēng)格。由于歷史的原因,滿(mǎn)族民歌除了部分被漢族漢化以外,傳承下來(lái)的很少。滿(mǎn)族民歌作為一種表現(xiàn)手段,我們當(dāng)今不僅要很好的傳承下去還要開(kāi)發(fā)新的演唱方式以適應(yīng)當(dāng)代審美需求,為繁榮和發(fā)展我國(guó)民族聲樂(lè)藝術(shù)做出更大的貢獻(xiàn)。
民族融合環(huán)境下的滿(mǎn)族民歌新發(fā)展
漢、滿(mǎn)及所有中國(guó)的少數(shù)民族是兄弟姐妹,是中華民族的共同組成部分。在長(zhǎng)期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中,滿(mǎn)族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和語(yǔ)言、生活方式等方面的特點(diǎn),在長(zhǎng)期、密切的經(jīng)濟(jì)文化交流過(guò)程中,滿(mǎn)族受到先進(jìn)的漢民族的影響,兩族人民的共同性愈來(lái)愈多,其中一部分滿(mǎn)人逐漸與漢民族融合。從滿(mǎn)族民歌的音樂(lè)特征上看,其藝術(shù)表現(xiàn)形式是多樣的,因此,滿(mǎn)族民歌是詩(shī)歌與音樂(lè)的有機(jī)結(jié)合。當(dāng)人們的思想情感無(wú)法用語(yǔ)言表達(dá)時(shí),民歌是最直接抒情的工具,在這種藝術(shù)審美交流中,人們的情感得到最大化的釋放,也實(shí)現(xiàn)了民歌的自身藝術(shù)價(jià)值。這種自然的融合,乃是正常的、進(jìn)步的現(xiàn)象,是人類(lèi)向未來(lái)的共產(chǎn)主義世界各民族大融合發(fā)展的必然趨勢(shì)。滿(mǎn)族的文化雖然出現(xiàn)了與漢族融合的新局面,但是也不能否定滿(mǎn)族民歌在新形勢(shì)下的客觀存在。首先從民族學(xué)角度看,既然民族存在,那么其文化就一定還存在。作為民族文化特征的基本要素之一的音樂(lè)文化在民族融合過(guò)程中的到了最充分的發(fā)展。其次從社會(huì)學(xué)角度出發(fā),音樂(lè)作為一個(gè)國(guó)家或一個(gè)民族的上層建筑,常常起到維系一定社會(huì)組織的功能作用。因此音樂(lè)文化在滿(mǎn)族融合的特殊政治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占有相當(dāng)重要的地位。最后,從文化人類(lèi)學(xué)角度來(lái)看,一個(gè)民族距離現(xiàn)代文明社會(huì)越遠(yuǎn),生產(chǎn)力就越落后,其民族音樂(lè)與生活的關(guān)系就越為密切。
原生態(tài)音樂(lè)對(duì)師院音樂(lè)教學(xué)的影響
原生態(tài)文化是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積淀,是各族人民所創(chuàng)造出來(lái)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產(chǎn)物,是獨(dú)特的精神和文化,有著鮮明的特色和獨(dú)有的感染力,原生態(tài)音樂(lè)是一種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有著深厚的內(nèi)涵,歷史文化的另一種展現(xiàn),能夠讓人們提高審美,并且有著極高的研究?jī)r(jià)值,是一種稀有的文化財(cái)富,我們是文化資源的大國(guó),音樂(lè)歷史悠久,資源豐富,我們56個(gè)民族各個(gè)民族幾乎都有自己的原生態(tài)音樂(lè)今,原生音樂(lè)文化擔(dān)負(fù)著重要的角色,是我們民族文化的延續(xù)和積累。原生態(tài)音樂(lè)與我們民族的發(fā)展是不可分割的,是我們民族文化的精髓,也是我們民族靈魂的體現(xiàn)。在中國(guó)漫長(zhǎng)的歷史進(jìn)程中,原生態(tài)音樂(lè)從形成到漸變,再到發(fā)展,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結(jié)晶,凝聚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力量和智慧,也傳承著我們中華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因此,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的教育在音樂(lè)教學(xué)中也越為重要,在社會(huì)上也得到越來(lái)越多的關(guān)注,原汁原味的音樂(lè)文化從逐漸消失到重新地回歸,它讓我們認(rèn)識(shí)到了,如今的潮流就是弘揚(yáng)和發(fā)展我們的民族文化。在我國(guó)璀璨的原生音樂(lè)文化中,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則是我們當(dāng)之無(wú)愧的代表。薩滿(mǎn)教是人類(lèi)社會(huì)早期的自然崇拜的產(chǎn)物,有著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萬(wàn)物有靈的理念,因此薩滿(mǎn)教也可以說(shuō)已成為世界性的文化現(xiàn)象。它蘊(yùn)含的哲理極為深刻。在人類(lèi)歷史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薩滿(mǎn)文化是維系氏族家族的精神和物質(zhì)生活的支柱。
在東北諸族中,滿(mǎn)族對(duì)薩滿(mǎn)文化形成繼承是最為突出薩滿(mǎn)音樂(lè)在文化傳承方面有著極為突出的社會(huì)價(jià)值。在歷史的發(fā)展時(shí)期,薩滿(mǎn)能夠在中國(guó)北方各部族中得以生存和發(fā)展是因?yàn)樗_滿(mǎn)有著深厚的民族文化堅(jiān)實(shí)根基。生存于各部族社會(huì)中的薩滿(mǎn),既是創(chuàng)造者,又是負(fù)載者,它創(chuàng)造者本民族的文化,特有的文化,對(duì)于音樂(lè)也是如此。經(jīng)調(diào)查研究,在原始的部落里都有著較高的審美藝術(shù),影響這一部人,并帶動(dòng)部落從而形成一種文化,在薩滿(mǎn)文化構(gòu)成的社會(huì)價(jià)值中,大部分就是音樂(lè)文化來(lái)體現(xiàn)的。一個(gè)民族音樂(lè)的靈魂和思想正是這個(gè)民族的音樂(lè)所展現(xiàn)出來(lái)的情感和精神,是這個(gè)民族的發(fā)源之根,通過(guò)文化我們才能深層次的了解音樂(lè),對(duì)于滿(mǎn)族薩滿(mǎn)音樂(lè)可追溯到禹舜時(shí)代,滿(mǎn)族祭祀音樂(lè)滿(mǎn)足了古代的音樂(lè)文化,也為世界提供了寶貴的研究資料,經(jīng)過(guò)了滿(mǎn)族人民的不斷發(fā)展很世代創(chuàng)造,使音樂(lè)取得了巨大的發(fā)展,載史冊(cè)記載中:官民歲時(shí)聚會(huì)做樂(lè),先命善歌者數(shù)背前行,士女相隨,更相隨和。只是一個(gè)能歌善舞的民族。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多賽用一唱眾和形式,以薩滿(mǎn)器樂(lè)伴奏,并構(gòu)成相呼應(yīng)的形式,并且多為同度,(大二度、大小三度)進(jìn)行,因?yàn)槭軡M(mǎn)語(yǔ)語(yǔ)音協(xié)和規(guī)律所制約;調(diào)式為兩種:一種是能明顯區(qū)分調(diào)式特征的,另一種調(diào)式不明顯,旋律由三個(gè)音組成,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是歌。舞。樂(lè)三位一體的表演歌舞表演貫穿于整個(gè)歌舞祭祀。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中,神鼓、腰鈴、抬鼓、晃鈴、拍板誒主要打擊樂(lè)器神鼓是薩滿(mǎn)音樂(lè)中震撼心靈的樂(lè)器,是薩滿(mǎn)跳神用的,在薩滿(mǎn)文化中都:鼓是可以讓人與神之間進(jìn)行溝通、神可以聽(tīng)清的音樂(lè)語(yǔ)言,薩滿(mǎn)全部活動(dòng)都是神鼓,在中國(guó)鼓文化研究中寫(xiě)出在薩滿(mǎn)鼓中保存最多的就是鼓的神秘,并且也是驅(qū)魔的重要法器。腰鈴與神鼓配合演奏:抬鼓、晃鈴、拍板等樂(lè)器也是在薩滿(mǎn)宗教儀式中出現(xiàn)及使用,并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和一定的象征意義。
在了解自己的民族音樂(lè)文化后,才能對(duì)祖國(guó)對(duì)民族有著無(wú)限的自豪和熱愛(ài),只有重視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發(fā)展,才能使我們的民族音樂(lè)快速發(fā)展。西方教育文化沖擊著我們的民族文化,只有繼承,我們的文化才不會(huì)消失。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在高師教育中有一定的壓力和阻力,受到語(yǔ)言的教學(xué)困擾和影響,我們要在教學(xué)中不斷實(shí)踐。如何更好的將原生態(tài)音樂(lè)在高師教育中進(jìn)行發(fā)展,需要大力推廣原生態(tài)音樂(lè),我們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原生態(tài)音樂(lè)教育中去,要樹(shù)立原生態(tài)音樂(lè)在高師音樂(lè)教育中的地位,要以繼承和傳播為基礎(chǔ),我們要知道原生態(tài)音樂(lè)是發(fā)展民族的,最淳樸的音樂(lè)形式,堅(jiān)持原生態(tài)的音樂(lè)教育,實(shí)踐與發(fā)展一同并進(jìn)。但是要與世界音樂(lè)教育發(fā)展相適應(yīng),要進(jìn)行全面的音樂(lè)教育學(xué)習(xí),要牢固樹(shù)立以民族音樂(lè)教育為本,堅(jiān)持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觀念,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高校音樂(lè)的創(chuàng)新和實(shí)踐。我們還要大力進(jìn)行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宣傳,讓人們了解原生態(tài)音樂(lè),使學(xué)生更加深入了解和體會(huì)原生態(tài)音樂(lè)蘊(yùn)含的意義和獨(dú)特魅力。并要提高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科技含量,將原生態(tài)音樂(lè)與現(xiàn)在相結(jié)合,必須要加大對(duì)于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研究與教學(xué)。其次,實(shí)踐原生態(tài)音樂(lè)教育給學(xué)生們提供一個(gè)感受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機(jī)會(huì),營(yíng)造唱民歌的環(huán)境,加強(qiáng)民族音樂(lè)母語(yǔ)教育,要學(xué)習(xí)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各個(gè)方面,體會(huì)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加強(qiáng)原生民歌的演唱,對(duì)于各個(gè)不同民族的文化強(qiáng)了解和學(xué)習(xí),為了增強(qiáng)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得培養(yǎng),高校要進(jìn)行文化講座,舉辦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活動(dòng),加強(qiáng)對(duì)文化的考察,培養(yǎng)優(yōu)秀的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的人才,提高學(xué)生們?nèi)ダ斫庠鷳B(tài)音樂(lè)文化的意識(shí)。
現(xiàn)在,我們的民族在競(jìng)爭(zhēng)中發(fā)展民族文化的堅(jiān)守發(fā)揚(yáng)傳承是最重要的,民族音樂(lè)教育在高師教育中的地位越來(lái)越重要,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是凝聚著民族精神的寶貴財(cái)富,原生態(tài)音樂(lè)反映出的是我們民族的深刻內(nèi)涵,原生態(tài)文化在高師中不斷地實(shí)踐探索,促進(jìn)的是我國(guó)文化的繁榮,也是我國(guó)精神文明的建設(shè),我們不能忽視著來(lái)自底層的原生態(tài)文化,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將為我們中國(guó)高師音樂(lè)教育開(kāi)闊新視野忽然和只是能源,傳承人類(lèi)文明,民族文化的弘揚(yáng),和諧文明的構(gòu)建這些都離不開(kāi)我們最民族最原生態(tài)的文化,就像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給世界帶來(lái)了多少的研究?jī)r(jià)值,薩滿(mǎn)音樂(lè)文化是無(wú)價(jià)之寶,這是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帶給我們的財(cái)富也是無(wú)價(jià)的。現(xiàn)在,在多元化趨勢(shì)下,我們中國(guó)的高校音樂(lè)教育對(duì)于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繼承發(fā)展研究創(chuàng)新有著義不容辭的責(zé)任,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國(guó)家,如果脫離了本土文化的根,那就發(fā)展下去,原生態(tài)音樂(lè)是我們的本土文化,是最原生態(tài)活動(dòng),也是有著獨(dú)特的藝術(shù)形式,是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寶貴財(cái)富的展現(xiàn),展現(xiàn)了我們中或民族特有的審美觀,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在高師音樂(lè)教育中的探究和實(shí)踐能增加學(xué)生們對(duì)原生態(tài)音樂(lè)文化的保護(hù),發(fā)揚(yáng),繼承。原生態(tài)音樂(lè)的培養(yǎng)對(duì)我們高校教育的建設(shè)有著重大意義。
作者:林代鑫陳特單位:吉林師范大學(xué)音樂(lè)學(xué)院
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舞蹈音樂(lè)論文
摘要:舞者唱奏是舞蹈表演方式之一,主要特征是舞者的表演集歌、舞、樂(lè)于一身。此類(lèi)舞蹈在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中廣泛存在、種類(lèi)繁多。根據(jù)內(nèi)容、題材的不同,文章將其大致分為:帶有宗教色彩舞蹈音樂(lè)中的舞者唱奏及其他類(lèi)型舞蹈音樂(lè)中的舞者唱奏,旨在通過(guò)分析典例對(duì)這一表演形式作進(jìn)一步了解。
關(guān)鍵詞:舞者唱奏舞蹈音樂(lè)少數(shù)民族
舞者唱奏,即集歌、舞、樂(lè)于舞者一身的一種表演形式。這類(lèi)舞蹈音樂(lè)在我國(guó)少數(shù)民族中廣泛存在,其內(nèi)容非常豐富、種類(lèi)繁多。可分為以下兩種類(lèi)型。
一、帶有宗教色彩舞蹈音樂(lè)中的舞者唱奏
舞者唱奏的表演形式在我國(guó)的宗教性舞蹈中有著久遠(yuǎn)的歷史。在原始社會(huì),有一個(gè)古老的氏族部落,叫“葛天氏”,他們的舞蹈形式是“‘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八闋’即八首歌,分別是《載民》,歌頌大地;《玄鳥(niǎo)》,歌頌氏族崇拜的圖騰;《遂草木》,祝愿草木茂盛;《奮五谷》祈禱五谷豐收;‘《敬天常》,向上天表達(dá)敬意;《達(dá)帝功》,歌頌天帝的功德;《依地德》,感謝土地德賜予;《總獸禽之極》,盼鳥(niǎo)獸繁殖’”。①由此可以看出,這是一部祭祀天地圖騰的舞蹈。表演的過(guò)程中除了歌唱外,還有舞:“三人操牛尾”,同時(shí)還有伴奏:“投足”(踏足為節(jié)),體現(xiàn)了舞者歌、舞、樂(lè)相結(jié)合的表演形式。這種舞者唱奏的表演方式,如今在我國(guó)民間流傳的各類(lèi)宗教舞蹈中仍可以看到鮮活的實(shí)例。
薩滿(mǎn)舞是薩滿(mǎn)(即巫師)在祈神、祭祀、驅(qū)邪、治病等活動(dòng)中表演的舞蹈,俗稱(chēng)“跳大神”。這種舞蹈是隨著原始宗教(薩滿(mǎn)教)產(chǎn)生的,反映原始狩獵、漁獵生活和圖騰崇拜,產(chǎn)生于原始母系氏族社會(huì)的繁榮時(shí)期。至今,薩滿(mǎn)舞在中國(guó)的蒙古、鄂倫春、滿(mǎn)族、赫哲、維吾爾等北方十幾個(gè)民族中還有遺存。各族薩滿(mǎn)舞的表演依其道具、服飾不同而各有特點(diǎn),但舞者唱奏這一形式卻是各族薩滿(mǎn)舞共有的特點(diǎn)。
民間藝術(shù)地域特征的區(qū)別及聯(lián)系
摘要:本文是基于傳統(tǒng)地氣理論對(duì)民間藝術(shù)的地域文化特色形成原因的分析,也是對(duì)民間藝術(shù)活態(tài)傳承所離不開(kāi)的地方語(yǔ)境的思考。傳統(tǒng)民藝中所講的“地氣”,出自《周禮・考工記》,是指因地方的地理?xiàng)l件不同導(dǎo)致的自然資源的差異。而在其后兩千多年的發(fā)展中,人們對(duì)于“地氣”有了更加全面的認(rèn)識(shí)。從社會(huì)學(xué)和人類(lèi)學(xué)的角度講,藝術(shù)品的產(chǎn)生與種族、時(shí)代、環(huán)境都有著密切聯(lián)系。因此,除了傳統(tǒng)意義之外,還可以用“地方的風(fēng)氣”來(lái)進(jìn)行解讀。本文以東北地區(qū)和山東地區(qū)的對(duì)比為例,從民族、歷史、信仰、民俗四個(gè)方面,剖析了地理?xiàng)l件引起的地方人文環(huán)境差異對(duì)民間藝術(shù)的地域文化特色產(chǎn)生的影響。
關(guān)鍵詞:民間藝術(shù);地域性;民族;歷史;信仰;民俗
在兩千多年前,《考工記》天時(shí)、地氣、材美、工巧成為當(dāng)時(shí)評(píng)判一件器物是否精美的標(biāo)準(zhǔn)。所謂地氣,在傳統(tǒng)造物觀念中多是指材料的地域性特征,即受到各地不同地理?xiàng)l件的影響,所產(chǎn)出的自然資源各有特色。然而隨著人類(lèi)文明的發(fā)展,各地形成了獨(dú)具特色的文化風(fēng)貌,又由于人口遷徙等原因造成了文化的傳播,使得地方的文化特色不僅是地理環(huán)境的影響,更多的是人文環(huán)境和歷史傳承等因素影響的結(jié)果。藝術(shù)作為文化的獨(dú)特組成部分,每一個(gè)民族或時(shí)代的藝術(shù)都是民族文化和時(shí)代文化的體現(xiàn)。同樣,地方的民間藝術(shù)也與地域文化特色有著密切聯(lián)系。
1.民族因素對(duì)地域性產(chǎn)生的影響
從文化人類(lèi)學(xué)的角度講,文化的發(fā)展都與人種及人的生活習(xí)慣有關(guān),一個(gè)民族藝術(shù)的發(fā)展往往依靠著該民族的文化,而一個(gè)民族文化的形成與其所處的地理環(huán)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早在1955年,美國(guó)進(jìn)化派人類(lèi)學(xué)家朱利安•斯圖爾德就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環(huán)境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guān)系,從而提出了“文化生態(tài)學(xué)”理論。縱觀歷史可以發(fā)現(xiàn),早期人類(lèi)文明的發(fā)生都伴隨在河流兩岸,出現(xiàn)了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guó)”。這些地方資源豐富,土壤肥沃,適合漁獵和采集,從而發(fā)展出早期的農(nóng)業(yè)和畜牧業(yè)。中國(guó)自古以來(lái)就是有名的農(nóng)業(yè)大國(guó),《易經(jīng)》中有記載:“包犧氏沒(méi),神農(nóng)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這就說(shuō)明在神農(nóng)氏時(shí)期,或者可以確定在石器時(shí)代,人們就已經(jīng)學(xué)會(huì)使用木制的農(nóng)用工具,使得人類(lèi)社會(huì)由采集、狩獵轉(zhuǎn)向農(nóng)耕社會(huì)發(fā)展。山東地處黃河下游,自然資源豐富,是我國(guó)遠(yuǎn)古經(jīng)濟(jì)文化發(fā)展最早的地區(qū)之一。人們用石頭和木頭等材料制作工具、建造房屋,甚至學(xué)會(huì)了燒制陶器,過(guò)上穩(wěn)定的生活,逐漸形成了聚落和城鎮(zhèn),發(fā)展出早期的農(nóng)耕文明。作為以農(nóng)耕為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的民族,安居而思靜,有著勤勞、節(jié)儉、團(tuán)結(jié)、友愛(ài)的文化傳統(tǒng)。從石器、骨器到陶器、鐵器,這些為滿(mǎn)足人們?nèi)粘I钚枰谱鞒鰜?lái)的生產(chǎn)生活工具,是人類(lèi)創(chuàng)造出的最早的藝術(shù)品。游牧民族的文化與農(nóng)耕文化有著本質(zhì)的不同。生產(chǎn)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現(xiàn)象,游牧民族就不會(huì)創(chuàng)造出犁、鋤頭、鐵鍬等農(nóng)用工具。生活在中國(guó)東北部干旱半干旱地區(qū)的東胡系民族,是比較典型的游牧民族。由于這一地區(qū)資源匱乏,生活環(huán)境惡劣,無(wú)法從事種植業(yè),對(duì)農(nóng)耕社會(huì)有所依賴(lài),遷徙、戰(zhàn)爭(zhēng)、掠奪是他們?yōu)榱松娑l(fā)展出來(lái)的文化傳統(tǒng)。游牧民族的生產(chǎn)生活方式最貼近原始社會(huì)的文化,他們以畜牧業(yè)為主,逐水草而居,以肉類(lèi)為主要的食物,強(qiáng)壯且善戰(zhàn)。動(dòng)物毛皮成為他們主要的一種工藝材料,不僅可以做衣服、毛氈等物,還能夠制作酒囊,是取代了陶器、青銅器等笨重器皿的盛酒器。游牧民族是生長(zhǎng)在馬背上的民族,為了適應(yīng)草原上的生存環(huán)境,長(zhǎng)期的遷徙生活使得他們對(duì)生活用具有著輕便易攜的要求,蒙古包、折疊家具、皮質(zhì)酒囊等物品的出現(xiàn)既是資源的合理利用,又符合當(dāng)?shù)厝藗兊男枨蟆?/p>
2.歷史因素對(duì)地域性產(chǎn)生的影響
埃文基人的民間信仰與文化傳承
摘要:埃文基人是俄羅斯的少數(shù)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yuǎn)東地區(qū)。薩滿(mǎn)教不僅是埃文基人對(duì)超自然力量的一種信仰,也是他們理性看待人與自然、動(dòng)物、世界和社會(huì)關(guān)系的一種特殊形式。俄羅斯埃文基人和中國(guó)的鄂溫克、鄂倫春族是文化同源民族,但兩國(guó)的現(xiàn)代薩滿(mǎn)教發(fā)展進(jìn)程和特點(diǎn)卻有很大差別。埃文基人(鄂溫克、鄂倫春族)作為中俄跨界民族,是東北亞各國(guó)不可忽略的文化紐帶。在全球化背景下,他們的價(jià)值和意義日益凸顯。
關(guān)鍵詞:俄羅斯;埃文基;民間信仰中俄比較;結(jié)論啟示
一、俄羅斯埃文基人的人口與分布
1931年,蘇聯(lián)進(jìn)行民族識(shí)別期間,生活在西伯利亞和遠(yuǎn)東地區(qū)的鄂溫克族(包括鄂倫春族)被官方認(rèn)定為埃文基人(эвенки)。2010年,俄羅斯的埃文基總?cè)丝跒?7843人,主要分布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和遠(yuǎn)東地區(qū)。1926年至2010年,埃文基人口增長(zhǎng)緩慢,變動(dòng)情況如表1,具體分布情況如表2。埃文基人的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具有地域特點(diǎn),北部地區(qū)以漁獵、馴鹿、毛皮和養(yǎng)殖業(yè)為主,并有石墨、煤炭等采礦業(yè),南部以加工業(yè)和制造業(yè)為主。埃文基自治區(qū)成立于1930年12月10日,隸屬于克拉斯諾亞爾斯克邊疆區(qū),土地面積為76.76平方公里。自治區(qū)中心為圖拉鎮(zhèn),距莫斯科5738公里。目前,僅有五分之一的埃文基人能講本民族語(yǔ)言。薩哈(雅庫(kù)特)共和國(guó)是埃文基人的主要聚居區(qū)之一,也是埃文基傳統(tǒng)文化保留較為完好的地區(qū)。
二、埃文基人的民間信仰
(一)薩滿(mǎn)。說(shuō)到埃文基人的日常生活和世界觀,就不得不提及他們的宗教———薩滿(mǎn)教。千百年來(lái),埃文基人在與大自然的相處過(guò)程中,形成了他們系統(tǒng)的行為規(guī)范,并制定了各種戒律和禁忌。他們認(rèn)為,生活在原始森林中的每一個(gè)人,都應(yīng)該遵守這些自然法則。人與神之間的媒介是薩滿(mǎn)教的核心,只有被稱(chēng)為“薩滿(mǎn)”的人,才可以擔(dān)當(dāng)人與神之間溝通的使者。薩滿(mǎn)教不僅是埃文基人對(duì)超自然力量的一種信仰,也是他們理性看待人與自然、動(dòng)物、世界和社會(huì)的一種特殊形式。那么,什么樣的人才能配得上薩滿(mǎn)的稱(chēng)謂呢?埃文基人認(rèn)為,只有多才多藝、智慧超群,且具有遠(yuǎn)見(jiàn)卓識(shí)的人,才可以成為薩滿(mǎn)。薩滿(mǎn)不僅是他們精神文化的傳人,也是古老風(fēng)俗的行家,還是出色的歌手和民間故事的講述者,是具有旺盛精力和特異功能的人,熟知祭祀儀式的隱藏秘密,掌握傳統(tǒng)民族醫(yī)學(xué)的奧秘和經(jīng)驗(yàn)。薩滿(mǎn)是人與天上力量———諸神之間的使者。在古代埃文基人的觀念中,世界上不存在等級(jí)制度,人類(lèi)不是大自然的主宰,永遠(yuǎn)也不可能征服自然。大自然對(duì)埃文基人來(lái)說(shuō),不是無(wú)生命的“僵尸”,而是鮮活的“生命體”。當(dāng)埃文基人接近大自然的時(shí)候,他們能夠感受到大自然給予的微妙回應(yīng)。埃文基薩滿(mǎn)的主要任務(wù)是關(guān)懷族人的心靈和他們的平安,這也是薩滿(mǎn)教儀式和跳神作法的主要內(nèi)容。薩滿(mǎn)教儀式分為三種類(lèi)型:第一種儀式是關(guān)于對(duì)族人的心靈關(guān)懷,傾聽(tīng)族人的疾苦和訴求。這個(gè)儀式反映的是,對(duì)從人體“分離”或者“脫離”的心靈,進(jìn)行尋找和安置,“捕獲”孩子的魂魄,以及將逝者的靈魂送往另一個(gè)世界。第二種儀式反映的是,對(duì)氏族物質(zhì)欲望的期盼,賦予獵人護(hù)身符“神”的力量,以及各種算卦和占卜儀式。第三種儀式則與薩滿(mǎn)的成長(zhǎng)、薩滿(mǎn)教精神和薩滿(mǎn)教法器的制作過(guò)程有關(guān)[1](P26)。民間醫(yī)生是薩滿(mǎn)在埃文基社會(huì)扮演的主要角色和最有價(jià)值的角色之一。埃文基薩滿(mǎn)會(huì)用各種植物、礦物質(zhì)、昆蟲(chóng)和小動(dòng)物制作特殊的“民族藥物”,長(zhǎng)達(dá)幾個(gè)世紀(jì)的醫(yī)學(xué)經(jīng)驗(yàn),幫助他們研制出數(shù)百種草藥,而且這些草藥的成分從來(lái)都不重復(fù)。這些不尋常的醫(yī)療方法只有他們知道,從而使得他們與普通的巫師絕然不同。例如,在雅庫(kù)特英格拉小村,有兩位著名的薩滿(mǎn)。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庫(kù)里巴爾金諾娃,是紐兒瑪干家族一位具有傳奇色彩的女薩滿(mǎn)。她出生在俄羅斯西伯利亞奧廖克明斯克兀魯思村一個(gè)孩子眾多的貧苦家庭。她在家中14個(gè)兄妹里排行老大,從小就幫助父母操持家務(wù),教育自己的弟弟妹妹們,沒(méi)有時(shí)間上學(xué)。后來(lái)她們?nèi)野岬搅擞⒏窭〈濉qR特廖娜•彼得羅夫娜知曉很多故事和神話(huà)傳說(shuō),在漫長(zhǎng)的夏夜里,孩子們聚集在她的周?chē)?tīng)她講述關(guān)于人類(lèi)、動(dòng)物和小鳥(niǎo)兒的精彩故事。她在50周歲的時(shí)候,正式成為薩滿(mǎn)。當(dāng)她跳神作法、吟唱、治療病人、占卜未來(lái)的時(shí)候,她會(huì)穿戴自己的薩滿(mǎn)服,擊打薩滿(mǎn)鼓。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深信,薩滿(mǎn)的使命即治病救人,幫助人們減輕痛苦,并獲得快樂(lè)。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是藥用植物方面的行家,她通常使用草藥醫(yī)治那些找她看病的人。她能夠預(yù)知天氣,預(yù)測(cè)狩獵人是否能打到獵物,救人于危難之中。當(dāng)她跳神作法的時(shí)候,她會(huì)用有節(jié)奏的擊鼓聲,為自己的歌聲伴奏,同時(shí)輕輕地跳躍和舞動(dòng),創(chuàng)造出一種與外部世界相連接的特別氛圍。馬特廖娜•彼得羅夫娜度過(guò)了漫長(zhǎng)、艱難但同時(shí)也充滿(mǎn)幸福的人生。她養(yǎng)育了9個(gè)孩子、7個(gè)孫子、25個(gè)重孫和14個(gè)玄孫,在其生命的第112年去世[1](P26)。這位偉大的女薩滿(mǎn)不僅聞名于整個(gè)雅庫(kù)特共和國(guó),而且也為域外人士所熟知。在英格拉小村,還有一位薩滿(mǎn)———色明•斯杰潘納維奇•瓦西里耶夫。1936年1月10日,色明•斯杰潘納維奇出生在紐克扎鎮(zhèn)一個(gè)埃文基世襲薩滿(mǎn)家族中,屬于伊尼阿拉斯(伊內(nèi)特)家族。這個(gè)家族的名稱(chēng)直譯過(guò)來(lái)就是“夜間飛行的小貓頭鷹”。色明•斯杰潘納維奇是一位老兵,退役后從事養(yǎng)鹿、狩獵和趕雪橇。1973年,在巴塔卡氏族元老會(huì)上,通過(guò)了關(guān)于選舉色明•斯杰潘納維奇為薩滿(mǎn)的決定。1975年春天,他在阿累拉克河邊舉行儀式,正式成為薩滿(mǎn),開(kāi)始主持各種宗教活動(dòng),開(kāi)展薩滿(mǎn)醫(yī)療救治。許多患有腎病、軟骨病、癲癇、心血管疾病和內(nèi)分泌疾病的人,前來(lái)向他尋求幫助[1](P25)。盡管在現(xiàn)代人眼里,尤其是在其他民族的眼里,薩滿(mǎn)活動(dòng)充滿(mǎn)了很多神秘的色彩,但薩滿(mǎn)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長(zhǎng)期積累的民族智慧、民族傳統(tǒng),以及民族醫(yī)學(xué)奧秘和精神文化價(jià)值的基礎(chǔ)上開(kāi)展的。(二)動(dòng)物崇拜:埃文基人生活中的熊埃文基人歷來(lái)十分崇拜大森林的主人,包括一切動(dòng)植物。每一代人都崇拜,過(guò)去崇拜,現(xiàn)在也崇拜。由于他們長(zhǎng)期在森林里生活,所以,很多野生動(dòng)物便成為他們圖騰崇拜的對(duì)象。埃文基人把熊尊為最早的人類(lèi),對(duì)熊的圖騰崇拜尤為明顯。中國(guó)的鄂倫春人同樣如此,他們對(duì)熊的崇拜和訴說(shuō),仿佛無(wú)法用世間的語(yǔ)言來(lái)表達(dá)心中的敬畏、依賴(lài)、慈悲和相互的接納。在鄂倫春人的心目中,他們與熊第一次目光交流的瞬間,人與熊的靈魂就已融為一體,無(wú)法分離。作為叢林霸主的森林熊,天賜神力,鄂倫春人尊稱(chēng)它為“阿瑪哈”(鄂倫春語(yǔ)“大爺”之意)。在過(guò)去原始的狩獵過(guò)程中,鄂倫春獵人用古老的狩獵工具很難捕獵到它,不僅如此,熊可以像人一樣直立行走,雄性擁有人類(lèi)一樣的生殖器。被剝皮后的雄性肢體,仿佛是一個(gè)沉睡的拳王,冥冥之中,那無(wú)畏一切的人型獸,以它不可動(dòng)搖的威力牽引著森林人的心靈,仿佛另一個(gè)我,以另一個(gè)目光審視著這個(gè)世界的過(guò)去、現(xiàn)在和未來(lái)。總之,俄羅斯的埃文基人和中國(guó)的鄂溫克、鄂倫春人,作為同源民族,他們對(duì)大自然的認(rèn)知和理念是十分相似的。在很久以前,埃文基人是不準(zhǔn)獵熊的。隨著狩獵工具的不斷進(jìn)步,以及人們宗教觀念的變化,禁止獵熊的禁忌也逐漸淡漠。但是,埃文基人對(duì)熊依然充滿(mǎn)敬畏,圖騰崇拜的文化遺存延續(xù)至今。埃文基人獵熊的方法與獵取其他偶蹄類(lèi)動(dòng)物沒(méi)什么兩樣。一般來(lái)說(shuō),熊很少被逮住,除非是受傷或者不冬眠的熊。當(dāng)熊追逐鹿群的時(shí)候,只要在被咬死的鹿旁邊設(shè)伏,或者安放帶有誘餌的捕獸器,就可以將熊捕獲。出于本能,埃文基人不會(huì)放過(guò)任何獵取熊的機(jī)會(huì)。當(dāng)熊被射殺后,所有的旁觀者和參與狩獵的人都向它奔去,殺死熊的埃文基人對(duì)熊說(shuō):“殺你的人不是我,是某某人或者別的什么人”。所有在場(chǎng)的人都跟著殺死熊的獵人反復(fù)說(shuō)著類(lèi)似的話(huà)。然后,人們把熊的身體翻過(guò)來(lái),背朝下,在地上鋪上一些樹(shù)條或者青苔,就開(kāi)始剝皮。殺死熊的獵人第一個(gè)走過(guò)來(lái),用刀在熊的肚子上劃一道口子,然后,在場(chǎng)的人按照長(zhǎng)幼順序依次重復(fù)這個(gè)動(dòng)作。任何一個(gè)參與狩獵的人都可以參與剝熊皮的過(guò)程,但必須從一個(gè)方向進(jìn)行,因?yàn)樵讷C熊的時(shí)候不可以一開(kāi)始就從兩邊圍捕。在大家剝熊皮的時(shí)候,一些參與狩獵的獵人會(huì)用落葉松的樹(shù)皮制作一些平面烏鴉塑像,在“烏鴉”嘴上蘸上熊的血液,再在上面放上一小塊肉。然后他們把“烏鴉”掛在附近的樹(shù)樁上,或者掛在守候野獸的臺(tái)子上。埃文基人想以此證明:殺死熊的兇手不是人類(lèi),而是這些“烏鴉”,鐵證如山!除了熊掌,熊皮被完整地剝下來(lái)。然后,劃開(kāi)熊的胸腔,每一個(gè)參與狩獵的人都切下一小塊熊心,生吞下肚。按照熊的骨節(jié)對(duì)熊肉進(jìn)行分割,盡量不要把肉弄碎。分割過(guò)程中,每次遇到骨節(jié)的時(shí)候,獵人都要對(duì)熊說(shuō):“老爺爺,小心,這兒有根木頭!”。如果是母熊,他們則稱(chēng)熊為“奶奶”或“伯母”。待熊肉冷卻后就分給大家,髕骨以下的肉,以及四只熊掌、內(nèi)臟、腹內(nèi)油脂、臀部油脂、熊頭和熊皮歸殺死熊的獵人,剩下的部分獵人們平均分配[1](P35)。埃文基人認(rèn)為,熊不僅是人類(lèi)的朋友,更是森林之王,所以對(duì)熊很崇敬。但這種觀念在年輕人當(dāng)中,開(kāi)始逐漸淡化。(三)“萬(wàn)物有靈”觀念埃文基人相信萬(wàn)物有靈,特別崇拜祖先神“瑪魯”,同時(shí)崇拜其他各種神靈,比如“舍利神”,他們深信,惹怒“舍利神”會(huì)使人生病。埃文基人的信仰體現(xiàn)在方方面面,如占卜、夢(mèng)兆、神話(huà)傳說(shuō)等。夢(mèng)境、幻覺(jué)、預(yù)測(cè)等現(xiàn)象在埃文基人的生活中司空見(jiàn)慣。他們把做的夢(mèng)分為吉兇兩種,好夢(mèng)三天之內(nèi)不能告訴他人,兇夢(mèng)必須盡快說(shuō)出來(lái),并用一些法器和咒語(yǔ)破解,以免災(zāi)難發(fā)生。夢(mèng)到捕魚(yú)和見(jiàn)到大魚(yú),預(yù)示能打到獵物,夢(mèng)見(jiàn)太陽(yáng)升起,預(yù)示有好事發(fā)生。夢(mèng)到渡河,預(yù)示全家平安。夢(mèng)見(jiàn)掉牙或剪頭發(fā),預(yù)示家人生病或馴鹿將要死亡[2]。此外,埃文基人對(duì)“火”充滿(mǎn)無(wú)限敬畏,祭火儀式,涵蓋了埃文基人生活的所有領(lǐng)域。例如,埃文基人的“巴噶騰”節(jié)(歡慶節(jié)),是指生活在阿穆?tīng)柡樱ㄖ袊?guó)稱(chēng):黑龍江)流域和雅庫(kù)特地區(qū)的埃文基人的傳統(tǒng)節(jié)日,每年夏季舉行。這個(gè)節(jié)日的主要目的是,使生活在不同地區(qū)的埃文基人有機(jī)會(huì)經(jīng)常交流,建立廣泛聯(lián)系,在節(jié)日期間,教授孩子學(xué)習(xí)傳統(tǒng)文化,以活躍和復(fù)興埃文基語(yǔ)言。通過(guò)傳統(tǒng)技藝比賽,增強(qiáng)埃文基人的文化自信,不讓埃文基的文明之火熄滅。在教育孩子熟悉自己家園的過(guò)程中,讓他們愛(ài)上自己的文化。節(jié)日慶典開(kāi)始以后,首先進(jìn)行祭火儀式,伴隨著贊美歌聲,參加慶典的人穿越“天門(mén)”,驅(qū)邪凈化,祈禱幸福平安。埃文基人在所有的場(chǎng)合都要祭火,因?yàn)槿祟?lèi)生活始終與火為伴。埃文基人認(rèn)為,火神魔力巨大,可以祈求給予自己一切,可以祈求得到野獸,火神能夠讓你過(guò)上溫飽的生活,可以保佑你的父母健康,保佑你和家人遠(yuǎn)離不幸和疾病。節(jié)日當(dāng)天,要舉行各種娛樂(lè)活動(dòng),如服飾展演,埃文基禮儀比賽,歌舞比賽,傳統(tǒng)體育競(jìng)技比賽,民族工藝品展示,學(xué)術(shù)研討,等等。舞蹈如:《埃文基人的土地》《凍土蘇醒》《森林的色彩》《小鹿的生日》,歌曲如:《雅庫(kù)特姑娘》《鹿———你是我的朋友》《北方的夜》《春天來(lái)到馴鹿的故鄉(xiāng)》等。這些傳統(tǒng)歌舞,自上演以來(lái),經(jīng)久不衰,影響深遠(yuǎn)。埃文基人在歌聲中唱道:“我們是埃文基人,我們有皮襖,為了好好地活著,為了不挨餓,請(qǐng)熱愛(ài)大自然,請(qǐng)親吻我們腳下的土地!大地孕育了一切,人類(lèi)只是她的一粒塵埃。天神,請(qǐng)賜予我們食物,請(qǐng)賜予我們幸福!火神,請(qǐng)賜予我們光明,請(qǐng)賜予我們溫暖!”[3]
小議舞蹈創(chuàng)作中的人文精神元素
人類(lèi)最古老、最久遠(yuǎn)又和生活、和時(shí)代最密不可分的藝術(shù)就是舞蹈藝術(shù)。舞蹈又是一門(mén)綜合性的藝術(shù)。它以深遠(yuǎn)廣闊的生活內(nèi)容,生動(dòng)鮮明的藝術(shù)形象,多姿多彩的感性體現(xiàn),靈動(dòng)張揚(yáng)的表現(xiàn)欲望來(lái)展示歷史,贊美時(shí)代,歌頌生活,描繪人生。舞蹈中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淀和豐富的人文精神元素,構(gòu)成了舞蹈藝術(shù)中人的悲歡離合、人的喜怒哀樂(lè)、人的進(jìn)取成長(zhǎng)、人的千姿百態(tài)……
一、人文精神的內(nèi)涵
在西方,“人文精神”一詞應(yīng)該是humanism,通常譯作人文主義、人本主義、人道主義。
狹義是指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的一種思潮,其核心思想為:一,關(guān)心人,以人為本,重視人的價(jià)值,反對(duì)神學(xué)對(duì)人性的壓抑;二,張揚(yáng)人的理性,反對(duì)神學(xué)對(duì)理性的貶低;三,主張靈肉和諧、立足于塵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對(duì)神學(xué)的靈肉對(duì)立、用天國(guó)生活否定塵世生活。
廣義則指歐洲始于古希臘的一種文化傳統(tǒng)。按照我對(duì)這一傳統(tǒng)的理解,人文精神的基本內(nèi)涵可以確定為三個(gè)層次:一是人性,對(duì)人的幸福和尊嚴(yán)的追求,是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二是理性,對(duì)真理的追求,是廣義的科學(xué)精神;三是超越性,對(duì)生活意義的追求。簡(jiǎn)單地說(shuō),就是關(guān)心人,尤其是關(guān)心人的精神生活;尊重人的價(jià)值,尤其是尊重人作為精神存在的價(jià)值。人文精神的基本涵義就是:尊重人的價(jià)值,尊重精神的價(jià)值。
“人文精神是構(gòu)成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地區(qū)文化個(gè)性的核心內(nèi)容;是衡量一個(gè)民族、一個(gè)地區(qū)的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一個(gè)國(guó)家的國(guó)民人文修養(yǎng)的水準(zhǔn),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guó)民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地位和水平。”(《21世紀(jì)素質(zhì)教育系列教材——藝術(shù)的意蘊(yùn)》,陳旭光著,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
版畫(huà)創(chuàng)作民間藝術(shù)論文
一、高等藝術(shù)院校吸取民間剪紙藝術(shù)形態(tài)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教學(xué)研究的歷史概述
高等藝術(shù)院校專(zhuān)家學(xué)者都對(duì)各地區(qū)、各民族的獨(dú)特剪紙這一原始藝術(shù)形式進(jìn)行了深入而系統(tǒng)的研究,并吸取民間剪紙藝術(shù)形態(tài)進(jìn)行了多種樣式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教學(xué)研究"比如: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呂勝中先生對(duì)于民間剪紙等民間美術(shù)進(jìn)行了系統(tǒng)研究,將民間原生態(tài)中極為豐富的剪紙語(yǔ)匯加以提煉,并通過(guò)在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開(kāi)辟了實(shí)驗(yàn)藝術(shù)系"不斷提倡深入發(fā)掘本土文化精神,開(kāi)拓民間原生態(tài)藝術(shù)與當(dāng)代藝術(shù)思想觀念的表達(dá)兩者之間的對(duì)接"
二、東北高校版畫(huà)專(zhuān)業(yè)吸取民間剪紙藝術(shù)形態(tài)進(jìn)行藝術(shù)創(chuàng)作及教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
作為東北特殊地域環(huán)境下的高校版畫(huà)教學(xué),其任務(wù)是在承揚(yáng)傳統(tǒng)西方創(chuàng)作性版畫(huà)的教學(xué)基礎(chǔ)上融入多維的教學(xué)資源,制定趨于現(xiàn)代意識(shí)和學(xué)術(shù)意識(shí)的多元化教學(xué)氛圍,轉(zhuǎn)變版畫(huà)形式化的肌理符號(hào)和游戲性的創(chuàng)作傾向,恢復(fù)版畫(huà)在當(dāng)代開(kāi)放性藝術(shù)環(huán)境中專(zhuān)業(yè)語(yǔ)言的寬泛和張力,特別是應(yīng)吸取東北地域長(zhǎng)期根存和優(yōu)秀的民間藝術(shù)傳統(tǒng)"理由如下:
1.版畫(huà)藝術(shù)自身具有較強(qiáng)的民間藝術(shù)根基
中國(guó)民間版畫(huà)歷史悠久,不但在民間是群眾喜聞樂(lè)見(jiàn)的藝術(shù)形式,而且以它廣泛的表現(xiàn)內(nèi)容、精湛?jī)?yōu)美的表現(xiàn)技巧、久遠(yuǎn)的歷史傳統(tǒng)和普遍豐厚的審美層次,成為中國(guó)繪畫(huà)史上的精美一頁(yè)"民間木版插圖畫(huà)自唐宋起,便作為印刷雕版技術(shù)印刷書(shū)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明清時(shí)期中國(guó)木版畫(huà)發(fā)展到了鼎盛時(shí)期,特別是以陳老蓮為代表的畫(huà)家親自參與到木刻版畫(huà)設(shè)計(jì)并創(chuàng)作的/水滸葉子0等作品,在中國(guó)木版畫(huà)發(fā)展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進(jìn)而形成了中國(guó)木版年畫(huà)各地不同、獨(dú)樹(shù)一幟的藝術(shù)特色,并輾轉(zhuǎn)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