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敘事評析
時間:2022-02-04 11:53:26
導語: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敘事評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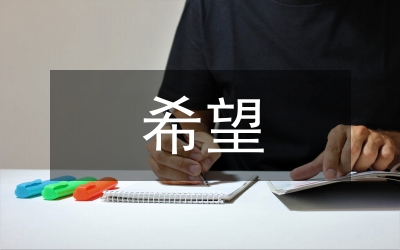
摘要:電視劇《希望的大地》通過群像式的人物塑造,全方位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平民英雄譜寫人生新篇章的過程。該劇通過詩性圓融的敘事結構,表達了時間意識上的現代精神和空間視野上的全局觀念,在對意識形態的建構和對人的精神向度的表達中,使社會變革與人物命運成為一種互文性書寫、個人理想與國家愿景構成互動性敘事張力。
關鍵詞:敘事張力;平民英雄;詩性敘事;精神向度
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描述了以馬塵、柳瑩、田慶豐、董望春、吳欣然、吳蔚然、柳誠、吳文淵等為代表的普通人,在改革開放政策帶來的契機下,勇敢嘗試,克服困難,大膽創新,最終成就一番事業的故事。因此,《希望的大地》成為“中國夢”敘事系統中的一個典型樣本。
一、類型擴展下的平民英雄群像
英雄主義是中國乃至世界各國影視文化的一個永恒主題。英雄敘事承載著國家意識形態傳播的重要功能,以精神方式參與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歷史進程。現實題材電視劇中的平民英雄是中國電視劇英雄譜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電視劇《希望的大地》將宏觀社會背景與微觀個體命運相結合,用“小切口、大時代”的敘事方式,選取了以馬、吳、柳、田為代表的4個家庭十幾位主人公,全方位地展現了改革開放以來各行各業平民英雄奮力拼搏、譜寫人生新篇章的過程。作為獨立的個體,這群在希望的大地上奮力追求的人,性格各不相同:有充滿激情、敢想敢干的馬塵,有遇到挫折容易打退堂鼓的吳蔚然,有堅持“想,都是問題;做,才有活路”的農村大隊長田慶豐,有溫婉賢淑、善良隱忍的工程師柳瑩,也有熱情大方、開朗樂觀的財經記者吳欣然,還有知識淵博、待人友好的老教授吳文淵……電視劇通過突出人物主要特征來塑造人物形象,使人物有血有肉,擺脫了扁平、刻板與沒有人情味的一面。這些性格各異的普通人,都是改革路上的踐行者。他們銳意進取,迎難而上,是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創作者力求“化類為型”,提煉出不同人物身上“滿懷希望迎接新時代”的群體共性。1978年,月亮灣大隊剛拿到大學通知書的知青馬塵突遭晴天霹靂:因為祖父的政治身份問題,他將無緣大學夢。發誓要逆天改命的馬塵與吳蔚然、柳瑩扒火車去南方,卻被當作偷渡人員抓進看守所。馬塵一路披荊斬棘,歷經坎坷,在華陽大學做旁聽生,開飯店,做電子廠廠長,最后成為一名優秀的企業家。與馬塵一樣,月亮灣大隊的大隊長田慶豐也表現出了敏銳的觀察力、超強的好奇心和執著的精神。他不顧父母的反對,召集村里年輕人實行承包制。在嘗到了包產到戶帶來的甜頭之后,田慶豐頂著重重壓力,組織村民種花生,搞蔬菜大棚,養雞。但是,田慶豐帶領農民致富的道路也并不順利,先是銷售黃瓜被供銷社阻攔,繼而被銷售專員拐跑兩萬只小肉雞和五千斤雞蛋。只是,在馬塵、田慶豐等人身上,全然沒有失敗后的一蹶不振與灰心喪氣。在改革開放的試驗場,他們以堅忍頑強的姿態成為改革開放的踐行者,實現了個人的人生價值。這種群體形象的塑造,完整地體現了一代開創者的精神世界。在人物關系的設置上,電視劇《希望的大地》呈現出多點互動的網狀敘事結構和全景式的創作格局,顯示出一種豁達與開放的態度。整個故事網是由各個功能項結構起來的整體,而各個功能項的主人公也都有自己獨立的思想。柳瑩是馬塵的前女友,但是陰差陽錯,二人沒有走到一起。憑著堅忍頑強和執著鉆研的精神,柳瑩最終贏得科研成果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并為馬塵的新星電子集團實現了液晶夢。而為了柳瑩的夢想,吳蔚然也主動賣出自己的小家電公司支持馬塵的集團。電視劇在對家庭內部的人倫之情如夫妻之情、父子之情的描寫中,體現了一種理想的人際關系。馬塵與吳欣然的愛情是平等的,對理想的追求是一致的。他們在互相幫助與扶持中,走向廣闊的人生之路。用父親吳文淵的話說就是:“在年輕朋友眼里,愛情和婚姻不是一回事。但在我女兒欣然眼里,它就是一回事!”作為華陽大學的一名教授,吳文淵心懷赤誠,對他人的愛博大而無私。不同于尋根文學中的父子對抗敘事,吳文淵身上呈現的是一種理想之父的形象。事實上,知識分子作為知識、價值的創造者、維護者和傳播者,最能充分地體現時代文化的精神品格。吳文淵退休的那天,學生們從全國各地趕來送別。平等和諧的人物互動關系體現了樸實與平凡的人性。尊師如父、愛徒如子的美好品德,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可以說,人物關系的構建背后,是深層次的人倫觀念,可以更好地平衡個體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系。
二、尋根視野下的詩性敘事結構
一個優秀的創作者必然關注本民族的文化積淀與歷史沿革,正如泰納所說的,看待藝術的方式主要包括“民族、環境和時代”。電視劇《希望的大地》對藝術世界的建構,遵循兩個重要的參照系,一個是時間意識上的現代精神,一個是空間視野上的全局觀念。《希望的大地》將人物為中心,圍繞人物命運進行情節布局。故事一開始便是2012年馬塵和眾知青們回到當年下鄉的玉泉公社月亮灣大隊聚會的場景。盡管這種“歸來”意象將敘事引向了過去,但不同于傳統的尋根話語對于創傷回憶濃墨重彩的描寫,《希望的大地》將敘事重點放在了知青們離開月亮灣之后擁抱新生活的過程。電視劇用倒敘手法,呈現了1978年到2012年之間的溫情歲月與改革開放歷程。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給這些渴望春天到來的人們極大的鼓舞。馬塵興奮地歡呼:“每個人和國家一起,終于等到了這個重要的歷史轉折。”工、農、商、學、兵各路人馬,擁抱新生活。他們像一顆顆小小的星星,匯成改革開放這一幕絢爛的滿天星。知青們進入校園,重新獲得了新生;基層干部董旺春、田慶豐帶領農民脫貧致富;嘗遍生活艱辛的工人子弟馬昊子承父業,憑借高超的焊接技術屢屢獲獎……社會的變革與人生之路成為一種互文性書寫。最終,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馬塵的新星集團順利完成產業升級。這種“花開幾朵,各表一枝”的敘事方式,互相交織,將個人的成長曲線匯成一條希望中國的前進之路。因此,故事情節不僅僅是一條線索,呈現了時代和社會發展進步重要節點,更是代表了歷史的演進過程。《希望的大地》空間場域涉及范圍比較廣,從月亮灣到省城華陽、從北方農村到南方都市,劇中鄉村和城市的發展是“共時態”的。改革開放的到來,“仿佛一夜之間,不僅我們對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圖景都經歷了原先不可思議的巨變。”①《希望的大地》以開闊的視野對地理文化的重新闡釋,建構一種詩性的空間。在知青題材的影視劇中,鄉村多是一種寓言式的存在。閉塞與野蠻的農村環境是作為現代文明的對立面存在的。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沒有回避城鄉之間的矛盾。事實上,城鄉矛盾一直是中國現代化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電視劇第一集的沖突就集中在月亮灣大隊社員排隊分救濟糧的過程。饑餓的社員和知青們翹首以盼,卻沒有等到救濟糧的到來。而且因為經濟貧困,月亮灣的社員只能靠換親來解決男大當婚的難題。但是,電視劇《希望的大地》沒有拘泥于對農村落后狀況的描寫,而是著力刻畫農民窮則思變的心路歷程。大隊長田慶豐積極考查道林地區畝產翻番的經驗,學習安徽小崗村包產到戶的方式,讓月亮灣的村民吃上了新麥饅頭。當然,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田慶豐、董旺春也遇到各種各樣的阻撓。比如固執保守的父親田家旺和鎮上的牛書記。田家旺經常跟兒子說的話就是:“你就悄悄地吧。”他之所以收斂鋒芒,小心翼翼,害怕冒進與危險,是因為曾經由于堅持改革路線而被打擊,蹲過兩年監獄。隨著故事的推進,他逐漸認可了兒子的做法,雖然依舊旁敲側擊:“只許看,不許發表意見。”這樣一個審時度勢的父親,在時代的發展變遷中,逐漸認清現實,與年輕人一起開創新的生活。這正體現了時展過程中的個體選擇與倫理姿態。“文化是一種時間觀念,也是一種空間意識,但文化的時空性并非就是固態和封閉的,而是流動與敞開的。”②劇情最后一集又回到知青們的月亮灣之旅。可以說,月亮灣之旅是一次“重溫崢嶸歲月,再續知青情誼”的過程。“歸來作為一個永恒的母題,是人類非常原始的生命體驗。”③月亮灣之旅一方面代表著這些知青們對于昔日生活過的故土的情感,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對歷史的接力棒傳遞到新一代手中的豁達與希望。這是人生的感悟與超越,也是一種文化觀念。通過這種詩性的時空敘事,觀眾不僅能夠追思歷史,更能夠洞察未來。創作者“不只屬于一個時代,他的情感和智慧應能超越時代,不僅有感于今人,也能與古人和后人溝通。他眼前過往著現世景象,耳邊常有時代的召喚,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個更深沉、更渾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喚—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喚。”④
三、現代性背景下的精神向度
“人類社會行為及社會機制從根本上說是象征性的。社會之存在以及它影響個體的可見行為方式,都是通過那些不可見的命名、規則以及定位系統來實現的,這些系統是個人進行認同及定向的對象。”⑤《希望的大地》用符合觀眾的心理模式,通過對這群奮爭的平民英雄的塑造,體現了一種積極向上的社會精神氣質。“想象一種語言就意味著想象一種生活形態。”⑥選擇一個表現過去的形式就是選擇一種對現在的理解方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傷痕文學以一種與過去割裂的姿態,多表現對的批判以及知青生活的屈辱與無奈。《希望的大地》的敘事話語突破了純粹的二元對立,走向多元統一的表達。為了籌集資金克服養殖場的危機,田慶豐連夜編織籮筐去集市販賣,結果又被工商局抓。關鍵時刻,月亮灣的老百姓紛紛拿出自家的糧食支援養殖場。田慶豐為了感謝百姓,將養殖場變為集體經濟。這種個人與集體關系的建構,是對集體力量的肯定,意味著一種互相的理解與包容。當馬塵面臨窘境,全體職工自愿加班,在合同交付當日保質保量地拿出來兩千臺電話機。從深圳考查回來的市長看到這一切,對馬塵的拼搏精神感動,也對新星電子廠的市場意識給予了肯定與支持。這種精神向度,是對于主流意識形態的回應。這是作品內部與外部的對話關系,使文本意義在文化語境中實現了增殖。滲透在文化結構中的價值態度、情感傾向,通過一定社會的生活方式與文化方式體現出來。戰士柳誠作為孤兒,無比珍視自己身上的軍裝,對部隊生活充滿感情。當部隊面臨裁撤,他不顧艱難,選擇去雪域高原做雪鷹突擊隊隊長。柳誠的所作所為代表了對國家的忠誠,對人民的熱愛。為了抗洪搶險,柳誠奮不顧身,最終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這里,“自我成為身體中的一種‘社會’,并有著自己的‘國家’結構。”⑦也就是說,作為一種集體性的主體,“中國”是中國人個體存在的共同體。《希望的大地》塑造了生動、接地氣的人物形象。他們的理想與熱情,憧憬與想象,體現了人類對心靈世界的探索。比如馬塵、馬昊兄弟身上,帶著一種自然的率真和來自靈魂的激情。靈魂的激情“是靈魂自身的一種直覺行為。在一定情況下,它的產生也需要依賴人的經驗、理性和意志,因此同時也就體現了一種主動性的內涵。”⑧通過靈魂的力量,生命的行動才得以進行。靈魂的激情散發出的,除了想象力,還有一種智性和理性。所以,現代性背景下的文化敘事,并不意味著主體的消逝,而是一種能動的主體的存在。《希望的大地》用一種整體化的話語表達方式,表達了對希望之光“自強不息”的探索。
四、結語
電視劇《希望的大地》全方位展示了改革開放以來城鄉、軍民、產業、科研各個領域的成就。在事件與時間的交織中,人物與故事互相推進。電視劇體現著創作者對時代變革的思考。這種對現實語境的回應,介入了對歷史的重塑和再造過程。這是藝術作品與現實的互動,也是創作者與觀眾的互動,啟發觀眾在社會變遷中去發現自我與宏觀世界的關聯,并激發起對完整人格的追求。正如該劇導演吳子牛所說:“我們希望從普通百姓的柴米油鹽、喜怒哀樂中折射偉大的時代變遷與社會進步,使觀眾在濃厚懷舊感和親切感的縈繞下,真切體察到改革背景下幸福指數的節節攀高與生命尊嚴的步步提升。”
作者:徐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