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課堂教學的制度性思考
時間:2022-07-08 11:18:27
導語:大學課堂教學的制度性思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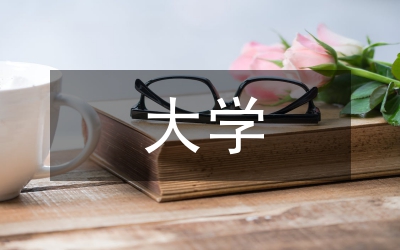
片面強調專業性也是現代教學的一個誤區。專業越分越細姑且不說,即使是反對者提倡的通識教育也墮入到這種思維中。比如,中山大學博雅教育的初衷是為了學生的全面發展,然而它又局限地認為專業越全面,學生的發展就越全面。因此,雖然博雅教育反對當下的專業教育,反而它又成了更加專業性的教育,不同之處,就是它強調的不是一種專業,而是多個專業的“大集合”。實際上,用四年時間想要融會中西各種經典,即使是業界的知名學者都難,何況剛進入大學的學生,這種教學的結果只能使學生養成眼高手低、妄自尊大的毛病。筆者在課堂教學時也發現,學生對專業性教育要么是毫無興趣,要么是才一知半解,就對教師的講述不屑一顧,這都導致了學生在課堂不能專心致志地聽講。現代大學課堂的教學方式并不利于師生之間的交流。早在上世紀20年代,就發現課堂教學的這種弊端,認為:“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過是一種商行為罷了”。當時學校的弊端,到現在發展得更為顯著。同時,教師評價體系也高度功利性,即使是對教學的考查,也以發表教改論文為標準,量化式科研迫使教師不得不減少本應該花費在教學上的精力,從而大大削弱了教師對教學的熱情,加之學生對非技術性課程的漠視,師生間的距離就更加被拉大。另外,現在很多教師過度依賴PPT等多媒體技術,以致很難走入到學生當中,學生也就樂于躲在教室的角落里自行其事,在上百人的大型課堂中這種情況表現得就更加明顯。教學內容的平面化也是現在課堂教學的一個重要問題。從現實中看,學生的性格、氣質、愛好大多都不相同,在大學以前奠定的知識水平也不盡相同。而課堂教學由于師生之間互不了解,加之教學方式陳舊,教師的講義只能針對某一水平的學生,并不能適應所有學生,因此教師根本無法因材施教,教師所樂教,未必是學生所好學、所能學。水平高的學生對自己熟知的內容往往不屑一顧,而聽不懂的學生當然是一片茫然,這樣下來,接受者其實只是很少一部分人。這一少部分很容易被大部分人的情緒所影響,久而久之,最終便造成整個課堂的厭聽、厭學氣氛。
傳統書院在教學方面的優勢
相對于現代大學課堂教學在上述幾個方面的不足,傳統書院表現出了它的優長,筆者將其總結如下:相對于由功利導致的現代學校教育理念與教學方式的斷裂,中國傳統書院目標極為明確,所有的知識都指向人格的培養。宋學家執掌岳麓書院,指出書院教育不是為了“決科利祿”,而是要起到“成就人才,傳道而濟斯民”的作用。古代的書院基本都有學規,很多學規既有教育理念的闡釋,也包含了對教學方式的規定。比如,朱熹在《白鹿洞書院揭示》中,就將人格培養作為終極目標,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以及“懲忿窒欲、遷善改過”等作為具體的修養方法。這樣,傳授、學習知識與人格培養就形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中國傳統書院是“通才教育”,教學內容于四書、五經、史傳、辭章、典章制度靡不涉及。然而如此廣闊的學習范圍,仍不至于散亂,原因就在于它們都指向了人格的培養。在朱熹看來,讀書應該先從《大學》開始,然后《論語》《孟子》,最后再到史傳、辭章、典章制度,認為這是一個清晰而完整的序列,強調不能變亂知識的“難易、遠近、大小”順序。朱熹特別反對毫無章法的廣泛涉獵,在其看來,“若務求多,則反不曾讀得”。在主張“循序漸進”的同時,朱熹還強調要“涵泳”,亦即對所學的知識進行消化、融貫。只有這樣,才能使知識積累雖然多,卻又有條理,從而最終有益于人格的提升。書院基本上實行住院制,師生們長年在一起生活,同時,書院招生規模一般都很小,即便是受到官方資助的大型書院如岳麓書院,在清嘉慶四年只有正課68名、副課70名,總共138名學生,而由岳麓書院發展而來的湖南大學現在卻有學生三萬余人。很多私立性質的書院制度更為寬松,教師與學生基本上是一種亦師亦友的關系。同時,由于書院規模很小,師生交流很頻繁,因而彼此也有很深的感情,這些從書院師生之間的詩歌酬唱中很容易看出。書院沒有正規的課堂教學,也沒有特定的學習年限,自由研究是書院學生學習的主要方式。就具體的教學形式來看,主要有考試、講會、詩會等,多種方式交叉,使書院教學呈現出一片勃勃生機。不同的學生,可以適應不同考查方式,比如有人會在考試中名列前茅,有人會在講會上奪人先聲,有人會在詩會上一展身手。由于書院規模小,師生之間交流頻繁,尤其是講會中師生互相辯難,有更為自由的交流,而不是像現在上課鈴聲響了才來、下課鈴聲一響就走,一個學期下來,師生之間還形同陌路。
書院模式引入的制度性構想
書院模式引入大學課堂,當然不能照搬,同時在相當程度上也必須有教育理念、教學評估指標作相應的配合,總之,它是一個系統工程。然而在有限的范圍內,作為教師,筆者在這里只是提出一些初步設想,至于教育理念、教學評估的配套改革已非所能了。一般而言,超過30余人的班級就不易管理,現在本科教學的規模每級少則30人左右,多則可能上百人。對此,一方面,我們可以從學校的層面盡量控制班級人數,隨著我國人口增長的大幅度降低,學生數量一定程度上必然會呈現減少趨勢,這為控制班級人數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對于大班,就有必要進行分組,比如30人可分為兩組,60人分為四組,上百人的大班可以組下再分組,這樣每組組長直接對教師負責。教師只要抓住幾個組長,就能有效地控制課堂管理。課堂小組長只在教學中發揮組織作用,可由班長、學習委員、文藝委員、組織委員等來擔任。王陽明就是采用這樣的方式,當時由于來學者甚眾,不能一一親自指點,就先由王畿、錢德洪代為傳授。本科生進入大學之后,很容易呈現一種散漫狀態,走向高中生活的反面。現行的輔導員制雖然有專職之利,但也有缺點,就是并不能延伸到教學領域中去。因此,有些學校已經在嘗試實行本科導師制。比如,岳麓書院所招的兩個本科班,就實行導師制,三到兩人配導師一名,其中有碩導、也有博導。這樣,本科生在大學除了班級的“生活圈”之外,就還有一個導師帶領的“學習圈”,在其中可與導師及碩、博學長交流感情,進行學術觀摩和探討。這個導師最好是本院并且給學生上課的教師,這樣教師就能通過自己的學生加強對全班學生情況的掌握,增進與全班多數同學的情感。胡適其實早就指出過,中國的書院制與西方的道爾頓制(導師制)相仿,它對于學生提升學術研究水平很有幫助。在加強與學生交流和掌握學生情況的基礎上,分析學生的問題所在。教師可將學生關心的問題一一列出來,在這個基礎上設計講義。每節課的講義應該比較集中地講述一個問題,但又不能過于艱深。講義之外,教師還應當為學生指定書目,可以根據學生水平將其分為必讀、選讀兩類,讓學生自己選擇。同時,在講課進程中,要注意對這些書目進行解釋,并將這些內容與講義結合起來。這樣就會使學生在學習一門課程時,既獲得較為廣博的知識,同時又循著一條主線往前走,多而不亂,博而有約。課堂提問非常關鍵,宋明時代的語錄不少都是書院師生問答的結晶,這些問答中往往有相當精彩之處。現在課堂教學中,許多教師并無問題設計,或者將問題設計得過于艱深。問題的設計實際上并不是要為難學生,而是要營造寬松的氣氛,使學生敢于表達意見。因此,題目應該精心設計,而且要注意使提問有機地融入到講課過程中。同時,對提問的對象也要精心選擇,防止某些學生被叫起來支吾應付的尷尬局面。另外,提問對象也要盡量照顧全面,防止某些學生由于總是被排除在教師的關注之外而對整個課堂產生疏離感。當然,也可以組織學生提問,不過在師生關系生疏的情況下,這種方式往往只是得到一個冷場的結果。可以在課前做好某些準備,指定某些學生提問,從而帶動其他學生提問的積極性。
本文作者:王勝軍工作單位:貴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