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研究
時間:2022-04-14 10:32:38
導語: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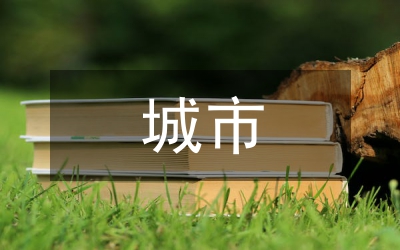
摘要:社會公平問題已成為公共空間研究的焦點問題之一。從公共空間的本質出發,解讀公共空間的特性和相關的都市政策。借助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定性研究方法,從使用者的角度去探討城市公共空間的開放性、公平性和可達性。大部分的公共空間在規劃布局和設計上存在三種現象:主觀化、支配性和形式化。然而,決策者角度下的安全性、可達性和易用性往往與用戶的需求相矛盾。在進行城市設計尤其是公共設施設計的過程中,開放溝通渠道,協助用戶主動參與到空間設計中,最大限度地實現利益的均衡,社區互動空間的全齡融合等設計策略有助于構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公共空間。
開放度城市公共空間是為所有人開放的場所。“公共性”(Publicness)是研究高密度城市公共空間設計的視角之一。目前為止,關于城市公共空間公共性的研究并不少,如城市設計對于處理中國城市公共性空間的作用[1],公共性視角下的城市公共空間發展路徑探究[2],“公共性”的沒落到復興——與歐洲城市空間對照下的中國城市公共空間[3]。這些研究較多從宏觀和決策層面去探討公共空間的公共性,而從微觀和使用者角度出發去討論公共空間設計的并不多[4-5]。因此,本文借助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定性研究方法,從使用者的角度去探討城市公共空間的開放性(openness)、公平性(equity)和可達性(accessibility),從而導向一種更友好共融的生活環境。
一、城市公共空間的本質
(一)解讀“公共空間”。“公共空間”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古希臘的公共空間是一個體現民主的場所,公民可以在里面進行投票、集會和各種日常交流,例如討論公共政策的集會廣場[6]。在古羅馬時期,公共空間的形式和功能變得更加豐富,例如一些神廟、競技場、市政廳、司法廳等。到了中世紀,隨著各種商業交易活動的出現,集市等廣場也成為公共空間一種表現形式。在當代社會,公共空間有著更廣義的概念。公共空間是所有人都有權進入和使用的場所。任何具有大眾聚會、交流、參與、社會交往和互動功能的開放性空間都可以視為公共空間[7-8]。它不僅包括自然的環境空間,還包括各種可以自由出入的人造空間,例如街道、廣場、公園等具有居住、商業功能的空間[9]。“開放性”(openness)是公共空間的本質屬性[10]。在討論公共空間時,有三個方面需要考慮的:(1)有責任的:設計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使用者的需求;(2)民主的:所有使用者都能暢通無阻地到達和使用;(3)有意義的:有助于建立個體與場所之間的緊密聯系[11]。夏鑄九在《公共空間》一書中談及,“公共空間”意味著“為所有人開放”(openforall),“非私有”(non-private)和“所有人共有”(belongstoall)[12]。(二)公平性與可達性。列斐伏爾(1996)在《城市生活的權利》(TheRighttotheCity)中提到,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們都能有工作和接受教育的權利、有享受公共設施和大眾運輸的權利、有休閑休憩的權利[13]。大衛•哈維也提出,所謂的“城市權利”,并不僅限于個體獲取城市資源的權利,同時也包括居民主動改變與創造城市生活的權利[14]。然而,底層大眾在無意識參與構建城市面貌的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些無序、零散和雜亂,這些都與城市管理者所希望的有序、整齊、嶄新的城市面貌背道而馳。因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推動都市的翻新,各種自下而上打造出來的舊有的“空間”被一步一步消滅,從而實現城市空間豪宅化。重構后的空間往往與社會等級密切相關,暗示著特定群體可以進入,同時也把某些群體排除在外。由此可見,都市中的公共空間并非每個人都能共享可達[15]。(三)與高密度匹配的都市政策。在高密度都市中,城市公共空間及公共設施往往由政府主導。公共交通、街道、廣場、公園、綠地等公共空間及設施對于在高密度城市中生活的人們來說顯得至關重要,尤其在城市空間極為匱乏的香港[16-17]。近年來,香港政府就如何提供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策略,但大部分的討論都聚焦在經濟增長上。同時,為了使每個人都能夠暢通無阻隨心所欲地到達每一個公共空間、享有各種資源,政府也提出構建無障礙環境。然而,政策和準則的制定也往往取決于決策者的喜好,而忽視了不同使用者的真實需求和使用喜好,導致部分用戶在使用過程中因行動能力和年齡因素等限制被排除在外。
二、香港公共空間的案例研究
基于上述理論框架,我們對香港公共空間進行了一系列的使用研究。本研究以使用者為中心進行研究,訪談對象包括政府官員、非營利組織、不同類型的使用者群體(包括特殊需要人士如輪椅人士、視障人士、老人等)。其中,我們更邀請部分訪談者到指定的公共空間進行活動,并及時記錄所觀察到的情況。在實地觀察和用戶訪談過程中,我們發現香港的公共空間依然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現象。(一)主觀化。研究結果表明,大部分的公共空間在規劃布局和設計上是由決策者決定的,由于缺乏足夠的用戶調研,導致一些公共空間和設施在使用上并不能真正地滿足用戶的需求。這種意見偏頗在無障礙環境的構建方面顯得尤為明顯。決策者角度下的安全性、可達性和易用性往往與用戶的需求相矛盾。有視障人士表示,在實際使用過程中,政府會出于“安全性”的角度而把他們排除在外。例如,在地鐵站內的盲道會把視障人士引導去使用升降梯和長長的樓梯,而非大多數人習慣使用的扶手電梯。而事實上,香港的大部分視障人士都有接受過使用扶手電梯的專業培訓,他們懂得如何在不依賴他人的情況下根據聲音提示信號安全地使用扶手電梯。而且,升降梯對于他們來說使用體驗并不良好,因為他們需要花費很多時間去尋找控制面板和對應的樓層。因此,在可以選擇的情況下,他們更偏向使用扶手電梯。同時,他們也表示絕大多數的危險通常不是發生在使用扶手電梯時,而是在注意力沒有那么集中的情況下,如前方突然出現的凸起來的階梯,如圖1。(二)支配性。開放性對城市管理者而言意味著不穩定(uncertainty),而這種往往是決策層和管理層不愿意看到的,因為任何不穩定因素都阻礙了政府的管理,使城市空間因為缺乏規矩而產生混亂或危險。因此,在城市公共空間的管理中,決策者和管理者會通過各種自上而下的方式去建立秩序(builtorder),并嘗試通過設計和管理去支配使用者的行為。比如,為防止露宿者或其他人在長凳上睡覺,長凳在設計時就會在中間加上兩到三個扶手作為間隔,限制性的設計讓使用者只能坐而不能躺在長椅上。再比如,草坪是一個很好的休息空間,不少人喜歡躺在草坪上享受日光浴,這也是一種自發性的休閑活動方式。然而,為保持整齊有序的城市形象,游客并不允許躺在公園里,因此,公園會安排工作人員定期進行巡查管理,如發現有任何人違反規定,立即驅趕,如圖2。正如米歇爾•德•塞托在探討城市空間中人的日常生活實踐中提到,城市使用者往往有自己的使用方式,他們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利用一些“策略”和“戰術”繞過機制和規訓去進行日常活動。他們會通過一些自發性的活動去打破秩序,在空間和時間上作出調整,如拆卸欄桿,又或者在管理人員離開后繼續保持原有的休閑活動方式。(三)形式化。為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讓更多民眾有機會使用政府提供的公共設施,政府在公共空間及公共設施的包容性設計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紅綠燈路口、扶手電梯口前增加發聲或震動裝置,從而輔助視障/聽障人士單獨出行。然而在公共空間包容性方面也存在不少形式化的設計,比如在沒有任何提醒的情況下,突如其來的觸摸地圖或者盲道,這種從天而降的設計往往忽視了殘障人士的真實使用習慣。而在標準的制定上,很多設計原則和規定并不能有效地傳達給執行者,導致執行者在方案的實施上存在理解的偏頗,他們的關注點更多放在是否有提供這些設施,而不是是否提供了合理有效的設施。比如,海濱步道為大眾提供了一個休閑散步的空間,這種空間應該最大限度地滿足暢達性。然而,為了突出所在區域的觀賞性,很多公共空間在設計時候并沒有考慮特殊人群的使用。鵝卵石的地磚錯落有致地排開,為輪椅人士和推嬰兒車的人們帶來極大的不便。在實際使用中,他們只能曲折地繞過這些極具裝飾性的凹凸地帶,如圖3。
三、公共性角度下的公共空間設計策略
(一)開放溝通渠道,協助用戶主動參與到城市的設計。公共空間從城市治理角度來說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和限制性。在城市公共環境的構建中,公共空間經常“被規劃”和“被限制”。這種由決策層自上而下的設計往往與城市使用者的需求存在很大的差異。由于缺乏充分的溝通和彈性制度,現今大部分的公共空間都是單一的,充滿限制的。然而,公共空間不應該僅為政府團體和精英階層服務,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們才是真正的使用者。這意味著城市公共空間在促進社會創新的同時也要兼顧可持續設計和全民幸福感。因此,設計者和規劃者需要從使用者的角度去理解用戶的需求和期待,制定彈性制度。讓不同的利益相關者參與設計,有助于從他們的角度去了解問題,最大限度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從而提供更多有效的解決途徑。各種協作式的民間組織和非營利機構可以在決策者和用戶之間建立緊密的聯系。這種自下而上的社會組織通常比較容易取得用戶的認同和信任,協助用戶主動參與到城市的設計中,如圖4。(二)通過人群精細化分類,提高公共空間的可達性和安全性。公共空間及設施應最大限度地考慮到社會弱勢群體的需要,讓人們不會因為社會階層、行動能力、性別年齡等因素而不能平等地使用[18-20]。公共設計需要兼顧空間的公平性和開放性,考慮老人、小孩、婦女、殘障者以及不同群體的需要。因此,最大程度地把人群進行精細化分類有助于設計師和規劃者基于用戶的使用方式去了解他們對公共生活的期待。例如是老舊小區公共空間的微改造,可以根據居民日常生活圈的需求,按5~10分鐘的步行距離對公共空間進行合理分配,優先安排弱勢群體的活動空間和設施。在實踐規劃和管理過程中,由于涉及到各方利益沖突和經費預算等多種限制因素,包容性設計不可能做到嚴格意義上的公平。然而,正如其中一個受訪者提及到,殘疾人需要的是公平享有空間使用的“權利”,但并不是“特權”。換句話說,這需要各方利益相關者進行互動、溝通、適應、妥協與和解,開放設計通道,最大限度地實現利益的均衡,而不是把某方的利益凌駕于他方之上。在此過程中,用戶能被理解被尊重,身份得到認同,從而對公共空間的使用產生一種安全感和依賴感。(三)配合“在地老化”養老模式理念,實現社區互動空間的全齡融合。“在地老化”是我國臺灣地區應對老齡化社會問題的重要方針政策,通過整合既有資源,因地制宜,以為老年人提供不同需求的服務,是老年人能夠持續在自己熟悉的地方愉悅地生活。在高密度城市中,社區公園、廣場的對于老年人的作用尤為重要。雖然不同年輕群體對空間需求不一樣,但是老年人和兒童對于空間安全性的要求卻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在社區營造中,可以結合老年人和兒童兩個群體進行考慮,如兒童游戲區域與康樂設施或休閑空間的鄰近設施。這樣就可以讓老年人與兒童互動的過程中得到精神滿足。此外,可以設置不同類型的安全步道和休憩空間,把動態活動區和靜態活動區串聯起來,可以讓不同群體(如老年人、年輕人、兒童、帶小孩的父母)在社區交往中獲得親情和情感的滿足,形成全齡社區的融合氣氛。
公共空間與人民的生活緊密相連。尤其在高密度城市中,公共空間可以使人們的生活變得更加豐富。開放性是公共空間的本質屬性,然而都市中的公共空間、設施并非每個人都能共享可達。由于決策、設計和管理問題導致部分用戶在使用過程中因各種因素被排除在外。另外,因為不同群體的需求具有差異性,公共空間的設計也面臨也如何實現利益均衡的問題。通過對公共空間的解讀和案例分析,我們認為在進行城市設計尤其是公共環境設計的過程中,彈性和多元的設計思路有助于構建更加平等、包容的公共空間。
作者:羅名君 蕭嘉欣 單位:1.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 2.廣東工業大學藝術與設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