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聲讀物傳播現狀與評價體系研究
時間:2022-05-11 08:55:43
導語:有聲讀物傳播現狀與評價體系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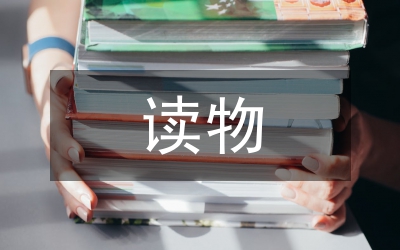
摘要:隨著我國網民數量的激增和互聯網覆蓋范圍的攀升,國內專家學者對有聲讀物的研究呈現井噴之勢。本文運用期刊文獻分析法,對中國知網中以有聲讀物為主題的相關期刊論文進行分析整理,了解當前我國學界對于有聲讀物的研究現狀。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對現階段此類研究內容歸納為有聲讀物含義、受眾類型、有聲讀物App以及播讀評價體系等不同維度。通過梳理國內學者對有聲讀物的研究現狀,結合目前有聲讀物市場的實際發展情況,闡述有聲讀物存在的問題、解決措施,以及有聲讀物播讀評價體系的相關問題,以期對未來有聲讀物在營銷策略制作、產品質量標準、品牌建設、宣傳策略、有聲讀物的播讀評價體系等方面的研究提供借鑒,進一步開展我國有聲讀物研究。
關鍵詞:有聲讀物;有聲讀物受眾;有聲讀物App;播讀評價體系
傳統有聲讀物是指大眾通過廣播、電視、配套磁帶、CD,其有聲讀物的內容和受眾比較單一。傳統有聲讀物多以英語教學資料和兒童讀物為主要內容,受眾也相應地主要集中在兒童、部分視覺有障礙等特定人群中,覆蓋的范圍很小,發展很緩慢。隨著計算機的問世、互聯網的覆蓋、智能終端的誕生以及大眾對閱讀需求的攀升,新的有聲讀物應運而生,它是以聲音為主要展示形式,需存儲在特定載體并通過播放設備解碼載體內容,以聽覺方式閱讀的音像作品。[1]隨著使用互聯網的大眾規模不斷擴大和互聯網普及率的急速攀升,新的有聲讀物呈現出載體形式、種類和內容多樣、多元的發展態勢。有聲讀物所具有的日常伴隨的屬性,逐漸成為大眾在“零碎”時間里學習知識和娛樂放松的新興趣點。有聲讀物是一項新產業,不僅滿足了數字新媒體時代受眾的普遍心理方面的需求,又成為由傳統的媒介向智能數字化新媒介轉換進程中拓展新市場的有效途徑。截至目前,我國的有聲讀物風生水起,一片欣欣向榮。但是我國的有聲讀物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發展之速不可估量。對此,我國專家學者關于有聲讀物的相關觀點,集中概括為四方面。
1.有聲讀物含義
關于有聲讀物的含義,美國音頻出版商協會給出的定義為我國國內大部分學者所認同,即其中包含不低于51%的文字內容,復制和包裝成盒裝磁帶、高密度光盤或單純數字文件等形式進行銷售的錄音產品。認同的原因有兩點。其一,有聲讀物源于二戰時部分歐洲國家與美國,歐美等國為了給在戰爭中導致雙目失明的戰士提供文化精神食糧,開始以“聽書的形式”替換“視覺閱讀”。值得慶幸的是,英國于20世紀30年代成立首個國家級的“有聲讀物圖書館”,面向“視覺閱讀”不便的普通大眾開放。自此以后,獲得了普通受眾的大力支持,并且有聲讀物開始成為普通受眾日常習慣性的閱讀方式之一。其二,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了相應文化的匹配,很多家庭把小轎車作為日常出行的必要交通工具,這相應導致大眾養成一邊開車一邊收聽有聲讀物的習慣,大眾開始對有聲讀物產生聽覺“依賴”。然而,有聲讀物的類型層出不窮,我國國內專家學者開始對有聲讀物的定義進行相應延展,打破之前有聲讀物是“錄音產品”的看法。專家學者把有聲讀物概括為:“以聲音為主要展示形式,需存儲在特定載體并通過播放設備解碼載體內容,以聽覺方式閱讀的音像作品。”將有聲讀物提升為“音像作品”。鑒于上述,針對有聲讀物定義,我國專家學者暫無統一定論。前面談到的國內學者對有聲讀物所概括定義與“美國音頻出版商協會”對有聲讀物的定義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筆者認為,一是,將有聲讀物界定為“錄音/音像作品”存在滯后性。當前,新媒體、自媒體大發展的背景下,各種音頻層出不窮,有“先錄后播”和“在線直播”形式,而且更讓人驚喜的是主播與聽眾可以進行實時互動,拉近了傳播者與受眾之間的距離。二是,有聲讀物題材豐富,包括戶外直播、“語音圖書作品”、評書、小品、脫口秀等豐富的音頻產品。有聲讀物定義沒有達成一致的原因是有聲讀物的多樣與廣泛。因此,今后對有聲讀物研究中,應針對音頻作品的類別、不同受眾需求、不同受眾體驗,進而進行科學性、細致性的分門別類地劃分。
2.有聲讀物受眾分類
有聲讀物屬于“聽覺精神文化產品”,體現出豐富受眾精神文化生活的社會功能與為出版(集團)公司、文化(集團)公司帶來利潤的經濟功能。目前我國專家學者對有聲讀物受眾的劃分,歸納為兩大類。第一大類,具有特定空閑時間,但無文本閱讀條件的人。[2]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城鎮現代化的建設、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人口基數的增長和交通擁堵的現狀,各類上班族花費在擠公交、擠地鐵、待在車上的空閑時間有所增加;刷手機短視頻,看各種網絡小說,玩手機游戲,刷博客、微博、微信、朋友圈等活動,空余時間對于眼睛已經為零,但是耳朵不一樣,它有“開發”的可能性。第二大類,是指文本閱讀能力有欠缺的人。我國多數研究者、學者都認可這種分類,指出此類群體包括:少兒、老年人以及視力障礙人群。由于老年人、少兒和視覺障礙者的文本閱讀能力弱,他們主要通過耳朵來收聽有聲讀物來獲得需要的相關信息。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網絡無處不在,今后有聲讀物會有更廣闊的市場。通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當前我國學術界對有聲讀物受眾分類停滯在對受眾的如何分類、分為哪幾類的階段,對用戶的收聽內容、喜好、時長和對受眾的收聽之后的體驗、意見反饋等缺乏詳細相關數據。原因主要有:國內有聲讀物平臺,考慮到保護平臺用戶數據的隱私和維護自身的核心競爭,相關數據一般不公布于眾。造成學者、專家在研究過程中,缺少準確可靠的相關數據資料。我國地域廣闊、音頻節目瞬時、用戶使用頻繁對其受眾進行研究,只能對某一個區域用戶進行數據分析、統計。不能提供全面廣泛的數據,導致研究有聲讀物內容和音頻制作、受眾需求與反饋等方面的困難。
3.有聲讀物App
有聲讀物項目的開發和發展之所以能暢通無阻的進行,是因為政策紅利為其提供保障。據相關媒體報道,2016年,財政部扶持文化產業的發展專項資金高達44.2億元,惠及文化產業944個,比2015年多出近100個。有聲書領域既符合申領標準又極具市場發展潛力,受到了國家各個層面、領域的重視。隨著使用多功能智能手機人數的攀升和互聯網科技的大發展,以及智能終端技術的不斷創新,有聲讀物的市場逐漸崛起。[6]人們將獲得信息、娛樂的媒介由傳統紙質、電視廣播媒體轉換為智能手機,手機音頻隨之成為必不可少的元素。一是,關于有聲讀物App的內容生產。我國學者專家將有聲讀物的內容生產主體分為“內容生產者”與“平臺運營者”兩類,對此可以進一步地細分為UGC(User-generatedContent,用戶生產內容)和PGC(Professionally-generatedContent,專業生產內容)兩種方向。二是,App盈利模式。國內有聲讀物App的盈利模式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內容付費。社交媒體時代的傳播,“名人效應”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代表是羅振宇的“羅輯思維”,其特點是:他制作大量優秀的節目來吸納大量忠實大眾,讓忠實大眾成為其會員;成為會員就會有優先的福利,即他分享的好書好文,以及組織線下見面會和粉絲們、會員們圈子聚會等。第二類,廣告推送。[3]要想實現有聲讀物App平臺與贊助商家互利共贏,必須根據有效數據進行精準投放廣告,這樣其準確性、到達率以及商品銷售量同步提高。第三類,研發智能硬件。[4]喜馬拉雅FM把硬件廠商的合作做到了極致,研發出各式各樣的設備,點讀筆、故事機以及車載“隨身聽”智能硬件都出自喜馬拉雅。研發出自己的智能芯片,將其裝入家里常用的家具和家電,家電就相應具有音頻播放的功能。如現今已經研發成功了的智能產品有冰箱、燈具等等。從以上學術研究得出,研究有聲讀物App的運營模式方法較為單一。原因可能是,一是作品質量有待提高,二是宣傳策略不到位。鑒于通過對以上研究現狀的梳理,筆者對有聲讀物有聲書市場的未來發展方向進行預判:第一,內容為王;第二,知識付費將成為主流。比如,喜馬拉雅對內容的打磨集中在三個方面:主播、IP資源以及基礎內容。平臺上有詳細的主播成長體系介紹,同時提供了錄音指導和運營推廣策略。有效地帶動了音頻主播的入駐和成長,也為高質量的內容輸出帶來了保障。從資金、流量和創業孵化三個層面,全面扶持音頻內容創業者。這一戰略足以看出主播培養已成為精品內容沉淀的關鍵。除此之外,與線下多領域廠商合作,將內容植入到更多硬件當中,包括音響、智能家居和汽車。喜馬拉雅FM通過內容深耕和多場景接入,不斷擴展自己的市場邊界。現如今,它再也不是單純的移動音頻服務商,而是一個以音頻為主要形式的全場景文娛平臺。未來,如果更多資源介入,喜馬拉雅可能會轉向多內容形式的綜合性平臺,內容會包括文字、視頻、音頻等,綜合性意味著多行業交叉合作,涵蓋出版、傳媒、娛樂、智能硬件等更多領域。我們不難看出,喜馬拉雅FM的市場空間要比單一移動音頻的市場空間要大。據《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目前,喜馬拉雅的平臺激活用戶量已達4.7億,至少還有3億用戶空間有待發掘,隨著多功能智能手機用戶量的增加,喜馬拉雅的用戶規模也會持續增長。
4.播讀評價體系
有聲讀物屬于舶來品。在20世紀90年代有聲讀物開始在中國陸續發行。隨著互聯網的大發展,智能終端的涌現,人們通過有聲讀物來獲得知識、尋求娛樂的可能性加大。有聲讀物使用人群以男性為主,30歲以下用戶占半數以上,可以看出有聲讀物未來的用戶呈現出年輕化的趨勢。曾志華指出,僅從有聲讀物播讀這個層面分析,存在創作稱謂混亂隨意、門檻設置隨性過低、播讀水平良莠不齊、評價標準粗糙空缺等問題。同時提出文本內容的價值和播讀水準的高低是有聲讀物評價的重要因素,有聲讀物是一個綜合體,囊括了文化性、物質性、藝術性、傳播性、知識性。進而,勾勒出表1——有聲讀物播讀體系評價指標。作為“十三五”文化重大工程之一的全民閱讀工程備受矚目,故而首個國家級“全民閱讀”規劃于2016年正式出臺。有聲讀物的核心是播讀者傳播的內容、如何傳播,什么樣的傳播才是有效傳播、怎樣進行有效傳播等,這就需要一個標準來衡量。“耳朵閱讀”緊密貼合國家政策是新時代的一種重要形式。時至今日,關于有聲讀物的播讀體系尚未定論。不過,曾志華、盧彬在《中國有聲讀物播讀評價體系構建研究》(《現代傳播》2018年第7期)一文給出了建議:“第一,在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廣播電視總局等部委的指導下依照有關規定建立有聲讀物播讀專業委員會。第二,每年定期舉辦有聲讀物評獎活動。第三,有聲讀物生產傳播機構落實有聲讀物播讀評價體系的實施。第四,激發生產者的創作熱情,引導和鼓勵更多的有聲讀物作品提高創新創優的能力和水平。”[5]這項工作是一項系統性、藝術性、專業性、操作性很強的工作,要在有聲讀物播讀實踐中完善綜合評價體系的相關程序、方式和內容。故而,要想讓播讀評價體系具有應用價值、科學性,就需要全面、科學的評價指標作指導。結語我國科研學者對有聲讀物的研究可謂是嘔心瀝血、成果豐碩。中國知網上以有聲讀物為主題的期刊論文共604篇,最早一篇為1981年5月25日劉昭青在《國際問題資料》期刊上發表的題為《美國風行有聲讀物》的論文,開啟了中國研究有聲讀物的先河。截止到2020年8月我國關于有聲讀物的研究集中在有聲讀物定義與受眾分類、有聲讀物營銷、發展、應對各種問題的措施以及關于有聲讀物開發建設等方面。對于有聲讀物的營銷策略、產品質量標準、品牌建設、宣傳策略、有聲讀物的播讀評價體系等方面的研究,還有待深入探究。不過可喜的是,2018年以來,有聲讀物期刊論文研究開始關注兒童,但對盲人開發的有聲讀物少,有聲讀物站在生產者位置發表的論文期刊甚多,對受眾的收聽的滿意度、都需要什么樣的內容以及用何種策略讓更多的人使用有聲讀物等方面需要提高重視。總而言之,關于有聲讀物提出問題的論文頗豐,真正解決問題的論文甚少。如何讓有聲讀物這個舶來品,更好的符合中國的國情,在中國的大地上碩果累累,需要更進一步地研究。
參考文獻
[1]淳姣,趙媛,薛小婕.有聲讀物圖書館及其構建模式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0(23):106-110.
[2]史秋雨.中國有聲讀物研究綜述[J].圖書館論壇,2012(4):32-35.
[3]石姝莉,王月.自媒體環境下網絡電臺APP的廣告營銷模式研究:以喜馬拉雅FM為例[J].新聞研究導刊,2016(19):30-31.
[4]劉峰.音頻傳播生態圈的構建:移動互聯時代的機遇與挑戰:以喜馬拉雅FM為例[J].中國廣播,2016(3):59-60.
[5]曾志華,盧彬.中國有聲讀物播讀評價體系構建研究[J].現代傳播,2018(7):88-94.
[6]余人,王令薇.從傳播學視角看新型電子有聲讀物的崛起與發展[J].出版發行研究,2016(9):35-37.
作者:孫建敏 單位:河南大學
- 上一篇:武俠電影在海外傳播的得與失
- 下一篇:林業技術推廣在林業生態建設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