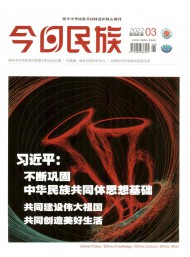民族民間藝術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19 10:12:1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民族民間藝術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羌族建筑起源頗早。羌族人民來到今羌族地區(qū)之前,居住于體現(xiàn)游牧生活方式特色的帳幕之中,來到岷江上游定居之后,才以石砌之室取而代之。由帳幕居住形態(tài)轉(zhuǎn)變?yōu)檗r(nóng)業(yè)定居形式形態(tài),雖然建筑形態(tài)和空間功能都呈現(xiàn)出很大的變化,但是在精神和審美等方面仍保持著悠久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
(一)外部形態(tài)方面
從外部的形態(tài)來看,羌族民居建筑主要借助片石和粘合力極強的泥土來進行修建,總體上呈現(xiàn)為方形。從樓層的布局來看,主要分為三層,底下一層主要用于圈養(yǎng)牲畜,第二層為人的主要活動空間,第三層為曬臺與罩樓。這種建造格局主要是受到羌族宗教思想方面的影響,羌族人在觀念上認為,建筑的總體結(jié)構就像是一個人的構造,中間的才是心臟,頂層相當于一個人的頭,羌族人在樓頂供奉的白石就是天神的化身,通過與天的不斷接近來實現(xiàn)與天神的直接對話。因此,在羌族民居的建造過程中,都會在房頂?shù)奈恢靡约胺孔拥乃膫€角落放置白石,是羌族在中白石崇拜的重要體現(xiàn)。羌族建筑在房頂部分采取半開敞半封閉的建造方式,形成一種開敞的、富于靈動性及哲理性的建筑空間,與羌族人崇拜自然的觀念相契合。羌族民居建筑的總體布局與周圍環(huán)境相協(xié)調(diào),根據(jù)所處環(huán)境,契合地形來進行房屋修建。一方面節(jié)約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另一方面又使建筑與自然環(huán)境相融合,房屋與房屋之間相互銜接、錯落有致,使建筑具有獨特的外觀形態(tài)與豐富的層次感。
(二)內(nèi)部空間方面
在羌人的意識觀念里,住宅是作為一種“人神共居”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室內(nèi)空間的結(jié)構格局跟之間具有十分重要的關系。羌族民居的內(nèi)部結(jié)構復雜而多變,具有多重的象征意義,是羌族傳統(tǒng)居住文化以及宗教意識的綜合體現(xiàn)。在羌人的生活空間中,火塘是家庭中最為神圣的部分,也是整個建筑中最主要的功能空間,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火塘是議事或者家庭會議的重要場所,具有神崇拜的內(nèi)涵,神圣不可侵犯;同時也是人們?nèi)粘I钆c活動的中心,是家庭凝聚力的重要體現(xiàn),具有農(nóng)業(yè)文明室內(nèi)空間特色的氛圍。這主要源于羌人對火神崇拜的傳統(tǒng),說明了火在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除了火塘,羌人的另外一個重要的精神寄托則是角角神位,在傳統(tǒng)的羌族民居中,角角神位與火塘同處于對角軸線之上,位于主屋門的左前方的屋角,由木板組合做成。主要是為了供奉家神,起著鎮(zhèn)邪的保護作用,是羌族民居內(nèi)部空間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最具審美價值的物件。
(三)羌族民居建筑藝術中美的解讀
建筑是一種藝術形式,作為藝術與審美的表達,給人以美的感受。建筑藝術借助于視覺的要素來表達其客觀的形式美,主要通過形態(tài)、質(zhì)感以及色彩等方面來綜合體現(xiàn)。羌族人民在修房造屋時,其外觀形態(tài)主要通過幾何造型來表達,比如碉樓的形狀有四角、六角、八角形等,具有非常穩(wěn)固的形態(tài)和豐富的藝術表現(xiàn)力。而當?shù)夭牧系倪\用則使建筑的質(zhì)感強烈,灰調(diào)的色彩與周邊環(huán)境極其相融。因此,羌族民居建筑憑著獨特的外部造型和富于變化的層次獨具形式美感,體現(xiàn)了羌族民居建筑的民族性與地域性。內(nèi)部空間功能劃分合理,嚴謹?shù)母窬忠约翱臻g的合理使用體現(xiàn)了羌族精神文化方面的豐富內(nèi)涵,成為了羌族建筑文化中極具代表性的部分,也使羌族民居建筑成為了中國民族建筑中濃墨重彩的一筆。羌族民居建筑藝術中的審美實際上是一項非常復雜的精神性活動,通過特殊而復雜的精神活動來實現(xiàn)審美在主體和客體之間的相互轉(zhuǎn)化。羌族的民居建筑分為碉房、邛籠、阪屋三種形式,其中以碉房即碉樓民居為主。由于羌族的聚居地岷江上游河谷皆高山峽谷,因此,建筑形式多為臨坡傍巖。一座座的石砌房屋順著陡峭的山坡建造,氣勢恢宏,具有結(jié)構堅固、高大雄偉、棱角突出的特點。在外觀造型上挺拔高直,呈現(xiàn)出一種多邊梯形向上的發(fā)展態(tài)勢,形成一種獨特的視覺效果,有著非常強烈的視覺沖擊力,給人以雄偉震撼的力量。在建筑的本體上,一方面,通過石片的壘砌來實現(xiàn)收縮與凝聚,呈現(xiàn)出一種多面多角的向上傾斜方式,使建筑本身產(chǎn)生一種向心向上的凝聚力;另一方面,通過片石的契合來實現(xiàn)碉樓的堅固性保障,形成了一種兼具藝術性和技術性的獨特的建筑審美形式。羌族采取結(jié)群而居的生活方式,因此通常由十幾戶甚至上百戶人家共同組成規(guī)模不等的村寨聚落。聚落選址位于高山峽谷地帶,無論山有多險峻,只要有生存的可能,就會有人居住而有聚落的存在。因此,與高山峽谷為伴的羌族人,生存環(huán)境十分惡劣,然而,正是這樣的環(huán)境,造就了羌族人民堅韌不屈和剛毅樸實的民族性格,給予了他們更加雄偉而壯麗的審美感受,在建筑的審美上體現(xiàn)為一種剛健、厚重與樸實的精神。同時,羌族民居建筑的建造受到地域環(huán)境方面的制約,根據(jù)實際情況進行就地取材,主要以片石、泥土、木材等作為建筑材料,憑借大自然的厚遇以及羌族人精湛的建筑技藝修建房屋。因此,受到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tài)觀念的影響以及地方物產(chǎn)材料方面的限制,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呈現(xiàn)出一種審美上的質(zhì)樸性和材料上的厚重性,形成獨特的形式美感。在方面,羌族主要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為主,這使得羌族民居建筑帶有一絲神秘而濃郁的宗教色彩。羌族人轉(zhuǎn)變傳統(tǒng)的客觀認識,通過神、人以及物三者關系的主觀化來體現(xiàn)的精神,實現(xiàn)傳統(tǒng)文化的不斷延續(xù)以及行為模式上的規(guī)范,對于社會傳統(tǒng)的維持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從歷史性及傳統(tǒng)性來看,主要生活西北各地和中原地區(qū)的古羌族人,經(jīng)過兩次大的遷徙才到了岷江上游地區(qū)的險峻高山之中。已經(jīng)傳承了數(shù)千年歷史的羌族民居建筑藝術,不僅是羌族建筑文化在物質(zhì)層面的重要符號,也是羌族建筑文化發(fā)展過程中精神層面的重要象征。同時,艱難的遷徙經(jīng)歷和不斷傳承與發(fā)展的建筑經(jīng)驗,成為了羌族人共同的心理記憶,歷煉了他們不屈的開拓精神,而內(nèi)心的不斷豐富實現(xiàn)了文化內(nèi)涵與審美意識方面的積淀,最終創(chuàng)造出感染力極強的建筑藝術形式。
二、總結(jié)
篇2
關鍵詞:少數(shù)民族文學;話語;生態(tài)倫理
文學作為一門語言藝術,是以言語為基本符號,以社會語境為中介,通過讀者與作者的心靈溝通而得以成全的話語系統(tǒng),是一種社會權利關系纏繞的意識形態(tài)形式。哲學認為,“社會存在決定著社會意識,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具有能動的反作用”。伴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的飛速運轉(zhuǎn),生產(chǎn)力的高度解放、發(fā)展,現(xiàn)代科技的快速升級換代,市場經(jīng)濟的不斷壯大,以及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由大自然的神秘而致的對大自然的那份敬畏,以及與大自然和諧共處的“族親”意識正日趨消減。這種消減首先表現(xiàn)為現(xiàn)代文明進程中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對大自然神秘感的“祛魅”。人類對自然界產(chǎn)生敬畏的諸多因素之一,是自然神秘感的存在,然而隨著現(xiàn)代社會理性色彩的日趨加強,許多原來不可知的現(xiàn)象得到了自然科學的解釋,于是,自然界的神秘性就消失了。“葉廣苓《長蟲二顫》中,在顫坪調(diào)研的中醫(yī)學院教師王安全,用中醫(yī)學的知識重述了殷姑娘用扁豆花下蠱的傳說,消解了山間巫蠱之術的神秘性”;“《老虎大福》中黑子撲朔迷離的野性背景,在二福從楊陵農(nóng)學院獲得生物學知識后被終結(jié),‘豹和犬是兩個科目,受基因限制,它們之間不可能有任何雜交成果,黑子……沒有任何野性背景’”①。科學話語的傳入,使自然的神秘性消解,人類對大自然的敬畏之心也由此淡化。其次,這種削減也表現(xiàn)為,市場經(jīng)濟不斷壯大中商業(yè)話語對人類與非人類生命“族親”意識的淡漠。隨著市場經(jīng)濟的引入,“族親”意識已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神話,金錢成為衡量生命價值的一般等價物。出于金錢的考慮,利益誘惑產(chǎn)生了人對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理直氣壯無所顧及的掠奪:“籠里的猴對村民來說都是錢,活的錢”(《猴子村長》)②,迫切的致富欲望和精明的物質(zhì)利益計算,使村民對猴群進行了滅絕式捕殺。在商業(yè)話語系統(tǒng)中“錢”成為了使用頻率最高的詞匯,人與大自然、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族親”之愛被淡漠了。
由上可知,伴隨著現(xiàn)代文明而出現(xiàn)的科學話語、科學理性、商業(yè)話語使人對大自然的敬畏、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族親”之愛消解了。然而,與現(xiàn)代文明的科學性、商業(yè)性相比,少數(shù)民族文學話語系統(tǒng)中保留了較強的生態(tài)倫理意義,處理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的倫理關系。這一倫理體系的核心是人對自然及非人類生命的敬畏,以及“族親”之愛。
少數(shù)民族大多分布在云南、貴州、廣西、內(nèi)蒙、新疆等邊緣地區(qū),由于地勢原因經(jīng)常處于青山、綠水、奇花、異草、野生動物等的環(huán)圍之中,因而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作品中,關于這些動植物的描述以及圍繞著它們展開的故事較多,基本上每個民族的民間故事集中都有關于動植物的描寫。仔細分析這些少數(shù)民族民間動植物故事,發(fā)現(xiàn)它們都摹寫出了人與自然、人類對其他非人類生命真誠相待的友愛圖景,這主要是通過兩種形式來進行呈現(xiàn):一是正面書寫人出于天性的善良、淳樸對動物的友愛。如錫伯族民間故事《黃狗小巴兒》中,傻子老二好心收留黃狗小巴兒,在被嫂子趕出家門后仍和小巴兒相依相靠和諧生活,在黃狗小巴兒被嫂子棒打死后,如伙伴般將其安葬,經(jīng)常上墳探望,表現(xiàn)出一份“族親”之愛。與此相類的故事還有錫伯族民間故事《鸚哥的故事》、滿族民間故事《扇子參》等。二是側(cè)面烘托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之情。如錫伯族民間故事《狗和人是怎樣交朋友》狗在分別與野兔、狼、熊的相處中每次都因自己的叫聲而被排擠,幾經(jīng)選擇、幾經(jīng)對比,最后轉(zhuǎn)向人類,人類沒有排擠它反而視它為朋友。在選擇與對比中,側(cè)面表現(xiàn)出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另外,錫伯族民間故事《老虎、蛇、蚊子、燕子和人》、《狗和兔子》,瑤族民間故事《馬交朋友》等也都以同樣的形式側(cè)面表現(xiàn)了人對動物的友愛之情。
與人對動物的寬容、友愛相聯(lián)系的是由它而衍生的動物對人的友愛的回報。少數(shù)民族民間故事中有一大部分故事都通過動物對人善行報答的形式,表現(xiàn)了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主題,研究者將這一形式通稱為“動物報恩型”模式。如滿族民間故事《達布蘇與梅花鹿姑娘》通過達布蘇解救、悉心照料小鹿,之后小鹿幻化為一美麗姑娘與之成親的故事,表現(xiàn)出了人對動物友愛,動物對人進行善報的主題。在這里報恩的動物不僅限于溫順的鹿、蛙、兔等,甚至兇猛的動物也懂得報滴水之恩。當然,與之相反也有表現(xiàn)惡有惡報主題的作品,如滿族民間故事《薩滿捉參》中薩滿捉參的結(jié)果就是被海浪卷進江底淹死了;《棒槌孩》中小蘑菇頭他訥、他瑪捉棒槌精吃以求長生不老的結(jié)果便是被打個頭破血流。特定空間的倫理取向的提煉與凈化,顯現(xiàn)了話語系統(tǒng)中的生態(tài)倫理色彩。
總之,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人對動物的友善以及“動物報恩型”的模式都表現(xiàn)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之間深深的“族親”之愛,體現(xiàn)了強烈的生態(tài)倫理意義。與此同時,少數(shù)民族民間故事中保留的許多自然景觀的由來、形成背景也顯現(xiàn)了一種生態(tài)倫理意義。滿族民間故事中的風物傳說《湯池的來歷》,孝敬公婆的媳婦用手捧著火柴燒熱了結(jié)冰的水泡子,從而化作驅(qū)病除邪的湯池;《紅羅女》,美麗正直的紅羅女把昏憒的皇帝捉弄的丑態(tài)百出,最后幻演成鏡泊湖景觀之一。這些故事中演繹自然景觀的由來是跟人類的善行、善德聯(lián)系在一起的,表現(xiàn)出了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
少數(shù)民族話語系統(tǒng)從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友善相待的“族親”之愛,以及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天人合一、和諧共處的愿望中體現(xiàn)了生態(tài)倫理意義,表現(xiàn)出了人對自然的敬畏,與非人類生命和諧、平等、共存的愿望。這不僅為近年伴隨著現(xiàn)代化進程飛速運轉(zhuǎn)帶來的日趨嚴峻的生態(tài)問題而產(chǎn)生的像于堅、賈平凹、張煒、遲子建等的生態(tài)創(chuàng)作,以及由之興起的生態(tài)環(huán)境美學奠定了基礎,同時也暗示出現(xiàn)代話語對原有空間倫理關系的沖擊與破壞,并隨之衍生出了更為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體系,即在“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原始”與“文明”之間文學該如何為自己尋求合適和合理的支點。“現(xiàn)代”“文明”的進程在理論上本應是促進文學不斷進步的動力,然而文學的發(fā)展似乎并不與文明的進化相符相成。伴隨著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而文學一直恒久不變的東西是“人文精神”“人文關懷”,它們是文學得以生存的不竭動力。回顧百年文學,上世紀處以來,中國文學以不斷書寫對人的價值和權利尊重的人文精神追隨著“德先生”的指引。在少數(shù)民族文學中,少數(shù)民族作家們把人文精神中尊重的對象拓展到人之外的自然和其他非人類生命,實現(xiàn)了生態(tài)倫理與人文精神的對接,是人文精神發(fā)展至生態(tài)倫理精神,使自由、平等、博愛的理念由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調(diào)整惠及到自然和非人類,拓展了人文精神的理論內(nèi)涵。我們在談論保持人類尊嚴的時候,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發(fā)展,保持人對動物的尊重,是保持人類尊嚴的一個重要部分。然而,“科學”“文明”和“民主”一樣,在一個世紀以來一直散發(fā)著激動人心的光華。現(xiàn)代科技在帶來舒適、方便和快捷的同時,漸漸也顯示了它在賦予人類征服自然能力之后對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負面影響,因而如何評價現(xiàn)代科技為文學敘事的一個重要維度。理性考究,其實現(xiàn)代科技本身并不具備善惡品質(zhì),區(qū)別在于如何使用,而關鍵點還在操控它的人類。我們在接受現(xiàn)代科技的同時,也要尊重傳統(tǒng)的生態(tài)倫理;破除封建傳說的同時,也要尊重其蘊含的生態(tài)倫理,只有這樣才能通過話語生態(tài)的重建來達到恢復和保護自然生態(tài)的目的。少數(shù)民族作家作品中的這種人與自然、人類與其他非人類生命的生態(tài)倫理意識,為文學處理現(xiàn)代與傳統(tǒng)、科學與人文關懷之間復雜的價值立場和倫理關系體系,尋求到了合適合理的平衡點。中國文學的敘事書寫既可以從中獲取一套生態(tài)話語系統(tǒng),同時也能通過對現(xiàn)代科技的合理評價來搭建保護自然生態(tài)的橋梁,在這一點上少數(shù)民族文學給予中國文學予重大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李玫.空間生態(tài)倫理意義與話語形態(tài)[j].民族文學研究,2007,(4).
[2]烏丙安,李文剛,俞智生,金天一.滿族民間故事選[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