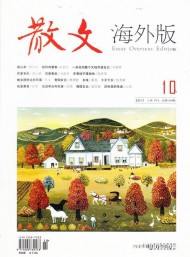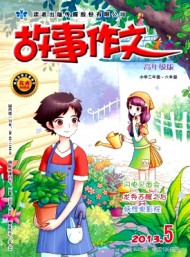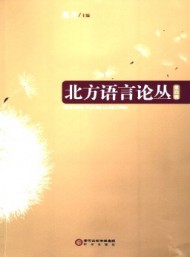描寫音樂論文范文
時間:2023-03-25 08:17:2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描寫音樂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論文摘要:魏晉時期是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此時人們對音樂的追求,開始面向一些新的領域,將注意力轉到認識音樂自身的藝術特征及其表現方式上來,對某些理論問題的再認識,促成了音樂朝著與過去不完全相同的方向發展。這一時期最重要的兩位代表人物——阮籍和嵇康。以他們各自的論著闡述了自己的觀點。本文由魏晉南北朝時期美學產生的背景開始,論述這一時期的兩位主要代表人物及其他們的主要理論以及對后世產生的影響。
一、前言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轉折時期,這一時期的哲學思想、建安文學、田園詩文、書法繪畫等都對后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先秦、兩漢哲學和美學所奠定的深厚基礎上又獲得了全面的發展。像這一時期這樣高度重視審美與藝術問題,專門性的著作如此之多,思想如此之豐富多彩,是后世再也不曾見到的。名士一詞最早見于《禮記•月令》:“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此名士,大約相當于隱士。不過隨著秦漢大一統王朝的建立,士子們對君王和國家政權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紛紛干祿求進,不再隱居不仕,叢而使名士之含義由隱士逐漸向有名氣的人轉化。這些名士們曠達不群,傲然獨得,高度任性。在他們身上體現出率真脫俗,瀟灑自然的人生態度和避世超俗,縱情任性,蔑視禮法,我行我素的話言行風范。整個時代都張揚著一種慷慨奔放的奇麗空氣。正如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散文《遙遠的絕響》①中說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亂世。是一個無序和黑暗的‘后英雄時期’。名士們為了所謂的風流,風度,風神,風情,風姿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后世所看到的這些風貌特異的魏晉名士,他們的形成卻有著極其復雜的歷史背景。
二、魏晉音樂美學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論
(一)阮籍的《樂論》及他的美學思想。
1.《樂論》及阮籍的音樂美學思想。
阮籍的音樂美學思想,集中表現在他的《樂論》中。阮籍從他的中心論點出發,認為最好的音樂就是“平和之聲”,反對哀音聲,認為音樂的功用可以“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他之所以斥責哀音,因為哀音使人情緒波動變化,使人內心的壓抑得到某種認同與宣泄。所謂的聲,就是對人的情感意緒的自然放縱,也即依據人的感性需要,從而滿足這一需要。阮籍也認為音樂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而變化,但萬變不離其宗,變得只是形式,至于“樂聲”要達到的審美的人的心靈趨于寧靜,這樣不悲不喜,靈魂哪兒來大起大落的震蕩?阮籍這篇短短的《樂論》,多次提到的“平和”,并把它樹為音樂之本,“平和之聲”也是要扼制人的欲望,減弱人的創造激情與活力。阮氏的音樂思想,客觀上是捆縛阻礙人的激情與生命活力的,是儒家音樂思想的忠誠繼承者。其中透出的儒家文化的理性精神,愈來愈走向了文明的反面,變為窒息人扼殺人的音樂創造力的精神桎梏,更可憂慮的是這一桎梏隱形地深埋滲透在我們的血脈中,使它化為一種深層意識而暗暗地規定制約著我們的現在。
(二)嵇康的《聲無哀樂論》及他的美學思想。
嵇康就說于音樂的言論其實并不多,一生共留下兩部著作。一部《聲無哀樂論》,(以下簡稱《聲論》),另一部《琴賦》。其中《聲論》一書探討了音樂美學問題,筆者認為它基本反映出了嵇康的音樂美學思想。為了清晰起見,下面從三個方面來分析。
1.音樂本質問題。
音樂的本質問題是音樂美學諸問題中具有關鍵性的論題,對它的認識將直接影響到對其它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在研究中,歷來都為爭論的焦點。因為,它一方面居于音樂美學思想大廈的底層,另一方面它是世界觀和音樂觀相聯系的紐帶。關于音樂本質,《聲論》認為音樂是一種獨立的客觀存在,它與人的主觀意志無關。作者從兩個方面對這一論點進行了論述。
(1)音樂的產生:“夫天地合德,萬物資生,寒著代往,五行以成,章為五色,發為五音”。作者認為音樂是自然的產物,不為人心所生,它相對于人來說,彼此獨立而存在。
(2)音樂的自身表現:作者認為聲音和諧地組織起來,最能感動人心。人們賞樂時,最大的愿望是能夠從音樂中感受到和諧的存在,而這和諧也正是人們傾注的對象。它不僅形式上給人的感官帶來快慰,而且使得人能從心理上獲得平衡。
2.音樂的審美感受。
音樂的審美感受問題是《聲論》全文探討的中心,作者從“聲無哀樂”的論點出發,以自己對音樂本質的認識為基點,闡述了對審美客體和審美主體性質的理解。涉及到具體問題時,得出以下幾種結論。
(1)音樂不能喚起人相應的情感。
(2)人在聽音樂時會有情感出現,但各人的體驗卻不盡相同。只有和諧的音樂才能激發起人的情感。
(3)欣賞者不能與創作者在情感上獲得溝通。
3.音樂的社會功用。
《聲論》對于音樂的社會功用問題的探討,是圍繞著“移風易俗”間題展開的。他認為音樂進行移風易俗依靠的是自身的“和諧”精神。嵇康所認為的音樂“和諧”精神對于人心的影響,是指人在賞樂時能夠獲得性情方面的陶冶。
三、魏晉名士對音樂美學思想做出的貢獻對后世的影響
魏晉時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方面發生的巨大變化,給音樂的發展帶來巨大影響。
漢以來,儒家音樂思想,對其音樂進一步的發展起了極大的阻礙作用。嵇康音樂思想的出現,打破了這種可悲的局面。他在《聲無哀樂論》中,指出音樂本身并無哀樂可言,音樂中屬于藝術的因素,同儒家附加上的非音樂藝術因素相區別,他反對將音樂同哀樂混在一起。與此同時,他直接將注意力集中到音樂藝術的許多具體方面,對某些樂器的藝術表現特點作了分析比較,究其異同,對一些樂曲進行了鑒賞,對有關音樂美學及表演藝術等理論問題有所探討。這種種探討的作法本身就應看做是一大進步。而阮籍的《樂論》影響不大的原因在于并沒有提出一種新的觀點,但這不能說《樂論》缺乏研究價值。一方面,《樂論》作為阮籍直接闡述藝術問題的著作,是探究阮籍美學思想的重要文本;另一方而,雖然《樂論》所表達的觀點基本上同儒家傳統樂論一脈相承,但并不是儒家樂論的轉述,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場對儒家樂論的闡釋發揮,因而其審關觀念在思維方式及總體特征上呈現出新的面貌。
注釋:①《遙遠的絕響》是余秋雨的代表作之一。文中主要描寫了魏晉時期兩位名士--阮籍和嵇康,文筆優美,意蘊深刻。
參考文獻:
【1】李澤厚 劉綱紀:《中國美學史》安徽文藝出版社
【2】修海林 羅小平:《音樂美學通論》 上海音樂出版社
【3】夏野:《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 上海音樂出版社
【4】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 人民音樂出版社
篇2
關鍵詞:物感說;物;情;情景交融
一、 “物感”說釋義
中國古典美學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基礎上,人心與“天”(“道”)“一氣流通”融為一體,無有間隔。在中華民族的審美心理中,天地自然如人一樣,充溢著生命氣息,而且人的生命就是宇宙生命的凝聚,因而人可以“上與造物者游,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莊子?天下》)。建立在這種哲學基礎上的審美理論不可能是主體與客體對立的認識論,而只能是主體與客體交感的體驗論。[1]5“物感說”正是這樣一種體驗論。
大體上看,所謂“物感”,一是“感興”,即主體的情感由外物觸發,這是一種感性的興發活動。二是感會,強調主體與客體的相互作用,這是一種不分主客的交融互滲。從深處看,“物感說”實際上論述的是審美活動中最為重要的一種關系,即主客、物我、情景的關系。而在這之中,“情”又是物我、主客之間的橋梁。審美就是在這種物我一體,主客交融的狀態中產生的。
二、 “物感”說發展軌跡的研究現狀
學界較為流行的觀點認為,“物感說”成熟于劉勰的《文心雕龍》。其理由主要在于《文心?物色》將“物感說”從“感興”發展到了“感會”,即由外物對人情感的觸發發展到了人以情觀物,物我交感。翟傳霞在其《中國古典美學中的物感說》[2]148中就持這種觀點。表面上看,這種觀點似乎無懈可擊,但深入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種觀點是有待商榷的。這種觀點只注意到了“物感說”的表層含義,即“感興”與“感會”兩個方面的含義,而沒有考慮到其深層含義,即“物”與“情”都成為具有獨立審美價值的對象。殊不知在劉勰的《文心雕龍》中“物”雖取得了獨立地位,擺脫了秦漢時期“比德說”中的道德修養的附屬物這一地位,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而“情”還沒有從儒家傳統的園囿中解放出來,還沒有獲得獨立的審美價值(這一點后文將會具體論述)。在“情”尚未獲得獨立的審美價值的情況下就說“物感說”已經成熟,是值得再度思考的。
本文擬從“物感說”的深層含義出發,從“物”與“情”的逐步獨立成為審美對象的過程中去論述“物感說”的奠基、發端、發展與成熟。
三、“物感”說的奠基、發端、發展、成熟
“感”是中國文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凡論文學創作緣起者,多言“感物”。而“感”的含義,卻是在《周易》中最初展示出來的。
(一)“物感”說的哲學奠基
《周易?系辭上》說:“《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3]370大意是說,《易》之道,彌綸天地,人能隨感而應,便可通曉天下之事。這講的是人如何得“道”的。《周易》中講“感”最為集中的,是“咸”卦。“感”是這一卦的主要含義。現將《彖》辭摘引如下: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3]164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這是對宇宙普遍規律的概括。天地萬物,無不是既相互對待又相互需要的,只有雙方相感相和,才能達到穩定而美好的狀態。“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說天地萬物又都是在互相感應中生存發展、在互相感應中表現自己的。在這里,一切都是互相感應,相互感應化生一切。
中國文學理論中的“物感”說,就是在這種觀念的基礎上產生的。“物感”說的“感”是感應或感發,而不是西方文論中的反映。正是這種觀念奠定了“物感”說的基本含義。
(二)“物感”說的理論濫觴
據現有資料記載,最早在文藝理論中談到“物感”的是《樂記》。《樂記》中說: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于人心之感于物也。[4]271
《樂記》中的這段話以動態的模式:物動―心動―聲應―變音―成樂,談論音樂的產生。這段話在《樂記》這部音樂理論文獻中第一次談到“物感”,雖未明確提出文學審美意義上的“物感”,但其在理論上的發軔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這里已經明確提出“音”之起在于“人心之感于物”,其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們也不能忽視其作為儒家樂論的先天弱點。
先秦秦漢時期,儒家出于維護封建統治的需要,把個人正常的自然之情視為洪水猛獸:“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4]274他們認為個人感情是天理的對應物,所以對“情”進行了嚴格的倫理規范:“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43]282這里,儒家提出用禮樂來節制“人情”,“情”有“天”“人”之別。可見,這里的“情”更多的是“天”情,是儒家倫理道德意義上的“情”,而非人的自然之情。
結合儒家在先秦至秦漢時期時所倡導的禮樂文化,我們就會發現,《樂記》的“物感”是有其特定限制意義的。“物”雖不排除自然風物,但更多的卻是以儒家的“人事”,即與社會倫理有密切關系的社會人事;是“智者樂山,仁者樂水”(《論語?雍也》)之下的“物”,即君子“比德”的對象。“情”也主要是指儒家的倫理情感。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是“物”還是“情”,都沒有取得獨立的地位,不具有獨立的審美價值。而這也為“物感”說的進一步發展留下了空間。
(三)“物感說”的發展
宗白華在其《美學散步》中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的一個時代”[5]208。隨著人的覺醒,自然山水之美的發現,“物感”說也得到了發展,其代表為陸機的《文賦》和劉勰的《文心雕龍》。
陸機《文賦》論述構思時說道:
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于典墳。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于勁秋,喜柔條于芳春。心懔懔以懷霜,志眇眇而臨云。[6]170
《文賦》明確指出了“物”的內涵為自然景觀,即四時景物。“物”在這里已經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獨立,不再是僅僅具有人事、倫理意義上的“物”。但從整體上看,這里的“情”仍限于自然物所感發的“悲喜”之情,其論述仍語焉不詳。但《文賦》已初步提出了文學審美意義上的“物感說”。
《文心雕龍》有許多篇談到“物感”,并有意于將“物感”由“感興”發揮到“感會”。如《詮賦》篇的“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睹,故辭必巧麗”[7]92,已經由“感興”發揮到了“感會”。這些言論的基本宗旨,就是完整意義上的“感物”說。當然,這之中還是《物色》篇談得最多: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時之動物深矣。[7]519
這段話的主題是論述“心”與“物”的關系,即“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而對這個問題的論述,是從“微蟲猶或入感”說起的。微蟲應節律而動,說明天地萬物深微而普遍的、息息相通的內在的生命關聯。進而談到作為最有生命靈性的人,人具有最敏銳、最豐富的感應力,無時無處不與萬物相通,一葉一蟲皆足感志。
《物色》篇的“贊曰”,是對上面這段話的精確概括:
贊曰:山沓水匝,樹雜云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7]526
心物之間,親密交往,互相應答,情趣融融,詩意盎然。文學和審美就是這樣萌發的。這樣,《文心?物色》就把“物感”發展到了“感會”,這種論述是較為全面的,完整的,整體上達到了“物感”說的完整意義。
但這個意義上的“物感”說似乎顯得不夠深刻,“物”雖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解放和獨立,但仍沒有超越其自然屬性而獲得完整的意義。“情”相對于《文賦》也沒有取得真正的突破,仍局限于自然物色之變所引起的“悅豫”、“郁陶”之情。“情”沒有獲得獨立的主體地位,這個意義上的“物感”說沒有真正理解“物感”的意義,也沒有給“物感”說以應有的地位。而《詩品》則在深度上作了很好的發揮。
(四)“物感說”的成熟
《詩品》的序是這樣開始的: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8]15
這里把詩、情、物、氣,四者聯系起來,指出詩是情性的表現,性情是物之感人的結果,而物之感人源于氣的運動。在此之后,《詩品序》又對“物之感人”做了詳細深入的分析: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于詩矣。[8]20
可以看到,鐘嶸所說的“物之感人”的“物”,已不限于自然景物,甚至主要不是自然景物,而是社會生活、人生遭際。人的心情自然會受到自然景物的觸發,但其真正的根源顯然是人生遭際。主要以社會生活、人生遭際為“物”,這樣的“感物”說就不再是景物描寫的問題了,而是上升到詩如何產生,詩的本質與宗旨的層次了。“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只有詩與文藝能夠抒發人生的感慨,能夠呈現人的內心世界。“情”在這里也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
人之所以需要詩與文藝在于此,世界之所以會產生文藝亦由乎此。這個意義上的“物感”說才是“感物”說的本意,才是“感物”說的真正意義所在。正如王夫之所說:“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限。”(《姜齋詩話》)劉勰雖屢次談到“人稟七情,應物斯感”、“物色之動,心亦搖焉”,卻沒有真正理解“物感”說的意義,也沒有給“物感”說以應有的地位。
中國文學理論史上的“物感說”,哲學奠基于《周易》,理論發端于《樂記》,但在此時無論是“物”還是“情”都還未取得獨立的地位,其意義也是有很大局限的。發展于魏晉南北朝,“物”的內涵在陸機《文賦》和劉勰《文心雕龍》中得到了擴大,并取得了獨立的地位,獲得了獨立的審美價值。“物感”的含義也在《文心雕龍》中由“感興”發展到了“感會”,獲得了完整意義。但此時的“情”還囿于自然之物所感之情。成熟于鐘嶸之《詩品》,“情”的內涵在《詩品》中得到了深化,人生遭際之“情”獲得了獨立審美價值,文學作品的意義也在此處得到了體現。(作者單位: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文學院)
參考文獻
[1]陳望衡:《中國美學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翟傳霞:《中國古典美學中的物感說》,《文學教育》,2011年11月。
[3]郭譯注:《周易》,中華書局,2006年版。
[4]陳戍國撰:《禮記校注》,岳麓書社,2004年版。
[5]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6]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