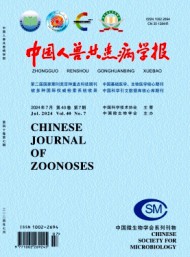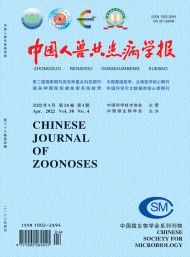中獸醫(yī)學(xué)的概念范文
時(shí)間:2023-12-06 18:01:02
導(dǎo)語(yǔ):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中獸醫(yī)學(xué)的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義務(wù)教育物理課程標(biāo)準(zhǔn)(2011版)》強(qiáng)調(diào):“科學(xué)探究既是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目標(biāo),又是重要的教學(xué)方式”.根據(jù)初中物理課程所涉及的探究性課題的內(nèi)容特點(diǎn),可以把探究性教學(xué)分為:建立某種概念和規(guī)律的探究活動(dòng),觀察、發(fā)現(xiàn)和解決問(wèn)題的探究活動(dòng),尋求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和模型的探究活動(dòng),技術(shù)設(shè)計(jì)與創(chuàng)新的探究活動(dòng),與社會(huì)問(wèn)題相聯(lián)系的探究活動(dòng)(包括當(dāng)代科學(xué)技術(shù)發(fā)展的社會(huì)熱點(diǎn)問(wèn)題及科學(xué)技術(shù)史中的問(wèn)題)等.
筆者結(jié)合蘇科版《物理?八年級(jí)上冊(cè)》“速度”一節(jié)的課堂教學(xué)設(shè)計(jì)案例,談?wù)勅绾芜\(yùn)用探究性的教學(xué)模式,“以問(wèn)題為中心”從相互依存的物理量中構(gòu)建新的物理概念.
2“速度”新授課教學(xué)設(shè)計(jì)案例
2.1教學(xué)分析
“速度”這個(gè)詞在小學(xué)數(shù)學(xué)和科學(xué)課中就已經(jīng)遇到過(guò),但是當(dāng)時(shí)比較關(guān)注速度的數(shù)值,對(duì)其單位未作要求.到了初中,以蘇科版物理教材的編排體系為例,在學(xué)習(xí)物體的運(yùn)動(dòng)之前,學(xué)生就已經(jīng)接觸了聲音的傳播速度和光的傳播速度,但仍然是關(guān)注速度的數(shù)值,對(duì)其單位也沒(méi)有特別要求.總體來(lái)講,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這節(jié)內(nèi)容之前對(duì)速度已經(jīng)有了初步的認(rèn)識(shí),學(xué)生對(duì)速度并不陌生,但是僅僅局限于速度的大小,對(duì)為什么要用這個(gè)概念,這個(gè)概念又是怎樣來(lái)的并不清楚.
2.2教學(xué)目標(biāo)
2.2.1知識(shí)與技能
(1)理解速度的概念,能用速度描述物體的運(yùn)動(dòng).
(2)了解常見(jiàn)物體的速度和測(cè)量速度的一些方法,能用速度公式進(jìn)行簡(jiǎn)單計(jì)算.
2.2.2過(guò)程與方法
(1)通過(guò)探究活動(dòng)培養(yǎng)學(xué)生初步的觀察能力、概括能力和實(shí)驗(yàn)操作能力.
(2)通過(guò)速度概念的建立,讓學(xué)生了解研究問(wèn)題和定義物理量的一種方法.
2.2.3情感、態(tài)度與價(jià)值觀
(1)培養(yǎng)學(xué)生學(xué)習(xí)物理的興趣,養(yǎng)成主動(dòng)探究問(wèn)題、積極主動(dòng)尋求解決方法的良好習(xí)慣.
(2)在探究過(guò)程中形成實(shí)事求是的科學(xué)態(tài)度,增強(qiáng)學(xué)生克服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2.3教學(xué)過(guò)程
2.3.1創(chuàng)設(shè)情景,提出問(wèn)題
運(yùn)用多媒體展示如下情景:(1)獵豹追捕野鹿;(2)緩慢爬行的蝸牛.問(wèn)題1:物體的運(yùn)動(dòng)有快有慢,如何比較它們的快慢呢? 2.3.2合作學(xué)習(xí),探索問(wèn)題
學(xué)生獨(dú)立思考、相互討論,并提出解決問(wèn)題的方案.
方案1:相同的時(shí)間,比較物體運(yùn)動(dòng)的路程.
方案2:相同的路程,比較物體運(yùn)動(dòng)的時(shí)間.
問(wèn)題2:生活中什么時(shí)候運(yùn)用了方案1的方法?
賽跑、游泳比賽過(guò)程中,觀眾評(píng)判運(yùn)動(dòng)員運(yùn)動(dòng)快慢的方法.
問(wèn)題3:生活中什么時(shí)候運(yùn)用了方案2的方法?
賽跑、游泳比賽結(jié)束后,裁判員評(píng)判運(yùn)動(dòng)成績(jī)好壞的方法.
小結(jié)1比較物體運(yùn)動(dòng)快慢的方法:相同時(shí)間比較路程或相同路程比較時(shí)間.
2.3.3活動(dòng)探究,強(qiáng)化認(rèn)知
活動(dòng)1:比較紙錐下落的快慢
如圖1所示,剪裁兩個(gè)等大的圓紙片,其中一個(gè)圓紙片裁去的扇形的圓心角比另一個(gè)大,再分別將它們粘貼成兩個(gè)錐角不等的紙錐.
問(wèn)題4:將兩個(gè)紙錐從同一高度同時(shí)釋放,哪一個(gè)紙錐下落的快?
問(wèn)題5:你是怎樣比較紙錐運(yùn)動(dòng)快慢的?
相同的路程,比較紙錐下落時(shí)間的長(zhǎng)短.
問(wèn)題6:有沒(méi)有其他比較紙錐運(yùn)動(dòng)快慢的方法?
相同的時(shí)間,比較紙錐下落路程的長(zhǎng)短.
2.3.4認(rèn)知沖突,深化探究
問(wèn)題7:如果將兩個(gè)紙錐從不同的高度釋放,又該如何比較它們運(yùn)動(dòng)的快慢?
學(xué)生獨(dú)立思考、相互討論,并提出解決新問(wèn)題的方案.
2.3.5建立概念,化解沖突
當(dāng)紙錐運(yùn)動(dòng)的路程和時(shí)間都不相同時(shí),我們運(yùn)用“小結(jié)1”中的兩種方法都無(wú)法比較紙錐下落的快慢,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方法,也就是比較路程和時(shí)間的比值,即比較單位時(shí)間內(nèi)紙錐運(yùn)動(dòng)的路程.我們把物體在單位時(shí)間內(nèi)通過(guò)的路程叫做速度,速度是描述物體運(yùn)動(dòng)快慢的物理量.
若用符號(hào)v表示速度,s表示路程,t表示時(shí)間,則速度公式可寫成: v=s/t.
2.3.6沖突再起,再次攻堅(jiān)
問(wèn)題8:用速度來(lái)比較物體運(yùn)動(dòng)的快慢,實(shí)際上是比較物體在單位時(shí)間內(nèi)所通過(guò)的路程,本質(zhì)上是用了“小結(jié)一”中的第一種方法.有的學(xué)生提出能否用第二種方法,比如都取相同的距離1 m,看誰(shuí)通過(guò)相同的路程所用的時(shí)間短,也就是用t/s來(lái)比較物體運(yùn)動(dòng)的快慢?
學(xué)生獨(dú)立思考、相互討論,嘗試解決新的問(wèn)題.
2.3.7教師引導(dǎo),重視生成
當(dāng)學(xué)生解決上述問(wèn)題有較大困難時(shí),教師應(yīng)當(dāng)適時(shí)點(diǎn)撥,提醒學(xué)生如果用這種方法來(lái)表示物體運(yùn)動(dòng)的快慢,比值越小運(yùn)動(dòng)越快,不如用單位時(shí)間運(yùn)動(dòng)的路程來(lái)定義速度更容易被人們理解.
2.3.8動(dòng)手實(shí)踐,學(xué)以致用
活動(dòng)2:測(cè)量紙錐下落的速度
問(wèn)題9:要測(cè)量紙錐下落的速度,你認(rèn)為要測(cè)量哪些物理量?
問(wèn)題10:你選用的實(shí)驗(yàn)器材有哪些?
問(wèn)題11: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的記錄表該如何設(shè)計(jì)?
將實(shí)驗(yàn)數(shù)據(jù)記錄在自己設(shè)計(jì)的表格中,并計(jì)算紙錐下落一段距離對(duì)應(yīng)的速度(在學(xué)習(xí)下一節(jié)“變速直線運(yùn)動(dòng)”相關(guān)內(nèi)容時(shí),再指出該活動(dòng)測(cè)量的實(shí)質(zhì)是平均速度).
3關(guān)于概念新授課教學(xué)模式的探討
3.1案例評(píng)析
本節(jié)課教學(xué)設(shè)計(jì)堅(jiān)持“以問(wèn)題為中心”的原則.首先,從貼近學(xué)生生活的情景切入課題,并提出問(wèn)題.然后,讓學(xué)生自己先獨(dú)立思考、再討論,并提出解決問(wèn)題的方案.接下來(lái),在具體的探究活動(dòng)中,對(duì)學(xué)生提出的具體方案加以演練,強(qiáng)化已有的認(rèn)知.緊接著,教師有意識(shí)地給學(xué)生制造認(rèn)知沖突,將問(wèn)題探究引向深入,為速度這一新概念的建立奠定基礎(chǔ).伴隨著學(xué)生的思考、討論,從而水到渠成地建立起速度這一新的物理概念來(lái)解決新的問(wèn)題.然而,課堂教學(xué)并沒(méi)有到此為止,由于學(xué)生的創(chuàng)造性思維和好奇心的緣故,又提出了新的問(wèn)題.課堂教學(xué)又以新問(wèn)題為新起點(diǎn),將教學(xué)引向更高更深層次.
正是在學(xué)生認(rèn)知矛盾的發(fā)生和解決、再發(fā)生和再解決的過(guò)程中,學(xué)生主動(dòng)地建構(gòu)知識(shí),而不是被動(dòng)地灌輸和接受.學(xué)生在探究中發(fā)現(xiàn)問(wèn)題,在探究中建立概念解決問(wèn)題,學(xué)生參與到物理概念建立的全過(guò)程,真正體現(xiàn)了學(xué)生在學(xué)習(xí)中的主體地位,教師在整個(gè)教學(xué)過(guò)程中,是“編劇”、是“策劃”、又是“導(dǎo)演”,是教學(xué)的主導(dǎo).
3.2“以問(wèn)題為中心”的概念新授課教學(xué)模式的實(shí)施策略
在中學(xué)物理教學(xué)中,與速度類似的概念還有功率、密度、熱值、電阻、比熱容等.它們的共同特點(diǎn)是:從兩個(gè)物理量的依存關(guān)系中構(gòu)建另一個(gè)新的物理概念,它所反映的本質(zhì)與這兩個(gè)物理量都沒(méi)有關(guān)系.這種“以問(wèn)題為中心”、從相互依存的物理量中構(gòu)建新概念的探究性教學(xué)模式,整體的教學(xué)思路是從個(gè)別到一般再到個(gè)別、從具體到抽象再到具體.在實(shí)施這種教學(xué)模式時(shí),我們首先要結(jié)合學(xué)生的心理特點(diǎn)和認(rèn)知水平創(chuàng)設(shè)合適的問(wèn)題情景,圍繞問(wèn)題展開(kāi)探究.實(shí)驗(yàn)后,應(yīng)引導(dǎo)學(xué)生進(jìn)行抽象的思維活動(dòng),幫助學(xué)生提取本質(zhì)因素、澄清錯(cuò)誤觀念、形成對(duì)概念的正確認(rèn)識(shí)和真正理解,并選擇新的情景讓學(xué)生應(yīng)用概念,以實(shí)現(xiàn)及時(shí)反饋而達(dá)到鞏固的目的.
篇2
關(guān)鍵詞: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
中圖分類號(hào):G642.0 文獻(xiàn)標(biāo)志碼:A 文章編號(hào):1674-9324(2015)34-0249-02
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質(zhì)量直接關(guān)系到科學(xué)研究結(jié)果的準(zhǔn)確性、可靠性和可重復(fù)性。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在感染,特別在是隱性感染狀態(tài)下,往往會(huì)從免疫調(diào)節(jié)、代謝產(chǎn)物調(diào)節(jié)和與宿主細(xì)胞間的相互作用等多個(gè)方面導(dǎo)致科學(xué)試驗(yàn)失敗,或?qū)е驴茖W(xué)研究結(jié)果不準(zhǔn)確和不可重復(fù),造成人力、物力、財(cái)力和時(shí)間的嚴(yán)重浪費(fèi),嚴(yán)重阻滯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作為我國(guó)最早開(kāi)設(sh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的高等院校,揚(yáng)州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系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設(shè)置、本科教學(xué)及人才培養(yǎng)方面進(jìn)行了大量嘗試,取得了較好的成效。本文結(jié)合揚(yáng)州大學(xué)獸醫(yī)學(xué)院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系近年來(lái)開(kāi)設(sh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的經(jīng)歷,談?wù)剬?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研究范疇,課程開(kāi)設(shè)的目的意義,課程內(nèi)容設(shè)置、講述重點(diǎn)及在課程教學(xué)過(guò)程中的一些體會(huì),以期為更好地培養(yǎng)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學(xué)生提供一些借鑒。
一、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研究范疇
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是美國(guó)獸醫(yī)協(xié)會(huì)認(rèn)可的獸醫(yī)學(xué)范疇中的一個(gè)專業(yè)領(lǐng)域,其職責(zé)范圍涉及作為生物醫(yī)學(xué)業(yè)務(wù)活動(dòng)對(duì)象的各種動(dòng)物的疾病診斷、治療和預(yù)防,其中也包括探索盡量減輕科研用動(dòng)物的疼痛或不適的各種方法,以及鑒定影響利用動(dòng)物開(kāi)展科學(xué)研究的各種因素。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是指經(jīng)人工培育和人工改造,對(duì)其攜帶的微生物和遺傳、營(yíng)養(yǎng)、環(huán)境實(shí)行控制,來(lái)源清楚、遺傳背景明確,用于科學(xué)研究、教學(xué)、生產(chǎn)、檢定及其他科學(xué)試驗(yàn)的動(dòng)物。眾所周知,標(biāo)準(zhǔn)化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是獲得可靠試驗(yàn)結(jié)果的有力保障和支撐,絕大多數(shù)重要的生命科學(xué)相關(guān)成果的取得都取決于以標(biāo)準(zhǔn)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進(jìn)行的動(dòng)物試驗(yàn),也正是動(dòng)物試驗(yàn)推動(dòng)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促使了科研工作者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病原學(xué)、流行病學(xué)、診斷措施和防控策略,以及病原感染對(duì)科學(xué)研究的潛在性干擾,逐步形成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研究范疇。
二、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學(xué)習(xí)和教育
作為一門新興學(xué)科,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較短,其發(fā)展主要伴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的發(fā)展,也是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中微生物質(zhì)量控制的延伸、豐富和拓展。目前,國(guó)內(nèi)外尚未有專門的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教程,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從業(yè)人員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學(xué)習(xí)主要依賴于繼續(xù)教育、會(huì)議交流、通訊咨詢、相關(guān)論文雜志、課題研究,以及通過(guò)從工作中學(xué)習(xí)或通過(guò)各類交叉學(xué)科的培訓(xùn)等方式,從而達(dá)到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相關(guān)內(nèi)容的了解、理解和掌握,并進(jìn)而推動(dòng)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行業(yè)整體健康發(fā)展,近些年來(lái),隨著生命科學(xué)的蓬勃發(fā)展,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質(zhì)量的日趨嚴(yán)格,也加快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發(fā)展,增加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再教育和自我提高的機(jī)會(huì)。
三、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設(shè)置的目的和意義
為系統(tǒng)性建設(shè)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課程,推動(dòng)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科學(xué)事業(yè)更好、更快地發(fā)展,以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主要易感病原為主體,以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感染病原后的對(duì)科學(xué)研究的干擾為抓手,驅(qū)動(dòng)學(xué)生深層次理解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感染病原微生物對(duì)科學(xué)研究和生產(chǎn)檢定產(chǎn)生干擾的危害性;促進(jìn)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學(xué)生深入理解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微生物檢測(cè)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中規(guī)定的必須和必要檢查項(xiàng)目的意義以及標(biāo)準(zhǔn)制定的依據(jù);推動(dòng)學(xué)生更好地理解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環(huán)境要求,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設(shè)施,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設(shè)施的建設(shè)及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飼料、飲水和墊料管理等授課內(nèi)容;進(jìn)一步明確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標(biāo)準(zhǔn)化對(duì)生命科學(xué)相關(guān)行業(yè)健康發(fā)展的重要意義。
四、課程內(nèi)容和設(shè)置
1999年,揚(yáng)州大學(xué)依托獸醫(yī)學(xué)院,在科技部的大力支持下,在全國(guó)率先設(shè)置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專業(yè),經(jīng)15年的探索和經(jīng)驗(yàn)積累,已經(jīng)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專業(yè)方向,培養(yǎng)了一大批專業(yè)性人才,為我國(guó)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xiàn)。《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是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的主干課程,其主要講述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相關(guān)概念、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環(huán)境與設(shè)施、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遺傳、繁殖與繁育體系、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飼養(yǎng)管理及常規(guī)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等內(nèi)容。因課時(shí)量限制,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微生物質(zhì)量控制基本不作講述。然而,近些年來(lái)全國(guó)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微生物的質(zhì)量檢查結(jié)果不容樂(lè)觀,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群體如嚙齒類動(dòng)物感染重要病原的比例仍然較高,且經(jīng)常能聽(tīng)到客戶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質(zhì)量問(wèn)題的反饋,這已經(jīng)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行業(yè)造成了較大的影響。因此,為從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微生物質(zhì)量角度更好地掌握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的內(nèi)容,及時(shí)發(fā)現(xiàn)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的微生物和寄生蟲(chóng)感染,規(guī)避其影響科學(xué)研究的風(fēng)險(xiǎn),減少人、財(cái)、物力的浪費(fèi),揚(yáng)州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系于2010年開(kāi)設(shè)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由于沒(méi)有參考教材,講授內(nèi)容主要依據(jù)《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2nd edition》和《Natural Pathogens of Laboratory Animals Their effects on Research》兩本英文原版書籍,同時(shí)結(jié)合國(guó)外著名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機(jī)構(gòu)網(wǎng)站以及揚(yáng)州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系的相關(guān)研究結(jié)果,自編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講義。以嚙齒類動(dòng)物(大鼠、小鼠、倉(cāng)鼠、豚鼠和兔)、犬及非人靈長(zhǎng)類動(dòng)物為對(duì)象,主要講述病原特性、流行病學(xué)(重點(diǎn)講述傳播途徑和易感動(dòng)物品系)、臨床表現(xiàn)、病理變化、診斷、防控,著重闡述病原感染對(duì)科學(xué)研究的干擾。目前,課程設(shè)置為40個(gè)學(xué)時(shí),其中理論課24學(xué)時(shí),實(shí)驗(yàn)課16學(xué)時(shí),實(shí)驗(yàn)課程緊扣理論課程,實(shí)驗(yàn)課主要以病原模擬感染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從臨床表現(xiàn)、診斷和對(duì)科學(xué)研究產(chǎn)生干擾等方面進(jìn)一步掌握理論課程所授內(nèi)容,較好地做到了理論與實(shí)踐相結(jié)合。
五、教學(xué)體會(huì)
自2010年起,揚(yáng)州大學(xué)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系自設(shè)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堅(jiān)持從英文原版書籍及原始文獻(xiàn)中汲取營(yíng)養(yǎng),堅(jiān)持不斷修改教學(xué)大綱、完善教學(xué)內(nèi)容;堅(jiān)持以更好地掌握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內(nèi)容和技能為宗旨,從無(wú)到有,由點(diǎn)到面,逐步積累,初步形成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課程體系,明確了授課的側(cè)重點(diǎn),有效地補(bǔ)充了本專業(yè)的授課內(nèi)容,豐富了本專業(yè)的教學(xué)內(nèi)容,拓展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專業(yè)的研究方向。我們認(rèn)為,要上好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這門課,首先要充分了解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這門主干課程,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課程是本專業(yè)的基石,充分掌握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課程內(nèi)容,才能更好地有側(cè)重點(diǎn)地闡述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其次,充分利用網(wǎng)絡(luò)資源,跟蹤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病原的研究進(jìn)展,不斷更新和完善教學(xué)大綱及授課幻燈,挖掘與本專業(yè)相關(guān)的經(jīng)典案列,活躍課堂,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積極性;最后,堅(jiān)持理論課和實(shí)驗(yàn)課相結(jié)合,理論課講解概念、方法和基礎(chǔ)理論知識(shí),實(shí)驗(yàn)課以動(dòng)物實(shí)驗(yàn)推動(dòng)學(xué)生進(jìn)一步理解理論課的內(nèi)容,相輔相成。經(jīng)過(guò)5年的探索,我們初步建立了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醫(yī)學(xué)課程的講授體系,促進(jìn)了學(xué)生對(duì)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相關(guān)知識(shí)的掌握和應(yīng)用,師生反映效果較好。
參考文獻(xiàn):
[1]隋麗華,范薇,楊敬,等.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微生物、寄生蟲(chóng)抽樣調(diào)查及分析[J].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與比較醫(yī)學(xué),2008,28(4):259-62.
[2]李厚達(dá).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學(xué)[M].第2版.北京: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出版社,2007.
[3]熊忠良,趙海忠,甘伏生.實(shí)驗(yàn)動(dòng)物在獸用生物制品研究和生產(chǎn)中的應(yīng)用[J].畜牧與獸醫(yī),2011,43(1):84-87.
[4]James G. Fox,Lynn C.Anderson,F(xiàn)ranklin M.Loew,F(xiàn)red W. Quimby. Laboratory Animal Medicine 2nd edition[M].California:Academic Press,2002.
[5]David G.. Baker. Natural Pathogens of Laboratory Animals-Their Effects on Research[M].Washington:ASM Press,2003.
[6]McCaskey SJ,Rondini EA,Clinthorne JF,et al. Increased presence of effector lymphocytes during Helicobacter hepaticus-induced colitis[J]. World J Gastroenterol,2012,18(13):1459-1469.
[7]高正琴,岳秉飛,賀爭(zhēng)鳴.首次從中國(guó)小鼠中分離到肝螺桿菌及其鑒定[J].中國(guó)共患病學(xué)報(bào),2008,25(3):210-213.
[8]Zhang Q,Xu X,Yuan Y,et al. IPS-1 plays a dual function to directly induce apoptosis in murine melanoma cells by inactivated Sendai virus[J]. Int J Cancer,2014,134(1):224-34.
篇3
庫(kù)恩之后,科學(xué)研究的視角發(fā)生轉(zhuǎn)換:“我們都關(guān)心獲得知識(shí)的動(dòng)態(tài)過(guò)程,更甚關(guān)心科學(xué)成品的邏輯結(jié)構(gòu)”,“要分析科學(xué)知識(shí)的發(fā)展就必須考慮科學(xué)的實(shí)際活動(dòng)方式”[1]。同時(shí),維特根斯坦后期哲學(xué)影響日盛,其“語(yǔ)言游戲”說(shuō)強(qiáng)調(diào),任何活動(dòng)都植根于特定的語(yǔ)言游戲或生活形式,從而受制于社會(huì)的、歷史的和文化的情境。以此為背景,一場(chǎng)重估科學(xué)知識(shí)的形態(tài)的運(yùn)動(dòng)展開(kāi)了,“作為實(shí)踐的科學(xué)”觀念開(kāi)始取代“作為表象的科學(xué)”觀念:科學(xué)是一種介入性的實(shí)踐活動(dòng)而不是對(duì)世界的表象。因此科學(xué)研究理應(yīng)把科學(xué)活動(dòng)本身作為對(duì)象,而對(duì)科學(xué)活動(dòng)的考察本質(zhì)上是經(jīng)驗(yàn)性的社會(huì)學(xué)研究。這種新的社會(huì)學(xué)不對(duì)科學(xué)做內(nèi)在論考察,不局限于科學(xué)的獨(dú)特的理性品質(zhì)、認(rèn)識(shí)邏輯、觀念史。它也作為“科學(xué)知識(shí)社會(huì)學(xué)”(SSK)而區(qū)別于墨頓學(xué)派的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墨頓學(xué)派的科學(xué)社會(huì)學(xué)預(yù)設(shè)了不受社會(huì)污染的純粹的知識(shí)過(guò)程和知識(shí)內(nèi)容,把科學(xué)技術(shù)的內(nèi)容排除在社會(huì)學(xué)研究之外,僅把社會(huì)因素作為促進(jìn)或阻礙知識(shí)過(guò)程的外部因素;而科學(xué)知識(shí)社會(huì)學(xué)取消了知識(shí)的內(nèi)容和情境之間的區(qū)分,把社會(huì)因素作為知識(shí)的構(gòu)成性因素,對(duì)知識(shí)的構(gòu)造活動(dòng)進(jìn)行了廣泛的經(jīng)驗(yàn)研究,產(chǎn)生了大量富有啟發(fā)的成果。
但是,科學(xué)研究最近二十年的發(fā)展表明,“或者社會(huì)科學(xué)精致得足以解釋科學(xué)的內(nèi)容但是整個(gè)社會(huì)的創(chuàng)制卻陷入一片漆黑,或者宏觀社會(huì)學(xué)恢復(fù)作用但是科學(xué)的細(xì)節(jié)消失在視界之外。”[2]以布盧爾和巴恩斯為代表的愛(ài)丁堡學(xué)派的利益分析保留了宏觀社會(huì)學(xué)和政治批判的旨趣,但是其對(duì)階級(jí)利益等宏觀社會(huì)變量的訴求并不能說(shuō)明知識(shí)的微觀構(gòu)造。而柯林斯的爭(zhēng)議分析、林奇的民族方法論等微觀研究盡管在揭示知識(shí)的微觀構(gòu)造方面成果斐然,卻缺乏宏觀社會(huì)學(xué)的關(guān)注,不能宏觀地說(shuō)明科學(xué)與社會(huì)的關(guān)系,而這樣的所謂社會(hu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內(nèi)在論研究”[2]。拉圖爾采用的人類學(xué)考察方法似乎為打通宏、微觀研究提供了途徑。這種人類學(xué)考察把經(jīng)驗(yàn)的案例研究作為科學(xué)研究的基礎(chǔ),強(qiáng)調(diào)對(duì)知識(shí)的生產(chǎn)現(xiàn)場(chǎng)、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過(guò)程進(jìn)行實(shí)時(shí)實(shí)地的考察,不僅追蹤科學(xué)事實(shí)在實(shí)驗(yàn)室中的微觀構(gòu)造,而且還追蹤科學(xué)家在所謂實(shí)驗(yàn)室外部的活動(dòng)。拉圖爾采取的人類學(xué)方法首先要求通過(guò)參與式觀察取得科學(xué)活動(dòng)的第一手資料;其次,運(yùn)用“轉(zhuǎn)熟為生”的策略,懸置以往的有關(guān)科學(xué)的成見(jiàn),保持對(duì)觀察對(duì)象的距離,單單從當(dāng)下的科學(xué)活動(dòng)本身出發(fā)構(gòu)造對(duì)科學(xué)的理解;再次,這種人類學(xué)的方法還要求研究者對(duì)這種人類學(xué)構(gòu)造保有反思性;最后,至關(guān)重要地是,要求追蹤正在創(chuàng)制之中的科學(xué)技術(shù)而不是既成的知識(shí)和技術(shù)制品,這一點(diǎn)成為他考察科學(xué)的第一原則:“我們研究行動(dòng)中的科學(xué)而非既成的科學(xué)和技術(shù);我們或者在事實(shí)和機(jī)器被黑箱化之前到達(dá),或者追蹤重新開(kāi)啟黑箱的[科學(xué)]爭(zhēng)議。”[3]我們不妨追隨拉圖爾,去考察科學(xué)活動(dòng)本身,追蹤工作中的科學(xué)家和正在制作中的科學(xué)事實(shí),看這種考察能獲得什么樣的結(jié)果。
二、構(gòu)造自然:實(shí)驗(yàn)室生活
實(shí)驗(yàn)室是科學(xué)知識(shí)的典型的生產(chǎn)場(chǎng)所。拉圖爾首先把實(shí)驗(yàn)室生活作為研究對(duì)象,考察實(shí)驗(yàn)室日常的知識(shí)生產(chǎn)活動(dòng),是“實(shí)驗(yàn)室研究”的開(kāi)創(chuàng)者之一。不過(guò),“實(shí)驗(yàn)室”并不局限于通常的有圍墻的具體的實(shí)驗(yàn)室,其擴(kuò)展意義為“知識(shí)的生產(chǎn)場(chǎng)所”,強(qiáng)調(diào)對(duì)實(shí)際的科學(xué)活動(dòng)進(jìn)行實(shí)時(shí)實(shí)地的考察。相比之下,以往的科學(xué)研究都是事后考察,即在接受已確立的科學(xué)事實(shí)的前提下去重構(gòu)科學(xué)的發(fā)現(xiàn)史、觀念史。實(shí)驗(yàn)室研究也不同于對(duì)實(shí)驗(yàn)的研究,因?yàn)閷?shí)驗(yàn)研究往往以提煉科學(xué)獨(dú)有的方法為目的,而實(shí)驗(yàn)室研究則以科學(xué)事實(shí)的實(shí)際制作過(guò)程為目標(biāo),基本上是一種社會(huì)學(xué)考察。實(shí)驗(yàn)室研究采用了人類學(xué)的田野研究方法,這種方法適合于新視角下對(duì)科學(xué)活動(dòng)本身的考察。拉圖爾從1975年進(jìn)入薩爾克(Salk)研究所,做了近兩年的實(shí)地考察。
現(xiàn)在讓我們跟隨人類學(xué)家進(jìn)入薩爾克研究所的實(shí)驗(yàn)室。實(shí)驗(yàn)室包括各種復(fù)雜的實(shí)驗(yàn)儀器,實(shí)驗(yàn)材料,實(shí)驗(yàn)室人員,科學(xué)文本。實(shí)驗(yàn)儀器構(gòu)成一組組“銘寫裝置”(inscriptiondevices),銘寫裝置把實(shí)驗(yàn)材料轉(zhuǎn)化成可以直接用作科學(xué)爭(zhēng)論之證據(jù)的銘寫符號(hào)(inscriptions)(數(shù)字、圖表、圖像等可以呈現(xiàn)在文本中的符號(hào))。典型的科學(xué)活動(dòng)是,把實(shí)驗(yàn)材料聯(lián)接或放入銘寫裝置,經(jīng)過(guò)一系列規(guī)范的操作生成銘寫符號(hào),再根據(jù)這些銘寫符號(hào)完成科學(xué)論文,提出科學(xué)命題或主張,參與科學(xué)爭(zhēng)論,再依據(jù)爭(zhēng)論的情況繼續(xù)做實(shí)驗(yàn),強(qiáng)化或修改命題或主張,直至特定的科學(xué)命題或主張變成事實(shí)。在上述觀察中,首要的是實(shí)驗(yàn)室的物質(zhì)環(huán)境。“這個(gè)實(shí)驗(yàn)室的特別之處在于儀器——我們稱之為‘銘寫裝置’的特殊配置。這種物質(zhì)安排的至關(guān)重要性在于,作為實(shí)驗(yàn)室成員的談?wù)摗畬?duì)象’的任何現(xiàn)象并不能脫離這種物質(zhì)安排而存在。比如,沒(méi)有生物測(cè)定,就不能說(shuō)一種物質(zhì)存在。生物測(cè)定不是簡(jiǎn)單的獲得某種被獨(dú)立給予的實(shí)體的方式;生物測(cè)定構(gòu)成了物質(zhì)的構(gòu)造。...不僅如此,現(xiàn)象完全由實(shí)驗(yàn)室的物質(zhì)環(huán)境所構(gòu)成。人工實(shí)在——實(shí)驗(yàn)室成員用客觀實(shí)體來(lái)描述——事實(shí)上為銘寫裝置所構(gòu)造。借用Bachelard的‘現(xiàn)象技術(shù)’(phenomenotechnique)這個(gè)術(shù)語(yǔ),這樣一種實(shí)在經(jīng)由物質(zhì)技術(shù)的構(gòu)造而呈現(xiàn)出現(xiàn)象的外觀。”[4]這表明,科學(xué)不單單是思維現(xiàn)象、語(yǔ)言現(xiàn)象或者對(duì)世界的理論解釋,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物質(zhì)過(guò)程,是對(duì)不確定世界的物質(zhì)性介入,而正是這種介入構(gòu)造出科學(xué)對(duì)象。玻爾認(rèn)為對(duì)量子現(xiàn)象的描述不能脫離對(duì)實(shí)驗(yàn)環(huán)境的描述。實(shí)際上,這對(duì)十七世紀(jì)以來(lái)的實(shí)驗(yàn)室科學(xué)是普遍適用的。
拉圖爾記錄了科學(xué)家在日常的科學(xué)活動(dòng)中的言談并加以分析,對(duì)科學(xué)事實(shí)的微觀構(gòu)造過(guò)程做了考察。科學(xué)家的日常言談表明,科學(xué)“證據(jù)”的接受很難說(shuō)是邏輯上必然的推論,而是做出判斷的問(wèn)題,同行間的協(xié)商問(wèn)題。比如說(shuō)某種肽的靜脈注射是否具有心理行為效應(yīng)的問(wèn)題是一個(gè)實(shí)踐問(wèn)題,取決于注入量,取決于科學(xué)家把什么注入量作為標(biāo)準(zhǔn)。拉圖爾還發(fā)現(xiàn),科學(xué)家對(duì)特定科學(xué)主張的評(píng)估往往不限于所謂純粹的科學(xué)內(nèi)容,而是包括研究興趣上的側(cè)重、職業(yè)實(shí)踐的迫切需要、學(xué)科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時(shí)間上的限制,乃至對(duì)科學(xué)從業(yè)人員的權(quán)威甚或人格的評(píng)價(jià),如此等等。這些考慮直接影響到特定科學(xué)主張的接受和否定。“評(píng)估的豐富性使得這種構(gòu)想——思維過(guò)程或推理程序同這些討論發(fā)生于其中的實(shí)際物質(zhì)環(huán)境相隔絕——變得不可能。”[4]。拉圖爾從言談分析中得出結(jié)論:科學(xué)事實(shí)“完全是一種社會(huì)的構(gòu)造”[4]。“社會(huì)的”在這里并具有其在墨頓或布魯爾那里的含義,只是表明區(qū)別于純粹邏輯推理過(guò)程的微觀構(gòu)造過(guò)程。
拉圖爾還從人類學(xué)角度進(jìn)行了歷史案例研究,描述了促甲狀腺素釋放因子(TRF(H))化學(xué)序列的確定過(guò)程,給我們呈現(xiàn)出科學(xué)事實(shí)的典型的構(gòu)造過(guò)程。[①]1962年,“大腦控制促甲狀腺素的分泌”已成為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學(xué)界的公認(rèn)事實(shí)。吉爾曼(Guillemin)認(rèn)定這種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腦的一種新因子,他將之命名為促甲狀腺因子(TRF),并認(rèn)定它是一種肽,決定用化學(xué)分析方法確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時(shí)下丘腦因子的生理學(xué)研究頗有成果,卻沒(méi)有分析出下丘腦因子化學(xué)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種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著作用。因此,該決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徑,沒(méi)有它神經(jīng)內(nèi)分泌學(xué)照樣會(huì)繼續(xù)發(fā)展。盡管如此,吉爾曼1963年提出了確定新釋放因子存在的14條嚴(yán)格標(biāo)準(zhǔn),從而徹底地重塑了釋放因子的研究領(lǐng)域。以前有關(guān)新釋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張都被取消了。可以說(shuō),在這套研究標(biāo)準(zhǔn)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這些標(biāo)準(zhǔn)要求更精密而昂貴的實(shí)驗(yàn)設(shè)備和技術(shù)。日本、英國(guó)的競(jìng)爭(zhēng)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進(jìn)TRF的提純方法。把一種餾分認(rèn)定為TRF的根據(jù)僅僅是它能在生物測(cè)定中穩(wěn)定地產(chǎn)生出與基線峰值有顯著差異的曲線。到1966年,已能獲得相當(dāng)純的所謂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實(shí)驗(yàn)都未能破壞TRF的生物活性,吉爾曼因此主張“TRF或許不是一種肽”。沙利(Schally)的團(tuán)隊(duì)采用了與吉爾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線,盡管他們認(rèn)為這種新物質(zhì)是一種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發(fā)現(xiàn)TRF含有His、Pro、Glu三種氨基酸,不過(guò)只占TRF總質(zhì)量的30%。盡管存在著其他解釋,由于沙利認(rèn)可吉爾曼的權(quán)威,因此無(wú)視三種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結(jié)論:“TRF不是肽”。而這意味著研究方向?qū)l(fā)生發(fā)生重大改變。其時(shí),與TRF的生理學(xué)研究相比,TRF的化學(xué)分析無(wú)甚進(jìn)展。美國(guó)全國(guó)衛(wèi)生研究所準(zhǔn)備召開(kāi)一個(gè)針對(duì)該領(lǐng)域的評(píng)審會(huì)議,這將直接影響該領(lǐng)域的資金分配,進(jìn)而決定著TRF化學(xué)分析的存亡。吉爾曼的團(tuán)隊(duì)將會(huì)議拖延到1969年1月,在該會(huì)議上公布了他們獨(dú)自做出的發(fā)現(xiàn):His、Pro、Glu三種氨基酸占TRF總質(zhì)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進(jìn)入最后階段。確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種氨基酸合成各種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較,看兩者在銘寫裝置上產(chǎn)生的銘寫符號(hào)是否足夠相似。沙利的團(tuán)隊(duì)使用薄層色譜儀來(lái)進(jìn)行這項(xiàng)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學(xué)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的團(tuán)隊(duì)認(rèn)為兩種物質(zhì)在薄層色譜儀上所產(chǎn)生的譜線的微小差異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結(jié)論。他們認(rèn)為只有原子水平的質(zhì)譜儀才能最終確定TRF的結(jié)構(gòu)。1969年9月質(zhì)譜儀終于產(chǎn)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與天然TRF的幾乎完全相似的光譜。爭(zhēng)議停止了。此時(shí),本體論轉(zhuǎn)換發(fā)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吉爾曼和沙利都因TRF序列的“發(fā)現(xiàn)”而獲得諾貝爾生理學(xué)醫(yī)學(xué)獎(jiǎng)。
上述過(guò)程表明TRF序列的確定不是單線的邏輯發(fā)現(xiàn)過(guò)程,而是一個(gè)充滿不確定性和多種可能性的構(gòu)造過(guò)程,而實(shí)驗(yàn)設(shè)備對(duì)不確定世界的介入在整個(gè)構(gòu)造過(guò)程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科學(xué)事實(shí)的“發(fā)現(xiàn)”不過(guò)是曲折的充滿爭(zhēng)議的構(gòu)造過(guò)程的結(jié)果。只有在構(gòu)造過(guò)程結(jié)束之后,科學(xué)事實(shí)的構(gòu)造才變成“發(fā)現(xiàn)”,變成獨(dú)立于構(gòu)造過(guò)程的外在事實(shí),構(gòu)造過(guò)程本身以及實(shí)驗(yàn)室的物質(zhì)環(huán)境被掩蓋了。當(dāng)我們深入知識(shí)的實(shí)際生產(chǎn)過(guò)程,知識(shí)的品質(zhì)立刻發(fā)生變化:與其說(shuō)知識(shí)是靜態(tài)的表象,毋寧說(shuō)知識(shí)是一個(gè)動(dòng)態(tài)的構(gòu)造過(guò)程;知識(shí)的力量不是表現(xiàn)為對(duì)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現(xiàn)為對(duì)世界的型塑。就知識(shí)的靜態(tài)含義而言,它不過(guò)是對(duì)型塑過(guò)程及其結(jié)果的記錄,知識(shí)更多的是一種“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識(shí)。不妨給知識(shí)下個(gè)新的定義:何為知識(shí),知識(shí)就是型塑世界的過(guò)程或能力。知識(shí)的力量的表現(xiàn)之一就是對(duì)“自然”的構(gòu)造。TRF的構(gòu)造史已經(jīng)表明科學(xué)事實(shí)或者說(shuō)“自然”是構(gòu)造的結(jié)果,先在的“自然”并不能說(shuō)明科學(xué)事實(shí)的生產(chǎn)。“由于爭(zhēng)論的解決是自然表象的原因而非其結(jié)果,因此我們決不能用這個(gè)結(jié)果——自然——來(lái)說(shuō)明爭(zhēng)論如何以及為什么被解決了。”[3]
三、型塑社會(huì):實(shí)驗(yàn)室的擴(kuò)張
上述考察的焦點(diǎn)是科學(xué)事實(shí)的微觀構(gòu)造,問(wèn)題是發(fā)端于“實(shí)驗(yàn)室研究”的考察知識(shí)活動(dòng)現(xiàn)場(chǎng)的人類學(xué)方法能擴(kuò)展到“科學(xué)、技術(shù)與社會(huì)”(SST)水平上的宏觀研究嗎?我們把“實(shí)驗(yàn)室”定義為“知識(shí)的生產(chǎn)場(chǎng)所”,而實(shí)際上知識(shí)生產(chǎn)活動(dòng)并不局限于通常的圍墻內(nèi)的實(shí)驗(yàn)室,隨著知識(shí)活動(dòng)的實(shí)際展開(kāi),“實(shí)驗(yàn)室”的構(gòu)造也隨之?dāng)U展。拉圖爾認(rèn)為“實(shí)驗(yàn)室‘內(nèi)部’與‘外部’的區(qū)別、‘微觀’水平和‘宏觀’水平的區(qū)別恰恰是實(shí)驗(yàn)室的建造要破除和取消的”[5]。“追蹤工作中的科學(xué)家和行動(dòng)中的科學(xué)”的原則自然會(huì)導(dǎo)向宏觀層次的科學(xué)研究,導(dǎo)向?qū)?shí)驗(yàn)室的擴(kuò)展構(gòu)造、實(shí)驗(yàn)室在社會(huì)中的定位及其型塑社會(huì)的力量的考察。在這種追蹤中,總會(huì)發(fā)現(xiàn)有一部分科學(xué)家在所謂實(shí)驗(yàn)室“外部”活動(dòng),同科學(xué)界、政府、生產(chǎn)部門、用戶、傳媒、公眾保持著聯(lián)系。一旦這些聯(lián)系中斷,實(shí)驗(yàn)室內(nèi)部的研究工作將陷入停頓。這表明,對(duì)實(shí)驗(yàn)室內(nèi)部和外部做出截然區(qū)分是成問(wèn)題的。這種區(qū)分把實(shí)驗(yàn)室想像為隔絕于社會(huì)的知識(shí)生產(chǎn)地,從中產(chǎn)生出純粹的自然知識(shí),這種知識(shí)隨后毫無(wú)代價(jià)地?cái)U(kuò)散到實(shí)驗(yàn)室之外。這種成見(jiàn)掩蓋了實(shí)驗(yàn)室的構(gòu)造及其在社會(huì)中的定位,進(jìn)而使實(shí)驗(yàn)室的力量神秘化。且來(lái)看個(gè)案例。[②]
19世紀(jì)末法國(guó)的農(nóng)場(chǎng)發(fā)生炭疽疫情。巴斯德把瘟疫界定為細(xì)菌傳染病,而此前細(xì)菌學(xué)與炭疽病毫不相干。他在發(fā)生疫情的農(nóng)場(chǎng)研究疫情,把獸醫(yī)學(xué)的用語(yǔ)轉(zhuǎn)譯成細(xì)菌學(xué)的術(shù)語(yǔ),比如說(shuō)把“疫情潛伏期”轉(zhuǎn)譯成“桿菌的孢子”,從而把細(xì)菌學(xué)同疫情聯(lián)系起來(lái)。其后,他排除了農(nóng)場(chǎng)的其他復(fù)雜因素而把培養(yǎng)成的細(xì)菌病原體帶回巴黎高等師范學(xué)院的實(shí)驗(yàn)室,他在這里可以任意地控制條件對(duì)桿菌做各種試驗(yàn)。他向外界宣稱:“若想解決炭疽病疑難請(qǐng)到我的實(shí)驗(yàn)室來(lái)。”經(jīng)過(guò)無(wú)數(shù)次試錯(cuò),巴斯德偶然地發(fā)現(xiàn)了降低桿菌毒性的實(shí)驗(yàn)室條件,制出了炭疽病疫苗。這種疫苗在實(shí)驗(yàn)室中的小規(guī)模活牛實(shí)驗(yàn)中獲得成功,如其所愿地引起了農(nóng)場(chǎng)主、獸醫(yī)、衛(wèi)生學(xué)家等利益團(tuán)體的注意。但是這并不能讓這些群體完全相信巴斯德的實(shí)驗(yàn)室能控制疫情,因?yàn)橐呙缭阱e(cuò)綜復(fù)雜的農(nóng)場(chǎng)中的成功并不能得到保證。因此,巴斯德需要在某個(gè)農(nóng)場(chǎng)中演示其疫苗的有效性。實(shí)際上,有許多非控制的因素會(huì)導(dǎo)致失敗。因此巴斯德需要把關(guān)鍵的實(shí)驗(yàn)室條件擴(kuò)展到農(nóng)場(chǎng)。巴斯德成功地與這些代表達(dá)成妥協(xié),把農(nóng)場(chǎng)變成了準(zhǔn)實(shí)驗(yàn)室,巴斯德的“預(yù)言”實(shí)現(xiàn)了,在外界看來(lái),實(shí)驗(yàn)獲得了“奇跡般的”成功。巴斯德實(shí)驗(yàn)室的疫苗被廣泛地用于法國(guó)農(nóng)場(chǎng)。由此,巴斯德實(shí)驗(yàn)室成為相關(guān)利益群體的強(qiáng)制通行點(diǎn),巴斯德名垂史冊(cè),法國(guó)農(nóng)業(yè)的面貌為之一新,獸醫(yī)職業(yè)和衛(wèi)生學(xué)都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巴斯德的細(xì)菌理論與實(shí)踐深刻地影響了法國(guó)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當(dāng)巴斯德和衛(wèi)生學(xué)者提出細(xì)菌——傳染病的傳染源——的概念時(shí),他們并沒(méi)有把社會(huì)看作是由窮人和富人、資產(chǎn)階級(jí)和無(wú)產(chǎn)階級(jí)組成的,而是由傳染病患者、健康的但是危險(xiǎn)的細(xì)菌攜帶者、有免疫力的人、接種疫苗的人這樣的群體組成的。他們給這些群體的界定加入了非人的行動(dòng)者:細(xì)菌——共同的敵人。共同的利益被制造出來(lái),一種新的社會(huì)連帶類型產(chǎn)生了。以前因?yàn)殡A級(jí)對(duì)立而被視作階級(jí)壓制工具的衛(wèi)生法令得以實(shí)施。
巴斯德的實(shí)驗(yàn)室重塑了各類社會(huì)行動(dòng)者,轉(zhuǎn)譯了他們的利益和社會(huì)關(guān)系,成了型塑社會(huì)的力量。我們可以從巴斯德的工作中提煉出許多有意義的結(jié)論。首先,“社會(huì)”在很大程度上是科學(xué)活動(dòng)的結(jié)果。“在我們的現(xiàn)代社會(huì)中,大多數(shù)真正新的力量來(lái)自科學(xué),而不是來(lái)自古典的政治過(guò)程。”[5]“既然[科學(xué)]爭(zhēng)議的解決是社會(huì)獲得穩(wěn)定狀態(tài)的原因,我們不能用社會(huì)來(lái)解釋[科學(xué)]爭(zhēng)議如何和為什么被解決了。”[3]布魯爾的社會(huì)實(shí)在論用社會(huì)說(shuō)明知識(shí),其根源在于他仍局限于表象主義的窠臼,認(rèn)為知識(shí)是以社會(huì)為中介的對(duì)客觀實(shí)在的表述。而我們通過(guò)對(duì)知識(shí)活動(dòng)的考察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過(guò)程就是實(shí)在的構(gòu)造過(guò)程。“描述(account)和實(shí)在不存在先天的(apriori)區(qū)別;...描述就是實(shí)在。”[6]其次,我們發(fā)現(xiàn)了科學(xué)力量的源泉——實(shí)驗(yàn)室。當(dāng)巴斯德把病原體帶回巴黎的實(shí)驗(yàn)室時(shí),一個(gè)關(guān)鍵的轉(zhuǎn)換發(fā)生了:研究場(chǎng)所由有著無(wú)數(shù)不可控因素的大規(guī)模的農(nóng)場(chǎng)變成條件可控制的實(shí)驗(yàn)室,巴斯德可以在該實(shí)驗(yàn)室中任意地對(duì)病原體做各種試驗(yàn)。同時(shí),實(shí)驗(yàn)室成果的應(yīng)用并不是簡(jiǎn)單的傳播,而是把農(nóng)場(chǎng)轉(zhuǎn)變成準(zhǔn)實(shí)驗(yàn)室。“既然科學(xué)的事實(shí)在實(shí)驗(yàn)室里被制作出來(lái),為了使它們擴(kuò)散開(kāi)來(lái),你需要建構(gòu)它們能在其中維持其脆弱效力的昂貴的網(wǎng)絡(luò)。如果這意味著把社會(huì)轉(zhuǎn)變成一個(gè)巨大的實(shí)驗(yàn)室,那就這樣做吧。”[5]似乎可以說(shuō),科學(xué)通過(guò)把社會(huì)轉(zhuǎn)變成巨大的準(zhǔn)實(shí)驗(yàn)室而型塑社會(huì)。再次,我們發(fā)現(xiàn),實(shí)驗(yàn)室本身的構(gòu)造也包含了農(nóng)場(chǎng)主、農(nóng)業(yè)協(xié)會(huì)、獸醫(yī)、衛(wèi)生學(xué)家乃至普通公眾這些社會(huì)行動(dòng)者。巴斯德始終在努力把這些行動(dòng)者的利益同他的實(shí)驗(yàn)室聯(lián)系起來(lái),竭力讓他的實(shí)驗(yàn)室成為這些行動(dòng)者的強(qiáng)制通行點(diǎn)。可以想像,假如他的實(shí)驗(yàn)室未能成功地維持這些行動(dòng)者的興趣,或者他未能同他們達(dá)成把農(nóng)場(chǎng)變成準(zhǔn)實(shí)驗(yàn)室的妥協(xié),那么炭疽病疫苗的實(shí)驗(yàn)室制作就不會(huì)成功。可見(jiàn),知識(shí)的成功構(gòu)造以成功轉(zhuǎn)譯相關(guān)社會(huì)行動(dòng)者的利益并贏得其支持為前提,實(shí)驗(yàn)室不是封閉的實(shí)驗(yàn)室,實(shí)驗(yàn)室的構(gòu)造必須納入社會(huì)行動(dòng)者。
四、科學(xué)自然社會(huì)的同時(shí)構(gòu)造:走向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理論
前述對(duì)科學(xué)活動(dòng)的人類學(xué)考察已經(jīng)揭示,“自然”和“社會(huì)”都是在科學(xué)活動(dòng)中得以塑造,都是科學(xué)爭(zhēng)議趨于穩(wěn)定的結(jié)果。傳統(tǒng)的社會(huì)學(xué)分析框架不再有效了,因?yàn)檫@種分析框架有著預(yù)定的社會(huì)范疇和嚴(yán)格的社會(huì)/自然區(qū)分。以往的科學(xué)研究預(yù)設(shè)了“自然實(shí)在”或“社會(huì)實(shí)在”這兩極。要么用自然來(lái)說(shuō)明知識(shí)和社會(huì);要么用社會(huì)來(lái)說(shuō)明知識(shí)和自然;要么用“自然”和“社會(huì)”的雜交來(lái)說(shuō)明知識(shí)。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xué)派所倡導(dǎo)的新的社會(huì)學(xué)研究框架試圖顛倒說(shuō)明方向,不再用預(yù)定的自然或社會(huì)來(lái)說(shuō)明科學(xué)活動(dòng),而是考察科學(xué)活動(dòng)如何重構(gòu)著自然和社會(huì)。他們主張,如果不研究科學(xué)和技術(shù)作為其一部分的社會(huì)情境同時(shí)發(fā)生的重構(gòu),科學(xué)知識(shí)和技術(shù)系統(tǒng)的發(fā)展就無(wú)法被理解。只有同時(shí)追蹤創(chuàng)制中的科學(xué)和型塑中的社會(huì)才能把握知識(shí)活動(dòng)的本質(zhì)。“自然的”和“社會(huì)的”要素性質(zhì)上不加區(qū)分的參與了知識(shí)的構(gòu)造,同時(shí)作為結(jié)果被重塑。巴黎學(xué)派據(jù)此發(fā)展出所謂的“轉(zhuǎn)譯社會(huì)學(xué)”(sociologyoftranslation),又名“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理論”。那么科學(xué)、自然和社會(huì)是如何構(gòu)成無(wú)縫之網(wǎng)的呢?我們來(lái)看卡龍所做的著名的案例研究。[③]
1973年,EDF(ElectricitedeErance)籌劃開(kāi)發(fā)新型電車(VEL:electricvehicle),該計(jì)劃不僅規(guī)定了新型汽車純粹技術(shù)上的特征,而且界定了這種汽車在其中運(yùn)營(yíng)的社會(huì)場(chǎng)域。首先,EDF界定了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中的城市消費(fèi)者。這場(chǎng)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把矛頭指向內(nèi)燃汽車。內(nèi)燃機(jī)是工業(yè)時(shí)代的產(chǎn)物,產(chǎn)生空氣污染和噪音等副產(chǎn)品;私車還是社會(huì)地位的標(biāo)志,此乃受批判的工業(yè)社會(huì)的消費(fèi)模式。新型電車能擁有更優(yōu)的性能/價(jià)格比,進(jìn)而成為普通消費(fèi)品。它還能改善城市公交。EDF在提出計(jì)劃時(shí)已經(jīng)考慮了開(kāi)發(fā)電化學(xué)電池的技術(shù)可能性:首先,公交系統(tǒng)能裝配改進(jìn)過(guò)的鉛蓄電池;其次,蓄電池和燃料電池能使電力汽車的時(shí)速達(dá)到90公里進(jìn)而開(kāi)拓更廣闊的私車市場(chǎng)。EDF不僅界定了后工業(yè)社會(huì)取代工業(yè)社會(huì)的社會(huì)史和技術(shù)史,而且也對(duì)制造商做了界定。在EDF的項(xiàng)目規(guī)劃里,雷諾汽車公司只負(fù)責(zé)裝配底盤并制造車身。而雷諾汽車公司一直雄心勃勃地想成為歐洲最大的汽車制造商。EDF還尋求政府各部門提供支持:制定有利于電車的法規(guī),為對(duì)電車感興趣的市政當(dāng)局提供資助。還要求公交公司同研究中心和科學(xué)家們合作。EDF的電車計(jì)劃還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蓄電池、燃料電池、電極、電子、催化劑和電解液等非人類實(shí)體,與人類實(shí)體同等重要。蓄電池開(kāi)發(fā)的失敗同消費(fèi)者的不合作一樣對(duì)于電車的存亡是決定性的。電車的構(gòu)成實(shí)際上包括了電子、消費(fèi)者、政府部門、雷諾汽車、鉛蓄電池、后工業(yè)社會(huì)等社會(huì)的和非社會(huì)的要素。該項(xiàng)目在最初幾年里并未受到挑戰(zhàn),雷諾汽車公司似乎默認(rèn)了這場(chǎng)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的不可阻擋性。但雷諾汽車在1976年對(duì)自己的利益做了新的定位,對(duì)開(kāi)發(fā)高性能電池的可能性、消費(fèi)者的需求做了新界定,挑戰(zhàn)EDF的安排。在1973年時(shí),VEL存在,而到1976年就瓦解了。
EDF實(shí)際上在建構(gòu)一個(gè)世界,卡龍稱之為“行動(dòng)者-世界”或“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所謂的技術(shù)對(duì)象VEL隸屬于EDF正在建構(gòu)的行動(dòng)者-世界,可以說(shuō),VEL本身的構(gòu)造就是這個(gè)特定的行動(dòng)者-世界的構(gòu)造。“行動(dòng)者-世界”的概念使得理解社會(huì)和技術(shù)對(duì)象如何同時(shí)被型塑成為可能。我們現(xiàn)在對(duì)行動(dòng)者-世界做一說(shuō)明。首先,行動(dòng)者-世界的構(gòu)成是異質(zhì)的,既包括社會(huì)行動(dòng)者,又包括非社會(huì)行動(dòng)者。消費(fèi)者、政府部門、制造商、蓄電池、電子等社會(huì)和非社會(huì)行動(dòng)者共同構(gòu)成了VEL,決定了它的技術(shù)內(nèi)容。在卡龍看來(lái),“不描述型塑技術(shù)對(duì)象的異質(zhì)的和規(guī)模更大的行動(dòng)者-世界就不可能描述技術(shù)對(duì)象。”[7]“社會(huì)的”不再意味著“外部的”,科學(xué)技術(shù)的內(nèi)容滲透著社會(huì)因素,區(qū)分科學(xué)的內(nèi)部與外部不再有意義。其次,行動(dòng)者-世界是通過(guò)轉(zhuǎn)譯過(guò)程而被建構(gòu)的。行動(dòng)者-世界并非外部世界中的預(yù)定的行動(dòng)者的簡(jiǎn)單組合。這些行動(dòng)者的利益、身份、角色、功能和位置都在新的行動(dòng)者世界中加以重新界定。比如說(shuō),雷諾汽車公司在EDF構(gòu)造的世界里不得不服從新社會(huì)運(yùn)動(dòng)而降格為制造底盤和車身的廠商。在轉(zhuǎn)譯過(guò)程中,“社會(huì)的”和“非社會(huì)的”要素都發(fā)生改變。不過(guò)轉(zhuǎn)譯的成功與否取決于轉(zhuǎn)譯者的轉(zhuǎn)譯能力和被轉(zhuǎn)譯者的抵抗力。在上述案例中,雷諾汽車公司不?視謁贓DF所構(gòu)造的世界中的位置,它努力建構(gòu)自己的行動(dòng)者-世界,進(jìn)而瓦解了EDF的行動(dòng)者世界,VEL也隨之死亡了。技術(shù)對(duì)象的堅(jiān)固性對(duì)應(yīng)于行動(dòng)者-世界的堅(jiān)固性。再次,轉(zhuǎn)譯過(guò)程表明,科學(xué)技術(shù)的力量已體現(xiàn)在建構(gòu)過(guò)程之中,因?yàn)榭茖W(xué)技術(shù)的建構(gòu)過(guò)程就是型塑社會(huì)和自然的過(guò)程,科學(xué)技術(shù)的成功建構(gòu)就是社會(huì)和自然成功型塑。同時(shí),行動(dòng)者-世界囊括了眾多社會(huì)的和自然的要素,這些要素構(gòu)成科學(xué)的力量源,足以解釋科學(xué)在社會(huì)生活中的巨大力量。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社會(huì)的準(zhǔn)實(shí)驗(yàn)室化”,科學(xué)的力量不再神秘。要言之,在科學(xué)活動(dòng)的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中已區(qū)分不出純粹的“科學(xué)的”、“技術(shù)的”、“自然的”和“社會(huì)的”內(nèi)容,因?yàn)榭茖W(xué)活動(dòng)本身已經(jīng)把它們結(jié)成無(wú)縫之網(wǎng),“自然”和“社會(huì)”在這張無(wú)縫之網(wǎng)中被共同建構(gòu)。
五、結(jié)語(yǔ)
對(duì)知識(shí)的生產(chǎn)現(xiàn)場(chǎng)進(jìn)行人類學(xué)考察,同時(shí)追蹤創(chuàng)制中的科學(xué)和型塑中的社會(huì),結(jié)果發(fā)現(xiàn),知識(shí)生產(chǎn)把各種社會(huì)的和非社會(huì)的因素納入其中,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過(guò)程就是型塑自然和社會(huì)的過(guò)程,知識(shí)不是對(duì)世界的表象而是型塑世界的過(guò)程和能力;科學(xué)在建構(gòu)一張科學(xué)、技術(shù)、自然與社會(huì)構(gòu)成的無(wú)縫之網(wǎng),也在這張網(wǎng)中被建構(gòu)。在這種考察中發(fā)展出了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理論。科學(xué)的浪潮把人類卷入知識(shí)社會(huì),知識(shí)社會(huì)是高風(fēng)險(xiǎn)的社會(huì),其風(fēng)險(xiǎn)很大程度上源自對(duì)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過(guò)程及力量機(jī)制的無(wú)知和失控。科學(xué)的人類學(xué)和行動(dòng)者-網(wǎng)絡(luò)理論為考察知識(shí)的生產(chǎn)過(guò)程以及知識(shí)與社會(huì)的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提供了新的方法和理論平臺(tái),尋求在降低知識(shí)社會(huì)的風(fēng)險(xiǎn)方面發(fā)揮作用。我們需要做的是,對(duì)知識(shí)社會(huì)中的知識(shí)活動(dòng)進(jìn)行更廣泛和深入的經(jīng)驗(yàn)性研究。
注釋:
[1]庫(kù)恩:《必要的張力·發(fā)現(xiàn)的邏輯還是研究的心理學(xu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p.265,p.267。
[2]B.Latour,OneMoreTurnAftertheSocialTurn...,inM.Biagioli(Eds.),TheScienceStudiesReader,NewYorkandLondon:Routledge,1999,p.276-289。
[3]B.Latour,ScienceinAction,MiltonKeynes:OpenUniversityPress,1987,p.258,p.99,p.144。
[4]B.LatourandS·Woolger,LaboratoryLife:TheConstructionofScientificFacts,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6,p.64,p.159,p.144。
[5]B.Latour,GiveMeaLaboratoryandIWillRaiseTheWorld,inKnorr-CetinaandMulkay(eds.),ScienceObserved:PerspectivesontheSocialstudyofScience,LondonandBeverlyHills:SagePublicationsLtd.,1983,p.141-170。
[6]S.Woolgar,CritiqueandCriticism:TwoReadingsofEthnomethodology,SocialStudiesofScience,vol.11,1981,p.504-14。
[7]M.Callon.,TheSociologyofanActor-Network:TheCaseofTheElectricVehicle,InMechelCallon,JohnLawandArieRip(eds),MappingTheDynamicsofScienceandTechnology,London:TheMacmilianPressLTD,1986,p.23。
[①]此案例參見(jiàn)《實(shí)驗(yàn)室生活》(LaboratoryLife)第三章“一個(gè)事實(shí)的構(gòu)造:TRF(H)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