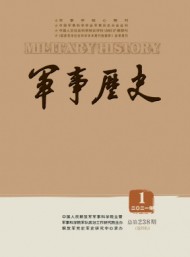歷史地理學的定義范文
時間:2023-12-07 18:03:2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歷史地理學的定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本文通過回顧30年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及其未來走向,討論對學科發展至為重要的繼承與創新的問題。筆者認為,學科交叉是歷史地理學前進的必由之路,歷史人文地理與歷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廢,傳統研究要與新技術運用相結合,要善于從現實需要探討歷史地理的重大問題,并用科學研究成果為現實服務,并就區域研究的價值與方法提出具體的看法。
[關鍵詞]歷史地理學;發展;未來走向
[中圖分類號]K90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518X(2012)04-0005-09
吳松弟(1954-),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歷史經濟地理、經濟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顧頡剛先生和譚其驤先生發起,以燕京、北大、輔仁等三所大學的教員和學生為基本力量,成立禹貢學會籌務處、出版《禹貢》半月刊,作為中國具有現代意義的歷史地理學開始形成的標志性事件的話,則1979年6月在西安召開首次全國性學術會議,會上決定成立歷史地理專業委員會、籌辦歷史地理刊物,無疑是歷史地理學進入大發展時期的標志性事件。自2011年開始,復旦大學、北京大學、陜西師范大學三個最重要的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來或即將迎來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創始人譚其驤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誕辰,浙江大學也舉行了慶賀陳橋驛先生90華誕的活動。許多歷史地理學者都在思考一個共同的問題:如何繼承前輩學者的光榮傳統,開創歷史地理新的發展局面?筆者不揣淺陋,通過回顧30年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并展望未來,就這一學科的繼承和創新問題,談一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學科交叉是歷史地理學前進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中明確提出:“歷史地理學是現代地理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對象是人類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變化,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動和影響而產生的。歷史地理學的主要工作,不僅要‘復原’過去時代的地理環境,而且還必須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當前地理環境的形成和特點。這一研究對當前地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有極大的關系;同時也直接有助于當前的經濟建設。”譚其驤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對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贊同。譚先生認為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與現代地理學完全一致,僅僅是時間上的不同而已,同時他又多次強調歷史地理研究時運用歷史學方法和歷史文獻資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認為,“以前歷史地理學還屬于歷史學的范疇,自然要運用治史的方法進行探索”,“既然(歷史地理學)是地理學的組成部分,就該兼用地理學的方法從事研究”。此后,多數學者都認為歷史地理學屬于現代地理學向后的部分,應該采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然而,關于歷史地理學的性質和研究對象的爭論,盡管已沉歇一段時間,卻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統一。2001年,孫天勝等發表《歷史地理學的學科屬性辨析》一文,認為把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的任務放在歷史地理學的名頭上是有欠思量的,應該稱之為“地理歷史學”,即從歷史角度或時間維度研究地理環境,真正意義上名副其實的歷史地理學應該回歸于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研究。侯甬堅于2007年著文,認為近代以來歷史地理學處在歷史學和地理學的相互接觸面上而不斷求取進步,受此影響它一直保持著學科的最大特點——兼為歷史學、地理學發展貢獻自身的學科價值。因此個別地理學者近年提出歷史地理學的名實之辨問題,顯系學術史和歷史地理學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極力強調的歷史地理學“研究社會歷史發展與地理環境關系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具有積極的學科建設意義,有助于形成新的學科定義。他通過對歷史地理學學科特性、近年學術界研究動向、泛歷史地理化的分支學科建立方式的詳細考察,提出了歷史地理學定義的增改意見和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認為歷史地理學是復原研究歷史時期地理環境及其變化過程,同時研究認識人類社會在這一地理舞臺上形成發展及演變規律的跨專業學科,歷史地理學研究的終極目標是努力促進人類社會進步、文明的演進和發展、人類與自然的永久和諧相處。
篇2
關鍵詞:生態史學 思想框架 研究思路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生態史(或稱環境史)[1]研究如新筍破土、蓬勃向上,呈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中國史學的一個嶄新分支——生態史學正在逐步建立之中。然而,應當如何建立和建立怎樣的中國生態史學?生態史學應當具有什么樣的思想框架?如何在史學體系中給予它以合理的學科定位?它與中國史學的其它分支、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是什么關系?對于這些問題,學者時或言之,專門系統的論述則未嘗見,故筆者草成本文,陳述幾點初步想法,期以拋磚引玉。
一、中國生態史學的本土淵源
從世界范圍來說,生態環境史研究大約興起于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中國學者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專門研究稍晚一些,80年代初開始出現在題目上標注“生態環境”一詞的史學論文,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最近幾年來逐漸成為熱門課題,一些學者相繼呼吁建立中國環境史學,筆者甚為贊同,但更愿意稱之為“中國生態史學”。
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外環境史學的影響,這一點毋須諱言。近三十余年來,歐美國家的環境史研究不斷發展,新論迭出,漸成熱門之學,并且有的外國學者還致力于研究中國歷史上的環境問題[2],令國內學者聞風聳動。不過,根據筆者的觀察,直至今日,除臺灣學者之外,國內對西方環境史學的了解仍然很少,有關方面的理論方法尚處于初步引進的階段[3]。也就是說,迄今為止,國內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思想理論和技術方法上并未受到歐美環境史學的顯著影響,而主要是依憑本國的學術基礎。換言之,由于“歐風美雨”的刺激,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在較短時間里快速興起,以致最近若干年來標榜“環境史”或“生態史”的研究課題日益增多,但無論就問題意識還是就理論方法來說,它都具有不可否認的“本土性”[4],可從上個世紀中國史學自身發展的脈絡中找出它的學術淵源和軌跡。只不過早先的相關研究是在不同學科中分頭進行的,顯得非常零散,也沒有明確打出“生態史”或者“環境史”的旗號。筆者以為:構建中國生態史學,固須積極引進和學習國外相關理論和方法,對國內學者所作的前期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績進行一番認真清理亦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中國生態史學方能建立在更加堅實的學術基礎之上,更好地結合本國實際開展研究工作,并免受“邯鄲學步”之譏。為此,筆者先對大陸學者以往的相關研究作一個簡要的評述。
1.考古學和古生物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中國學術界,最早關注歷史生態環境的是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向以歷史早期的物質文化遺存為主要研究對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出土文化遺存時,除了關心人體骨骸、人造事物(如器具、建筑、墓葬、手工業場所等)之外,也注意動物骨骸、植物籽粒或核殼等。出土動物骨骸、植物籽粒和核殼,指示著遠古時代各地動植物種類的構成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構造。上個世紀前期,當考古學家在殷墟遺址中清理出大象的遺骨和古文字學家從甲骨文中發現“獲象”、“來象”之類的記載時,學者逐漸認識到這種動物曾在華北地區棲息,也很自然地想象當地古今生態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著其它多種喜溫動植物遺存(如犀牛和竹鼠的遺骸、水蕨孢子等)亦在華北各地不斷出土,學者做出了遠古中國氣候和動植物構成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判斷[5]。
上世紀末期以來,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危機受到社會的普遍關切,考古學者也深受震撼,在國外考古學的影響下,大陸和臺灣都有一批學者積極著手建立中國的環境(生態)考古學,試圖對遠古人類聚落的生態環境進行某種程度的重建,并考察特定區域的生態環境因素對遠古社會組織、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的影響。與此同時,古生物學家也不再孤立地認識某些野生動植物,而是逐漸采用生態變遷的大視野,根據動物和植物考古資料,考察某個區域動植物區系和物種構成和特定動植物種類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及其原因。應該說,考古學和古生物學家所開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的,至少為我們長時段地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提供了豐富的和古今對比強烈的歷史信息。
2.歷史地理學和氣候史學者的相關研究
歷史地理學以自然和社會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為主要研究內容,致力于探討人地關系演變的過程和規律,與生態環境史研究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由于特殊的專業優勢,歷史地理學者具有令人贊嘆的廣闊思維空間,他們不僅注意到了歷史上的森林破壞、河湖變遷、沙漠擴張和一些珍稀野生動植物分布區域的歷史變化,也注意到了歷史上聚落、城市及經濟產業的分布與生態環境的關系。雖然他們的思想框架和研究方法是歷史地理學的,但前輩學者如史念海、譚其驤、侯仁之、文煥然、何業恒等人的不少論著實堪稱生態史研究的經典。
氣候史方面,早在民國時期,竺可楨就已注意到中國歷史上氣候的冷暖變遷問題。1972年,他在早年研究的基礎上,發表了題為《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4]的著名論文,對中國東部氣候的周期性寒暖波動進行了系統論述,成為學者引用頻率最高的史學論文。繼他之后,有一批學者先后在這方面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出版了數量可觀的論著[5]。
從最近10多年的成果來看,歷史地理學者顯然不再滿足于考察和描繪某些自然和社會文化現象的歷史空間分布,而是日益關注自然現象與社會文化現象之間的彼此聯系,在人口與環境、經濟生產和生活方式與環境、社會變動與氣候變遷、疾疫和災害與環境、民俗與環境等諸多方面,都進行了卓有成績的探討;一些研究其實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歷史地理學課題了[6]。假如它們仍然必須被稱為歷史地理學的話,那么只能說生態史學和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對象本來即有很大的重疊,兩者間的界線事實上非常模糊,幾乎無法斷然劃清。直到目前,我們所進行的許多生態史課題,往往是由歷史地理學者提出并率先開展研究的。如果說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主要是從歷史地理學中生長出來的,也不算言過其實。我們要想特別標立一種與歷史地理學相區別的生態史學,必須從學理上進行認真辨別,對兩者的理論方法和學術指向做出必要的判分[7]。
3.農牧林業史學者的研究
農業、牧業和林業的本質,是充分利用各種自然條件如水、土、光、熱和物種資源,干預動植物的生命過程,促進那些經濟動物和經濟植物的再生產,獲得以衣食原料為主的各種產品。任何一個類型的農牧林業生產都不可能離開特定的生態環境,它們的歷史發展,與生態環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系,因此農牧林業史家比較早地關注到歷史生態環境問題,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我國農牧林業史家關注生態環境,大約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8]。在此之前,個別學者已發表過若干相關論文,如雷海宗先生在1950年代曾發表《古今華北的氣候與農事》[9],根據古書記載概述華北氣候的變遷及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但并未形成一種群體性的學術傾向。20世紀80年代前后,東西方農業科學界都在反思“石油農業”和過量使用化肥、農藥對農業生態系統的危害,提倡所謂“有機農業”(后來又提出“生態農業”,再往后則是“可持續農業”;日本則有人基于道家思想提倡所謂“自然農法”),不少中外農學家稱贊中國傳統農業技術方法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使中國農史學家受到了鼓舞,于是有人開始論說傳統農作方式對維持生態平衡的積極作用,比如重視水土保持和積肥施肥、實行作物輪作間作套種、種植與飼養相結合、采用生物防治等等,對促進有機物質循環和保持農業生態平衡的作用和意義,試圖闡發傳統農學的現代價值,其中江南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桑基魚塘”、“蔗基魚塘”生態農業模式被賦予了典范意義。農田水利作為農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向來受到重視,有大量的論著發表,學者很早就關注農田水利建設對水資源調配的重要作用,及其對農業生態環境正反兩方面的影響。與考古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相比,農牧林業史家對歷史生態問題的論說顯得更加專業,這一方面由于他們具備良好的自然科學特別是生物學基礎,另一方面則由于他們一開始就注重對生態學(特別是農業生態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90年代以后,農牧林業史家的研究思路漸趨開闊,對于中國歷史上農牧林業與生態環境的關系,漸漸不再只是強調好的一面,而是開始反思傳統的農業資源開發利用方式的弊病及其所造成的生態惡果,例如關于黃土高原過度開墾所造成的嚴重后果、宋代以后長江中下游的圍湖造田和明清以來山區墾殖對生態環境的破壞等問題,均取得了不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一批學者從農業史和經濟史入手探討中國歷史上的“天人關系”,也取得了相當可喜的成績[10]。盡管農林牧業史學者的研究范圍大抵局限于對產業內部歷史問題的探討,但由于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大國,直到上個世紀才開始走上工業化道路,此前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其實也主要表現在農牧林業生產方面,離開了這些方面的基礎研究,想要真正認清中國生態環境變遷的歷史,殆無可能。事實上,自譚其驤、史念海以來,歷史地理學家探討中國古代生態環境問題,亦主要從農、林、牧業入手。
由上所述,我們不難發現:在中國,與生態環境史有關的學術研究可以追溯到上個世紀前期,并且已經取得了不少成績,為進一步考察中國生態環境變遷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為我們著手建立中國生態史學積累了較為豐富的學術資源。
然而,已有的研究尚不足以構成中國生態史學。首先,以往相關探討大抵只是考古學、古生物學、歷史地理學和農牧林業史等學科研究的外向拓展和延伸,而非以系統繪制中國歷史生態環境圖像為學術指歸。研究者對生態歷史問題的考察仍是立足于各自不同的專業,并沒有凸現出全面認識中國歷史生態環境、最終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系統重建的意向,更沒有從開始生態環境出發對社會歷史運動進行系統解釋的努力,這就造成相關研究與主流史學之間存在相當大的隔膜,其成果也未能很好地被一般史學著述所吸收;其次,盡管以往已經探討了許多重要論題,在研究思路和技術方法上也作了諸多有益的探索,為中國生態史學的建立準備了一些重要的構件。但是,這些論題、思路和技術方法顯得相當零碎和分散,彼此之間互不關聯,尚不足以構成學術界域分明、結構層次清晰并具有內在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生態史學框架;其三,由于“自然”與“社會”二元分立的思想觀念根深蒂固,以往對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理解和定位存在著不容回避的嚴重偏差:人們普遍將它視為社會歷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傳統史學一向重人事、輕自然,對自然的歷史用力甚少,對許多問題的認識幾乎是一片空白,生態環境史研究者立志加以填補,這是可以理解的。但矯枉未免過正,早先的生態環境史研究明顯偏重對自然層面的考察,社會層面的問題則被嚴重忽視了,從而造成了新的偏頗,以致許多人以為生態環境史的研究目標只是考察古今自然環境之變;其四、與以上幾個方面相聯系,盡管越來越多的學者逐漸認識到了開展環境史研究的必要性,實際介入這一領域者亦已不可謂少,但極少有人對這一新研究進行學理上的論說。迄今為止,國內的生態環境史研究仍局限于具體問題的探研,附屬在不同的相關學科之下,如果上升到“專門之學”這個層次加以考量,則仍存在著嚴重的學科理論缺失。正因為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生態環境史研究只不過是探討一些邊邊角角的歷史問題,算不上什么專門的學問,至多只能充當歷史著述的“緣飾”和“花邊”,難登史學的大雅之堂。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1] “生態史”又稱“環境史”,中外學者都往往混用,但“環境史”的叫法更加流行。個人認為:這一研究的基本理論框架應是生態學,因此更愿采用“生態史”一詞。另外,“環境史”仍有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人為分割的嫌疑,而在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中,兩者是一個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協同演變的整體,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應被視為地球生態大系統的一部分。
[2]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亞著名中國經濟史和環境史家Mark Elvin (伊懋可),他在多年前即開始了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其中包括對洱海、巢湖、杭州灣、近代結核病與環境等問題的專門研究。伊氏曾與臺灣學者劉翠溶合作主編會議論文集——《積漸所止:中國環境史論文集》(上、下冊),由臺灣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2000年出版中文版,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版(Sediments of Time: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與中文版所收論文略有不同),在中西方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最近,伊懋可又以《大象的退卻:中國環境史》(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為題,對中國環境史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系統論述。
[3] 近年來,一些研究外國史的學者如侯文蕙、、包茂宏、梅雪芹、高國榮等做了不少這方面的譯介工作,提供了相當豐富的學術信息,令人欽佩。
[4] 筆者這里使用“本土性”一詞意在說明: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主要并非導源于近30年來在國外興起的環境史學,而是基于本國學者在相關領域的前期研究。請切勿作過分寬泛的理解。
[5] 例如關于遠古動物,徐中舒早在1930年就發表了題為《殷人服象及象之南遷》的長文[1](pp.51~71),根據殷墟出土甲骨卜辭中“獲象”、“來象”之文,參以其它文獻記載和出土實物,對商代河南產象及象之南遷事實進行了論述。其后,德日進、楊鐘健、劉東生等人又先后,對殷墟出土哺乳動物群進行了系統研究[2][3]。這些均可視為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先聲。
[6] 例如青年歷史地理學者王建革關于華北平原和內蒙古草原生態、經濟與社會史研究的系列論文,其實更多地采用了生態學而非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方法,與傳統的歷史地理學研究大異其趣,可為顯著的例證。
[7] 關于環境史學與歷史地理學的關系,同行學者時有議論,但對兩者究竟如何判分,并未形成成熟的意見。個人認為:環境史(生態史)的理論基礎是生態學,它的主要著眼點是“生命系統”,重在考察生物(特別是人類)與環境、生物與生物之間的歷史關系;歷史地理學雖然一向強調人地關系,但其理論基礎是地理學,主要著眼點是“空間構造”和“空間運動”。因此,歷史地理學并不能包辦環境史學的研究工作。
[8] 從上個世紀80年代初開始,《中國農史》、《農史研究》和《農業考古》等幾家農業史刊物,均陸續刊載有題目上出現“生態”一詞的論文。在同一時期的農業史著作中,更時常見有“生態農業”、“生態平衡”、“生態破壞”等詞句,有關論述也不斷增多。
[9] 該文收入氏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
[10] 上世紀80年代以來,在中國農業史研究中,“風土”和天、地、人“三才”觀一直是學者關注的重要課題,先后有不少論著發表。1999年12月,中國農業歷史學會、中國經濟史學會古代史分會和《中國經濟史研究》編輯部聯合召開了“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 學術討論會,分別從天人哲學、農林牧業生產實踐、資源保護等多方面探討人類經濟活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會議論文由李根蟠、原宗子和曹幸穗等結集為《中國經濟史上的天人關系》,由中國農業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二、作為一個獨立學科的中國生態史學
誠然,從不同學科出發考察歷史生態環境的具體問題,是非常有意義、也是十分必要的,但相關研究必須加以有機整合。若欲改變目前的“零打碎敲”局面,開展全面系統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以獲得對環境歷史變遷的貫通認識,并由此取得對社會歷史的更加透徹的理解,就必須建立一種專門之學——生態史學,使之成為中國史學中的一個獨立分支學科。
毫無疑問,生態環境史研究要想提升為一個專門獨立的史學分支,必須具備獨特的思想框架和理論方法。然而,完成生態史學框架體系的構建工作,恐怕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西方學者已就“什么是環境史”、“環境史主要研究什么”這些基本問題討論了數十年,并提出了多種定義和構想,但各家的意見并不是很一致的;國內雖也有個別學者提出了一些設想[1],但事實上還沒有人真正著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在此,筆者也只能提出自己的一點粗淺見解。
我們認為:生態史學作為一個新的史學分支,其新穎和獨特之處,不僅僅在于它的研究對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思想理論和方法,首先(應當)體現在它將現代生態學理論方法應用于歷史研究,以生態學以及它的分支學科——人類生態學(生態人類學)、人口生態學、社會生態學和文化生態學等,作為觀察和解釋歷史的思想導引和分析工具。簡要地說,生態史學是運用生態學理論方法來處理史料、解釋歷史現象和歷史運動(既包括自然現象和自然運動,也包括社會現象和社會運動)的一種新史學。它的基本學術指向是采用廣泛聯系、彼此作用、互相反饋和協同演化的生態系統思想,陳述和剖析人類社會與生態環境互動變遷的歷史經驗事實,并就如何協調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發表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與一般的歷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的觀察視野不局限于社會和人事,而是將目光較多地投向人類的生物屬性和與人類社會活動發生過種種聯系的那些自然事物和現象;但生態史學又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史研究,它事實上只著眼于自然界(特別是地球生物圈)中與人類活動發生過關聯的那些方面。也就是說,生態史學的學科特點表現在研究對象上,是它立足于自然生態與社會文化的中間界面開展學術探討,對于這個中間界面,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天人之際”一詞加以概括。[2]在生態史學者看來,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乃是一個彼此影響、互動作用、協同演變的統一整體,自然環境和人類活動彼此施加于對方的歷史作用,人們對這種彼此作用的認識和反應,以及這些認識和反應的道德、價值、符號、組織、制度和各種行為體現,都是生態史研究者理應探討的內容。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面貌和變遷過程,固然是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但考察生態環境及其變遷作用下的社會文化運動亦應作為它的基本任務之一,而正確認識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和過程,則是這一新興學科的最高追求[3]。
很顯然,生態史學雖然看起來應當集中考察歷史“自然”問題(這既是先前的研究所造成的錯覺,也是一種矯枉過正的結果),事實上卻堅決反對將社會和文化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不過,生態史學者之關注社會和文化,與一般歷史學者關注社會和文化相比,在視角上有較大區別——生態史學強調人類的生物屬性,以及社會現象與環境因素的歷史關聯,文化則被視為人類這種特殊生物同周遭環境(在這里,“環境”既包括自然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打交道的方式和方法體系。也許可以不甚恰當地說,生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人類還原為一種動物——同其它動物一樣需要空氣、食物、水和各種其它資源,人類的繁衍方式、人口密度、生命維持體系和社會組織形式等等,同樣深受特定生態條件的影響和制約。所不同的是,人類具有創造、學習和傳承文化的能力,在應對環境的過程中,構建了復雜的工具、技術、組織、規范、價值觀念和意義象征體系,而一般動物只是渾渾噩噩的寄居者;人類依靠其所創造的文化而生存,一般動物只是憑著本能而已。
在生態史學看來:人類的任何一種社會歷史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中進行的,離不開特定的環境條件,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種種生態因素的影響,如將生態環境排除在觀察視野之外,就難以全面揭示人類社會發展的真正秘密。因此,具體(而非抽象)、實證(而非玄學化)地考察生態環境因素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影響,理應成為歷史學的一項重要任務。
與一般歷史學相比,生態史學不但有其特定的觀察視野和理論方法,而且具有獨特的社會歷史觀。它特別強調:無論文明怎樣發達、社會如何進步,人類始終都是動物界中的一員,人類的歷史始終都是地球生物圈中生命系統流轉的一部分。正如其它物種因生態環境的區域差異和時代變遷不斷發生變化一樣,人類社會和文化亦因所處環境的地域和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因此,社會和文化的許多歷史變異和差別,不但需從其自身的發生、演化過程中尋找答案,而且應從其所處的生態環境中求索根源。生態史學將告訴我們:在不同的時代和區域,社會文化如何受到各種生態環境因素的影響,并且在這些影響之下不斷發展演變?
另一方面,與自然史研究不同,生態史學雖然重視考察各種歷史自然現象,但時空界域圈定在人類誕生以來、與人類活動發生了關聯的那些部分。而在這一時空界域內的生態環境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人類的各種活動及其方式和結果,都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影響因子和表現。隨著人類實踐能力的不斷增強,人類活動在生態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生態史研究的另一重要目標,就是要弄清生態環境在歷史上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人類在其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從一定的意義上說,它事實上想要搞清楚:由人類活動所造成的“第二自然”是如何逐步形成、并且不斷發生改變的?這些改變又如何對社會產生反饋作用,影響人類的繼續生存和發展?
要之,在生態史學的思想框架中,環境是有人類的環境,人類活動是生態環境變遷的重要促發和推動因素;社會是一定生態條件下的社會,許多生態因素都是社會歷史運動的重要參與要素——從總體上說,人類社會文化系統是地球生態大系統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雖然在具體研究實踐中,我們既可側重探討人類活動影響下的環境變遷,亦可側重考察環境影響下的社會文化發展——這兩個側重構成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學術指向,但兩者事實上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如果割裂了兩者之間的聯系,就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生態史學。
根據以上想法,我們對自己所設想的中國生態史學的基本框架作如下幾點歸納:
一、生態史學作為一種新史學,并非刻意拋棄傳統的史學理論、方法和命題,而是要在歷史觀察中引入生態學的理論方法,強化對生態環境與人類活動相互關系的歷史探討;
二、生態史學擯棄“人類中心主義”,人類及其社會和文化的歷史被視為地球大生態系統演變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但也不是簡單地主張“生態中心主義”,雖然生態史學的一個重要目標是對生態環境的歷史進行系統描述和某種程度的“重建”,但人類活動及其方式和成果仍然被放置在關鍵的位置。因此,生態史學的歷史觀既非“文化決定論”,亦非“環境決定論”,而是“人類——環境互動論”;
三、生態史學從社會文化和生態環境的中間界面尋找和選擇論題,它的基本內容(根據側重點不同)包括兩大方面:一是歷史時期的生態環境面貌及其在人為作用下所發生的種種變遷;二是在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生態環境及其諸要素所發揮的重要影響和作用[4];
四、生態史學研究的最終目標,是探索人類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系統地描繪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協同變遷的歷史圖式。
顯而易見,生態史學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跨學科研究,它所要考察的,不僅僅是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也不僅僅是自然現象和環境因素,并且也不是兩者的簡單堆砌和相加,而是自然和社會兩大領域眾多現象和因素之間的有機、互動的歷史關系與過程。
毫無疑問,開展生態史學研究是一項極為艱巨的工作,研究者需要具備復雜、綜合和廣泛聯系的思想方法,需要具備廣博的知識——最好兼受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方面的訓練,并且需要具備超越于兩個學科領域之上的進行綜合、整體思辨的能力。由于以往學科劃分和教學方式的局限,一般中國學者在知識結構和思維訓練上都存在不可忽視的缺陷和不足。正因為如此,盡管目前生態環境史研究越來越熱門,已經觸及了非常廣泛的問題,但就所見的成果來看,多數論著的學術水平并不很高,總體上說,研究深度仍未超出1993年香港“中國生態環境歷史學術討論會”的會議論文[5]。我們注意到:一般歷史學者的相關論著中時或出現一些常識性的錯誤,而由具備不同自然科學背景的學者所進行的研究,又往往局限于各自的專業領域,彼此之間缺少必要的聯結和貫通,未能有機地整合起來形成系統的歷史認識。要想很好地開展這一研究,不僅需要有豐富的知識貯備、系統的理論方法訓練,而且要求不同專業領域的學者密切交流、通力協作。
[1] 例如,包茂宏在《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一文(載《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4期)曾就此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設想。
[2] 之所以特別指出“借用”,是因為筆者并不認為“天人之際”的歷史含義并非今天所說的“人類與自然之間”。一些學者將“天”理解為“自然”,將“天人之際”、“天人合一”解釋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人類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是很不恰當的。但從歷史文獻中,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更簡約的詞匯來表達這種關系,只好暫且借用。
[3]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6]一文認為:環境史是研究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史,研究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歷史過程。顯然,在景先生看來,環境史所關注的“環境”并非寬泛意義上的“自然”,而是與人類發生了關系的自然環境。在這一點上,我們的觀點是一致的。不過,雖然他所主張的環境史研究強調人類與自然的“關系”,但觀察的重點仍在于“環境”,而筆者所主張的生態史學是從生態學立場出發的,更強調人類與環境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不僅為了理解環境的歷史,同時更是為了理解人類和社會的歷史。
[4]景愛認為環境史研究應主要圍繞三個方面進行:第一,要研究自然環境的初始狀態;第二要研究人類對自然環境的影響;第三,要研究探索人類開發利用自然的新途徑[6]。梅雪芹在吸收西方學者觀點的基礎上,將環境史研究分為四個層次:一是探討自然生態系統的歷史,二是探討社會經濟領域和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三是研究一個社會和國家的環境政治和政策,四是研究關于人類的環境意識,即人類概述周圍的世界及其自然資源的思想史[7](pp.10~11)。盡管他們都強調人類與環境的相互影響,但基本學術指向仍是理解“環境”,仍不能包容我們所設想的生態史學。
[5] 這次會議的絕大多數論文均收入前揭伊懋可、劉翠溶主編論文集。其中中文版除《序》和《導論》之外,設立了《比較的觀點》、《對自然環境的詮解》、《人類的聚落》、《邊疆地區》、《水文與水利》、《氣候》、《疾病》、《環境的形象-官方的心態》、《環境的形象-文學的和通俗的感受》和《環境與近代經濟發展-臺灣和日本》等欄目,一些論文視角之新穎、論說之深入十分值得贊嘆。 三、中國生態史學研究的兩種理路
如上所言,我們所主張的生態史學,將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視為統一的整體,致力于探索兩者之間的歷史互動關系與過程,它所研究的是“天人之際”的歷史問題。這就決定了它既不能像傳統史學那樣只重視歷史上的社會和人事,曾被嚴重忽視的自然歷史變動將被當作重點突破的對象;亦不能像先前的相關研究那樣只對自然層面的問題情有獨鐘,眾多的社會歷史問題同樣需要認真加以考察,傳統史學所探討的諸多重要問題,仍將成為生態史學的重要論題,只是采用了新的思想方法,變換了論說的角度。換句話說,生態史學研究的對象,既包括自然歷史現象和問題,也包括社會現象和問題,橫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領域,是一種典型的交叉學科。
與多數成熟的史學分支相比,生態史學具有顯著的“邊緣學科”性質。然而,在這里,“邊緣”意指它的思想空間是在多個多科領域的聯結和交匯部分,而不是說它應該被定位在歷史學科的邊緣位置——盡管它目前仍然多少有些尷尬地被視為一種邊角的學問。事實上,只要稍微回顧一下學術史,我們不難發現:一種學術究竟屬于“主流”還是“邊緣”,未必就是命定的,而是既取決于相關成果的積累,更取決于不同時期的學術興奮點——而學術的興奮點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現實問題密切關聯。隨著歷史條件和社會情境的改變,曾經的主流學術可能被邊緣化,邊緣學術亦可能向中心位移而成為顯學。筆者大膽預測:生態環境史研究將逐漸登上中國史學的大堂正殿[1]。
當然,這仍需生態環境史學者做出持續不斷的努力,開展更扎實系統的研究并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為了達到這個目標,還必須努力改變研究理路,具體來說,需要更多地關注人與社會的歷史,從生態史學的立場出發切入主流史學所長期關注的那些相關歷史命題,即在一定程度上向主流史學、特別是目前居于顯學地位的社會史研究靠攏。這不僅僅是一種爭取學術地位的“技巧”,同時也是推進社會歷史認識的需要——觀察社會歷史運動和解釋社會歷史現象,原本即是生態史學的“應有之義”,只是路徑和方法有所不同而已。
回顧過去一個時期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的發展,我們不難注意到:不論從學術動機還是從實際研究情況來看,兩者之間都似乎少有瓜葛。直到最近10余年來,情況才發生了可喜的變化:這兩種分途發展的學術研究逐漸出現了互相交融、彼此會通的趨勢。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重視和努力推進的學術走向,向來重人事、輕自然和將自然與社會相分離的史學傳統,將可能因此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應該說,互相溝通和彼此聯結乃是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不斷深入而產生的共同學術訴求。
試細言之。
按照先前的觀念,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目標是認識自然環境、而非社會文化的歷史。如前所述,中國學者早先的相關研究,正集中于歷史上的氣候、森林、野生動物、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河流湖泊、海岸變遷和農業生態平衡等方面,研究者大多具有一定自然科學背景,如氣象學、地理學、農(牧、林)學、文水(水利)學等等[2]。歐美早期的生態史研究大抵也是如此,美國的生態環境史研究,雖然早期的研究已多與環保、邊疆和拓殖的歷史相聯系,但重點仍在于自然方面[3],目前這一領域的權威雜志——《環境史》是由美國環境史學會與森林史學會合辦的。但是,隨著相關研究不斷深入,學者日益意識到:生態變遷并不是一個純粹的自然過程,至少自農業時代以來,生態環境的諸多變遷與種種人為因素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無視人類活動的影響,就無法理解生態環境的歷史變化。正因為如此,最近一個時期以來,關于生態環境的歷史著述愈來愈重視社會性因素的影響和作用。美國“進入90年代以后,環境史與社會史合流成為一種趨勢,性別、種族都被納入環境史的研究內容。”[4]歐洲的環境史研究視野也在不斷擴展,從歐洲環境史學會網所刊1976-2004年間的相關論著目錄看,雖然近年的論著從數量上說仍以討論氣候、水源、森林、景觀、污染、災害疾病等問題者居多,但經濟、社會和文化與環境的歷史關系愈來愈受到重視[5]。在我國,關于近一萬年來(農業起源以來)生態環境變遷是否主要由于人類活動所致,學者尚有不同的看法,但生態破壞的社會原因日益受到重點關注卻是無可爭議的事實,譚其驤、史念海等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其實已經率先做了若干十分精湛的開創性研究[6]。
社會史研究致力于考察人類群體(即社會)發展的既往經歷,理所當然應以解釋社會歷史現象為鵠的。然而,單純從社會來解釋社會、或者僅將生態環境視為社會發展的“背景”,顯然無法對眾多社會歷史現象做出圓融的解釋[7]。從年鑒學派開始,法國的社會史家逐漸不再只是在理論上承認環境對社會的影響,而是將生態環境視為影響社會歷史進程的結構性要素,通過實證研究探索其影響的具體機制,成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視角,并對歐美社會史、文化史和經濟史研究的發展發揮了重要引導作用。最近若干年來,中國社會史研究者特別是地域社會史、災害疾病社會史和社會生活史研究者,也開始將生態環境作為能動因素納入各自研究思考的范圍[8];在經濟史和文化史研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學術趨向。
雖然國內迄今仍無人對生態史和社會史研究相互結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作專門系統的探討,但在我們看來,這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發生關聯,互相對話、借取和觀照,走向匯流融通,卻是一種必然的學術發展走向和趨勢。這既是兩者均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途徑,更是生態史學研究應取的理路。
站在目前主流史學的立場,人們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生態史研究對于認識中國歷史究竟有何意義?最容易得到認同的回答是:有助于認識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這樣的回答自然并沒有錯,但從生態史學的立場來看,則仍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很偏頗的。這是因為,在生態史學觀念中,生態環境不僅是社會發展演變的自然背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能動參與因素。對生態史研究進行合理的學術定位并與社會史研究真正有機地結合起來,完全可能為深化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更多貢獻,而不僅僅是為演繹社會歷史戲劇鋪設一個“自然的布景”。
筆者曾經指出:生態史與社會史研究互相滲透和結合,可能導致新的學科交叉,根據側重點不同,形成兩個學術分支:一是生態社會史,二是社會生態史[8]。前者的目標主要是了解自然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但與某些生態史研究相比,它特別強調并具體論證生態變遷過程中人類活動和社會(及其文化)因素的影響;后者則試圖采用生態學理論來研究歷史上的社會,強調自然環境因素的能動作用和影響,以期更好地認識人類社會及其發展演變,目的在于理解社會的歷史運動。簡而言之,前者是研究人類活動作用下的生態環境的歷史,后者則是研究生態環境參與下的人類社會的歷史。
為了進一步闡明我們的想法,且將自人類誕生以來的歷史不恰當地濃縮為一個童話式的簡短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片茂密的叢林,林中有一個小村,村里居住著幾戶人家。村民們世世代代在這里勞作和生息……。”生態社會史家主要講述這片叢林的故事,談論這片叢林曾經有多大,生長過哪些樹木,棲息過哪些動物?進一步,會談論這片叢林逐步縮小、或至消失的歷史過程及其社會原因,如由于村莊的人口不斷增長,需要開墾更多土地、搭建更多房屋、樵采更多燃料等等,樹木因此不斷遭到砍伐,叢林面積逐漸縮小,原先棲息在這片叢林中的許多動物,也因無處藏匿和覓食逐漸逃逸、終至絕跡……等等;社會生態史家則主要講述這個村莊中的人的故事,亦即描述由這幾戶人家所組成的社會的歷史,談論諸如村落社會結構、經濟狀況、生活習慣、婚姻風俗、文化娛樂、生老病死……等等問題。如果想把故事說得更加清晰和完整,就要進一步談論叢林和叢林中其它物種的變化,以及這些變化對村民的謀生方式、利益分配、權力結構、生育死亡、安全保障、娛樂活動,乃至信息交流、觀念情感等各個方面曾經發揮過的作用和影響。很顯然,由于歷史關注的側重點不同,可能分別做出不同的歷史敘述。而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叢林與村莊乃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彼此互為變化的因果,任一方面的變化都是促使另一方面發生改變的能動因素。
側重“自然”一面的生態社會史研究,基于這樣一個預設:人類活動、特別是經濟活動,至少從農業時代以來就是生態變遷的主因之一。因此,有關研究雖然著眼于生態環境變遷,但強調人類活動的影響,對生態變遷的討論不是從生態環境到生態環境,而是將人口、技術、生產與生活方式、風俗習慣乃至意識形態等等社會性因素,與水、土、光、熱、生物、礦物等自然因素,一同視為參與物質循環、能量流動、信息傳遞乃至整個生態系統演變的重要因子,在特定情況下,甚至視為比自然因素更加重要的歷史變量。沿著這種思路所展開的生態史研究,實際上差不多是考察人類改變生態環境的歷史。
社會生態史研究,則將人類社會視為地球生物圈內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它一方面承認人類與其它動物相比具有極為特殊的智能,即創造、傳播、積累和更新文化的能力,承認由于這種能力,人類社會具有高度的復雜性;另一方面,它同時認為:人類必須服從生態規律的最終支配,社會發展變遷的歷史過程,從根本上說,乃是人類不斷調整與生態環境關系(包括經過自己改造的生態環境)的過程——技術體系的進步、生業方式的改變、社會組織的變遷,乃至風俗習慣和思想觀念的嬗變,都在很大程度上歸因于社會對生態變遷的適應性調整,或者間接地跟從于這些調整;經濟類型、社會結構、生活方式乃至精神風貌等等許多方面的地域差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生態環境差異所造成的;生態環境的歷史變遷,同樣導致上述方面發生種種改變。正由于人類社會在地球生態大系統中與周圍環境存在著廣泛的物質、能量和信息交流,是其中的一個特殊生命系統,因此人類社會的歷史,也就存在著采用生態學理論方法加以認識的可能性。
社會生態史的主要研究對象,仍然是歷史上形形的社會現象、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流轉不息的生命運動。但與一般的社會史研究相比,它更側重探討社會現象的生物性質和自然基礎,致力于尋找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社會現象與自然現象、社會因子與生態因子之間的歷史聯系。在這里,紛繁復雜的社會歷史現象,諸如衣、食、住、行、生產、消費、婚姻、生育、疾病、死亡、遷徙、社交、娛樂、戰爭等等,以及因之所產生的技術、組織、結構、制度、規范、習俗、思想意識,就不單純地被理解為“社會的”或者“文化的”,同時還被理解為“生物的”,是在特定“自然”和“生態”影響下產生、并反映特定自然生態環境的;家庭、宗族、村落、城邑等等,也就不應只是被理解為社會的單元或聚落,同時還是大小不同的生態單位或系統,可以采用生態學方法加以考察。要之,社會生態史學者承認文化因素的生衍變異和社會系統的發展演化具有自己的內在邏輯,但卻不認為它們是(至少不完全是)封閉、自限和自我決定的過程,而是與生態環境及其眾多因素彼此影響、協同演進的過程。
這樣一來,生態史學研究就有了兩個側重點不同的可取理路:即生態社會史和社會生態史研究。如果選取前者,即使在具體實踐中十分強調人類社會活動的影響作用,也仍然屬于社會史之外的另一學術領域,它的學術目標是系統地描繪生態環境及其變遷的歷史圖像,當然客觀上也可為講述人類社會的歷史故事增添一個“布景”和“底圖”;如果選取后一種理路,則不僅是生態史學研究的一部分,而且可以視為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新的思想框架。這種新的思想框架,將社會及其所處的環境視作一個有機、統一和整體的生命系統納入考察范圍,不僅考慮各種社會因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將各種生態因素視為重要的參與變量,從而呈顯出一種新的社會歷史觀,我們姑且稱之為“社會(文化)——生態史觀”。一旦采用了這種新的框架,史家對“叢林中的村落社會”的觀察,既可能提出許多新的問題,對一些老問題的認識也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而不僅僅是在敘述故事時簡單地添加一些在過去看來無關緊要的內容。生態史家有信心為社會歷史觀察提供新的視角、問題意識、解釋途徑乃至新的歷史觀念,并對推進中國社會歷史認識做出獨特的貢獻。
從生態史學的視角來觀察社會歷史可能會提出哪些新的論題,現在還難以預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必定會提出并討論許多從前不曾思考的歷史問題;以往曾經探討的不少論題,包括一些長期爭辯的重大問題,亦完全可以、而且應當重新研究,并可望做出新的解釋。事實上,已經有些學者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比如關于歷史上中國南北文明進程的差異、胡漢民族的沖突與融合、周期性的社會動蕩、經濟重心的轉移、水利與專制政體的關系[9]等等,已陸續出現了一些結合生態環境而重作思考的新論。還有不少重大問題,例如中國“封建社會”何以長期延續、何以歷史上漢文化不斷成功地向南擴張卻難以向長城以北推進?……等等,亦都可從人類——環境的互動關系和過程中重新求索。微觀層面上的許多歷史問題,同樣可以采用這一思想框架加以考察。當我們全面考察某個地域社會的歷史時,決不能置當地的山川形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特別是經濟動、植物)構成乃至礦產資源于不顧,因為當地社會在生產模式、飲食結構、服飾式樣、居處方式、交通設施、疾病、災害以及娛樂、信仰、知識等眾多方面所呈現出來的地方特色,都毫無疑問是根植于其獨特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的水資源環境,必然要影響當地的生產結構和生活習慣,迫使人們圍繞水源控制管理和水旱災害防治形成某些特殊的組織、制度和秩序,甚至進一步影響到當地民眾的心態,形成某些特殊巫術、禁忌和神靈信仰。如果不充分生態環境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能動作用,許多宏觀和微觀層面的歷史現象都將無法得到合理圓融的解釋。
當然,筆者也曾指出:采用社會生態史的框架來認識社會,只是社會歷史觀察的一個特殊途徑,不能期望所有問題都能由此得到圓滿的回答。這是因為,社會生態史研究并不能完全取代一般的社會史研究,有些社會歷史問題并不在它的觀察范圍;更重要的是,現代生態學畢竟導源于生物學,而人類不僅具有生物屬性,同時還具有文化屬性(特別強調一點:文化具有自我演繹性),擁有復雜文化和思想情感的人類畢竟不同于其它動物,人類社會系統與其它生命系統的差距很大,其系統結構、系統功能與運行機制的復雜性遠遠超過其它任何生命系統,在觀察社會歷史問題方面,現有生態學理論方法的解釋力仍然有所不足,對于現代生態學概念、術語和技術方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的適用程度,不能期望過高,更不能簡單機械地套用,而應在認真披揀、選擇和改造其適用部分的基礎上,努力構建符合中國歷史研究需要的新的理論方法體系[8]。如果將人類社會簡單類同于一般動物系統,而忽略它的特殊性和復雜性,所得出的結論將可能是十分荒謬可笑的。
參考文獻:
[1]徐中舒.徐中舒歷史論文選輯[M].北京:中華書局,1998.
[2]德日進、楊鐘健.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J].北京:中國古生物志(丙種第12號第1期),1936.
[3]楊鐘健、劉東生.安陽殷墟之哺乳動物群補遺[J].北京:中國考古學報(中國科學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十三第4冊),1949.
[4]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J].北京: 考古學報,1972,(1).
[5]葛劍雄、華林甫.二十世紀的中國歷史地理研究——回顧與展望[J].北京:歷史研究,2002,(3).
[6]景愛.環境史:定義、內容與方法[J].開封:史學月刊,2004,(3).
[7]梅雪芹.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王利華.社會生態史——一個新的研究框架[J].天津:社會史研究通訊(內部交流刊),2000,(3).
[1] 這一點可由《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史學理論研究》、《中國史研究》、《史學月刊》、《歷史地理》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等權威學術期刊頻繁刊載有關方面的學術論文可以看出。
[2] 關于過去一個時期中國生態環境史研究的發展情況,張國旺:《近年來中國環境史研究綜述》(載《中國史研究動態》2003年第6期)、佳宏偉:《近十年來生態環境變遷史研究綜述》(載《史學月刊》2004年第6期)分別作了較系統的回顧;王子今:《中國生態史學的進步及其意義——以秦漢生態史研究為中心的考察》(載《歷史研究》2003年第1期)也提供了一些線索,可參閱。
[3]關于西方環境史學的發展,曾華壁《論環境史研究的源起、意義與迷思:以美國的論著為例之探討》(臺灣《臺大歷史學報》1999年第23期)、包茂宏《環境史:歷史、理論和方法》及《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載《中國學術》2002年第4期)和梅雪芹《20世紀晚期的環境史及其學術意義》(收入氏著《環境史學與環境問題》,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等文分別有所介紹,可參閱。
[4]高國榮《美國環境史學研究綜述》(“中華文史網”2004年9月22日刊發)。對于這一轉變,包茂宏《美國環境史研究的新進展》一文也提供了不少信息。此外,J.R.McNeill“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載 History and Theory, Theme Issue 42,December 2003,5-42。茲據historyandtheory.org/McNeill.pdf)一文也有專門的論述。
[5] 由于筆者不懂英語以外的其它西方語言,以上印象只是根據 European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 (Eseh)網“Bibliography”英文部分得出的,讀者若欲了解詳細,請登錄 eseh.de/bibliography.html 。
[6] 例如譚其驤《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出現一個長期安流的局面》(收入《長水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7年)、史念海《隋唐時期重要的自然環境的變遷及其與人為作用的關系》(收入所著《河山集》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均為經典之作。
[7]盡管中國史家早就注意到自然對人事具有重要歷史影響(例如司馬遷將“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視為史家的基本任務,至少隱含了關注自然環境影響社會人事的思想傾向),近代以來中外史學家都曾就“環境決定論”和“文化決定論”展開過熱烈討論,但自然環境(中國古人多稱“風土”)在傳統史學中曾長期被視為一種恒久不變的客觀存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被“玄學化”了,“究天人之際”并未真正付諸實證性的學術實踐。
篇3
Scholte(1997)指出全球化內涵包含3個層次:跨越邊界、開放邊界和超越邊界。跨越邊界意味著國際化,側重于描述要素在不同國家之間的流動及其對東道國的影響;開放邊界意味著自由化,側重于從政治與制度的角度分析全球化過程中國際秩序的變革,以消除要素流動的壁壘。二者主要以地域為基本分析單元。而超越邊界則強調以全球為整體,在超越地域概念的基礎上重構空間。從全球層面上看,全球化重塑了全球生產、國際關系、文化交流、知識傳播等過程的空間結構,并且參與主體呈現出鮮明的多元化特征,進而導致結果具有顯著的不確定性。在當前背景下, 全球化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問題, 它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文化問題,當代人文地理的研究在全球化的研究中逐漸開始占有重要地位。
當代人文地理學家對于全球化的定義,包含三種不同的態度-超全球化論、懷疑論和轉型論。超全球化論者認為,全球化是不可抑制的巨大力量,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高度發達的技術和全球化消費觀念的擴散使得信息、資本和創新的"流"達到最大的狀態。最大化的自由的 "流"建了一個生產、貿易和金融的跨國網絡,這使得世界經濟成為 "無邊界的"狀態。懷疑論者質疑了已經存在的全球化,認為全球化是過于夸大的思想和分析的概念。他們認為全球化不是決定性的,而是被決定的。區域主義被認為是反全球化的有力的證據。懷疑論者認為國家政府在全球化經濟的構建和管理行為者中仍占有中心性的地位。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人文地理學者從不同維度開展了全球化研究:既包括了以問題為導向的社會經濟分析要素流動、經濟增長、區域發展、世界城市等,也涵蓋了對政治與制度的解構(制度變革、國家轉型、城市治理等);既涉及對學科理論與方法的揚棄,也注重跨學科的交叉與綜合。值得注意的是,人文地理學者尤為重視對尺度與空間的理論重構,反對全球化意味著"地理終結"的論調,指出全球化不僅代表著跨國聯系的強化,同時還推動著代表異質性的地方力量崛起和國家力量變革。
隨著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社會生活的轉換由物質-政治-文化的轉化程度不斷加深。在當代全球化階段,國家已經無法維持持續的社會繁榮和經濟的增長,個體開始突破國家尺度的管理,最值得關注的是全球文化的"普遍化 "顯示文化的全球化和滲透性,突出了全球化文化的重要意義,認為全球化歷史主要體現在全球化文化的擴散和滲透,全球化文化由表層面的物質文化,中層面的制度文化,和深層面的精神文化的不斷加深。從全球化的動力機制來看,是文化結構要素的自身出現的發展危機導致了全球化階段變化。Murray 的全球化波動歷史理論的核心思想強調了結構性危機是每一次波動產生的動力。歐洲的貿易殖民導致了工業變革和資本主義的加強,這種文化的改變對經濟和政治產生了深入的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 "后殖民主義文化"培育了全球化的政治制度。在現代化階段國家發展主義大力推進跨國公司是資本主義文化擴散的主要動力;1970年的石油危機則導致了全球 "新自由主義"文化興起,國家的力量受到全球制度和市民社會的挑戰。其核心是致力于縮短資本循環周期的資本主義文化的擴散,其導致的空間結果是通過技術的革新帶來的 "時空的壓縮"。獨立于領土空間的力量的存在使得全球化空間力量的結構表現越來越復雜,同時處于不斷的變化中。他認為:一是全球化并不是像地毯一樣均勻的鋪展開來的。二是全球化也不是什么新的現象,但不同的全球化波動階段存在一些明顯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差異。
總體來看,當代西方人文地理學有影響力的理論方法論包括計量地理學、后結構主義地理學、地理學、女性地理學、制度主義地理學和關系的地理學,它們在全球化的研究主題、態度、分析的框架上各有特色,同時也存在交叉。分析龐雜的 '全球化'的概念,可以發現當代人文地理學的全球化態度的演化經歷了 "超全球化論-懷疑論-轉型論"的演化。對 "空間 "概念的理解經歷了 "絕對空間-相對空間-比喻空間"演化;空間辯論走向了 "真實的空間(地方空間)和比喻空間 (流的空間)共存"。總之全球化和地方化相互作用的觀點成為當代人文地理學關于全球化空間辯論的主導方向。對于空間規模的理解,全球的 、國家的 、區域的和地方的多種規模空間權利存在,關于制度 (權力)空間結構的理解經歷了 "分離的層級性-協調共存的層級性-網絡的交織"的演化。從全球化的歷史地理學研究上,對全球化的動力機制的分析,地理學理論方法和后結構主義的方法得到較多的體現。
長期以來,我國人文地理學一直將 "空間"研究作為研究的核心。即人文地理學關注解決 "what"和 "where"的問題,而其他學科則解決"why"和"how"的問題。這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文地理學的發展和學科地位的提升。當代西方人文地理學發展的方向性顯示,"空間"開始由 "研究的對象"轉向了"研究手段 (way)",研究的對象則轉向解決"why"和"how"的問題。面對復雜的全球變化,我國的人文地理學家也需要認真的思考和討論學科的發展方向問題。關于全球化的研究,目前我國的人文地理學主要是關注經濟層面的全球變化對區域產生的影響,相關的文獻主要集中FDI 和產業集群的研究。就實質上看,就是思考如何被動"響應"全球化,而不是如何積極的"牽制"全球化。全球化是一種復雜的過程,僅僅從單方面,單層面入手是無法發現問題的癥結和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因此,多尺度的空間規模,多元化的行為者以及相互作用的網絡關系的研究需要在全球化的研究中得到更多的體現。而這些問題的研究也需要其他更多相關學科理論的融入,如社會學,管理學等。
參考文獻:
1、彼得?迪肯--《全球性轉變--重塑21世紀的全球性經濟地圖》
2、徐海英 -- 《人文地理》
3、賀燦飛、毛熙彥 -- 《地理科學進展》
4、高柏枝 -- 《環球人文地理》
篇4
關鍵詞:鄉土景觀,鄉土聚落,傳統文化景觀,學科流派,研究路徑
Abstract: In the 1980s, the rural landscape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atten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scape ecology in the country, so far, the local landscape is still at a preliminary stage of growth, which adapt to the new direction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has a leading role. Due to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and local culture have lost the original style, people-land relationship has also been a serious threat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local conditions is also behind all over the country local flavorgradually devour. In recent years on the basis of the local landscape research, integrated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disciplinary genre studies explore the connotations of the local landscap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ral landscape and the weight of the body discipline as the core path structure, and analy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roposed research prospects. Through the above research, the hope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model to further explore one of China's actual situation,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landscape.
Key words:Local landscape; local villages;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landscape; genre subjects; research path
中圖分類號:TU984.1 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2095-2104(2012)
中圖分類號: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在20世紀80年代,由于我國大部分鄉村地區經歷了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城市化進程也逐步加快,“國際一體化”越來越深入的影響到我們的生活環境,越來越多的地域景觀和當地文化都已失去原有的風貌,人地關系也受到嚴重威脅,因地制宜的基本原則也被拋在腦后,全國各地的鄉土氣息也逐步被吞噬掉。在這一過程當中,無科學的規劃發展將會破壞在歷史長河中保留下來的鄉土風貌和文化景觀,破壞生態環境,最終無法滿足可持續發展,所有的美好風光只能存留在人們腦海里的一種想象。這種問題同樣出現在中國的景觀學科界,對于鄉土景觀的研究在相關學科的學者們對于“全球均質化”的討伐聲中正逐步得到發展。鄉土景觀研究在國外起步于20世紀40-50年代,我國學者對鄉土景觀的關注是20世紀80年代才開始的,到90年代研究隊伍逐漸壯大。鄉土景觀最初的研究學科主要集中在建筑學學科,更傾向于對我國傳統聚落的研究,目前有關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多個學科,主要有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和風景美學等相關學科。
1 鄉土景觀的概念與內涵
“一條崎嶇的山間小路,一片生機的綠色稻田,一排錯落有致的農家小屋......”,這就是傳統印象中“鄉土”傳達給我們的影像。實際上,“鄉土”是由“Vernacular”一詞得來,來源于拉丁語“verna”,意思是在領地的某一房子中出生的奴隸。鄉土引入國內的翻譯,被大部分接受的還是“鄉土、家鄉、故土、或是地方、區域”。(如圖一)
圖一鄉土印象(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有關鄉土景觀的概念界定迄今沒有統一,甚至連稱謂都沒有統一。與其相近的研究主題主要有“文化景觀”(cultural landscape)、“鄉村景觀”(rural landscape)、“鄉土建筑”(vernacular architecture)等概念。一般認為,“文化景觀是指居住在其土地上人的集團為了滿足某種實際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有意識地在自然景觀上疊加了自己的勞動所創造的景觀”(司徒尚紀,近年我國文化地理學研究的新進展)。而“鄉村景觀是指鄉村地域范圍內不同土地單元鑲嵌而成的嵌塊體,以農業特征為主,是人類在自然景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自然生態結構與人為特征的綜合體”(試論我國鄉村景觀的特點及鄉村景觀規劃的目標和內容,劉黎明等人);鄉土建筑是指“在某一特定時期 ,某一特定國度 ,結合本地地理位置、氣候條件、風土人情、文化特征的一種建筑風格。它是人類從穴居、半穴居或架木為巢開始 ,經過漫長的歲月 ,逐漸積累了結構上的技巧和技術 ,創造出來的符合地方條件 ,與自然協調的建筑形式”(川西北鄉土建筑的生態特征初探 ,成斌)。
俞孔堅學者對鄉土景觀的概念有著較為詳細的定義,他將鄉土景觀分為三種不同的理解進行詮釋,分別是地域性景觀、鄉村景觀、尋常景觀,認為所謂鄉土景觀是指當地人為了生活而采取的對自然過程、土地和土地上的空間及格局的適應方式,是此時此地人的生活方式在大地上的顯現。因此,鄉土景觀是包含土地及土地上的城鎮、聚落、民居、寺廟等在內的地域綜合體。[俞孔堅. 論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J]. 建筑學報, 1993, (2): 10-14.
]可見,各個學者所處研究領域不同,對鄉土景觀也有不同的見解,但也有一定的聯系,根據社會的進步以及設計學科的需要,鄉土景觀的概念也在變化。
2鄉土景觀研究的各學科流派
鄉土景觀是一門較景觀生態學更為年輕的學科,由于各個學科在研究鄉土景觀的出發點與應用其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同,從而形成鄉土景觀在應用研究上形成的差異,形成以學科為圓心的若干流派,不斷的在學科交叉網中深化研究。學科包括本體學科與外部學科,各個學科研究主體不一,因此研究成果與研究方法各有不同。
2.1 地理學研究流派
地理學主要以地理環境為研究對象,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人文地理學、歷史地理學,其研究內容主要是在不同地理特征基礎上形成不同特色景觀的類型及演變,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金其銘、劉沛林等人。金其銘等人認為鄉土景觀是在鄉村地區具有一致的自然地理基礎、利用程度和發展過程相似、形態結構及功能相似或共軛、各組成要素相互聯系、協調統一的復合體[ 項紅梅.宋立.初寶順.鄉土景觀的國內研究狀況. [J]. 中國園藝文摘.2010/01.],金其銘主要是對城市地理與文化地理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文化景觀研究,另一個是農村聚落地理研究,主要成果有早期的《農村聚落與土地利用》、《農村聚落地理研究》等文章。劉沛林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地理、聚落地理、景觀規劃及人居環境學,他運用景觀基因全新概念,對景觀差異性進行了相應的分析研究,并對農村聚落文化沉淀進行相關研究,主要成果包括《基于景觀基因完整性理念的傳統聚落保護與開發》、《景觀基因圖譜:聚落文化景觀區系研究的一種新視角》等文章。
2.2 景觀設計學研究流派
景觀設計學科主要以景觀保護與再利用為研究對象,景觀設計學科對于鄉土景觀的研究目的在于幫助設計師用一種新的、非自我的視角,設計內在人生活的景觀,從一種不自覺的、沒有設計師的景觀和唯設計師的景觀,走向自覺的為使用者而設計的景觀。[ 俞孔堅.王志芳.黃國平.《論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J]. 建筑,2005/04,第23卷.]俞孔堅教授在這方面有很多理論研究以及成功的案例,將人地關系的和諧與否放在首位,重視人行回歸,土地回歸,認為只有尊重與善待土地,才能重建人地關系的和諧,他在《續唱之歌―白話的城市與白話的景觀》一文中,提到了當代中國設計創新的動力與評價中國現代設計的根本標準的兩種危機意識,一種是指民族身份,另一種就是指人地關系,這兩種危機意識出現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本土性的忽視。[ 俞孔堅.李偉.《續唱之歌―白話的城市與白話的景觀》[J].建筑學報. 2004/08.]俞孔堅教授在于2006年提交給國務院領導和有關部委的“三個建議中”[ 俞孔堅.《關于防止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破壞、鄉土文化景觀保護和工業遺產保護的三個建議》.中國園林[J].2006.]也提到了對于鄉土文化景觀的保護,并認為風景園林學科應將這個事業視作本身的使命,在其中起到極為關鍵的作用。俞教授在進行理論研究的同時,并進行了很多設計實踐項目,很多實踐項目都是作為成功案例被行內用來教學研究以及學習。在美國景觀設計師協會2002年大會上,俞孔堅領銜設計的中山岐江公園獲得年度大獎,這是國際景壇最高獎項之一(如圖二)。中山岐江公園建造在廢棄造船廠舊址上,是俞孔堅景觀理念的代表作。其主導思想是保留、更新和利用造船廠原有地基與植被,充分提煉工業時代的標符,同時進行新的設計和藝術加工,采用現代景觀語言來強化場地及景觀作為特定文化載體的意義。比如重新包裝水塔,使之變成了照亮過去50年過往時間的燈塔。這個曾受到國內眾多專家反對的方案后來卻受到了國際評委的高度贊賞,被稱為“工廠有幸化公園”,“船塢和齒輪成為城市的懷舊藝術”。成功案例還有沈陽建筑大學的稻田校園設計,運用原始的農田肌理營造的鄉土校園景觀, 這是一個用水稻、作物和當地野草,用最經濟的途徑來營造一個校園環境的案例,景觀中應用了大量的水稻和莊稼,并通過舊材料的再利用,試圖對莊稼、野草和校園做一個重新的認識。(如圖三)
圖二 廣州中山岐江公園
圖三沈陽建筑大學稻田校園景觀及設計草圖
由此可見,俞孔堅教授運用獨特新穎的專業知識使理論不再是空談,對于鄉土景觀的重視不僅僅是作為一名景觀設計師的身份去提出問題,更多考慮的是整個名族未來發展興衰與否。
2.3 景觀生態學研究流派
景觀生態學流派主要是主要集中在城鄉交錯帶的景觀格局和鄉村土地整理研究以及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研究上。此外,還包括從20世紀90年代村落生態學科對村落生態系統的分布與模式的研究,近年來,關于景觀生態學的過程、格局與尺度方面研究較多,景觀類學科基本都是遵循景觀生態學的研究方法與研究模式,這為鄉土景觀的研究有很好的指導和研究基礎。[ 項紅梅.宋立.初寶順.鄉土景觀的國內研究狀況. [J]. 中國園藝文摘.2010/01. ]主要代表人物有王云才、謝花林、郭文華、王浩、王向榮等人。王云才多年來對傳統地域文化景觀做了多方面的研究,他的研究熱點包括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的整體性與孤島化現象、傳統地域“欠發達”與文化景觀邊緣化現象、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的地方性與現代化、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的真實性與商業化。并在《傳統地域文化景觀空間特征及形成機理》一文中提到,在“四化”(城市化、工業化、現代化、商業化)對傳統地域文化景觀沖擊下,傳統與現代、地方性與國際化、保護繼承與創新發展的矛盾日益尖銳,不同作用不同過程下呈現出不同的空間特征與機理,因此要建立完善的傳統地域文化景觀保護與可持續發展的控制體系。
2.4 建筑學研究流派
建筑學研究流派主要集中于對鄉土聚落及民居研究,基本側重于古建、古民居以及聚落的組織、布局以及形態,鄉土聚落適應于當地的鄉土環境,并呈現出明顯的地域性特征,由于不同地區的鄉土環境的差異,導致各地鄉土聚落形態、規模、布局、職能等方面存在著明顯差異,同樣也可歸為鄉土景觀研究部分。主要的代表人物有阮儀三、彭一剛、陳志華、張松等。阮儀三學者多年也致力于鄉土建筑與古村落的保護及相關研究,表達了對所謂民族之根的關注與重視。彭一剛學者在此方面的著作主要有《傳統村鎮聚落景觀分析》,書中主要對傳統村鎮聚落形態形成與傳統村鎮聚落的景觀分析進行了大量的描述,這對于今后的鄉土聚落研究部分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還包括陳志華學者的《浙江省新葉村鄉土建筑》以及清華大學出版的《諸葛村鄉土建筑》等著作,都是重要的研究著作。目前,鄉土建筑是最脆弱,也是受到最大威脅的文化遺產,眾多學者也是共同呼吁全社會都能關注日漸消失的鄉土建筑,重視對鄉土建筑與它多體現的地方文化多樣性的保護問題。
2.5 風景園林學研究流派
風景園林學學科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鄉土景觀和鄉村景觀,本學科的代表人物為同濟大學劉濱誼教授,他在幾十年的教學以及實踐經驗中,成果以研究鄉村景觀居多,他認為鄉土景觀是可開發利用的綜合資源,是具有效用、功能、美學、娛樂和生態五大價值屬性的景觀綜合體。他發表了《風景景觀工程體系化》、《圖解人類景觀―環境塑造史論》、《現代景觀規劃設計》等學術專著;并應美國芝加哥公署司的特別邀請,獨立完成了迄今為止在美國最大的中國式園林“芝加哥中國城公園”的規劃方案。他的設計傾向于對當代國外設計方法與中國本土景觀園林相結合,為中國當代景觀設計謀求更為適應當代社會發展要求的景觀設計方法,在我國景觀園林研究領域獨樹一幟。
3以景觀生態學學科為核心的研究路徑重構
以景觀生態學學科為核心的研究路徑包括三種,分別是學科本體路徑、外部學科路徑、應用路徑。以景觀生態學學科本體路徑為核心看待鄉土景觀,以景觀生態學理論作為鄉土景觀的研究基礎,以研究鄉土景觀發生過程及內在屬性為目標,對鄉土景觀垂直及水平要素的特征加以描述,主要研究鄉土景觀的過程、功能、結構。以其他視角為核心看待鄉土景觀,通過對鄉土建筑、傳統文化景觀、鄉土園林所影響到的社會、文化、地理背景的研究,深層次的發掘鄉土景觀的內涵與過程研究。本類研究不再是以建筑自身為主體,而是以“關系”為主體,從這些學科的視角觀察建筑與學科之間的關系,從而揭示鄉土景觀在學科外部多方面的屬性及特點,這些學科包括景觀設計學、風景園林學、地理學、建筑學、風景美學、文化學、考古學等。外部學科路徑符合當代“各門學科在不斷分化的同時又在相互交叉點上產生綜合”的趨勢[ 岳邦瑞.地域資源約束下的新疆綠洲聚落營造模式研究.2010.
],目前看來,其研究領域為“跨”,但其研究理論與方法實為“借”,取“外部學科”的視角,依靠“引進方法”,持“拿來主義”的態度對待研究對象,比如研究鄉土建筑與社會學的關系,則廣泛采用社會學中一般研究方法―社會調查方法;若從人文地理學角度,則采用地圖方法等,距離真正意義上的“研究交叉”尚有一段距離,有待針對性更強的理論、方法的創新與整合。
在應用路徑方面,小城鎮規劃建設隨著現代城市建設中,大量的鋼結構、膜結構被應用其中,由此出現的是大量的豪華硬質鋪裝、只可遠觀的大草坪、大型硬質廣場等景觀。城市原本的地域特征逐漸消失,區域特征也開始不明顯,眾多學者提出在城市設計中的鄉土化研究,俞孔堅教授提出反規劃的景觀系統模式,確實是一種讓城市可持續發展的鄉土化城市景觀有效模式,趙永斌在他所寫的《鄉土化城市景觀初探》中同樣提到,為了避免我國的城市景觀趨于雷同的這種現狀,必須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特色去設計創造我們的城市,利用具有鄉土化特色的景觀來裝飾我們的城市空間,只有這樣我們的生活環境才能更加舒適。對于小城鎮規劃建設過程中的運用,將鄉土景觀與小城鎮建設規劃相結合,沈雷洪描述了鄉土景觀的四大特點分別是:實際功用性、多樣性、文化意義、時代性與社會性,并討論了鄉土景觀所具有的景觀、社會、經濟、生態、科研、教育等價值對建設有中國特色小城鎮的重要意義;在鄉土景觀元素與現代園林的結合運用方面,孫新旺的《鄉土與園林―鄉土景觀元素在園林中的運用》一文中,他依據不同的表現形態,將鄉土景觀元素歸納為:鄉土的“物”、鄉土的“事”和鄉土的“意”3類,并探討了鄉土景觀元素在園林創作中的運用,分別提煉出不同類型鄉土景觀元素的表達方法;住區設計對鄉土景觀的運用方面,曾慶華與彭重華在《鄉土景觀設計特征對居住區景觀限額設計的啟示》中也提到了鄉土景觀設計是“百姓的設計”,其特征能為居住區景觀限額設計帶來許多啟示,例如空間上追求人性化尺度和親和感、設計元素以綠色、土為主體、材料選擇上扎根于地域性、場地性等。
每一個學術研究必須要有自己的理論學科為基礎,也需要其他外部學科多視角研究,理論到實踐的終點就是達到應用路徑層面,任何一個本體學科無法完全支撐起整個學科學術研究,但是本體學科必須擁有本體學科自有的基礎理論研究,才能使本學科更好的發展及相關外部學科之間有更好的融會貫通。
4 整合與重構――鄉土景觀研究存在問題以及展望
如上所述,鄉土景觀的研究并不是某單一學科就能夠解決的,它在地理學、景觀生態學、建筑學、風景園林學、城市規劃等學科的基礎上進行多學科、多角度綜合研究,其研究目前還處于初級探索階段,有很大的發展研究空間。目前,鄉土景觀還沒有一套完整的理論研究體系,其系統性的研究還是相對落后,相應的理論研究體系有待完善;鄉土景觀在創作上仍然處于摸索前行的狀態,許多相關設計給世人展現出驚喜的同時仍舊存在許多紕漏,考慮到視覺沖擊的同時,對景觀營造帶來的某些不和諧因素沒有得到很好的調和。
因此,準確的理解國內鄉土景觀并發展鄉土景觀,這對于探尋一種適合我國實際情況的建設模式有很重要的推動作用,只有這樣,才能使其得以可持續發展,使我們明天的生活環境更加美好。對于鄉土景觀的研究的任務是任重而道遠,這對于更多的設計者來說是最基礎最具有意義的研究,對于其未來的研究展望有如下幾點:一、將鄉土景觀的研究不要僅僅作為景觀設計師的研究使命,更是設計相關行業工作者的使命;二、政府的政策支持與民間組織的支持,政策支持主要是政策文件實施以及資金方面,民間組織主要是指民眾中非設計者的參與與呼吁;三、完善的法規體系和科學的管理是最大保障。相信在越來越多致力于鄉土景觀研究的學者們共同努力下,鄉土景觀營造在設計領域和學術領域都將取得可喜的成果。在將來的研究中,應針對各個地區不同的地域資源進行鄉土景觀的調查和分析,來實現鄉土景觀在多個領域的運用,更多的是如何保護現擁有的鄉土景觀資源,以便讓我們的生活充滿更多的鄉土氣息,讓我們的生活多一些自然的味道。
參考文獻:
[1] 俞孔堅.王志芳.黃國平.論鄉土景觀及其對現代景觀設計的意義 [J]. 建筑,2005/04,第23卷.
[2] 項紅梅.宋立.初寶順.鄉土景觀的國內研究狀況. [J]. 中國園藝文摘.2010/01.
[3] 俞孔堅.李偉.《續唱之歌―白話的城市與白話的景觀》[J].建筑學報. 2004/08. [5] 俞孔堅.《關于防止新農村建設可能帶來的破壞、鄉土文化景觀保護和工業遺產保護的三個建議》.中國園林[J].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