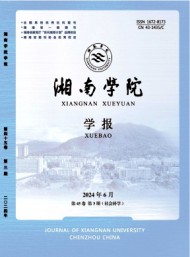軟組織腫瘤范文
時(shí)間:2023-03-23 10:31:40
導(dǎo)語(yǔ):如何才能寫(xiě)好一篇軟組織腫瘤,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xiàn),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患者,男,46歲,主因右側(cè)大腿腫瘤切除術(shù)后4個(gè)月腫瘤復(fù)發(fā)于2007年5月9日入院。患者于2007年1月因右側(cè)大腿惡性纖維組織細(xì)胞瘤復(fù)發(fā)在外院行腫瘤切除術(shù),術(shù)后4個(gè)月發(fā)現(xiàn)腫瘤再次復(fù)發(fā)來(lái)我院就診,為行手術(shù)治療而入院。患者2001年5月因發(fā)現(xiàn)右臀部包塊伴右下肢疼痛、麻木3個(gè)月余在北京某醫(yī)院就診,B超檢查示右臀大肌深層5cm×8cm大小實(shí)性腫物,術(shù)前診斷為“神經(jīng)纖維瘤”,行腫瘤局部切除術(shù),術(shù)后病理診斷為惡性纖維組織細(xì)胞瘤。2002年4月因腫瘤復(fù)發(fā)再次手術(shù),此后2003年1月、2003年12月、2004年10月、2005年8月、2006年4月、2006年12月均因腫瘤復(fù)發(fā)在該醫(yī)院行手術(shù)治療,共計(jì)8次。
入院查體:一般狀況可,心、肺、腹部未見(jiàn)明顯異常。右側(cè)大腿近端可見(jiàn)結(jié)節(jié)狀腫物,由會(huì)延伸至臀部,大小約8cm×12cm,表面皮膚水腫明顯,質(zhì)硬,壓痛明顯,活動(dòng)差,肢體遠(yuǎn)端輕度腫脹,感覺(jué)、血運(yùn)、活動(dòng)正常(見(jiàn)圖1)。
入院診斷:右側(cè)大腿惡性纖維組織細(xì)胞瘤術(shù)后復(fù)發(fā)。
輔助檢查:常規(guī)化驗(yàn)檢查未見(jiàn)明顯異常;肺CT掃描未見(jiàn)異常;骨盆及右股骨X線(xiàn)未見(jiàn)骨質(zhì)破壞。MRI示右側(cè)大腿近端腫瘤(見(jiàn)圖2)。
治療經(jīng)過(guò):入院后行術(shù)前化療兩個(gè)周期,2007年6月20日在全麻下行腫瘤廣泛切除(見(jiàn)圖3),局部皮瓣轉(zhuǎn)移修復(fù)術(shù),術(shù)后傷口一期愈合。擬于術(shù)后3周開(kāi)始行放、化療,患者拒絕后續(xù)治療而離院。2008年6月因雙肺多發(fā)轉(zhuǎn)移瘤死亡。
評(píng)析
本例為何會(huì)發(fā)生誤診?
該患者術(shù)前診斷為神經(jīng)纖維瘤,是一種常見(jiàn)的軟組織良性腫瘤,通過(guò)局部切除可治愈。術(shù)后病理診斷為惡性纖維組織細(xì)胞瘤,屬于發(fā)病率較高的軟組織惡性腫瘤(即軟組織肉瘤),惡性程度高,治療需行腫瘤廣泛切除,切除不徹底易復(fù)發(fā),晚期可發(fā)生遠(yuǎn)隔臟器轉(zhuǎn)移而危及生命。
分析此例誤診原因:
首先從發(fā)病率來(lái)講,原發(fā)軟組織腫瘤良、惡性之比>100:1,臨床中常見(jiàn)到的軟組織腫瘤多為良性(如脂肪瘤);此外,成人軟組織肉瘤的發(fā)病率隨年齡增長(zhǎng)而增加,平均發(fā)病年齡為65歲,該患者初診時(shí)年齡僅40歲。
從臨床表現(xiàn)來(lái)看,在3個(gè)月內(nèi)腫瘤大小變化不明顯,不具有常見(jiàn)惡性腫瘤生長(zhǎng)迅速的特點(diǎn),腫瘤位于坐骨神經(jīng)走行區(qū),良性腫瘤也可引起肢體疼痛、麻木等壓迫癥狀。
術(shù)前B超檢查示臀大肌深層5cm×8cm大小實(shí)性腫物,包膜完整,與周?chē)M織界限清楚,影像學(xué)檢查未見(jiàn)惡性腫瘤特異性表現(xiàn)。
回顧分析該病例術(shù)前有哪些惡性腫瘤的特征?
主要有兩點(diǎn):生長(zhǎng)部位與腫瘤最大直徑。據(jù)統(tǒng)計(jì),軟組織良性腫瘤99%生長(zhǎng)位置表淺,最大直徑5cm的表淺軟組織腫瘤和所有位置深在的腫瘤中,惡性腫瘤的可能性約為10%。
如何提高軟組織腫瘤良惡性的鑒別診斷能力?
簡(jiǎn)單講就是遵循臨床――影像――病理三結(jié)合的原則。仔細(xì)詢(xún)問(wèn)病史,認(rèn)真查體,根據(jù)腫瘤生長(zhǎng)部位、大小、邊界、活動(dòng)度、質(zhì)地、有無(wú)壓痛等做出初步定性。良性腫瘤多生長(zhǎng)緩慢,界限清楚,有良好活動(dòng)度;而惡性腫瘤往往生長(zhǎng)迅速或短時(shí)間內(nèi)變化較快,除位置表淺者可有一定活動(dòng)度外,多數(shù)界限不清,活動(dòng)度差。
軟組織腫瘤的影像學(xué)檢查,B超簡(jiǎn)便易行,能提供腫瘤的大小、囊實(shí)性、包膜及與相鄰組織器官的關(guān)系等信息,可在基層醫(yī)院進(jìn)行,但對(duì)腫瘤的定性診斷幫助有限。
核磁共振(MRI)檢查可準(zhǔn)確判定腫瘤大小、多個(gè)層面的腫瘤及其與周?chē)∪狻⒔钅ぁ⒐呛蜕窠?jīng)血管的關(guān)系,提供水腫、出血、壞死等情況,是軟組織腫瘤首選影像學(xué)檢查方法。
螺旋CT掃描不受氣體組織界面和活動(dòng)假象的影響,適于檢查胸腔和腹腔的軟組織腫瘤。良性軟組織腫瘤不需要活檢,如果腫瘤直徑>5cm或生長(zhǎng)位置較深(筋膜下),根據(jù)臨床表現(xiàn)不能做出單一而準(zhǔn)確的臨床診斷或影像學(xué)檢查提示腫瘤呈侵襲性生長(zhǎng),不論腫瘤大小、生長(zhǎng)部位如何,都應(yīng)行病灶活檢明確病理診斷。本例初診未進(jìn)行活檢就進(jìn)行手術(shù),是應(yīng)該汲取的教訓(xùn)。
軟組織肉瘤被誤診為良性腫瘤進(jìn)行了切除該如何處理?
如果術(shù)后病理檢查所有手術(shù)切緣均無(wú)腫瘤殘留,腫瘤組織學(xué)分級(jí)為低級(jí)別腫瘤,可進(jìn)行密切隨診,組織學(xué)分級(jí)為高級(jí)別腫瘤,可行放射治療,對(duì)化療敏感的腫瘤還可行輔助化療;如果術(shù)后病理檢查提示手術(shù)切緣有腫瘤殘留,應(yīng)毫不猶豫地盡早再次手術(shù)行腫瘤廣泛切除,當(dāng)不具備治療條件時(shí)應(yīng)及時(shí)將患者轉(zhuǎn)往專(zhuān)業(yè)的腫瘤中心進(jìn)行治療。
結(jié)合本病例在軟組織腫瘤的診治過(guò)程中應(yīng)注意哪幾方面?
軟組織腫瘤臨床表現(xiàn)復(fù)雜,部分惡性腫瘤的臨床表現(xiàn)以及影像學(xué)檢查常缺乏特異性,易發(fā)生誤診誤治,治療前應(yīng)明確腫瘤性質(zhì),必要時(shí)行活檢。
生長(zhǎng)緩慢,直徑
篇2
何種情況下不用活檢
臨床物理檢查和影像學(xué)都支持確診為良性腫瘤者不用活檢。如脂肪瘤、神經(jīng)鞘瘤等。這些腫瘤相對(duì)表淺、體積較小,宜行切除,如皮下脂肪瘤患者,物理檢查和核磁能基本確定診斷,則可行切除手術(shù),術(shù)后送病理,以進(jìn)一步明確診斷(見(jiàn)圖1)。
何種情況下不能活檢
比較明確不能進(jìn)行活檢的腫瘤就是黑色素細(xì)胞瘤,因?yàn)榭赡艽碳ず蟪霈F(xiàn)惡變或轉(zhuǎn)移(見(jiàn)圖2)。對(duì)于該腫瘤直接擴(kuò)大切除,術(shù)后病理證實(shí)如為惡性,應(yīng)進(jìn)一步放療。
何種情況下需要活檢
在物理檢查和影像學(xué)檢查完成后不能確定性質(zhì)及高度疑診為惡性腫瘤者。
活檢的分類(lèi)
病理活檢的方式通常分為切除活檢、穿刺活檢、切開(kāi)活檢,不同部位不同性質(zhì)的腫瘤應(yīng)采取不同的活檢方式。
切除活檢
對(duì)于不能確定性質(zhì)、體積又較小的腫瘤,可以直接切除活檢,切除時(shí)以擴(kuò)大切除術(shù)為宜,這樣既能達(dá)到診斷的目的,同時(shí)又能達(dá)到治療的目的。術(shù)后注意病理結(jié)果及腫瘤邊緣切除是否徹底,有無(wú)殘留。切除活檢應(yīng)當(dāng)掌握嚴(yán)格的適應(yīng)證,錯(cuò)誤的切除活檢可能會(huì)導(dǎo)致腫瘤擴(kuò)散、惡性腫瘤未能擴(kuò)大切除、切除范圍不夠等不良后果(見(jiàn)圖3)。
切除活檢的另一種適應(yīng)證是腫瘤生長(zhǎng)于人體關(guān)鍵部位,如不切除會(huì)對(duì)人體重要功能構(gòu)成嚴(yán)重?fù)p害。如椎管內(nèi)腫瘤,已有明顯神經(jīng)根壓迫癥狀,如雙下肢感覺(jué)運(yùn)動(dòng)障礙及二便失禁等。此時(shí)無(wú)論腫瘤為何種性質(zhì),均應(yīng)及時(shí)切除及椎管減壓。術(shù)中宜盡量徹底清除病灶,并將切除組織送病理活檢,以明確診斷(見(jiàn)圖4)。
穿刺活檢
穿刺活檢的優(yōu)點(diǎn)是簡(jiǎn)單、快速,感染或血腫的危險(xiǎn)小,是臨床上常用的另一病理活檢方法。穿刺活檢的并發(fā)癥包括針道感染、血管神經(jīng)束損傷、血腫及針道污染。穿刺針道應(yīng)在隨后的腫瘤切除手術(shù)中一并切除。
穿刺活檢適用于位置較深而解剖結(jié)構(gòu)較復(fù)雜的腫瘤,以明確診斷。對(duì)于骨髓源性的腫瘤(如多發(fā)性骨髓瘤),骨髓穿刺活檢更具有重要價(jià)值。臨床上常用穿刺活檢的方式是從髂骨或胸骨穿刺獲取病理組織,證實(shí)腫瘤的病理組織、細(xì)胞分化的程度,為確診提供依據(jù)。其他骨與軟組織腫瘤多用骨活檢穿刺針進(jìn)行活檢,當(dāng)腫瘤病變較小、位置較深時(shí),可在X線(xiàn)或CT的引導(dǎo)下進(jìn)行穿刺。堅(jiān)硬的骨病變需要能夠切割骨組織的環(huán)鉆,這樣形成的骨窗為圓形,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骨折。而細(xì)胞成分高的腫瘤、骨髓腫瘤、轉(zhuǎn)移癌等應(yīng)加用病灶抽吸的方法(見(jiàn)圖5)。
切開(kāi)活檢
切開(kāi)活檢是臨床上常用的另一種病理活檢方式,主要用于腫瘤位置較深、體積較大、無(wú)法完整切除、或穿刺活檢不易獲取有價(jià)值的病理組織時(shí)。對(duì)于深在的巨大腫瘤,行腫瘤部分切除,送病理活檢對(duì)明確腫瘤的良惡性質(zhì)、細(xì)胞分化程度、以決定手術(shù)的方式有重要價(jià)值。如果已有廣泛轉(zhuǎn)移的腫瘤,需要病理證據(jù),也可以切開(kāi)活檢。
篇3
【關(guān)鍵詞】腔室;軟組織肉瘤;惡性腫瘤; 保肢手術(shù);屏障切除術(shù);
【Abstract】Objective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soft tissue malignant tumor resection of the chamber, curative effect and clinical value.Methods Chamber on soft tissue malignant tumor resection of the clinical data of 20 patients, all follow-up, the clinical data of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ere analyzed retrospectively study, judg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operation and clinical popularization value. Results 20 cases of application of chamber resection in patients with malignant tumor of soft tissue, 19 cases of postoperative recurrence, local recurrence rate was 5%, the limb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normal. Conclusion For limb soft tissue malignant tumor, chamber resection is a more ideal method at present.
【key words 】compartment;soft tissue sarcoma(STS);Malignant tumor; extremity retention operation ;barrier resection;
【中圖分類(lèi)號(hào)】R738.6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B【文章編號(hào)】1004-4949(2014)04-0162-01
軟組織惡性腫瘤(肉瘤)系一組間葉細(xì)胞起源、具有不同臨床病理特征和生物學(xué)行為,極罕見(jiàn)的異質(zhì)性實(shí)體瘤的總稱(chēng)。起源于粘液、纖維、脂肪、平滑肌、橫紋肌等具有不同解剖學(xué)及病理學(xué)特點(diǎn)的源于胚胎期的間葉組織以及外周神經(jīng)系統(tǒng)腫瘤。在成人的惡性腫瘤中肉瘤大約占1% ,而在兒童約占15%。國(guó)內(nèi)資料統(tǒng)計(jì)發(fā)病率為1.1~2.0/10萬(wàn),呈逐年上升趨勢(shì) [1-4]。因此提高肢體軟組織肉瘤的治療水平有重要意義。
腫瘤切除徹底與否是四肢惡性軟組織腫瘤保肢治療的前提。局部復(fù)發(fā)率與切除范圍有直接關(guān)系[5],70 年代Simon等提出了間室切除的理論,張如明等依據(jù)致密結(jié)締組織具有屏障作用并綜合廣泛切除和根治性切除術(shù)的優(yōu)點(diǎn)提出了屏障切除術(shù)的概念即腔室概念[6]。我們通過(guò)對(duì)以往大量文獻(xiàn)報(bào)道的回顧性研究,說(shuō)明在治療四肢軟組織惡性腫瘤,腔室切除術(shù)是目前較理想的方法。
1臨床資料
1987年以來(lái),我院對(duì)軟組織惡性腫瘤進(jìn)行腔室切除術(shù)20例患者臨床資料。其中纖維肉瘤7例、平滑肌肉瘤6例、惡性纖維組織細(xì)胞瘤(MFH)4例、皮膚隆突性纖維肉瘤1例、橫紋肌肉瘤1例、滑膜肉瘤1例。首次發(fā)病15例,外院手術(shù)后復(fù)發(fā)后于我院再次治療病例5例。腫瘤直徑>5cm 者8例,
2方法
首先考慮腫瘤的位置,與腔室單位的關(guān)系,并遵循如下幾項(xiàng)原則:
2.1按生物的天然屏障,即沿著肌肉的解剖間隙切除,縱行方向切除超過(guò)一束肌肉的起、止點(diǎn),橫向范圍分離需超過(guò)病變周?chē)慕钅ぃ_(dá)到無(wú)瘤切緣的目的。
2.2在無(wú)生物天然屏障側(cè),四周的切緣距瘤緣為3-5cm,這種“距離”也是一種屏障[6]。3~5 cm切緣,是按照肉瘤生長(zhǎng)特點(diǎn)設(shè)計(jì)的。 形成一腫瘤周?chē)娜S切除范圍。
2.3術(shù)中切緣的再確認(rèn),如為陽(yáng)性,在有天然屏障側(cè),再切除相臨近的一個(gè)腔室單位,如為無(wú)生物天然屏障側(cè),則向切緣周?chē)贁U(kuò)大3-5cm范圍。這樣的切除范圍是相對(duì)徹底的。
2.4盡量保留肢體的功能,最大恢復(fù)受損的肢體功能,縫合皮膚。
2.5對(duì)于巨大創(chuàng)面的,原則是采用包括皮片移植、各種組織瓣、皮瓣、肌皮瓣及肌腱的轉(zhuǎn)位或著移植。
3結(jié) 果
20例應(yīng)用腔室切除術(shù)的軟組織惡性腫瘤患者中,19例術(shù)后無(wú)復(fù)發(fā),局部復(fù)發(fā)率5%,20例中1例失訪(fǎng),來(lái)診時(shí)5例為外院手術(shù)后復(fù)發(fā),經(jīng)2次手術(shù)后4例局部無(wú)復(fù)發(fā)超5年,1例(左顳纖維肉瘤)二次手術(shù)后未滿(mǎn)5年,失訪(fǎng)1例及左顳部神經(jīng)纖維肉瘤1例均視為未超過(guò)5年生存,故超過(guò)5年生存者共18例,5年生產(chǎn)率為90%。患者肢體功能基本正常。
4討 論
腫瘤治療的根本目的;(1)延長(zhǎng)病人的生存期(2)控制局部復(fù)發(fā)率(3)提高病人的生活質(zhì)量 延長(zhǎng)病人的生存期將是治療腫瘤的關(guān)鍵。截肢治療軟組織惡性腫瘤并不能提高病人的存活率,相反的對(duì)病人生理的破壞及心理上的打擊是十分嚴(yán)重的[7-9]。
腔室切除術(shù)從解剖學(xué)層面保證了陰性的腫瘤切緣,進(jìn)一步減少局部復(fù)發(fā)而延長(zhǎng)生存期。解剖腔室的概念――它是對(duì)軟組織惡性腫瘤擴(kuò)散的良好的人體天然屏障。比如肌肉周?chē)纳罱钅ぁ⒓‰臁㈦炷ぁ㈨g帶、關(guān)節(jié)囊和骨膜等。并附著于相應(yīng)骨骼的起止點(diǎn)形成骨筋膜室,互不相通,形成獨(dú)立的間室(腔室)[10-11]。 對(duì)腫瘤有一定的約束作用,我們將此類(lèi)結(jié)構(gòu)連同肉瘤全部切除,可視為局部根治性切除。無(wú)屏障側(cè),在腫瘤周?chē)?-5cm的正常組織間切除腫瘤,這種距離也可視為屏障。在長(zhǎng)骨,這一屏障是骨皮質(zhì)和關(guān)節(jié)的軟組織。在軟組織,這一屏障則是大的筋膜腔室和肌腱的起止點(diǎn)。
軟組織肉瘤見(jiàn)于全身任何部位,肢體占半數(shù)以上(以下肢較多),其他依次為軀干、腹膜后間隙(各占30%)、泌尿生殖系、上肢和頭頸部,極少數(shù)發(fā)生于內(nèi)臟器官[12]。
常見(jiàn)的軟組織肉瘤好發(fā)部位多集中于四肢,所以說(shuō),四肢軟組織肉瘤在保肢與截肢之間的選擇上就顯得尤為重要。除了肉瘤巨大,肢體功能不能恢復(fù)者;或侵犯了骨骼、及主要神經(jīng)、血管,或局部有嚴(yán)重感染,壞死及放射損傷嚴(yán)重者外,一般不主張截肢。外科治愈也可以通過(guò)對(duì)原發(fā)灶肉瘤的完整切除而達(dá)到目的,腔室切除后進(jìn)行形態(tài)修復(fù)和功能重建,常可避免截肢,減少截肢手術(shù)的發(fā)生。切緣恰當(dāng)與否,將是唯一與局部復(fù)發(fā)有關(guān)的易變量。切除的范圍與局部復(fù)發(fā)有極為重要的關(guān)系。
從理論上說(shuō),軟組織惡性腫瘤手術(shù)范圍應(yīng)該達(dá)到根治性切除的要求,但在實(shí)際中是保肢手術(shù)的切緣大多也只能達(dá)到廣泛切除的要求,甚至也僅僅是邊緣切除,而后者極有可能進(jìn)入腫瘤的反應(yīng)區(qū)。
盡管近30年來(lái)許多機(jī)構(gòu)和學(xué)者以對(duì)骨與軟組織肉瘤治療進(jìn)行了不懈的努力,但臨床結(jié)果卻有很大差異。其具體原因(1)軟組織肉瘤的分期系統(tǒng)較多,普遍缺乏統(tǒng)一性;(2)軟組織肉瘤的處理很不統(tǒng)一;多數(shù)軟組織肉瘤第一次處理在基層醫(yī)院,首診醫(yī)生往往缺乏經(jīng)驗(yàn)。也有一些專(zhuān)科醫(yī)生考慮到廣泛切除腫瘤后軟組織修復(fù)的困難,常進(jìn)入病灶內(nèi)切除腫瘤,首次手術(shù)切除范圍不夠,延誤病情,影響療效。
對(duì)于高度惡性肉瘤的手術(shù)的目的是切除盡可能多的腫瘤組織以達(dá)到治愈結(jié)果,并切除盡可能少的正常組織以保持其肢體功能。所有的報(bào)道均發(fā)現(xiàn)截肢的治愈率比保肢的治愈率高,但沒(méi)有統(tǒng)計(jì)學(xué)顯著差異。多數(shù)研究發(fā)現(xiàn)肉瘤截肢治療后局部復(fù)發(fā)率為1% ~3%。
對(duì)于四肢軟組織惡性腫瘤,以控制腫瘤及保存機(jī)體為治療核心,腔室切除術(shù)是目前較理想的方法。盡管施行腔室切除術(shù)的保肢病人局部復(fù)發(fā)率輕度升高,但和截肢病人具有相同的存活率。采用局部的根治性腔室切除術(shù)保留肢體治療與采用截肢方法治療,其局部復(fù)發(fā)率差異并無(wú)顯著性意義。腫瘤局部復(fù)發(fā)傾向與腫瘤組織類(lèi)型無(wú)關(guān),與腫瘤組織學(xué)分級(jí)及腫瘤體積大小有直接關(guān)系。而最重要的是病人保存了肢體功能及形態(tài),沒(méi)有了截肢病人在生存質(zhì)量上出現(xiàn)的痛苦。這說(shuō)明了保肢手術(shù)的優(yōu)勢(shì)。腔室切除術(shù)在治療軟組織惡性腫瘤的諸多方法中替代截肢術(shù)并取得同樣的治療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 Lin PP , Guzel VB , Plsters PW, et al . Surgical management of soft tissuee sarco-mas of the hand and foot [J ] . J Cancer , 2002 ;95 (4) :852~61
[2] 秦風(fēng)展, 陳振東, 樊青霞, 等. 腫瘤內(nèi)科治療學(xué). 第1版. 北京: 人民軍醫(yī)出版社, 2004: 717.
[3] Christopher DM. Pathology and genetics of tulnors of soft tissueand bone[M]. Lyon: IARC Press, 2002: 12 - 15.
[4] Jemal A, Siegel R,Ward E, et al. Cancer Statistics, 2007 [J]. CA Cancer J Clin,2007, 57 (1) : 43 - 66.
[5] 牛曉輝,李遠(yuǎn). 肢體軟組織肉瘤的外科治療[J]. 中國(guó)實(shí)用外科雜志, 2007;27(4):322 - 325
[6] 張如明 ,張琥 ,滕勝 ,衛(wèi)曉恩 ,劉印文 ,談繹文 ,孫駿,邢汝維,張瑾.屏障切除術(shù)治療復(fù)發(fā)性軟組織肉瘤的療效分析[J].中華腫瘤防治雜志2007; 14 (6): 450 451
[7] Johnstone PA,Wexler LH, Venzon DJ, et al. Sarcomas of thehand and foot: analysis of local control and functional resultwith combined modality therapy in extremity p reservation [ J ].Int J Radiat Oncol Biol Phys, 1994, 29 (4) : 735 - 745.
[8] Gould SW, Agarwal T , Benoist S , et al . Resection of soft tissue sarcomas with intra - operative magnetic resonance guidance [J] . J MagnReson Imaging , 2002 ;15 (1) :114~9
[9] Tsuchiya H, Tomita K,Mori Y, et al. Marginal excision for osteosarcoma with caffine assisted chemotherapy. Clin Orthop, 1999, 358:27 - 35.
[10] Hoos A, Lewis JJ, Brennan MF. Soft tissue sarcoma: p rognosticfactors and multimodal treatment[ J ]. Chirurg, 2000, 71 ( 7) : 787- 794.
篇4
[關(guān)鍵詞] 負(fù)壓封閉引流;擠壓傷;急性腎損傷;膿毒癥;感染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R64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673-7210(2015)08(a)-0067-04
Effect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on treating severe crush injury of limbs soft tissue
YANG Wei1 LIU Yang2 ZHAO Mingyan1
1.Department of ICU,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 150001, China; 2.Department of Orthopedic,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Heilongjiang Province,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VSD) on treating severe crush injury of limbs soft tissue. Methods From October 2012 to October 2014, in 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Harbin Medical University, 62 Gustilo Ⅲ crush injured patients were chosen and divided into observed group (n = 35) and control group (n = 27), according to using VSD or dressing change after debridement. After debridement, the observed group was installed VSD, the control group was used dressing change 1-2 times/d. With the positive therapy, all the patients were detected including white blood cell count (WBC), concentration of serum K+, levels of serum creatinine (Scr) and urea nitrogen (BUN), and urine protein quantity. The rates of complication were observed including acute kidney injury (AKI), systemic inflammatory response syndrome (SIRS), sepsis and multiple organ dysfunction syndrome (MODS), and both groups were calculated the mortality. At discharge, wound closure time, times of blood purification, hospital stays and ratio of amputation were measured as prognostic index. Results WBC [(13.25±3.16)×109/L], serum K+ [(5.04±1.07) mmol/L], Scr [(163.43±53.27) μmol/L], BUN [(6.92±2.61) mmol/L] and urine protein [(2.09±0.83) scores] in the observed group were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WBC: (18.63±4.58)×109/L, serum K+: (5.93±1.42) mmol/L, Scr: (334.56±109.82) μmol/L, BUN: (10.35±3.48) mmol/L, urine protein: (2.67±1.12) scores],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The rates of complication AKF (42.9%), SIRS (60.0%), sepsis (48.6%), MODS (11.4%) in observed group were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70.4%, 85.2%, 77.8%, 33.3%),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Wound closure time [(14.26±4.32) d], times of blood purification [(6.28±3.69) times] and hospital stays [(27.38±6.75) d] in the observed group were less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19.73±5.47) d, (8.74±4.23) times, (35.49±10.18) 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However, the rates of mortality (2.86%) and amputation (11.1%) in observed group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in control group (5.9%, 16.7%), the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technique of VSD can reduce the absorption of hazardous material after soft tissue injury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systemic toxemic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Key words]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Crush injury; Acute kidney injury; Sepsis; Infection
隨著工業(yè)文明的不斷進(jìn)步,交通事故、建筑意外以及大型機(jī)械碾壓等使軟組織擠壓傷的發(fā)病率逐年增高。軟組織擠壓傷常伴有開(kāi)放性骨折,除造成局部組織感染、壞死外,組織溶解及壞死物質(zhì)的吸收還會(huì)導(dǎo)致全身多器官功能障礙[1],包括急性腎損傷(AKI)、膿毒癥、全身炎癥反應(yīng)綜合征(SIRS)以及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MODS)等,嚴(yán)重威脅患者的生命安全。負(fù)壓封閉引流術(shù)(VSD)是近年來(lái)廣泛用于控制感染的外科引流技術(shù)[2],但對(duì)于應(yīng)用VSD技術(shù)在軟組織擠壓傷后清除壞死組織,減輕全身中毒癥狀的報(bào)道較少。為此,本研究選取哈爾濱醫(yī)科大學(xué)附屬第一醫(yī)院(以下簡(jiǎn)稱(chēng)“我院”)收治的四肢軟組織擠壓傷患者,清創(chuàng)后行VSD引流,觀(guān)察其對(duì)全身中毒癥狀的改善作用,取得滿(mǎn)意療效,現(xiàn)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2012年10月~2014年10月收治的四肢Gustilo Ⅲ型軟組織擠壓傷患者62例。根據(jù)清創(chuàng)術(shù)后選擇VSD引流或常規(guī)換藥治療分為觀(guān)察組(35例)和對(duì)照組(27例)。兩組年齡、性別等一般資料比較,差異均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具有可比性。見(jiàn)表1。本研究經(jīng)醫(yī)院醫(yī)學(xué)倫理委員會(huì)批準(zhǔn),所有患者和/或家屬均知情同意并簽署知情同意書(shū)。
納入標(biāo)準(zhǔn):①診斷明確的四肢擠壓傷外傷史;②受傷至清創(chuàng)開(kāi)始時(shí)在6 h以?xún)?nèi);③軟組織損傷Gustilo Ⅲ型[3],即皮膚、皮下組織和肌肉的廣泛損傷,合并或不合并重要血管神經(jīng)的損傷;④患者年齡>18周歲。排除標(biāo)準(zhǔn):①伴有致死性合并傷,包括顱腦外傷、頸脊髓損傷以及重要的內(nèi)臟器官損傷;②既往有周?chē)懿∽儯虎酆喜⑻悄虿 ⒓卓旱葍?nèi)分泌系統(tǒng)疾病;④伴有腎小球腎炎、尿毒癥等泌尿系統(tǒng)疾病;⑤伴有凝血功能異常的血液系統(tǒng)疾病。
1.2 治療方法
1.2.1 手術(shù)治療 入院時(shí)出現(xiàn)休克患者積極抗休克治療,待休克糾正后給予清創(chuàng)術(shù),無(wú)休克患者急診行清創(chuàng)術(shù)。術(shù)中由淺至深,切除污染和失去活力的皮膚、皮下組織、筋膜、肌肉,對(duì)于肌腱、血管、神經(jīng)盡量予以保留,避免遺漏死角和無(wú)效腔。骨折端根據(jù)患者情況給予外固定架固定或鋼板內(nèi)固定,清創(chuàng)結(jié)束后再次用生理鹽水、3%過(guò)氧化氫溶液及0.1%活力碘清洗傷口。對(duì)照組患者清創(chuàng)術(shù)后選擇常規(guī)換藥治療,觀(guān)察組患者清創(chuàng)術(shù)后選擇VSD治療。對(duì)照組患者用骨折周?chē)浗M織覆蓋骨折處,傷口敞開(kāi),用無(wú)菌敷料濕敷,術(shù)后根據(jù)傷口情況每日換藥1~2次。觀(guān)察組患者應(yīng)用VSD技術(shù),將明膠泡沫剪成與創(chuàng)腔相同形狀,略大于創(chuàng)腔,確保充分填入,避免留有空隙,兩根硅膠引流管從正常皮膚處穿出,并用4-0縫合線(xiàn)固定,創(chuàng)口用生物半透膜覆蓋。接通負(fù)壓-125~-450 mmHg(1 mmHg = 0.133 kPa),觀(guān)察到明膠癟陷,半透膜下液體被迅速抽走為負(fù)壓有效標(biāo)志。VSD每周期為5~7 d,到期后取出VSD,根據(jù)肉芽生長(zhǎng)狀況決定更換VSD或行皮瓣轉(zhuǎn)移術(shù)閉合傷口。兩組患者中對(duì)于局部傷口感染難以控制,雖經(jīng)積極治療但全身狀況仍不斷惡化者,采用截肢術(shù)根除感染灶。
1.2.2 全身治療 術(shù)后除對(duì)受傷部位行局部治療外,還進(jìn)行積極的全身治療,包括:①根據(jù)組織液的藥敏檢查結(jié)果全身應(yīng)用敏感抗生素;②脫水、利尿減輕患肢腫脹;③維持水、電解質(zhì)、酸堿平衡;④堿化尿液,保護(hù)腎功能,積極應(yīng)用血液凈化腎臟替代治療;⑤合理的營(yíng)養(yǎng)支持治療。
1.3 觀(guān)察指標(biāo)
1.3.1 實(shí)驗(yàn)室檢測(cè)指標(biāo) 兩組患者均在術(shù)后48 h抽取靜脈血,檢測(cè)白細(xì)胞(WBC)計(jì)數(shù),鉀離子(K+)濃度,血肌酐(Scr)、尿素氮(BUN)水平。留取尿液通過(guò)半定量方法,以(-)、(±)、(1+)、(2+)、(3+)表示尿蛋白水平,分別記為0、1、2、3、4分。
1.3.2 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及病死率 術(shù)后觀(guān)察患者并發(fā)AKF、SIRS、膿毒癥及MODS的比率,并計(jì)算患者病死率。AKI采用2005年急性腎損傷網(wǎng)絡(luò)(AKIN)診斷標(biāo)準(zhǔn)[4]:48 h內(nèi)Scr升高≥26.5 μmol/L,或Scr達(dá)到基線(xiàn)水平的1.5倍,或6 h尿量持續(xù)
1.3.3 預(yù)后指標(biāo) 患者出院時(shí)統(tǒng)計(jì)患者清創(chuàng)術(shù)至二期皮瓣轉(zhuǎn)移術(shù)閉合傷口時(shí)間,住院時(shí)間,血液凈化次數(shù),以及截肢率。截肢率=(組內(nèi)截肢例數(shù)/組內(nèi)患者數(shù))×100%。
1.4 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應(yīng)用SPSS 20.0統(tǒng)計(jì)軟件對(duì)結(jié)果進(jìn)行分析,正態(tài)分布計(jì)量資料以均數(shù)±標(biāo)準(zhǔn)差(x±s)表示,兩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yàn);計(jì)數(shù)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yàn)。以P
2 結(jié)果
2.1 兩組實(shí)驗(yàn)室檢測(cè)指標(biāo)比較
兩組實(shí)驗(yàn)室檢測(cè)指標(biāo)比較,觀(guān)察組WBC計(jì)數(shù)、血清K+濃度、Scr、BUN及尿蛋白水平均優(yōu)于對(duì)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見(jiàn)表2。
表2 兩組實(shí)驗(yàn)室檢測(cè)指標(biāo)比較(x±s)
注:WBC:白細(xì)胞計(jì)數(shù);K+:鉀離子;Scr:血肌酐;BUN:血尿素氮
2.2 兩組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及病死率比較
兩組并發(fā)癥及病死率比較,觀(guān)察組AKF、SIRS、膿毒癥及MODS的發(fā)生率均低于對(duì)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兩組病死率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見(jiàn)表3。
表3 兩組并發(fā)癥發(fā)生率及病死率比較[n(%)]
注:AKF:急性腎損傷,SIRS:全身炎癥反應(yīng)綜合征,MODS: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
2.3兩組預(yù)后指標(biāo)比較
兩組因患者死亡,共4例脫落,其中觀(guān)察組1例和對(duì)照組3例。兩組預(yù)后指標(biāo)比較,觀(guān)察組傷口閉合時(shí)間、血液凈化次數(shù)及住院天數(shù)均優(yōu)于對(duì)照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兩組截肢率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見(jiàn)表4。
表4 兩組預(yù)后指標(biāo)比較(x±s)
3 討論
隨著軟組織擠壓傷發(fā)病率的上升,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對(duì)擠壓傷所致全身病理生理變化的研究也不斷深入。軟組織擠壓傷后,局部組織因缺血缺氧發(fā)生壞死,致壓物解除后缺血再灌注損傷導(dǎo)致局部橫紋肌溶解,使得局部有害物質(zhì)進(jìn)入血液循環(huán),患者出現(xiàn)以高鉀血癥、代謝性酸中毒為主要表現(xiàn)的水電失衡,同時(shí)出現(xiàn)肌紅蛋白尿、氮質(zhì)血癥等急性腎衰竭表現(xiàn),甚至發(fā)展為MODS,臨床上稱(chēng)之為擠壓綜合征[6]。有研究表明[7],雖然軟組織擠壓傷發(fā)展為擠壓綜合征的概率僅為10%,但導(dǎo)致急性腎衰竭的概率高達(dá)50%。本研究中AKF的發(fā)生率明顯高于50%,可能與研究對(duì)象均為Gustilo Ⅲ型重度軟組織損傷有關(guān)。因此,軟組織擠壓傷后維持內(nèi)環(huán)境的穩(wěn)態(tài)成為亟待解決的問(wèn)題。
VSD技術(shù)是近年來(lái)用于控制外科感染的重要方法之一,其主要作用是通過(guò)灌洗清除局部代謝產(chǎn)物,利用半透膜提供一個(gè)密閉空間,使得肉芽組織盡快在明膠泡沫周?chē)L(zhǎng),降低二次感染率[8]。對(duì)于軟組織擠壓傷,VSD除能控制局部感染外,還能持續(xù)清除局部壞死組織。國(guó)外研究表明[9],在軟組織損傷后,即使行擴(kuò)大清創(chuàng)術(shù),術(shù)后局部壞死產(chǎn)物也會(huì)增多,這是由于缺血再灌注后氧化應(yīng)激所致的遲發(fā)型組織損傷,在清創(chuàng)術(shù)后正常組織還會(huì)發(fā)生壞死或者凋亡。因此,即使對(duì)局部進(jìn)行徹底清創(chuàng),術(shù)后單純換藥治療仍難以降低毒素的吸收,局部的好轉(zhuǎn)并不能改善全身多器官的惡化[10]。本研究結(jié)果分析,觀(guān)察組術(shù)后血鉀濃度和氮質(zhì)血癥程度均較對(duì)照組有所降低(P < 0.05),說(shuō)明了VSD技術(shù)能夠通過(guò)持續(xù)清除局部壞死物質(zhì)從而降低毒素的吸收,改善全身中毒癥狀。這與林武[11]應(yīng)用VSD治療骨筋膜室綜合征的報(bào)道結(jié)果相一致。
根據(jù)SCCM/ESICM指南標(biāo)準(zhǔn),SIRS、膿毒癥、MODS是序貫發(fā)生的病理過(guò)程。由于SIRS的診斷標(biāo)準(zhǔn)比較寬泛,因此從結(jié)果看兩組SIRS的發(fā)病率均較高,但近年來(lái)普遍認(rèn)為SIRS并不是單一疾病,而是一種病理狀態(tài)用于判斷疾病的嚴(yán)重程度[12-13],兩組SIRS的高發(fā)病率也提示在臨床中對(duì)于嚴(yán)重?cái)D壓傷患者應(yīng)早期由重癥監(jiān)護(hù)病房(ICU)進(jìn)行觀(guān)察和治療。膿毒癥的治療原則是控制感染灶和全身支持治療[14-16]。本研究中在局部應(yīng)用VSD治療的同時(shí)積極應(yīng)用血液凈化治療,在術(shù)后48 h即將血鉀降至正常水平,并且由膿毒癥發(fā)展為MODS的比率明顯降低,說(shuō)明了血液凈化治療在改善全身中毒癥狀中的重要作用。在控制感染方面,除根據(jù)細(xì)菌培養(yǎng)和藥敏結(jié)果選用敏感抗生素外,還要注意VSD半透膜可能形成的局部缺氧環(huán)境,防止厭氧菌感染[17-20]。兩組患者病死率和截肢率比較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 0.05),可能與樣本量較少有關(guān),尚需擴(kuò)大樣本量進(jìn)一步研究。
綜上所述,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能夠有效降低軟組織損傷后局部有害物質(zhì)的吸收,減輕全身中毒癥狀,提高治療效果。
[參考文獻(xiàn)]
[1] 楊帆.物理負(fù)壓促進(jìn)創(chuàng)面愈合機(jī)制的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xué),2010.
[2] Wang J,Zhang H,Wang S. Application of vacuum sealing drainage in the treatment of internal fixation instrument exposure after early postoperative infection [J]. Minerva Chir,2015,70(1):17-22.
[3] Fochtmann A,Mittlb?ick M,Binder H,et al. Potential prognostic factors predicting secondary amputation in third-degree open lower limb fractures [J]. J Trauma Acute Care Surg,2014,76(4):1076-1081.
[4] Strametz R,Pachler C,Kramer JF,et al. Laryngeal mask airway versus endotracheal tube for percutaneous dilatational tracheostomy in critically illpatients [J]. Cochrane Database Syst Rev,2014,6:CD009901.
[5] 岳金鳳,吳大瑋,李琛,等.以急性腎損傷網(wǎng)絡(luò)標(biāo)準(zhǔn)評(píng)估重癥監(jiān)護(hù)病房患者急性腎損傷的發(fā)病率、預(yù)后及死亡相關(guān)危險(xiǎn)因素[J].中華醫(yī)學(xué)雜志,2011,91(4):260-264.
篇5
關(guān)鍵詞: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皮膚軟組織缺損;骨髓炎
骨髓炎為一種骨的感染和破壞,可由需氧或厭氧菌、分歧桿菌等病菌引起,其可導(dǎo)致多種并發(fā)癥的發(fā)生,包括畸形、關(guān)節(jié)強(qiáng)直甚至癌變等,而對(duì)于其治療如何盡快修復(fù)創(chuàng)面、防止感染破壞等是臨床治療的重點(diǎn)。我院近年來(lái)應(yīng)用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VSD)治療伴皮膚軟組織缺損的嚴(yán)重骨髓炎患者取得了較為滿(mǎn)意效果,現(xiàn)報(bào)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我院在2012年1月~2014年1月收治的伴皮膚軟組織缺損的嚴(yán)重骨髓炎患者60例,所有患者均符合《實(shí)用骨科學(xué)》中相關(guān)診斷標(biāo)準(zhǔn),并排除伴有嚴(yán)重心肝腎功能損害以及合并敗血癥、糖尿病等患者。將所有患者隨機(jī)分為兩組,觀(guān)察組和對(duì)照組,各30例,觀(guān)察組男性21例,女性9例,年齡27~68歲,平均年齡(40.8±6.3)歲,損傷部位:(損傷部位以脛骨為主要,其次為股骨,指骨可刪除,可增加跟骨)股骨11例,脛骨9例,指骨6例,橈骨4例,皮膚缺損面積6×10~25×30cm2,平均面積為15×20cm2;對(duì)照組男性22例,女性8例,年齡23~64歲,平均年齡(39.1±5.7),損傷部位:股骨15例,脛骨18例,指骨5例,橈骨5例,皮膚缺損面積5cm×10cm~26cm×30cm,平均面積為14cm×21cm;兩組患者一般資料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1.2.1觀(guān)察組應(yīng)用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VSD)治療。具體方法:首先給予患者創(chuàng)面徹底清創(chuàng)處理,(按照骨髓炎手術(shù)原則常規(guī)處理)并常規(guī)止血、保護(hù)神經(jīng)血管,然后按照患者創(chuàng)面大小和形狀修剪醫(yī)用泡沫,將修剪好的材料內(nèi)鉆孔,引入引流管,把帶有引流管的醫(yī)用泡沫填充入創(chuàng)面,而后接通負(fù)壓引流裝置,調(diào)至負(fù)壓至200mmHg,見(jiàn)填入的醫(yī)用泡沫塊明顯塌陷,薄膜下午液體積聚,證實(shí)負(fù)壓有效,并檢查有無(wú)漏氣,7~10d后根據(jù)引流情況拔出引流或更換VSD敷料,并根據(jù)創(chuàng)面肉芽生殖情況行植皮或組織瓣移植術(shù)。
1.2.2對(duì)照組(按照骨髓炎手術(shù)原則常規(guī)處理)給予常規(guī)換藥治療。根據(jù)創(chuàng)面情況1~2d更換一次敷料,較大創(chuàng)面放置引流條引流,(手術(shù)前)并同時(shí)行細(xì)菌培養(yǎng),根據(jù)細(xì)菌培養(yǎng)結(jié)果選用針對(duì)性抗生素給予抗感染治療。
1.3觀(guān)察指標(biāo)對(duì)兩組患者治療后創(chuàng)面縮小程度、換藥次數(shù)、植皮時(shí)間以及植皮愈合時(shí)間進(jìn)行觀(guān)察比較。
1.4療效判定標(biāo)準(zhǔn) 優(yōu):傷口一期愈合,X線(xiàn)檢查髓腔清晰;良:傷口有少許滲液,經(jīng)數(shù)次換藥后愈合,X線(xiàn)檢查髓腔較治療前明顯好轉(zhuǎn);中:傷口有滲液,經(jīng)數(shù)次換藥后愈合,X線(xiàn)檢查髓腔較治療前有所改善;差:傷口滲液較多,經(jīng)換藥治療效果無(wú)改善。
1.5統(tǒng)計(jì)學(xué)方法 應(yīng)用SPSS16.0統(tǒng)計(jì)分析資料,計(jì)量資料采用x±s表示,比較應(yīng)用t檢驗(yàn);計(jì)數(shù)資料比較應(yīng)用χ2檢驗(yàn);以P
2 結(jié)果
2.1觀(guān)察指標(biāo)比較 對(duì)兩組患者創(chuàng)面縮小程度、換藥次數(shù)、植皮時(shí)間以及植皮愈合時(shí)間的比較,觀(guān)察組均明顯小于對(duì)照組,且差異具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2.2療效比較 觀(guān)察組和對(duì)照組優(yōu)良率分別為93.3%、76.7%,兩組比較,觀(guān)察組優(yōu)良率明顯大于對(duì)照組(P
3 討論
骨髓炎感染常由血源性微生物引起,或從感染組織擴(kuò)散而來(lái),包括置換關(guān)節(jié)感染、污染性骨折以及骨手術(shù)等,臨床上常反復(fù)發(fā)作,并嚴(yán)重影響患者的身心和勞動(dòng)能力。對(duì)于伴有皮膚軟組織缺損的嚴(yán)重骨髓炎患者除全身使用抗生素以抗感染外,消滅死腔,促進(jìn)肉芽組織生長(zhǎng),提高植皮存活率是治療的重點(diǎn)[1]。
臨床傳統(tǒng)的方法是在徹底清創(chuàng)后給予常規(guī)換藥,該治療方法不僅會(huì)導(dǎo)致患者劇烈疼痛,同時(shí)易出現(xiàn)引流不暢,病原體清創(chuàng)不徹底,嚴(yán)重影響創(chuàng)面愈合。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VSD)可使整個(gè)創(chuàng)面處于一個(gè)全封閉的負(fù)壓引流狀態(tài),有效減少了創(chuàng)面和環(huán)境的接觸面積,從而降低了感染的幾率[2],且關(guān)鍵在于VSD可有效、及時(shí)的清除創(chuàng)面內(nèi)的滲出液和膿液,醫(yī)用泡沫的可塑性,可充分覆蓋創(chuàng)面,并使引流物經(jīng)泡沫材料與引流管隔開(kāi),避免死腔形成,保證引流通暢[3]。負(fù)壓引流是此項(xiàng)技術(shù)的關(guān)鍵,首先其可快速清除引流區(qū)內(nèi)的滲出物和壞死組織,防止感染的擴(kuò)散,同時(shí)持續(xù)負(fù)壓引流利于局部微循環(huán)環(huán)境的改善,促進(jìn)組織水腫的消退,刺激肉芽組織生長(zhǎng),加速創(chuàng)面愈合[4]。從本組研究結(jié)果可以看出,給予VSD治療的觀(guān)察組其在促進(jìn)創(chuàng)面縮小程度、減少換藥次數(shù)、縮短植皮時(shí)間以及植皮愈合時(shí)間方面均明顯優(yōu)于常規(guī)換藥的對(duì)照組(P
總之,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在伴有皮膚軟組織缺損的嚴(yán)重骨髓炎患者的治療中效果顯著,對(duì)快速促進(jìn)創(chuàng)面愈合,提高植皮成功率具有顯著作用,值得臨床推廣應(yīng)用。
參考文獻(xiàn):
[1]李曉輝,苑青和,賀紹民,等.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治療感染性骨不連伴皮膚軟組織缺損[J]骨科,2011,12(4):195-196.
[2]林陽(yáng),陳安民,李鋒.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在四肢皮膚軟組織缺損中的應(yīng)用[J]生物骨科材料與臨床研究,2007,4(4):212-214.
[3]劉偉娟,周翔.創(chuàng)面負(fù)壓封閉引流技術(shù)治療皮膚軟組織缺損的護(hù)理體會(huì)[J]護(hù)理雜志,2010,12(19):1476-1477.
篇6
[關(guān)鍵詞] 乳突切除術(shù);耳后壁重建;膽脂瘤中耳炎
[中圖分類(lèi)號(hào)] R764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 A [文章編號(hào)] 1674-0742(2017)02(b)-0001-03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value of soft tissue posterior canal wall reconstruction and tympanoplasty for patients with cholesteatoma of middle ear. Methods Convenient selection 97 cases of patients with cholesteatoma of middle ear from February 2010 to August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treatment plans, the group A with 40 cases adopted the Open radical mastoidectomy, while the group B adopted the classic improved wall mastoidectomy, and the group C with 27 cases adopted the open mastoidectomy, and the different in the cur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The recurrence of cholesteatoma in the group A was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at in the group B(3 cases vs 7 cases), and the difference ha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P0.05), and the hearing improvement rate and average dry ear rate in the group A were obviously better than those in the group C(P
[Key words] Mastoidectomy; Posterior canal wall reconstruction; Otitis media with cholesteatoma
在臨床中,多數(shù)膽脂瘤型中耳炎病癥常因骨性外耳道后壁不完整,或者病變侵犯范圍擴(kuò)大而采用完壁式乳突切除術(shù)醫(yī)治,但無(wú)法將病灶處全部予以清除[1]。現(xiàn)發(fā)現(xiàn)利用顳肌骨膜瓣轉(zhuǎn)移外耳道后壁重建技術(shù)以及鼓室重建技術(shù)[2]治療中耳膽脂瘤病癥已然取得臨床認(rèn)可。為分析中耳膽脂瘤患者使用軟組織耳道后壁重建與鼓室成形術(shù)治療的有效性,現(xiàn)將該院2010年2月―2016年8月收治的97例患者作分組試驗(yàn),給予不同術(shù)式療法,現(xiàn)報(bào)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全組97例中耳膽脂瘤患者均方便選自于該院收治的患者,經(jīng)術(shù)中探查均證實(shí)膽脂瘤型中耳炎。其中男女比例59∶38,年齡介于13~69歲,年齡均值(36.5±12.7)歲;根據(jù)治療方式的差異性將其分組如下:A組:共40例,病變范圍較為廣泛而經(jīng)開(kāi)放式乳突根治術(shù)后,利用顳肌骨膜瓣轉(zhuǎn)移外耳道后壁重建術(shù)+鼓室成形術(shù);鼓室成形術(shù)類(lèi)型:I型者10例,Ⅱ型者28例,Ⅲ型者2例。B組:30例,采用經(jīng)典完壁式乳突切除術(shù)鼓室成形術(shù)醫(yī)治;鼓室形術(shù)種類(lèi):I型14例,Ⅱ型12例,Ⅲ型4例。C組:27例,本組均接受開(kāi)放式乳突根治術(shù),不給予鼓室成形術(shù)。
1.2 治療方案
A組(40例):顳肌骨膜瓣轉(zhuǎn)移外耳道后壁重建術(shù)+鼓室成形術(shù)移植方案。該組患者均由麻醉師行全麻,待全麻插管誘導(dǎo)麻醉成功后,取耳后為開(kāi)口,將皮膚和皮下組織迅速分離開(kāi)來(lái);實(shí)施蒂位經(jīng)耳道后壁U型顳肌骨膜瓣操作,將瓣長(zhǎng)設(shè)定為2.0 cm,寬保持約為1.5 cm。將乳突拉鉤操作保證手術(shù)視野清晰,慎重地將外耳道后壁以及上壁皮瓣完全剝離,盡量保持其完整性;后采用磨鉆將上鼓室外側(cè)壁處以及骨性外耳道后壁,乳突均切除,斷橋;經(jīng)顯微鏡協(xié)助下明確病灶處并切除,對(duì)聽(tīng)骨鏈連接及活動(dòng)性探查,將咽鼓管探通后并對(duì)神經(jīng)骨管的檢測(cè),輪廓化乳突術(shù)腔。全組病患均于一側(cè)顳肌筋膜采取夾層法或內(nèi)植法予以鼓膜修補(bǔ);其中針對(duì)34例聽(tīng)骨部分不完整者,采用自體聽(tīng)骨或者假體聽(tīng)骨將骨鏈重建。于術(shù)中參照術(shù)腔和鼓竇口的大小,選取對(duì)應(yīng)的硅膠管將乳突術(shù)腔放入,將其做為支架和引流管可從耳后開(kāi)口引出。緩慢地將耳后帶蒂顳肌骨膜瓣移動(dòng)到原骨性外耳道后壁處;并和移植的顳肌筋膜的后緣側(cè)相接通;采用硅膠管予以支持乳突術(shù)腔,復(fù)原耳道后壁全部的筒狀皮瓣后,于耳道內(nèi)填充碘仿砂條;術(shù)腔支架引流管可在術(shù)后21 d拔除。B組(30例病患):經(jīng)典完壁式乳突切除術(shù)鼓室成形術(shù)方案。該組病患均取顳肌筋膜采用夾層法或者內(nèi)植法骨膜修復(fù)醫(yī)治;其中14例均選用自體聽(tīng)骨或者軟骨重建聽(tīng)骨鏈醫(yī)治;經(jīng)耳后切口予以依次縫合;于術(shù)后48 h可將乳突術(shù)腔置引流管取出。C組(27例):該組患者均接受開(kāi)放式乳突根治術(shù)式,于術(shù)后行換藥醫(yī)治,直到術(shù)腔上皮化出現(xiàn)。
1.3 觀(guān)察指標(biāo)
對(duì)3組醫(yī)治前后的術(shù)后聽(tīng)力改善比例,術(shù)后干耳的平均時(shí)間情況,術(shù)后干耳發(fā)生率,膽脂瘤復(fù)發(fā)率等詳細(xì)地統(tǒng)計(jì)在案,同時(shí)對(duì)術(shù)后外耳道功能恢復(fù)的情況予以評(píng)定。
1.3.1 聽(tīng)力改善評(píng)定 參照WHO制定的聽(tīng)力改善評(píng)定標(biāo)準(zhǔn)[3],取術(shù)后6個(gè)月內(nèi)的500 Hz、1 000、2 000 Hz等3個(gè)頻率的平均值:①氣導(dǎo)提出高需超過(guò)15 dB以上者;②氣道水平不低于40 dB,而氣導(dǎo)聽(tīng)力提高應(yīng)不低于10 dB;③骨氣導(dǎo)差不低于20 dB,氣導(dǎo)聽(tīng)力提升不低于10 dB。以上所述,任一項(xiàng)滿(mǎn)足即為聽(tīng)力改善。
1.3.2 外耳道術(shù)后結(jié)構(gòu)和功能良好判定 ①干耳現(xiàn)象;②外耳道具有自?xún)艄δ埽葱杳块g隔2~3個(gè)月前來(lái)檢查可觀(guān)耳道未有成團(tuán)角化上皮,僅有少量的片狀耵聹屑存在,鼓膜較光亮,耳道呈干燥;③耳道未有死角,且呈光滑[4]。
1.3.3 復(fù)發(fā)評(píng)估 經(jīng)隨訪(fǎng)1~5年后,針對(duì)患者的臨床表現(xiàn)以及影像學(xué)檢測(cè),電子而鏡等了解患者遠(yuǎn)期治療情況。
1.4 統(tǒng)計(jì)方法
利用SPSS 20.0統(tǒng)計(jì)學(xué)軟件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信息,計(jì)數(shù)資料用[n(%)]表示,行χ2檢驗(yàn),計(jì)量資料用(x±s)表示,行t檢驗(yàn),P
2 結(jié)果
該次研究結(jié)果顯示,A組40例,37例于g后20 d將引流管拔除,予以引流管口縫合,乳突腔閉合;6例因術(shù)腔支撐架較大均于29 d后予以耳后切口將其取出,同時(shí)予以術(shù)腔探查,未有復(fù)況;可觀(guān)術(shù)腔部分黏膜化現(xiàn)象,后關(guān)閉切口。經(jīng)隨診1~5年,耳道后壁未有顯著的后陷情況,耳道呈現(xiàn)較寬;圓滑且無(wú)盲角,耳道具有正常的自?xún)艄δ埽瑑H觀(guān)察到些許的片狀耵聹屑,且骨膜正常,聽(tīng)力不受影響。且A組的膽脂瘤復(fù)發(fā)率顯著低于B組,其他指標(biāo)均相當(dāng),差異無(wú)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0.05);而在聽(tīng)力改善率以及平均干耳天數(shù)[平均干耳天數(shù)A組為(38.2±8.1)d,B組為(41.5±7.8)d、C組為(87.9±9.9)d]方面,A組顯著優(yōu)于C組,兩組差異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P
3 討論
隨著臨床醫(yī)學(xué)的進(jìn)步,開(kāi)放式和完壁式乳突根治術(shù)的局限性逐漸浮現(xiàn)。乳突切除術(shù)式當(dāng)前醫(yī)治中耳膽脂瘤的首選方法,其重在將病灶清除而取得干耳為醫(yī)治重點(diǎn)。對(duì)病變范圍廣以及氣化差,咽鼓管功能有礙的膽脂瘤病患采用開(kāi)放式乳突根治術(shù)難以清除病灶,且術(shù)后可導(dǎo)致遺留耳后壁損害,同時(shí)對(duì)寬大腔需定期處理,以免降低聽(tīng)力[5]。現(xiàn)隨著臨床技術(shù)的優(yōu)化,現(xiàn)聯(lián)合鼓室成形術(shù),可將骨性缺外耳道后壁以及上鼓室外壁保持完整,并能保持原有外耳道的形態(tài)和鼓室容積,經(jīng)中耳構(gòu)造重建的基礎(chǔ)上可提高聽(tīng)力;但是該術(shù)式的膽脂瘤復(fù)發(fā)率極高[6]。
該組研究中發(fā)現(xiàn),A組的膽脂瘤復(fù)發(fā)7.5%顯著低于B組23.3%(P0.05);但A組聽(tīng)力改善率,平均干耳率顯著高于C組。提示對(duì)中耳膽脂瘤患者采用軟組織耳道后壁重建與鼓室成形術(shù)的療效可觀(guān),可清除病灶,提高術(shù)后聽(tīng)力等優(yōu)勢(shì)[7-8]。在臨床中實(shí)施骨性耳后壁重建后以及自體皮質(zhì)骨上鼓室再次重建亦可取得顯效效果,但該治療方案時(shí)常有以下難以突[9]:其一,采用VASE方法,術(shù)中難以獲得合理的骨片,于鑿骨時(shí),稍有不慎將會(huì)造成面神經(jīng)骨折;其二,再利用自體髂骨骨質(zhì)予以外耳道骨壁和上鼓室外側(cè)壁重建時(shí)[10-11],其操作可將創(chuàng)傷范圍擴(kuò)大,并增大經(jīng)碎骨片于耳后壁原被去除部位的操作的難度。且經(jīng)耳道填塞時(shí),極易發(fā)生因擠壓而發(fā)生脫落和移動(dòng)現(xiàn)象。若耳道后壁皮膚位置較薄時(shí),將其覆蓋在缺損的骨架位置,仍會(huì)觀(guān)察到耳道壁后有缺陷情況。經(jīng)朱忠壽等人[12]研究3組的膽脂瘤復(fù)發(fā)率分別為4.4%、22.2%、0.0%,聽(tīng)力改善率分別為75.6%、77.8%、9.1%,與該次研究結(jié)果相近。
而該組應(yīng)用帶蒂顳肌膜瓣重創(chuàng)建耳道外壁術(shù)式,可獲得頗高療效;另外其U型帶蒂的肌骨膜瓣能夠供給優(yōu)質(zhì)的血供,有助于術(shù)后存活,且肌肉和骨膜組織可將耳后壁原有皮瓣顯著增加,且不易發(fā)生耳后壁塌陷情況。故在操作中應(yīng)將肌骨膜瓣的帶蒂適量留寬,防止發(fā)生轉(zhuǎn)移肌骨膜瓣吸收萎縮情況;同時(shí)可于周?chē)筌浗M織轉(zhuǎn)移,獲取骨片較易;合理的肌骨膜更能保證轉(zhuǎn)移直到深部,繼而使缺損范圍得以復(fù)原。此外,于術(shù)后采用的乳突術(shù)腔引流管主要承擔(dān)著支撐的作用,經(jīng)重建的耳后壁不會(huì)因外耳道填充壓迫而移動(dòng)塌陷,且對(duì)術(shù)后乳突腔和耳道后壁具有極高的塑形功能,修復(fù)鼓室和乳突容積,排出鼓室和乳突術(shù)腔內(nèi)的滲出異物,還能灌注藥水,達(dá)到對(duì)咽鼓管疏通之效。
綜上所述,中耳膽脂瘤患者采用軟組織耳道后壁重建和鼓室成形術(shù)治療,可清除病灶組織,快速恢復(fù)外耳道功能,提高聽(tīng)力,該醫(yī)治方案具有可行性。
[參考文獻(xiàn)]
[1] 朱曉丹.370例慢性化膿性中耳炎及中耳膽脂瘤患者面神經(jīng)情況分析[D].鄭州:鄭州大學(xué),2014:22-23.
[2] 陳雪生,王威,陶靜,尹安平.耳后多種自體中胚層軟組織及皮質(zhì)骨粉填充乳突修復(fù)耳道后壁在開(kāi)放式手術(shù)中的臨床應(yīng)用[J].山東大學(xué)耳鼻喉眼學(xué)報(bào),2014(5):18-22.
[3] 陳雪生,陶靜,尹安平,等.開(kāi)放式鼓室成形術(shù)中耳道成形與手術(shù)療效的相關(guān)性探討[J].中國(guó)眼耳鼻喉科雜志,2014,10(6):374-378.
[4] 張德軍.改良完壁式乳突切開(kāi)鼓室成形術(shù)治療中耳膽脂瘤[D].長(zhǎng)春:吉林大學(xué),2012:29-30.
[5] 汪普.完壁式及開(kāi)放式乳突切開(kāi)I期鼓室成形術(shù)評(píng)價(jià)分析[D].杭州:浙江大學(xué),2015:16-19.
[6] 楊名保,趙海亮,柴福,等.乳突開(kāi)放術(shù)后自體骨粉填塞重建外耳道后壁的臨床觀(guān)察[J].中國(guó)耳鼻咽喉顱底外科雜志,2015(6):478-482.
[7] 雪生,陶靜,王威,等.開(kāi)放式手術(shù)耳后多種自體中胚層組織填充乳突修復(fù)耳道后壁的臨床效果觀(guān)察[J].疑難病雜志,2014,20(12):1275-1278,1282.
[8] 李冬影,白玉,張海川.開(kāi)放式與完壁式鼓室成形伴聽(tīng)骨鏈重建術(shù)后效果對(duì)比分析[J].中國(guó)耳鼻咽喉顱底外科雜志,2013(4):357-359.
[9] Hardie Elizabeth M,Linder Keith E,Pease Anthony P.Aural cholesteatoma in twenty dogs[J].Veterinary Surgery,2009:378.
[10] 宋昱,馬芙蓉.完壁式乳突根治鼓室成形術(shù)的發(fā)展及應(yīng)用[J].中國(guó)微創(chuàng)外科雜志,2015,15(8):755-758.
[11] 陳杰,楊燁,顧亞軍,等.完壁式乳突切開(kāi)鼓室成形治療膽脂瘤型中耳炎的臨床分析[J]. 中國(guó)醫(yī)藥指南,2014(28):94-95.
篇7
關(guān)鍵詞 鼻腔腫瘤;CT診斷;病理診斷
鼻腔腫瘤臨床診斷一般較為容易,但若并存感染或出血時(shí),診斷有一定困難。鼻腔鏡檢查只能了解腫瘤的表面情況,而CT掃描不但能顯示鼻腔軟組織腫塊的范圍,并能明確其鄰近組織結(jié)構(gòu)、骨骼以及副鼻竇是否受侵等。筆者回顧分析了我院1990~1996年經(jīng)病理證實(shí)的55例鼻腔腫瘤,現(xiàn)總結(jié)如下。
1.1 一般資料:本組55例,其中男33例,女22例。年齡10~73歲,平均32歲、臨床主要表現(xiàn)為鼻塞、血性分泌物、鼻衄,其次為頭昏,頭痛、鼻部隆起及面頰部疼痛,突眼及視力下降等。病程自1個(gè)月至3年不等。有鼻部手術(shù)史5例,其中2例曾進(jìn)行過(guò)兩次手術(shù),1例作過(guò)3次手術(shù)。
l.2 手術(shù)及病理診斷:55例中經(jīng)手術(shù)及病理證實(shí)41例,活檢病理證實(shí)14例。全組中良性腫瘤25例,惡性腫瘤30例。其中良性腫瘤:纖維血管瘤15例,狀瘤6例,骨化性纖維瘤2例,內(nèi)翻狀瘤及腦膜瘤各1例;惡性腫瘤中鱗狀細(xì)胞癌10例,淋巴瘤、及惡性肉芽腫各4例,腺癌3例,未分化癌、腺樣囊性癌及神經(jīng)母細(xì)胞瘤各2例,透明細(xì)胞癌、惡性血管內(nèi)皮瘤及胚胎性橫紋肌肉瘤各1例。
1.3 方法:全部病例檢查均采用島律 3000TE全身CT機(jī)。病人仰臥位,下頷內(nèi)收,于硬腭平面上頜骨齒槽突開(kāi)始,平行于眶耳線(xiàn),以層厚5mm,層距5mm向上連續(xù)掃描至眶底止。部分病例加鼻腔冠狀位掃描以及增強(qiáng)掃描。
2 結(jié)果
本組病例CT掃描,經(jīng)病理證實(shí)為良性腫瘤25例,所有病例一側(cè)(6例雙側(cè))鼻腔見(jiàn)有軟組織腫塊,腫塊邊緣多數(shù)光滑清楚。25例中有10例鼻腔有膨脹性改變,鼻中隔向?qū)?cè)移位,12例患者合并同側(cè)副鼻竇炎癥,表現(xiàn)為上頜竇或(和)篩竇密度增高,但其密度一般較鼻腔腫塊密度稍低,3例病變向鼻咽部蔓延;6例向篩竇蔓延;1例侵犯眶尖并引起突眼,4例引起周?chē)琴|(zhì)破壞。30例惡性腫瘤中,全部見(jiàn)有鼻腔軟組織腫塊,腫塊邊緣大多不規(guī)則或模糊,除4例沒(méi)有骨質(zhì)破壞外,其余都有骨質(zhì)破壞。18例侵犯上頜竇或(和)篩竇,6例面額部及翼腭窩見(jiàn)軟組腫塊,3例侵犯眼眶并引起突眼。
3 討 論
3.1 本組術(shù)前CT診斷有5例誤診,25例良性腫瘤中有2例誤診為惡性腫瘤,其中纖維血管瘤及內(nèi)翻狀瘤各1例,這2例均可見(jiàn)骨質(zhì)破壞。1例鼻腔鱗狀細(xì)胞癌誤診為良性腫瘤,患者早期僅表現(xiàn)為鼻后腔軟組織塊影,無(wú)骨質(zhì)破壞,術(shù)后病理證實(shí)為鱗癌,術(shù)后 3個(gè)月該病人復(fù)發(fā), CT表現(xiàn)為病變廣泛侵犯周?chē)M織及引起骨質(zhì)破壞。另外,淋巴瘤及惡性肉芽腫各有1例,由于均無(wú)骨質(zhì)破壞而誤診為良性腫瘤。
3.2 通過(guò)對(duì)本組55例鼻腔腫瘤的CT分析,筆者認(rèn)為鼻腔良惡性腫瘤的區(qū)別主要有以下幾個(gè)特點(diǎn):①良性腫瘤表現(xiàn)為腫塊呈膨脹性生長(zhǎng),可壓迫周?chē)潜冢贡乔粩U(kuò)大或產(chǎn)生壓迫性骨質(zhì)缺損;惡性腫瘤則呈浸潤(rùn)性生長(zhǎng),可直接侵蝕破壞周?chē)墙Y(jié)構(gòu);②良性腫瘤表現(xiàn)為病變邊緣光滑,與周?chē)Y(jié)構(gòu)分界清楚;而惡性腫瘤表現(xiàn)為病變邊緣模糊,與周?chē)Y(jié)構(gòu)分界不清;③良性腫瘤一般不侵犯腔外軟組織,而惡性腫瘤常侵犯腔外軟組織。本組病例顯示有腔外軟組織受侵的均為惡性腫瘤,與王煥申等報(bào)告相符。對(duì)于良性腫瘤與惡性腫瘤均可出現(xiàn)“骨質(zhì)破壞”,則應(yīng)特別強(qiáng)調(diào)破壞方式的重要性。Som把CT上所見(jiàn)到的骨質(zhì)破壞分為侵入性骨質(zhì)破壞和骨改建,認(rèn)為這樣有助于良惡性腫瘤的鑒別。在侵入性骨質(zhì)破壞中骨骼很快被侵蝕和破壞,提示腫瘤生長(zhǎng)快;多見(jiàn)于惡性腫瘤。本組大多數(shù)惡性腫瘤均呈侵入性骨破壞;骨改建反映腫瘤在緩慢生長(zhǎng)過(guò)程中,在鄰近腫瘤的骨內(nèi)被侵蝕的同時(shí),在骨外面又有新骨形成,結(jié)果形成了骨骼被腫瘤推移或繞腫瘤形成弓形,這種表現(xiàn)常見(jiàn)于良性腫瘤。本組4例良性腫瘤所引起的骨質(zhì)破壞均為骨改建后骨破壞,與文獻(xiàn)報(bào)道相符。
3.3 內(nèi)翻狀瘤:內(nèi)翻狀瘤是鼻和鼻竇少見(jiàn)的上皮腫瘤,多見(jiàn)于中鼻甲和中鼻道外側(cè)壁,易侵犯同側(cè)上頜竇和篩竇。切除術(shù)后30%~60%復(fù)發(fā),有5%~15%惡變,內(nèi)翻狀瘤和鱗癌可同時(shí)存在。CT表現(xiàn):鼻腔和同側(cè)上頜竇見(jiàn)軟組織塊影,晚期可波及雙側(cè)和鄰近組織,骨質(zhì)破壞以上頷竇內(nèi)側(cè)壁為主,晚期可有廣泛破壞;鼻腔擴(kuò)大多不明顯,腫瘤內(nèi)可見(jiàn)點(diǎn)狀、條狀鈣化。本組1例CT表現(xiàn)左鼻腔和左上頜竇軟組織塊影,左上頜竇內(nèi)側(cè)壁骨質(zhì)破壞,腫瘤內(nèi)見(jiàn)斑點(diǎn)狀及弧形鈣化。由于對(duì)該病認(rèn)識(shí)不足,曾誤診為惡性腫瘤。本例曾作過(guò)3次手術(shù)。
篇8
13例骨巨細(xì)胞瘤發(fā)病部位:脊柱4例均累及單個(gè)椎體,2例誤診為椎體結(jié)核,1例誤診為神經(jīng)源性腫瘤,1例誤診為骨髓瘤;其余9例均為單側(cè)發(fā)病,發(fā)生在髂骨3例,恥骨2例,跟骨2例,坐骨及下頜骨各1例,誤診為骨囊腫4例,動(dòng)脈瘤樣骨囊腫3例,嗜酸性肉芽腫1例,轉(zhuǎn)移瘤1例。
1.1X線(xiàn)表現(xiàn):病變邊緣清楚的8例,呈膨脹樣破壞,皂泡樣改變較典型,偏心性表現(xiàn)不明顯,破壞區(qū)有少量分隔,病灶周?chē)瞧べ|(zhì)變薄,邊緣無(wú)硬化。邊緣欠清的囊狀骨破壞透亮區(qū)5例,其中周?chē)?jiàn)鉆孔樣改變者3例,周?chē)浗M織間隙模糊。累及脊柱者其中2例椎體附件骨質(zhì)破壞,3例椎體破壞呈楔形改變。
1.2CT表現(xiàn):7例患者中,髂骨2例,恥骨2例,脊柱2例,下頜骨1例,CT表現(xiàn)均為骨質(zhì)膨脹性破壞,主要為囊性或不均勻的軟組織密度影,CT值為20~65Hu,其中4例可見(jiàn)骨性分隔,可以顯示出病灶邊緣的骨質(zhì)硬化。2例脊椎腫瘤僅表現(xiàn)為溶骨性骨質(zhì)破壞,椎體附件及椎間盤(pán)無(wú)破壞;發(fā)生在髂骨者周?chē)浗M織可見(jiàn)腫塊,脂肪間隙模糊,1例位于髂骨者腫瘤實(shí)性成分居多,軟組織腫塊較大,誤診為轉(zhuǎn)移瘤。
1.3MR征象:6例行MRI檢查,脊柱2例、骨盆2例、跟骨2例。病變呈囊狀膨脹性改變,在T1WI呈均勻低信號(hào)或中等信號(hào),在T2WI表現(xiàn)為高信號(hào)或混雜的中等及較高信號(hào),部分可見(jiàn)分隔,表現(xiàn)為典型的鵝卵石征。發(fā)生于脊椎者病變信號(hào)相對(duì)均勻,本組病例均累及1個(gè)椎體,不同程度呈楔形改變,邊界較為清楚,2例合并軟組織腫塊,其中1例腫瘤偏惡性,實(shí)性部分居多,表現(xiàn)為T(mén)1加權(quán)像上的不規(guī)則狀軟組織信號(hào)影,椎管及椎間盤(pán)受累及,增強(qiáng)掃描后病變明顯為不均勻明顯強(qiáng)化信號(hào)。2.4右側(cè)髂骨骨巨細(xì)胞瘤影像學(xué)表現(xiàn)。
2討論
骨巨細(xì)胞瘤是臨床上常見(jiàn)的骨腫瘤,好發(fā)年齡為20~40歲的青壯年,無(wú)明顯性別差異。腫瘤組織來(lái)源不明,主要成分為多核巨細(xì)胞和梭形間質(zhì)細(xì)胞,多數(shù)學(xué)者認(rèn)為,該腫瘤起源于單核基質(zhì)細(xì)胞,而非巨細(xì)胞本身[2]。病理上將骨巨細(xì)胞瘤分為3級(jí):Ⅰ級(jí)為良性,Ⅱ級(jí)為侵襲性即生長(zhǎng)活躍的骨巨細(xì)胞瘤,Ⅲ級(jí)為惡性或惡變,惡性骨巨細(xì)胞瘤又稱(chēng)為骨巨細(xì)胞肉瘤[3]。常規(guī)通過(guò)X線(xiàn)可對(duì)發(fā)生于股骨下端及脛骨上端的骨巨細(xì)胞瘤進(jìn)行初步診斷,但是對(duì)于發(fā)生在其他不規(guī)則骨的骨巨細(xì)胞瘤由于組織相互重疊,且周?chē)M織結(jié)構(gòu)細(xì)小,或解剖部位復(fù)雜,單純依靠X線(xiàn)易造成誤診及漏診。CT能更清晰地顯示病變部位的骨質(zhì)破壞范圍、位置及程度,通過(guò)多平面重建及容積再現(xiàn)圖像可以直觀(guān)顯示腫瘤形態(tài)及與周?chē)M織的關(guān)系。對(duì)于骨皮質(zhì)變薄、中斷、病灶內(nèi)分割的具體形態(tài)的顯示明顯優(yōu)于X線(xiàn),平片所示典型的皂泡樣改變?cè)贑T上表現(xiàn)為骨質(zhì)破壞區(qū)內(nèi)殘留骨小梁形成的骨嵴[4],CT對(duì)骨殼的完整性及軟組織腫塊的正確判斷影響到骨巨細(xì)胞瘤的分級(jí),良性骨巨細(xì)胞瘤邊緣骨殼完整或部分消失,主要是膨脹性生長(zhǎng),溶骨性破壞,與周?chē)M織分界清晰,侵襲性骨巨細(xì)胞瘤表現(xiàn)為蟲(chóng)蝕樣、鉆孔樣骨質(zhì)破壞,腫瘤邊緣不規(guī)則,向周?chē)浗M織浸潤(rùn),因此對(duì)腫瘤的診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MRI有良好的軟組織分辨率,能更清楚地顯示出腫瘤的邊界,尤其是對(duì)于發(fā)生于脊柱部位的侵襲性骨巨細(xì)胞瘤,可判斷腫瘤對(duì)椎管、神經(jīng)根的累及程度。MRI對(duì)骨皮質(zhì)、骨嵴及鈣化的顯示不及CT及X線(xiàn)敏感,因此不能完全依靠MRI檢查做出診斷。
位于不規(guī)則骨骨巨細(xì)胞瘤的影像學(xué)表現(xiàn)與長(zhǎng)管狀骨大致相仿,表現(xiàn)為囊性膨脹性骨質(zhì)破壞或溶骨性骨質(zhì)破壞,而溶骨性破壞更為顯著,病灶內(nèi)無(wú)鈣化,可局部形成軟組織腫塊。本組2例發(fā)生于髂骨的病例骨殼殘缺,形成的軟組織腫塊與骨膨脹程度不成比例,當(dāng)腫瘤突破骨質(zhì)向外生長(zhǎng),形成的軟組織腫塊較大時(shí)會(huì)影響到診斷的準(zhǔn)確性,與長(zhǎng)管狀骨骨巨細(xì)胞瘤相比有以下特點(diǎn):腫瘤呈膨脹性生長(zhǎng)但偏心性表現(xiàn)不典型,破壞的骨質(zhì)邊緣欠光整;腫瘤形成的軟組織腫塊較大時(shí)侵犯鄰近組織結(jié)構(gòu),失去骨巨細(xì)胞瘤固有特征[5]。本組病例中僅發(fā)生于髂骨的3例表現(xiàn)為典型的皂泡樣骨質(zhì)改變,并可見(jiàn)骨性分割,位于其他部位者由于部位不規(guī)則,骨巨細(xì)胞瘤的典型表現(xiàn)難以表現(xiàn)。骨巨細(xì)胞瘤血供豐富,尤其是實(shí)性成分居多時(shí),增強(qiáng)掃描后腫瘤內(nèi)部及間隔多明顯強(qiáng)化。筆者認(rèn)為,不規(guī)則骨骨巨細(xì)胞瘤由于缺少特征性表現(xiàn),部分病變經(jīng)強(qiáng)化后可顯示出特征性的“皂泡樣”改變,而且腫瘤血供豐富的特點(diǎn)易與其他良性骨腫瘤性病變相鑒別。MRI應(yīng)行常規(guī)平掃加增強(qiáng)掃描,對(duì)于腫瘤周?chē)浗M織的顯示可以更加清晰顯示,結(jié)合CT多平面重建圖像就可以更準(zhǔn)確地觀(guān)察腫瘤的范圍及軟組織侵犯情況,有助于病變的定性診斷,同時(shí)可以為臨床治療提供參考依據(jù)。在不規(guī)則骨發(fā)生的骨巨細(xì)胞瘤表現(xiàn)不典型時(shí),應(yīng)注意與以下病變鑒別。
篇9
關(guān)鍵詞: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X線(xiàn);磁共振成像;CT
周?chē)窠?jīng)鞘瘤起源于雪旺細(xì)胞和其他周?chē)窠?jīng)細(xì)胞被膜,這種腫瘤包括良性神經(jīng)鞘瘤、神經(jīng)纖維瘤和惡性神經(jīng)鞘瘤。但發(fā)生于骨組織中周?chē)窠?jīng)鞘瘤較為罕見(jiàn),常為發(fā)生于骨髓腔內(nèi)良性腫瘤,占所有骨內(nèi)骨腫瘤的0.1%-0.2%,多為單發(fā),少見(jiàn)多發(fā)[1]。主要臨床表現(xiàn)為:局部腫脹、疼痛、神經(jīng)放射痛,尤其夜間明顯,部分患者出現(xiàn)神經(jīng)感覺(jué)異常。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文獻(xiàn)報(bào)道較少,現(xiàn)回顧性報(bào)道8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的影像學(xué)特點(diǎn)及病理結(jié)果,旨在為臨床診斷提供參考。
1材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
收集本院2008-04~2015-10之間8例經(jīng)手術(shù)證實(shí)的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患者,其中男5例,女3例,年齡26-53歲,平均38.3歲。臨床表現(xiàn):局部疼痛6例、伴夜間疼痛3例,其中坐骨神經(jīng)痛伴感覺(jué)障礙2例。所有患者治療進(jìn)行腫瘤刮除術(shù)或截?cái)嘈g(shù)獲得病理材料,經(jīng)病理確證為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
1.2影像學(xué)檢查及參數(shù)設(shè)置
采用GE公司DR攝片機(jī)進(jìn)行X線(xiàn)檢查,拍攝正位或正側(cè)位片,必要時(shí)補(bǔ)照切線(xiàn)位(以完整顯示病變);應(yīng)用日本Aquilion64排螺旋CT進(jìn)行掃描檢查,采集掃描橫斷位,層厚3mm、層間距3mm,用以顯示微小病變。掃描參數(shù):管電壓125kV、管電流380mA、準(zhǔn)直64mm×0.625mm、檢查野256mm×256mm、矩陣512×512、螺距0.964∶1,球管旋轉(zhuǎn)1圈0.8s,有效層厚0.625mm,重建間隔0.625mm。然后將其傳至工作站進(jìn)行后處理工作,重建矢狀位和冠狀位等;結(jié)合多種后處理技術(shù):多平面重組法(multiplanarreformation,MPR);曲面重建法(curveplanarreformation,CPR);最大密度投影法(maximumintensityprojection,MIP),容積再現(xiàn)技術(shù)(volumere-construction,VR)采用多方位、多角度地整體觀(guān)察腫瘤大小、與周?chē)M織關(guān)系,突顯腫瘤全貌。MR檢查采用PhilipsIngenia3.0T超導(dǎo)MRI掃描儀核磁共振機(jī)進(jìn)行橫斷面、冠狀面、矢狀面掃描,快速自旋回波(fastspinecho,F(xiàn)SE)橫斷面T1WI掃描(TR250ms,TE12ms),F(xiàn)OV256mm×256mm,層厚3.0mm,層間距0.5mm,快速自旋回波(fastspinecho,F(xiàn)SE)橫斷面T2WI(TR2450ms,TE130ms)、FOV256mm×256mm,層厚3.0mm,層間距0.5mm,短時(shí)間反轉(zhuǎn)恢復(fù)(shottimeinversionrecovery,STIR)(TR4500ms,TE23ms,TI90),F(xiàn)A=9,層厚1.5mm,F(xiàn)OV=256mm×256mm,矩陣448×320。所有患者未進(jìn)行增強(qiáng)掃描。
1.3影像和病理資評(píng)估
由兩位影像學(xué)專(zhuān)家對(duì)每個(gè)患者影像資料進(jìn)分析,最后在討論會(huì)達(dá)成一致。X線(xiàn)/CT評(píng)估腫瘤部位、形態(tài)結(jié)構(gòu)、大小、骨質(zhì)密度,骨膜反應(yīng),骨質(zhì)破壞及周?chē)奂扒闆r等。MR評(píng)估腫瘤部位、大小、內(nèi)部信號(hào)特點(diǎn)、骨質(zhì)破壞情況、周?chē)莾?nèi)水腫樣信號(hào)強(qiáng)度、腫瘤周?chē)M織情況及合并癥等特點(diǎn)。病理資料由2名從事多年病理診斷專(zhuān)家評(píng)估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的病理特點(diǎn),包括腫瘤的形態(tài)結(jié)構(gòu),腫瘤細(xì)胞特點(diǎn),是否排列規(guī)整,有無(wú)細(xì)胞異型性,有無(wú)侵襲性生長(zhǎng)方式,S-100、Ki-67細(xì)胞免疫組織化學(xué)結(jié)果等。
2結(jié)果
2.1腫瘤發(fā)生部位及一般情況
腫瘤位于脛骨為4例,位于股骨為1例,位于骨盆為2例和位于跟骨旁1例。8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其中6例為單發(fā),2例為多發(fā)。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平均直徑為31.6mm(范圍:11-156mm)。
2.2X線(xiàn)和CT檢查表現(xiàn)
所有患者均進(jìn)行X線(xiàn)和CT檢查。8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囊性溶骨性破壞,其中6例單發(fā)囊性溶骨性破壞,2例為多囊性溶骨性破壞(見(jiàn)圖1)。6例觀(guān)察到軟組織腫塊,其中4例軟組織腫塊邊界清晰,2例軟組織腫塊邊界不清。2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顯示不規(guī)則鈣化或骨化影,其中1例位于股骨,1例位于脛骨。4例表現(xiàn)邊界清晰,其中2例可見(jiàn)明顯硬化緣,2例表現(xiàn)邊界不清楚,其中1例可見(jiàn)斷續(xù)硬化緣。6例管狀骨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囊性溶骨性破壞,骨皮質(zhì)變薄、典型病變邊緣呈扇貝征樣破壞(見(jiàn)圖2A-C)。本組病理未見(jiàn)明顯病理性骨折和骨膜反應(yīng)。管狀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發(fā)生于干骺端,扁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好發(fā)于人體中軸位置。本組病例未見(jiàn)假關(guān)節(jié)形成。6例進(jìn)行MRI檢查。4例管狀骨神經(jīng)鞘瘤中,3例位于脛骨近端干骺端,1例位于股骨遠(yuǎn)端干骺端。6例腫瘤T1WI呈等信號(hào)或低信號(hào)(與肌肉比較),T2WI呈不均勻高信號(hào)(與肌肉比較),然而其中2例表現(xiàn)為低信號(hào),可能是細(xì)胞成分較多的區(qū)域。3例觀(guān)察到短粗線(xiàn)樣骨小梁呈低信號(hào)影,形成典型扇貝征(見(jiàn)圖2D-E),1例表現(xiàn)腫瘤中央可見(jiàn)斑點(diǎn)狀無(wú)信號(hào)影,可能鈣化或礦化物質(zhì)。本組病例未發(fā)現(xiàn)靶征影。1例T2WI表現(xiàn)為更高信號(hào),代表壞死或黏液區(qū)。2例腫瘤表現(xiàn)為邊界清楚,其中2例在T1WI、T2WI可見(jiàn)低信號(hào)硬化緣,2例表現(xiàn)為邊界不清楚。2例腫瘤周?chē)撬鑳?nèi)可見(jiàn)水腫樣信號(hào),與鄰近軟組織水腫有關(guān);8例患者明顯未見(jiàn)骨膜反應(yīng)和供應(yīng)血管影。其中1例患者表現(xiàn)為侵襲性生長(zhǎng)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和巨大軟組織腫塊,可見(jiàn)明顯軟組織向外擴(kuò)散。
2.3病理學(xué)表現(xiàn)
所有病例均經(jīng)病理組織學(xué)診斷明確。8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腫瘤表現(xiàn)典型病理學(xué)特點(diǎn),腫瘤細(xì)小呈梭狀、束狀或漩渦狀,排列成柵欄狀。細(xì)胞核細(xì)而長(zhǎng)、深染、顯示細(xì)胞核增大并顯示多形性,具有明顯核分裂像,腫瘤細(xì)胞低密度(Antoni型A)和高密度區(qū)(Antoni型B)編織狀排列。其中6例可見(jiàn)Verocay小體,局部可見(jiàn)明顯壞死、出血及黏液樣變性;細(xì)胞間質(zhì)內(nèi)含有豐富的細(xì)長(zhǎng)網(wǎng)狀纖維,間有淋巴細(xì)胞和組織細(xì)胞(見(jiàn)圖3A,B)。免疫組織化學(xué)顯示,S-100彌漫強(qiáng)陽(yáng)性(圖3C),神經(jīng)特異性烯醇局部染色,Ki-67細(xì)胞染色明顯低于1%(見(jiàn)圖3D)。
3討論
原發(fā)單發(fā)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常發(fā)生于20-60歲,無(wú)性別差異,少量報(bào)道女性多見(jiàn),大部分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散在發(fā)病,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性疾病。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生長(zhǎng)緩慢,臨床癥狀包括局部疼痛、觸痛、腫脹和病理性骨折,較少惡變[2]。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占所有骨內(nèi)原發(fā)腫瘤少于1%[3]。大部分腫瘤位于長(zhǎng)管狀骨,也可發(fā)生于頜骨、椎骨、骶骨、顱骨及其他骨組織。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尚未明確具體來(lái)源,可能來(lái)源于伴隨滋養(yǎng)動(dòng)脈的有髓和無(wú)髓血管運(yùn)動(dòng)纖維。多發(fā)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往往邊界清晰,常為神經(jīng)纖維瘤病2(NF2),發(fā)生率為1/40000-1/1700000[4]。本組病例僅為2例。本組病例無(wú)NF1型伴多發(fā)軟組織腫瘤神經(jīng)鞘瘤。
3.1X線(xiàn)/CT表現(xiàn)及病理特點(diǎn)
骨內(nèi)單發(fā)神經(jīng)鞘瘤表現(xiàn)為邊界清晰溶骨性破壞,具有輕度膨脹樣改變,周?chē)梢?jiàn)明顯硬化緣,有明顯軟組織腫塊影。骨內(nèi)多發(fā)性神經(jīng)鞘瘤常表現(xiàn)為累及多塊骨質(zhì),呈明顯膨脹溶骨性破壞,常認(rèn)為與神經(jīng)走形有關(guān)。在本組資料中,6例單發(fā)囊性溶骨性破壞,2例為多囊性溶骨性破壞。4例軟組織腫塊邊界清晰,2例軟組織腫塊邊界不清。筆者發(fā)現(xiàn),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呈單囊性溶骨性破壞伴軟組織腫塊、多囊性溶骨性破壞伴軟組織腫塊和軟組織神經(jīng)鞘瘤侵犯到骨質(zhì)結(jié)構(gòu)。在本組病例中未見(jiàn)到軟組織神經(jīng)鞘瘤侵犯到骨質(zhì)結(jié)構(gòu)。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分為兩種類(lèi)型:腫瘤細(xì)胞低密度(Antoni型A)和高密度區(qū)(Antoni型B)編織狀排列,AntoniA區(qū)由密集的梭形細(xì)胞排列形成,以軟組織影像表現(xiàn),AntoniB區(qū)細(xì)胞成分較少,呈疏松網(wǎng)狀結(jié)構(gòu)排列,呈囊性影像表現(xiàn)。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囊實(shí)性的多寡取決于A(yíng)ntoniA區(qū)和AntoniB區(qū)所占的比例分布[5],本組研究結(jié)果以AntoniB區(qū)為主。腫瘤局部可見(jiàn)明顯壞死、出血及黏液樣變性,因而腫瘤密度表現(xiàn)為多樣化,中央可見(jiàn)壞死、不規(guī)則鈣化等。骨皮質(zhì)變薄、典型病變邊緣呈扇貝征樣破壞是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具有的特點(diǎn),是指破壞區(qū)邊緣殘留的骨性突起,呈扇貝征樣改變,常伴有膨脹變薄改變,本組資料中75%的病例能觀(guān)察到此種征象,有助于良惡性神經(jīng)鞘瘤鑒別。
3.2MRI表現(xiàn)及病理特點(diǎn)
MRI能夠明確腫瘤分布及范圍,顯示與鄰近神經(jīng)血管關(guān)系。腫瘤在T1WI呈低信號(hào)或等信號(hào)影,在T2WI呈不均勻高信號(hào),T2WI表現(xiàn)低信號(hào)區(qū)代表細(xì)胞成分較多的區(qū)域,T2WI表現(xiàn)高信號(hào)區(qū)代表細(xì)胞成分少,結(jié)構(gòu)排列疏松,表現(xiàn)為囊性改變,內(nèi)可見(jiàn)更高信號(hào)或更低信號(hào),提示腫瘤壞死或黏液樣變性、鈣化[6]。在本組資料中,腫瘤在T1WI呈低信號(hào)或等信號(hào)影,在T2WI呈不均勻高信號(hào),與相關(guān)文獻(xiàn)報(bào)道一致[7],同時(shí)發(fā)現(xiàn)腫瘤周?chē)0橛兴[信號(hào)。本組資料中,1例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表現(xiàn)侵襲性生長(zhǎng),術(shù)前誤診為軟組織肉瘤侵犯骨質(zhì),表現(xiàn)為不規(guī)則溶骨性破壞,可見(jiàn)巨大軟組織腫塊,可能由于對(duì)該病認(rèn)識(shí)較少。本研究觀(guān)察到短粗線(xiàn)樣骨小梁呈低信號(hào)影,形成典型扇貝征,這種改變是由于腫瘤沿神經(jīng)破壞,殘留骨嵴影。相關(guān)文獻(xiàn)報(bào)道[8],70%骨內(nèi)腫瘤可見(jiàn)硬化邊,而在本文僅為50%(4/8),可能由于病例較少原因,筆者認(rèn)為硬化緣完整性對(duì)鑒別良惡性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具有明顯診斷幫助,但對(duì)診斷特異性不高。也有相關(guān)文獻(xiàn)報(bào)道[9],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亦可顯示“靶征”,具有診斷特異性,在本組無(wú)病例筆者未觀(guān)察到“靶征”特點(diǎn),與一些文獻(xiàn)報(bào)道相似[10],另外,據(jù)報(bào)道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也可伴有病理性骨折[11],本研究未觀(guān)察到,筆者同時(shí)認(rèn)為伴病理骨折不具有特異性。
3.3骨內(nèi)神經(jīng)鞘瘤鑒別診斷
篇10
血管周細(xì)胞瘤(HPC),又稱(chēng)血管外皮細(xì)胞瘤,是一種非常少見(jiàn)的血管源性軟組織腫瘤,占所有血管源性腫瘤的1%。為了提高對(duì)其認(rèn)識(shí),現(xiàn)將青島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附屬醫(yī)院收治的1例發(fā)生在左側(cè)翼腭窩區(qū)的HPC報(bào)告如下。
病人,男,57歲。左側(cè)面部麻木2年,左眼外凸約1年,左眼視力下降半年。MRI表現(xiàn):左側(cè)翼腭窩內(nèi)不規(guī)則形中等T1中等T2異常信號(hào)影,大小約30 mm×55 mm×30 mm,其內(nèi)見(jiàn)斑片狀長(zhǎng)T1長(zhǎng)T2信號(hào)壞死區(qū)。除腫瘤壞死區(qū)在FLAIR像上顯示為低信號(hào)外,腫瘤組織在FLAIR和DWI像上皆為中等信號(hào)。軟組織包塊邊界清楚,左側(cè)眶尖和左側(cè)上頜竇后外側(cè)壁受壓。MRI增強(qiáng)掃描示軟組織包塊明顯強(qiáng)化,壞死區(qū)無(wú)強(qiáng)化(圖1~5)。術(shù)前根據(jù)MRI影像特征診斷為神經(jīng)源性腫瘤。全麻下行腫瘤切除,術(shù)中見(jiàn)包塊有包膜,質(zhì)硬,血運(yùn)極為豐富,術(shù)中出血約1 500 mL,切除腫瘤組織合計(jì)直徑約30 mm。病理檢查:HPC,生長(zhǎng)活躍。免疫組化:CD34(+),Vim(+),EMA(-)。
①T1WI圖像示左側(cè)翼腭窩區(qū)中等T1異常包塊影,其內(nèi)見(jiàn)長(zhǎng)T1信號(hào)壞死區(qū);②T2WI圖像示左側(cè)翼腭窩區(qū)中等T2異常包塊影,其內(nèi)見(jiàn)長(zhǎng)T2信號(hào)壞死區(qū);③、④FLAIR和DWI圖像示左側(cè)翼腭窩區(qū)中等信號(hào)包塊影,壞死區(qū)為低信號(hào);⑤強(qiáng)化T1WI示左側(cè)翼腭窩區(qū)包塊強(qiáng)化。
討論
HPC可發(fā)生于身體的任何部位,多見(jiàn)于骨骼、肌肉系統(tǒng)(以雙下肢、腹膜后多見(jiàn)),其次為肺、肝、脾和腎臟,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少見(jiàn)。約15%~30%的HPC發(fā)生在頭頸部,其中5%發(fā)生于鼻腔及鼻竇區(qū)域,發(fā)生在翼腭窩區(qū)域的腫瘤少見(jiàn)報(bào)道。
HPC最早由STOUT和MURRY在1942年命名并報(bào)道,起源于毛細(xì)血管Zinmerman外皮細(xì)胞,即周細(xì)胞(pericyte),1993年WHO將其歸類(lèi)為間質(zhì)源性的腫瘤。病理學(xué)上HPC鏡下特征為:以血管為中心周細(xì)胞增生,血管壁菲薄,甚至僅為一層扁平的內(nèi)皮細(xì)胞,使管腔呈裂隙狀,有的擴(kuò)張成血竇,相互吻合成鹿角狀。壞死、出血及囊變多見(jiàn),生長(zhǎng)周期越短、復(fù)發(fā)越早者出血、壞死、囊變?cè)街亍C庖呓M化特征性表現(xiàn)為Vim及CD34呈陽(yáng)性反應(yīng)。HPC為潛在惡性腫瘤,可以有或無(wú)完整包膜,原發(fā)腫瘤手術(shù)切除后易復(fù)發(fā)或遠(yuǎn)處轉(zhuǎn)移。也有作者認(rèn)為約30%的HPC表現(xiàn)為惡性腫瘤特征。
HPC在MRI上多表現(xiàn)為邊界清楚的軟組織包塊影,形態(tài)多不規(guī)則。軟組織包塊多為中等T1中等T2信號(hào),壞死區(qū)域?yàn)殚L(zhǎng)T1長(zhǎng)T2信號(hào),少見(jiàn)鈣化信號(hào)。以往研究很少涉及HPC在FLAIR和DWI像上的特征,本文病人在FLAIR和DWI圖像上軟組織包塊表現(xiàn)為中等信號(hào)。MR增強(qiáng)掃描示軟組織包塊多明顯強(qiáng)化。
HPC在CT圖像上多為軟組織密度包塊,可以存在低密度壞死區(qū),高密度鈣化少見(jiàn),包塊邊界多較清楚,腫瘤對(duì)周?chē)琴|(zhì)的壓迫或侵蝕可導(dǎo)致骨質(zhì)吸收或缺損。CT增強(qiáng)掃描腫瘤組織多明顯強(qiáng)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