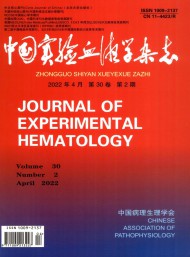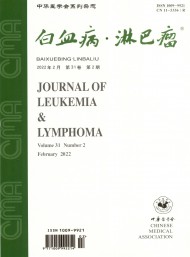骨髓瘤范文10篇
時間:2024-02-04 12:35:53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骨髓瘤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治療骨髓瘤的對策
多發性骨髓瘤(MM)是較為典型的疑難重癥,西藥治療效果不佳,預后不良,而中醫治療該病倒是顯示了很好的前景,有些病人已治愈十年以上。本文試就相關的幾個問題作一簡單探討,謬誤之處請同道不吝指正。
一、中醫可以根治多發性骨髓瘤
髓為奇恒之府,比較而言,較五臟發病更易治療。大量臨床也證實多發性骨髓瘤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多發性骨髓瘤是漿細胞惡性增生所致的惡性腫瘤,主要侵犯骨髓,以溶骨性損害為主。常見癥狀為骨痛、病理性骨折、貧血、出血、發燒等。中晚期則多伴以反復感染、腎功能損害等。值得注意的是,該病早期骨痛常呈游走性,中晚期則多為固定部位。而其骨折,多為腰椎壓縮性骨折,及肋骨骨折,也可見肱骨骨折。
本病起病在骨,而其根在髓。腎主骨而生髓,故治療上以補腎為第一要務,輔以益氣養血、活血通瘀,或佐以清化痰濁。腎氣壯而精氣生,正勝則邪退,不治瘤而瘤細胞自消;瘤細胞消退,則骨髓功能恢復,氣血自生,其病自愈。筆者創立的中藥復方渙膈飲系列,2號工于補益元氣、化瘀血、逐痰濁,而渙膈5號則有調理氣血、補腎壯骨之功效,故與多發性骨髓瘤正相吻合。而渙膈3號長于祛瘀生新,并能醒脾開胃,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該系列方在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上顯現了諸多獨特之處:一是見效快,一至三個療程即可使瘤細胞下降,血像好轉,體質增強。二是基本無毒副作用,除個別人,尤其是化療后者,可能出現惡心、嘔吐、輕度腹瀉外,未見其它不良反應。山東省醫工所及山醫大藥理教研室的藥理實驗也證實“無明顯不良反應”。三是具有根治的作用。由于無毒,無副作用,適于連續治療,很多患者在服用6-12療程之后(多者可達24個療程),癥狀消除,漿細胞正常,血像正常,骨損害恢復,宣告治愈所以說,治愈多發性骨髓瘤并非萬難之事,在治療之初樹立起堅定的信念是治好本病的前提
二、治骨痛、骨折不可漫用活血、“接骨”藥
治療骨髓瘤的方法芻議
多發性骨髓瘤(MM)是較為典型的疑難重癥,西藥治療效果不佳,預后不良,而中醫治療該病倒是顯示了很好的前景,有些病人已治愈十年以上。本文試就相關的幾個問題作一簡單探討,謬誤之處請同道不吝指正。
一、中醫可以根治多發性骨髓瘤
髓為奇恒之府,比較而言,較五臟發病更易治療。大量臨床也證實多發性骨髓瘤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多發性骨髓瘤是漿細胞惡性增生所致的惡性腫瘤,主要侵犯骨髓,以溶骨性損害為主。常見癥狀為骨痛、病理性骨折、貧血、出血、發燒等。中晚期則多伴以反復感染、腎功能損害等。值得注意的是,該病早期骨痛常呈游走性,中晚期則多為固定部位。而其骨折,多為腰椎壓縮性骨折,及肋骨骨折,也可見肱骨骨折。
本病起病在骨,而其根在髓。腎主骨而生髓,故治療上以補腎為第一要務,輔以益氣養血、活血通瘀,或佐以清化痰濁。腎氣壯而精氣生,正勝則邪退,不治瘤而瘤細胞自消;瘤細胞消退,則骨髓功能恢復,氣血自生,其病自愈。筆者創立的中藥復方渙膈飲系列,2號工于補益元氣、化瘀血、逐痰濁,而渙膈5號則有調理氣血、補腎壯骨之功效,故與多發性骨髓瘤正相吻合。而渙膈3號長于祛瘀生新,并能醒脾開胃,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該系列方在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上顯現了諸多獨特之處:一是見效快,一至三個療程即可使瘤細胞下降,血像好轉,體質增強。二是基本無毒副作用,除個別人,尤其是化療后者,可能出現惡心、嘔吐、輕度腹瀉外,未見其它不良反應。山東省醫工所及山醫大藥理教研室的藥理實驗也證實“無明顯不良反應”。三是具有根治的作用。由于無毒,無副作用,適于連續治療,很多患者在服用6-12療程之后(多者可達24個療程),癥狀消除,漿細胞正常,血像正常,骨損害恢復,宣告治愈所以說,治愈多發性骨髓瘤并非萬難之事,在治療之初樹立起堅定的信念是治好本病的前提
二、治骨痛、骨折不可漫用活血、“接骨”藥
多發性骨髓瘤治療血清中白介素論文
【關鍵詞】骨髓瘤
多發性骨髓瘤(Multiplemyeloma,MM)是血液系統常見腫瘤之一,多見于中老年人。許多研究表明白介素-6(IL-6)MM的療效及預后有重要意義,它可以促進骨髓瘤細胞增殖,并抑制其凋亡,介導細胞耐藥;另外,還參與骨質破壞、腎功能損害等。筆者通過臨床檢測MM治療前后血清中IL-6表達水平的變化以探討其作為臨床判斷療效和預后指標之一的意義。
1資料與方法
1.1研究對象11例標本均來自我院住院的MM患者,診斷符合《血液病診斷及療效標準》,其中男8例,女3例,年齡52~69歲,中位年齡63歲。按Durie-Salmon分期標準:Ⅱ期5例,Ⅲ期6例。其中有7例患者獲得部分緩解后出現疾病進展。正常對照為11例體檢健康中老年人,男9例,女2例。MP方案治療4例,VAD方案治療7例。
1.2方法
1.2.1檢測方法分別取11例患者初診時和治療后的靜脈血1.5ml,靜置分離血清。試劑盒購自北京晶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采用ELISA雙抗體夾心法檢測IL-6的水平。操作按說明書提供步驟進行。
多發性骨髓瘤治療研究論文
【摘要】目的:觀察益腎活血飲聯合沙利度胺治療難治復發多發性骨髓瘤的近期療效。方法:25例難治復發多發性骨髓瘤患者隨機分為中西醫結合組15例和西藥組10例。西藥組口服沙利度胺100mg,每晚1次,中西醫結合組在口服沙利度胺的基礎上加服中藥益腎活血飲,共治療6個月。結果:中西醫結合組15例中,完全緩緩解1例,部分緩解8例,穩定4例,進展2例,總有效率60%。西藥組10例中,完全緩解1例,部分緩解3例,穩定1例,進展5例,總有效率40%。中西醫結合組臨床療效優于西藥組(P<0.05)。與治療前比較,兩組治療后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水平均明顯下降,但中西醫結合組的作用更強(P<0.05)。結論:益腎活血飲聯合沙利度胺治療難治復發多發性骨髓瘤療效較好,且有降低血清VEGF水平的作用。
【關鍵詞】多發性骨髓瘤益腎活血飲沙利度胺VEGF
多發性骨髓瘤為惡性漿細胞疾病,屬于血液腫瘤,其發病率逐年上升,以貧血、骨痛、腎功能衰竭為主要表現。骨髓瘤細胞容易產生耐藥導致疾病難治及復發,化療或骨髓移植乃至分子靶向治療的療效均有限,中位生存期為3年。研究表明,骨髓瘤患者血清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水平升高,與疾病的惡性程度及預后相關。筆者應用益腎活血飲聯合沙利度胺治療難治復發多發性骨髓瘤,取得較好的療效,報道如下。
1臨床資料
25例為本院2004年~2007年住院及門診患者,均符合《血液病的診斷和療效標準》[1]中多發性骨髓瘤的診斷標準,拒絕或不具備條件進行化療及干細胞移植,心肝腎功能正常。排除病情危重,不配合治療。25例均為復治者,既往曾用MP(馬法蘭、潑尼松)和VAD(長春新堿、阿霉素、地塞米松)等不同方案多療程化療但未緩解或緩解后復發。按3∶2隨機分為中西醫結合組15例,男9例,女6例,年齡62~78歲,中位年齡67歲;病程9個月~2年,中位病程13個月;IgG型11例,IgA型4例;Ⅱ期2例,Ⅲ期13例。西藥組10例,男6例,女4例,年齡59~79歲,中位年齡68歲;病程10個月~2年,中位病程14個月;IgG型7例,IgA型3例;Ⅱ期1例,Ⅲ期9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中醫辨證標準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2]相關標準擬定。中西醫結合組15例中腎虛血瘀型13例,腎虛濕熱型2例。
小議多發性骨髓瘤
多發性骨髓瘤(MM)是較為典型的疑難重癥,西藥治療效果不佳,預后不良,而中醫治療該病倒是顯示了很好的前景,有些病人已治愈十年以上。本文試就相關的幾個問題作一簡單探討,謬誤之處請同道不吝指正。
一、中醫可以根治多發性骨髓瘤
髓為奇恒之府,比較而言,較五臟發病更易治療。大量臨床也證實多發性骨髓瘤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多發性骨髓瘤是漿細胞惡性增生所致的惡性腫瘤,主要侵犯骨髓,以溶骨性損害為主。常見癥狀為骨痛、病理性骨折、貧血、出血、發燒等。中晚期則多伴以反復感染、腎功能損害等。值得注意的是,該病早期骨痛常呈游走性,中晚期則多為固定部位。而其骨折,多為腰椎壓縮性骨折,及肋骨骨折,也可見肱骨骨折。
本病起病在骨,而其根在髓。腎主骨而生髓,故治療上以補腎為第一要務,輔以益氣養血、活血通瘀,或佐以清化痰濁。腎氣壯而精氣生,正勝則邪退,不治瘤而瘤細胞自消;瘤細胞消退,則骨髓功能恢復,氣血自生,其病自愈。筆者創立的中藥復方渙膈飲系列,2號工于補益元氣、化瘀血、逐痰濁,而渙膈5號則有調理氣血、補腎壯骨之功效,故與多發性骨髓瘤正相吻合。而渙膈3號長于祛瘀生新,并能醒脾開胃,起到了很好的輔助作用。該系列方在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上顯現了諸多獨特之處:一是見效快,一至三個療程即可使瘤細胞下降,血像好轉,體質增強。二是基本無毒副作用,除個別人,尤其是化療后者,可能出現惡心、嘔吐、輕度腹瀉外,未見其它不良反應。山東省醫工所及山醫大藥理教研室的藥理實驗也證實“無明顯不良反應”。三是具有根治的作用。由于無毒,無副作用,適于連續治療,很多患者在服用6-12療程之后(多者可達24個療程),癥狀消除,漿細胞正常,血像正常,骨損害恢復,宣告治愈。所以說,治愈多發性骨髓瘤并非萬難之事,在治療之初樹立起堅定的信念是治好本病的前提。
二、治骨痛、骨折不可漫用活血、“接骨”藥
靜脈血栓用藥分析和藥學監護
1病例簡介
患者,男,70歲,身高165cm,體質量65kg。2015年9月,患者無明顯誘因開始右下肢痛,疼痛未向下肢放射,無肩背痛,無尿頻、尿急,無下肢麻木及腫脹。無發熱,無胸悶、氣促,惡心、腹脹,無嘔吐、腹痛。2016年2月疼痛加劇,無法行走,2016年3月前轉身時突然疼痛加劇,無法站立,到我院就診,發現右股骨干病理骨折,PET-CT顯示右股骨異常放射濃聚,行局部固定術,病理提示漿細胞瘤。為進一步診治到我院就診,門診以“多發性骨髓瘤”收入院。
2治療經過
患者入院后行血常規示:WBC9.4×109•L-1,Hb126g•L-1,Plt451×109•L-1;纖維蛋白原(FIB)4.6g•L-1,D-二聚體(D-D)3.28mg•L-1,纖維蛋白降解產物(FDP)7.7mg•L-1。生化檢查:ALT35U•L-1,AST22U•L-1,SCr122μmol•L-1。血免疫球蛋白G(IgG)25.70g•L-1,κ輕鏈(KAP)28.40g•L-1。行骨髓檢查骨髓瘤細胞占41%。可明確診斷多發性骨髓瘤IgG-κIII期A(DS分期)。入院后于2016年5月4~7日行TAD方案化療:沙利度胺100mgqn,多柔比星脂質體40mgd1,地塞米松40mgd1~4,過程順利。醫囑給予阿司匹林100mgqd預防血栓形成。5月9日應用沙利度胺第6日,患者右上肢及右下肢水腫(患者10d前已完善雙下肢深靜脈彩超,未見明顯異常),并再次行雙下肢深靜脈彩超。5月10日深靜脈彩超示右小腿腓靜脈、肌間靜脈血栓,D-D3.99mg•L-1,FDP9.9mg•ml-1,主管醫生咨詢臨床藥師給藥方案,藥師考慮下肢靜脈血栓可能與多發性骨髓瘤疾病本身和使用沙利度胺聯合多柔比星的化療方案相關,患者Ccr45.8ml•min-1,建議給予低分子肝素鈉1mg•kg-1,ih,q12h抗凝治療,無需調整劑量。主管醫生采納,但降低了給藥劑量,給予依諾肝素鈉注射液40mg,ih,q12h抗凝治療。同時,血管外科會診與臨床藥師一致,建議低分子肝素嚴格抗凝治療,及時復查凝血指標,觀察D-D變化,并囑患者臥床制動,抬高患肢。5月16日低分子肝素鈉抗凝治療1周,患者D-D1.34mg•L-1,FIB441.7g•L-1。5月20日患者復查彩超示右下肢深靜脈血栓較前減少,凝血指標D-D1.63g•L-1,FIB451.2g•L-1,醫囑繼續予依諾肝素鈉注射注40g,ih,q12h治療。
3討論
3.1患者血栓形成的原因腫瘤患者VTE與多種因素相關,美國臨床腫瘤學會AS-CO指南[2]指出腫瘤患者VTE危險因素主要包括腫瘤相關因素,治療相關因素、患者因素和生物標記4大方面,其中包括的危險因素與國內2015年腫瘤相關靜脈血栓栓塞指南[3]和NCCN在2016年的腫瘤相關靜脈血栓栓塞指南[4]基本一致。(1)腫瘤因素:腫瘤本身是VTE發生的重要高危因素。惡性腫瘤細胞及其產物與宿主細胞相互作用產生高凝狀態,引起機體防御血栓形成的功能減低。惡性腫瘤患者多有凝血機制異常,表現為FDP增高、血小板增多、血小板聚集功能亢進、纖維蛋白溶解低下和高FIB血癥等。普通人群中靜脈血栓栓塞包括深靜脈血栓和肺栓塞的年發病率為0.1%[5]。腫瘤患者發生VTE的風險較非腫瘤患者至少增加4~7倍[6,7],并導致其存活率顯著下降。該患者多發性骨髓瘤,高黏滯血癥,發生VTE的風險增加[8]。(2)治療因素:主要包括化療、放療、使用糖皮質激素、免疫調節藥、促紅細胞生成素、輸血、手術、深靜脈置管等。本例患者的化療方案為TAD方案,含有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沙利度胺為免疫調節藥,可多靶位攻擊漿細胞微環境,使細胞凋亡、抑制血管生成和細胞因子環路,并產生其他抑制作用,在初診和復發難治性多發性骨髓瘤的治療中均有顯著療效,而且價格便宜,國內2015版指南[9]將其推薦為初始治療方案的藥物,但是NCCN2017V2版多發性骨髓瘤指南認為沙利度胺毒性較大(包括血栓風險等),已不再推薦,僅保留DT-PACE一個含有沙利度胺的方案。沙利度胺促使血栓形成的可能機制如下:①在沙利度胺治療的第1個月內,抗凝途徑輔因子血栓調節蛋白的血清水平出現暫時性降低,并在隨后的2個月逐漸恢復[10];②暴露于蒽環類藥物后,沙利度胺可增加內皮細胞表達蛋白酶激活受體-1(proteaseactivatedreceptor-1,PAR-1)[11],可導致與血管內皮結合的凝血酶增加,并可部分解釋沙利度胺與某種蒽環類藥物聯用時所見的血栓形成風險增加;③一項研究表明,接受沙利度胺治療的MM患者血管性血友病因子抗原和FⅧ的水平極高,而在普通人群中,已知這兩者與發生VTE的風險增加有關[12];④單核苷酸多態性(singlenucleotidepolymorphisms,SNPs)的基因分析顯示,在藥物轉運/代謝、DNA修復和細胞因子平衡方面重要的基因和通路中富含與MM患者的沙利度胺相關性VTE事件有關的那組SNPs[13~15];⑤通過免疫調節衍生物(如沙利度胺和來那度胺)下調PU.1可導致骨髓成熟阻滯,進而引起早幼粒細胞蓄積,而早幼粒細胞的嗜天青顆粒含有較高水平的組織蛋白酶G[16]。組織蛋白酶G是一種血小板功能激動藥,可促進VTE的風險。然而,研究證實,沙利度胺單藥治療并不會顯著增加血栓形成風險[8]。但是,多發性骨髓瘤采用基于沙利度胺的聯合化療方案(包括高劑量地塞米松、多柔比星和其他多藥聯合方案)會使VTE風險增加[8]。該研究指出與地塞米松合用VTE發生率可達26%,與多柔比星合用可達27%。美國東部腫瘤協作組(EasternCooperativeOncologyGroup,ECOG)一項大型隨機試驗,在102例接受thal/dex方案治療的患者中,17例(17%)患者出現DVT發作;而在102例僅接受地塞米松治療的患者中,僅有3例(3%)。另有報道多發性骨髓瘤患者使用糖皮質激素聯合沙利度胺治療的方案,VTE風險明顯增高約35%,并與糖皮質激素的劑量呈相關性[17]。值得注意的是,糖皮質激素單藥也與VTE風險增加相關[18]。一項基于人群的病例對照研究對比了將近39000例VTE患者與無VTE的年齡性別匹配對照組中糖皮質激素使用的比率。相對于之前使用過糖皮質激素(使用時間為VTE前超過3個月),最近使用(少于3個月)與VTE風險增至前者的1.2到2倍相關。該風險在初次使用者中最高(發生率比3.06,95%CI2.77~3.38),且隨著累積劑量而增加(以潑尼松龍等效劑量計,潑尼松龍1~2g的發生率是小于10mg的2倍)。并且,此相關性似乎與基礎疾病的嚴重度和存在已知會增加血栓形成風險的疾病等混雜因素無關。糖皮質激素致血栓形成的機制可能是:使血漿中凝血酶原、血管性血友病因子和抗凝血酶水平增加,纖維蛋白原和纖溶酶原水平下降。此外,Tran等[19]研究報道,在血液腫瘤患者中,中心靜脈置管VTE的發生率為7.8%,但發生主要是上肢深靜脈血栓。本例患者化療方案包括了沙利度胺、地塞米松和脂質體多柔比星,而且使用PICC置管,因此VTE發生風險較大。(3)患者因素:主要有高齡、種族(非洲、美洲人高,亞洲人低)、肥胖、既往VTE病史、合并癥(感染、腎臟疾病、肺部疾病)、遺傳因素等。(4)生物標記:主要包括WBC(≥11×109•L-1)、Hb(≤10g•dl-1)和Plt(≥350×109•L-1)3項,本例患者Plt為451×109•L-1。本例患者年齡70歲,診斷為多發性骨髓瘤,入院時Plt451×109•L-1,FIB4.6g•L-1,D-D3.28mg•L-1,FDP7.7mg•L-1,采用含沙利度胺和地塞米松的多藥聯合化療方案,均為VTE的危險因素。患者入院前檢查沒有靜脈血栓,在TAD方案治療第6日右上肢和右下肢水腫,下肢靜脈彩超示右小腿腓靜脈、肌間靜脈血栓,D-D3.99mg•L-1,FDP9.9mg•L-1較前升高。根據血栓形成的時間及VTE危險因素分析,臨床藥師認為本例患者右小腿腓靜脈、肌間靜脈血栓形成與沙利度胺聯合地塞米松和多柔比星的化療方案密切相關。3.2患者抗凝治療方案評價國內指南鼓勵對所有住院腫瘤患者進行VTE風險評估。對于無抗凝治療禁忌的所有腫瘤住院患者(或臨床疑似腫瘤患者),若患者的活動量不足以減少VTE的危險(例如臥床)或屬于VTE高危患者,則應進行預防性抗凝治療。抗凝治療應貫穿整個住院期間。對于聯合使用沙利度胺、地塞米松和多柔比星化療的患者推薦預防性抗凝治療,低危患者推薦使用阿司匹林預防,高危患者推薦使用低分子肝素或足量華法林。目前主要推薦的VTE風險評估量表主要有Khorana預測模型和Caprini量表等,在ASCO及NCCN指南中推薦Khorana預測模型用于預測腫瘤患者靜脈血栓栓塞風險,而該模型僅包括了危險因素中腫瘤相關因素及生物學標記2部分6項內容,臨床藥師認為此模型方便操作,但缺少患者因素及治療因素,存在一定的不足,對于門診或初始治療患者的評估可能更合適,而NCCN腫瘤相關靜脈血栓栓塞指南引入了Palumbo[20]提出的針對使用沙利度胺、來那度胺或泊馬度胺的多發性骨髓瘤患者的VTE危險因素的風險評估模型,適用于本例患者。在Palumbo的評估模型中,使用含沙利度胺方案治療的患者,對于無危險因素或只有1個危險因素推薦阿司匹林預防;而≥2個危險因素的患者則推薦使用低分子肝素或足量華法林。本案例中患者診斷多發性骨髓瘤即為1個危險因素,加上使用多柔比星脂質體(地塞米松160mg每月屬于低劑量),以及血液高黏滯共3個危險因素,應該采用低分子肝素鈉或者口服華法林預防性治療,指南認為新型口服抗凝藥用于腫瘤相關靜脈血栓栓塞支持的證據不足,因此不推薦使用。醫生在開始化療后給予阿司匹林100mgqd預防靜脈血栓栓塞,不大適宜,但是考慮到華法林治療窗較窄,且與藥物食物相互作用較多,需要密切抽血監測,一旦使用不當患者出血風險明顯增高,低分子肝素長期使用,需要注射不方便,還會出現皮膚青紫,也會帶來出血風險。臨床藥師認為顧慮到以上情況,患者開始的抗凝治療方案選擇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是存在風險的。3.3患者腓靜脈和肌間靜脈血栓形成后治療方案的調整該患者發現左腿脛后靜脈血栓時,臨床藥師首先建議醫生停用沙利度胺,并給予患者低分子肝素鈉治療,按NCCN和ASCO指南推薦1mg•kg-1ihq12h治療,國內2015年版指南推薦治療量需要80~100U•kg-1(0.8~1mg•kg-1)ihq12h,患者體質量65kg,需要劑量為52~65mg,ih,q12h。臨床醫生認為患者70歲,Ccr45.8ml•min-1,給予40mg,ih,q12h。10d后再次復查患者靜脈彩超時未見腓靜脈血栓,肌間靜脈血栓減少,同時患者D-D1.63mg•L-1,FIB451.2g•L-1,較前下降,可見使用低分子肝素對于腫瘤患者新發血栓治療作用是肯定的,表明在腫瘤患者新發深靜脈血栓的治療,使用低分子肝素鈉40mg,ih,q12h的治療是安全、可行的,但可能足量給予治療效果會更加顯著。3.4后續防治建議及藥學監護通過對既往方案以及患者血栓形成的原因分析,藥師建議:沙利度胺作為免疫調節藥對多發性骨髓瘤具有很好的反應率,特別是對于經濟基礎較差的患者,仍是首選藥物之一。患者出現靜脈血栓栓塞并積極治療后,可以重新考慮恢復使用沙利度胺,同時積極預防靜脈血栓栓塞。如果患者繼續使用含沙利度胺的治療方案,根據Palumbo模型,目前已有多發性骨髓瘤、血液高黏滯、聯合使用多柔比星、既往VTE病史4項危險因素,推薦使用低分子肝素鈉40mgqd或口服足量的華法林預防,不推薦阿司匹林預防。應注意的是,長期使用低分子肝素需要對患者抗Ⅹa因子活性進行監測,并定期監測血常規及凝血功能,口服華法林需監測INR值,以提高用藥安全性;如果患者采用不含沙利度胺的化療方案,可以考慮使用阿司匹林預防。應囑患者沙利度胺在睡前服用,如果出現嚴重皮疹等過敏反應,咳嗽、咳痰、發燒等感染征象,以及嚴重的頭暈等須立即就醫。
干細胞移植病患皮膚藥物護理探究論文
【摘要】目的觀察碘伏溶液及洗必泰溶液對外周血干細胞移植患者的皮膚護理效果。方法將患者25例隨機分為兩組,觀察組予0.05%碘伏溶液而對照組予0.02%洗必泰溶液作移植前藥浴及移植期間的皮膚護理。結果觀察組皮膚不適及感染發生率為18.18%,對照組為85.71%,兩組比較差異有高度顯著性(P<0.01)。結論碘伏對外周血干細胞移植患者皮膚護理效果優于洗必泰。
【關鍵詞】干細胞移植碘伏皮膚護理
外周血干細胞移植是治療白血病、惡性淋巴瘤等惡性疾病的重要手段。無論是自體移植還是異體移植,在移植前均需接受預處理,即超大劑量的放療和化療,使患者骨髓造血功能和免疫系統明顯受到抑制,此時極易發生出血和感染等并發癥,而皮膚感染是移植患者常見的并發癥之一。2002年8月~2006年12月我科對25例外周血干細胞移植患者分別采用0.05%碘伏溶液及0.02%洗必泰溶液作皮膚護理,并進行效果觀察,現將結果報告如下。
一、資料及方法
1.1一般資料
2002年8月~2006年12月在我科作外周血干細胞移植患者25例,其中觀察組11例,男4例,女7例,年齡13~52歲,平均38.6歲;急性白血病6例,慢性白血病3例,多發性骨髓瘤2例;行異體干細胞移植2例,自體干細胞移植9例。對照組14例,男6例,女8例,年齡21~56歲,平均41.2歲;急性白血病8例,慢性白血病3例,多發性骨髓瘤2例,淋巴瘤1例。行異體干細胞移植2例,自體加異體干細胞移植1例,自體干細胞移植11例。兩組患者移植前均采用馬利蘭/環磷酰胺(BU/CY)或馬利蘭/阿糖胞苷(BU/Ara-C)作預處理,男女構成、年齡、病情方面差異無顯著性(P>0.05),具有可比性。
議NAP在血液病中鑒別診斷的應用
【摘要】目的研究中性粒細胞堿性磷酸酶(NAP)活性測定在血液病鑒別診斷中的應用價值。方法采集215例血液病患者和30名健康人的靜脈血制備血涂片,經Kaplow偶氮偶聯法進行NAP細胞化學染色,顯微鏡油鏡觀察100個成熟中性粒細胞,以五級積分值記錄結果。結果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類白血病反應(LR)、再生障礙性貧血(AA)、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CLL)、多發性骨髓瘤(MM),真性紅細胞增多癥(PV)6組疾病NAP積分明顯高于對照組(P<0.01);CLL、惡性組織細胞病(MH)、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DS-RAEBT)、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癥(PNH)4組疾病NAP積分明顯低于上述6組疾病和對照組(P<0.01);AMLNAP積分略低于對照組,但差異無顯著性(P>0.05),與ALL比較差異有高度顯著性(P<0.01)。結論NAP活性測定可支持血液病的鑒別診斷。
【關鍵詞】堿性磷酸酶;血液病
堿性磷酸酶主要見于成熟中性粒細胞、網狀細胞和吞噬細胞,其他細胞皆為陰性反應。總結我院血液科215例血液病人的中性粒細胞堿性磷酸酶(NAP)活性觀察,進行對比分析,以探討NAP在血液病中鑒別診斷的應用價值。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本組215例血液病均來源于我院血液科2002~2007年經骨髓涂片細胞學分析、病理檢查及有關實驗室檢查并結合臨床參照文獻[1]確診病例,其中再生障礙性貧血(AA)47例、骨髓增生異常綜合征(MDS-RAEBT)5例、真性紅細胞增多癥(PV)4例、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ML)69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ALL)50例、惡性組織細胞病(MH)3例、類白血病反應(LR)13例、陣發性睡眠性血紅蛋白尿癥(PNH)4例、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13例、多發性骨髓瘤(MM)4例、慢性淋巴細胞性白血病(CLL)3例。健康人群30例為對照組,其中男18例,女12例。患者和健康人群均采集靜脈血制備血涂片2張。
1.2試劑Kaplow偶氮偶聯法:①固定液:25%甲醛乙醇溶液;②丙二醇緩沖液:0.05mmol/L2-氨基-2-甲基-1,3-丙二醇溶液(pH9.75);③基質孵育液(pH9.4-9.6新鮮配制):α-磷酸萘酚鈉20mg溶于緩沖液20ml,再加入堅牢藍RR20mg;④蘇木素復染液。細胞染色方法:新鮮血片用固定液冷固定(4~10℃)30s,水洗、晾干后放入基質孵育液(按上述方法新鮮配制)中,37℃溫浴30min,流水沖洗,晾干后蘇木素復染液復染5min,水洗、晾干。顯微鏡油鏡觀察100個成熟中性粒細胞,按每個細胞漿內顆粒多少分成五級:(-)、(1+)、(2+)、(3+)、(4+),用半定量記分法,以積分值記錄結果[2]。
中西醫結合抗腫瘤研究論文
【摘要】從非特異性免疫及特異性免疫兩個方面對中西醫結合抗腫瘤機制進行了綜述。
【關鍵詞】中西醫結合抗腫瘤免疫學
在眾多的對腫瘤治療方法的探索中,各種治療方式的結果大多不如預期有效[1],而傳統的化療藥具有明顯的毒副作用及耐藥性,從天然產物中提取可以用于臨床的有效成分激發機體免疫系統的活性一直是多年來學術界感興趣的重要研究課題。我國傳統醫學不但具有獨特的優勢,而且與西醫相比,中醫更重視整體認識疾病發生的條件,強調“治未病”。中醫認識到正虛是疾病的重要內因,即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虛學說已被現代醫學認識和承認。西醫比較能融合現代科學成就,認識病癥具體、深入。越來越多的意向認為中西醫應當互相補充,但如何互相補充又是擺在人們面前的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我們認為,這種結合或補充,不但在于臨床實踐中的摸索,而且還應同時解決理論上的問題,只有這樣才能被國際醫學界認可。現將中西醫結合抗腫瘤的免疫學機制研究綜述如下。
1對非特異性免疫抗腫瘤的影響
機體免疫機能狀態的異常及腫瘤免疫逃逸是腫瘤發生的重要原因,同時腫瘤細胞及其產生的腫瘤性免疫抑制因子往往導致荷瘤機體免疫機能低下,由于腫瘤細胞抗原性較弱或抗原調變等因素導致腫瘤特異性免疫往往難以奏效,因此非特異性免疫在機體抗腫瘤免疫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機體的非特異性免疫包括單核巨噬細胞及NK細胞所構成的機體腫瘤免疫監視中的第一道防線。
1.1中西醫聯合對巨噬細胞抗腫瘤的影響欖香烯是從姜科植物溫郁金中提取的抗癌有效成分。將其用專利方法制備出Hca-F欖香烯復合瘤苗HSP70(HSP70HTCV),分析其對小鼠腹腔或脾臟巨噬細胞功能的影響及抗免疫作用的機制,發現HSP70HTCV免疫小鼠脾臟巨噬細胞分泌TNF的能力高于HSP70BCG免疫小鼠的脾臟巨噬細胞,且巨噬細胞吞噬中性紅的能力亦明顯增強,由此得出結論[2],HSP70HTCV免疫誘導的巨噬細胞對腫瘤細胞有更強的殺傷活性。
慢性中性粒細胞白血病分子診斷探討
慢性中性粒細胞白血病(chronicneutrophilleukemia,CNL)是一種極為少見的BCR-ABL陰性骨髓增殖性腫瘤(myeloproliferativeneoplasms,MPN),其特征是持續地外周血成熟中性粒細胞明顯增多、骨髓粒系增生和肝脾腫大,無髓系細胞發育異常形態改變和BCR-ABL1、PDGFRA、PDG-FRB、FGFR1重排。以往由于缺乏特定的分子標志,本病的明確診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仔細地鑒別反應性粒細胞增多和表現相近的其他髓系腫瘤,基本屬于排除性診斷。隨著2013年發現大多數患者具有集落刺激因子3受體基因(CSF3R)突變[1],并經嚴格定義的CNL中驗證,確認其為CNL發病分子基礎,2016年WHO淋巴與造血組織腫瘤分類中納入CSF3R突變作為CNL診斷主要指標[2],使得CNL不再是排除性的診斷,而成為一種形態學和分子遺傳學定義的髓系腫瘤。現就CNL分子診斷研究進展介紹如下。
1CSFR
CSF3R基因定位于染色體1p34.3,含有17個外顯子,編碼813個氨基酸的集落刺激因子跨膜受體,為粒細胞提供增殖和生存信號,并有助于其分化和功能。CSF3R是一單鏈細胞表面受體,屬于細胞因子受體Ⅰ型超家族,其胞質部分包括有不同的功能區,即近膜區域有絲分裂信號傳導,行使增殖功能;遠端區域羧基末端與成熟信號傳導有關,行使分化和增殖調節功能[3]。CSF3R與其配體G-CSF結合后,通過經典的下游途徑,包括JAK-STAT,SRC家族激酶(尤其是LYN),非受體酪氨酸激酶SYK、Ras/Raf/MAP激酶和PI3K/Akt通路發揮作用,誘導中性粒細胞分化、增殖、存活,并刺激中性粒細胞功能。研究證明CSF3和CSF3R在粒細胞生成過程起著非常重要作用,小鼠缺乏CSF和CSF3R基因缺陷可表現嚴重的粒細胞缺乏。在嚴重先天性粒細胞缺乏患者,除了明確的遺傳性致病基因(如ELANE或HAX1)突變外,有報道40%可伴有獲得性造血干細胞CSF3R胞質遠端羧基末端過早截斷的基因無義突變,通過與其它癌基因共同作用延長細胞生存,增加克隆優勢,被認為與高急性白血病轉化相關[4-5]。另外,CSF3R基因胚系突變尚可導致顯性遺傳的先天性中性粒細胞增多或家族性慢性中性粒細胞白血病[6-7],偶爾在急性髓系白血病也報道檢出這種類似突變。
2CSF3R突變與CNL診斷
為了查找潛在的分子發病原因,2013年Max-son等[1]采用原代細胞深度測序結合酪氨酸激酶特異的小干擾RNA或小分子激酶抑制劑作用的方法,對傳統臨床診斷的CNL和不典型慢性髓系白血病(aCML)進行研究,27例患者中16例(59%)檢出CSF3R突變,其中9例CNL患者中8例(89%)檢出CSF3R突變,均涉及位于外顯子14的胞外近膜結構域點突變,7例(78%)為CSF3RT618I突變,1例為CSF3RT615A突變。這些近膜結構域點突變單獨發生更為多見,少部分與另一類導致CSF3R胞質尾部過早截斷的移碼突變或無義突變共同存在,形成復合突變。胞外近膜結構域點突變和胞質尾部過早截斷突變兩種類型突變分別通過下游JAK-STAT通路和SRC酪氨酸激酶通路介導,均具有體外轉化能力,并相應地對激酶抑制劑蘆可替尼和達沙替尼呈現不同敏感性。以CSF3RT618I表達的造血細胞進行移植,小鼠發生致死性的MPN,表現為突出的成熟粒細胞增多、骨髓明顯活躍和肝脾成熟粒細胞浸潤[8]。Pardanani等[9]在按照嚴格WHO標準診斷的12例CNL患者中更是100%檢出CSF3R基因突變,10例為CSF3RT618I突變;而aCML、漿細胞病相關CNL、原發性骨髓纖維化癥(PMF)和慢性粒-單細胞白血病(CMML)患者無一例檢出該突變。這些均表明CSF3R突變在CNL非常常見,是CNL一致性的生物學特征;CSF3RT618I是CNL敏感而特異的分子標志,應納入CNL診斷標準。2016年修訂的WHOCNL診斷標準將CSF3RT618I和其他激活突變納入診斷[2],即:①外周血白細胞計數≥25×109/L,分葉核+帶狀核中性粒細胞≥80%,前體中性粒細胞(早幼、中幼和晚幼粒細胞)<10%,原粒細胞少見,單核細胞<1×109/L,無粒系形態發育異常;②骨髓增生活躍,中性粒細胞比例及數量增多,中性粒細胞形態正常,原粒細胞占有核細胞比例<5%;③不符合WHO定義的BCR-ABL1陽性慢性粒細胞白血病(CML)、真性紅細胞增多癥(PV)、原發性血小板增多癥(ET),或原發性骨髓纖維化(PMF);④無PDGFRA、PDGFRB或FGFR1基因重排,無PCM1-JAK2融合基因;⑤CSF3RT618I或其他活化CSF3R基因突變,或持續性(≥3個月)的中性粒細胞增多、脾腫大,且沒有可識別原因的反應性中性粒細胞增多,包括無漿細胞腫瘤,或者如果存在漿細胞病,須有髓系細胞細胞遺傳學或分子學研究證實的克隆性證據。
3繼發性或反應性粒細胞增多的排除更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