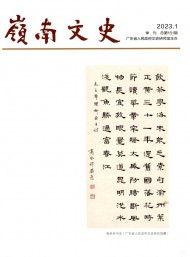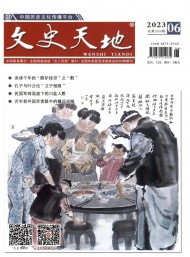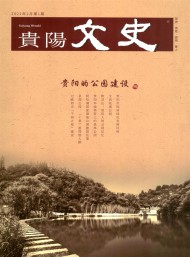文史之學范文10篇
時間:2024-03-26 10:34:59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文史之學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探究論文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論文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文史之學與經史之學分析論文
【提要】該文從史學與經學、史學與文學的關系著眼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學的發展。提出了如下的觀點:第一,魏晉時期史學雖然從經學當中獨立了出來,但事實上二者仍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史學從經學那里,尤其是古文經學那里繼承了許多東西。第二,這一時期史學與文學也有著密切的聯系,直到南朝,文與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確劃分。不過,這主要不是因為人們對史學有了更多的認識,而是由于文學獲得了迅速發展,從而將“史”從“文”的領域排斥了出去。該文的特點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學史的演變,而是試圖將其置于更廣泛的學術史的背景下來加以考慮,在注意學術分化、演變的同時,也注意到了學術發展的連續性、繼承性。
【關鍵詞】經史、文史、史學、魏晉南北朝
較之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不論是史學著作的種類還是數量都大大增加了。《隋書·經籍志》史部所列史書共計十三類,即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系、簿錄。其中,每一門類除開頭一種或少數幾種為三國以前著述外,幾乎全部都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著作。[1]史學的發展不是孤立的,它與同一時期的經學、文學都有著密切的關系。本文以下將圍繞著經史之學與文史之學這兩條線索展開討論,以期把握史學發展的脈絡。
(一)
這一時期史學發展的最大特點莫過于史學學科的獨立了。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依據西漢末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把《國語》、《世本》、《戰國策》、《太史公書》等史書都附于《春秋》經之下,史學沒有獨立的地位。但是到晉代,情況發生了變化,西晉荀勗作《中經新簿》,分書籍為四部,史學著作為獨立的一類,屬丙部,東晉李充又改定次序,將其置于乙部。《隋書·經籍志》不用乙部之說而謂之史部,實質并無變化。
史學著作在圖書分類上的變動不是沒有原因的。梁代阮孝緒編制《七錄》,其一為經典錄,其二為記傳錄。他解釋說:"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眾家紀傳倍于經典,猶從此志,實為蘩蕪"。[2]阮氏所說有一定的道理,從漢末至梁代,史籍數量確實大增,別開一類,勢在必行。但是在西晉,新的史著并不是很多,恐怕還不能這樣解釋。
浙東史學研究論文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浙東史學研究論文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浙東史學研究論文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章學誠的學問觀研究論文
摘要:章學誠在乾嘉考證學盛行之時,提出了獨特的學問觀,對繁瑣的考據學風有所糾正和補救。章學誠的學問觀是以“學問”和“功力”之辨為基礎,以“性情”而入,“博”與“約”的相互結合,達到對“道”的全知,最終以“貴開風氣”、“去弊而救其偏”的經世致用為目的。他的學問觀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章學誠;學問觀;清代學術
章學誠(1738-1801)論學貴“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義》中對學術多有獨特的見解,呂思勉即評日“精深透辟,足以矯前此之失,而為后人導其先路者甚多”。他結合自我的為學經驗對“學問”與“功力”作了精辟的論述。章學誠逆乾嘉考據學風明確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學主張,對后世學者有著很大的啟發意義。
章學誠處在乾嘉學術鼎盛時期,其時考據之風盛行。以戴震和錢大昕為首的學者提倡“經學訓詁”的學術方法,試圖通過“詮釋古訓,究索名物”以達到對六經的徹底而正確的解釋。章學誠反對這種皓首窮經、無關世事的學術方法和學術態度,認為學術應該“經世致用”,提出“文史校讎”的治學途徑。與主流學風的格格不入使章學誠的學術在當時不能彰顯和光大,正所謂“生時既無灼灼之名”。然而正是處在當世學風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學界的弊端和隱患,“實齋著《通義》,實為針砭當時經學而發”。針對當時的學風,章學誠在書中提出了自己的學術主張和心得。
一、功力、學問與性情
“功力”和“學問”之辨是章學誠學問觀的出發點。他認為“功力”和“學問”是不同的,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同時又有著顯而易見的差別。“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博約中》)學問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積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當成學問,“指功力以謂學,是猶指秫黍以謂酒也”(《博約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學問”的本質區別:兩者之間要有一個轉化的過程,更存在一個實質性的轉變。在他看來“博學待問”并不是學問,“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學問。著述之難前人多有論述,如顧炎武《日知錄》十九卷中有“著書之難”條專門討論此問題,他認為《呂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書不過是“取諸子之言匯而成書”,“今人書集一一盡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呂覽》、《淮南》之類耳”。其所持觀點與章學誠的“纂輯”和“著述”很相似。“纂輯”指“搜羅摘抉,窮幽極微”,“著述”則指“專門成學”(《博約中》)。“纂輯”雖然是博聞強識之學,但它只是記誦之學,沒有達到由博而返約,它只是學問的一個階段,而非終點,只是求學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轉化成“學問”,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性情”,“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謂學問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謂有美質而未學者也”(《博約中》)。每一個學者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性情”,好的“性情”就是“美質”,要以功力深之才能有所成就。
捐資辦學思想實踐管理論文
摘要:近代,資本主義國家紛紛輸入宗教文化制度,進行文化侵略,寧波等五個通商口岸首當其沖。吳錦堂,作為早期海外寧波華商的僑領,不忘故國鄉土,在日本發家致富后,積極投入到救國的運動中去。他先后在日本、寧波捐資創辦華僑學校、錦堂學校等近代新式學校,在捐資辦學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辦學特色。本文就吳錦堂捐資辦學的實踐,試其辦學特色、動因及其。
關鍵詞:近代中國吳錦堂辦學思想辦學實踐
Abstract:InthemoderntimeofChina,thecapitalistcountriesexportedwesternreligionandcultureinstitutiontoChina,doingculturalaggression.SometradingportssuchasNingboencountereditfirst.AsaleaderofearlyNingbooverseasChinese,WujintangsetupaoverseasChineseschoolinJapanandJintangschoolinNingbo,takingpartinthemovementofrescuingChinawitheducationpositively,andformedhisownfeaturesofrunningaschoolintheprocessofinvestingeducation.ThisarticleisaimedatWujintang''''spracticeofinvestingineducationtostudyhisfeaturesofrunningaschool,thecauseofrunningaschoolandtheeffect.
Keywords:ModerntimeofChinaWuJintangIdeologyofrunningaschoolPracticeofrunningaschool
鴉片戰爭后,寧波被迫開放,西方列強紛紛在甬開辦教會學校,進行文化的侵略。面對這種局面,寧波一批有識之士為謀求育才圖強,抵御外來侵略,紛紛捐資創辦各類新式學堂。他們為近代寧波的教育事業,特別是近代新式學校的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當時,在國內最著名的有陳謙夫1、葉澄衷、“海上聞人”虞洽卿、巨子秦潤卿等人;而在海外,最為積極的應首推旅日華商吳錦堂。
吳錦堂,原名吳作鏌,1855年11月14日生于慈溪北鄉一個賓海小村東山頭張家村(今觀城鎮西房村)。吳錦堂早年家境貧困,后在上海做幫傭,1885年在友人的幫助下東渡日本。因經營有道,資財達百萬日元。吳錦堂作為海外寧波商人的僑領,先后在日本和寧波捐資辦學,為中國近代教育四處奔走出錢出力。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國職業教育社”在評論中就把吳錦堂列為“辦學三賢”之一,與陳嘉庚、聶云臺齊名。本文就吳錦堂對中國近代教育作出的貢獻,試分析其辦學特色及其動因。
章學誠的易學研究論文
《文史通義》開卷的《易教》上、中、下三篇,是章學誠史學理論的基礎;另外,在全書一些重要的章節中,章學誠以易理闡發對史學的認識,對歷史的見解,這些認識與見解也是章學誠史學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要從深層次上認識章學誠史學的特點,應當討論章學誠的易學認識。
章學誠的易學見解
《四庫全書總目》的作者,把中國兩千余年的易學變化,概括為兩派六宗。象數與義理兩派經歷一系列變化。古代易學到兩漢,發生了變化,“一變而為京(房)焦(延壽),入于@①詳;再變而為陳(摶)邵(雍);務窮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頤)子,始闡明儒理。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又參證史事。易遂啟其論端,此兩派六宗,已互相攻駁。”[1]在這兩派六宗中,李光、楊萬里言易理參證史事,他的《誠齋易傳》以史事言窮通變化,在易學諸家中顯示出自己的特點。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易》的形成,本來與古代史官的活動結下了不解之緣,《易》的經與傳的思想,與古代史家對自然、對社會認識,又是密切不可分的。因此,無論哪一派、哪一宗,在解《易》時,都不可能沒有一點歷史的影子,都不可能完全脫離歷史解《易》。即使從現象上看,宋學家程頤重經輕史,但他的《程氏易傳》,言《易》理,談社會變革問題,提出要“順理而治”時,同樣是與歷史經驗思考結合在一起,這是其一。其二,楊萬里在易學史上的特點,是“參證史事”言《易》理,而真正地以易學的通變思想,對歷史盛衰變化提出精到的深邃認識,在西漢是司馬遷,在明清之際是王夫之。不能把他們歸之于象數派,但說他們是義理派也不很貼切。這不是兩派六宗所能概括得了的。
章學誠提出他的史學觀點往往與易理的闡釋結合在一起,是他史學理論的重要特色。他提出很多重要的易學見解,在易學史上應當有一定的地位。
章學誠的易學見解,主要的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中國哲學的特質分析論文
由于中國傳統中本無“哲學”一詞,“哲學”一詞日本哲學家西周對philosophy一詞的翻譯而由我們加以引進,所以現代中國哲學家始終有對中國哲學身份的焦慮。近年來關于中國哲學合法性問題的討論,正是這種焦慮新的又一次體現。
在一般人看來,中西哲學的區別顯而易見,根本不需特意加以區分。其實不然。由于中國人是在西方哲學的影響下對古代中國哲學開始研究的,自然而然會比照西方哲學的樣子來理解和重塑中國哲學。明明知道中西哲學有重大的不同,中國哲學不是西方哲學,可是在實際研究時卻往往不自覺地以西方哲學的問題、形態、范疇和概念來論述和要求中國哲學,結果是邯鄲學步,失其故步。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因為西方哲學以本體論(ontology,應譯為“存在論”)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所以我們也要在中國哲學中找出本體論,卻不知將ontology理解為“本體論”本身已經錯了。Ontology是對“存在”的研究,而在中國古代哲學中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因此,中國古代根本就不可能有存在論。但由于首先將ontology誤解為“本體論”,因而以為既然宋儒那里已經有了“本體”概念,中國哲學當然有本體論。殊不知傳統中國哲學的“本體”概念與西方哲學的存在概念根本不是一回事。
再比如人們在談論中國傳統哲學時開口“主體”,閉口“主體性”,甚至認為中國哲學的基本特質就是主體性。例如,牟宗三在《中國哲學的特質》一書中就說,中國哲學的特質“用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話來說,就是中國哲學特重‘主體性’與‘內在道德性。”[1]勞思光認為哲學或歸于主體性,或歸于客體性。“中國哲學傳統中,誠然有宇宙論,形上學等等,但儒學及中國佛學的基本旨趣,都在‘主體性’上,而不在‘客體性’上。”[2]這種對中國哲學特質的認定是成問題的。
“主體性”(subjectivity)并不像那些先生所想象的那樣,是一個哲學的普遍原則;而是一個非常西方的概念。并且,它在漫長的西方經歷了幾次重大的變化。主體性這個概念是從主體(subject)這個概念派生的。現代西文中Subject(主體)這個概念來自拉丁文subjectum,,而它又是希臘詞hypokeimenon的拉丁文翻譯,意思是“支撐者”,在中世紀經院哲學中,這個詞指屬性的承載者。這個意義上的主體的意思近于Substance(實體)。因此,在邏輯推理當中,它又是一切謂語的主語(支撐者)。到了近代,從這里引申出靈魂或精神是一切意識狀態的承載者或支撐者的意思。根據這種用法,主體是指意識的統一性,與“我”或“自我”基本同義。主體性概念就是建立在這個起源于17世紀的主體語義上,換言之,它建立在主體的一種特殊的(近代西方哲學)語義上。康德是這種主體和主體性概念的最后完成者(上述港臺哲學史家心目中的主體性基本是康德意義上,也就是近代西方主體性哲學意義上的主體性)。黑格爾和馬克思盡管也使用主體和主體性的概念,但正是從他們開始,主體和主體性概念在西方哲學中開始了它們自己的去主體或結構過程。一個世紀以來,主體性的衰落早已是現代西方哲學的標志性景觀,論述主體性衰落或“主體性的黃昏”的著作汗牛充棟,不絕如縷。一個多世紀的西方哲學家對主體性概念的批判,使得主體性哲學內在隱含的問題暴露無遺,也使得17、18世紀西方哲學的主體性概念注定只是一個歷史的概念,而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學的普遍原則。
近代西方哲學的這兩個基本概念的產生不僅與西方哲學本身發展的理路有關,也與近代西方科學文化的發展有關,飽含這方面的內容。除此之外,還與西方語言嚴格區分主謂語有關。而漢語由于“沒有分明的動詞,所以謂語不分明,而因為謂語不分明,遂致主語不發明。主語不分明,乃致思想上‘主體’(subject)與‘本體’(substance)的概念不發達。”[3]所有這些決定了中國傳統思想中不可能有“主體”和“主體性”這樣的東西。我們不能用中國哲學中沒有的東西來表明中國哲學的特質。
有趣的是,幾乎沒有一個中國哲學的寫作者和研究者會不強調或不承認中西哲學的根本不同。然而,這種承認的基本模式一直沒有擺脫近代那種比較簡單機械的做法,就是先指出西方哲學的特點,然后中國哲學一定與之相反。如西方哲學重思辨,中國哲學重實踐;西方哲學重知識,中國哲學重道德;西方哲學追求的是知識的真理,中國哲學追求的則是超知識的真理;西方哲學重分析,中國哲學重直覺;西方哲學求客觀世界的真相,中國哲學求內圣外王;西方哲學的核心觀念是自然,中國哲學的核心觀念是生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總之,彷佛上帝有意安排,中西哲學總是反向而行。這種獨斷機械的對中西哲學特征的對舉概括,幾乎沒有一個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