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跨性別表達研究
時間:2022-11-16 03:18:16
導語:電視劇跨性別表達研究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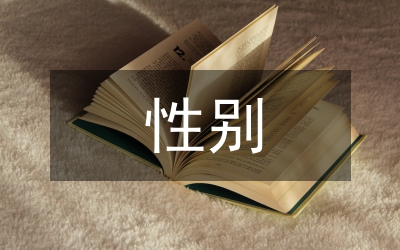
摘要:隨著性別議題越來越多地在公共空間討論,跨性別作為性少數(shù)群體的媒介生存環(huán)境與社會權益也得到了更多關注。本文以電視劇中的呈現(xiàn)的跨性別形象為研究對象,分析其人物形象與劇情設計上的特點,解析其背后的性別權利邏輯,從而反映跨性別群體的媒介權益與社會認知程度。
關鍵詞:跨性別;電視劇;呈現(xiàn)
電視因其大眾傳媒的屬性而擁有廣泛的受眾基礎和傳播影響力,在所有類型的電視節(jié)目中,電視劇的收視比重和編排時長一直穩(wěn)居第一。2015至2017年,電視劇收視比重以29.9%、29.2%、30.9%的比率穩(wěn)居收視市場第一,遠超其他節(jié)目類型。高收視、長時長意味著其受眾的廣泛與多樣性,因此與電影充滿個人敘事意味的“先鋒性”以及網(wǎng)絡自制劇的青年受眾定位不同,電視劇在價值觀呈現(xiàn)上往往具有更廣闊的面向和兼容性,能夠迎合大眾最基本的價值預設,體現(xiàn)一定時期內社會主流的價值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會的主要議題與價值觀的流變。1同時,電視劇能夠通過呈現(xiàn)社會議題,將價值傾向融入情節(jié)發(fā)展中,在潛移默化間將預設的價值判斷傳遞給受眾,從而產生一定的“教化作用”。因此,對電視劇中塑造的跨性別2形象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大眾對跨性別的認知程度以及電視媒體期望傳遞的態(tài)度傾向。本文選取2010年至今播出的收視率與網(wǎng)絡話題度較高的電視劇中的跨性別形象(此處的“跨性別形象”指人物在劇情發(fā)展中出現(xiàn)了性別形象的改變,在劇中同時出現(xiàn)其兩性裝扮形象,與電視劇角色是否與演員的性別匹配無關,即《武媚娘傳奇》中尼姑由男性扮演這種情況不屬于本研究討論的范疇)為研究對象,從劇集類型、跨性別人物形象與情節(jié)設置特點三個方行分析電視劇呈現(xiàn)跨性別形象的特點及呈現(xiàn)出如此特點的原因。
一、不同劇集類型對跨性別形象的呈現(xiàn)
從2010年至今熱播的電視劇中,本文選取十二部(系列劇合算成一部)電視劇(見表1)中的男性跨性別,即男扮女裝的人物形象為研究對象。由表格可以看出,男扮女裝的形象總體并不多,且以古裝劇居多,現(xiàn)當代都市題材中較少。古裝劇中的跨性別形象明顯多于時裝劇是因為服飾具有明顯的時代感,由于古代裝束不會在當下穿著,古裝劇中的跨性別扮演不具備現(xiàn)實中的可模仿性,因此受眾在消費的過程中也不會引起心理的不安與警戒。而時裝劇中的跨性別形象為了贏得受眾的青睞,穿著的都是符合當下流行時尚審美的服裝,這種可接觸、可模仿、可復制的跨性別形象更能引起受眾對性別本身的關注。因此,時裝劇中的跨性別人物形象與情節(jié)在設置上需更加具有特殊性,如扮演孕婦、穿著和服都是為了規(guī)避可能引起的效仿,而對于《把愛帶回家》中夏星塵的時裝扮相則需要通過大量表現(xiàn)身體不適應的特寫鏡頭與被揭穿遭辱罵的情節(jié)來實現(xiàn)對既有性別規(guī)范的回歸。
二、電視劇中跨性別人物形象——對女性特質的夸張性呈現(xiàn)
從人物形象上看,在電視劇中,當男性反串扮演女性時,從發(fā)飾、妝容(特別是眼妝與口紅)到衣著都會更換成時下具有明顯的女性特點的裝飾物,除潘長江所反串的中年女性(齊剪短發(fā))以外,其余的男扮女裝形象均是皮膚白皙、大眼紅唇、留長發(fā)、著裙裝的年輕女性形象,在當代都市劇中,甚至會穿上高跟鞋來增加女性氣質,如《把愛帶回家》中于朦朧扮演的夏星塵反串的女性形象即穿著高跟鞋。在拍攝上,鏡頭也會給予這些明顯帶有女性形象標簽的部位特寫。同時,人物或多或少在言行上也會刻意做出一些改變,如將聲音變得細而柔,增加肢體扭動而減少穩(wěn)重感,捂嘴而笑,拋媚眼或增加眨眼頻率,跺腳等,從而使自己的女性形象更具說服力。毫無疑義,這些言行裝束是符合大眾對當時女性形象的認知和審美預期的,電視劇在形象上對男扮女裝的形象是以美化為主趨勢的,扮演女性的男演員無論是男裝還是女裝扮相都廣受贊譽,劇中的男扮女裝形象幾乎總是能獲得其他男性角色的青睞和強烈的愛欲表達。媒體的報道中亦多采用“妖嬈”、“嫵媚”、“驚艷”等詞匯來形容這些男扮女裝形象,對于一個女性表征的人物形象來說,這無疑是正面評價。當這些“女性特質”被加諸于男性身體并受到大眾的認可,這也說明了社會性別表征的可建構性,即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之間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社會性別是可以被選擇和塑造的。同時,男演員在表演時并不是在對女性形象進行復制,而是帶有明顯的戲劇夸張。演員的別扭狀態(tài)給受眾傳遞出不自然、不舒服的暗示,而這種夸張成分也反映出演員本身所希望表達的抽離狀態(tài),即讓大眾意識到其中的“扮演”成分,這既是為了確保戲劇效果,畢竟如果表演得過于真實,讓觀眾無法立即反映出其男扮女裝的本質,男扮女裝所要達到的視覺沖擊與喜劇效果也就無從談起。同時這種夸張也是演員本身作為男性對女性形象的一種隔離,企圖消解掉性別扮演帶給觀眾的真實感和可信感,帶有對男女兩性界限的肯定。例如《天涯明月刀》中葉開的扮演者陳楚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扮演過女性后產生了障礙,“以后都不會再扮演女人了”。這種表演方式與論調讓傳統(tǒng)的性別規(guī)約反而得到鞏固。
三、電視劇中跨性別形象出場的情節(jié)分析
通過對研究所涉及的12部電視劇中跨性別形象出現(xiàn)的情節(jié)、戲份進行分析可以看出,其在情節(jié)設置上表現(xiàn)出一定的相似性,即跨性別扮裝形象的出現(xiàn)都是出于一定的功利性目的而非出于性
別認同需求,目的達到則換回原有性別裝扮,這也讓跨性別形象出現(xiàn)的時長極短。而對于整個故事情節(jié)的發(fā)展來說,這樣的情節(jié)段落也并非必須存在。(一)跨性別裝扮成為目的實現(xiàn)的手段。從電視劇情節(jié)來看,跨性別形象的運用通常出現(xiàn)在人物遭遇與性別相關的身份困境時,如《愛情公寓3》中呂子喬想進入酒吧須得打動門衛(wèi)保鏢,《怪俠一枝梅》中賀小梅必須轉移日本使者的注意,《古劍奇譚》里方蘭生想進幾乎只有男性的山寨探查真相,《美人制造》中張易之欲接近大臣以竊取機密,當諸如此類須以男性為引誘或轉移注意的對象,人物的男性形象無法在短時內取得信任,又無法找到合適的女性幫助者的情況下,劇中人物只好自愿或在同伴慫恿下扮作女裝。跨性別扮裝成為人物實現(xiàn)目的的手段而非個體性別認同的需求。而這種具有現(xiàn)實功利性目的的呈現(xiàn)方式會在無形中誤導受眾對實際生活中跨性別者的認知,讓受眾在審視現(xiàn)實中的跨性別者時自然地帶出某種目的猜想。這顯然是不利于跨性別社會接受度的提高。電視劇中的人物雖然都是出于非惡意性目的進行喬裝,但回到現(xiàn)實語境,大眾的跨性別特別是男扮女裝目的的認知卻存在非正當性目的刻板印象。現(xiàn)實中的跨性別者由于社會包容度低,大多處于“不可見”狀態(tài),受眾對他們的印象主要來自于社會新聞報道,而與“男扮女裝”、“變性”語素相關的報道中有不少是與“搶劫”、“偷窺”等犯罪行為相關。這是新聞在編碼上存在的非刻意性引導,但電視劇的情節(jié)編排方式顯然在一定程度上會加深受眾的這類聯(lián)想。(二)短時呈現(xiàn)背后的形象消費。由于男扮女裝通常被作為人物實現(xiàn)目的的手段,目的一旦達到,人物就會恢復男性裝扮。因此,電視劇中男扮女裝的人物形象持續(xù)的時間都很短,其戲份最多不超過10分鐘,并沒有像花木蘭女扮男裝入軍營這種長期裝扮成異性的形象出現(xiàn)。從文化上講,在古代中國,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的思想根深蒂固,男性在社會地位上有著天然的優(yōu)越性,朝堂、軍營是絕對的男性領域,明令禁止女性涉足,文學等領域也都是男性話語主導,女性所能扮演的社會角色也很少。時裝裝扮則更多地涉及到現(xiàn)實指涉與價值觀導向的問題。從四部設置有男扮女裝形象的當代都市電視劇來看,《愛情公寓》中曾小賢扮女裝是以戲中戲的方式呈現(xiàn),是存在于室友的想象中,而非曾小賢的生活中;《愛情公寓3》子喬的扮裝、《美麗的契約》中潘長江的反串以及胡歌飾演的鮑家明突發(fā)奇想扮孕婦都帶有明顯的喜劇成分。《把愛帶回家》中夏星塵以長發(fā)、套裝加高跟鞋的女性裝扮陪夏以沫參加選角則是唯一一個交代了男扮女裝被揭穿的后果的電視劇,且不論夏星塵坦然地身著女裝進男廁并不完全是現(xiàn)實跨性別者“衛(wèi)生間困境”的真實反映,被拆穿后不問緣由就被斥為“變態(tài)”、“人妖”的情節(jié),卻是表現(xiàn)出了社會對跨性別者的抗拒,也契合了電視劇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呈現(xiàn)與迎合的特點。正是由于這種必然的迎合姿態(tài),電視劇的編創(chuàng)無法在長時間的跨性別人物刻畫中既不觸碰傳統(tǒng)的性別觀念,又不引起關于性別歧視的爭論。短時呈現(xiàn)成了最安全的消費方式。同時,短時呈現(xiàn)讓電視劇對跨性別的處理停留在形象消費的層面,其所消費的僅僅是男扮女裝的形象,而不是跨性別這一性別文化。它將男扮女裝的形象作為消費賣點推向受眾,跨性別被當為狂歡元素使用,成為劇集強推情節(jié)高潮、制造話題、招徠收視的手段,而不是跨性別者現(xiàn)實困境的故事化呈現(xiàn)。這種短時呈現(xiàn)里沒有易裝的心理糾葛,沒有社會或同伴的不理解,沒有被識破的麻煩,有的只是對性別形象奇觀的消費,也消解了跨性別所具有的對傳統(tǒng)性別觀念的顛覆意義。受眾接收到的只是電視劇編碼后的狂歡圖景,而不是其背后承載的性別意義。這種意義消解式的呈現(xiàn)方式使電視劇既達到了消費跨性別的目的,又謹慎地不觸碰大眾關于社會性別規(guī)范的敏感神經(jīng),卻也能在不帶任何價值判斷的情況下降低大眾對跨性別的奇觀化認知。電視劇作為大眾媒介,其傳播特點決定了其對跨性別的呈現(xiàn)方式。在消費社會的邏輯下,隨著電視劇呈現(xiàn)的跨性別形象的增多,被娛樂的電視受眾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對跨性別的奇觀化認知,在時裝劇中的呈現(xiàn)也讓受眾意識到現(xiàn)實中跨性別存在的可能。社會性別的操演性在一次次的易裝中被反復論證,但按照性別刻板印象中對另一性別的想象而塑造的跨性別形象未必具有性別顛覆力,反而固化了社會性別的“理想型”,消解了多樣存在的可能。電視劇在跨性別者所涉情節(jié)的設計上表現(xiàn)出的帶有目的化色彩的短時間呈現(xiàn)是編碼者在消費文化與性別文化中選取的最優(yōu)路徑,其本質是創(chuàng)作者主觀上仍在傳統(tǒng)兩性觀框架下將跨性別視為“異化”而借以形成對比性戲劇沖突。這樣的呈現(xiàn)既表示了創(chuàng)作者對主流性別文化的歸順,又收獲了跨性別所帶來了消費意義。但也反映出電視制作者并未真正考量跨性別的性別意義而只是將其作為娛樂消費品呈現(xiàn)給受眾。
參考文獻
[1]卜衛(wèi).媒介與性別[M].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
[2]劉利群.社會性別與媒介傳播[M].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4.
[3]凱特•伯恩斯坦.廖愛晚.譯.性別是條毛毛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4]王周生.從男女平等到性別平等——當代婦女觀與“跨性別”弱勢群體[J].鄧小平理論研究,2006(8):73-76.
[5]張志安、沈菲.新傳播形態(tài)下的中國受眾:總體特征及群體差異(上)[J].現(xiàn)代傳播,2014(3):27-31.
[6]高慶.被集體圍觀的小眾:“偽娘”的個性表達與社會糾結[J].中國青年研究,2012(9):79-84.
[7]劉紀紅.性別觀的歷史演進與當代建構[D].河南:鄭州大學,2010.
作者:馮莉 單位:瀘州職業(yè)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