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文學產生背景及曲折道路
時間:2022-07-10 08:44:27
導語:網絡文學產生背景及曲折道路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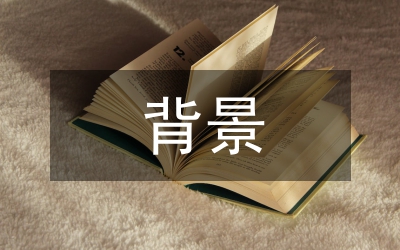
中國網絡文學誕生以來,歷經20年發展壯大。現已呈現出氣勢如虹、蔚為大觀的萬千氣象;而理應伴隨網絡文學創作共生共進的網絡文學批評和研究———網絡文學理論卻顯得薄弱和蕭條,底氣不足;且不說批評和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如何,就連一本普及性的“網絡文學概論”也沒有。對網絡文學的批評和研究,僅只零星地出現在網站的(微)博客和散見于專業文藝性報端或學術性期刊,遠未形成氣候。由此可見,作為網絡文學重要兩翼的網絡文學創作和網絡文學理論是極不相稱和極不平衡的。其實,穿越網絡文學迅猛發展的風光的一面,可以窺見文學界對網絡文學褒貶不一、爭論不休,甚至極端指責、質疑的尷尬的另一面;個別網絡作家因為糾結于不休止的“非文學”爭論,已經注定給自己的聲譽帶來損害。的確,圍繞網絡文字的文本知識和文本理論,從歷史的視角考察網絡文學的產生、網絡文學的身份含義和特征、網絡文學的現狀和發展,從比較的邏輯分析網絡文學的質量和水平、網絡文學的影響和價值、網絡文學的現存缺陷及其發展前瞻等,進行深入探討和研究,力求系統地詮釋網絡文學的基本知識和基本理論,正確地評估網絡文學的得失價值,科學地預見網絡文學發展的方向,不僅可以給讀者(網民)閱讀(瀏覽)網絡文學作品提供富于啟迪意義的理性導向,而且使從事網絡寫作的網絡文學作家由于受到理論界的關注而享受到應有的尊嚴,更重要的是通過卓有成效的研究構建有別于傳統文學而屬于網絡文學自己的美學標準和評價體系,從而給網絡文學的生存提供更加豐厚的土壤,同時也為網絡文學的健康持續發展開辟更為廣闊的道路,有利于網絡文學融入傳統文學的主流,并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更大的發展和繁榮。研究網絡文學的迫切性、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在于此。
一、網絡文學的產生———世紀之交的寫作革命
現代社會在本質上是一個由觀念形態向技術形態過渡和轉型的社會。在這里發生的每一項社會變革都和數字技術革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然而最終的主導者是網絡。當人類社會進入了文字、聲音、圖像三位一體的信息社會———網絡媒介時期,便意味著人類走進了網絡社會;是網絡社會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也深刻地影響并改變著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誕生于20世紀末葉、脫胎自傳統文學、對數字技術存在一定依賴并受網絡主導的網絡文學稱之為世紀之交的寫作革命,并未言過其實。實際上,從寫作方式、傳播方式到寫作觀念、寫作思維全方位的變革,都是網絡社會影響的結果;一言以蔽之,網絡文學是數字技術、網絡社會的產物。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有作家用電腦代替傳統的紙和筆進行寫作;雖然鋼筆換成鍵盤,稿紙換成了屏幕,但這樣的寫作和操作打字機沒有實質性差別,寫出來的作品還不能稱之為網絡文字。直到運用數字技術,在電的系統中,由若干元件組成特定的電路,使電的信號按一定要求傳輸,形成計算機網絡,后來又把電話和電腦連接起來,上升為互聯網,繼而產生了適合網絡特性的網絡語言、博客寫作、手機文學、手機報刊、數字出版等新技術新發明,通過自己開通的博客或微博寫作和發表,自認為質量好、有價值的作品,可以通過互聯網,輸送到文學網站發表,完成這樣一個過程,才真正成為一種新媒體寫作———網絡文學。那么,漢語網絡文學究竟何誕生?中國網絡文學的第一篇作品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事情要追溯到世紀之交的上個世紀90年代,當時“留學美國的中國學生嚴永欣、李楓峰分別開發出的漢字處理軟件‘下里巴人’和HZ漢碼網絡傳輸方案,解決了當時的計算機和網絡不支持漢字傳輸的難題。這是我們能看到的屬于漢語網絡文學界最重要的一項技術發明。也僅僅是依靠這項發明,以張郎朗登載在1991年4月5日全球第一份中文網絡雜志《華夏文摘》創刊號上的散文《太陽縱隊傳說》為起點,漢語網絡文學誕生了。”[1]由此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沒有數字技術,就沒有計算機網絡;沒有計算機網絡,就沒有中國網絡文學。說到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及一個剛離開這個世界不久的人:美國蘋果公司前董事長史蒂夫•喬布斯,是他對網絡技術作出了杰出貢獻,他于1983年發明電腦,1990年將電話與電腦連接起來,給我們創造了一個全新的網絡社會,從此改變了傳統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生存方式和思維方式,寫作革命的果實———網絡文學也就應運而生。網絡文學作為網絡文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一種新媒體寫作,是世紀之交發生的一場寫作革命。這場寫作革命從一開始便向本質主義文學范式發起顛覆性的沖擊,開拓了全民書寫和閱讀的新時代,由網絡虛擬空間搭建起的開放性公共平臺,完全拆除了文學作品發表和閱讀的門檻,把傳統和世俗一直視為專屬知識精英的神圣寫作事業一下子徹底地毫無保留地推向平民化和大眾化,讓底層民眾有了更多的寫作自由和閱讀(瀏覽)選擇,開放的文化話語權解放了文學生產力,憑借數字支撐的網絡空間圓了數以千萬計的草根文人的“作家夢”。于是,這里云集了自有文學史以來最為龐大的寫作隊伍、浩繁的作品存量和不勝其數的讀者群體,演繹了數字傳媒時代文學空前火爆的新神話,以致于歷來的文壇圣殿唯少數作家權貴獨尊的格局被斷然打破,不管人們愿意不愿意,這場寫作革命已經既成事實地導致整個文學界“舊貌換新顏”。中國網絡文學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初,起步于20、21世紀之交,經過短短幾年的蓄勢,現在已經跨越式地進入到發展的快車道。筆者認為,如果說媒介技術革命的崛起是網絡文學誕生的必備條件,那么社會公眾心理的演變則是網絡文學迅速發展的深層原因。當今的中國社會已經進入休閑時代,這一時代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公民的休閑訴求已成為占據社會心理主導地位的公共意識。在這種社會心理支配下,人們普遍崇尚一種自主、隨意、簡單、便捷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這恰恰與網絡的特性是吻合的。因此,人們對于網絡世界的東西,包括文字、聲音、圖片、游戲、動漫、音頻、視頻等有一種微妙的新鮮感、親近感甚至癡迷感;在休閑的心境下,遨游、消遣于虛擬的網絡世界,尋求精神上的愉悅、刺激和慰藉。只要是網民,不論是七八十歲的老人,還是五六歲的頑童,莫不如此。這就是較之紙質印刷的傳統文學,網絡文學更能滿足“底層”閱讀需要,因而也更受人們青睞的一個重要原因。除了崇尚休閑,這個時代還有一種典型的社會公眾心理,那就是崇尚娛樂。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人們,尤其是廣大民眾有太多的壓力、太多的訴求、太多的無奈。這是一個數以千萬的散戶因股票被套牢而悲催的年代,是一個數以千萬的打工族為維護合法權益、追求公平公正生活待遇奔走呼號未果而煩惱的年代,是一個廣大人民群眾為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問題而郁悶的年代……于是,人們不約而同地對娛樂性的生活方式趨之若鶩,目的是為了釋放生活造成的種種壓力。在這種社會公眾心理影響下,內容質樸、形式簡單、風格輕松的“草根文藝”、“快餐文化”、“網絡文化”成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需求,這其中當然也包括網絡文學。人們打開電腦,只需點擊幾下,就可以瀏覽到網絡作家上傳的各種風格類型的網絡文學作品,這是何等便捷、輕松、愜意的享受啊!誰還有心機多此一舉地手捧一本本紙張印刷的傳統文學作品去啃呢?由此,人們對傳統文學持輕漫、拋棄的態度也就不足為怪了。相反,卻為曲折中前行的網絡文學提供了一個順勢而上、迅速發展的契機,并開創了今天山花爛漫的局面。
二、網絡文學的曲折道路———與生俱來的身份之爭
中國網絡文學的誕生既然是一場寫作革命,那就注定了它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筆直的。正是由于中國網絡文學從它誕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以一種對傳統文學“離經叛道”的“革命面孔”走進人們視線的,“數字化”網絡傳媒在寫作、發表、流通、消費等各個領域環節的介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網絡”與傳統作家在生存樣式、工作方式以及審美標準等方面的重大分歧甚至對立;因此,針對網絡文學連同其作家的話題引發的各種爭論訖今為止并未消停,甚至對網絡文學的“合法身份”也曾一度產生重大質疑。關于網絡文學的最激烈、最尖銳、最持久的一次爭論,是借助于2009年12月16日至2010年6月12日,遼寧日報歷時半年,成功推出“重估中國當代文學價值”大型系列策劃這一契機,由于討論的深入而牽涉對網絡文學、網絡作家的爭論。持針鋒相對觀點的兩位代表人物,一位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另一位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后肖鷹。對于網絡文學和新生代作家的評價,向來褒貶不一。“陳曉明代表了一種溫和的肯定態度,肖鷹則是激烈的質疑方。陳曉明對中國當代文學和網絡文學持肯定和贊賞的態度,在國民普遍唱衰中國當代文學現狀的時候,他卻反其道高唱贊歌,認為中國當代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提出了四個方面的理論依據,列舉了幾位代表作家的名字:閻連科、賈平凹、劉震云、莫言等,“并聲稱:這個時代的文學讓我感到驕傲”。[2]而肖鷹卻針鋒相對地提出:“中國文學在走下坡路,現在作者比讀者多,文學僅僅是批評家和作者之間暖昧的自娛自樂,連基本的讀者群體都沒有;這是一個文學基本影響力都沒有的時代”,對陳曉明極力推崇的那幾個代表作家:王安憶、賈平凹、莫言、阿來、閻連科等,肖鷹表示對他們的創作現狀感到嚴重失望。肖鷹認為:“賈平凹代表鄉土文學的頹敗;阿來寫的與其說是文學,倒不如說是旅游招貼;賈平凹的《秦腔》,寫的是變態文學;而王安憶,從《長恨歌》之后就沉入到上海小女人式的自愛自憐的自我重復之中去了……”[2]不但言詞鑿鑿,而且幾近苛刻的程度,對這些被公認為中國當代文壇一流的作家不留一點值得肯定的余地。前面提到,陳曉明對網絡文學及新生代作家是一昧褒揚的,他在相關的公開場合,闡述了自己對網絡文學的幾個觀點:其一,網絡文學可能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個重要的生存方式;其二,對于網絡寫作,不應該有、也不可能有太高的標準;其三,如果批評家無視網絡文學,就等于自絕于這個時代;其四,韓寒、郭敬明預示著“后文學”時代的到來。“我一直積極評價網絡文學,因為它是文學民主化大眾化的一個廣大基礎,它的出現,具有很重要的積極的意義,有了這樣一個基礎,文學才能發展下去,才能冒出有價值的作品和面向未來的作品。”陳曉明認為,“韓寒是‘80后’中少有的有創造力的人物;郭敬明是他們這代人內心經驗深刻的體驗者和表達者。“80后”不僅是市場的幸運兒,他們也有他們的開掘和創造,他們的寫作和傳播預示著一個‘后文學’時代的到來。”[4]對網絡文學及其“作家”,質疑派肖鷹的看法與陳曉明截然相反。肖鷹認為:其一,網絡文學不是文學。在肖鷹看來,網絡文學是“前文學”。他說:“網絡文學并沒有經過準入程序,沒有獲得文學準入證。網絡是愿意怎么寫就怎么寫,同時,由于網絡是‘瀏覽’式閱讀,因此,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讀者,那些所謂在閱讀網絡文學的人,僅僅是在瀏覽,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閱讀。”在網絡上寫作就叫網絡文學,有些作家也許在廁所中寫作,難道我們也要搞一個‘廁所文學’嗎?‘網絡寫作’是有上網機會的公民表達的權利;文學寫作是真正的作家的能力”,“只有網絡寫作,沒有網絡文學”[2]。對網絡文學的身份持根本否定態度。公開不承認存在網絡文學的還不止肖鷹一人。就在最近,作家邱華棟在接受某報記者采訪時就公開表示:“文學只存在文學和非文學。因為文學只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不是以媒介來劃分的。認為到目前為止,我們的網絡文學絕大部分不是文學,是文字和文字垃圾。”[3]對于新生代作家,肖鷹的態度依舊是堅守純文學的標準,他直言:“我不承認郭敬明是個作家,他就是無靈魂的販賣文字的。”[7]對網絡文學及其作家存在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推崇備至,另一種是全盤否定。顯然,這兩種意見既有合理的成分,也有偏頗的地方。筆者認為,作為一種文體及其寫作實踐,網絡文學和網絡本身,的確也存在著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其一,網絡寫作離不開媒介技術,技術含量越高、越全面,通過網絡產生的作品文體就越成熟。目前的中國網絡文學對媒介技術的綜合運用還處于低端水平,網絡寫作還只是新媒體寫作的一種初級形態,其作品形式尚未成為成熟的文體。成熟的網絡文學文體應該是:新媒體依靠鏈接和互通,將構成網絡文學的要件———網絡語言、博客寫作、手機報刊、網絡閱讀、數字出版等集結構建成為一個集文字、圖像、動畫、視頻、音頻等各種符合系統于一身的敘述文體或抒情文體。客觀地說,目前的網絡文學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水準。因此,成熟網絡文體的優點和長處沒有得到充分體現,而不成熟網絡文體的毛病卻暴露無遺,這就難免會受到指責。其二、幾千年來,在中國文化權力制度中,紙媒印刷出版一直處于中心地位,形成了穩定、厚重、嚴肅的紙媒印刷文化情結,與根深葉茂的傳統文學結成不可分割的文化體系。傳統的精英作家歷來以創作嚴肅的傳統文學為榮,并以傳統的文學期刊或出版社(集團)發表或出版文字成果而滿足,對在網站連載發表的方式不以為然,因此,他們很少涉足網絡寫作;目前從事網絡文學寫作的多數是二、三流作家和數目龐大、魚龍混雜的網絡。這樣一來,倘若以傳統文學的評價標準衡量,現階段中國網絡文學的質量在總體上肯定偏低無疑。那么,人們對目前網絡文學的質量等問題提出非議也就理所當然了。其三,少數受到推崇和吹捧的網絡文學代表作家,行為不端、口碑不佳,雖然只是個別現象,但負面影響不小,有損網絡文學聲譽。以年版稅收入2450萬元登上2011年度中國作家富豪榜之首的郭敬明,當年以一部抄襲作品作為代表作申請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被網民譏諷為“郭抄抄”,這一不端行為使他再度成為爭議焦點,許多作家紛紛表示反對郭敬明加入中國作協。接著,“人造韓寒”、“海巖”等事端鬧得沸沸揚揚。韓寒對方舟子的起訴和撤訴,緣起一場“非文學爭論”,孰是孰非無關原則,只有閑得無聊和好奇心重的人可能感興趣;也許事件最后會以“不了了之”告終,但韓家父子的言行絕對不會是什么“文壇佳話”。還有一些網絡,商業化寫作的意識過于強烈,對網絡寫作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在利益驅動下,連篇累牘地生產質量低劣的作品,受到讀者的嚴肅批評。網絡文學和網絡作家本身現存缺陷和不足的問題當然不止這些,在后面的系列論文中還將系統地提出并作深入的分析。
三、對網絡文學的身份認可和資質接納
網絡文學盡管道路曲折,但依然不可遏止地頑強前行;作為一種尚未成熟的新的文學形態,它受到了開放包容的中國當代文學的接納,它的文學身份得到了官方機構、社會團體的支持和認可。承認和接納網絡文學,這絕不僅僅是一個身份概念的簡單取舍問題,它意味著網絡文學將在21世紀中國文學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包括我們在下文列舉的官方機構和社會團體對網絡文學支持和認可的一系列材料,也將作為寶貴的史料載入未來的中國文學史。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作出的《決定》,兩次提到要推動發展健康向上的網絡文化,制作適合互聯網和手機等新興媒體傳播的精品佳作,鼓勵網民制作格調健康的網絡文化作品。這當然也包括了作為網絡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網絡文學。這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發展格調健康、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和網絡文學的高度重視[4]。中國作協“全國網絡文學重點園地聯席會議”工作機構自2009年成立以來,定期召開有中國作家網、盛大文學、中文在線、新浪讀書頻道、搜狐讀書頻道等五家網站參加的聯席會議,關注和引導網絡文學創作[5]。魯迅文學院從2009年開始舉辦網絡文學作家培訓班、網絡文學編輯培訓班,至今已開班4期,加強了對網絡作家、編輯的培養[5]。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項目繼2010年首次將3部網絡文學創作選題列入扶持范圍給予經費上的支持后,2011年度該項目再度評選出攜愛再漂流《酒店風云》、聶丹《我們的青春》、劉英亭《暗斗》3部網絡文學創作選題和理論評論類項目《網絡文學寫作引論》給予重點扶持[5]。中國作協為構建網絡文學與傳統文學融合互補的平臺,架起網絡作家與傳統作家交流溝通的橋梁,組織開展了網絡作家與傳統作家“結對交友”活動,來自全國各地的18位知名作家、評倫家與來自7家網站的18位網絡作家結成“對子”。通過這一活動,傳統作家可以從網絡作家那里學習他們對生活的敏銳感受力和新鮮的、富有時代氣息的文學表現樣式,網絡作家也能從傳統作家那里學習他們更為嚴謹的創作態度等[5]。吸收網絡作家加入中國作協這一中國最高的作家機構。時至2011年,中國作協已吸收當年明月、唐家三少、笑看云起、月關、晴川、跳舞、酒徒、煙雨江南、千里煙等20多位網絡作家入會;其中唐家三少作為一名年輕代表不僅參加了第八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并且當選為中國作協第八屆全國委員會委員,成為第一位網絡作家委員[5]。為引導網絡文學創作、提升網絡文學的社會影響力,有關官方機構和單位連續組織開展網絡作品、手機文學等征文評獎活動。如:2011年4月27日,第七屆新浪原創文學大賽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頒獎典禮;主辦單位是新浪網、上海文藝出版社、新華傳媒集團、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收到各類稿件六千部,最終獲獎16部;新浪文學大賽自2003年舉辦至今,參賽作品數以萬計,從中走出了不少知名作者。2011年6月中旬,由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指導,北京市互聯網宣傳管理辦公室、北京網絡媒體協會主辦的“回顧90年歲月,紀錄點滴真情———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網絡作品征集活動”獲獎作品在京揭曉;此次活動,主辦方收到作品一萬多件,網民投票超百萬,總瀏覽量突破千萬人次,評出一等獎作品18件、二等獎作品60件、三等獎作品90件、優秀獎作品150件,產生巨大社會反響。2011年9月1日,由中國作協、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聯合主辦的“指尖傳遞紅色記憶”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手機文學征文獎在“中國作家館”舉行頒獎儀式。此次活動僅一個月,從全國各網站收到手機文學作品一千多件,探索了手機文學新的內容形態,也探索了紅色文化新的傳播方式,它推動了大量珍貴的紅色記憶在指尖傳遞和留存,也使很多作者實現了創作并發行作品的夢想。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書記、副主席何建明出席頒獎儀式并講話。目前網絡文學的盜版現象非常嚴重,中國作協始終如一反對盜版,積極參與打擊盜版,堅決支持網絡作家依法維護自己的正當權益。2011年7月15日,由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的“作家在線”網站正式上線。以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為代表的一批文學界領導、著名作家、評論家題詞,表示對網絡文學的大力支持并寄予厚望。他們的題詞分別是:鐵凝:讓文學和作家更具尊嚴和影響力王蒙:關注網絡關注文學何建明:作家至上文學至上雷達:未來的好文學必將在網絡的海洋上揚帆遠航葉辛:網絡文學的明天更美好張抗抗:好作品常在線張賢亮:新時代新文學新的傳播方式①一些省市作家協會、黨委宣傳部門也加大對網絡文學的指導、關心、支持力度。如廣東省作協積極吸收網絡作者入會,創辦《網絡文學評論》雜志等。最后鄭重列舉的一項是: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公開向網絡文學征集參評作品。中篇小說《網逝》入圍魯迅文學獎;《從呼吸到呻吟》、《遍地狼煙》、《青果》、《成長》、《國家脊梁》、《辦公室風聲》、《刀子嘴與金鳳凰》等7部長篇小說入圍茅盾文學獎,這意味著傳統文學對網絡文學的身份認可和資質接納[5]。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認為:“如果批評家無視網絡文學,就等于自絕于這個時代,網絡文學的未來是不可限量的。”[2]作為一個文化學者,我持同樣的觀點。也許隨著媒介技術革命的推進和人的全面發展,未來的網絡文學可能千變萬化,不可端倪,但它的成熟和輝煌是必定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