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權利論文:城市化的農民權利及保障透析
時間:2022-02-19 09:58:38
導語:農民權利論文:城市化的農民權利及保障透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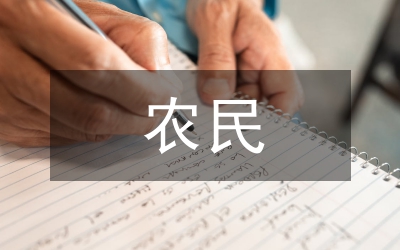
本文作者:高新軍工作單位: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
農地征收中農民權益的保障更多體現為官民博弈的結果
在我國城市化過程中,既保護好農民的權利,又適應城市化的發展,一直是我們追求的雙贏目標。其中,制度化一般被公認為解決問題的主要手段。但筆者在調查中發現,這些制度要真正起作用,則是官民博弈的結果。這種博弈既顯示了農民在博弈中不斷成長的過程,也反映了我國制度變遷的規律。一般認為,制度化是各種社會集團實現自身利益訴求的正常和理想的規范化渠道。這種制度包括各種法律、規章、政府政策等是以明確形式確定下來的,并通過一定法定程序被立法和權力機構批準,向社會公布的正式制度。在中國目前的轉軌時期,人們大多認為推進制度的不斷演變,對于中國實現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非常重要。同時,我們也在社會實踐中發現,盡管自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正式的制度已經有了巨大的發展,但令人遺憾的是,制度的執行卻相差很遠。而且這種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顯然,如果我們不能找到使制度真正起作用的關鍵環節的缺陷,并實際工作中加以改進,那么這種“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局面就仍會長期存在,并實際增加對我國成為現代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阻力,甚至可能造成轉軌的失敗。那么,在什么條件下制度才能真正起作用呢?這顯然與制度所約束的社會各方的力量對比有密切的關系。在這里,實際上存在著這樣一種現象:監督的邊際效用等于制度效用的臨界點。這里的監督,是指制度所約束的社會各利益集團之間的相互關系,實現這種監督必須完全建立在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和平衡上。因此,如果社會利益集團關系中出現不平衡,即出現某一集團權力十分強大,而其他相關方力量十分弱小時,制度是不會被遵守的。這時,無論權力強大的一方是地方政府、利益團體,還是普通民眾,都概莫能外。同時,社會各利益集團在博弈中,相互監督的邊際效益正是制度發揮作用的臨界點,也就是說,超出了這一邊界,不僅監督的效益呈下降趨勢,而且制度也不會被遵守,并開始失去作用。我國的制度變遷就是在這種平衡、平衡的打破、又建立起新的平衡的循環往復的螺旋式上升運動中,逐步實現的。我國目前在建立服務型政府、公共財政、信息公開、制度創新及其可持續發展等很多方面面臨的制度瓶頸,恰恰就是在實現社會各利益集團博弈、力量平衡和監督方面,存在著缺陷。筆者近期在對浙江溫州、安徽淮北、重慶忠縣和開縣、內蒙巴彥淖爾市臨河區關于城鎮土地征用的調查證明了這一點。目前,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十分迅速。由此帶來的城鎮土地征用方面的矛盾和問題也成為了社會關注的熱點。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反映出來的制度化矛盾與問題,有鮮明的典型意義和方法論上的指導作用。對這個問題的剖析有助于對我國制度變遷軌跡的理解和認識。在調查中,浙江溫州在土地征用和城市化方面走在了前列。②目前溫州已經基本完成了城市化的過程。一個明顯的跡象是,溫州目前已經沒有可供征用的土地了。溫州市在土地征用上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③:第一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由于市場經濟處于起步階段,用地沒有指標控制,用地政策比較寬松,地方政府在征地上所擁有的權力幾乎是無限的,農民基本上處于被地方政府任意擺布的地位。對農民的安置主要是安排工作,戶口遷為城市居民。第二階段從90年代末到2005年。由于1999年新的《土地管理法》出臺,房地產業開始啟動,建設用地開始趨于緊張,安置用地指標的價值開始顯現,農民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逐漸增強,與政府開始就土地征用補償進行博弈,并且開始迫使地方政府和企業在利益方面對農民的要求進行價外補償。這個階段的土地補償形式主要是貨幣補償為主。第三階段從2005年至今。隨著溫州市土地價格的飛速飆升以及國家對土地管理的日益嚴格,農民與地方政府之間在土地問題上的博弈,開始進入了一個力量相對平衡的時期,即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方面不僅要面對中央政府的督查,而且要面對強大民間力量的對抗。過去地方政府常用的強力措施在這時已經大為削弱,農民、企業和地方政府此時都希望能夠在現有法律政策的基礎上,進行協商,用法律和政策來約束對方,實現三方的共贏。在調查中,當地官員也承認,當地方政府在征地問題上擁有幾乎無限的權力時,他們是沒有動力去遵守有關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規定的。最初對農民的補償主要就是安排工作和將戶口從農村遷往城市以及給予失去勞動能力農民的部分貨幣補償。當1994年以上補償措施失去作用后,貨幣補償就成為了主要的形式。也就是從這時開始,1999—2004年,溫州各級地方政府拖欠農民的征地款10億元,占整個征地補償款的1/8。對農民土地的剝奪還以多種形式存在:2004年溫州有開發區47個,實際批準的只有21個,26個未批準的開發區中還有15個未備案。1999—2003年,批準征用土地27萬畝,實際征用數字是它的三倍,包括1/3的道路建設、1/3農戶違章建設、1/3的開發區建設用地。地方政府違規通過低價收購儲備農民的集體土地,用以今后高價出售。如2005年樂清北白象鎮貸款一個多億,收儲農民土地5000余畝計劃建設園區;洞頭縣在出臺片區綜合價之前,大肆收購儲備農民集體土地,面積達該縣前五年報經征用土地的三倍,并強迫農民領取“征地款”;另一個縣也用建設經濟開發區的名義,收儲和預征農民集體土地2655.8畝,而支付的“征地補償費”僅為規定金額的50%—70%。此種對農民土地權益的強勢剝奪,大多是地方政府與當地村干部聯手實施的,這也引發了不少村干部的腐敗行為,激起了廣大農民的反抗,甚至引起了社會的動蕩。顯然,農民并不會對此種剝奪熟視無睹和長期忍受下去。他們也在采取各種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利益。價外補償就是其中的一種。當農民對土地征用補償感到不滿時,他們通常的做法是通過阻攔施工來獲得價外補償。例如,1999—2003年瑞安市征地的標準補償為每畝3.7萬元,但安陽街道征地實際補償款到村最少要每畝5.7萬元,其中2萬元為土地填方費用。實際上,被征地農民收到填土方的款項后,并不會去填,最終還是要用地單位去填。但是如果不交這筆錢,用地單位就無法進場施工。瑞安市1999—2003年五年間征地標準補償總額為99065萬元,實際到村委會賬戶的征地款達192240萬元,額外補償達93175萬元,實際補償水平超過標準補償金額的94%。這種現象在溫州非常普遍,而且到后來逐漸演變為農民和村委會對開發商和地方政府的敲詐勒索。由此,地方政府和開發商也需要用法律法規和政策來約束農民和村委會的非法要求。④為了協調農民、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補償方面的矛盾,除了需要各方都能夠按照法律法規和政策來辦事之外,溫州也創造了一些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辦法。其中,用位置較好的城鎮宅基地置換農民的承包地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種存量土地的調整方法,農民把自己的承包地讓出來,以換取在城鎮里面積小很多的宅基地,多出來的土地就成為了地方政府和開發商的可使用土地。用這種辦法,農民可以獲得價值很高、面積較小的宅基地,并可以在城市經商、居住,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得到的則是多出來的承包地。顯然,在城市化和市場經濟較之內地率先發展的溫州,其在農民土地征用補償方面的經驗教訓,對于我國中西部地區是有借鑒意義的。筆者在重慶市忠縣調查時,就發現當地在如何處理農民、開發商和地方政府關于土地征用的問題上,有了與溫州類似的創造。⑤這種被稱為“地票”的制度創新的含義是:地方政府通過政策鼓勵和支持農民建設“巴渝新居”,將分散的農民住房相對集中起來,新建房按照“巴渝新居”的圖紙進行施工,這就將節省出一部分宅基地的土地,這些節省出來的土地集中起來后,可以拿到重慶市的“土地交易所”掛牌交易,土地交易收益在扣除了成本后,每畝地當地鎮政府可以得到5.4萬元。2009年筆者調查的忠縣三匯鎮就通過這種土地整理,得到400畝地,準備在2010年拿去進行交易。農民建“巴渝新居”則可以得到政府的各種建房補助,包括:每人5000元;每戶3000元;磚混結構住房每平米補助150元;磚木結構每平米補助80元;土木結構每平米補助50元。積極搬遷建房還在以上基礎上再獎勵5%。當地政府通過這種做法來實現農民、開發商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和補償方面的三贏。在保護農民利益方面,筆者在安徽淮北市⑥和內蒙古巴彥淖爾市⑦看到的農民土地征用補償情況,都比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七八年好了許多。失地農民普遍得到了養老保險,征地補償金也有了大幅度提高,盡管還有不少不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有關利益集團都開始學習在法制軌道上,依法來解決彼此的利益分配關系。這顯示出,經過30多年的市場經濟發展,民眾的力量逐漸取得了與地方政府談判的地位,雙方力量開始向均勢方向發展,這是值得我們期待的。筆者在很多地方城鄉統籌綜合發展試驗中,都看到了地方政府對農民財產權等權利的敬畏。這種制度創新是否可持續呢?地方政府能否在沒有民眾直接選舉的壓力下,在一輪又一輪地方經濟發展的浪潮中,持續尊重農民的財產權等權利呢?換句話說,如果一些地方政府確實做到了這一點,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們尊重了農民的財產權和權利?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能夠看到的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尊重農民的權利,實現社會民主、科學發展,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亟待突破的制度瓶頸。長期以來,在經濟領域調整政府與資本的關系方面,中國有了長足的進步,其核心是我們終于承認了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但是,在社會轉型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在如何加快社會建設、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正義方面,或者說,在處理好與人民的關系上,進步較小。所以,當改革進入深水區后,這種一快一慢的不協調狀況,很快成為矛盾的焦點。對于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農民來說,如何保護好他們的權利,激發他們的參與意識,使他們真正成為與其他社會成員地位平等的公民,顯然關系著我國改革開放成敗的命運。歷史發展規律告訴我們,要想實現可持續發展,就必須在尊重農民權利的基礎上,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而農民的所有權利都是建立在土地產權基礎上的。目前一些地方政府的制度創新,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順應了時代的要求,滿足了農民的愿望。可以看到他們在歷史潮流方面的自覺和主動。二是地方官員在實踐中認識到,尊重農民的財產權等權利是一個雙贏的結果。強大的政府權力在中國始終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提高辦事效率;也可能超越邊界,管了它不該管的事;還可能由于缺乏監督,為政府官員留下貪污腐敗的空間。長期以來,各級政府大都在扮演無限責任承擔者的角色,如果這種狀況長期下去,不僅政府將不堪重負,而且現代公民社會的發展也將遙遙無期。現在,城鄉統籌綜合改革試驗在農民的財產權等權利方面實現了突破,破解了長期困擾農民增收、農村公共服務、農民權利保護、農民參政議政、農村社區建設等一系列問題。政府在這個過程中密切了和農民的關系,實現了多年的施政目標,促進了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縮小了城鄉差別和貧富差別。顯然,這是一個雙贏的結果。民主政治在社會資源分配中終于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地方干部也在實踐中嘗到了民主執政的甜頭。三是農民的權利意識,隨著城市化進程和土地流轉,已經逐步覺醒。農民已經開始組織起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中國社會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長期的城市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城市和農村都要經歷巨大的變遷。對于城市來說,大量農民進城成為新市民,面對權利的不平等,這些新市民會為自己爭取平等的權利。對于農村來說,土地流轉凸顯出土地作為農民財產和收入的重要性,也激發起農民組織起來,在與實力強大的公司談判和與政府的對話中,爭取自己的話語權。這些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農民議事會”、“土地股份合作社”,在維護農民利益,搭建土地流轉平臺,參與土地流轉談判,解決農民內部糾紛等方面,都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可以想見,這還只是農民組織的初級形式,隨著我國農村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這種組織還會有更高級的形式,實現全鄉、全縣的聯合。有恒產者有恒心。當有了自己的財產權和經濟利益時,農民組織起來,參政議政就是必然的選擇。這也倒逼著地方政府加快職能轉變,以適應變化了的形勢。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實質是要從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轉變。農民對自己財產權利的維護,既不能建立在地方官員個人品質的基礎上,也不能建立在道德力量的基礎上。這種基礎是不牢固的,因為它可能會出現“人走政息”的情況,從而形成農民和地方政府的對峙局面,給當地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帶來負面影響。從目前來看,制約地方政府比較有效的手段,是賦予農民對縣鄉級地方官員的直接選舉權。在過渡期,我們通過擴大選拔地方官員的公開程度和參與程度,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們希望在擴大基層選舉范圍和層次上有更大的突破,因為這是農民權利不受侵犯的基本制度保證。
從制度上保障農村土地流轉中農民的合法權益
溫州市的農村土地流轉肇始于20世紀80年2009年春耕備耕期間,溫州瑞安市飛云鎮農民出現競價包地現象。農民歷昌榮拿出29萬元承包了1180畝農田,一舉成為當地承包農田最多的大戶。在此情形下,另一農民陳慶福趕緊在原有的每畝350元的價格基礎上再加上20元,才挽回部分流轉地。⑧在安徽淮北市,截止2010年3月底,全市農村土地流轉面積已達22.5萬畝,其中流轉耕地面積16.7萬畝。⑨流轉的主要形式有:淮北市21個鄉鎮辦事處普遍建立了農村土地流轉服務中心(或辦公室)和土地流轉市場,326個行政村全部配備了農村土地流轉信息員。全市已有40多家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農村土地流轉建立規模種養基地,發展高效規模農業。自2009年以來,淮北市通過土地流轉新建規模(50畝以上)養殖小區(場)19個,高效種植(50畝以上)小區115個。該市還組建了農村土地股份合作社4家;農村土地信用合作社13家;農村土地流轉合作社4家。僅2009年,淮北市財政扶持土地流轉資金就達到了617.55萬元,而且每年安排300萬元農村土地流轉專項資金,用于扶持農業規模經營、土地流轉合作社和中介組織建設,引導業主增加投入,放大資金扶持效果。⑩在安徽淮北濉溪縣百善鎮的“安徽省財政廳農業綜合開發示范區”內,筆者了解到,該示范園區面積2.8萬畝,現已經進入了4家企業。筆者考察了由順達公司(經營房地產、建筑和酒類)和大自然公司(經營養豬)一期投入650萬元成立的安徽厚望食品有限公司。該公司2009年從農民那里承租土地520畝,每畝每年租金800元,期限30年,建起了100個半地下式日光溫室,從事綠色蔬菜生產。出租土地的農民130多人在企業工作。農民收益是:公司保證每戶農民每年每畝可得1000元租金;產品銷售盈利四六分成,農民得六,公司得四;每月收入不低于1000元。該企業2009年10月成立,運轉半年來已初見成效。公司則可以從政府那里得到補貼,主要包括土地流轉補貼:淮北市每畝200元,濉溪縣每畝50元;菜籃子補助:市每畝8000元,縣每畝5000元;省農業綜合開發補助52.5萬元(一次性);還有修路、水利補助等。厚望食品有限公司蔬菜基地負責人王傳魁告訴筆者,他們看好這項投資,預計三年后,就可收回投入。瑏瑡重慶市的忠縣是柑桔之鄉。那里的農地流轉主要有五種形式:公司租賃;大戶承包;農民公司;代耕代種;認購經營。到2009年底,該縣已流轉農民承包地31.25萬畝,占全縣耕地的1/3,28家龍頭企業參與其中。具體分布是:用于糧油生產的13萬多畝;蔬菜3萬畝;水果14萬畝;養殖業6000畝;茶葉2000畝。忠縣流轉土地的原則是:依法、自愿、有償、有序、集中經營。美國博富文柑桔有限公司租賃了柑桔園9.62萬畝,每年每畝租金440元,農民在該公司工作的勞務收入為每月400元。瑏瑢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瑏瑣,當地企業“內蒙古游牧一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臨河區一牧民租賃1.5萬畝沙漠的50年使用權,用來種植中藥材“蓯蓉”。筆者訪問了這位牧民,他表示非常樂意將自己承包的沙漠出租出去,以獲得更高的收益。在筆者調查的很多中西部省區,勞動力轉移的幅度非常大。在重慶市忠縣的三匯鎮,當地勞動力外出比例為70%—80%,有10%的農戶已經不再回農村居住了。安徽淮北市2009年有農村勞動力65萬人,其中外出務工的有39.7萬人。由此可見,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必然帶來農村生產要素土地的大規模流動。這是千家萬戶的農民與千變萬化的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必然選擇,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政府在這種農民組織制度的創新中,要因勢利導,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對制度創新進行規范。農村土地通過流動產生出的經濟效益,必將成為農村繼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稅費改革之后,推動農業向前迅猛發展的強大引擎;預示著農村的經濟發展,將在組織制度創新方面迎來新局面,展現更強的活力,持續支撐我國經濟長期、穩定、健康、高速發展。
- 上一篇:農合經濟論文:文山農合經濟發展探究
- 下一篇:新農村論文:農民教育思想及新農村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