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研究
時間:2022-05-08 08:58:17
導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律研究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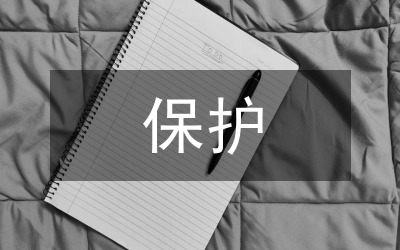
摘要:本文以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視角作為切入點,針對湖南省湘西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法律保護中存在的執法松懈、權利義務主體不明確、追責機制的不完善、傳承人救濟方式的欠缺、立法視角及保護手段的單一化等具體問題進行了研究。輔以研究數據,有針對性的對完善我國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領域的法制建設提出解決的對策方案。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適用;法律保護;模式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簡稱湘西州)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與湖北、貴州、重慶接壤,境內分布有苗族、土家族等30多個民族。悠久的發展歷史,給湖南留下了豐厚的非遺。其中,湘西州地區的少數民族非遺保護現狀令人堪憂。目前而言,我國專家學者對非遺的法律保護著重從產權法、經濟法、生態法等領域做出針對非遺的法律保護問題研究,其次,國外以FedericoLenzerini等學者為例,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非遺在國際人權法領域做出了相應法律保護的研究。國內外對非遺保護法律層面的研究視角多樣,內容逐漸深入,但對非遺的立法保護并不成熟。在這一背景下,通過對少數民族非遺保護的法律問題調研,能深刻了解到非遺保護所面臨的法律現狀,司法操作過程中的漏洞,從而更具針對性的解決其問題。
一、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現狀考察
文化問題一直是本世紀以來備受各國熱議的話題,其中對非遺方面的議論紛爭也一直不斷。筆者認為,研究非遺的相關問題,首要任務是對非遺的概念、特征等方面進行清晰地界定。(一)法律定義下非遺的特征界定及基本情況。從現行法給出的定義中看出非遺外延之廣:可以是口頭傳述、表演藝術、社會風俗,也可為傳統手工藝技能,甚至是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識實踐。就其特征而言,筆者認為其特征最直接體現為其自身的“非物質性”。即:不依賴物質形態而存在的屬性,強調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驗等方面的內容,這種特征在現實的非遺形態中是為一種文化的活態流變所展現。從保護性政策的出臺方面看,湖南省已有四部針對非遺保護的行政管理條例,且均在內容的設計上都體現出較明顯的簡易性。在地方性法規條例中非遺被定義為: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及與其文化表現形式相關的實物與場所。相較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地方性法規條例對非遺定義的更為粗略且一定程度上使非遺內涵的外延窄化,加大了非遺法律認定的難度。(二)湘西地區非遺的具體表現形態及基本情況。以湘西地區為例,非遺在該地是指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得以積累保存下來的傳統美術、戲劇、舞蹈、醫藥、技藝;民俗風情;傳統體育競技等。如:陽戲、水沖石硯、踏虎鑿花、苗族鼓舞、苗繡等藝術形式。湘西地區非遺種類繁多,截至2011年列入省級非遺名錄的共50項。湖南省湘西古丈縣地區,截至2012年8月,古丈縣地區共有國家級非遺6項,省級8項,州級16項,縣級49項,非遺傳承人散布各區共計112人,并形成了以“中國民間文化藝術之鄉”——默戎鎮苗鼓舞文化和斷龍山鄉土家族文化為中心的“非遺”傳承保護基地。
二、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之制度瓶頸
我國已有15部針對非遺保護的法規條例,對非遺的整體性保存、傳承;代表性項目名錄建立;管理使用;認定獎罰等方面進行了較全面的立法。但非遺保護情況仍不樂觀,其面臨的制度瓶頸經整合后集中體現為以下:(一)非遺保護的法律執行、實施存在松懈。在非遺保護的實際操作過程中,時常受到來自不同主體、形式的不法侵害。主要表現為:其一,相關執法部門執法力度不夠。未能及時履行其法定義務,處決相關爭議事宜時對核心程序進行了不同程度的簡化,導致非遺保護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缺乏實質性的法律扶持。其二,社會個人、組織、團體等主體不尊重其內涵,歪曲地使用非遺,更甚損害其合法權益。以湘西默戎鎮地區為例,作為傳統苗族聚居地,其非遺大多以“傳統苗寨”作為物質載體。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商業團體利用對“傳統苗寨”的開發、改造創造大量經濟效益的同時,也以非遺的大量破壞和流失作為巨大代價。(二)現行法立法內容缺乏時效性,保護手段單一。在我國2011年頒布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法》中,就非遺傳承人這一主體而言,現行法賦予其:政府提供必要的傳承場所及必要的經費資助其開展傳藝、交流等活動;支持其參與社會公益性活動等權利。同時也要求其履行:培養后繼人才;配合文化主管部門進行非遺調查等義務。權利義務的有效實現,必有相應的追責機制做保障。但就目前,大部分法規條例僅在其權利義務所屬章節后附有簡易粗略的懲戒辦法,少部分還存在相應的立法空缺。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條例》為例,該條例僅從搶救保護、認定傳承、管理利用、獎勵處罰四個方面簡易的設置保護辦法。相較于權利得不到保障,該條例針對部分主體法定義務的不履行所規定的追責辦法大多于前者,總體分布零散未形成健全的追責機制。(三)立法過于注重制度性設計且視角單一。非遺法律保護問題的長期存在,表明在非遺保護的立法上仍有缺陷。鑒于以上兩點,我國目前的立法設計既未形成健全的追責機制,也沒有清晰規定執法管理主體,立法成果大部分以近幾年關于非遺事宜糾紛為依托而初步形成。由于非遺自身的特殊性、復雜性及歷史性,導致其真正的權益主體無法確定,相關非遺作品、研究成果等派生品無法定性,當處理與非遺有關的各類糾紛時,我國并沒有相關的法律條例可供參考,整體現行法設計缺乏靈活性,視角過于單一且多為制度性的設計,沒有實操性的立法內容呈現。
三、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有效實現之路徑選擇
通過上述對非遺法律保護現狀的分析,筆者認為,我國應建立起相應的法律責任追究制,加入適當的行政處罰作為懲戒。同時也建議從公、私法相結合的角度切入完善立法,這樣不僅能形成全面的法律責任追究機制,還能化解因重視制度性法律設計忽略實際司法操作中面臨的后續法律問題給國家立法、非遺保護帶來的困境。而中的關鍵是以下三點:(一)基本路徑:明確主體,法律責任追究機制專門化。我國現行法中對追責機制的設立過于簡化,基于我國非遺法律保護現狀考察及立法剖析,筆者認為:結合我國非遺保護中存在的法律實施松懈現狀,應將針對與非遺保護主體相關的追責機制進行專門化設立。如在《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條例》中,并未對執法力度松懈作出明晰的追責規定,僅用簡短的篇幅概括,導致非遺問題不能及時得到解決及非遺傳承人對政府等機關不再信任,產生“自暴自棄”的想法,加大了我國非遺法律保護方面的工作困難。綜上,我國當下應結合現行法中關于法律追責板塊的立法梳理,設立一部或多部具有較強針對性的部門法規,對各主體應履行的義務進行規制,對其責任進行更為精準的分類,使責任主體明確,追責方式清晰,為處理非遺爭議性事務提供工作方向,使司法實踐有據可依。(二)關鍵路徑:傳承人社會保障機制法律化。傳承人作為非遺保護最直接、關鍵的基層人物,立法保護工作中更不應忽略這一核心主體。由于非遺內在文化價值轉換為經濟效益存在巨大困難,故農村地區傳承人迫于生活壓力而多數放棄對非遺的傳承。筆者建議:國家加大社會保障資金投入,針對非遺傳承人建立社會保障機制。該保障機制應當以國家社會保障基金為依托,以保證傳承人的基本生存權利為主要內容。為確保傳承人權益得到實際保障,可借鑒美國針對傳承人權益保護設立各主體獎罰分明的考核機制的做法。此機制的建立不僅有利于化解傳承人因生活無保障而自行放棄繼承的瓶頸,還將此種專門化社會保障機制上升到國家保護的高度,也為相關部門在處理與之相關的糾紛時提供依據。(三)現實路徑:完善公、私法保護機制,構建健全“雙法”保護模式。要突破現行立法中注重行政式保護、私法保護體制的不健全,筆者認為:應提高公、私法保護領域的立法水平,構建體系完備且運作高效的“雙法”保護機制。1.公法方面,我國繼《非物質文化遺產》推行以來,總體呈現出以行政式保護為主的特點。此種行政法保護模式較為健全的以日本、韓國為代表。建議可借鑒日本在國家層面設置非遺專門保護機構,韓國從中央到地方建立職責分明的非遺專職管理系統等做法。結合我國非遺立法保護現狀,可依行政區域級別進行初步劃分,以此為基礎,加以各地區非遺數量的分布等基本情況及所在地經濟發展水平等進行“分級別,分版塊”專職管理機構的設立,同時輔以監督機構的監督,配套建立起各地區相應的法律保護制度,以此完善并加強我國在公法領域對非遺的立法保護體制建設。2.從私法方面,筆者建議:我國可借鑒以美國、突尼斯為代表的知識產權法保護模式。以“山東魯錦商標權糾紛”為例,雖山東省高院對商標專用權和商品通用名稱的公共利益保護權給予了同等保護,駁回了山東魯錦公司請求,孰不知,該判決是山東高院作出的“摸索式”判決,在此領域立法的缺失給司法操作中帶來的困難可見一斑。而美國在針對本國非遺的專利申報、專利保護及商標申請等環節都加以了明晰的法律規定,且配備有主體界定明確的追責條例。如:1990年美國頒布的《印第安藝術和手工藝法》中,明確規定了對傳統手工藝品交易中假冒商標等侵權行為予以民事或刑事處罰。此外,結合我國非遺“大分散”的實際,筆者建議:可借鑒美國針對原始土著居民地區建立“非遺大數據庫”的做法,針對我國經濟發展滯后,交通閉塞地區建立非遺大數據庫,并將其地位法律化。以屬地原則為基礎,并入專職管理機構進行管理,并為非遺大數據庫的運營等系列管理工作建立起配套的法律制度。
參考文獻:
[1]財政部、文化部.關于印發《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通知.2012年5月4日.
[2]苗族自治州人大常務委員會.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條例.2006年6月1日.
[3]劉小冬、譚啟平.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基本問題研究.西南政法大學.2010.
[4]李依霖、徐中起.少數民族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研究.中央民族大學.2013.
[5]王吉林、陳晉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權利主體研究.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4).
[6]薛亞君.非物質文化遺產特別權利研究.江蘇科技信息.2014(19).
[7]張邦鋪.論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韶關學院學報.2008(11).
[8]郭海霞.論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困境與對策.特區經濟.2010(6).
[9]趙寧、閻其華.我國經濟法視域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2).
[10]李華.生態法視域下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機制的構建.河南社會科學.2009(5).
[11]唐清海.國外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前沿問題的研究綜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3).
[12]趙方.知識產權制度與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沖突與契合.西安財經學院學報.2010(2).
[13]后曉瑩.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過程中的法律政策、機構設置和傳承人三者間的關系研究——以玉溪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考察為例.云南藝術學院.2015.
作者:唐子媛 劉影 李梓銘 單位:吉首大學法管學院
相關文章
精品范文
10非物質文化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