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nóng)民生育偏好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9 09:17:00
導(dǎo)語:農(nóng)民生育偏好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wǎng)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chuàng)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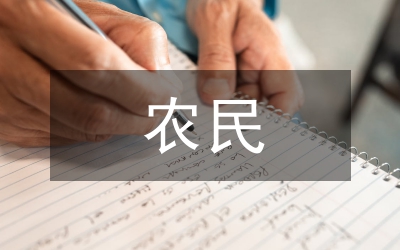
〔摘要〕傳統(tǒng)理論認(rèn)為,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取決于傳統(tǒng)的生育文化,經(jīng)濟(jì)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論能夠從不同的側(cè)面解釋農(nóng)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為,但是無法解釋當(dāng)今農(nóng)民“適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樣、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選擇。社會解構(gòu)模型則能夠較好地解釋當(dāng)今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經(jīng)濟(jì)解構(gòu)、文化解構(gòu)、需求解構(gòu)從反方向侵蝕、消解農(nóng)民的傳統(tǒng)生育文化,從反方向影響、沖擊農(nóng)民的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行為。
〔關(guān)鍵詞〕生育偏好;生育行為;生育文化;生育邏輯;社會解構(gòu)模型
對于農(nóng)民的生育動機與行為,專家學(xué)者都從農(nóng)民生育偏好,即農(nóng)民“生多少”、“生什么”、“什么時候生”三個方面考察,現(xiàn)有的理論和分析框架都是圍繞著“生男而多生”、“生男而早生”的偏好及行為而建構(gòu)的,如功能論、效用能、文化論、需求論等都是如此。但是20世紀(jì)末期以來,部分地區(qū)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及行為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農(nóng)民從“多生”轉(zhuǎn)向“少生”、從“生男”偏好轉(zhuǎn)向“男女無所謂”。這種偏好與行為變化具有革命性的意義。為什么會發(fā)生這樣的變化呢?現(xiàn)在以“生男、多生、早生”為問題意識所建構(gòu)的生育理論與分析框架無法解釋這種相反變化。本文借鑒吉登斯社會學(xué)的社會結(jié)構(gòu)理論和經(jīng)濟(jì)學(xué)的成本約束理論,建構(gòu)“社會解構(gòu)模型”,以此解釋中國部分地區(qū)部分農(nóng)民生育偏好與行為的新變化。
一、文獻(xiàn)梳理與問題提出
農(nóng)民生育偏好與行為是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社會學(xué)家的重要研究內(nèi)容,歸納起來大約有四大理論系列:生育效用論、生育功能論、生育文化論和生育需求論。
(一)生育效用論
生育效用論是從經(jīng)濟(jì)學(xué)的角度考察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及行為。效用理論可以追溯到馬爾薩斯。他認(rèn)為,生育數(shù)量取決于結(jié)婚年齡和生育能力,同時認(rèn)為收入會影響生育數(shù)量。馬爾薩斯并沒有具體研究生育偏好及其選擇,只是研究了家庭對生育數(shù)量的兩種控制方法:一是主動控制,即“道德控制”;二是被動控制,即“罪惡控制”。達(dá)爾文在馬爾薩斯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自然選擇論,這屬于典型的“能者多生”的進(jìn)化論觀點。〔1〕其實達(dá)爾文的“能者多生”的觀點只有效用論意義,而沒有效用論實質(zhì)。斯賓格勒首先提出了家庭規(guī)模的“成本-效用”理論,用成本與效用分析家庭人口的最優(yōu)規(guī)模。其實真正將經(jīng)濟(jì)學(xué)引入家庭及其生育領(lǐng)域的是貝克爾,他在《人類行為的經(jīng)濟(jì)分析》中考察了生育偏好、選擇及其影響因素。他認(rèn)為子女是一種“心理收入”或“滿足的來源”,可以將子女看成一種“消費商品”;子女還可以提供貨幣,因而還是一種“生產(chǎn)品”。作為耐用消費品,子女被認(rèn)為可以提供“效用”,作為生產(chǎn)品,子女可以提供收入和幫助。〔2〕效用取決于偏好,而偏好又由信仰、種族、年齡等因素決定,特別是受家庭收入、扶養(yǎng)成本及子女提供的“效用”共同決定,〔3〕“(子女帶來)收入增加和價格的下降會增加對子女的需求”〔4〕,“如果孩子干家務(wù)、在家庭作坊或市場上勞動,對家庭收入作出了貢獻(xiàn),那么,孩子的凈成本就會減少。因此,孩子’收入’潛力的增加會擴(kuò)大孩子的需求”。〔5〕顯然,效用增加和扶養(yǎng)成本的降低會刺激家庭增加子女?dāng)?shù)量。①如果用偏好表示,就是生育的效用偏好,即追求子女提供的效用最大化,同時家庭根據(jù)相關(guān)約束條件選擇最佳子女?dāng)?shù)量。貝克爾既從需求層面進(jìn)行了分析,也從供給層面分析了家庭生育的偏好,及在相關(guān)變量約束下的主體選擇行為。
貝克爾的生育效用理論為學(xué)界用經(jīng)濟(jì)學(xué)的理論和方法研究社會家庭、生育問題提供了新的范式,特別是與中國學(xué)者不同的是,他既從需求視角進(jìn)行考察,也從供給視角進(jìn)行了考察。但是貝克爾的生育效用理論也有不少缺陷:一是該理論是以西方文化傳統(tǒng)為研究對象,是生育文化約束較弱條件的經(jīng)驗概括和總結(jié)。二是該理論主要是從經(jīng)濟(jì)角度進(jìn)行分析,放棄了人所具有的一些“人性動機”,即假定人主要受經(jīng)濟(jì)約束,對其他的因素具有免疫能力。三是該理論受經(jīng)濟(jì)學(xué)研究范式的影響,是個體主義研究方法,即決策者是個人,而不是家庭,從個人效用最大化的角度考慮問題。此理解可以較好地解釋西方家庭的生育動機與行為,但是無法合理地解釋中國農(nóng)民的生育動機和行為。中國農(nóng)民是以家庭為單位考慮生育需求、動機與行為;中國農(nóng)民受傳統(tǒng)宗族文化的浸染,傳宗接代與繼嗣問題內(nèi)化為農(nóng)民的責(zé)任。四是中國的傳統(tǒng)生育文化也對農(nóng)民的生育動機和行為有著巨大的影響。貝克爾的生育效用理論無法對中國農(nóng)民,特別是當(dāng)今中國農(nóng)民的生育動機及行為選擇作出合理的解釋。
(二)生育功能論
所謂生育功能論就是從功能角度分析生育偏好及其行為,即生育子女干什么,多生育子女為的什么,拼命生育男孩圖的什么。生育功能理論主要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勞力說;二是養(yǎng)老說;三是還債說。俗語“不孝有三,無后為大”、“不能斷子絕孫”等都是此種觀念的具體體現(xiàn)。生育功能論者的典型學(xué)者是李銀河,她認(rèn)為,“對勞動力尤其是對男勞力的需求,仍然是農(nóng)民要生孩子(特別是男孩)的一個強烈動因”,“農(nóng)村孩子至少在婚前是為父母動的”。其次李銀河也支持生育養(yǎng)老說,“除了以子女作為直接的勞動力之外,農(nóng)民還把生育子女作為老年生活保險的主要投資方式”,“還有期待兒子媳婦提供照顧老年生活的服務(wù)這樣一種動機”。〔6〕另外李銀河還持還債論的觀點,“生養(yǎng)孩子是為了報父母的生養(yǎng)之恩,把生孩子叫做’還債’,由此衍生出’討債’和’還債’的說法”。〔7〕但是后來,李銀河又將勞力說、養(yǎng)老說歸結(jié)為投資與效用的追求,她一方面反對生育效用論,一方面又堅持生育效用論,她的生育理論充滿了矛盾。其實,農(nóng)民生育的勞力、養(yǎng)老動機是一種典型的功能性需求。當(dāng)然如果要用效用來概括,所有的行為、包括文化規(guī)范都可以歸納為效用。對于生育功能論還有不少學(xué)者對此作出過學(xué)術(shù)增量貢獻(xiàn),如梁中堂、景躍軍、殷豐、方向新、陳永平、鄧小敏、李永時、唐貴忠、董輝等在20世紀(jì)90年代就對此進(jìn)行過深入研究。
(三)生育文化論
生育文化論包涵多種觀點和學(xué)說。首先,人類學(xué)家認(rèn)為,文化在生育中起了重大作用。生育文化論者可以追溯到英國人類學(xué)家馬林諾夫斯基,他認(rèn)為,“家庭不是生物團(tuán)體的單位,婚姻不是單純的兩性結(jié)合”,“種族的需要并不是靠單純的生理行動及生理作用而滿足的,而是一套傳統(tǒng)的規(guī)則和一套相關(guān)的物質(zhì)文化的設(shè)備活動的結(jié)果”。〔8〕費孝通繼承了老師的文化論傳統(tǒng),并以中國經(jīng)驗進(jìn)行了研究,他認(rèn)為,“’種族’需要綿續(xù)是發(fā)生生育制度的基礎(chǔ)”,“生育制度是人類種族綿延的人為保障”,“種族綿延是人們所要達(dá)到的一個目的,為了要達(dá)到這個目的,所以發(fā)生種種活動,形成我在這里想提出來分析的生育制度”。費老認(rèn)為生育制度或者生育文化就是種族綿延的產(chǎn)物,種族綿續(xù)是生育的目的,也是生育的動機。他又認(rèn)為,生育是一項“損己利人”的事情,一項“吃虧不討好”的事情,可是人人還樂此不疲,而且還要多生。這就是由儒家和祖?zhèn)飨聛淼姆N族綿延、傳宗接代的文化所決定的。李銀河也持同樣的觀點,生育偏好是由文化所決定的,主要體現(xiàn)為“家本位”和“村莊面子”,“他們從一降生入世就落入了’生存繁衍原則’的生活邏輯之中,一生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家庭的傳宗接代和興旺發(fā)達(dá),在’家’面前,’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人人的享樂是無足輕重的”。“我們發(fā)現(xiàn),農(nóng)民在生育、結(jié)婚、喪葬這些事上,全都顯出一種’身不由己’的樣子。為什么要生孩子?因為不生別人要罵’絕后’??在婚喪嫁娶、紅白喜事的投資數(shù)目上,個人選擇的余地是多么小。在農(nóng)民心中重得不得了的’面子’、’別人的閑話’,實際上就是文化規(guī)范的壓力”〔9〕。李銀河將此歸結(jié)為東方式的“恥辱文化”,“不愿這樣做或做不到的人就會蒙受恥辱。很明顯,這正是村落文化中的人們拼命要生兒育女的一大動因”。〔10〕劉中義不同意李銀河的生育養(yǎng)老說,借用布什亞的符號社會學(xué)理論進(jìn)行分析,“農(nóng)民眼里的性別偏好和嬰兒出生性別選擇行為在實質(zhì)上已經(jīng)不僅僅是簡單地出于養(yǎng)老的現(xiàn)實效用考慮,而更多的是追求一種與養(yǎng)老無關(guān)的符號意義”。〔11〕他的結(jié)論是,人們偏好生男孩、拼命多生只不過追求的是一種表面性的符號意義。養(yǎng)兒防老只不過是一個幌子、一個表面的借口而已。同時劉中一又借助布迪厄?qū)嵺`理論,通過建構(gòu)“場域”和“慣習(xí)”兩個概念解釋農(nóng)民的生育動機與行為,“在農(nóng)民生育行為的研究過程中,場域和慣習(xí)概念的邏輯展開,不僅能夠有效地規(guī)避以往研究中在個人與社會(文化)之間非此即彼的選擇,而且也可以有效地將行動者和社會結(jié)構(gòu)雙向能動性集中起來,從而使研究結(jié)論更加深刻、更加貼近于現(xiàn)實。”〔12〕鄭衛(wèi)東借助阿爾切的“文化與能動者”理論建構(gòu)了一個“社會結(jié)構(gòu)--文化”解釋模式,以此解釋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農(nóng)民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文化的變化,他認(rèn)為,“社會結(jié)構(gòu)因素與文化因素在共同的載體行動者身上發(fā)生互動,使得行動者表現(xiàn)出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生育行動,這種生育行動的結(jié)果必然對行動者以及周圍群體的生育觀念發(fā)生影響,從而鞏固或者修正了原來的生育文化內(nèi)容,這就是生育文化的精致化”〔13〕。其實鄭衛(wèi)東的觀點與黃平的主體與結(jié)構(gòu)的二重互動有相似性。劉爽還提出了“文化-制度”解釋模式。
(四)生育需求論
穆光宗和陳俊杰通過建立需求層次理論解釋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他們認(rèn)為,生育偏好中存在一種由文化自覺編排好的內(nèi)在邏輯,不能用成本-效用理論解釋中國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及其行為,而應(yīng)該對“本土文化”進(jìn)行深入的剖析,尋找中國農(nóng)民生育的內(nèi)在決策機制,這個機制由六種層次不同的需求組成:即“終極價值的需求”、“繼嗣需求”、“情感需求”、“續(xù)夢需求”、“社會需求”、“經(jīng)濟(jì)需求”,在觀念層面上,自終極價值的需求而傳宗接代的需求,再情感需求和續(xù)夢需求,在現(xiàn)象層面上,則包括社會需求和經(jīng)濟(jì)需求。〔14〕李具恒也持生育需求論的觀點,他將農(nóng)民的生育需求分為內(nèi)在需求和外在需求,農(nóng)民的生育行為是由內(nèi)在需求和外在需求共同決定的。〔15〕需求論其實是一種對上述各種理論的綜合,將農(nóng)民生育的各種觀點以“需求”的方式進(jìn)行綜合和概括。
上述理論都能夠在現(xiàn)實中得到經(jīng)驗支持,也能夠部分解釋農(nóng)民的多生、生男、早生的生育偏好和行為,但是這些理論無法合理地解釋“適度生育”、“生男生女皆可”的生育動機和行為。20世紀(jì)末期以來部分地區(qū)農(nóng)民改變了“拼命生育、非生男孩”不可的生育理念,轉(zhuǎn)向“適度生育、男女皆可”的生育動機與行為。對于這一變化,一些學(xué)者已經(jīng)進(jìn)行過探討,如陳俊杰、穆光宗、鄔滄萍、賈珊、顧寶昌、鄭衛(wèi)東等,分別從制度、文化、經(jīng)濟(jì)等方面進(jìn)行解釋,但是仍然沿襲傳統(tǒng)的研究進(jìn)路。
(五)假設(shè)性陳述
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改變,經(jīng)濟(jì)、制度、文化及其三者組成的系統(tǒng)都發(fā)生過作用,但是這些作用可以歸納為一個因素:社會化。農(nóng)戶特別是生育主體卷入社會化的程度越來越深,水平越來越高,農(nóng)民生育不是僅僅依靠家庭就能夠完成了,即農(nóng)民生育小孩不僅僅是家庭的事,不僅僅扶養(yǎng)就完事了。過去,小孩一旦出生,“產(chǎn)品”就已經(jīng)完成。但是現(xiàn)在小孩子是一個“社會產(chǎn)品”,必須經(jīng)過社會化的過程、經(jīng)過社會化的檢驗才能夠變成合格“產(chǎn)品”,在出生與成為合格“產(chǎn)品”之間,有很長的路要走,要花費大量的心血和經(jīng)濟(jì)成本。社會化這條流水線將淘汰“不合格產(chǎn)品”,“不合格產(chǎn)品”將難以生存。筆者認(rèn)為,生育變成了家庭和社會共同決定的事情,社會化過程影響著現(xiàn)代父母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行為。
二、農(nóng)民生育偏好與行為:逆?zhèn)鹘y(tǒng)生育
如果說前幾年農(nóng)民大多偏好于“生男、多生、早生”,“適度生育、生男生女都一樣、晚生”是極少數(shù),2000年以來,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樣,甚至喜歡生育女孩的現(xiàn)象在一些地區(qū)的農(nóng)民中開始出現(xiàn)。筆者曾經(jīng)深度訪談的四個村莊:河南府君寺村、湖南湖村、江西長岡村、四川魯家庵村,呈現(xiàn)出完全不同的生育偏好和選擇,湖村和魯家庵村的大部分農(nóng)民已經(jīng)改變了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而府君寺村和長岡村則沿襲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
1.生育偏好轉(zhuǎn)換以一定生育數(shù)量為基礎(chǔ)。傳統(tǒng)生育偏好也有一個基礎(chǔ),必須生育一個男孩,生育男孩的動機導(dǎo)致了多生和早生的偏好,多生和早生都是圍繞著生男動機而展開的,必須“有男孩”是傳統(tǒng)生育偏好的基礎(chǔ),也是傳統(tǒng)生育觀念的基本邏輯,更是農(nóng)民接受既定生育數(shù)量和結(jié)構(gòu)的基礎(chǔ),如一男多女、一男一女,甚至一男。湖南湖村、四川魯家庵村的農(nóng)民偏好于“適度生育、生男生女一個樣”,也有一個前提條件,必須有生育。也就是說,必須生育一個小孩。生育是人的天性,也是做人的職責(zé),更是家庭綿續(xù)的需要。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兩村的青年農(nóng)民選擇“丁克家庭”的幾乎沒有。一般而言,結(jié)婚后很快就選擇生育。他們認(rèn)為,反正要生育,晚生還不如早生,生后了了一樁事。另外,結(jié)婚就選擇生育,也與青年農(nóng)民希望早些完成生育任務(wù),方便外出打工有關(guān)。只有生育小孩后,外出打工,長輩們才安心,年輕人也認(rèn)為生育了事后,可以放心在外面打拼。農(nóng)民將生育看成一樁事、一個任務(wù)、一個責(zé)任。既然是任務(wù),就會有數(shù)量要求,必須完成;既然是任務(wù),早完成,早了事,早方便。只有在完成生育任務(wù)的基礎(chǔ)上,才有可能有其他的偏好選擇。生育一胎是其他生育偏好選擇的基礎(chǔ)。也就是說,生育偏好的轉(zhuǎn)變是以一定的生育數(shù)量為基礎(chǔ)的,達(dá)到了這個基礎(chǔ),家庭才會放心,農(nóng)民也會安心,才不會再追求更多的生育數(shù)量。可見,傳統(tǒng)生育偏好與湖村、魯家庵村的生育偏好大相徑庭,前者以生男為系列偏好的基礎(chǔ),后者以生育為系列偏好的基礎(chǔ)。
2.內(nèi)心偏好男孩,生育后則是男女一個樣。傳統(tǒng)生育偏好不管是內(nèi)心,還是情緒表現(xiàn)都是偏好生育男孩,需求愿望、動機、目標(biāo)和行為都非常明確--生育男孩,只有生到男孩,才算完成任務(wù)。由于浸染傳統(tǒng)的生育觀念,湖村、魯家庵村農(nóng)民內(nèi)心還是偏好男孩,這種期盼至今沒有多大的變化。但是期盼的強度已經(jīng)大大減弱。雖然農(nóng)民內(nèi)心有生育男孩的期盼,但是一旦生育,則接受既成事實,男女都能夠接受。在兩個村莊,調(diào)查時我問年輕人,你們想要男孩還是女孩?他們都會說“男女一樣”,“女孩還好些”。其實如果只生一胎,他們的內(nèi)心還是希望生育一個男孩。但是小孩一旦降生,男孩女孩都可以接受,即“生男孩好,生女孩也不賴”。顯然“生男生女一個樣”也有一個前提條件,在既成事實基礎(chǔ)之上,它是事后確認(rèn)原則,也是一個被動接受的原則。但是農(nóng)民能夠從“非要生男不可”到“事后被動接受”也是一個不小的進(jìn)步。
3.有些農(nóng)民甚至走得更遠(yuǎn),喜歡生育女孩。傳統(tǒng)生育偏好中,即使存在少數(shù)農(nóng)民持生男生女無所謂的態(tài)度,但是要說喜歡生育女孩的人則是鳳毛麟角。在傳統(tǒng)觀念中,女孩總被認(rèn)為是“賠錢貨”,即使不認(rèn)為是“賠錢貨”,也談不上喜歡的地步,可以說在傳統(tǒng)生育偏好中,大部分農(nóng)民對女孩的偏好屬于中性,只有總是生育女孩的家庭才會對女孩有一定的成見,但是極少有人說喜歡生育女孩。在湖南湖村、四川魯家庵村的調(diào)查中,我還發(fā)現(xiàn)有些青年農(nóng)民偏好生育女孩。這種偏好在湖南湖村有不少。我問他們喜歡女孩的理由,往往說是“女孩貼心”,“女孩對父母好些”,“女孩負(fù)擔(dān)輕些”。他們認(rèn)為,嫁女的費用相對于娶媳婦少多了,有就多給嫁妝,沒有就少給嫁妝。四川魯家庵村也有同樣的觀點,女孩對父母更關(guān)心,經(jīng)常能夠問寒問暖。女兒讀書也可以少讀幾年,教育成本也低些,當(dāng)然能夠讀書的女孩,父母都會支持,但是大部分農(nóng)民認(rèn)為女孩少讀幾年也沒有關(guān)系。特別是湖村女孩在服務(wù)行業(yè)工作的多,打工收入高,對父母的反饋也多,女孩脫離農(nóng)村的機會也多些。這些因素促成不少青年農(nóng)民偏好生育女孩,它與傳統(tǒng)生育觀念背道而馳。雖然持類似觀念的農(nóng)民還不是特別多,但是我們應(yīng)該將此看成一個新現(xiàn)象予以關(guān)注,它的出現(xiàn)肯定有其內(nèi)在的邏輯。
4.只完成生育任務(wù),打死都不多生。傳統(tǒng)生育偏好是“男孩主導(dǎo)型”,為了生育男孩,必然會導(dǎo)致某些家庭多生、早生的偏好,當(dāng)然也有些家庭偏好多生育,認(rèn)為“多子多福”。湖村與魯家庵村的農(nóng)民在生育一個小孩后,大多不再生育,家里是獨子的可能會選擇生育第二胎。在魯家庵村,我問農(nóng)民,為什么不想再生了?“一個都養(yǎng)不活,怎么還能生兩個呢”,“生得起,養(yǎng)不起呀”。我又問,是不是超生罰款太重了,交不起罰款?“現(xiàn)在是罰得起,但是養(yǎng)不起”。我又問一些老人家,你們不想要一個孫子嗎?“我想要,他們不生,有什么辦法。”魯家庵村的有些青年人反映,“打死都不生了”。從湖村來看,湖村在10年前農(nóng)民就不想多生了,他們認(rèn)為,“生兒好,生女也不賴”,“多生受累,少生幸福”,“多兒多女多冤家”。當(dāng)然老一輩的人還是希望兒媳能夠多生一胎,能夠再生育一個男孩,有些甚至用利益誘導(dǎo),“生兒將負(fù)擔(dān)全部費用”,“生后我們帶”等,有些晚輩開玩笑說:“要生,你們生,打死我也不生了”。〔16〕可見,“男孩主導(dǎo)型”的生育偏好必定導(dǎo)致多生,“生育任務(wù)型”的生育偏好肯定是“打死都不多生”。
經(jīng)過湖南湖村、四川魯家庵村的對比分析可以發(fā)現(xiàn),與傳統(tǒng)生育偏好相比,兩村的生育邏輯、生育偏好、生育行為及生育決策權(quán)都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
1.生育邏輯已經(jīng)從“生男”邏輯轉(zhuǎn)向“生育”邏輯。“生男”邏輯是以生男為動機、目標(biāo)和行為的一系列關(guān)系,在“生男”邏輯下,農(nóng)民夫婦必須要有男孩,如果沒有生到男孩,必須繼續(xù)生育,直到生育男孩為止,生男邏輯必然導(dǎo)致“多生”。“生育”邏輯是以完成生育任務(wù)為動機、目標(biāo)和行為的一系列關(guān)系,農(nóng)民夫婦將生育視為自己做人的責(zé)任,也將此視為家庭發(fā)展的需要,但是只要完成生育任務(wù),即只要生育小孩(不管男女)都行。雖然兩者都具有強制性,但是強制性的內(nèi)容不同,導(dǎo)致生育的結(jié)果也就大相徑庭。
2.生育偏好已經(jīng)從“多生”偏好轉(zhuǎn)向“適可”偏好。生育偏好是心理層面的,它包括愿望、動機和目標(biāo)。生育偏好是一個系列,從傳統(tǒng)生育偏好系列來看,包括生男、多生、早生三個偏好。由于湖南湖村和四川魯家庵村的生育邏輯已經(jīng)從“生男”邏輯轉(zhuǎn)向“生育”邏輯,因此生育的主導(dǎo)偏好也就發(fā)生了較大的變化,從“男孩主導(dǎo)型”的生育偏好系列轉(zhuǎn)向“生育任務(wù)型”偏好系列,前者偏好“多生”,后者偏好“生育即可”,適度、適可在現(xiàn)實中表現(xiàn)為生育一胎,生了即行。
3.生育行為已經(jīng)從“非理性”轉(zhuǎn)向“理性”。理性就是講求生育的成本和收益,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行為使生育成為“吃虧不討好”的事情,這是一個理性的人不會選擇的事情。從湖村和魯家庵村的情況來看,這種生育的“非理性”行為開始讓位于“理性”,農(nóng)民不再愿意多生,也不再追求非生男孩不可,而是選擇生育適度,打死都不多生,不罰款都不生。農(nóng)民生育行為方面開始走向理性。
4.生育決策權(quán)已經(jīng)從“家本位”分化成“家本位”和“個人本位”的結(jié)合。從湖村和魯家庵村來看,農(nóng)民的生育決策權(quán)已經(jīng)從“家本位”向“個人本位”轉(zhuǎn)移。生育與否是“家本位”決策,生育是家庭的事情,生育數(shù)量則是“個人本位”決策,生多生少變成了個人的事情,即“生不生”仍然是“家本位”,“生多生少”則是“個人本位”,由青年農(nóng)民夫婦自己決定。生育決策權(quán)由“家本位”轉(zhuǎn)向二元并立,“家本位”和“個人本位”共同選擇。另外,湖村和魯家庵村生育偏好與傳統(tǒng)生育偏好相比,還有一個方面沒有完全改變,即“早生”偏好。“生男主導(dǎo)型”的生育偏好體系必然導(dǎo)致早生,同樣“生育任務(wù)型”的生育偏好體系同樣會導(dǎo)致早生。前者為生男孩而早生,早得男孩,早完成任務(wù)。后者為生育而早生,早生育,早了事;早生育,早完成任務(wù);早生育,早擺脫束縛。也就是說,如果生育決策仍然是“家本位”與“個人本位”共同決定,如果生育仍然是一個必須完成的任務(wù),則早生肯定避免不了,因為它內(nèi)生于“生育任務(wù)型”的生育偏好體系之中。
三、農(nóng)民生育偏好逆變的解釋:社會解構(gòu)模型
現(xiàn)在有關(guān)農(nóng)民生育偏好與行為的理論大多是圍繞農(nóng)民為什么生男、多生、早生而建構(gòu)的,如文化論、需求論、功能論都是解釋多生、生男的理論,成本-效用論既可以解釋多生,也可以解釋少生,但是中國學(xué)者已經(jīng)從多方面對此理論在中國的解釋力進(jìn)行了批判,難道此理論不能解釋中國農(nóng)民多生、生男、早生的偏好,解釋中國農(nóng)民少生、生男生女一個樣就有效嗎?顯然,我們需要對湖村和魯家庵村農(nóng)民生育偏好的逆向變化,即農(nóng)民為什么選擇少生,生男生女皆可以接受,而且打死也不愿意多生尋求其他的解釋。筆者認(rèn)為,有必要對新出現(xiàn)的生育偏好與行為建構(gòu)新的解釋模型。對于湖村和魯家庵村的生育偏好變化,不能說是文化的單一作用,也不能說是功能的失效,更不是經(jīng)濟(jì)因素的約束,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農(nóng)民所面對的經(jīng)濟(jì)、社會、政治、文化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了變化,生育主體偏好的變化是對結(jié)構(gòu)變化的一種反應(yīng)。不管是文化層面,還是經(jīng)濟(jì)、社會層面,有一點是共同的:農(nóng)民的社會化水平提高,社會性質(zhì)增強。過去個人面對的是家庭和家族的約束,現(xiàn)在個人面對的是社會和家庭的約束,而且社會約束超越了家庭約束,即社會化嵌入家庭,社會化改變了農(nóng)民所面臨的社會經(jīng)濟(jì)文化系統(tǒng),根據(jù)系統(tǒng)調(diào)整偏好及行為是農(nóng)民的理性選擇。
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改變主要是生育性別的選擇與生育數(shù)量的選擇,現(xiàn)在存在的理論都不足以解釋這一逆向變化,筆者在此建構(gòu)一個“社會解構(gòu)模型”,即社會化從反方向解構(gòu)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及行為,從經(jīng)濟(jì)社會化、文化社會化及功能社會化三個維度解構(gòu)傳統(tǒng)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及行為的變化。
(一)養(yǎng)育貨幣化:經(jīng)濟(jì)解構(gòu)
湖村與魯家庵村農(nóng)民生育觀念的改變,在很大程度上是經(jīng)濟(jì)約束條件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農(nóng)民養(yǎng)育子女的成本很低,只要“給碗飯吃”就行了,是一種自然的“放養(yǎng)模型”,吃飯是養(yǎng)育的最大成本和最大約束,如果有能力保證子女有碗飯吃就能夠生育。它是自然經(jīng)濟(jì)、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在生育觀念和行為上的體現(xiàn)。但是在市場化、社會化程度大大提高的當(dāng)今,能夠“給碗飯吃”已經(jīng)不是生育的約束條件,因為家庭承包責(zé)任制的安排,吃飯問題基本解決,現(xiàn)在農(nóng)民生育面臨的約束條件是養(yǎng)育貨幣化的問題,社會化和市場化條件下,養(yǎng)育成本是用貨幣來體現(xiàn)和衡量的。生育時、培育時、結(jié)婚時能否拿出貨幣完成子女養(yǎng)育任務(wù)和責(zé)任成了父母生育的最大約束條件。一是生育成本貨幣化,現(xiàn)在青年農(nóng)民也講究優(yōu)生,也講究健康和衛(wèi)生,懷孕期間需要大量的營養(yǎng)品,生育時也傾向到醫(yī)院生育,這些都需要錢,少說生個小孩也需要4000-5000元。過去只需要幾碗米飯、幾十個雞蛋、幾斤紅糖就夠了,消炎都不需要。二是培育貨幣化,過去的小孩,有錢就送到學(xué)堂讀幾年書,沒有錢就算了,一切都根據(jù)家庭經(jīng)濟(jì)條件而定。但是當(dāng)今小孩子必須讀書,不讀書很難在社會上生存,可讀書需要大筆貨幣成本,小學(xué)讀書一年要1500元左右,魯家庵村已經(jīng)沒有村辦小學(xué),必須到鄉(xiāng)鎮(zhèn)中心小學(xué)讀書,一年起碼得要3000元。初中和高中分別為3000元和5000元。大學(xué)就不用說了,按照目前的水平,一年10000元。農(nóng)民很容易就能夠算出來,兩口子的收入只能夠維持一個小孩子的培育成本。三是結(jié)婚成本,農(nóng)民對子女一般有一個選擇,選擇讀書,結(jié)婚基本不資助,如果不選擇讀書,結(jié)婚成本由父母資助。現(xiàn)在青年農(nóng)民結(jié)婚可不容易,修棟新房起碼得5-8萬元,舉行婚禮起碼也得兩三萬元,結(jié)婚需要10萬元左右。湖村大約是這個水平,魯家庵村結(jié)婚成本較低,因為青年農(nóng)民不愿意在家建房,結(jié)婚并不必然需要新房。從湖村來看,農(nóng)民前半輩子的積蓄只能夠支持一個兒子結(jié)婚。養(yǎng)育的貨幣化和巨額養(yǎng)育成本是當(dāng)今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經(jīng)濟(jì)約束,現(xiàn)在不僅要生育,還要養(yǎng)育;生育成本有限,養(yǎng)育成本卻是一個天文數(shù)字。在生多生少、生男生女方面,任何農(nóng)民都會掂量掂量。可見養(yǎng)育的貨幣化、養(yǎng)育的社會化從反向解構(gòu)農(nóng)民的傳統(tǒng)生育偏好及行為。
(二)示范社會化:文化解構(gòu)
生育問題研究的學(xué)者大多認(rèn)為,中國農(nóng)民熱衷于“只虧不賺”的生育偏好和行為,只能從文化方面進(jìn)行解釋。筆者也認(rèn)為,文化的確能夠解釋農(nóng)民的一些表面上看起來“非理性”的偏好和行為。同樣隨著家庭融入社會、勞動力的社會化配置,這些經(jīng)濟(jì)社會變化對生育文化產(chǎn)生了巨大的沖擊,從反方向解構(gòu)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及行為。示范社會化其實只是一個極不嚴(yán)謹(jǐn)?shù)母拍睿驗樗鼰o法概括社會化對農(nóng)民生育文化的侵蝕和解構(gòu),但是它影響和改變著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示范社會化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農(nóng)民外出打工、接觸外部信息形成的外部文化對鄉(xiāng)土生育文化的侵蝕和解構(gòu)。農(nóng)民外出打工,接觸到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追求生育質(zhì)量,而不是生育數(shù)量;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多子多福。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追求體現(xiàn)在生育、生活質(zhì)量方面,而不是體現(xiàn)在男孩、多子方面;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追求個體理性,這些都對進(jìn)城的青年農(nóng)民產(chǎn)生巨大的影響,而且青年農(nóng)民打工后,自己的獨立性大大增強,經(jīng)濟(jì)的獨立也會反過來支撐青年農(nóng)民接受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促使農(nóng)民獲得生育方面的部分決策權(quán),即獲得生育決策的相對獨立。另外,電視和現(xiàn)代教育也都對農(nóng)民傳統(tǒng)生育文化產(chǎn)生侵蝕作用,特別是現(xiàn)在進(jìn)入生育年齡的青年農(nóng)民大多是觀看現(xiàn)代電視、學(xué)習(xí)現(xiàn)代知識長大的一代,他們接受現(xiàn)代文明和科學(xué)生育文化的經(jīng)歷與傳統(tǒng)文化對他們的影響一樣深遠(yuǎn)。
本地青年農(nóng)民的先鋒性偏好和行為對鄉(xiāng)土生育文化的沖擊和瓦解。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改變與本村少數(shù)農(nóng)民生育選擇的示范效應(yīng)也有較大的關(guān)系,有部分外出打工或者讀書較多的青年農(nóng)民,偏好于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樣,而且身體力行。這部分農(nóng)民對其他青年農(nóng)民有較大的示范效應(yīng)。少生、生男生女都一樣的觀念模仿、學(xué)習(xí)將會導(dǎo)致鄉(xiāng)土性生育文化的瓦解和放棄。另外,“少生”或者“生男生女都一樣”都會導(dǎo)致一個結(jié)果:只生育一個小孩,不論男女都接受和認(rèn)可,也心滿意足。只生育一個小孩的家庭與生育兩三個小孩家庭的家庭負(fù)擔(dān)、家庭幸福水平有相當(dāng)大的差距,前者幸福、瀟灑,后者貧窮、痛苦,進(jìn)入生育年齡的青年農(nóng)民看在眼里,也會記在心上,輪到自己選擇時即使受一些家庭、長輩的壓力也會抵制,而且會以前者為榜樣進(jìn)行說服和辯護(hù)。所以,在養(yǎng)育經(jīng)濟(jì)約束日趨嚴(yán)峻的情況下,先鋒農(nóng)民的示范效應(yīng)將會迅速擊潰傳統(tǒng)鄉(xiāng)土生育的防線。外部新文化的沖擊和內(nèi)部新文化的侵蝕將會迅速瓦解傳統(tǒng)的生育文化,即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和行為將會被解構(gòu)。
(三)功能多樣化:需求解構(gòu)
對農(nóng)民擁有根深蒂固的傳統(tǒng)生育偏好與行為的解釋,除了文化論、經(jīng)濟(jì)論外,還有功能論與需求論。這兩大理論從正方向影響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在社會解構(gòu)理論看來,正是因為相關(guān)功能的多樣化,導(dǎo)致了功能理論和需求理論的失效,或者說農(nóng)民相關(guān)功能性需求的多樣化解構(gòu)了農(nóng)民的相關(guān)功能性需求,導(dǎo)致了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改變。總體而言,功能多樣化主要包括養(yǎng)老功能的失靈、勞動力功能的市場化、還債功能的淡漠化。
養(yǎng)老功能的失效。從筆者的調(diào)查來看,湖村和魯家庵村農(nóng)民的養(yǎng)老則是一個很難界定的概念,什么時候養(yǎng)老,怎么養(yǎng)老?在兩個村莊我都沒有發(fā)現(xiàn)養(yǎng)老比較好的模式。現(xiàn)在農(nóng)村名義上是養(yǎng)兒防老,或者兒子養(yǎng)老,其實大部分老年農(nóng)民是自己養(yǎng)活自己,占調(diào)查樣本總數(shù)的37.43%,另外就是與兒女住在一起的養(yǎng)老模式,大約占39.67%。〔17〕也就是說有接近40%的農(nóng)民養(yǎng)老主要依靠自己。農(nóng)民基本沒有退休的概念,除非自己走不動,只要能夠走動,就不會需要兒子養(yǎng)老,當(dāng)然兒子也不會養(yǎng)老。跟著兒女生活的農(nóng)民也并非完全是享福,只要能夠下床就必須勞動,很難說與兒子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就是兒子提供養(yǎng)老,其實年邁父母提供的貢獻(xiàn)可能還大于兒子提供的養(yǎng)老。這可以從兄弟們爭搶父母親看出端倪,大家都要充分利用父母的剩余勞動價值。可以說養(yǎng)老只是有口飯吃而已。養(yǎng)兒防老功能的式微勢必影響農(nóng)民生男、多生子女的生育偏好和選擇。因此,有些農(nóng)民戲言:養(yǎng)兒還不如養(yǎng)豬,說明了現(xiàn)實的殘酷和人情的冷漠。
勞動力功能的市場化。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行為還有一個功能性需求--勞動力需求,希望多生育、多得勞動力。農(nóng)民有句俗話:“人少好過年,人多好插田”、“人多力量大、人多辦事容易”。但是現(xiàn)在勞動力需求功能已經(jīng)大大下降,特別是湖村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環(huán)節(jié)幾乎全部社會化和市場化,幾乎不需要勞力就能夠完成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即使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兒童和年邁體衰的老年人,也能夠從事種植業(yè)生產(chǎn)。農(nóng)民再也不用擔(dān)心勞動力不足了。勞動力需求功能的衰弱當(dāng)然會從反方向影響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
還債功能的淡漠性。傳統(tǒng)生育偏好還將生育比喻成還債,但是現(xiàn)在青年農(nóng)民根本不認(rèn)同這個觀念,特別是許多80后的青年農(nóng)民更是如此。80后一代青年農(nóng)民與城市80后青年一樣,以自我為中心,個體本位強于家庭本位,個人主義重于家庭集體主義,只有認(rèn)為父母欠自己的,很少有認(rèn)為自己欠父母的。孝觀念的淡化,必然導(dǎo)致還債功能弱化。青年農(nóng)民壓根兒不存在生育還債的觀點,自然會影響其生育偏好。
上述分析清楚地顯示,支持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行為的四大理論基本上被社會化的三個維度所解構(gòu),三個維度瓦解、擊潰農(nóng)民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及其行為。它們并非作用相同、力度一樣。
經(jīng)濟(jì)解構(gòu)力是最重要的約束條件,它是農(nóng)民生育性別、生育數(shù)量選擇的門檻,沒有達(dá)到一定的經(jīng)濟(jì)條件,根本沒有能力生育更多的小孩。因為現(xiàn)在不像從前,不用通過市場、貨幣和社會就能夠?qū)⑿『B(yǎng)大成人,現(xiàn)在的小孩要經(jīng)過社會化的過程和社會化的檢驗,需要貨幣將小孩扶養(yǎng)成人,而貨幣是農(nóng)民最為缺少的東西,也是最難獲得的東西。經(jīng)濟(jì)解構(gòu)力是農(nóng)民生育偏好的重要基礎(chǔ),也是農(nóng)民生育動機和行為的根本約束。
文化解構(gòu)力是次重要的影響因素,它是農(nóng)民生育性別、生育數(shù)量選擇變化的環(huán)境和條件變量。在經(jīng)濟(jì)約束和貨幣支付壓力下,受過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熏陶的青年農(nóng)民,在本地先鋒青年農(nóng)民的示范下,找到回?fù)魝鹘y(tǒng)鄉(xiāng)土生育文化的借口,也找到了拒絕傳統(tǒng)生育文化要求的理由。在預(yù)期的經(jīng)濟(jì)壓力下,在城市文化和現(xiàn)代文明的影響下,在本地先鋒青年的示范下,傳統(tǒng)生育文化逐漸失去往日的約束和規(guī)范能力,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和行為也逐漸被修正。需求解構(gòu)力是最不重要的影響因素,它是農(nóng)民生育性別、生育數(shù)量選擇變化的輔助變量。農(nóng)民生育功能論主要從需求角度考察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但是隨著市場化、社會化的推進(jìn),農(nóng)民生育方面的一些功能性需求相繼失效,或者市場化,或者淡漠化,生育方面的功能已經(jīng)非常簡單:完成生育任務(wù),再也不具有其他的功能性需求。因此,需求解構(gòu)力也從反方向影響著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行為。
三個維度的作用力其實有一個共同的內(nèi)容就是社會化,生育及家庭的社會化,生產(chǎn)、生活和交往的社會化瓦解了傳統(tǒng)的生育文化,解構(gòu)了農(nóng)民的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生育文化。因此,這個解釋模型可以概括為“社會解構(gòu)模型”。
四、幾個簡單結(jié)論
通過對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逆向變化的分析和解釋,可以得出如下幾個簡單結(jié)論:
1.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其行為在某些地區(qū)的確已經(jīng)發(fā)生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些地區(qū)是市場化、社會化程度比較高的地區(qū),農(nóng)戶生育和生產(chǎn)、生活、交往的貨幣需求增加。貨幣壓力加大的地區(qū),同時也是農(nóng)民與外部交往密切,特別是勞動力外出務(wù)工經(jīng)商比較多的地區(qū),而促成傳統(tǒng)生育文化瓦解的先鋒青年的示范效應(yīng)也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必須看到,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逆向變化已經(jīng)開始,但是并不特別普遍,同時我們也不能證明,2000年以來部分地區(qū)農(nóng)民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行為的變化是傳統(tǒng)生育偏好和生育行為變化的轉(zhuǎn)折點(拐點),還是一種隨機的突變點。
2.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其行為的變化是對結(jié)構(gòu)變化的反應(yīng)。農(nóng)民生育偏好和行為的改變是農(nóng)民對經(jīng)濟(jì)、社會、文化結(jié)構(gòu)變化的反應(yīng),生育的經(jīng)濟(jì)約束條件升高,社會功能需求的多樣化,以及文化約束和規(guī)范能力的降低,都為農(nóng)民生育偏好和行為的改變提供了動力和壓力。湖村和魯家庵村大部分農(nóng)民選擇少生、生男生女一樣就是農(nóng)民這個生育主體面對結(jié)構(gòu)變化,進(jìn)行反復(fù)調(diào)整和調(diào)適的結(jié)果。其他地方的農(nóng)民可能還沒有完全調(diào)整到位,或者正處于調(diào)試之中。如果是這樣,我們可以大膽推測,目前就是農(nóng)民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和行為改變的轉(zhuǎn)折時期。
3.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變化是“家本位”決策-行為單位向“家本位”和“個人本位”決策-行為單位轉(zhuǎn)變的結(jié)果。過去由家決策并由家承擔(dān)風(fēng)險,但是勞動力的社會化配置導(dǎo)致決策-行動單位發(fā)生了位移,雖然總體上以家為決策單位,但是外出務(wù)工勞動力的風(fēng)險承擔(dān)卻個人化,個人化的風(fēng)險承擔(dān)者也就分擔(dān)了部分決策權(quán)利,從而導(dǎo)致了決策-行為單位的二元化。生育與否由家決策,生男生女、生多生少由個人決策,面臨社會化風(fēng)險的個人,必然從理性的角度選擇生育行為。
4.社會解構(gòu)模型能夠較好地解釋農(nóng)民生育偏好及行為的變化。傳統(tǒng)生育偏好及行為理論只能解釋農(nóng)民多生、生男的現(xiàn)象,但是無法解釋農(nóng)民少生、生男生女一樣的現(xiàn)象。社會解構(gòu)模型從經(jīng)濟(jì)、文化、功能三個維度解釋經(jīng)濟(jì)、文化、需求從反方向瓦解、侵蝕、解構(gòu)傳統(tǒng)生育文化,并逐步促使農(nóng)民改變傳統(tǒng)的生育偏好和行為。在三個維度或者三個變量中,經(jīng)濟(jì)約束條件和經(jīng)濟(jì)變量是最主要的變量,解釋能力最強。
〔參考文獻(xiàn)〕
〔1〕〔2〕〔3〕〔4〕〔5〕〔美〕加里·S·貝克爾.家庭論〔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5.162,211,212,233,165.
〔6〕〔10〕李銀河.生育與村落文化:一爺之孫〔M〕.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2003.91-95,85.
〔7〕〔9〕李銀河,陳俊杰.個人本位、家本位和生育觀念〔J〕.社會學(xué)研究,1993,(2).
〔8〕費孝通.生育制度〔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9.45.
〔11〕劉中一.“養(yǎng)兒防老”觀念的后現(xiàn)代主義解讀〔J〕.中國農(nóng)業(yè)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5,(3).
〔12〕劉中一.場域、慣習(xí)與農(nóng)民生育行為:布迪厄?qū)嵺`理論視角下農(nóng)民生育行為〔J〕.社會,2005,(6).
〔13〕鄭衛(wèi)東.村落社會變遷與生育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
〔14〕穆光宗,陳俊杰.中國農(nóng)民生育需求的層次結(jié)構(gòu)〔J〕.人口研究,1996,(3).
〔15〕李具恒.中國農(nóng)民生育需求的再認(rèn)識〔J〕.西北人口,1998,(2).
〔16〕〔17〕鄧大才.湖村經(jīng)濟(j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7.25,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