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與土地研究論文
時間:2022-11-29 11:33:00
導語:農民與土地研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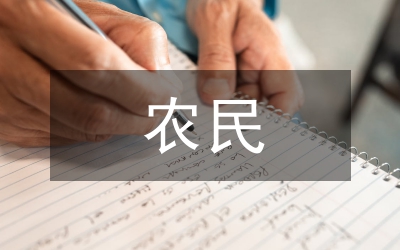
[摘要]土地是農民財富的重要來源,是農民生存的重要保障,是農民精神的重要寄托,農民真誠的愛著土地。但由于土地束縛了農民的發展空間,成了農民的負擔,土地的經營收入不斷下降,土地調整頻繁,土地產權模糊,農民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土地權利屢遭侵害,對土地的保護軟弱無力,農民對土地的感情又有恨的一面。
[關鍵詞]農民;土地;愛;恨
民以食為天,食以農為源,農以地為主。土地是直接為人類生產生活所利用的重要自然資源,是農民最基本的勞動對象和經營基礎,是農民賴以生存的自然條件,也是農民生存的物質基礎,土地還是農民的衣食父母,是農民生養的根本,是農民的命根、農業的源頭、農村發展的根基。
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農民對土地的一種態度與傾向。了解和把握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有利于黨和政府制定更加符合農村實際和農民真正需求的土地政策,有利于解決目前日益嚴重的由征地引起的一些社會問題,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促進農村的和諧發展。
農民對土地的感情是復雜的,既愛又恨,愛恨交加。一方面,土地是農民財富的重要來源,是農民生存的重要保障,是農民精神的重要寄托,農民對土地懷有深厚的感情,真誠的愛著土地,這種愛是主動的、發自內心的;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束縛了農民的發展空間,成了農民的負擔,加之目前的土地調整頻繁、使用權不穩定,農民的土地權利屢遭侵害、農民對土地的保護軟弱無力,農民對土地的感情又有恨的一面,但這種恨是被動的、也是無奈的。總的說來,愛與恨是農民對土地感情的兩個維度。
一、農民對土地感情的一個維度:愛
土地是農民財富的重要來源,是農民生存的重要保障,是農民精神的重要寄托,農民對土地懷有深厚的感情,真誠的愛著土地,對土地的愛是農民對土地感情的一個維度。
1.土地是農民財富的重要來源。被譽為“政治經濟學之父”的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曾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是農民財富的重要來源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土地本身就是農民財富的一部分。“有土此有財,悖入財不久”。在農業時代,社會財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為衡量標準,財富的多少,社會地位的高低,取決于占有土地的多少以及依附人口的數量。今天,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特別是一些城市郊區農民的土地,土地成了一種資本金,是農民參與工業化,分享產業利潤,分享發展紅利的土地股;第二,一切財富都是從土地上創造出來的。農業、采掘業是直接從土地中獲得財富的產業,工業和服務業創造財富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土地面積和地理位置的制約;第三,更重要的是農民可以通過辛勤勞動在土地上創造出更多的財富。重農學派認為“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只有農業能夠增加財富”。[1]“黃土生金”,“人勤地不懶,地內出黃金。”農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歸,規規矩矩,勤勤懇懇,在土地上播種、鋤地、拔草、澆水、施肥,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創造出更多的財富。
2.土地是農民生存的重要保障。首先,民以食為天,國以農為本,土地是農民立足的場所,是農民勞動過程能夠得以實現的基本條件,土地不僅為農民提供了生存空間,更重要的它是糧食的生長場所。農民與土地的關系可以說是唇齒相依,沒有土地就沒有農民和農村。其次,土地在農民生活中扮演著最關鍵的角色。對于常年呆在農村的農民,土地不僅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資料,土地也是農民的衣食父母,是衣食住行的源泉,是生存和生活的根本,而且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即使是對于半工半耕的農民,土地依然是生存的重要保障。農業生產季節性很強,農民“半年辛苦半年閑”,農民在空閑季節也會到城市打工,目前在我國半工半耕的現狀相當普遍,“整個半工半耕制度的邏輯是:人多地少的過密型農業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民外出打工,而外出打臨時工的風險又反過來迫使人們依賴家里的小規模糧地作為保險。”[2]目前確實有大量的農民離開了農村在城市就業,但真正能夠在城市定居下來、不再回鄉的畢竟還是極少數,大多數農民往返在城鄉之間,“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因為在農村有土地,萬一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回家還可以種田。再次,土地是農民自身保障和家庭保障的基礎,也是農民養老的重要保障。長期以來,特別是那些在農村經濟和農民的收入來源中,農業所占比重大的農村,農民的社會保障,主要是以土地為中心的非正規保障,因為大多數地區的農民除了土地之外還沒有別的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
3.精神的重要寄托。在傳統的農耕文化中,土地不僅是財富的象征,也是農民的生存方式,更是農民的精神家園。因為土地是農民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農民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土地,因而農民自古以來就有著“土生萬物由來遠,地載群倫自古尊”的土地崇拜觀念,土地崇拜是中國農民重要的人生觀、價值觀,土地的存在是農民生存的最終根源與目的,也是農民一生快樂、痛苦的最終根源。農民與土地難割難舍的關系,深刻影響著農民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道德觀念和價值取向。土地如同神靈一般被農民敬仰著,“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低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3]土地是農民心中的神,農村有土地神,俗稱土地公公(土地爺爺),農民怕他孤單,還給他配備了老伴叫土地婆婆(土地奶奶)。農民離不開土地,土地是農民文化的靈魂,勤勞、質樸的農民對土地有一種深深的愛戀。“莊稼百樣巧,地是無價寶”,“田是根,地是本”,“地是父母面,一天見三見”,“人不虧地皮,地皮才不虧肚皮”。土地在農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人離不開土地。雖然農民進城打工,但大部分農民最后還是會回鄉耕種,進城打工是暫時的、階段性的,回鄉耕種是長期性的、必然的、最后的選擇,“窮家難舍,熟地難離。”即使是那些在城市創業成功的農民,也有落葉歸根、故土難離之情。土地從來就是農民的命根,是農民一切生活的起點,是農民所有憧憬的歸宿,也是農民生命的全部寄托和生存的精神支柱。
二、農民對土地感情的另一個維度:恨
但由于土地束縛了農民的發展空間,成了農民的負擔,土地的經營收入不斷下降,土地調整頻繁,土地產權模糊,農民又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土地權利屢遭侵害,對土地的保護軟弱無力,農民對土地的感情又有恨的一面。這種恨是被動的、又是無奈的。恨土地是農民對土地感情的另一個維度。
1.恨土地束縛了農民的發展空間。因為農業具有天生的穩定性,農業的主要生產資料—土地是固定不動的,因此,農業在事實上就意味著流浪生活的終止,這種定居型農業使農民世世代代聚居在村落共同體中。而地緣又與血緣緊密相關,“血緣性表明其生物學的特征,聚居性表明其地理學的特征。”[4]血緣和地緣的結合進一步把農民束縛在土地上。農村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不流動的社會,村落共同體構成了農民幾乎全部的生存空間。狹小的土地、艱難的生存空間,千百年來,使農民的眼光局限在那塊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的土地上,農民像嬰兒眷戀自己的母親一樣眷戀著土地,只要土地還沒有被剝奪,農民一切都可以忍受。農民在對土地的依戀中變成了土地的附屬品,他們的生活節奏就如同從土地中生長出來的植物一樣,在四季交替的循環中運轉。土地讓農民一年年地播種著希望,卻收獲著世世代代循環的苦難,在狹小的空間里耕作,用牛耕地,用手工播種,用鐮刀收割,人地捆綁在一起,方圓幾畝的土地,就足以把農民牢牢束縛住,在土地上耗盡一生的時光。農民恨土地把自己限制在土地上,束縛了自己的發展。
2.恨土地成了農民的負擔。農民對土地的愛是真摯的,他們把土地當作命根子。中國農民是最勤勞的,在土地上面朝黃土背朝天地精耕細作,但土地并沒有給他們帶來財富,相反,現在出現了農民只有遠離土地才能致富的現象,土地成了農民手中的燙手山芋,成了農民的負擔。一方面,日趨沉重的農民負擔有相當一部分是按地分攤的。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有可能面臨罰款。農民外出打工不管種不種田,各種稅費一分都不能少,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民的負擔多少由承包土地的多少決定、在減輕非農戶負擔的同時,但加重了農戶,特別是純農戶的負擔,形成了人少地多的農民負擔重,出現了“多種地、多負擔、多吃虧”的不公平現象,沉重的負擔使一些農民“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土地已成為農民的沉重包袱,被一些農民看作套在腳上的腳鐐。
3.恨土地的經營收入不斷下降。近年來,土地經營的收入在農民的收入結構中比重不斷下降,農民收入中相當一部分來自非農收入。而多數農產品提價的空間非常小,降價的壓力大,自中國加入WTO后,農產品提價的空間越來越小,而農產品成本卻依然在不斷增加,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的轉移、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以及社會的進一步發展,今后土地經營在農民收入中的比重仍然會不斷下降。因而土地在農民生活中的位置在進一步下降,在農民生活中所發揮的作用也會越來越小。日趨沉重的土地負擔,使越來越多的農民感到土地“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不少農民將土地視同包袱。農民對土地是愛也深,恨也深,農民想離開土地的愿望也會越來越強烈,對土地的感情越來越疏遠,因而撂荒現象進一步加劇。“安徽省有統計的土地撂荒面積為135萬畝,占總承包面積的1.2%,2000年,湖北省季節性撂荒面積達200多萬畝,占耕地總面積的4%左右。江西省撂荒面積為65萬畝,占全省現有耕地的2%左右,其中季節性撂荒占撂荒面積的80%。重慶市今年土地季節性撂荒估計將達到189萬畝”。[5]撂荒現象是農民對土地經營收入不斷下降的一種無奈的反映,是農民對土地由愛變恨的集中體現,農民對土地的恨通過撂荒現象毫無保留地表露出來,但是農民對土地的這種恨不是主動的,而是被動的,是一種無奈的恨。
4.農民恨土地調整頻繁,使用權不穩定。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在村的范圍內將土地按照人口進行平均分配,根據“增人增地、減人減地”原則,農戶家庭人口的變動,人口減少的農戶應該退出相應的一份土地,新增加人口的農戶得到一份相應的土地,人口不發生變動的家庭所耕種的地塊,則不進行調整。但部分農村土地調整過于頻繁,“據調查,從1978年以來,農民承包的土地已經平均調整3.01次,至少有超過60%的村莊和60%的農戶經歷過土地調整。”[6]為了更好地避免在承包期限內隨意調整農戶的承包地。1999年1月1日開始實行的新的《土地管理法》有非常明確的規定:農戶承包土地的期限為30年。在最初的15年承包期滿后,政府又決定延長土地承包30年不變,但在農村,3至5年調整一次相當普遍,少數村甚至年年有調整。而土地與其他的生產要素相比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要提高一塊土地的產出率,只能想辦法改善這塊土地的生產條件,如農用機械、生產工具、運輸工具、灌溉設施、排水設施、塑料大棚、修建田埂、改良土壤、水土保持以及使用農家肥等投資。這樣的投資,投入大但回收期長。而且這種投資一旦發生,就無法與特定地塊相脫離。而土地調整可能會使農戶在下一次調整中失去現在所耕種地塊的使用權,導致農戶無法獲得進行長期投資的預期回報,從而會削弱農戶進行長期投資的積極性。一方面,農民恨如果沒有對土地進行投資,那么土地的產出率就無法得到提高;另一方面,農民恨如果對土地進行投資,那么對土地的投入可能會付諸東流,難以得到應有的回報。
5.農民恨模糊的農村土地產權。我國憲法第10條規定“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于國家所有的以外,屬于集體所有”,《土地管理法》和《農業法》規定“農村土地屬于鄉、村、組集體經濟組織所有。”但是這些法律并沒有具體規定土地歸屬哪一級集體所有,表面看來我國農村土地由集體所有,具體是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村民委員會或者村民小組占據所有者身份,但是事實上卻又都不是,土地的產權相當模糊。
6.農民恨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一方面,農民的土地在使用權上受到法律約束,除了農業用途,不得它用,有些土地甚至不得農耕,只能種草種樹,此外,土地的處置權也受到一定的約束,農民不得將自己的土地賣掉;另一方面,我國農村土地完全是由政府壟斷,集體的土地要經過政府征用后才能進入市場,政府可以憑借其對土地市場的壟斷地位,利用行政權力來征地。低價從農民手里征地,然后以征地價格的幾倍、十幾倍、幾十倍的高價賣給開發商。現在政府只要想用地隨時可以把看中的土地征過來。農民使用著土地并不等于農民真正有土地使用權,事實上農民并沒有真正完整意義上的土地使用權。
7.農民恨各級干部掌握了實際的土地所有權和分配權,恨土地權利屢遭侵害、對土地的保護軟弱無力。改革開放以來,持續的經濟高速增長,既帶動了城市規模的擴大,又帶來了非農建設用地的迅速增加。按照“取之于土、用之于土”的原則,土地出讓金應該主要用于農村建設和農民增收,但事實卻是大多數土地出讓金被政府用于城市建設,“雖取之于農,卻用之于城”,農民非但沒有成為大規模征地過程中的最大受益者,反而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失去土地的農民,成為種田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日前,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有關負責人透露說,近10年,由于我國城鎮化速度加快,被征地農民達到4000多萬。他預測,十一五期間,每年還要新增被征地農民300萬。換言之,每天我們的身邊還會增加約1萬失地農民。”[7]盡管《農村土地承包法》賦予承租方對土地租賃的合法權益,但在農村,租賃的最終權仍然由各級干部掌握,肆無忌憚的開發者對土地的掠奪仍然具有很大的威脅。農民本來應該是土地的主人,但實際的土地所有權和分配權掌握在各級干部手中,無權參與有關土地征用的談判,更由于農民缺少確定的權利保障,在強勢的政府面前,農民明顯處于弱勢地位,無力保護自己的土地。農村財富則以土地流轉的方式轉入了城鎮,“改革開放以來,政府通過征地從農民手中拿了2萬億元。”[8]農民對土地的恨在農民的土地權利屢遭侵害,尤其是在土地被征后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而這種恨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農民對土地的愛,是農民對土地那種愛恨交加的復雜感情的最好體現。
參考文獻:
[1].魁奈.魁奈經濟著作選集[M].商務印書館,1979年,第333頁
[2].黃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J].讀書.2006(2),第37頁
[3].費孝通.鄉土中國生育制度[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7頁
[4].王滬寧.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5].張紅宇.正確看待農村土地撂荒現象[N].中國經濟時報,2001-5-11
[6].遲福林.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N].人民日報,1999-1-5
[7].杜駿飛.日增一萬失地農民出路何在?[N].廣州日報,2006-08-09
[8].王運寶.土地政策改弦更張[J].決策咨詢,2004(10),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