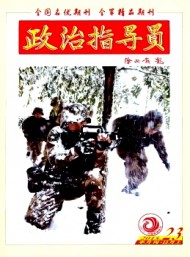政治社會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6 14:35:50
導語:這里是公務員之家根據多年的文秘經驗,為你推薦的十篇政治社會論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文章,歡迎參考。

社會政治理論論文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政治社會”思想源于亞里士多德,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社會政治”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政治學》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治和被統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社會政治”的思想,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出來。摩爾根發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節”。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家”,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實”[4](第253頁)。“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現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賓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視野雖然擴大了研究政治社會的眼界,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現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會認識眼界引向階級社會的歷史最深處,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以說是我們兩人的――唯物主義的歷史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來闡明摩爾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產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社會主義政治模式研究論文
「摘要」如何在吸收人類政治文明普遍成果以及保證中國共產黨執政黨地位的基本前提下,設計符合我國國情的政治模式,已經成為我國改革當前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本文提出了以“多數黨法定制”為核心,司法、行政與統計審計三權分立,但在嚴格條件下又受制于立法機構的、不同于西方三權分立的社會主義新政治模式。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模式
一、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4點基本共識
1.1必須尊重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謂“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即諸如“權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基本原則。經過世界各國漫長的政治文明實踐,這些原則都已經得到了充分證明。
在“人類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必須承認我國在整體上沒有達到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很明顯的一點基本事實就是,在國內企事業單位的各種政治學習材料中,傳統風格的思想政治教育內容占據絕大部分,而對于現代政治學經典理論甚至是這些理論的經典案例也罕見涉及。臺灣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吳文程在為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托利(GiovanniSartori)著、雷飛龍翻譯、臺灣國立編譯館1998年出版的《比較憲政工程》一書做序時指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都是眾多自稱馬克思主義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語并非妄言。因此,中國政治制度必須吸收世界先進政治文明的精髓。在此基礎上,才能夠進一步考慮中國特色的創新。
政治社會化本質研究論文
摘要:政治社會化本質上是統治階級主導的,傳播主流政治文化的過程,根本目的在于實現和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政治社會化在改造舊的政治文化,傳播、灌輸和確立新的政治文化;推動社會政治化,維護和保持主流政治文化;整合亞文化,促進社會政治文化趨同主流政治文化;順應社會政治變遷,實現主流政治文化的自我變更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關鍵詞:政治社會化;本質;功能
政治社會化理論研究即使在我國當下也不是什么時興和前沿的事情了,但是從實踐層面上看,政治社會化的效果仍有待于提高。在我國,公民的政治意識仍然不強,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程度仍然較低。因此,加強政治社會化問題研究,客觀地揭示政治社會化的本質,全面分析政治社會化的功能,對于我國的政治民主化進程有著重要的推進作用。
一、政治社會化的內涵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政治社會化研究最早發軔于美國,產生于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一種著重研究人們怎樣獲取以社會政治文化為基本特征的政治信念、政治準則和政治價值,以及社會怎樣實現其特有政治文化的繼承和發展的理論。
研究政治文化問題的學者們認為,政治文化作為政治心理、政治信仰、政治認識、政治理論等,這些是不能遺傳的,任何人也不能把他自己所具有的政治文化通過生理途徑傳給他的下一代;一般來說,政治文化都是后天得來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政治學者們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對政治社會化概念進行了界定,其中較為經典的界定就是“政治社會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維持和改變的過程”。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論文
同志在十六大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在我們黨的文獻中首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命題,既是十六大報告的理論亮點,也是重要的理論創新,標志著我們黨把對社會主義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新水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最新發展。深刻認識和準確把握對十六大報告關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論述,切實推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對于全面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現實和歷史意義。
一、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任務的提出,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
政治文明是人類社會政治生活的進步狀態,從靜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程中取得的全部成果;從動態的角度看,它是人類社會政治進化發展的具體過程。它是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三個組成部分構成的有機整體。其中,政治意識文明是政治文明之“魂”,是政治制度和政治行為的精神指導;政治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之“繩”,是政治意識的規則化和政治行為的具體規范。政治行為文明是政治文明之“形”,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制度作用于環境的活動,也是政治意識和政治制度的具體體現。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史的一個嶄新階段,包括社會主義政治意識文明、政治制度文明和政治行為文明等內容,它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代表著人類社會進步的發展方向,具有較高的自覺性、廣泛的人民性和前途的光明性等特點,其核心和精髓就是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民主,保證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理想目標得以實現。“文明”作為人類社會的進步狀態,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有機部分。其中,物質文明是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礎,而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對政治文明有著重大的促進作用。它們相互作用,共同推動社會文明程度的不斷提高。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論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關系時就指出:“物質生活的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馬克思不是將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所制約的對象簡單地劃分為“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而是劃分為并列的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三個方面。與此相適應,文明應包括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事實上,人類文明的發展總是表現為三個文明的協同發展。人類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最初表征,不僅表現為勞動產品的剩余和文字的產生,而且還表現為階級或等級的分野和政治權力的產生。古希臘留下的文明遺產,不僅包括一度發展的商品經濟、自由探索的精神、各種形式的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而且包括對個人自由和責任的強調、民主政體的理論和實踐。近代資產階級創造的文明成果,既包括發達的市場經濟和民主、自由、人權的基本理念,還包括民主的政治體制和規范的政治運作程序。不僅如此,政治文明還在一定程度上制約或影響著其它兩個文明乃至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從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看:1.政治文明為物質文明建設提供正確的政治方向。因為物質文明本身是無所謂價值目標的,但是作為人類意識的活動——政治文明建設則是有著明確的價值目標的。不同時代、不同階級所進行的物質文明建設都是圍繞著一定的利益關系而展開的。2.政治文明為物質文明建設創造安定團結的政治環境。古往今來,凡是物質文明蓬勃發展的時代,必定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時代;反之,凡是政治腐敗、社會動蕩的時代,必定是物質文明衰落或倒退的時代。凡是有遠見的政治家都十分重視安定團結的國內政治局面的維持與和平共處的國際環境的營造。正因為如此,所以,鄧小平多次強調: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沒有穩定的環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從政治文明與精神文明的關系看:1.政治文明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必要的前提條件。縱觀人類文明發展史,凡是精神文明發展程度高的時代,精神文明都是作為物質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伴生物而出現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古希臘之所以能在哲學、政治學、倫理學、數學、天文學、建筑學、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取得令世人矚目的成就,歸根到底在于當時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和城邦民主制的建立。歐洲文藝復興之所以從意大利興起,是因為意大利最早出現了近代歐洲政治精神,統治者最早打破了封建傳統,實行了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法。可見,政治文明建設是帶根本性、全局性的文明建設,沒有政治文明創造的前提條件,就不可能有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2.政治文明為精神文明建設提供基本的政治方向和必要的政治保障。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精神文明建設都離不開政治權力的扶持和幫助。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國家,經濟的騰飛和文化的進步,尤其需要政治文明的牽動。沒有政治文明發展所提供的前提條件和政治保障,精神文明建設的奮斗目標就是一句空話。總之,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與政治文明建設是密不可分的。脫離政治文明建設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不僅不會成功,反而會使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迷失方向和失去保障條件。
政治文明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內在屬性,主要在于:1.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核心內容——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的核心與主體。它與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及上層建筑的其它部分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統一的社會主義社會。2.社會主義社會與其它社會形態的根本區別在于:它從根本上否定了生產資料與政治權力少數人的占有,實現了生產資料占有的社會化和政治權力的民主化。如果一個社會在政治上不是多數人當家作主,正像在經濟上不是多數人占有生產資料一樣,這個社會就絕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鄧小平同志指出: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因此,提出政治文明建設的任務,強調堅持“三個文明”一起抓,正如十六大報告中所指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就是要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了與“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相統一,是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豐富和發展,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體目標要求和實踐活動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二、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任務的提出,是對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經驗的科學總結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論文
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志。同志在黨的十六大的報告中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的重要目標。”他在考察中國社會科學院時也曾強調,“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應是我國經濟、政治、文化全面發展的進程,是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全面建設的進程。”(注:參見《文匯報》2002年7月17日。)把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提到了新世紀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戰略目標的高度,提到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的地位,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創新。深入探討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問題,對于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不斷發展和完善,加快中國政治發展和政治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
關于“文明”的概念,西方大多數進步思想家和學者是從“進步的文化”這個意義上來理解和使用的。美國著名人類學家、民族學家摩爾根認為“文明”是特指與蒙昧社會和野蠻相區別的歷史階段,是反映歷史(文化)進步的狀態。
馬克思主義認為,文明是一個社會歷史范疇。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指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頁。)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明確指出:“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個過程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0頁。)顯然,政治文明是隨著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的階段,伴隨著人類歷史(文化)的進步,國家的產生和民族的形成而產生的,是與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政治文明作為一個社會歷史范疇,是與社會公共權力相關聯的社會政治關系和政治權利、政治制度和體制、政治文化和理念、政治運行規則和政治行為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互相影響、彼此溝通和協調發展的統一體,是政治實踐的科學總結和政治智慧的運用藝術,是人們改造世界所獲得政治成果和政治發展和進步狀態的總和,是人類解放的實現程度的體現。由于各國的社會、經濟、政治、歷史、文化傳統各有特色且發展水平不同,所以政治文明不可能是一種模式,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是多元的、豐富多彩的和不斷演進的。
事實上,人類開始他們的政治生活以來,就不斷探求政治生活的奧秘及其本質,思索人類和政治共同體的關系,設計符合人類本性的政治生活模式,追求和諧、美好的政治生活。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人類政治生活的發展是與人類政治文明的進步聯系在一起的。人類越發展,社會越發展,政治文明發展的程度就越高。人類政治生活質量的提高和改善,是在人類政治文明不斷進步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的。
海洋政治社會研討論文
摘要我國既是大陸國家,又是海洋國家。保護我們的藍色國土是我們的責任。近年來,人們在談論藍色國土的時候對南海問題投以高度關注的目光。南海問題反映出海洋政治社會對海權、海洋資源的關注,海防、海洋軍力和海洋安全問題,海洋政治社會中的大國博弈等等。
關鍵詞南海問題;海權;海洋政治
我國有960萬平方公里的陸地國土,還有300多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有人說我國的國土象一只雄雞,但如果把我國的海洋算進去,我國的領土更像一把火炬。保護我們的藍色國土是我們的責任。
近年來,人們在談論藍色國土的時候對南海問題投以高度關注的目光。所謂南海問題,即指中國與東南亞部分國家圍繞南中國海主權歸屬及海洋資源開發所產生的爭議。其實質是東南亞某些國家否認我國在南海U形斷續線內的主權,從而非法占據并大肆掠奪資源。爭議的主要內容有兩個:領土主權爭議和海洋資源開發權歸屬。[1]南海問題作為中國與其他南海周邊國家關系中一個十分復雜而又重要的問題,由于其涉及國家主權、歷史、法律及敏感的現狀,使其成為政治學、歷史學、國際法學、國際關系等學科專家學者共同關注的焦點。
南沙群島地處廣闊浩瀚的南海南端。
南沙群島是我國南海四大群島中分布最廣,位置最南的群島,位于北緯4度到11度30分和東經109度30分到117度50分之間,有230多個島嶼、礁灘和沙洲,南北長500多海里,東西寬400多海里,總面積24.47萬平方海里,現屬海南省轄區。南沙群島地處熱帶,漁業資源特別豐富,富含海藻、海帶等熱帶資源,以及非常可觀的海洋能源和鹽業資源。此外,南沙還蘊含極為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據估計,南沙西南直到沙撈越的廣大地區,是亞洲大陸架3個最大的貯油地區之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科學家發現南沙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其中曾母盆地、沙巴盆地、萬安盆地的石油儲量豐富,估計總儲量將近二百億噸,是世界上尚待開發的大型油藏之一,其中有一半以上儲量分布在中國海域。
社會政治理論分析論文
[摘要]“社會政治”是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政治社會”思想源于亞里士多德,是一種以國家為中心的政治觀;而“社會政治”思想始見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后被馬克思、恩格斯作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闡釋,指的是無階級社會或階級后社會的政治。“社會政治”理論與19世紀實證主義者所主張的政治社會學理論有著根本的區別,其方法論基礎是歷史唯物主義。“社會政治”理論的提出和研究,對詮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發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在西方政治-社會思想史上,關于“政治社會”與“社會政治”兩個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經歷了很長一段時間的演化過程。“社會政治”與“政治社會”相對應的兩個術語,并不是同時出現的。要了解什么是“社會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會”一詞的含義和由來。一、“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的思想起源關于“政治社會”的思想,從其思想淵源來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第一個提出和系統論述了“社會團體”和“政治團體”的概念。《政治學》開宗明義就指出:“我們見到每一個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種類的社會團體,一切社會團體的建立,其目的總是為了完成某些善業——所有人類的每一種作為,在他們自己看來,其本意總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會團體都以善業為目的,那么我們也可說社會團體中最高而包含最廣的一種,它所求的善業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廣的:這種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團體就是所謂‘城邦’,即政治團體(城市團體)。”[1](第3頁)看來,他把實施統治和被統治的“城邦政治”稱為“政治團體”(如亞氏稱一種“海太利”的組織為“政治社會”)[1](第98,483頁)。西方傳統政治理論中的國家即“政治社會”的觀點,其理論始源就是直接來自這里。不過亞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團體)視為“社會團體中?罡叨罟愕囊恢幀?即整個社會組織的一個部分,認為社會團體同政治團體是有區別的。后來,人們使用政治社會的內含又有所變化:稱政治社會即指國家社會。盧梭就是這一觀點的典型代表。他在寫作《社會契約論》的過程中,曾明確地將國家體制稱作政治社會,把國家、社會共同體、社會契約等詞,幾乎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1。這就為西方“政治社會”說奠定了基礎。盧梭以“社會契約”理論假設,說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歷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國家同社會完全混同了起來。使后來的西方思想家們把有國家存在的社會看做是一個亙古的“政治社會”。19世紀初,孔德、斯賓塞雖然提出用實證主義、社會有機體等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現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會”的范圍內。“社會政治”的思想,到19世紀70年代才萌發出來。摩爾根發表《古代社會》一書,實現了人類學的革命。該書從社會進化論觀點出發,運用社會實證的方法,詳細地考察了人類“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類社會的“兩種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認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產生于社會(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發生于國家(Civitas)。他指出:“人類是從發展階梯的底層開始邁步,通過經驗知識的緩慢積累,才從蒙昧社會上升到文明社會的。”[2](第3頁)“我們可以在這里提出一個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態都可歸納為兩種基本方式,此處使用方式(plan)一詞系就其科學意義而言。這兩種方式的基礎有根本的區別。按時間順序說,先出現的第一種方式以人身、以純人身關系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社會。這種組織的基本單位是氏族;在古代,構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聯盟,它們是順序相承的幾個階段。后來,同一地區的部落組織成為一個民族,從而取代了各自獨占一方的幾個部落的聯合。這就是古代社會從氏族出現以后長期保持的組織形式,它在古代社會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臘人和羅馬人當中,直至文明發展以后,這種組織依然存在。第二種方式以地域和財產為基礎,我們可以名之為國家。這種組織的基礎或基本單位是用界碑劃定范圍的鄉或區及其所轄之財產,政治社會即由此而產生。”[2](第6頁)又說:人類社會“政治的萌芽必須從蒙昧社會狀態中的氏族組織中尋找”。對于這種政治的萌芽,摩爾根稱為Government,以區別政治社會的Politics。[2](第4頁)
這就十分明白,摩爾根已經把整個原始社會的政治生活叫社會的政治方式,把產生國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稱為“政治社會”。在這里,摩爾根已經超出了以往資產階級思想家關于國家、社會的學術眼光,提出了人類社會初始階段的“社會政治”的理論。恩格斯就是以摩爾根提供的材料為依據,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對原始社會中的“Government”,即無階級社會的政治,首次作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詮釋。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就是他們兩人在理論與事實的結合上,把人類社會中的“政治社會”和“社會政治”兩個基本的概念作了區分,為建立“社會政治”的科學理論奠定了基礎。然而,從《社會契約論》到《古代社會》、《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在時間上從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間相隔的一個多世紀里,西方思想家關于政治與社會關系的思想,也發生了重要的演變。從霍布斯到盧梭,再到邊沁,經歷了17世紀的“自然的社會結構論”、18世紀的“市民社會論”的演進,那末,到19世紀及以后的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就逐漸開始認識到資產階級現代社會“是一種以國家和市民社會分離的社會”[3](第87-88頁),開始在一定意義上把政治(國家)與社會(市民社會)作為相對獨立的兩大領域來對待。幾個世紀一直將政治、國家、社會視為同一的“社會共同體”、政治社會即國家社會的社會契約論主流派的傳統觀點,首先受到了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大師——黑格爾的挑戰。黑格爾從其客觀唯心主義的基本命題出發,將自由派的政治經濟學及市民社會概念與孟德斯鳩的國家觀相調和,提出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相區別。黑格爾在對人的“社會化”進行社會分析時指出:人的社會化過程,需要依靠經濟利益關系和倫理世界的理性關系的結合才能實現。也就是說,一是需要作出經濟關系層面的“市民社會”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層面的“國家”分析。在黑格爾看來,所謂“市民社會”就是指連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內的社會經濟關系的總和。只有在這樣的市民社會里,每個人才有條件以自身為目的,同其他的人發生關系。黑格爾說:個別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為自己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來規定他們的知識、意志和活動,并使自己成為社會聯系的鎖鏈中的一個環節。”[4](第201頁)在市民社會里,實現的只能是社會成員個人之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關系,市民社會只是一個“中介的、否定的環節”。要將個體與共同體完全統一起來,融合為一體,那還需要借助于國家的力量。也就是說,國家是人實現“社會化”必要的理性基礎。所謂“國?搖?在黑格爾看來,它是“倫理世界”和“倫理理念現實”[4](第253頁)。“現代國家的本質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結合的”[4](第261頁),“個人本身只有作為國家成員才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4](第254頁)。黑格爾出于唯心主義的本性,把國家(即道德倫理關系)看做是決定性因素,而市民社會(即經濟利益關系)是被決定性因素,使兩者因果關系發生了顛倒。但他強調國家與市民社會相區別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19世紀西方現代國家與市民社會發生適度分離的歷史新趨勢,反映了社會發展的某種現實性的狀況,這對以后的思想家們思考、分析關于政治(國家)與社會關系問題,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然而,黑格爾把國家當做“最高倫理的表現”加以崇拜,在事實上美化了當時德國封建專制的國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現出黑格爾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賓塞在19世紀初期和中期分別提出社會進化實證論和社會有機整體論,建立起了現代社會學的基礎,從而使20世紀中期有可能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政治社會”,建立一門“政治社會學”。在傳統的政治學家們眼里,政治社會主要指政治國家和政治權力;而在孔德、斯賓塞以及后來的政治社會學家那里,政治社會學則主要是強調對國家政治的社會分析,這種學科?右八淙煥┐罅搜芯空紊緇岬難勱?但沒有跳出原有“政治社會”的基本框架。在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經比較充分地暴露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熱衷于把自然科學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會領域,抽象地強調社會有機整體,而忽視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階級關系的具體分析,回避已經尖銳起來的社會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他們的這種政治社會觀表現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現代西方“政治社會學”,在思想體系和方法論上仍然繼續著古典政治社會學抽象的社會觀。所以,政治社會理論與我們所稱的社會政治理論有本質的區別。
二、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會政治”的方法論基礎
19世紀40年代中后期,馬克思、恩格斯創立了科學的唯物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形態的經濟關系中,特別是從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有了剩余和社會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現、階級的產生的事實中,分析社會的政治上層建筑,形成了這樣的一個基本思想:“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社會的全部歷史(從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會解體以來)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即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斗爭的歷史;這個階級斗爭的歷史包括有一系列發展階段,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一勞永逸地擺脫一切剝削、壓迫和以及階級差別和階級斗爭,就不能使自己從進行剝削和統治的那個階級(資產階級)的奴役下解放出來”[5](第257頁)。《共產黨宣言》就是根據這一基本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關于什么是階級政治的著名論斷:在資本同勞動根本對立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圍繞政權所發生的“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5](第281頁)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將人們的社?崛鮮堆勱繅蚪準渡緇岬睦紛釕畬?跨進前人所沒有探索過的階級政治關系的新領域。這不能不說是對社會史、政治史在認識上的一個新突破。恩格斯后來在寫《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時總結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該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革中去尋找;不應當到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到有關時代的經濟中去尋找。”[6](第740—741頁)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將社會中的政治歸結為觀念的東西,而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切政治觀念,最終都應歸結為社會物質關系。所有受階級關系制約的政治,說到底,它只是階級社會的產物。
然而,非階級社會的經濟關系,其經濟基礎同與之相適應的政治上層建筑之間是否發生必然的關系呢?這是一個關系到要不要將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到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于馬克思、恩格斯來說,必須要有進一步的明確回答。馬克思、恩格斯自從創立了自己的唯物歷史觀和階級政治論以來,也一直試圖從一般唯物史觀上解決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他們無論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還是在《資本論》、《哥達綱領批判》以及《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人們只要仔細研讀這些重要文獻,就不難發現,他們在思考和論述關于史前社會和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在事實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層建筑問題(即不存在階級和國家的社會條件下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到底怎樣)時,總是有一種強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種科學的假設基礎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實,來證實他們的社會經濟基礎與政治上層建筑的辯證法原理和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科學的真實性和正確性。這個愿望直到他們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來實現。19世紀70年代中期,馬克思仍以極大的熱情研究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及其他人類學知識。關于這一點,恩格斯后來說得很明白:“不是別人,正是卡爾·馬克思曾打算聯系他的——在某種限度內我可?運凳俏頤橇餃說摹ㄎ鎦饕宓睦費芯克貿齙慕崧劾床髂Χ難芯砍曬?并且只是這樣來闡明這些成果的全部意義。原來,摩爾根在美國,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發現了40年前馬克思所發現的唯物主義歷史觀,并且以此為指導,在把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加以對比的時候,在主要點上得出了與馬克思相同的結果。”[7](第1頁)摩爾根所提供的大量關于史前社會的史實,“為全部原始歷史找到了一個新的基礎”[7](第14頁),證明了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完整社會歷史觀的科學性和正確性。理解這一點,不僅對于把握馬克思、恩格斯歷史唯物主義的整體社會觀有重要意義,而且,對于我們全面把握馬克思、恩格斯的整體歷史政治觀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意義的。這一整體社會歷史觀說明,階級和階級的政治,在人類歷史上,只是一種暫時性的社會歷史現象。在19世紀60年代以前,由于還沒有產生真實可靠的人類社會發展的知識足以說明史前社會為何物,人們的認識視野中雖然提到了“原始社會”,但對其實際狀況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論中的所謂“人類自然狀態”說,也僅僅是一種虛構的理論假設,不足為據。某些關于原始血緣家庭的論著,也正如恩格斯后來所說的那樣,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們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也講到了人類社會早期的社會生?止ぁ⒉柯淥兄頻萚5](第68—70頁),但他們認為,不能輕信那些資產階級的學者們對“史前時期”的種種描述。[5](第79—80頁)他們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原理,初步確認了人類“原初的歷史的關系的四個要素”[5](第78—81頁),并以此作為文明社會發展的起點。但是這在當時還是一種抽象的理論設想:在文明社會之前的人類社會歷史存在著一種有組織的社會形態,還沒有可能確切地知道史前社會的具體生活狀態,因而也就談不上論及原始社會的人們到底怎樣過“政治生活”的問題了。這也就是為什么他們兩人在后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都認定“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5](第272頁),人類社會的政治生活都是階級政治斗爭的政治的一個重要緣由。也正因如此,在他們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將國家與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民主政治與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論文
摘要:政治文明是人們改造國家制度及國家治理方式所取得的成果,表現為國家治理的改善和政治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目標和任務就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就是要改革不適應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政治體制,適應經濟和政治發展要求完善國家體制和運用新的治理方式,使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理念得以逐步實現,其中,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
關鍵詞: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政治體制改革
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將政治文明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并列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目標,這對于加強政治文明建設,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中國的政治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政治文明與民主政治建設
政治文明于十六大第一次寫入黨的政治報告。但早在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就已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主要背景有兩個方面:一是中共十二大報告正式提出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在設計十二大報告時,胡喬木主張并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分法,政治民主屬于精神文明的范疇。但許多人不同意,十二大報告專門另列了社會主義民主的部分。但這時沒有提出政治文明的概念。二是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中,學術界認為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僅僅提兩個文明還不夠,因為兩個文明的建設需要通過體制改革加以推進,兩個文明的成果需要通過制度建設加以保障,為此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更多的是以制度文明的概念出現的。
中共十六大報告關于政治文明的提法是對十二大報告的繼承和創新,是將政治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論述的,同時明確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
我國政治社會化研究論文
[摘要]文章從研究的學科視角、內容等方面綜合敘述了我國近十余年來政治社會化的研究狀況及研究結論,并分析了現有研究的一些不足,以期能在一定程度上推進我國政治社會化研究,為我國政治思想教育提供一定的決策依據。
[關鍵詞]我國;政治社會化;述評
政治社會化這一概念誕生于國外。自1958年美國學者戴維·伊斯頓(DavidEaston)首次發表有關政治社會化研究的論文以來,國內外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特別關注,政治社會化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政治社會化能否順利進行,進行的效果如何,都影響著國家的穩定與發展,世界各國統治階級都極其重視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我國對政治社會化問題歷來都很關注,但從真正意義上進行的研究起步較晚。盡管如此,20世紀90年代中期至今,我國學者經過努力,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下面分析整理近十年來我國學者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成果,發現其不足,以期推動我國政治社會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為我國政治文明建設提供有利的思想環境。
一、學科研究視角
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社會化屬于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重要專業術語。但其他學科也對此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如教育學、心理學等。不同學科對社會化研究的側重點和角度不同,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政治社會化無論何時都是政治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至今仍然是政治學界研究的熱點。政治學認為政治社會化是一個社會內政治取向和社會模式的學習、融合、傳播、繼承過程。社會學側重于研究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認為政治社會化是個人逐漸學會被現存政治制度接受和采用的規范、態度、行為的過程。盡管政治社會化是社會學中分支學科政治社會學中的核心組成部分,可真正深入細致研究政治社會化在社會學中卻為數較少。相反,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人們文化水平的提高,學者們日益注重素質教育的研究,許多教育者把政治社會化作為青年學生素質教育中的一項重要指標來進行研究,主要關心向年輕人灌輸知識和信仰,將社會主導政治文化內化學生的政治知識結構和思維能力之中。另外,心理學對政治社會化的研究也略有涉及,側重于研究充滿誘惑與機遇的轉型社會中,個體的政治認知及政治心理變遷過程。
二、研究內容
政治參與機制與和諧社會研究論文
論文關鍵詞: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機制;政治參與意義
論文摘要:黨的十七大提出了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要求,而政治參與機制是民主政治運行的橋梁。本文認為,加強政治參與機制建設不僅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內在要求,而且其能促進政治穩定、實現對政府的有效監督及促進社會公平和促進黨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隨著經濟社會發展而不斷深化,與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不斷提高相適應。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從十七大報告可以看出,使政治體制適應人民日益提高的政治參與積極性,成為我們當前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使政治體制容納人民的政治參與,在這其中政治參與機制具有非常重要意義。有效的政治參與機制能為政治參與提供順暢的溝通渠道,最終帶來政治穩定、社會公平,形成對政府權力的監督。因此,政治參與機制建設是黨的十七大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們進一步推進和諧社會建設根本途徑。
一、政治參與機制建設的必要性
1.政治參與理論上的分歧。西方文藝復興以來,啟蒙思想家運用社會契約理論對政治進行了深入闡述。盡管各個思想家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不同,但基本上都認為自然狀態已不適宜人的生存發展,所以大家放棄、讓渡自己的部分權利統一交給國家行使,以過一種有序的政治生活。這就意味著國家是所有人的國家而不是某個人或某個團體的國家,國民一律平等而任何人不得享有特權或遭受歧視。既然國家屬于國民且人人平等,那么人民就有權參與公共事務的管理。但是在人民如何參與管理國家事務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觀點:強調公民政治參與和限制公民政治參與。參與制民主主義者,包括盧梭、約翰·穆勒,以及近些年的帕特曼和巴勃等人都主張最大限度地擴大普通公民直接參與制訂政治性政策的機會。在現代一些大國,這還包括將許多決策的權力下放給地方共同體以及廣泛地應用公民投票來決定政策。與此相反,另一些人如熊彼特則贊成一種較為有限的公民參與;他們認為,在當選的職業政治家與普通公民之間應當有一種政治分工,前者負責決策,后者的作用是在定期的選舉中免除或黜選這些政治家及其政黨。根據這種觀點,現代民主制國家就是由政治家們治理的,而普通公民的參與是有限的和間斷的。我們知道,在一定時期國家權力和社會權力總量是一定的——社會權力強國家權力就弱;社會權力弱,國家權力就強。政治參與實質是社會權力和國家權力的博弈。不充分的政治參與意味著社會權力弱而國家權力強,導致的是強權政治;而過度的政治參與意味著社會權力強國家權力弱,那么國家的權威就要削弱,帶來政治失序、社會動亂。所以政治參與理論的分歧關鍵在于政治參與深度的問題,也就是政治參與的界限是什么,這可以從現代化的進程中可以看出。
2.現代化進程中的政治參與。在現代化初期,啟蒙思想家們提出了人民主權,以聯合廣大人民推翻封建專制統治,人民主權的思想深入人心。所以,在共和國建立后,人民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有權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但是在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每個人都來管理公共事務顯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在從現代化初期向現代化中期轉變中,前期為了推翻封建制度而宣揚的直接民主觀念,帶來了普遍的政治失序和社會動亂,反而成了現代化進程的阻礙。而在現代化中期向現代化后期的轉變中,人們才擺脫直接民主的觀念,認識到民主在現代社會只能是代議制民主,通過對前期教訓的反思,人們才認識到——政治參與也不是人民直接參與公共管理,而是選出自己的人代表自己來管理公共事務或者以多種方式和途徑來影響政府活動。所以,只有從現代化的進程才可以理解為什么盧梭宣揚直接民主,而密爾、熊彼特等思想家卻堅信代議民主。因此,對于正在進行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政治參與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參加國家政權的管理,而緊緊意味著對公共事務管理施加以影響。所以,為了維護政治的平穩運行,必須建立有效的政治參與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