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寫作藝術的要素
時間:2022-08-09 02:17:00
導語:通訊寫作藝術的要素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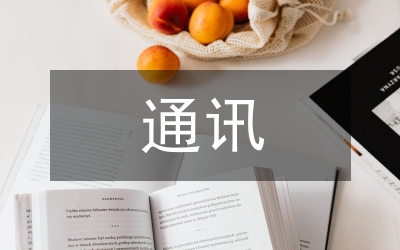
通訊是較為詳盡、生動地報道新聞事件和人物風貌的新聞體裁,是“比消息更為詳盡的新聞”。通訊寫出的事件更完整,人物更豐滿,可以讓人們更全面地了解新聞事件的全貌。新聞工作者往往捕捉生活中最典型的事實或形象,以生動的情節和豐富的情感去再現這種典型,從而表現時代的精神和主旋律,因此,通訊要能真正引導人、感染人,發揮其應有的社會作用,除了其作為新聞體裁的一些基本要求外,典型、生動、含情應作為其寫作藝術不可或缺的審美要素。
一、典型
新近發生的事一般都可以成為消息,但不一定能寫成通訊。這是因為消息只是滿足人們的知曉欲,強調有意義;而通訊則是要用生動的事實教育人,豐富的情感感染人,它更具有導向性和啟迪性,自然通訊選材也就更為嚴格,其根本點就是要反映典型,寫人、寫事、寫情節都必須具有典型意義。典型具有代表性,能反映客觀事物本質和規律;典型具有社會導向性:,一個典型即一面旗幟。通訊以生活中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為報道對象,可以弘揚正氣,宣傳先進,反映時代精神。正如列寧所說:“用生活中生動的具體事例和典型來教育群眾。”所以通訊寫作首先要想到所報道的人或事是否具有時代精神和現實指導意義。只有充分表現時代精神,具有強烈現實意義的典型報道才能產生震撼力,才有可能成為讓人過目不忘的優秀通訊,才能做到“以正確輿論引導人,以先進的人物激勵人,以真實的事件震撼人”。如新華社的長篇通訊《20歲的人生跨越》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先后被一百零九家報紙刊用,拉開了全國范圍內集中、廣泛宣傳李向群英雄事跡和成長道路的“宣傳戰”,從中央到地方都極為重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部長丁關根說:“李向群這個典型抓得好,思想蘊涵非常豐富,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為李向群題詞:“努力培養和造就更多李向群式的英雄戰士。”這正是因為李向群的事跡反映了當代青年的本質和主流,具有強烈的時代性、典型性和導向性。
通訊作品是否抓住了典型是衡量一個記者思想和業務水準的尺度之一。一個優秀的記者往往獨具慧眼,獨具匠心,精心選擇,精心設計,站在歷史的高度,以鮮明的個性揭示時代主題,反映人民的呼聲。在九八抗洪斗爭中,除了李向群外,還涌現了高建成、楊德勝、吳良珠、李長志等英雄人物,也產生了《寫在大江兩岸》、《大江作證》、《砥柱中流》等一系列優秀的通訊作品。這些作品集中反映了抗洪官兵舍生忘死、堅韌不拔的英雄事跡,有力宣傳了軍隊威武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以強烈的震撼力感染影響人們;形象具體地展示了人民軍隊和武警戰士“不愧為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不愧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子弟兵,不愧為保衛國家和人民的鋼鐵長城”;弘揚了人民解放軍是新時期最可愛的人的光輝形象!可見作為一個新聞人要認真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多思多想,宏觀上把握,微觀上操作,選擇事例從個別到一般,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只有這樣選出的人或事才能是百里挑一,以一當十。
二、生動
通訊既不似消息要言不繁地敘述事實,也不似評論以邏輯推理來顯示真理所在。通訊可以用敘述、描寫、抒情、議論等方法詳細形象地報道人物事件。當然,它以生動形象見長。
生動性首先來自新聞事實本身的生動性,黑格爾在分析美的要素時說:“美的要素可分成兩種,一種是內在的,即內容;另一種是外在的,即內容借以現出意蘊和特性的東西。”事實本身是內在的,即內容。通訊要抓住最具特色和最具感染力的人和事進行描寫,讓人物和事件本身內在美得以最大顯現。所以通訊的生動性主要體現在對人物情節展開描述。不論是人物通訊還是事件通訊,人物都是重要的表現對象。對人物的外形、語言、行動等進行細致入微的描寫,使人物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形神畢現,以此來表現人物精神風貌,反映時代精神,增強通訊感染力。例如:《英烈父子》一文寫李向群父子兩人的事跡,并突出父承子業這一主題,其中有很多感人描寫。在寫到李向群的父親替兒子抗洪來到連隊,當連里點名到“李向群”時,“只見父親挺胸抬頭,一步跨上前,大聲答到:‘到!’”這里連用了四個動詞——挺、抬、跨、答,把英雄堅定果斷的作風和堅韌不拔的性格全盤端給了讀者,讀來頗有一種悲壯氛圍,更增添了我們對英雄父親的敬佩之情。
又如《學海勤求索,茛菪伴人生——記我國微循環與茛菪類藥研究開拓者楊國棟教授》報道了楊國棟教授伴隨茛菪度過了大半生,通過艱苦的努力,在研究茛菪類藥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同行稱他為茛菪藥物研究和開拓的帶頭人,新聞媒體冠以“茛菪仙子”的美稱,其中有一段楊教授的語言描寫:“我選中了莨菪類藥的研究,就要永不停息地為之奮斗下去。在學海中求索,在崎嶇山路上攀登,要的就是一股韌勁,一點精神。”這擲地有聲的話語表現了楊國棟那種不屈不撓,勇于開拓的精神,既是他研究取得成功的原因,也是他大半生奮斗的寫照,從中我們仿佛看到了楊國棟老人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身影,可見這段語言描寫對人物極具表現力。在通訊寫作中,適當地對人物進行描寫,不僅有表現力,而且能產生強烈的藝術效果,可以避免概念化地介紹,增加通訊的生動性。
除了人物,情節是通訊內容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人物通訊和事件通訊中,情節可以說是通訊的血肉。著名記者陳柏生說:“通訊與新聞不同,新聞強調用事實說話,而通訊除了事實以外還要有情節,有鏡頭,有聯想。”一些膾炙人口的優秀通訊之所以能在讀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引起強烈反響,原因之一就是具有不少能深刻表現人物的典型情節。通訊作者就是運用情節表現人物,體現主題。如新華社通訊《四百壯士戰洪魔》將壯觀的場面描寫和細膩的人物刻畫融為一體,展示了一組組精彩感人的鏡頭:
“……被滾滾洪流迎頭沖散的官兵.浮出游渦的笫一件事,依然是救助他人。官兵們一個個把自己僅有的救生器材推給群眾:有一件救生衣拖帶著一兩個群眾同洪水搏斗。有些官兵被沖出幾百米后,把當時所能抱住的大樹,一次一次地讓給群眾或戰友。”
“……戴應忠少將落水前沒穿救生衣。某旅通信參謀眼見洪流沖來,一把撕下自己的救生衣遞給他。55歲的戴應忠在幾名戰士幫助下爬上一棵樹后,為給后來上樹的戰士騰出一個枝丫立身,救一腳蹬著另一棵樹,在流速每秒三四米的滾滾洪流中一直堅持了近10個小時。”
這些活生生的畫面具體形象逼真,讀后讓人如聞其聲,如臨其境。
在情節展開的過程中,極具表現力的是細節。細節描寫是指對人的行為、外貌、心理等細小部分進行細膩地描寫。細節雖小但并非是可有可無的細枝末節,它是報道事實表現主題的重要手段。細節在通訊中作用是不容忽視的,“于細微處見精神”——生動典型的細節富有生命力,能夠加強通訊的思想性和藝術性。沒有感人的細節,就會缺乏生活氣息,人物、事件、思想都會顯得蒼白無力,很難產生表現力與感染力,也就談不上生動性了。美國記者休·馬利根說:“生動的細節可以使紙面上的文章留在人的心靈上,滲透到情感中去。”新華社資深社記者馮東書說:“細節是簡單的,但是由于它是有特定個性的實事,給人的印象能勝過許多形容詞;細節又是具體的,有見微知著的魅力,有時比抽象的道理更具說服力。報道中顯形傳神傳情要細節。”無疑細節是新聞的活力所在,它可以給通訊帶來強烈的感染力。
要抓細節就要深入基層,深入采訪現場,掌握大量生動、鮮活的第一手材料,并且深入挖掘精心選擇那些最能說明問題最能反映人們本質的富有特征的典型細節。只有這樣的細節才具有動人的魅力。在通訊《保衛科爾沁》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一天,直升飛機起飛前,通過機場的地方工作人員發現機長正在機組人員的胸前別著什么。‘是不是勛章?’這位工作人員走過去一看,原來是一排明晃晃的鋼針。機長的話很簡單:‘必要時在大腿上扎一下,提醒提醒自己。”公務員之家:
在科爾沁草原,直升機組成員在短短的20多天飛行425駕次,航程近8萬公里,空投空運食品、帳篷等物資400余噸,搶救運送被洪水圍困群眾200余人次。作者為表現他們超負荷、超強度勞作,選擇了別鋼針這一細節,典型而又有說服力,使文章精神盡顯,具有催人淚下、過目不忘的強烈效果,表現了人民子弟兵面對滾滾洪流、滔滔濁浪所表現出的戰天斗地的英雄氣概和心系人民的赤誠本色。可見生動精練的細節,言簡意賅、樸實深刻、可視性強,能夠收到“以一當十、窺斑見豹”的效果。三、含情清代袁枚在《讀詩品》中寫道:“作者情生文,讀者文生情。”以情動人是成功通訊的又一法寶。通訊雖然也是要客觀報道事實,但它又可由作者直接抒發對客觀事物的感受。古人云:“無物似情濃。”文章的好壞與否,關鍵在于作者有無真實的感情,通訊也是如此。“志思蓄憤”,對事物感受深、激情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寫出來的東西自然能打動人心;反之,如果作者對所報道對象無動于衷,不帶一點感情,那別人讀了也就不痛不癢,毫無味道。前蘇聯領導人加里寧有句名言:寫東西“要加點血進去”,所謂“血”就是指濃烈的情感。記者應該有濃烈的情感,愛其所愛,恨其當恨,并將這種情感溶進作品之中。所以通訊要有滲透力、感染力很強的“情”,記者要伴隨作品中所描述人物的喜怒哀樂做有情之人,敘有情之事,抓動情之時,把情感滲透到字里行間,讓記者、讀者進行感情交流,以真摯美好的情感去打動人,引起讀者的廣泛共鳴。
通訊的抒情既可以融于對事實的敘述中,情感表達得含蓄蘊藉,也可以與景物描寫結合起來,產生情景交融,情隨景生的效果;還可以直抒胸臆,酣暢淋漓地抒寫作者的情懷。采取什么方式,根據需要作者可以選擇,但不管以什么方式抒情,情感必需健康真實、自然充沛,用真切的思想感受表達一種褒貶揚抑,讓情感自然滲透到文章字里行間,并且流入讀者心中。只有這樣,才能打動人心,喚起共鳴,產生強烈的藝術效果。例如何平、劉思揚就是滿懷對鄧小平同志的深厚感情,寫下了《在大海中永生——鄧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記》一文。全文以大海為主線,以撒骨灰為切入點,寫出了鄧小平波瀾壯闊的一生;體現了鄧小平與大海同在、與祖國同在、與人民同在的主題。文章將現實、政論與抒情相結合,用“飛機盤旋,鮮花伴著骨灰,撒向無垠的大海;大海嗚咽,寒風卷著浪花,痛悼偉人的離去……”這樣的句子進行反復,形成了雄渾悲愴的主旋律,展現了鄧小平同志崇高的思想情操,抒發了各族人民對鄧小平同志的摯愛之情,有一種蕩氣回腸、深情難抑的強烈的藝術感染力。許多人是含著眼淚讀完這篇通訊的。1997年4月8日,北京音樂廳還以“在大海中永生”為題舉行了痛悼鄧小平同志的音樂朗誦會,著名配音演員喬榛、丁建華含淚朗誦了“在大海中永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書記處書記和觀眾一起出席音樂會,并對這篇作品給予高度評價,認為寫出了億萬人民對小平的感情。
綜上所述,一篇優秀的通訊一經發表,在社會上便會引起廣泛的、強烈的反響。這主要是由于作者在深入采訪的基礎上,不僅能夠站在歷史的高度、時代的前沿,深入挖掘事物的本質意義,表現其典型性和時代感;而且善于運用細膩的筆觸,描摹生動具體的情節,抒寫真摯美好的情致。只有具有深刻的典型性,藝術的生動性和豐富的情感性的通訊才能獨具魅力,讓人過目不忘,才能發揮其應有的宣傳和教育作用,使人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