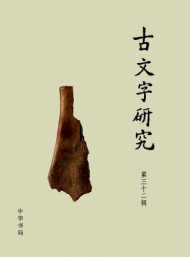古文學(xué)論文范文10篇
時間:2024-05-04 07:22:26
導(dǎo)語: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為你推薦的十篇古文學(xué)論文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古文學(xué)中的詩性語言特點論文
詩歌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學(xué)形式對中國的文學(xué)發(fā)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自春秋中葉出現(xiàn)的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jīng)》以來,中國歷代的文學(xué)作品中,尤其是古代的散文、韻文、駢文等文體,都體現(xiàn)出詩性語言的特點,直至到后來出現(xiàn)了唐詩宋詞兩大對峙的文學(xué)高峰,更是將詩性語言的特點展現(xiàn)無遺。
通過觀察,我認為“詩性語言”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大量修辭手法的使用。漢語的詩性語言中,比喻、引用、夸張、互文等修辭手法使用頻繁,增強了語言的表達效果和語言的美感。例如,李煜的“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就運用了比喻,將“愁”比作了“一江春水”,化無形抽象的“愁”為有形,使抽象的情思具體化了,讓讀者能深切的感覺到“愁”之深、之切。而其他比喻的使用,如“紅杏枝頭春意鬧”,一個“鬧”字,將原本靜態(tài)的紅杏寫活,將其人格化,表現(xiàn)出一派春天的生機勃勃之景。又如,“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引用的使用不但能借典故生動的說明作者所要表達的意思,而且能使文章顯得典雅精煉。再比如,李白的“白發(fā)三千丈,緣愁似個長”,用夸張的手法,突出了“愁”,同樣使表達更加生動形象。
但是,也要看到,在有些情況下,修辭手法的運用也會對讀者理解句意產(chǎn)生影響。就如上面例子中,“英雄無覓孫仲謀處”,如果不能發(fā)現(xiàn)其中的引用手法,而機械的對其進行翻譯,就很難體會作者所要表達的含義。而對于“白發(fā)三千丈”一句,有些人單純從客觀事實角度出發(fā),就會說,一個人的頭發(fā)怎么可能那么長,從而,忽略了對作品內(nèi)在含義的理解而片面的探討作者的寫作是否符合客觀事實。還有修辭中倒置的使用,如果不能應(yīng)從修辭角度的去理解,注意到倒置的使用,就會影響意思的理解。例如江淹的“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其實際順序應(yīng)為“孤臣墜涕,孽子危心”,若未能注意到修辭手法的使用,進行翻譯,就會出現(xiàn)錯誤。
二、打破語法規(guī)則的限制。一方面,正如前一點中“倒置”修辭手法的使用,并未遵循固定的句法結(jié)構(gòu),打破語法規(guī)則的限制,卻收到特別的表達效果,像杜甫的“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和《詩經(jīng)》中的“愿言思伯,甘心首疾”等句,改變了句子原有的平淡,增加了詩意,增強了韻律感、節(jié)奏感,也使語意變得錯落有致,而由于中斷了語流,使人們更加注意關(guān)注語句含義。但也正如上文所說,對句子的理解造成困難。
另一方面,在很多古典詩詞中,作者很少,甚至是不使用連詞、介詞等,僅把多個意象連綴起來。如,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只是簡單的將“枯藤”、“老樹”、“昏鴉”等幾個意象連綴到一起,卻成功的描摹出一派秋天的蕭瑟凄涼之景,表達出作者的孤獨之感與思鄉(xiāng)之情,并收到了電影中蒙太奇的表現(xiàn)效果。這種通篇意象的列舉,而無句法關(guān)系的連接,可以說是中國詩性語言的一個重要特征,雖然從一般的語法角度看不合規(guī)矩且缺乏連貫性,但從詩的角度看,語言凝練、簡潔,形象鮮明、突出。
古文學(xué)中的酒店婦女形象論文
譚正璧先生在其《中國女性的文學(xué)生活》中說“婦女文學(xué)是正宗文學(xué)的核心”,他的這句話說的如專指女性作家的文學(xué)活動,那就略顯偏頗。但如指涉及女性的文學(xué)活動,那就切合實際了。但是,千百年來由于婦女地位的問題,涉及女性的作品及活動多不被學(xué)者重視,直至近代,西方女性主義的傳入加上我國學(xué)術(shù)思想自身的發(fā)展,有關(guān)女性的文學(xué)才備受重視,女性作品的研究發(fā)展到今天,觸角已深入到能涉及的所有領(lǐng)域,從先秦到近代的各類女性形象都已涉及,歌女才女農(nóng)家女,女妓女妖女藝人,無一遺漏,然而,當我們翻開古代書卷,我們還會發(fā)現(xiàn)一類被人們遺忘在角落的人物——當壚女。大概從《史記》《漢書》的《司馬相如傳》,以及《西京雜記》記述卓文君私奔后當壚賣酒以來,才子佳人的佳話吸引了浪漫國人的想象,于是酒肆當壚女就成了編織浪漫傳奇的極好對象。當壚女是拋頭露面的良家女子,沒有妓女的卑賤歧視,卻又沾以美酒待客的風流,于是她們就成了無數(shù)文人筆下的精靈,不單寄寓了他們的愛情理想,還有他們的道德價值,更有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獨特認識,這些女性背后的文化意義,不容忽視。本文將從歷代相關(guān)的文學(xué)作品中對她們做出一定的分析,借以引起人們的重視。申明:本畢業(yè)論文由張翛然撰寫,版權(quán)歸作者所有。
1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的酒店婦女形象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古代文學(xué)中“酒店婦女”形象,但確切的說“酒店婦女”一詞在中國古代社會中并不存在。據(jù)考證酒店作為飲食場所在春秋戰(zhàn)國即已出現(xiàn),而作為固定行業(yè)名稱則在南北朝才開始出現(xiàn),如《南史·顏延之傳》:“文帝嘗召延之,傳召頻不見,常日但酒店裸袒挽歌,了不應(yīng)對。”但這種稱呼在文學(xué)作品中并不多見,“酒肆”“酒家”還是更為普及。因此將古代文學(xué)作品中與酒店相關(guān)的女性形象稱為“酒店婦女”并不貼切,如果追本溯源那么“當壚女”是大概更能概括其含義,古代酒店中放置酒的臺子被稱為“壚”,因此“壚”字也成了酒店的代稱,“當壚”就成了賣酒的意思。因此“當壚女”一般指賣酒女或酒店女主人。本文中“酒店婦女”一詞實為“當壚女”的現(xiàn)代稱謂,即指酒店的女主人或買酒女。只是為遷就當今時代的語言習(xí)慣,而稱“酒店婦女”。酒店婦女在文學(xué)作品中出現(xiàn),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是《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有關(guān)卓文君的描述。從這個才子佳人故事開始,“美女當壚”成為文人筆端的花朵,一代一代的綻放著,更絢麗多彩,也更迷離復(fù)雜。
1.1酒店婦女整體形象的整體演變
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被今人分為三個歷史階段——上古(先秦、兩漢)、中古(魏晉南北朝隋唐兩宋)、近古(明清鴉片戰(zhàn)爭前)。這一分法的科學(xué)性我們在此不做討論,最起碼它對于我們研究古代文學(xué)中的酒店婦女形象的演變歷程來說,是正確的。古代文學(xué)中酒店婦女作為主角出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中,大概應(yīng)是從《史記·司馬相如列傳》開始,這一段的描寫為我們奠定了當壚女明快健美的基調(diào),此后,樂府詩中的《羽林郎》《隴西行》更可見一斑。而到了《西京雜記》《世說新語》等筆記小說中以及后來的傳奇話本以及唐詩宋詞,則是豪放灑脫的“胡姬”,如李白的“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胡姬招素手,延可醉金樽”但是隨之王朝落日的到來,她們的形象也染上了滄桑。而到了明清以來,社會安定了,則出現(xiàn)了是女豪杰與女夜叉并存、順從者與掙脫者同在的的分裂形象。這些豐富的人物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幅時代畫卷。
1.1.1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
古代文學(xué)課教學(xué)研討
中國古代文學(xué)課是最具有傳統(tǒng)文化底蘊的科目,這門課一直是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的必修課。它的責任和義務(wù)之一就是從民族文化典籍中挖掘優(yōu)秀的文化思想,引導(dǎo)當代青年到經(jīng)典作品中去了解中華文化,到經(jīng)典作品中去了解賢者們的聰慧,到經(jīng)典作品中去體味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研究古代文學(xué)課的教學(xué)現(xiàn)狀與發(fā)展定位就顯得非常重要。
一、對外漢語專業(yè)古代文學(xué)課現(xiàn)狀分析
1.時代變遷與認識偏頗導(dǎo)致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方向迷失隨著社會經(jīng)濟的急劇膨脹,整個社會更趨于物質(zhì)化、技術(shù)化、工具化。實用主義和急功近利的心理已經(jīng)逐漸占據(jù)了主導(dǎo)地位。在大學(xué)校園,古代文學(xué)遠不如經(jīng)濟、法律、新聞、公關(guān)、市場營銷等課程來得實在。學(xué)生普遍認為多背幾首唐詩宋詞不如多考過幾個計算機等級證書和英語等級證書更能獲取就業(yè)機會,所以,在古文學(xué)課上看外語書、背外語單詞的大有人在,在下面看小說、雜志的也不乏其人。多數(shù)學(xué)生認為古代文學(xué)可學(xué)可不學(xué),更不愿在古代文學(xué)的學(xué)習(xí)上投入時間和精力。多數(shù)對外漢語專業(yè)的學(xué)生認為對外漢語教學(xué)只是一種語言教學(xué),教學(xué)內(nèi)容就是語言。一些教師和學(xué)生認為古代文學(xué)這門課離現(xiàn)實太過遙遠,在今后的實際工作中用途不大。這恰恰是忽視了文學(xué)與語言的必然聯(lián)系,忽視了文學(xué)是語言載體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其實語言和文學(xué)是彼此關(guān)照的。尤其是古典文學(xué),它不僅包含著文學(xué)意味,又不失中國古文明文化和經(jīng)典語詞。
2·教學(xué)時數(shù)的縮減導(dǎo)致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流于條框的闡釋經(jīng)過幾輪的教改,一般院校的古代文學(xué)課均降到200課時左右,甚至更少。于是,為了保證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多數(shù)教師在教學(xué)中只能停留在對中國古代文學(xué)發(fā)展史的簡單勾勒。教師講授的主要是《古代文學(xué)史》,而與之配套的《歷代文學(xué)作品選》則很少有時間顧及,即使對部分作品進行分析,也只能蜻蜓點水,浮光掠影,很少有時間對具體作品有一個比較全面的分析和闡釋。另外,課堂上教師為了節(jié)省時間也總是把結(jié)論性的東西以最簡潔的方式交代給學(xué)生,至于在課堂上充分發(fā)揮學(xué)生學(xué)習(xí)的主動性來對作品進行更多的剖析和理解只會使已經(jīng)很緊張的課時變得更加緊張。正因為如此,學(xué)生在課后很少關(guān)照古代文學(xué),考試的時候,也只是提前幾天苦背,在考場再一股腦地全部交給老師。學(xué)生的分析能力、思維能力很少有機會得到訓(xùn)練和提升。
3·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缺失導(dǎo)致古代文學(xué)教學(xué)的單一性使用最多的文學(xué)史教材有四部:第一部是游國恩等人編寫的《中國文學(xué)史》(1964),這部文學(xué)史目前是受批評最厲害的一部教材。第二部是章培恒、駱玉明編撰的《中國文學(xué)史》(1996),但教材內(nèi)容偏重“心理”或“人性”。第三部是郭預(yù)衡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1998),但疏誤不少。第四部是袁行霈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1999),這是一部現(xiàn)在使用較多的一部教材,包容性較強,吸收了大量較新的研究成果,但也因此出現(xiàn)了明顯的拼合、觀點重復(fù)和論證混亂等現(xiàn)象。該文學(xué)史試圖把具體細節(jié)和對整體的理解與把握聯(lián)系在一起,而整體的復(fù)雜性總是使簡單的概括顯出不足。另外,《中國文學(xué)史》從其涵蓋的范圍來看,應(yīng)該是指整個中國(包括少數(shù)民族)在鴉片戰(zhàn)爭之前的文學(xué)流派、文學(xué)現(xiàn)象和文學(xué)作品的綜合。而已使用過的四部教材無一例外的都只有漢族文學(xué),對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xué)很少提及。其實,少數(shù)民族并非沒有藝術(shù)水平比較高的文學(xué)作品,比如《格薩爾王傳》等等。中國文學(xué)多樣性的特點除文體的多樣性外,更主要的應(yīng)該體現(xiàn)在民族的多樣性上。各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xué)對文學(xué)史上所強調(diào)的主流文學(xué)有著或多或少的影響。而少數(shù)民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以其特殊的民族風格和氣質(zhì)展示了自身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和審美標準,豐富了華夏文學(xué)寶庫。在教學(xué)中如果加入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只能使課時更加緊張;如果不加入,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和創(chuàng)作技巧以及所蘊含的民族個性就會悄然流逝。
二、對外漢語專業(yè)古代文學(xué)課程的教改設(shè)想
語文教育思想探討論文
提要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現(xiàn)代散文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語文教育家。其思想理論體系的構(gòu)成可以概括為:朱自清超乎尋常地把語文教育的目的確立在使學(xué)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學(xué)生欣賞文學(xué)的能力的嶄新意義上,他鮮明提出作文訓(xùn)練(培養(yǎng)學(xué)生寫作能力)和技術(shù)訓(xùn)練(培養(yǎng)學(xué)生欣賞能力)才是語文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雖然講解、分析、辨別、練習(xí)早已普遍成為語文教育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但朱自清則獨具一格地極力倡導(dǎo)“讀”應(yīng)當成為整個語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變革的關(guān)鍵所在。
關(guān)鍵詞了解與欣賞作文訓(xùn)練技術(shù)訓(xùn)練精讀略讀講讀誦讀
**
引論
朱自清是中國現(xiàn)代散文領(lǐng)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們發(fā)現(xiàn)他還是現(xiàn)代中國一位出色的語文教育家。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總是無法擺脫朱自清是一位現(xiàn)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響,或者說朱自清大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創(chuàng)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蓋了他實際上相當豐厚細致的語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從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畢業(yè)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師范、揚州第八中學(xué)、吳淞中國公學(xué)、臺州六師、溫州第四中學(xué)、寧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華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學(xué)校南遷,任昆明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論著有與葉圣陶合著的《國文教學(xué)》、《精讀指導(dǎo)舉隅》、《略讀指導(dǎo)舉隅》、《標準與尺度》和《語文拾零》等。我們把目光從他的散文作品轉(zhuǎn)移到他眾多的教育論著,明顯可以看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自成體系。我想:站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審視作為語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斷地從各個方面來加深對他的教育思想的認識,將十分有助于提高我們目前以及將來語文教育發(fā)展解決重大問題的自覺性。我們把朱自清關(guān)于教育目的、教育內(nèi)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獨特主張和論述,總稱為朱自清的語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一、“使學(xué)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賞文學(xué)能力”
語文教育思想管理論文
提要朱自清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現(xiàn)代散文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出色的語文教育家。其思想理論體系的構(gòu)成可以概括為:朱自清超乎尋常地把語文教育的目的確立在使學(xué)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并且提高學(xué)生欣賞文學(xué)的能力的嶄新意義上,他鮮明提出作文訓(xùn)練(培養(yǎng)學(xué)生寫作能力)和技術(shù)訓(xùn)練(培養(yǎng)學(xué)生欣賞能力)才是語文教育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雖然講解、分析、辨別、練習(xí)早已普遍成為語文教育的基本手段和方法,但朱自清則獨具一格地極力倡導(dǎo)“讀”應(yīng)當成為整個語文教育的方法和手段變革的關(guān)鍵所在。
關(guān)鍵詞了解與欣賞作文訓(xùn)練技術(shù)訓(xùn)練精讀略讀講讀誦讀
***
引論
朱自清是中國現(xiàn)代散文領(lǐng)域里成就很高的作家,但我們發(fā)現(xiàn)他還是現(xiàn)代中國一位出色的語文教育家。只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們總是無法擺脫朱自清是一位現(xiàn)代著名散文家的深刻影響,或者說朱自清大量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尤其是他在散文創(chuàng)作方面的成就多少有些掩蓋了他實際上相當豐厚細致的語文教育思想。朱自清1920年從北京大學(xué)哲學(xué)系畢業(yè)后先后在杭州第一師范、揚州第八中學(xué)、吳淞中國公學(xué)、臺州六師、溫州第四中學(xué)、寧波四中等校任教,1925年-1932年任清華大學(xué)中國文學(xué)系教授、系主任,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后,隨學(xué)校南遷,任昆明西南聯(lián)大中文系主任,其教育論著有與葉圣陶合著的《國文教學(xué)》、《精讀指導(dǎo)舉隅》、《略讀指導(dǎo)舉隅》、《標準與尺度》和《語文拾零》等。我們把目光從他的散文作品轉(zhuǎn)移到他眾多的教育論著,明顯可以看到他的語文教育思想自成體系。我想:站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今天的眼光第一次審視作為語文教育家的朱自清,不斷地從各個方面來加深對他的教育思想的認識,將十分有助于提高我們目前以及將來語文教育發(fā)展解決重大問題的自覺性。我們把朱自清關(guān)于教育目的、教育內(nèi)容、教育方法方面的獨特主張和論述,總稱為朱自清的語文教育思想。本文不揣冒味,對此作一初步探討。
一、“使學(xué)生了解本國固有文化并且提高欣賞文學(xué)能力”
高中語文課堂教學(xué)優(yōu)化策略
摘要:高中語文是對學(xué)生語言積累和表達能力的綜合教學(xué)。因此,優(yōu)化高中語文課堂教學(xué)策略需要充分為學(xué)生創(chuàng)設(shè)自主語言表達環(huán)境,將教學(xué)環(huán)節(jié)以貼近學(xué)生認知途徑和探究學(xué)習(xí)目的的方式來呈現(xiàn)。同時,在教學(xué)實踐過程中,教師還要綜合審視學(xué)生的語文應(yīng)用能力和課程教學(xué)目標要求之間的差距,融合創(chuàng)新教學(xué)風格,增設(shè)新型教學(xué)輔助方法,真正提升學(xué)生在語文教學(xué)中的自主參與度,不斷深化高中語文課程教學(xué)改革。
關(guān)鍵詞:高中語文;課堂教學(xué);優(yōu)化策略
教師在教學(xué)中應(yīng)該增強對學(xué)生情感融入、文字表達自主性的引導(dǎo),不斷深入教材內(nèi)容,提高學(xué)生的思考深度。這樣學(xué)生能充分發(fā)揮課程學(xué)習(xí)與探索的積極性,針對課程問題和訓(xùn)練模塊展開有效討論,在小組合作學(xué)習(xí)中不同學(xué)生思考的切入點進行相互碰撞,有助于激發(fā)學(xué)生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和文字表達的準確性。
一、激發(fā)學(xué)習(xí)興趣,提升情境創(chuàng)設(shè)有效性
在課程設(shè)計時,教師要回歸課文內(nèi)涵,通過創(chuàng)設(shè)虛擬情境,有效將學(xué)生的閱讀情感構(gòu)建在文字理解的基礎(chǔ)上,這樣能借助課堂情境激發(fā)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興趣。例如,在教學(xué)統(tǒng)編版《普通高中課程標準實驗教科書·語文2必修》(以下統(tǒng)稱“必修2”)《游褒禪山記》這篇課文時,針對高中語文古文學(xué)習(xí),教師可以為學(xué)生創(chuàng)設(shè)古文學(xué)習(xí)的課堂情境,幫助學(xué)生更好地將個人情感融入作者的寫作意境中。教師先利用多媒體剪輯出王安石筆下的褒禪山的奇?zhèn)ス妍惥吧囊曨l,然后帶領(lǐng)學(xué)生從文章層次分析作者視角——從褒禪山外部到人跡罕至的景色進行深入探索。這種帶著好奇心進行情境創(chuàng)設(shè)的語文學(xué)習(xí)方式,能激發(fā)學(xué)生自主閱讀古文的興趣。教師要提升學(xué)生對文章深層含義的自主理解能力,可以從課文中選出不同的段落向?qū)W生提出相關(guān)問題:“而世之奇?zhèn)ァ⒐骞帧⒎浅V^,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見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根據(jù)這段話聯(lián)想生活中的例子,如何證明險境之處自有風景?學(xué)生結(jié)合自身語文知識的積累和《游褒禪山記》提出的論點,對教師提出的開放性問題進行深度思考,并積極回答:王安石用褒禪境遇暗示人生不要選擇好的路,而要勇于探索,遵從內(nèi)心,才能突破常人視野看見一番天地。在情境創(chuàng)設(shè)的過程中,學(xué)生能融入個人閱讀情感,將課文揭示的主旨建立在已經(jīng)掌握的知識層面上。在學(xué)習(xí)興趣的指引下,學(xué)生回答問題的思路更加多元化,有利于提升課堂互動學(xué)習(xí)效果。由此可見,教師要在課程中營造學(xué)生自主深入的課程環(huán)境,借助多媒體的輔助教學(xué)效果,將課文意境轉(zhuǎn)變?yōu)榫呦蠡恼n程情境,激發(fā)學(xué)生自主探索的學(xué)習(xí)興趣。
二、鼓勵平等溝通,營造合作氛圍
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影響
【摘要】從某種程度上講,漢代的古文經(jīng)學(xué)對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更多的是追求相對簡明的文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長篇大論,也使得文學(xué)創(chuàng)作逐漸向由繁趨簡發(fā)展。此外,漢代的古文經(jīng)學(xué)更加講究兼通,可以博采眾長,文化創(chuàng)作過程中借鑒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能夠使文章的表現(xiàn)題材更加包羅萬象以及無所不至,增強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批判精神。本文就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相關(guān)影響展開詳細論述。
【關(guān)鍵詞】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文學(xué)創(chuàng)作;影響
從專業(yè)化角度出發(fā),與今文經(jīng)學(xué)表現(xiàn)出來的煩瑣以及迷信相比較,漢代的古文經(jīng)學(xué)更多表現(xiàn)出了不同的解經(jīng)取向。具體來說,最主要的特點之一在于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的簡明性,一般情況下不會為章句之學(xué)。其次是講求兼通,而不重視家法師法,可以博采眾長。最后是通常會反對讖緯,而不會憑空臆說,具有相對較少的迷信成分。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引起自身的優(yōu)點為當前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來了深遠影響。
一、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所具有的簡明文風有助于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
漢代的古文經(jīng)學(xué)通常情況下不會是章句之學(xué),也沒有廣征博引,而是盡量追求簡明文風,并以才學(xué)為勝,從而使得文章可以深刻地表現(xiàn)出才氣橫溢。從歷史角度出發(fā),古文經(jīng)學(xué)得到廣泛重視是在東漢時期,影響深遠,其文學(xué)著作也逐漸向由繁趨簡方向進行發(fā)展。漢大賦所表現(xiàn)出來的鴻篇巨制也已經(jīng)逐漸消解,短篇式小賦日益興盛。該種短篇式小賦內(nèi)容方面并不追求富博,在抒寫過程中也非常平淡,但是卻可以把物、志趣、景、事與情感因素進行有機結(jié)合,形成虛實相襯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其想象空間,有效增強了文章的藝術(shù)感染力。例如蔡邕作品《蟬賦》、趙壹作品《窮鳥賦》以及阮!作品《紀征賦》都是短篇小賦[1]。此外,小賦由于其自身的體式相對簡短,而且更加注重章法,再加上取材相對集中、講究意趣,具有相對較強的個性以及情深意切,所以技巧彌精,在人物刻畫方面非常細致,章法趨嚴以及辭采日美。文章的氣韻相對生動,具有言短意長的特點,從而為之后的詩體創(chuàng)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比如張衡的《思玄賦》已經(jīng)逐漸暗合了七言詩體。漢代的史傳文學(xué)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xiàn)出了古文經(jīng)學(xué)所具有的簡明特點,將《史記》以及《漢書》進行對比,能夠看出《漢書》在語言內(nèi)容方面已經(jīng)相當簡練[2]。《史記》作者司馬遷是私家著史,所以受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影響較少,且司馬遷在實際寫作過程中將自己的滿腔熱情也融入其中,以此發(fā)憤抒情,在相對客觀的史實敘述過程中,已經(jīng)傾注了大量的正義評判。但是《漢書》作者班固則不同,他的著史是官修,受正統(tǒng)思想影響非常大,沒司馬遷深沉。《班固傳》中評價班固贍而不穢以及詳而有體,顯然與《史記》有著較大差異。從某種程度上講,司馬遷以及班固之間的分歧也是時代所盛行的風氣造成的。
二、漢代古文經(jīng)學(xué)迷信色彩較輕有助于增強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理性思維
胡適對白話文學(xué)貢獻
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有一位對新文學(xué)的成長投入了滿腔熱情,披荊斬棘、勇往直前地積極開拓的元勛,這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qū)作家胡適先生。過去很長一段時期,我們由于受極左思想的影響,關(guān)于胡適對白話文學(xué)的貢獻,常戴著有色眼鏡來評價這位為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過卓越貢獻的歷史人物,也很少對其作出客觀公允的評價。這既違背了史家“不掩惡,不溢美”的作史道德,也不符合唯物主義者實事求是的科學(xué)態(tài)度。因此,我們應(yīng)當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興起作一個全面的回顧,對在這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文學(xué)運動中立下汗馬功勞的胡適先生重新認識和評價。
胡適對白話文學(xué)的貢獻主要在詩歌和文學(xué)主張方面。早在1915年,二十四歲的胡適在留學(xué)美國時,就破天荒地提出了“文學(xué)革命”的口號。當時與胡適一同去美國的青年,支持胡適的人寥寥無幾,但胡適文學(xué)改革的意志異常堅定,可以說是義無反顧。當他的好友梅光迪反對他時,胡適寫了一首詩進行反駁并自我鼓勵: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學(xué)久枯餒,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xué)革命其時矣。吾輩誓不容坐視,且復(fù)號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褂,鞭笞驅(qū)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作歌今送梅生行,狂言人道臣當烹。我自不吐定不快,人言未足為重輕。胡適在這首如同大白話的詩中,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文學(xué)革命”的口號。這一主張早于《新青年》三年,可以說,文學(xué)革命發(fā)軔于胡適一點都不夸張。與此同時,胡適更不顧在美國留學(xué)的同仁們的反對,自己嘗試著用白話作文寫詩、寫劇本。他的《嘗試集》是我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盡管其詩歌寫得幼稚且缺乏情趣,但詩集的開拓之功是不容磨滅的。他在1916年8月4日寄給好朋友任叔永的信中說:“我自信頗能用白話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韻文,私心頗欲以數(shù)年之力,實地練習(xí)之。倘數(shù)年之后,竟能用白話作文作詩,無不隨心所欲,豈非一大快事?”胡適極力主張廢除文言文,改用人民群眾的口頭語言作詩、作文,他說:“今日所需,乃是一種可讀,可聽,可歌,可講,可記的言語。要讀書不須口譯,演說不須筆譯;要施諸講臺舞臺而皆可,誦之村嫗婦孺皆可懂。”當他的好朋友都竭力勸他莫冒險提倡白話文學(xué)時,胡適的決心更大,他說:“吾志決矣。
吾自此以后,不更作文言詩詞。”可見他在思想上做好了失敗的打算,抱定了百折不回的決心。這些對文言痛加排斥,全盤否定而又不遺余力地實踐新文學(xué)的觀點為白話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不僅如此,胡適還在報紙上和給朋友的信中大肆宣傳白話文學(xué),主張人們都摒棄文言文,改用白話文。他從中國文學(xué)史中梳理出白話文學(xué)的傳統(tǒng),指出了文學(xué)發(fā)展的趨勢,更從歐洲文學(xué)革命取得的經(jīng)驗中獲得啟發(fā),斷定以口語代替遠離口語的毫無生氣的古文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雖然他的文學(xué)革命主張受到了復(fù)古派的圍攻和喧囂鼓噪,盡管他只有單槍匹馬一個人,但他始終毫不懈怠地為白話文學(xué)吶喊,文學(xué)革命的信念從來不曾動搖過。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上發(fā)表了他著名的論文《文學(xué)改良芻議》。這篇在復(fù)古派看來非常荒唐而又離經(jīng)叛道的文章,卻為白話文學(xué)注入了一支強心劑,是一篇討伐文言文的戰(zhàn)斗檄文。在這篇文章中,他旗幟鮮明地提出了文學(xué)革命的八項主張:一曰,須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須講求文法。四曰,不作無病呻吟。五曰,務(wù)去濫調(diào)套語。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講對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語。
今天看來這八項主張并不算多么新穎驚人,可那時卻是驚世駭俗之語。這八項主張實是對空洞無物的文言文徹底鏟除,雖然有些觀點并不是很完美,但它對僵死的文言文已構(gòu)成摧枯拉朽的掃蕩之勢。這些文學(xué)主張的拋出奠定了胡適作為文學(xué)革命大旗手的歷史地位。
當然,胡適作為一個資產(chǎn)階級的學(xué)者、詩人、文學(xué)理論家,他的思想感情同勞苦大眾的思想感情還有不小的距離。因此,他的文學(xué)革命主張也只能是在推翻古文學(xué),提倡白話文學(xué)方面產(chǎn)生積極的作用。它不可能構(gòu)建一種內(nèi)容充實,生動活潑,帶有勞動人民感情,為廣大的勞動人民所喜聞樂見的嶄新的文學(xué)形式。但是胡適在新文學(xué)誕生期,為新文學(xué)的滋生、培育,身體力行地親身實踐,為新文學(xué)的發(fā)展做出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當我們回顧那段翻天覆地的歷史時,無論如何,都應(yīng)該肯定這位新文化運動先驅(qū)曾經(jīng)立下的豐功偉績。
東漢儒學(xué)對文學(xué)影響
儒學(xué)和文學(xué),同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一個時代的思想和文學(xué),會受到其時期經(jīng)濟基礎(chǔ)的影響。文學(xué)風貌與時代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創(chuàng)作主體的關(guān)系較為明顯,而與思想和學(xué)術(shù)的關(guān)系則相對隱晦。雖然如此,思想和學(xué)術(shù)依然是影響文學(xué)發(fā)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東漢儒學(xué)發(fā)展變化為線索,論述儒家思想和學(xué)術(shù)對文學(xué)的影響。
自武帝獨尊儒術(shù)之后,儒學(xué)成為統(tǒng)治兩漢社會的主流思潮,是兩漢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tài)。但儒學(xué)發(fā)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種文化思潮的影響,使兩漢儒學(xué)思想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面貌。西漢末年,伴隨著漢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讖緯學(xué)說為主要內(nèi)容的神學(xué)思潮,繼承了董仲舒的災(zāi)瑞之說,以神學(xué)理論附會儒家經(jīng)典,開始侵入到儒學(xué)內(nèi)部。進入東漢初期,儒學(xué)面貌就逐漸發(fā)生變化,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整個東漢王朝,從初期的儒學(xué)面貌發(fā)生變化開始,到中期儒學(xué)的統(tǒng)治地位產(chǎn)生動搖,到漢末儒學(xué)徹底衰頹下去,儒學(xué)經(jīng)過了一個由盛轉(zhuǎn)衰的發(fā)展變化過程,這是一條貫穿東漢社會思潮的主要線索。而由儒學(xué)派生的讖緯神學(xué)“、自由學(xué)派”①以及“漢末子學(xué)”,它們或附會儒學(xué),或補充儒學(xué),或修正儒學(xué),這些內(nèi)容共同形成了東漢儒學(xué)的整體風貌。東漢初期,由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學(xué)思潮占據(j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制高點,必然會與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發(fā)生沖突。而東漢初期的今文經(jīng)學(xué),以追逐利祿為其強大的發(fā)展動力,大量的繁瑣解經(jīng)、饾饤成文之風又導(dǎo)致了今文經(jīng)學(xué)本身陷入僵化,必須尋找生存和發(fā)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祿的本性使得今文經(jīng)學(xué)很快向神學(xué)靠攏,經(jīng)學(xué)必須依靠神學(xué)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神學(xué)也需要借助經(jīng)學(xué),才能將其荒謬的思想和學(xué)說正統(tǒng)化、經(jīng)典化,今文經(jīng)學(xué)因此很快走向神學(xué)化的道路。神學(xué)化的今文經(jīng)學(xué)是儒學(xué)的變異,它產(chǎn)生的是一種學(xué)術(shù)的怪胎。它通過神化孔子和六經(jīng),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漢的預(yù)言家;通過肢解六經(jīng)原文,把六經(jīng)弄成讖緯之書。于是大量關(guān)于孔子的預(yù)言和六經(jīng)的緯書充斥于東漢初期的儒學(xué)之中,成為東漢初期儒學(xué)思想的最主要理論形態(tài)。這種變異后的儒學(xué),是儒學(xué)的表象,神學(xué)的本質(zhì)。它是兩漢儒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沒有儒學(xué)內(nèi)部的今古文之爭和外部“自由學(xué)派”的強烈反對,儒學(xué)將在神學(xué)思潮的侵襲下面目全非。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僵化的學(xué)風,以及和神學(xué)聯(lián)姻之后的荒誕思想,必然導(dǎo)致它走向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強勢推動之下,它得以占據(jù)學(xué)術(shù)思潮的統(tǒng)治地位,成為東漢初期最主要的學(xué)術(shù)形態(tài)。到了東漢中期,隨著王朝的政權(quán)開始走向衰亡,今文經(jīng)學(xué)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這期間各種各樣的學(xué)術(shù)思潮,在反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過程中應(yīng)運而生,逐漸占據(jù)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重要地位。
東漢中期,儒學(xué)整體上處于內(nèi)部的自我調(diào)整之勢,今文經(jīng)學(xué)趨于衰落,古文經(jīng)學(xué)代之興起,這是儒學(xué)自我調(diào)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經(jīng)學(xué)在其誕生初期,就由于治學(xué)的風格不同存在爭端,只是由于今文經(jīng)學(xué)得到統(tǒng)治者的支持,一直壓倒古文經(jīng)學(xué),但古文經(jīng)學(xué)因其靈活務(wù)實的學(xué)風而廣為流傳,也幾度立于學(xué)官。尤其是今文經(jīng)學(xué)與神學(xué)聯(lián)姻之后,古文經(jīng)學(xué)雖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學(xué)思潮,但總體上與神學(xué)比較疏離,保持自己學(xué)術(shù)上的獨立性。到了東漢中期,今文經(jīng)學(xué)退出學(xué)術(shù)的主要陣地,古文經(jīng)學(xué)代之興起,成為儒學(xué)在東漢中期的代表,占據(jù)重要的思想地位,并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古文學(xué)者與今文學(xué)者相比,更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知識,古文經(jīng)學(xué)不拘于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家法”、“師法”,轉(zhuǎn)益多師,具有靈活的傳承關(guān)系和廣采博納的學(xué)風。古文經(jīng)學(xué)追求對經(jīng)書本義的正確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經(jīng)學(xué)為迎合統(tǒng)治者和神學(xué)思潮而曲解經(jīng)文、謬申經(jīng)義。古文經(jīng)學(xué)多從文字訓(xùn)詁、名物典制入手,力圖達到對經(jīng)文思想內(nèi)容的準確把握,這種樸實求真的學(xué)風,比較質(zhì)實可靠,對后世學(xué)風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從學(xué)術(shù)內(nèi)容上,今文經(jīng)學(xué)以《春秋公羊》為主,以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yīng)為主要特色,古文經(jīng)學(xué)以《周禮》為主,拒絕或者疏離神學(xué),由今文經(jīng)學(xué)言災(zāi)異的特點,而向樸實禮學(xué)轉(zhuǎn)化。從學(xué)術(shù)風氣上,古文經(jīng)學(xué)由今文經(jīng)學(xué)那種虛妄的作風,轉(zhuǎn)向求真務(wù)實。古文經(jīng)學(xué)就是以這種學(xué)術(shù)姿態(tài),占據(jù)東漢中期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重要陣地,對東漢社會以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東漢末期,儒學(xué)徹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戶異議,人殊論”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遠處于混亂之中,漢末“子學(xu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興盛起來。子學(xué)的興盛,并沒有完全脫離儒學(xué)發(fā)展的軌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xiàn)出對東漢儒學(xué)的反拔。漢末“子學(xué)”的典型特征是對時政的批判,它們在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反思與批判中,構(gòu)建自己的思想理論。以王符、崔寔、仲長統(tǒng)為代表的漢末子學(xué)家,都有代表他們思想成果的專著:《潛夫論》、《政論》、《昌言》。王符掀起了東漢批判思潮,崔寔繼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發(fā)展,仲長統(tǒng)則代表了漢末批判思潮的終結(jié)。它們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華,它們的思想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點。漢末“子學(xué)”主要繼承中期“自由學(xué)派”的學(xué)風,哲學(xué)上反對神學(xué)思潮,體現(xiàn)出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現(xiàn)實上對漢末腐朽的社會進行分析和批判。漢末“子學(xué)”雖然尚不能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它們并非簡單的就事論事,而是進行深刻理性的分析,嚴肅的哲學(xué)思考,體現(xiàn)出和漢末政論文不同的學(xué)術(shù)的特征,并對漢末的時代和社會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文學(xué)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一個社會的思想主潮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尤其是在東漢儒學(xu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響,出現(xiàn)一些新變的特征。東漢初期,文學(xué)以賦體為主,延續(xù)著西漢以來的歌頌傳統(tǒng)。隨著上層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生較大的變化,神學(xué)思潮侵襲著整個社會,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響。東漢初期的詩賦創(chuàng)作,都包含有明顯的神學(xué)思想內(nèi)容,作品引用讖緯祥瑞所占的比重,遠高于西漢時期。這種神學(xué)內(nèi)容在詩賦創(chuàng)作之中,主要用來歌頌大漢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這是神學(xué)思想影響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表現(xiàn)。今文經(jīng)學(xué)雖然與神學(xué)融合,但儒學(xué)的根本屬性并沒有完全喪失,依然以其強大的慣性力量影響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在歌頌帝王的時候,特別注重發(fā)揚他們在禮樂文化方面的功業(yè),將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儒家圣賢的形象。這些禮樂文化,無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內(nèi)容,實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學(xué)和神學(xué)的雙重特征。東漢初期的詩賦,集中描繪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禮樂教化,正是東漢初期的儒學(xué)神學(xué)化影響文學(xué)的表現(xiàn)。
東漢中期,隨著今古文經(jīng)學(xué)此消彼長,文學(xué)面貌也發(fā)生較大的變化。具體來說,今文經(jīng)學(xué)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學(xué)化桎梏的漢代文學(xué),獲得了一定的“自由”發(fā)展的空間,主要表現(xiàn)是詩賦向抒情化的文學(xué)本質(zhì)回歸。由東漢初期的“理勝于情”的述志賦,向純粹吟詠人生況味的抒情小賦轉(zhuǎn)化,這是漢末文學(xué)變革的前奏。古文經(jīng)學(xué)對文學(xué)的影響,不僅增加了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涵和意蘊,也使文學(xué)作品具有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廣大的知識容量。東漢末期,儒學(xué)整體走向衰落,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很大的沖擊和影響。漢代文學(xué)幾百年的發(fā)展,一直籠罩在儒學(xué)的光環(huán)之下。失去儒學(xué)制約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非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沒有了儒家教條的束縛,以各種方式加快了向文學(xué)本位回歸的步伐。具體來說,儒學(xué)衰微首先影響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轉(zhuǎn)化的過程,并逐漸向才情和藝術(shù)的方向發(fā)展,這為漢末儒學(xué)的變革準備了主觀上的條件。漢末各體文學(xué)的繁盛,是一個重要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它們與儒學(xué)衰微也有一定的關(guān)系,它們大體遵循“儒學(xué)陵替,文風趨華”的整體趨勢,但不同的文體發(fā)展變化也顯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體甚至出現(xiàn)反向逆動的情況,這種現(xiàn)象應(yīng)該與文體內(nèi)部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關(guān)。儒學(xué)衰微所引起的漢末文學(xué)的變化,在詩賦體裁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它是儒學(xué)變化所引起的文學(xué)變化的主要體現(xiàn)。儒學(xué)衰微導(dǎo)致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束縛減弱,詩賦的創(chuàng)作也從這種束縛中跳出來,以各種方式回歸文學(xué)的道路。對于詩歌來說,最大的變化是抒情的增強。詩歌創(chuàng)作逐漸脫離儒教的影響,表達內(nèi)心喜怒哀樂的真實感受。《古詩十九首》作為漢末抒情詩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詩歌抒情增強的集中體現(xiàn)。脫離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詩言志”,真正回到了詩歌抒情的本質(zhì)特征。由此也帶來詩歌表現(xiàn)形式和詩風相應(yīng)的變化,使詩歌最終取代賦體而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它帶給后世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中國文學(xué)由此走上了以詩歌創(chuàng)作為主體的道路,抒情也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征。對于漢賦來說,占領(lǐng)文壇主流兩百年的漢大賦基本衰落,賦體創(chuàng)作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有了新變,在東漢中期題材擴大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開拓了遠離儒教影響的幾種題材,并表現(xiàn)出不同以往的藝術(shù)特征。辭賦可以批判社會,可以寫艷情,寫新婚,寫美女,寫游戲,情感抒發(fā)出自內(nèi)心而非大賦的因文造情,為后世種類繁多的抒情賦的崛起奠定了基礎(chǔ)。漢末文學(xué)的這種變化,都是在儒學(xué)衰落之后,由于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作用的結(jié)果。在漢末儒學(xué)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學(xué)”的興盛是伴隨著儒學(xué)的衰落。“子學(xué)”的發(fā)展作為一種學(xué)術(shù)的系統(tǒng)還不夠成熟,它對文學(xué)的影響只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有明顯的體現(xiàn)。由于“子學(xué)”和漢末政論的內(nèi)容都是基于對漢末社會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它們同受漢末社會現(xiàn)實的影響,漢末“子學(xué)”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為主,對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視國君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社會變革的關(guān)鍵所在;希望國君能夠任用賢臣,疏遠小人,以達到國家中興。漢末政論文的批判現(xiàn)實雖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維護政權(quán)而不是改變的目的,其矛頭也是首先指向國君,既譴責了國君忠奸不分、揚惡罰善的昏聵行為,也依然對國君寄托了希望,向國君推薦賢臣,希望國君重用他們,以挽救危難中的國家和社會。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漢末政論文的批判方式,較多以災(zāi)異發(fā)端,具有明顯的荒誕性,所以才會出現(xiàn)政論家以其政論文中多災(zāi)異而免罪的怪事。漢末子學(xué)家則在冷靜觀察歷史和現(xiàn)實的過程中,構(gòu)建自己的批判理論,從而對現(xiàn)實社會進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漢末“子學(xué)”繼承和發(fā)展了東漢“自由學(xué)派”的思想,反對天命神學(xué)論,而漢末政論文還延續(xù)漢初政論以災(zāi)異推演政治的風氣。同樣是針對漢末社會,“子學(xué)”和政論文的批判方式卻完全不同。“子學(xué)”和政論文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關(guān)系,漢末子學(xué)會影響到政論文的思想和內(nèi)容,而政論文也會促進漢末子學(xué)在政治理論上的構(gòu)建;漢末子學(xué)和政論文在漢末政治社會的背景之下,既獨立平行的發(fā)展,也會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補充,共同促進。
儒學(xué)對于文學(xué)影響的強弱,往往取決于儒學(xué)是否成為“官學(xué)”。儒學(xué)一旦成為官方文化的代表,對文學(xué)影響比較明顯;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對文學(xué)影響便隱微。東漢一代的儒學(xué)和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也呈現(xiàn)出這樣的態(tài)勢。東漢初期,神學(xué)思潮具有強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學(xué)內(nèi)部,改變了此期儒學(xué)的面貌,而且對此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來極為明顯的影響。讖緯神學(xué)本是荒誕的學(xué)說,但王莽、劉秀都依靠它們走向政治舞臺,于是他們在掌握皇權(quán)之后,以國家的意志將讖緯神學(xué)頒行天下,以為天下法則。正是因為有最高統(tǒng)治者的強勢推動,神學(xué)思潮得以充斥整個漢初的社會。儒學(xué)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不得不迎合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向神學(xué)靠攏,乃至和神學(xué)融為一體。讖緯神學(xué)就這樣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力推動之下,占據(j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地位。當然,儒學(xué)根本的屬性還沒有完全異化,也還能以其長期的慣性力量,影響到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這個時期的文學(xué)就帶有儒學(xué)和神學(xué)的雙重特征,儒學(xué)和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就很密切。到了東漢中期,隨著國家政權(quán)開始衰落,儒學(xué)也失去了強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間流傳的思潮就開始占據(jù)學(xué)術(shù)的陣地,為了這一社會思潮的變化,儒學(xué)就進入內(nèi)部的自我調(diào)整時期。以揚雄、桓譚、王充為代表的“自由學(xué)派”,他們的思想本身就反對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學(xué)和經(jīng)學(xué),屬于“民間學(xué)術(shù)”,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還可能受到官方的壓制,桓譚為此幾乎送掉了性命,但它們在反對今文經(jīng)學(xué)、推動今文經(jīng)學(xué)走向衰落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學(xué)的這種變化,使之失去了對文學(xué)的直接干預(yù)力量,因此儒學(xué)對文學(xué)的影響就沒有東漢初期那樣顯著。到了東漢末年,國家政權(quán)頻臨滅亡,儒學(xué)完全失去了對國家社會和士人的影響力,也就無可救藥的衰頹下去,受到儒學(xué)思想長期控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因為這種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發(fā)出文學(xué)自身的力量,而煥發(fā)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控制影響的能力,漢末文學(xué)以各種方式向文學(xué)本位回歸。漢末“子學(xué)”以批判時政為主要思想內(nèi)涵,完全是一種“民間學(xué)術(shù)”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撐,而此時漢室政權(quán)已經(jīng)走向了滅亡的邊緣,任何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都無法挽救其覆滅的命運,只能等待新的政權(quán)和思想取而代之。
東漢儒學(xué)變化對文學(xué)影響
儒學(xué)和文學(xué),同屬于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一個時代的思想和文學(xué),會受到其時期經(jīng)濟基礎(chǔ)的影響。文學(xué)風貌與時代政治、社會經(jīng)濟和創(chuàng)作主體的關(guān)系較為明顯,而與思想和學(xué)術(shù)的關(guān)系則相對隱晦。雖然如此,思想和學(xué)術(shù)依然是影響文學(xué)發(fā)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東漢儒學(xué)發(fā)展變化為線索,論述儒家思想和學(xué)術(shù)對文學(xué)的影響。
自武帝獨尊儒術(shù)之后,儒學(xué)成為統(tǒng)治兩漢社會的主流思潮,是兩漢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tài)。但儒學(xué)發(fā)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種文化思潮的影響,使兩漢儒學(xué)思想呈現(xiàn)出復(fù)雜的面貌。西漢末年,伴隨著漢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讖緯學(xué)說為主要內(nèi)容的神學(xué)思潮,繼承了董仲舒的災(zāi)瑞之說,以神學(xué)理論附會儒家經(jīng)典,開始侵入到儒學(xué)內(nèi)部。進入東漢初期,儒學(xué)面貌就逐漸發(fā)生變化,呈現(xiàn)出新的特征。整個東漢王朝,從初期的儒學(xué)面貌發(fā)生變化開始,到中期儒學(xué)的統(tǒng)治地位產(chǎn)生動搖,到漢末儒學(xué)徹底衰頹下去,儒學(xué)經(jīng)過了一個由盛轉(zhuǎn)衰的發(fā)展變化過程,這是一條貫穿東漢社會思潮的主要線索。而由儒學(xué)派生的讖緯神學(xué)“、自由學(xué)派”①以及“漢末子學(xué)”,它們或附會儒學(xué),或補充儒學(xué),或修正儒學(xué),這些內(nèi)容共同形成了東漢儒學(xué)的整體風貌。東漢初期,由于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學(xué)思潮占據(j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制高點,必然會與儒家思想的統(tǒng)治地位發(fā)生沖突。而東漢初期的今文經(jīng)學(xué),以追逐利祿為其強大的發(fā)展動力,大量的繁瑣解經(jīng)、饾饤成文之風又導(dǎo)致了今文經(jīng)學(xué)本身陷入僵化,必須尋找生存和發(fā)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祿的本性使得今文經(jīng)學(xué)很快向神學(xué)靠攏,經(jīng)學(xué)必須依靠神學(xué)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fā)展,神學(xué)也需要借助經(jīng)學(xué),才能將其荒謬的思想和學(xué)說正統(tǒng)化、經(jīng)典化,今文經(jīng)學(xué)因此很快走向神學(xué)化的道路。神學(xué)化的今文經(jīng)學(xué)是儒學(xué)的變異,它產(chǎn)生的是一種學(xué)術(shù)的怪胎。它通過神化孔子和六經(jīng),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漢的預(yù)言家;通過肢解六經(jīng)原文,把六經(jīng)弄成讖緯之書。于是大量關(guān)于孔子的預(yù)言和六經(jīng)的緯書充斥于東漢初期的儒學(xué)之中,成為東漢初期儒學(xué)思想的最主要理論形態(tài)。這種變異后的儒學(xué),是儒學(xué)的表象,神學(xué)的本質(zhì)。它是兩漢儒學(xué)發(fā)展過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沒有儒學(xué)內(nèi)部的今古文之爭和外部“自由學(xué)派”的強烈反對,儒學(xué)將在神學(xué)思潮的侵襲下面目全非。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僵化的學(xué)風,以及和神學(xué)聯(lián)姻之后的荒誕思想,必然導(dǎo)致它走向一條沒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強勢推動之下,它得以占據(jù)學(xué)術(shù)思潮的統(tǒng)治地位,成為東漢初期最主要的學(xué)術(shù)形態(tài)。到了東漢中期,隨著王朝的政權(quán)開始走向衰亡,今文經(jīng)學(xué)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這期間各種各樣的學(xué)術(shù)思潮,在反對今文經(jīng)學(xué)的過程中應(yīng)運而生,逐漸占據(jù)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重要地位。東漢中期,儒學(xué)整體上處于內(nèi)部的自我調(diào)整之勢,今文經(jīng)學(xué)趨于衰落,古文經(jīng)學(xué)代之興起,這是儒學(xué)自我調(diào)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經(jīng)學(xué)在其誕生初期,就由于治學(xué)的風格不同存在爭端,只是由于今文經(jīng)學(xué)得到統(tǒng)治者的支持,一直壓倒古文經(jīng)學(xué),但古文經(jīng)學(xué)因其靈活務(wù)實的學(xué)風而廣為流傳,也幾度立于學(xué)官。尤其是今文經(jīng)學(xué)與神學(xué)聯(lián)姻之后,古文經(jīng)學(xué)雖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學(xué)思潮,但總體上與神學(xué)比較疏離,保持自己學(xué)術(shù)上的獨立性。到了東漢中期,今文經(jīng)學(xué)退出學(xué)術(shù)的主要陣地,古文經(jīng)學(xué)代之興起,成為儒學(xué)在東漢中期的代表,占據(jù)重要的思想地位,并產(chǎn)生廣泛的影響。古文學(xué)者與今文學(xué)者相比,更具有開闊的視野和廣博的知識,古文經(jīng)學(xué)不拘于今文經(jīng)學(xué)的“家法”、“師法”,轉(zhuǎn)益多師,具有靈活的傳承關(guān)系和廣采博納的學(xué)風。古文經(jīng)學(xué)追求對經(jīng)書本義的正確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經(jīng)學(xué)為迎合統(tǒng)治者和神學(xué)思潮而曲解經(jīng)文、謬申經(jīng)義。古文經(jīng)學(xué)多從文字訓(xùn)詁、名物典制入手,力圖達到對經(jīng)文思想內(nèi)容的準確把握,這種樸實求真的學(xué)風,比較質(zhì)實可靠,對后世學(xué)風也有相當大的影響。從學(xué)術(shù)內(nèi)容上,今文經(jīng)學(xué)以《春秋公羊》為主,以陰陽五行和天人感應(yīng)為主要特色,古文經(jīng)學(xué)以《周禮》為主,拒絕或者疏離神學(xué),由今文經(jīng)學(xué)言災(zāi)異的特點,而向樸實禮學(xué)轉(zhuǎn)化。從學(xué)術(shù)風氣上,古文經(jīng)學(xué)由今文經(jīng)學(xué)那種虛妄的作風,轉(zhuǎn)向求真務(wù)實。古文經(jīng)學(xué)就是以這種學(xué)術(shù)姿態(tài),占據(jù)東漢中期學(xué)術(shù)領(lǐng)域的重要陣地,對東漢社會以及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影響。東漢末期,儒學(xué)徹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戶異議,人殊論”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遠處于混亂之中,漢末“子學(xu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興盛起來。子學(xué)的興盛,并沒有完全脫離儒學(xué)發(fā)展的軌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現(xiàn)出對東漢儒學(xué)的反拔。漢末“子學(xué)”的典型特征是對時政的批判,它們在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反思與批判中,構(gòu)建自己的思想理論。以王符、崔寔、仲長統(tǒng)為代表的漢末子學(xué)家,都有代表他們思想成果的專著:《潛夫論》、《政論》、《昌言》。王符掀起了東漢批判思潮,崔寔繼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發(fā)展,仲長統(tǒng)則代表了漢末批判思潮的終結(jié)。它們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華,它們的思想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點。漢末“子學(xué)”主要繼承中期“自由學(xué)派”的學(xué)風,哲學(xué)上反對神學(xué)思潮,體現(xiàn)出明顯的唯物主義傾向;現(xiàn)實上對漢末腐朽的社會進行分析和批判。漢末“子學(xué)”雖然尚不能構(gòu)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它們并非簡單的就事論事,而是進行深刻理性的分析,嚴肅的哲學(xué)思考,體現(xiàn)出和漢末政論文不同的學(xué)術(shù)的特征,并對漢末的時代和社會產(chǎn)生深遠的影響。
文學(xué)作為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一個社會的思想主潮有著不可分離的關(guān)系,尤其是在東漢儒學(xué)不斷變化的過程中,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響,出現(xiàn)一些新變的特征。東漢初期,文學(xué)以賦體為主,延續(xù)著西漢以來的歌頌傳統(tǒng)。隨著上層學(xué)術(shù)思想發(fā)生較大的變化,神學(xué)思潮侵襲著整個社會,文學(xué)創(chuàng)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響。東漢初期的詩賦創(chuàng)作,都包含有明顯的神學(xué)思想內(nèi)容,作品引用讖緯祥瑞所占的比重,遠高于西漢時期。這種神學(xué)內(nèi)容在詩賦創(chuàng)作之中,主要用來歌頌大漢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這是神學(xué)思想影響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表現(xiàn)。今文經(jīng)學(xué)雖然與神學(xué)融合,但儒學(xué)的根本屬性并沒有完全喪失,依然以其強大的慣性力量影響到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xué)作品在歌頌帝王的時候,特別注重發(fā)揚他們在禮樂文化方面的功業(yè),將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儒家圣賢的形象。這些禮樂文化,無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內(nèi)容,實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學(xué)和神學(xué)的雙重特征。東漢初期的詩賦,集中描繪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禮樂教化,正是東漢初期的儒學(xué)神學(xué)化影響文學(xué)的表現(xiàn)。東漢中期,隨著今古文經(jīng)學(xué)此消彼長,文學(xué)面貌也發(fā)生較大的變化。具體來說,今文經(jīng)學(xué)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學(xué)化桎梏的漢代文學(xué),獲得了一定的“自由”發(fā)展的空間,主要表現(xiàn)是詩賦向抒情化的文學(xué)本質(zhì)回歸。由東漢初期的“理勝于情”的述志賦,向純粹吟詠人生況味的抒情小賦轉(zhuǎn)化,這是漢末文學(xué)變革的前奏。古文經(jīng)學(xué)對文學(xué)的影響,不僅增加了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涵和意蘊,也使文學(xué)作品具有更加廣闊的視野,更加廣大的知識容量。東漢末期,儒學(xué)整體走向衰落,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很大的沖擊和影響。漢代文學(xué)幾百年的發(fā)展,一直籠罩在儒學(xué)的光環(huán)之下。失去儒學(xué)制約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并非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學(xué)創(chuàng)作沒有了儒家教條的束縛,以各種方式加快了向文學(xué)本位回歸的步伐。具體來說,儒學(xué)衰微首先影響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轉(zhuǎn)化的過程,并逐漸向才情和藝術(shù)的方向發(fā)展,這為漢末儒學(xué)的變革準備了主觀上的條件。漢末各體文學(xué)的繁盛,是一個重要的文學(xué)現(xiàn)象,它們與儒學(xué)衰微也有一定的關(guān)系,它們大體遵循“儒學(xué)陵替,文風趨華”的整體趨勢,但不同的文體發(fā)展變化也顯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體甚至出現(xiàn)反向逆動的情況,這種現(xiàn)象應(yīng)該與文體內(nèi)部的發(fā)展規(guī)律有關(guān)。儒學(xué)衰微所引起的漢末文學(xué)的變化,在詩賦體裁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它是儒學(xué)變化所引起的文學(xué)變化的主要體現(xiàn)。儒學(xué)衰微導(dǎo)致儒家思想對人們的束縛減弱,詩賦的創(chuàng)作也從這種束縛中跳出來,以各種方式回歸文學(xué)的道路。對于詩歌來說,最大的變化是抒情的增強。詩歌創(chuàng)作逐漸脫離儒教的影響,表達內(nèi)心喜怒哀樂的真實感受。《古詩十九首》作為漢末抒情詩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詩歌抒情增強的集中體現(xiàn)。脫離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詩言志”,真正回到了詩歌抒情的本質(zhì)特征。由此也帶來詩歌表現(xiàn)形式和詩風相應(yīng)的變化,使詩歌最終取代賦體而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流。它帶給后世的影響是相當巨大的,中國文學(xué)由此走上了以詩歌創(chuàng)作為主體的道路,抒情也成為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主要特征。對于漢賦來說,占領(lǐng)文壇主流兩百年的漢大賦基本衰落,賦體創(chuàng)作從內(nèi)容到形式都有了新變,在東漢中期題材擴大的基礎(chǔ)上,進一步開拓了遠離儒教影響的幾種題材,并表現(xiàn)出不同以往的藝術(shù)特征。辭賦可以批判社會,可以寫艷情,寫新婚,寫美女,寫游戲,情感抒發(fā)出自內(nèi)心而非大賦的因文造情,為后世種類繁多的抒情賦的崛起奠定了基礎(chǔ)。漢末文學(xué)的這種變化,都是在儒學(xué)衰落之后,由于文學(xué)自身發(fā)展規(guī)律作用的結(jié)果。在漢末儒學(xué)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學(xué)”的興盛是伴隨著儒學(xué)的衰落。“子學(xué)”的發(fā)展作為一種學(xué)術(shù)的系統(tǒng)還不夠成熟,它對文學(xué)的影響只在一定的范圍內(nèi)有明顯的體現(xiàn)。由于“子學(xué)”和漢末政論的內(nèi)容都是基于對漢末社會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間有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它們同受漢末社會現(xiàn)實的影響,漢末“子學(xué)”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為主,對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視國君的地位和作用,認為這是社會變革的關(guān)鍵所在;希望國君能夠任用賢臣,疏遠小人,以達到國家中興。漢末政論文的批判現(xiàn)實雖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維護政權(quán)而不是改變的目的,其矛頭也是首先指向國君,既譴責了國君忠奸不分、揚惡罰善的昏聵行為,也依然對國君寄托了希望,向國君推薦賢臣,希望國君重用他們,以挽救危難中的國家和社會。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漢末政論文的批判方式,較多以災(zāi)異發(fā)端,具有明顯的荒誕性,所以才會出現(xiàn)政論家以其政論文中多災(zāi)異而免罪的怪事。漢末子學(xué)家則在冷靜觀察歷史和現(xiàn)實的過程中,構(gòu)建自己的批判理論,從而對現(xiàn)實社會進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漢末“子學(xué)”繼承和發(fā)展了東漢“自由學(xué)派”的思想,反對天命神學(xué)論,而漢末政論文還延續(xù)漢初政論以災(zāi)異推演政治的風氣。同樣是針對漢末社會,“子學(xué)”和政論文的批判方式卻完全不同。“子學(xué)”和政論文之間,也存在相互影響和促進的關(guān)系,漢末子學(xué)會影響到政論文的思想和內(nèi)容,而政論文也會促進漢末子學(xué)在政治理論上的構(gòu)建;漢末子學(xué)和政論文在漢末政治社會的背景之下,既獨立平行的發(fā)展,也會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補充,共同促進。
儒學(xué)對于文學(xué)影響的強弱,往往取決于儒學(xué)是否成為“官學(xué)”。儒學(xué)一旦成為官方文化的代表,對文學(xué)影響比較明顯;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對文學(xué)影響便隱微。東漢一代的儒學(xué)和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也呈現(xiàn)出這樣的態(tài)勢。東漢初期,神學(xué)思潮具有強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學(xué)內(nèi)部,改變了此期儒學(xué)的面貌,而且對此期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帶來極為明顯的影響。讖緯神學(xué)本是荒誕的學(xué)說,但王莽、劉秀都依靠它們走向政治舞臺,于是他們在掌握皇權(quán)之后,以國家的意志將讖緯神學(xué)頒行天下,以為天下法則。正是因為有最高統(tǒng)治者的強勢推動,神學(xué)思潮得以充斥整個漢初的社會。儒學(xué)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fā)展,不得不迎合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向神學(xué)靠攏,乃至和神學(xué)融為一體。讖緯神學(xué)就這樣在最高統(tǒng)治者的大力推動之下,占據(jù)社會意識形態(tài)的主要地位。當然,儒學(xué)根本的屬性還沒有完全異化,也還能以其長期的慣性力量,影響到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這個時期的文學(xué)就帶有儒學(xué)和神學(xué)的雙重特征,儒學(xué)和文學(xué)的關(guān)系就很密切。到了東漢中期,隨著國家政權(quán)開始衰落,儒學(xué)也失去了強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間流傳的思潮就開始占據(jù)學(xué)術(shù)的陣地,為了這一社會思潮的變化,儒學(xué)就進入內(nèi)部的自我調(diào)整時期。以揚雄、桓譚、王充為代表的“自由學(xué)派”,他們的思想本身就反對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學(xué)和經(jīng)學(xué),屬于“民間學(xué)術(shù)”,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還可能受到官方的壓制,桓譚為此幾乎送掉了性命,但它們在反對今文經(jīng)學(xué)、推動今文經(jīng)學(xué)走向衰落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學(xué)的這種變化,使之失去了對文學(xué)的直接干預(yù)力量,因此儒學(xué)對文學(xué)的影響就沒有東漢初期那樣顯著。到了東漢末年,國家政權(quán)頻臨滅亡,儒學(xué)完全失去了對國家社會和士人的影響力,也就無可救藥的衰頹下去,受到儒學(xué)思想長期控制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因為這種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發(fā)出文學(xué)自身的力量,而煥發(fā)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對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控制影響的能力,漢末文學(xué)以各種方式向文學(xué)本位回歸。漢末“子學(xué)”以批判時政為主要思想內(nèi)涵,完全是一種“民間學(xué)術(shù)”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撐,而此時漢室政權(quán)已經(jīng)走向了滅亡的邊緣,任何思想和意識形態(tài)都無法挽救其覆滅的命運,只能等待新的政權(quán)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學(xué)和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是一種社會文化現(xiàn)象,透過這種現(xiàn)象,能夠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發(fā)展演變與文學(xué)發(fā)展演變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揭示文學(xué)發(fā)展變化的社會動因。而儒學(xué)對文學(xué)的影響結(jié)果,很難以好或壞來評判。東漢文學(xué)逐漸脫離了儒學(xué)的影響,至漢末呈現(xiàn)出全新的文學(xué)風貌,似乎是儒學(xué)制約了文學(xué)的發(fā)展。但儒學(xué)深厚的思想內(nèi)涵,能夠直接影響到文學(xué)作品的精神,這是作品的“文學(xué)描寫”難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學(xué)適合儒家思想,出現(xiàn)過許多優(yōu)秀的作家,如杜甫、韓愈、白居易、陸游等。文學(xué)部分離開儒家思想,也出現(xiàn)過許多優(yōu)秀作家,如陶淵明、李白、蘇軾、曹雪芹等。”②精確地揭示了儒學(xué)和文學(xué)之間的關(guān)系。文學(xué)部分離開儒家思想的時候,文學(xué)作品的思想內(nèi)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類型的思想來填充,如陶淵明、李白、蘇軾,他們的作品都呈現(xiàn)出超然物外、通達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紅樓夢》則表現(xiàn)出佛教“萬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學(xué)無論是“文以載道”,還是“獨抒性靈”,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礎(chǔ)之上,一種時代思想主潮必然對文學(xué)產(chǎn)生或隱或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