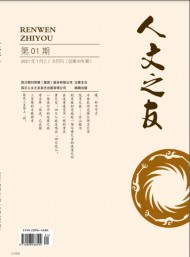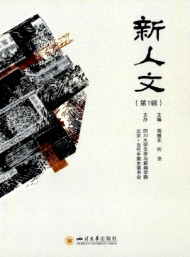人文主義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時間:2023-06-08 17:38:26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文主義文學研究綜述,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從莎士比亞時代開始,西方莎學研究至今已有400年的歷史,歷經新古典主義、啟蒙主義、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直到后現代時期,其間的理論思潮此起彼伏。特別是20世紀以來,各種文學流派都把莎士比亞當成作其理論的試金石,形成了蔚為壯觀、紛擾繁復的景象。而其中現代主義的豐富解讀使得莎學研究的意蘊得到了無限的擴展和延伸,所出現的專著和文章,可謂浩如煙海,令人望洋興嘆。近讀李偉民教授的《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國戲劇出版社,2006年),深切感受到作者對莎學研究執著的探索精神。著者文化視野宏闊,文獻資料豐實,理論闡述清新,這是一部不乏真知灼見的厚重佳作。通觀全書,可從以下幾個方面予以論之。一、資料翔實,研究深入細致筆者也是莎學研究愛好者,經常拜讀李偉民的文章,覺得李偉民先生不僅研究認真,而且還花大力開展莎學情報資料工作。本書的撰寫也不例外,體現了他一貫的認真扎實的學術風范。在此之前,他全面搜集、分析了近年來年外國文學刊物、高等學院學報、社科院系統刊物、文藝理論與批評刊物、戲劇與文化類刊物上發表的莎學文章,論述了中國莎學新時期發展的軌跡,為今后的中國莎學研究提出了一些思考。他先后撰寫了《1993-1994年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及戲劇研究綜述(1995-1996)》《、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著作與論文的引文分析和評價》、《1993-1994年高等學校學報(人文、社科版)《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引文分析與評價》《、艱難的進展與希望———近年來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述評》《、二十世紀末中國莎學研究綜述》《、中國莎士比亞研究論文的統計與分析》《、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研究五十年》《、臺灣莎學研究情況綜述》等,以及朱生豪、梁實秋、張泗洋、李賦寧、楊周翰、卞之琳的莎學研究思想等系列論文。“這些系列論文在中國莎學研究史上第一次對中國莎學研究文獻情報成果從質和量兩個方面進行了全面的計量研究;對中國莎學研究的一些外部特征和深層結構進行了文獻計量學角度的對比評價,通過對中國莎學文獻引文有關數據的分析與比較,論述了中國莎學研究的主要特征、趨勢,客觀地揭示了中國莎學學術研究的學科動向、進展以及現階段的學術水平”。[1]27這些基礎性的研究工作對這本著作的撰寫提供了大量的資料,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書后,僅主要參考數目就列了20多頁,足見作者的資料搜集范圍之廣、力度之深。當然,這不是一般莎士比亞批評的資料匯編,而是這些年來作者在莎學研究領域勤奮耕耘,“十年磨一劍”,厚積薄發的一部學術性著作。
二、結構模式新穎獨特,富有創見和開拓精神首先,在緒論中,作者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作為起點,從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契丹人”切入,細細梳理了莎士比亞在中國的傳入、接受和影響的歷史流變。全書內容分為七章,作者從《哈姆萊特》入手,進而進入悲劇的文本與舞臺,以及莎氏歷史劇和戲劇的人民性與人性的關系;另外,對莎氏的傳奇劇和詩歌批評進行了專門探討。第五、六兩章是本書的一大亮點,莎士比亞翻譯批評和莎氏戲劇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環境下的還原與變形也是莎學研究者值得深入的一個領域。最后一章是多元化的批評方式,特別是現代性的莎學批評更是值得關注的。莎士比亞悲劇研究歷來是莎學研究中的重點,四大悲劇又構成了莎氏悲劇中的重點《,哈姆萊特》研究則又是重中之重。因此作者并沒有按部就班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記下莎學研究的“流水帳”,而是從《哈姆雷特》著手,全面剖析了哈姆雷特在中國形象批評在中國的演進以及對哈姆雷特的形象認識辨析,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見。我們知道,對待哈姆雷特這個不朽的人物形象,幾個世紀以來人們眾說紛紜,多棱鏡里的哈姆雷特的影像也是霧里看花,使人琢磨不透。李偉民從哈姆雷特強烈的自殺意識、一個極端利己主義者以及對女人的看法和行為等幾個方面深入細致的論述了哈姆雷特不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哈姆雷特在中國的形象問題,作者提出了應該全面看待這個人物形象而不是僅僅局限于一個人文主義者的觀點。應該從人民性、人文主義者、并非人文主義者進行研究。事實上,在哈姆雷特身上,很難看到人文主義的思想精神,卻存在相當多的非人文主義思想。接下來,在第二章,作者從莎氏四大悲劇出發,探討了中國語境下文本與舞臺的莎學批評演進。重點論述了作為舞臺演出的莎氏戲劇在進入中國后對中國本土戲劇的影響以及對莎翁戲劇的改編接受情況。莎士比亞的貢獻除了悲劇之外,歷史劇和喜劇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作者從莎氏作品中的人民性與人性的獨特視角出發,進一步探究了莎士比亞批評在中國語境下的接受與認識。莎士比亞是歐洲文藝復興時期英國偉大的戲劇家和詩人,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高度評價他是最“偉大的戲劇天才”,把他的作品譽為“世界藝術高峰之一”。歷來文學研究家們都把莎士比亞當作試金石,作為檢驗其理論的依據。因此,對莎學批評也不可能是單一的,而是多元化的方式。進入20世紀,由于莎士比亞的豐富內涵及深遠意義,傳統的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批評日顯局限。歷史學派針對浪漫主義對莎劇詩性、閱讀性和不可演出性的無限擴大和盲目崇拜,研究莎士比亞與當時歷史背景的契合,包括研究伊麗莎白時代的劇院、舞臺及演員表演,揭開了對莎士比亞“現代”解讀的龐大序幕。于是,種種冠以“現代主義”、“現代性”、“現代派”等以“現代”語詞為核心的解讀此起彼落,甚至一涌而上,使這一世紀的莎評既呈現出極其壯觀的景象,又放射出無比怪異的光芒。其壯觀固然體現出了莎士比亞研究的可喜成果,其怪異卻也展示了對莎士比亞的無限夸大和歪曲,并產生了對莎學研究的深深困惑。作者在最后一章就是采取多元化的視角對莎學研究在中國的接受背景與選擇方式進行了深入探究,從“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的批評演進為出發點,從哲學上矛盾對立和美學范疇來認識這一對文學觀念的深層涵義。
三、宏闊的理論視野和文學批評理念第五章:從歷史走向未來。主要論述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50年的發展脈絡,也是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中國莎評通過對蘇俄莎評的譯介,特別是對莎評的譯介,打開了中國人的眼界,聯系自己國家和民族命運,中國人對莎作有了更深的體會。20世紀30年代對蘇俄莎學的介紹,從總體到細微處對莎士比亞的劇作也有了較系統的觀照。這一時期中國莎士比亞研究深受蘇聯莎評的影響,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莎士比亞被中國的政治涂上了各種油彩,在中國政治的影響下不斷變臉。階級斗爭的政治環境對中國莎學研究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在中國莎學中,翻譯莎士比亞作品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莎士比亞作品的評論、研究與莎士比亞戲劇的演出在中國莎士比亞傳播史上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對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構成了評論、研究與演出的基礎。”[2]272中國的莎學研究大都是從文本出發,但是卻鮮有人對他們的翻譯經驗,翻譯研究中的各種批評觀點進行系統的梳理和學理的探討。顯然,這與翻譯莎作的巨大成就相比是極不相稱的。有鑒于此,作者對20世紀后50年的中國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作了一番梳理,以便對此有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作者不僅對這一時期的莎士比亞翻譯作了資料性的梳理,更重要的是從具體譯家出發,通過梁實秋和魯迅對于莎士比亞翻譯的論爭進一步探討了翻譯中的理論問題。另外,莎劇翻譯中的版本問題也是值得關注的。在莎士比亞作品的翻譯中,版本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在早期的莎作翻譯中,相當多的譯者忽視了莎作版本的選擇。早期的莎劇譯者或限于條件或考慮不夠,一般不大講究版本。朱生豪、梁實秋采用的是牛津版,而牛津版在19世紀的莎學版本中,地位實在不能算是很高。由于在版本的選擇上或因條件限制,或因認識不足,因而對版本問題注意不夠;那么在對莎氏時代的語言的性質、語音、拼法和詞匯的研究就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因此,一些莎作的翻譯受到了批評。顧綬昌認為,粱實秋譯的莎劇,在文字上顯得干燥乏味,每句似乎都通順,合起來整段卻不像舞臺上的對話,并且譯文語氣很少變化,原文詩意也很少保存,這是譯文最大的缺點。朱生豪譯文雖做到“明白曉暢”,然而喜歡重組原句,損益原文,不是太羅嗦,就是太簡,有些譯得比較優美的段落,往往又過于渲染鋪張,它的最大缺點是任意漏譯,并且譯文中還時常夾雜些不必要的詮釋。[2]285本書在研究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基礎上進而對莎士比亞翻譯批評的思考,不僅總結了中國莎士比亞翻譯的成果,也提出了以后研究的方向。如對莎氏翻譯家比較系統、全面的翻譯思想的探討基本上是空白。在莎士比亞翻譯批評中有些批評的目的并不在翻譯批評本身,而是為了思想和文學論爭的需要。這樣的批評雖然也涉及到對莎作的翻譯批評,但是醉翁之意不在莎作批評,而是在于政治、文化、思想、文學、翻譯觀點的論戰。[2]304-305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問題仍然與莎士比亞時代的問題有很多相似之處:生死、戰爭與和平、人與宗教、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等和諧問題都是應當引起我們注意的。因此,閱讀莎士比亞、研究莎士比亞,目的是從文化、文學傳播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視野全面吸收莎氏的思想、藝術精髓,結合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點進行闡釋,為我們今后把握世界文化發展的潮流提供了有益的啟示。“通過對莎士比亞作品的批評以及對這種批評的梳理,或許我們會在現代意義上更為深刻地理解人類面臨的各種問題”。[2]505這是因為莎士比亞是英國的,但同時他又是屬于世界的。約翰遜曾這樣稱贊莎士比亞作品的永恒性“:一場洪水所堆積的泥沙被另一場洪水沖走了,但巖石始終堅守陣地。時間的洪流經常沖刷其他詩人們的容易瓦解的建筑物,但莎士比亞像花崗石一樣不受時間洪流的任何損傷。”[3]125李偉民莎學研究的視野開闊,研究方法多樣。在這本專著中,讀者可以看到偉民的莎學研究涉及了各個不同的角度和側面,有文本研究、比較研究、辭書研究,也有莎學傳記研究、莎學批評研究和莎學家的研究,還有從文獻計量學角度的研究。做到了史論結合,以中國當代莎學發展史為線索,又對莎學研究的發展特定作出了自己的新見解。總之,研究角度豐富多采,研究方法多種多樣,充分顯示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富有創見的莎學學者思想的活躍和視野的開闊。總的來看,這本厚重的著述是中國語境下對莎學研究的“全景式”解讀。正如著者在緒言中所說,中國莎學組成了一個多聲部的規模宏大聲音色彩鮮明響亮的長篇巨制交響樂,而蘊涵其中的“莎士比亞批評”則顯示了我們中國人比較的眼光,構成了中國莎學研究的最鮮明之處,形成了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特色。在《中國莎士比亞批評史》中,李偉民先生對這種特色加以梳理,勾勒其歷史的痕跡,研究中國莎士比亞批評的規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把握莎氏作品的本質和特色,掌握文藝批評規律,提高對莎作的鑒賞水平和批評的理論水平。
參考文獻:
[1] 曹樹鈞.簡論四川學者李偉民的莎學研究[J].四川戲劇,2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