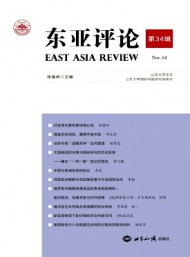東亞傳統音樂的特征范文
時間:2023-10-25 17:25:45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東亞傳統音樂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民族音樂;音樂文化區;地域差異
所謂一方水土養育一方人,不同地區音樂也各不相同,正如我們所知道的中國北方音樂大都豪放粗獷,南方較之秀婉靈巧,高原音樂高亢燎亮,而平原下游地區表現得舒展自如。江南水鄉,培育了江南一帶的細膩柔情,江南絲竹嗚嗚咽咽,如泣如訴,聞者也斷腸!西北大漠之下的人民豪邁,爽直,一陣迅入雷雨的安塞腰鼓,直震得人豪氣滿腸……根據音樂風格的差異,世界音樂被劃分為包括東亞音樂文化區,東南亞音樂文化區,拉丁美洲音樂文化區,黑人非洲文化區等九大區域。民族音樂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說法能更精確地表現地域生態對民族音樂的影響:民族音樂指的是扎根于各民族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具有該民族的音樂形態特征的傳統音樂。從這定義可以看出,不同地域下的地理、氣候、政治、經濟、文化,宗教以及在這環境下形成下的人思想意識等都和民族音樂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音樂就是在文化的脈絡中,圍繞著人類的自然環境,社會形態,文化背景的精密關系中得以傳承的。
自然環境在民族音樂中起著基礎性作用。何為民族?民族不等同于種族,是由共同地域、語言、經濟關系、生理素質在長期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形成的人們共同體。在這里,共同地域作為民族形成與否的一個判斷標準,就足以看出自然環境對于民族的重要性,民族音樂作為民族特性的一個方面,也依賴于自然環境。
其中,各民族所使用的樂器的不同可以表明音樂與當地風土的密切關系。在東南亞等一些適宜竹子生長的濕潤地帶,用竹子為材料而制作的笛子等竹制樂器就特別多。而在干燥的阿拉伯地區,用葦稈制成的納伊笛則盛行。再如,東亞一帶由于盛產木材,在弦鳴樂器中的琵琶是用整塊的大木頭挖空制作而成。氣候干燥的中亞各地幾乎不生產什么大木頭,樂器制作所需的材料也就只能委曲求全――改為小型的或大型樂器只能用木片拼湊而成。在植物生態環境下生長的動物同樣對音樂產生重要影響。以鼓為例,蒙在鼓框胭體兩面的皮革有羊皮、駱駝皮、牛皮、馬皮,蛇皮等,不同的皮革來源于不同的生態環境,因為他們大多是就地取材。當地動物品種的飼養制約引導了樂器材料的使用。同時,以日照量、雨量為劃分標準的氣候也對音樂差異產生直接影響。以音階為例,在溫帶的東亞地區主要使用五聲音階;在熱帶,亞熱帶的東南亞地區,同時使用五聲音階和七聲音階。以水系,山脈等為劃分標準的地形同樣是形成各地獨特音樂風貌的客觀基礎。
從古代人類四大發明的發源地就可以看出河流的貢獻:埃及文明發生在尼羅河流域,黃河流域是中國文明的搖籃,古印度文明與印度河密切相關,古巴比倫文明發源于兩河流域。同樣與此緊密相關的埃及音樂、中國音樂、印度音樂,美索不達米亞音樂等也吸收了河流營養的汁液。山脈對音樂的影響則從反面體現出來,它常常對音樂文化的擴散起著阻擋和分割的作用。最明顯的就是高大的喜馬拉雅山山脈,它劃分丁東方兩個主要的音樂形態: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音樂文化區與以印度為代表的南亞音樂文化區,兩者在音樂組織、節奏以及樂器演奏形態方面都迥然不同。
自然環境是滋生民族音樂的土壤,文化是社會的生活形態,社會環境對民族音樂的影響在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尤為明顯。社會環境中的政治因素首先對音樂產生重要影響。一個國泰民安的民族,音樂往往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一個戰亂連連的民族,在戰爭的焦土上一般不會出現音樂繁榮的局面的,恐怕有的只是抒發國破家亡的靡靡之音。民族音樂在這種大勢之下求得生存也是與政治密切相關的。一個開放的民族,比如一個多年前的盛世唐朝,其統治者以兼容并包的風貌來面向自己統治下的眾多民族和外來民族,以音樂為代表的藝術空前繁榮。也就是在這時,西域音樂包括佛教音樂傳到中國,湮沒很久的少數民族音樂終于沿著長安街流入中原。沒有壓迫,沒有歧視,反而更加鼓勵,支持,民族音樂在這種開明的政策下勢必要走向繁榮。
文化作為音樂的母體,對音樂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尤其是語言,其差異性直接影響了民族音樂風格特點的形成。中國有著五十六個民族,各個民族的語言都不同,同唱一首歌,其中的蘊味就會各顯千秋。例如,漢族通用的語言是普通話,用普通話表現的唱詞就表現的字正腔圓,感情深厚。蒙古族的蒙古語顯得瑣碎綿長,蒙古民歌中具有代表意義的長調就能表現出那種重在語調語勢上的唱法。與歐洲民族相比較,漢語由于聲調具有明確語義的作用,所以樂音往往在其運動過程中發生有意識的音高,力度和音色的變化。而在歐洲民族語言中,由于不重視音調,聲調不具有明確語義的作用,音樂與樂音之間呈現明顯的直線性的階梯式狀態。
篇2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05--01
《兔俠傳奇》是一部以武俠片為背景、宣揚誠信的影片,其音樂主題是由琵琶和笛子來演奏的,笛聲的悠揚和柔美極具俠骨柔情。本部影片中對民族器樂的利用使得電影有著強烈的中國韻味,在表現故事情節的同時,還彰顯了中國的特色文化。《兔俠傳奇》中以民族樂器為主的電影音樂的應用無疑是該電影的一大成功之處。
一、電影中的民族樂器
《兔俠傳奇》是一部國產動畫電影,在整部影片中,音樂是以民族器樂為主的配樂,主要的樂器為笛子和琵琶。琵琶是東亞地區較為傳統的一種彈撥樂器,最早起源于秦朝,至今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現今,依據平均律依半音順序對琵琶上的音位進行排序,通常安裝有六相二十五品,琵琶的音域由A至e組成了音域較廣的十二平均律。由于音色的豐富多樣和技法的復雜多變,琵琶被稱作“彈撥樂之王”。
笛子的材質通常為竹子,因此,笛子還被稱為“竹笛”。笛子是我國傳統樂器中最主要的一種樂器,它的音色清脆且明亮高亢,在發聲時不僅依靠腔體的共鳴,還依賴于笛膜的震動[1]。在世界各地的笛子中,僅有我國的竹笛存在竹膜,這是其最明顯的一個特征及優勢。我國笛子由來已久,在新石器時代便已經存在了。很久以前的人們利用骨笛傳遞訊息,驅走猛獸。在河南出土的有年代的骨笛中,有些能吹奏六、七聲音階,另外還有極個別能吹奏出變音[2]。笛子是我國傳統音樂中一種較為常見的橫吹木管樂器,一般在一個民族樂隊里,笛子是一種較為重要的吹管樂器,是我國民族吹管樂主要的代表性樂器。
二、電影中具體的音樂表現
將觀眾帶入整部電影氛圍的是嘹亮而悠長的笛聲,從一開始影片就隨著音樂充斥著神秘而又有濃郁的武俠氣氛,明快、節奏感強的打擊樂結合充滿仙風道骨、飄逸的笛聲直接顯現出整個電影的主題――“俠”。在影片一開始出現笛聲以后,加入琵琶聲對同一旋律進行重復,把片頭音樂逐漸推向了,隨后慢慢變弱從而引出該動畫電影的具體情節。
在影片開頭,兩米和師傅在追逐奔跑,此時,音樂為交響樂和笛子的結合,這樣柔和而又清新的旋律呈現出溫馨和諧的氣氛,緊跟著是兩米送信的情節,這個時候音樂突然停止,繼而出現用笛子模仿鳥鳴的聲音結合琵琶的輪指,這樣令人緊張的節奏帶給觀眾詭異的感覺,為之后熊天霸的出場作鋪墊,這樣的音樂表現多用于發生危險或出現不好的事情前。在影片中兔二做炸糕這一情節時,配樂是以琵琶與木魚為主的接切節奏,極具詼諧幽默、愉悅的感覺。在影片中,師傅傳授給兔二武功時,影片開頭以笛子為主的旋律結合著交響樂再次出現在影片中,音樂旋律層層推進,帶給觀眾一種輝煌、偉大的氣勢。在長途跋涉、打劫等場景中,都多次出現琵琶和笛子的音樂,不斷凸顯著本部影片中民族器樂的音樂基調。
在兔二進京的情節中,琵琶、笛子、揚琴、梆子以及小鑼等多種民族樂器混合的配樂出現,結合畫面內容,更生動形象地體現出京城一片繁華、熱鬧的景象,以直觀的聽覺感受帶領觀眾進入到電影的故事情節中。在武林大會這一場景中,為了體現現場氣氛的熱鬧非凡,在配樂中加入了笛聲、琵琶聲、大堂鼓聲以及揚琴聲等多種聲音混合。在接近電影結尾處,兔二和熊天霸戰斗的畫面場景中,以笛子為主題的旋律再次出現,這意味著快要迎來勝利。在戰斗結束后,出現以笛子為主題的旋律,表明故事即將結束,此時,主題旋律的應用配合著畫面內容營造了一個溫馨動人的場面。
三、民族器樂在電影音樂中的發展
在電影音樂中加入民族器樂元素是順應電影音樂發展潮流后的必然趨勢。在《走進現代的陜北民歌》中,著名的民族音樂學家張振濤曾經指出,任一民族若中斷了傳統文化,即便這個民族的物質再豐富,民族的發展也是沒有前途的[3]。電影音樂極度渴求民族、民間音樂元素,這些元素不斷應用在電影音樂中。在電影事業的發展過程中,電影音樂不乏有民族民間音樂元素的加入,例如往年的《霸王別姬》、《刮痧》以及近期的《金陵十三釵》等不斷將民族民間元素融入進電影音樂,這樣的情況也在預示著未來電影音樂的發展走向。
篇3
曼紐爾?吉瑪?拉比1950年生于西非的加納首都阿克拉,1964年到1971年在阿克拉的阿齊莫塔(Achimota)學校接受音樂啟蒙教育,1973年開始在加納大學學習音樂和哲學,1976年取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后,繼續跟隨圖克森(Turkson)學習作曲,同時以專業作曲者的身份跟隨恩凱蒂亞(Nketia)學習傳統音樂。1979年在美國伊利諾斯大學取得理論和作曲的碩士學位,1983年在美國俄亥俄州的辛辛納提大學取得理論和作曲的博士學位。在結束了近20年的專業音樂學習之后,拉比正式開始了自己的教學、創作和研究生涯。他目前定居美國,就職于華盛頓大學。迄今為止,拉比的創作大致包括:兩部交響樂、為管弦樂隊而寫的幻想曲《民間漁歌》(Tunes of the Fisheffolks)、弦樂四重奏《完美無瑕的蜂窩》(Al the Immaculate Beehive)、為長笛、低音單簧管和鋼琴而作的五個樂章的三重奏《空間幻想》(Visions of Spacc)、定音鼓協奏曲《遠古的視角-3》(Ancient perspective-3)、兩首無伴奏大號作品以及一套非洲風格的鋼琴作品《方言》(Di-alects)等。
《方言》是拉比題獻給自己的音樂啟蒙老師――[英]約翰?博翰姆(John Barlum)的作品。據作曲家所說,這套作品的創作是開放式的,即永無終止,到目前為止,已經完成了六首,分別是:《獵人之歌》(The Hunter's Song,Op.18,1986。Key’d.1998);《蓮花》(The Lotus,Op.21 1987,Rev’d.1997);《地球的節奏》(Earth Beats,Op.22,1988,Rev’d.1997);《菠蘿》(The Pineapple,Op.23,1991);《遠古再現》(The Andents Re-visited,Op.24,1993)以及《Esentre的春天》(The springs of Esentre Op.28,1999)。
《蓮花》是《方言》中的第二首,其創作靈感源于作曲家對神秘的東方主義的解讀。作品表達的中心是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諭旨人要保持高潔的品質,堅持真實的自我。作曲家提醒音樂愛好者和專業演奏家們,在第一次演奏時可能會感覺該作品與那些古典的、人們以往熟識的作品風格不一樣,這主要是因為它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純歐洲風格的鋼琴音樂,而是以加納傳統民間元素為基礎的非洲當代鋼琴音樂。
《蓮花》的音樂創作特點
《蓮花》創作完成于1987年,是一首以東方主義為創作主旨、以歐洲藝術形式為表現手段、以非洲傳統元素為創作素材的多元混合的藝術作品,是作曲家的一種全新的創作嘗試,表現出非洲當代音樂創作在多元文化影響下的混合風格特征。
一、作品主旨 蓮花,原產于中國,是我國十大名花之一。早在三千多年我國就有蓮花的栽培,后來又傳至其他地區,一般分布在中亞和西亞國家的亞熱帶和溫帶的池塘、沼澤地。蓮花與文化的關系體現最深的就在中國,古往今來的中國文人都驚嘆于它的清姿素容而訴之筆端高歌詠嘆,并譽之為“花之君子”。中國人喜愛這種植物,認為它是潔身自好、高潔品質的象征,因此詩人有“蓮生淤泥中,不與泥同調”的贊譽。中國文學中借蓮花抒情的詩詞歌賦比比皆是,最著名的當屬北宋周敦頤《愛蓮說》中的千古名句。
吉瑪?拉比身為一名非洲作曲家,有感于蓮花的這種高潔品質,并受中國文化在數千年的發展中所形成的“寫意”的美學特點的影響,借“蓮花”為音樂主旨來抒發自己對這種神秘的東方主義的追求,也提醒自己要堅持自我,做一個志潔高尚的人。
二、音樂主題 《蓮花》的音樂主題是一條代表蓮花高潔品質的“東方旋律”。
全套《方言》創作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它多變的音樂構思,作曲家總是以音樂表現主體的實際形態來設計樂曲結構,《蓮花>也不例外。蓮常年生長在水底的淤泥當中,泥土中混積了大量的雜質,這種生存環境非常渾濁。于是,作曲家就用大量不協和的二度音程、并置的四度音程和各種類型的減和弦來表現這種環境的惡劣。但是在這種由不協和音造成的“躁雜”的聲響上方,時隱時現著一條清晰的主題旋律。
一開始是暫露頭角,在第61小節才呈現全型,之后又斷斷續續地變化重復,直至接近曲終時才又完整再現。這是全曲惟一的一條“線性旋律”,即“蓮花”的音樂主題,旋律清新素雅,象征著高雅圣潔的蓮花品質。
線性旋律是東亞音樂文化的一大特色。東亞音樂在音樂審美方面的最大特點是追求古樸典雅的橫向旋律的音樂美,為了達到這個審美需求,音樂的形態講究彈性的節拍和節奏,運用五聲音階和五聲性的旋法,采用漸變的音樂結構,偏愛單音性的線性旋律。雖然有一些音樂也表現出多聲性的性質,但是它們是以橫向旋律的展開為宗旨的,依然強調線性旋律的特點。《蓮花》以這種極具東方色彩的線性旋律作為全曲的主題句,每一次出現都極其醒目。
三、調性《蓮花》的調性無從確定,它沒有以三度音程為基礎的和弦、沒有功能和聲的進行、沒有不協和音響向協和音響的解決等表現調性的依據,屬于無調性音樂。
同時,《蓮花》的無調性里還零星散布著一些半音進行。
它出現在第65小節,即上節所述蓮花主題第一次完整展現時的尾部的低音聲部。這些半音的進行在原本已經不和諧的音響上造成了進一步的緊張感,這就更強調了整首樂曲的無調性感,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不再一一列舉。這種半音化的表達方式也表現出20世紀后期歐洲音樂無調性半音化的特點。無調性半音化以半音階為旋律與和聲的音樂思維基礎,沒有調性中心或中心和弦,沒有單純的能產生調中心作用的三和弦,使音樂整體進一步呈現不協和的和聲音響。
四、節奏 《蓮花》的節奏有典型的非洲傳統音樂的特點。在非洲,鼓樂盛行,但是由于鼓與其他樂器相比缺少了在音色和旋律上的變化,因此“節奏的高度復雜化”成為非洲音樂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非洲傳統音樂語言中,節奏的基礎是一種“律動結構”。它能夠分成2和2的倍數、3和3的倍數兩種,即非洲音樂里的二拍子節奏和三拍子節奏。均分的節奏可以按二拍子、三拍子或‘二、三拍子的交替’組合起來”。“二、三拍子的交替”節奏是按時值長短組合的一種橫向的節奏語言,除此之外,縱向節奏的對位變化也十分常見。多線條節奏的組合產生出兩種節奏效果,一種是交叉節奏,另一種是復節奏。“交叉節奏的相互作用出現了并置的節奏,而這些節奏是按不同的律動結構組合起來的。……即縱向的二 拍節奏和三拍節奏在相互起作用”;復節奏是“節奏型按進入點間隔開來”。
在這首《蓮花》里,可以找到很多如上節奏組合的運用,以下簡單截取幾例:
五、和音 《蓮花》運用了一種和音語言,叫做“Quartal”(四度和弦),這是西非的艾維人常用的一種特殊的演唱技巧。艾維(Ewe)是指原本居住在現在西尼日利亞的Oyo地區、后來從東邊遷移到現在的加納東南、沃爾塔瓦河東部一帶、居住在加納東南部、多哥和貝寧灣地區的黑人種族。艾維人說艾維語,與其他說Gbe語的人群,如多哥、貝尼灣的豐族和阿佳族有著親緣關系。艾維人在歌唱時常常通過聲音的持續不斷地跳進來表達自己的情感,這并非客意而為,而是一種感情的自然流露。在器樂創作中,這種不間斷的持續跳進則體現了對樂器極限音域的頻繁挑戰。Quartal技法在《蓮花》里并不是第一次被使用,早在1992年拉比就把它用在了受奧瑞恩?馬歇爾(Oren Marshall,大號演奏家,曾在1992年早期到加納大學視察)之托創作的兩首無伴奏大號作品《2Ancient Perspectives》(Op.24)“Dzagidi”和“Vodzogbe”里。《蓮花》充分發揮了quaml的技術特點,使它成為全曲重要的音樂語言。
綜上幾點所述,《蓮花》的創作廣泛集合了東方、歐洲和非洲的創作特征與表現手法,打破了傳統與現代的界限,顯現出多元的混合的特點。
由《蓮花》引起的思考
《蓮花》所表現出的多角度的多元混合實際上意味著拉比的鋼琴創作已經走進了后現代主義。
后現代語境中一個重要特征是主體性的死亡以及到處彌漫的社會性精神分裂癥的乘虛而入(F?杰姆遜)。“身份的破裂”(Fragmentation)是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問題。當今,這種分裂的主體性在后現代文化形態中則是以一種膚淺的混合風格得以展現的,在專業音樂創作領域則表現為“無序”、“解構”、“反形式”和“多元混合”。具體到《蓮花》,它表面上所顯現出的多角度的“多元混合”實際上是后現代主義中“破裂”的一種表現。破裂意味著與完整的統一主體之間無可挽回的徹底決裂,這種決裂在文化中的表現最為突出。
從《蓮花》的作曲家本身來講,拉比是出生在非洲、生活在美洲、學習歐洲音樂知識的“混合個體”,他的身份屬性是混合的。身份的混合意味著身份主體變得模糊,于是,人的主體就變成了破碎的影子。《蓮花》的創作構思是東方文學對蓮花的借物言志,創作手法是歐洲鋼琴對非洲傳統民間合唱的移植模仿,創作結果是非洲的鋼琴作品,但是這種表現結果卻與傳統的非洲文化分裂了,也與古典的歐洲鋼琴割裂了,也就是說這首作品的主體屬性是破裂的。
杰姆遜認為對后現代主義的判斷應該包括如下因素@,即1、摹襲;2、對文化的掠奪和再造;3、對其他文本和圖像的直接祈求。
中國學者在將英文的“Pastiche”(n.混成曲:模仿畫)解譯為“摹襲”時,就使后現代主義的這一判斷因素具有了兩種含義。“摹襲”出自清代陳田的《明詩紀事戊簽?靳學顏》中的“子愚,頗擅才華,集中有《七諷》《解嘲》等篇,類以作者自命。詩則古體摹襲前人,時有佳作”。“摹襲”即解為“模仿和沿襲”。模仿是照某種現成的樣子學著做;沿襲是依照舊傳統或原有的規定辦理。后現代主義把已存在的音樂看做是一種實物現成品,以此作為模仿和沿襲的對像,將各種風格拼貼起來,重建和組合,形成新的作品。這首《蓮花》就具有以上兩種手法,首先它“模仿”了非洲的傳統樂器,用筆將它們在傳統演奏中的節奏和旋律模式記寫在紙面上;其次它“沿襲”了歐洲鋼琴音樂的創作邏輯,將非洲傳統音樂語匯精挑細選出來,排列、拆分和重組,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后現代音樂語言風格。因此《蓮花》符合后現代主義的第一點判斷因素:摹襲。
對非洲傳統音樂的謄寫、拆分和重組的創作行為,毫無疑問是對非洲傳統文化的一種掠奪和再造。因為這些行為并不是將傳統音樂的形式完整地保存下來,而是為了適應現代藝術音樂的表演和欣賞需求,更是為了適應世界范圍的接受群體的欣賞習慣而進行的再創造。它已經脫離了非洲藝術原本的文化語境,變成了另外一種更適應時展需要的文化表達方式。
“音樂聲音作為一種動力過程,是在概念下引導出的實際行為,并轉變成為結構和表現。很明顯,概念和行為是必須經過習得的。文化作為一個整體是習得的行為,各種文化依據它自己的觀念和價值形成了習得的過程”。非洲傳統音樂的最簡單和最普遍的習得行為就是模仿。然而,彈奏《蓮花》這類的非洲鋼琴音樂卻是一項長時期的專業技術訓練,這種專業的技術訓練并非模仿那么簡單。
在非洲社會中,音樂活動總的來說是社團成員間、種族親戚間的社交活動,通過這些音樂活動人們之間相互認識,音樂做為表達共同情感的渠道將各種社會關系連接在一起。非洲音樂沒有鮮明的演出者和欣賞者的界限,所有的演出者都是聽眾、所有的聽眾都是演出者。當然,非洲并不是沒有獨唱或獨奏的演出形式,只是人們更注重集體的音樂活動而不是個人的音樂表演。非洲鋼琴音樂的表演形式完全打破了舊有的模式,演出者和欣賞者界線分明,他們各居其位、履其職責。
以上這些都使非洲原本的音樂文化遭到破壞,而出現新的文化習慣,因此《蓮花》又符合了后現代主義的第二點判斷因素:對文化的掠奪和再造。
對于像筆者這樣的中國學生而言,欣賞類似于《蓮花》這樣的非洲鋼琴音樂存在理解上的差異。造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是:欣賞者總會與作曲家處于不同的社會和文化背景之下,在意識形態、思想感情等各方面都存在著很大的距離。對非洲作曲家本人而言它是本國文化的藝術作品,而對欣賞者而言它卻是異國文化的藝術作品,這種欣賞是“跨文化”的。作曲家作為一名黑人音樂家,他的音樂創作與非洲母體文化有著密切的聯系,而對于大多數處于“非”非洲文化體系下的人來說是一個新鮮而陌生的領域。對音樂研究而言,這涉及到“跨文化”的立場問題,作曲家是其所處文化體系的“局內人”而研究者有時卻是“局外人”。局內人與局外人的角色劃分,“體現著對文化的理解方式:是從文化內部的眼光來看待文化,還是從文化外部的眼光來看待文化,其結論完全不同。”《局內人》與研究對象處在相同的文化系統中,他們使用相同的語言、具有相同的審美習慣,相互之間不存在文化上的隔閡。同時,“局內人”對研究對象的觀察又總能細致入微,這種與生俱來的“親近”是“局外人”望塵莫及的。“局外人”不能真正地進入研究對象的文化系統中,“局內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對于“局外人”來講卻是“不知所云”、“何以謂之”。這樣一來,無論欣賞者還是研究者都急需借助其他文本或圖像來消除這種理解上的隔閡,而作曲家也確實這么做了。他在樂譜之前附加文字資料或是專門發表文章來闡述自己的創作意圖和創作手法,這對“局外人”理解音樂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因此,《蓮花》也符合了后現代主義的第三點判斷因素:對其他文本和圖像的直接祈求。
篇4
劉傳啟認為,敦煌佛教歌曲對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區佛教的盛行起到了積極推動作用,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是宣揚儒家孝悌觀念的另一個重要陣地[8]。張雪等人通過實驗研究指出,電針可結合佛曲治療中風后抑郁,該方法能改善抑郁給患者帶來的負性情緒,副作用小并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9]。近五年國內對佛教音樂功用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其在當代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意義和心理治療及保健功能。結合以上學者對佛教音樂內涵的理解,筆者認為,佛教音樂作為一種具有很強韻律、旋律、明確節奏和完整曲式結構的宗教儀式音樂,是指佛教信徒進行佛事弘法時的唱誦,是修習定學法門之一,同時具有心理治療及保健功能。
二、佛教音樂的發展
在中國音樂的發展過程中,作為傳統音樂重要組成部分的佛教音樂自身也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不斷進行著發展變遷。對于中國佛教音樂的歷史發展階段劃分,郭紅麗指出,唐朝是佛教音樂在中國的創造階段,宋元和明清時期是其在中國的融合和完善階段[10]。盧藝指出,東晉至南北朝時期,佛教音樂進入初盛發展期,隋唐時期以法曲為代表的佛樂進入了鼎盛階段,宋、元之后,佛教音樂愈加通俗化[11]。在國內近五年研究文獻中,關于佛教音樂發展的研究很多,主要從佛教音樂的融合與創新、佛教音樂的華化和佛教音樂的民間化與世俗化三個角度來開展研究。有部分學者研究了佛教音樂的融合發展與創新問題。潘龍華論述了佛教音樂與中國傳統音樂的相互影響,指出兩者在發展過程中是互相吸收和互為融合的[12]。凌翼云從《魚山梵唄》的視角對佛教音樂與本土音樂的融合過程進行了分析,并指出佛教音樂本土化的同時,它也被本土音樂汲取和融入[13]。李鑫賽以《萬物生》音樂專輯為例剖析了我國佛教音樂元素與流行音樂元素二者的融合與創新問題[14]。常麗文從《禪宗少林音樂大典》來研究了佛教禪宗和佛教音樂兩者的藝術結合,并指出禪宗和宗教音樂兩者之間存在的共性是二者結合的基礎[15]。隋唐時期的佛教音樂達到其鼎盛階段,至唐代時佛教梵唄徹底華化。傅暮蓉論述了佛教音樂梵唄華化的具體方法和過程,并指出華嚴字母是梵唄華化的橋梁[16]。她還對佛教梵唄華化的創始人進行辨別和考證,并指出中國梵唄的第一創制人非曹植,而是早期的譯經家支謙,曹植是中國梵唄的實踐者和弘揚者[17]。佛教音樂的本土化、民間化與世俗化不僅豐富了中華音樂文化的藝術形式,還使得經過融合和創新發展的佛教音樂更易貼近民眾和吸引世人的關注。姚慧指出,佛事音樂在后期通過民間喪禮走出寺院、回歸民間,經歷了“佛教音樂民間化”的再造歷程,佛教音樂又因為民間市井、俗人百姓服務而去凈去雅、逐漸俗化[18]。劉傳啟、張榮軍對敦煌佛曲民間話語形態進行了研究,指出敦煌佛曲是佛教進入庶民生活的重要手段之一[19]。陳華麗通過對廣東新興國思寺僧人進行的關于佛教音樂觀念的問卷調查分析后,指出該寺的佛教音樂世俗化明顯[20]。無論佛教音樂的本土化、民間化與世俗化如何發展變遷,只要經過融合和創新發展后的音樂能達到凈化人心等佛教功能都可視為是佛教音樂自身生存和發展的歷史必然選擇。佛教音樂的發展過程會受到各種文化和環境等因素的影響。楊民康論述了佛教寺院的叢林制度對佛教音樂發展產生的重要影響,對佛教叢林制度與佛教音樂風格區的相互關系進行了深入探討[21]。對佛教音樂梵唄的發展研究當然離不開對“魚山梵唄”和“華嚴字母”的研究。魚山梵唄作為漢傳梵唄的初創,同時也是中國化佛教音樂的精髓,在佛教音樂的發展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五年對魚山梵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魚山梵唄的源流演化及其樂譜形式研究。釋永悟認為曹植是創作中國佛教梵唄的第一人,并梳理了不同歷史時期魚山梵唄的發展演變過程[22]。王哲同樣認為是曹植結合中國語言音韻規律創制了魚山梵唄。“魚山梵唄”的源流演化是有爭論的[23]。參考文獻17中指出中國梵唄的第一創制人是早期的譯經家支謙。英K.P.K.Whitaker也指出對曹植作為梵唄創制者的這一角色,在歷史文獻中缺乏有力證據[24]。王淑梅指出“魚山梵唄”在南朝劉宋時期已經廣為流傳,并與道教音樂有所融通,她還進一步對“魚山梵唄”的樂譜形式進行了分析[25]。王小盾、金溪對魚山梵唄傳說的道教背景進行了深入剖析,并揭示了魚山梵唄傳說的歷史內涵和發生原理[26]。漢傳佛教梵唄《華嚴字母》作為佛教梵唄中大型的經典套曲曲目,同樣在佛教音樂研究中具有重要價值。近五年對其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梵唄《華嚴字母》的歷史淵源和音樂特色研究,對其開展研究的學者主要有中央音樂學院音樂學研究所的傅暮蓉和上海大學數碼藝術學院音樂系的徐菲。傅暮蓉指出,因為有梵唄華嚴字母的傳入中國佛教音樂梵唄才能徹底華化,并對它的來源、語言系統、特征及意義進行了深入探討[27]。她指出依照諷誦《華嚴經》的儀式,其梵唄華嚴字母儀式中的音樂分為誦《華嚴經》之前的梵唄和誦《華嚴經》后的梵唄華嚴字母套曲[28]。傅暮蓉認為,梵唄華嚴字母的出現標志著印度梵文及語言發音和梵唄在中國的徹底華化,并從華化的華嚴字母漢譯注音及構成表、漢譯梵唄華嚴字母及其原理和梵唄華嚴字母中的鼻韻幾個視角探討了梵唄華嚴字母的華化[29]。徐菲對上海市普陀區的真如寺、松江西林禪寺和青浦區莊嚴禪寺三個寺院的《華嚴字母》的開始本分“華嚴字母贊”進行音樂風格的對比分析[30]。徐菲從曲式結構、旋律特色和演唱中的多聲部形式等幾個方面對漢傳佛教梵唄《華嚴字母》的音樂藝術特色進行了分析[31]。另外,徐菲還對《華嚴字母》的同曲變體特征進行了深入研究[32]。漢傳佛教梵唄《華嚴字母》具有獨具特色的音樂結構和旋律特色,對其音樂和藝術特色及其唱誦的研究仍需民族音樂和宗教藝術學者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深入研究。
三、佛教三大體系音樂研究
中國佛教體系包括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和南傳佛教三個組成部分,佛教音樂體系相應地也可以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分別是漢傳佛教音樂、藏傳佛教音樂和南傳佛教音樂。近五年對于佛教音樂的部分研究也可從這三方面來進行梳理。近五年對于漢傳佛教音樂的研究主要側重于漢傳佛教的音樂功能與佛教儀式音樂特征的分析。王黎玨從梵唄、音樂和法器兩方面分析了中國漢傳佛教音樂的基本形式與藝術特征,并對其音樂功能進行了論述[33]。張喬指出,初創期的佛教題材編創歌曲藝術特征有通俗性、時代性和傳統性,發展期的佛教題材編創歌曲藝術特征具有國際化、多元化和舞臺化[34]。傅暮蓉對漢傳佛教儀式音樂的音樂形式和文化特征進行了研究[35]。此外,周耘還對20世紀以降中國大陸漢傳佛教音樂研究的歷史與現狀之整體進行了系統梳理與歸納[36]。近五年對于藏傳佛教音樂的研究主要側重于藏傳佛教的音樂形態特征、寺院器樂、儀式與法會音樂的研究。王進指出,藏傳佛教音樂由誦經音樂、羌姆樂舞和寺院器樂三個部分組成,并認為三類藏傳佛教誦經音樂的主要區別在于誦經音調的音樂性與語言性強弱程度[37]。田聯韜指出,藏傳佛教的誦經音樂基于音樂旋律性的強弱程度可分為頓、達和央3類[38]。才讓措研究了藏傳佛教誦經音樂的發聲特點和音調特征[39]。桑德諾瓦認為,云南藏傳佛教音樂形態主要集中表現在音階、調式、旋律、節拍、節奏、速度、曲式、詞律、結構以及樂隊組合等幾方面[40]。對于藏傳佛教寺院器樂、儀式和法會音樂的研究主要有對藏傳佛教覺囊派藏哇寺寺院器樂音樂研究[41]、覺囊派中壤塘確爾基寺歲末驅魔法會音樂[42]、藏傳佛教臨終關懷與亡靈超度儀式音樂[43]、藏傳佛教“死亡修行”儀式音樂思想[44]、藏傳佛教宗教祭祀儀式羌姆樂舞音樂[45]。近五年對于南傳佛教音樂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南傳佛教的音樂風格及其儀式音樂的考察。董宸從唱詞系統與誦經經腔系統兩方面研究了云南南傳佛教儀式音樂誦經風格,并對云南南傳佛教誦經風格的構成及其要素進行了深入分析[46]。董宸還對南傳佛教擺多教派和擺潤教派二者的音樂風格進行了對比分析,并指出兩教派在共時性平臺上呈現出的經腔系統,形成包含對應和交叉對應的關系[47]。吳學源指出南傳佛教的儀式音樂可分為聲樂和器樂兩種[48]。此外,焦丹還對德昂族三臺山南傳佛教音樂進行了研究,并從佛教音樂作為對信眾宣傳教義的重要手段、對德昂族傳統音樂的影響和成為村寨娛樂的重要形式三方面論述了南傳佛教音樂對德昂族村寨的重要作用[49]。
四、佛教音樂的對比研究及其旅游資源的開發與利用
篇5
一、語言有較大的包容性。
歐洲國家的語言屬拉丁語系,很多語言是相通的,法國歌曲使用英文歌詞,英語歌詞中又夾雜意大利語或西班牙語,都較為常見。例如由法國小天后Alizee演唱的《la isla bonita》,題目意為“美麗的海島”,是西班牙語。歌詞中除反復唱到“la isla bonita”這句西班牙語之外,其他部分都是英語。這首歌的原唱是麥當娜,經法國音樂人改編后,用更富有動感的節奏和熱烈的吉他演奏加強了西班牙式的熱情,洋溢著青春活力。由于“la isla bonita”是西班牙語,所以發音時要把重音放在倒數第二個音節,而且t這個字母要發,不能像英語一樣發。
除此類歌曲外,大部分法國流行歌曲,還是用法語歌唱,比如由伊蓮娜·霍萊在1993年發行的單曲《Je m’appelle Hélène》(我的名字叫伊蓮娜)。這首歌曲在法國獲得了連續25周冠軍單曲的傲人成績,在國際上的傳播范圍也較廣,應該是國人最熟悉的法語歌曲了。
二、展現了語言與音樂的音韻相和。
相傳,拿破侖說過:我們對敵人講德語,對朋友講英語,對女性要講法語。 無論拿破侖是否真說過這句話,至少它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不同國家的語言的特性。德語鏗鏘有力用來震懾敵人,英語方便交流用來廣交朋友,而面對女性則要用優雅高貴的法語,顯示對女性的尊重。法語之美不僅在于其拼寫規范、語法結構嚴密,更是因為在法語語音中,元音多達16個,元音的豐富使語言的音樂性大大增加,更加悅耳動聽。
以弗朗索瓦·費爾德曼經典的歌曲《magic boulevard》(魔力大道)為例,這首歌曲生動地刻畫一位影院領座員,一天天重復著同樣的工作,看著同樣的電影,內心隨著電影畫面起伏著,卻總避免不了電影散場后日復一日同樣的寂寞。法語中,單詞詞末的輔音若非與下一個單詞開頭的元音結合,都不發音,這首歌的第一段歌詞每句的韻尾都落在上,大部分句子的音節以元音-輔音-元音-輔音或輔音-元音-輔音-元音的結構進行。而曲調每句四音的模仿進行,與歌詞每句四個元音音節的主要組合形式形成了絕佳的配合,渲染出了影院領座員落寞的身影和孤寂的心靈。正因如此,這首歌曲成為了北京電視臺《環球影視》節目長達13年的經典結束曲。
Elle voit des films 她一部電影
Cent fois les memes 要看上百遍
Les memes crimes 同樣的罪行
Et les memes scenes 同樣的場景
三、歌詞極富跳躍性、象征性。
法國是單民族國家,其民族性格十分鮮明,法蘭西民族如同她的語言一樣,講求高貴內斂,不喜直抒胸臆,而是以暗示、影射等手法表達細膩的感情。法國文學浩如煙海,尤其是19世紀下半葉的象征主義文學,提倡用隱晦象征的手法表達深層的意念,而象征主義詩歌更是把語言的音樂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這些都對音樂的創作和風格走向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法國電影《蝴蝶》的主題曲《Le papillion》(蝴蝶)中,歌詞以一位老人和一個小朋友的對話作為歌詞,一老一少,一答一問,體現了法國人跳躍性極強的思維和充滿了豐富想象力的童趣。
為什么雞會下蛋?因為蛋都變成小雞。
為什么情侶要親吻?因為鴿子們咕咕叫。
為什么漂亮的花會凋謝?因為那是游戲的一部分。
為什么會有魔鬼又會有上帝?是為了讓好奇的人有話可說。
歌詞每一句都以“pourquoi”也就是“為什么”開頭,曲調配合著歌詞以相鄰的兩個音自下而上提出問題,而回答的部分則無曲調,直接說出,表現出了小朋友的好奇天真與老人的和善幽默。
另一首由童聲組合演唱的歌曲《L’Oiseau》(飛鳥),帶著法國式的淡淡憂傷,與活潑可愛的《蝴蝶》迥然不同。童聲組合Vox Angeli(天使之聲)組建于2008年,是一支由6名13-16歲的孩子組成的歌唱組合,純真無瑕、清澈透明的聲音,唱出美好的童真,像天使般傳達幸福與愛的訊息。
《飛鳥》這首歌的歌詞沒有很明確的主旨,像在敘述一段回憶,描寫一種心境,曲調高亢、樂句線條較長,音域也較高,不像《蝴蝶》那般短促跳躍,而是如鳥兒在空中飛過,漸漸地消逝在天際般飄渺。
四、不同流派相互滲透,多種音樂風格相互融合。
法國流行音樂始終不停地在自我更新,它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和創造性,不斷地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音樂中汲取養分、不停地在自己的音樂傳統中挖掘、從而創造出新的音和調。現略列舉一二:
1、融入阿拉伯風格的歌曲。上個世紀60年代法國本土勞動力匱乏,大量來自阿拉伯的移民涌入法國。而這些移民也將自己民族的音樂融進了法國音樂之中,很多歌曲都能看到阿拉伯音樂的影子。《comme toi》(像你一樣)就是其中一首很具代表性的作品。它由法國家喻戶曉的音樂制作人吉恩創作,許多歌手都演唱過。這首歌曲關注的是一群純真孩童,他們像所有孩子一樣喜歡童話、音樂、書籍,但因為沒有好的出身,這一切只能是夢想,夢想著“像你一樣”享受美好的生活。歌曲間奏有一段吟唱,運用了阿拉伯風格的唱腔,其中增二度音程是阿拉伯音樂的典型特征。這段吟唱仿佛是一個美麗神秘卻又飄渺的夢,吟唱之后,音樂風格又回到了一般的流行音樂,夢想隨之回到現實。
2、東亞元素也受到法國音樂創作者的喜愛。由娜達莎演唱的歌曲《Un Ange Frappe a ma Porte》(天使在敲我房門)由于音域適中、旋律瑯瑯上口,流行較廣,而歌曲中就加入了很明顯的東亞風格。歌曲由一段日語表達的問候與歉意引出,配以五聲調式的鋼琴旋律作為前奏:
而歌唱部分一進入,卻立即呈現典型的西方自然小調色彩。到了音樂的副歌部分,又展現出鮮明的五聲調式色彩:
在這段旋律中,前兩句五聲調式的色彩十分鮮明,后兩句雖說帶有西方小調色彩,但四句式的樂句組合又顯現出“起承轉合”這種典 型的東方風格。
3、用宗教風格創作歌曲。歌曲《leila》(萊拉)是這一類歌曲的代表作之一。《leila》將猶太教傳說中的天使萊拉作為歌唱的對象,她司掌著妊娠,對人類特別是受懷孕之苦的母親充滿憐憫。該曲借萊拉之名,頌揚偉大的母性和自我犧牲的精神,音樂仿佛吟誦經文一般神圣不可侵犯。
這首歌的演唱者瑪蓮·法莫Mylene Farmer,被稱為法語流行音樂界首席女歌手,有著非常強烈獨特的個人風格。她的歌聲另類、穿透力極強,空靈的唱腔營造出一種既古典又現代、既流行又高雅的獨特氛圍。在《萊拉》這首歌中,我們既能感受到她中低聲區的沉厚有力,又能感受到她高聲區的空靈自如。音樂伴奏剛開始只有蜻蜓點水般的伴奏,節奏樂器隨著音樂的發展慢慢加入,造成了音樂層層遞進的效果。
五、音樂充滿著豐富的調性色彩變化。
法國是一個音樂藝術源遠流長的國家,有著獨特的藝術魅力——高貴卻不傲然,深情卻不放縱,優雅又斂致。法國的流行音樂,也受到了民族藝術文化底蘊的深刻影響。《Les rois du monde》(世界上的國王們)是法國音樂劇《羅密歐與茱麗葉》中的著名唱段,前奏一開始是e和聲小調,而主唱一開始,卻沒有任何過渡地直接轉到了D自然大調,小調與大調的迅速切換帶來了調性色彩由暗到明的變化。
《Concerto pour deux voix》(雙聲協奏曲)由法國當代作曲家圣·普洛創作,由宛若天籟的童聲演唱,因而此曲也被稱為《天使之聲協奏曲》。這首作品沒有歌詞,因為一切歌詞修飾都是多余的,只用婉轉高昂的聲音足以表現音樂的美妙。這首歌曲的演唱難度比較大,不僅音區很高,而且有很多臨時變化音,曲調上下起伏,如天使在云中飛舞一般。
綜上所述,法國流行音樂的流行程度,雖不能與英美國家的流行音樂相媲美,但其藝術魅力卻別具一格。它賦予了流行音樂更豐富的內容、更深刻的思考、更多樣的變化,雖是“非主流”,卻也不失“流行”。
責任編輯:曉芳
參考文獻:
艾莉婕(Alizée Jacotey),生于1984年,法國女歌手。
伊蓮娜·霍萊(Hélène Rolles),生于1966年,法國女歌手。
弗朗索瓦·費爾德曼(Francois Feldman),法國著名音樂人。
《環球影視》,開播于1994年,停播于2007年。
正文中的五號字部分皆為歌詞。
《蝴蝶》(Le Papillion),法國電影,上映于2002年。
吉恩·雅克·古德曼(Jean Jacques Goldman),出生于1951年,法國著名音樂制作人、詞曲作者。
娜達莎·圣-皮耶(Natasha St-Pier),1982年出生于加拿大,后于法國發展,女歌手。
篇6
摘 要:德籍韓裔作曲家尹伊桑是當代作曲家,其音樂具有明顯的民族特征并把西方音樂寫作手法融入其中。他的作品涉及所有管弦樂器,以獨奏和重奏為主,并使用其最新演奏技法來表現音樂的內容。尹伊桑《現代長笛練習曲》是尹伊桑于1974于德國創作的。此曲是現代長笛練習曲中的高難度作品。而其中的第五首,整首作品在曲式結構,寫作手法方面都是長笛練習曲中的一個巨大突破。
關鍵詞:尹伊桑(,1917-1995);長笛;《現代長笛練習曲》;第五首
中圖分類號:J647.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2.04.020
作者簡介:徐 戈(1972~),女,文學碩士,武漢音樂學院管弦系副教授(武漢 430060)。
收稿日期:2012-07-23
作為交響樂隊中不可或缺的長笛,其主要特征是音色甜美、輕快靈活。從歷史上看,長笛音樂最大的發展與改變,主要在于對于音色的處理和表現上,而炫技性的長笛作品卻略顯貧乏。自從20世紀以來,西方作曲家與長笛演奏家們為此做出了不斷的創新與嘗試,為長笛創編出多種演奏技法和具有豐富表現手法的長笛音樂作品。因為演奏技法的擴充,使得長笛的表現力不單單是優美,也可以表現出“力量”的一面,真正做到了剛柔并重。著名的韓國作曲家尹伊桑為長笛演奏技法的開創做出了杰出貢獻。以下以尹伊桑現代長笛練習曲中的第五首為例,闡述尹伊桑對長笛新演奏技法的的特征。
一、尹伊桑其人
尹伊桑是著名詩人庸文鉉之子。尹伊桑出生于1917年9月11日的韓國統營(現釜山附近)。14歲開始音樂創作,并在兩年后正式開始系統的學習音樂。1935年,尹伊桑前往日本本土的大阪學提琴,并在東京修讀作曲及對位法。當日本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他回到了韓國。當時的韓國半島正在被日木占領,由于尹伊桑參與韓國獨立運動,1943年他遭到了日本的監禁。“二戰”后,韓國獨立。他在為戰爭孤兒建立的孤兒院里從事福利工作,并在統營和釜山擔任音樂老師。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后,他開始在漢城國立大學里教書。1955年,他獲得由漢城頒發的漢城城市文化獎,也因此獲得了去巴黎和柏林學習的機會。
在巴黎和西柏林就讀期間,他師從皮埃爾·伊夫、鮑里斯·布拉謝、約瑟夫·魯夫(勛伯格的弟子)和萊茵哈德·施瓦茨-席林教授學習現代音樂。在德國達姆斯塔特,他參加了國際現代音樂夏令營,并首演了自己的五部鋼琴作品和一部七樂章的管弦樂作品,從此開始了他在歐洲的音樂職業生涯。他的音樂融合了東亞與西方傳統古典音樂。 之后在德國成為了十二音體系的領軍人物。
1965年,尹伊桑的頌佛宗教劇《唵嘛呢叭彌吽》(Om Mani Padme Hum)得到了巨大的反響,并在1966年與BEAK交響樂團在德國多瑙埃興根音樂節的首演上獲得了空前的成功。1967年,尹伊桑因牽涉到東柏林間諜事件中而被韓國派來的特工從柏林押送回漢城(包括他的妻子和當時一些在西柏林的韓國留學生),并被冠以了判國的罪名,一審判決為終生監禁。后來由于斯特拉文斯基和卡拉揚帶頭的200多位藝術家共同簽署的請愿書遞交韓國政府,考慮到國際主張問題他于1969年被釋放,并終身不得返回韓國。隨后,尹伊桑回到柏林,并于1971年加入德國國籍。
尹伊桑先于漢諾威音樂學院任教一年,1970年至1985年期間又在西柏林藝術大學擔任作曲教授。尹伊桑不僅吸取了大量歐美現代派的技巧,另一方面也極力表現東方文化,尤其是道家的一些思想,他的歌劇很多取材于中國古典文學。他一生共創作了近百部作品,其中包括4部歌劇和一定數量的管弦樂作品。1980年他創作了四部相互關聯的標題交響曲,并且在這一時期他的音樂在對于刻畫形象上更注重協調、平和。與此同時,他也參加一些國際組織和聯合國會議致力于呼吁韓國民主化、和解朝鮮半島以及國家統一等政治問題。[1]
尹伊桑于1995年11月3日在柏林去世,在他去世后他獲得了榮譽公民的稱號,并且還獲得了各類藝術學院及藝術協會頒發的榮譽獎項。后人為紀念尹伊桑把統營當地一條街命名為“尹伊桑街”,并每年舉辦統營國際音樂節。
二、《現代長笛練習曲》的技法特征
1.關于《現代長笛練習曲》
尹伊桑《現代長笛練習曲》是一部由五首練習曲組成的長笛獨奏曲。此集于1974年5月5日寫作完成。整部作品使用了最常見的四件長笛樂器,分別是長笛、短笛、中音長笛和低音長笛。其樂曲總時長為23分鐘。
以下是每首的速度與樂器的具體說明:
以上是對于練習曲中的一些特殊演奏技法的一個歸納,作者不僅僅在長笛技巧上引用新的演奏法進行大膽突破,更在力度與音色上著力體現長笛的不同變化,下面將以第五首為例,進一步分析作者在創作上的突破。
三.《現代長笛練習曲》第五首的演奏
雖然是長笛的練習曲,但它的層次非常分明也可作為單獨的樂曲使用。樂曲由4 / 4拍組成,從速度上大體分為快、慢、快三個部分,如下圖:
第一部份,每小節一拍等于86,速度較快,見例1(前三小節):
在音樂表現方面主要是從ff逐漸力度加強,同時音樂的密度也逐步的加強,處出現連續的7連音,如此增加了音樂的緊張度。樂曲的樂句并不規整,但非常分明,使得演奏者能準確的劃分出呼吸的位置。在第一部分中主要音域在小字二組以上,因此,主要考驗演奏者氣息的控制。
第二部分是每小節一拍等于72,速度較慢。作者主要意愿是與之前的部分在音樂上形成對比,因此在演奏者表現此段落時,氣息已經不單單是控制而是最大限度的拉長。力度一直保持在中弱的位置。讀譜可發現,在第二部分的音樂最密集處也只是出現單獨的8連音,
相對于前一部分更加的平靜,給聽眾一種緩和的感覺。這一部分的音域跨度非常的大,最低音在小字一組,而最高音則達到了小字三組,其中跨過兩個八度,并且在69—70小節還是使用低音的泛音。見例2。
因此,氣息的把握就不能太過于死板,要自然的過渡過去。
第三部分每小節一拍等于86,速度回到了第一部分。第三部分其實是第一部分的發展,通過讀譜便可發現它們在音樂材料等各個方面都是一致的。不同在于,第三部分的音域較第一部分更廣,基本使用了長笛所有的演奏音域,并且在力度上也是大幅度使用p—f—fff的跳進加梯形力度,再加上所有上行的音階,使得音樂更加積極,給人以前進的感覺。特別注意是在110小節到結尾處,音樂基本為長音,但力度卻在做很明顯的變化,要控制好音量,自然的收尾,直到以pppp的力度結束音樂。見例3(第110—116小節)。
在整首練習曲中最難的地方在于使用顫音時的氣息控制和使用氣息對于顫音頻率的把握。在長笛演奏中顫音的運用是至關重要的,它起著表現與豐富樂曲感染力的作用。如同一位歌唱家在演唱歌曲時,沒有了優美的顫音做尾墜,就無法表達歌曲的思想情感和樂曲的深刻內涵,同時從聽覺上來說也是平淡無奇的,回樣在樂器的演奏中亦是如此。在此曲中演奏者最該注意的是使用顫音一定不要用氣波動過于繁密,這樣會使得音樂在視聽方面顯得特別零碎,沒有整體感。
“我們作曲家沒有必要單純的去追求歐洲音樂的創作形式,而是必須尋找自己的音樂源泉。在歐洲音樂中不可能的事,在亞洲音樂中卻存在著。”①德籍韓裔作曲家尹伊桑將東方思維與西方現代技法相結合獨創“主要音技法”從此站上20世紀歐洲現代音樂的歷史舞臺,主要音技法便是源自于《易經》中的“道”。他曾說:“我的音樂與“道”的思想有密切聯系,不懂得“道”,就不可能了解我的音樂”。② 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中我們得知萬物是由“道”演變而來,萬物不論如何演化,其中都存有最原始的“道”,是萬物的本體。換言之,一切的變化都基于最初的“道”。這種觀念也被滲透到尹伊桑的音樂創作中,他的作品中以單音為核心,都以促成單音的不斷延伸為目的,他說:“一個單音,再加上一些演奏標記,就是音樂”,被稱為主要音的單音在延伸,而一切縱向或橫向的變化都源于這種靜態單音之上。這是道之“不易”。見例4。
第五首的開頭第一句,我們通過對尹伊桑“單音”的認識,可以清晰的將這一長句簡化為兩個音:e1和d3。而再看節奏型分配,4 / 4的節拍中最長時值是6拍,最短時值是1/32,如此對比的節奏型剛好順應了作者“單音”理念。
“歐洲音樂中的裝飾是通過瞬間促動來加強個別的音,而我的音樂中的裝飾則是半小節、兩小節,等,我稱之為“環繞”,目的是使單音再次出現更為之生動”②所以,在剖析作品時,我們應當做得就是看到其中的“本源”。演奏時心中要始終有本體單音的存在。誠然,演奏者在練習時需要將裝飾部分慢練,只有慢練才可以達到最終的服務于單音的烘托效果。并且仔細觀察密集節奏的音群,也可以找到主要音d3,所以演奏者應當時刻把握住“單音延伸”這個理念。
尹伊桑對于“道”的研究還延伸到了對中國書法繪畫領域。所以,這“道”也可“變易”。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任何事物都存在陰陽兩極矛盾體,兩部分相互作用使得萬物處于不斷變化和運動之中。靜中有動、動中有靜這是道教中的陰陽學說,它使得亞洲的音樂有著更為廣闊的天地。以一個音為中心,形成一條線型結構,這個線條不斷向前發展,不斷出現裝飾音,樂句中的強與弱,長與短,快與慢,以及運動與靜止。
“一個單音出現的音高變化,不常被看做獨立的。構成旋律的音程,倒更多地被看作對這個音的裝飾,看作這個音的一部分……人們可將我們的音調與書畫筆法做一比較。每個單音從起奏到消失,都富于變化,即裝飾。倚音,滑奏,力度變化等等都被有意識地獨立表達方式加以運用”。②
在第五首中,富有音響效果的旋律,每一個小節以至于每個音都有音響力度的變化,更值得一提的是這句將尹伊桑的“單音”理念表現的淋漓盡致,一個單音上我們感受到了衍生,即興、音響和音色對比。這種技法就好似中國書法中:石濤先生的“一畫論”,雖為一筆,但這一筆也是自始自終血脈不斷瞬息萬變。藏匿著無限的生命“一畫立而萬物著矣”。
對于這種在力度,技巧上都有緊密要求的樂句,我們需要頭腦清晰,顧大局,抓重點,不僅在練習時要將這些裝飾技巧把握清楚,在演奏時也要能夠隨時進入狀態完成每一步的音樂效果,由慢到快,由平坦到音響上的跌宕起伏。見例6。
觀察這一段的力度符號,要求做到的力度比較密集,并且一直在出現fff,所以我們在演奏時需要將音響的起點與終點的對比幅度表現出來,而在復雜節奏中,40小節第四拍的節奏型也是尹伊桑比較喜歡使用的主要音關系構成的裝飾性素材,包括41小節的第二拍也是使用了顫音裝飾主要音,通過這種方式構成了由主要音到裝飾性素材的轉變。主要音決定線條,而裝飾性音符則與主要音形成鮮明的對比,在對立統一中形成豐富的旋律樂句。
例7是該曲中一個困難片段,之所以困難,是因為需要使用單旋律樂器演奏和聲音符,雙音加上花舌再加上滑音還有力度變化,這對于演奏者來說確實是一個頭疼的事,尹伊桑說:“如果一個音響聽起來很渾濁的話,這說明音樂中不僅僅有旋律和節奏,音響本身就有一種力量,因此沒有明確的旋律結構。旋律線什么時候向上運動,什么時候向下運動,這一切只能是作曲家的想象和直覺,在聽我作品時,你必須抓住這點,這樣你就不會混亂了。”①
那么,我們再來看這段復雜的旋律,我們是否可以將它簡化成a2—#c3—bb2—a呢?然后,我們再在這組單音上加上花舌,用低音的指法再加上花舌,找若隱若現的高音,最后加上滑音。身體上作出的是這三個步驟,而腦海里我們需要時刻哼唱單音,要知道,作者是在主要音上加花,而不是為了花去譜曲。我們只有在牢牢把握主要音以后才能更準確的予以修飾。“這不僅僅是表現力度的,用這些可以寫出奇妙的音樂,主要看你用什么樣的深度來敘述,來表現,甚至你故意戛然而止,也能引起聽眾的想象。我的音樂就是用了這種方法,他們就像中國書法中的枯筆一樣,這枯筆中蘊藏著巨大的,藝術上的含義。”①
例8是該曲的結尾,pppp的力度作者試圖營造余音繚繞不絕于耳的意境,演奏在不同音域內的C,再一次的體現音樂之根本“一”。根據旋律線條,C1顫音流向C1單音同步出現C2的泛音,最后滑向在C3的泛音以制造虛無縹緲的意境,所以,需要演奏者精準的把握三個步驟的音色以及氣息控制做到自然的收尾。
尹伊桑在西方文化下尋找新的創作路程中,不僅加入了韓國傳統民間音樂的元素,還通過對中國古代哲學,美學,書法的認識予以應用于其作品中,正如他所說“朝鮮傳統音樂中沒有和聲,沒有對位,也沒有結構上的透視,只有單音,它是靈魂,必須做出最大的努力使之得以持續不斷地延續下去……”①
結 語
尹伊桑的《現代長笛練習曲》最大的特點是它在力度上強弱對比,節奏上有張有弛。其音樂的強弱對比,在此曲中一般使用以下兩個方法來演釋: 其一,使用傳統演奏方法,用氣息來改變音樂的力度,表現出極強和極弱的差別;其二,使用現代技法,卷動長笛在調整音高的同時也能使音樂有中強或中弱的小幅度對比(主要用于樂句結束時)。因為強弱較多的變化,故而,以上兩種演奏方法應該穿插使用,據譜面記號改變其演奏方法。
尹伊桑的《現代長笛練習曲》在音樂上的松與緊對比,是從兩個方面可以反映出來:其一,在于音的時值的運用,使用頻率最高的在于6拍的長音之后緊接一組7連音;其二,高低音的運用,一般都是低音之后緊接高音,并且一般情況是低音時間較長,而高音體現在它的密集度。這一高一低,也反映樂曲松與緊的對比。
尹伊桑作為韓國偉大的作曲家,為音樂的發展史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的作品是用西方的寫作手法表現出民族內涵。他的這首長笛練習曲具有樂曲所具備的所有必備條件,音樂完整,具體,極具有表現力,無論是在視覺還是聽覺方面都具有巨大的沖擊力。對于演奏方面,此樂曲為長笛在演奏技法方面填補了空白,也給長笛演奏者在力度,速度,氣息控制力和手指靈巧度方面提供了更大的表現空間。
注釋:
①轉引自:朱紹武《尹伊桑先生論音樂創作》,載《音樂藝術》1987年第2期。
②轉引自:羅新民《主要音透視——尹伊桑音樂創作的觀念與技法研究》,載《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7年第1期。
[參 考 文 獻]
[1](英)肯尼迪(英)布萊恩編,唐其競等譯.牛津簡明音樂辭典(第四版)[Z]. 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
[2]道德經·第四十二章[M].
Isang.Yun's modern Flute Etude Fifth performance and research
XU Ge
篇7
一個民族音樂學者對學科前景的思慮
像往常一樣,大多數論文宣講都是報告自己近年的學術研究成果。然而,在第二天的大會研討中,美國加大洛杉磯分校提姆西·賴斯(Timothy Rice)教授卻以《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 in Times of Trouble)為題發表講演,對民族音樂學的走向表達了自己深切的思慮。他在回顧了從越戰時期到目前的全球一體化和經濟衰退始終處于亂世的45年研究生涯之后感慨地說,大概只有15年的研究相對而言是有成效的。他于是提出了“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是否要改變研究方法”、“我們對音樂本質的理解是否能夠對那些問題重重的地方有所幫助”和“亂世中的民族音樂學如何影響我們對音樂本質的理解”三個關鍵問題。他的結論是:
第一,在社會和經濟總體上不平等的條件下研究音樂會導致民族音樂學家們重新思考他們的研究方法,從而把知識結構從縱向轉至橫向,而橫向知識要在各社區及社區音樂家們都處于平等的伙伴關系前提下創造;第二,民族音樂學家對音樂本質的認識和對音樂在人類社會中的能動作用的理解可以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法去幫助社會教育項目和政策的創新;第三,行動的>中動在實踐上有賴于社會語境,而民族音樂學家們在自己國家工作所產生的沖動應該比在國外更強烈i第四,人們可能利用音樂做好事,也可能利用音樂做壞事;第五,在有麻煩的地區從事音樂研究已經引起了對某些民族音樂學家們所聲稱的音樂自身可以改變和建設新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理解的懷疑;第六,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音樂研究可能促使民族音樂學家們朝向那些音樂仍在實踐著、音樂的本質仍是可以認知的聲音領域作進一步的研究,或者說,這種進步可能引導我們走向另一種民族音樂學;第七,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的音樂研究可能對縮小我們的領域中現存的理論研究和應用研究之間的裂痕有所幫助:第八,在亂世和有麻煩的地區從事的音樂研究可能引導我們走向有關音樂本質的新理論,而新理論的“鍛造”,正如安東尼·西格爾所說,只能出自于“行動的坩爐”。
眾所周知,賴斯教授從年輕的時候起就敢于向權威挑戰,并且在上世紀90年代成為西方民族音樂學的領軍人物之一。他用含蓄的話語所提出的尖銳問題和有前瞻性的看法代表了嚴肅的西方民族音樂學家們對民族音樂學研究目前所處的困境和今后走向的思考。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學者可能不會像賴斯教授這樣“候鳥”般地發聲。他這種始終保持著學者的批判精神和社會良知的品質是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的。
在小組發言中,筆者聽到國內學者們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繼承、保護和發揚的關注。質疑之聲集中在兩點:第一,近期在舞臺上表演的“原生態”音樂是否真正原生態,或者在質量上是否能代表某個原生態藝術;第二,國家認證的“非遺”品種和傳人是否被地方把持變為旅游資源,而真正創造和繼承這種遺產的普通人群卻與他們的傳統音樂生活剝離,得不到關注。據筆者看,我國近十年來所進行的“非遺”申報和保護工作成果還是相當可觀的。處于社會邊緣的地方音樂和少數民族音樂從幾乎自生自滅到“非遺”遍地開花是一個成績巨大的起步,有了這個起步才可能優化提高。質疑的第一點是個“如何做好”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當然要從學術角度爭論,但更重要的是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去行動。例如,對“原汁原味”的保存應當通過立項的方式組成由民族音樂學家為核心的專業化攝制組在源頭采錄樣品,制成具有公共產權的音像產品,形成定格,藏之于民。而原生態音樂在民間的保存,則應當允許和鼓勵一定程度的加工,成為舞臺表演藝術,參與旅游文化的競爭和國際巡回演出。否則,沒有發展,就不可能存活。當然,“加工”的方法可能良莠混雜。這次大會的第二場音樂會,是來自云南省民族藝術研究院昆明藝術職業學院表演的云南多民族原生態歌舞專場《彩云之南》。看得出來,這場演出的策劃者和編導是從舞臺表演的需要出發精心篩選節目的。每一個節目代表一個民族或地方的歌、舞、樂精華,總體安排上又有體裁形式的相互配合,情緒上起伏跌宕,從始至終扣人心弦。歌、舞的伴奏只用幾件民間樂器,毫無添加;舞蹈和多聲部合唱有一定編排,但動作和唱法絕對原生態;服飾也有為舞臺整體形象需要的加工搭配,但絕無矯揉造作。在舞臺上,我們看到老翁老婦,也有娃娃;有“非遺”傳人,也有正在學歌習舞的學生。從包括幾百名國內外民族音樂學家在內的觀眾反應上看,這場演出在四場音樂會中最震撼人心。這樣的精彩演出相信在其他地區也有。這證明如果把原生態音樂打造成感人肺腑的經典性舞臺藝術精品也是一條通途。至于質疑的第二點,也正是賴斯教授所說的音樂可能用來做好事,也可能用來做壞事。這是在歷史進程中不可避免的現象。所以,他意識到要改變民族音樂學研究的方向和方法,把縱向的理論研究和橫向的應用研究結合起來,并且要積極行動,以期對時代的進步產生正面的影響。
迎頭趕上的中國學者們
作為國際會議的東道國,上海音樂學院為會議的組織和服務做出了極大的努力,而直接受惠的是國內學者。這使得各大音樂院校、地級的音樂院系甚至自由學者和研究生們都有機會參會宣講論文。這是國際傳統音樂學會繼2004年在福建師范大學召開的第37屆世界大會之后的第二次,可謂機會難得。總的來說,我感到中國的民族音樂學者們正在意氣風發地迎頭趕上,宣講論文與國外同層次論文比較毫不遜色。
年輕學者們大多就自己的課題描述一個民間曲種或一種音樂現象的個案。其中,青島大學音樂學院祁慧民的《五音戲音樂發展軌跡研究》給我的印象深刻。她描述了一個地方曲藝小班子如何通過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傳統劇目走向衰亡的大趨勢中崛起,終于脫胎換骨,發展成有聲有色的大戲的成長過程。通過她的描述,我們了解到山東五音戲的崛起有兩個重要因素:其一是最初的五人(山東話“人、音”同聲)執著地在自己承傳的傳統上不斷吸收其他劇種的長處發展壯大,特別是在唱腔和劇目上豐富出新,同時廣納人才,表現出十足的自信、自立精神。從演示的音像看,他們的形式是傳統的,觀念是現代的,未必成熟,但不保守,具有潛力。這是五音戲能夠崛起的內因。其二是地方政府的支持,使劇團能夠借助國內一流專家的協助提高舞臺表演藝術質量和擴大演出面。這是外因。這個課題抓住了現時社會的脈搏,敘事簡明清晰,在文化承傳和戲曲發展兩個方面都具有典型性,表現出作者的學術眼光。盡管在限時的宣講中我們不可能看到五音戲發展軌跡的全部細節,也沒有聽到作者對這個發展過程更深入的理論性探討,但如果繼續追蹤下去,加深機體解剖式的綜合研究,可能是一部有助于民族音樂發展的力作。
中年學者的論文表現出了研究的深度。如香港中文大學Tse Chun Yan教授的論文《古代中國音樂的半音五聲音階:歷史音樂起源的實證研究》提出了“半音五聲音階”的概念來解釋用“三階”理論很難厘清的半音變化現象,是企圖超越歷史上的正統觀念而以當代的實證研究重新解釋傳統音樂理論的可喜進步。美國Kenyon College(肯楊學院)的韓梅博士的論文《“聲”和“音”:傳統中國箏的美學體現》提出箏演奏的右手撥弦產生“聲”而左手按壓產生“音”的看法,是對上世紀90年代出現的“聲、音語義分離論”的一種延伸,也不啻是一種佐證。但“聲、音語義分離”目前只是一種說法,是否可成定論,還需要從漢語語義、音樂史學和文獻學等方面繼續論證。華中師范大學臧藝兵教授結合師范專業的論文《鋼琴教育和暴力:中國鋼琴教育中兒童受暴力現象研究》觸及的也是一個帶有普遍意義的橫向論題,應當引起重視。上海音樂學院趙維平教授的論文《由敦煌琵琶譜的解釋引發的對古代音樂復原的思考》回顧了古譜破譯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難以超越的困惑并提出一些建議。在大會第三場音樂會《東亞之夜》的后半場,首演了上海音樂學院葉國棟教授的新作《唐朝傳來的音樂》。這部為亞洲樂器群(古琴、玄琴、牙箏、三味線、三弦詩琴、杖鼓、3篳篥、2笛子)、女聲合唱、管風琴和4管交響樂隊而作的音響宏大、構思精細的交響曲引用了畢鏗譯譜的唐樂《酒胡子》作為主題和交響發展的素材。據作曲家考證,這個譯譜是“具有唐朝音樂特征而遺傳至今的”(引自節目單)。我們從交響曲中部由遠而近的主題陳述中也確實聽到了比早期譯譜更加順暢的古樸曲調。這說明,盡管國內的古譜學研究步履艱難,從世界范圍看,古譜破譯還是有進展的,并且得到了應用。畢鏗的譯譜為什么相對較好,值得我們深思。
在大型學術會議上由資深教授帶領研究生或青年教師參會是~種傳統。來自不同國家的這種團隊一般把論文集中在教授主持的課題之下,從不同角度強調同一個主題。如韓國漢陽大學權五圣教授的團隊把論題集中在朝鮮音樂傳統中的“神明”觀念;福建師范大學王耀華教授的團隊在《旋律結構、族源與移民》的題目下論證了用“腔音列”形態分析作為移民遷徙和族源認證依據的可能;臺灣國立大學的團隊則把焦點集中在內地不太熟悉的作曲家周蘭萍的工作與生活軌跡上。東亞國家由于文化語境差別在國際交流中有巨大的語言藩籬,適當地組成團隊參會不失為一個過渡性的好方法。
觀念和方法的更新
通過這次大會,筆者認識到更新觀念和方法,使我們的闡釋在國際論壇上表達得更有說服力,獲得更多的話語權,是我們應當重視的改進方面。人們常常誤以為生吞活剝時髦的詞語或跟著國外某個時髦潮流跑就是觀念和方法的更新,其實不然。沒有學術定力和敢于為天下先的首創精神,“更新”的追求可能顯得很幼稚。比如,同是以“樣板戲”為研究對象,香港浸信大學John Winzenburg的論文《“樣板戲”音樂戲劇實驗:以(長城)為例》和美國肯塔基大學Yawen Ludden的論文《將理論納入實踐:于會泳及其現代京劇(杜鵑山)》從舞臺表演和音樂本體研究出發,探討其繼承、革新和融合的經驗。但也有脫離具體分析,僅以西方歷史學家的觀念為“準繩”做泛政治化的評論。兩相比較,哪個更具建設性,更有利于音樂文化的積累,是很清楚的。
在研究方法上,進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學性,用最現代化、最有效的手段使我們的學術成果產生最大的社會效益應作為我們的目標。在這方面,丹東市文化局劉桂騰研究員的文獻片《諾敏河的降神人——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薩滿祭祀儀式音樂》率先邁出了可喜的一步。這部30分鐘的HDV高清晰文獻片的全部素材由包括主持者在內的兩名攝像者于2009年8月在內蒙古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尼爾基鎮西博榮村拍攝。鏡頭角度的選擇、畫面的轉換、景深的調配、音響的清晰度等都令人滿意。后期制作也相當專業化。這部影片記錄達斡爾族薩滿降神儀式,包括主祭大薩滿、升級薩滿和培訓薩滿三個人物的神靈附體過程,從清晨曰出之前到日落之后,時間相當長。那么,如何在現場抓拍足夠的素材和如何通過剪接使所有的細節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展示,就是關鍵。另外,對一個宗教儀式的記錄必然牽涉到人物、器物、事件和樂舞等方面,如何分配鏡頭也需要精心構思。據筆者的粗略印象,此片對樂器、祭器、服飾的介紹多用短鏡頭和短鏡頭推拉組合。片中的人物是分主次的,以大薩滿和陪祭薩滿的長鏡頭為主,但在大薩滿冗長的一句體歌宣唱中用音像分離的辦法穿插信眾頂禮膜拜或其他事件的場景。對祭祀過程的記錄按順序從日出之前樹“托若”(魂靈通天神樹)開始,經過祭敖包、備祭、祭天、神靈附體、信眾酬神祈福、祭牲,到傍晚祭黑羊結束,交代得十分清楚。劉桂騰在影片放映前有一句令筆者震驚的話,說他把這部文獻片看成是一個民族音樂學家對研究對象的不同于文字版本的“轉述”。這就是說,音樂民族志的學術文獻片是一種用音像手段表述的學術研究成果。在目前高清晰錄像機比較普及的情況下,以經過錄像技術訓練的民族音樂學家團隊協作錄制準專業的田野調查現場實況,會大大提高我們在國際會議上的表達效果,也有益于對民族音樂志資料的保存積累。據筆者看,這部影片還可以在保留所有鏡頭的前提下再剪接得更干凈、精細一些,效果可能更好。畫面下方的文字提示很簡潔,不吸引觀眾的注意力,但由于沒有配音解說,信息量顯得不夠。對不了解薩滿文化的觀眾來說,如果把儀式的主要項目包括薩滿宣唱的歌詞大意都用簡約的中英文字幕顯示效果可能會更好。片頭畫面深邃,字體莊重,有文獻片的嚴肅感。但標題出現兩次,似無必要。如果第一次出現長度加5-10秒,刪除第二次,可以給觀眾更充裕的時間閱讀引言。田野文獻片的好處是只要現場素材抓拍得好,后期制作可以反復修改、精益求精。在我所見的此類影片中,曼特爾·胡德1964年在加納用8毫米單機采錄和制作的黑白電影《會說話的阿通龐神鼓》在攝影、編輯和解說等各方面都是典范之作。中國民族音樂學者能夠奮起直追,令筆者刮目相看。希望劉桂騰先生對此片再做錘煉并將經驗與大家分享。
意外的收獲
篇8
>> 電影《成吉思汗》的文化人類學研究 文化人類學的身體動作研究及其對體育人類學的啟示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開啟傳播學研究的新視野 社會文化人類學的語境問題 文化人類學的危機及其解決路徑 賞析《故鄉》中的文化人類學 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民間情懷 圖像與文化人類學的結合 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儀式”探究 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中國物質文化研究 文化人類學中的性研究及其在華語世界中的表達 民族傳統體育的文化人類學研究計量分析 文化人類學視野下的貴州少數民族票據研究 “雙軌水利”:農村水利運行機制的文化人類學研究 廣西南丹那地村“地牯牛”運動的文化人類學研究 以文化人類學視野論旅游文化 佛教儀式音樂的文化人類學研究及對心理影響的價值挖掘 文化人類學視野下邊遠地區教師繼續教育的主客位研究 從文化人類學視野考察民俗新聞傳播學的構建 花鼓起源:文化人類學視角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
[4] 樸一根. “拔河也被韓國搶占”――拔河登載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中國不高興了[EB/DL]. (2015-12-03) [2015-12-07]. http://.
[5] 任章赫. 傳統體育拔河的歷史[J]. 韓國體育學會會刊,2009,14(1):105-115.
[6] 樸開洪. 韓國民俗學概論[M]. 首爾:螢雪出版社,1997.
[7] 金光彥. 東亞細亞的游戲[M]. 首爾:民俗院,2004.
[8] 新羅時代的遺物,民眾的東萊索戰[N]. 韓亞日報,1938-01-05(01).
[9] 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38[M]. 首爾:民俗文化促進會,2006.
[10] 洪錫謨. 東國歲時記[M]. 首爾:民俗院,1989.
[11] 今村昌平. 民俗人類學體系[M]. 首爾:民俗院,2009.
[12] 國史編撰委員會. 韓國史料叢書?續陰晴史(下冊)[M]. 首爾:國史編撰委員會,1980.
[13] 崔永年. 海東竹枝[M]. 首爾:奎章閣,1925.
[14] 鄭觀海. 觀瀾齋日記[M]. 首爾:國史編撰委員會,2001.
[15] 封演. 封氏聞見記[M]. 北京:中華書局,2005.
[16] 韓國史料叢書?輿地圖書?補遺篇[M]. 首爾:國史編撰委員會,1980.
[17] 村山智順. 朝鮮的鄉土娛樂[M]. 首爾:集文堂,1992.
[18] 許龍鎬. 民俗游戲的全國性分布和農業性基盤――以拔河、摔跤為中心[J]. 民俗文化研究,2004,41(2):41-60.
[19] 六千名的大蟹戲[N]. 東亞日報,1921-03-21(03).
[20] 徐永錫. 重要無形文化財保存20年[J]. 國立文化財研究所,1984(17):364-386.
[21] 宋英柱. 我們國家拔河的體育考察[D]. 清原郡:韓國教員大學,1993.
[22] 表仁柱. 榮山江流域拔河文化的構造分析和特征[J]. 韓國民俗學,2008,48(11):299-332.
[23] 徐鐘源. 拔河性格的持續和變化――以近代櫓行[J]. 實踐民俗學研究,2011,17(2):157-190.
[24] 李昌植. 拔河的傳承和正月元宵節[J]. 韓國文化和藝術,2015,15(3):207-252.
[25] 張籌根. 關于拔河的研究[J]. 韓國文化人類學,1968(1):56-62.
[26] 蘇赫肅. 稻作文化性拔河的傳承研究[J]. 南道民俗研究,2011,22(6):135-167.
[27] 林在海. 歲時風俗[J]. 韓國民俗學,1990,23(9):285-308.
[28] 趙國華. 生殖崇拜文化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
[29] 何星亮. 中國圖騰文化[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30] 列維?布留爾. 原始思維[M]. 丁由,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
[31] 尹光鳳. 歲時游戲的性象征體系[J]. 韓國民俗學,1995,27(12):257-281.
[32] 何根海. 繩化母題的文化解析和衍譯[J]. 中國文化研究,1998,19(2):74-81.
[33] 蘇赫肅. 韓國拔河的稻作文化性格[J]. 農業史研究,2010,9(2):1-16.
[34] 任兆勝,李云峰. 稻作與祭儀:第二屆中日民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35] 魏征. 隋書?卷三十一?地理下[M]. 上海:漢語大辭典出版社,2004.
[36] 彭定求. 全唐詩[M]. 北京:中華書局,1960.
篇9
【關鍵詞】AKB48 日本偶像 商業模式 課題
AKB48其名字取自東京的秋葉原地區(簡稱Akiba),并在秋葉原擁有名為AKB48劇場的專用表演場地,以“可以面對面的偶像”為理念,幾乎每天都在專用劇場進行公演。廣義的AKB48指的是48系,包括AKB48、SKE48、NMB48、HKT48及海外分團,以及下屬小分隊及成員solo,制作人均為秋元康。
一、AKB48成立時日本經濟環境與音樂市場分析
自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以來,日本經濟都一蹶不振。就業率低,各產業經濟蕭條。國民的幸福指數也只減不增。
與此同時,日本的音樂市場更是不容樂觀。總的來說有一下五個特征。
(1)日本市場低迷,CD銷量年年下降,唱盤公司多有赤字,百萬銷量唱片已數年未出現。
(2)音樂商業化,縱觀銷量大盤幾乎都是商業化娛樂化十足的杰尼斯男團所創造。
(3)純音樂的沒落,主打純路線的大唱片公司GIZA的衰落是證明。已很難創造商業價值。
(4)女團沒落,歌姬時代結束,男團音樂獨霸天下,日本女團已無出頭之地。
(5)音樂周邊的崛起,手機鈴聲下載成為新潮,其下載量也是權衡歌手名氣的有力工具。
二、AKB48獨特的商業模式
(1)平民偶像路線 “可以面對面的偶像”為理念,秋元康致力于打造日本首個平民女團:①成員:不像韓國的少女時代那個個可愛靚麗,舞技超群的女孩們。AKB48的成員來自普通家庭初期大都是姿色平庸,無一技之長的鄰家妹妹。也正是其獨有的親民性;②面對面的商業活動:在東京秋葉原AKB48劇場,幾乎每天都會有演出,票價也僅售1000日元,相比杰尼斯的藝人演唱會的6000日元此票價甚是親民;③透明式曝光率:AKB48所屬的娛樂節目就有10多項,此外還參與電視,電影,廣告,寫真等多項活動。其成員還開設自己的微博,每天至少更新一天。
(2)一“禁”二“競”三“制”。一“禁”:禁止談戀愛,雖然粉絲群很廣,各階級層都有。但因為其粉絲大多是日本獨特的社會團體“宅男”,自己喜歡的偶像談戀愛,就好像自己被劈腿一樣。對宅男而言都是難以接受的。二“競”:兩種大規模的競賽。由于AKB48及其所屬各個團體人數眾多,出單曲或參與廣告宣傳必須選出代表性的少數。就誕生了以實力和運氣兩種形式的大型比賽。一是憑實力和人氣的一年一度的總決選,第二種競賽便是為了給新人創造機會,也有憑運氣來參加單曲,寫真等錄制的。猜拳大會。不論資歷人氣,只憑運氣。勝者便有更高的出鏡率。三“制”:三種制度,①“階級制”,仿佛金字塔一般站在塔頂或高處的只有那幾個人,沒有日本特有的按資排輩AKB48里只要你足夠有人氣,短時間內站在高處也是很有可能;②“淘汰制”,初期的報名成員會有很多,可到最后留下來的卻只是少數。“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在哪里都一樣;③“畢業制”,不像日本傳統的事務所,比如說赫赫有名的杰尼斯,簽約近似于賣身契。而AKB48卻是有畢業制度,當成員人氣與實力都能獨當一面,就可以單飛獨立。
(3)CGM(Consumer Generated Media)這也是AKB48最具特色的偶像文化,可以說也是其成功的關鍵所在。我們可以從AKB總選舉這,粉絲為了所支持的偶像,選舉海報的設計、應援視頻的制作到投票對策的籌畫。
(4)連鎖量販化AKB48不像是單純的少女的偶像工廠更像是大型的連鎖量販店,零售業。其企業宗旨也似乎是“你想要的總能找到”。大致可以分為一下四種特色:品種齊全,開架式經營,固定商店,連鎖量販式:①品種齊全,AKB48及其姐妹團體,成員人數超過300人;②開架式販售。這也是“可以面對面的偶像”的經營理念所在。AKB的握手會;③固定商店。2005年,AKB在秋葉原的唐吉軻德8樓建立了它們的專屬劇場;④連鎖量販式。連鎖商店。AKB、SKE、NMB、HKT,在日本總共有四個團體、四個劇場、四個店面,尚有海外的SNH和JKT。有時會做銷售慶典像是總選和猜拳,而賣得好的商品會放在最顯眼的位置,AKB顛覆了以往對偶像的概念,它就像是偶像界的UNIQLO,它賣得主要是服務,它的核心價值是顧客優先,它現在甚至透過Google+開始了它的網路經營。
三、AKB48商業模式的課題
(1)強壓快速下的CD制作,瑕疵盡顯。講到AKB的商業模式時比較容易忽略它的樂曲制作部分,并且AKB的音樂全都由秋元康一人全盤操刀制作。從2010年開始AKB的單曲發賣時間便相對固定,總結為六字:時間短,唱片多。常會發現詞曲與PV像牛頭不對馬嘴而舞蹈越趨如團康健身操一樣,對比其他團體精益求精力求整齊劃一的歌舞表現上,AKB猶如三流偶像團般讓人看直冒冷汗。
(2)畢業制度,人氣成員的離開造成大批忠實粉絲的流失。在AKB48發展初期,就導入了日本80年代紅極一時的小貓俱樂部的成員畢業機制,定期對成員進行遞補換血以保持其“新鮮感”是一種作法,但這樣的作法卻也帶來負面的影響,當成員離去時有些固有的支持者也可能一同離去而不再支持團體。
(3)海外市場開拓,前途未卜。目前AKB的海外市場,JKT48(雅加達)和SNH48(上海)都還只算是「基礎建設,相對韓國偶像工廠從十年前就開始不斷嘗試和布局東亞來說明顯有很大的差距,AKB要如何去補上日本偶像這段空窗期呢?
篇10
馬龍?白蘭度、伊麗莎白?泰勒不過是越來越老吧,鮑勃?迪倫可能只不過越來越瘦,U2的波諾仍像20年前一樣宏大而亢奮,貓王和列儂還沒來得及變就死了。
從《顫栗》短片里的狼人、僵尸,到《他們不關心我們》MTV里第三世界勞苦大眾的代言人;從《尖叫》MTV里的黑袍大佛,到《你并不孤獨》MTV里伸出雙翅的天使;從82年專輯封面上一身白西裝領口微張的翩翩少年,到95年為推銷《HiStory》而遍布歐洲的巨型塑像;從請求“永遠別說再見”的黑人童星,到終日躲在傘下顫巍巍地豎起“勝利”手指的白臉異人。那是恒動的變量、流動的奇觀!
但誰是邁克爾?杰克遜?
那個他曾經在歌聲中宣布要改變,并在現實中不斷變形的“鏡中人”[1]是誰?
先想想他的“永無鄉”(Neverland)吧。
1940年代梁實秋翻譯巴里(J. M. Barrie)小說《彼得?潘》時,對這一幻想之島的翻譯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游戲,在烏有中捉迷藏的故鄉,生活在別處的暗喻。
1988年杰克遜花了近2000萬美金從經營高爾夫球場的William Bone那里買下了“楓谷牧場”(Sycamore Valley Ranch)后,又搞了3500萬美金的“豪裝”――巨型的花鐘和維多利亞風格的火車站,從翻天輪、旋轉木馬到海盜船應有盡有的游樂場,兩條火車軌道和一盤卡丁車道,當然還有著名的動物園、爬蟲館、放映廳等等――把這里變成了歡迎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難的孩子們和他自己的“永無鄉”。一座童年永駐的孤島,或許是“永無鄉”最恰當的翻譯了。
其實早在1981年他買下父親的家族莊園Hayvenhurst的一半土地后,就把它改造成了一個自己的游樂場。杰克遜不止一次表示除了孩子,沒有人――包括他最親近的母親凱瑟琳――是無辜的,沒有人他能信任。這一次次似乎跨越了正常邊界的夢回童鄉的嘗試,哪能像六歲便不再長大的彼得?潘一樣永葆童真的近乎絕望的希望,不是偶爾重拾兒時游戲這樣每個成年人都有過的奢望,而是把自己日夜置身于各色蠟像的叢林中、將自己籠罩在童鄉中無盡地兜圈子的火車汽笛聲和旋轉木馬的叮當聲之中的一種近乎瘋狂的偏執。如果我們不先入為主地認定邁克爾?杰克遜是一個超乎理喻的怪物、一個孌童癖的罪犯――從沒有定罪過――的話,或許我們會想杰克遜到底失去了什么讓他這樣竭力挽回,那列幻想的火車駛向的地方到底有什么值得他這樣地向往?
那就想想他的童年吧。
不說那個整日在外面尋花問柳、在家里呵斥鞭打的音樂教練兼父親,不說摩城音樂(Motown)和老板Berry Gordy對杰克遜五人兄弟組(Jackson 5)的盤剝,就聽聽他那時唱的歌,看看唱歌時他的圓臉。9歲起隨父兄們在脫衣舞場獻技,10歲出頭就在著名的艾德?蘇利文(Ed Sullivan)的節目里向全國觀眾講授愛情的ABC。找來1968年杰克遜在父兄的指揮下模仿靈歌教父詹姆士?布朗名作《有感覺》的錄像,布朗“寶貝來寶貝去”成年火辣的歌詞,杰克遜痙攣一樣抖動的四肢,還有他那張稚嫩的臉,組成了一幅讓人無法整合的圖像。在Gordy的包裝指導下,11歲的他在兄長的伴唱中動情地講《要你回來》的故事:“那時你是我的,但你卻要我離開……再給我一次機會吧,現在我看你在他的懷中,我要你回來”。在蘇利文的電視節目里,梳著黑人爆炸頭的他精致得像櫥窗里的玩偶,他無比堅定自信又沉穩地唱《ABC》:“你給我坐下,女孩,我想我愛上你了;不,你給我站起來,女孩,讓我看看你能做什么。抖動吧,抖動吧(shake it, shake it),寶貝,來呀,抖啊”。這里的“shake it”當然指的是俚語“shake your money-maker”(抖動你身上賺錢的家伙事兒)。那時他12歲,變音之前,成年人幻想最安全的傳聲筒。
模仿不是所有娛樂的內核嗎?模仿成年人不就是大家希望在童星身上找的樂兒嗎?十來歲的邁克爾?杰克遜唱得像真的一樣,唱得像他明白一切,就如同他雙腿顫動得真像詹姆士?布朗一樣嫻熟。“小大人”是一個多么可怕的詞。在模仿中失去的可能是本來就不存在的東西,“永無鄉”怎么能回去呢?
1978年Gordy出品,Sidney Lumet導演的電影《綠野仙蹤》中,杰克遜主動要求飾演稻草人。受難者一樣被綁在十字架上的稻草人,哀求戲弄他的烏鴉們把自己放下來,不成。他只能像唱哀痛的福音歌一樣唱起《你贏不了》:“你贏不了,孩子,你連想打個平手都不成,你逃不出這個游戲,逃不出去。”那是越出劇情語境的一幕,帶著刺痛的現實感。那年他正好20歲。
1995年,杰克遜帶著時過境遷的豁然和悵惘,在《童年》一歌里唱“你們見過我的童年嗎?在對我品頭論足之前,請試著愛我吧,請捫心自問,你們見過我的童年嗎?”
不管杰克遜的童年失去了什么,他的童聲留了下來。一直到他面頰上的一切都在幻化騰挪,終日蜷縮在保鏢舉起的擎天黑傘,為自己脆弱的皮膚躲避無處不在的陽光之后,他說話時的聲音仍保持了一種怪誕的稚嫩嬌柔。當然,對很多人來說,這只是他畸異的又一佐證。1991年,美國動畫片《辛普森一家》第三季第一集中,父親霍莫因為穿了一件粉紅色的上衣去核電站上班,而被認為是“自由思考的無政府主義者”,送進了精神病院。霍莫碰到了同樣被押的一個自稱是邁克爾的禿頭童聲者,原來對現實生活的一切充滿憤怒的利昂只有靠模仿杰克遜兒童一樣的嗓音才能受別人愛戴,同時也被認為腦子有病。霍莫把這個邁克爾/利昂帶回了家,邁克爾幫沒心沒肺的兒子巴特譜了一首生日歌送給妹妹莉薩,然后哼著小曲走向了“永無鄉”。在美國流行文化中舉目皆是的關于杰克遜的玩笑中,這是我看到的最讓人心暖的一則。希望生活在別處,自己是別人,不是最普通的奢望嗎?一個曾經用童聲唱男歡女愛娛樂成年人的藝人,在中年后,仍偏執地“模仿”童聲,這倒真有些孩童般的狡黠吧。
再想想邁克爾?杰克遜的臉,那張曾經很黑,后來越來越白的臉,那張像傷疤一樣讓很多非洲裔美國人不愿提及的臉。
讓我們回到黑人歌舞第一次進入白人娛樂的初始,那里有美國最早的童星之一,那里或許才是討論邁克爾?杰克遜應該開始的地方,而不是從奧迪斯?雷丁、詹姆士?布朗,或戴安娜?羅斯談起。
按照約翰?斯特拉斯堡(John Strausbaugh)的說法,給白人展示“黑”作為一種有利可圖的行為從1441年在葡萄牙展覽抓到的西非人那時就開始了。[2]這似乎扯得遠了。近點說,1830年左右,聰明的白人喜劇演員托馬斯?萊斯(Thomas D Rice)帶著5歲小童Joseph Jefferson,用燒焦的玉米棒混著鞋油把臉涂黑,穿上農場黑奴的服裝,冒充黑人,連歌帶舞地把黑人歌曲“Jump Jim Crow”在紐約著名的Bowery Theater一炮打響,巡演全國。[3] 很快,一兩人搭檔的白人演員們――大多是底層勞工階級的愛爾蘭裔白人――隨身攜帶著炭棒,頻繁出現在高檔的白人劇場,也給普通的中下層觀眾,黑著臉上演了一幕幕想象黑色他者的歌舞劇。這便是所謂的“黑臉民歌模仿秀”(blackface minstrelsy)。這是美國最早的大眾娛樂,也是美國黑人文化在白人帶著一面黑臉的模仿之中進入白人消費最開始的形式。
當然如學者埃里克?羅特(Eric Lott)所言,這種“黑臉模仿秀”體現了某種白人對黑人文化既懼怕又著迷的矛盾,是一種“對黑人文化嘲弄式的歡慶”,[4]但故事還沒有結束。不出十年,到了1840年前后,黑人自己也開始加入到這種娛樂活動中來了。被認為能更“真實”地表現黑人民歌舞蹈,這些黑人演出隊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迅速走紅。吊詭的是,為了能更“真實”地反映“黑奴”文化,黑人歌舞者不得不也像他們的白人同事一樣,涂黑了本來就是黑色的臉,把嘴唇抹得寬寬的,演繹觀眾假想中的黑人。[5] 不管是按法蘭克福學派的思路把這種對他者模仿的流行文化看作是偽裝的文化控制,還是按霍米?巴巴關于“模擬”的后殖民思辨,在黑人對戲仿的戲仿中看到文化權力重心不動聲色的位移[6],無法回避的是,在黑人音樂文化進入白人視野的第一次假面舞會中,在對鏡像的鏡像的反復折射的過程里,那個鏡子外面“真實”的本源已經變得格外模糊。
當全世界最著名的黑人藝人的臉不斷變白――不光指膚色,還包括面部特征――的時候,自然有人想起了19世紀中涂黑了臉的白人模仿者,以及模仿白人模仿黑人又涂黑了臉的黑人表演者,并在這些minstrel演員和漂白了臉,墊高了鼻子,拉細了眉毛的邁克爾?杰克遜之間劃上了令人不安的聯系。這種表面得近乎殘酷的聯系,讓那個懷疑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右翼極端學者邁克爾?霍夫曼說杰克遜是“煉丹術式minstrel秀的白臉明星(whiteface star of the alchemical minstrel show)”,他還進一步指出,杰克遜不過是19世紀模仿白人模仿黑奴的黑人minstrelsy傳統的可憐延續。[7]對于大部分人來說,黑人的自恨自怨以及種族歧視的美國社會自然成了杰克遜漂白自己最簡單的解釋。[8]著名的黑人喜劇演員不是很多年前就開過這樣的玩笑嗎:“我不明白我們黑人干嘛還老跟杰克遜較勁,人家自己都不想當黑人了?”
很多美國文化史和流行音樂史的學者也都把邁克爾?杰克遜的現象追溯到19世紀的minstrelsy,不過不是因為變色的臉,而是因為身體的顫動。在早期的“黑臉民歌模仿秀”中,沒有樂器伴奏,偽裝的“黑奴”們像真的黑奴一樣除了自己的身體一無所有,只能靠擊掌、跺腳,扭曲身體,給自己伴樂伴舞,這也成了minstrelsy吸引白人觀眾的最重要特征。痙攣一般的舞蹈不僅是白人演出推廣者親自訂下的賣點,而且也是種族被規定出的表征,或正因此成為賣點。著名的音樂史學家德里克?斯科特(Derek Scott)在其專著《都會之聲》中斷言,邁克爾?杰克遜的根在minstrelsy,整個勁舞靈歌的傳統就是從minstrelsy開始的。[9] 蘇珊?威利斯更因此直截了當地說,“邁克爾?杰克遜就是‘黑臉’minstrelsy的化身”。[10]是否將杰克遜的“遠祖”具體到“朱巴大師”(Master Juba)[11]這樣的人物或許并不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在將“黑人歌舞”定義、包裝賣給觀眾的初始就已經包含了很深的跨族際的模仿與成見。這仿佛成了一個黑人藝人無法逃脫的甜蜜陷阱,舞步越激蕩越“真實”――杰克遜說過自己的“太空步”是黑人貧民區的小孩身上學來的――越有觀眾,但不也越是那個“蹦跳的黑烏鴉吉姆”(“Jump Jim Crow”)嗎?那面想照出自己的鏡子里會不會跳出涂黑了臉的Thomas D Rice的幽靈呢?
據說舞王弗雷德?阿斯泰爾(Fred Astaire)曾在電話里對杰克遜說,“你是一個憤怒的舞者。”或許為何而怒我們永遠不得而知,但他每一次在舞蹈中崩潰摔倒,又屈腿蜷身立在豎起的腳尖上時,總像一個人正絕望地想要掙脫身上那張無形之網,但又在突圍間落網。
杰克遜借那張越發變形的臉又在擺脫什么呢?
邁克爾?杰克遜的臉是現實主義的邊界。與那些怕自己不夠黑、怕自己不夠像觀眾想象的黑奴模樣的黑人minstrel演員學著白人模仿者再涂黑自己的臉不同,杰克遜不模仿只發明。那張臉真的像白人嗎?有人說,不,像女人,像他崇拜的戴安娜?羅斯。不,更像模仿女人的亞裔異裝癖。自然,也有人說,他最像混血的變性人。不,還有更好的,像太空節目里幻想出的外星人――他不是在“永無鄉”里擺了一個思鄉而哭的E.T.蠟像嗎?拉爾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在其黑人文學經典《隱形人》(Invisible Man)(1952)中說過:黑人最大的挑戰“其實不是創造出關于他自己種族的獨特意識,而是創造出一張他自己的臉,沒有別人雕琢出的特征的臉……我們通過發明我們自己,發明一個種族。”《紐約時報》資深文化評論員瑪格?杰佛遜(Margo Jefferson)認為邁克爾?杰克遜做到了這一點,“他沒有模仿我們所知的任何生命”。[12]當然瑪格不過重復了藝術家基思?哈林(Keith Haring)1987年日志里說過的話:“用整容手術和其他現代科技,邁克爾把創造權掌握在自己手里,發明了一個非黑非白非男非女的生命……他在美國流行文化中大搖大擺地招搖過市的同時,把上帝造物的終結權搶回到自己手里。”[13]或許有人會說從貓王、滾石樂隊到艾米納姆都不是過卸了裝的minstrels,但杰克遜似乎想穿一套沒人見過的行頭。
誰是邁克爾?杰克遜?
答案可能不會只有一個。
當然,他是最偉大的舞者、藝人,但決不僅此而已。
有人說他是黑人的背叛者,有人說他是超越了非黑即白陳規的“后種族”(post-racial)英雄,更有人說他是“跨族際后現代幻形人”(trans-racial postmodern shape-shifter)。[14]
他是美國第一個白人家喻戶曉的黑人明星,他是后冷戰時期最瑯瑯上口的全球化力量[15],他是對各地方身份具有無限塑形力量的跨國文化產業最柔韌的載體,[16] 但也有人說他不過是一個生活在舞臺上始終戴著面具的小丑。
杰克遜生前就一直試圖建立一個譜系,定義自己的位置――他買下了艾爾維斯所有歌曲的版權,在貓王的Graceland后修了Neverland,又娶了貓王的女兒為妻;他出價高過保羅?麥卡特西,買下了甲克蟲樂隊全部歌曲的版權。他想說自己是搖滾王族的嫡傳,但也有人說他是搖滾精神的背叛。1962年迪倫堅定地告訴所有反戰的年輕人“答案在風中飄”,1974年列儂充滿憧憬地吟唱“集體的夢想就是現實”。1983年杰克遜卻只是勸“無所謂誰對誰錯,算了吧。”[17]
或許我們只能知道他希望自己是誰。從91年專輯《危險》之后,當說唱樂和Hip Hop逐漸將他的地盤蠶食殆盡時,杰克遜成了全世界最成功的主旋律歌曲創作者。[18]不管是“為了我們的孩子,拯救這個世界”(《拯救世界》)和《地球之歌》里的環保主義,還是“如果你想成為我的寶貝,無所謂你是白還是黑”(《黑或白》)的種族和諧平等,抑或是高唱愛的圣歌的《你并不孤獨》,他是最宏大的敘事,最直白的現代啟示錄,一切天災人禍最后的救世主。斯派克?李說他是全世界的公民。不僅如此。他不是對Oprah Winfrey說過他想模仿耶穌嗎?他希望是最后的史詩,就像他本來要上演的巡回演出的名字――This Is It――所暗示的一樣。那和耶穌死前說的話一樣:“Consummatum est”[19]。
然后是最后的謝幕。
注釋:
[1]在1988年首發的單曲《Man In the Mirror》(后收入專輯《真棒》)中,杰克遜說“想讓世界變得更好,就先改變鏡中的自己吧”。
[2]John Strausbaugh, Black Like You: Blackface, Whiteface, Insult and Imitation in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Jeremy (Penguin, 2006), 35-6.
[3]這段歷史請參看Eric Lott 1993的經典研究 Love and Theft: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請參看Love and Theft: Blackface Minstrelsy and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的第一章“Blackface and Blackness”。
[5]請參看Robert C. Toll, Blacking Up: The Minstrel Sho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6]比如著名學者Sylvia Wynter就認為在minstrelsy表面的種族成見之下,黑人文化見縫插針,“給美國規范的資產階級現實帶來了文化顛覆”。見Sylvia Wynter, “SambosMinstrels,” Social Text, No.1 (Winter, 1979), 155。
[7]
[8]記得喬治科魯尼主演的電影《奪金三王》(Three Kings)(1999)里的臺詞嗎?一個伊拉克士兵對美國軍官說:“你知道為什么邁克爾要把自己的黑皮漂白、卷毛拉直嗎?是因為你們那個變態國家叫黑人恨自己。”
[9]Derek B. Scott, Sounds of the Metropolis: The 19th-Century Popular Music Revolution in London, New York, Paris, and Vien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70.
[10]Susan Willis, “Is There a Place for Afro-American Culture in Commodity Culture?” in Changing Our Own Words: Essays on Criticism, Theory, 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 edited by Cheryl A. Wall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90.
[11]原名叫William Henry Lane,踢踏舞的早期大師,因為膚色不夠黑,也被白人老板用炭條涂黑了臉表演。有學者把布朗、杰克遜等人的舞步追溯到這被1840前后流行的“朱巴大師”,見Brenda Dixon Gottschild, The Black Dancing Body: A Geography from Coon to Cool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15.
[12] Margo Jefferson, On Michael Jackson (NY: Pantheon Books, 2006), 98.
[13]見Keith Haring, Keith Haring: Journals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6)。轉引自Margo Jefferson (2006), 81。
[14] Margo Jefferson, “The King and Us,” Washington Post Saturday, June 27, 2009.
[15]Tarak Barkawi, Globalization and War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xii.
[16]Kuan-Hsing Chen, “Not Yet the Postcolonial Era,” Cultural Studies, Vol. 10 No. 1 (Jan. 1996): 52.
[17]見杰克遜《Beat It》的歌詞。
[18] 或許與其找杰克遜對中國搖滾樂的影響,還不如看看他和中國公益歌曲發展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