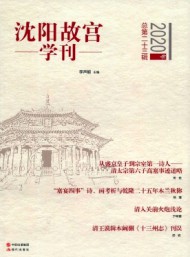清朝前期的文學藝術范文
時間:2024-03-26 16:48:5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清朝前期的文學藝術,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稅收作為國家的政治、經濟行為,能夠集中而深刻地反映國家與社會的發展階段、水平、性質。因此,領略中國稅收的歷史,可以從核心部位把握中國古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社會生活,以及兩千多年中國封建專制中央集權國家的興敗盛衰的運動過程,從而為參透中國歷史“迷津”,正確把握中國歷史傳統,提供一個明晰的新的視角。
夏、商、周( 西周) 三代的三種賦稅形態,史稱“貢”、“助”、“徹”。盡管形式上各有不同,但總的稅率大致都是十分之一,即所謂“什一而稅”。夏之貢近似于定 額課征形式;商之助和周之徹,均建立在井田制基礎上,前者為勞役課征形式,后者為勞役向實物課征的過渡形式。共同的特點是:稅率低,貢賦并重,租稅合一。它反映了在國家出現的早期階段,實行分封制政體,稅收的初級形態,也反映了稅收從自下而上的自愿形式向自上而下的強制形式的演化過程。三代時期的“工商食官”、“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到了西周后期,有了“關市之征”,即有了初始的商稅。
春秋、戰國時期,稅制改革成為各國政治經濟變革的重要內容。從魯國的“初稅畝”到秦國的商鞅變法――廢井田、履畝而稅,反映了土地由分封制步入國有制,由公共占有制到私人占有制,以及稅制由租稅合一進入稅人稅地的發展過程。隨著商品經濟的初步發展, “重農抑商”政策開始提出,加重工商稅,出現了國家專賣制度。
秦始皇建立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后,在全國范圍內統一了稅收制度,以“繁 法嚴刑”加以保證和規范。其特點是:
第一,通過土地登記和戶籍制度,“令黔首自實田”,標志著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確立。
第二,施行嚴厲的重農抑商政策,從而把農民牢牢地固著在土地上,確保國家田賦、兵役和力役的穩定來源,為中央集權的專制主義政體構筑了經濟基礎。
第三,實行“急政暴虐”的極權政治,賦稅達到橫征暴斂的地步,《漢書?食貨志》載云:“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制二十倍于古”,乃是秦朝迅即覆滅的重要原因之一。
漢代承襲和發展了秦朝的稅制,特別在重農抑商方面把秦制推向極致。在抑商方面,除苛征商人的關、市等稅外,從漢武帝開始,還對商人重征財產稅――“算緡”;施行國家絕對壟斷的鹽鐵專賣;國家直接經營商業、運輸業,稱“平準均輸”;加倍征收商人的人頭稅和其他附加稅,正如漢高祖《賤商令》所云:“重租稅以困辱之”。
在所謂重農方面,漢代雖然吸取了秦朝覆滅的教訓,強調“與民休息”、“輕徭薄賦”,漢高祖行十五稅一,漢景帝行三十稅一,而且終漢四百年而不改,但事實上,漢代施行的是輕田賦重口稅的政策。
漢代的稅制集中體現了漢武帝“外儒內法”的政略,把秦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體的稅制加以系統化、法律化、制度化,對之后兩千年的中國歷史產生莫大的影響。
三國時期,各國為解決軍餉和財政問題實行大規模屯田,并調整稅制。最有成效者當屬曹魏政權。值得注意的有兩項:
一為組織軍屯和民屯,把漢武帝始行的屯田制提到新的高度。官府和屯戶分配額為二五中分( 使用官牛的為分成),雖然退回到租稅混一的課征,但這一舉措卻使大批流民有所歸宿,回到土地上來。
二為實施“租調令”,把漢例三十稅一田租改為計畝定額稅;取消漢代人頭稅,改行按戶征收“戶調”( 戶稅),戶調開始成為常稅。
晉統一“三國”,在全國范圍實施占田、課田制和戶調式。即平民計口,規定男女人口可占田地畝數;計丁規定應征田租畝數;計資分等級規定戶調負擔。南北朝時期,北魏統一北方,孝文帝創行一體化的均田制、三長制和新租調制。均田制等舉措為北齊、北周承襲,并對隋唐兩代影響至深。
魏晉南北朝,北方商品經濟遭戰亂、少數民族政權割據破壞嚴重,而南方卻出現商品經濟的繁榮,南方六朝的工商雜稅成為政府重要收入之一。
隋文帝統一中國后,把北魏開創的均田制推向全國,并提高授田數量。在精減機構、裁汰冗員、減少國家負擔的同時,實行租調制,減免田賦徭役。更難能可貴的是,著力鼓勵工商――除山澤之禁,去鹽鐵之專利,免入市稅及鹽鐵等稅。重農抑商的傳統稅收政策得以空前馳放。在短短二十年間,經濟迅速發展,創歷代最好之財稅。馬端臨《文獻通考》稱 :“古今稱國計之富者,莫如隋。”個中奧妙值得深思。
唐代把中國古代稅收和稅制發展到更高階段。特別是唐初的租庸調制和唐中的兩稅法兩次稅制改革,對傳統稅制有著明顯的突破。主要有:
1. 從實物稅到貨幣稅的發展;
2. 從稅人到稅物、稅資的發展;
3. 徭役的賦稅化;
4. 商稅正式成為一項國稅,工商稅收占國家財政收入份額不斷增大;
5. 國家稅制統一,法律對稅收起了重要的保證和規范作用;
6. 確立“量入為出”的財稅原則,并根據經濟多元發展而采取了拓寬稅種、簡約稅制等措施。
所有這些,反映了自秦漢以來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已發展到成熟的階段,反映了中國古代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也反映了傳統重農抑商政策和非經濟強制對人身束縛的弱化。
五代和宋代的稅收基本上因襲了唐制。
宋代為防止五代十國割據局面的重演,把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推向更高階段,財稅大權一統于中央,標志著中國古代專制主義集權制國家財稅制度發展的高峰。
宋代把兩稅中的地稅和田稅劃一為以田畝為標準,人稱有田則有稅,無田則無稅,反映了當時土地買賣的自由和租佃關系的自由。
宋代大大拓寬了賦稅領域,了規范商業稅的《商稅則例》,設立了專管商稅的機構“商稅務”和專管外貿及進口關稅的“市舶司”。工商稅收躍為國家大稅,反映了商品經濟特別是商業外貿的空前發展。
宋代專賣項目繁多,但突破了官本格局而演化為官商合辦、官商共利的局面,也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充分發展使然。
宋太祖開始順應歷史潮流,實行“恤商”政策;而王安石新法雖有可取之處,但仍以陳腐的重農抑商為宗旨,把歷史拉向倒退,其失敗自是勢所難免。
宋代“生不逢時”,民族戰爭頻仍,內憂外患嚴重,軍費開支幾達稅收的百分之八十。因此,宋朝雖為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特別是商品貨幣經濟,以及與之相關的稅制發展變化最為迅速的朝代,但又是歷史上財政最為困難的朝代。以后幾代,在稅制方面雖有深度和廣度的進展,但并未見有質的方面的突破。
遼、金、元三代均屬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其稅制都表現為中原原來先進制度與游牧民族帶來的落后生產方式和政策的混合。
元代的官府和貴族、官僚兼并了大量土地。官田因戰亂、掠奪急劇增多。官田多實行屯田制,回到原始的租稅合一的課征形態,而屯戶事實上成為貴族與官府的農奴。私田因貴族、官僚以權占田而致集中,與宋代以錢買田而導致的集中,形成鮮明對比。元代稅收因地、因戶而異;政府為滿足財政急需,允許大戶包稅;重視商業,商人可享減免稅收或包稅等優惠。元朝稅收制度最為混亂,比唐、宋甚至遼、金都有明顯的倒退。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財稅上仍從清整戶籍、土地入手,先后實行“黃冊”和“魚鱗冊”制度,比較有效地解決了累代積存的土地和賦稅的混亂局面,增加了稅收。
明代中期,朝廷為擺脫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及財稅困難,先后推行過征一法、鼠尾法、 一串鈴法、十段錦法等稅制改革。萬歷九年(1581 年) 在全國頒行“一條鞭法”,將田賦、徭役和雜稅合并,按地畝征銀。它的簡約稅役、折銀征課,比唐宋兩稅法更加徹底,因而也更適應于商品貨幣經濟不斷發展的時勢。一條鞭法可以說是中國古代農業稅的至高形態。以后雖然有清朝的“攤丁入畝”,但也只在局部方面有所發展。
明代在財稅問題上,集中反映了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既極權又腐敗的特質。一條鞭稅法在維護和鞏固明朝專制集權統治上取得了短暫的“中興”效應,但無法改變專制國家江河日下的歷史趨勢。
清代的稅制以為分水嶺,分出前期與后期。前期沿著歷史傳統道路發展;后期因失敗、外國列強打開中國大門而被迫開始改弦易轍。
前期在稅制上最突出的事件為“攤丁入畝”。明代一條鞭法沒有徹底解決地丁合一問題,人丁和田賦仍是兩個稅目。清代經康、雍、乾三朝,攤丁入畝終于在全國鋪開,完成了地與丁、賦與役一統于田畝征銀的歷史任務。到此,兩千年來一直糾纏不清的稅人與稅地及人頭稅問題總算在法律上得以解決。一條鞭法和攤丁入畝制,應是中國古典稅制的終結。
明、清兩代都實行某種方式的海禁,清朝前期又實行礦禁,因而外貿稅收和工商稅收受到嚴重影響。這是對唐、宋、元開放政策的一個倒退。
后,稅制開始出現質的變化,走出一條似可稱為“中學為本、西學為用”的稅制變更道路。即舊的傳統仍保留著,但為適應國門被打開的局面,開始逐步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稅收的內容和形式。這種變動的主要驅動力是外國資本列強的侵入和強制,形成一種半封建專制半殖民地的稅制形態。
以后,清代稅收最大的變化是:兩千年來一直作為國家財政收入命根的田賦,在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急劇下降,逐步退為地方稅;而五口通商后新設的海關( 初稱“洋關”) 的關稅收入在國家財政總收入中的比例急劇上升,成為國家主要收入。從1842 年到清朝覆滅, 中國境內共設有60 余個海關。
稅收的半封建專制形態主要表現為,在標榜“輕徭薄賦”的同時,不顧百姓死活,以各種強制手段增加傳統的田賦、礦稅、鹽課、茶稅及各種工商雜稅,甚至采用借稅、厘金、義谷等手段橫征暴斂。
半封建半殖民地形態,在政治上主要表現為:海關自的喪失,不平等條約確定的“協定關稅”,以海關作為戰爭賠款和政府對外借款的抵押,海關管理權掌握在外國人手中等; 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不平等條約確定的海關低關稅制,進出口稅的失衡,中國人和外國人納稅的不平等……,從而為外國資本商品傾銷大開綠燈,嚴重影響中國工商業的發展。
當然,中國舊稅制的突破和對部分國外新稅制內容的吸收,也意味著中國開始走上與世界近現代稅收文明接軌的漫長之路。
中篇 中國古代稅收歷史的思考
檢視中國古代二十幾個朝代賦稅制度的因襲變遷,我們不能不為中國作為人類稅收文明重要發祥地,積累了四千年綿延不斷,豐富、系統、輝煌、完備的稅收文字歷史而驚嘆不已。但是,從歷史的長河看,四千年來稅制的發展,還是十分緩慢的。特別是唐宋以后近六百年間,稅收體制也和中國古代政治經濟的結構、制度一樣,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沒有質的重大突破,甚至更加保守、封閉、落后。這是值得深思的。稅收體制有古典體制和現代體制。現代體制是與市場經濟體制、科學技術普遍運用于生產領域、民主政治形態,以及自覺的納稅意識相聯系的。中國古代稅收屬于古典體制。
中國古代稅收體制的發展歷史,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發展過程的一面鏡子。從賦稅的國家職能角度而言,這種稅制可以定性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稅制。主要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稅收理所當然地是為滿足朝廷和皇室的財政需要。為了收稅,官府可以采取各種手段。征稅與納稅直接反映著統治與被統治、強制與服從的關系。
第二,這種稅制是由戰國時期法家提出,秦王朝確立的。法家主張國家至上、君主至上,主張“國富民貧”。漢武帝修正為“外儒內法”,道德倫理上宣揚儒家的“輕徭薄賦”,但實際上行法家的原則,總是賦斂不已。除正稅外,巧立名目征收各種附加稅。以后歷代統治者基本上都奉行“外儒內法”的政略。這種稅制的重要特征,是中央政府統攬財稅大權,沒有明確的地方稅,從而加劇了地方官吏的苛征苛派。
第三,這種稅制是以農業為基礎,把農民死死地固著在土地上,追求地產增殖的最大化,以實現國家對財稅和勞力需求的穩定性。它有強烈的人身束縛性和超經濟強制,稅田、 稅人常常攪和在一起。除田稅外,還有兵役、勞役、雜役等徭役,以及戶稅和人頭稅。歷代賦役制度雖有更易,但只是程度和形式上的不同。
第四,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往往還以政權為依托,壟斷商業、手工業、礦業、交通運輸等重要行業,其形式包括官工、專賣、禁榷、屯田、平準、均輸等,兼收利稅之益。可視為古代的國營企業和統購統銷政策。
第五,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的稅收體制,必然會出現專制而不能集權的局面。于是,嚴重腐敗現象就會出現。稅收中的腐敗是這種稅制的必然產物。
事實上,自有國家以來,土地國有觀念和國家對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是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傳統。它強烈地反映在稅收制度上,并制約著中國古代農業和整個社會經濟的發展。它的發展過程大致是:
首先,夏、商、周三代,是分封制下的土地宗族公共占有制。西周時期,國有觀念已然明確。有“詩”為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 可見,當時的輿論不僅認為土地屬國家( 最高統治者) 所有,而且臣民也屬國家所有。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在爭霸爭統中紛紛進行土地、稅役制度改革,其核心內容就是明確土地國有制――土地所有權歸國家、土地分配權歸國家。從“初稅畝”到“授田制”,從“廢井田”到“令黔首自實田”――這一史稱“土地私有化”的運動過程,只是終結了分封制下土地的宗族公共占有制,完成了從土地私人使用權到私人占有權的轉變。國家通過直接掌握土地,以保證對稅賦、兵役、勞役的征調。
再次,秦漢以后,“私有化”的進程更加迅猛。漢代的土地買賣已十分普遍,到唐宋及以后各代,土地自由買賣、自由租佃關系更一發不可收;地主經濟、自耕小農經濟成長為農村經濟結構的主體;國家對土地控制和對土地上民戶的人身控制日呈弱化;稅制的發展――從“兩稅法”到“一條鞭法”到“攤丁入畝”等,都反映了土地私有化的深入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對土地和土地上戶籍的控制也并未放松,表現出國家對土地的主宰權。歷代所推行的諸如“授田制”,“限田制”,“占田、課田制”,“均田制”及“方田均稅法”,開展的“削豪強”、“抑兼并”、“平賦稅”的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漢武帝通過“告緡”措施,就“罰沒”私人土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此 ”(《史記?平準書》),全國的總數更可想見;官府、貴族、官僚倚仗國家權勢強占民田,元代、清代入關之初實行“圈地”運動;等等。所有這些,都說明國家對公私土地具有“終極所有權”。而私人的土地所有權――從法權意義來說,還是有限的,不徹底、不完全的。
這種事實上存在的土地產權不明晰狀況,頑強地反映在稅收體制上,造成稅制不能適應經濟發展、產業結構變化的消極、被動、滯后的局面,從而成為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商品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土地國有觀念和事實上存在的國家對土地的終極所有權,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國家及其稅收體制運行的重要根據。
四、“重農抑商”是貫穿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經濟政策和稅收制度的“主線”,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稅收的基本特征和歷史傳統。
商業經濟發展的同時, 也帶來所謂社會分配不公和部分農民棄農經商的問題,使正處戰爭環境中的列國君主為之震驚。他們把工商業看成是對農業、對專制國家秩序的最大威脅。因為他們需要穩定的農業和農民,以滿足他們對糧草( 賦稅)、兵源的需求。于是,“農本工商末”、“重農抑商”、以及“農戰”、“輕重”的思潮洶涌澎湃起來,其代表人物是法家的政治思想家李悝、商鞅、李斯、韓非等。商鞅在變法中嚴厲貫徹了重農抑商原則,提出“不農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對不經批準從事工商業的農民,要罰作奴隸等;韓非更把工商業者指斥為國家“五蠹”( 五種蠹蟲)之一。
秦始皇在統一中國以后,把重農抑商(“上本除末”) 定為國策。漢代繼承秦制,全面實行對商人的“重租稅以困辱之”( 漢高祖) 的賦稅方針。“重農抑商”思想從此成為兩千多年經濟政策、稅收制度的一項基本原則。
“重農抑商”之“重農”,并不是重在農業生產和保障農民利益。商鞅是重農抑商的鼻祖之一。他主張的是兵強民弱、國富民貧,甚至要農民成為“家不積粟”的赤貧。漢武帝標榜“輕徭薄賦”,但實際是輕田租而重口賦,連三歲的孩子也要上人頭稅。“重農”之重在于把農民世代鎖定在土地上,重在穩定賦稅,穩定兵源,穩定極權統治。“抑商”是歷代王朝的常態。抑商的主要手段是:
第一,利用稅收作杠桿,“重租稅以困辱之”,這是經濟上抑商的最主要手段。漢代抑商最厲害,對商人的賦稅課征也最重。除市、關、資源等商業稅外,還要重課各種名目的財產稅 ( 緡錢稅)、雙倍的人頭稅及各種附加稅。又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錢”、宋朝的 “和買”,都是對商人的挖空心思的巧取豪奪。
第二,強力剝奪。一種是直接剝奪,如秦朝對商人。一種是類似稅罰,如漢武帝的“告緡”。有點像搞政治運動,發動民眾告發偷稅漏稅的商人,結果“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國家“得民財物以億計”。《( 史記?平準書》)
第三,通過國家專賣( 或禁榷)、平準、均輸等方式,對關系國計民生的某些商品的生產、運銷實施壟斷經營,達到既利稅雙收,又擠壓商人的目的。漢代、宋朝國家專賣都搞得很厲害,漢代是國家直接壟斷,宋朝是國家吸收大商人合作,實現壟斷。后者固然是商品經濟發展使然,但仍嚴重限制著私人工商業發展的空間。這種國家直接參與、操縱、控制經濟的傳統,一直流傳到近現代中國。
第四,國家從法律上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從倫理道德上損壞商人的人格,造成輕商、忌商、惡商、恐商、不敢言商的社會情緒和社會心理。這種心理,也許在今天的社會也未曾泯滅。實行“重農抑商”政策的結果,并不如政策制定者所想。西漢力主“重農抑商”的晁錯,已經看到了“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己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己貧賤矣”。(《漢書?食貨志》) 商業雖然還在發展,在持續的“重農抑商”高壓下,造成了經濟形態的扭曲。其后果為以下三點:
一是商人為安穩計,普遍把相當一部分資金投到農村,購買土地房宅。工商業資本相當一部分轉化為田地產,工商業者兼地主,形成中國古代經濟形態一大特色。其結果是加劇了農村土地的集中,而這些工商業者兼地主,往往又成為國家“抑兼并、平賦稅”的對象。
二是商人并沒有把土地集中起來搞規模經營,而是分割成小塊,以租佃關系出租給農民。商業資本以這種方式進入農村,并沒有從根本上動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的基礎,反而使這種封閉的落后經濟更加穩固。加之大商人又以金錢收買權力,出現了商人、地主、官僚一體化,并躋身于封建專制的權力體系之中,成為國家不可或缺的一根支柱。
三是“重農抑商”之抑,從根本上說,并不僅僅損害了商人( 或工商業者) 的利益,更主要的在于它栓塞了商品經濟發展的正常渠道,不論農業還是工商業,都不能沿著正常的商品經濟發展渠道發展。這是要害所在。
專制集權制的稅收體制――土地國家終極所有權――重農抑商政策和工商業中的國家壟斷( 專賣) 制度,似橫亙于中國古代稅收歷史進程中的三座閘門。認真研究、充分了解這三大存在,或是開啟中國幾千年稅收歷史“迷宮”大門的鑰匙。
下篇 中國古代稅收的文化傳統
世界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各行各業都在倡言文化。然而,什么是文化? 它和歷史是什么關系? 似乎很少有人認真去考慮它。
文化,從社會存在的意義上說,就是歷史演進過程的積淀及其軌跡,量化為所謂傳統文化,質化為所謂文化傳統。
特別是文化傳統,它滲透在人們的思想觀念、言論著述、行為習慣中,滲透在社會關系、社會活動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論是正面或負面的,積極或消極的,也不論人們對它是自覺或不自覺的,總之,它已沉淀凝結成一種人們的活動氛圍和社會環境。面對這種客觀存在的強大的文化傳統力量,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方針、不同的做法,后果自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正確、科學地認識它,積極地對待它,就會成為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巨大歷史動力;反之,就會成為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巨大阻力。
稅收本來就屬于歷史范疇,而且是社會演進、歷史變遷中舉足輕重的歷史范疇。所以學習稅收歷史,把握稅收文化傳統,就更具有現實意義。
稅收隨國家的產生而產生,又隨著國家的發展而發展,它的歷史和國家一樣悠遠。
稅收以國家為主體,通過超經濟手段、無償的方式,參與社會產品和財富的分配,是國家的一項主要職能。稅收所得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是國家賴以存在的物質保障。
稅收是國家調節社會的一根杠桿。幾千年來,牽系著千家萬戶,牽系著國計民生,牽系著社會經濟、社會活動、社會文明的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也成為社會貧困、社會災難、社會腐敗的淵藪。稅收是一個多元的歷史范疇:作為國家的職能,決定于也影響著國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疇;作為特殊的社會分配方式,制約著宏觀與微觀經濟的發展,因而融入了經濟的范疇;而稅收的歷史軌跡、歷史記載、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論著述、文書表格、行為規范、教育培訓、信息媒體,以及文學藝術上的反映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疇。
稅收是伴隨著政治和經濟的發展,不斷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歷史范疇。古代傳統的稅收,雖然也有一定的社會職能,但歸根結底是為國家服務的。當國家的政治體制從專制集權政體向民主政體轉化時,當經濟體制從自然經濟體制、“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化時,稅收體制也會亦步亦趨地跟著轉化。它的職能也會從主要為國家官僚機構服務轉為主要為社會、為人民、為納稅者服務,并以公開化、法制化、規范化,嚴格的監督機制為其主要特征,從而浮現出現代稅收體制與古代稅收體制的分水嶺。
什么是中國稅收文化傳統? 如何看待中國稅收文化傳統?
中國稅收文化傳統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有著世界最悠久的歷史,而且體制完備,內容豐富,文字記載幾千年,源遠流長。它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世界稅收文化的一大寶藏。
第二,在中國稅收文化傳統中,最深入人心的,當屬于“輕徭薄賦”、“富民強國”這一具有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傳統,而且兩千多年前就已明確。先秦諸子中,如管子的“薄稅斂,毋茍( 苛) 于民”;孔子的“惠民”,“斂從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罰、薄賦斂”;老子的“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墨子的“諸加費,不利于民者,圣之弗為”……他們的稅收思想和原則對后代有巨大深遠的影響。在先秦諸子中大概只有少數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調。如商鞅主張國富民貧;韓非主張重稅,反對足民。從思想文化而言,不是主流。漢初“輕徭薄賦”和隋初“恤商益民”的政策,都大大促進了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雖然歷史上的統治集團的貪欲總是和“輕徭薄賦”、“富民強國”思想原則相悖,而且現代學者也有人簡單地把這一思想原則斥為“小農意識”,但它畢竟反映了廣大民眾――納稅者的愿望和要求。這應該算是中國傳統稅收文化中的一個優良傳統。
第三,與上面相聯系的又一優良傳統,就是稅收有利于生產發展的思想原則。歷代許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認為,只有發展生產,國家稅收才能多起來。如春秋初年,輔佐齊桓公取得霸業的管仲就提出:“善為政者,田疇墾而國邑實”;孟子也認為,合理的稅收能夠促進生產,不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證國家財政收入。他說:“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荀子也認為“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 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強調“務本節用財無極”。西漢司馬遷經過長期調查研究提出“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執掌中央財政達三十年的西漢桑弘羊清醒地提出,為擴大國家稅收范圍,不僅要重視農業,更要促進農工商互動協調發展。他說:“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谷不殖,寶貨絕則財用匱”,主張“開本末之途,通有無之用”,“農工商師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確主張,稅收的基礎應是發展生產,“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這種稅收原則愈到后代,愈趨明確。
第四,強調稅收的社會協調、社會保障的職能。就是說,稅收作為國家財政收入,除用于皇室,用于養活官吏和官府的開銷,還要用于社會事業,備荒、濟貧、賑災、治水、修橋、修路等。如韓非提出:“征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西漢的賈誼提出:“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張通過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可以“佐百姓之急,足軍旅之費”,可以“平萬物而便百姓”。南北朝時代梁武帝還推行“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于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算是中國最早官辦的孤老院、孤兒院。在歷朝歷代稅收機制、設施和規定上,也對這種財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設“常平倉”,收“義倉稅”,實行“蠲免”等,在救災、救難中發揮了有效的作用。
第五,主張稅收“取民有制”或“有度”、“有常”,要求稅收規范化、制度化。管仲最早提出:“取民有度,用之有止”;孔子提出稅收要“度于禮”;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稅,則民費而不病”;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漢初年,朝廷把“量吏祿,度官用,以賦于民”(《漢書?食貨志》) 作為稅收原則。到了西晉,傅玄更明確提出“賦役有常”的主張,他強調“上不興非常之賦,下不進非常之貢,上下同也,以奉常數,民雖輸力致財,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務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為出”和“量出制入”之爭,也都是為了體現“有常”――要求規范化、制度化。
當然,中國稅收文化中還有其他值得肯定的傳統,如根據社會要求,對稅收問題和原則開展公開爭論;根據政治、經濟變化開展變法改制;等等。
但是,中國畢竟有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皇權統治的歷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的歷史,近三十年的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運行的歷史。這些歷史的積淀交揉融匯在一起,互為作用,使問題變得更加復雜,成為改革開放、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沉重包袱。
第一,稅收的屬性本是國家的職能,而且以強制性、無償性為其基本特征。在幾千年的中國稅收史中,這種特征占有絕對統治的地位,而稅收的社會性和與百姓利益的關切,則完全處于從屬的微弱地位。中國古代雖不乏明君賢相,有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們的財稅主張和措施客觀上或順應了歷史的發展,也反映了人民大眾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歸根結底是為了滿足以君王為代表的國家官僚機器的需求。收稅者和納稅者的利益關系,從根本上是不可能一致的。
第二,過去幾千年的中國,是自然經濟占據統治地位的農業國。從春秋戰國以來,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強調農業為本、重農抑商,并在稅收思想和稅收制度中占主導地位,從經濟上壓抑了商品經濟的自然發展,從政治上強化了封建的專制和集權。中國封建社會的長期停滯,或與此有關。中國文化傳統,包括稅收文化傳統中的農本主義、重農抑商的影響,在改革開放進程中成為一大歷史包袱,人們自有深切感受。
第三,“蘇聯模式”、“計劃經濟”在中國稅收文化中形成的最突出特點是,稅收作為國家一項職能異化為國家主義的機制。企業,公民作為納稅人沒有主體性資格( 甚至納稅人身份亦被掩蓋),征納雙方的權力( 權利)、責任和義務嚴重不對稱。國家的征稅權力被提高到絕對的程度。國家是原生物和至高無上的存在,而財富的創造者和納稅人則只是國家的衍生物。因此,在稅收的立法、征收、監督等方面不需要也不可能有什么公開化、規范化、法制化,更不可能產生為納稅人服務的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