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語語音范文
時間:2023-03-29 07:24:43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韓語語音,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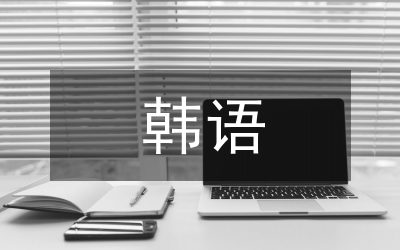
篇1
一、引言
語音室語言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chǔ),是語言的本質(zhì)。作為一門語言是最基本的要素之一。語音是否準確會關(guān)系到學(xué)生提說讀寫譯的學(xué)習效果,對外語教學(xué)具有重要意義。隨著中韓兩國交流的不斷深入,學(xué)習韓國語的學(xué)生越來越多,對韓語教學(xué)的要求也隨之提高,漢語語音教學(xué)作為韓語教學(xué)的基礎(chǔ),已成為韓語教學(xué)研究的重要課題。
韓國的文字叫韓字,是朝鮮第四代王世宗大王于1443年帶領(lǐng)一批學(xué)者創(chuàng)造出來的。韓文是一種表音的字母音節(jié)文字,其因素包括二十一個元音、十九個輔音和二十七和收音。
二、元音的發(fā)音方法 ?:嘴自然張開,舌頭接觸下齒齦,但不要貼上,嘴唇不要緊張,也不要成圓形。發(fā)音與漢語拼音的“a”相似,但比“a”稍靠后。?:先發(fā)“?”,然后迅速滑到“?”。?:口形比“?”小一些,舌后部稍微抬起,嘴唇不要緊張,也不要成圓形。?:先發(fā)“?”,然后迅速滑到“?”。?:嘴稍微張開,舌后部抬起,雙唇向前攏成圓形。與漢語拼音的“o”相似,但比“o”口形要小且圓。
?:先發(fā)“?”,然后迅速滑到“?”。
?:口形比“?”小一些,雙唇向前攏成圓形。與漢語拼音的韻母“u”相似。
?:先發(fā)“?”,然后迅速滑到“?”。?:嘴稍微張開,舌身稍向后縮,舌前部放平,舌后部略向軟腭抬起,嘴唇向兩邊拉開。與漢語拼音中“zi,ci,si,ri"的韻母的發(fā)音。練習時可先法”zi",然后,舌尖稍微往后縮,這時就可發(fā)出“?”。找到感覺后可直接發(fā)音“?”。?:與漢語拼音的“yi”相似。?:嘴張的比“?”要小一些,嘴唇向兩邊拉緊一點,舌尖頂住下齒,舌面抬起靠近硬腭,這時舌面左右兩邊夾在上下齒之間,舌面與硬腭形成扁的橢圓形。
?: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口形比“?”要小一些,嘴唇兩邊放松,舌尖頂住下齒,這時舌面硬腭之間比“?”圓。與漢語拼音中“ye,jie”的韻母e發(fā)音。?: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嘴張的與“?”相同,但舌位及舌形與“?”相同。練習時,先發(fā)一個“?”,然后變一下口形再發(fā)一個“?”,就這樣可以交替練習。?: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
?:口形與“?”相同,但舌位及舌形與“?”相同。練習時,先發(fā)一個“?”,然后變一下口形再發(fā)一個“?”,就這樣可以交替練習。?:先發(fā)一個“?”,然后迅速滑到“?”,即可發(fā)出此音。
三、基本輔音的發(fā)音方法
?:發(fā)音時,將舌面后部抬起,使舌根接觸軟腭,堵住氣流,然后放開,使氣流沖出而發(fā)聲。?:發(fā)音時,先用舌尖抵住上齒齦,堵住氣流,然后使氣流從鼻腔中留出來,同時舌尖離開上齒齦,震動聲帶而發(fā)音。
?:發(fā)音時,先用舌尖抵住上齒齦,堵住氣流,然后舌尖離開上齒齦,使氣流沖出,爆發(fā)、破裂成聲。?:發(fā)音時,先使舌尖和上齒齦接近,然后使氣流通過口腔,這是舌尖輕輕振彈一下而發(fā)聲。與漢語拼音的“r”相比,舌尖靠前的,而且舌尖也不可卷起來。?:發(fā)音時,首先緊閉嘴唇,堵住氣流,然后使氣流從鼻腔中流出的同時,雙唇破裂成聲。?:發(fā)音時,雙唇緊閉并稍向前伸,堵住氣流,然后用氣流把雙唇?jīng)_開,爆發(fā)成聲。?:發(fā)音時,舌尖抵住下齒,舌面前部接近硬腭,使氣流從舌面前部和硬腭之間的空隙處擠出來,磨擦成聲。
?:做為字的首音時不發(fā)音,只是起到裝飾作用。?:發(fā)音時,舌尖抵住下齒,舌面前部向上接觸上齒齦和硬腭堵住氣流,使氣流沖破阻礙的同時,磨擦出聲。?:發(fā)音時,方法與輔音“?”基本相同,只是發(fā)音時要用爆破性的氣流推出。?:發(fā)音時,方法與輔音“?”基本相同,只是發(fā)音時要用爆破性的氣流推出。?:發(fā)音時,方法與輔音“?”基本相同,只是發(fā)音時要用爆破性的氣流推出。?:發(fā)音時,方法與輔音“?”基本相同,只是發(fā)音時要用爆破性的氣流推出。。?:發(fā)音時,使氣流從聲門擠出,這時聲帶磨擦就發(fā)出此音。它與漢語拼音的“h”相似。
四、韓語語音教學(xué)的方法
在上文我們說明了韓語元音和輔音的一些發(fā)音方法,下面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自身的教學(xué)實踐對基礎(chǔ)階段的語音教學(xué)作初步探討。
1. 在教學(xué)中,學(xué)生離不開對教師和錄音的語音模仿,教師應(yīng)正確發(fā)音,并在學(xué)生模仿的同事即時加以糾正。并利用發(fā)音圖片及語音設(shè)備告訴學(xué)生正確的舌位及唇形,只有發(fā)音器官的位置是正確的才能發(fā)出標準的語音。
2. 在基礎(chǔ)階段韓語教學(xué)中,要注意在系統(tǒng)傳授語音知識的同時突出重點和難點,對于重點和難點要求要反復(fù)跟讀和大量練習。
3. 要采用合適的語音教材或自行設(shè)計合理的授課內(nèi)容,提高語音課的教學(xué)質(zhì)量。在語音課上,要在講練基本語音體系的同時,結(jié)合單詞和句子做大量的語音練習,以此來區(qū)分韓語語音系統(tǒng)中的清濁輔音的對立、送氣和不送氣輔音的對立以及緊輔音和松輔音的對立等較難掌握的語音現(xiàn)象。
4. 目前中國的韓語教育只把韓語語音教學(xué)作為初級階段韓語教學(xué)的重點內(nèi)容之一,在中高級階段的韓語教學(xué)中便被忽視。但很多學(xué)生的發(fā)音錯誤由于種種原因在高年級階段仍未被糾正過來,成為韓語教學(xué)中的難題。個人認為不能將韓語語音教學(xué)只當作基礎(chǔ)階段教學(xué)內(nèi)容,而應(yīng)該在學(xué)習中不斷強化韓語語音教學(xué),甚至在韓語專業(yè)的高年級中繼續(xù)堅持練習基礎(chǔ)發(fā)音。
5. 語音學(xué)習是一種“口耳之學(xué)”,也就是說,語音學(xué)習不僅僅要練習發(fā)音,還要學(xué)會聽音、辨音。聽力和口語這兩種教學(xué)要同時進行,讓學(xué)生進行聽音、辨音之后發(fā)音這樣會受到良好的教學(xué)效果。
篇2
摘 要:初中學(xué)生處于有利于語言習得的青少年時期,在學(xué)習漢語的過程中有著天然的優(yōu)勢,但是由于缺少語言環(huán)境、母語負遷移以及受英語學(xué)習習慣等因素的影響,韓國初中學(xué)生在學(xué)習漢語時還是會出現(xiàn)很多普遍性的問題,特別是在語音方面,聲母f、r、zh、ch、sh,j、q、x,韻母ü以及四聲聲調(diào)是韓國初中學(xué)生學(xué)習漢語時最大的難點。
關(guān)鍵詞:漢語;聲母;韻母;聲調(diào)
在中韓經(jīng)濟、文化等方面日益密切的交往中,越來越多的韓國人選擇漢語作為額外的外語學(xué)習內(nèi)容。韓國人民的漢語學(xué)習熱情十分高漲,而學(xué)習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也比較突出。在缺少語言環(huán)境的條件下,母語的負遷移是造成學(xué)生語音偏誤的最大因素,在聲母、韻母和聲調(diào)的學(xué)習上都有體現(xiàn),而英語的學(xué)習習慣也成為影響韓國學(xué)生學(xué)習漢語的一個重要因素。另外,漢語語音本身的復(fù)雜性,漢語拼音書寫和識讀規(guī)則也加大了韓國初中生學(xué)習漢語語音的難度。下面將從聲母、韻母和聲調(diào)三方面分別就學(xué)生普遍出現(xiàn)的學(xué)習問題進行分析。
一、聲母問題
母語的遷移是影響外語學(xué)習的重要因素。韓語發(fā)音中沒有唇齒音f和r,因此韓國學(xué)生習慣將唇齒音f替換為雙唇音p。例如“fēicháng”(非常)讀作“pēicháng”,“fēijī”(飛機)讀作“pēijī”。用舌邊音l代替r。例如:“rè”(熱)讀作“l(fā)è”,“rènshi”(認識)讀作“l(fā)ènshi”。另外還有學(xué)生會做出聲母r的相似舌位但是不發(fā)音,省略聲母直接發(fā)出卷舌音聲母后面的i的讀音,出現(xiàn)聲母缺失的問題,例如:“rìběn”讀作“-ìběn”。
另外,韓語中雖然有與漢語z、c、s相似的讀音,但是韓語中相似讀音的舌位介于漢語拼音平、卷舌音聲母舌位之間,更接舌音舌位,而且缺少成對的平翹舌對比音。因此z-zh、c-ch、s-sh是非常容易混淆的三組讀音。另外翹舌音發(fā)音時需要舌尖上翹,學(xué)生常常出現(xiàn)翹舌不到位或者卷舌過度的情況。特別是認讀由多個平翹舌聲母組合起來的詞語,更是難上加難。例如“shēngcí”(生詞),“sùshè”(宿舍),“chūzūchē”(出租車)。除了平翹舌混淆,聲母z-j、c-q、s-x也是很容易混淆的難點,例如:“zì”(字)讀作“jì”。此外,受英語拼讀習慣的影響,學(xué)生認讀聲母c和q時,會讀成拼音k的讀音,例如:“cāntīng”(餐廳)讀成“kāntīng”“qù”(去)讀成“kù”(韻母ü同時誤讀成u)。
除了聲母c的認讀出現(xiàn)問題,聲母d-t,g-k也是很容易混淆的兩組聲母。這兩組聲母在發(fā)音方法上不存在問題,只是部分學(xué)生在認讀時會認錯。加強識記練習可以有效幫助學(xué)生改正錯誤。
二、韻母問題
韻母ü是韓國學(xué)生漢語語音學(xué)習的最大難點。因為韓語中沒有ü音,而且在漢語拼音拼寫規(guī)則中,很多情況ü和u的寫法相同,容易造成學(xué)生的困擾。例如“yún”(云)讀成“wén”。在教學(xué)過程中常用的教授方法是告訴學(xué)生保持拼音i的發(fā)音,但是口型從韻母i的口型變成韻母u的口型。這樣的說明學(xué)生可以理解,但是練習發(fā)音時容易將ü的讀音分解變成u音和i音,無論讀還是聽都是兩個音。
韻母e對部分韓國學(xué)生來說也是學(xué)習難點,受母語影響,韓國學(xué)生發(fā)e音時發(fā)音位置過于靠后,和ri中的i([-i]后)發(fā)音位置較為相似,聽起來發(fā)音生硬、緊張。而且受英語影響,學(xué)生常常將拼音e讀作[]。
韓語缺少連讀的復(fù)韻母,因此韓國學(xué)生復(fù)韻母連讀意識差,在讀復(fù)韻母時出現(xiàn)發(fā)音中斷不連貫的情況,使發(fā)音不夠標準,影響聽讀。比較容易出現(xiàn)錯誤的韻母是ai讀成“a-i”,ei讀成“ei-i”。
部分韓國學(xué)生鼻韻母in和ing的發(fā)音也存在問題,一部分學(xué)生會將兩者混淆,更多的學(xué)生則是能夠區(qū)分兩個韻母,但是兩個發(fā)音都不標準。特別是ing的發(fā)音位置比較靠前,發(fā)音接近韻母in;或者韻頭i音發(fā)不準,發(fā)音偏向韻母ei。還有部分學(xué)生發(fā)ing音時嘴型攏圓,發(fā)音有iong的趨勢,同樣不是標準讀音。
受漢語拼音拼寫規(guī)則的影響,漢語拼音中省略部分讀音的復(fù)韻母寫法如un,ui,iu等拼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成為學(xué)生學(xué)習漢語識記的難點,學(xué)生按正常將單韻母組合拼讀成復(fù)韻母的習慣往往在這些韻母上出現(xiàn)問題,例如un(uen)讀作u-n,ui(uei)讀作u-i。
三、聲調(diào)問題
韓國學(xué)生在學(xué)習時總體來說對于四聲的調(diào)值掌握的都不理想,四個聲調(diào)均會出現(xiàn)調(diào)值或高或低的問題。就四個聲調(diào)分別而言,一聲陰平和四聲去聲發(fā)音較為容易,二聲陽平和三聲上聲發(fā)音最難。
一聲是比較好認讀的,但是如果一聲出現(xiàn)在句尾,學(xué)生會受母語習慣的影響,將55調(diào)讀作33調(diào)或者讀成51調(diào)。另外,由于一聲和二聲調(diào)值都比較高,學(xué)生常常會發(fā)生混淆,在讀一聲時聲調(diào)上揚,越讀調(diào)值越高。
二聲是韓國學(xué)生學(xué)習聲調(diào)的一個難點,學(xué)生掌握不好起始調(diào)值,將35調(diào)讀成45調(diào)或者更高。還有學(xué)生直接將二聲35調(diào)讀成一聲55調(diào),例如“yéye”(爺爺)讀成“yēye”。另外,在學(xué)生看來二聲和四聲的聲調(diào)書寫方式十分相似,兩個聲調(diào)的發(fā)音也都是高低的直線變化,因此會有學(xué)生將二聲與四聲混淆。
三聲無疑是韓國學(xué)生學(xué)習漢語聲調(diào)時遇到的最難的一個問題。但是很多學(xué)生掌握不好214調(diào)值,再加上已經(jīng)學(xué)習了一聲二聲,調(diào)值略高,因此常常讀錯,例如將214調(diào)讀成324調(diào);或者省略轉(zhuǎn)折部分,讀成212調(diào)、211調(diào)或114調(diào),并在此基礎(chǔ)上整體調(diào)值略高或略低。上聲變調(diào)的規(guī)則更為學(xué)生的學(xué)習增添了難度。因為上聲變調(diào)是根據(jù)情況將214調(diào)變成21調(diào),或35調(diào),學(xué)生往往簡單地將變化后的聲調(diào)理解為四聲和二聲。但是35調(diào)等于二聲,可21調(diào)并不是四聲,這樣就造成學(xué)生在認讀時出現(xiàn)問題。
四聲是學(xué)生比較好掌握的聲調(diào),但仍然存在調(diào)值不夠標準的情況。另外,如果四聲的字出現(xiàn)在疑問句句尾,學(xué)生容易按母語習慣將四聲讀作二聲,用上揚聲調(diào)來表達疑問語氣。
此外,輕聲也是學(xué)生們很難掌握的讀音。在學(xué)習四個聲調(diào)以后學(xué)生習慣根據(jù)聲調(diào)符號來認讀聲調(diào),而輕聲在書寫時沒有任何符號,學(xué)生生活在非漢語環(huán)境中,缺少語言體驗,因此很難把握讀音,常常讀作短促的一聲。
綜上所述,韓國初中生在學(xué)習漢語語音時,受母語和英語的學(xué)習習慣的影響,在聲母f、l、r、z、c、s、zh、ch、sh、j、q、x的認讀時會產(chǎn)生較大問題。韻母ü是韓國學(xué)生學(xué)習漢語時最難的一個讀音,而ü在書寫時的變形和與難度較大的聲調(diào)組合更給學(xué)生的認讀增加了難度。復(fù)韻母讀音中斷不連貫和鼻韻母in-ing的誤讀也是學(xué)生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問題。漢語語音最大的特點聲調(diào)同時也是韓國初中生學(xué)習漢語的又一個難點。聲調(diào)方面調(diào)值本身不容易讀準,再加上漢語聲調(diào)中的變調(diào)情況很多,使?jié)h語語音學(xué)習難上加難,學(xué)生在學(xué)習時出現(xiàn)的問題也更多。(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xué))
參考文獻:
篇3
【關(guān)鍵詞】韓國 漢語教學(xué) 音素教學(xué)
Abstract: Phoneme teach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honetic teaching for Korean learner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t is crucial in establishing a proper Chinese phonetic system among learners, which is fundamental in good pronunciation habits. Researchers in the past have investigated into related topics such as how to enhance better results in phonic teaching, ways to tackle with the “Mute Chinese Language” phenomenon etc.. Based on her one-year teaching experience in Korea and dep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ing order and methodology in phoneme teaching, the author analyses and summarises her personal experience in Chinese phoneme teaching to Korean learners. It is hoped that the study would provide insights and reference to the field of teaching-Chinese-to-Korean-learners.
Keywords: Korea;Chinese teaching; Phonemeteaching
目前韓國的漢語學(xué)習者與日俱增,韓國社會對漢語學(xué)習者語音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要求不僅聽力、閱讀、寫作水平達標,漢語發(fā)音更要準確流利,杜絕“韓腔怪調(diào)”的現(xiàn)象。這就為對韓漢語語音教學(xu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語音教學(xué)往往被分為“入門階段”和“高級階段”。“入門階段”針對零起點學(xué)生,一般都安排有兩周左右的集中的語音教學(xué)。“高級階段”則指在集中學(xué)習語音的階段之后的語音學(xué)習。[1]目前韓國高校中文系和孔子學(xué)院語音教學(xué)模式基本相同,普遍做法是“入門階段”單獨安排音素教學(xué),集中精力進行聲、韻、調(diào)的單項訓(xùn)練,學(xué)好單音節(jié)和單詞的本音、本調(diào),同時配合簡單的常用詞匯和語法教學(xué)。本文是基于筆者在韓國一年的任教經(jīng)驗,對于音素教學(xué)的教學(xué)順序和教學(xué)方法的探討。
(一)音素教學(xué)順序
漢語的語音系統(tǒng)由聲母、韻母和聲調(diào)三部分構(gòu)成。在逐個講解之前,可先對比韓語(如圖一、圖二)整體性地介紹給學(xué)生,使之有一個系統(tǒng)的感性認識。圖示一:
漢語發(fā)音??:韻母??(36?)+聲母??( 21?)+聲調(diào)??(4?)
圖示二:
關(guān)于韻母的教學(xué),筆者贊成趙金銘先生不必過于細致的講解每一個發(fā)音的觀點,認為只需教六個單韻母,四個開口呼的復(fù)韻母和四個開口呼的鼻韻母,其余的都可靠拼讀解決。單韻母的教學(xué),可參考朱勘宇先生的研究:兩個相鄰教授的韻母在舌位高度、舌位前后和唇形圓展中只有一個特征不同時,學(xué)生對新韻母的陌生感會降低,從而減輕認知負擔,提高學(xué)習效果。[2]目前普遍的教學(xué)順序aoeiuü中,ao,ei,iu都要經(jīng)歷兩個發(fā)音特征的改變。因此,為了加大相鄰教授的韻母的相似度和關(guān)聯(lián)度,我們可以改變單韻母的教學(xué)順序為:aeouüi,這樣一來,相鄰教授的韻母在發(fā)音特點上的區(qū)別點只有一個。圖示三舌位圖和圖示四唇形圖展示的教學(xué)順序可供教師和學(xué)生參考。
圖示三: 圖示四:
(?--e ?)(?---ü---?????????)
接下來是復(fù)韻母的教學(xué)。首先明確開口呼復(fù)合韻母的教學(xué)順序。目前普遍采用的順序是依據(jù)“漢語拼音方案”韻母表編排的:aieiaoouanenangengong。根據(jù)心理學(xué)中的線性排列的“向前靠”效應(yīng)(人們對開口部分相同的組合之記憶比對尾部相同的組合之記憶效果更好),我們把開頭字母相同的韻母排列到一塊兒,更整齊更有條理地編排為:aiaoanangeienengouong,使學(xué)習者記憶起來更為方便。齊齒呼、合口呼和撮口呼復(fù)合韻母內(nèi)部也遵循這樣的教學(xué)順序。
最后將單元音韻母和復(fù)元音韻母的教學(xué)順序制成圖示五(箭頭方向表示教學(xué)順序)如下:
圖示五:
聲母的教學(xué)順序可以根據(jù)普通話聲韻配合總表制定,由于聲母和韻母的配合有一定的選擇性,所以聲母的出現(xiàn)在教學(xué)中常由韻母決定,即在教授某組韻母時教授能與之組成音節(jié)的聲母。建議的聲母教學(xué)順序為:??b、p、m、f ????d、t、l、n ???g、k、h ???j、q、x ???? zh、ch、sh、r ???? z、c、s。單獨練習聲母的效果不佳,應(yīng)與韻母搭配組合練習,并且穿插常用詞匯和短句。以圖示六為例,先進行聲母發(fā)音練習,后與韻母組合搭配練習,再從聲韻組合中挑出常用詞匯和語法點進行學(xué)習。
圖示六:
不管是韻母還是聲母,在教學(xué)過程中都應(yīng)結(jié)合韓國學(xué)生母語負遷移和常見偏誤,有針對性地加強個別音素的練習。而聲調(diào)的教學(xué)應(yīng)配合韻母和聲母的教學(xué),首先理論圖示化加以講解,用定調(diào)法單獨練習。隨后應(yīng)與聲母、韻母組合搭配練習。
(二)音素教學(xué)方法
語音教學(xué)中常用的展示和操練語音的方法有:板書法、示范法、手勢法、帶音法、吹紙法、模仿法、四聲唱練法等。但是,“教無定法,貴在得法”,教學(xué)方法需要根據(jù)學(xué)生特點不斷創(chuàng)新改進。以下幾種是筆者在韓國任教過程中使用過的、取得良好效果的教學(xué)方法。
① 語音理論圖示法
對于多數(shù)韓國學(xué)生來說,語音學(xué)習就是“口耳之學(xué)”,即通過口來實踐、模仿,通過耳來辨識。但是只依靠模仿發(fā)音不能達到好的效果,學(xué)生對母語中沒有的音不敏感,或者不能看到教師的舌位只能模仿教師的嘴型。因此學(xué)生需要掌握一定的語音理論知識。教師要由只教發(fā)音轉(zhuǎn)為發(fā)音、理論并教。但是對于零起點的學(xué)生來說,較難理解理論知識,這時教師可盡量將語音理論圖示化。
如教給學(xué)生四個聲調(diào)時帶出第五個聲調(diào)“輕聲”,可以用圖示七解釋“輕聲”怎樣發(fā)音:
圖示七:
又如分辨“z”和“zh”,區(qū)分“zh”、“ch”、“sh”的舌位前后,了解發(fā)“ü”,時的舌頭形狀和氣流方向,可以用圖示八來解釋說明。
圖示八:
② 定調(diào)練習法
定調(diào)練習法是幫助學(xué)生在沒有教師幫助的情況下練習聲調(diào)的一種方法。以“ma”為例,通我們單獨教給學(xué)生:一聲“mā”, 二聲“má”,三聲“mǎ”,四聲“mà”。現(xiàn)在我們可以將四個聲調(diào)連起來說一遍再找到要發(fā)的聲調(diào),比如 “mā má mǎ mà ― má”,“mā má mǎ mà ― mǎ”。這就是“定調(diào)練習”,學(xué)生通過重復(fù)和找調(diào)這個過程熟悉并且牢記四個聲調(diào)的發(fā)音。在發(fā)錯聲調(diào)時,教師一提醒,便可自己可以找回正確的聲調(diào)。再結(jié)合詞可以延伸出稍微復(fù)雜的練習,比如:
tīn dú xiě kàn
dōu 聽 讀 寫 看
都 都聽 都讀 都寫 都看
hái
還 還聽 還讀 還寫 還看
yě
也 也聽 也讀 也寫 也看
yòu
又 又聽 又讀 又寫 又看
④ 以獎促學(xué)法
堅持聽寫固音是比較有成效的一種語音訓(xùn)練方法。每節(jié)課上課前聽寫十個拼音或字詞(有聽讀音寫拼音、聽讀音寫拼音和漢字、聽讀音寫聲調(diào)幾種方式),可訓(xùn)練學(xué)生的聽辨能力,區(qū)分易混淆發(fā)音。自己動手書寫也可幫助學(xué)生進一步熟悉漢字。但是聽寫這一過程卻是學(xué)生普遍比較頭疼的。這時可以設(shè)計一個有趣的獎勵機制,如對聽寫全對或者錯兩個以內(nèi)的學(xué)生,在其聽寫紙上蓋一個小印章(防止學(xué)生隨手扔掉聽寫紙),學(xué)生集齊五個印章就獲得抽獎的權(quán)力。抽獎箱里放有多種類型的兌換券,比如中國圖書券、中國食品券等。這種獎勵機制讓學(xué)生由“討厭聽寫”變成“期待聽寫”,有效地降低了學(xué)生對聽寫的抵觸心理。
關(guān)于音素教學(xué)的具體操作前人已總結(jié)過不少經(jīng)驗,這里筆者想強調(diào)兩點:一是教學(xué)過程中,聲母和韻母的教學(xué)順序需特別注意;二是要因材施教,根據(jù)韓國學(xué)生的自身特點制定教學(xué)方法。本文所討論的音素教學(xué)的教學(xué)順序和教學(xué)方法,是在韓國高校的漢語課堂上使用過且被證明是有效、受學(xué)生歡迎的,望能夠?qū)氖聦n漢語教學(xué)的工作者提供參考和借鑒。
【參考文獻】
[1]程棠.對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中的幾個問題[J]. 語言教學(xué)與研究,1996(3).
[2]陳雪竹.針對以漢語教學(xué)為目的的國外學(xué)習者的語音教學(xué)[J].首都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3(增刊).
[3]柴俊星.對外漢語語音教學(xué)有效途徑的選擇[J]. 語言文字應(yīng)用,2005(3).
篇4
摘要:由于古代中國強大的文化影響力,隨之漢字也傳入到了日本,經(jīng)過不斷的吸收、演變形成了現(xiàn)代日語。而對于日語學(xué)習者來說,要掌握到漢語中的讀音有一定的難度。基于此,本文從日語漢字音讀的來源作為切入點,并試著從現(xiàn)代漢語角度直觀對應(yīng)以及從古代漢語角度對應(yīng)關(guān)系中探討了一般對應(yīng)規(guī)律,以期促進日語學(xué)習者對日語學(xué)習的掌握。
關(guān)鍵詞:漢語韻母;日語漢字音讀;日漢漢字讀音對應(yīng)
基于語言學(xué)的角度來看,漢語與日語分屬于兩種不同的語言體系。故而,一般來講兩者間應(yīng)該不存在的對應(yīng)的規(guī)律,但由于日語中的漢字主要來自于漢語,尤其在現(xiàn)代日語中,不管是用字還是詞義上,其都與漢語有著密切相關(guān)的聯(lián)系。故而,加強對漢語韻母與日語漢字的音讀的分析,顯得尤為重要。
一、日語漢字音讀的來源分析
根據(jù)相關(guān)的歷史資料和文獻顯示,中國的漢字最早在公元一世紀起便開始逐步傳到了日本,但是日本真正意義上使用中國的漢字卻是從公元四世紀末期開始的。在日本人剛接觸到中國的漢字時,他們便直接將漢字的形、音、義等全部招辦,當然在剛開始時期,只有音讀,經(jīng)過逐步的發(fā)展后才產(chǎn)生了訓(xùn)讀。
在日語中,按照一定的分類原則可以將漢字的音讀劃分為吳音和漢音這兩大體系。其中吳音是以中國南京一帶為中心的讀音,其大致在公元七世紀前便傳到了日本,最有力的證據(jù)便是在日本的佛經(jīng)中經(jīng)典的誦讀全部是吳音;漢音則是模仿公元八世紀隋唐時代形成的,其主要以當時的長安、洛陽一帶的發(fā)音為中心,目前在日語漢字的音讀中還有許多。另外,還有一部分日語漢字的音讀是在十一世紀后,傳入的唐宋音以及慣用音。
在上述介紹中的讀音,表現(xiàn)在日語中則全是音讀,這種發(fā)音的規(guī)律最早起源于中國的古代韻書,并通過模仿這種中古發(fā)音而形成。當前有證可查的中國的古代韻書有隋朝時期所著的《切韻》、北宋時期重新編著的《廣韻》等,據(jù)相關(guān)的資料顯示,這些古代的韻書的主要功能是查字音,也可作為詩賦時韻文的參考書,而在這其中同聲調(diào)同韻母的字作為韻母,主要是用反切進行注音。所謂的“反切”是一種中國古代常用的注音方法,也就是采用兩個字組合的方式來表達一個字的音的方法。
二、漢語韻母與日語漢字的音讀淺議
(一)從現(xiàn)代漢語角度直觀對應(yīng)分析
一般來講,日語漢字的音讀有吳音、漢音、唐宋音及慣用音四種。通過對日語《常用漢字表》中出現(xiàn)的日語漢字音讀的統(tǒng)計可以看看,其一共有2187個讀音,而這一數(shù)據(jù)中,吳音占有467個;漢音占有935個;二者都有的占577個;剩余的部分則是唐宋音與慣用音。而在現(xiàn)代漢語中各類發(fā)音所占的比例如下文所示。
1、an(ian uan üan)en(uen)in ün等對應(yīng)拔音
在漢語中以an、en、in、ün等為韻母的漢字一共有358個,而如果再算上以ian、uan、üan等復(fù)韻母為音讀的漢字,其數(shù)量更加得多,即便如此在日語漢字中還是能找到與之相對應(yīng)的拔音。如安、看、萬、金、貞、忍等。此外,例如南、仁、分等漢字都各自有一定非拔音的慣用音對應(yīng),而例外的漢字也只有欠、肯、、傘Mü對《常用漢字表》中全部以拔音作為結(jié)尾的日語音讀漢字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現(xiàn)代漢語中不是前鼻音“n”的只有瓶、洗、厘、。
2、ang(iang uang)eng(ueng)ing ong(iong等對應(yīng)長音
經(jīng)過對《常用漢字表》的漢字音讀的統(tǒng)計,一共有1914個音讀的漢字,其中以ang、eng、ing、ong為韻母的漢字數(shù)量總共有278個,而這278個漢字全部都能同日語中的長音相對應(yīng)。如王、中、同、英、程、情、敬等,此外“想”在日語中有一個非長音的慣用音;“行”、“”在日語中則各自有一個非長音的唐宋音;“登”、“L”、“通”、“功”、“”等漢字都是用漢音來作長音,將吳音讀作短音。
3、ao(iao)ou(iou)與長音對應(yīng)
在中國的漢字中以ao、ou作為韻母的漢字數(shù)量比較多,據(jù)統(tǒng)計一共有166個,而在這之中又有146個漢字能與日語的長音相對應(yīng)。如桃、寶、要、厚、走、州等。在剩余的漢字中不能與日語對應(yīng)的一共有16個,其中除了慣用音的“授”之外,剩下的全都是入聲或吳音,如六、矛、告、茂等。
(二)從古代漢語角度對應(yīng)關(guān)系分析
古代漢語與現(xiàn)代漢語的讀音變化非常得大,在古代漢語中,大部分都是入聲字,故而在日語中的讀音也基本是與入聲對應(yīng)的。下文便從古代漢語的角度指出其中可以想對應(yīng)的部分。
1、a(ia ua)對應(yīng)ぁ段音或ぁ段音+つ
在漢語中以a(ia ua)為韻母的漢字一共有39個,而在這39個漢字中與日語漢字音讀有兩類對應(yīng)關(guān)系。第一類,與ぁ段音對應(yīng)的漢字有25個,如加、暇、花等;第二類,與ぁ段假名+つ對應(yīng)的有漢字一共有10個,而這類漢字又被稱作古入聲字。如察、伐、R等。
2、o(ou)對應(yīng)ぁ段音或ぁ段音+く或っ
在漢語中以0(ou)為韻母的漢字一共有51個,但由于在古代漢語中大多為入聲字,所以便形成了古漢語入聲“K”與日語“く”的27個相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t”與日語“っ”的10個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握、拓、抹、脫等。
3、e(ie üe)對應(yīng)ぁ段音、ゃ構(gòu)成的拗音或各段音+く(ま)或っ
通過相關(guān)的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在漢語中以e(ie üe)為韻母的音讀漢字一共有92個,但由于現(xiàn)代漢語將古入聲漢字納入了三聲,故而以e(ie üe)為韻母的漢字與日語漢字音讀便存在兩種對應(yīng)關(guān)系。第一類,對應(yīng)ぁ段音的漢字,其中包括拗音ゃ。如社、者、可、R等;第二類,對應(yīng)各段音+く(ま)或っ,如各、渴、穴、策、舌等。而除了上面所介紹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外,還有11個以ie為韻母的漢語有著較弱的對應(yīng)規(guī)律性。在這11個漢字中,有8個讀かぃ的漢字是街、介、戒、解、皆、街、A、械;在這11個漢字中還有2個漢字為入聲字為f、I。而其中由于揭字在古代漢語中屬于月部,因此其在日語漢字的音讀為けこ。
結(jié)束語
通過上文的介紹歸納可知,基于現(xiàn)代漢語角度來看,漢語韻母與日語的音讀漢字的確遵循著一定的規(guī)律。而由于漢語韻母的多年來的不斷演變及方言因素的存在,加之漢語聲母與韻母間的拼合以及介音的存在等關(guān)系,而要想完整地認識到漢語韻母與日語漢字音讀間的對應(yīng)規(guī)律,就需要不斷加強對漢語聲母、韻母、等對應(yīng)規(guī)律的分析整理。(作者單位:齊魯理工學(xué)院外國語學(xué)院)
參考文獻:
[1]李曉雪.聲母為“g、k、h”的漢字讀音與日語漢字音讀的對比[D].南京農(nóng)業(yè)大學(xué),2010.
[2]謝育新.日語漢字音讀與客家話對應(yīng)關(guān)系初探――以日語漢音和韻母為中心[J].日語學(xué)習與研究,2004,S1:30-33.
篇5
[關(guān)鍵詞]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語音;漢語教科書
[中圖分類號] H1-0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007(2017)03-0014-08
《漢語會話書――1910-30年代舊活字本9種》(以下簡稱《漢語會話書》)共收錄39種1911年至1938年間朝鮮日據(jù)時期刊行的漢語會話書。目前對上述教科書漢語語音史視角的專題研究尚未開展,相關(guān)研究也比較鮮見,僅有汪維輝(2012)的初步介紹,并指出本書為研究現(xiàn)代漢語和漢語教育史的重要資料。此后,陳明娥(2016)對該書有所論及,陳文指出14至20世紀,韓國先后經(jīng)歷了李氏王朝、日帝統(tǒng)治時期和大韓民國三個不同的歷史階段,政治上的動蕩自然會影響到漢語教育制度和政策的變化,這一r期出現(xiàn)的大量漢語會話教材,不同程度地反映出這些變化,成為研究古今漢語、韓語以及中朝(韓)社會文化關(guān)系變遷方面的真實可靠的文獻資料,揭示了這些教材在世界漢語教育史上的地位以及漢語史研究價值,并對韓國漢語教學(xué)研究、世界漢語教育史研究、國別化漢語教材的編寫等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意義。我們知道,“教科書詞語的選擇,往往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1](2)不同時期的漢語教科書大致能夠反映出相應(yīng)時期漢語的基本特點。上述朝鮮漢語會話書,較為真實地標記了當時漢語官話語音的基本面貌,與朝鮮朝漢語教科書在時間上形成了相應(yīng)的體系,記錄了明清官話在此時發(fā)生的質(zhì)變,反映了現(xiàn)代漢語普通話形成前期的面貌和近代漢語語音形成轉(zhuǎn)變的過渡期特征,十分值得關(guān)注。此外,會話書中出現(xiàn)了一些不同于當時一般漢語的特殊語音現(xiàn)象,這可能受到方言及近代白話的影響,也可能同時受到了作者母語的干擾,是一種雜糅的中介語音。這說明,域外學(xué)者編寫的漢語教科書的語言可能會帶有中介語性質(zhì),是需要重點關(guān)注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對《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的專題語音研究國外僅有玉昭榮(2009)《和的中韓譯音表記研究》一文有所論及,但未見原文。本文擬重點對《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所標記漢語官話語音現(xiàn)象及價值進行專題討論。
一、《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及其作者宋憲]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為宋憲]著,全一冊,共110頁。《漢語獨學(xué)》初版于明治44年(1911),《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出版于大正5年(1916),是《漢語會話書》中開篇第一本。在《漢語會話書》中,除《滿洲語自通》(“滿洲語”指山東方言)外,其余都采用官話編寫,并且經(jīng)過教科書作者依據(jù)漢語實際的“質(zhì)正”。可以說,《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正是在《漢語獨學(xué)》基礎(chǔ)之上“質(zhì)正”而成。此外,有些教科書甚至經(jīng)過中國人的審訂校正,如《華語教范》的審閱者是當時北京官話漢語講習會會長陳國棟。
朝鮮于1910年淪為日本殖民地。“日據(jù)”后的朝鮮總督府針對語言文字政策先后下達了四次《朝鮮教育令》,以期壓制和扼殺朝鮮的傳統(tǒng)語言教育。《漢語獨學(xué)》的第一版出版于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的第一年,也是朝鮮總督府針對語言政策下達第一個《朝鮮教育令》時期。自古以來,朝鮮半島一直奉中國為宗主國,有著事大慕華的傳統(tǒng),稱呼中國語言都使用“漢語”、“華語”。本書的書名沿用了“漢語”的稱呼。后期同一作者的著作――《自習完璧支那語集成》則用“支那語”替換為“漢語”,說明《漢語獨學(xué)》的編撰受到了日本語言文字政策的影響相對較小。
對于《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的作者宋憲],目前所見文獻并沒有對其詳細生卒年及生平的記錄。根據(jù)《初等自解日語文典》(1909)也僅能推測出他是生活在20世紀初期的朝鮮人。[2](5)除《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外,宋憲]還著有《日韓言文字通》(1905)、《日語文典》(1909)等等,以及一些小說和翻譯書,可以說,他是一位對漢語研究十分深入,并精通日語和德語的翻譯專家。《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凡例載:
凡例一、本書? 支那語學(xué)? 獨習? ? ?為? ? 編成?。 二、支那語? 音 ? 漢字 右邊? 朝鮮文?? 懸付? ? 自習? 便宜? 與? ? 下? 朝鮮語? 譯? ? 意味? 如何? ? 詳釋?。三、支那語? 發(fā)音? 上聲,去聲,上平,下平? 四聲? 有? ? 朝鮮文??? 完全? 區(qū)別? 難? ?? 其近似? 音?? 識別? ??? 覽者? 極? 注意? 可?。四、本書 六十課 ? 分排? ? 會話? 常言? 表示? ? 下附錄? 索引? 添? ? 各課中難止? 字? 參考解得??。
可見,《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 的教學(xué)對象是初級漢語自學(xué)者,以會話為主,依靠大量的會話練習來體會漢語語感和語法特點,以此來達到能用漢語交際的目的。書中的會話設(shè)計以上流社會流行的北京官話為基準,會話語句有濃重的北京官話及東北官話色彩,這說明朝鮮半島漢語教材官話“質(zhì)正”依據(jù)已經(jīng)由“南京官話”完全轉(zhuǎn)為“北京官話”。[3](157~165)但值得注意的是,會話書中東北官話的因素也十分明顯。
二、《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的漢語官話聲母標記
為反映本書所載語音面貌,梳理語音標記體系,本文從標音實際進行統(tǒng)計,分析并總結(jié)出《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聲母系統(tǒng)的特征。例如: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幫母字共計241例。其中“?”共27例,占11.2%;“?”共169例,占70.1%,“?”、“ ?”是標注漢語聲母發(fā)音幫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1)百 ??
(2)一把扇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非母字共計79例。其中“?”共3例,占3.8%;“?”共3例,“?”共3例,各占3.8%;“?”共70例,占88.6%,是標注聲母非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3)一間房 ???
(4)您販來的是什么貨物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滂母字共計24例。其中“?”1例,占4%;“?”共23例,占96%,是標注聲母滂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5)萬瀑洞 ?
(6)你的成衣鋪在那兒 ?
《增補改正漢語獨》中有端母字共計338例。“?”共52例,占15%;“?”共286例, 占85%,是標注聲母端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7)道路怎么樣 ??
(8)打發(fā)底下人已經(jīng)買了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明母字共計168例。其中“?”共168例,占100%,是標注聲母明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9)到處都可以馬車通行 ?
(10)名片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透母字共計121例。其中“?”共2例,占1%;“?”共1例,占0.8%;“?”共118個,占98%,是標注聲母透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11)這一條路是上北京的大道 ??
(12)我的牙疼的厲害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泥母字共計197例。其中“?”共1例,占0.5%;“?”共196例,占99%,是標注聲母泥母發(fā)音的主要規(guī)律。
例:(13)托您的福 ???
(14)你的成衣鋪在那兒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有來母字共計202例。其中“?”共202例,占100%,是標注聲母為來母字的主要規(guī)律。
例:(15)把擦臉的手巾拿來 ?
(16)貴恙怎么了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見母字共計144例。其中“?”共90例,占63%,是標注聲母“g”的主要規(guī)律;“?”共51例,占35%;“?”共2例,占1%;“?”共1例,占0.6%;“?”共90例,占63%,是標注聲母為見母字的主要規(guī)律。
例:(17)打算過了初三再出去 ?
(18)一只狗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溪母字共計49例。其中“?”共49例,占100%,是標注聲母溪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從苦中得甘 ?
前人開路后人行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匣母字共計156例。其中“?”共1例,占0.2%;“?”共155例,占99%,是標注聲母匣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19)前人開路后人行 ??
(20)福不雙至禍不單行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精母字共計179例。其中“?”共1例,占0.5%;“?”共4例,占2%;“?”共1例,占1%,其中“?”共173例,占96%,是標注聲母精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21)一葉既動,百枝皆搖 ? ??
(22)萬般皆由命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徹母字共計105例。其中“?”共6例,占5.7%;“?”共99例,占94%,是標注聲母徹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23)一個月多少錢 ?
(24)青春不再來 ?
《增a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邪母字共計149例。其中“?”共3例,占2%;“?”共2例,占1%;“?”共52例,占35%;“?”91例,占61%,是標注聲母邪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25)英雄無用武之地 ?
(26)我很愛鄉(xiāng)下的光景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照母字共計155例。其中“?”2例,占3%;“?”6例,占4%;“?”1例,占0.6%;“?”146例,占94%是標注聲母照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27)我也不知道那個屯里 ?
(28)這邊兒都是什么東西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穿母字共計82例。其中“?”共7例,占9%;“?”2例,占2.4%;“?”1例,占1.2%;“?”72例,占88%,是標注聲母穿母字的主要規(guī)律。
例:(29)你的成衣鋪在那兒 ?
(30)量一量尺寸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審母字共計445例。其中“?”3例,占0.6%;“?”120例,占27%;“?”119例,占27%;“?”203例,占46%,是標注聲母審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31)我要做一件衣裳 ?
(32)今兒個是三月初十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精母字共計284例。其中“?”85例,占30%;“?”199例,占70%,是聲母精母的主要標注規(guī)律。
例:(33)雹子 ??
(34)我在京城做買賣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有清母字共計43個,其中“?”共計6個,占14%。“?”共計1個,占2%。“?”共計2個,占5%。“?”共計34個,占79%,是標注聲母清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35)我到此地不過是一個月 ??
(36)那么量一量尺寸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心母字共計38個,其中“?”共計4個,占11%;“?”共計34個,占89%,是標注聲母心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37)三 ?
(38)瑣碎 ? ?
《增補改正漢語獨學(xué)》中有日母字共計125個。其中“?”共計39個,占31%;“”共計86個,占69%。是標注聲母日母的主要規(guī)律。
例:(39)他是法國人不是 ???
篇6
關(guān)鍵詞: 漢語“雷” 語義 隱喻分析
一、作為認知現(xiàn)象的隱喻
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認知語言學(xué)迅速發(fā)展,從90年代以來,因能對漢語許多現(xiàn)象提供強大的解釋力,而對漢語研究產(chǎn)生很大影響。從認知語言學(xué)的角度看,隱喻本質(zhì)上是一種認知現(xiàn)象。在西方隱喻理論研究中,理查茲(Richards)指出,隱喻是人類“語言無所不在的原理”;萊考夫(Lakoff,G)等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書中提出了著名的“概念隱喻”理論。胡壯麟(1997)認為,隱喻在開拓語言和概念的認知深度和廣度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文章中將隱喻分為概念隱喻、人際隱喻和語法隱喻。束定芳(1998)認為,隱喻不僅僅是一種語言現(xiàn)象,它本質(zhì)上是一種人類認知現(xiàn)象,是人類將其某一領(lǐng)域的經(jīng)驗用來說明或理解另一類領(lǐng)域經(jīng)驗的一種認知活動,是探索、描寫、理解和解釋新情景的有力工具。本文以認知語義學(xué)的隱喻理論為依據(jù),對漢語“雷”這一詞匯進行了隱喻分析。
二、“雷”的隱喻類型分析
隱喻是利用一種概念表達另一種概念,需要這兩種概念之間的相互關(guān)聯(lián),這種關(guān)聯(lián)是客觀事物在人的認知領(lǐng)域的聯(lián)想(趙艷芳,2004:99)。“源域”概念和“目的域”概念之間是靠相似性而產(chǎn)生互相聯(lián)系的,即“喻底”。隱喻的組成還有本體、喻體、喻詞。根據(jù)表達不同語義的需要,本體、喻體、喻詞和喻底會呈現(xiàn)出不同的排列與隱現(xiàn)情況。下面,將“雷”的隱喻分為以下幾種類型。
1.本體、喻體、喻詞、喻底同時出現(xiàn)。
A.老李打呼嚕像打雷一樣響。
在這一句子中,本體、喻體、喻詞、喻底同時出現(xiàn),喻底“響”的出現(xiàn)明確地揭示了本體與喻體之間的相似性,不需要聽者進行聯(lián)想。在“雷”的隱喻中,這種表達情況并不常見,究其原因,也許是“雷”與本體之間的相似性程度較高,且有一部分形成了約定俗成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如打雷與打呼嚕,已經(jīng)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較為固化),并不需要喻底來突出強調(diào)其所具有的相似性。
2.本體、喻體、喻詞同時出現(xiàn)。
B.暴跳如雷/鼾聲如雷/咆哮如雷
C.聽他說話,就像在打雷。
這種隱喻非常普遍,特別是在俗語與成語的運用中。
3.本體、喻體同時出現(xiàn)。
D.這人是個雷脾氣,你莫要去招惹他,見了面繞著走也就是了。
E.Lady gaga(美國女歌星)的扮相也太雷了!
這種隱喻一般情況下是最普遍的,但這種情況下“雷”的隱喻我們搜集到的語料較少。而E中“雷”的隱喻近兩年在流行語中大熱,其身影隨處可見,下面將作詳細分析。
4.本體出現(xiàn)。
只出現(xiàn)本體,喻體、喻底等都隱含的這類隱喻在語言中非常容易被忽視,其隱喻意義往往蘊含在表達中作為背景而不凸顯出來,或已經(jīng)成為通用的語言,不容易被人意識,也就是已經(jīng)“泛化”。這種情況下“雷”的隱喻語料我們并沒有搜集到(也可能是沒分析出來)。
5.喻體出現(xiàn)。
F.雷聲大,雨點小
G.大發(fā)雷霆/如雷貫耳
H.雷同
F、G兩例舉的是俗語與成語之例,F(xiàn)常表有名無實之意,指話說得很有氣勢而本領(lǐng)卻很少,也用于形容哭泣時只發(fā)出聲音而并沒有真正流下眼淚。F與G中本體都并未出現(xiàn),是依靠感知經(jīng)驗與約定俗成所推理出的。在篇章中,往往也會出現(xiàn)上下文已有交代,本體不出現(xiàn)的情況,在這里不一一列舉。
從隱喻的表現(xiàn)形式、功能和效果、認知特點等角度,可以把隱喻分為“顯喻與隱喻”、“根隱喻與派生隱喻”、“以相似性為基礎(chǔ)的隱喻和創(chuàng)造相似性的隱喻”等幾種不同的類別(束定芳,2000)。從這一論斷也可對“雷”的隱喻進行分類,分析其類型主要在于加深對隱喻現(xiàn)象的認識與對所學(xué)習的隱喻知識的運用,其他分類方式在此不再贅述。
三、“雷”本體與喻體具體語義特征相似點與隱喻認知基礎(chǔ)
1.從2008年起,“雷”開始盛行于網(wǎng)上,成了網(wǎng)絡(luò)流行語之一。“雷”在網(wǎng)絡(luò)上的新喻義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無意中看了自己不喜歡的東西,就會感覺不舒服,或?qū)δ撤N事物表示奇怪。在使用過程中,其感彩發(fā)生了變化,也可以解釋成因為事物的某些屬性而使看到的人產(chǎn)生無限熱愛的一種情況。具體使用例子如“雷人、雷語、被雷到”等。下面分析“雷”本體與喻體具體語義特征相似點。
隱喻是要通過一類事物來理解另一事物,其基礎(chǔ)是相似性。在隱喻發(fā)生時,原域的某些特性映射到了目標域上,建立起兩個概念域之間的相互聯(lián)系。而投射的認知基礎(chǔ),則是基本范疇概念與意向圖式概念。
2.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是一個范疇化的過程。認知語言學(xué)不同于經(jīng)典范疇理論,其認為,人類劃分出的是原型范疇,在范疇中有典型成員(即范疇的原型)與非典型成員,其以家族相似性理論聯(lián)系在一起。從這一理論看,語義范疇即是一個原型范疇,分為上位等級、基本等級與下屬等級,其原型義項就是基本等級概念,我們認識一個事物,也是從基本等級概念開始。在字典中,“雷”的原型義項是自然界的自然現(xiàn)象(我們對于這一判斷并未進行歷時的驗證,只不過根據(jù)理論推導(dǎo)與經(jīng)驗“想當然之”,今后要進行驗證),也是我們認識“雷”的開始;“雷”的另一個義項是“軍事用的爆炸武器”,如地雷、雷管、魚雷等。比較兩個義項,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之間的相似性是都會發(fā)出巨大的響聲,且武器爆炸時所騰出的煙霧也很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打雷時風起云涌、山雨欲來的景象。那么,是否可以推斷,“雷”所形成的語義范疇是通過家族相似性,在歷史的發(fā)展中逐漸吸收新的義項而形成的?其實,推廣到其他詞匯,其語義范疇中的部分義項也是通過隱喻,使用頻率增加,最后變成死喻,而固化成詞的義項。由此是否可以推斷,網(wǎng)絡(luò)流行語“雷”最終也將成為“雷”的新義項,以滿足語用要求?
3.意象圖式作為“人類經(jīng)驗和理解中一種聯(lián)系抽象關(guān)系和具體意象的組織結(jié)構(gòu),是反復(fù)出現(xiàn)的對知識的組織形式,是理解和認知更復(fù)雜概念的基本結(jié)構(gòu),人的經(jīng)驗和知識是建立在這些基本結(jié)構(gòu)和關(guān)系之上的”(趙艷芳,2001:68)。隱喻涉及到兩個概念域,也涉及到兩個語義場,如“雷”的事件圖式會包括:聚云、閃電、下雨等,當隱喻發(fā)生時,人們要通過意象圖式對兩個不同語義場進行對比與聯(lián)想,而非單純地對比其原型義項。上文的對比就能證明這點。
參考文獻:
[1]鄧莉.隱喻對語義變化的闡釋.安慶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4,(5).
[2]黃劍平.也談隱喻與轉(zhuǎn)喻的認知模式.長江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2007,(12).
[3]李文莉.隱喻的無意識性語義泛化與意象圖式.修辭學(xué)習,2003,(3).
[4]束定芳.論隱喻的基本類型及句法和語義特征.外國語,2000,(1).
篇7
摘要:隨函音義是指附于佛經(jīng)函末或卷末,對佛經(jīng)中疑難字詞進行注音、辨形和釋義的一種音義體。現(xiàn)存《思溪藏》附載有大量隨函音義,其中保存有眾多佛經(jīng)疑難俗字形體,可補充歷代辭書漏收的佛經(jīng)俗字;由于其采取隨經(jīng)注釋的形式,故這些疑難俗字很容易還原到所出經(jīng)文原文中去識別,有助于我們了解一些俗字的來源,從而使得這些字更具生命力,并可以之增補已有疑難俗字的同形字體,這對于漢語俗字研究具有重要價值。
中圖分類號:H109.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9-4474(2016)06-0056-06
近年來,漢語俗字研究方興未艾,眾多疑難俗字紛紛得到考證和辨析,這對于漢語俗字研究、大型字典的編纂以及相關(guān)典籍的校勘整理具有重要的意義。與此同時,佛經(jīng)音義在疑難俗字的收錄和整理上的價值越來越受到學(xué)界的重視,相關(guān)研究成果正源源不斷地產(chǎn)生,但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音義專書方面,而分布于經(jīng)律論三藏中為數(shù)眾多的隨函音義迄今尚未引起足夠的關(guān)注。其實這些隨函音義采取隨經(jīng)注釋的形式,所收錄的疑難俗字都是從附載的經(jīng)卷中摘錄出來的,更容易還原到佛經(jīng)原文中去,通過佛經(jīng)原文上下文來理解或與不同版本的異文進行對比,更容易識別,也更具有生命力。
有鑒于此,本文以《思溪藏》隨函音義為對象,擬從漢語俗字研究角度來揭示其價值,以便更好地發(fā)揮其作用。總的說來,其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補充歷代辭書漏收的佛經(jīng)俗字歷代字典辭書中,以后晉可洪的《新集藏經(jīng)音義隨函錄》(以下簡稱《可洪音義》)和遼代行均的《龍龕手鏡》搜羅佛經(jīng)疑難俗字最多,這兩部辭書大量收集和解釋撰寫時代(即后晉和遼代)佛經(jīng)中可見的疑難俗字、形體易誤字、傳抄訛誤字等,堪稱佛經(jīng)用字方面最完整的匯編。但是漢文佛典流傳日久,加之版本眾多,異文紛繁駁雜,漏收也在所難免。《思溪藏》隨函音義中保存有一些獨特字形,即未被二者收錄,示例如下。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收,也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而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崖”之俗字。《思溪藏》本《十住斷結(jié)經(jīng)》卷一隨函音義:“邊,下音宜,~(按:這是隨函音義中自帶的省略符號,“~”即是指要解釋的條目中的字,此處指“”字。下文中皆同此),際也,又吾佳反。”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菩薩所行不可思議,智無邊崖,亦無等侶。”〔T10,p0967a〕①。
西南交通大學(xué)學(xué)報(社會科學(xué)版)第17卷第6期譚翠《思溪藏》隨函音義與漢語俗字研究“崖”何以會寫作“”呢?”查《廣韻》,“崖”有兩讀,一音“魚羈切”,屬疑母支韻,意為崖岸;一音“五佳切”,屬疑母佳韻,意為高崖也,均與經(jīng)文意思契合。而“牙”,《廣韻》音“五加切”,屬于疑母麻韻,其中“加”為麻韻二等字,麻韻二等字和佳韻在唇牙喉音字中相混的現(xiàn)象早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就有所體現(xiàn)〔1〕。此處“崖”換聲旁俗寫作“”,蓋因這種俗讀所致。
此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收,也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而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瘦”字之訛。
《思溪藏》本《觀佛三昧經(jīng)》卷五隨函音義:“,瘦字。”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原文如下:“如是罪人欲命終時,多病消瘦,昏言囈語。”〔T15,p0674a〕即此字所出。又《龍龕手鏡?疒部》:“瘦,通(按:“通”是《龍龕手鏡》中的術(shù)語,意思是上面的形體是通行字體,就和“正”意義一樣,“正”代表正體);,正,所救反。”〔2〕《思溪藏》本《文殊師利問菩薩署經(jīng)》隨函音義:“病,下瘦字。”故“”當是“瘦”的手書俗訛字。又《可洪音義》卷二二《佛使比丘迦旃延說法沒盡偈百二十章》音義:“病,所佑反。”〔60/225c〕可資比勘。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現(xiàn)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該字形,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喪”之俗字。
《思溪藏》本《六度集經(jīng)》卷一隨函音義:“,蘇浪反。”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有“民之不善,咎在我身,愿喪吾命,惠民雨澤”〔T03,p0002a〕句,即此字所出。今考《碑別字新編》載《魏散騎侍郎元恩墓志》“喪”作“”,《唐嗣曹王妃鄭氏墓志》作“”〔3〕,可資比勘。據(jù)此,“”之所以會成為“喪”之俗字,蓋是手書中上述兩種情形進一步訛寫的結(jié)果,其為“喪”之俗字應(yīng)無疑問。
此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也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思溪藏》本《中阿含經(jīng)》卷二三隨函音義:“浣,胡伴反,洗~,二同。”今查《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彼染家得,或以淳灰、或以澡豆、或以土漬,極浣令凈。”〔T01,p0575a〕據(jù)此,“”乃“浣”之俗字。
又《思溪藏》本《增壹阿含經(jīng)》卷二二隨函音義:“浣,胡伴反,二同。”推其致俗之由,蓋因俗書中“完”與“p”常混用,則“浣”常俗寫作“”。《思溪藏》本《中阿含經(jīng)》卷五三隨函音義:“p完,戶官反,~,全也,二同。”《磧砂藏》本《悲華經(jīng)》卷三隨函音義:“完p,二同,戶官反;完,全也。”皆可證。
又“p”字常常寫作“”,只因“p”《說文》篆文作“”,隸變作“n”、“”等形,其中“n”為篆文的變體,“”又為“n”之變體,幾者常常發(fā)生混同,如《磧砂藏》本《佛本行集經(jīng)》卷三三隨函音義:“p,二同。”可證。
可見,“”之所以成為“浣”之俗字,是因“浣”先俗變作“”,又進一步俗寫作“”,再進一步俗變作“”。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收,亦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羝”之俗字。
《思溪藏》本《蘇悉地羯羅經(jīng)》卷中隨函音義:“部,下恐是字,音。”今查《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原文作:“佛部凈珠真言:(同上呼一句)遏部羝弭惹曳悉睇(二句)。”〔T18,p0684c〕據(jù)經(jīng)文可知,此處“”是譯音用字,無實際意義。今考“氐”旁《說文》作“”,隸變作“”、“”,“”、“玄”、“”、“u”旁,皆為“氐”旁的訛變體〔4〕。
《思溪藏》隨函音義中“氐”旁字“羝”作“”,“底”作“”、“”,“”作“邸鋇鵲人媧可見,“氐”之手書俗寫“”、“”等與“且”形體近似,故“”當是“羝”手書進一步訛寫的結(jié)果。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現(xiàn)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該字形,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杵”之俗字。
《思溪藏》本《佛說陀羅尼集經(jīng)》卷七隨函音義:“,昌與反。”查《廣韻?語韻》:“杵,昌與切。”〔5〕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有“即握作拳,如金剛把杵,作大_面”〔T18,p0855a〕句,即此字所出。又“午”、“”形近易混,故“”當為“杵”之俗書訛寫字。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見,亦未收錄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炙”之俗字。《思溪藏》本《六度集經(jīng)》卷四隨函音義:“為,下之夜反,肉~。”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有“以網(wǎng)收之,盡獲其眾,貢于太官,宰夫收焉,肥即烹之為肴”〔T03,p0017c〕句,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記曰:“肴,宋《資福藏》本作。”與《思溪藏》本隨函音義所言契合。
溯其致誤之由,蓋因俗書“夕”、“”每多相混。又據(jù)經(jīng)文可知,“炙”指烤熟的肉食,故“”蓋受經(jīng)文意思影響產(chǎn)生的換旁俗字。又“炙”俗寫作“”,佛經(jīng)中常見,如《北山錄》卷六:“則何太早計,見卯而求時夜,見彈而求^歟!”〔T52p0607c〕又《大正藏》本《鐔津文集》卷八:“彼則龍肉而資所贍,屠龍者彼人之事也。”〔T52,0683c〕可資比勘。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收,亦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而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之俗字。《思溪藏》本《一字佛頂輪王經(jīng)》卷三隨函音義:“,二同。”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又以四銀,一盛燒香,一盛于花,一盛白芥子、小石子等,一盛種種末香。”〔T19,p0249a〕即此字所出。
“”何以會寫作“”呢?今考《說文?木部》:“,承也。從木,般聲。o,古文,從金。P,籀文,從皿。”段注:“今字皆作‘P’。”可見,“P”同“”,自古以來即為“”之異體字。上揭經(jīng)文《大正藏》校勘記亦有:“,明本、甲本均作‘P’。”又因古文字中“舟”與“月”形體近似,故在隸定過程中,“般”與“股”二者常常混同,如漢碑《魯峻碑陰》“般”寫作“”,顧藹吉按:“《漢書?地理志》作‘般’,其字從舟,碑變從月,與‘股肱’之‘股’無別。”〔6〕漢碑《劉寬碑》“盤”亦寫作“”〔6〕。又《可洪音義》卷三《法義篇第四之四》音義:“j盂,上音P,下音于,器名也。”〔60/575b〕可資比勘。據(jù)此,“”之所以會成為“”之俗字,當是“”的隸書訛變體進一步訛寫的結(jié)果。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現(xiàn)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該字形,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蟒”之俗字。《思溪藏》本《諸佛要集經(jīng)》卷上隨函音義:“,二同,莫朗反,蛇中最大者,上非也。”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有“蟒蛇、鳥獸、麋鹿、蛟龍,承事若干殊異魍魎,是謂邪見”〔T17,p0757a〕句,即此字所出。
“”何以會成為“蟒”之俗字呢?今查《龍龕手鏡?蟲部》:“、、、,四俗;蟒,正,莫朗反,最大蛇王也。”〔2〕《可洪音義》卷二二《那先比丘經(jīng)》下卷音義:“大,莫朗反。”〔60/231a〕可見,隨函音義認為是正字的“”亦為“蟒”之俗字。又因形近,“蟒”亦俗寫作“”,并進一步訛寫為“”等形體。
“”字竊疑為上述形體的換聲旁俗字,抄手在抄寫過程中有可能發(fā)現(xiàn)“”之聲旁與“蟒”讀音相去甚遠,或者“”之聲旁是不成字部件,遂將“大”以下部件臆改作與“莽”讀音相近的“亡”,于是“蟒”字就寫成了“”形。
此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也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思溪藏》本《佛說法律三昧經(jīng)》隨函音義云:“,古典反,正作。”今查《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能覺魔事,不知皆在魔羅網(wǎng)中,如蠶作繭,還自纏裹。”〔T15,p0459a〕據(jù)此,“”乃“繭”之俗字,蓋是手書訛寫所致。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收,亦未見于現(xiàn)今大型字典,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頤”之俗字。
《思溪藏》本《大薩遮尼干子受記經(jīng)》卷六隨函音義:“,正作,余之反。”今查《大正藏》本經(jīng)文原文作“頰”,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十九者,沙門瞿曇身體廣長;二十者,沙門瞿曇身圓正直如尼拘樹王;二十一者,沙門瞿曇頰如師子;二十二者,沙門瞿曇四十齒滿;二十三者,沙門瞿曇齒間明密。”〔T09,p0342c〕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記云:“頰,宋、元、明、宮本作頤。”可見,隨函音義認為正字的“”亦為“頤”之俗字。又從上下文經(jīng)義看,上文主要描述瞿曇的身體,下文主要描述瞿曇的牙齒,竊疑“頤”受下文經(jīng)義的影響發(fā)生偏旁類化而產(chǎn)生換旁俗字“”,后又進一步異寫作“”。
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未載,現(xiàn)今大型字典亦未收該字形,見于《思溪藏》隨函音義,乃“猛”之俗字。
《思溪藏》本《真陀羅經(jīng)》卷上隨函音義:“,猛字。”今查《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如下:“已無極上僧那僧涅已深法,猛若如師子。”〔T15,p0348b〕即該字所出。又《可洪音義》卷二六《集今古佛道論衡一部四卷》卷甲音義:“軻,上音孟,下苦何反。”〔60/416c〕即“孟”作“”字例,可資比勘。據(jù)此,“”乃“猛”字手書俗寫所致。
另外,《思溪藏》隨函音義中如“效”的俗體“”(《文殊師利現(xiàn)寶藏經(jīng)》卷上隨函音義)、“郭”的俗體“”(《普超三昧經(jīng)》卷四隨函音義)等字形都未被《可洪音義》、《龍龕手鏡》和現(xiàn)今大型字典收錄。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茲不一一列舉。
二、有助于了解一些俗字的來源俗字的文獻來源、釋義和產(chǎn)生緣由等是我們考察這些俗字時常常要面對和思考的問題,《思溪藏》隨函音義可提供一些線索,加深我們對這些俗字形成原因的認識,使我們能進一步總結(jié)和掌握其產(chǎn)生規(guī)律。示例如下。
【ā
ǎ《龍龕手鏡?木部》:“今,五割反,伐木余~也;又揩摩、刮拭也。”〔2〕《漢語大字典?木部》:“同‘Y’。①樹木砍伐后留下的樁子。②草木砍伐后余樁重生的枝條。”〔7〕《中華字海?木部》略同。〔8〕從中可以看出,《龍龕手鏡》“ā弊窒隆翱摩、刮拭也”這個義項在現(xiàn)今大型字典中沒有得到承襲。又查《說文?木部》《方言》《玉篇?木部》《廣韻?曷韻》《集韻?曷韻》中“ā弊窒戮未見該釋義,可見該釋義前無所承,那么,它源自何處呢?《龍龕手鏡》所收俗字大體出于佛典,故竊疑該釋義即源自佛經(jīng)。
我們在《思溪藏》隨函音義中找到了該釋義的來源,《蘇悉地經(jīng)》卷中隨函音義:“施,上正作ǎ吾割反。”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正作“施”,原文如下:“若欲成就刀法者,取好鑌刀,量長兩肘,以小指齊闊四指,無諸瑕病,其色紺青,如施鳥弧!薄T18,p0689b〕從文字字形來看,“”與“卉”形體相近,故“ā庇搿啊痹詿舜σ追⑸混同;又就上下文經(jīng)意而言,“”為動詞,作用于“鳥弧保“揩摩、刮拭也”大體與經(jīng)文意思契合,由此推知行均所見經(jīng)本中“”確有作“ā閉擼《龍龕手鏡》“ā弊窒賂靡逑羆有可能出自《蘇悉地經(jīng)》。
然而,“ā弊趾我曰嵊小翱摩、刮拭”義呢?今查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卷三五《蘇悉地經(jīng)》卷中隨函音義:“施鳥翎,歷丁反,《韻英》云:鳥羽也,或作,經(jīng)從毛,非也;上字疑錯,所以不音,未詳何鳥也。”〔T54,p0543b〕可見,慧琳懷疑經(jīng)本中所見的“”字為錯字,故存疑不釋。
今查該字在《大正藏》中僅慧琳《一切經(jīng)音義》和《蘇悉地經(jīng)》兩見,那么,該字為何字之訛?zāi)兀繉Υ耍犊珊橐袅x》給我們留下了線索。該書卷九《蘇悉地經(jīng)》卷中音義:“施,上五割反,正作,《爾雅》:‘,余也。’諸師作、牒二音,非也。”〔59/876a〕據(jù)此可知,可洪所見經(jīng)本中該字寫作“”,可洪認為該字“正作”,即“ā弊鄭并引《爾雅》中“ǎ余也”的釋義。雖然此種釋義與上下文經(jīng)意不合,但可洪認為其“正作”卻為我們提供了重要線索,竊疑其為“插”字之形訛。從經(jīng)文意思來說,經(jīng)文中“如施鳥弧閉飧齠作,行均解釋為“揩摩、刮拭”,即穿入、插入鳥毛,該字在此處為動詞,且為手部動作,該字從“扌”旁應(yīng)無疑問;又從字形來看,“插”在俗書中常寫作“貳薄“c”等形〔9〕,與“”形體近似。因此,從字形和經(jīng)文意思來看,竊疑此處本為“插”字,因“插”俗書與“”形體近似而發(fā)生混同;又俗書中“扌”、“木”旁常因形近而互換,故該字又輾轉(zhuǎn)訛變作“”,后又進一步訛寫作“ā薄
《漢語大字典?水部》:“yù《改并四聲篇海?水部》引《搜真玉鏡》:‘,音御字。’《字匯補?水部》:‘,以去切,音御,義未詳。’”〔7〕《中華字海?水部》:“yù音遇。義未詳。見《篇海》。”〔8〕《漢語俗字叢考》曾根據(jù)《集韻》和《碑別字新編》中載錄的“御”的俗字形體,懷疑“”即“御”的俗字〔10〕。此說可從。
對此,《思溪藏》隨函音義可提供進一步的證據(jù)。《思溪藏》本《大智度論》卷一四隨函音義:“,正作R,音語,或作御。”今查《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正文作“”,原文如下:“風寒冷熱、水雨侵害,但求之。”〔T25,p0168a〕即此字所出;又校勘記亦云:“,宋、元、明、宮本作R;石本作御。”從上下文經(jīng)意來看,此處表示“抗拒,抵擋”義,作“R”更為恰當,但“御”、“R”二者常通用,故“”字極有可能也是“御”之俗字。
今查該字《可洪音義》、《龍龕手鏡》均未載,現(xiàn)今大型字典亦未收錄該字形。又查《集韻?語韻》:“,止也。或作御。”〔11〕《龍龕手鏡?彳部》:“,俗;御,今。”〔2〕據(jù)此,“”字當是“御”字在俗書中訛寫所致,又可換旁俗寫作“”。《碑別字新編》載“R”字《魏敬史君碑》寫作“”,《魏元端墓志》作“”〔3〕。《可洪音義》卷二九《弘明集》第十三卷音義:“末,上魚與反,正作R也。”〔60/541c〕可資比勘。又“”字所從的“彳”旁草書形似“氵”旁,在俗書中常發(fā)生混同,進而又訛作“”字。如《碑別字新編》載《魏恒州大中正于景墓志》“御”作“”。《思溪藏》本《真陀羅經(jīng)》卷上隨函音義:“氵卻,御字。”皆可資比勘。
三、增補已有疑難俗字的同形字體《思溪藏》隨函音義所收俗字眾多,其中有些俗字還是已有疑難俗字的同形字體,這種同形異字的現(xiàn)象值得我們關(guān)注。示例如下。
,《漢語大字典?水部》:“xí露光。《玉篇?水部》:,露光也。”〔7〕《中華字海?氵部》:“xí露光。見《玉篇》。”〔8〕但“”亦可作“法”之俗字。《思溪藏》本《文殊師利現(xiàn)寶三藏經(jīng)》卷上隨函音義:“,法字。”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原文如下:“如來所生,為法所進,過于弟子、緣覺之上,則非其類。”〔T14,p0453c〕即此字所出。
“法”為何會寫作“”呢?據(jù)《龍龕手鏡?水部》:“,古文法字。”〔2〕又《可洪音義》卷一七《曇無德部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音義:“之,音法。”〔60/57a〕今《大正藏》對應(yīng)經(jīng)文作“之法”。可見,行均、可洪所見經(jīng)本中“法”就有寫作“”、“”者,為“法”之手書訛寫字。又因俗書“缶”常寫作“”,與“”、“”的右邊部件形近,故“法”又進一步訛變作《思溪藏》隨函音義中的“”。
【l】
l,bèng《漢語大字典?土部》:“同‘堋’。落葬。”〔7〕《中華字海?土部》:“bèng把棺材放入墓穴。”〔8〕
但“l(fā)”也可以是“崩”的俗字。《思溪藏》本《中阿含經(jīng)》卷五隨函音義:“l(fā)崩,二同,下正。”今《大正藏》本經(jīng)文原文有“唯有一屋,崩壞穿漏,烏鳥所棲,弊不可居,不能舍離”〔T01,p0742a〕句,即該字所出。據(jù)經(jīng)文可知,“崩壞”指房屋的塌毀,而“l(fā)”則是受“壞”影響而產(chǎn)生的增旁俗字。
“”,現(xiàn)今大型字典失收,前輩學(xué)者曾考證其為“”之俗字〔12〕,但該字亦可作“沮”的俗字。
《思溪藏》本《十住斷結(jié)經(jīng)》卷一隨函音義:“沮,二同,才呂反,斷也,壞也,上非用。”今《大正藏》本對應(yīng)經(jīng)文有“得識辯才,常懷羞恥。堅固之行,心不可沮。覺道之力,無所不入”句〔T10,p0968a〕,即該字所出。從字形來看,“沮”左邊的形旁“氵”在草書中很容易連筆,與“公”形體近似,故“”蓋為“沮”的手書訛寫字。
【L】
L,《漢語大字典?酉部》:“tiān①摻和;調(diào)味。②同‘沾’。溢。”〔7〕《中華字海?酉部》:“tiān①摻和;②增添。”〔8〕
篇8
事實上,一年級語文書上已經(jīng)有筆順示意圖,我們完全可以指導(dǎo)孩子學(xué)會看筆順,自己掌握書寫順序。剩下的問題是:漢語拼音筆畫究竟怎么讀?
漢語拼音共有十種基本筆畫,它們的名稱是:
橫、 豎、左彎豎、右彎豎、豎左彎、豎右彎、左半圓、右半圓、左斜、右斜。
下面是6個單韻母和20個聲母的筆順:
a:第一筆左半圓,第二筆豎右彎
o:左上起筆,一筆寫成
e:中間起筆,從左至右一筆寫成
i:第一筆豎,第二筆點
u:第一筆豎右彎,第二筆豎
v:先寫u,后從左至右寫兩點
b:第一筆豎,第二筆右半圓
p:第一筆豎,第二筆右半圓
m:第一筆豎,第二筆左彎豎,第三筆左彎豎
f:第一筆右彎豎,第二筆橫
d:第一筆左半圓,第二筆豎
t:第一筆豎右彎,第二筆橫
n:第一筆豎,第二筆左彎豎
l:豎,一筆寫成
g:第一筆左半圓,第二筆豎左彎
k:第一筆豎,第二筆左斜右斜
h:第一筆豎,第二筆左彎豎
j:第一筆豎左彎,第二筆點
q:第一筆左半圓,第二筆豎
x:第一筆右斜,第二筆左斜
z:一筆寫成
c:左半圓一筆寫成
s:一筆寫成
r:第一筆豎,第二筆右彎
y:第一筆右斜,第二筆左斜
w:兩筆寫成
注:zh ch sh 筆順參考z c s h的筆順。
漢語拼音書寫
1、漢語拼音書寫兒歌:
拼音格,四條線,拼音字母住里邊。
住上格的不頂線,住下格的不貼邊,中格寫滿頂兩邊。
2、j q x 和 ü 相拼省點規(guī)則:
小ü 小ü真淘氣,從不和u在一起,見了聲母j q x,馬上就把點省去。點省去,還念ü 。
3、標調(diào)兒歌:
見 ɑ 別放過,沒 ɑ 找 o e , i u 并排標在后。
4、聲母與整體認讀音節(jié)區(qū)別兒歌:
z c s (zh ch sh r )是聲母, 發(fā)音輕短要記住,
zi ci si (zhi chi shi ri )是音節(jié),漢字注音它幫忙。
5、音節(jié)拼讀兒歌:
兩拼音節(jié)——前音輕短后音重,兩音相連猛一碰;
三拼音節(jié)——聲(母)輕介(母-指中間的 i u )快韻母響,三音連讀很順當。
6、復(fù)韻母這樣讀:
復(fù)韻母真有趣,兩個單韻母在一起。
前重后輕連著發(fā),一口讀出就是它。
7、練習讀準平舌音(z c s)與翹舌音(zh ch sh r):
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誰能分得清,請你試一試。
8、y、w 與 i u ü 開頭的韻母相拼規(guī)則:
i u ü 是小弟弟,從來不能排第一, 想成音節(jié)找 w 、y 。
篇9
關(guān)鍵詞:植物詞隱喻;共有隱喻;隱喻差異;因素分析
中圖分類號:H03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118(2012)04-0292-02
認知語言學(xué)認為人類是通過在自身與外界事物互動過程中獲得的經(jīng)驗去觀察和理解客觀世界,語言的體系結(jié)構(gòu)要受人類的認知特點制約。認知語言學(xué)概念還解釋了詞引申意義產(chǎn)生的機制,即概念隱喻理論。這個思想首先是在Lakoff&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提出來的。其理論的核心內(nèi)容有:隱喻是一種認知手段;隱喻的本質(zhì)是概念性的;隱喻是跨概念域的系統(tǒng)映射;映射遵循恒定原則;概念隱喻的使用是潛意識的等等。理論認為隱喻是從一個具體的概念域向一個抽象的概念域的系統(tǒng)映射;隱喻是思維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隱喻是思維方式和認知手段。概念隱喻理論的革命性觀點促進了認知語義學(xué)的整體發(fā)展。詞的派生意義可以通過隱喻和換喻兩種途徑產(chǎn)生。隱喻就是建立在兩個意義所反映的現(xiàn)實現(xiàn)象之間的某種相似的基礎(chǔ)上的引申方式。由此可見隱喻是詞義引申的一種重要方式。英漢語中大量的植物詞具有很多的引申義,其根本形成機制就是隱喻和換喻。本文將從隱喻機制的角度對英漢植物詞引申義進行比較。
一、英漢語言中動物詞語義微觀比較
(一)英語獨有的植物詞
經(jīng)過統(tǒng)計和整理之后,在英語里找到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詞匯,其隱喻只存在于英語文化中,在漢語中出現(xiàn)了語義缺失現(xiàn)象。
1、cabbage本義為甘藍(洋白菜、卷心菜);在非正式語中是“胸無大志的人”;在俚語里面指代錢,尤指紙幣;有時候還有指代“腦袋”。
2、Potato:本意為“馬鈴薯,土豆,甘薯”。在俚語中有(破的)襪子洞、難看的臉、(壘)球等意思。
3、Apple基本意思是“蘋果,蘋果樹”,其比喻意為“蘋果似的東西”,還指示“瞳孔、瞳仁、掌上明珠、心愛的寶貝”;在希臘神話中還是三女神爭奪的金蘋果;bigApple指“娛樂中心”。
4、Lemon的基本意義是“檸檬;檸檬樹,檸檬色”;“令人討厭的東西,無聊的人,沒有價值的東西”;在習慣語中handsb.Alemon指代“欺騙某人,把不值錢的東西賣給……”。
5、palm本義指“手掌,手心”習慣語中有“toknowsth.likepalmofone'shand對某事了如指掌;(常作為勝利的象征)勝利;榮譽;勛章:tobear(或carryoff)thepalm得勝;獲獎;得到莫大的榮譽”。
這些植物詞唯有在英語中存在的原因:其一,植被不一樣;其二,意義引申的方式不一樣。同時,英民族地域環(huán)境差異也造就了植物詞獨特性。
(二)漢語獨有的動物詞
同樣在漢語中我們也找到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詞匯,其隱喻意義只存在于漢語文化中,在英語語中出現(xiàn)了語義缺失現(xiàn)象。
1、“苦瓜”窮苦人,因為“苦”像膽汁或黃連的滋味。所以其意義是感覺難受的;而由苦構(gòu)成的詞語有“苦境;苦海(原為佛教用語,后喻很苦的環(huán)境);苦悶;含辛茹苦;吃苦耐勞等等”,它們的意義跟“不好的、難受的、負面的”意義有關(guān)系。
2、“蔥”在一些漢語文學(xué)作品中表示“女子纖細的手”,例如: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玉臺新詠·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還表示“青綠色”。
3、梅、蘭、竹、菊指:梅花,蘭花,竹,。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被人稱為“四君子”。品質(zhì)分別是:傲、幽、堅、淡。梅、蘭、竹、菊也成為中國人感物喻志的象征,也是詠物詩和文人畫中最常見的題材,正是根源于對這種審美人格境界的神往。它們的共同特點是“自強不息,清華其外,澹泊其中,不作媚世之態(tài)”。
這些植物詞的引申義唯有在漢語中出現(xiàn)中的原因重要在于漢民族傳統(tǒng)文化差異和認知的差異。這些植物詞唯有在漢語中存在的原因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
(三)英漢語共有植物詞比較
經(jīng)過比較和研究,英漢中存在著大量的共有的植物詞。其隱喻意義有同有異。舉例說明:
1、pepper指代辛辣(或富有刺激性)的事物;活力;勁頭;膽量;在美國英語中它還是“棒球賽前的熱身投擊球練習”;“墨西哥佬”;還有其構(gòu)成的短語:takepepperinthenose或growpepper表示“發(fā)怒,發(fā)脾氣,勃然大怒”。漢語中辣椒指那些“具有潑辣性格的人”。
2、Peach在英語中有“桃子;桃色,桃紅色;桃花;桃樹似的樹;桃子似的果實”,在美國俚語中它是“漂亮、動人的女子、受人喜歡的人(或物)、杰出的人、極好的東西”的代表;其中短語有“peachandcream(人)雪白的皮膚而雙頰桃紅”。而漢語中“桃”的意義比較繁多,它包含“桃樹的果實;桃花色;形容女子容顏;指形狀像桃的其他果實”。短語“桃之夭夭”來源于《詩·周南·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后來用它來形容“逃跑”,因為“桃”諧音“逃”。
3、Cherry在英語中的意思是“櫻桃;櫻桃色,鮮紅色;類似櫻桃的各種果實”。在美國俚語中是“處女;童男、處女膜、處女狀態(tài)、童貞;還有”初學(xué)者;無經(jīng)驗者;鮮紅色的,櫻桃色的;處女的,純潔的;嶄新的;在漢語中“櫻桃”經(jīng)常用來“比喻女子小而紅潤的嘴;櫻桃小口”。
4、Sesame在英語中本義是“芝麻屬的植物;芝麻油;開門咒”;其中短語“opensesame”,即“芝麻,開門!”源出《天方夜譚》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還有獲得許可、通行等的穩(wěn)當方法、口令;“敲門磚”的喻義。漢語中的“芝麻”通常形容“細小的事物”。
5、Rose在英文中指“薔薇科中三杰——玫瑰、月季和薔薇”。中文名稱為玫瑰,但在漢語中人們習慣把花朵直徑大、單生的品種稱為月季,小朵叢生的稱為薔薇,可提煉香精的稱玫瑰。Rose還具有“玫瑰色,玫瑰紅;紅潤的面色;蓮蓬式噴嘴;玫瑰狀寶石(或鉆石);玫瑰花飾;玫瑰花形紋章(尤指英國國徽);圓花窗;安樂的境地;容易的工作”等等意義。在漢語中玫瑰有“詩文之美;美玉”的意思。
6、Willow在英語中“柳木;柳木制品;(板球等的)球棒;星名,二十八宿之一”;在漢語中“柳”有姓氏;還有短語或詞組,如:柳花(柳樹的花);柳黃(像柳樹芽那樣的淺黃色);柳陌花街(尋花買笑的場所);垂柳枝多用以形容女子腰肢;比喻美女,多指歌姬、妓。在很多詞語組合中“柳”指代“下流的”,如:柳夭桃艷(形容女子貌美);柳戶花門(舊時稱妓院);柳市花街(舊指妓院密集之處);柳巷花街(柳陌花街。舊指妓院或妓院聚集之處)。
二、影響英漢動物詞隱喻異同的因素分析
(一)隱喻共性分析
隱喻的產(chǎn)生是物質(zhì)社會長期發(fā)展的結(jié)果,也是人腦的一種機能。當人類通過實踐將感性材料加工成概念的時,概念或者定義就產(chǎn)生了。英漢民族在對植物詞隱喻上的共性反映了在人類社會中的對自然界認知上的一致,這里包括對植物詞語基本有意義和隱喻義的心理約定。從這一點上,可以揭示出英漢植物詞語語義共性實際上源于人類在實踐過程中認知行為的共性。
(二)隱喻差異分析
英漢植物詞隱喻差異的原因較為復(fù)雜,歸納總結(jié)出幾點:
1、歷史原因。英國歷史上殖民地遍及了幾乎全世界。這為英語詞語的擴張?zhí)峁┝烁脵C會。英語能接觸到更多種類的植物,所以英語植物詞的隱喻內(nèi)容更加豐富。
2、多語言影響。英國受到過斯堪的納維亞語、法語、拉丁語、德語、希臘語,亞洲語言的影響。這樣很多詞語的隱喻意義來自于這些外來語,擴大了動物詞隱喻內(nèi)涵。
3、地域原因。世界很多國家使用英語,如,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家,不同的地理環(huán)境也造就了英語植物詞語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因此也造就了植物詞隱喻意義多義性的特征。
4、漢語語言本身的獨特性。漢語的植物詞隱喻基本上都是象征意義,就是所謂的抽象概念,這是一大部分原因是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
三、結(jié)語
通過英漢植物詞隱喻的對比,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人類認知行為模式具有共性。但是當作為各自的語言表達的一種方式又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色彩。英漢隱語運用各自的相似或不同的實踐體驗和視角創(chuàng)造出的色彩斑斕的隱喻意義與聯(lián)想意義。正是這種創(chuàng)造性推動了人類語言的發(fā)展。
參考文獻:
\[1\]何善芬.英漢語言對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
篇10
1、上節(jié)課我們學(xué)習了5個前鼻韻母,小朋友們還記得嗎?
2、開火車認讀5個前鼻韻母。
3、強調(diào)前鼻韻母一定要讀準“”的另外一種讀音。
二、學(xué)習新課:
1、導(dǎo)入:
我們今天要學(xué)的是叫做后鼻韻母,小朋友知道什么叫做后鼻韻母嗎?
我們來看看今天要學(xué)的后鼻韻母和前鼻韻母有什么區(qū)別呢?(出示“”和“”)
要學(xué)好后鼻韻母首先要發(fā)好“”的音。
2、學(xué)習“”
①學(xué)會了后鼻韻母的發(fā)音要領(lǐng)之后呢,我們來看看這四幅圖,(出示圖片)。先請小朋友來說說圖上的內(nèi)容。
②出示ang,“羊”的韻母就是我們今天學(xué)的第一個后鼻韻母,先請小朋友注意把“”發(fā)準確,在把“”帶上去。
③練習“”的發(fā)音,正音。
④“”的四聲:請小朋友給“”帶上聲調(diào)小帽子,自己試著讀一讀。老師抽讀檢查。
⑤給后鼻韻母“”找?guī)讉€朋友,兩拼音示范,三拼音師范。
⑥隨機抽一寫小朋友來練習音節(jié)(拓展)
3、學(xué)習“”
①后鼻韻母“”呢就是我們看到的圖上的“燈”當中的韻母了。小朋友記得后鼻韻母發(fā)音的秘訣嗎?請小朋友來說一說。
②再次強調(diào)后鼻韻母的發(fā)音方法,先發(fā)“”再發(fā)“”。
③小組比賽讀,正音。
④學(xué)習“”的四聲。
⑤音節(jié)拼讀,說詞語練習,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