剝削問題評析論文
時間:2022-11-12 07:43:00
導語:剝削問題評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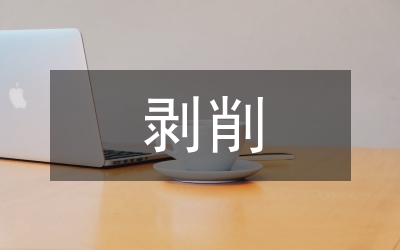
剝削問題是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問題,它對我們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有很重要的影響。在當今正確認識剝削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一、何為剝削
簡單講,剝削就是無償占有他人的勞動或產品。但是這不是一個很清晰的定義,因為真正要剝削的是產品(包括自然物品),對勞動的無償占有僅是剝削的過程,而非結果。這里的問題關鍵在于無償占有在實際上是個含糊不清的東西,不易界定。無償占有的本義在于白白地占有別人的東西,即得到的多出創造的那一部分就是無償占有,就是剝削。顯然這是說不清的,矛盾重重。譬如同樣搬一塊石頭,我們將發現搬運工的報酬現在比過去高幾十倍,在發達國家比在落后國家要高幾十倍。這種情形換成教書、理發、總統等等其它任何報酬,都是一樣的。尚若報酬低的地方都是剝削之故,則其剩余價值率或利潤率高得出奇,從而經濟發展速度也高得出奇。顯然這種出奇不曾有過。另一方面,總統是資本家的資本家,他們的收入也為何低呢?那又是誰剝削了資本家呢?這實在說不清。這里的關鍵問題僅在于其中“創造”是不成立的,在于任何獨立的人或其它要素都是什么都不能創造,而我們卻說他(它)創造了。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無法從一件產品中鑒別誰創造了多少。如一產品買5000元,其生產要素為10個工人、5個銷售人員、2個工程師、1個管理者(資本家)、5臺機器、一個廠房、一定電力等等,我們如何確定各要素分別創造了多少元?這是沒法確定的,因為這個生產過程中誰都不能少,且任何獨立的要素都沒法創造出這件產品。這樣,“各要素分別創造了多少”這個命題本身在實質上是個假命題,不成立,它打破了生產商品的整體性。只有當各要素合成一個整體時才談得上創造,再細分便沒有創造的概念。各要素的報酬在本質上僅是一個分配問題,而非創造問題,只是各要素報酬的和得等于5000元而己。
在實際經濟活動中,企業總是依據誰創造(或貢獻)的多少來分配這5000元錢,但是這不是真的,僅是“我認為”而已。當銷售有困難時,企業會認為推銷員創造的更多;當技術上急需改進時,企業會認為工程技術人員的貢獻最大;當企業經常被盜時,企業會認為保安比什么都重要。在不同工種間,企業從不曾真的鑒別出誰的貢獻大,誰的貢獻小。所謂的貢獻大,僅是重賞以解決困難而已。高層管理人員的高薪是典型的重賞,因為相對而言他們控制了更多的且絕秘的生產要素,如資訊、技術、客戶,給其高薪的真正原因大概不僅是他們的“貢獻”有多大,而是破壞有多大,破壞越大,薪水越高。因為這些生產要素能輕易地被他們偷賣或帶走,給企業造成巨大的破壞,且他們的風險極低。顯然,若高層管理人員控制的東西不易被偷走或帶走,如不是配方和技術,而是廠房和機器,企業就不擔心的他們的破壞了,他們也就拿不到高薪,起碼是拿不到那么多高薪。毫無疑問,經典理論中簡單地將實際操作和經驗系統當作科學原理,這同認為人有重的屬性別無二致。人沒有重的屬性,重僅是地球對人的吸引,沒有地球時人便沒有重量。
(二)在不同產品間,也同樣無法從創造角度確定各門部創造的多少。我們往往認為糧食一定是農民生產的,電視機一定是工人生產的,其實不然。實際上每種商品的生產中都必須用到語言、文字、數學、科技這些知識,而這些東西大多是前人留下來的,我們只是無償地使用著。顯然,沒有這些東西我們生產不出一粒糧食,也生產不出一臺電視機。站在社會這個角度看,教育、科研、國防、政府等也是同樣必不可少的,沒有這些部門的參與,糧食是種不好的,電視機是生產不出來的。各生產部門間還有更復雜的關系,沒有那個部門能獨立存在,能獨立的創造什么。從這個意義上講,任何一種商品都是歷史和社會的產物,沒有任何一個人、一個企業、一個部門能說某商品是他創造的①。【注①:這也是馬克思的觀點,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46卷下卷。】每個企業和部門都只是社會大生產中的一道工序而已,一個“生產要素”而已。任一個部門或企業的產值僅是分配的結果,絕非其創造的就是這么多,只是各部門的產值之和得等于社會創造的總產值。譬如同樣的企業生產同樣多的電視機,其產值在美國比在中國高,只因為國美總產出高。
可見,剝削的評價標準----即沒有剝削時的應該所得,僅是個分配問題,而非創造問題。同樣的總產出,由于選用的分配機制不同各要素的報酬是不同的,從而判斷剝削的標準也不同。所以,要確定剝削的判斷標準,必須先確定那種分配機制是正確的。顯然,這絕不是一個簡單問題,原因在于:一、分配始終與政治道德等有關,始終與主觀評價有關;二、在客觀的分配機制中,也由于沒有一種分配法則能貫穿整個經濟系統或整個社會系統,而是不同層面、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分配法則,從而也沒有一個能放之整個經濟系統而皆準的評判標準。所以評價剝削與否應在一定范疇內進行,否則就說不清。本文下面的分析只考慮經濟系統內的客觀的評判標準,盡量不考慮政治、法律、道德上的標準。
二、人對物的剝削
當將生產要素分為人和物(包括一般生物)兩大類時,則產品是由這兩類要素共同創造的,但是在分享共同創造的財富時,物類僅僅得到維護其必要消耗的部分,剩余的都給人類了,讓人類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越來越奢侈的日子。毫無疑問,若以公平為準則,則人類剝削了物類。但是這種剝削是天經地義的,是對人類智慧的獎賞,是有理的剝削。我們通常所說的剝削,都是這之后的事,是狹義的剝削,----即:人類共同剝削物類后的分贓,分贓不均便出現了人對人的剝削。三、工人與生產資料間的剝削
(一)總量分析。這是一種最有爭議的剝削,是工人剝削了生產資料,還是生產資料剝削了工人?回答如上所析,是工人剝削了生產資料。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真正要表述的,不是生產資料剝削工人,而是資本家占有社會積累(生產資料)及其個人消費比工人高。所以這其中實際上涉及兩個問題,一是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二是人與人之間分割終端總消費品的問題。這里先分析生產資料的歸屬問題。
人類是一種有組織的群居動物,組織是人類的本性,任何兩個人以上的群體必將自發地產生一個官----即組織者,群體行為的總步調由這個官控制。毫無疑問,組織必定限制個體的自由。也許從極端的自由主義上講組織不是個好東西,使每個人的潛能得不到最大發揮,然而,組織使群體中增加了一種結構關系,保證了群體整體的潛能得到更大的發揮。這種結構關系對群體的貢獻,與一定結構關系對金剛石的貢獻是類通的。沒有組織的一群人僅是一堆碳,一幫烏合之眾,而非金剛石。組織保證小數人說了算,從而保證了群體行為具有方向性和選擇性,保證了群體的合力遠大于各個體的力量之和(這里不是1+1=2,而是1+1>2),從而能戰勝巨大的自然對象,每個人獲益更多。顯然,如果人人說了算,必將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群體必將分裂成獨居動物,我們將是獅子老虎的盤中餐,更別說馴服火車飛機這樣的龐然大物。
經濟活動作為一種人類活動,是必然有組織的,只能是少數人掌握生產經營大權。這種現象在人類的經濟史中絕不會改變,不管生產資料在法律上的所有制如何,其正真的主人都只能是少數人,其他的人都是兵。這就是說,雖然生產資料在本質上是社會的共有財富,但是由于組織規律的約束,它總是要為少數人所支配。這是絕不以法律上所有制形式為轉移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認為少數人支配生產資料就是對多數人的剝削,是無理的。而認為一些少數人支配生產資料就是剝削(私有制),另一些少數人支配生產資料又不是剝削(公有制),這種評判本身就是不公正的。但是我們已習慣這種表述,本文也無意糾正這種錯誤的表述,所以將其納入有理剝削算了。
這里的真正問題只在于讓哪些少數人來當官。通常總是認為讓最有能力的人來當官,這不是真的。“何為最有能力”從來就是個含糊不清的東西,永遠不會有答案。少數組織者是選出來的。群體會依據群體應發展的方向等事宜建立一套選拔機制,于是誰擁有的選拔標準最多,誰便被視為最有能力,從而將官位給它。自然,這種選拔機制將選拔出這一部分少數人來當官,那種選拔機制將選拔出那一部分少數人來當官。選拔機制并非一定與生產資料所有權有關聯,原始公社和公有企業的選拔就說明了這一點。但是,如果群體認為效益最大化至關重要,且條件也只允許,則,群體就會設定生產資料所有權為選拔的重要標準,于是人們就先去爭奪生產資料所有權,從而獲得支配權,結果出現了兩權合一,產生私有經濟。私有制不是理論的產物,還沒有那種理論能夠證明兩權合一時效益一定最大化。私有制是實踐的產物,實踐證明在多數情況下兩權合一時的經濟效益更高。所有權在本質上僅是一種法律游戲,是法律讓某些人依照法律上的所有權取得代管社會共有財富的權力而已。在經濟效益高于一切的前提下,假如由于某種原因使得企業在兩權分離時效益更高,則所有權必將與支配權分離。股份企業便是輕微的兩權分離,一些企業得使用公有制也是這個道理。
從理論上講,公有制也是私有制,只是它私有得很平均,而通常說的私有制則私有得不平均。除此之外這二者再無本質差異。在實際中(包括原始公社)不曾有過真正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都只是政府所有制而已。這主要表現在生產資料和利潤的最終處理權都在政府那里,法律上所有者僅有勞動權而已,且對特定的企業,則只有特定的人才有勞動權。如何說清這是公有還是私有?如依公有制的含義,農業土地的所有者至少應該是農民,但是農民得向政府承包(租用)土地。土地只有政府才能賣,農民只能賣他的扁擔和茅屋。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看到,在通常說的私有制中,所有者始終具有使自己的部分或全部生產資料和利潤,轉化成個人消費的可能,這是典型的無理剝削,是對社會共有財富的無理侵占,----否則,私企的負債就得父債子還,而非倒閉。
總之,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總消費的分配形式,這種分配的公平才是社會主義所追求的東西。我們總是將所有制與分配制等同起來,并認為所有制決定分配制,于是在所有制上大做文章,結果越做越亂。其實,所有制僅決定對社會積累的支配(管理)形式,這是任何社會都得有的;分配制取決于對社會總消費的分配,這也是任何社會得有的,二者間并非一定有必然的聯系。
(二)個量分析。生產資料歸少數人支配為有理剝削,這絕不否認少數人因“儉財”而對工人的無理剝削。經濟活動有許多法則要遵循,積累法則就是其中一個。這個法則決定總產出中有多少將被積累,以使再生產是擴大的。但是進入微觀層面后,我們發現企業(尤其是私有企業)并不理會這個法則,而是追求最大利潤。作為企業行為這是無可厚非的,關鍵是如何獲得最大利潤。企業的效益好,利潤高,工人收入高;企業的效益差,利潤低,工人收入低,這都是必然的。但是這其中的工資是否達到合理的比例關系則是問題。也許永遠不能對這里的“合理”進行量化,但這并不表明這里不存在“合理”。如果工人的工資相對于企業的效益太高,就是工人無理剝削企業,這在公有企業和股份企業中很易發生,美國剛倒閉的幾個大企業中就出現這種情況。如果工人的工資隨企業效益的增加而太高,雖然能反映企業的仁慈,達到了“合理”的要求,沒有無理剝削或有較少的無理剝削,但是對整個社會來說這是無理剝削,是這部分工人對另一部分工人的無理剝削(下一節將討論)。所以收入不能太高。同樣,如果工人的工資相對于企業的效益太低,便是企業無理剝削工人。如果工人的工資隨企業效益的降低而太低,雖然反映工人與企業同甘共苦,但是這也是企業對其員工的無理剝削。企業的效益太差應選擇倒閉,少數人和多數人一起瓜分余資,然后一起下崗。
在個量上,企業對工人的無理剝削主要表現在:一、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而工資不作相應增加,于是企業利潤最大化。這是馬克思嚴厲批判了的。這里要補充的是,隨勞動時間延長和勞動強度的增加,人們的正常生理消耗速迅轉變成生理傷害和心理傷害,且這種傷害一旦不能即時修補,或過多,是不可逆轉的,最終表現為工人的壽命質量的降低或減少。在此種情形下,即使收入作相應增加亦無濟于事,己不是無理剝削這么簡單,而是謀財害命。這個世界上沒有比生命更寶貴的東西。我國剛推行每周五天八小時工作制時,許多企業鉆法律粗糙的漏洞,或扣除吃飯拉屎等必要時間,將上班時間延長到10~12小時;或將星期五的下班時間算至24點。增加勞動強度更是家常便飯。這種情形的剝削仍在漫延。二、降低勞動條件,主要是降低勞動安全保障,降低勞動舒適程度及降低食、住、行標準三大方面。這種情形在小型企業、采礦業、搬運業、建筑業等等及民工身上,表現得很突出。三、克減對工人的社會福利投入。四、少承擔對工人的疾病、生育及事故的責任,工人出事后往往遭到企業的遺棄或半遺棄。在我國目前,政府除對第三個方面有所管制外,其它的都是有文無行。轉四、部門間(地區間)的剝削
極端自由經濟理論中總是認為市場能完全自動實現配置最優,其實不然,市場的作用沒有這么大。拋開政治、自然等因素后,在完全自由的條件下,必將出現一個價格規律,即價格差規律。這個規律專門制造部門(或地區)間的不平等。該規律是由于科學技術在各部門(或地區)發展不平衡或應用不平衡而造成的。科學技術發度速度快的部門、科學技術應用頻度和程度高的地區,其商品的價格偏高,從而利潤高,工資水平高。反之,利潤低,工資水平低②。【注②:見曹國奇《價格論》一書,延邊大學出版社,2002年。】目前最大的價格差就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毫無疑問,價格偏高的部門(或地區)都是剝削者,價格偏低的部門(或地區)都是被剝削者。對經濟系統而言,價格差規律的作用是功過對半的,其好的一面是保證經濟系統的領頭羊----高新產業(或地區)能迅速發度壯大,從而帶動整個經濟系統的發展,其壞的一面是使經濟系統不均衡,又阻礙經濟系統的發展。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首先,經濟系統是個生態系,得有貧富差距,沒有貧富差距的經濟系統如同沒有高山和大海的生態系統一樣,死寂一片,生機全無。但是貧富差距又不能太大,否則又太違反平均化規律③,【注③:見曹國奇《價格論》一書,同②;另見曹國奇“價值在宏觀上的分配”一文,西南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2.1。】生機過度,變成洪災汗災。也許這里沒有一個量化標準,但是可以肯定,適度的這種剝削是經濟正常發度的必要條件,沒有這種剝削經濟不能正常發展,所以這部分剝削是有理的。自然,差別過大時的剝削是無理的,是要抑制或鏟除的。
不少人問,與工人相比,民工的工資很低,被剝削得很厲害,那么為何農民還是愿意進城打工,被資本家剝削呢?這里就在于農民“享受”看兩重剝削,而我們在看問題時只是簡單地進行對比分析,沒有看到部門(或地區)間這種更大的剝削。雖然農民進城打工時的收入較城里人低,但是只受一重剝削,而種田時則受兩重剝削。農民不是地主,即使是地主,也擺不脫被城鎮剝削的命運。在我國的實際中,除價格差規律造成的剝削外,農民還享受著政治、政策、自然等等的剝削,農民實際上享受三重剝削。在這個方面,農民從來就是第一批犧牲者。如1993年前后通貨膨脹,理論界大勢鼓吹過高的糧價貢獻了三分二的通貨膨脹,于是中央關閉了糧棉市場,抑制了糧價,直到今年才放開(現在說是補貼)。不知一些經濟學家的數學成績咋那么好,居然算出了三分之二的通脹貢獻,卻算不出其自己的收入通脹了!這不是經濟學家不會算賬,而是明著要犧牲農業。其實,在正常市場經濟中,糧食由于其生產技術更新速度較慢,其價格同房子、理發、書、勞動力等商品的價格一樣,是不斷上漲的。這是價格互動規律和價格上漲規律的必然決定④。【注④:見曹國奇“價格運動四大規律(之一)”一文,香港“現代教學研究”,2002.7。】即便糧價的這種上漲能夠實現,農民仍擺不脫價格差規律的制約,糧價始終偏低。補貼農業是長期的事,而非林毅夫所說的短期行為⑤。【注⑤:見林毅夫“中國還沒有達到工業反哺農業階段”一文,《南方周末》7月17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農業的長期補貼已說明了一切。當然,我國農業生產率已具備了大幅提高的技術條件,在這些技術迅速采用的幾十年里,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將大于工業,那時,我國的工農價格差將會反過頭來,糧價偏高。再過后,我國又得像美國現在這樣,不斷地補貼農業。
五、人與人之間的剝削
經典的經濟理論中大多將工資(或價格)的決定因素簡單化了,在我國主要認為工資是由按勞分配決定的,這是脫離實際的。價格(包括工資)是由眾多因素決定的,價格是疊加的⑥。【注⑥:見曹國奇“價值(價格)疊加原理”一文,經濟學家網站,/】個人的工資(收入或支出)取決于宏觀經濟水平及個人能力、天運、機遇、性格、社會認同、政治、政策、自然等等因素,絕非是一兩個因素決定的。如是國美公民而非北朝鮮公民;如天運好,會投胎,是李嘉誠的兒子;如機遇好,碰上好企業,經常在中央電視臺唱歌;如有戰事,而你天生是個軍人……。我們不可能僅用按勞分配來說明工資是不是應該所得,下面也只是大體談一下這個問題。
在宏觀層面,工資是平均化規律決定的,這個規律要求社會中所有盡力勞動的人,不分貴淺,不分殘全,不分老幼,其收入相等,這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規律。這個規律貫穿整個人類社會,是它決定了眾生平等,決定了公平的社會地位,決定了人們對公平的追求和向往。若以這個規律為標準,則凡工資(收入或支出)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人都是剝削者,凡工資(收入或支出)低于社會平均水平的人都是被剝削者。如當官的將企業的利潤轉化成個人消費(支出),使個人消費超出社會平均水平,就是剝削,----財會上會將這部分個人消費計入生產成本而非利潤轉移。很顯然,平均化規律不能身兼二職,只能作為剝削的評判標準,不能作為剝削有理性的評判標準。剝削的有理性是由微觀上的分配規律來評判的。
在微觀層面,決定工資(收入或支出)的分配規律眾多,絕非經典理論中的一兩個規律,如按勞分配、按資分配、權力分配、工齡分配、效用分配、名譽分配、救濟分配等等。它們都在平均化規律給定的基準上發生作用,使收入結構不是一坦平洋,而是高山與大海,從而一些人的收入高,一些人的收低,有的還得吃救濟。可能是除按勞分配和救濟分配等極少數分配規律外,其它分配規律都具有剝削性,如演員憑名譽分配獲得的高工資,如專利、點子憑效用分配獲得的高收入等等都是剝削。按勞分配的非剝削性也僅僅表現在確實有人盡力勞動,又確實有人沒盡力勞動。該規律的其它方面同樣具有剝削性質,且說不清。如有甲乙兩人都盡力勞動,但是由于工種不同,其工資往往不一樣;如同樣是電工,都盡力勞動了,但在不同企業其收入不一樣。這里的關鍵在于工資是由多個層面決定的,是疊加的,按勞分配僅僅決定其中的一部分而已。我們很難從一個規律上對整個工資的合理性作出評價。人和人之間的剝削性質應由從具體的微觀分配規律上來確定,不能籠統評判。譬如權力分配決定的收入,就應分權力內收入和權力外收。權力內收入是保證當官者盡忠盡職所必需的,是有理剝削;而權力外收入則正好相反,是無理剝削。這里順提一個法律悖論。權力外收入(部分)在公為腐敗,在私為奢侈,但是它們在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剝削⑦,【注⑦:這是一高姓私企付總的評價。】但是在公違法,在私合法。顯然私企的官將其企業賭垮了也絕不違法。法律不是偏袒了私企就是歧視了公企,----私企的官和公企的官都只是代管社會共有財富而已。、正確看待剝削
經濟系統在本質上是一個生態系統,各種經濟行為一環套一環,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也都是一把雙刃劍,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這其中,維護“公平”的經濟行為受制于人的利他本性,維護“差別”的經濟行為受制于人的自私本性。競爭是自私的必然表現,其本質就是淘汰,不會產公平,只會制造差別。雖然競爭產生了剝削,但是它確保人們能盡力勞動。這是至關重要的。勞動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有在保證這個原因的作用得到最大發揮后,才具備了最大限度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礎。組織是保證生活水平最大限度提高的另一因素,它使得生產資料只能由少數人支配----即剝削。這便是剝削的積極意義,是其有理性之所在。另一方面,人的利他本性必將產生公平(或平等)。顯然,公平(或平等)是人類能群居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人們無法群居,也就無所謂人類社會。但是公平(或平等)本身不會迫使人們盡力勞動,這也是馬克思在設想共產主義社會時,要假設人們能以勞動為第一需要的根本原因。由此我們便發現了一個生態矛盾:競爭雖然迫使人們努力勞動,但是其本質是淘汰,最終將使群體分裂,消滅了競爭;平均分配雖然保證了群體的存在,但是不能使人們努力勞動,最終大家都不勞動,消滅了平均。毫無疑問,經濟系統中應是二者共存,它們相互補充,相生相克,相互摧動,從而維系著經濟系統的整體性(即一元),使經濟不斷發展。由此不難知道,經濟系統中真正要抑制或鏟除的是無理剝削,因為它使貧富差距太大,違反了平均化規律,使群體趨于分裂。同樣,也要抑制或鏟除無理平均(即太過平均),因為它抑制了競爭機制,使人們不努力勞動。實際的經濟活動只能是玩太極,左右兼顧。
我們過去的認識是片面的,極端的,只看到剝削有害的一面,簡單地將剝削當成了害蟲,當成了豺狼虎豹,以趕盡殺絕、斬草除根而后快。卻不知,經濟系統是一個生態系統,消滅了剝削也便消滅了公平,消滅了公平也便消滅了剝削。據華盛頓電子郵報前不久介紹的國美情況,一方面少數企業組織拒絕降低工人工資,一方面少數工會組織拒絕為工人加薪。雖然他們的表面理由都不是經濟生態,但是其最終理由同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福特公司主動為工人加薪的理由一樣,在于經濟生態的平衡。這里不否認消滅剝削后可以建立一個新的經濟生態,但是過去的經驗證明新經濟生態十分脆弱,整體效益十分低下,誰都沒好處。我國過去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太小看了馬克思給定的一個條件,即勞動為人們的第一需要。剝削是競爭的必然產物,在沒有新的機制來保證人們都努力勞動時,是不能消滅剝削的,只能消滅無理剝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