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彈性條件下的失業分析
時間:2022-04-28 09:22:00
導語:工資彈性條件下的失業分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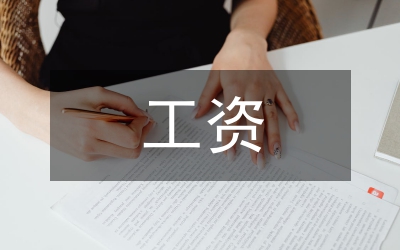
內容提要主流經濟學關于失業問題的研究通常集中于工資缺乏伸縮性的情形,而對工資伸縮性(wageflexibility)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失業則未予以應有的關注。本文通過構建一個基于向下傾斜勞動供給曲線的就業決定模型,解析出了一種筆者稱之為“支出約束引致型”的失業。這種失業即便在工資伸縮性條件下也會出現,是主流經濟學尚未深究過的失業新類型;它顯現于許多處在工業化初期的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對它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關于失業問題的理論和政策空間。
關鍵詞工資伸縮性就業決定模型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
一、問題的提出
迄今為止,貨幣工資是否具有伸縮性(wageflexibility)一直是主流經濟學解釋失業的基點,但以此為基點,卻容易忽視在貨幣工資伸縮性條件下可能出現的失業問題。古典學派包括新古典經濟學信奉市場是出清的,認為貨幣工資的伸縮性總能使勞動力市場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長期持續的(非自愿)失業不可能存在。凱恩斯主義革命后,主流經濟學尤其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將貨幣工資缺乏伸縮性作為解釋失業問題的一個關鍵假設(Leijonhufvud,1968;Malinvaud,1977;Romer,1993),認為貨幣工資缺乏伸縮性妨礙了勞動力市場的連續出清,從而造成失業。事實上,無論是隱性合約理論(Azariadis,1975;Rosen,1985)、交錯合約理論(Tayor,1980)、議價理論(McDonaldandSolow,1981;NickellandAndrews,1983)、內部人―外部人理論(LindbeckandSnower,1988)、效率工資理論(Solow,1979;ShapiroandStiglitz,1984;AkerlofandYellen,1986)、搜尋和匹配理論(Phelps,1970),還是分割勞動力市場理論(Leontaridi,1998)、失業回滯理論(Cross,1988),某種意義上都是在詮釋為何工資存在剛性或粘性。誠然,“貨幣工資缺乏伸縮性”可以探討勞動力市場缺乏靈活性對失業的影響,但客觀地說,以此為基點卻會在思維邏輯上妨礙主流經濟學提煉出這樣的問題:工資具有伸縮性是否一定能夠消除失業?或者說,是否存在貨幣工資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類型?假如它存在,又是哪些因素造成的?怎樣有的放矢地改進它?這些問題,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
相比之下,凱恩斯本人倒是在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當時的代表人物庇古(A.C.Pigou)的觀點時提及過類似問題,認為失業是貨幣工資剛性與有效需求不足共同造成的,不能一味地把經濟制度無法自行調節的責任推到貨幣工資剛性身上。不過,凱恩斯理論是一種總量分析,在他那里,就業總量、生產總量和國民收入是三個可以互換的概念,從而,他在考察失業(就業)時一方面幾乎沒有討論勞動力市場,造成宏觀經濟分析缺乏微觀基礎,甚至可以說他還沒有從古典理論的微觀基礎中“掙扎”出來;另一方面,他也未就有效需求對失業的影響展開分析,而是把重點轉向到論述要提高就業水平,與其降低貨幣工資,不如增加貨幣數量(凱恩斯,1936,第19章)。關于有效需求不足對失業的影響,倒是Barro和Grossman(1971)在區分古典失業和凱恩斯失業時有所涉及。可見,凱恩斯至多僅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貨幣工資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問題。實際上,對于失業的微觀基礎的探尋,即便是嗣后的新古典綜合派,仍舊是需求曲線與向右上方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相權衡(Samuelson,1992),圍繞著貨幣工資缺乏伸縮性打轉。總之,主流經濟學尚未深究在貨幣工資伸縮性條件下是否會出現失業的問題。
本文通過構建一個基于向下傾斜勞動供給曲線的就業決定模型,提出一種即使在工資具有伸縮性條件下也可能出現失業的情形。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經典勞動供給模型(thecanonicallaborsupplymodel)所描述的向后彎曲的勞動供給曲線,對于一些學者已經察覺到現象──低工資中勞動供給曲線出現向右下方傾斜(簡稱“向下傾斜”),只能作為經典勞動供給曲線的“例外”情況。筆者則以“最低必需支出”為鍥入點,將“最低必需支出約束”引入經典勞動供給模型,由此解析出低工資中向下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這里的最低必需支出,是指勞動者為了獲得基本生存條件而必須支付的剛性支出。在經濟理論史上,與最低必需支出相關聯的術語和思想由來已久。比如,早期理論中就有糊口工資、生存工資、或最低生活費(subsistence)的提法;威廉•配第、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卡爾•馬克思等著名思想家也有過論述,不過,他們主要是從勞動或勞動力價值決定的角度考察的。然而,嗣后的新古典經濟學,卻淡化乃至忽視了對最低必需支出問題的研究。在推導出低工資中向下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的基礎上,結合勞動需求展開就業分析,我們從中就可以解讀出一種主流經濟學沒有探究過的失業新類型──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它是一種即使在工資具有伸縮性條件下也會出現失業的類型。
二、基于向下傾斜勞動供給曲線的就業決定模型
1、拐點視角下的勞動供給曲線
在探討拐點視角下的勞動供給曲線之前,我們有必要對經典勞動供給模型作出一些相關的說明。眾所周知,經典勞動供給模型是以條件極值的形式來表達的,其一般形式(記為條件極值Ⅰ):。其中,、、、、和依次表示效用函數、支出水平、閑暇時間、市場工資率、非勞動收入以及可用于勞動和閑暇的總時間。條件極值Ⅰ表示,勞動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過程中決定了閑暇時間和支出水平。由于總時間為常數,從而,當閑暇時間決定后,勞動時間也隨之確定。市場工資率與均衡的勞動時間之間形成一條向后彎曲的經典勞動供給曲線,見圖1中的CBA曲線。其中,A點所對應的工資率wr為保留工資率。
但是,該模型隱含著如下假設──勞動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過收入的任意水平。實際上,勞動者的支出不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還有自身的規定性。譬如,一旦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其最低必需支出,最低必需支出就將對其勞動供給行為構成剛性制約。由此,筆者(2005a,2005b)將“最低必需支出約束”引入經典勞動供給模型,相應地,經典勞動供給模型修正為如下的條件極值(記為條件極值Ⅱ):。其中,表示勞動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我們將勞動者欲望層次發生變換的轉折點定義為拐點,出現拐點時的市場工資率稱為拐點工資率(用wF表示),再記為勞動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過程中提供勞動所掙得的勞動收入,則在市場工資率w下降的過程中,只要,條件就變成松弛約束,條件極值Ⅱ還原成條件極值Ⅰ,勞動供給曲線CBF仍由經典勞動供給模型所描述,勞動者追求的則是第二層次欲望。當時,最低必需支出構成了勞動者決策的硬約束,他所追求的只能是第一層次欲望;此時有,整理得,這是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見圖1的FK段曲線;它與CBA曲線的交點F則是經典勞動供給曲線的拐點;KJ段垂直線則表示勞動者提供了最大勞動時間,但仍不能彌補最低必需支出。總之,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約束后,經典勞動供給曲線出現了拐點F,而延續拐點后的勞動供給曲線變異為FK段和KJ段。
2、基于向下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的勞動力供求組合
在拐點視角下,勞動者的勞動供給曲線變為CBFKJ,但CBFKJ到目前為止仍只是代表性勞動者的勞動供給曲線,如果將其應用于宏觀層面上的分析,則需要進行變換,變換后的勞動力供給曲線形狀仍與此類似,見圖2。關于該曲線更詳細的闡釋,參見郭繼強(2005a)。本文的工作則是在此基礎上將其與勞動力需求相結合,分析它們相互作用的狀況,聚焦于由此形成的失業(就業)問題。
根據勞動力供求曲線的相對位置,我們大體上可以將勞動力供給和需求之間的關系歸結為以下兩種組合狀態:
組合A:需求曲線D1與FB段供給曲線相交。此時,向右上方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與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相互作用可以獲得穩定的均衡。這種狀態就是以往主流經濟學所著重考察的,也是主流經濟學討論失業問題的微觀基礎。在失業問題上,古典學派包括新古典經濟學信奉“貨幣工資的伸縮性會消除勞動力市場上任何多余的供給”,勞動力市場是出清的,不存在(非自愿)失業。新古典綜合派同樣將這種狀態理解為失業的微觀基礎,認為一個以完全伸縮性的工資為特征的勞動力市場不會包含非自愿失業。但在筆者看來,以往主流經濟學由于沒有“勞動供給拐點”的視角,解析不出低工資中向右下方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從而,也就難以找到探討工資具有伸縮性條件下失業的切入點。
組合B:需求曲線D2位于供給曲線CBFKJ的左邊。在圖2中,當需求從D1減少為D2時,勞動力供過于求,這種過飽和的狀況會迫使市場工資率下降。當市場工資率低于wF時,勞動力供給曲線進入拐點F以下的FKJ階段。在FK段勞動力供給曲線上,隨著工資率下降,勞動者為獲得最低必需支出而須提供的勞動增加,勞動力供給量也相應地增長,在現實經濟中表現為已經就業的人在制度勞動時間之外加班或謀取其他兼職,以貼補家用;或者他們的家人中原本不參與勞動力市場活動的某些成員,如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輔助勞動力,也涌入勞動力市場尋求工作。這在擴大勞動力供求缺口的同時也增加了市場對工資率向下的壓力,形成正反饋右下方發散型振蕩,趨向于wr所對應的水平線AJ與需求曲線D2的交點H,其結果一是工資鎖定(lockin)于保留工資水平,二是造成HJ數量的失業。組合B這種狀態,筆者稱之為基于向下傾斜勞動供給曲線的就業決定模型。此時所呈現的失業姑且稱其為“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它是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從而是向下傾斜的勞動力供給與相對不足的勞動力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它表明,即使工資具有伸縮性,并且勞動者愿意接受不低于保留工資的市場工資,也仍然會出現失業。
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是以往主流經濟學沒有關注到的。凱恩斯雖然提出了失業是貨幣工資剛性和有效需求不足共同造成的,但對于有效需求不足如何影響失業并沒有展開論述,倒是Barro和Grossman等人在非瓦爾拉均衡理論框架下進行過分析。在后者看來,古典失業是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而商品市場卻供不應求的宏觀非均衡狀態,凱恩斯失業則是勞動力市場和商品市場都處于供大于求的一種宏觀非均衡(BarroandGrossman,1971)。當商品市場供過于求時,商品價格下跌,一般物價水平下降,在貨幣工資既定的情況下實際工資趨于上漲;這就給原本經由降低實際工資來減除失業的市場機制增添了調節難度乃至陷于某種程度的失靈。也正由于此,盡管凱恩斯和古典學派(新古典經濟學)都主張降低實際工資以減少失業,但凱恩斯更強調迂回的方法,即通過增加通貨,促使物價上漲來降低實際工資。筆者以為,就失業問題而言,商品市場狀態間接地體現在對勞動力市場實際工資的影響上,可以歸類于對工資伸縮性程度的制約;至于失業的微觀基礎,主流經濟學既有的分析仍與古典理論一樣,由向右上方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與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所組成的勞動供求狀態來表達,從而當存在失業時,只要實際工資能夠下降,勞動力供給量的減少和需求量的增加便可減除失業。在這里,工資伸縮性與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轉換,在降低實際工資的同時也緩解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簡而言之,在主流經濟學看來,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來消除失業。也正由于此,凱恩斯之后的主流經濟學均將失業歸咎于工資的剛性或粘性。然而,本文的分析卻表明:在某些情況下,工資伸縮性與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無法相互轉換的,所產生的失業也不是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所能消除的。例如,在本文的組合B狀態下,較之于向下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勞動力的有效需求不足時,即使貨幣工資具有伸縮性也仍然會出現失業。
從失業的形成機理上劃分,如果我們把工資缺乏伸縮性造成的失業看成是一種失業類型,那么,本文所描述的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則是另一種類型──工資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解析出這種新類型的失業,我們就不再僅僅囿于探討工資剛性或粘性的成因、提出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各種措施,而且還可以針對這種失業類型有的放矢地改進制度安排和勞動政策,提高減除失業的有效性。
三、理論實證及現實分析
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存在于許多發展中國家或處在工業化初期的國家,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發展經濟學的大師們盡管把注意力集中于經濟發展,并沒有重點涉及失業問題,但他們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暗含著對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的考察。W.A.Lewis(劉易斯)在其經典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1954)所提出的傳統農業部門(維持生計部門)在生存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無限供給假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現代城市部門視角對組合B狀態的描述。R.Nurkse在1953年出版的《不發達國家的資本形成問題》中,提出了“貧困惡性循環論”(viciouscircleofpoverty),認為不發達國家存在一個難以打破“低收入(低工資)―低儲蓄能力―低資本形成―低生產率―低產出―低收入(低工資)”的惡性循環,由此得出一個著名的命題:“一國窮是因為它窮”(acountryispoorbecauseitispoor)。R.R.Nelson則于1956年在論文《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中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論,認為不發達國家人口的過快增長是阻礙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須大規模投資,使投資和產出的增長超過人口的增長,實現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經濟增長。誠然,Nurkse和Nelson都在探究不發達國家貧窮的癥結,都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強調了資本形成的重要性,但在筆者看來,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組合B狀態(工資鎖定于保留工資水平+存在HJ數量的失業)在宏觀上的一種表現形式,或者說,基于向下傾斜勞動供給曲線的就業決定模型是低水平均衡的微觀基礎。歷史和現實表明,許多不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次級勞動力市場(secondarylabormarket)往往呈現出組合B的狀態。
關于不發達國家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Rakshit(1982、1988)作出過有影響的分析。對于一個業已取得一定程度發展的勞動剩余經濟,為什么會產生需求約束,王檢貴從消費需求梗阻、投資需求梗阻和出口需求梗阻角度進行了梳理;他還將我國宏觀經濟運行的核心問題歸結為“勞動與資本雙重過剩”,也就是“勞動力剩余條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問題”(王檢貴,2002,第10–11、57–92、214–227頁)。鑒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多元性和復雜性,為了簡化分析,筆者聚焦于我國城市次級勞動力市場中的農民工的勞動力供求,認為它在現階段呈現出相當典型的組合B狀態,由此也產生了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筆者經過計量和分析得出,在城市次級勞動力市場上打工掙錢的農民工尚處于滿足最低必需支出的階段,農民工的勞動供給與工資正反饋向下直至工資鎖定于保留工資水平(郭繼強,2005b)。的確,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巨大的人口基數、嚴峻的“三農”問題以及現行的制度安排,共同推動著農民工隊伍的快速膨脹。目前中國已有9400萬農村勞動力在城市就業,還有1.5億剩余勞動力有可能繼續涌向城市。“我國農民工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據估計,目前,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高達約2億人,而城市所能吸納的勞動力遠遠低于這個數字,這樣,就造成了農民工勞動力市場長期處于供大于求的境地。”(李強,2004,第80頁)而大部分農民工受自身文化素質、城市就業體制和城市發展對勞動力需求的制約,只能躋身于那些工資低廉、工作條件差、就業不穩定的次級勞動力市場。從既有的研究和實際政策看,人們對農民工的關心多集中于工資問題和勞動環境問題,而對他們的失業問題關注不足。不難預計,隨著我國統籌城鄉發展的深化,農民工的失業問題將進一步凸顯。
在考察英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初期的工資和失業時,馬克思揭示了這樣一幅圖景:工人工資趨向于工資的最低限度(勞動力價值的最低限度);由于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和相對人口過剩規律的作用,在工資下降的同時,工人的失業問題也如影隨形。這一圖景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本文組合B刻畫。在失業問題上,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正比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離’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與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馬克思,1867,第691、702頁)這就是說,資本積累以及相伴而生的技術進步,會不斷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使就業相對減少并造成人口相對過剩,因而,作為一種趨勢,資本積累必然會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失業隊伍。不待而言,19世紀中后期,馬克思主義革命和邊際革命將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一分為二:前者逐步演繹成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后者則演進為我們現在通常所說的主流經濟學(或稱西方經濟學),兩者常常被描述成是相抵觸的。然而,在筆者看來,倘若撥開遮蔽的枝葉和籮蔓,就經濟學本身而言,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可貫通和互補之處。以失業分析為例,本文給出的就業決定模型也可以用于剖析馬克思所考察的工人階級境況,如果說馬克思主要是從宏觀經濟運行角度考察失業,那么,本文的分析模型則側重于探尋這種失業的微觀基礎。對于工人惡劣的生產條件、微薄的工資和艱辛的生活,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中進行過深刻的揭露。許多史學家、社會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都曾揭露過英國工業革命初期工人惡劣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以及普遍的貧困。可以認為,勞動者的工資水平確實在工資的最低限度附近徘徊,而在工資水平處于勞動力價值下限(工人的保留工資)情況下所造成的失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因為此時的工資已是工人維持貧困化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無法再通過降低工資來消除失業。
四、分析性小結和政策性啟示
以低工資中向下傾斜的勞動供給曲線為基礎所構建的就業決定模型,揭示了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的形成機理,本文由此提出了一種新的失業類型──工資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這種失業的類型,無論在新古典經濟學還是在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中都沒有深究過。
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不同于發達國家現行的失業類型,主流經濟學沒有深究這種失業類型是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的。我們知道,主流經濟學的故鄉是英美等發達的國家,經濟學研究的重點大多是以這些國家亟需解決的現實問題為導向的。這些國家自20世紀30年代走出大蕭條以后,逐步進入成熟的工業化社會和后工業化社會,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社會保障和福利使她們的國民基本上超越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約束,消費模式也已從生活必需品時代轉向耐用消費品時代;在正常情況下,他們的勞動供給行為基本上可以由經典勞動供給模型所描述。但是,發展中國家包括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國家,其勞動力市場尤其是次級勞動力市場往往呈現出組合B的狀態,形成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因此,本文的基本啟示是:中國(以及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尤其是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國家)不能簡單地套用西方某些經典理論,而是要依據本國的現實對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
必須指出的是,本文提出這種新的失業類型,并非否定或取代主流經濟學在工資缺乏伸縮性條件下對失業的探討,而是作為一種有益的補充和完善,使經濟學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普遍意義。實際上,現實經濟中的失業就是由成因各異的不同類型的失業迭加而成的。
解析這種失業新類型,有助于我們針對各種失業類型的不同成因,有的放矢的采取對策措施,提升減除失業的效率。對于由工資剛性或粘性導致的失業,增強勞動力市場靈活性的各種措施無疑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也是提高工資伸縮性的有效途徑;但是,對于支出約束引致型失業,或者更一般地說,對于工資具有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如果僅僅依靠市場自身力量、依靠增強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則難免隔靴搔癢,無法有效消除這種類型的失業。筆者認為,勞動力市場所暴露出來的這種癥結問題,首先突出了勞動力市場的制度結構的重要性。要最低勞動標準、最低社會保障、勞資關系立法等手段,將勞動力市場可能出現的向下發散失衡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圍之內,同時,界定和保護勞動力產權,營造良好的勞動關系環境,改善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的勞動者境況。
本文的分析還蘊涵著以下的政策性啟示:改變造成組合B狀況的社會經濟條件。政府應采取包括制度安排和政策導向在內的多種措施,盡力將勞動力供求狀況推向組合A的狀態。從需求角度來看政策的傾向性,就是要增加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努力使需求曲線與供給曲線的BF段相交;從供給角度看,就是按照經濟發展所派生的對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要求,加強人力資本投資,提高工人的知識、技能和收入掙得能力,增加主要勞動力市場(primarylabormarkets)的勞動力供給,相應地減少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勞動力供給,至少可以使KF段勞動力供給曲線左移,用調整供給結構的方式來減緩乃至解決失業總量問題。對我國來說,緩解乃至有效解決“三農”問題,也可有效地減少民工對城市次級勞動力市場的供給。此外,在相當長時期內通過控制人口總量,使人口生產與可利用資源、與物質生產相協調,從而保持經濟持續協調發展,也是十分必要的。
工資伸縮性條件下的失業,無論在學術研究還是經濟實踐方面,都有著值得關注的價值。本文只是解析出了其中的一種可能形式,至于是否存在其他形式,還有待我們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