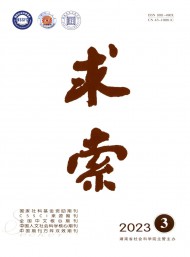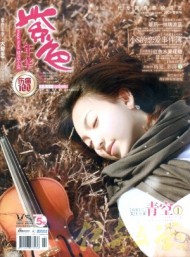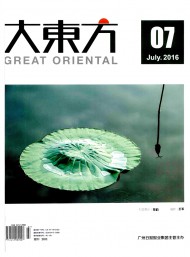引人注目造句子范文
時間:2023-04-03 17:27:02
導(dǎo)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引人注目造句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wù)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一、教學片段
師:自由閱讀第3自然段,邊讀邊思考:這一自然段是圍繞哪句話來寫的?(學生讀后回答。)
師:圍繞這句話,說說作者是按什么的結(jié)構(gòu)來寫壁畫內(nèi)容的?
生:作者是按總分結(jié)構(gòu)來寫的。
師:你是從哪里看出來的?(學生陳述理由。)
師:這樣寫有什么好處呢?
生:使文章條理清楚,讓讀者一目了然。
(師生合作讀,體會總分結(jié)構(gòu)的好處。)
師:莫高窟壁畫內(nèi)容豐富多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數(shù)飛天了。飛天的樣子美,作者的語言運用得更美。你能列舉一二嗎?
生1:作者準確地運用了“引人注目”“翩翩起舞”等成語。
生2:作者運用了“有的……有的……有的……”的排比句式。
師:請同學們用心讀讀相關(guān)的句子,想想這些句子有什么特點。
生:這些句子句式相同,結(jié)構(gòu)相似。
師:成語和排比句式的運用,形象地再現(xiàn)了飛天的不同姿態(tài),讓我們仿佛身臨其境。讓我們伴隨著同樣美妙的琵琶曲美美地讀一讀吧。(教師指導(dǎo)朗讀。)
生:飛天是敦煌藝術(shù)的標志,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讀了這組排比句,我真想親自到莫高窟欣賞一番。
師:好的,老師就滿足你的這個美好的愿望。讓我們一同走進莫高窟宏偉瑰麗的壁畫,看看飛天還有哪些姿態(tài)?(課件播放飛天圖,教師配樂朗誦第三自然段。)
師:看了這些飛天,你想說些什么?
生1:這些姿態(tài)萬千的飛天真是太精美了!
生2:中國的古代藝術(shù)真是太偉大了!
生3:壁畫上的飛天惟妙惟肖、姿態(tài)優(yōu)美。
師:你能學著書上寫飛天的樣子用八字詞語來說一說嗎?
生1:輕扭腰肢,翩翩起舞。
生2:腳踩祥云,婀娜多姿。
生3:雙掌合十,默默祈禱。
師:請同學們根據(jù)老師的提示寫話。(課件出示:壁畫上的飛天惟妙惟肖、姿態(tài)優(yōu)美。有的 ;有的 ;有的 。)
生1:壁畫上的飛天惟妙惟肖、姿態(tài)優(yōu)美。有的手執(zhí)拂塵,騰云駕霧;有的手托蟠桃,放聲歌唱;有的腳踩祥云,婀娜多姿。
2生:壁畫上的飛天惟妙惟肖、姿態(tài)優(yōu)美。有的閉目凝神,側(cè)耳傾聽;有的雙掌合十,默默祈禱;有的手握竹笛,盡情吹奏。
師:看著這些精美的壁畫,就像是——(引讀:走進了燦爛輝煌的藝術(shù)殿堂。)
二、教后反思
(一)選得準,咬定青山不放松
學生語文能力高低的一個重要判斷依據(jù)是語言表達,這就要求語文教師在引領(lǐng)學生閱讀感悟時,要更多地關(guān)注語言習得,這也是語文課的核心價值所在。目前,比較可行的方法就是結(jié)合具體文本、具體語言、具體情境,在語言表達處、在文本奧妙處、在遣詞造句處、在謀篇布局處時時喚醒,常常提示。如《莫高窟》第三自然段典型的總分總構(gòu)段形式及排比句式為學生片段仿寫提供了范例。此外,由于學生大多沒有到過敦煌,沒有見過令人驚嘆的壁畫飛天,故對洞窟內(nèi)的珍貴文物缺乏感性認識,如果突破不了這一難點,將無法實現(xiàn)跨越現(xiàn)實與歷史的時空,達到厚實課堂、融通心靈、積淀文化的目的。基于以上認識,我以此作為讀寫結(jié)合的切入口。
(二)練得實,洗盡鉛華呈素姿
練筆也是一種言語交際訓練。教師要為學生創(chuàng)設(shè)真實的交際情境,激發(fā)學生的想象,多方位喚起他們的生活積累,激發(fā)他們參與言語交際的愿望,進而在雙向或多向的語言實踐中提高言語表達能力。如《莫高窟》的教學中,多媒體的運用為學生營造了良好的練筆情境,激發(fā)了學生的想象,使學生從內(nèi)心燃起了對制作眾多惟妙惟肖飛天的古代勞動人民的贊嘆之情,繼而促進了學生思維的內(nèi)化,達到了加深理解文本、品悟文字內(nèi)涵的目的。
(三)方法巧,天光云影共徘徊
課堂練筆托生閱讀課堂,融合了閱讀寫作,其首要目的是為了讓學生更好地理解內(nèi)容,感悟人物形象,習得語言技巧。這就需要教師的指導(dǎo)方法要巧妙。在教學該自然段時,我就采用了“觀察與想象相交融”的互動方式,即我先帶領(lǐng)學生賞讀,再引導(dǎo)學生領(lǐng)悟文章寫法并歸納小結(jié),然后出示神態(tài)各異的其他飛天,并輔以聲情并茂的朗誦,最后讓學生遵循作者的思路去思考,按照文本的表達方式去仿寫。學生想象力豐富,回答妙趣橫生。這樣集朗讀感悟、想象補白于一體,既有效突破了難點,又提高了學生的讀寫能力。這樣的練筆設(shè)計靠船下篙,學生有了文本作為范例,很快就能遷移運用,而且還在仿寫的過程中對飛天的姿態(tài)優(yōu)美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這樣的練筆設(shè)計不僅檢驗了學生對課文內(nèi)容和情感內(nèi)涵的理解程度,還有效地進行了具體敘述的訓練,達到了言意兼得的效果,實現(xiàn)了語言與精神的共舞。
篇2
一、“字”在中文表達理解中的核心作用
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句法的基點是“字”。“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文心雕龍?章句》)是中國古代語言學對“字”和“句”關(guān)系的基本認識。在“字”和“句”中間,完全沒有“詞”的位置。即無須“詞”的轉(zhuǎn)換,漢字天然就是一個基本的語言單位。而“詞”這個觀念,在漢語中原來是一種文學樣式,是將詩文配上曲調(diào)加以演唱的形式。“詞”的word含義,是由翻譯外來詞而產(chǎn)生的,它并不是一個中文的概念。在現(xiàn)代漢語的分析范疇中,“單音詞”和“字”對應(yīng),兩者并無沖突。“雙音詞”把兩個字的較為穩(wěn)定的組合視為一個基本單位,并非沒有道理。首先,單個漢字字義豐富,卻不夠明確。雖然中文高度依賴語境,但當我們僅僅指稱一個概念的時候,指稱本身的明晰就成了概念清晰的一個基本條件。中文不斷創(chuàng)造新的概念、新的指稱,其方法就是將有限的漢字靈活組合,產(chǎn)生新的組合義,從而創(chuàng)新了語匯。由此,新的組合義(1+1>2或1+1≠2的組合義),是雙字組結(jié)構(gòu)“合法性”即“詞化”的必要條件。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明”表示bright,“白”表示white,而兩者組合后的“明白”表示understand(組合義)。其次,中文的表達喜好單雙音節(jié)交錯的節(jié)律,因此新的概念的產(chǎn)生,即字的組合和“意會”,大都發(fā)生在一個穩(wěn)定的雙字組范圍內(nèi)。甚至即使在意義上是1+1=2的字組,也會因雙音化而“凝固”起來,成為一個基本單位。前者如“然則”,王力分析說:“‘然’是‘如此’,‘則’是‘那么’,‘然則’本來是兩個詞,即‘既然如此,那么……就’的意思。后來由于它們常常結(jié)合在一起,就凝固起來,成為一個連詞了。”
又如“所以”,“在上古時期,‘所以’應(yīng)該認為是兩個詞,‘以’字有它表示工具語的本來意義。”“‘所以’這個仂語,在古代漢語里是最常見的凝固形式之一。”更有些1+1=1的字組,其組合不惜以意義的冗余去湊足一個雙音節(jié)。例如,古代漢語中大量的“偏義復(fù)詞”,諸如用“吉兇”指“兇”,用“國家”指“國”。“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杜甫《石壕吏》),“出入”實指“入”;“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史記?項羽本紀》),“出入”實指“出”。又如古代漢語中大量的“同義并行復(fù)合詞”,“涕淚”同義,“誅殺”同義,“憂虞”同義,“愿望”同義,“愛憐”同義。“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公輸》)的“既已”、“斧斤以時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斧斤”,都是十分典型的1+1=1的組合。在漢語史的發(fā)展中,基本表達單位的雙音節(jié)化是一個長期的趨勢。然而,即使受雙音化的影響,漢語的“雙音詞”仍然與歐洲語言的“word”有根本的不同。其關(guān)鍵在于漢語的雙音組合是“字”組,漢字在組合中有很大的分析性。這就造成了中國語言學的一個世紀糾結(jié):當兩個漢字組合起來的時候,我們無法清晰地判斷哪些組合是“word”,哪些組合不是。即使是那些很有把握判斷為“詞”的字組,只要提供合適的語境,組合中的字就有可能獨立表意,由此形成漢語表達中十分獨特的“組義分合二重性”。經(jīng)典的例子如“非常”,合則為“很”,分則為“不尋常”;又如“半天”,合則為“好久”,分則為“白天的一半”。漢字的分析性使得“字”即使在一個成熟的組合中都潛藏著很大的游離性,這種游離性甚至能轉(zhuǎn)換結(jié)構(gòu)的性質(zhì)。一個引人注目的現(xiàn)象就是“動賓強勢轉(zhuǎn)換”。例如,聯(lián)合結(jié)構(gòu)“唱歌”強勢轉(zhuǎn)換為動賓結(jié)構(gòu)(“唱了一個歌”),聯(lián)合結(jié)構(gòu)“睡覺”強勢轉(zhuǎn)換為動賓結(jié)構(gòu)(“睡好覺”),偏正結(jié)構(gòu)“小便”強勢轉(zhuǎn)換為動賓結(jié)構(gòu)(“小便小不出來”),甚至貌似不可分析的連綿詞、音譯詞也難擋漢字的游離,連綿詞“慷慨”強勢轉(zhuǎn)換為動賓結(jié)構(gòu)(“慷他人之慨”),音譯詞“幽默”強勢轉(zhuǎn)換為動賓結(jié)構(gòu)(“幽他一默”)。這一因漢字特點而造成的理解上的分合二重性,稍加擴展就成為漢語表達中習以為常的“結(jié)構(gòu)重新分析”。
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音韻節(jié)律的基點也是“字”。“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聲,或用仄聲;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jié)迥異。故字句為音節(jié)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jié)見矣;歌而詠之,神氣出矣。”(劉大櫆《論文偶記》)漢語的表達,天然講究對稱與和諧。這種講究,在口語中粗放地表現(xiàn)為單雙音節(jié)的配合,而一旦要深究其規(guī)律,必須推敲書面語中每一個字的音韻表現(xiàn),所謂“神氣不可見,于音節(jié)見之;音節(jié)無可準,由字句準之。”(《論文偶記》)“字正”才能“腔圓”,字音是句子音律的基礎(chǔ)。在漢語的句子組織中,意義的基點也是“字”。漢語是一種高度依賴語境的語言。漢語的說話人奉行“聽話人負責”的言說策略,對聽話人的默契有很深的信任。因此漢語句子的建構(gòu)講究“人詳我略”。句子的意義依靠有限的文字作充分的意會,這樣的文字在句子的理解中就成了一個一個的意義支點,在多方意會中靈活地組合起來,字義成為句義乃至篇章之義的基礎(chǔ)。漢語句子的理解,在“字斟句酌”和“字里行間”展開,形成“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shù)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王充《論衡?正說》)的意義格局。這樣一個特點,造成了中文簡潔凝練、靈活自由的風格,這也是為什么唐詩和宋詞成為中國古代文學的高峰。正如張新所說:“中國文字這種高度凝聚力,對短小的抒情能勝任,而對需要鋪張展開描述的敘事卻反而顯得太凝重與累贅。所以中國詩向來注重含蓄。所謂練字、詩眼,其實質(zhì)就是詩人企望在有限的文字中凝聚更大的信息量即意象容量。”[3]漢字的凝練是中國文學充滿詩意、中國人的思維充滿豐富的意象和詩意的重要原因。中國語文研究傳統(tǒng)高度評價“字”在漢語結(jié)構(gòu)的組織和理解中作為基本要素的功用。劉勰指出:“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句之精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文心雕龍?章句》)我在上世紀80年代的博士論文《〈左傳〉句型研究》中曾指出:“(劉勰)強調(diào)‘因字而生句’,這是同西方形態(tài)語言的因‘框架’(形態(tài)配合關(guān)系)而生句完全異質(zhì)的一種組織方略。因‘框架’而生句,以大統(tǒng)小,以虛攝實,是先有句法關(guān)系模式,然后在這個圖式內(nèi)的各條‘透視線’上刻意經(jīng)營。這是一種靜態(tài)的空間體造句。因字而生句,是以小組大,散點經(jīng)營,以流程見局勢。這是一種動態(tài)的時間流造句。劉勰所謂‘正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其中的‘本’、‘一’,都體現(xiàn)出漢語句子以‘字’為立足點的建構(gòu)而非‘填構(gòu)’的語言組織方略。”
當然,就漢語句子的格局而言,僅僅有字的立足點還是不夠的,字的運用必須和“氣”聯(lián)系起來,并且渾然一體,形成句讀段,才能產(chǎn)生強大的鋪排延宕能力,使?jié)h語的思維和表達流動起來,在語境的觀照下形成生發(fā)語義的整體(這一點,正是后來有人提出的“字本位”語法的很大的局限)。而“氣”的形成,依然是“字”的有節(jié)律的組合。汪曾祺曾提出過一個觀點:作為漢字書面語的詩歌和小說,用口語朗誦,甚至配樂朗誦,聽上去就像隔靴搔癢,很不過癮,因為離開了漢字視覺,會損傷原作的意境。他以柯仲平的“人在冰上走,水在冰下流……”為例,指出:“這寫得很美。但是聽朗誦的都是識字的,并且大都是有一定的詩的素養(yǎng)的,他們還是把聽覺轉(zhuǎn)化成視覺的(人的感覺是相通的),實際還是在想象中看到了那幾個字。如果叫一個不識字的,沒有文學素養(yǎng)的普通農(nóng)民來聽,大概不會感受到那樣的意境,那樣濃厚的詩意。‘老嫗都解’不難,叫老嫗都能欣賞就不那么容易。‘離離原上草’,老嫗未必都能擊節(jié)。”因此,漢字書面語的閱讀效果比耳聽更好。與其聽書,“不若直接看書痛快。”
篇3
關(guān)鍵詞:閱讀教學;經(jīng)典語段;習作起步
中圖分類號:G623.2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3-0034-01
《語文新課程標準》對三、四年級學生習作的要求是"留心周圍事物,樂于書面表達,增強習作的自信心。愿意將自己的習作讀給人聽,與他人分享習作的快樂。"剛進入三年級的學生,由于不明白作文的規(guī)范性,缺乏生活經(jīng)驗和習作經(jīng)驗,常常感到寫作文很吃力,往往對寫作文有畏難情緒和厭倦心理。這一現(xiàn)狀迫使作為教師的我們陷入沉思:怎樣才能使學生由不會寫作文,怕寫作文到愿寫作文,會寫作文甚至愛寫作文呢?著名作家、教育家葉圣陶先生說"教材無非是個例子。"認真研讀教材后,我發(fā)現(xiàn)小學語文教材中的課文,篇篇文質(zhì)兼美,意境雋永,尤其是其中的經(jīng)典語段更是三年級學生習作起步的最佳范例。于是我做了《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書面表達》的小課題研究。經(jīng)過一年的探索與實踐,我發(fā)現(xiàn)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書面表達是激發(fā)學生習作興趣,增強習作信心,提高寫作能力的一條捷徑。那么怎樣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書面表達呢?
1.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豐富語言
處于三年級年齡段的孩子特別愛動、好玩,對周圍事物充滿了好奇,他們愛說、想說,喜愛表達,但卻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描述自己的聞和表達心中的感悟。這些合適的語言從哪兒習得呢?當然應(yīng)該在閱讀中習得。在閱讀教學中,教師要有意識的豐富學生的語言,讓學生跟著作家學習遣詞造句。例如:三年級上冊第一課《我們的民族小學》的最后一自然段:"這就是我們的民族小學,一所邊疆的民族小學。"作者用一就話來表達對自己母校的贊美和懷念。我在教學時,就讓學生像作者一樣贊美我們我們的學校。 "這就是我們的學校,一所( )小學。"學生們就會說:"這就是我們的學校,一所(農(nóng)民工子女)小學。""這就是我們的學校,一所(干凈整潔的)小學。"接著我又叫學生夸贊我們的家鄉(xiāng)重慶,學生們就說出了這樣的句子:"這就是我的家鄉(xiāng)重慶,一座山清水秀的城市。""這就是我的家鄉(xiāng)重慶,一座美麗山城。"最后又叫他們夸贊自己想夸贊什么就夸贊什么。三年級上冊的課文中像這樣的經(jīng)典語言很多,如第二課《金色的草地》第二自然段中的"就這樣,這些并不引人注目的蒲公英,給我們帶來了不少快樂。"第四自然段中的"多么可愛的草地!多么有趣的蒲公英!"只要老師在閱讀教學中適時引導(dǎo)學生模仿,學生自然而然就會表達自己心中的感悟了。
學生不但要學會表達心中的感悟,還要學會描述自己所看到的事物。三年級上冊第十一課的第二自然段:" 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繽紛的顏料。你看,它把黃色給了銀杏樹,黃黃的葉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哪扇哪,扇走了夏天的炎熱。它把紅色給了楓樹,紅紅的楓葉像一枚枚郵票,飄哇飄哇,郵來了秋天的涼爽。金黃色是給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紅色是給果樹的,橘子、柿子你擠我碰,爭著要人們?nèi)フ兀∠勺拥玫降念伾透嗔耍霞t的、淡黃的、雪白的……美麗的在秋雨里頻頻點頭。"作者運用了比喻擬人的的手法生動形象的描寫自己看到的秋天的景物。我在教學這一段時,不僅讓學生背下這些語句,而且讓學生練習像作者一樣描寫校園里的景物。
2.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觀察方法
《小學語文新課程標準》習作要求中段學生"留心周圍事物,樂于書面表達。"就是將習作表達的視野引向生活,要求學生善于觀察生活,了解社會,發(fā)現(xiàn)與探索自然。三年級的學生在習作時不知道寫什么,無話可說,不是因為他們沒有觀察周圍的事物,而是他們不知道怎樣仔細觀察,在他們的心中觀察就是看一眼,當然就很少有新奇的發(fā)現(xiàn),更沒有想表達的沖動。要想讓學生在習作中有話可說,老師必須教會學生一些常用的觀察方法,讓學生學會仔細觀察,養(yǎng)成留心觀察周圍事物的習慣。老師什么時候教,怎樣教學生觀察方法呢?當讓步是習作指導(dǎo)時的空洞說教,而是在閱讀教學利用可課文經(jīng)典語段,引導(dǎo)學生揣摩,感悟作家觀察事物時所用的方法,并拿來用在自己的觀察中。
3.跟著課文經(jīng)典語段學習構(gòu)段方法
篇4
一、詞性的非常規(guī)化
詩歌中為表情達意的需要而臨時改變詞性是很常見的現(xiàn)象。余光中的《碧潭》寫道:“如果碧潭再玻璃些/就可以照我憂傷的側(cè)影/如果舴艋再舴艋些/我的憂傷就滅頂”。句中的“玻璃”、“舴艋”本為名詞,在這里,余先生用作動詞,其用語新奇,意蘊豐厚。“玻璃”透明, “舴艋”小巧,詩句蘊含著在清澈透明的水中泛舟,思念的憂傷己使小船承載不起。余光中先生在這里,活用詞類,新穎別致,引人聯(lián)想。蔣捷《一剪梅?舟過吳江》中的:“流光容易把人拋,紅了櫻桃,綠了芭蕉。”“紅了櫻桃,綠了芭蕉”,其中的表顏色的形容詞“紅”和“綠”在詩中都活用作動詞,將無形的不可捉摸的意象轉(zhuǎn)化為具體可感的事物,生動形象,深受后人喜愛。
二、搭配的非常規(guī)化
是指兩個詞突破規(guī)范而在一起使用,以形成一種陌生化的新奇語言效果,使之萌生出新的意蘊,增加詩的美感。如徐志摩的《沙楊娜拉》中的“那一聲珍重里有甜蜜的憂愁”,原本憂愁和甜蜜是毫不相干的,但這種反常搭配用在詩中,則表達了詩人與日本女郎臨別時內(nèi)心復(fù)雜的情感,“甜蜜”是在回憶往昔相處的甜蜜,“憂愁”是因為離別在即,“甜蜜的憂愁”是一種跨越時空的兩種對立情緒的搭配,起到了一種耐人尋味的審美藝術(shù)效果。再如宋代杰出女詞人李清照《武陵春》詞云:“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詞人想借泛舟雙溪排遣凄楚心情,卻又恐怕她的哀愁太深太重,一只形似蚱蜢的小舟無以承載,由此可見詞人的哀愁何其多何其深,舴艋舟又輕又小,哀愁又多又重,在愁重舟輕的鮮明對比中,大大增強了抒情的力度與深度。
三、修辭的非常規(guī)化
比喻、雙關(guān)、指代、夸張、用典、互文、避復(fù)、連及、列錦等是詩歌中廣泛運用的修辭手法,它不僅能造成語言的陌生化,同時也能實現(xiàn)詩歌的最佳隱喻效果。富有新意的修辭手法不但能恰當?shù)孛枘∏闋睢⑹愀校移浞浅R?guī)性會給人一種語言的沖擊力,甚至形成獨特的“張力”。勇于創(chuàng)新的詩人總是在前人的基礎(chǔ)上推陳出新,《六月,我們看海去》里就有一些非常規(guī)性的反復(fù):“六月是我們的季節(jié)很久我們就期待我們期待了很久/看海去看海去沒有駝鈴我們也要去遠方”。此詩除了題目有一標點,全詩沒有其他標點,造成整體上的陌生化效果,同時詩歌也用“看海去看海去沒有駝鈴我們也要去遠方”進行首尾反復(fù)。這個句子里作者還很冒險地使用了非常簡潔、直白的句內(nèi)反復(fù),充分表達出青春少年出門遠行的迫切愿望,其語氣、語味非常符合青春少年風風火火、歡歡樂樂、匆匆忙忙的年齡特點。再如“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溫庭筠《商山早行》),全句以名詞或名詞短語組成,里面沒有一個動詞或形容詞謂語,完全不符合我們?nèi)粘5谋硎隽晳T,但寫景抒情、敘事述懷卻異常突出,這正是運用了列錦的修辭法。明代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談到,此二句“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于言意之表,不知二句中不用一二閑字,止提掇出緊關(guān)物色字樣,而音韻鏗鏘,意像俱足,始為難得。”
四、語序的非常規(guī)化
就是詩人有意突破慣常的語法規(guī)范,在語言的組合次序上造成一種新奇感,從而引起讀者的審美注意。詩中語序的顛倒,主要包括句中詞序的顛倒和篇中句序的顛倒兩種情況。
詞序的顛倒。如我們熟悉的杜甫的名句“香稻啄余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這兩句詩的正常語序應(yīng)該是“鸚鵡啄余香稻粒,鳳凰棲老碧梧枝”,但“語不驚人誓不休”的杜甫把語序顛倒過來,詩意卻因此鮮明而且豐富了。周振甫分析說:“原來杜甫這詩是寫回憶長安景物,他要強調(diào)京里景物的美好,說那里的香稻不是一般的稻,是鸚鵡啄余的稻;那里的碧梧不是一般的梧桐,是鳳凰棲息的梧桐。所以這樣造句,就是‘香稻――鸚鵡啄余粒,碧梧――鳳凰棲老枝’,采用描寫句,把重點放在香稻和碧梧上,是側(cè)重的寫法。要是改寫為‘鸚鵡啄香稻余粒,鳳凰棲碧梧老枝’,便成為敘述句,敘述鸚鵡鳳凰的動作,重點完全不同了。再說,照原來的描寫句,側(cè)重點在香稻碧梧,那么所謂鸚鵡啄余、鳳凰棲老都是虛的,只是說明香稻碧梧的不同尋常而已。要改成敘述句,好像真的有鸚鵡鳳凰的啄和棲,反而顯得拘泥了。”杜甫將句式切斷和重組,使語序倒裝,重點前置,不僅強調(diào)了重點,增強了視覺效果,而且還產(chǎn)生了富于彈性的美感效應(yīng),讓讀者在反復(fù)品味中獲得多層次的意蘊和美感,因而使詩意增值。正如沈括所言:“語反而意寬。”徐志摩《再別康橋》中的“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別離的笙簫;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沉默是今晚的康橋!”是典型的主謂倒裝。設(shè)想一般性日常語言的表述:夏蟲也為我沉默,今晚的康橋也為我沉默。多么沉悶乏味!但徐志摩作為語言的魔術(shù)師,通過句法變異,展示了語言藝術(shù)的魅力。“夏蟲也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橋!”首先是符合文體要求,“康橋”與“笙簫”押韻;其次運用了頂真的修辭手法,“沉默”蟬聯(lián)而下,與“悄悄”相呼應(yīng),使外物與心境的靜默更具有連貫性。
句序的顛倒。如蘇軾的《水調(diào)歌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按通常句序應(yīng)是:“把酒問青天。明月幾時有?”但這就成了平庸之筆。其所以把“明月幾時有”提到句首,因為它是詩人突出的重心,同時也是格律的需要。句序顛倒之后,起勢突兀,精力彌滿,非常引人注目。再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小樹顫抖著》第一節(jié):“小樹顫抖著,當小鳥在上面飛。我的心顫抖著,當我想到了你。”這是一首被翻譯成六十多種外語的愛情小詩,深受廣大讀者的喜愛。這節(jié)詩先寫結(jié)果,后寫原因,頗耐人尋味。小樹為什么顫抖著?原來是有小鳥在上面飛。我的心為什么顫抖著?因為我想到了你。前兩行若按古代詩論的說法,是“起興”;若按現(xiàn)代詩論的觀點,則是一種隱喻。前后互相生發(fā),注入了情趣,增濃了詩意。如果按正常語序。先說原因,后說結(jié)果。又將如何?當小鳥在上面飛,(所以)小樹顫抖著;當我想到了你,(所以)我的心顫抖著。這就成為對二者因果關(guān)系的解釋和說明,詩味蕩然無存了。可見有時句序的顛倒確有造成懸念,刺激審美注意,增強情感張力的藝術(shù)效果。
五、邏輯的非常規(guī)化
詩歌創(chuàng)作中,常常有一些“無理”的、不合常規(guī)的表現(xiàn)。比如月亮多情、花朵含笑、丁香結(jié)愁……至于“淚眼問花”、“怨春不語”、“淚染霜林”,從邏輯的角度看是不合事理的,但用藝術(shù)的眼光看,卻是情感真實的最高表現(xiàn)。唐代金昌緒的《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是寫女主人公盼望心上人,心情急切;喜鵲的幾聲鳴叫就把她引向了門前,終因未能如愿而遷怒于不諳人事的喜鵲;由于思念心上人竟然對啼叫的黃鶯兒大動肝火,雖然“怒”得無理,怪得“奇怪”,但卻合乎人情。正所謂“情有者理必無,理有者情必無。”我們再來看現(xiàn)代詩人顧城的《遠和近》:“你/一會看我/一會看云/我覺得/你看我時很遠/你看云時很近”,這里存在著有趣的“物理距離”和“心理距離”的演變:“你”與“我”的物理距離實際上很近,但“我”覺得“很遠”;“你”與“云”的實際距離很遠,而“我”卻覺得“很近”。從現(xiàn)實生活的真實距離來看,這完全是悖理的,為何作者要違背常規(guī)顛倒遠近呢?把它放在更深的語境,這是詩人的一種特定的心理,是詩人所感應(yīng)的人際關(guān)系的缺憾和追求美的協(xié)調(diào)所致,是不正常的環(huán)境帶來的人的隔膜使然。這種事理上、情感上的邏輯變異,反而使詩歌蘊涵了更深刻的含義,如果剝離了這種變異,詩歌反而索然無味。
篇5
一是習作對象內(nèi)容空洞,或不合邏輯,或常識錯誤,即言之無物。如一位同學這樣描寫新疆喀納斯,“我們來到了臥龍灣,只見四周森林茂密,繁花似錦,綠草如茵,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經(jīng)過與小作者交談,筆者得知學生游覽時觀察不細致,習作時憑借模糊印象,再調(diào)動自己積累的好詞好句,就出現(xiàn)了多種景象云集的不合邏輯的情況。
二是習作語言干巴無力,或缺乏想象,或詞句單一,即言之無文。如一位同學寫小蠻腰:“小蠻腰的夜景很漂亮,整個塔身五光十色,有藍色、黃色、綠色、紅色、紫色,真好看!一到放煙花的時候就更漂亮了,煙花千奇百怪,有的直接發(fā)射,有的繞著小蠻腰發(fā)射,真是壯觀!”這段文字描寫了小蠻腰的夜景,光色和煙花,求真求實,若整篇文章都是這樣的文字,就會缺少想象、詞句單一,語文的味道不濃。
三是習作雜亂無章,或段落無序,或句子無序,即言之無序。如一位同學描寫自己的小區(qū),先寫門口花壇如何美不勝收,再寫小區(qū)如何大、是孩子們的娛樂天地,最后又掉過頭寫花壇如何美,顯得結(jié)構(gòu)混亂。
因此,筆者以人教版部分寫景課文和其他課文的部分段落為閱讀材料,結(jié)合寫景習作模型,探索文本的寫景規(guī)律,做了一番“言之有物”“言之有文”和“言之有序”的嘗試,為提高小學生的寫景能力提供新的途徑。
一、 觀察有道,言之有物
一般來說,觀察的完成需要經(jīng)過三個步驟:占有表象、比較差異、篩選要點。考慮到寫景特點,筆者認為觀察景物要做到如下三步。
1.整體印象
第一印象一般是整體的,可運用多覺法、跟蹤法、鳥瞰法等欣賞景物的整體及構(gòu)成景物的要素,如:《桂林山水》,整體感覺是山水如畫;學習《頤和園》后,人們感覺頤和園是一個美麗的大公園。
2.篩選要點
巴爾扎克曾說“細節(jié)成就作品價值”。在欣賞整體美的感覺下,總有一兩處景物格外引人注目。如《桂林山水》,最吸引人的還是桂林的山和漓江的水,其他景物,如空中迷蒙云霧、山間綠樹紅花、江上竹筏小舟只做點綴。
3.抓住特點
景物是豐富多彩的,通過比較觀察,能夠欣賞景物與眾不同的特點。同樣描寫山,繁花似錦的七月的天山、如筍似玉的桂林的山、云霧飄渺的黃山,就有很大不同,吸引游客的魅力也不一樣。如《索溪峪的“野”》一課,張家界的風光千奇百怪,最吸引人的卻是它的“野味十足”,繼而通過山野、水野、動物野和人野四個方面展開描寫。筆者以《桂林山水》為例,引導(dǎo)學生重溫觀察景物的三個步驟。
師:桂林山水給作者的總體印象是什么?
生:桂林山水甲天下。或者“舟行碧波上,人在畫中游”。(總體印象)
師:《桂林山水》寫了哪些景?
生:漓江的水,桂林的山,還有竹筏小舟、綠樹紅花。
師:最能體現(xiàn)桂林風光甲天下的是什么景?
生:漓江的水和桂林的山,即桂林山水。(篩選要點)
師:桂林的山水和其他地方的山水有什么不同?具體描述一下。
生:漓江的水……桂林的山……(抓住特點)
師:你們?nèi)ミ^哪處景點?總體印象如何?里面有哪些景物?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它有什么特點?具體描述一下。請依據(jù)這些提示寫一寫。
學生之所以寫不出什么東西,言之無物,主要是因為其觀察的精確性不高、判斷力不準、目的性不強。有人對小學生的觀察力進行了實驗研究,結(jié)果顯示:高年級學生觀察的精確性提高,對事物進行分化觀察的能力增強,但不具普遍性;開始區(qū)分觀察事物的主次特征,注意有表現(xiàn)力的特征,但不具普遍性;一般能按先后順序觀察;觀察目的性增強,但與低年級學生的隨意觀察無顯著差異。精確性與判斷力方面的特性反映到學生習作中就是容易出現(xiàn)言之無物,即描寫籠統(tǒng)、泛化,注意無表現(xiàn)力的特征,忽略有表現(xiàn)力的特征。以教材中的寫景文為范文,可以讓學生明白觀察的重要性,明白觀察是有路可循的,只有做到觀察整體、篩選要點、抓住特點,才可以將自己覺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的內(nèi)容寫清楚。
二、 養(yǎng)護想象,言之有文
想象實質(zhì)上是觀察的深化,如果說觀察是為了真實地反映景物的本來面目,是一種“無我之境”,那么想象就是景物在游客心目中的主觀呈現(xiàn),是一種“有我之境”,運用想象不僅可以增加作品的文采、藝術(shù)魅力,還可以讓景物的意境更有情,更能凸顯寫作者的獨特感受。
兒童心理學研究表明,小學生的思維以形象思維為主,表現(xiàn)在語言這一物質(zhì)外殼上,則是大量使用擬人、比喻。因此,寫景習作可以引導(dǎo)學生多用比喻、擬人等富有想象力的辭格,來抓住景物的特點寫清楚,傳達對景物的某種情感,增強習作的魅力。
筆者以《山雨》為例,重點引導(dǎo)學生通過聯(lián)想和想象表達自己對風景的獨特感受。
(學生已經(jīng)把握課文的描寫順序和描寫內(nèi)容)
師:作者運用什么表達技巧寫出山雨的韻味呢?結(jié)合相關(guān)語句說說。
生1:作者寫雨聲,用了比喻,把沙啦啦的小雨比喻成無字的歌謠,而且越來越清晰、響亮,突出了山雨越下越大的特點。
師:比喻的手法,抓住了雨勢的特點。
生2:作者寫雨聲,還加進了幻想的色彩,他把雨絲比喻成柔軟的手指,把巖石比喻成琴鍵,給人一種很唯美的畫面。
師:是什么樣的畫面?再想一想。
生3:山雨,像煙一般,雨里的一切都變得朦朧起來,雨姑娘優(yōu)雅地彈起鋼琴,琴聲美妙動聽。
師:也是比喻,卻隱含著一幅畫。作者正是通過聯(lián)想和想象,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山雨飄灑圖。同樣是描寫雨聲,如果這雨是下在別處,你又能聯(lián)想到什么呢?
生4:“啪噠,啪噠……”咦,是誰在敲打我的窗?掀開窗子,哦,原來是雨來拜訪了。
生5:雨越下越大,風越刮越狂,像極了森林狂想曲,不是狼嚎就是獅吼。
生6:雨過天晴,瓦片上的雨滴依然落個不停,滴在石板上,叮咚――,真是余韻悠長呀!
……
師:同學們的聯(lián)想真豐富,擬人、比喻可以幫助我們表達獨特的感受。
對六年級的學生來說,運用比喻、擬人來描寫景物并不難,難在抓住特點把景物寫優(yōu)美,寫出語文的味道,寫出自己的獨特感受。因此要在閱讀教學中不斷品味作者的遣詞造句,感受表達技巧,并結(jié)合文本情境再造畫面以調(diào)動學生已有的生活經(jīng)驗,激發(fā)學生的靈感,做到言之有文。
三、 理清表達,言之有序
1.觀之有序,言之有序
觀察要有一定的順序,思維才有條理,表達才能層次分明,否則,事倍功半。小學生習作中出現(xiàn)最多的順序就是觀察順序,觀察到什么就先寫什么。因為學生觀察的無序,導(dǎo)致了習作的無序。因此引導(dǎo)學生有序觀察,就非常必要了。從課文中,我們可以學到一段時間內(nèi)景物的時間變化順序,如《小興安嶺》的“春夏秋冬”和“早中晚”,《錢塘江大潮》的“潮來前、潮來中、潮過后”,甚至《火燒云》中的短暫時間變化順序“一會……一會……”。
2.移步換景,游中有序
按照一定的順序?qū)懢埃瑢W生基本能掌握時間變換的順序,但在運用空間變換的順序時容易出現(xiàn)混亂,特別是定點觀察和游覽兩種。定點觀察就是固定觀察點,按照視線移動的順序,依次寫出景物,或由遠及近,如《觀潮》;或由近及遠,如《山中訪友》等。而游覽就是邊走邊看,移步換景。要想讓學生會用游覽順序,宜采取“扶――半扶半放――放”的方式,鼓勵學生從課文入手,找出游覽的語句,抓住游覽的動詞,畫出游覽示意圖;再領(lǐng)著學生游覽一下校園,沿著自己的足跡逐一觀察發(fā)現(xiàn)的美景,并在自己的本子上記錄自己曾經(jīng)到過的地點、看到的風景,畫出游覽圖;最后讓學生自己用學到的方法獨立完成習作。
筆者以《頤和園》為例,引導(dǎo)學生理清文路,言之有序。
師:自由讀課文的2~5自然段,畫出每個自然段的第一句話?
(“進了頤和園的大門,繞過大殿,就來到有名的長廊”,“走完長廊,就來到了萬壽山腳下”,“登上萬壽山,站在佛香閣的前面往下望,頤和園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從萬壽山上下來,就是昆明湖”。)
師:開火車讀畫出的第一句話,想想這是什么順序?(游覽順序)
師:請把作者游覽過程的動詞圈出來,再把作者的旅游路線畫下來。
師:讓我們到校園里走一走,寫寫我們的游覽順序。
師:根據(jù)剛才的游覽,寫一處景物。例如:進入校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這是筆者在發(fā)現(xiàn)一些學生不會運用游覽順序時做出的一次補救,旨在探索文路、體會文章的結(jié)構(gòu)美,并不惜時間把課堂搬到了校園,讓學生在游覽中學習游覽順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果是在習作前進行這樣的指導(dǎo),相信效果會更突出。
綜上所述,寫景習作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觀察、想象、表達缺一不可。觀察,求真,讓習作有話可寫,言之有物;想象,求美,讓習作生動形象,言之有文;表達,求清,讓習作文路清晰,言之有序。
參考文獻
[1] 潘新和:語文:表現(xiàn)與存在[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2] 林可夫.基礎(chǔ)寫作概論[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
[3] 張明.小學生心理健康教育[M],北京:中國輕工業(yè)出版社,2009.
[4] 王崧舟.“寫作本位”:讀寫觀念的重構(gòu)――著名語文教育家潘新和先生言訪談錄[J].小學語文教師,2008(6).
篇6
關(guān)鍵詞:杜甫;吳體;拗體;拗律;拗格
中圖分類號:I207.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972(2008)05-0068-06
杜甫在《愁》一詩之下曾有自注:“戲為吳體。”后世學者一般認為,杜甫所說的“吳體”即拗體。這類詩以七言為主,在杜集內(nèi)數(shù)量不小,面貌引人注目,宋代以來,對此的關(guān)注,已成為整個杜詩研究的一大重要問題。但直到現(xiàn)在,這項研究依然還疑點重重。
一、七言八句的七古不是拗律嗎
討論杜甫七言拗律,一般是在浦起龍《讀杜心解》所編的151首內(nèi)討論。金啟華從中拎出18首進行詮釋,認定為拗體七律。鄺健行同樣是在這個范圍中考察,得出的結(jié)論是:拗得顯著的26首,大拗的7首。韓成武則從中區(qū)分出113首嚴整七律和38首七言八行體詩。
不過,浦起龍的分體是否可靠,這是需要追問的。筆者以為需要對杜詩中所有字數(shù)、句數(shù)與七律相同的詩進行研究,而《讀杜心解》卷二所編141首七古中便有32首為八句體七言詩。這32首分別為《秋雨嘆三首》《戲贈閿鄉(xiāng)秦少公短歌》《題壁上韋偃畫馬歌》《越王樓歌》《海棕行》《姜楚公畫角鷹歌》《光祿坂行》《苦戰(zhàn)行》《去秋行》《漁陽》《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發(fā)閬中》《天邊行》《閬山歌》《閬水歌》《青絲》《引水》《近聞》《秋風二首》《縛雞行》《折檻行》《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大覺高僧蘭若》《自平》《夜歸》《前苦寒行二首》《發(fā)劉郎浦》《夜聞篥》,現(xiàn)代讀者不容易把它們與七律區(qū)別開來。現(xiàn)在不妨從這32首詩的討論開始。
王力在《漢語詩律學》中指出,律詩有三個要素,即字數(shù)合律、對仗合律、平仄合律。他提出了簡單的分辨似律非律詩的方法,即: “如果三個要素具備,就是純粹的律詩;如果只具備前兩個要素,就是古風式的律詩,亦稱拗律;如果只具備第一個要素,就不算是律詩,只是字數(shù)偶然相同而已。”但如果把討論范圍設(shè)置在所有八句體七言詩中,上述三要素的第一條似應(yīng)改為:協(xié)韻的合律。律詩要求通篇協(xié)一韻,不可換韻。這是基本規(guī)則,不可更易。
我們可以據(jù)此討論這32首詩。從用韻的角度審視,很容易就發(fā)現(xiàn):其中有24首換了韻,譬如《近聞》:“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凈,隴山蕭瑟秋云高。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shù)有關(guān)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yīng)難棄。”這首詩除字數(shù)、句數(shù)與七律無異外,三、四兩句還構(gòu)成對仗,但整體語感卻是明顯的古體味,其中關(guān)鍵的就在于:前四句協(xié)平聲四豪韻,后四句卻換協(xié)去聲四置韻。韻的變換徹底打破了律詩原有的在整體統(tǒng)一中實現(xiàn)轉(zhuǎn)折變化的韻律感,僅此就使它與律詩劃開了界線。這應(yīng)是不必再加商討的。
馀下的8首,加上浦氏編入的151首,為159首,正好符合方回在《瀛奎律髓》卷二五“拗字類”中“老杜七言律一百五十九首”的說法,方回言及的數(shù)字究竟何指,現(xiàn)在不得而知,此處也置而不論。若綜合考察這8首詩的用韻和對仗,可見四種類型。
第一類包括《閬水歌》和《秋風二首》其二。兩詩用的都完全合乎律詩規(guī)定,都是平聲韻一韻到底,而且《閬水歌》中間四句構(gòu)成兩幅對仗,《秋風二首》其二則第三、四句相為偶對,它們與其他被向來認定為拗律的詩是否同類,似乎很難看出什么區(qū)別。
第二類包括《閬山歌》和《光祿坂行》 《發(fā)閬中》。《閬山歌》:“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云,江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斗且未歸,應(yīng)結(jié)茅齋著青壁。”前四句協(xié)韻字為人聲陌韻,后四句為入聲錫韻。此二韻為鄰韻,詩中本多通協(xié),故此詩可視為未換韻的仄韻詩。另外,詩的中間四句為兩幅精妙對仗,全詩聲調(diào)的拗峭與整體韻律的和諧,形成耐人諷誦的美感。《光祿坂行》《發(fā)閬中》也協(xié)仄韻,但各有一個對仗聯(lián)。它們與律詩的貼合程度究竟如何認定,應(yīng)是需要討論的。
第三類包括《去秋行》《天邊行》二詩,它們協(xié)仄韻,與上一類不同的是沒有對仗聯(lián)。第四類為《秋風二首》其一,用韻與第一類全同,但沒有對仗。這兩類又該如何認定,也需要特別加以討論。
現(xiàn)在不妨作進一步討論。前述三要素的用韻,這8首詩中的第一類符合拗律規(guī)定,據(jù)此可視其為拗律。按照詩律學者的意見,仄韻律詩罕見,但仍然是允許的,那么第二類也有進入拗律的資格。而如果規(guī)定律詩“不許通韻”,則《閬山哥歌》不是拗律,而同類的《光祿坂行》《發(fā)閬中》兩詩沒有鄰韻相協(xié),則更有理由成為拗律。再考慮第二要素即對仗,律詩一般中間兩聯(lián)對仗,由此看來,第三、四兩類應(yīng)排除在拗律的范圍之外,第一、二類中的《閬水歌》最有資格成為拗律,《光祿坂行》《發(fā)閬中》和《秋風二首》其二只有一聯(lián)對仗,也講究了對仗,可以視為拗律。若“不許通韻”的規(guī)定不過于嚴苛,《閬山歌》似亦可視作拗律。據(jù)此可知,浦起龍收入七古的32首八句體詩,可當作拗律看待的似僅有此5首。
相關(guān)的是,《讀杜心解》中收入卷四的《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似乎把它歸入古體。筆者經(jīng)過比對,發(fā)現(xiàn)曾氏《十八家詩鈔》抄錄杜甫七律所根據(jù)的藍本即為《讀杜心解》,但曾氏抄錄的150首杜甫七律,惟獨只棄置了這一首。浦起龍沒有給出特別的說明,他顯然視其為當然的拗律。實際上,方回《瀛奎律髓》拗字類中就已收入了此詩,即是說,曾有權(quán)威認定此詩的拗律身份。
二、杜甫嚴整七律的認定
在全面討論拗律標準之前,先來看看正格七律(或稱嚴整七律)是怎樣的。
韓成武根據(jù)嚴格的律詩標準檢核《讀杜心解》卷四的151首詩,得出結(jié)論:其中有113首為嚴整的七律。
現(xiàn)在不妨對照金啟華所詳細討論過的18首七言拗律,具體觀察韓先生一一列出的113首嚴整七律名單,韓先生特別加以說明的有三首,為《題鄭縣亭子》《白帝》和《黃草》。同類而沒有注明的有《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這四首都各有一個音節(jié)不合律,前三首因使用地名所致,后一首開頭兩句“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大家(音為gū)”當平而仄,韓先生認為這樣的小失無損于全詩格律的嚴整。但是,金啟華卻視《題鄭縣亭子》為拗律。那么,未被金先生列出的另三首,按金先生的規(guī)則衡量,自然也為拗律無疑了。
另外,上述113首詩中的《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和《小寒食舟中作》,金先生認為是拗律,因為是它們各有一拗句。這兩個拗句分別是“東閣官梅動詩興”和“云白山青萬馀里”。原來,
“動”、“萬”兩字宜平而仄,同樣,“詩”、“馀”宜仄卻用了平聲字,與最標準的格式要求有出入。
與第一種情況近似的,金先生還舉了僅首句不合律的《見螢火》。此詩首聯(lián)為“巫山秋夜螢火飛,疏簾巧入坐人衣”,首句只要稍稍調(diào)整順序,改成“秋夜巫山螢火飛”,就完全合律。金先生分析認為“螢火”二字平仄倒,次句不救,認為是拗律。韓先生并不把此詩看作與《題鄭縣亭子》等同類,所列113首的名單中不見此篇,想必是因為“巫山秋夜螢火飛”這樣的詩句并非不可避免的需要違律,并且此句不合律的程度已達兩個節(jié)奏點。
第二種情況涉及到的是被王力稱為“平仄特殊形式”,即“仄仄平平仄平仄”(在五言中為“平平仄平仄”),王先生認為它可認為是“仄仄平平平仄仄”的另一式,兩式是“任人擇用的”。王先生統(tǒng)計了《唐詩三百首》中的仄起五律的尾聯(lián)出句,得到的結(jié)果為:在總共50首仄起五律當中,有25首的尾聯(lián)出句(第七句)用這種形式,更具體點是:平平仄平仄24首;仄平仄平仄1首;平平平仄仄7首;仄平平仄仄10首;平平仄仄仄8首。[41113筆者統(tǒng)計《唐詩三百首》中所有五七言律詩的相關(guān)句子,得出的結(jié)果為:
五律共80首,用到“平平平仄仄”、“平平仄平仄”及其近似平仄格式的詩句共156句,其中格式為“平平仄平仄”的39句,近似的3句,約占全部同型詩句的27%。
七律共53首,其中需用“仄仄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仄”與近似平仄格式的詩句共88句,實際所用前一式及其近似式的79句,后一式及其近似式9句。
筆者的統(tǒng)計顯示,王力的統(tǒng)計方法不夠科學,得到的結(jié)論有所偏差。郭錫良說“‘仄仄平平仄平仄’的句式,在近體詩中反而比“仄仄平平平仄仄”用得更普遍”,更不確切。但是,在五律中的“平平仄平仄”和七律中的“仄仄平平仄平仄”,雖然使用頻度有別,卻都是常用的。郭錫良認為應(yīng)看作“正格”而不是拗格,其意見是正確的。
具體落實到杜甫七律,檢核《讀杜心解》所收151首,用到“仄仄平平仄平仄”及其近似式的詩句共24首25句。這24首中,已被韓成武認定為嚴整七律的18首,如果用金啟華的標準,似乎韓先生所列的113首嚴整七律名單中,就得再減去上列各種情況,所剩的只有89首正格了,而拗體七律的數(shù)字至少有62首,拗體七律為其所有七律的41%,若加上前節(jié)所討論的5首拗體則有67首,比例約為43%。這樣的結(jié)果,顯然與歷來人們對杜甫七律的認識出入太大,只能說是標準定得過于嚴苛。
根據(jù)上述分析,筆者傾向于采用較為通達的態(tài)度來認定杜甫正格七律,那就是說,在滿足律詩的幾大要素時,允許有一定的彈性,個別性或偶然性的違律,不妨礙其為標準七律。因此,筆者不同意金啟華的嚴苛態(tài)度,認為韓成武所分辨的杜甫嚴整七律比較合理。也即說,可以優(yōu)先認定的杜甫正格七律約為113首。
三、杜詩不合律的表現(xiàn)方式
根據(jù)上面兩節(jié)的討論,《讀杜心解》卷四的全部151首詩和卷二的5首七言八句體詩,字句數(shù)全部合律,對仗和用韻也大致合乎要求,按一般觀點,只有在平仄聲調(diào)上細心體味,才能明白其合律與否。根據(jù)詩律學的知識,杜甫上述156首詩,不合律的表現(xiàn)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失對。律詩的根本美學規(guī)范是每聯(lián)從聲調(diào)、詞類等方面都力求保持相反而相成,對立而和諧,錯落而均衡。一聯(lián)的上下兩句平仄相對,正是基本要素,一首詩如果完全不顧及上下句的平仄相對,則將喪失作為律詩的美學品格。(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愁》、《晝夢》等幾首就屬于如此。大量拗句的使用,到了嚴重失對的程度,律詩之名恐難再適合其詩之實吧。而同樣失對,《曉發(fā)公安》《簡吳郎司法》只表現(xiàn)在首聯(lián);作于大歷二年末的《即事》,只因第三句違律而致失對;《立春》因首句前兩步節(jié)、第七句第一步節(jié)違律,而導(dǎo)致兩聯(lián)失對,這幾首的失對情況程度稍輕,與正格律詩相離不遠,似可視為拗體七律。
第二,失黏。律詩的整一性特征很重要的一個方面表現(xiàn)在聯(lián)與聯(lián)之間的黏合上。只是盛唐以前,尤其在七律中,失黏的現(xiàn)象還較多,這大約是因為七律產(chǎn)生不久,它與歌行的界線還不很清晰所致。然而,杜甫151首被認定的七律,未失黏的已居于絕對主導(dǎo)性地位,為133首,因此,有理由相信杜甫已經(jīng)完全掌握了七律的黏對規(guī)則。而另一方面,其失黏的七律也有18首之多,約占12%,又說明杜甫的確是有意識地進行突破。統(tǒng)計之后可見,其失黏有兩種類型,一是兩聯(lián)同時失黏,這種詩例7首,二是失黏表現(xiàn)于一聯(lián)之中,其中因頸聯(lián)而起的10首,因頷聯(lián)失黏的1首。平仄聲調(diào)的對與黏是律詩的本質(zhì)屬性,杜甫在這兩方面的出離,數(shù)量多達數(shù)十首,用拗律一詞來簡單解釋是否合適,這是應(yīng)該認真研究的。
第三,“三平調(diào)”。歷代詩律專家在研究大量詩例的基礎(chǔ)上提出了“三平調(diào)”的概念,認為:一個詩句的末尾三字都是平聲字,就稱為“三平調(diào)”,它是古體詩尤其是七古的標志性特征。然而,在杜甫151首七律中卻有多達14首出現(xiàn)了“三平調(diào)”,其中一半是既有三仄,又有三平,另一半僅僅出現(xiàn)三平。這種詩句的一再使用,使這批作品產(chǎn)生了拗峭奇崛的拗體效果。若僅有這方面的問題,直接認定為拗體,是非常合理的。
第四,孤平。王力曾在《全唐詩》里尋覓犯孤平的詩句,結(jié)果只找到高適和李頎各一例,因此指出:“犯孤平的句子少到幾乎找不著的程度”。不過,在杜甫151首七律中就發(fā)現(xiàn)了兩個這樣的例句:一是《雨不絕》的首句“鳴雨既過細雨微”,“過”應(yīng)讀為平聲,“既”和“細”均為仄聲,此例即為孤平。二是《覃山人隱居》的首句“南極老人自有星”,“老”和“自”為仄聲,“人”就成了孤平。按王力的說法,這是犯了大忌。但是就全詩而論,前首并不因孤平而顯得格外拗,后首的拗更主要表現(xiàn)在次句“北山移文誰勒銘”,此句連續(xù)出現(xiàn)的四個平聲字才是拗的根本原因。此條雖然詩律專家特加強調(diào),但就杜詩看來,尚非構(gòu)成拗律的主要因素。
上述有關(guān)平仄格式的四個方面,前二者關(guān)涉到律詩的根本特性,后二者是相對次要的方面,杜詩都有明顯的出離傾向。
除此之外,詩律學專家并不用作辨析考量的,其實還有一條節(jié)奏方面的因素。七律的誦讀節(jié)奏基本上可歸納為兩種方式,一是“二二二一”,二是“二二一二。其規(guī)則有兩項:
(1)“三字尾”規(guī)則。每個詩句的末尾一般需要有結(jié)合較緊的三字組合,不符合這一特征的句子讀來就接近于口語化或散文化。在這方面,杜甫的律詩造句是非常注重句意與上述誦讀節(jié)奏形式的統(tǒng)一,盡管有的學者歸納出杜甫七律的“三四”式、“二五”式、“一六”式、“五二”式等多種造句樣式,但又同時都看到:杜律多樣化的造句樣式對一般誦讀節(jié)奏并未形成很大的沖突,換言之,句意與節(jié)奏并不形成很大的矛盾。舉例來說,《登高》末聯(lián)“艱難苦恨繁
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按句意,其詞語構(gòu)成方式實為“二五”式,上句的“艱難”構(gòu)成語意段,“苦恨繁霜鬢”構(gòu)成第二個語意段,下句同此,但由于“繁霜鬢”、“濁酒杯”仍能有很強的結(jié)合度,以“二二二一”式節(jié)奏來誦讀仍然不妨礙句意。但在杜甫七律中也有與這條規(guī)則沖突較大的句例,如《白帝城最高樓》的第七句“杖藜嘆世者誰子”,因虛詞“者”只能與前四字結(jié)合,形成一個相對較完整的語意段,無法形成結(jié)合較緊的三字組合作結(jié)尾,讀來感覺異常怪異。此詩的拗體特征,這是極為重要的一個表現(xiàn)。
(2)與上項相關(guān)的規(guī)則是:律詩以兩個字占一步節(jié)為主,單字步節(jié)僅用于最后兩個步節(jié)。于是,七律的節(jié)奏式就應(yīng)避免出現(xiàn)“一二二二”、“二一二二”、“一一二二一”、“三一三”等類式樣。如《崔二”、“一一二二一”、“三一三”等類式樣。如《崔氏東山草堂》“盤剝白鴉谷口栗,飯煮青泥坊底芹”,雖然符合“三字尾”規(guī)則,但因句首的“盤”、“飯”從語意上無法與“剝”、“煮”結(jié)合為主謂結(jié)構(gòu),它們都是單字占用一個步節(jié),誦讀起來甚感拗硬。《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一方面,后四字構(gòu)成語意段,違背了常規(guī)的“三字尾”規(guī)則;另一方面,由于“船”、“如”和“花”、“似”在句內(nèi)均需要一個頓點,頓點過多,改變了律句和諧圓轉(zhuǎn)的美感特征。
然而,在分析詩語節(jié)奏時,需要特別指出:古漢語界向來是以邏輯化的眼光來歸納,往往將上例的“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看作是二五分節(jié),而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閣夜》)、“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宿府》)視為五二分節(jié),全作為非常規(guī)節(jié)奏看待。就杜詩而言,這樣的分析并不令人愜心當意。事實上,讀者賞讀時大多都會發(fā)現(xiàn),杜甫造句節(jié)奏平順者居多,奇異怪誕者為少。這是因為人們讀詩時,會以更為直接的方式進入詩意,而不需要轉(zhuǎn)換成符合語法規(guī)則的邏輯化語句。誦讀時,“春水船”、“老年花”的組合更為自然;“五更鼓角/聲悲壯”、“永夜角聲/悲自語”的讀法也比“五更鼓角聲德壯”、“永夜角聲悲伯語”更為讀詩者所采用。因此,分析杜詩節(jié)奏,凡在不產(chǎn)生嚴重歧義時,都應(yīng)盡可能納入常規(guī)節(jié)奏方式,也就是說,不應(yīng)將《閣夜》《宿府》等詩視為拗體。
根據(jù)以上標準衡量,卷二的5首,不合律比較明顯,卷四的151首中有38首分別在不同程度上有違于律詩標準。
四、總結(jié)性討論
很明顯,在認定杜甫拗體七律時,要把握兩方面的分界,一是律與非律的分界,二是七律正格與拗體的分界。理論上看,只有在前一方面的分辨中認定為律詩的,才能進入后一方面的分辨。然而由于浦起龍《讀杜心解》分體并非嚴格的邏輯性分辨,今人在《讀杜心解》卷四范圍內(nèi)討論拗律,顯然存在邏輯缺陷。因此,被許多學者認定為拗律的《十二月一日三首》其二、《愁》、《晝夢》、《早秋苦熱堆案相仍》、《江雨有懷鄭典設(shè)》等作品,雖然收錄于《讀杜心解》卷四,卻并不比收錄于卷二的((秋風二首》其二、《閬水歌》等更具有七律的資格。換言之,這些詩與其說是拗體七律,倒不如稱之為古體詩,浦氏把其中幾首收入卷四,另幾首收于卷二;方回以來的其他學者將杜甫本人自注“戲為吳體”的《愁》和其他近似的詩看作是拗律或“拗字類”詩,實際上是模糊了律詩的概念。按這樣一種態(tài)度,律詩已失去穩(wěn)定的性質(zhì)。
與此相反的是自董文渙以來的一些詩律學專家的態(tài)度。董在《聲調(diào)四譜圖說》中批評趙執(zhí)信《聲調(diào)讖誤以古體當拗律,以嚴守古、律界限為宗旨。韓成武《杜詩藝譚》一書即在董說基礎(chǔ)上,用嚴格七律的標準辨析出杜甫113首嚴整的七律。但是韓先生又否定拗律的概念,認為《讀杜心解》卷四中其馀38首不是七律,而只是“七言八行體詩”。這種看法概念清晰,合乎邏輯,對于認識律詩的性質(zhì)是有意義的。但是,由于中國傳統(tǒng)的思維方式并不是嚴格的邏輯思維,如果用邏輯式來表示,中國傳統(tǒng)最為常見的現(xiàn)象是:在對象A與非A之間總有中間性的似A非A的對象存在。譬如,文體中的詩與文,并非邏輯化的對立,它們之間還有似詩非詩、似文非文的賦。同樣,詩中的古體與律體的關(guān)系也是如此,在律詩形成期間固然有古律混雜的“齊梁體”,就是到了律詩成熟、定型以后,詩人們有時也還繼續(xù)寫作既有古體性質(zhì)又有近體性質(zhì)的詩。這類似古似律的詩如果一概都打入古體,律詩固然顯得很“純潔”,但古體不是成為混雜無比、大而亂之化之的混沌之物了嗎?古體的“純潔”又置于何地?顯然,這種態(tài)度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科學。
進一步地說,拗律概念既非杜甫,甚至也不是將拗律推波助瀾的黃庭堅提出,而是在南宋詩論家反思江西詩派經(jīng)驗教訓的背景下逐漸產(chǎn)生的。陳巖肖《庚溪詩話》曾以“聲韻拗捩”一語批評“江西格”,宋末方回則正式標出“拗字類”之目,但拗體、拗律的明確用語則似乎晚至明代中期以降才被詩學專家全面接受和采用。這當中,關(guān)于杜甫正格七律之外的七言八句詩的創(chuàng)作機制,一般的觀點認為是“以古人律”,也即認為杜甫在七律成熟后有意識地引入古體句律改造律詩,達到破棄正體格律的目的。其直接結(jié)果,則是形成了許多平仄聲調(diào)上毫無規(guī)律的拗句。而清代趙執(zhí)信、翟犟、董文渙則似乎傾向于提出:杜甫是在有意識地創(chuàng)制正體律詩之外的新格律詩,今人王碩荃等人則在更為具體的聲律分析與統(tǒng)計的基礎(chǔ)上,認為杜甫拗律不是蔑棄規(guī)律,而是在探索各種新的格律形式。
如所周知,并非所有八句的詩都可以稱之為律詩,《讀杜心解》卷二的七古類所收的32首七言八句體詩,雖然從表面外形看,很多人根本無法把它們與七律區(qū)別開來,但具有詩律專業(yè)知識者輕而易舉就能發(fā)現(xiàn)其中大多數(shù)為古體。同樣,浦起龍編入卷四的一些被稱作拗律的作品,如果脫離杜詩的環(huán)境單獨存在,也有相當一批會被人判定為古體。從平仄聲調(diào)去分辨,有學者經(jīng)過細致的聲調(diào)分析與統(tǒng)計,試圖描述出杜甫不合律的七言八句詩的平仄模式,但似乎沒有誰能說明詩人杜甫確實可以掌握這套復(fù)雜與精密的描述式。把所有這類出離常規(guī)格律的作品都看作是新格律詩,筆者以為并沒有說服力。
至于這些出離常規(guī)格律的作品究竟該看作是古體還是拗律,王力《漢語詩律學》提出的拗律分辨標準只有兩條,即字數(shù)與對仗,本文第一節(jié)根據(jù)一般詩律學常識增加了第三條即用韻。但即使如此,浦起龍卷二也仍然有5首基本合律,按詩律學的知識,它們應(yīng)歸入拗律,然而浦氏視其為古體,學界對此幾無爭議。可見,按詩律學的一般方法進行分辨,產(chǎn)生的結(jié)果與實際情況不符。
而且,上述5首中的《閬山歌》《閬水歌》和《光祿坂行》,詩題明確地標示了“歌”或“行”這樣的樂府題,浦起龍未將它們收入七律類,最大的可能是考量了作者本人所擬的詩題。此外的《秋風二首》其二,《讀杜心解》雖然收在七古類,但卻引邵長蘅評語云:“作律詩讀,格轉(zhuǎn)高老。”《杜詩詳注》也引胡夏客評語道:“似拗體律詩。”邵、浦、胡、仇四位杜詩專家似乎對它該看作古體還是拗律,一方面有躊躇,另一方面又傾向于拗律一端,終極依據(jù)不過是語感。再看《發(fā)閬中》一詩,歷來從沒有人把它當拗體七律來看,雖然在字句數(shù)、用韻、對仗等三方面基本符合拗律要求,其緣由應(yīng)是該詩缺乏律詩的渾融、整一之感,從語感(進而言之是章法)上更符合古體的常規(guī)。
如此看來,詩律形式因素之外的作者自我定位、語感或章法等也應(yīng)引入到古體與拗律的分辨中來。
在平仄和節(jié)奏等兩方面辨析古體與拗律,筆者提出兩條意見:
(1)“三平”、“三仄”、“孤平”或節(jié)奏上不合常規(guī)格律,這些特征會使詩作顯得峭拔、生新與怪異,但并不對律詩的本質(zhì)屬性形成悖離。辨析時若把握過嚴,用歷史的眼光看,這是把律詩靜態(tài)化了,當作了一成不變的體式,從發(fā)展的角度看,又顯然限制了律詩的活力。從寬,才是比較正確的態(tài)度。一首詩在符合律詩其他基本要求之后,若有這類表現(xiàn),可以看作是一種特殊的律詩,命名為“拗律”、“拗字詩”或“古風式律詩”,都無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