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家庭教育論文
時間:2022-05-26 04:10:00
導語:青少年家庭教育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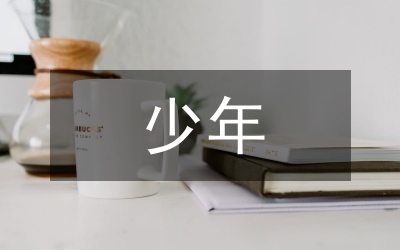
洛陽市澗西區人民法院少年案件審判庭審理了一起未成年人搶劫案件。該案在當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筆者特以此案為例,結合當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點,淺談一下現代社會中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問題。
案情:被告人張軍偉與同案犯李智輝、趙剛、郝南(已另案處理)在洛陽某電子游戲廳相遇(在案發前,張軍偉只認識李智輝)后,趙剛開玩笑地提出找人“練練”(指打架),其余三人均表示同意,四人即攔住剛從電子游戲廳出來的受害人王治、萬全(均十四歲),將二人帶到附近的某公司院內進行毆打,并將兩人身上的現金70余元及西服2件搶走。
當前未成年犯罪的特點
筆者綜合澗西法院歷年來所辦理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根據當前青少年犯罪的特點,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對未成年犯罪作以下簡要分析:
1、偶發性
據李智輝供述“我和趙剛、郝南在樂樂游戲廳玩,碰到張軍偉。趙剛說‘找兩個人練練’,我們都同意。然后我們就出去找人,正好有兩個人從對面的開心游戲廳里出來,張軍偉說‘站住’,就上去打了其中高個子一巴掌,跺他了兩腳……”
趙剛供述:問?“打人之前,你們是怎么商量的?”
答:“沒有商量,他們同意弄個人來打打。”
其他二名被告人的供述和李智輝、趙剛的供述一致。
四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和兩個均十四歲的孩子之間無緣無仇,僅僅是在玩過電子游戲后為了“找兩個人練練”,或者說是“找兩個人來打打”,尋求一下刺激,事發前并沒有作任何商量,而此時剛好遇到比他們年齡小、也比他們人數少的王治、萬全從游戲廳出來。于是王治和萬全成了他們四人的練習對象。在經過一番拳腳之后,他們還順手將兩名受害人的現金及衣物“拿”走。
在事發前,他們并沒有任何犯罪目的及犯罪目標,僅僅由于趙剛“找兩個人練練”這一句玩笑話,使四個人產生了找人打架的共同目的。在尋找練習對象時,剛好碰到了他們能夠打得過的王治和萬全,在毆打二人過程中才產生了索要錢財和衣服的目的。這一系列的動機和目的都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正是由此才一步步地從找人打架發展為搶劫,行為性質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事發前沒有明顯的犯罪動機和明確的作案目標,因簡單的一句話、一個眼神或一件小事發生口角,頭腦一熱,不考慮行為的后果,最終導致刑事案件的發生。事件發生的偶然性,這是當前青少年犯罪的一個最顯著特點。
2、盲目性
本案的四名被告人中,除張軍偉外,其余三人均為獨生子,三人的父母均為在職職工或干部,家庭條件較好。正如被告人李智輝在檢查中所寫的:“我感到十分后愧(悔),自已做出這么傻的事,自已家里也不缺錢,我卻去打人、還搶錢,當時不知道這種行為就是搶劫。經過公安機關的教育,我認識到了這種行為的嚴重性。”
本案的四名被告人均系初犯,在此之前未受過任何法律及行政處分,在犯罪時均為在校就讀的學生,其中除趙剛剛滿16周歲外,張軍偉、李智輝均不滿16周歲,而被告人郝南在犯罪時尚不滿15周歲。由于他們這個特定的年齡階段使他們在認識社會、辨別是非以及處理問題的能力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因而,形成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也是不完善的。他們對自己的行為不能夠很好地予以規范,當外界的情況發生變化時,他們不能夠加以控制。就本案來講,四被告人本來是出來玩電子游戲的,在其中一人提出找人打架時,其他人連考慮都不考慮,就積極響應。當另外有人提出搶錢時,他們又忘記了他們當初找人的目的是為了打架的。由此看出,這個年齡段的孩子在做一件事之前沒有特定的目的,隨著情況的變化,目的也隨之而變化,當自己的行為觸犯了法律的時候還渾然不知。
在對受害人的毆打過程中,四被告人不計后果地的朝其面部、頭部進行拳打腳踢,并用拳刺、木棍等對受害人實施侵害。如受害人萬全講“木棍都打斷了”,公安機關的提取筆錄也和受害人的陳述相印證。由此看來,這個時期的青少年對自己行為的危害程度也不能作出適當的預測,像拳刺、木棍等,如果擊中人體的要害部位完全有致人重傷、死亡嚴重后果的可能。他們在做某件事情時的行為和要達到的實際效果往往不能統一起來,在是非識別能力方面是比較模糊的,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在頭腦中沒有一個明確的界限。雖然當今各國刑法在立法時對這種客觀情況也給予了充分的考慮,對此年齡階段的犯罪行為作出了予以從輕或減輕處罰的規定,但量刑上的從輕或減輕畢竟是事后的懲罰,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青少年的法制觀念,加強預防措施,避免這種盲目行為的發生。
3、團伙性
據有關資料表明:“處于青少年階段的未成年人和同齡人相處的時間要遠遠多于其他年齡段的孩子,他們更愿意和同齡的孩子交朋友”。隨著年齡的增長,處于該階段的青少年逐漸地和父母有所疏遠,有些事情不再依賴父母了,同時他們和同年齡段的孩子接觸多了。這個時期的孩子在思想上認為自己已經是大人了,當他們受到欺負或委屈時寧愿告訴同伴而不愿意告訴家長和老師,在這種情況下,如果忍讓,就可能成為被欺負的對象,如果反抗則可能采取過激行為,最終導致校園搶劫、校園傷害等未成年犯罪的發生。
本案中的被告人張軍偉和李智輝、趙剛、郝南三個人是在電子游戲廳時認識的,并且在事發前張軍偉和趙剛、郝南根本不認識。在張軍偉的檢查中,他是這樣說的:“我在游戲廳碰到了李智輝和另外兩個孩子,那兩個孩子叫什么當時我也不清楚,后來才知道他們分別叫趙剛和郝南”。四個年齡相當的孩子遇到一起,在剛剛認識后,在連對方的名字都不知道的情況下,當其中一人提出一個非法的行動后,其他人就能很輕易地參與,這不能不說和這個年齡段的孩子的性格特點是分不開得。正如專家所講“當他們和父母、老師的關系疏遠的時候,他們就會出于本能地向同齡人靠近”。這個階段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子)他們逞強好盛,以講哥們義氣為榮,總認為只要共同參加一些活動(即使是非法的),就是所謂的“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朋友。于是他們以最本能的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的原則,選擇了兩個比他們年齡小的孩子進行所謂的“練練”。不僅將兩人打傷了,并且不搶走了兩人的現金和衣物,四個被告人也因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當今的家庭教育之我見
本案被告人李智輝、趙剛、郝南和被告人張軍偉分別代表了當今未成年人犯罪的兩個方面。李智輝、趙剛、郝南均是家中的獨生子女,三被告人的父母也都是在職職工或干部,家庭收入穩定,生活條件較好。優越的家庭生活環境和不當的教育方法造就了當今部分城市青少年特定的性格。而被告人楊保坤家在河北某縣,家中兄妹四人,家庭環境不是很好。從《少年犯家庭情況調查表》得知其幼年母親早逝,現在和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父親、繼母共同生活,而父親和繼母常年在外為生計奔波,在子女的教育上不能夠給予更多的照顧,教育方法簡單粗暴。這樣的家庭環境給張軍偉的內心蒙上了陰影,使他總認為自己在各方面都不如別人,產生自卑心理。
兩種完全不同的家庭環境下成長起來的孩子卻同樣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歸根結締還是教育方法的不當。有社會學家將十四歲至十八歲這一年齡段稱為“危險年齡時期”,因為這一年齡時期的孩子處于兒童時期和成人時期的銜接段。首先在思想上,他們不再依賴于父母,他們會自己思考一些問題,甚至于有時他們對父母的一些作法提出異議,有時家長也會覺得孩子的想法挺獨特。其次,在行為上他們對父母的意見也不再“言聽計從”了,正象有的父母說的“我這孩子怎么越大越不聽話了?”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成長過程中都會提出這樣的疑問。
其實這一年齡階段的孩子在心理上大多都有一種逆反心理。在一些個性比較強的孩子身上表現為我們所俗稱的“叛逆性格”,由于他們的思想比較活躍,所以即使玩兒起來也比那些老師、家長認為聽話的孩子更會玩兒,因此他們往往被認為是“不聽話”的孩子,所以大部分家長還是能夠提前給予足夠的重視,管得比較嚴,一般不會出問題,但是對這類思維較靈活的孩子,如果有父母或老師的積極正確引導反而能夠取得比聽話的孩子更好的成績。在另外一些性格內向、不愛活動的孩子身上則表現為看上去比較聽話,但他們一旦受外來因素的負面影響,就可能觸犯法律,這也是少年犯罪偶發性的另一個原因,如該院辦理的被告人王某搶奪一案,王某是父母和老師眼中的好孩子、好學生,在因故和父親吵了一架后,一氣之下將一女青年的背包搶走,包內有現金一萬元。
針對這一年齡的青少年,父母在子女的教育方面要給予更多的關注。首先要取得孩子對你的認同感,當然這種認同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形成的,它需要從小就給予孩子充分的尊重,使他們自認為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自己的事情讓他自己拿主意,這樣即使到了青少年時期,他們在思想和行為上的轉變也不會很大,父母也不會因為孩子思想和行為的轉變而不能接受。我們中國的父母在孩子童年時期喜歡對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攬,當孩子到了能夠自己處理問題的時候,父母還是不放心,而孩子則對父母關心不能理解,因此就產生了兩者之間所謂的“代溝”。
要解決這一矛盾,我們認為這也就是父母如何做才是對孩子的尊重的問題。父母首先要給孩子講話的權利,當孩子做錯了事情的時候,要給他解釋的機會,詢問一下孩子做這件事之前是怎么考慮的,并給他下一次做同樣事情時一個合適的建議。其次,對事關全家的大事最好能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見,使其關心家里的事情,這樣一方面適當地增強了他的家庭責任觀念,使其心理上有一種歸屬感,另一方面當他要提出不正當的經濟要求時,也會設身處地地為父母著想。而我們父母們在子女教育上的誤區則是總認為孩子操心家里的事兒,耽誤學習。最后一點就是屬于孩子自己的事情盡量讓他自己拿主意,父母如果過多地關心反而適得其反,這一點在此不再贅述。
針對未成年犯罪的盲目性和團伙性,筆者認為這關系到家庭、學校和社會的共同責任。在此僅就家庭中青少年教育加以探討。青少年犯罪的盲目性不僅僅表現為法律意識淡薄,更重要地表現在由于他們在認識社會、辨別是非以及處理問題上的局限性,因而,對自己行為的規范能力以及抵御外界誘因的能力較弱。在做一件事情時,目的不明確,往往隨著外界情況的變化而變化。
增強青少年的法制觀念,在實踐中真正做起來還是比較容易的,但關鍵是家長和子女都要有這個思想意識。生活中的各種傳媒如電視、報刊、雜志等,都有法制類的文章或欄目,當然首先父母要有學法的興趣,這樣子女在家長的熏陶下,經過耳濡目染,會不自覺地樹立法律意識。另外在一些學校開設有法制講座,社會上也經常有法制宣傳,這幾方面如果能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樣對提高青少年的法律意識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對于青少年認識社會、辨別是非以及處理問題上的局限性,這是由他們這個年齡段所決定的,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全面提高未成年人的綜合素質來著手。在日常生活中家長應有意識地教給他們處理突發事件的方法,鍛煉他們解決這類問題的能力,而不是簡單地告訴他們這個必須做、那個不能做。這樣,通過逐漸地有意訓練,當他們在生活中遇到類似問題時就會自覺地運用這種已形成的思維定式。同時,筆者認為解決未成年人的局限性應和未成年犯罪的團伙性的特點相結合,利用青少年喜歡和同齡人交朋友的特點,鼓勵并引導他們多參加一些學校組織或家長參與的積極健康的集體活動,如參加各種興趣活動小組、特長班等,使他們有更多的時間和老師、同學、家長度過,相應地減少了他們自己處理不適宜由這個年齡段處理的問題的機會,同時也使他們在情感上對父母和老師更加認同,對他們社會角色的轉變和人際交往能力也是一個很好的鍛煉。這樣,在盡可能避免青少年面對突發問題前提下,使他們具備這種能力,即使真正遇到這類問題時,他們也能夠冷靜面對、從容解決,從而也避免了解決問題的盲目性。
- 上一篇:城市社區黨建工作調研報告
- 下一篇:市人才狀況的調研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