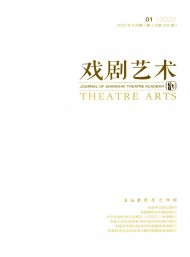導(dǎo)演世界范文10篇
時(shí)間:2024-01-17 18:30:20
導(dǎo)語(yǔ):這里是公務(wù)員之家根據(jù)多年的文秘經(jīng)驗(yàn),為你推薦的十篇導(dǎo)演世界范文,還可以咨詢客服老師獲取更多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參考。

導(dǎo)演世界管理論文
內(nèi)容摘要:李安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最重要的新生代導(dǎo)演之一。他以“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而蜚聲國(guó)際影壇,并從此開(kāi)始了他沖擊好萊塢的電影歷程。李安以其在電影中表現(xiàn)出的關(guān)注家庭生活中的倫理,關(guān)注中西文化對(duì)比的執(zhí)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壇,在藝術(shù)上和商業(yè)上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現(xiàn)的家庭題材,他是以一個(gè)完整并且強(qiáng)大的敘事力來(lái)完成其表達(dá)的中西方文化對(duì)比的主題。李安的這種獨(dú)特的貫穿中西方文化的電影風(fēng)格值得我們研究和思索。本文著重論述的就是李安學(xué)貫中西的導(dǎo)演風(fēng)格。對(duì)從李安的個(gè)人經(jīng)歷、整個(gè)社會(huì)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攝的影片中所反映出來(lái)的文化意識(shí)與倫理道德批判意識(shí)進(jìn)行全面的分析、比較和論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他的電影也是兩種社會(huì)文化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本文試圖就李安及其所帶來(lái)的“李安現(xiàn)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對(duì)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提供一種借鑒和學(xué)習(xí)。
序言
侯孝賢、楊德昌、李安三人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新生代最重要的導(dǎo)演。臺(tái)灣著名資深影評(píng)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賢和楊德昌兩個(gè)人對(duì)電影的不同認(rèn)知和信念加以對(duì)比,她認(rèn)為侯孝賢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的,感情飽滿而豐富;楊德昌是西方的、現(xiàn)代的,感情冷靜而內(nèi)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現(xiàn)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楊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賢的情感之間,“取其道而用之”。學(xué)貫中西,正是李安的導(dǎo)演風(fēng)格。
第一章與電影結(jié)緣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導(dǎo)演,當(dāng)他拍攝完成其處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導(dǎo)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時(shí),是1991年,當(dāng)時(shí)他已經(jīng)37歲。
導(dǎo)演世界管理論文
內(nèi)容摘要:李安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最重要的新生代導(dǎo)演之一。他以“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而蜚聲國(guó)際影壇,并從此開(kāi)始了他沖擊好萊塢的電影歷程。李安以其在電影中表現(xiàn)出的關(guān)注家庭生活中的倫理,關(guān)注中西文化對(duì)比的執(zhí)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壇,在藝術(shù)上和商業(yè)上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現(xiàn)的家庭題材,他是以一個(gè)完整并且強(qiáng)大的敘事力來(lái)完成其表達(dá)的中西方文化對(duì)比的主題。李安的這種獨(dú)特的貫穿中西方文化的電影風(fēng)格值得我們研究和思索。本文著重論述的就是李安學(xué)貫中西的導(dǎo)演風(fēng)格。對(duì)從李安的個(gè)人經(jīng)歷、整個(gè)社會(huì)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攝的影片中所反映出來(lái)的文化意識(shí)與倫理道德批判意識(shí)進(jìn)行全面的分析、比較和論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他的電影也是兩種社會(huì)文化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本文試圖就李安及其所帶來(lái)的“李安現(xiàn)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對(duì)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提供一種借鑒和學(xué)習(xí)。
序言
侯孝賢、楊德昌、李安三人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新生代最重要的導(dǎo)演。臺(tái)灣著名資深影評(píng)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賢和楊德昌兩個(gè)人對(duì)電影的不同認(rèn)知和信念加以對(duì)比,她認(rèn)為侯孝賢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的,感情飽滿而豐富;楊德昌是西方的、現(xiàn)代的,感情冷靜而內(nèi)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現(xiàn)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楊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賢的情感之間,“取其道而用之”。學(xué)貫中西,正是李安的導(dǎo)演風(fēng)格。
第一章與電影結(jié)緣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導(dǎo)演,當(dāng)他拍攝完成其處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導(dǎo)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時(shí),是1991年,當(dāng)時(shí)他已經(jīng)37歲。
導(dǎo)演世界管理論文
內(nèi)容摘要:李安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最重要的新生代導(dǎo)演之一。他以“父親三部曲”:《推手》、《喜宴》、《飲食男女》而蜚聲國(guó)際影壇,并從此開(kāi)始了他沖擊好萊塢的電影歷程。李安以其在電影中表現(xiàn)出的關(guān)注家庭生活中的倫理,關(guān)注中西文化對(duì)比的執(zhí)著精神,征服了世界影壇,在藝術(shù)上和商業(yè)上都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李安的成功在于他在影片中表現(xiàn)的家庭題材,他是以一個(gè)完整并且強(qiáng)大的敘事力來(lái)完成其表達(dá)的中西方文化對(duì)比的主題。李安的這種獨(dú)特的貫穿中西方文化的電影風(fēng)格值得我們研究和思索。本文著重論述的就是李安學(xué)貫中西的導(dǎo)演風(fēng)格。對(duì)從李安的個(gè)人經(jīng)歷、整個(gè)社會(huì)的背景以及他所拍攝的影片中所反映出來(lái)的文化意識(shí)與倫理道德批判意識(shí)進(jìn)行全面的分析、比較和論述。李安是中西方教育結(jié)合的產(chǎn)物,他的電影也是兩種社會(huì)文化結(jié)合的產(chǎn)物。本文試圖就李安及其所帶來(lái)的“李安現(xiàn)象”作一深入的分析,以期對(duì)中國(guó)電影的發(fā)展提供一種借鑒和學(xué)習(xí)。
序言
侯孝賢、楊德昌、李安三人被認(rèn)為是目前臺(tái)灣新生代最重要的導(dǎo)演。臺(tái)灣著名資深影評(píng)人焦雄屏女士曾把侯孝賢和楊德昌兩個(gè)人對(duì)電影的不同認(rèn)知和信念加以對(duì)比,她認(rèn)為侯孝賢是中國(guó)的傳統(tǒng)的,感情飽滿而豐富;楊德昌是西方的、現(xiàn)代的,感情冷靜而內(nèi)省。而李安所采取的是現(xiàn)代人的中庸之道,他游刃于楊德昌的理智和侯孝賢的情感之間,“取其道而用之”。學(xué)貫中西,正是李安的導(dǎo)演風(fēng)格。
第一章與電影結(jié)緣
一、往事
李安是一位大器晚成的導(dǎo)演,當(dāng)他拍攝完成其處女作影片也是奠定了其杰出導(dǎo)演地位的影片《推手》時(shí),是1991年,當(dāng)時(shí)他已經(jīng)37歲。
世界電影元素管理論文
在張藝謀、陳凱歌、鞏俐、葛優(yōu)以及眾多中國(guó)電影新生代不斷成為世界影壇的新聞話題的同時(shí),來(lái)自臺(tái)灣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和后來(lái)的《理智與情感》,來(lái)自香港的吳宇森在好萊塢先后導(dǎo)演了《終極標(biāo)靶》、《斷箭》、《變臉》和《碟中碟(2)》,陳沖與顧長(zhǎng)衛(wèi)合作拍攝了《紐約的秋天》,華人導(dǎo)演似乎已經(jīng)進(jìn)入了世界電影主流。2001年,美國(guó)《時(shí)代》周刊在評(píng)選年度10大優(yōu)秀影片時(shí),竟然同時(shí)有四部華人導(dǎo)演的電影榜上有名,在被傳媒塑造為一個(gè)文化盛典的奧斯卡評(píng)獎(jiǎng)中,李安的《臥虎藏龍》獲得了10項(xiàng)提名4項(xiàng)大獎(jiǎng)。華人儼然成為了新世紀(jì)世界電影文化的一道風(fēng)景。
的確,中國(guó)元素是一道風(fēng)景,在我們?yōu)槭澜珉娪爸性絹?lái)越醒目的東方元素而彈冠相慶的時(shí)候,我們也會(huì)意識(shí)到,對(duì)于這個(gè)由經(jīng)濟(jì)強(qiáng)權(quán)所支配的世界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更像是一個(gè)陌生的奇觀、一個(gè)遙遠(yuǎn)的童話、一個(gè)離奇的故事,因而,《花木蘭》其實(shí)是一個(gè)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guó)故事,《臥虎藏龍》中的東方俠士和東方美女只不過(guò)是為看多了《007》與《終極警探》中那些肌肉發(fā)達(dá)、動(dòng)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發(fā)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觀眾提供了新鮮快餐。
在好萊塢電影歷史上,利用外國(guó)演員、外國(guó)導(dǎo)演和外國(guó)題材、外國(guó)人物來(lái)征服外國(guó)觀眾,一直卓有成效。從20世紀(jì)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萊塢陸續(xù)吸收了法國(guó)、德國(guó)、英國(guó)、意大利、瑞典等許多國(guó)家的優(yōu)秀導(dǎo)演、明星,如喜劇大師卓別林、懸念大師希區(qū)柯克、演員葛麗泰·嘉寶、費(fèi)雯·麗、英格里·葆蔓等都來(lái)自歐洲,好萊塢還有許多導(dǎo)演、演員、甚至制片人來(lái)自東歐、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許多美國(guó)電影的題材也來(lái)自世界不同國(guó)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所有這些外來(lái)人和外來(lái)文化都經(jīng)過(guò)好萊塢的商業(yè)改造,有時(shí)甚至是美國(guó)的政治改造,一方面為主流的美國(guó)電影帶來(lái)異域情調(diào)和注入文化營(yíng)養(yǎng),另一方面也為美國(guó)電影進(jìn)入外國(guó)市場(chǎng)帶來(lái)文化親同感和文化共鳴。90年代以來(lái),不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國(guó)的花木蘭、圣經(jīng)里的摩西出埃及這樣的東方故事、題材紛紛出現(xiàn)在好萊塢電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萊塢排斥的華人導(dǎo)演、演員、攝影師也開(kāi)始越來(lái)越多地被邀請(qǐng)到好萊塢創(chuàng)作主流電影。好萊塢一方面利用東方情調(diào)來(lái)為主流好萊塢觀眾創(chuàng)造一種文化奇觀和獲取新的市場(chǎng)資源,同時(shí)也利用這些電影人在原住國(guó)和地區(qū)的地位、影響、名聲來(lái)獲得華文化圈的認(rèn)同。好萊塢以一種"世界電影"的形象為自己進(jìn)入東方做了文化包裝。
近年來(lái),"好萊塢"興起一種懷舊熱、古典熱,而時(shí)下這群懷舊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東方歷史和文化,而那些有著東西文化學(xué)術(shù)背景和生活經(jīng)歷的導(dǎo)演們,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東方歷史文化資源,又對(duì)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觀影習(xí)慣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會(huì)在充滿奇觀的東方故事中,溫柔、敦厚、神秘的東方文化在潛意識(shí)中給了他們一種母性和家園的感覺(jué),所以好萊塢也開(kāi)始借助"東方化"來(lái)實(shí)現(xiàn)西方人的"還鄉(xiāng)"夢(mèng)想。
其實(shí),好萊塢的東方元素不過(guò)是被好萊塢化的東方。因而,東方元素在世界電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種點(diǎn)綴。當(dāng)然,也許在當(dāng)今這個(gè)信息傳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為東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別是當(dāng)我們?cè)噲D"走向世界",試圖"國(guó)際接軌"的時(shí)候更是如此。
小議真實(shí)與虛擬的鏡頭內(nèi)外
摘要:“真實(shí)”有時(shí)候是人們最渴望也最不敢面對(duì)的詞匯,“虛擬”是看似飄忽存在,人卻難以捉摸的感覺(jué)。電影鏡頭記錄著真實(shí)和虛擬的生存空間,而這種真實(shí)和虛擬,有時(shí)候很難建立在一個(gè)由理性思想建構(gòu)的和諧空間中,但是,有時(shí)候“心靈”卻可以讓這種虛擬和真實(shí)同時(shí)存在。《楚門(mén)的世界》以人們對(duì)現(xiàn)代生活的視角出發(fā),引發(fā)電影與受眾之間的情感審美體驗(yàn),激發(fā)人們對(duì)現(xiàn)代精神生活的思考,體驗(yàn)生活對(duì)心靈的震顫。
關(guān)鍵詞:真實(shí)虛擬鏡頭空間心靈
“真實(shí)”在這個(gè)多元的社會(huì)中不單單指生活真實(shí),在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也有對(duì)“真實(shí)”的別樣理解。平日里我們把生活真實(shí)理解為社會(huì)生活中實(shí)際存在的人和事,它屬于客觀事實(shí)。而藝術(shù)真實(shí)的主體是藝術(shù)家在人生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加工、提煉、改造等活動(dòng),以另外一種所謂的虛擬的形式揭示出生活的本質(zhì)和真諦,使其更鮮活、更典型、更集中地表現(xiàn)藝術(shù)家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主觀評(píng)價(jià)和情感。藝術(shù)真實(shí)凝聚著藝術(shù)家對(duì)事物理解的觀念和真實(shí)情感。藝術(shù)家的這種主觀評(píng)價(jià)和情感與生活真實(shí)相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藝術(shù)真實(shí)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體的高度統(tǒng)一形式。如果用情感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存在,那么你會(huì)發(fā)現(xiàn),真實(shí)在人們的心靈中的存在是非常復(fù)雜的。《心理學(xué)大辭典》中認(rèn)為:“情感是人對(duì)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態(tài)度體驗(yàn)。”那么,在我們生存的這個(gè)宇宙空間社會(huì)中,如何看待和判斷自己身邊的“真實(shí)”狀態(tài),電視、電影、廣播、各種媒介的藝術(shù)真實(shí)真的就是我們所認(rèn)識(shí)的生活真實(shí)的藝術(shù)化結(jié)果嗎?那么,如何衡量這個(gè)結(jié)果的好壞呢?
電影是媒介傳達(dá)方式之一,它是一個(gè)商業(yè)行為的文化符號(hào),從這個(gè)詞匯誕生之日起便與生活這個(gè)詞匯緊密相連。電影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鏡子,鏡頭是藝術(shù)家記錄劇本的工具,影片是溝通觀眾、演員和生活真實(shí),塑造藝術(shù)真實(shí)的橋梁,通過(guò)影片引起觀眾對(duì)事件、事物的情感溝通。在舊有的觀念中影片的情節(jié)都是導(dǎo)演、演員根據(jù)編劇劇情的需要情景再現(xiàn)的一個(gè)過(guò)程,但是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影片的類(lèi)型也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變革。一種以電視傳媒為介質(zhì),為了一個(gè)明確的目的,以生活真實(shí)的發(fā)展為線索而被實(shí)時(shí)記錄下來(lái)的鏡頭出現(xiàn)了,即所謂的“真人秀”,還有人把它定義為“特定虛擬空間中的真實(shí)故事,以全方位、真實(shí)的近距離拍攝和以人物為核心的戲劇化的后期剪輯而做成的節(jié)目”而獲得廣泛的經(jīng)濟(jì)效益的電視節(jié)目。但是有多少人想過(guò)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這種虛擬空間建立在一個(gè)真人真事的基礎(chǔ)上的時(shí)候,會(huì)給一個(gè)人帶來(lái)什么樣的后果呢?電影《楚門(mén)的世界》中的“真”是否真的體現(xiàn)了藝術(shù)真實(shí)的價(jià)值?
一、鏡頭內(nèi)真實(shí)的情感——真
好萊塢的派拉蒙影業(yè)制作公司,拍了一部紀(jì)實(shí)性電影名字叫做TheTrumanShow。創(chuàng)下了很客觀的票房成績(jī),全美首映票房:S|31542121.00(單位:美元),全美累計(jì)票房:S|125618201.00(單位:美元),海外累計(jì)票房:S|138500000.00(單位:美元)。如此高額的票房成績(jī)顯然證明該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劇中的男主角對(duì)他的成功以及公司的成功卻全然不知,換另一個(gè)角度思考的話,我們應(yīng)該會(huì)產(chǎn)生另一種疑問(wèn):這種成功是真的成功,還是凌駕在別人痛苦之上的一個(gè)鬧劇呢?
世界電影元素管理論文
在張藝謀、陳凱歌、鞏俐、葛優(yōu)以及眾多中國(guó)電影新生代不斷成為世界影壇的新聞話題的同時(shí),來(lái)自臺(tái)灣的李安先后推出《推手》、《喜宴》、《飲食男女》和后來(lái)的《理智與情感》,來(lái)自香港的吳宇森在好萊塢先后導(dǎo)演了《終極標(biāo)靶》、《斷箭》、《變臉》和《碟中碟(2)》,陳沖與顧長(zhǎng)衛(wèi)合作拍攝了《紐約的秋天》,華人導(dǎo)演似乎已經(jīng)進(jìn)入了世界電影主流。2001年,美國(guó)《時(shí)代》周刊在評(píng)選年度10大優(yōu)秀影片時(shí),竟然同時(shí)有四部華人導(dǎo)演的電影榜上有名,在被傳媒塑造為一個(gè)文化盛典的奧斯卡評(píng)獎(jiǎng)中,李安的《臥虎藏龍》獲得了10項(xiàng)提名4項(xiàng)大獎(jiǎng)。華人儼然成為了新世紀(jì)世界電影文化的一道風(fēng)景。
的確,中國(guó)元素是一道風(fēng)景,在我們?yōu)槭澜珉娪爸性絹?lái)越醒目的東方元素而彈冠相慶的時(shí)候,我們也會(huì)意識(shí)到,對(duì)于這個(gè)由經(jīng)濟(jì)強(qiáng)權(quán)所支配的世界來(lái)說(shuō),中國(guó)更像是一個(gè)陌生的奇觀、一個(gè)遙遠(yuǎn)的童話、一個(gè)離奇的故事,因而,《花木蘭》其實(shí)是一個(gè)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guó)故事,《臥虎藏龍》中的東方俠士和東方美女只不過(guò)是為看多了《007》與《終極警探》中那些肌肉發(fā)達(dá)、動(dòng)作勇猛的西方英雄和挺胸露臂、金發(fā)碧眼的性感女郎的西方觀眾提供了新鮮快餐。
在好萊塢電影歷史上,利用外國(guó)演員、外國(guó)導(dǎo)演和外國(guó)題材、外國(guó)人物來(lái)征服外國(guó)觀眾,一直卓有成效。從20世紀(jì)的20年代到40年代,好萊塢陸續(xù)吸收了法國(guó)、德國(guó)、英國(guó)、意大利、瑞典等許多國(guó)家的優(yōu)秀導(dǎo)演、明星,如喜劇大師卓別林、懸念大師希區(qū)柯克、演員葛麗泰·嘉寶、費(fèi)雯·麗、英格里·葆蔓等都來(lái)自歐洲,好萊塢還有許多導(dǎo)演、演員、甚至制片人來(lái)自東歐、拉美、加拿大等等,而許多美國(guó)電影的題材也來(lái)自世界不同國(guó)家、不同文化和不同歷史,所有這些外來(lái)人和外來(lái)文化都經(jīng)過(guò)好萊塢的商業(yè)改造,有時(shí)甚至是美國(guó)的政治改造,一方面為主流的美國(guó)電影帶來(lái)異域情調(diào)和注入文化營(yíng)養(yǎng),另一方面也為美國(guó)電影進(jìn)入外國(guó)市場(chǎng)帶來(lái)文化親同感和文化共鳴。90年代以來(lái),不僅像金字塔中的木乃伊、中國(guó)的花木蘭、圣經(jīng)里的摩西出埃及這樣的東方故事、題材紛紛出現(xiàn)在好萊塢電影中,而且一直被好萊塢排斥的華人導(dǎo)演、演員、攝影師也開(kāi)始越來(lái)越多地被邀請(qǐng)到好萊塢創(chuàng)作主流電影。好萊塢一方面利用東方情調(diào)來(lái)為主流好萊塢觀眾創(chuàng)造一種文化奇觀和獲取新的市場(chǎng)資源,同時(shí)也利用這些電影人在原住國(guó)和地區(qū)的地位、影響、名聲來(lái)獲得華文化圈的認(rèn)同。好萊塢以一種"世界電影"的形象為自己進(jìn)入東方做了文化包裝。
近年來(lái),"好萊塢"興起一種懷舊熱、古典熱,而時(shí)下這群懷舊的西方人又欣喜若狂地把目光投向了東方歷史和文化,而那些有著東西文化學(xué)術(shù)背景和生活經(jīng)歷的導(dǎo)演們,既能游刃有余地利用東方歷史文化資源,又對(duì)西方人的心理需求和觀影習(xí)慣了然于心,把西方人所熟知的方式和概念融會(huì)在充滿奇觀的東方故事中,溫柔、敦厚、神秘的東方文化在潛意識(shí)中給了他們一種母性和家園的感覺(jué),所以好萊塢也開(kāi)始借助"東方化"來(lái)實(shí)現(xiàn)西方人的"還鄉(xiāng)"夢(mèng)想。
其實(shí),好萊塢的東方元素不過(guò)是被好萊塢化的東方。因而,東方元素在世界電影中不可避免地是一種點(diǎn)綴。當(dāng)然,也許在當(dāng)今這個(gè)信息傳播不平衡的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東方主義不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為東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別是當(dāng)我們?cè)噲D"走向世界",試圖"國(guó)際接軌"的時(shí)候更是如此。
“作者電影”的自我表述與銀幕拓新
作為產(chǎn)生于20世紀(jì)50年代伴隨著法國(guó)新浪潮電影運(yùn)動(dòng)而流行的一種電影類(lèi)型,“作者電影”從其產(chǎn)生開(kāi)始就有著來(lái)自于法國(guó)電影界的理論支撐,有著其自身的獨(dú)特風(fēng)格。而作為一種兼具理論探索與實(shí)踐支撐的電影類(lèi)型,“作者電影”從產(chǎn)生開(kāi)始,其影響就逐步擴(kuò)散到世界各地,成為了一種具有世界影響力,對(duì)后世電影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推動(dòng)作用的電影類(lèi)型。在“作者電影”的創(chuàng)作者中,法國(guó)導(dǎo)演特呂弗作為“作者電影”的重要理論家與電影創(chuàng)作者,無(wú)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作為特呂弗的代表作,其在電影《四百擊》就以極為生動(dòng)真實(shí)的電影風(fēng)格講述了叛逆少年安托萬(wàn)在家庭與學(xué)校之間的流浪之路。而時(shí)至今日,當(dāng)重新對(duì)這部電影進(jìn)行審視,其對(duì)導(dǎo)演自我人生的投注表達(dá),敘事策略上的真實(shí)風(fēng)格與創(chuàng)新的拍攝手法可以說(shuō)正是“作者電影”的一個(gè)代表,對(duì)后世的電影發(fā)展有著巨大的示范意義所在。
一、導(dǎo)演掌控下的自我投注與主體表達(dá)
作為20世紀(jì)最具有影響力的電影運(yùn)動(dòng),法國(guó)新浪潮電影運(yùn)動(dòng)給法國(guó)乃至全世界的電影發(fā)展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從理論淵源而言,法國(guó)新浪潮電影承接了當(dāng)時(shí)歐洲社會(huì)所普遍具有的后現(xiàn)代主義思潮,對(duì)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進(jìn)行了懷疑,當(dāng)時(shí)的年輕人經(jīng)歷了世界大戰(zhàn)所帶來(lái)的身心創(chuàng)傷,目睹了現(xiàn)代的文明社會(huì)對(duì)于人類(lèi)心靈的壓迫,因而普遍具有孤獨(dú)、懷疑、焦躁的心靈狀態(tài)。于是,包括存在主義、精神分析等相關(guān)理論盛行一時(shí),新浪潮電影運(yùn)動(dòng)就此展開(kāi)。在20世紀(jì)50年代的法國(guó),以《電影手冊(cè)》為主要陣地,巴贊、特呂弗、戈達(dá)爾等一批電影人從理論角度對(duì)傳統(tǒng)電影的那種僵化風(fēng)格提出了批判,并提出要拍攝具有導(dǎo)演自身風(fēng)格的電影。導(dǎo)演不再是劇本和制片廠之下的機(jī)械受控者,而應(yīng)當(dāng)成為電影的真正制作者,這也就是“作者電影”的由來(lái)。可以說(shuō),這種“作者論”在電影中“重新彰顯了電影作者的主體性方面”[1]。以此為理論指導(dǎo),新浪潮電影人進(jìn)行了一系列的電影創(chuàng)作實(shí)踐,并由此開(kāi)始對(duì)整個(gè)世界的電影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yuǎn)的影響,成為了傳統(tǒng)電影與現(xiàn)代電影的分界點(diǎn)。而在其中,作為新浪潮電影運(yùn)動(dòng)中的代表人物以及“作者論”的直接提出者,特呂弗以其代表作《四百擊》親身踐行了“作者電影”的理論。從某種程度上來(lái)說(shuō),特呂弗和他的《四百擊》正是“作者電影”的典范代表。“作者電影”從字面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就是對(duì)于電影的“作者”重要性的強(qiáng)調(diào)。作為西方理論中有著悠久含義的詞匯,“作者”一詞從人文主義開(kāi)始就為西方文藝?yán)碚摷覀兯匾暎⒃?9世紀(jì)的浪漫主義運(yùn)動(dòng)中被理論家們所一再?gòu)?qiáng)調(diào)。“作者”作為文藝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不可忽視的主體要素,其從誕生開(kāi)始就與主體自我的自由性、創(chuàng)造力所深深聯(lián)系在了一起。而在電影領(lǐng)域,“作者”一詞所指的就是導(dǎo)演這一電影的直接創(chuàng)作者。“作者電影”所強(qiáng)調(diào)的就是導(dǎo)演在電影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主導(dǎo)地位與自身風(fēng)格,是對(duì)當(dāng)時(shí)日益走向僵化刻板的電影制作方式的一次反撥。在1954年,特呂弗在法國(guó)《電影手冊(cè)》雜志上就以《法國(guó)電影的某種傾向》一文指出,“導(dǎo)演應(yīng)該而且希望對(duì)他們表現(xiàn)的劇本和對(duì)話負(fù)責(zé)”[2],批判了當(dāng)時(shí)法國(guó)傳統(tǒng)的編劇型電影。這一理論的提出重新彰顯了電影作為一種藝術(shù)門(mén)類(lèi)的獨(dú)立價(jià)值,確立了電影導(dǎo)演所應(yīng)具有并在電影中得以展現(xiàn)的風(fēng)格魅力,強(qiáng)調(diào)了導(dǎo)演自身在其電影創(chuàng)作過(guò)程中的自我投注與傾入。電影《四百擊》就正是其中的代表。其中的主角安托萬(wàn)的流浪之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導(dǎo)演特呂弗自身童年經(jīng)歷的一個(gè)投影。特呂弗以影像空間中流離在家庭與校園之間的少年形象暗示了自身的童年歲月,以自傳式的自我投注為這部電影塑造了自身的深刻烙印。《四百擊》的名字來(lái)自于法國(guó)的一句俚語(yǔ),原意說(shuō)的是胡作非為的蠢事,電影因而也有另一個(gè)《胡作非為》的譯名。而和電影內(nèi)容相結(jié)合,這個(gè)名字就代表了對(duì)于主人公少年時(shí)代叛逆行為的代稱(chēng)。而從導(dǎo)演自身的經(jīng)歷而言,特呂弗的童年并不幸福。從小生父不明,幼年時(shí)由外婆撫養(yǎng),少年時(shí)與母親和繼父之間并不親近。家庭里的陌生感和學(xué)校中的規(guī)矩令他從小就排斥這些存在。如特呂弗自身所言“和別人的青春期比起,我的青春期相當(dāng)痛苦”[3],而所有這些在他的電影《四百擊》中都得以體現(xiàn)。影片圍繞著少年安托萬(wàn)的生活展開(kāi)。同樣是幼年時(shí)由外婆撫養(yǎng),同樣是母親和寄付組成的家庭,看似完整的家庭環(huán)境中,其所潛藏的是陌生與疏離的情緒表達(dá)。而在學(xué)校中,老師的嚴(yán)厲管教之下是對(duì)學(xué)生的不信任感。這些情節(jié)在塑造著調(diào)動(dòng)觀眾情感的情緒氛圍的同時(shí),其所蘊(yùn)藏的則是導(dǎo)演特呂弗自身童年時(shí)代的情感回憶。在這種環(huán)境下,安托萬(wàn)的逃離,和好朋友逃學(xué)去看電影,偷父親辦公室中的打字機(jī)……這些叛逆的行為表達(dá)了安托萬(wàn)對(duì)自身生活的失望與反抗。而這種自我投注的情節(jié)設(shè)計(jì)為電影本身灌輸了自傳式的氣質(zhì)與超越時(shí)空的情緒氛圍,塑造了影像世界中屬于叛逆少年安托萬(wàn)的影像空間,在此之下,則是導(dǎo)演特呂弗所親身經(jīng)歷過(guò)的童年世界。導(dǎo)演自我與影片的主角達(dá)成了情緒體驗(yàn)上的一致性,這在影像空間的情節(jié)背后傳達(dá)出了來(lái)自導(dǎo)演自傳式表達(dá)的情感符號(hào)。從這個(gè)角度上來(lái)說(shuō),電影《四百擊》所描繪的正是懸置在影像世界里的導(dǎo)演自身的童年經(jīng)歷,少年安托萬(wàn)則是特呂弗童年形象的自我象征。而這種導(dǎo)演掌控下自我投注的象征表達(dá),這一導(dǎo)演主體化風(fēng)格的鮮明顯現(xiàn),這正是“作者電影”最為鮮明的特征之一。
二、敘事特征轉(zhuǎn)向:貼合真實(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
《四百擊》作為“作者電影”的代表作品之一,其另一個(gè)突出的特點(diǎn)就是電影中對(duì)于無(wú)序人生的真實(shí)生活的貼切表達(dá)。傳統(tǒng)電影在其敘事的表現(xiàn)策略上大多沿用的是經(jīng)典好萊塢時(shí)代的線性敘事策略,其包括完整的從開(kāi)端、發(fā)展、高潮和結(jié)局的敘事結(jié)構(gòu),以及在時(shí)間向度向前推進(jìn)過(guò)程中的種種因果邏輯的設(shè)計(jì)和安排。而其中,“而戲劇性和巧合(敘事意義上的偶然性)也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謂‘無(wú)巧不成書(shū)’和‘意料之外,情理之中’”[4]。例如以《關(guān)山飛渡》《育嬰奇譚》等為代表,經(jīng)典好萊塢時(shí)代的諸多電影將這種敘事策略逐步推向了巔峰。相比于這種傳統(tǒng)敘事策略,以《四百擊》為代表的則是另一種敘事方法。正如新浪潮電影運(yùn)動(dòng)中的電影理論家們所強(qiáng)調(diào)的,“作者電影”所追求的是對(duì)于真實(shí)生活的表達(dá),反對(duì)那種在電影中一味追求戲劇沖突和因果邏輯的敘事策略。在“作者電影”的敘事表達(dá)中,其所著力體現(xiàn)的是那種并非總是由無(wú)數(shù)因果沖突所交織的戲劇生活,而是一種更加貼切于生活原型的由許多無(wú)意義的瑣碎小事所摻雜的生活邏輯。《四百擊》就是特呂弗對(duì)于這種非傳統(tǒng)化敘事策略的表達(dá)實(shí)踐。在青少年的成長(zhǎng)歷程中,家庭和學(xué)校往往構(gòu)成了其人生建構(gòu)過(guò)程中的支柱性力量。因而在以青少年為主角的電影中,家庭和學(xué)校往往成為了其影像世界中的地理坐標(biāo),為電影中的戲劇沖突提供了主要的助推力量。然而,對(duì)于電影《四百擊》而言,這種傳統(tǒng)的戲劇化的敘事特征被導(dǎo)演賦予了最大限度的削弱與調(diào)整。電影圍繞著少年安托萬(wàn)的生活進(jìn)行了影像表達(dá),而這種表達(dá)在電影中則呈現(xiàn)為了片段化的呈現(xiàn)。從安托萬(wàn)在學(xué)校被處罰為開(kāi)端,影片圍繞著安托萬(wàn)的生活進(jìn)行了碎片化的影像刻畫(huà)。安托萬(wàn)逃課和朋友出去玩,安托萬(wàn)向老師撒謊被揭露,安托萬(wàn)被家長(zhǎng)處罰后離家出走和好友一起廝混,安托萬(wàn)偷打字機(jī)結(jié)果被發(fā)現(xiàn),安托萬(wàn)被關(guān)進(jìn)少管所,安托萬(wàn)從少管所逃跑……這些片段化的事件構(gòu)成了整部電影片段化的敘事結(jié)構(gòu)。家庭和學(xué)校同樣是少年安托萬(wàn)的生活兩極,然而在《四百擊》的非邏輯化的無(wú)序表達(dá)之中,它們不再被刻意的從生活空間中抽離出來(lái)成為戲劇化了的空間符號(hào),而是更為自然地被囊括進(jìn)了主人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了安托萬(wàn)生活片段中的背景影像。在此之下,電影從一個(gè)情節(jié)跳躍到另一個(gè)情節(jié),其中缺乏連貫因果邏輯的鋪墊和收束,也不具有從開(kāi)端到高潮再到結(jié)尾的完整敘事結(jié)構(gòu)。在《四百擊》中,安托萬(wàn)會(huì)在離家出走后偶然發(fā)現(xiàn)母親和其他人幽會(huì),會(huì)在沒(méi)有事先謀劃的條件下選擇從少管所中逃離,電影摒棄了對(duì)于事件前后戲劇沖突的強(qiáng)調(diào)與刻意描繪,代之以白描化的客觀表達(dá)與寫(xiě)實(shí)刻畫(huà)。疏離的家庭,嚴(yán)苛的學(xué)校,白天繁忙的大街上行走的人群,夜晚寂寞的街道里孤獨(dú)的身影,在此之下,安托萬(wàn)的日常生活并更加完整的建構(gòu)了起來(lái)。電影中最為突出的情感傳遞在于安托萬(wàn)的表情,從他和好友去玩轉(zhuǎn)盤(pán)機(jī)器時(shí)興奮的樣子,到和家人看電影之后的興高采烈的神情,再到被帶去少管所的車(chē)上和得知被父母拋棄后的流淚的樣子。這些表情以影像的形式對(duì)安托萬(wàn)的生活片段進(jìn)行了情感的傳遞刻畫(huà),在白描化的內(nèi)斂表達(dá)中傳遞出了更加真實(shí)而富有感染力的情感共鳴。而從電影的敘事表達(dá)來(lái)說(shuō),導(dǎo)演正是借由這些看似無(wú)序的人生片段的描繪,在更高層次上對(duì)人物的內(nèi)在情感世界進(jìn)行了真實(shí)的情感傳遞,表達(dá)了生活中的瑣碎事件里的真實(shí)生活經(jīng)驗(yàn)。電影本身有自身的特異性所在,是將生活中的邏輯與線索進(jìn)行更高具象化了的影像建構(gòu)。因而在傳統(tǒng)電影的敘事策略中往往強(qiáng)調(diào)戲劇化的強(qiáng)烈沖突與起承轉(zhuǎn)合的敘事結(jié)構(gòu)。然而,相比傳統(tǒng)電影,以《四百擊》為代表的“作者電影”則是另一種“散文”化了的敘事策略。這一電影類(lèi)型不再是對(duì)生活中的戲劇沖突追求集中的線性表達(dá),而是力求達(dá)成一種貼近于生活原貌的片段化了的影像表現(xiàn),在看似非邏輯的無(wú)序事件之上,建立起影像世界中主人公們的內(nèi)在情感畫(huà)像。如特呂弗所言:“在我看來(lái),電影是散文藝術(shù),要拍攝美,卻又好像沒(méi)有刻意雕琢。”[5]電影《四百擊》正是在這種敘事策略下,以片段化的無(wú)序影像最大限度的保留了生活經(jīng)驗(yàn)的真實(shí)風(fēng)貌,從而在情感的傳遞上達(dá)成了更加真實(shí)的共鳴體驗(yàn),進(jìn)一步喚起了觀眾們切身的情感經(jīng)驗(yàn)。而以此為開(kāi)始,這種現(xiàn)代化的電影敘事方法逐步流行開(kāi)來(lái),與傳統(tǒng)的經(jīng)典敘事策略達(dá)成了互補(bǔ),從而完成了現(xiàn)代電影的敘事模式建構(gòu),對(duì)后世電影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以華語(yǔ)電影世界而言,王家衛(wèi)的一系列電影便可看見(jiàn)對(duì)這種敘事方法的繼承。包括在《重慶森林》《阿飛正傳》中的那種非軸心式的斷裂化的敘事結(jié)構(gòu),對(duì)人物形象的切斷前因后果的片段化刻畫(huà),以及在此之下對(duì)人物的情感心理狀態(tài)進(jìn)行重點(diǎn)展現(xiàn)的表達(dá)策略。這種對(duì)生活偶然無(wú)序的真實(shí)經(jīng)驗(yàn)進(jìn)行描繪的方式,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duì)于“作者電影”敘事方式的繼承與發(fā)展。
三、拍攝方法與鏡頭表現(xiàn)的創(chuàng)新表達(dá)
真實(shí)與虛擬的鏡頭內(nèi)外透析
[摘要]“真實(shí)”有時(shí)候是人們最渴望也最不敢面對(duì)的詞匯,“虛擬”是看似飄忽存在,人卻難以捉摸的感覺(jué)。電影鏡頭記錄著真實(shí)和虛擬的生存空間,而這種真實(shí)和虛擬,有時(shí)候很難建立在一個(gè)由理性思想建構(gòu)的和諧空間中,但是,有時(shí)候“心靈”卻可以讓這種虛擬和真實(shí)同時(shí)存在。《楚門(mén)的世界》以人們對(duì)現(xiàn)代生活的視角出發(fā),引發(fā)電影與受眾之間的情感審美體驗(yàn),激發(fā)人們對(duì)現(xiàn)代精神生活的思考,體驗(yàn)生活對(duì)心靈的震顫。
[關(guān)鍵詞]真實(shí);虛擬;鏡頭空間;心靈
“真實(shí)”在這個(gè)多元的社會(huì)中不單單指生活真實(shí),在文學(xué)、藝術(shù)領(lǐng)域也有對(duì)“真實(shí)”的別樣理解。平日里我們把生活真實(shí)理解為社會(huì)生活中實(shí)際存在的人和事,它屬于客觀事實(shí)。而藝術(shù)真實(shí)的主體是藝術(shù)家在人生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通過(guò)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加工、提煉、改造等活動(dòng),以另外一種所謂的虛擬的形式揭示出生活的本質(zhì)和真諦,使其更鮮活、更典型、更集中地表現(xiàn)藝術(shù)家對(duì)生活真實(shí)的主觀評(píng)價(jià)和情感。藝術(shù)真實(shí)凝聚著藝術(shù)家對(duì)事物理解的觀念和真實(shí)情感。藝術(shù)家的這種主觀評(píng)價(jià)和情感與生活真實(shí)相一致或者基本一致。藝術(shù)真實(shí)是事真、情真、理真的三位一體的高度統(tǒng)一形式。如果用情感的角度去看待生活真實(shí)和藝術(shù)真實(shí)的存在,那么你會(huì)發(fā)現(xiàn),真實(shí)在人們的心靈中的存在是非常復(fù)雜的。《心理學(xué)大辭典》中認(rèn)為:“情感是人對(duì)客觀事物是否滿足自己的需要而產(chǎn)生的態(tài)度體驗(yàn)。”那么,在我們生存的這個(gè)宇宙空間社會(huì)中,如何看待和判斷自己身邊的“真實(shí)”狀態(tài),電視、電影、廣播、各種媒介的藝術(shù)真實(shí)真的就是我們所認(rèn)識(shí)的生活真實(shí)的藝術(shù)化結(jié)果嗎?那么,如何衡量這個(gè)結(jié)果的好壞呢?
電影是媒介傳達(dá)方式之一,它是一個(gè)商業(yè)行為的文化符號(hào),從這個(gè)詞匯誕生之日起便與生活這個(gè)詞匯緊密相連。電影是反映生活的一面鏡子,鏡頭是藝術(shù)家記錄劇本的工具,影片是溝通觀眾、演員和生活真實(shí),塑造藝術(shù)真實(shí)的橋梁,通過(guò)影片引起觀眾對(duì)事件、事物的情感溝通。在舊有的觀念中影片的情節(jié)都是導(dǎo)演、演員根據(jù)編劇劇情的需要情景再現(xiàn)的一個(gè)過(guò)程,但是隨著時(shí)代的發(fā)展,影片的類(lèi)型也發(fā)生著各種各樣的變革。一種以電視傳媒為介質(zhì),為了一個(gè)明確的目的,以生活真實(shí)的發(fā)展為線索而被實(shí)時(shí)記錄下來(lái)的鏡頭出現(xiàn)了,即所謂的“真人秀”,還有人把它定義為“特定虛擬空間中的真實(shí)故事,以全方位、真實(shí)的近距離拍攝和以人物為核心的戲劇化的后期剪輯而做成的節(jié)目”而獲得廣泛的經(jīng)濟(jì)效益的電視節(jié)目。但是有多少人想過(guò)這樣一個(gè)問(wèn)題,這種虛擬空間建立在一個(gè)真人真事的基礎(chǔ)上的時(shí)候,會(huì)給一個(gè)人帶來(lái)什么樣的后果呢?電影《楚門(mén)的世界》中的“真”是否真的體現(xiàn)了藝術(shù)真實(shí)的價(jià)值?
鏡頭內(nèi)真實(shí)的情感——真
好萊塢的派拉蒙影業(yè)制作公司,拍了一部紀(jì)實(shí)性電影名字叫做TheTrumanShow。創(chuàng)下了很客觀的票房成績(jī),全美首映票房:S|31542121.00(單位:美元),全美累計(jì)票房:S|125618201.00(單位:美元),海外累計(jì)票房:S|138500000.00(單位:美元)。如此高額的票房成績(jī)顯然證明該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劇中的男主角對(duì)他的成功以及公司的成功卻全然不知,換另一個(gè)角度思考的話,我們應(yīng)該會(huì)產(chǎn)生另一種疑問(wèn):這種成功是真的成功,還是凌駕在別人痛苦之上的一個(gè)鬧劇呢?
第六代電影審美特征論文
摘要:以張?jiān)錈睢⑼跣洝①Z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dǎo)演群體,以個(gè)人化的敘事策略和對(duì)都市場(chǎng)景與邊緣人、小人物生活的展示以及強(qiáng)烈的影像塑造意識(shí),體現(xiàn)出他們共同的“代”的意識(shí)與審美特質(zhì)。
關(guān)鍵詞:第六代個(gè)人化都市邊緣人小人物影像
以張?jiān)錈睢⑼跣洝①Z樟柯等為代表的第六代電影導(dǎo)演群體是在80年代相對(duì)開(kāi)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接受教育的,同時(shí)也是在中國(guó)電影面對(duì)一個(gè)新的環(huán)境中開(kāi)始拍攝的。與“第五代”相比,他們有著諸多不足以自成一派的因素,甚至其中很多導(dǎo)演也拒絕這種代際劃分。但就筆者個(gè)人的看法,隨著“第六代”作品的不斷問(wèn)世,他們?cè)陔娪皩徝雷非笊系墓餐幰矟u次清晰。因此,對(duì)他們電影的整體特征進(jìn)行描述,也許是可行的。
一、個(gè)人化的敘事策略
“個(gè)人化”這一概念,濫觴于日本的“私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它是一種無(wú)視社會(huì)意義、專(zhuān)寫(xiě)私生活、敢于自我暴露的寫(xiě)作。是在現(xiàn)代主義哲學(xué)思想活躍,“反傳統(tǒng)情緒、個(gè)人主義思想,為之彌漫。一般人由關(guān)心國(guó)家變?yōu)殛P(guān)注自我,由國(guó)家主義轉(zhuǎn)為‘沉潛的個(gè)人主義’”的社會(huì)思潮下,某些對(duì)自身處境不滿、對(duì)社會(huì)極端失望的作家的產(chǎn)物。筆者之所以借用“個(gè)人化”這一概念,是因?yàn)椤暗诹钡臄⑹鏊囆g(shù),與小說(shuō)界的“個(gè)人化”寫(xiě)作很類(lèi)似。
“個(gè)人化”敘述的特征首先是,放棄“社會(huì)代言人”的角色,回歸個(gè)人的敘事?tīng)顟B(tài),遠(yuǎn)離公共話語(yǔ)和宏大敘述,而面向個(gè)人的狹小生活。“第六代”的作品從《頭發(fā)亂了》,到《北京雜種》、《小武》、《長(zhǎng)大成人》、《蘇州河》、《月蝕》、《陽(yáng)光燦爛的日子》、《非常假日》、《蔓延》……無(wú)不如此。青春的困惑、成長(zhǎng)的煩惱等存在主義意義上的精神狀態(tài),成為影片中作為主人公的個(gè)人化敘述的中心話語(yǔ),雖然在這些作品中有社會(huì)因素存在,但那不過(guò)是作為故事的背景而已。在他們的作品中,盡管有很多對(duì)社會(huì)陰暗現(xiàn)象的揭示,但敘述者并不以“代言人”的口氣,而只是一種“平民當(dāng)事人”的個(gè)人化講述與宣泄。其次,是敘述中總有紀(jì)實(shí)與自傳的敘述框架。影片主人公多是在焦慮和失落中茫然而行的少年或青年,他們的故事在大眾心目中幾乎無(wú)足輕重,但由于導(dǎo)演與作品的主人公在年齡、經(jīng)歷、命運(yùn)方面往往具有相關(guān)性——如姜文,在《日光燦爛的日子》中,干脆找一個(gè)酷似自己的“小姜文”,以示與自己經(jīng)歷的相關(guān)——人物形象便不僅是解讀影片的顯形符碼,還成為解讀導(dǎo)演的隱形符碼,因此有理由認(rèn)為“第六代”電影具有紀(jì)實(shí)與自傳的敘述性質(zhì)。再次,是“第六代”多不采用“第五代”所擅長(zhǎng)的影像象征、暗示等寓言模式。而善于采用直截了當(dāng)?shù)膬?nèi)心獨(dú)白方式,表現(xiàn)某種敢于抗?fàn)幍摹⑼媸啦还Ш腿涡缘摹o(wú)拘無(wú)束的精神狀態(tài)。在這個(gè)意義上,“個(gè)人化”敘述成了第六代表達(dá)個(gè)人情緒的一種策略。
談馬儷文電影創(chuàng)作新趨勢(shì)
2002年,馬儷文憑借處女作《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gè)人去了》在中國(guó)銀幕上嶄露頭角,2005年,她的第二部作品《我們倆》摘得中國(guó)電影金雞獎(jiǎng)桂冠并在東京國(guó)際電影節(jié)上大放光彩。這兩部都是具有濃郁抒情風(fēng)格的寫(xiě)實(shí)電影,導(dǎo)演深入挖掘潛藏于人們?nèi)粘I顑?nèi)部的濃濃真情,是少有的小成本佳作。也正是因?yàn)檫@兩部影片的成功,馬儷文成為中國(guó)女性導(dǎo)演中的佼佼者,當(dāng)馬儷文的風(fēng)格被定性為日常、溫情、淳樸時(shí),2008年她以一種全新的創(chuàng)作模式推出了集葛優(yōu)、鄔君梅、范冰冰等大牌明星于一體的反映現(xiàn)代人情感生活的喜劇電影《桃花運(yùn)》,以及2011藍(lán)正龍、韓彩英、許志安等傾情出演的反應(yīng)赤裸裸金錢(qián)利益的《巨額交易》。現(xiàn)對(duì)馬儷文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新態(tài)勢(shì)做一分析。
一、敘事主題:人間真情——現(xiàn)代人對(duì)物欲的貪婪
主題是一部影片的靈魂,是導(dǎo)演思想和情感的傳達(dá),也是與觀眾產(chǎn)生共鳴的最核心的部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gè)人去了》、《我們倆》是馬儷文早期的兩部作品,故事簡(jiǎn)單,人物樸實(shí),《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gè)人去了》中,導(dǎo)演用鏡頭講述了知名女作家與母親相處的最后一段時(shí)間,有無(wú)奈、有愧疚、有自責(zé)也有掙扎,更多的是與母親之間那溢于言表的親情。再多的愛(ài)也無(wú)法挽留母親離去的腳步,導(dǎo)演用幾幅靜態(tài)畫(huà)面承載了女兒巨大的悲痛:母親睡過(guò)的沙發(fā)、坐過(guò)的輪椅、窗前的跑步機(jī)、紅酒的杯子、整齊的一沓零錢(qián)、老家的鑰匙。影片用最真誠(chéng)的母女情溫暖并感動(dòng)著每一個(gè)人。《我們倆》講述一老一小之間特殊的友誼,他們之間沒(méi)有直接的血緣關(guān)系,只是房東與房客簡(jiǎn)單的利益身份,甚至連最基本的融洽都難以做到,每天矛盾重重,但在日后的相處中卻產(chǎn)生了難以割舍的情誼。小馬兩次看望老太太時(shí),導(dǎo)演都用特寫(xiě)鏡頭定格那緊緊握在一起的兩雙手。馬儷文導(dǎo)演用這樣一個(gè)個(gè)簡(jiǎn)單的故事傳達(dá)著濃濃的情誼。
從2008年的《桃花運(yùn)》到最新上映的《巨額交易》,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觀念發(fā)生了很大的轉(zhuǎn)變,這首先表現(xiàn)在主題上,直接對(duì)準(zhǔn)了現(xiàn)代人貪婪的物欲和迷茫的情感婚姻生活,金錢(qián)成為當(dāng)今社會(huì)成功的代名詞和生活的保證,“白骨精”毫不忌諱的喊出要找“特別有錢(qián)的老公”“三有一無(wú),有錢(qián)有房有車(chē)無(wú)老婆”,一個(gè)可以給予她優(yōu)厚生活待遇的男人,金錢(qián)就是愛(ài)情的等價(jià)品。《巨額交易》更是一場(chǎng)赤裸裸的“金錢(qián)交易”,每個(gè)人腦子里充斥的詞語(yǔ)都是“挖金”、“賺錢(qián)”,愛(ài)情在財(cái)富面前是卑微的,王云鵬的老婆甚至以生孩子作為威脅。導(dǎo)演向我們展現(xiàn)著這個(gè)人情冷漠、人心浮躁、物欲橫流的社會(huì),人與人之間的交往變得不再單純、簡(jiǎn)單。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轉(zhuǎn)變既是對(duì)過(guò)去樸實(shí)人心的懷念,又是對(duì)當(dāng)今社會(huì)的諷刺和惋惜。
二、劇作結(jié)構(gòu):?jiǎn)尉€條為主——多線條交織
在馬儷文早期的作品中,故事情節(jié)比較集中,影片圍繞一條主線展開(kāi),其他情節(jié)和人物的加入都是為這一條線索服務(wù),如《我們倆》中把故事發(fā)生的空間集中到北京的一個(gè)小四合院里,鏡頭記錄了一老一小由矛盾重重到相互依賴再到難舍難分的整個(gè)情感歷程,老太太的孫子、小馬的男友和弟弟的出現(xiàn)增加了故事的豐富性和戲劇性,但他們只是整個(gè)故事主線的補(bǔ)充和細(xì)化。《世界上最疼我的那個(gè)人去了》這部影片更是聚焦于女作家與母親的相處的最后一段日子,酸甜苦辣,五味俱全。從《桃花運(yùn)》開(kāi)始,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模式發(fā)生了轉(zhuǎn)變,在劇作結(jié)構(gòu)上呈板塊式發(fā)展,同一個(gè)主題下有不同的故事情節(jié),他們之間可以存在微妙的聯(lián)系,也可以獨(dú)立存在,各自成型,影片不再集中于一個(gè)故事,而是多條線索相互交織,共同發(fā)展,但絲毫不影響影片的完整性。80年代臺(tái)灣新電影運(yùn)動(dòng)時(shí)這種板塊式的結(jié)構(gòu)曾風(fēng)靡一時(shí),如由四個(gè)導(dǎo)演分別執(zhí)導(dǎo)四個(gè)獨(dú)立故事組成的影片《光陰的故事》;由侯孝賢、曾壯祥、萬(wàn)仁等共同執(zhí)導(dǎo)的《兒子的大玩偶》。比起臺(tái)灣新浪潮導(dǎo)演,馬儷文影片結(jié)構(gòu)的創(chuàng)新形式是委婉的,各自獨(dú)立的故事在講述上相互交織,以保證不會(huì)削弱影片所營(yíng)造的整體感。導(dǎo)演的創(chuàng)作風(fēng)格不是單一的,他們力求創(chuàng)新,不滿足于局限在一種模式中,如新生代導(dǎo)演姜文早期執(zhí)著于文藝片的探索,《太陽(yáng)照常升起》的冷門(mén)曾一度成為導(dǎo)演的傷痛,在隨著市場(chǎng)化的進(jìn)程中,拍出了迎合大眾口味的商業(yè)片《讓子彈飛》,讓姜導(dǎo)著實(shí)“飛”了一把。馬儷文導(dǎo)演同樣如此,她一直探索著影片的模式以更好的傳達(dá)出所想表達(dá)的思想。
熱門(mén)標(biāo)簽
相關(guān)文章
2電視導(dǎo)演應(yīng)當(dāng)具備的創(chuàng)作技巧
3電視文藝導(dǎo)演策劃與經(jīng)營(yíng)模式初探
4廣播電視導(dǎo)演藝術(shù)創(chuàng)作構(gòu)思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