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慕容散文集范文
時間:2023-04-08 13:18:42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席慕容散文集,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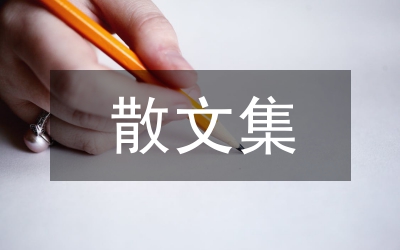
篇1
《燕子》的作者是席慕蓉,該篇散文是對燕子的美好懷念,也是對自己童年時期的懷念。
席慕蓉介紹:
席慕容,女,臺灣著名詩人,散文家,畫家,祖籍內蒙古察哈爾盟明安旗,是蒙古族王族之后,外婆是王族公主,后隨家定居臺灣,她于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新詩集《七里香》,在臺灣刮起一陣旋風,其銷售成績也十分驚人,一九八二年,她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成長的痕跡》,表現她另一種創作的形式,延續新詩溫柔淡泊的風格,代表作品有《記憶廣場》《成長的痕跡》等。
(來源:文章屋網 )
篇2
關鍵詞:1950年代;臺灣文學;女性散文;地位;影響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981(2012)04-0109-05
一、大陸學界對于發生階段的臺灣當代女性散文缺乏整體的獨立研究
在兩岸漸漸突破政治隔閡、共同發揚中華文化的今天,當我們再次回顧政治巨變年代的創作,特別是1950年代臺灣女性散文創作及其在大陸的接受情況時,樓肇明在20世紀90年代的判斷:“臺灣地區的散文在已往的中國文學史上不曾占有顯赫的席位”依然未變。在這背后,除了政治偏見外,還有大量的性別、體裁、題材等的偏見存在。如,曾以散文集《綠天》在大陸名噪一時、一度與冰心、丁玲等齊名的蘇雪林,或許是因為曾發表言論、與左派作家打筆戰等原因,在兩岸政治對峙的年代里幾乎成了“化外之民”,常被中國現代文學史忽略。這使得她沒有得到較中肯的評價,文學史地位也遠不如上述同期的作家。又如,同樣是學貫中西,在詩、散文、小說、翻譯、評論五方面皆有不凡成就的張秀亞以及同樣兼事寫作與翻譯、評論的徐鐘驪、謝冰瑩等女作家,就并沒有踩著她們腳印成長的學生輩“四棲”男作家余光中那么幸運,在各方面都受到大陸足夠的關注。
此外,綜觀大陸學界對1950年代臺灣女性創作頗為寂寥的關注,我們不難發現,人們甚至對散文的評價尚未達成共識。在有限的研究中,人們常習慣于觀念先行,無需論證就直接得出結論。如有人認為:“從總體上看,50年代臺灣散文的成就并不大”,而女作家群雖“在當時的文壇占有一席之地”,卻又“總體上看天地不寬,閨秀氣重”。又有人認為“50年代的臺灣女作家,成為臺灣散文創作的重要力量,成績斐然……她們以創作實績推動臺灣散文的起步與發展”。而在更多研究者的視野中,整個50年代女性散文創作并未受到足夠重視而獲得獨立的研究。他們或是將它與其他體裁放在一起籠統評價;或是把五六十年代臺灣散文混在一起總體概括,而其中50年代又為60年代所遮蓋。前者如一些文學史中缺乏論證的籠統結論:“50年代的臺灣女性文學創作,為此后女性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祖國大陸遷臺的女作家,承擔了臺灣女性文學拓荒者的角色,構成了五六十年代臺灣女性創作的主體”,“她們在懷鄉文學的創作潮流中充當了主力軍的角色”。后者較典型的如黃萬華的文章,雖指出傳承五四傳統的臺灣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是“臺灣散文的主導力量”,但論述中除以極少篇幅點出張秀亞50年代的一些作品外,其余例證皆用60年代的作品,這其中又以男作家的占絕大多數。上述這些都說明大陸學界對于臺灣當代散文發生階段的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1950年代臺灣女性散文創作在大陸學界仍缺乏整體的獨立的研究。
二、1950年代是臺灣女性散文發展中承前啟后的分水嶺
光復后特別是遷臺后的1950年代是臺灣女性散文發展的一個分水嶺。此前,日據時期的執政者企圖在“去中國化”思想的指導下弱化、消泯中國文化對臺灣的影響,而增強臺灣民眾對日本文化的認同。這使得本就不多的臺灣女作家在封閉中只能以日文閱讀、創作,或通過日本文學去間接接受西方文學的影響。女性散文總體成就不大。而與此同時,冰心、白薇、陳衡哲、蕭紅、凌叔華、蘇雪林、謝冰瑩、袁昌英、張愛玲等大陸方面的女作家在中國傳統散文、宋元以來白話小說、晚明小品、東西洋散文等多種文學傳統的影響下,揚棄傳統糟粕,漸漸步入現代的進程,而在散文理論與創作實績方面皆有較大的收獲。光復后特別是遷臺后,幾代作家、知識女性齊聚臺灣,自此,來自大陸與臺灣的兩批女作家(或知識女性)匯集臺島,開啟了臺灣女性散文寫作的新歷程。
雖然臺籍女作家因語言轉換等現實問題多處在缺席狀態,而外省渡海來臺的女作家在創作水平上也參差不齊,但遷臺女作家們對中國特別是五四以來各時期散文創作經驗的整體性、共時性移植使得1950年代臺灣女性散文園地空前繁榮。這從“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所舉辦的“四十四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中就不難看出。在散文類的10部得獎作品中,除了梁容若與鳳兮兩位男作家的作品外,女作家的竟占到了8部,它們是:艾雯的《青春篇》,張秀亞的《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冊》,徐鐘珮的《我在臺北》,謝冰瑩的《愛晚亭》,鐘梅音的《冷泉心影》,蘇雪林的《綠天》。其中除了《綠天》全本及《愛晚亭》中的極少篇目屬早年作品外,其余均是在臺所作。另外,從散文專集出版的情況來看,也可見此時臺灣女性散文的成績及其在臺影響力之一斑。除上列入選作者外,林海音、琦君、王文漪、蕭傳文、張漱菡、邱七七、孟瑤、郭晉秀、侯榕生、劉枋、李萼、王琰如等此期都有專集出版,有的甚至還不斷再版。對于這個時期的臺灣散文創作而言,女作家們將遍布全國各地的多樣化地域文化因素注入文中,極大地豐富了臺灣文學的文化內涵,使臺灣文學因此成為包含最豐富最完全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學板塊。正如學者朱二先生所言,這是臺灣文學中最值得驕傲的,且在整個中文文學中也是獨一無二的。這些女性散文在官方倡導“抗俄”的戰斗文藝年代為文壇注入的清流,可謂開風氣之先,對此后臺灣散文創作的豐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三、多元寫作范式及創作理念為文壇后來者提供有力參照
如上所述,因為共時性整體移植的關系,此期臺灣女性散文創作不管是在風格、題材、性別意識還是在寫作理念上,都是承上啟下的。一方面,作家們的到來與繼續創作使五四以來的創作風格等在臺灣得到了活的傳承;另一方面,因為臺灣長時間的政策等所導致的臺灣在中國現代文化(包括文學)方面的閉塞,這些在大陸生、大陸長,只因政局變遷而來臺的女作家們的所思所寫便理所當然地成為文壇后學們想象中國的原型;她們的寫作經驗也將對當代臺灣散文創作產生較大的影響。限于篇幅,以下我們結合代表性作家的創作狀況從不同層面不同類型來簡要論述這些影響,以期證實此期臺灣女性散文創作常被忽視的重要價值,引起大陸學界足夠的重視和繼續的研究。
(一)多元風格的影響
1 學者散文
集作家、學者等多種身份于一身,一生筆耕不輟的五四女作家蘇雪林,1950年代遷臺后雖以學術研究為主,但仍同時進行文學創作。此期主要有散文集《歸鴻集》(1955)、《讀與寫》(1959)等。學養豐厚的蘇雪林在歷經家國巨變后,從昔日《綠天》等自傳式書寫的筆觸中轉入常為男性獨霸的學者散文領域。她以學理見長、頗具學者風范的寫作,為臺灣當代散文創作開拓了視野,提供了較成熟的學者散文寫作范式。《歸鴻集》較好地體現了蘇氏散文關注面廣、題材多樣、學養豐厚的特點。集子中有以率直樸厚的語言回憶舊人的,有有理、有趣地回憶離國前舊事的,有對諸畫家、畫作等做真情解讀或中肯評價的,有哀悼世事巨變中書的離散的,有中西方制度等比較的,另外還有不少為友人書籍所作的序跋等。正如致力于蘇雪林研究的安徽大學沈暉教授所言:“這些散文文字凝重,情感真粹,思想深邃,見解深刻。將人情世事與學問,坦蕩的襟懷與豪邁的才情,一爐共冶,中外比較,古今對照,筆下流出的是作者學養濃厚的智慧澄液,洋溢著高雅的情趣和書卷氣”。
2 詩化散文
曾被痖弦稱作“臺灣近四十年來美文的開拓者”的張秀亞很早就開始了文藝創作,并從凌叔華、伍爾芙等中外女作家的作品中吸取了養分。她是惟一一位在上述臺灣青年最喜歡閱讀的作品評選中以三部作品入選的散文作家。她的行文淡雅、雋逸,常“以詩人的心情來創作自己的散文”,用象征手法營造詩化意境,將朦朧空靈的美感注入字里行間。其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就是這種詩化散文的代表。書中她總是將個人情感、生活經歷以及自己那份宗教情懷融入字里行間,再以詩的手段將它升華,然后抒情造境。濃郁的詩化氛圍與獨特內蘊消弭了同時代諸多散文中強烈的功利色彩,形成了50年代更具純文學特質的寫作,影響著諸多后來者。正如符立中所言:“在那個文藝年代……每個人心中都住著一個張秀亞。從三毛、歐陽子、呂大明到瓊瑤,那種在生命幽谷編織幻夢,交錯著朦朧和感傷的‘秀亞式’魅力是無遠弗屆的”。也如林海音所說,四五十年代的中學生,誰不是讀著張秀亞的作品長大的?張瑞芬則認為,張氏融合了京派美文傳統與女性特質的散文成了幾代人初期寫作的范本。即便是在今天經濟高度發達的臺灣,張氏詩化散文依然有著積極的意義:“在這樣一個光怪陸離的時代,張秀亞那行云流水、清新秀麗的田園文學,對人們失去已久的、屬于心靈的純美素質,具有一種喚起、警醒的作用”。
3 主婦散文
不同于上述在大陸時期就已頗具文名的知性、詩意女作家們,以遷居臺灣為創作起點、以家庭為圓心進行寫作的鐘梅音,是位典型的家庭主婦型散文作家。1949年,鐘梅音以發表于《中央日報·婦女周刊》的《雞的故事》開啟其在臺的寫作生涯,屬典型的拉家常的主婦風格:體制短小,主題多樣,充滿情趣,在溫情委婉的背后有著繁復瑣細的特質。此期她的散文集子中,書寫臺灣東部蘇澳冷泉鄉居生活情趣的《冷泉心影》最富于主婦特色。其中《我的生活》、《雞的故事》、《賣蛋記》、《阿蘭走了以后》、《鄉居閑情》等文通過對來臺后鄉居小家庭生活點滴的書寫,描劃出了一幅寧靜的合家歡景象。作者細膩的文采使得原本繁雜瑣碎的家居生活題材文章流出自然的真情。正如王文漪所說:“原來只是一個小小的泉池,她卻寫得那樣美”。《冷泉心影》也因其真實生活記錄的風格與“家臺灣”的親切表現等為讀者所鐘愛,而在前述評選中榜上有名。
(二)多樣題材的影響
此期女性散文創作的題材,總體來講大致可分為異地化與在地化書寫兩大類。所謂異地化書寫是指身在臺灣,卻自臺灣以外的異地取材的書寫;所謂在地化書寫是指在臺灣寫臺灣的做法。這兩方面的書寫在1950年代都有不少成熟的作品,所以它們對之后作家們的取材意向都產生了明顯的影響。
1 異地化書寫 因為出境的不易,此期的異地化書寫不像之后那樣多寫海外游歷見聞,而主要體現在作者對大陸生活的種種回憶上。作家們通過懷舊憶往,表現對故鄉、過往的眷戀與對時光、人事難再的感慨。正如琦君所說,在陌生的臺灣,“此心如無根的浮萍,沒有了著落,對家鄉的苦戀,也就與日俱增了”。在遠距離的凝視中,故鄉已不再僅限于某一具體的村落,過去的一切隔著時空的距離時隱時現,都顯得那么親切、美好。
這時期幾乎所有作家在這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或許是因資料不易得等原因,大陸學界在論及臺灣懷舊散文時,總習慣于將光環集于琦君一身。誠然,琦君的懷舊散文在六七十年代確已接近爐火純青的地步,但在50年代,她仍處于起步階段,她的文章如下文所述也仍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以偏概全地獨拜一人而忽略、擠壓其他同類作家在文學史上生存位置等的做法,讓我們再次看到大陸學界對于50年代臺灣散文發生期的研究依舊道遠。
曾寫出“文化沙漠的年代的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1951)、并以此在“四十四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測驗”散文類評選中獲得第一名的作者艾雯,在大陸學界卻極少有人關注。而她50年代的創作,不管是小說的關注社會、人性,還是“私密散文”的風格,都得到了業內人士的好評。艾雯這時期的散文視野開闊、題材豐富,兼有異地化、在地化、哲思等的書寫。其懷舊散文所表現出的濃濃眷戀以及對于當下現實的無奈,由于相同的社會心理與高超的寫作技巧等原因,曾引起了廣泛的共鳴。《青春篇》中,作者從不知如何寄予她(故鄉蘇州)密如雨層的“惦念”(《惦念》)到把思鄉之情化作對水城蘇州的“水的戀念”(《水的戀念》):“但愿我是那片白云,越過高矗的山嶺,去親近那可愛的水、水、水”;而《它》則回憶起了在童年時期,“孤獨寂寞”——它,就總是如影隨行地跟著自己,為當前的孤獨寂寞尋找到了一個詩意解脫的源頭。而在其他集子如《漁港書簡》中,不管是對故人——如有著瀟灑不羈的蘇州舊文士氣的父親對自己人生的影響(《虹一般的憶念》),還是對故地——如在國難家變接踵而至中生活了十年的贛南山城的記憶(《山城憶》),皆俯首可拾。
六七十年代在懷舊散文方面成為首屈一指大家的琦君,此期亦在孤寂中開啟回憶之門,以寄托對故人、舊事情思的散文《金盒子》開始了她在臺灣不平凡的散文創作歷程。但這時期她的散文并不多(主要以《琴心》這本散文、小說合集中的作品為代表),且受到官方主流的影響,字里行間難免流露出時代的主流印跡。雖如此,其散文寫作的基本風格,如強烈的自傳色彩、緬懷舊時大陸人、事、物的題材和小說化筆法——重視情節的結構和人物的塑造等已露端倪,以后,她正是順著這條路子漸入佳境的。
2 在地化書寫 “一切的藝術永遠是聯系著時代的,它不僅是表現一己的感情生活,更要從這時代人民大眾豐富的生活中去提煉”。許多作家正是在這樣的寫作理念下,自懷舊之外也將眼光放在當時當地的臺灣的。從作者們對臺灣現實環境、社會心態、自然風光、人文風情等的細膩觀察與描繪上,我們不難看到一般印象中凄風苦雨的50年代臺灣的另一面。從遷居臺灣到發現臺灣的轉變中,字里行間所流露的是女作者們對新家園的認同。此期,除了前述鐘梅音多自臺灣鄉居取材寫作外,其他不少作家在這方面都有成熟之作。
擅長明凈、重思維的“中性文體”的徐鐘珮的《我在臺北》(1951)一書,主要記述了她來臺后所碰到的人、事、物、景等,展露了那個特殊時代的臺灣生活風貌。《浮萍》中寫了一批滿懷壯志的鴻儒撤退來臺之后只能楚囚相對,殘酷的現狀迫使他們只能退而求其次,在臺灣設法照顧一家老小,讓漂泊的浮萍重新長出一點根來;《我的家》、《嘗試》寫了作者初來臺灣時的生活狀況,并以開朗的心態面對來臺生活的簡陋及女仆的無禮;《發現了川端橋》寫在時間漸漸沖淡鄉愁之后,作者對近在家門口的川端橋等有了全然不同的新體驗,字里行間流露出對新家園的認同與對新環境的依戀。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在某種程度上,《發現了川端橋》等同于“發現臺灣”,更是《我在臺北》的絕佳見證。作者理性幽默的文筆與調整后的心態使其筆下的臺灣生活顯露出同期散文中較少有的親切感。
而在艾雯的《漁港書簡》一書中,作者通過對所游歷的臺灣各地的風土人情的描寫,甚至開啟了日后人們所熱衷的旅游散文。《從贛南到臺灣》記錄了她逃難來臺時所見到的臺灣特有的自然風景與人文景觀;《四重溪之春》寫了重游四重溪的經過及這過程中所領受的美景;《白云深處覓歌舞》寫了在山地游中體會到的原住民的人情之美;《山在虛無縹渺間》寫了琉球嶼之游的自然美與人文美;《晴山綠縈西子灣》寫了西子灣枕山懷海的美與媚等。特別是在《漁港書簡》一文里,她以一個外地人的身份去感受當地的人文環境,并用溫柔細膩的筆致來書寫海的多變、漁民生活的貧窮、艱辛,并為他們唱出生命的哀愁與希望,充分體現了一個散文家的觀察能力與悲憫情懷。
就在這潔白美麗的大理石圍墻內,便圍著矮小簡陋的漁民之家。在漁島,據說人的繁殖跟魚類一樣的迅速,每一家都有一串梯形的孩子,人們在黯沉沉的小屋子里就像關在簍里的群蟹,蠕蠕蠢動。這便是漁人的家!漁人的家里充滿著海洋的咸腥味,也彌漫著貧窮的氣息。海洋是豐饒的、肥沃的,但在海洋懷抱中的這一塊陸地,卻是這樣貧瘠……
沒有怨尤,沒有憤恨,這便是他們對貧苦生活的答復。他們不曉得什么是享受,只求免受凍餒,風平浪靜。他們不懂什么叫愛情,只有互相合作,同嘗甘苦。他們沒有豐富的知識,卻有一肚子海的學問。……海的兒女們,他們才是上帝最善良純真的子民!
(三)女性意識的影響
此期臺灣女性散文所彰顯的女性意識,主要體現在作家們對女性生存狀況的不平之鳴上。如張秀亞由自敘婚變發出的不平之鳴:“在這畸形的社會,受犧牲的,往往不是不正常的男性,而是正常的女性”。艾雯由瑣碎的主婦生活體驗中發出的不平之鳴:“尤其是作為一個家庭主婦,長年被繁冗而瑣碎的家務囚系在小圈子中,不免深深地感到生活的枯燥乏味”。徐鐘珮由對職業女性因家庭而犧牲事業的社會觀察中發出的不平之鳴:“家和工作,幾乎等于熊掌和魚,我常想兩菜同燒,結果兩道菜都燒得半生不熟”。相比于五四時期,這時期女性散文中的女性意識,在超越傳統倫理及社會性別觀念等方面已失去了昂揚的狂飆精神。女性徘徊在傳統與現代、家庭與事業間,雖已感到不滿,卻缺少勇往直前的抉擇。如在沉默中承受失婚痛苦的張秀亞雖飽受心靈的煎熬,卻“宥于禮俗,我含恨在心,難以啟齒,不敢告訴,也不能告訴,更向誰告訴!在這凄慘環境下,我縱受了十六年新式教育,卻只有將一腔痛苦,委諸天命,形影相吊,抱恨終身!”。即便是開朗、明快的徐鐘珮,在兩難處境中也只有順應時局,黯然神傷:“我愛家,也愛工作,我就生活在這矛盾的愛里,像三明治里的夾肉,窒息得無以自處……于是我賭氣一腳踢翻熊掌,專心在家煮魚……在這轉變里,只有我一個人不欣賞我自己。我總漠然傾聽他們的謬獎,眼睛悵然注視著我案頭生銹的筆尖,我坐在明窗凈幾的書室里,卻覺得心頭積了厚厚一層灰塵”。
女作家們在女性視角下自我書寫的可觀創作實績,向我們展現了那個時期女性內心被壓抑的生存處境。而這些徘徊于現代與傳統之間、處于臺灣當代文學發生期的女作家們在女性意識方面覺醒了卻又向傳統退去的不徹底做法,則成為臺灣文壇后來者們所參照的源頭。在之后較長的時間里,雖然臺灣經濟、文化全力擁抱現代西方,但即便是在第二次女權運動高漲的60年代,臺灣女性文壇也未沖破底線完全西化,而是承接50年代女作家們的影響,在婚戀觀、職業觀等方面回歸保守的傳統。如在博得一個又一個時代掌聲的琦君的溫柔敦厚的散文中,母親即便是在父親變心娶妾進門后也從未反抗,而是以逆來順受和沉默自持的半生換回父親年老病痛之后的懺悔。在前衛的歐陽子的《秋葉》中,雖然年歲相仿的繼母子間也曾出現了《雷雨》中周萍與繁漪模式中的悶熱,但在最后的關頭,作者卻未讓繼母邁出那一步。而從60年代《心鎖》在一片喊打聲中成為禁書及其作者受打壓、甚至被逐出文學團體的命運上,我們都不難看出,那些想要逾越“傳統”的做法,在多數臺灣女作家中是不被允許、也不被接受的。五四時期郁達夫、、丁玲、廬隱等沖破性別文化咒語及倫理桎梏等的同、愛等多元書寫模式在此遭遇斷流(至少在較長時間內成為潛流),冰心式的對母愛、童心、自然的追求與對田園牧歌氣息的詩意描繪經過50年代女作家之手,在很長一段時間的臺灣文壇,特別是散文領域頗有市場。
(四)典范與理念的影響
篇3
第一次接觸張愛玲的著作,是十年前讀大學的時候。江南七月,荷葉田田,荷塘邊月色下是大學的露天電影院。青春逼人的莘莘學子神采飛揚,在露天影院里觀看根據張著改變的電影。胡琴咿咿呀呀的拉著,在萬盞燈火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胡琴上的故事是應當由光艷的伶人來扮演的,長長的兩片紅胭脂夾住瓊瑤鼻,唱了,笑了,袖子擋住了嘴……然而這里只有白四爺單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陽臺上,拉著胡琴。胡琴凄涼的聲音在月光下若有若無的時候,銀幕上就變戲法似的出現了幾個字——傾城之戀!
記得那次電影看完以后,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電影里的幾個鏡頭和對白。一場是白流蘇和范柳原在香港飯店的舞會上邊舞邊說的那段。“流蘇笑道:你怎末不說話呀?柳原笑道:可以當著人說的話,我全說完了。流蘇噗嗤一聲笑道:鬼鬼祟祟的,有什末背人的話?柳原道:有些傻話,不但是要背著人說,還得背著自己。讓自己聽見了也怪難為情的。譬如說,我愛你,我一輩子都愛你。”看到這里的時候,真有些讓人啼笑皆非的悲涼。其實此時,在情場上浸得有些疲倦了的范柳原,對白流蘇也只是三心二意;而剛從一場失敗的婚姻里走出來,在娘家又被擠兌得唉聲嘆氣無處立足的白流蘇,對于范柳原也是七上八下,心里忐忑的很。她下定決心跟著范柳原來到香港,一方面是要逃脫那個讓她無法承受的娘家和聽不完的閑言碎語,另一方面是覺得自己的青春年華已經成秋后的螞蚱,對于婚姻只有舍命一賭了。在這樣的情景下聽著這樣的調侃,白流蘇如何我不知道,我心頭當時的“涼”是一直延續的現在的。
可是,更凄涼的事情是在有一天的晚寢之后。“深夜里,她已經上床多時,只是翻來覆去。好容易朦朧了一會兒,床頭的電話鈴突然朗朗響了起來。她一聽,確是柳原的聲音,道:我愛你。就掛斷了。流蘇心跳得撲通撲通,握住了耳機,發了一會愣。方才輕輕的把它放回原處,誰知才擱上去,又是鈴聲大作。它再度拿起聽筒,柳原在那邊問道:我忘了問你一聲,你愛我麼?她低聲道:你早該知道了。我為什末上香港來?柳原嘆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擺著的事實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蘇,你不愛我。流蘇道:怎見得我不?柳原不語,良久方道:詩經上有一首詩我念給你聽——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釋得對不對。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末小,多末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流蘇沉思了半晌,不由得惱了起來:你干脆說不結婚不就完了!還繞著大彎子!什末做不了主,連我這樣守舊的人家,也還說‘初嫁從親,再嫁從身’哩,你這樣無拘無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誰替你做主?柳原冷冷道:你不愛我,你有什末辦法,你做得了主嗎?我不至于那末糊涂,犯不著花錢娶一個對我毫無感情的人來管束我。對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許你不在乎。根本你就以為婚姻就是長期的……”看到這里的時候,電影場里一片大笑。可是在笑過之后,一股悲涼的感覺從脊梁上嗖嗖躥上來,“婚姻就是長期的!”這突如其來的羞辱與調侃,真如一盆冰水兜頭潑下,怎不讓白流蘇羞惱成怒?!
整個《傾城之戀》中,張愛玲以其絕世的才華,不動聲色地編織著一個引人入勝卻又讓人嘆謂的愛情故事。在熱熱鬧鬧的情節中蘊含著一股幽幽的凄涼基調。讓人不由想起籠罩在《紅樓夢》里的那股悲涼和厚重,如同秋天早晨原野上的濃霧,美麗凄涼,揮之不去。其實,看完《傾城之戀》,人們都會想到,如果不是日軍侵占了香港,如果不是當時當地的形格勢禁,誰也不會相信,范柳原會娶白流蘇。可是上天造化,城傾了,戀成了。正如張愛玲說的那樣,“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個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誰知道什末是因?什末是果?……胡琴咿咿呀呀的拉著,在萬盞燈的夜晚,拉過來又拉過去,說不盡的蒼涼的故事——不問也罷!”
張愛玲真是一個躲在角落里極富才情的精靈,在胡琴咿咿呀呀的聲音中,我們被引入了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故事。在胡琴咿咿呀呀的聲音中,故事結束了。故事結束了,我們的感受和思索沒有結束,它像蒼涼的月光下若有若無的胡琴的聲,久久地纏繞著我們的心靈。
2
在張愛玲帶給我們的文學世界中,我們不能不對人生有著更加深沉的體悟和思考,而伴隨著思考過程的唯一的感覺,就是冷!幽幽地有點凄美的冷!其實,天才的作家都是靠著自己天才的感悟來寫作的。科學已經證明,最早的生命是起源于藍色的冰冷的海洋里那些雌雄一體的簡單的生物。后來,生物的進化使雌雄一體的細胞開始裂變分化,由雌雄一體分解為雌雄異體。一個生命分解成兩個生命,帶著自己另一半的遺傳信息,生命的一半在自身成長的過程中,開始了凄凄慘慘的尋尋覓覓歷程。人的歷史和人類的歷史,或者說從亞當夏娃開始的所有的愛情故事,就是這種尋找的不斷和延續。《紅樓夢》里賈寶玉初見林黛玉時心里想的那些話“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見過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以及見面之后說的那句“這個妹妹我見過”,決不是虛妄的無稽之談。而張愛玲卻以她天才的感悟,牢牢的把握住生命最初的那種冰涼的感覺,幽幽的還原著生命在尋找自己另一半過程中精彩或者暗淡、曲折或者順利、優美或者悲傷,引人入勝或者寡然索味的一個個冰涼的故事。
張愛玲不動聲色的冷,除了在《傾城之戀》里流露無遺外,在她的另一部小說《金鎖記》里面,也同樣有著出色的表現。
《金鎖記》是以一個出身于油坊家庭的少女七巧,被哥哥騙嫁給豪門世家的一個患有骨癌的少爺為妻說起的。七巧的粗俗和刁鉆,娘家的貧窮和丈夫的病,都是她在這個豪門世家里被欺受氣的理由。她犧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愛情夢想,好不容易熬到丈夫死了,婆婆也死了,她終于分到了一筆財產并獲得了人身的自由,可是財產和自由帶給她的是更讓她窒息的桎栲和更卑微的心態。她總是感到身邊所有的人都在打著她財產的主意。她要誓死保衛自己的財產,那是比她的命還要寶貴的東西,是她賴以生存的唯一的根據。守著自己的財產,她抽大煙,也讓兒子和女兒抽大煙。為了所謂的臉面,她讓女兒纏當時已經沒人再纏的小腳,又讓女兒讀上海灘最時髦的洋學堂。兒子她不僅不制止,反而覺得那是有錢人的排場。兒媳婦的家境比她家差一點,她就變本加厲地在人前冷嘲熱諷,致使親家母無臉見人,兒媳婦活活氣死。她時時處處都表現出一種乖戾的病態,晦暗而有發霉!冷森而又可惡!
張愛玲在這個晦暗的故事中,籠罩上一層淡淡的憂傷惆悵而有凄涼的韻味,一個很有思想力度的悲劇性的冰涼的基調。小說寫七巧的女兒長安在學堂里弄丟了一樣東西,七巧就要到學校找校長大興問罪之師,“長安著了急,攔阻了一聲,七巧便罵道:天生的敗家精!拿你娘的錢不當錢。你娘的錢是容易得到的?——將來你出嫁,你看我有什末陪送給你!——給也是白給!長安不敢作聲,卻哭了一個晚上。她不能在她的同學跟前丟這個臉。對于十四歲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她母親去鬧一場,她以后拿什末臉去見人?她寧死也不到學校里去了。她的朋友,她所喜歡的音樂教員,不久就會忘記有這末一個女孩子,來了半年,又無緣無故的悄悄地走了。走得干凈,她覺得她這犧牲是一個美麗的、蒼涼的手勢。”
“半夜里她爬下床來,伸手到窗外去試試,漆黑的,是下了雨麼?沒有雨點。她從枕頭下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來。猶疑地,Long Long Ago的細小的調子在龐大的夜里裊裊漾開。那嗚嗚的口琴聲時斷時續,如同嬰兒的哭泣……”
長安退學了,陪著她媽媽七巧抽煙,久而久之出脫成一個當年的七巧。她沒有理想,沒有愛情,她成了一個被人遺忘的病懨懨的老姑娘。不知是命運故意的捉弄,還是命中注定的造化,在她心如死灰的時候,一份意外的比較理想的愛情光顧了她。就要談婚論嫁之際,她的母親橫加阻攔,固執的認為那個男人是沖著她的陪嫁來的,即使不是,他也是在外洋有過女人,在鄉下也有過女人的人了。長安嫁給他是丟臉的事。她以自己的陰險和絕情親手扼殺了女兒的愛情。小說寫道“她知道母親會放出什末手段來,遲早要出亂子,遲早要決裂。這是她生命里頂完美的一段,與其讓別人給她加上一個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結束了它。一個美麗而蒼涼的手勢……”看,又是一個手勢,與離開學校時的那個手勢多麼似曾相識!張愛玲以大師的圓熟和獨到,用一個虛幻的手勢寫盡了千言萬語,讓我們想起席慕容“仿佛雨霧中的揮手別離”那個依依的冰涼的手勢。在寫到長安與童世舫分別的時候“長安悠悠忽忽聽到了口琴的聲音,遲鈍的吹出了Long Long Ago ……長安著了魔似的,去尋那吹口琴的人。迎著陽光走著,走到樹底下,一個穿著黃短褲的男孩騎在枝椏上顛顛著,吹著口琴,可是他吹的是另一個調子。長安仰面看著,眼前一陣黑,像驟雨似的,淚珠一串串的披了一臉。”凄涼憂傷如同長安退學前的那晚,那口琴……
張愛玲就是這樣摹寫一個女人的命運,勾畫一個女人如何“三十年來帶著黃金的枷,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殺了幾個人,沒死的也送了半條命。”如同《傾城之戀》里開頭和結尾那咿咿呀呀的胡琴一樣,《金鎖記》開頭和結尾的月亮,如同一管嗚嗚幽咽的洞簫,又如荒涼月光下城墻上游走的夜風,吹得人心冷颼颼的,緊緊地縮在一起。
其實,張愛玲本人的命運以及她和胡蘭成的愛情,又何嘗不似這凄涼的洞簫,或者長安手頭的口琴與白四爺的胡琴吹拉出的憂傷呢?
一個冰清玉潔絕世風華的女人的傾城之涼啊!